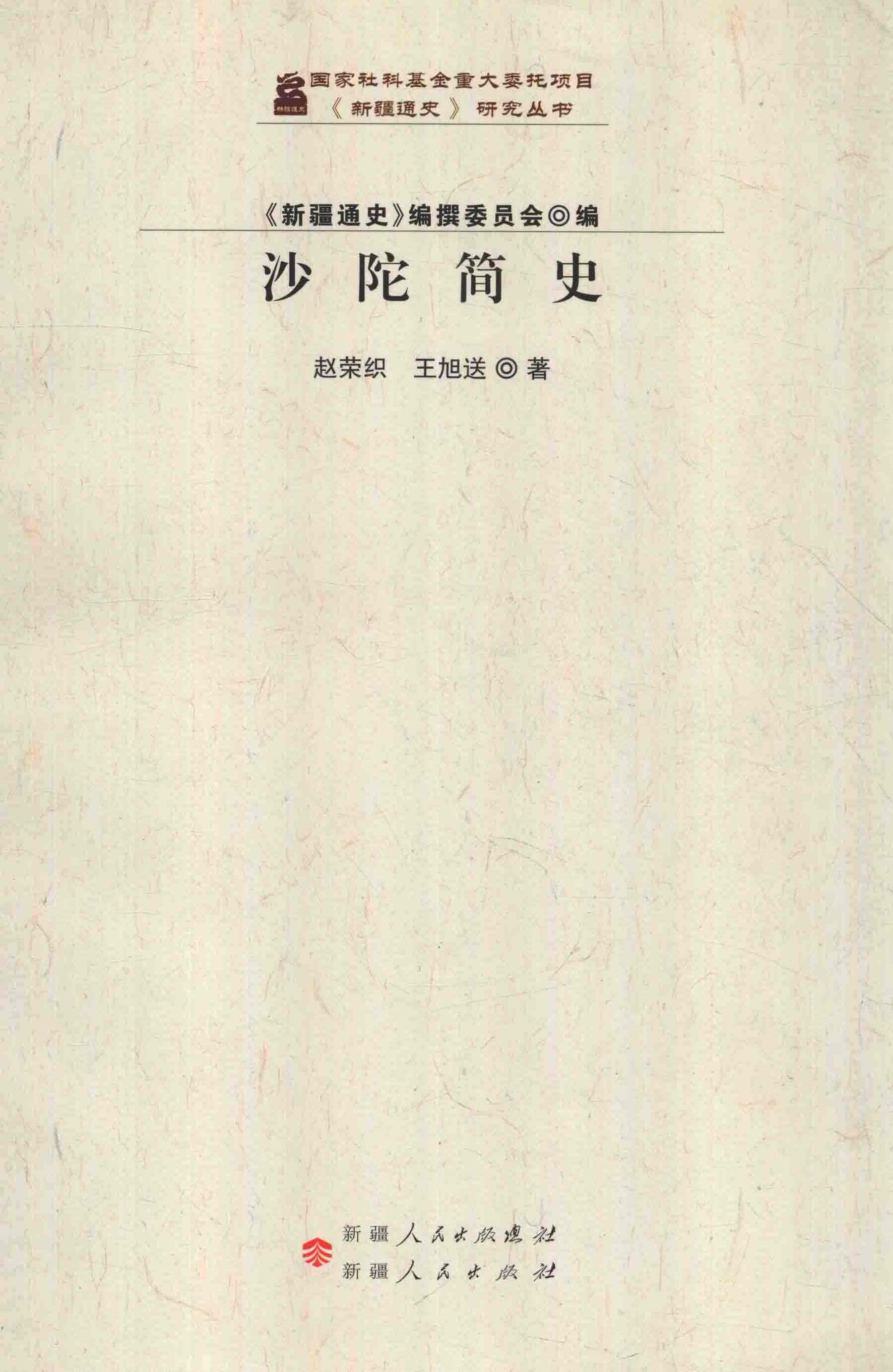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甘州地区,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沙陀不堪其苦,遂揭橥东归大唐之举。内迁之后,沙陀被安置于唐朝北部边陲,替唐御边,其间沙陀几经迁徙,最终定居代北。代北时期的沙陀在替唐朝御边同时,以其骁勇善战冠盖代北,成功将昭武九姓等边陲民族纳入其部落,从而形成“沙陀三部落”。此外,沙陀还奉旨南下,成功帮助唐朝政府镇压庞勋起义。
第一节 沙陀内迁的原因及过程
一、沙陀内迁的原因
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安置在甘州地区,游牧于祁连山一带。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因归附吐蕃有功,被吐蕃赞普封为“军大论”。“大论”一词藏文作blonchedpo,在吐蕃王朝中只有王族高等官员才有资格享有此衔①。尽管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得到了吐蕃赐予的崇高荣誉,但并没有给整个沙陀部落带来好运,吐蕃封朱邪尽忠“军大论”看中的是沙陀的骁勇善战,目的是驱使沙陀为其冲锋陷阵。史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吐蕃)同,而驰射趫悍过之,虏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繇此亦衰。”①由此可见,沙陀军队骑马射箭勇猛矫捷,在吐蕃之上。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吐蕃与唐朝、回纥战争的前沿——甘州,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
沙陀在甘州待了二十余载,最终不堪忍受吐蕃的统治,整体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关于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元和三年(808年),回奉诚可汗曾一度打败吐蕃,从其手中夺回凉州。由此,可能有人在赞普面前进谗言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于是,吐蕃欲将沙陀迁到河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以散弱其类”②。就甘州地理位置而言,所谓“河外”指的是“今青海省境黄河之南地域,即黄南州、海南州东部之地。这一带被黄河从南、西、北三面围绕,中古时代较为荒凉偏僻”
③。迁到河外无异于绝种,为保持种族不被灭绝,沙陀最终选择了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④。第二种观点认为,元和时期,唐朝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听说沙陀“北方推其勇劲”,故“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⑤。
我们认为,沙陀归唐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因素。首先,沙陀与回纥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平定安史之乱时沙陀曾与回纥并肩抗击叛军,沙陀首领沙陀金山还曾担任过回纥的副都护,《后唐懿祖纪年录》则径直称沙陀为回纥部人;吐蕃侵犯北庭之时双方又并肩抗击吐蕃的入侵。因此,吐蕃怀疑“尽忠持两端”、“贰于回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当时镇守边陲的节度使范希朝是一名具有极高声望的大将。史载,范希朝镇朔方时,大力加强边防设施,在要处建堡栅,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居官清廉,对诸蕃部落进献的奇驼名马“一无所受”;他见边地树木稀少,“于它处市柳子,令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因此,当时人将他比作西汉名将赵充国,号称当世善将①。投归范希朝门下对于身处绝境中的沙陀而言算是一条光明大道。与此同时,作为封疆大吏,范希朝也需要像沙陀这样的劲旅为其冲锋陷阵、保卫边疆。因此,第二种观点亦有其合理性。此外,吐蕃对待沙陀过于残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迁至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其伤亡肯定很大。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之外,沙陀内迁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唐王朝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从唐初以来,“四夷”各族就纷纷内附。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以内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有856个,比正州多出528个。唐王朝也欢迎各族的归附,对他们予以种种优惠待遇。如在经济上,唐朝《赋役令》中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二年以上复四年,三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没落外蕃得还者”在免征赋役上优惠出许多。在政治上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有的甚至做到了高②。唐朝提拔起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首领,级将领。在武将的提拔任用上,胡人往往要优于汉人。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在文化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其至进入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会对沙陀贵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内迁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生存之需,而是在华夷一家的内地谋求更好的发展。
其次,汉族先进的物质、精神文化及中原地区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吸引力。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吸引力。甘霖在《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指出:“东亚的黄河流域..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特别是唐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无疑对周边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沙陀人也不例外。
再次,沙陀对唐朝统治的认可及其汉化的加深。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了唐朝,成为唐朝臣民。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自此以后,沙陀数世为唐朝守边,至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人内迁中原时己有一个多世纪,其间沙陀首领还数度前往长安朝贡,亲眼目睹中原灿烂的文化。一个多世纪的耳濡目染,沙陀人内心深处已经形成民族认同思想。《后唐懿祖纪年录》中记载的朱邪执宜与其父朱邪尽忠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①当时朱邪执宜仅“及冠”之年,涉世不深,但他却自觉将自己视为“唐臣”,将唐朝视为“本朝,”可见其沙陀人对唐朝的认可程度。同时,沙陀在同唐朝的接触中,已经呈现汉化趋势。前引吐鲁番文书《朱邪部落请纸牒》,是开元十六年迁居西州的一支沙陀朱邪部落向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沙陀本是游牧部落,“随地治畜牧,”唐初以羁縻之道治之,当无请纸笔之需。从这件西州朱邪部落请纸牒可以看出,文书用汉文所写,且符合唐代公文之规范,即使该文书非朱邪人所写,亦能说明朱邪部落已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说明其本身开始汉化。
二、沙陀的初次内迁
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在朱邪尽忠父子率领下开始东归大唐,为吐蕃发现之后,派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为此,沙陀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东迁路线。本来甘州距离灵州不过几百公里,可径直前往,但是沙陀却选择了沿甘州东北方向蒙古草原上的乌德鞬山①向东的路线。艾冲先生认为,沙陀的这种迁移路线“与彼时政治形势、地理形势相矛盾,而且过于迂远绵长,对于沙陀突厥来说,实际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史书所载之“乌德鞬山”属史官之笔误,“乌德鞬山”当为“西倾山②。我们认为,西倾山”误写为“乌德鞬山”的可能性不大,艾先生之说法过于牵强。沙陀与回纥关系极为密切,回纥攻陷凉州之举被吐蕃怀疑为沙陀与之勾结的结果,亦绝非空穴来风。故,沙陀为摆脱吐蕃之围追堵截,选择取道回纥归唐的迂回方式应是一种减少伤亡的明智选择。
即便如此,沙陀亦未能避免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向东北方向行军三日之后,吐蕃追兵赶上,沙陀被迫向南迁移,一直到洮河(今甘肃临洮地
区)。自洮河开始,沙陀与吐蕃军队边打边走,一直转战至石门关(宁夏固原西北地区)。本来数百公里的距离,沙陀却“委曲三千里”③。
沙陀东迁归唐之路崎岖坎坷,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史载,沙陀与吐蕃交战“凡数百回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④。最终,“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⑤。
朱邪执宜父子率领的沙陀主部东归大唐之后,仍有残部陆续归唐。其一,部分溃散的沙陀“童耄”(老弱病残)自凤翔府、兴元府者、太原府辗转至盐州与沙陀主部聚合。其二,同年六月,朱邪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部众七百人,抵达振武边塞归降。
关于沙陀东迁的时间,《后唐懿祖纪年录》将之定为贞元十三年(797年)⑥,而《资治通鉴》则将之定为元和三年(808年),而且司马光还对《后唐懿祖纪年录》所云之贞元十三年进行了考证:“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今从《实录》、《旧传》、《新书》。”①可见,沙陀东迁时间当在元和三年。
关于沙陀归唐之前及归唐之初的人数,史载不一。《新唐书》云:“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②;《资治通鉴》云:“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大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③;《册府元龟》云:“本出甘州有九千余人,五月到灵州者,才二千余人,橐驼千余头,马六七百匹,馀皆战死、馁死及散失。”④
以上三种记载出入很大:首先,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之初的人数,《资治通鉴》云“部落三万”,而《新唐书》云“三万落”,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太平广记》卷一四七《裴仙先》条记载:“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⑤;《资治通鉴》载: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⑥。则,沙陀在北庭之时人数不过万帐。沙陀被吐蕃迁往甘州之后,沙陀在甘州居住时间仅20余年,且时常为吐蕃冲锋陷阵,伤亡甚众,其人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故《新唐书》所云“三万落”有误。
其次,沙陀到达灵州后所剩人数,《新唐书》云“士裁二千,骑七百”;《资治通鉴》云“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册府元龟》云“才三千余人”,相差亦甚远。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因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归唐之后不久,范希朝即“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以领之,为其战斗,所至有功。如是,则沙陀归唐之前骑当在千二百之上,故《新唐书》、《册府元龟》所云有误。《资治通鉴》所载沙陀至灵州者犹近万人,骑三千数目较为合理。
沙陀东迁归唐之后,仍有小部在甘州游牧,他们活动的地区主要在甘州南百余里祁连山中的鹿角山,因此这支沙陀余部被称为“鹿角山沙陀”。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张匡邺出使于阗,路经甘州,曾经获知这一沙陀余部的简单情况,被记录在五代平居诲所撰《于阗国行程记》中。记载如下:“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①这支部落明显是沙陀主部东迁灵武之后遗留之部分。
三、沙陀的再迁
沙陀东迁归唐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摆脱了灭种的危机,而且逐渐走向辉煌。自此以后,沙陀由一个仅万人的小部落,逐渐吸纳其他民族成分,成为称霸一方的藩镇,并最终在中原建立三个王朝。
东迁归唐的沙陀部受到了唐朝政府的高度重视: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亲自率众迎接于塞上;唐宪宗“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葛勒阿波归降之后,唐廷又任命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府都督。沙陀历来强悍好斗,范希朝想利用沙陀部来抵御夷狄入侵,故沙陀东迁归唐之后,范希朝除了专门设阴山都督府安置他们外,还为沙陀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业,以使他们休整繁衍;同时,范希朝对沙陀军队亦给以特殊照顾,如元和四年三月辛未,范希朝“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朝廷“许之”②。
为了答谢唐朝政府的优抚,沙陀部首领朱邪执宜在沙陀部安顿之后,亲自到唐都长安觐见唐宪宗。唐宪宗为酬劳沙陀归唐之功,“赐(朱邪执宜)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
沙陀在盐州被妥善安置之后,很快成为灵、盐地区的一支劲旅,“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①。
沙陀在盐州待的时间很短,仅隔一年左右,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便因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也随其迁转河东。迁转原因有三:首先,范希朝需要像沙陀这样一支刚强彪悍的劲旅为其守疆,同时范希朝因厚遇沙陀亦甚得沙陀之信任;其次沙陀居住之盐州靠近吐蕃统治区,唐朝怕其再度投靠吐蕃;第三,沙陀加入盐州之后,使当地人口大增,唐朝害怕当地粮食因此供应紧张。
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举军从之”。到达河东之后,范希朝挑选沙陀劲骑一千二百,号称沙陀军,并且设置军使进行管理;剩下的士兵则被范希朝安置在定襄川。朱邪执宜“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亦记载其事,云:“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关于迁往河东的沙陀人数,《新五代史》记载恐有误。因为,沙陀迁至灵州之时仅有万余人,骑兵三千,其军队数量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骤增至“数万骑”。
关于沙陀军队驻扎之“黄花堆”,《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胡三省注云:黄花堆“按朔州有黄花堆,在神武川②;关于神武川,意即黄瓜堆,”“”《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三省注云:“神武川在汉代郡桑乾县界,后魏置神武郡,后周废郡为神武县,属朔州。此时其地在马邑善阳县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后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宁武府神池县东北。”唐代善阳县即今山西朔州市,则沙陀军队当时驻扎之地就在今山西朔州市及今神池县东北一带。关于“定襄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定襄川,唐定襄县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县西北”;《大事记续编》卷六三云:“忻州定襄郡有定襄县。”两相比较,当以后者为是。因为,大同一带地处唐代边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唐朝不可能将一群老弱病残安置于战争的前沿。故,沙陀“童耄”所居之“定襄川”当在今忻州定襄县牧马河一带。
沙陀甫迁河东,便显示了其强劲的军事势力。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命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王承宗、朱邪执宜率领700人为先锋。在这次战争中,朱邪执宜与王承宗埋伏在木刀沟,与数万敌军相遇,飞矢如雨,执宜率军杀入敌阵,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大败镇州。战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任为蔚州(今河北蔚县)刺史。
之后不久,王锷代范希朝出任河东节度使。王锷家财颇丰,常有行贿之举,但具治边才干。王锷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河东兵员不过3万,马匹不足600。王锷到任之后,兵员达到5万,马匹达到5000,仓库物资亦十分充盈。王锷看到沙陀强劲剽悍,且聚族而居,恐其势力强大后难于控制,于是上疏云:“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于是,朝廷设置十府,安置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鹘军队越过漠南,攻取西城、柳谷①。唐宪宗下诏,令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驻守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阻止回鹘军队南下。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袭节度使自封统帅,窃取兵权。兵燹舞阳、叶县,略襄城、阳翟,许州、汝南人民深陷战乱之苦。唐宪宗以乌重胤兼汝州刺使,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帅,率领大军征讨吴元济。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队随李光颜参战。战争中,沙陀军队英勇作战,在时曲打败蔡人,并攻取凌云栅。吴元济叛乱被平定之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为检校刑部尚书,但仍隶属李光颜军。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朱邪执宜亲自到唐都长安朝贡,唐穆宗赐其“官诰、绵綵银器”②;同时,唐穆宗留朱邪执宜在朝宿卫,并拜其为金吾卫将军①。
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善于治边及安抚少数民族,史载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遇。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②。
沙陀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③所畏伏”,柳公绰上任河东节度使之后,给予沙陀部以重任。史载:“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而朱邪执宜本人温雅知礼,亦博得柳公绰的信任。史载:“执宜与诸酋长人谒,神采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后来,朱邪执宜母亲、妻子前去拜见,柳公绰让夫人与她们一起饮酒,并且馈赠礼物给她们。朱邪执宜非常感激柳公绰的知遇之恩,做事竭尽全力。史载:“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④
沙陀不仅为唐朝竭力守边,而且对当时叛乱藩镇的拉拢给以坚决拒绝。太和元年(827年),王庭凑帮助原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之子李同捷叛乱,为了增加叛乱的力量,王庭凑派遣使者带着重礼贿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希望朱邪执宜能与其联兵共同抗击唐朝,朱邪执宜对这种叛乱分裂的行径给以坚决拒绝⑤。
第二节 “沙陀三部落”的形成及其内迁初期的主要成就
一、“沙陀三部落”的形成
朱邪执宜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是沙陀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代北“九姓六州胡”加快了与沙陀的结合,“沙陀三部落”开始逐步形成。
所谓“沙陀三部落”,史有明载。《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云:(乾符四年十月,877年)“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白义诚、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广明元年六月,880年)“沙陀首领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时克用率御燕军于雄武军。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开门迎大军,克用闻之,亟来赴援,为李可举之兵追击,大败于药儿岭。..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中和元年二月,881)“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①。可见,所谓“沙陀三部落”即指沙陀、萨葛(亦称薛葛、索葛)、安庆三个部落。
关于萨葛(薛葛、索葛),张广达先生经考证认为,萨葛、薛葛、索葛都是粟特的同音异译②,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关于安庆的族属,由于缺乏史料支撑,学界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师道刚先生认为,安庆即“俟斤”之另一音译,将安庆归于突厥人③;樊文礼先生则从安庆都督史敬存的姓氏推断安庆属于粟特人④。我们比较认同安庆为粟特人之说,但仅从姓氏上判断其族别,尚不足以服人。隋唐时期,代北不仅有粟特人之史姓,亦有突厥人之史姓,而安庆都督史敬存当属突厥人。《元和姓篡·七歌阿史那氏下》云:“突厥处罗苏尼失等归化,号阿史那,开元间改为史氏”;《新唐书》卷一一〇《史大柰传》云:“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勤)也,与处罗可汗入隋,事炀帝。从伐辽,积劳为金紫光禄大夫。后分其部于楼烦。高祖兴太原,大柰提其众隶麾下。..赐姓史。”据此,代北地区亦有突厥可汗裔胤之史姓,不能仅仅以姓氏上断定安庆为粟特人,还需其他佐证。《旧五代史》卷十九《氏叔琮传》云:“(后梁)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县牧马于道间。”①从这条史料看出,内迁之后“深目虬须”者在沙陀集团逐渐占据多数,而“深目虬须”正是粟特人的典型体貌特征。沙陀集团既以“深目虬须”为其体貌特征,则融入沙陀集团的粟特人已经远远超过沙陀人。按此比例,安庆应是粟特人。
“沙陀三部落”最早见诸史载的时间是唐文宗开成中(838年前后)。《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刘沔传》云:“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②当然,这不是“沙陀三部落”形成的时间。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沙陀已经“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说明此前沙陀与六州胡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而朱邪执宜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可以直接控制六州胡,则进一步加快了沙陀与六州胡之间的融合。可以说,朱邪执宜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时期是“沙陀三部落”形成的关键时期。
朱邪执宜自元和三年(808年)开始统辖沙陀部,其死亡时间不详。樊文礼先生将朱邪执宜死亡的时间定在开成年间(836—840年),其立论依据是:朱邪赤心统辖沙陀部见诸文献的最早时间是开成四年(839年)③。我们认为朱邪执宜死亡的时间当在835—836年之间,证据如下:《五代会要》卷十八记载后唐张昭奉敕修史时,他提出一份修史计划,有如下记载:“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景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立国朝。”从张昭的这份修史计划可以看出,张昭对朱邪尽忠、朱邪执宜实录的撰修都是自他们任沙陀部首领时开始写起的,则太和之际自然也是朱邪赤心任沙陀部首领的开始时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朱邪执宜死亡时间就在太和之际,即835—836年之间,朱邪执宜统辖沙陀部近30年,死后葬于代州雁门县,墓曰永兴陵。
二、沙陀内迁初期的主要活动
太和之际,朱邪赤心嗣位,统辖沙陀部。朱邪赤心嗣位之后,继续为唐王朝效力,功勋不亚于其父。朱邪赤心时期沙陀的主要活动有:
一、开成初年,时任盐州刺史的王宰“失羌人之和”,“好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①,由此导致党项不断侵扰周邻。开成二年(837年)七月,党项寇振武②;三年,党项又大扰河套以西。振武节度使刘沔率领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到达银、夏讨袭,大破党项,俘获万计,胜利而还③。
二、开成四年(839年),回大饥荒,族帐离散,又为黠戛斯所迫,回鹘骑兵遂直过碛口,进抵榆林塞。宰相掘罗勿荐公以良马三百贿赂朱邪赤心,约其一起进攻回鹘的彰信可汗(胡特勤),彰信可汗兵败自杀后,朱邪赤心奏勿荐公为可汗。《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后唐献祖纪年录》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开成四年,回鹘大饥荒,族帐离散,复为黠戛斯所逼,渐过碛口,至于榆林。天德军使温德彝请帝(朱邪赤心)为援,遂帅骑赴之。时胡特勤可汗牙帐在近,帝遣使说回鹘相温没斯,为陈利害云云。温没斯然之,决有归国之约。俄而回鹘宰相勿笃(荐)公叛可汗,将图归义,遣人献良马三百,以求应援。帝自天德引军至碛口援之,为回鹘所薄,帝一战败之,进击可汗牙帐。胡特勤可汗势穷自杀,国昌因奏勿笃公为署飒可汗。”
三、会昌二年(842年),回乌介可汗经过天德,到达杷头峰北面,掳掠云、朔北部地区。唐武宗经朝议,决定主动出击。于是,任命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张仲武充任回纥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回纥西南面招讨使,军队在太原汇集。并下诏从太原调发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各部落,委任石雄为前锋。命易定兵士一千人守卫大同军;契芯通、何清朝统领沙陀、吐浑六千骑兵紧急奔赴天德戍守①。
四、会昌三年(843年),回鹘大肆掠夺云、朔地区的北部边境,还在五原建立了牙帐。刘沔命石雄选择骁勇健将,乘敌不备,直捣虏寇军营,击退回鹘。石雄接到刘沔的命令后,亲自挑选强悍的骑兵,得到了朱邪赤心所统沙陀三部落及契苾、拓跋杂虏共三千骑兵的大力支持。他们趁月暗夜黑,从马邑出发,直奔乌介可汗的牙帐。乌介可汗闻讯率骑兵逃窜,石雄率沙陀三部落等劲骑一直追杀到胡山,经过一番激战,共斩首万级,活捉五千,唐军大获全胜②。
五、会昌四年(844年)四月,昭义镇(又名泽潞,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死。他的侄儿刘稹秘不发丧,准备自为“留后”。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主张,决定打击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是年七月初,唐朝大军兵分四路,前往讨伐刘稹。朝廷下令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率领代北三千名骑兵隶属石雄充当前锋军队。战争中,沙陀军队先是攻克石会关,后协助王宰攻下天井。
六、刘稹之乱时,河东发生了杨弁兵乱。会昌三年(843年)末,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屯军榆社,以兵力不足,请朝廷支援。河东节度使李石命都将杨弁率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增援榆社。因太原府库藏困乏,故发放军饷不足,同时士卒要求未能满足,杨弁乘士卒怨怒发动兵变,并勾结刘稹共同对抗朝廷,唐武宗下令征讨杨弁。刚刚结束征讨刘稹之乱的沙陀军队再度上阵。他们联合太原军队,停驻榆社,与监军使吕义忠一起将杨弁擒获③。刘稹、杨弁之乱被镇压之后,朱邪赤心因战功升迁为朔州刺史,仍兼任代北军使。
七、大中初年(847年),吐蕃论恐热趁唐武宗死亡,引诱党项及回鹘残余部众侵犯河西,太原王宰率领代北诸军进兵讨伐。战争中,沙陀军队常常深入敌境,其英勇居于诸军之首。朱邪赤心所到之处,敌军便望风披靡,他们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①到宣宗时,沙陀军队已经收复了秦、原、安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征西的戍兵由此停罢。由于沙陀为唐朝守边立下汗马功劳,朝廷升迁朱邪赤心蔚州刺史、云中守捉使。
八、朱邪赤心任沙陀首领时期最主要的贡献是参与平定庞勋起义。唐懿宗三年(862年),南诏攻陷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唐朝招募徐泗兵三千人增援安南,其中八百人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按照规定,戍卒戍守三年即可换防回乡,但直到咸通九年七月,戍卒已经苦戍六年,思乡情浓,而徐泗观察使崔彦仍让他们再戍守一年,加之尹戡等将官贪猥欺凌,遂导致戍卒怨愤,忍无可忍。于是,大家推举庞勋为都帅,发动起义,自行北归。起义军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泗水入淮咽喉,切断了东南漕驿入长安之路,朝野震动。
起义军规模越来越大,唐朝政府被迫于咸通九年(868年)派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神武大将军王晏权、羽林将军戴可师等十八大将率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前往镇压。康承训奏请以沙陀三部落及吐谷浑、鞑靼、契芯等部酋长各率其部以自随,获得朝廷批准。朱邪赤心遂以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军使的职衔率领沙陀、鞑靼、契苾、吐谷浑等部三千人马出征②。
在镇压庞勋起义的战场上,沙陀士卒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为唐朝镇压庞勋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阵却敌,十镇之兵伏骑骁勇。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挝重围,拔出承训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③。
其后,王宏立率所部三万人攻康承训。乙亥,王宏立引兵夜袭鹿塘寨,“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白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两万余级”①。康承训率沙陀士卒大破王宏立之后,“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②。是年八月,庞勋带领两万兵马,从石山向西进发。康承训知道其动向之后,“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略毫州,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者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③。
镇压庞勋起义中,沙陀士卒大显身手。沙陀参战士卒仅三千,但全是骁勇善战之辈,故在战争中以一抵十,关键时刻能化险为夷,充分展示了骑兵在战争中的优势。战后,朝廷为嘉奖沙陀之功,在云州置大同军,命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同时,唐懿宗亲自召见朱邪赤心,留他做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为李国昌,入郑王家族名籍,而且赏赐给他亲仁里豪华宅邸④。
朱邪赤心加入郑王籍,对于沙陀部立足中原并最终问鼎中原有着重要意义。中国自秦汉大一统格局出现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梁启超在其《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为伪也⑤。中国传统正统观念非常重视“华夷之辨”,讲求“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之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⑥。因此,一个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与种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朱邪赤心加入郑王籍,极大淡化了其原来的民族身份,使其比较容易得到中原士人的认可,从而为其日后问鼎中原扫平了种族上的障碍。
九、李国昌担任大同节度使不久,回鹘攻打榆林,侵扰灵、盐地区,皇帝下诏令李国昌转任鄜延节度使以抵御回鹘入侵;嗣后,回鹘又侵扰天德地区,朝廷再度迁任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晋升为检校司徒,以抵御回鹘入侵①;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王仙芝起义军攻占荆、襄地区,朝廷征兵讨伐。沙陀士卒又参加到镇压王仙芝起义的行列之中。据史料记载,乾符四年(877年),王仙芝帅起义军进攻荆南。荆南节度使杨知温以文章才学仕进,不懂用兵之道。面对起义军的进攻,杨知温未加设防。危急时刻,杨知温派遣使者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告急。李福调集属下全部人马,亲自率领前往救援。“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②。此战,沙陀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与镇压起义的沙陀军队可能有两支:一支由李国昌之次子李克让率领。由于沙陀作战英勇,最终“平定贼军”,李克让亦因战功被授予金吾将军,并留在长安担任宿卫③;另一支则由沙陀大将刘迁率领云中精锐骑兵参与,亦作战勇敢,屡立奇功④。
李国昌任沙陀首领时间史无明载,其死亡时间却有记载,但说法不一。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对此有详细记载: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纪》:“国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见闻录》:“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旧书》:“中和三年,十月,国昌卒。”《后唐献祖纪年录》:“光启中,薨于位。”《新·沙陀传》:“光启三年,国昌卒。”《大祖纪年录》光启三年正月云:“是岁献祖文皇帝之丧,太祖哀毁行服,不获专征。”最终,《资治通鉴》以“《实录》置此年二月,今从之”,从而将李国昌死亡时间定于光启三年⑤。然《册府元龟》卷三十一《帝王部·奉先四》载,同光二年正月丁巳,所司奏“懿祖昭烈皇帝八月十四日忌,昭烈皇后十一月八日忌,献祖文皇帝十月十三日忌,文景皇后九月六日忌,太祖武皇帝正月二十日忌”。最后敕令,“敬依旧典”①。该史料所云李国昌之忌日十月十三日,恰与《唐末见闻录》相吻合,而《唐末见闻录》作者王仁裕,生活于唐末五代,其所述当更贴近史实。故,我们认为李国昌死亡时间应为中和三年(883年)。后唐建立后,追尊李国昌文景皇帝称号,庙号献祖②。
李国昌统帅沙陀部近三十载,为唐朝攘外安内立下汗马功劳,是一位有功之臣。然其后期,随着功劳的增多及其沙陀部的日益强大,李国昌开始恃功自傲,目无法纪、割据称霸之迹象日渐暴露。史载:咸通十三年(872年)“七月,以前义昌军节度使卢简方为太仆卿。十二月,以振武节度李国昌为检校右仆射、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国昌恃功颇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乃移镇云中。国昌称病辞军务,乃以太仆卿卢简方检校刑部尚书、云州刺史,充大同军防御等使。上召简方于思政殿,谓之曰:‘卿以沧州节镇,屈转大同。然朕以沙陀、羌、浑挠乱边鄙,以卿曾在云中,惠及部落,且忍屈为朕此行,安慰国昌,”由此可见,具达朕旨,勿令有所猜嫌也。’③李国昌后期,沙陀开始持强自重,危及唐朝统治的安全。
第一节 沙陀内迁的原因及过程
一、沙陀内迁的原因
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安置在甘州地区,游牧于祁连山一带。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因归附吐蕃有功,被吐蕃赞普封为“军大论”。“大论”一词藏文作blonchedpo,在吐蕃王朝中只有王族高等官员才有资格享有此衔①。尽管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得到了吐蕃赐予的崇高荣誉,但并没有给整个沙陀部落带来好运,吐蕃封朱邪尽忠“军大论”看中的是沙陀的骁勇善战,目的是驱使沙陀为其冲锋陷阵。史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吐蕃)同,而驰射趫悍过之,虏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繇此亦衰。”①由此可见,沙陀军队骑马射箭勇猛矫捷,在吐蕃之上。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吐蕃与唐朝、回纥战争的前沿——甘州,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
沙陀在甘州待了二十余载,最终不堪忍受吐蕃的统治,整体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关于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元和三年(808年),回奉诚可汗曾一度打败吐蕃,从其手中夺回凉州。由此,可能有人在赞普面前进谗言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于是,吐蕃欲将沙陀迁到河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以散弱其类”②。就甘州地理位置而言,所谓“河外”指的是“今青海省境黄河之南地域,即黄南州、海南州东部之地。这一带被黄河从南、西、北三面围绕,中古时代较为荒凉偏僻”
③。迁到河外无异于绝种,为保持种族不被灭绝,沙陀最终选择了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④。第二种观点认为,元和时期,唐朝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听说沙陀“北方推其勇劲”,故“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⑤。
我们认为,沙陀归唐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因素。首先,沙陀与回纥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平定安史之乱时沙陀曾与回纥并肩抗击叛军,沙陀首领沙陀金山还曾担任过回纥的副都护,《后唐懿祖纪年录》则径直称沙陀为回纥部人;吐蕃侵犯北庭之时双方又并肩抗击吐蕃的入侵。因此,吐蕃怀疑“尽忠持两端”、“贰于回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当时镇守边陲的节度使范希朝是一名具有极高声望的大将。史载,范希朝镇朔方时,大力加强边防设施,在要处建堡栅,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居官清廉,对诸蕃部落进献的奇驼名马“一无所受”;他见边地树木稀少,“于它处市柳子,令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因此,当时人将他比作西汉名将赵充国,号称当世善将①。投归范希朝门下对于身处绝境中的沙陀而言算是一条光明大道。与此同时,作为封疆大吏,范希朝也需要像沙陀这样的劲旅为其冲锋陷阵、保卫边疆。因此,第二种观点亦有其合理性。此外,吐蕃对待沙陀过于残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迁至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其伤亡肯定很大。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之外,沙陀内迁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唐王朝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从唐初以来,“四夷”各族就纷纷内附。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以内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有856个,比正州多出528个。唐王朝也欢迎各族的归附,对他们予以种种优惠待遇。如在经济上,唐朝《赋役令》中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二年以上复四年,三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没落外蕃得还者”在免征赋役上优惠出许多。在政治上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有的甚至做到了高②。唐朝提拔起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首领,级将领。在武将的提拔任用上,胡人往往要优于汉人。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在文化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其至进入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会对沙陀贵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内迁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生存之需,而是在华夷一家的内地谋求更好的发展。
其次,汉族先进的物质、精神文化及中原地区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吸引力。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吸引力。甘霖在《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指出:“东亚的黄河流域..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特别是唐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无疑对周边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沙陀人也不例外。
再次,沙陀对唐朝统治的认可及其汉化的加深。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了唐朝,成为唐朝臣民。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自此以后,沙陀数世为唐朝守边,至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人内迁中原时己有一个多世纪,其间沙陀首领还数度前往长安朝贡,亲眼目睹中原灿烂的文化。一个多世纪的耳濡目染,沙陀人内心深处已经形成民族认同思想。《后唐懿祖纪年录》中记载的朱邪执宜与其父朱邪尽忠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①当时朱邪执宜仅“及冠”之年,涉世不深,但他却自觉将自己视为“唐臣”,将唐朝视为“本朝,”可见其沙陀人对唐朝的认可程度。同时,沙陀在同唐朝的接触中,已经呈现汉化趋势。前引吐鲁番文书《朱邪部落请纸牒》,是开元十六年迁居西州的一支沙陀朱邪部落向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沙陀本是游牧部落,“随地治畜牧,”唐初以羁縻之道治之,当无请纸笔之需。从这件西州朱邪部落请纸牒可以看出,文书用汉文所写,且符合唐代公文之规范,即使该文书非朱邪人所写,亦能说明朱邪部落已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说明其本身开始汉化。
二、沙陀的初次内迁
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在朱邪尽忠父子率领下开始东归大唐,为吐蕃发现之后,派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为此,沙陀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东迁路线。本来甘州距离灵州不过几百公里,可径直前往,但是沙陀却选择了沿甘州东北方向蒙古草原上的乌德鞬山①向东的路线。艾冲先生认为,沙陀的这种迁移路线“与彼时政治形势、地理形势相矛盾,而且过于迂远绵长,对于沙陀突厥来说,实际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史书所载之“乌德鞬山”属史官之笔误,“乌德鞬山”当为“西倾山②。我们认为,西倾山”误写为“乌德鞬山”的可能性不大,艾先生之说法过于牵强。沙陀与回纥关系极为密切,回纥攻陷凉州之举被吐蕃怀疑为沙陀与之勾结的结果,亦绝非空穴来风。故,沙陀为摆脱吐蕃之围追堵截,选择取道回纥归唐的迂回方式应是一种减少伤亡的明智选择。
即便如此,沙陀亦未能避免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向东北方向行军三日之后,吐蕃追兵赶上,沙陀被迫向南迁移,一直到洮河(今甘肃临洮地
区)。自洮河开始,沙陀与吐蕃军队边打边走,一直转战至石门关(宁夏固原西北地区)。本来数百公里的距离,沙陀却“委曲三千里”③。
沙陀东迁归唐之路崎岖坎坷,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史载,沙陀与吐蕃交战“凡数百回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④。最终,“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⑤。
朱邪执宜父子率领的沙陀主部东归大唐之后,仍有残部陆续归唐。其一,部分溃散的沙陀“童耄”(老弱病残)自凤翔府、兴元府者、太原府辗转至盐州与沙陀主部聚合。其二,同年六月,朱邪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部众七百人,抵达振武边塞归降。
关于沙陀东迁的时间,《后唐懿祖纪年录》将之定为贞元十三年(797年)⑥,而《资治通鉴》则将之定为元和三年(808年),而且司马光还对《后唐懿祖纪年录》所云之贞元十三年进行了考证:“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今从《实录》、《旧传》、《新书》。”①可见,沙陀东迁时间当在元和三年。
关于沙陀归唐之前及归唐之初的人数,史载不一。《新唐书》云:“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②;《资治通鉴》云:“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大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③;《册府元龟》云:“本出甘州有九千余人,五月到灵州者,才二千余人,橐驼千余头,马六七百匹,馀皆战死、馁死及散失。”④
以上三种记载出入很大:首先,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之初的人数,《资治通鉴》云“部落三万”,而《新唐书》云“三万落”,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太平广记》卷一四七《裴仙先》条记载:“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⑤;《资治通鉴》载: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⑥。则,沙陀在北庭之时人数不过万帐。沙陀被吐蕃迁往甘州之后,沙陀在甘州居住时间仅20余年,且时常为吐蕃冲锋陷阵,伤亡甚众,其人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故《新唐书》所云“三万落”有误。
其次,沙陀到达灵州后所剩人数,《新唐书》云“士裁二千,骑七百”;《资治通鉴》云“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册府元龟》云“才三千余人”,相差亦甚远。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因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归唐之后不久,范希朝即“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以领之,为其战斗,所至有功。如是,则沙陀归唐之前骑当在千二百之上,故《新唐书》、《册府元龟》所云有误。《资治通鉴》所载沙陀至灵州者犹近万人,骑三千数目较为合理。
沙陀东迁归唐之后,仍有小部在甘州游牧,他们活动的地区主要在甘州南百余里祁连山中的鹿角山,因此这支沙陀余部被称为“鹿角山沙陀”。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张匡邺出使于阗,路经甘州,曾经获知这一沙陀余部的简单情况,被记录在五代平居诲所撰《于阗国行程记》中。记载如下:“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①这支部落明显是沙陀主部东迁灵武之后遗留之部分。
三、沙陀的再迁
沙陀东迁归唐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摆脱了灭种的危机,而且逐渐走向辉煌。自此以后,沙陀由一个仅万人的小部落,逐渐吸纳其他民族成分,成为称霸一方的藩镇,并最终在中原建立三个王朝。
东迁归唐的沙陀部受到了唐朝政府的高度重视: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亲自率众迎接于塞上;唐宪宗“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葛勒阿波归降之后,唐廷又任命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府都督。沙陀历来强悍好斗,范希朝想利用沙陀部来抵御夷狄入侵,故沙陀东迁归唐之后,范希朝除了专门设阴山都督府安置他们外,还为沙陀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业,以使他们休整繁衍;同时,范希朝对沙陀军队亦给以特殊照顾,如元和四年三月辛未,范希朝“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朝廷“许之”②。
为了答谢唐朝政府的优抚,沙陀部首领朱邪执宜在沙陀部安顿之后,亲自到唐都长安觐见唐宪宗。唐宪宗为酬劳沙陀归唐之功,“赐(朱邪执宜)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
沙陀在盐州被妥善安置之后,很快成为灵、盐地区的一支劲旅,“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①。
沙陀在盐州待的时间很短,仅隔一年左右,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便因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也随其迁转河东。迁转原因有三:首先,范希朝需要像沙陀这样一支刚强彪悍的劲旅为其守疆,同时范希朝因厚遇沙陀亦甚得沙陀之信任;其次沙陀居住之盐州靠近吐蕃统治区,唐朝怕其再度投靠吐蕃;第三,沙陀加入盐州之后,使当地人口大增,唐朝害怕当地粮食因此供应紧张。
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举军从之”。到达河东之后,范希朝挑选沙陀劲骑一千二百,号称沙陀军,并且设置军使进行管理;剩下的士兵则被范希朝安置在定襄川。朱邪执宜“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亦记载其事,云:“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关于迁往河东的沙陀人数,《新五代史》记载恐有误。因为,沙陀迁至灵州之时仅有万余人,骑兵三千,其军队数量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骤增至“数万骑”。
关于沙陀军队驻扎之“黄花堆”,《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胡三省注云:黄花堆“按朔州有黄花堆,在神武川②;关于神武川,意即黄瓜堆,”“”《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三省注云:“神武川在汉代郡桑乾县界,后魏置神武郡,后周废郡为神武县,属朔州。此时其地在马邑善阳县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后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宁武府神池县东北。”唐代善阳县即今山西朔州市,则沙陀军队当时驻扎之地就在今山西朔州市及今神池县东北一带。关于“定襄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定襄川,唐定襄县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县西北”;《大事记续编》卷六三云:“忻州定襄郡有定襄县。”两相比较,当以后者为是。因为,大同一带地处唐代边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唐朝不可能将一群老弱病残安置于战争的前沿。故,沙陀“童耄”所居之“定襄川”当在今忻州定襄县牧马河一带。
沙陀甫迁河东,便显示了其强劲的军事势力。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命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王承宗、朱邪执宜率领700人为先锋。在这次战争中,朱邪执宜与王承宗埋伏在木刀沟,与数万敌军相遇,飞矢如雨,执宜率军杀入敌阵,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大败镇州。战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任为蔚州(今河北蔚县)刺史。
之后不久,王锷代范希朝出任河东节度使。王锷家财颇丰,常有行贿之举,但具治边才干。王锷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河东兵员不过3万,马匹不足600。王锷到任之后,兵员达到5万,马匹达到5000,仓库物资亦十分充盈。王锷看到沙陀强劲剽悍,且聚族而居,恐其势力强大后难于控制,于是上疏云:“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于是,朝廷设置十府,安置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鹘军队越过漠南,攻取西城、柳谷①。唐宪宗下诏,令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驻守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阻止回鹘军队南下。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袭节度使自封统帅,窃取兵权。兵燹舞阳、叶县,略襄城、阳翟,许州、汝南人民深陷战乱之苦。唐宪宗以乌重胤兼汝州刺使,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帅,率领大军征讨吴元济。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队随李光颜参战。战争中,沙陀军队英勇作战,在时曲打败蔡人,并攻取凌云栅。吴元济叛乱被平定之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为检校刑部尚书,但仍隶属李光颜军。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朱邪执宜亲自到唐都长安朝贡,唐穆宗赐其“官诰、绵綵银器”②;同时,唐穆宗留朱邪执宜在朝宿卫,并拜其为金吾卫将军①。
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善于治边及安抚少数民族,史载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遇。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②。
沙陀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③所畏伏”,柳公绰上任河东节度使之后,给予沙陀部以重任。史载:“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而朱邪执宜本人温雅知礼,亦博得柳公绰的信任。史载:“执宜与诸酋长人谒,神采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后来,朱邪执宜母亲、妻子前去拜见,柳公绰让夫人与她们一起饮酒,并且馈赠礼物给她们。朱邪执宜非常感激柳公绰的知遇之恩,做事竭尽全力。史载:“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④
沙陀不仅为唐朝竭力守边,而且对当时叛乱藩镇的拉拢给以坚决拒绝。太和元年(827年),王庭凑帮助原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之子李同捷叛乱,为了增加叛乱的力量,王庭凑派遣使者带着重礼贿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希望朱邪执宜能与其联兵共同抗击唐朝,朱邪执宜对这种叛乱分裂的行径给以坚决拒绝⑤。
第二节 “沙陀三部落”的形成及其内迁初期的主要成就
一、“沙陀三部落”的形成
朱邪执宜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是沙陀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代北“九姓六州胡”加快了与沙陀的结合,“沙陀三部落”开始逐步形成。
所谓“沙陀三部落”,史有明载。《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云:(乾符四年十月,877年)“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白义诚、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广明元年六月,880年)“沙陀首领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时克用率御燕军于雄武军。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开门迎大军,克用闻之,亟来赴援,为李可举之兵追击,大败于药儿岭。..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中和元年二月,881)“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①。可见,所谓“沙陀三部落”即指沙陀、萨葛(亦称薛葛、索葛)、安庆三个部落。
关于萨葛(薛葛、索葛),张广达先生经考证认为,萨葛、薛葛、索葛都是粟特的同音异译②,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关于安庆的族属,由于缺乏史料支撑,学界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师道刚先生认为,安庆即“俟斤”之另一音译,将安庆归于突厥人③;樊文礼先生则从安庆都督史敬存的姓氏推断安庆属于粟特人④。我们比较认同安庆为粟特人之说,但仅从姓氏上判断其族别,尚不足以服人。隋唐时期,代北不仅有粟特人之史姓,亦有突厥人之史姓,而安庆都督史敬存当属突厥人。《元和姓篡·七歌阿史那氏下》云:“突厥处罗苏尼失等归化,号阿史那,开元间改为史氏”;《新唐书》卷一一〇《史大柰传》云:“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勤)也,与处罗可汗入隋,事炀帝。从伐辽,积劳为金紫光禄大夫。后分其部于楼烦。高祖兴太原,大柰提其众隶麾下。..赐姓史。”据此,代北地区亦有突厥可汗裔胤之史姓,不能仅仅以姓氏上断定安庆为粟特人,还需其他佐证。《旧五代史》卷十九《氏叔琮传》云:“(后梁)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县牧马于道间。”①从这条史料看出,内迁之后“深目虬须”者在沙陀集团逐渐占据多数,而“深目虬须”正是粟特人的典型体貌特征。沙陀集团既以“深目虬须”为其体貌特征,则融入沙陀集团的粟特人已经远远超过沙陀人。按此比例,安庆应是粟特人。
“沙陀三部落”最早见诸史载的时间是唐文宗开成中(838年前后)。《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刘沔传》云:“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②当然,这不是“沙陀三部落”形成的时间。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沙陀已经“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说明此前沙陀与六州胡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而朱邪执宜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可以直接控制六州胡,则进一步加快了沙陀与六州胡之间的融合。可以说,朱邪执宜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时期是“沙陀三部落”形成的关键时期。
朱邪执宜自元和三年(808年)开始统辖沙陀部,其死亡时间不详。樊文礼先生将朱邪执宜死亡的时间定在开成年间(836—840年),其立论依据是:朱邪赤心统辖沙陀部见诸文献的最早时间是开成四年(839年)③。我们认为朱邪执宜死亡的时间当在835—836年之间,证据如下:《五代会要》卷十八记载后唐张昭奉敕修史时,他提出一份修史计划,有如下记载:“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景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立国朝。”从张昭的这份修史计划可以看出,张昭对朱邪尽忠、朱邪执宜实录的撰修都是自他们任沙陀部首领时开始写起的,则太和之际自然也是朱邪赤心任沙陀部首领的开始时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朱邪执宜死亡时间就在太和之际,即835—836年之间,朱邪执宜统辖沙陀部近30年,死后葬于代州雁门县,墓曰永兴陵。
二、沙陀内迁初期的主要活动
太和之际,朱邪赤心嗣位,统辖沙陀部。朱邪赤心嗣位之后,继续为唐王朝效力,功勋不亚于其父。朱邪赤心时期沙陀的主要活动有:
一、开成初年,时任盐州刺史的王宰“失羌人之和”,“好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①,由此导致党项不断侵扰周邻。开成二年(837年)七月,党项寇振武②;三年,党项又大扰河套以西。振武节度使刘沔率领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到达银、夏讨袭,大破党项,俘获万计,胜利而还③。
二、开成四年(839年),回大饥荒,族帐离散,又为黠戛斯所迫,回鹘骑兵遂直过碛口,进抵榆林塞。宰相掘罗勿荐公以良马三百贿赂朱邪赤心,约其一起进攻回鹘的彰信可汗(胡特勤),彰信可汗兵败自杀后,朱邪赤心奏勿荐公为可汗。《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后唐献祖纪年录》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开成四年,回鹘大饥荒,族帐离散,复为黠戛斯所逼,渐过碛口,至于榆林。天德军使温德彝请帝(朱邪赤心)为援,遂帅骑赴之。时胡特勤可汗牙帐在近,帝遣使说回鹘相温没斯,为陈利害云云。温没斯然之,决有归国之约。俄而回鹘宰相勿笃(荐)公叛可汗,将图归义,遣人献良马三百,以求应援。帝自天德引军至碛口援之,为回鹘所薄,帝一战败之,进击可汗牙帐。胡特勤可汗势穷自杀,国昌因奏勿笃公为署飒可汗。”
三、会昌二年(842年),回乌介可汗经过天德,到达杷头峰北面,掳掠云、朔北部地区。唐武宗经朝议,决定主动出击。于是,任命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张仲武充任回纥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回纥西南面招讨使,军队在太原汇集。并下诏从太原调发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各部落,委任石雄为前锋。命易定兵士一千人守卫大同军;契芯通、何清朝统领沙陀、吐浑六千骑兵紧急奔赴天德戍守①。
四、会昌三年(843年),回鹘大肆掠夺云、朔地区的北部边境,还在五原建立了牙帐。刘沔命石雄选择骁勇健将,乘敌不备,直捣虏寇军营,击退回鹘。石雄接到刘沔的命令后,亲自挑选强悍的骑兵,得到了朱邪赤心所统沙陀三部落及契苾、拓跋杂虏共三千骑兵的大力支持。他们趁月暗夜黑,从马邑出发,直奔乌介可汗的牙帐。乌介可汗闻讯率骑兵逃窜,石雄率沙陀三部落等劲骑一直追杀到胡山,经过一番激战,共斩首万级,活捉五千,唐军大获全胜②。
五、会昌四年(844年)四月,昭义镇(又名泽潞,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死。他的侄儿刘稹秘不发丧,准备自为“留后”。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主张,决定打击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是年七月初,唐朝大军兵分四路,前往讨伐刘稹。朝廷下令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率领代北三千名骑兵隶属石雄充当前锋军队。战争中,沙陀军队先是攻克石会关,后协助王宰攻下天井。
六、刘稹之乱时,河东发生了杨弁兵乱。会昌三年(843年)末,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屯军榆社,以兵力不足,请朝廷支援。河东节度使李石命都将杨弁率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增援榆社。因太原府库藏困乏,故发放军饷不足,同时士卒要求未能满足,杨弁乘士卒怨怒发动兵变,并勾结刘稹共同对抗朝廷,唐武宗下令征讨杨弁。刚刚结束征讨刘稹之乱的沙陀军队再度上阵。他们联合太原军队,停驻榆社,与监军使吕义忠一起将杨弁擒获③。刘稹、杨弁之乱被镇压之后,朱邪赤心因战功升迁为朔州刺史,仍兼任代北军使。
七、大中初年(847年),吐蕃论恐热趁唐武宗死亡,引诱党项及回鹘残余部众侵犯河西,太原王宰率领代北诸军进兵讨伐。战争中,沙陀军队常常深入敌境,其英勇居于诸军之首。朱邪赤心所到之处,敌军便望风披靡,他们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①到宣宗时,沙陀军队已经收复了秦、原、安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征西的戍兵由此停罢。由于沙陀为唐朝守边立下汗马功劳,朝廷升迁朱邪赤心蔚州刺史、云中守捉使。
八、朱邪赤心任沙陀首领时期最主要的贡献是参与平定庞勋起义。唐懿宗三年(862年),南诏攻陷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唐朝招募徐泗兵三千人增援安南,其中八百人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按照规定,戍卒戍守三年即可换防回乡,但直到咸通九年七月,戍卒已经苦戍六年,思乡情浓,而徐泗观察使崔彦仍让他们再戍守一年,加之尹戡等将官贪猥欺凌,遂导致戍卒怨愤,忍无可忍。于是,大家推举庞勋为都帅,发动起义,自行北归。起义军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泗水入淮咽喉,切断了东南漕驿入长安之路,朝野震动。
起义军规模越来越大,唐朝政府被迫于咸通九年(868年)派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神武大将军王晏权、羽林将军戴可师等十八大将率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前往镇压。康承训奏请以沙陀三部落及吐谷浑、鞑靼、契芯等部酋长各率其部以自随,获得朝廷批准。朱邪赤心遂以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军使的职衔率领沙陀、鞑靼、契苾、吐谷浑等部三千人马出征②。
在镇压庞勋起义的战场上,沙陀士卒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为唐朝镇压庞勋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阵却敌,十镇之兵伏骑骁勇。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挝重围,拔出承训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③。
其后,王宏立率所部三万人攻康承训。乙亥,王宏立引兵夜袭鹿塘寨,“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白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两万余级”①。康承训率沙陀士卒大破王宏立之后,“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②。是年八月,庞勋带领两万兵马,从石山向西进发。康承训知道其动向之后,“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略毫州,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者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③。
镇压庞勋起义中,沙陀士卒大显身手。沙陀参战士卒仅三千,但全是骁勇善战之辈,故在战争中以一抵十,关键时刻能化险为夷,充分展示了骑兵在战争中的优势。战后,朝廷为嘉奖沙陀之功,在云州置大同军,命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同时,唐懿宗亲自召见朱邪赤心,留他做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为李国昌,入郑王家族名籍,而且赏赐给他亲仁里豪华宅邸④。
朱邪赤心加入郑王籍,对于沙陀部立足中原并最终问鼎中原有着重要意义。中国自秦汉大一统格局出现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梁启超在其《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为伪也⑤。中国传统正统观念非常重视“华夷之辨”,讲求“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之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⑥。因此,一个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与种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朱邪赤心加入郑王籍,极大淡化了其原来的民族身份,使其比较容易得到中原士人的认可,从而为其日后问鼎中原扫平了种族上的障碍。
九、李国昌担任大同节度使不久,回鹘攻打榆林,侵扰灵、盐地区,皇帝下诏令李国昌转任鄜延节度使以抵御回鹘入侵;嗣后,回鹘又侵扰天德地区,朝廷再度迁任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晋升为检校司徒,以抵御回鹘入侵①;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王仙芝起义军攻占荆、襄地区,朝廷征兵讨伐。沙陀士卒又参加到镇压王仙芝起义的行列之中。据史料记载,乾符四年(877年),王仙芝帅起义军进攻荆南。荆南节度使杨知温以文章才学仕进,不懂用兵之道。面对起义军的进攻,杨知温未加设防。危急时刻,杨知温派遣使者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告急。李福调集属下全部人马,亲自率领前往救援。“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②。此战,沙陀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与镇压起义的沙陀军队可能有两支:一支由李国昌之次子李克让率领。由于沙陀作战英勇,最终“平定贼军”,李克让亦因战功被授予金吾将军,并留在长安担任宿卫③;另一支则由沙陀大将刘迁率领云中精锐骑兵参与,亦作战勇敢,屡立奇功④。
李国昌任沙陀首领时间史无明载,其死亡时间却有记载,但说法不一。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对此有详细记载: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纪》:“国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见闻录》:“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旧书》:“中和三年,十月,国昌卒。”《后唐献祖纪年录》:“光启中,薨于位。”《新·沙陀传》:“光启三年,国昌卒。”《大祖纪年录》光启三年正月云:“是岁献祖文皇帝之丧,太祖哀毁行服,不获专征。”最终,《资治通鉴》以“《实录》置此年二月,今从之”,从而将李国昌死亡时间定于光启三年⑤。然《册府元龟》卷三十一《帝王部·奉先四》载,同光二年正月丁巳,所司奏“懿祖昭烈皇帝八月十四日忌,昭烈皇后十一月八日忌,献祖文皇帝十月十三日忌,文景皇后九月六日忌,太祖武皇帝正月二十日忌”。最后敕令,“敬依旧典”①。该史料所云李国昌之忌日十月十三日,恰与《唐末见闻录》相吻合,而《唐末见闻录》作者王仁裕,生活于唐末五代,其所述当更贴近史实。故,我们认为李国昌死亡时间应为中和三年(883年)。后唐建立后,追尊李国昌文景皇帝称号,庙号献祖②。
李国昌统帅沙陀部近三十载,为唐朝攘外安内立下汗马功劳,是一位有功之臣。然其后期,随着功劳的增多及其沙陀部的日益强大,李国昌开始恃功自傲,目无法纪、割据称霸之迹象日渐暴露。史载:咸通十三年(872年)“七月,以前义昌军节度使卢简方为太仆卿。十二月,以振武节度李国昌为检校右仆射、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国昌恃功颇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乃移镇云中。国昌称病辞军务,乃以太仆卿卢简方检校刑部尚书、云州刺史,充大同军防御等使。上召简方于思政殿,谓之曰:‘卿以沧州节镇,屈转大同。然朕以沙陀、羌、浑挠乱边鄙,以卿曾在云中,惠及部落,且忍屈为朕此行,安慰国昌,”由此可见,具达朕旨,勿令有所猜嫌也。’③李国昌后期,沙陀开始持强自重,危及唐朝统治的安全。
附注
①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6页。
②《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五十六《外臣部一·种族》,第11076页
③艾冲:《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④《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1—7652页;《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书·武皇纪上》,第331页。
⑤《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范希朝传》,第4059页。
①《新唐书》卷一百七十《范希朝传》,第5167—5168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第6247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2页。
①关于乌德鞬山的位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乌德鞬山在回鹘牙帐之西,甘州东北。曰:‘《唐历》云即郁督军山,虏语两音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1页)。乌德鞬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
②艾冲:《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③《后唐懿祖纪年录》,《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2页
④《后唐懿祖纪年录》,《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1页。
⑤《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5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2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2页。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5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1页。
④《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五十六《外臣部一·种族》,第11076页。
⑤《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七《裴伷先》,中华书局,1961年,第1059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第7520页。
①《中华野史》宋朝卷一,第285页,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8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第7653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第6445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5页;《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所记稍有出入,云:“是月,回纥部落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为回纥声言讨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回纥入寇,且当渐绝和事,不应便来犯边,但须设备,不足为虑’因请自夏州至天德,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缓急。”
②《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第499—500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注引《资治通鉴考异》将此事定为元和元年(806年),当误,应为长庆二年。(《资治通鉴》,第7652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唐纪六十》,第7870页。
③所谓“九姓”是指昭武九姓胡人,他们是从中亚迁徙而来的粟特人的后裔;所谓“六胡州”即唐朝初年唐朝为安置那些依附于突厥的昭武九姓而在黄河河套以南而设置的六州。六胡州设置于调露元年(679年),《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宁朔郡条云:“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后来,六胡州居民参与安史之乱,并几度迁徙后来,六胡州居民又再度迁回代北其原居住地。如,《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唐与吐蕃在盐、夏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唐命马隧率河东军击吐蕃,马燧至石州(今山西离石),“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
④同上。
⑤《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第7855页。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00页、707页、710页。
②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③师道刚:《读后晋史匡翰碑的几条札记》,《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7页。
④樊文礼:《李克用评传》,山东大学出版社,第22页。
①《旧五代史》卷十九《氏叔琮传》,第256页;《新五代史》卷四十三《氏叔琮传》则云:“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须者,牧马襄陵道旁,晋人以为晋兵。”(第467页)。
②《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刘沔传》,第4234页;另见《册府元龟》卷三五九《将帅部》。
③樊文礼:《李克用评传》,第24页。
①《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田弘正附子牟传》,第4786页。
②《新唐书》卷八《文宗纪》,第237页。
③《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刘沔传》,第4234页。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第593页。
②《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石雄传》,第4235页。
③《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李石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6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6页。
②《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第665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第8140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第814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第8141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第8149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第8150页;《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6页。
⑤《饮冰室文集》第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0页。
⑥《春秋公羊传》(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64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第8195页。
③《旧五代史》卷五十《李克让传》,第681页。
④《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6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纪七十二》,第8345页。
①《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三十一《帝王部·奉先第四》,第315页。
②《旧五代史》卷二十九《唐书五·庄宗纪第三》,第404页。
③《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81页。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