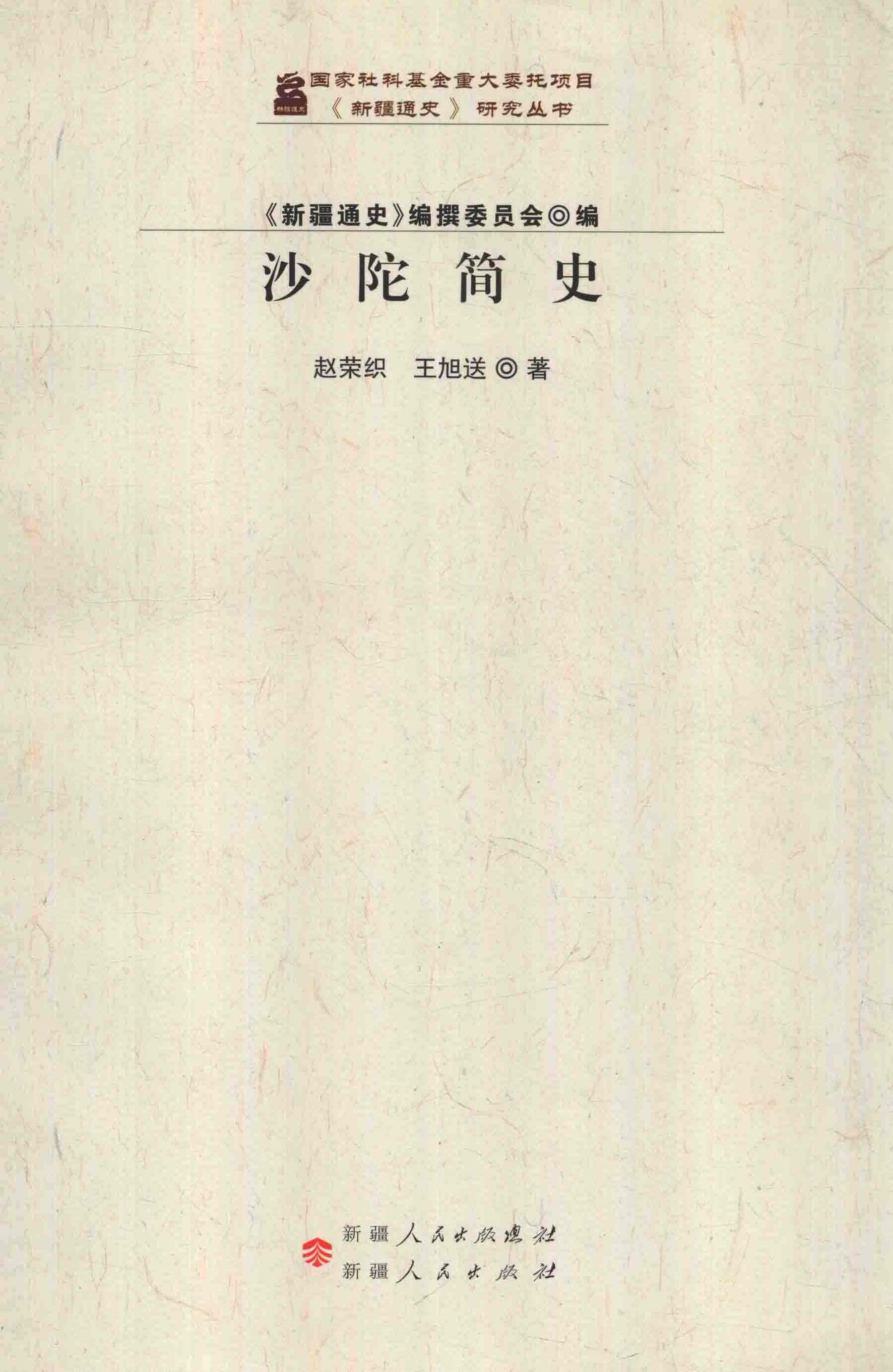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沙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周边许多民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其中与沙陀交往较多的有四个民族:西突厥、回纥、吐蕃、葛逻禄。本文试图对沙陀与这四个民族的关系做一个系统、全面的论述。
一、沙陀与西突厥之关系
在沙陀与周边诸民族关系中,沙陀与西突厥接触最早且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突厥初期,沙陀就与西突厥发生了关系。《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载:“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异。”《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亦云:“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密杂居。”关于沙陀与西突厥的关系,史书多称其为“西突厥别部”①,有些史书因此径直称其为“沙陀突厥”②,沙陀应是被西突厥征服之后处于西突厥统治之下的一个部落。沙陀作为西突厥的一个属部,其归唐前主要活动都是在西突厥最高统治者指挥下进行的,其政治立场与西突厥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沙陀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之时正是西突厥由盛转衰内乱、分裂不断,最高统治者频繁更换之时,作为西突厥属部,沙陀在短暂的几十年内先后依附于西突厥统治阶层的不同派系。
咥利失统治时期(?—638年):处月活动最早见诸史书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是年十月乙亥“处月遣使入贡”①。其时统治西突厥的是受唐朝册封的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作为西突厥的属部,此时的处月当属咥利失统辖,但是此时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处月作为西突厥属部,断无单独遣使朝贡之权,其敢于单独遣使朝贡说明处月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独立性,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这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一直维系到贞观十一年(637年)咥利失与欲谷设之间的伊犁河大战,此时,处月与弩失毕、处密等部尚归咥利失管辖②。
乙毗咄陆统治时期(638—?年):伊犁河大战之后的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处月部又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证据如下:贞观十二年,乙毗咄陆曾征发处月、处密部兵马,联合高昌国,攻打咥利失势力范围内的焉耆国。《旧唐书·焉耆传》云:“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咥利立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与焉耆为援。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③而根据薛延陀呈唐太宗的一份报告可知,联合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的处月、处密部的幕后指挥就是欲谷设,即乙毗咄陆可汗。《册府元龟》云:“太宗贞观十三年,薛延陀遣使上言:‘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厚,尝(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前导,驱以讨之’。”④
乙毗咄陆统治下的天山东部处月、处密等部落和平局面维系不久便发生了内讧,其原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其兄阿史那步真驱逐,“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阿史那步真自立为咄陆叶护⑤。由此,处月部一分为二,小部随阿史那弥射入唐,而大部仍留原地。未几,阿史那步真因部众不服,又因唐交河道行军进逼,也投降唐朝。
阿史那步真入唐之后,统治处月等部落的是阿史那贺鲁。《册府元龟》记载:“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①
贞观十五年乙毗咄陆攻杀唐朝政府册立的泥孰系沙钵罗叶护可汗②,复击败吐火罗,东进寇略唐朝在西域的范围,此时的西突厥基本已统于乙毗咄陆,其势力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乙毗咄陆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发处月、处密部连寇伊州和西州之天山县。《新唐书·突厥》下云:“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两千,自乌骨狙击,败之。咄陆以处月、处密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密]部而归。”此事之后,乙毗咄陆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西突厥弩失毕部的请求下,唐朝政府“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③
乙毗咄陆失败之后,乙毗射匮势力迅速向处月、处密等部所处的天山东部地区发展,企图填补乙毗咄陆失利后该地区形成的政治空白。而此时统治天山东部诸部的阿史那贺鲁在乙毗咄陆败亡之后面临着日益窘迫的局面。《通典》载:“咄陆西走吐火罗国,射匮可汗遣兵迫逐,贺鲁不常厥居。”④
乙毗射匮统治及其间短暂归唐时期(?—648年):在乙毗射“遣兵迫逐”阿史那贺鲁的情况下,原来隶属于阿史那贺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在乙毗射匮的挟制下归附乙毗射匮,同时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阿史那忠碑》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其云:“既而句丽、百济,互相侵逼;处月、焉耆,各为唇齿,肆回邪于荒裔,轸吊伐于皇情,天□□□□□□□□躅□□□□□乃□绥边□□诏公□〔西〕域安抚,载叶□如之寄,右地聋□,加授上柱国。”①从《阿史那忠碑》我们可以看出,在贞观十九年之前处月、处密已经和焉耆一起“肆回邪于荒裔”,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针对西域出现的新叛乱,唐朝政府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对于乙毗射匮与唐王朝之间对处月等部落的争夺,相关史传没有记载,但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政府发布的《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却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
《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云:“西域之地,经途遐阻,自遭乱离,亟历岁月,君长失抚驭之方,酋帅乘叶赞之义,虐用种落,肆行残忍,遂使部众离心,战争不息,远近涂炭,长幼怨嗟,大监小王,无所控告,顿颡蹶角,思见含养。朕受命三灵,君监六合,御朽之志,无忘寝兴;纳隍之怀,宁隔夷夏;乃眷西顾,良深矜惕;宜命輶轩,星言拯救。可令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蜜〔密]部落,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问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②《阿史那忠墓志》云:“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泑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侍辇幽燕,言过汾晋。于时延陀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驿赴救,事宁而反。”③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阿史那忠的西域“抚慰”之行达到预期目的,“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处月等部落名义上又重新归附唐朝。但这并非出自真心,事后很快又归附乙毗射匮。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军讨伐龟兹。这次讨伐处月也是打击对象,这从昆丘道行军之前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资治通鉴》载:“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①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处月、处密等部此时已经归附乙毗射匮,唐朝政府组织的这次针对乙毗射匮的昆丘道行军其讨伐对象亦包括处月、处密部。唐太宗行军前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首先就将处月、处密击败②。
阿史那贺鲁统治时期(648—657年):就在唐朝政府组织昆丘道行军征讨乙毗射匮之时,遭乙毗射匮追逐,四处漂泊无所寄托的阿史那贺鲁投降了唐朝政府。阿史那贺鲁此举得到了唐朝政府的礼遇,《新唐书·突厥传》载:“贺鲁无常居,部多散亡。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③处月原为阿史那贺鲁旧部,昆丘道行军中处月遭受唐军重创,加之阿史那贺鲁降唐受到唐朝政府礼遇。于是不久,处月在其阙俟斤朱邪阿厥带领下“亦请内属”④。自此,处月重新成了阿史那贺鲁的麾下。
阿史那贺鲁降唐之举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阿史那贺鲁随昆丘道行军征讨两个月之后,唐朝政府便在天山东部地区设立瑶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⑤,很快唐朝政府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晋封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大将军。但是阿史那贺鲁骨子里是反唐的,他降归唐朝其目的是借助唐朝势力发展壮大自己。在唐政府的扶持下,“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⑥,阿史那贺鲁很快统一了西突厥诸部。阿史那贺鲁的羽翼刚刚丰满,便暴露出其反唐的本质,他“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⑦于永徽元年⑧反唐,并于次年自封沙钵而《新唐书》及《唐会要》则记作“永徽二年”(《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53页;《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第1322页)。罗可汗,建牙双河及千泉,拥兵十万,西突厥诸部皆归属之。起兵之后,阿史那贺鲁首先入侵庭州,攻破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对唐政府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是年七月丁未,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发秦、成、歧、雍汉兵三万、回纥兵五万,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一次征讨。征讨之前,庭州刺史骆宏义上言,主张征讨之前应招降处月、处密等部落,以减少行军的阻力,同时与之合兵共讨阿史那贺鲁。骆宏义云:“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沿袭,大军顿于凭(洛)水,秣马蓄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①高宗最初采纳了此建议,派出各路使者招慰西突厥各部。但事与愿违,是年十二月壬子,处月酋长朱邪孤注首先杀害唐朝政府招慰使单道惠,与阿史那贺鲁联兵抗唐。只有作为沙陀族源的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拒绝随阿史那贺鲁叛唐,应招降唐。唐朝政府的招慰计划宣告失败。永徽三年唐朝大军开始西进征讨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闻讯西遁,而处月部朱邪孤注则居牢山自守,企图借地势之险要以拒唐军西进。“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是年癸亥,唐军数路并进,一举攻克牢山,斩处月酋长朱邪孤注,俘获处月、处密等部渠帅六十余人,斩首五千余级,俘生口万余计以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西域诸部纷纷随②。处月依附阿史那贺鲁叛唐,阿史那贺鲁叛唐之时,“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事后唐高宗以阿史那贺鲁以前所任瑶池都督一职授予沙陀那速③。
对于这次行军的原因,有的史料将之归结为处月等部的反叛④,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此次行军的主要目的就是讨伐阿史那贺鲁,而平定处月、处密叛乱只能看作是本次行军的最终收获①。
弓月道行军之后,唐朝于永徽四年(653年)正式撤销瑶池都督府,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②,至此处月部落中的朱邪部以羁縻州府的形式正式纳入唐朝政府的统治。
弓月道行军并没有和阿史那贺鲁正面交锋,所征服的仅仅是阿史那贺鲁前锋——处月、处密部之主力,此外仍有预支部依附阿史那贺鲁顽强对抗唐朝,所以弓月道行军基本是以失败告终。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此次征讨唐军深入西突厥腹地,与阿史那贺鲁属部交锋,取得辉煌战果。“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③。至此处月预”支部基本为唐军所征服。
显庆二年(657年)唐朝政府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三次征讨。此次征讨处月部未降者再次遭到重创。“(阿史那)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帅众来降”④。最终唐军大破阿史那贺鲁,西突厥被彻底平定,沙陀余部亦归唐,沙陀与西突厥的从属关系宣告彻底结束,沙陀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沙陀与回纥之关系
回纥是继突厥之后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汉朝时期的丁零,北魏时期为铁勒(别号高车)六部之一的袁纥部。沙陀与回纥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最早的接触是在唐军征讨西突厥过程中,当时双方以敌对关系出现;其后在吐蕃攻占西域过程中又与回纥结成友军共同抵抗吐蕃的进攻;沙陀内迁后,沙陀作为唐朝守边者与侵扰唐朝的回纥再次交锋,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了敌对关系。
沙陀与回纥最早的接触是在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西域战场上。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帅铁勒各部联合唐军一举灭亡薛延陀,后在回纥的请求下,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春正月在薛延陀、回纥、铁勒及其他各部地区设立六府七州,“北荒悉平”①。漠北的平定不但消除了唐朝北部边患,而且为唐朝提供了充沛的兵员。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的征讨过程中回纥数次参与,为唐朝平定西突厥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行军大总管发动了昆丘道行军讨伐龟兹。以回纥为首的“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②首次参加了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战争,而且是行军的主力。在这次行军中回纥等部骑兵在阿史那社尔率领下,相继攻占焉耆、龟兹,接着打败西突厥援军,向西攻占拔换城。这次战役震惊整个西域,塔里木南缘的于阗、疏勒及葱岭以西之安国“皆相率请降,凡得七百余城,掳男女数万口”③。至第二年十月,唐军完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西突厥失去了在天山南路的立足之地。唐于是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并建立安西四镇。此次昆丘道行军除征讨龟兹之外,处月也是该次行军的重要征讨对象。前引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云:“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唐太宗之预言不差丝毫,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④,昆丘道行军首战即以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沙陀与回纥的首次接触,其结局是回纥铁骑作为昆丘道行军的主力成功将沙陀击破。
唐军的西征引起乙毗射匮反对派阿史那贺鲁的强烈响应,他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己亥降唐,并获得厚赐。其后,阿史那贺鲁在唐朝政府的扶持下很快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及西域诸国。随着羽翼丰满,其反唐之心开始暴露,“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叛”,先是攻破唐控制的金岭城及蒲类县,继而攻陷北庭。唐政府以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兵五万击之”①,而且回纥这次出兵由吐迷度之子婆闰亲自率领,并兼任行军副总管②,足见回纥部众在此次行军中的主导作用。此次征讨,大破贺鲁收复北庭,并击破处月朱邪部落,斩其酋长朱邪孤注。这是沙陀与回纥的第二次交锋,同样以沙陀的失败而告终。
永徽六年,唐高宗以开国元老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显庆元年(656年)葱山道行军正式从长安出发西征。紧随其后,唐朝政府于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庚戌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阿史那贺鲁战役。关于这两次征讨,《旧唐书·回纥传》将之并到一起叙述:“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之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③由此可知,回纥军队在其首领婆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两次征讨。
弓月道行军之后尚有沙陀预支部仍随阿史那贺鲁负隅抵抗,葱山道行军唐军与处月预支部兵戎相见。史载:“(显庆元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罗、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④由此可以推知,沙陀与回纥在葱山道行军中再次兵戎相见,并且又是以回纥的取胜告终。
阿史那贺鲁叛乱被平定之后沙陀归唐,在唐朝政府统治之下沙陀与回纥再度接触。在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回纥立下汗马功劳,平叛后首领婆闰被授予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府都督。婆闰上任之后不久便染病去世,其侄比粟毒继位。比粟毒继位后并不甘心服从于唐朝,遂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勾结同罗、仆骨进犯唐朝边境。高宗令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共同率军讨伐①。沙陀部首领沙陀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一同征讨,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又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这是沙陀归唐后和回纥的首次接触,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是此次交锋是以沙陀的胜利告终。
天宝初年,骨力裴罗在位时,回纥汗国兴起于漠北,其势力西抵金山③。首领骨力裴罗也因内附先后被唐玄宗封为奉义王、怀仁可汗④。此时沙陀居住地毗邻回纥汗国的势力范围,同为大唐臣民,双方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政府还册封沙陀首领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⑤。
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沙陀在其首领骨咄支率领下随回纥助唐平叛。沙陀虽随回纥参加平叛,但双方在平叛战场上并不存在依附关系。据史载:“(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邪、契、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⑥据此可知,沙陀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与回纥之间亦不存在依附关系。由于沙陀在平叛中的优秀表现,唐封其首领骨咄支为特进、骁卫上将军⑦。
唐朝政府遭遇安史之乱之时,安西、北庭边兵大量内调,吐蕃乘机扩张势力,它在占据河陇地区后,乘势向天山南北扩张。此时的安西四镇及北庭还掌握在唐军手里,但因吐蕃占领河陇地区而割断了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为了与内地取得联系,安西、北庭都护府使臣辗转数十年,最终借道回纥,“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①。由此,不但北庭、安西守军“附庸”之,“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②。此时沙陀与回纥之间已由安史之乱及其以前的彼此友好、协同作战的关系转变为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是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维系未几便破裂,主要原因是回纥对沙陀等部的苛刻统治。史称“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而沙陀对回纥的肆行抄夺,尤所厌苦”③。
回纥对所统诸族的苛刻统治,引起北庭部众强烈不满。吐蕃趁机以厚赂引诱各部,促使北庭诸部叛回纥附吐蕃。在吐蕃“厚赂见诱”下,葛(逻)禄、白服突厥先后归附吐蕃,稍后吐蕃与葛逻禄、白服突厥一起急攻北庭,遭受回纥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至此,由于回纥的“贪狠、征求无度”最终导致沙陀摆脱回纥统治,双方附属关系宣告结束。
归附吐蕃之后的沙陀不但在战争中常被驱为前锋,而且被吐蕃无端猜疑为私通回纥,面临被迁至河外的危险境地。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举众归唐,掀开其历史发展中崭新的一页。
三、沙陀与吐蕃之关系
吐蕃是历史上由藏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其族源可追溯至西羌的一支发羌。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也是发生在唐朝征讨西突厥的战场上。双方之间关系也是经历了“敌—友—敌”的转变。
沙陀与吐蕃的首次接触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昆丘道行军中。此次行军之前唐朝曾对吐蕃发起过洮河道行军,但双方很快结束战争化敌为友,此后唐又应吐蕃请求于贞观十五年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与吐蕃间结成了甥舅关系①。在此背景下,吐蕃作为唐朝友军与铁勒十三州、(东)突厥、吐谷浑等一道参加了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征讨西突厥的昆丘道行军②。如前所述,此次行军首战便以大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史料记载的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疲于应付叛乱,吐蕃乘机屡次入侵唐朝。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③;“乾元以后,吐蕃乘机间隙,日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④。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地区基本为吐蕃所占领。
吐蕃进攻河陇地区时,沙陀可能在唐朝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从当时唐朝政府授予沙陀首领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骨咄支)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⑤唐朝政府遥授朱邪尽忠“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说明沙陀在河西地区与吐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继续进攻北庭,此时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守军相依,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御。五代人赵凤所撰《后唐懿祖纪年录》对此有详细记载:“德宗贞元五年,回纥葛禄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纥忠贞可汗,附于吐蕃,因为向导,驱吐蕃之众三十万寇我北庭。烈考(朱邪尽忠)谓忠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灵、盐,闻唐天子欲与赞普和亲,可汗数世有功,尚主,恩若娇儿,若赞普有恩于唐,则可汗必无前日之宠矣。’忠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将杨袭古固守北庭,无路归朝,今吐蕃、突厥并兵攻之,倘无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没,次及于吾,可汗得无虑乎!’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⑥但是回纥与沙陀的救援并没有改变北庭陷落的命运,加上回纥对其“贪狠、征求无度”,最终沙陀随北庭守军一道于贞元六年(790年)投降了吐蕃。至此,沙陀与吐蕃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了从属关系。
沙陀降蕃后其首领朱邪尽忠被授予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被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由于沙陀人骁勇善战,勇冠诸胡,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①,故沙陀部落死伤甚多,加上吐蕃对其横征暴敛,沙陀对吐蕃的统治无法忍受。后来,“回鹘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即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地域,当时为偏僻荒凉之地),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行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俞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欲迁②。回纥取凉州被吐蕃怀疑为沙陀勾结回纥所为③其于河外,导致沙陀举族愁怨,最终东归唐朝。沙陀与吐蕃仅二十年的从属关系宣告结束。
元和三年沙陀脱离吐蕃统治,开始了东归唐朝、投靠灵州节度使范希朝的历程。沙陀的东归激起了吐蕃的愤怒,吐蕃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此时沙陀与吐蕃已由原来的从属关系重新转变为敌对关系。
对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记载:“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傍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落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裒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④沙陀自甘州出发之际,共有部众“三万余落”,东归途中遭吐蕃追杀,到达盐州时仅剩近三千人,且已饥寒交迫,劳疲不堪。
四、沙陀与葛逻禄之关系
葛逻禄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活动中心“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①,相当于今新疆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它与处月一样,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属西突厥之别部。由于葛逻禄地处东、西突厥之间,因此常视双方力量之消长而叛附不定②。
沙陀与葛逻禄之间的关系发生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左右。其时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归唐,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命叶护阿史那贺鲁统治东部天山地区。史称:“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③沙陀与葛逻禄开始发生关系。
唐朝平定西突厥之前,沙陀与葛逻禄一道在阿史那贺鲁指挥之下对抗唐朝。永徽元年(650年),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④反唐。之后,唐朝政府组织了数次行军,征讨西突厥。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⑤。葛逻禄与处月在同唐军对抗中遭受重创。
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之后,唐朝于显庆三年(658年)设立羁縻州府以处置葛逻禄部众:以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至阿拉湖一带;以炽俟部置大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青河以南、乌伦古河下游地区;以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以北、斋桑泊以南地区。沙陀之处月、射脾部亦设金满州、沙陀州以妥善安置。归唐后的沙陀与葛逻禄之间再度发生关系。
近年出土的《唐龙朔二、三年(662—663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及《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①两份文书记载了两者之间发生的一件事:龙朔元年,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被贼人打散,有一千帐从金山(阿尔泰山)南下,在金满州地域停住,金满州都督沙陀某某将这一信息上报朝廷。朝廷分别给燕然都护府、哥(葛)逻禄部下敕令,命燕然都护府与西州都督府相知会,将停住金满州的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遣返大漠都督府原住地。龙朔二年,燕然都护府获取哥(葛)逻禄首领咄俟斤乌骑支陈状,云该部在龙朔元年敕令下达之前已经在金满州有水之处种下麦田,而且该部所放养的牲畜因遭受暴风雪,缺乏充足的草料,无法长途跋涉回归原住地,希望迁往甘州。之后龙朔三年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又相知会,力促哥(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留住金满州的葛逻禄仅五十帐,其他帐已经入京,故未能立马返回原住地。
通过这两份出土文献可以看出,葛逻禄归唐之后,曾流落至金满州境内,并从事农业生产,其间肯定得到了沙陀的照顾。尽管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数次规劝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葛逻禄留恋金满州之地,迟迟不归。该文书没有显示该事的最终结果,但从葛逻禄的态度上看,估计有部分葛逻禄人留在了金满州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最终融入沙陀部落当中。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减弱,沙陀同葛逻禄、白服(一作白眼)突厥一道处于回鹘的统治之下。然而“回鹘数侵掠之”,贞元五年(789年),葛逻禄部“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接着,吐蕃率葛逻禄、白服之众进略北庭,回鹘数战皆败。最终,遭受回鹘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此后,沙陀被吐蕃迁往河西地区,而葛逻禄主要活动于中亚一带,沙陀与葛逻禄的交往由此中断。
一、沙陀与西突厥之关系
在沙陀与周边诸民族关系中,沙陀与西突厥接触最早且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突厥初期,沙陀就与西突厥发生了关系。《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载:“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异。”《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亦云:“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密杂居。”关于沙陀与西突厥的关系,史书多称其为“西突厥别部”①,有些史书因此径直称其为“沙陀突厥”②,沙陀应是被西突厥征服之后处于西突厥统治之下的一个部落。沙陀作为西突厥的一个属部,其归唐前主要活动都是在西突厥最高统治者指挥下进行的,其政治立场与西突厥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沙陀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之时正是西突厥由盛转衰内乱、分裂不断,最高统治者频繁更换之时,作为西突厥属部,沙陀在短暂的几十年内先后依附于西突厥统治阶层的不同派系。
咥利失统治时期(?—638年):处月活动最早见诸史书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是年十月乙亥“处月遣使入贡”①。其时统治西突厥的是受唐朝册封的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作为西突厥的属部,此时的处月当属咥利失统辖,但是此时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处月作为西突厥属部,断无单独遣使朝贡之权,其敢于单独遣使朝贡说明处月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独立性,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这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一直维系到贞观十一年(637年)咥利失与欲谷设之间的伊犁河大战,此时,处月与弩失毕、处密等部尚归咥利失管辖②。
乙毗咄陆统治时期(638—?年):伊犁河大战之后的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处月部又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证据如下:贞观十二年,乙毗咄陆曾征发处月、处密部兵马,联合高昌国,攻打咥利失势力范围内的焉耆国。《旧唐书·焉耆传》云:“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咥利立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与焉耆为援。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③而根据薛延陀呈唐太宗的一份报告可知,联合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的处月、处密部的幕后指挥就是欲谷设,即乙毗咄陆可汗。《册府元龟》云:“太宗贞观十三年,薛延陀遣使上言:‘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厚,尝(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前导,驱以讨之’。”④
乙毗咄陆统治下的天山东部处月、处密等部落和平局面维系不久便发生了内讧,其原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其兄阿史那步真驱逐,“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阿史那步真自立为咄陆叶护⑤。由此,处月部一分为二,小部随阿史那弥射入唐,而大部仍留原地。未几,阿史那步真因部众不服,又因唐交河道行军进逼,也投降唐朝。
阿史那步真入唐之后,统治处月等部落的是阿史那贺鲁。《册府元龟》记载:“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①
贞观十五年乙毗咄陆攻杀唐朝政府册立的泥孰系沙钵罗叶护可汗②,复击败吐火罗,东进寇略唐朝在西域的范围,此时的西突厥基本已统于乙毗咄陆,其势力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乙毗咄陆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发处月、处密部连寇伊州和西州之天山县。《新唐书·突厥》下云:“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两千,自乌骨狙击,败之。咄陆以处月、处密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密]部而归。”此事之后,乙毗咄陆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西突厥弩失毕部的请求下,唐朝政府“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③
乙毗咄陆失败之后,乙毗射匮势力迅速向处月、处密等部所处的天山东部地区发展,企图填补乙毗咄陆失利后该地区形成的政治空白。而此时统治天山东部诸部的阿史那贺鲁在乙毗咄陆败亡之后面临着日益窘迫的局面。《通典》载:“咄陆西走吐火罗国,射匮可汗遣兵迫逐,贺鲁不常厥居。”④
乙毗射匮统治及其间短暂归唐时期(?—648年):在乙毗射“遣兵迫逐”阿史那贺鲁的情况下,原来隶属于阿史那贺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在乙毗射匮的挟制下归附乙毗射匮,同时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阿史那忠碑》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其云:“既而句丽、百济,互相侵逼;处月、焉耆,各为唇齿,肆回邪于荒裔,轸吊伐于皇情,天□□□□□□□□躅□□□□□乃□绥边□□诏公□〔西〕域安抚,载叶□如之寄,右地聋□,加授上柱国。”①从《阿史那忠碑》我们可以看出,在贞观十九年之前处月、处密已经和焉耆一起“肆回邪于荒裔”,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针对西域出现的新叛乱,唐朝政府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对于乙毗射匮与唐王朝之间对处月等部落的争夺,相关史传没有记载,但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政府发布的《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却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
《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云:“西域之地,经途遐阻,自遭乱离,亟历岁月,君长失抚驭之方,酋帅乘叶赞之义,虐用种落,肆行残忍,遂使部众离心,战争不息,远近涂炭,长幼怨嗟,大监小王,无所控告,顿颡蹶角,思见含养。朕受命三灵,君监六合,御朽之志,无忘寝兴;纳隍之怀,宁隔夷夏;乃眷西顾,良深矜惕;宜命輶轩,星言拯救。可令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蜜〔密]部落,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问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②《阿史那忠墓志》云:“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泑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侍辇幽燕,言过汾晋。于时延陀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驿赴救,事宁而反。”③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阿史那忠的西域“抚慰”之行达到预期目的,“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处月等部落名义上又重新归附唐朝。但这并非出自真心,事后很快又归附乙毗射匮。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军讨伐龟兹。这次讨伐处月也是打击对象,这从昆丘道行军之前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资治通鉴》载:“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①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处月、处密等部此时已经归附乙毗射匮,唐朝政府组织的这次针对乙毗射匮的昆丘道行军其讨伐对象亦包括处月、处密部。唐太宗行军前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首先就将处月、处密击败②。
阿史那贺鲁统治时期(648—657年):就在唐朝政府组织昆丘道行军征讨乙毗射匮之时,遭乙毗射匮追逐,四处漂泊无所寄托的阿史那贺鲁投降了唐朝政府。阿史那贺鲁此举得到了唐朝政府的礼遇,《新唐书·突厥传》载:“贺鲁无常居,部多散亡。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③处月原为阿史那贺鲁旧部,昆丘道行军中处月遭受唐军重创,加之阿史那贺鲁降唐受到唐朝政府礼遇。于是不久,处月在其阙俟斤朱邪阿厥带领下“亦请内属”④。自此,处月重新成了阿史那贺鲁的麾下。
阿史那贺鲁降唐之举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阿史那贺鲁随昆丘道行军征讨两个月之后,唐朝政府便在天山东部地区设立瑶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⑤,很快唐朝政府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晋封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大将军。但是阿史那贺鲁骨子里是反唐的,他降归唐朝其目的是借助唐朝势力发展壮大自己。在唐政府的扶持下,“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⑥,阿史那贺鲁很快统一了西突厥诸部。阿史那贺鲁的羽翼刚刚丰满,便暴露出其反唐的本质,他“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⑦于永徽元年⑧反唐,并于次年自封沙钵而《新唐书》及《唐会要》则记作“永徽二年”(《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53页;《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第1322页)。罗可汗,建牙双河及千泉,拥兵十万,西突厥诸部皆归属之。起兵之后,阿史那贺鲁首先入侵庭州,攻破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对唐政府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是年七月丁未,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发秦、成、歧、雍汉兵三万、回纥兵五万,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一次征讨。征讨之前,庭州刺史骆宏义上言,主张征讨之前应招降处月、处密等部落,以减少行军的阻力,同时与之合兵共讨阿史那贺鲁。骆宏义云:“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沿袭,大军顿于凭(洛)水,秣马蓄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①高宗最初采纳了此建议,派出各路使者招慰西突厥各部。但事与愿违,是年十二月壬子,处月酋长朱邪孤注首先杀害唐朝政府招慰使单道惠,与阿史那贺鲁联兵抗唐。只有作为沙陀族源的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拒绝随阿史那贺鲁叛唐,应招降唐。唐朝政府的招慰计划宣告失败。永徽三年唐朝大军开始西进征讨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闻讯西遁,而处月部朱邪孤注则居牢山自守,企图借地势之险要以拒唐军西进。“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是年癸亥,唐军数路并进,一举攻克牢山,斩处月酋长朱邪孤注,俘获处月、处密等部渠帅六十余人,斩首五千余级,俘生口万余计以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西域诸部纷纷随②。处月依附阿史那贺鲁叛唐,阿史那贺鲁叛唐之时,“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事后唐高宗以阿史那贺鲁以前所任瑶池都督一职授予沙陀那速③。
对于这次行军的原因,有的史料将之归结为处月等部的反叛④,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此次行军的主要目的就是讨伐阿史那贺鲁,而平定处月、处密叛乱只能看作是本次行军的最终收获①。
弓月道行军之后,唐朝于永徽四年(653年)正式撤销瑶池都督府,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②,至此处月部落中的朱邪部以羁縻州府的形式正式纳入唐朝政府的统治。
弓月道行军并没有和阿史那贺鲁正面交锋,所征服的仅仅是阿史那贺鲁前锋——处月、处密部之主力,此外仍有预支部依附阿史那贺鲁顽强对抗唐朝,所以弓月道行军基本是以失败告终。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此次征讨唐军深入西突厥腹地,与阿史那贺鲁属部交锋,取得辉煌战果。“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③。至此处月预”支部基本为唐军所征服。
显庆二年(657年)唐朝政府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三次征讨。此次征讨处月部未降者再次遭到重创。“(阿史那)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帅众来降”④。最终唐军大破阿史那贺鲁,西突厥被彻底平定,沙陀余部亦归唐,沙陀与西突厥的从属关系宣告彻底结束,沙陀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沙陀与回纥之关系
回纥是继突厥之后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汉朝时期的丁零,北魏时期为铁勒(别号高车)六部之一的袁纥部。沙陀与回纥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最早的接触是在唐军征讨西突厥过程中,当时双方以敌对关系出现;其后在吐蕃攻占西域过程中又与回纥结成友军共同抵抗吐蕃的进攻;沙陀内迁后,沙陀作为唐朝守边者与侵扰唐朝的回纥再次交锋,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了敌对关系。
沙陀与回纥最早的接触是在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西域战场上。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帅铁勒各部联合唐军一举灭亡薛延陀,后在回纥的请求下,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春正月在薛延陀、回纥、铁勒及其他各部地区设立六府七州,“北荒悉平”①。漠北的平定不但消除了唐朝北部边患,而且为唐朝提供了充沛的兵员。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的征讨过程中回纥数次参与,为唐朝平定西突厥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行军大总管发动了昆丘道行军讨伐龟兹。以回纥为首的“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②首次参加了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战争,而且是行军的主力。在这次行军中回纥等部骑兵在阿史那社尔率领下,相继攻占焉耆、龟兹,接着打败西突厥援军,向西攻占拔换城。这次战役震惊整个西域,塔里木南缘的于阗、疏勒及葱岭以西之安国“皆相率请降,凡得七百余城,掳男女数万口”③。至第二年十月,唐军完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西突厥失去了在天山南路的立足之地。唐于是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并建立安西四镇。此次昆丘道行军除征讨龟兹之外,处月也是该次行军的重要征讨对象。前引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云:“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唐太宗之预言不差丝毫,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④,昆丘道行军首战即以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沙陀与回纥的首次接触,其结局是回纥铁骑作为昆丘道行军的主力成功将沙陀击破。
唐军的西征引起乙毗射匮反对派阿史那贺鲁的强烈响应,他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己亥降唐,并获得厚赐。其后,阿史那贺鲁在唐朝政府的扶持下很快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及西域诸国。随着羽翼丰满,其反唐之心开始暴露,“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叛”,先是攻破唐控制的金岭城及蒲类县,继而攻陷北庭。唐政府以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兵五万击之”①,而且回纥这次出兵由吐迷度之子婆闰亲自率领,并兼任行军副总管②,足见回纥部众在此次行军中的主导作用。此次征讨,大破贺鲁收复北庭,并击破处月朱邪部落,斩其酋长朱邪孤注。这是沙陀与回纥的第二次交锋,同样以沙陀的失败而告终。
永徽六年,唐高宗以开国元老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显庆元年(656年)葱山道行军正式从长安出发西征。紧随其后,唐朝政府于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庚戌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阿史那贺鲁战役。关于这两次征讨,《旧唐书·回纥传》将之并到一起叙述:“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之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③由此可知,回纥军队在其首领婆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两次征讨。
弓月道行军之后尚有沙陀预支部仍随阿史那贺鲁负隅抵抗,葱山道行军唐军与处月预支部兵戎相见。史载:“(显庆元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罗、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④由此可以推知,沙陀与回纥在葱山道行军中再次兵戎相见,并且又是以回纥的取胜告终。
阿史那贺鲁叛乱被平定之后沙陀归唐,在唐朝政府统治之下沙陀与回纥再度接触。在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回纥立下汗马功劳,平叛后首领婆闰被授予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府都督。婆闰上任之后不久便染病去世,其侄比粟毒继位。比粟毒继位后并不甘心服从于唐朝,遂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勾结同罗、仆骨进犯唐朝边境。高宗令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共同率军讨伐①。沙陀部首领沙陀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一同征讨,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又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这是沙陀归唐后和回纥的首次接触,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是此次交锋是以沙陀的胜利告终。
天宝初年,骨力裴罗在位时,回纥汗国兴起于漠北,其势力西抵金山③。首领骨力裴罗也因内附先后被唐玄宗封为奉义王、怀仁可汗④。此时沙陀居住地毗邻回纥汗国的势力范围,同为大唐臣民,双方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政府还册封沙陀首领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⑤。
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沙陀在其首领骨咄支率领下随回纥助唐平叛。沙陀虽随回纥参加平叛,但双方在平叛战场上并不存在依附关系。据史载:“(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邪、契、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⑥据此可知,沙陀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与回纥之间亦不存在依附关系。由于沙陀在平叛中的优秀表现,唐封其首领骨咄支为特进、骁卫上将军⑦。
唐朝政府遭遇安史之乱之时,安西、北庭边兵大量内调,吐蕃乘机扩张势力,它在占据河陇地区后,乘势向天山南北扩张。此时的安西四镇及北庭还掌握在唐军手里,但因吐蕃占领河陇地区而割断了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为了与内地取得联系,安西、北庭都护府使臣辗转数十年,最终借道回纥,“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①。由此,不但北庭、安西守军“附庸”之,“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②。此时沙陀与回纥之间已由安史之乱及其以前的彼此友好、协同作战的关系转变为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是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维系未几便破裂,主要原因是回纥对沙陀等部的苛刻统治。史称“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而沙陀对回纥的肆行抄夺,尤所厌苦”③。
回纥对所统诸族的苛刻统治,引起北庭部众强烈不满。吐蕃趁机以厚赂引诱各部,促使北庭诸部叛回纥附吐蕃。在吐蕃“厚赂见诱”下,葛(逻)禄、白服突厥先后归附吐蕃,稍后吐蕃与葛逻禄、白服突厥一起急攻北庭,遭受回纥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至此,由于回纥的“贪狠、征求无度”最终导致沙陀摆脱回纥统治,双方附属关系宣告结束。
归附吐蕃之后的沙陀不但在战争中常被驱为前锋,而且被吐蕃无端猜疑为私通回纥,面临被迁至河外的危险境地。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举众归唐,掀开其历史发展中崭新的一页。
三、沙陀与吐蕃之关系
吐蕃是历史上由藏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其族源可追溯至西羌的一支发羌。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也是发生在唐朝征讨西突厥的战场上。双方之间关系也是经历了“敌—友—敌”的转变。
沙陀与吐蕃的首次接触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昆丘道行军中。此次行军之前唐朝曾对吐蕃发起过洮河道行军,但双方很快结束战争化敌为友,此后唐又应吐蕃请求于贞观十五年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与吐蕃间结成了甥舅关系①。在此背景下,吐蕃作为唐朝友军与铁勒十三州、(东)突厥、吐谷浑等一道参加了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征讨西突厥的昆丘道行军②。如前所述,此次行军首战便以大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史料记载的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疲于应付叛乱,吐蕃乘机屡次入侵唐朝。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③;“乾元以后,吐蕃乘机间隙,日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④。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地区基本为吐蕃所占领。
吐蕃进攻河陇地区时,沙陀可能在唐朝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从当时唐朝政府授予沙陀首领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骨咄支)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⑤唐朝政府遥授朱邪尽忠“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说明沙陀在河西地区与吐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继续进攻北庭,此时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守军相依,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御。五代人赵凤所撰《后唐懿祖纪年录》对此有详细记载:“德宗贞元五年,回纥葛禄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纥忠贞可汗,附于吐蕃,因为向导,驱吐蕃之众三十万寇我北庭。烈考(朱邪尽忠)谓忠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灵、盐,闻唐天子欲与赞普和亲,可汗数世有功,尚主,恩若娇儿,若赞普有恩于唐,则可汗必无前日之宠矣。’忠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将杨袭古固守北庭,无路归朝,今吐蕃、突厥并兵攻之,倘无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没,次及于吾,可汗得无虑乎!’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⑥但是回纥与沙陀的救援并没有改变北庭陷落的命运,加上回纥对其“贪狠、征求无度”,最终沙陀随北庭守军一道于贞元六年(790年)投降了吐蕃。至此,沙陀与吐蕃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了从属关系。
沙陀降蕃后其首领朱邪尽忠被授予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被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由于沙陀人骁勇善战,勇冠诸胡,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①,故沙陀部落死伤甚多,加上吐蕃对其横征暴敛,沙陀对吐蕃的统治无法忍受。后来,“回鹘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即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地域,当时为偏僻荒凉之地),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行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俞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欲迁②。回纥取凉州被吐蕃怀疑为沙陀勾结回纥所为③其于河外,导致沙陀举族愁怨,最终东归唐朝。沙陀与吐蕃仅二十年的从属关系宣告结束。
元和三年沙陀脱离吐蕃统治,开始了东归唐朝、投靠灵州节度使范希朝的历程。沙陀的东归激起了吐蕃的愤怒,吐蕃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此时沙陀与吐蕃已由原来的从属关系重新转变为敌对关系。
对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记载:“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傍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落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裒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④沙陀自甘州出发之际,共有部众“三万余落”,东归途中遭吐蕃追杀,到达盐州时仅剩近三千人,且已饥寒交迫,劳疲不堪。
四、沙陀与葛逻禄之关系
葛逻禄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活动中心“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①,相当于今新疆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它与处月一样,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属西突厥之别部。由于葛逻禄地处东、西突厥之间,因此常视双方力量之消长而叛附不定②。
沙陀与葛逻禄之间的关系发生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左右。其时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归唐,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命叶护阿史那贺鲁统治东部天山地区。史称:“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③沙陀与葛逻禄开始发生关系。
唐朝平定西突厥之前,沙陀与葛逻禄一道在阿史那贺鲁指挥之下对抗唐朝。永徽元年(650年),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④反唐。之后,唐朝政府组织了数次行军,征讨西突厥。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⑤。葛逻禄与处月在同唐军对抗中遭受重创。
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之后,唐朝于显庆三年(658年)设立羁縻州府以处置葛逻禄部众:以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至阿拉湖一带;以炽俟部置大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青河以南、乌伦古河下游地区;以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以北、斋桑泊以南地区。沙陀之处月、射脾部亦设金满州、沙陀州以妥善安置。归唐后的沙陀与葛逻禄之间再度发生关系。
近年出土的《唐龙朔二、三年(662—663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及《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①两份文书记载了两者之间发生的一件事:龙朔元年,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被贼人打散,有一千帐从金山(阿尔泰山)南下,在金满州地域停住,金满州都督沙陀某某将这一信息上报朝廷。朝廷分别给燕然都护府、哥(葛)逻禄部下敕令,命燕然都护府与西州都督府相知会,将停住金满州的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遣返大漠都督府原住地。龙朔二年,燕然都护府获取哥(葛)逻禄首领咄俟斤乌骑支陈状,云该部在龙朔元年敕令下达之前已经在金满州有水之处种下麦田,而且该部所放养的牲畜因遭受暴风雪,缺乏充足的草料,无法长途跋涉回归原住地,希望迁往甘州。之后龙朔三年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又相知会,力促哥(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留住金满州的葛逻禄仅五十帐,其他帐已经入京,故未能立马返回原住地。
通过这两份出土文献可以看出,葛逻禄归唐之后,曾流落至金满州境内,并从事农业生产,其间肯定得到了沙陀的照顾。尽管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数次规劝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葛逻禄留恋金满州之地,迟迟不归。该文书没有显示该事的最终结果,但从葛逻禄的态度上看,估计有部分葛逻禄人留在了金满州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最终融入沙陀部落当中。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减弱,沙陀同葛逻禄、白服(一作白眼)突厥一道处于回鹘的统治之下。然而“回鹘数侵掠之”,贞元五年(789年),葛逻禄部“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接着,吐蕃率葛逻禄、白服之众进略北庭,回鹘数战皆败。最终,遭受回鹘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此后,沙陀被吐蕃迁往河西地区,而葛逻禄主要活动于中亚一带,沙陀与葛逻禄的交往由此中断。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