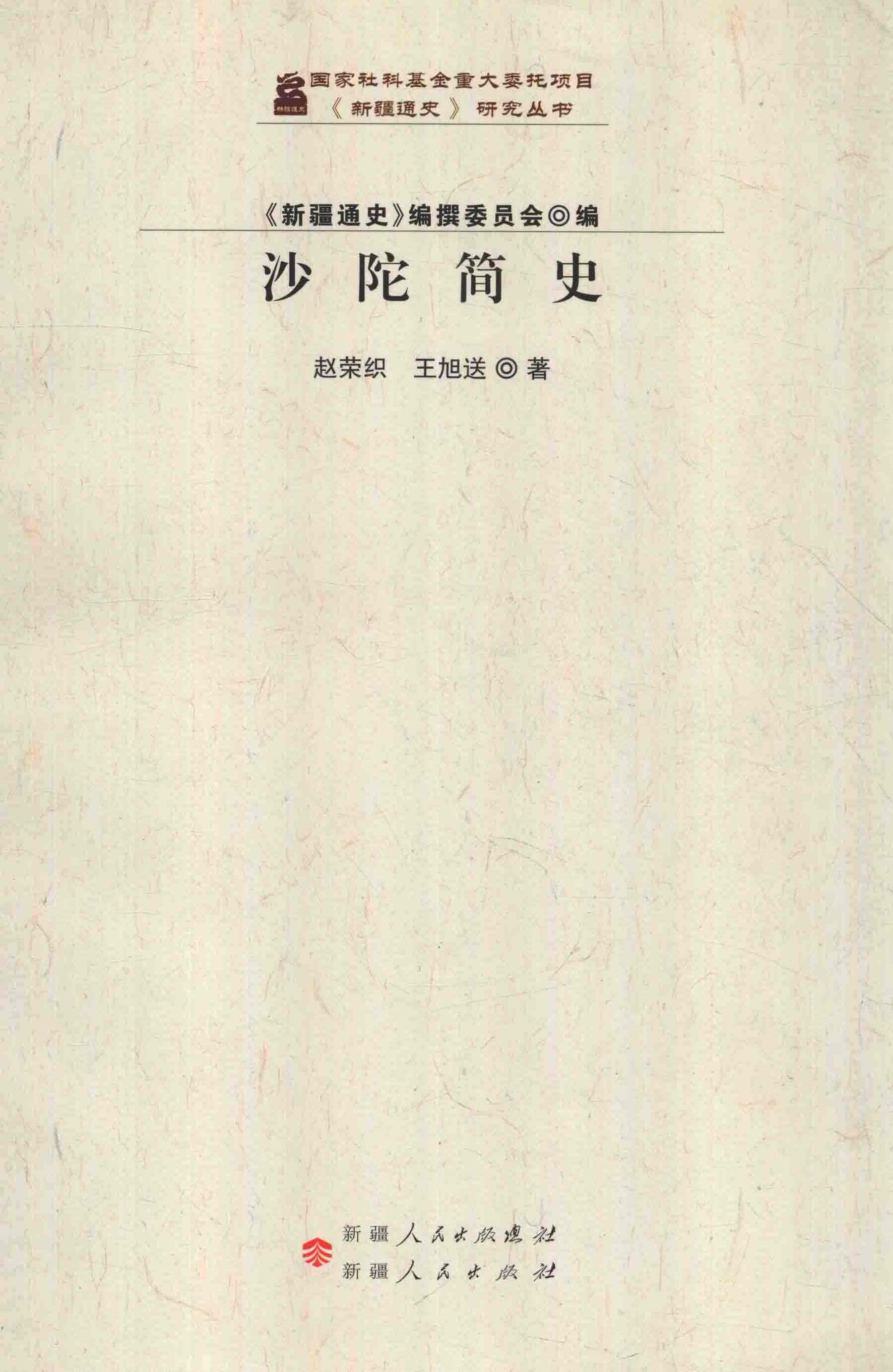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一、学界观点综述
关于沙陀的源出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沙陀源自回纥部。五代孙光宪持此说。他于《北梦琐言》云:“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陁碛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①回纥和沙陀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之间经历了唐朝平阿史那贺鲁时的敌对关系,到安史之乱及吐蕃取西域时的同盟关系,再到沙陀内迁后的重新敌对的关系,但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能说明沙陀源自回纥。对此,樊文礼通过详细分析对沙陀族源回纥说进行了驳斥,这里无需赘言①。
第二,沙陀乃月氏别种。清代和宁(和瑛)持此说。其《三州辑略》云:“沙陀金山,月氏别种西突厥之苗裔,本号朱邪,世居金沙山之阳,蒲昌海之北。”②然作者并未对其立论依据进行阐述。
第三,沙陀源自铁勒之同罗、仆固部。陶懋炳、韩国磐持此说③。其主要依据是《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所记。《唐书·武皇纪》云:“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④这种观点早在宋代时就已经遭到欧阳修的质疑,其于《新五代史·庄宗纪上》云:“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夷狄无姓氏,硃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硃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⑤这种观点的错误可从两方面说明:一、从从属关系上讲,沙陀属西突厥统治,而同罗、仆固则属东突厥强部;二、从地理位置而言,沙陀位于东部天山,而同罗、仆固位于漠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沙陀源自粟特。钱伯泉、李树辉即持此说。钱伯泉认为:“沙陀突厥应是投归突厥,自成部落,由经商而改营游牧的粟特人部落”⑥;李树辉据《新唐书·沙陀传》认为,“处月也便是沙陀。沙陀即粟特”⑦。两位先生主要根据语音对转及其沙陀人的体貌特征作此论断,尚无可靠史料佐证。
第五,沙陀源自突厥乌古斯。苏联学者巴托尔德持此观点。他于《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云:“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有一部分迁到中国东突厥斯以后,中国人称为沙陀(Sǎ-to),即草原居民之意,这一批突厥人早在九世纪初期就据有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破城子),其后由于西方自己同族人的压迫,只得继续向东进入中国领土内,参加了在九世纪后期在中国爆发的内乱。”①此种观点,不知作者何据。
第六,沙陀族源多源。张西曼、朱绍侯持沙陀族源双元论:张西曼认为“沙陀—萨尔特(缠回)就是回纥和大月氏的混合种..沙陀的母系主要为大月氏..父系主要为回纥”②;朱绍侯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是由大月氏土著和回纥人混合形成的”③。持族源多元论者比较多,概其要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徐庭云于《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认为,史籍中记载的“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这无疑是正确的”,除此外,“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三个主要的民族成分,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④;蔡家艺认为,“沙陀”一称,“主要是指以处月部为主,包括处密、射脾二部在内的游牧群体”⑤;郭平梁认为,沙陀渊源于处月、处密、射脾部⑥;宋肃瀛认为,沙陀是以射脾部为主,与留居高昌北山的各个部落结合而成的⑦。
第七,沙陀源自处月。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说者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中的一段史料:“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①,其后的胡三省在《通鉴考异》也持此说②,后世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王仲荦云:“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因此人称之沙陀突厥”“西突厥强盛时,处月③;林幹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处月部,与西突厥别部杂处,分据伊丽河流域,后西突厥衰乱,处月徙居蒲类海之东,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④;林惠祥云:“沙陀突厥原为西突厥之处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实即处月异译也”⑤;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⑥;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属于西突厥”,“为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处月’、‘朱邪’为同音异译,皆为突厥语‘沙碛’之意”⑦;刘义棠云:“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后并以朱邪为姓..朱邪、处月乃为突厥语沙碛之义,而沙陀却为汉语之称”⑧;周伟洲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其源于西突厥处月部。”⑨樊文礼则将沙陀族源细化到处月的分支——朱邪部,其大作《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云:“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⑩
在沙陀族源诸说之中,持沙陀源自处月说占主流。我们认为,在沙陀早期历史中,沙陀与处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下面我们将利用相关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的相关成果进行阐述。
二、早期沙陀与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
关于沙陀与处月的关系,学者多囿于《新唐书·沙陀传》的相关记载,认为两者为一。元代耶律铸则在此基础上有更深入的论述,其《涿邪山诗》云:“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为川阙。”①古人的这些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黄文弼即云,“处月”部姓“朱邪(或称朱耶)”,“朱邪”、“处月”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意为“沙碛”②;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亦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③;蔡家艺也认为上述说法“大体可信”④。显然,他们普遍认为“沙陀”、“处月”、“朱邪”虽称呼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
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先生就在其大作《隋唐史》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一,“哥舒翰所领诸蕃兵,朱邪与沙陀分为两部(见廿七节)⑤;二,“只看《新·传》太宗时有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新·纪》永徽二年有处月朱邪孤注,同时复有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处月、朱邪往往连称,朱邪不能概处月,盛昱阙特勤碑已举其证”⑥。岑先生通过分析,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一、处月、朱邪非一声之音转;二、早期沙陀、处月是二非一。岑先生所论甚确。然岑先生的论证并未引起学界太多注意。
下面我们将在岑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早期沙陀、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的观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处月与朱邪之间的关系。《新唐书·沙陀传》载:“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旧唐书·高宗传》载:“显庆元年八月..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哥逻禄获刺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从上述引文来看,朱邪阙俟斤、预支俟斤分别代表处月的两支部落。则,朱邪乃处月下属部落之一无疑。
关于沙陀部落早期活动的记载甚少,唯有《新唐书·沙陀传》中有一详细记载:“永徽(650—655年)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在这段话中,处月属部之一的朱邪与沙陀两个部落同时并称,而且这两部落在“贺鲁反”这一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一方站在唐朝一边,唐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而另一方则以逆唐而遭首领被斩、九千人被俘的悲惨结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沙陀、处月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退一步说,两者顶多是同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个部落。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我们从一些出土墓志、碑铭、文书中也发现了相关佐证。2004年春,洛阳邙山出土了唐代名将李释子墓志。志石青石质,广73厘米、宽73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书32行,行满32字,志文由中散大夫褚秀撰。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久视初(700年),(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①在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之时,沙陀部的首领沙陀金山正在墨离军讨击使任上,直到长安二年(702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沙陀金山所任墨离军讨击使在当时归属瓜州府管辖,则沙陀金山所统之沙陀部当不在李释子所任之“处月大使”管辖范围内,从地理范畴来讲沙陀与处月应不是同一部落。
又,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从中国掠走的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文书,即:《开元十六年(728年)朱邪部落请纸文书》(大谷5840)。兹移录全文如下:
〔第一纸〕朱邪部落请纸文书
(前欠)
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典渠思 忠牒
2 首领阙俟斤朱邪波德〓
3 付 司 楚 珪 示
4 十九日
5 八月十九日录事 礼 受
6 录事参军 沙安 付
7 检 案 沙 白
8 十九日
...................
〔第二纸〕
9 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10 八月 日 史 李 艺 牒
11 朱 邪 部 落 所 请 次 案 共
12 壹 伯张 状来。检 到 不
13 虚。 记 谘。沙安白。
14 十九日。
15 依 判 谘 希 望 示
16 十九日
17 依 判 谘 球 之 示
18 十九日
19 依 判 楚 珪 示
20 十九日
...................
〔第三纸〕
2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22 史 李 艺
23 录事参军 沙安
24 史。25 八月十九日受。即日行判。
26 录 事 礼 检 无 稽 失。
27 录事参军 自判
28 案为朱邪部落检领纸到事。
(后略)①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邪波德的签署,时间是开元十六年(728年)。作为未经统治者人为篡改的原始档案,吐鲁番文书的可靠性应是高于其他文献的。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至迟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朱邪”仍然以一个部落的名义出现。相同的证据还见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阙特勤碑》汉文部分是唐玄宗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碑文有如下内容:“君讳阙特勤碑(685—731年)...故能承顺友爱,辅成规略,北燮玄雷之境,西邻处月之郊..以亲我有唐也。”②该碑文说明,阙特勤在位之时处月部落尚存。而据《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距开元十六年不久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有沙陀部落居于伊州。其原文如下:“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③在相近的时间内,出现两个身处不同地区、名称截然不同的部落:朱邪和沙陀,则处月和沙陀在730年左右仍是两个不同的部落。
三、沙陀的源出射脾及射脾简史
关于民族的源出,学界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不同观点。持“一元论”者从民族成分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先后顺序出发,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部族成分看成是该民族的唯一族源。在他们看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像一条大河蜿蜒变化,虽然在其奔流过程中不断有“支流”加入,然而其源头只有一个。持“多元论”者大都受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论”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不一定是由某一个氏族或部族一成不变地世代相袭至今,而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部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从而形成多元统一体。
我们认为,对于许多缺乏文字记载的弱小民族而言,是无法确定该民族的哪一个部族成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因此也无法断定其最早的族源成分,沙陀应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比较认同其源出“多元论”。我们认为,沙陀的源出应以处月和射脾为主,并整合处密等其他部落。
对于处月和射脾的合并,我们认为应作如下解释:首先,射脾本与处月无干,只是在两者归唐之后,文献常将两者混为一谈,称部落名为“沙陀”,族姓则为“朱邪”。其原因可能是,唐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因射脾酋长沙陀那速归唐有功,唐朝以原阿史那贺鲁所领授予之,且以其姓命名该部,而原阿史那贺鲁统治之下的处月则转归沙陀那速统治,由此开始了射脾与处月合并之路。其次,尽管两个部落在归唐之后走上合并之路,但从人数来看,处月应远在射脾之上,仅永徽二年(651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在对处月一战之中即“俘九千人”。为平衡两者关系,可能后来新的沙陀部遂以“沙陀”为部族之名,而以“朱邪”为部族之姓。
对于沙陀与射脾的关系,岑仲勉先生从语音学角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证。首先,岑先生认为射脾即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失毕”①之异译:“按贺鲁所统为失毕五姓及处月、处蜜等众。..失毕亦翻失卑。准此以推,射脾盖失毕之异译。..五失毕之长为俟斤。《新唐书·沙陀传》言射脾俟斤,又射脾即失毕之旁证。”②岑先生言“失毕亦翻失卑”甚确,然岑先生认为射脾亦即弩失毕,我们认为欠妥。在阿史那贺鲁之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时,已将所统突厥部落划分十部,五咄陆居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之西①。而阿史那贺鲁牙帐在西州之北多逻斯川,其所统之五部均在东部天山地区②,两者地理位置根本不符。我们认为,阿史那贺鲁所统部“弩失毕”之“弩”为衍(吴玉贵亦持类似观点)③。其次,岑先生认为沙陀之语原即唐史中常见之“失毕”或“矢毕”:“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之‘sadapyt’相比;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④综合岑先生上述论证中可以看出,岑先生主张“沙陀”从语原上源自“射脾”。
射脾是唐朝初期活动在东部天山地区且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一个部落。阿斯塔纳一七一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关于射脾活动的记载,是目前所知的射脾最早的活动。这是一件记载高昌麴氏王朝与突厥人往来的官方文书。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
[前欠]
1 次羁人赵头六、王欢儿贰人,付宁僧护,用看珂
2 懃苏弩胡鹿大官、公主时健大官
3 付毛海龙,用看毗伽公主寒
(略)
9 纥达官伍日。次小张海柱,付康善财,用看坞耆来射卑
10 妇儿伍日。令狐资弥胡,付王善祐子,用看尸不遝〓
(略)
21 看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次吕隆伯,付(略)
33 伯儿,用看居〓抴使伍日。次赵小儿,付康善财,用看
34 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侍郎麴延陀侍讲辛武护
(略)①
这件文书第9行、21行、34行的“坞耆”为“焉耆”的异译,“射卑”也即“射脾”。②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射脾是游牧于焉耆境内天山之中而且与高昌麴氏王朝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部落。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高昌延寿十四年统治西域的西突厥可汗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同俄设,则此时的射脾当归沙钵罗蛭利失可汗统治。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在位时期西突厥内忧外患交加、危机四伏,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十三年,“咥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③。咥利失之后继位者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与乙毗咄陆瓜分西突厥汗国,游牧于焉耆附近的射脾当归属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统治。
贞观十五年(641年),“咄陆可汗与叶护颇相攻击..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乙毗咄陆可汗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之后,“自恃其强,专擅西域”④,整个西域处于乙毗咄陆可汗统治之下,此时的射脾应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
乙毗咄陆统辖下的射脾早期是否曾归统辖东部天山诸部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由于史料阙如,尚不得而知,但阿史那贺鲁继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东部天山诸部时期,射脾归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当无疑。阿史那贺鲁统治天山东部时期进行过一系列反唐活动,射脾也追随阿史那贺鲁参与了反唐活动。高宗初年唐政府组织弓月道行军征讨阿史那贺鲁之前,首任庭州刺史骆宏义所上唐帝之疏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该疏云:“臣闻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事无常准。今有降胡来言:贺鲁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积雪,汉兵必不远来。诚宜乘其此便,一举可以除剿。若迁延待春,恐事久生变,纵不能结援诸国,必应远迹遁逃。且兵马此行,本诛贺鲁,处密已许款诚,处木昆等各思免祸,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虑更乌合。然严冬风劲,马瘦兵寒,瘃堕之忧,难量进退。又不可久停兵马,虚费边粮。见我不前,成其党附。伏望且宽处月、处密之罪,以诛贺鲁为名,除祸务绝其原,未可先取其枝叶。但此两姓,见其坐夺,不示招携,必自深据。如弃而西过,则近有后忧。先事诛夷,未可即克。舍而勿问,则惑义前驱,事定从宜。除申吊伐,此乃威恩兼举,远慑迩安。向使兵马早来,贺鲁久已悬首。前机虽失,须为别图。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芯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掩袭。大军顿于凭水,秣马畜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且番人行动,须约汉兵,东西犄角,又资翘翼,简胡骑以率其前,率汉兵以蹑其后。贺鲁进退无路,理即可擒,百胜之谋,在斯一举。臣恐建方至日,为计不同,军谋乖舛,后悔无及。”①
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诸部的招慰活动中,射脾部在其首领沙陀那速的领导下归唐,归唐后的射脾部获得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前所领的权力,从而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射脾的族源似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因为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前,“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为铁勒诸部落游牧之地。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这些铁勒部落几乎全部改用“突厥”族名,虽然他们同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关系亲疏不一,但他们“族名相同,语言相近,风俗相似”,是异姓突厥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射脾所处之位置恰与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所处之位置相吻合,故射脾极有可能源自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中之一部。芮传明从语音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铁勒属部之“苏婆”(suo一b’u〓)和射脾(dz’ia—b’jie)从语音来看极为接近,可以被看作为同一名称的异译,因此他断定,射脾源自西域铁勒部落中的苏婆部②。
关于沙陀的源出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沙陀源自回纥部。五代孙光宪持此说。他于《北梦琐言》云:“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陁碛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①回纥和沙陀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之间经历了唐朝平阿史那贺鲁时的敌对关系,到安史之乱及吐蕃取西域时的同盟关系,再到沙陀内迁后的重新敌对的关系,但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能说明沙陀源自回纥。对此,樊文礼通过详细分析对沙陀族源回纥说进行了驳斥,这里无需赘言①。
第二,沙陀乃月氏别种。清代和宁(和瑛)持此说。其《三州辑略》云:“沙陀金山,月氏别种西突厥之苗裔,本号朱邪,世居金沙山之阳,蒲昌海之北。”②然作者并未对其立论依据进行阐述。
第三,沙陀源自铁勒之同罗、仆固部。陶懋炳、韩国磐持此说③。其主要依据是《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所记。《唐书·武皇纪》云:“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④这种观点早在宋代时就已经遭到欧阳修的质疑,其于《新五代史·庄宗纪上》云:“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夷狄无姓氏,硃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硃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⑤这种观点的错误可从两方面说明:一、从从属关系上讲,沙陀属西突厥统治,而同罗、仆固则属东突厥强部;二、从地理位置而言,沙陀位于东部天山,而同罗、仆固位于漠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沙陀源自粟特。钱伯泉、李树辉即持此说。钱伯泉认为:“沙陀突厥应是投归突厥,自成部落,由经商而改营游牧的粟特人部落”⑥;李树辉据《新唐书·沙陀传》认为,“处月也便是沙陀。沙陀即粟特”⑦。两位先生主要根据语音对转及其沙陀人的体貌特征作此论断,尚无可靠史料佐证。
第五,沙陀源自突厥乌古斯。苏联学者巴托尔德持此观点。他于《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云:“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有一部分迁到中国东突厥斯以后,中国人称为沙陀(Sǎ-to),即草原居民之意,这一批突厥人早在九世纪初期就据有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破城子),其后由于西方自己同族人的压迫,只得继续向东进入中国领土内,参加了在九世纪后期在中国爆发的内乱。”①此种观点,不知作者何据。
第六,沙陀族源多源。张西曼、朱绍侯持沙陀族源双元论:张西曼认为“沙陀—萨尔特(缠回)就是回纥和大月氏的混合种..沙陀的母系主要为大月氏..父系主要为回纥”②;朱绍侯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是由大月氏土著和回纥人混合形成的”③。持族源多元论者比较多,概其要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徐庭云于《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认为,史籍中记载的“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这无疑是正确的”,除此外,“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三个主要的民族成分,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④;蔡家艺认为,“沙陀”一称,“主要是指以处月部为主,包括处密、射脾二部在内的游牧群体”⑤;郭平梁认为,沙陀渊源于处月、处密、射脾部⑥;宋肃瀛认为,沙陀是以射脾部为主,与留居高昌北山的各个部落结合而成的⑦。
第七,沙陀源自处月。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说者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中的一段史料:“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①,其后的胡三省在《通鉴考异》也持此说②,后世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王仲荦云:“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因此人称之沙陀突厥”“西突厥强盛时,处月③;林幹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处月部,与西突厥别部杂处,分据伊丽河流域,后西突厥衰乱,处月徙居蒲类海之东,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④;林惠祥云:“沙陀突厥原为西突厥之处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实即处月异译也”⑤;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⑥;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属于西突厥”,“为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处月’、‘朱邪’为同音异译,皆为突厥语‘沙碛’之意”⑦;刘义棠云:“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后并以朱邪为姓..朱邪、处月乃为突厥语沙碛之义,而沙陀却为汉语之称”⑧;周伟洲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其源于西突厥处月部。”⑨樊文礼则将沙陀族源细化到处月的分支——朱邪部,其大作《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云:“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⑩
在沙陀族源诸说之中,持沙陀源自处月说占主流。我们认为,在沙陀早期历史中,沙陀与处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下面我们将利用相关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的相关成果进行阐述。
二、早期沙陀与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
关于沙陀与处月的关系,学者多囿于《新唐书·沙陀传》的相关记载,认为两者为一。元代耶律铸则在此基础上有更深入的论述,其《涿邪山诗》云:“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为川阙。”①古人的这些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黄文弼即云,“处月”部姓“朱邪(或称朱耶)”,“朱邪”、“处月”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意为“沙碛”②;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亦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③;蔡家艺也认为上述说法“大体可信”④。显然,他们普遍认为“沙陀”、“处月”、“朱邪”虽称呼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
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先生就在其大作《隋唐史》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一,“哥舒翰所领诸蕃兵,朱邪与沙陀分为两部(见廿七节)⑤;二,“只看《新·传》太宗时有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新·纪》永徽二年有处月朱邪孤注,同时复有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处月、朱邪往往连称,朱邪不能概处月,盛昱阙特勤碑已举其证”⑥。岑先生通过分析,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一、处月、朱邪非一声之音转;二、早期沙陀、处月是二非一。岑先生所论甚确。然岑先生的论证并未引起学界太多注意。
下面我们将在岑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早期沙陀、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的观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处月与朱邪之间的关系。《新唐书·沙陀传》载:“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旧唐书·高宗传》载:“显庆元年八月..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哥逻禄获刺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从上述引文来看,朱邪阙俟斤、预支俟斤分别代表处月的两支部落。则,朱邪乃处月下属部落之一无疑。
关于沙陀部落早期活动的记载甚少,唯有《新唐书·沙陀传》中有一详细记载:“永徽(650—655年)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在这段话中,处月属部之一的朱邪与沙陀两个部落同时并称,而且这两部落在“贺鲁反”这一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一方站在唐朝一边,唐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而另一方则以逆唐而遭首领被斩、九千人被俘的悲惨结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沙陀、处月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退一步说,两者顶多是同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个部落。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我们从一些出土墓志、碑铭、文书中也发现了相关佐证。2004年春,洛阳邙山出土了唐代名将李释子墓志。志石青石质,广73厘米、宽73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书32行,行满32字,志文由中散大夫褚秀撰。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久视初(700年),(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①在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之时,沙陀部的首领沙陀金山正在墨离军讨击使任上,直到长安二年(702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沙陀金山所任墨离军讨击使在当时归属瓜州府管辖,则沙陀金山所统之沙陀部当不在李释子所任之“处月大使”管辖范围内,从地理范畴来讲沙陀与处月应不是同一部落。
又,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从中国掠走的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文书,即:《开元十六年(728年)朱邪部落请纸文书》(大谷5840)。兹移录全文如下:
〔第一纸〕朱邪部落请纸文书
(前欠)
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典渠思 忠牒
2 首领阙俟斤朱邪波德〓
3 付 司 楚 珪 示
4 十九日
5 八月十九日录事 礼 受
6 录事参军 沙安 付
7 检 案 沙 白
8 十九日
...................
〔第二纸〕
9 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10 八月 日 史 李 艺 牒
11 朱 邪 部 落 所 请 次 案 共
12 壹 伯张 状来。检 到 不
13 虚。 记 谘。沙安白。
14 十九日。
15 依 判 谘 希 望 示
16 十九日
17 依 判 谘 球 之 示
18 十九日
19 依 判 楚 珪 示
20 十九日
...................
〔第三纸〕
2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22 史 李 艺
23 录事参军 沙安
24 史。25 八月十九日受。即日行判。
26 录 事 礼 检 无 稽 失。
27 录事参军 自判
28 案为朱邪部落检领纸到事。
(后略)①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邪波德的签署,时间是开元十六年(728年)。作为未经统治者人为篡改的原始档案,吐鲁番文书的可靠性应是高于其他文献的。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至迟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朱邪”仍然以一个部落的名义出现。相同的证据还见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阙特勤碑》汉文部分是唐玄宗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碑文有如下内容:“君讳阙特勤碑(685—731年)...故能承顺友爱,辅成规略,北燮玄雷之境,西邻处月之郊..以亲我有唐也。”②该碑文说明,阙特勤在位之时处月部落尚存。而据《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距开元十六年不久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有沙陀部落居于伊州。其原文如下:“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③在相近的时间内,出现两个身处不同地区、名称截然不同的部落:朱邪和沙陀,则处月和沙陀在730年左右仍是两个不同的部落。
三、沙陀的源出射脾及射脾简史
关于民族的源出,学界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不同观点。持“一元论”者从民族成分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先后顺序出发,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部族成分看成是该民族的唯一族源。在他们看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像一条大河蜿蜒变化,虽然在其奔流过程中不断有“支流”加入,然而其源头只有一个。持“多元论”者大都受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论”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不一定是由某一个氏族或部族一成不变地世代相袭至今,而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部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从而形成多元统一体。
我们认为,对于许多缺乏文字记载的弱小民族而言,是无法确定该民族的哪一个部族成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因此也无法断定其最早的族源成分,沙陀应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比较认同其源出“多元论”。我们认为,沙陀的源出应以处月和射脾为主,并整合处密等其他部落。
对于处月和射脾的合并,我们认为应作如下解释:首先,射脾本与处月无干,只是在两者归唐之后,文献常将两者混为一谈,称部落名为“沙陀”,族姓则为“朱邪”。其原因可能是,唐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因射脾酋长沙陀那速归唐有功,唐朝以原阿史那贺鲁所领授予之,且以其姓命名该部,而原阿史那贺鲁统治之下的处月则转归沙陀那速统治,由此开始了射脾与处月合并之路。其次,尽管两个部落在归唐之后走上合并之路,但从人数来看,处月应远在射脾之上,仅永徽二年(651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在对处月一战之中即“俘九千人”。为平衡两者关系,可能后来新的沙陀部遂以“沙陀”为部族之名,而以“朱邪”为部族之姓。
对于沙陀与射脾的关系,岑仲勉先生从语音学角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证。首先,岑先生认为射脾即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失毕”①之异译:“按贺鲁所统为失毕五姓及处月、处蜜等众。..失毕亦翻失卑。准此以推,射脾盖失毕之异译。..五失毕之长为俟斤。《新唐书·沙陀传》言射脾俟斤,又射脾即失毕之旁证。”②岑先生言“失毕亦翻失卑”甚确,然岑先生认为射脾亦即弩失毕,我们认为欠妥。在阿史那贺鲁之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时,已将所统突厥部落划分十部,五咄陆居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之西①。而阿史那贺鲁牙帐在西州之北多逻斯川,其所统之五部均在东部天山地区②,两者地理位置根本不符。我们认为,阿史那贺鲁所统部“弩失毕”之“弩”为衍(吴玉贵亦持类似观点)③。其次,岑先生认为沙陀之语原即唐史中常见之“失毕”或“矢毕”:“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之‘sadapyt’相比;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④综合岑先生上述论证中可以看出,岑先生主张“沙陀”从语原上源自“射脾”。
射脾是唐朝初期活动在东部天山地区且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一个部落。阿斯塔纳一七一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关于射脾活动的记载,是目前所知的射脾最早的活动。这是一件记载高昌麴氏王朝与突厥人往来的官方文书。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
[前欠]
1 次羁人赵头六、王欢儿贰人,付宁僧护,用看珂
2 懃苏弩胡鹿大官、公主时健大官
3 付毛海龙,用看毗伽公主寒
(略)
9 纥达官伍日。次小张海柱,付康善财,用看坞耆来射卑
10 妇儿伍日。令狐资弥胡,付王善祐子,用看尸不遝〓
(略)
21 看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次吕隆伯,付(略)
33 伯儿,用看居〓抴使伍日。次赵小儿,付康善财,用看
34 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侍郎麴延陀侍讲辛武护
(略)①
这件文书第9行、21行、34行的“坞耆”为“焉耆”的异译,“射卑”也即“射脾”。②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射脾是游牧于焉耆境内天山之中而且与高昌麴氏王朝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部落。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高昌延寿十四年统治西域的西突厥可汗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同俄设,则此时的射脾当归沙钵罗蛭利失可汗统治。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在位时期西突厥内忧外患交加、危机四伏,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十三年,“咥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③。咥利失之后继位者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与乙毗咄陆瓜分西突厥汗国,游牧于焉耆附近的射脾当归属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统治。
贞观十五年(641年),“咄陆可汗与叶护颇相攻击..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乙毗咄陆可汗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之后,“自恃其强,专擅西域”④,整个西域处于乙毗咄陆可汗统治之下,此时的射脾应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
乙毗咄陆统辖下的射脾早期是否曾归统辖东部天山诸部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由于史料阙如,尚不得而知,但阿史那贺鲁继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东部天山诸部时期,射脾归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当无疑。阿史那贺鲁统治天山东部时期进行过一系列反唐活动,射脾也追随阿史那贺鲁参与了反唐活动。高宗初年唐政府组织弓月道行军征讨阿史那贺鲁之前,首任庭州刺史骆宏义所上唐帝之疏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该疏云:“臣闻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事无常准。今有降胡来言:贺鲁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积雪,汉兵必不远来。诚宜乘其此便,一举可以除剿。若迁延待春,恐事久生变,纵不能结援诸国,必应远迹遁逃。且兵马此行,本诛贺鲁,处密已许款诚,处木昆等各思免祸,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虑更乌合。然严冬风劲,马瘦兵寒,瘃堕之忧,难量进退。又不可久停兵马,虚费边粮。见我不前,成其党附。伏望且宽处月、处密之罪,以诛贺鲁为名,除祸务绝其原,未可先取其枝叶。但此两姓,见其坐夺,不示招携,必自深据。如弃而西过,则近有后忧。先事诛夷,未可即克。舍而勿问,则惑义前驱,事定从宜。除申吊伐,此乃威恩兼举,远慑迩安。向使兵马早来,贺鲁久已悬首。前机虽失,须为别图。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芯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掩袭。大军顿于凭水,秣马畜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且番人行动,须约汉兵,东西犄角,又资翘翼,简胡骑以率其前,率汉兵以蹑其后。贺鲁进退无路,理即可擒,百胜之谋,在斯一举。臣恐建方至日,为计不同,军谋乖舛,后悔无及。”①
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诸部的招慰活动中,射脾部在其首领沙陀那速的领导下归唐,归唐后的射脾部获得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前所领的权力,从而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射脾的族源似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因为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前,“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为铁勒诸部落游牧之地。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这些铁勒部落几乎全部改用“突厥”族名,虽然他们同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关系亲疏不一,但他们“族名相同,语言相近,风俗相似”,是异姓突厥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射脾所处之位置恰与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所处之位置相吻合,故射脾极有可能源自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中之一部。芮传明从语音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铁勒属部之“苏婆”(suo一b’u〓)和射脾(dz’ia—b’jie)从语音来看极为接近,可以被看作为同一名称的异译,因此他断定,射脾源自西域铁勒部落中的苏婆部②。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