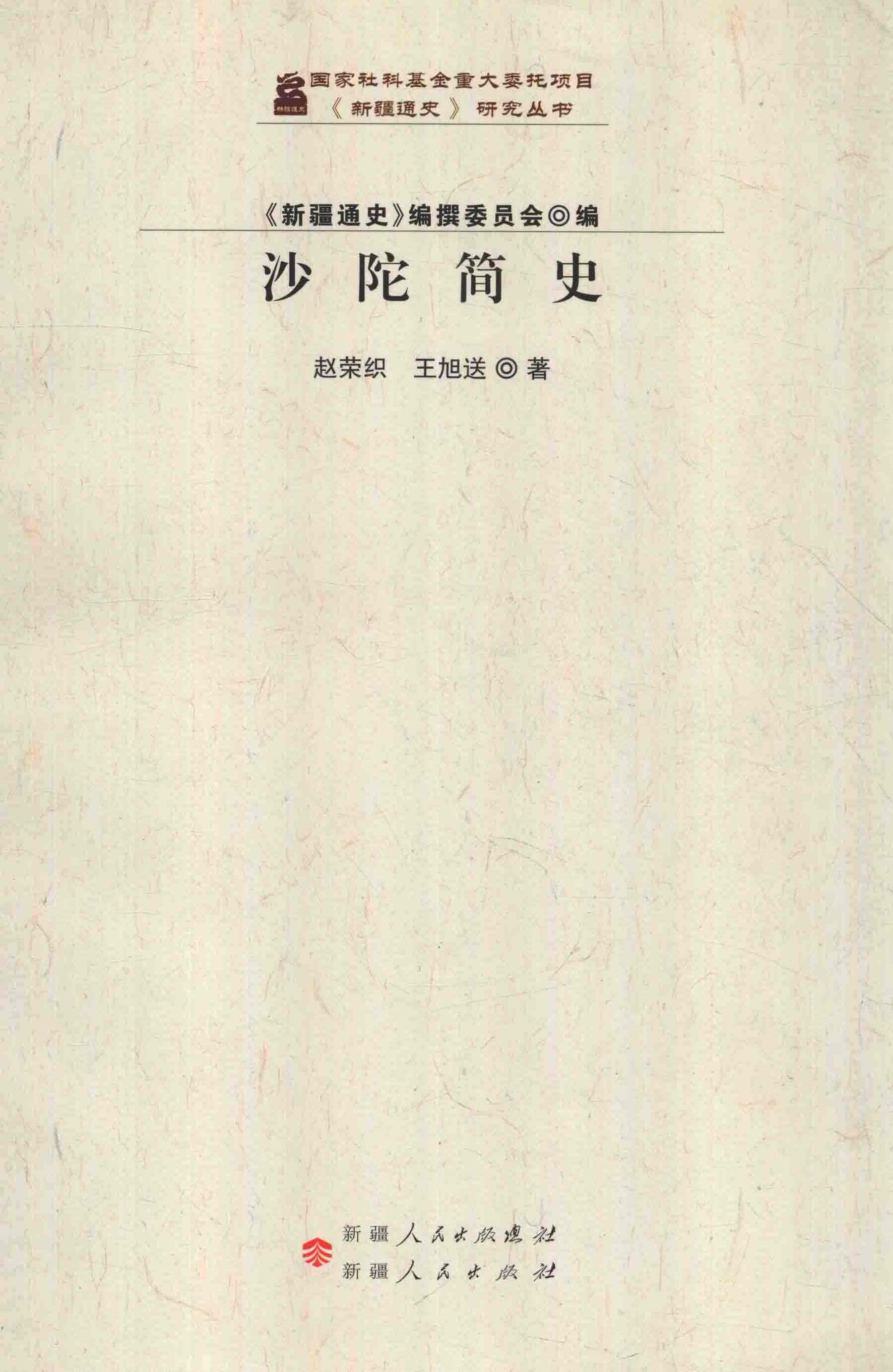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沙陀原是唐朝时期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一个弱小部族,本身没有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传统,而相关史料也缺乏准确、详细的记载,导致后世对沙陀早期的历史认识不清。本章试图从“沙陀的族源”、“沙陀早期活动区域”、“沙陀名号考实”、“沙陀与周边民族之关系”四个方面对沙陀早期历史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
第一节 沙陀之源出
一、学界观点综述
关于沙陀的源出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沙陀源自回纥部。五代孙光宪持此说。他于《北梦琐言》云:“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陁碛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①回纥和沙陀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之间经历了唐朝平阿史那贺鲁时的敌对关系,到安史之乱及吐蕃取西域时的同盟关系,再到沙陀内迁后的重新敌对的关系,但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能说明沙陀源自回纥。对此,樊文礼通过详细分析对沙陀族源回纥说进行了驳斥,这里无需赘言①。
第二,沙陀乃月氏别种。清代和宁(和瑛)持此说。其《三州辑略》云:“沙陀金山,月氏别种西突厥之苗裔,本号朱邪,世居金沙山之阳,蒲昌海之北。”②然作者并未对其立论依据进行阐述。
第三,沙陀源自铁勒之同罗、仆固部。陶懋炳、韩国磐持此说③。其主要依据是《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所记。《唐书·武皇纪》云:“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④这种观点早在宋代时就已经遭到欧阳修的质疑,其于《新五代史·庄宗纪上》云:“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夷狄无姓氏,硃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硃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⑤这种观点的错误可从两方面说明:一、从从属关系上讲,沙陀属西突厥统治,而同罗、仆固则属东突厥强部;二、从地理位置而言,沙陀位于东部天山,而同罗、仆固位于漠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沙陀源自粟特。钱伯泉、李树辉即持此说。钱伯泉认为:“沙陀突厥应是投归突厥,自成部落,由经商而改营游牧的粟特人部落”⑥;李树辉据《新唐书·沙陀传》认为,“处月也便是沙陀。沙陀即粟特”⑦。两位先生主要根据语音对转及其沙陀人的体貌特征作此论断,尚无可靠史料佐证。
第五,沙陀源自突厥乌古斯。苏联学者巴托尔德持此观点。他于《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云:“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有一部分迁到中国东突厥斯以后,中国人称为沙陀(Sǎ-to),即草原居民之意,这一批突厥人早在九世纪初期就据有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破城子),其后由于西方自己同族人的压迫,只得继续向东进入中国领土内,参加了在九世纪后期在中国爆发的内乱。”①此种观点,不知作者何据。
第六,沙陀族源多源。张西曼、朱绍侯持沙陀族源双元论:张西曼认为“沙陀—萨尔特(缠回)就是回纥和大月氏的混合种..沙陀的母系主要为大月氏..父系主要为回纥”②;朱绍侯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是由大月氏土著和回纥人混合形成的”③。持族源多元论者比较多,概其要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徐庭云于《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认为,史籍中记载的“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这无疑是正确的”,除此外,“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三个主要的民族成分,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④;蔡家艺认为,“沙陀”一称,“主要是指以处月部为主,包括处密、射脾二部在内的游牧群体”⑤;郭平梁认为,沙陀渊源于处月、处密、射脾部⑥;宋肃瀛认为,沙陀是以射脾部为主,与留居高昌北山的各个部落结合而成的⑦。
第七,沙陀源自处月。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说者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中的一段史料:“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①,其后的胡三省在《通鉴考异》也持此说②,后世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王仲荦云:“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因此人称之沙陀突厥”“西突厥强盛时,处月③;林幹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处月部,与西突厥别部杂处,分据伊丽河流域,后西突厥衰乱,处月徙居蒲类海之东,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④;林惠祥云:“沙陀突厥原为西突厥之处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实即处月异译也”⑤;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⑥;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属于西突厥”,“为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处月’、‘朱邪’为同音异译,皆为突厥语‘沙碛’之意”⑦;刘义棠云:“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后并以朱邪为姓..朱邪、处月乃为突厥语沙碛之义,而沙陀却为汉语之称”⑧;周伟洲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其源于西突厥处月部。”⑨樊文礼则将沙陀族源细化到处月的分支——朱邪部,其大作《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云:“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⑩
在沙陀族源诸说之中,持沙陀源自处月说占主流。我们认为,在沙陀早期历史中,沙陀与处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下面我们将利用相关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的相关成果进行阐述。
二、早期沙陀与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
关于沙陀与处月的关系,学者多囿于《新唐书·沙陀传》的相关记载,认为两者为一。元代耶律铸则在此基础上有更深入的论述,其《涿邪山诗》云:“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为川阙。”①古人的这些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黄文弼即云,“处月”部姓“朱邪(或称朱耶)”,“朱邪”、“处月”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意为“沙碛”②;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亦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③;蔡家艺也认为上述说法“大体可信”④。显然,他们普遍认为“沙陀”、“处月”、“朱邪”虽称呼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
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先生就在其大作《隋唐史》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一,“哥舒翰所领诸蕃兵,朱邪与沙陀分为两部(见廿七节)⑤;二,“只看《新·传》太宗时有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新·纪》永徽二年有处月朱邪孤注,同时复有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处月、朱邪往往连称,朱邪不能概处月,盛昱阙特勤碑已举其证”⑥。岑先生通过分析,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一、处月、朱邪非一声之音转;二、早期沙陀、处月是二非一。岑先生所论甚确。然岑先生的论证并未引起学界太多注意。
下面我们将在岑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早期沙陀、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的观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处月与朱邪之间的关系。《新唐书·沙陀传》载:“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旧唐书·高宗传》载:“显庆元年八月..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哥逻禄获刺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从上述引文来看,朱邪阙俟斤、预支俟斤分别代表处月的两支部落。则,朱邪乃处月下属部落之一无疑。
关于沙陀部落早期活动的记载甚少,唯有《新唐书·沙陀传》中有一详细记载:“永徽(650—655年)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在这段话中,处月属部之一的朱邪与沙陀两个部落同时并称,而且这两部落在“贺鲁反”这一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一方站在唐朝一边,唐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而另一方则以逆唐而遭首领被斩、九千人被俘的悲惨结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沙陀、处月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退一步说,两者顶多是同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个部落。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我们从一些出土墓志、碑铭、文书中也发现了相关佐证。2004年春,洛阳邙山出土了唐代名将李释子墓志。志石青石质,广73厘米、宽73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书32行,行满32字,志文由中散大夫褚秀撰。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久视初(700年),(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①在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之时,沙陀部的首领沙陀金山正在墨离军讨击使任上,直到长安二年(702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沙陀金山所任墨离军讨击使在当时归属瓜州府管辖,则沙陀金山所统之沙陀部当不在李释子所任之“处月大使”管辖范围内,从地理范畴来讲沙陀与处月应不是同一部落。
又,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从中国掠走的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文书,即:《开元十六年(728年)朱邪部落请纸文书》(大谷5840)。兹移录全文如下:
〔第一纸〕朱邪部落请纸文书
(前欠)
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典渠思 忠牒
2 首领阙俟斤朱邪波德〓
3 付 司 楚 珪 示
4 十九日
5 八月十九日录事 礼 受
6 录事参军 沙安 付
7 检 案 沙 白
8 十九日
...................
〔第二纸〕
9 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10 八月 日 史 李 艺 牒
11 朱 邪 部 落 所 请 次 案 共
12 壹 伯张 状来。检 到 不
13 虚。 记 谘。沙安白。
14 十九日。
15 依 判 谘 希 望 示
16 十九日
17 依 判 谘 球 之 示
18 十九日
19 依 判 楚 珪 示
20 十九日
...................
〔第三纸〕
2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22 史 李 艺
23 录事参军 沙安
24 史。25 八月十九日受。即日行判。
26 录 事 礼 检 无 稽 失。
27 录事参军 自判
28 案为朱邪部落检领纸到事。
(后略)①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邪波德的签署,时间是开元十六年(728年)。作为未经统治者人为篡改的原始档案,吐鲁番文书的可靠性应是高于其他文献的。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至迟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朱邪”仍然以一个部落的名义出现。相同的证据还见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阙特勤碑》汉文部分是唐玄宗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碑文有如下内容:“君讳阙特勤碑(685—731年)...故能承顺友爱,辅成规略,北燮玄雷之境,西邻处月之郊..以亲我有唐也。”②该碑文说明,阙特勤在位之时处月部落尚存。而据《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距开元十六年不久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有沙陀部落居于伊州。其原文如下:“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③在相近的时间内,出现两个身处不同地区、名称截然不同的部落:朱邪和沙陀,则处月和沙陀在730年左右仍是两个不同的部落。
三、沙陀的源出射脾及射脾简史
关于民族的源出,学界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不同观点。持“一元论”者从民族成分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先后顺序出发,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部族成分看成是该民族的唯一族源。在他们看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像一条大河蜿蜒变化,虽然在其奔流过程中不断有“支流”加入,然而其源头只有一个。持“多元论”者大都受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论”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不一定是由某一个氏族或部族一成不变地世代相袭至今,而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部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从而形成多元统一体。
我们认为,对于许多缺乏文字记载的弱小民族而言,是无法确定该民族的哪一个部族成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因此也无法断定其最早的族源成分,沙陀应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比较认同其源出“多元论”。我们认为,沙陀的源出应以处月和射脾为主,并整合处密等其他部落。
对于处月和射脾的合并,我们认为应作如下解释:首先,射脾本与处月无干,只是在两者归唐之后,文献常将两者混为一谈,称部落名为“沙陀”,族姓则为“朱邪”。其原因可能是,唐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因射脾酋长沙陀那速归唐有功,唐朝以原阿史那贺鲁所领授予之,且以其姓命名该部,而原阿史那贺鲁统治之下的处月则转归沙陀那速统治,由此开始了射脾与处月合并之路。其次,尽管两个部落在归唐之后走上合并之路,但从人数来看,处月应远在射脾之上,仅永徽二年(651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在对处月一战之中即“俘九千人”。为平衡两者关系,可能后来新的沙陀部遂以“沙陀”为部族之名,而以“朱邪”为部族之姓。
对于沙陀与射脾的关系,岑仲勉先生从语音学角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证。首先,岑先生认为射脾即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失毕”①之异译:“按贺鲁所统为失毕五姓及处月、处蜜等众。..失毕亦翻失卑。准此以推,射脾盖失毕之异译。..五失毕之长为俟斤。《新唐书·沙陀传》言射脾俟斤,又射脾即失毕之旁证。”②岑先生言“失毕亦翻失卑”甚确,然岑先生认为射脾亦即弩失毕,我们认为欠妥。在阿史那贺鲁之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时,已将所统突厥部落划分十部,五咄陆居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之西①。而阿史那贺鲁牙帐在西州之北多逻斯川,其所统之五部均在东部天山地区②,两者地理位置根本不符。我们认为,阿史那贺鲁所统部“弩失毕”之“弩”为衍(吴玉贵亦持类似观点)③。其次,岑先生认为沙陀之语原即唐史中常见之“失毕”或“矢毕”:“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之‘sadapyt’相比;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④综合岑先生上述论证中可以看出,岑先生主张“沙陀”从语原上源自“射脾”。
射脾是唐朝初期活动在东部天山地区且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一个部落。阿斯塔纳一七一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关于射脾活动的记载,是目前所知的射脾最早的活动。这是一件记载高昌麴氏王朝与突厥人往来的官方文书。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
[前欠]
1 次羁人赵头六、王欢儿贰人,付宁僧护,用看珂
2 懃苏弩胡鹿大官、公主时健大官
3 付毛海龙,用看毗伽公主寒
(略)
9 纥达官伍日。次小张海柱,付康善财,用看坞耆来射卑
10 妇儿伍日。令狐资弥胡,付王善祐子,用看尸不遝〓
(略)
21 看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次吕隆伯,付(略)
33 伯儿,用看居〓抴使伍日。次赵小儿,付康善财,用看
34 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侍郎麴延陀侍讲辛武护
(略)①
这件文书第9行、21行、34行的“坞耆”为“焉耆”的异译,“射卑”也即“射脾”。②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射脾是游牧于焉耆境内天山之中而且与高昌麴氏王朝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部落。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高昌延寿十四年统治西域的西突厥可汗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同俄设,则此时的射脾当归沙钵罗蛭利失可汗统治。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在位时期西突厥内忧外患交加、危机四伏,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十三年,“咥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③。咥利失之后继位者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与乙毗咄陆瓜分西突厥汗国,游牧于焉耆附近的射脾当归属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统治。
贞观十五年(641年),“咄陆可汗与叶护颇相攻击..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乙毗咄陆可汗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之后,“自恃其强,专擅西域”④,整个西域处于乙毗咄陆可汗统治之下,此时的射脾应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
乙毗咄陆统辖下的射脾早期是否曾归统辖东部天山诸部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由于史料阙如,尚不得而知,但阿史那贺鲁继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东部天山诸部时期,射脾归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当无疑。阿史那贺鲁统治天山东部时期进行过一系列反唐活动,射脾也追随阿史那贺鲁参与了反唐活动。高宗初年唐政府组织弓月道行军征讨阿史那贺鲁之前,首任庭州刺史骆宏义所上唐帝之疏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该疏云:“臣闻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事无常准。今有降胡来言:贺鲁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积雪,汉兵必不远来。诚宜乘其此便,一举可以除剿。若迁延待春,恐事久生变,纵不能结援诸国,必应远迹遁逃。且兵马此行,本诛贺鲁,处密已许款诚,处木昆等各思免祸,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虑更乌合。然严冬风劲,马瘦兵寒,瘃堕之忧,难量进退。又不可久停兵马,虚费边粮。见我不前,成其党附。伏望且宽处月、处密之罪,以诛贺鲁为名,除祸务绝其原,未可先取其枝叶。但此两姓,见其坐夺,不示招携,必自深据。如弃而西过,则近有后忧。先事诛夷,未可即克。舍而勿问,则惑义前驱,事定从宜。除申吊伐,此乃威恩兼举,远慑迩安。向使兵马早来,贺鲁久已悬首。前机虽失,须为别图。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芯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掩袭。大军顿于凭水,秣马畜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且番人行动,须约汉兵,东西犄角,又资翘翼,简胡骑以率其前,率汉兵以蹑其后。贺鲁进退无路,理即可擒,百胜之谋,在斯一举。臣恐建方至日,为计不同,军谋乖舛,后悔无及。”①
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诸部的招慰活动中,射脾部在其首领沙陀那速的领导下归唐,归唐后的射脾部获得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前所领的权力,从而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射脾的族源似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因为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前,“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为铁勒诸部落游牧之地。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这些铁勒部落几乎全部改用“突厥”族名,虽然他们同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关系亲疏不一,但他们“族名相同,语言相近,风俗相似”,是异姓突厥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射脾所处之位置恰与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所处之位置相吻合,故射脾极有可能源自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中之一部。芮传明从语音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铁勒属部之“苏婆”(suo一b’u〓)和射脾(dz’ia—b’jie)从语音来看极为接近,可以被看作为同一名称的异译,因此他断定,射脾源自西域铁勒部落中的苏婆部②。
第二节 “沙陀”名称之演变
“沙陀”名称经历了由部落酋长之姓氏到部落之称号的转变,其间又成功将处月部落涵化并融入沙陀部落中。我们在此对“沙陀”名称之演变略作考证。
“沙陀”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新唐书·沙陀传》云:“永徽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竹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第一,“沙陀”为“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之姓;第二,阿史那贺鲁叛唐,处月酋长朱邪孤注追随贺鲁反唐,而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却弃贺鲁归唐,两者态度截然不同;第三,唐廷对朱邪孤注和沙陀那速赏罚分明,对前者派大军镇压,擒获斩首,对后者不但命其统领贺鲁部众,而且“置金满、沙陀一州,皆领都督”。“沙陀”之名,可能是唐廷为嘉奖沙陀那速的忠诚,以其姓氏为都督府之称。沙陀那速的归唐及沙陀州的设置,使沙陀之名,远扬内地。
因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归唐有功,故“沙陀”之名日益彰显,而“朱邪”之姓日渐淡漠。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唐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①,这是沙陀那速之后第二个载入史册的沙陀酋长,其后陆续有沙陀辅国、沙陀骨咄支等沙陀酋长,沙陀之名代代相传。
对于“朱邪”重新出现,我们认为主要是在吐蕃进逼,北庭难保的情势下,原一直与唐朝对抗的处月部暗通吐蕃,并在吐蕃的扶持下逐渐获得沙陀的统治权所致。
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弃城西逃,退守甘州。永泰元年(765年)十月,“沙陀杀杨志烈”②。从处月部屡次叛唐的历史来看,杀害杨志烈的沙陀人,应该就是处月部人。这也说明,早在吐蕃进攻北庭之前,处月已经背叛了唐朝。
在吐蕃的扶持下,处月势力在沙陀部中迅速膨胀,遂导致沙陀部酋长沙陀尽忠被迫改姓为“朱邪”,名曰“尽忠”。从史料记载来看,沙陀部酋长由“沙陀”姓改为“朱邪”自沙陀尽忠开始。沙陀尽忠之名,见之于《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六③。而更多的史料则将之称为朱邪尽忠。朱邪尽忠可能就是遭受到了处月部的威胁,被迫改姓“朱邪”,并率部投降吐蕃的沙陀部首领。
第三节 沙陀早期的活动区域
射脾、处月归唐之后,两者逐步走上合并之路,新的沙陀族日渐形成。归唐之后,沙陀主要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但是对于其活动的具体区域,相关文献记载甚少。对此,我们通过文献、考古资料及实地考察,对沙陀早期的活动区域进行初步探讨。
一、沙陀在“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一带的活动
“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是沙陀人当年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域,根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其境内“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关于沙陀所居之“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大致位置,学界观点不一:毛凤枝认为,“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就是“吐鲁番之南罗布泊之东之大戈壁矣”①;岑仲勉认为,金娑山及遏索山,也即额林哈毕尔噶山,处月部“在额林哈毕尔噶山之南,自空格斯流域,迄于天山之北”②,即伊犁河流域;丁谦认为“金娑山在巴里坤城东北三百余里,《西图》作尼赤金山。蒲类海即巴尔库里泊,即巴里坤湖。湖之东山之阳,地皆沙漠,处月部居此”③;沙畹认为,《新唐书·沙陀传》之金娑山即新疆北部之博格达山(Bokdoola)④。以上诸说当中以丁谦的观点较为贴近事实,后世学者亦多从此说⑤。通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丁谦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即沙陀的活动地在今巴里坤县和伊吾县之间;对于史书所云其境内之大碛,应是中蒙边境上的“二百四戈壁”。
“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原系处月部游牧之地,后来由于处月部屡次叛唐,为分割处月势力,唐政府遂在平定处月之后将此地封给在唐平定西突厥过程中有功的射脾部。由于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归唐有功,该州便以射脾部首领沙陀那速之姓来命名⑥。沙陀州存在的时间可能不长,《新唐书·沙陀传》云:“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可知,龙朔初(661年),沙陀金山随薛仁贵讨铁勒,沙陀部便离开沙陀州,居瓜州西北千里之墨离军。沙陀金山离开巴里坤草原,沙陀州很可能随即废止,该地成为了伊州管辖范围内的一处重要军事基地。《新唐书·地理志》云,伊吾郡“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军,景龙四年置。”《旧唐书·地理志》云:“伊吾军,开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镇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在北庭东南七百里。”《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吾军,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奉敕置,至开元六年(718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四十匹。”①由上述史料可知,沙陀金山率部离开沙陀州之后,该地成为伊吾军的驻扎之地。伊吾军军城所在之甘露川即位于巴里坤县城东北15.5公里处大河之阳的大河古城。该城东西长420米,南北宽约200米,分主城和附城,中有通道相连接,城外有护城壕。该城历经近一千三百年的风吹雨打,厚约9米,高约6米的城墙已大部裂塌,唯西北一段约30米的城墙仍屹立高耸。我们踏上这座残城之时,仍能感受到该城昔日之规模和雄风。
离开巴里坤草原之后的沙陀首先在沙陀金山率领下北征铁勒,之后又迁转至沙州西北千里之墨离军。长安二年(702年)随着沙陀金山升迁为金满州都督,沙陀部又迁转至庭州境内。沙陀部的这次迁转似乎说明如下问题:一、活动于庭州一带的处月部再度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不安定因素。2003年洛阳出土的李释子墓志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该墓志记载,李释子“久视(700年)初,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根据该墓志记载,在沙陀金山升迁金满州都督的前两年,李释子开始任盐、甘、肃州刺史兼处月大使,这似乎说明处月部又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障碍;二、仅距李释子任处月大使两年沙陀金山便任金满州都督,其目的可能就是安抚处月。三、沙陀金山任金满州都督,沙陀、处月二部同处一地,可能加速了沙陀、处月合并的步伐。
当然,沙陀与处月合并非一帆风顺,其间部分处月部族可能不满沙陀金山的统治,离开了其长期活动的庭州地区,迁转他乡。根据吐鲁番文书记载,其中就有部分处月人迁移到了西州地区(详见下文)。两部合并之后的沙陀部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仅仅事隔三十余年,由于“刘涣凶逆处置狂疏”,沙陀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后又迁转至伊州,短暂居留。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记载了此事:“敕伊州刺史、伊吾军使张楚宾: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蹔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与盖嘉运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计必思归,从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处置了日,具以状闻。夏中盛热,卿及将士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①
沙陀乃游牧部落,且人数不少,安置这样一个游牧部落,在伊州地区只有巴里坤草原,同时巴里坤草原又是伊吾军驻扎之地,沙陀迁移至此,既占水草丰美之利,又便于唐军监控。故沙陀在“刘涣凶逆处置狂疏”之后可能又曾短暂活动于巴里坤草原。
沙陀除了活动于巴里坤草原之外,还曾活动于哈密东北部地区。该地曾属沙州府管辖范围,沙州府墨离军军城曾短暂存在于此地区。龙朔年间,沙陀首领沙陀金山曾在此任墨离军讨击使。关于墨离军早期军城的位置,《新唐书·地理志四》“瓜州晋昌郡”条记载:“有府一,曰大黄,西北千里有墨离军”;《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凉州”条记墨离军云:“瓜州西北一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东去理所一千四百余里”;《通典》卷一百二十七“墨离军”条与《元和郡县图志》同。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早期墨离军军城位于瓜州西北千里之处。关于墨离军的确切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吾县”条记伊州八到云:“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九百里。”瓜州距离伊吾不过900余里,则墨离军当在哈密天山以北的大川。林梅村将墨离军军城位置定在今伊吾县城东48公里处的下马崖古城,为此我们曾亲身前往下马崖进行过实地考察。下马崖古城位于下马崖乡水库南侧,东北距离乡政府3公里。古城基本呈正方形,边长100余米,城墙之上设有射口,而且城中偶尔发现清代钱币,故学界一般将其定为清代建筑。将该城断为清代当属不误,但说此城清代建成,恐有疑问。我们认为,此城应是唐朝时期一边镇,后被沿用直到清代。下马崖所处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它地处天山东部尾端,地势平坦,是连接蒙古草原、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的要冲。在此设置军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认为,该处可能就是唐初①唐朝经营西域时设置的墨离军之所在。但是据我们考察,该处非如文献所记载之“气候温暖,冬夏季均饮用及灌溉农田,为利非鲜”②。该城所处之下马崖乡总人口仅700余人,四周均是一片茫茫戈壁,基本不适合大队人马长期居住。故我们认为,墨离军初设于此,实属军事战略之权宜之计。
龙朔初(661年)沙陀金山随武卫将军薛仁贵讨伐铁勒,龙朔二年铁勒被平定,事后沙陀金山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此时的沙陀金山部可能就驻扎在今下马崖古城一带。但是,沙陀金山任墨离军讨击使一职为时不久,长安二年(702年)便升为金满州都督,从此沙陀离开了下马崖。沙陀部在其酋长沙陀金山的率领下,在下马崖共生活了近40年。
墨离军军城驻扎下马崖的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后来随着沙陀金山升迁为金满州都督而废止,之后墨离军撤回沙州城。其间墨离军军城之位置经历了由沙州西北“十里”到“千里”的变迁③。
墨离军撤离下马崖之后,其军城可能又被伊吾军短暂启用,证据如下:《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吾军,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奉敕置,至开元六年(718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四十匹。”则,最初伊吾军之军城不在今巴里坤大河古城。《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又载:“庭州瀚海军、西州天山军交河县,伊州伊吾军柔远县。”则,伊吾军设置初期,其军城在昔日柔远县境内。而下马崖亦属昔日柔远县之管辖范围,且其附近有烽火台。因此,墨离军撤离下马崖之后,唐朝于景龙四年所设之伊吾军军城地址就在今下马崖,初设至此,亦属权宜之计,后伊吾军迁转至水草丰美的巴里坤大草原,于今大河古城重建军城。
二、沙陀在北庭附近的活动
庭州地区是处月沙陀部的活动中心,《西州图经》(残卷)在叙述白水涧道时有如下记载:“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马车。”①该史料显示,处月的活动中心应在交河县以北的庭州地区,即今吉木萨尔、奇台一带。
处月部活动范围以庭州为中心,最东达巴里坤、伊吾一带,最西可达乌鲁木齐。《新唐书·西突厥传》在叙述阿史那贺鲁叛乱,庭州刺史骆宏义献策时云:“愿发射脾、处月、处密、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住凭洛水上为之助景,此驱戎狄攻豺狼也。”这说明处月的活动范围最远不过凭洛水。关于凭洛水,学界观点不一,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凭洛镇在府(庭州)西三百七十里”之记载。该凭洛镇定是凭洛水沿岸一重镇,因以为名。根据里程,此凭洛水应在今乌鲁木齐附近②,则处月活动范围西限也应在今乌鲁木齐附近。
处月归唐之后,唐朝在处月活动地区设羁縻金满州以安置之。金满州治所之位置,应在庭州州治附近境内。首先,庭州治所与其下属金满县治所同治一城,均在今吉木萨尔破城子。清朝中叶徐松勘察北庭之后,于《西域水道记》云:“济木萨唐为金满县,北庭都护府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即今吉木萨尔县城西北角之古城遗址)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庭州与金满县同治一城无疑矣。其次,羁縻金满州既冠以“金满”,其活动范围当在金满县境内。故,金满州治所距庭州治所破城子不远。还有的学者认为金满州治所与庭州治所均在同一城,我们认为不妥。首先,作为汉人居住的郡县与安置少数民族之羁縻州、府截然不同。毛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卷三云:“金满州与金满县本系两地,金满县中国郡县之地,由中朝命官而往,即今之流官;金满州为外蕃羁縻之地,其酋长世袭都督,如今之土司是也。”③作为外蕃羁縻之地的金满州,其治所亦不可能与作为汉人郡县的金满县之治所放在一起。但既名为“金满州”,其治所应在金满县境内;又,《新唐书,沙陀传》载:“先天初(712年)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714年),复领金满州都督。”这段记载显示,金满州治所距庭州尚有一段距离,否则沙陀金山就不会“徙部北庭”。
处月在庭州地区除从事游牧生活外,还从事定居生活,因为根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郭孝恪平定乙毗咄陆之乱时曾“拔处月俟斤之城”。此处的“处月俟斤之城”就是处月部活动中心之所在。我们认为“处月俟斤之城”应该就是后来唐朝所设羁縻金满州之治所。关于“处月俟斤之城”之位置,据薛宗正认为,很可能是庭州东之蒲类县,今奇台唐朝墩古城废墟①。我们认为不妥,唐朝墩古城乃唐朝蒲类县治所之所在,早在贞观十四年就与庭州同时设立②。作为中国郡县治所,断然不能与外蕃羁縻之金满州同在一处。
三、沙陀在西州的活动
沙陀除在今哈密、昌吉地区活动之外,还曾在吐鲁番地区留下过活动的足迹。
活动于吐鲁番的是处月部中的一个分支,上引吐鲁番出土文书《开元十六年朱邪部落请纸牒》(大谷5840)记录的就是当时处月一个分支在西州的一些活动情况。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邪波德的签名,时间是开元十六年(728年)。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开元十六年之时,处月部已有分支活动于西州境内。对于这支部落迁移到西州的原因,李方先生认为是“先天初(712年)避吐蕃,徙部北庭”中未到庭州而是分道扬镳来到西州的③。我们认为不妥,这支处月部落迁移到西州的时间应是702年沙陀金山任金满州都督前后。其时,处月发动了新的叛乱,唐朝政府除任命李释子兼任处月大使力图安抚之外,又命沙陀金山任金满州都督直接统辖处月部。这期间部分处月部可能不满沙陀金山的统治,因此迁移到了与庭州毗邻的西州。
第四节 沙陀与周边民族之关系
沙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周边许多民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其中与沙陀交往较多的有四个民族:西突厥、回纥、吐蕃、葛逻禄。本文试图对沙陀与这四个民族的关系做一个系统、全面的论述。
一、沙陀与西突厥之关系
在沙陀与周边诸民族关系中,沙陀与西突厥接触最早且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突厥初期,沙陀就与西突厥发生了关系。《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载:“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异。”《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亦云:“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密杂居。”关于沙陀与西突厥的关系,史书多称其为“西突厥别部”①,有些史书因此径直称其为“沙陀突厥”②,沙陀应是被西突厥征服之后处于西突厥统治之下的一个部落。沙陀作为西突厥的一个属部,其归唐前主要活动都是在西突厥最高统治者指挥下进行的,其政治立场与西突厥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沙陀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之时正是西突厥由盛转衰内乱、分裂不断,最高统治者频繁更换之时,作为西突厥属部,沙陀在短暂的几十年内先后依附于西突厥统治阶层的不同派系。
咥利失统治时期(?—638年):处月活动最早见诸史书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是年十月乙亥“处月遣使入贡”①。其时统治西突厥的是受唐朝册封的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作为西突厥的属部,此时的处月当属咥利失统辖,但是此时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处月作为西突厥属部,断无单独遣使朝贡之权,其敢于单独遣使朝贡说明处月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独立性,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这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一直维系到贞观十一年(637年)咥利失与欲谷设之间的伊犁河大战,此时,处月与弩失毕、处密等部尚归咥利失管辖②。
乙毗咄陆统治时期(638—?年):伊犁河大战之后的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处月部又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证据如下:贞观十二年,乙毗咄陆曾征发处月、处密部兵马,联合高昌国,攻打咥利失势力范围内的焉耆国。《旧唐书·焉耆传》云:“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咥利立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与焉耆为援。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③而根据薛延陀呈唐太宗的一份报告可知,联合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的处月、处密部的幕后指挥就是欲谷设,即乙毗咄陆可汗。《册府元龟》云:“太宗贞观十三年,薛延陀遣使上言:‘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厚,尝(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前导,驱以讨之’。”④
乙毗咄陆统治下的天山东部处月、处密等部落和平局面维系不久便发生了内讧,其原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其兄阿史那步真驱逐,“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阿史那步真自立为咄陆叶护⑤。由此,处月部一分为二,小部随阿史那弥射入唐,而大部仍留原地。未几,阿史那步真因部众不服,又因唐交河道行军进逼,也投降唐朝。
阿史那步真入唐之后,统治处月等部落的是阿史那贺鲁。《册府元龟》记载:“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①
贞观十五年乙毗咄陆攻杀唐朝政府册立的泥孰系沙钵罗叶护可汗②,复击败吐火罗,东进寇略唐朝在西域的范围,此时的西突厥基本已统于乙毗咄陆,其势力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乙毗咄陆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发处月、处密部连寇伊州和西州之天山县。《新唐书·突厥》下云:“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两千,自乌骨狙击,败之。咄陆以处月、处密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密]部而归。”此事之后,乙毗咄陆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西突厥弩失毕部的请求下,唐朝政府“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③
乙毗咄陆失败之后,乙毗射匮势力迅速向处月、处密等部所处的天山东部地区发展,企图填补乙毗咄陆失利后该地区形成的政治空白。而此时统治天山东部诸部的阿史那贺鲁在乙毗咄陆败亡之后面临着日益窘迫的局面。《通典》载:“咄陆西走吐火罗国,射匮可汗遣兵迫逐,贺鲁不常厥居。”④
乙毗射匮统治及其间短暂归唐时期(?—648年):在乙毗射“遣兵迫逐”阿史那贺鲁的情况下,原来隶属于阿史那贺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在乙毗射匮的挟制下归附乙毗射匮,同时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阿史那忠碑》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其云:“既而句丽、百济,互相侵逼;处月、焉耆,各为唇齿,肆回邪于荒裔,轸吊伐于皇情,天□□□□□□□□躅□□□□□乃□绥边□□诏公□〔西〕域安抚,载叶□如之寄,右地聋□,加授上柱国。”①从《阿史那忠碑》我们可以看出,在贞观十九年之前处月、处密已经和焉耆一起“肆回邪于荒裔”,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针对西域出现的新叛乱,唐朝政府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对于乙毗射匮与唐王朝之间对处月等部落的争夺,相关史传没有记载,但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政府发布的《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却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
《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云:“西域之地,经途遐阻,自遭乱离,亟历岁月,君长失抚驭之方,酋帅乘叶赞之义,虐用种落,肆行残忍,遂使部众离心,战争不息,远近涂炭,长幼怨嗟,大监小王,无所控告,顿颡蹶角,思见含养。朕受命三灵,君监六合,御朽之志,无忘寝兴;纳隍之怀,宁隔夷夏;乃眷西顾,良深矜惕;宜命輶轩,星言拯救。可令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蜜〔密]部落,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问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②《阿史那忠墓志》云:“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泑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侍辇幽燕,言过汾晋。于时延陀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驿赴救,事宁而反。”③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阿史那忠的西域“抚慰”之行达到预期目的,“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处月等部落名义上又重新归附唐朝。但这并非出自真心,事后很快又归附乙毗射匮。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军讨伐龟兹。这次讨伐处月也是打击对象,这从昆丘道行军之前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资治通鉴》载:“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①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处月、处密等部此时已经归附乙毗射匮,唐朝政府组织的这次针对乙毗射匮的昆丘道行军其讨伐对象亦包括处月、处密部。唐太宗行军前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首先就将处月、处密击败②。
阿史那贺鲁统治时期(648—657年):就在唐朝政府组织昆丘道行军征讨乙毗射匮之时,遭乙毗射匮追逐,四处漂泊无所寄托的阿史那贺鲁投降了唐朝政府。阿史那贺鲁此举得到了唐朝政府的礼遇,《新唐书·突厥传》载:“贺鲁无常居,部多散亡。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③处月原为阿史那贺鲁旧部,昆丘道行军中处月遭受唐军重创,加之阿史那贺鲁降唐受到唐朝政府礼遇。于是不久,处月在其阙俟斤朱邪阿厥带领下“亦请内属”④。自此,处月重新成了阿史那贺鲁的麾下。
阿史那贺鲁降唐之举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阿史那贺鲁随昆丘道行军征讨两个月之后,唐朝政府便在天山东部地区设立瑶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⑤,很快唐朝政府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晋封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大将军。但是阿史那贺鲁骨子里是反唐的,他降归唐朝其目的是借助唐朝势力发展壮大自己。在唐政府的扶持下,“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⑥,阿史那贺鲁很快统一了西突厥诸部。阿史那贺鲁的羽翼刚刚丰满,便暴露出其反唐的本质,他“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⑦于永徽元年⑧反唐,并于次年自封沙钵而《新唐书》及《唐会要》则记作“永徽二年”(《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53页;《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第1322页)。罗可汗,建牙双河及千泉,拥兵十万,西突厥诸部皆归属之。起兵之后,阿史那贺鲁首先入侵庭州,攻破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对唐政府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是年七月丁未,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发秦、成、歧、雍汉兵三万、回纥兵五万,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一次征讨。征讨之前,庭州刺史骆宏义上言,主张征讨之前应招降处月、处密等部落,以减少行军的阻力,同时与之合兵共讨阿史那贺鲁。骆宏义云:“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沿袭,大军顿于凭(洛)水,秣马蓄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①高宗最初采纳了此建议,派出各路使者招慰西突厥各部。但事与愿违,是年十二月壬子,处月酋长朱邪孤注首先杀害唐朝政府招慰使单道惠,与阿史那贺鲁联兵抗唐。只有作为沙陀族源的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拒绝随阿史那贺鲁叛唐,应招降唐。唐朝政府的招慰计划宣告失败。永徽三年唐朝大军开始西进征讨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闻讯西遁,而处月部朱邪孤注则居牢山自守,企图借地势之险要以拒唐军西进。“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是年癸亥,唐军数路并进,一举攻克牢山,斩处月酋长朱邪孤注,俘获处月、处密等部渠帅六十余人,斩首五千余级,俘生口万余计以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西域诸部纷纷随②。处月依附阿史那贺鲁叛唐,阿史那贺鲁叛唐之时,“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事后唐高宗以阿史那贺鲁以前所任瑶池都督一职授予沙陀那速③。
对于这次行军的原因,有的史料将之归结为处月等部的反叛④,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此次行军的主要目的就是讨伐阿史那贺鲁,而平定处月、处密叛乱只能看作是本次行军的最终收获①。
弓月道行军之后,唐朝于永徽四年(653年)正式撤销瑶池都督府,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②,至此处月部落中的朱邪部以羁縻州府的形式正式纳入唐朝政府的统治。
弓月道行军并没有和阿史那贺鲁正面交锋,所征服的仅仅是阿史那贺鲁前锋——处月、处密部之主力,此外仍有预支部依附阿史那贺鲁顽强对抗唐朝,所以弓月道行军基本是以失败告终。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此次征讨唐军深入西突厥腹地,与阿史那贺鲁属部交锋,取得辉煌战果。“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③。至此处月预”支部基本为唐军所征服。
显庆二年(657年)唐朝政府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三次征讨。此次征讨处月部未降者再次遭到重创。“(阿史那)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帅众来降”④。最终唐军大破阿史那贺鲁,西突厥被彻底平定,沙陀余部亦归唐,沙陀与西突厥的从属关系宣告彻底结束,沙陀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沙陀与回纥之关系
回纥是继突厥之后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汉朝时期的丁零,北魏时期为铁勒(别号高车)六部之一的袁纥部。沙陀与回纥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最早的接触是在唐军征讨西突厥过程中,当时双方以敌对关系出现;其后在吐蕃攻占西域过程中又与回纥结成友军共同抵抗吐蕃的进攻;沙陀内迁后,沙陀作为唐朝守边者与侵扰唐朝的回纥再次交锋,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了敌对关系。
沙陀与回纥最早的接触是在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西域战场上。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帅铁勒各部联合唐军一举灭亡薛延陀,后在回纥的请求下,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春正月在薛延陀、回纥、铁勒及其他各部地区设立六府七州,“北荒悉平”①。漠北的平定不但消除了唐朝北部边患,而且为唐朝提供了充沛的兵员。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的征讨过程中回纥数次参与,为唐朝平定西突厥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行军大总管发动了昆丘道行军讨伐龟兹。以回纥为首的“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②首次参加了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战争,而且是行军的主力。在这次行军中回纥等部骑兵在阿史那社尔率领下,相继攻占焉耆、龟兹,接着打败西突厥援军,向西攻占拔换城。这次战役震惊整个西域,塔里木南缘的于阗、疏勒及葱岭以西之安国“皆相率请降,凡得七百余城,掳男女数万口”③。至第二年十月,唐军完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西突厥失去了在天山南路的立足之地。唐于是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并建立安西四镇。此次昆丘道行军除征讨龟兹之外,处月也是该次行军的重要征讨对象。前引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云:“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唐太宗之预言不差丝毫,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④,昆丘道行军首战即以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沙陀与回纥的首次接触,其结局是回纥铁骑作为昆丘道行军的主力成功将沙陀击破。
唐军的西征引起乙毗射匮反对派阿史那贺鲁的强烈响应,他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己亥降唐,并获得厚赐。其后,阿史那贺鲁在唐朝政府的扶持下很快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及西域诸国。随着羽翼丰满,其反唐之心开始暴露,“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叛”,先是攻破唐控制的金岭城及蒲类县,继而攻陷北庭。唐政府以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兵五万击之”①,而且回纥这次出兵由吐迷度之子婆闰亲自率领,并兼任行军副总管②,足见回纥部众在此次行军中的主导作用。此次征讨,大破贺鲁收复北庭,并击破处月朱邪部落,斩其酋长朱邪孤注。这是沙陀与回纥的第二次交锋,同样以沙陀的失败而告终。
永徽六年,唐高宗以开国元老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显庆元年(656年)葱山道行军正式从长安出发西征。紧随其后,唐朝政府于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庚戌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阿史那贺鲁战役。关于这两次征讨,《旧唐书·回纥传》将之并到一起叙述:“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之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③由此可知,回纥军队在其首领婆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两次征讨。
弓月道行军之后尚有沙陀预支部仍随阿史那贺鲁负隅抵抗,葱山道行军唐军与处月预支部兵戎相见。史载:“(显庆元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罗、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④由此可以推知,沙陀与回纥在葱山道行军中再次兵戎相见,并且又是以回纥的取胜告终。
阿史那贺鲁叛乱被平定之后沙陀归唐,在唐朝政府统治之下沙陀与回纥再度接触。在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回纥立下汗马功劳,平叛后首领婆闰被授予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府都督。婆闰上任之后不久便染病去世,其侄比粟毒继位。比粟毒继位后并不甘心服从于唐朝,遂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勾结同罗、仆骨进犯唐朝边境。高宗令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共同率军讨伐①。沙陀部首领沙陀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一同征讨,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又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这是沙陀归唐后和回纥的首次接触,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是此次交锋是以沙陀的胜利告终。
天宝初年,骨力裴罗在位时,回纥汗国兴起于漠北,其势力西抵金山③。首领骨力裴罗也因内附先后被唐玄宗封为奉义王、怀仁可汗④。此时沙陀居住地毗邻回纥汗国的势力范围,同为大唐臣民,双方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政府还册封沙陀首领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⑤。
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沙陀在其首领骨咄支率领下随回纥助唐平叛。沙陀虽随回纥参加平叛,但双方在平叛战场上并不存在依附关系。据史载:“(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邪、契、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⑥据此可知,沙陀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与回纥之间亦不存在依附关系。由于沙陀在平叛中的优秀表现,唐封其首领骨咄支为特进、骁卫上将军⑦。
唐朝政府遭遇安史之乱之时,安西、北庭边兵大量内调,吐蕃乘机扩张势力,它在占据河陇地区后,乘势向天山南北扩张。此时的安西四镇及北庭还掌握在唐军手里,但因吐蕃占领河陇地区而割断了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为了与内地取得联系,安西、北庭都护府使臣辗转数十年,最终借道回纥,“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①。由此,不但北庭、安西守军“附庸”之,“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②。此时沙陀与回纥之间已由安史之乱及其以前的彼此友好、协同作战的关系转变为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是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维系未几便破裂,主要原因是回纥对沙陀等部的苛刻统治。史称“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而沙陀对回纥的肆行抄夺,尤所厌苦”③。
回纥对所统诸族的苛刻统治,引起北庭部众强烈不满。吐蕃趁机以厚赂引诱各部,促使北庭诸部叛回纥附吐蕃。在吐蕃“厚赂见诱”下,葛(逻)禄、白服突厥先后归附吐蕃,稍后吐蕃与葛逻禄、白服突厥一起急攻北庭,遭受回纥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至此,由于回纥的“贪狠、征求无度”最终导致沙陀摆脱回纥统治,双方附属关系宣告结束。
归附吐蕃之后的沙陀不但在战争中常被驱为前锋,而且被吐蕃无端猜疑为私通回纥,面临被迁至河外的危险境地。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举众归唐,掀开其历史发展中崭新的一页。
三、沙陀与吐蕃之关系
吐蕃是历史上由藏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其族源可追溯至西羌的一支发羌。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也是发生在唐朝征讨西突厥的战场上。双方之间关系也是经历了“敌—友—敌”的转变。
沙陀与吐蕃的首次接触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昆丘道行军中。此次行军之前唐朝曾对吐蕃发起过洮河道行军,但双方很快结束战争化敌为友,此后唐又应吐蕃请求于贞观十五年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与吐蕃间结成了甥舅关系①。在此背景下,吐蕃作为唐朝友军与铁勒十三州、(东)突厥、吐谷浑等一道参加了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征讨西突厥的昆丘道行军②。如前所述,此次行军首战便以大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史料记载的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疲于应付叛乱,吐蕃乘机屡次入侵唐朝。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③;“乾元以后,吐蕃乘机间隙,日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④。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地区基本为吐蕃所占领。
吐蕃进攻河陇地区时,沙陀可能在唐朝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从当时唐朝政府授予沙陀首领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骨咄支)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⑤唐朝政府遥授朱邪尽忠“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说明沙陀在河西地区与吐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继续进攻北庭,此时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守军相依,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御。五代人赵凤所撰《后唐懿祖纪年录》对此有详细记载:“德宗贞元五年,回纥葛禄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纥忠贞可汗,附于吐蕃,因为向导,驱吐蕃之众三十万寇我北庭。烈考(朱邪尽忠)谓忠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灵、盐,闻唐天子欲与赞普和亲,可汗数世有功,尚主,恩若娇儿,若赞普有恩于唐,则可汗必无前日之宠矣。’忠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将杨袭古固守北庭,无路归朝,今吐蕃、突厥并兵攻之,倘无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没,次及于吾,可汗得无虑乎!’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⑥但是回纥与沙陀的救援并没有改变北庭陷落的命运,加上回纥对其“贪狠、征求无度”,最终沙陀随北庭守军一道于贞元六年(790年)投降了吐蕃。至此,沙陀与吐蕃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了从属关系。
沙陀降蕃后其首领朱邪尽忠被授予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被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由于沙陀人骁勇善战,勇冠诸胡,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①,故沙陀部落死伤甚多,加上吐蕃对其横征暴敛,沙陀对吐蕃的统治无法忍受。后来,“回鹘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即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地域,当时为偏僻荒凉之地),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行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俞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欲迁②。回纥取凉州被吐蕃怀疑为沙陀勾结回纥所为③其于河外,导致沙陀举族愁怨,最终东归唐朝。沙陀与吐蕃仅二十年的从属关系宣告结束。
元和三年沙陀脱离吐蕃统治,开始了东归唐朝、投靠灵州节度使范希朝的历程。沙陀的东归激起了吐蕃的愤怒,吐蕃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此时沙陀与吐蕃已由原来的从属关系重新转变为敌对关系。
对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记载:“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傍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落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裒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④沙陀自甘州出发之际,共有部众“三万余落”,东归途中遭吐蕃追杀,到达盐州时仅剩近三千人,且已饥寒交迫,劳疲不堪。
四、沙陀与葛逻禄之关系
葛逻禄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活动中心“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①,相当于今新疆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它与处月一样,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属西突厥之别部。由于葛逻禄地处东、西突厥之间,因此常视双方力量之消长而叛附不定②。
沙陀与葛逻禄之间的关系发生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左右。其时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归唐,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命叶护阿史那贺鲁统治东部天山地区。史称:“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③沙陀与葛逻禄开始发生关系。
唐朝平定西突厥之前,沙陀与葛逻禄一道在阿史那贺鲁指挥之下对抗唐朝。永徽元年(650年),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④反唐。之后,唐朝政府组织了数次行军,征讨西突厥。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⑤。葛逻禄与处月在同唐军对抗中遭受重创。
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之后,唐朝于显庆三年(658年)设立羁縻州府以处置葛逻禄部众:以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至阿拉湖一带;以炽俟部置大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青河以南、乌伦古河下游地区;以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以北、斋桑泊以南地区。沙陀之处月、射脾部亦设金满州、沙陀州以妥善安置。归唐后的沙陀与葛逻禄之间再度发生关系。
近年出土的《唐龙朔二、三年(662—663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及《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①两份文书记载了两者之间发生的一件事:龙朔元年,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被贼人打散,有一千帐从金山(阿尔泰山)南下,在金满州地域停住,金满州都督沙陀某某将这一信息上报朝廷。朝廷分别给燕然都护府、哥(葛)逻禄部下敕令,命燕然都护府与西州都督府相知会,将停住金满州的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遣返大漠都督府原住地。龙朔二年,燕然都护府获取哥(葛)逻禄首领咄俟斤乌骑支陈状,云该部在龙朔元年敕令下达之前已经在金满州有水之处种下麦田,而且该部所放养的牲畜因遭受暴风雪,缺乏充足的草料,无法长途跋涉回归原住地,希望迁往甘州。之后龙朔三年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又相知会,力促哥(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留住金满州的葛逻禄仅五十帐,其他帐已经入京,故未能立马返回原住地。
通过这两份出土文献可以看出,葛逻禄归唐之后,曾流落至金满州境内,并从事农业生产,其间肯定得到了沙陀的照顾。尽管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数次规劝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葛逻禄留恋金满州之地,迟迟不归。该文书没有显示该事的最终结果,但从葛逻禄的态度上看,估计有部分葛逻禄人留在了金满州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最终融入沙陀部落当中。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减弱,沙陀同葛逻禄、白服(一作白眼)突厥一道处于回鹘的统治之下。然而“回鹘数侵掠之”,贞元五年(789年),葛逻禄部“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接着,吐蕃率葛逻禄、白服之众进略北庭,回鹘数战皆败。最终,遭受回鹘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此后,沙陀被吐蕃迁往河西地区,而葛逻禄主要活动于中亚一带,沙陀与葛逻禄的交往由此中断。
第一节 沙陀之源出
一、学界观点综述
关于沙陀的源出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沙陀源自回纥部。五代孙光宪持此说。他于《北梦琐言》云:“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陁碛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①回纥和沙陀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之间经历了唐朝平阿史那贺鲁时的敌对关系,到安史之乱及吐蕃取西域时的同盟关系,再到沙陀内迁后的重新敌对的关系,但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能说明沙陀源自回纥。对此,樊文礼通过详细分析对沙陀族源回纥说进行了驳斥,这里无需赘言①。
第二,沙陀乃月氏别种。清代和宁(和瑛)持此说。其《三州辑略》云:“沙陀金山,月氏别种西突厥之苗裔,本号朱邪,世居金沙山之阳,蒲昌海之北。”②然作者并未对其立论依据进行阐述。
第三,沙陀源自铁勒之同罗、仆固部。陶懋炳、韩国磐持此说③。其主要依据是《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所记。《唐书·武皇纪》云:“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④这种观点早在宋代时就已经遭到欧阳修的质疑,其于《新五代史·庄宗纪上》云:“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夷狄无姓氏,硃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硃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⑤这种观点的错误可从两方面说明:一、从从属关系上讲,沙陀属西突厥统治,而同罗、仆固则属东突厥强部;二、从地理位置而言,沙陀位于东部天山,而同罗、仆固位于漠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沙陀源自粟特。钱伯泉、李树辉即持此说。钱伯泉认为:“沙陀突厥应是投归突厥,自成部落,由经商而改营游牧的粟特人部落”⑥;李树辉据《新唐书·沙陀传》认为,“处月也便是沙陀。沙陀即粟特”⑦。两位先生主要根据语音对转及其沙陀人的体貌特征作此论断,尚无可靠史料佐证。
第五,沙陀源自突厥乌古斯。苏联学者巴托尔德持此观点。他于《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云:“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有一部分迁到中国东突厥斯以后,中国人称为沙陀(Sǎ-to),即草原居民之意,这一批突厥人早在九世纪初期就据有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破城子),其后由于西方自己同族人的压迫,只得继续向东进入中国领土内,参加了在九世纪后期在中国爆发的内乱。”①此种观点,不知作者何据。
第六,沙陀族源多源。张西曼、朱绍侯持沙陀族源双元论:张西曼认为“沙陀—萨尔特(缠回)就是回纥和大月氏的混合种..沙陀的母系主要为大月氏..父系主要为回纥”②;朱绍侯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是由大月氏土著和回纥人混合形成的”③。持族源多元论者比较多,概其要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徐庭云于《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认为,史籍中记载的“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这无疑是正确的”,除此外,“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三个主要的民族成分,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④;蔡家艺认为,“沙陀”一称,“主要是指以处月部为主,包括处密、射脾二部在内的游牧群体”⑤;郭平梁认为,沙陀渊源于处月、处密、射脾部⑥;宋肃瀛认为,沙陀是以射脾部为主,与留居高昌北山的各个部落结合而成的⑦。
第七,沙陀源自处月。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说者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中的一段史料:“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①,其后的胡三省在《通鉴考异》也持此说②,后世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王仲荦云:“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因此人称之沙陀突厥”“西突厥强盛时,处月③;林幹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处月部,与西突厥别部杂处,分据伊丽河流域,后西突厥衰乱,处月徙居蒲类海之东,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④;林惠祥云:“沙陀突厥原为西突厥之处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实即处月异译也”⑤;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⑥;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属于西突厥”,“为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处月’、‘朱邪’为同音异译,皆为突厥语‘沙碛’之意”⑦;刘义棠云:“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后并以朱邪为姓..朱邪、处月乃为突厥语沙碛之义,而沙陀却为汉语之称”⑧;周伟洲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其源于西突厥处月部。”⑨樊文礼则将沙陀族源细化到处月的分支——朱邪部,其大作《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云:“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⑩
在沙陀族源诸说之中,持沙陀源自处月说占主流。我们认为,在沙陀早期历史中,沙陀与处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下面我们将利用相关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的相关成果进行阐述。
二、早期沙陀与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
关于沙陀与处月的关系,学者多囿于《新唐书·沙陀传》的相关记载,认为两者为一。元代耶律铸则在此基础上有更深入的论述,其《涿邪山诗》云:“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为川阙。”①古人的这些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黄文弼即云,“处月”部姓“朱邪(或称朱耶)”,“朱邪”、“处月”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意为“沙碛”②;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亦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③;蔡家艺也认为上述说法“大体可信”④。显然,他们普遍认为“沙陀”、“处月”、“朱邪”虽称呼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
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先生就在其大作《隋唐史》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一,“哥舒翰所领诸蕃兵,朱邪与沙陀分为两部(见廿七节)⑤;二,“只看《新·传》太宗时有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新·纪》永徽二年有处月朱邪孤注,同时复有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处月、朱邪往往连称,朱邪不能概处月,盛昱阙特勤碑已举其证”⑥。岑先生通过分析,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一、处月、朱邪非一声之音转;二、早期沙陀、处月是二非一。岑先生所论甚确。然岑先生的论证并未引起学界太多注意。
下面我们将在岑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早期沙陀、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的观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处月与朱邪之间的关系。《新唐书·沙陀传》载:“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旧唐书·高宗传》载:“显庆元年八月..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哥逻禄获刺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从上述引文来看,朱邪阙俟斤、预支俟斤分别代表处月的两支部落。则,朱邪乃处月下属部落之一无疑。
关于沙陀部落早期活动的记载甚少,唯有《新唐书·沙陀传》中有一详细记载:“永徽(650—655年)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在这段话中,处月属部之一的朱邪与沙陀两个部落同时并称,而且这两部落在“贺鲁反”这一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一方站在唐朝一边,唐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而另一方则以逆唐而遭首领被斩、九千人被俘的悲惨结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沙陀、处月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退一步说,两者顶多是同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个部落。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我们从一些出土墓志、碑铭、文书中也发现了相关佐证。2004年春,洛阳邙山出土了唐代名将李释子墓志。志石青石质,广73厘米、宽73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书32行,行满32字,志文由中散大夫褚秀撰。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久视初(700年),(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①在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之时,沙陀部的首领沙陀金山正在墨离军讨击使任上,直到长安二年(702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沙陀金山所任墨离军讨击使在当时归属瓜州府管辖,则沙陀金山所统之沙陀部当不在李释子所任之“处月大使”管辖范围内,从地理范畴来讲沙陀与处月应不是同一部落。
又,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从中国掠走的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文书,即:《开元十六年(728年)朱邪部落请纸文书》(大谷5840)。兹移录全文如下:
〔第一纸〕朱邪部落请纸文书
(前欠)
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典渠思 忠牒
2 首领阙俟斤朱邪波德〓
3 付 司 楚 珪 示
4 十九日
5 八月十九日录事 礼 受
6 录事参军 沙安 付
7 检 案 沙 白
8 十九日
...................
〔第二纸〕
9 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10 八月 日 史 李 艺 牒
11 朱 邪 部 落 所 请 次 案 共
12 壹 伯张 状来。检 到 不
13 虚。 记 谘。沙安白。
14 十九日。
15 依 判 谘 希 望 示
16 十九日
17 依 判 谘 球 之 示
18 十九日
19 依 判 楚 珪 示
20 十九日
...................
〔第三纸〕
2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22 史 李 艺
23 录事参军 沙安
24 史。25 八月十九日受。即日行判。
26 录 事 礼 检 无 稽 失。
27 录事参军 自判
28 案为朱邪部落检领纸到事。
(后略)①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邪波德的签署,时间是开元十六年(728年)。作为未经统治者人为篡改的原始档案,吐鲁番文书的可靠性应是高于其他文献的。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至迟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朱邪”仍然以一个部落的名义出现。相同的证据还见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阙特勤碑》汉文部分是唐玄宗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碑文有如下内容:“君讳阙特勤碑(685—731年)...故能承顺友爱,辅成规略,北燮玄雷之境,西邻处月之郊..以亲我有唐也。”②该碑文说明,阙特勤在位之时处月部落尚存。而据《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距开元十六年不久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有沙陀部落居于伊州。其原文如下:“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③在相近的时间内,出现两个身处不同地区、名称截然不同的部落:朱邪和沙陀,则处月和沙陀在730年左右仍是两个不同的部落。
三、沙陀的源出射脾及射脾简史
关于民族的源出,学界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不同观点。持“一元论”者从民族成分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先后顺序出发,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部族成分看成是该民族的唯一族源。在他们看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像一条大河蜿蜒变化,虽然在其奔流过程中不断有“支流”加入,然而其源头只有一个。持“多元论”者大都受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论”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不一定是由某一个氏族或部族一成不变地世代相袭至今,而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部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从而形成多元统一体。
我们认为,对于许多缺乏文字记载的弱小民族而言,是无法确定该民族的哪一个部族成分最早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因此也无法断定其最早的族源成分,沙陀应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比较认同其源出“多元论”。我们认为,沙陀的源出应以处月和射脾为主,并整合处密等其他部落。
对于处月和射脾的合并,我们认为应作如下解释:首先,射脾本与处月无干,只是在两者归唐之后,文献常将两者混为一谈,称部落名为“沙陀”,族姓则为“朱邪”。其原因可能是,唐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因射脾酋长沙陀那速归唐有功,唐朝以原阿史那贺鲁所领授予之,且以其姓命名该部,而原阿史那贺鲁统治之下的处月则转归沙陀那速统治,由此开始了射脾与处月合并之路。其次,尽管两个部落在归唐之后走上合并之路,但从人数来看,处月应远在射脾之上,仅永徽二年(651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在对处月一战之中即“俘九千人”。为平衡两者关系,可能后来新的沙陀部遂以“沙陀”为部族之名,而以“朱邪”为部族之姓。
对于沙陀与射脾的关系,岑仲勉先生从语音学角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证。首先,岑先生认为射脾即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失毕”①之异译:“按贺鲁所统为失毕五姓及处月、处蜜等众。..失毕亦翻失卑。准此以推,射脾盖失毕之异译。..五失毕之长为俟斤。《新唐书·沙陀传》言射脾俟斤,又射脾即失毕之旁证。”②岑先生言“失毕亦翻失卑”甚确,然岑先生认为射脾亦即弩失毕,我们认为欠妥。在阿史那贺鲁之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时,已将所统突厥部落划分十部,五咄陆居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之西①。而阿史那贺鲁牙帐在西州之北多逻斯川,其所统之五部均在东部天山地区②,两者地理位置根本不符。我们认为,阿史那贺鲁所统部“弩失毕”之“弩”为衍(吴玉贵亦持类似观点)③。其次,岑先生认为沙陀之语原即唐史中常见之“失毕”或“矢毕”:“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之‘sadapyt’相比;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④综合岑先生上述论证中可以看出,岑先生主张“沙陀”从语原上源自“射脾”。
射脾是唐朝初期活动在东部天山地区且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一个部落。阿斯塔纳一七一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关于射脾活动的记载,是目前所知的射脾最早的活动。这是一件记载高昌麴氏王朝与突厥人往来的官方文书。现移录相关内容如下:
[前欠]
1 次羁人赵头六、王欢儿贰人,付宁僧护,用看珂
2 懃苏弩胡鹿大官、公主时健大官
3 付毛海龙,用看毗伽公主寒
(略)
9 纥达官伍日。次小张海柱,付康善财,用看坞耆来射卑
10 妇儿伍日。令狐资弥胡,付王善祐子,用看尸不遝〓
(略)
21 看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次吕隆伯,付(略)
33 伯儿,用看居〓抴使伍日。次赵小儿,付康善财,用看
34 坞耆来射卑妇儿伍日。侍郎麴延陀侍讲辛武护
(略)①
这件文书第9行、21行、34行的“坞耆”为“焉耆”的异译,“射卑”也即“射脾”。②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射脾是游牧于焉耆境内天山之中而且与高昌麴氏王朝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部落。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高昌延寿十四年统治西域的西突厥可汗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同俄设,则此时的射脾当归沙钵罗蛭利失可汗统治。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在位时期西突厥内忧外患交加、危机四伏,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十三年,“咥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③。咥利失之后继位者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与乙毗咄陆瓜分西突厥汗国,游牧于焉耆附近的射脾当归属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统治。
贞观十五年(641年),“咄陆可汗与叶护颇相攻击..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乙毗咄陆可汗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之后,“自恃其强,专擅西域”④,整个西域处于乙毗咄陆可汗统治之下,此时的射脾应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
乙毗咄陆统辖下的射脾早期是否曾归统辖东部天山诸部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由于史料阙如,尚不得而知,但阿史那贺鲁继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统治东部天山诸部时期,射脾归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当无疑。阿史那贺鲁统治天山东部时期进行过一系列反唐活动,射脾也追随阿史那贺鲁参与了反唐活动。高宗初年唐政府组织弓月道行军征讨阿史那贺鲁之前,首任庭州刺史骆宏义所上唐帝之疏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该疏云:“臣闻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事无常准。今有降胡来言:贺鲁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积雪,汉兵必不远来。诚宜乘其此便,一举可以除剿。若迁延待春,恐事久生变,纵不能结援诸国,必应远迹遁逃。且兵马此行,本诛贺鲁,处密已许款诚,处木昆等各思免祸,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虑更乌合。然严冬风劲,马瘦兵寒,瘃堕之忧,难量进退。又不可久停兵马,虚费边粮。见我不前,成其党附。伏望且宽处月、处密之罪,以诛贺鲁为名,除祸务绝其原,未可先取其枝叶。但此两姓,见其坐夺,不示招携,必自深据。如弃而西过,则近有后忧。先事诛夷,未可即克。舍而勿问,则惑义前驱,事定从宜。除申吊伐,此乃威恩兼举,远慑迩安。向使兵马早来,贺鲁久已悬首。前机虽失,须为别图。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芯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掩袭。大军顿于凭水,秣马畜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且番人行动,须约汉兵,东西犄角,又资翘翼,简胡骑以率其前,率汉兵以蹑其后。贺鲁进退无路,理即可擒,百胜之谋,在斯一举。臣恐建方至日,为计不同,军谋乖舛,后悔无及。”①
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诸部的招慰活动中,射脾部在其首领沙陀那速的领导下归唐,归唐后的射脾部获得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前所领的权力,从而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射脾的族源似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因为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前,“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为铁勒诸部落游牧之地。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这些铁勒部落几乎全部改用“突厥”族名,虽然他们同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关系亲疏不一,但他们“族名相同,语言相近,风俗相似”,是异姓突厥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射脾所处之位置恰与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所处之位置相吻合,故射脾极有可能源自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中之一部。芮传明从语音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铁勒属部之“苏婆”(suo一b’u〓)和射脾(dz’ia—b’jie)从语音来看极为接近,可以被看作为同一名称的异译,因此他断定,射脾源自西域铁勒部落中的苏婆部②。
第二节 “沙陀”名称之演变
“沙陀”名称经历了由部落酋长之姓氏到部落之称号的转变,其间又成功将处月部落涵化并融入沙陀部落中。我们在此对“沙陀”名称之演变略作考证。
“沙陀”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新唐书·沙陀传》云:“永徽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竹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第一,“沙陀”为“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之姓;第二,阿史那贺鲁叛唐,处月酋长朱邪孤注追随贺鲁反唐,而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却弃贺鲁归唐,两者态度截然不同;第三,唐廷对朱邪孤注和沙陀那速赏罚分明,对前者派大军镇压,擒获斩首,对后者不但命其统领贺鲁部众,而且“置金满、沙陀一州,皆领都督”。“沙陀”之名,可能是唐廷为嘉奖沙陀那速的忠诚,以其姓氏为都督府之称。沙陀那速的归唐及沙陀州的设置,使沙陀之名,远扬内地。
因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归唐有功,故“沙陀”之名日益彰显,而“朱邪”之姓日渐淡漠。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唐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①,这是沙陀那速之后第二个载入史册的沙陀酋长,其后陆续有沙陀辅国、沙陀骨咄支等沙陀酋长,沙陀之名代代相传。
对于“朱邪”重新出现,我们认为主要是在吐蕃进逼,北庭难保的情势下,原一直与唐朝对抗的处月部暗通吐蕃,并在吐蕃的扶持下逐渐获得沙陀的统治权所致。
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弃城西逃,退守甘州。永泰元年(765年)十月,“沙陀杀杨志烈”②。从处月部屡次叛唐的历史来看,杀害杨志烈的沙陀人,应该就是处月部人。这也说明,早在吐蕃进攻北庭之前,处月已经背叛了唐朝。
在吐蕃的扶持下,处月势力在沙陀部中迅速膨胀,遂导致沙陀部酋长沙陀尽忠被迫改姓为“朱邪”,名曰“尽忠”。从史料记载来看,沙陀部酋长由“沙陀”姓改为“朱邪”自沙陀尽忠开始。沙陀尽忠之名,见之于《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六③。而更多的史料则将之称为朱邪尽忠。朱邪尽忠可能就是遭受到了处月部的威胁,被迫改姓“朱邪”,并率部投降吐蕃的沙陀部首领。
第三节 沙陀早期的活动区域
射脾、处月归唐之后,两者逐步走上合并之路,新的沙陀族日渐形成。归唐之后,沙陀主要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但是对于其活动的具体区域,相关文献记载甚少。对此,我们通过文献、考古资料及实地考察,对沙陀早期的活动区域进行初步探讨。
一、沙陀在“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一带的活动
“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是沙陀人当年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域,根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其境内“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关于沙陀所居之“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大致位置,学界观点不一:毛凤枝认为,“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就是“吐鲁番之南罗布泊之东之大戈壁矣”①;岑仲勉认为,金娑山及遏索山,也即额林哈毕尔噶山,处月部“在额林哈毕尔噶山之南,自空格斯流域,迄于天山之北”②,即伊犁河流域;丁谦认为“金娑山在巴里坤城东北三百余里,《西图》作尼赤金山。蒲类海即巴尔库里泊,即巴里坤湖。湖之东山之阳,地皆沙漠,处月部居此”③;沙畹认为,《新唐书·沙陀传》之金娑山即新疆北部之博格达山(Bokdoola)④。以上诸说当中以丁谦的观点较为贴近事实,后世学者亦多从此说⑤。通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丁谦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即沙陀的活动地在今巴里坤县和伊吾县之间;对于史书所云其境内之大碛,应是中蒙边境上的“二百四戈壁”。
“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原系处月部游牧之地,后来由于处月部屡次叛唐,为分割处月势力,唐政府遂在平定处月之后将此地封给在唐平定西突厥过程中有功的射脾部。由于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归唐有功,该州便以射脾部首领沙陀那速之姓来命名⑥。沙陀州存在的时间可能不长,《新唐书·沙陀传》云:“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可知,龙朔初(661年),沙陀金山随薛仁贵讨铁勒,沙陀部便离开沙陀州,居瓜州西北千里之墨离军。沙陀金山离开巴里坤草原,沙陀州很可能随即废止,该地成为了伊州管辖范围内的一处重要军事基地。《新唐书·地理志》云,伊吾郡“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军,景龙四年置。”《旧唐书·地理志》云:“伊吾军,开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镇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在北庭东南七百里。”《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吾军,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奉敕置,至开元六年(718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四十匹。”①由上述史料可知,沙陀金山率部离开沙陀州之后,该地成为伊吾军的驻扎之地。伊吾军军城所在之甘露川即位于巴里坤县城东北15.5公里处大河之阳的大河古城。该城东西长420米,南北宽约200米,分主城和附城,中有通道相连接,城外有护城壕。该城历经近一千三百年的风吹雨打,厚约9米,高约6米的城墙已大部裂塌,唯西北一段约30米的城墙仍屹立高耸。我们踏上这座残城之时,仍能感受到该城昔日之规模和雄风。
离开巴里坤草原之后的沙陀首先在沙陀金山率领下北征铁勒,之后又迁转至沙州西北千里之墨离军。长安二年(702年)随着沙陀金山升迁为金满州都督,沙陀部又迁转至庭州境内。沙陀部的这次迁转似乎说明如下问题:一、活动于庭州一带的处月部再度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不安定因素。2003年洛阳出土的李释子墓志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该墓志记载,李释子“久视(700年)初,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根据该墓志记载,在沙陀金山升迁金满州都督的前两年,李释子开始任盐、甘、肃州刺史兼处月大使,这似乎说明处月部又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障碍;二、仅距李释子任处月大使两年沙陀金山便任金满州都督,其目的可能就是安抚处月。三、沙陀金山任金满州都督,沙陀、处月二部同处一地,可能加速了沙陀、处月合并的步伐。
当然,沙陀与处月合并非一帆风顺,其间部分处月部族可能不满沙陀金山的统治,离开了其长期活动的庭州地区,迁转他乡。根据吐鲁番文书记载,其中就有部分处月人迁移到了西州地区(详见下文)。两部合并之后的沙陀部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仅仅事隔三十余年,由于“刘涣凶逆处置狂疏”,沙陀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后又迁转至伊州,短暂居留。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记载了此事:“敕伊州刺史、伊吾军使张楚宾: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蹔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与盖嘉运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计必思归,从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处置了日,具以状闻。夏中盛热,卿及将士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①
沙陀乃游牧部落,且人数不少,安置这样一个游牧部落,在伊州地区只有巴里坤草原,同时巴里坤草原又是伊吾军驻扎之地,沙陀迁移至此,既占水草丰美之利,又便于唐军监控。故沙陀在“刘涣凶逆处置狂疏”之后可能又曾短暂活动于巴里坤草原。
沙陀除了活动于巴里坤草原之外,还曾活动于哈密东北部地区。该地曾属沙州府管辖范围,沙州府墨离军军城曾短暂存在于此地区。龙朔年间,沙陀首领沙陀金山曾在此任墨离军讨击使。关于墨离军早期军城的位置,《新唐书·地理志四》“瓜州晋昌郡”条记载:“有府一,曰大黄,西北千里有墨离军”;《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凉州”条记墨离军云:“瓜州西北一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东去理所一千四百余里”;《通典》卷一百二十七“墨离军”条与《元和郡县图志》同。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早期墨离军军城位于瓜州西北千里之处。关于墨离军的确切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吾县”条记伊州八到云:“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九百里。”瓜州距离伊吾不过900余里,则墨离军当在哈密天山以北的大川。林梅村将墨离军军城位置定在今伊吾县城东48公里处的下马崖古城,为此我们曾亲身前往下马崖进行过实地考察。下马崖古城位于下马崖乡水库南侧,东北距离乡政府3公里。古城基本呈正方形,边长100余米,城墙之上设有射口,而且城中偶尔发现清代钱币,故学界一般将其定为清代建筑。将该城断为清代当属不误,但说此城清代建成,恐有疑问。我们认为,此城应是唐朝时期一边镇,后被沿用直到清代。下马崖所处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它地处天山东部尾端,地势平坦,是连接蒙古草原、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的要冲。在此设置军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认为,该处可能就是唐初①唐朝经营西域时设置的墨离军之所在。但是据我们考察,该处非如文献所记载之“气候温暖,冬夏季均饮用及灌溉农田,为利非鲜”②。该城所处之下马崖乡总人口仅700余人,四周均是一片茫茫戈壁,基本不适合大队人马长期居住。故我们认为,墨离军初设于此,实属军事战略之权宜之计。
龙朔初(661年)沙陀金山随武卫将军薛仁贵讨伐铁勒,龙朔二年铁勒被平定,事后沙陀金山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此时的沙陀金山部可能就驻扎在今下马崖古城一带。但是,沙陀金山任墨离军讨击使一职为时不久,长安二年(702年)便升为金满州都督,从此沙陀离开了下马崖。沙陀部在其酋长沙陀金山的率领下,在下马崖共生活了近40年。
墨离军军城驻扎下马崖的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后来随着沙陀金山升迁为金满州都督而废止,之后墨离军撤回沙州城。其间墨离军军城之位置经历了由沙州西北“十里”到“千里”的变迁③。
墨离军撤离下马崖之后,其军城可能又被伊吾军短暂启用,证据如下:《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吾军,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奉敕置,至开元六年(718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四十匹。”则,最初伊吾军之军城不在今巴里坤大河古城。《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又载:“庭州瀚海军、西州天山军交河县,伊州伊吾军柔远县。”则,伊吾军设置初期,其军城在昔日柔远县境内。而下马崖亦属昔日柔远县之管辖范围,且其附近有烽火台。因此,墨离军撤离下马崖之后,唐朝于景龙四年所设之伊吾军军城地址就在今下马崖,初设至此,亦属权宜之计,后伊吾军迁转至水草丰美的巴里坤大草原,于今大河古城重建军城。
二、沙陀在北庭附近的活动
庭州地区是处月沙陀部的活动中心,《西州图经》(残卷)在叙述白水涧道时有如下记载:“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马车。”①该史料显示,处月的活动中心应在交河县以北的庭州地区,即今吉木萨尔、奇台一带。
处月部活动范围以庭州为中心,最东达巴里坤、伊吾一带,最西可达乌鲁木齐。《新唐书·西突厥传》在叙述阿史那贺鲁叛乱,庭州刺史骆宏义献策时云:“愿发射脾、处月、处密、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住凭洛水上为之助景,此驱戎狄攻豺狼也。”这说明处月的活动范围最远不过凭洛水。关于凭洛水,学界观点不一,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凭洛镇在府(庭州)西三百七十里”之记载。该凭洛镇定是凭洛水沿岸一重镇,因以为名。根据里程,此凭洛水应在今乌鲁木齐附近②,则处月活动范围西限也应在今乌鲁木齐附近。
处月归唐之后,唐朝在处月活动地区设羁縻金满州以安置之。金满州治所之位置,应在庭州州治附近境内。首先,庭州治所与其下属金满县治所同治一城,均在今吉木萨尔破城子。清朝中叶徐松勘察北庭之后,于《西域水道记》云:“济木萨唐为金满县,北庭都护府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即今吉木萨尔县城西北角之古城遗址)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庭州与金满县同治一城无疑矣。其次,羁縻金满州既冠以“金满”,其活动范围当在金满县境内。故,金满州治所距庭州治所破城子不远。还有的学者认为金满州治所与庭州治所均在同一城,我们认为不妥。首先,作为汉人居住的郡县与安置少数民族之羁縻州、府截然不同。毛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卷三云:“金满州与金满县本系两地,金满县中国郡县之地,由中朝命官而往,即今之流官;金满州为外蕃羁縻之地,其酋长世袭都督,如今之土司是也。”③作为外蕃羁縻之地的金满州,其治所亦不可能与作为汉人郡县的金满县之治所放在一起。但既名为“金满州”,其治所应在金满县境内;又,《新唐书,沙陀传》载:“先天初(712年)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714年),复领金满州都督。”这段记载显示,金满州治所距庭州尚有一段距离,否则沙陀金山就不会“徙部北庭”。
处月在庭州地区除从事游牧生活外,还从事定居生活,因为根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郭孝恪平定乙毗咄陆之乱时曾“拔处月俟斤之城”。此处的“处月俟斤之城”就是处月部活动中心之所在。我们认为“处月俟斤之城”应该就是后来唐朝所设羁縻金满州之治所。关于“处月俟斤之城”之位置,据薛宗正认为,很可能是庭州东之蒲类县,今奇台唐朝墩古城废墟①。我们认为不妥,唐朝墩古城乃唐朝蒲类县治所之所在,早在贞观十四年就与庭州同时设立②。作为中国郡县治所,断然不能与外蕃羁縻之金满州同在一处。
三、沙陀在西州的活动
沙陀除在今哈密、昌吉地区活动之外,还曾在吐鲁番地区留下过活动的足迹。
活动于吐鲁番的是处月部中的一个分支,上引吐鲁番出土文书《开元十六年朱邪部落请纸牒》(大谷5840)记录的就是当时处月一个分支在西州的一些活动情况。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邪波德的签名,时间是开元十六年(728年)。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开元十六年之时,处月部已有分支活动于西州境内。对于这支部落迁移到西州的原因,李方先生认为是“先天初(712年)避吐蕃,徙部北庭”中未到庭州而是分道扬镳来到西州的③。我们认为不妥,这支处月部落迁移到西州的时间应是702年沙陀金山任金满州都督前后。其时,处月发动了新的叛乱,唐朝政府除任命李释子兼任处月大使力图安抚之外,又命沙陀金山任金满州都督直接统辖处月部。这期间部分处月部可能不满沙陀金山的统治,因此迁移到了与庭州毗邻的西州。
第四节 沙陀与周边民族之关系
沙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周边许多民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其中与沙陀交往较多的有四个民族:西突厥、回纥、吐蕃、葛逻禄。本文试图对沙陀与这四个民族的关系做一个系统、全面的论述。
一、沙陀与西突厥之关系
在沙陀与周边诸民族关系中,沙陀与西突厥接触最早且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突厥初期,沙陀就与西突厥发生了关系。《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载:“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异。”《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亦云:“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密杂居。”关于沙陀与西突厥的关系,史书多称其为“西突厥别部”①,有些史书因此径直称其为“沙陀突厥”②,沙陀应是被西突厥征服之后处于西突厥统治之下的一个部落。沙陀作为西突厥的一个属部,其归唐前主要活动都是在西突厥最高统治者指挥下进行的,其政治立场与西突厥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沙陀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之时正是西突厥由盛转衰内乱、分裂不断,最高统治者频繁更换之时,作为西突厥属部,沙陀在短暂的几十年内先后依附于西突厥统治阶层的不同派系。
咥利失统治时期(?—638年):处月活动最早见诸史书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是年十月乙亥“处月遣使入贡”①。其时统治西突厥的是受唐朝册封的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作为西突厥的属部,此时的处月当属咥利失统辖,但是此时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处月作为西突厥属部,断无单独遣使朝贡之权,其敢于单独遣使朝贡说明处月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独立性,处月与西突厥的这种从属关系已经相当松散。这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一直维系到贞观十一年(637年)咥利失与欲谷设之间的伊犁河大战,此时,处月与弩失毕、处密等部尚归咥利失管辖②。
乙毗咄陆统治时期(638—?年):伊犁河大战之后的贞观十二年(638年),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处月部又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证据如下:贞观十二年,乙毗咄陆曾征发处月、处密部兵马,联合高昌国,攻打咥利失势力范围内的焉耆国。《旧唐书·焉耆传》云:“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咥利立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与焉耆为援。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③而根据薛延陀呈唐太宗的一份报告可知,联合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的处月、处密部的幕后指挥就是欲谷设,即乙毗咄陆可汗。《册府元龟》云:“太宗贞观十三年,薛延陀遣使上言:‘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厚,尝(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前导,驱以讨之’。”④
乙毗咄陆统治下的天山东部处月、处密等部落和平局面维系不久便发生了内讧,其原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其兄阿史那步真驱逐,“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阿史那步真自立为咄陆叶护⑤。由此,处月部一分为二,小部随阿史那弥射入唐,而大部仍留原地。未几,阿史那步真因部众不服,又因唐交河道行军进逼,也投降唐朝。
阿史那步真入唐之后,统治处月等部落的是阿史那贺鲁。《册府元龟》记载:“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①
贞观十五年乙毗咄陆攻杀唐朝政府册立的泥孰系沙钵罗叶护可汗②,复击败吐火罗,东进寇略唐朝在西域的范围,此时的西突厥基本已统于乙毗咄陆,其势力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乙毗咄陆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发处月、处密部连寇伊州和西州之天山县。《新唐书·突厥》下云:“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两千,自乌骨狙击,败之。咄陆以处月、处密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密]部而归。”此事之后,乙毗咄陆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西突厥弩失毕部的请求下,唐朝政府“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③
乙毗咄陆失败之后,乙毗射匮势力迅速向处月、处密等部所处的天山东部地区发展,企图填补乙毗咄陆失利后该地区形成的政治空白。而此时统治天山东部诸部的阿史那贺鲁在乙毗咄陆败亡之后面临着日益窘迫的局面。《通典》载:“咄陆西走吐火罗国,射匮可汗遣兵迫逐,贺鲁不常厥居。”④
乙毗射匮统治及其间短暂归唐时期(?—648年):在乙毗射“遣兵迫逐”阿史那贺鲁的情况下,原来隶属于阿史那贺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在乙毗射匮的挟制下归附乙毗射匮,同时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阿史那忠碑》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其云:“既而句丽、百济,互相侵逼;处月、焉耆,各为唇齿,肆回邪于荒裔,轸吊伐于皇情,天□□□□□□□□躅□□□□□乃□绥边□□诏公□〔西〕域安抚,载叶□如之寄,右地聋□,加授上柱国。”①从《阿史那忠碑》我们可以看出,在贞观十九年之前处月、处密已经和焉耆一起“肆回邪于荒裔”,站在了唐朝政府的对立面。针对西域出现的新叛乱,唐朝政府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对于乙毗射匮与唐王朝之间对处月等部落的争夺,相关史传没有记载,但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政府发布的《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却透露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
《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云:“西域之地,经途遐阻,自遭乱离,亟历岁月,君长失抚驭之方,酋帅乘叶赞之义,虐用种落,肆行残忍,遂使部众离心,战争不息,远近涂炭,长幼怨嗟,大监小王,无所控告,顿颡蹶角,思见含养。朕受命三灵,君监六合,御朽之志,无忘寝兴;纳隍之怀,宁隔夷夏;乃眷西顾,良深矜惕;宜命輶轩,星言拯救。可令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蜜〔密]部落,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问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②《阿史那忠墓志》云:“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泑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侍辇幽燕,言过汾晋。于时延陀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驿赴救,事宁而反。”③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阿史那忠的西域“抚慰”之行达到预期目的,“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处月等部落名义上又重新归附唐朝。但这并非出自真心,事后很快又归附乙毗射匮。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芯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军讨伐龟兹。这次讨伐处月也是打击对象,这从昆丘道行军之前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资治通鉴》载:“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①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处月、处密等部此时已经归附乙毗射匮,唐朝政府组织的这次针对乙毗射匮的昆丘道行军其讨伐对象亦包括处月、处密部。唐太宗行军前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首先就将处月、处密击败②。
阿史那贺鲁统治时期(648—657年):就在唐朝政府组织昆丘道行军征讨乙毗射匮之时,遭乙毗射匮追逐,四处漂泊无所寄托的阿史那贺鲁投降了唐朝政府。阿史那贺鲁此举得到了唐朝政府的礼遇,《新唐书·突厥传》载:“贺鲁无常居,部多散亡。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③处月原为阿史那贺鲁旧部,昆丘道行军中处月遭受唐军重创,加之阿史那贺鲁降唐受到唐朝政府礼遇。于是不久,处月在其阙俟斤朱邪阿厥带领下“亦请内属”④。自此,处月重新成了阿史那贺鲁的麾下。
阿史那贺鲁降唐之举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阿史那贺鲁随昆丘道行军征讨两个月之后,唐朝政府便在天山东部地区设立瑶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⑤,很快唐朝政府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晋封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大将军。但是阿史那贺鲁骨子里是反唐的,他降归唐朝其目的是借助唐朝势力发展壮大自己。在唐政府的扶持下,“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⑥,阿史那贺鲁很快统一了西突厥诸部。阿史那贺鲁的羽翼刚刚丰满,便暴露出其反唐的本质,他“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⑦于永徽元年⑧反唐,并于次年自封沙钵而《新唐书》及《唐会要》则记作“永徽二年”(《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53页;《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第1322页)。罗可汗,建牙双河及千泉,拥兵十万,西突厥诸部皆归属之。起兵之后,阿史那贺鲁首先入侵庭州,攻破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对唐政府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是年七月丁未,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发秦、成、歧、雍汉兵三万、回纥兵五万,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一次征讨。征讨之前,庭州刺史骆宏义上言,主张征讨之前应招降处月、处密等部落,以减少行军的阻力,同时与之合兵共讨阿史那贺鲁。骆宏义云:“望请于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沿袭,大军顿于凭(洛)水,秣马蓄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①高宗最初采纳了此建议,派出各路使者招慰西突厥各部。但事与愿违,是年十二月壬子,处月酋长朱邪孤注首先杀害唐朝政府招慰使单道惠,与阿史那贺鲁联兵抗唐。只有作为沙陀族源的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拒绝随阿史那贺鲁叛唐,应招降唐。唐朝政府的招慰计划宣告失败。永徽三年唐朝大军开始西进征讨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闻讯西遁,而处月部朱邪孤注则居牢山自守,企图借地势之险要以拒唐军西进。“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是年癸亥,唐军数路并进,一举攻克牢山,斩处月酋长朱邪孤注,俘获处月、处密等部渠帅六十余人,斩首五千余级,俘生口万余计以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西域诸部纷纷随②。处月依附阿史那贺鲁叛唐,阿史那贺鲁叛唐之时,“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事后唐高宗以阿史那贺鲁以前所任瑶池都督一职授予沙陀那速③。
对于这次行军的原因,有的史料将之归结为处月等部的反叛④,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此次行军的主要目的就是讨伐阿史那贺鲁,而平定处月、处密叛乱只能看作是本次行军的最终收获①。
弓月道行军之后,唐朝于永徽四年(653年)正式撤销瑶池都督府,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②,至此处月部落中的朱邪部以羁縻州府的形式正式纳入唐朝政府的统治。
弓月道行军并没有和阿史那贺鲁正面交锋,所征服的仅仅是阿史那贺鲁前锋——处月、处密部之主力,此外仍有预支部依附阿史那贺鲁顽强对抗唐朝,所以弓月道行军基本是以失败告终。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此次征讨唐军深入西突厥腹地,与阿史那贺鲁属部交锋,取得辉煌战果。“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③。至此处月预”支部基本为唐军所征服。
显庆二年(657年)唐朝政府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三次征讨。此次征讨处月部未降者再次遭到重创。“(阿史那)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帅众来降”④。最终唐军大破阿史那贺鲁,西突厥被彻底平定,沙陀余部亦归唐,沙陀与西突厥的从属关系宣告彻底结束,沙陀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沙陀与回纥之关系
回纥是继突厥之后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汉朝时期的丁零,北魏时期为铁勒(别号高车)六部之一的袁纥部。沙陀与回纥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最早的接触是在唐军征讨西突厥过程中,当时双方以敌对关系出现;其后在吐蕃攻占西域过程中又与回纥结成友军共同抵抗吐蕃的进攻;沙陀内迁后,沙陀作为唐朝守边者与侵扰唐朝的回纥再次交锋,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了敌对关系。
沙陀与回纥最早的接触是在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西域战场上。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帅铁勒各部联合唐军一举灭亡薛延陀,后在回纥的请求下,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春正月在薛延陀、回纥、铁勒及其他各部地区设立六府七州,“北荒悉平”①。漠北的平定不但消除了唐朝北部边患,而且为唐朝提供了充沛的兵员。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的征讨过程中回纥数次参与,为唐朝平定西突厥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唐太宗以龟兹王仰仗西突厥,“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以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行军大总管发动了昆丘道行军讨伐龟兹。以回纥为首的“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②首次参加了唐朝军队征讨西突厥的战争,而且是行军的主力。在这次行军中回纥等部骑兵在阿史那社尔率领下,相继攻占焉耆、龟兹,接着打败西突厥援军,向西攻占拔换城。这次战役震惊整个西域,塔里木南缘的于阗、疏勒及葱岭以西之安国“皆相率请降,凡得七百余城,掳男女数万口”③。至第二年十月,唐军完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西突厥失去了在天山南路的立足之地。唐于是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并建立安西四镇。此次昆丘道行军除征讨龟兹之外,处月也是该次行军的重要征讨对象。前引唐太宗与侍臣之间的一段对话云:“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唐太宗之预言不差丝毫,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④,昆丘道行军首战即以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沙陀与回纥的首次接触,其结局是回纥铁骑作为昆丘道行军的主力成功将沙陀击破。
唐军的西征引起乙毗射匮反对派阿史那贺鲁的强烈响应,他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己亥降唐,并获得厚赐。其后,阿史那贺鲁在唐朝政府的扶持下很快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及西域诸国。随着羽翼丰满,其反唐之心开始暴露,“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叛”,先是攻破唐控制的金岭城及蒲类县,继而攻陷北庭。唐政府以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兵五万击之”①,而且回纥这次出兵由吐迷度之子婆闰亲自率领,并兼任行军副总管②,足见回纥部众在此次行军中的主导作用。此次征讨,大破贺鲁收复北庭,并击破处月朱邪部落,斩其酋长朱邪孤注。这是沙陀与回纥的第二次交锋,同样以沙陀的失败而告终。
永徽六年,唐高宗以开国元老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起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显庆元年(656年)葱山道行军正式从长安出发西征。紧随其后,唐朝政府于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庚戌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阿史那贺鲁战役。关于这两次征讨,《旧唐书·回纥传》将之并到一起叙述:“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之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③由此可知,回纥军队在其首领婆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两次征讨。
弓月道行军之后尚有沙陀预支部仍随阿史那贺鲁负隅抵抗,葱山道行军唐军与处月预支部兵戎相见。史载:“(显庆元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罗、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④由此可以推知,沙陀与回纥在葱山道行军中再次兵戎相见,并且又是以回纥的取胜告终。
阿史那贺鲁叛乱被平定之后沙陀归唐,在唐朝政府统治之下沙陀与回纥再度接触。在平定西突厥过程中回纥立下汗马功劳,平叛后首领婆闰被授予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府都督。婆闰上任之后不久便染病去世,其侄比粟毒继位。比粟毒继位后并不甘心服从于唐朝,遂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勾结同罗、仆骨进犯唐朝边境。高宗令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共同率军讨伐①。沙陀部首领沙陀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一同征讨,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又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②。这是沙陀归唐后和回纥的首次接触,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是此次交锋是以沙陀的胜利告终。
天宝初年,骨力裴罗在位时,回纥汗国兴起于漠北,其势力西抵金山③。首领骨力裴罗也因内附先后被唐玄宗封为奉义王、怀仁可汗④。此时沙陀居住地毗邻回纥汗国的势力范围,同为大唐臣民,双方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政府还册封沙陀首领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⑤。
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沙陀在其首领骨咄支率领下随回纥助唐平叛。沙陀虽随回纥参加平叛,但双方在平叛战场上并不存在依附关系。据史载:“(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邪、契、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⑥据此可知,沙陀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与回纥之间亦不存在依附关系。由于沙陀在平叛中的优秀表现,唐封其首领骨咄支为特进、骁卫上将军⑦。
唐朝政府遭遇安史之乱之时,安西、北庭边兵大量内调,吐蕃乘机扩张势力,它在占据河陇地区后,乘势向天山南北扩张。此时的安西四镇及北庭还掌握在唐军手里,但因吐蕃占领河陇地区而割断了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为了与内地取得联系,安西、北庭都护府使臣辗转数十年,最终借道回纥,“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①。由此,不但北庭、安西守军“附庸”之,“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②。此时沙陀与回纥之间已由安史之乱及其以前的彼此友好、协同作战的关系转变为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是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维系未几便破裂,主要原因是回纥对沙陀等部的苛刻统治。史称“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而沙陀对回纥的肆行抄夺,尤所厌苦”③。
回纥对所统诸族的苛刻统治,引起北庭部众强烈不满。吐蕃趁机以厚赂引诱各部,促使北庭诸部叛回纥附吐蕃。在吐蕃“厚赂见诱”下,葛(逻)禄、白服突厥先后归附吐蕃,稍后吐蕃与葛逻禄、白服突厥一起急攻北庭,遭受回纥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至此,由于回纥的“贪狠、征求无度”最终导致沙陀摆脱回纥统治,双方附属关系宣告结束。
归附吐蕃之后的沙陀不但在战争中常被驱为前锋,而且被吐蕃无端猜疑为私通回纥,面临被迁至河外的危险境地。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举众归唐,掀开其历史发展中崭新的一页。
三、沙陀与吐蕃之关系
吐蕃是历史上由藏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其族源可追溯至西羌的一支发羌。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也是发生在唐朝征讨西突厥的战场上。双方之间关系也是经历了“敌—友—敌”的转变。
沙陀与吐蕃的首次接触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昆丘道行军中。此次行军之前唐朝曾对吐蕃发起过洮河道行军,但双方很快结束战争化敌为友,此后唐又应吐蕃请求于贞观十五年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与吐蕃间结成了甥舅关系①。在此背景下,吐蕃作为唐朝友军与铁勒十三州、(东)突厥、吐谷浑等一道参加了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组织的征讨西突厥的昆丘道行军②。如前所述,此次行军首战便以大败处月、处密而告捷。这是史料记载的沙陀与吐蕃的最早接触。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疲于应付叛乱,吐蕃乘机屡次入侵唐朝。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③;“乾元以后,吐蕃乘机间隙,日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④。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地区基本为吐蕃所占领。
吐蕃进攻河陇地区时,沙陀可能在唐朝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从当时唐朝政府授予沙陀首领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骨咄支)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⑤唐朝政府遥授朱邪尽忠“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说明沙陀在河西地区与吐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继续进攻北庭,此时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守军相依,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御。五代人赵凤所撰《后唐懿祖纪年录》对此有详细记载:“德宗贞元五年,回纥葛禄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纥忠贞可汗,附于吐蕃,因为向导,驱吐蕃之众三十万寇我北庭。烈考(朱邪尽忠)谓忠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灵、盐,闻唐天子欲与赞普和亲,可汗数世有功,尚主,恩若娇儿,若赞普有恩于唐,则可汗必无前日之宠矣。’忠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将杨袭古固守北庭,无路归朝,今吐蕃、突厥并兵攻之,倘无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没,次及于吾,可汗得无虑乎!’忠贞惧,乃命其将颉干迦斯与烈考将兵援北庭。”⑥但是回纥与沙陀的救援并没有改变北庭陷落的命运,加上回纥对其“贪狠、征求无度”,最终沙陀随北庭守军一道于贞元六年(790年)投降了吐蕃。至此,沙陀与吐蕃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了从属关系。
沙陀降蕃后其首领朱邪尽忠被授予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被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由于沙陀人骁勇善战,勇冠诸胡,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①,故沙陀部落死伤甚多,加上吐蕃对其横征暴敛,沙陀对吐蕃的统治无法忍受。后来,“回鹘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即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地域,当时为偏僻荒凉之地),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行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俞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欲迁②。回纥取凉州被吐蕃怀疑为沙陀勾结回纥所为③其于河外,导致沙陀举族愁怨,最终东归唐朝。沙陀与吐蕃仅二十年的从属关系宣告结束。
元和三年沙陀脱离吐蕃统治,开始了东归唐朝、投靠灵州节度使范希朝的历程。沙陀的东归激起了吐蕃的愤怒,吐蕃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此时沙陀与吐蕃已由原来的从属关系重新转变为敌对关系。
对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记载:“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傍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落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裒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④沙陀自甘州出发之际,共有部众“三万余落”,东归途中遭吐蕃追杀,到达盐州时仅剩近三千人,且已饥寒交迫,劳疲不堪。
四、沙陀与葛逻禄之关系
葛逻禄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活动中心“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①,相当于今新疆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它与处月一样,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属西突厥之别部。由于葛逻禄地处东、西突厥之间,因此常视双方力量之消长而叛附不定②。
沙陀与葛逻禄之间的关系发生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左右。其时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归唐,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命叶护阿史那贺鲁统治东部天山地区。史称:“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月、处(因)密、始(姑)苏、哥逻禄、卑失五姓之众。”③沙陀与葛逻禄开始发生关系。
唐朝平定西突厥之前,沙陀与葛逻禄一道在阿史那贺鲁指挥之下对抗唐朝。永徽元年(650年),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④反唐。之后,唐朝政府组织了数次行军,征讨西突厥。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发动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二次征讨。“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颉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⑤。葛逻禄与处月在同唐军对抗中遭受重创。
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之后,唐朝于显庆三年(658年)设立羁縻州府以处置葛逻禄部众:以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至阿拉湖一带;以炽俟部置大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青河以南、乌伦古河下游地区;以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辖地在今新疆塔城以北、斋桑泊以南地区。沙陀之处月、射脾部亦设金满州、沙陀州以妥善安置。归唐后的沙陀与葛逻禄之间再度发生关系。
近年出土的《唐龙朔二、三年(662—663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及《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①两份文书记载了两者之间发生的一件事:龙朔元年,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被贼人打散,有一千帐从金山(阿尔泰山)南下,在金满州地域停住,金满州都督沙陀某某将这一信息上报朝廷。朝廷分别给燕然都护府、哥(葛)逻禄部下敕令,命燕然都护府与西州都督府相知会,将停住金满州的哥(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遣返大漠都督府原住地。龙朔二年,燕然都护府获取哥(葛)逻禄首领咄俟斤乌骑支陈状,云该部在龙朔元年敕令下达之前已经在金满州有水之处种下麦田,而且该部所放养的牲畜因遭受暴风雪,缺乏充足的草料,无法长途跋涉回归原住地,希望迁往甘州。之后龙朔三年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又相知会,力促哥(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留住金满州的葛逻禄仅五十帐,其他帐已经入京,故未能立马返回原住地。
通过这两份出土文献可以看出,葛逻禄归唐之后,曾流落至金满州境内,并从事农业生产,其间肯定得到了沙陀的照顾。尽管金满州与西州、燕然都护府数次规劝葛逻禄返回原住地,但是葛逻禄留恋金满州之地,迟迟不归。该文书没有显示该事的最终结果,但从葛逻禄的态度上看,估计有部分葛逻禄人留在了金满州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最终融入沙陀部落当中。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减弱,沙陀同葛逻禄、白服(一作白眼)突厥一道处于回鹘的统治之下。然而“回鹘数侵掠之”,贞元五年(789年),葛逻禄部“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接着,吐蕃率葛逻禄、白服之众进略北庭,回鹘数战皆败。最终,遭受回鹘苛刻统治的沙陀同北庭守军一道投降吐蕃。此后,沙陀被吐蕃迁往河西地区,而葛逻禄主要活动于中亚一带,沙陀与葛逻禄的交往由此中断。
附注
①孙光宪:《北梦琐言》第十七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6页。
①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年6期,第68—77页。
②和宁:《三州辑略》第一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8页。
③陶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④《旧五代史》卷二十五《武皇纪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1页。
⑤《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页。
⑥刘维新主编:《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⑦李树辉:《哥逻禄新论》,《龟兹学研究》第一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1页。
①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②《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下册,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第669页。
③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史学问题解答》,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3—74页。
④徐庭云:《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6期。
⑤陈佳华主编:《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177页。
⑥郭平梁:《回鹘西迁考》,《西域史论丛》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41页。
⑦宋肃瀛:《回纥的由来及其发展》,《西域史论丛》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9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3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二,“庄宗光圣神悯孝皇帝上”条下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8879页。
③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30页。
④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130页。
⑤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3页。
⑥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40页。
⑦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⑧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第300页。
⑨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52页。
⑩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年6期,第68—77页。
①《双溪醉饮集》卷二,辽海丛书本。
②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③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27页。
④陈佳华主编:《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77—178页。
⑤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
⑥岑仲勉:《隋唐史》,第514页。
①张乃翥:《裴怀古、李释子、和守阳墓志所见盛唐边政之经略》,《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3页。
①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三),法藏馆2002年,第209—210页。
②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828页。
③《全唐文》卷二百八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2883页。
①“失毕”在不同文献中称呼不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作“失毕”,第6256页;《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传》作“卑失”,第4119页;《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下》作“失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86页;《通典》卷一百九十九《边防十五》作“毕矢”,中华书局,1988年,第5459页。
②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第6060页。
②《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记载:“西突厥贺鲁者,成曵步利设射匮特勒越之子也。初,阿使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统处因、处密、始苏、歌罗禄、卑失五姓之众。”《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四十·交侵》,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20页。
③《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云:“弩失毕部此时不属贺鲁管辖,且弩失毕本有五姓,加处月、处蜜、姑苏、哥逻禄四姓,已有九姓,不当合称‘五姓’,此姑存疑。”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④岑仲勉:《隋唐史》,第513页注释③。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2—135页。
②参阅钱伯泉:《从传供状和客馆文书看高昌王国与突厥的关系》,《西域研究》,1995年1期;芮传明:《天山东部地区铁勒部落考——〈隋书〉铁勒诸部考》,《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1—2期。
③《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传》下,第5184页。
④《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传》下,第5185页。
①《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三百六十六《将帅部二十七·机略六》,第4143页。
①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14页。
②芮传明:《天山东部地区铁勒部落考》,《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1—2期。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②《新唐书》卷六《代宗纪》,第172页。
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五十六《外臣部一·种族》,第11076页。
①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影印本)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②岑仲勉:《西突厥史料及其补阙》,中华书局,2004年,第194—201页。
③丁谦:《新唐书沙陀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民国4年。
④沙畹著,冯承钧译:《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
⑤张云:《沙陀早期历史初探》,《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517页;艾冲:《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⑥黄盛璋先生亦将沙陀与处月分为二,认为“沙陀与处月杂处,而沙陀州亦以处月地置”。黄盛璋:《炽俟考》,《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①王仲荦《〈沙州伊州志〉残卷考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①《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1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3223页。
①《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记载:“墨离军,本是月氏旧国,武德(618—626年)初置军焉。《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90页。②《哈密专区兵要地志》,转引自钟兴麒:《唐伊吾军驻所甘露川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③严耕望先生云:“顷检《唐会要》七八节度使目,‘墨离军本是月氏旧国,武德初置’。或者唐初就有月氏旧国置军在瓜州西北一千里,其后移就沙州城,例以瓜州刺史兼充军使,《通典》、《元和志》合先后事书之耳,不觉自歧也。”《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程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85年,第441页。
①王仲荦:《敦煌石室出〈西州图经〉残卷考释》,《文史哲》1991年第6期,第71—73页。
②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
③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影印本)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①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
②《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6页。
③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
①《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五十六《外臣部·种族》云:“沙陀突厥本西突厥之别种也”;《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云:“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文献通考,·四裔考》云:“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第四》:“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中华书局,1986年,第6153页。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第6116页。
②《通典》卷一九九《边防一五·突厥》下云:“弩失毕、处月、处密等并归咥利失。”中华书局,1984年,第5457页。
③《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焉耆国传》,第5301—5302页。
④《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七十三《外臣部·助国讨伐》,第11264页。
⑤《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88页。
①《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第11520页。
②《唐会要》卷九十四《西突厥》,中华书局,1990年,第1693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第6168-6169页。
③《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59页。
④《通典》卷一百九十九《边防一五·突厥下》,1078页。
①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780页。
②《文馆词林》,《存佚丛书》第二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12月版。
③《阿史那忠墓志》,《考古》,1977年第2期。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第6253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第6261页。
③《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第6060页;类似记载又见《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一百零九《帝王部·宴享一》,第1035页。④《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3页。
⑤《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第5197页。
⑥《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第6274页。
⑦《新唐书》卷三十五《契苾何力传》,第4119页。
⑧《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第68页。
①《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三百六十六《将帅部(二十七)·机略六》,第4143页。
②《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契芯何力传》,第4119页;卷一百四十下,《突厥传》下,第6061页;《旧唐书》卷四《高宗传》第70页;《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下,5186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第6277页。
③《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④《旧唐书》卷一百零九(第3293页)《契苾何力传》云:“永徽二年,处月、处密叛,以何力为弓道大总管,讨平之,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
①松田寿男亦持类似主张,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97页。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③《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0页。
④《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传》下,第5187页。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第6245页。
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龟兹》,第5053页。《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八十五《外臣部·征讨第四》(第11406页)作“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
③《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第6264—6265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第6261页。
①《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53页,卷一百四十下《突厥传》下,第6061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第6274—6275页。
②《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传》上,第6113页。
③《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回纥传》,第5197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第6298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第6326页。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③《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传》上云:“(骨力裴罗)斥地俞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第6115页)
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第5198页。
⑤《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通鉴考异》引《安禄山事迹》,第6943页。
⑦《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①《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第329页。
②《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传》上,第6124—6125页;《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回纥传》,第5209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第7521页。
③《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回纥传》,第5209页。
①《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传》上,第5221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第6251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第7011页。
④《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传》上,第5236页。
⑤《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1—7652页。
①《文献通考》卷三百四十八《四夷考》,第272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4—6155页。
③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记载,有人在吐蕃赞普面前进谗言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第7652页。
④《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5页。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传》下,第6143页。
②《唐会要》卷一百《葛逻禄国》云:葛逻禄“地当东、西突厥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也”。《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1788页。
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第11520页。
④《新唐书》卷三十五《契苾何力传》,第4119页
⑤《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0页。
①《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309—325页、57—59页。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