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草原艺术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79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草原艺术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7 |
| 页码: | 250-256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伊犁历代文学艺术、草原艺术我们很难在草原文学和艺术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 |
| 关键词: | 伊犁 草原艺术 文学艺术 |
内容
我们很难在草原文学和艺术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是因为草原文学中的民歌、英雄史诗、叙事诗等实在属于歌者的范畴,都是靠演唱征服听众和流传下来的。但记录下来的书面形式——诗歌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故往往又划入文学范畴。关于草原民族的民歌、英雄史诗等已在《草原文学》一节中论及,在此不赘。在这一节中主要是论及被称为草原视觉艺术的岩画、石人、鹿石和民间工艺等。而现代人将岩画、石人、鹿石等视为造型艺术时,对史前先民来说,它们都是功能性的。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仅仅作为纯艺术看待,应看做是先民的心理、精神的产物,具有文化功能意义。如果离开这点,就与这些史前遗物制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伊犁、阿勒泰、塔城是新疆史前岩画、石人、鹿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在已发现的新疆150余处岩画中,伊、阿、塔三地区就占了80余处。这些岩画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是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也有少部分是有史时代的遗物。伊犁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伊宁县、巩留县、昭苏县、霍城县、特克斯县、新源县等地境内。阿尔泰山系岩画分布于阿勒泰市、青河县、富蕴县、布尔津县、福海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等地。塔城地区岩画分布于塔城市、裕民县、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岩画中,90%以上画面反映有洞角类、鹿科类、马科类等10多种动物形象。
从天山、阿尔泰山的这些岩画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野生动物,只有极少数如马、狗等为家养动物形象,而且出现的人形图像或与动物间有某种关联,或是象征人类生殖的组合图像。这表明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后期伴有少量畜牧业,即使在游牧社会,也不完全排除狩猎活动),人们最关注的是氏族人口的繁衍和猎取动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猎牧社会的文化也是一种狩猎文化,但是天灾人祸,很难保证人口的高存活率和每次都能猎获动物。在这样一个前科学时代,巫术思维的产生直接导致人们借助于运用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正如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所言:“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巫术的世界。开始,原始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力’。奇妙的‘力’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存在和石头的坚硬、水的湿润一样的确定无疑。这种‘力’仅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超自然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真实的和自然。”①人们在信奉神灵之前,是普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的。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②巫术思维导致的是巫术操作。岩画正是施法者实施巫术操作仪式的工具。这种巫术思维和巫术操作一直从旧石器时代起,经过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有史时代。西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都充满着这种巫术仪式。从已发现的天山、阿尔泰山岩画中不难得知,人与动物生殖“力”的传递形式有四种:一是感应式;二是接触式;三是相交式;四是距离交合式,都属于交感巫术范畴。已完成的岩画既可能是自足图像,又可能是非自足图像。
西域岩画中有一类在我国其他地方绝少有的洞窟彩绘岩画,它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其一是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乌孙山发现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岩画绘于阿克塔斯山高1850米处的岩洞内,洞高2.5~3米,洞口宽5米。岩画绘于洞口右面岩壁上,均用赭石绘制。画面由7只北山羊、2匹马和2组大小圆圈和一个“〉”形及“◎”形、“工”、“)”符号组成。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第一个岩洞在半山腰离地面25米处,洞窟高11.5米,宽20米,深11.8米。岩画绘于洞顶和正面、侧面岩壁上。画面由一组4个里外两层中间为圆圈的椭圆形图案和两个圆圈、手印以及被认为萨满帽、铜镜的图形组成,此外还有一组表意符号和所谓的人面像。唐巴勒塔斯2洞距离第一洞约60米,位于海拔1000米处,洞宽4.9米,高3.2米,深4米。画面由拿弓箭欲射的两人、脚印、两只野兽和叉腿、手臂平放或上举的4组人形图像组成。其三是阿勒泰市西北25公里处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洞窟在海拔1000米处,高1.31.5米,深浅不一,从1~4米左右。在二组50余道竖短杠组成的类似围栏内分别绘有一椭圆形图案和双腿叉开,高举双手的人形图像。此外还赭绘有牛、马、大角羊的图像。其四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乡的洞窟彩绘岩画,为两处,一处在杜阿特沟,另一处在松哈尔沟。杜阿特沟洞窟彩绘岩画又分5洞。第一洞海拔650米,洞高不过1米,宽也仅1.6米,赭石绘有牛和人物图像,人头部有“V”形饰物。第二洞在海拔605米处,洞高1~5米,宽1.7米,深1.3米。画面由一双手下垂、有尾饰的人物图像和牛形象以及一些表意符号组成,其中布满大而有规则的赭石圆形斑点。第三洞只绘有较粗的类似栅栏的竖道。第四洞是两个双腿叉开、双臂伸展的人物图像,有尾饰。第五洞仅有两只牛和一个人物图像。人像头部有两仰角物,尾饰特征显著。松哈尔沟洞窟彩绘岩画在一个高2.5米,宽8米,深4.5米的岩洞内的洞顶。在洞顶10余平方米的岩画上绘有人、动物和其他符号,实为一巨幅岩画。画面中心为一匹有赭石斑点的马,四周绘有羊、虎、牛等动物,人物图像形状与前述洞窟彩绘岩画相同,但与动物图像比较,人形都较小。此外,还绘有6个大手掌印,似栅栏的竖道,赭石实心圆以及虚线组成的不知名图形。从图像看,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多次使用的痕迹。伊犁、阿勒泰洞窟彩绘岩画完全可以根据狩猎文化中的典型动物祭祀仪式和与之有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来加以解释。①
在这些萨满岩画中保留了法力强大的萨满的最早形象。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为带角的拟人像,这一形象同样出现在杜阿特沟洞窟岩画中,而这些萨满形象无一例外都附有尾饰。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媒介者,他的任务就是沟通地上人类与天上神灵。早期的萨满本身就是巫师,装扮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角”。萨满在一种出神状态下,借助神灵的助佑者——鹿与神沟通。头上带角萨满岩画正是象征萨满的助佑神灵。羽毛状头饰、放射状头饰的功能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些人形身下的尾饰往往被误释为阳具,这是不了解早期萨满的装扮所致。从欧洲奥瑞纳文化时期史前岩画发现,岩画上的巫师(萨满)头上戴着鹿角,身上披着兽皮,臀部安有马毛,全身呈激烈跳动状,这就是原始萨满的典型形象。因此,洞窟岩画中萨满也应是头戴鹿角、披兽皮、安兽尾的形象。当然萨满也装扮成鸟的形象,羽毛状头饰即属此种。在阿勒泰洞窟岩画中还出现戴面具的萨满形象。对萨满的这种形象,朱狄先生解释为:“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做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西域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头戴兽冠、披着兽皮的萨满形象。在一个氏族里,萨满既是沟通人神者,也是保证氏族繁衍、狩猎成功的力的源泉。从这点看,萨满头戴象征神灵助佑者的鹿冠,身披兽皮正是在进行狩猎巫术仪式,它并不是出于单纯模仿的动机。萨满面具早期也是狩猎祭祀仪式的狩猎巫术面具。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神秘的“力”把物体的推动力转向另一物体。之后,面具成为萨满的固定道具,又附加了跳神(包括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供奉等多种功能。
石人和鹿石是草原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草原中段的伊犁、阿勒泰、塔城的草原地带也是石人、鹿石的集中分布地域。这些地区的石人最初产生于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6~9世纪达到兴盛期,衰落于11世纪左右。鹿石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以地域分类为伊犁石人、阿勒泰石人、塔城石人等;按族属分类为塞人石人、乌揭石人、突厥石人、铁勒石人、蒙古石人等,亦按设置情况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还可以按雕刻技法分类等。鹿石主要根据碑体形状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也有按族属、典型与否分类的。在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石人手持器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中古时期。手持器皿者分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右手持杯状物,另一种是双手抱罐、碗、瓶、钵之类器皿。其他还有手握刀、剑等兵器和手托鹰等形象。即使是手持杯的石人,其杯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如阿勒泰市境内阿克塔木墓地石人右臂屈至胸,手执一种角状杯;而温泉县境内阿尔卡特石人右臂屈,手执圆底罐形杯;内蒙古巴兰恩特利格突厥石人左手下垂,右手置于胸前执一筒状杯;吉尔吉斯草原发现石人右臂稍屈直,手托高足凸肚状杯,有的石人右臂屈,手执高脚杯。从青铜时代开始,右手执杯状物或双手抱罐、钵等器皿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对于这类墓地石人手持器皿的含义,学者们作过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认为是饮酒的酒杯;(2)神圣的器物;(3)丰产的象征物;(4)盛动物乳汁物的器皿。几种解释都无大错,问题是这些器皿是作为一般的饮器,还是另有它用?谁有资格使用这些器皿?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使用?这些答案还必须在萨满文化情境中寻解。手执器皿者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少这类形象往往在腰带上佩有条状装饰物,但它们既非刀剑之类,也非装物的皮袋,而是在垂条或垂绳上挂有垂饰。这在南西伯利亚、中国新疆、蒙古等地的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都十分常见。此外,石人与一些遗迹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有两种情况:一是石人竖立在祭祀石堆附近,石堆下面埋有牺牲的残余,有动物的骨骼、祭祀灰烬和各种器物,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6世纪的石人就属此类;二是南西伯利亚、中亚、内蒙古、新疆的确存在墓葬区的石人,齐木尔齐克石人墓的发掘证明墓地石人从青铜时代一直延至铁器时代。这些考古发现恰恰证明执器皿石人应是萨满形象,因为在后世萨满形象中的确能见到穿条状萨满服,腰带系垂绳挂铃、镜、挂饰、石球、动物骨关节等饰物的情景。萨满作法时这些物件叮当作响,目的是以响声传达人间与神界的信息,这些物件也是除邪镇魔的利器。结合遗迹关系分析,无论是祭祀堆石人还是墓葬区石人,均是萨满祭祀的形象,不管是祭祀祖先还是举行狩猎等仪式,都离不开萨满,他们总是这些仪式中的主角,不过祭祀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现在回到手持器皿的萨满形象上来。对于萨满来说,所用器皿是神圣的,同萨满神服、神帽、神具一同组成萨满的神物。阿契门尼德时期波斯的契形文字文献将塞人分为三大支:提格拉豪达塞克(尖帽塞克)、豪玛瓦尔格塞克(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和提艾伊·达拉伊雅塞克(近海塞克)。其中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极有可能是指其首领(也是萨满)是饮用豪麻汁的,即一种麻醉汁。据说萨满通神时必须处在一种迷狂、神志恍惚的“出神”状态,需要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因此,石人所持的也应是盛豪麻汁的器物。在充满萨满教信仰的氏族部落社会中,萨满最有资格持盛豪麻汁的器皿。在氏族、部落中萨满的神圣职能几乎囊括氏族、部落的所有活动,如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生产与生育、神判与记事等等。从近世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得知,萨满使用盛器见之于以下活动:一是治病时的喷术。起先治病时是喷气,后来是喷酒或水、药。在诸如得疮伤、骨折、长疖子、中风不语、口眼歪斜、错迷不醒等疾病时,往往用盛器盛水、酒或熬制的草药运气喷至病人身上,以达消炎、驱热之效。萨满常常在跳神治病仪式上向患者施之喷术,喷术功也成为萨满的内养功,平时要坚持练运内气、吹功。由此观之,立于祭台前的手执杯类器皿的石人应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上的施喷术的形象。二是与萨满教的神偶嗜血的灵魂观有关。“萨满教观念认为,血能育魂养魂,魂血相生互卫,所谓魂依血流,血行魂行,血凝魂止,则浮离体外,曰浮魂。魂依血养,魂凭血育,血旺魂壮,血热魄强,无敌天茬,鬼魔难当,曰养魂。神偶作为灵魂的依托体,其保持灵性和神性的奥秘在于常享祭物,尤以嗜血最益于养魂,使偶体内的灵魂常存。基于这种观念,萨满祭祀十分重视备牲、养牲、杀牲,无牲不祭成为萨满教不成文的规则。”①于是在萨满教祭祀仪式上,萨满常常是在神灵附体后,手持盛动物血的器皿喝血,也往往将器皿中的血弹或涂在祭祀的神偶身上。手持盛动物血器皿的石人也应是血祭诸如祖先、酋长、英雄等神偶的萨满形象。三是蒙古族的“行博”仪式也离不开容器。古代蒙古族凡进行渔猎、游牧、征战、治病、占卜、送葬、祈雨等仪式时都要请博(萨满)进行祈祷请神、附体求神、送神活动。在仪式中萨满常常在室外手持酒杯向诸神敬酒答谢,感谢神灵的庇佑。四是萨满为显通神的法力,常常要喝下圣水(可能是清水、酒或动物血等),目的是神灵会更显神力。在喝圣水时,萨满往往双手持碗等容器,以示虔诚。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对于索解手持盛器的草原石人之谜应是合乎情理的。
欧亚草原上的鹿石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此,仅探讨雕刻有鹿纹的典型鹿石。这些鹿石上的鹿形有如下特征:喙状头部前伸,嘴巴大张;两只枝状角仰向背部,一上一下(这说明与那种严整的动物侧影形不相符合);额部相应地有两处前突起;颈部和躯干前半部过长;前后腿相距甚近,一般都小而细得不合比例,有时仅有上半截,像被砍断一般。有时,当腿部全部雕刻出时,则呈弯曲状,前腿离于后腿,二者连接不严,中间留有空隙。蒙古——外贝加尔和中国新疆发现的鹿石都属此类带有图案化的鹿纹样的类型。雕刻这些鹿形图案的鹿石是一些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的石柱或石板。不过晚期的鹿石并非通体都是鹿的图案,而是雕刻成人形,这类鹿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鹿石是做什么用的?鹿形图案有象征意义吗?这不能不与欧亚草原民族的早期萨满教信仰联系起来考虑。在萨满教世界观中,高山、大树都是作为萨满通神的宇宙山、世界树出现的,而方柱体、圆柱体的鹿石也应是萨满通天通神的工具。萨满是一个送魂者,保证祖先或英雄的灵魂升天而不是人地狱的方式是在祭祀仪式中以巫术操作手段通过刻凿鹿石中的图像达到其目的。研究者认为,在萨满教中往往出现萨满庇护神:“每个萨满,肯定都有一个动物母亲或动物祖先。它通常被描绘成大角鹿,有时也是一头熊。这个动物自己生活,不与萨满在一起。大概,最好是把它设想成在大地上飞翔的,萨满那火一样的力量”①。不过从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材料发现,庇护和培育萨满的精灵常常是鹿、鹰、蛇等,其中鹿和鹰是萨满庇护神最具代表性和最权威的形象。鹿石上刻凿的鹰喙鹿身图案正是萨满庇护神的形象,天上飞翔的鹰与地上奔驰最快的鹿的组合已经成为普遍的萨满职业象征。特别是那些有人头形和鸟喙鹿身的鹿石是萨满正在实施巫术时的产物,刻凿过程也是巫术操作的过程。这是后代萨满通过这种巫术操作与前代萨满(祖先)的灵魂沟通。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鹿、鹰等萨满的庇护神或者是亡故的前代萨满,或者无异于萨满的配偶,抑或还是晚辈萨满的庇护者。因为萨满的灵魂均是由这些动物庇护神作为向导和保护者前往上界的。难怪有些鹿石上部刻凿有象征天界的圆圈、圆点和半月形纹饰,它们与人头形、鹰喙鹿身组成萨满灵魂升天的全景式图像。不过,鹿石雕凿展现的是萨满通神时巫术操作时的文化情境,而萨满服的缀饰变成了凝固的符号象征物,但它们在萨满教信仰中同样是神圣的。
在草原艺术造型中,动物纹样占有特殊地位。塞人、匈奴、大月氏、乌揭等早期部族的动物纹样来自于猎牧活动中的动物。常见的凶兽猛禽,如狮、虎、熊、鹰、狼、鹿、豺、野猪等,也有驯养的马、牛、羊、狗等形象。特别是一些野兽形象,多为啮咬、争斗状,形体往往扭曲变形。无论是塞人风格的动物纹样还是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绝对不是出于审美需求的艺术装饰,而具有功能意义。这些部族把动物形象装饰在牌、扣、钩、徽章、矛、剑、马具、带等须臾不离身的物件上是视其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塞人的狮神、吐火罗人的双马神(即龙神)、车师人的虎神、匈奴人的神兽、鲜卑人的瑞兽、蒙古人的“白海青”等,或来源于早期氏族图腾,或衍化成部落保护神。鲜卑人的带钩——犀比为瑞兽,即神兽,实际上鲜卑就是以“瑞兽”相称的部落。草原民族的这类动物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早期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以后在普遍存在的萨满教信仰中被信奉为部落保护神了。即使这样,功能性的动物纹样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草原民族个性和心灵世界的基本表现方式。
所谓草原民间工艺艺术是在传承中积淀凝聚民间智慧,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定型,富有民族普遍性并产生于日常生活能够真实反映草原民族心灵世界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弥漫于日常生活有普泛性。游牧民族的毡房、马具、服饰、毡毯都富有装饰性,特别是讲究以自然界的花草、动物角等抽象变形对称装饰,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搭配色彩。这种色彩搭配往往反差强烈,色泽艳丽。装饰用具、美化生活几乎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存在没有装饰的生活,也不存在离开生活的装饰。如果细细列举,诸如手帕、荷包、头巾、枕头、腰巾、围裙、毡帽、毛袜、领口、袖头、衣襟、裤角、被面、垫褥、罩单、帷帘、壁挂、壁围、花毡、织毯、草帘、编带、马褥、披肩等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恰到好处的纹样和色彩加以装饰美化。一些几何及植物纹样装饰图案的出现不能单纯归于某些游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后反对偶像崇拜所致。其实,这类装饰性图案起源很早,不亚于动物纹样。在塞人金银器中,匈奴织物中除动物纹样主题外,同样有花纹、三角形、圆形等装饰性图案,似乎都不是写实风格的。
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其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对象关系及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都直接联系着他们的文化艺术。他们在马背上吟唱着牧歌和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喜庆场合高唱婚礼歌、祝酒歌,并以歌舞相娱;他们的腰带上佩挂有镶嵌对兽猛禽图案的牌饰、带扣、短剑;他们在所迁徙之地雕琢了无数幅岩画;他们还在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座石人像、鹿石;他们还在毡毯上、服饰上飞针走线,留下了流光溢彩的精美图案..他们的艺术无处无时不在,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圆形毡房也富有艺术韵味。
伊犁、阿勒泰、塔城是新疆史前岩画、石人、鹿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在已发现的新疆150余处岩画中,伊、阿、塔三地区就占了80余处。这些岩画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是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也有少部分是有史时代的遗物。伊犁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伊宁县、巩留县、昭苏县、霍城县、特克斯县、新源县等地境内。阿尔泰山系岩画分布于阿勒泰市、青河县、富蕴县、布尔津县、福海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等地。塔城地区岩画分布于塔城市、裕民县、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岩画中,90%以上画面反映有洞角类、鹿科类、马科类等10多种动物形象。
从天山、阿尔泰山的这些岩画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野生动物,只有极少数如马、狗等为家养动物形象,而且出现的人形图像或与动物间有某种关联,或是象征人类生殖的组合图像。这表明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后期伴有少量畜牧业,即使在游牧社会,也不完全排除狩猎活动),人们最关注的是氏族人口的繁衍和猎取动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猎牧社会的文化也是一种狩猎文化,但是天灾人祸,很难保证人口的高存活率和每次都能猎获动物。在这样一个前科学时代,巫术思维的产生直接导致人们借助于运用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正如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所言:“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巫术的世界。开始,原始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力’。奇妙的‘力’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存在和石头的坚硬、水的湿润一样的确定无疑。这种‘力’仅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超自然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真实的和自然。”①人们在信奉神灵之前,是普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的。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②巫术思维导致的是巫术操作。岩画正是施法者实施巫术操作仪式的工具。这种巫术思维和巫术操作一直从旧石器时代起,经过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有史时代。西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都充满着这种巫术仪式。从已发现的天山、阿尔泰山岩画中不难得知,人与动物生殖“力”的传递形式有四种:一是感应式;二是接触式;三是相交式;四是距离交合式,都属于交感巫术范畴。已完成的岩画既可能是自足图像,又可能是非自足图像。
西域岩画中有一类在我国其他地方绝少有的洞窟彩绘岩画,它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其一是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乌孙山发现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岩画绘于阿克塔斯山高1850米处的岩洞内,洞高2.5~3米,洞口宽5米。岩画绘于洞口右面岩壁上,均用赭石绘制。画面由7只北山羊、2匹马和2组大小圆圈和一个“〉”形及“◎”形、“工”、“)”符号组成。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第一个岩洞在半山腰离地面25米处,洞窟高11.5米,宽20米,深11.8米。岩画绘于洞顶和正面、侧面岩壁上。画面由一组4个里外两层中间为圆圈的椭圆形图案和两个圆圈、手印以及被认为萨满帽、铜镜的图形组成,此外还有一组表意符号和所谓的人面像。唐巴勒塔斯2洞距离第一洞约60米,位于海拔1000米处,洞宽4.9米,高3.2米,深4米。画面由拿弓箭欲射的两人、脚印、两只野兽和叉腿、手臂平放或上举的4组人形图像组成。其三是阿勒泰市西北25公里处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洞窟在海拔1000米处,高1.31.5米,深浅不一,从1~4米左右。在二组50余道竖短杠组成的类似围栏内分别绘有一椭圆形图案和双腿叉开,高举双手的人形图像。此外还赭绘有牛、马、大角羊的图像。其四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乡的洞窟彩绘岩画,为两处,一处在杜阿特沟,另一处在松哈尔沟。杜阿特沟洞窟彩绘岩画又分5洞。第一洞海拔650米,洞高不过1米,宽也仅1.6米,赭石绘有牛和人物图像,人头部有“V”形饰物。第二洞在海拔605米处,洞高1~5米,宽1.7米,深1.3米。画面由一双手下垂、有尾饰的人物图像和牛形象以及一些表意符号组成,其中布满大而有规则的赭石圆形斑点。第三洞只绘有较粗的类似栅栏的竖道。第四洞是两个双腿叉开、双臂伸展的人物图像,有尾饰。第五洞仅有两只牛和一个人物图像。人像头部有两仰角物,尾饰特征显著。松哈尔沟洞窟彩绘岩画在一个高2.5米,宽8米,深4.5米的岩洞内的洞顶。在洞顶10余平方米的岩画上绘有人、动物和其他符号,实为一巨幅岩画。画面中心为一匹有赭石斑点的马,四周绘有羊、虎、牛等动物,人物图像形状与前述洞窟彩绘岩画相同,但与动物图像比较,人形都较小。此外,还绘有6个大手掌印,似栅栏的竖道,赭石实心圆以及虚线组成的不知名图形。从图像看,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多次使用的痕迹。伊犁、阿勒泰洞窟彩绘岩画完全可以根据狩猎文化中的典型动物祭祀仪式和与之有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来加以解释。①
在这些萨满岩画中保留了法力强大的萨满的最早形象。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为带角的拟人像,这一形象同样出现在杜阿特沟洞窟岩画中,而这些萨满形象无一例外都附有尾饰。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媒介者,他的任务就是沟通地上人类与天上神灵。早期的萨满本身就是巫师,装扮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角”。萨满在一种出神状态下,借助神灵的助佑者——鹿与神沟通。头上带角萨满岩画正是象征萨满的助佑神灵。羽毛状头饰、放射状头饰的功能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些人形身下的尾饰往往被误释为阳具,这是不了解早期萨满的装扮所致。从欧洲奥瑞纳文化时期史前岩画发现,岩画上的巫师(萨满)头上戴着鹿角,身上披着兽皮,臀部安有马毛,全身呈激烈跳动状,这就是原始萨满的典型形象。因此,洞窟岩画中萨满也应是头戴鹿角、披兽皮、安兽尾的形象。当然萨满也装扮成鸟的形象,羽毛状头饰即属此种。在阿勒泰洞窟岩画中还出现戴面具的萨满形象。对萨满的这种形象,朱狄先生解释为:“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做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西域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头戴兽冠、披着兽皮的萨满形象。在一个氏族里,萨满既是沟通人神者,也是保证氏族繁衍、狩猎成功的力的源泉。从这点看,萨满头戴象征神灵助佑者的鹿冠,身披兽皮正是在进行狩猎巫术仪式,它并不是出于单纯模仿的动机。萨满面具早期也是狩猎祭祀仪式的狩猎巫术面具。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神秘的“力”把物体的推动力转向另一物体。之后,面具成为萨满的固定道具,又附加了跳神(包括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供奉等多种功能。
石人和鹿石是草原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草原中段的伊犁、阿勒泰、塔城的草原地带也是石人、鹿石的集中分布地域。这些地区的石人最初产生于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6~9世纪达到兴盛期,衰落于11世纪左右。鹿石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以地域分类为伊犁石人、阿勒泰石人、塔城石人等;按族属分类为塞人石人、乌揭石人、突厥石人、铁勒石人、蒙古石人等,亦按设置情况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还可以按雕刻技法分类等。鹿石主要根据碑体形状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也有按族属、典型与否分类的。在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石人手持器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中古时期。手持器皿者分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右手持杯状物,另一种是双手抱罐、碗、瓶、钵之类器皿。其他还有手握刀、剑等兵器和手托鹰等形象。即使是手持杯的石人,其杯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如阿勒泰市境内阿克塔木墓地石人右臂屈至胸,手执一种角状杯;而温泉县境内阿尔卡特石人右臂屈,手执圆底罐形杯;内蒙古巴兰恩特利格突厥石人左手下垂,右手置于胸前执一筒状杯;吉尔吉斯草原发现石人右臂稍屈直,手托高足凸肚状杯,有的石人右臂屈,手执高脚杯。从青铜时代开始,右手执杯状物或双手抱罐、钵等器皿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对于这类墓地石人手持器皿的含义,学者们作过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认为是饮酒的酒杯;(2)神圣的器物;(3)丰产的象征物;(4)盛动物乳汁物的器皿。几种解释都无大错,问题是这些器皿是作为一般的饮器,还是另有它用?谁有资格使用这些器皿?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使用?这些答案还必须在萨满文化情境中寻解。手执器皿者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少这类形象往往在腰带上佩有条状装饰物,但它们既非刀剑之类,也非装物的皮袋,而是在垂条或垂绳上挂有垂饰。这在南西伯利亚、中国新疆、蒙古等地的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都十分常见。此外,石人与一些遗迹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有两种情况:一是石人竖立在祭祀石堆附近,石堆下面埋有牺牲的残余,有动物的骨骼、祭祀灰烬和各种器物,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6世纪的石人就属此类;二是南西伯利亚、中亚、内蒙古、新疆的确存在墓葬区的石人,齐木尔齐克石人墓的发掘证明墓地石人从青铜时代一直延至铁器时代。这些考古发现恰恰证明执器皿石人应是萨满形象,因为在后世萨满形象中的确能见到穿条状萨满服,腰带系垂绳挂铃、镜、挂饰、石球、动物骨关节等饰物的情景。萨满作法时这些物件叮当作响,目的是以响声传达人间与神界的信息,这些物件也是除邪镇魔的利器。结合遗迹关系分析,无论是祭祀堆石人还是墓葬区石人,均是萨满祭祀的形象,不管是祭祀祖先还是举行狩猎等仪式,都离不开萨满,他们总是这些仪式中的主角,不过祭祀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现在回到手持器皿的萨满形象上来。对于萨满来说,所用器皿是神圣的,同萨满神服、神帽、神具一同组成萨满的神物。阿契门尼德时期波斯的契形文字文献将塞人分为三大支:提格拉豪达塞克(尖帽塞克)、豪玛瓦尔格塞克(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和提艾伊·达拉伊雅塞克(近海塞克)。其中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极有可能是指其首领(也是萨满)是饮用豪麻汁的,即一种麻醉汁。据说萨满通神时必须处在一种迷狂、神志恍惚的“出神”状态,需要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因此,石人所持的也应是盛豪麻汁的器物。在充满萨满教信仰的氏族部落社会中,萨满最有资格持盛豪麻汁的器皿。在氏族、部落中萨满的神圣职能几乎囊括氏族、部落的所有活动,如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生产与生育、神判与记事等等。从近世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得知,萨满使用盛器见之于以下活动:一是治病时的喷术。起先治病时是喷气,后来是喷酒或水、药。在诸如得疮伤、骨折、长疖子、中风不语、口眼歪斜、错迷不醒等疾病时,往往用盛器盛水、酒或熬制的草药运气喷至病人身上,以达消炎、驱热之效。萨满常常在跳神治病仪式上向患者施之喷术,喷术功也成为萨满的内养功,平时要坚持练运内气、吹功。由此观之,立于祭台前的手执杯类器皿的石人应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上的施喷术的形象。二是与萨满教的神偶嗜血的灵魂观有关。“萨满教观念认为,血能育魂养魂,魂血相生互卫,所谓魂依血流,血行魂行,血凝魂止,则浮离体外,曰浮魂。魂依血养,魂凭血育,血旺魂壮,血热魄强,无敌天茬,鬼魔难当,曰养魂。神偶作为灵魂的依托体,其保持灵性和神性的奥秘在于常享祭物,尤以嗜血最益于养魂,使偶体内的灵魂常存。基于这种观念,萨满祭祀十分重视备牲、养牲、杀牲,无牲不祭成为萨满教不成文的规则。”①于是在萨满教祭祀仪式上,萨满常常是在神灵附体后,手持盛动物血的器皿喝血,也往往将器皿中的血弹或涂在祭祀的神偶身上。手持盛动物血器皿的石人也应是血祭诸如祖先、酋长、英雄等神偶的萨满形象。三是蒙古族的“行博”仪式也离不开容器。古代蒙古族凡进行渔猎、游牧、征战、治病、占卜、送葬、祈雨等仪式时都要请博(萨满)进行祈祷请神、附体求神、送神活动。在仪式中萨满常常在室外手持酒杯向诸神敬酒答谢,感谢神灵的庇佑。四是萨满为显通神的法力,常常要喝下圣水(可能是清水、酒或动物血等),目的是神灵会更显神力。在喝圣水时,萨满往往双手持碗等容器,以示虔诚。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对于索解手持盛器的草原石人之谜应是合乎情理的。
欧亚草原上的鹿石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此,仅探讨雕刻有鹿纹的典型鹿石。这些鹿石上的鹿形有如下特征:喙状头部前伸,嘴巴大张;两只枝状角仰向背部,一上一下(这说明与那种严整的动物侧影形不相符合);额部相应地有两处前突起;颈部和躯干前半部过长;前后腿相距甚近,一般都小而细得不合比例,有时仅有上半截,像被砍断一般。有时,当腿部全部雕刻出时,则呈弯曲状,前腿离于后腿,二者连接不严,中间留有空隙。蒙古——外贝加尔和中国新疆发现的鹿石都属此类带有图案化的鹿纹样的类型。雕刻这些鹿形图案的鹿石是一些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的石柱或石板。不过晚期的鹿石并非通体都是鹿的图案,而是雕刻成人形,这类鹿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鹿石是做什么用的?鹿形图案有象征意义吗?这不能不与欧亚草原民族的早期萨满教信仰联系起来考虑。在萨满教世界观中,高山、大树都是作为萨满通神的宇宙山、世界树出现的,而方柱体、圆柱体的鹿石也应是萨满通天通神的工具。萨满是一个送魂者,保证祖先或英雄的灵魂升天而不是人地狱的方式是在祭祀仪式中以巫术操作手段通过刻凿鹿石中的图像达到其目的。研究者认为,在萨满教中往往出现萨满庇护神:“每个萨满,肯定都有一个动物母亲或动物祖先。它通常被描绘成大角鹿,有时也是一头熊。这个动物自己生活,不与萨满在一起。大概,最好是把它设想成在大地上飞翔的,萨满那火一样的力量”①。不过从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材料发现,庇护和培育萨满的精灵常常是鹿、鹰、蛇等,其中鹿和鹰是萨满庇护神最具代表性和最权威的形象。鹿石上刻凿的鹰喙鹿身图案正是萨满庇护神的形象,天上飞翔的鹰与地上奔驰最快的鹿的组合已经成为普遍的萨满职业象征。特别是那些有人头形和鸟喙鹿身的鹿石是萨满正在实施巫术时的产物,刻凿过程也是巫术操作的过程。这是后代萨满通过这种巫术操作与前代萨满(祖先)的灵魂沟通。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鹿、鹰等萨满的庇护神或者是亡故的前代萨满,或者无异于萨满的配偶,抑或还是晚辈萨满的庇护者。因为萨满的灵魂均是由这些动物庇护神作为向导和保护者前往上界的。难怪有些鹿石上部刻凿有象征天界的圆圈、圆点和半月形纹饰,它们与人头形、鹰喙鹿身组成萨满灵魂升天的全景式图像。不过,鹿石雕凿展现的是萨满通神时巫术操作时的文化情境,而萨满服的缀饰变成了凝固的符号象征物,但它们在萨满教信仰中同样是神圣的。
在草原艺术造型中,动物纹样占有特殊地位。塞人、匈奴、大月氏、乌揭等早期部族的动物纹样来自于猎牧活动中的动物。常见的凶兽猛禽,如狮、虎、熊、鹰、狼、鹿、豺、野猪等,也有驯养的马、牛、羊、狗等形象。特别是一些野兽形象,多为啮咬、争斗状,形体往往扭曲变形。无论是塞人风格的动物纹样还是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绝对不是出于审美需求的艺术装饰,而具有功能意义。这些部族把动物形象装饰在牌、扣、钩、徽章、矛、剑、马具、带等须臾不离身的物件上是视其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塞人的狮神、吐火罗人的双马神(即龙神)、车师人的虎神、匈奴人的神兽、鲜卑人的瑞兽、蒙古人的“白海青”等,或来源于早期氏族图腾,或衍化成部落保护神。鲜卑人的带钩——犀比为瑞兽,即神兽,实际上鲜卑就是以“瑞兽”相称的部落。草原民族的这类动物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早期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以后在普遍存在的萨满教信仰中被信奉为部落保护神了。即使这样,功能性的动物纹样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草原民族个性和心灵世界的基本表现方式。
所谓草原民间工艺艺术是在传承中积淀凝聚民间智慧,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定型,富有民族普遍性并产生于日常生活能够真实反映草原民族心灵世界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弥漫于日常生活有普泛性。游牧民族的毡房、马具、服饰、毡毯都富有装饰性,特别是讲究以自然界的花草、动物角等抽象变形对称装饰,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搭配色彩。这种色彩搭配往往反差强烈,色泽艳丽。装饰用具、美化生活几乎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存在没有装饰的生活,也不存在离开生活的装饰。如果细细列举,诸如手帕、荷包、头巾、枕头、腰巾、围裙、毡帽、毛袜、领口、袖头、衣襟、裤角、被面、垫褥、罩单、帷帘、壁挂、壁围、花毡、织毯、草帘、编带、马褥、披肩等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恰到好处的纹样和色彩加以装饰美化。一些几何及植物纹样装饰图案的出现不能单纯归于某些游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后反对偶像崇拜所致。其实,这类装饰性图案起源很早,不亚于动物纹样。在塞人金银器中,匈奴织物中除动物纹样主题外,同样有花纹、三角形、圆形等装饰性图案,似乎都不是写实风格的。
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其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对象关系及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都直接联系着他们的文化艺术。他们在马背上吟唱着牧歌和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喜庆场合高唱婚礼歌、祝酒歌,并以歌舞相娱;他们的腰带上佩挂有镶嵌对兽猛禽图案的牌饰、带扣、短剑;他们在所迁徙之地雕琢了无数幅岩画;他们还在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座石人像、鹿石;他们还在毡毯上、服饰上飞针走线,留下了流光溢彩的精美图案..他们的艺术无处无时不在,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圆形毡房也富有艺术韵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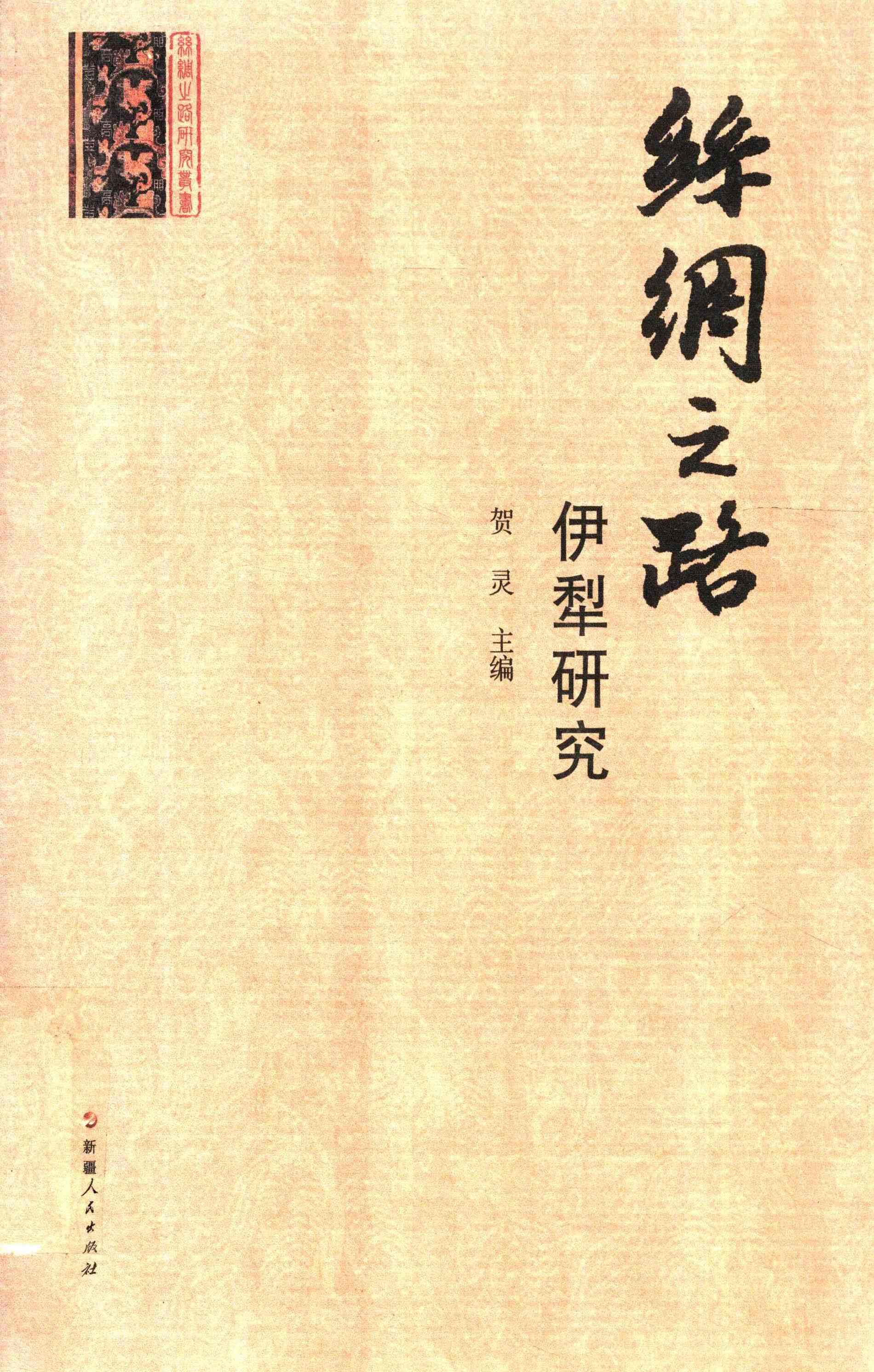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