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草原文学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77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草原文学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7 |
| 页码: | 238-244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伊犁历代文学艺术吟咏歌唱近乎草原游牧民族的天性,于是产生了与他们生产生活及其习俗密切相关的草原民歌和传说故事。 |
| 关键词: | 伊犁 草原文学 文学艺术 |
内容
吟咏歌唱近乎草原游牧民族的天性,于是产生了与他们生产生活及其习俗密切相关的草原民歌和传说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形式是构成草原文学的主流文学,特别是在早期更是这样,而书面文学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关于活动在伊犁、阿勒泰等草原地带早期民族的口头文学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这些充满草原气息的民间文学也随着这些民族的消亡而消失了。活动于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中的塞人、匈奴、呼揭、月氏、乌孙、铁勒等部族肯定都是富有口头文学传统的草原民族,如果不是汉文典籍偶有记载,人们对他们的民歌几乎一无所知。汉文文献存留了一首《匈奴歌》和另一首《敕勒歌》,前者是匈奴人痛失草原的绝唱:“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一泣一唱,一哭一回头,是多么的痛心疾首。后者被认为是铁勒(即敕勒)人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抒情味极浓的民歌,正如《诗薮》所言:“此歌成于信口,咸谓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无意发之,所以浑朴苍茫,使当时文士为之,便欲雕绘满眼。”天然无雕饰的民歌总是以清新、淳朴的秉性博得人们的青睐,远非文人创作能比。早期草原民族的吟唱中除淳朴、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外,还有一种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密不可分的萨满歌,即祷告歌。它是萨满在举行周期和非周期性祈祷仪式时的吟唱,属咒语一类的韵文。在献祭仪式、治病仪式、征战仪式中吟唱祝文是萨满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草原早期民族的战歌、情歌、摇篮曲、哀歌、婚礼颂歌等,在最初都是具有巫术、宗教的意义,带有咒语的性质。越是在早期,萨满在氏族部落中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萨满的祷告歌也无处无时不在,成为神圣的祈福禳灾的吟唱。
在草原文学中,古代突厥人和成吉思汗西征前操突厥语诸部落的民歌独树一帜,对后期草原诸民族的民歌也曾产生广泛影响。自6世纪80年代西突厥统辖阿勒泰以西广大地区后,突厥文化成了阿勒泰至伊犁草原地带最主要的草原游牧文化,而自9~13世纪则有诸如葛逻禄、炽俟、踏实力、样磨、乌古斯等操突厥语部落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突厥语大词典》中对各操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进行了介绍,并辑录了这些部落的民歌作为例证。这些民歌中很可能包括西突厥人的民歌,因为9世纪后的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不少就是从东西突厥汗国中分化出来的游牧部落。从大词典所记“伊犁”、“额尔齐斯”等地名、河名看,他们都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他们的民歌多与草原景物、狩猎活动以及生产生活习俗有关。一些狩猎民歌可能是古代突厥人的早期民歌,因为绝大部分草原游牧民族早期均是狩猎民族,而演进到游牧民族后,狩猎仍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大词典所录一首狩猎民歌为:
擎兔鹰,
跨骏马,
追逐盘羊,
放猎犬,
捕狐狸,
猎取黄羊。
活脱脱一幅紧张激烈的草原狩猎图。更有些狩猎民歌擅长描写猎犬捕狼时的打斗场面:
我的狗把它扑翻在地,
狠劲地撕咬它的毛皮。
把它的脑袋按在地上,
用利爪扼住了它的脖子。
这种描写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动感。也有些狩猎民歌是展示年轻猎手本领的:
带兔鹰去狩猎,纵猎犬去撕咬;
用石击狐狸野猪,
我们以本领自豪。
用石击都能捕获猎物,可见身手不凡。草原游牧民族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马,马是他们的坐骑,用于放牧、狩猎、迁徙,于是出现了大量以马为题材的民歌。有一首民歌是以驯马为题材的:
跨上烈马任它跳,
把那烈性驯服了;
让狗去追回猎物,
我们希望它猎到。
寥寥数语交代清楚驯马过程后,又叙写驯马与狩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在长期以马为伴的生活中,还积累了识马、相马的丰富经验,特别对疾驰如飞的骏马钟爱有加:“骏马在疾驰飞奔,马蹄下贱出火星;火星点燃了枯草,火焰在熊熊燃烧”。略嫌夸张的手法让人们领略到骏马如飞的身姿。同样,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十分熟悉所饲养的各种羊的习性,特别是公羊和母羊的分群、母羊和羊羔合群是能否挤奶的标志:“公羊公山羊分开了,母羊群会集起来了,乳汁统统地流出了,羊羔山羊羔合群了”。一般在夏季母羊与公羊分群,母羊合群后挤奶季节就开始了;而母羊和羊羔合群,由于哺乳羊羔,就不再挤奶了。他们经过严冬后对万物复苏的春天充满了喜悦:“山头被绿色笼罩,遮盖了隔年干草;湖泊盈溢着春天,公母牛哞哞欢叫。”这首民歌是春天的赞歌,满目葱绿,牲畜繁衍,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赏心悦目呢?①
应该说,蒙古人活动于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的历史并不短,从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起,到卫拉特蒙古四部,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了。但蒙元时期生活在阿力麻里一带蒙古人的民间文学状况怎样,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像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蒙古人对阿力麻里的征服,但不见有这一地区蒙古族民歌的只言片语记载。生于波斯的志费尼倒是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蒙古人征服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时的诗歌。这些诗歌多是对成吉思汗及诸子西征战绩的歌颂和征战场面的描写,但已非民歌范畴,而是被征服地的文人创作了。蒙古人的文学传统——包括民歌、英雄史诗、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文学形式经数百年的口头传承,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蒙古族民歌中最被称道的是长调民歌,这些长调常常是高低音同度一致的,但当两个或更多的蒙古人一起唱时,往往有出色的歌手唱出延长音,延长到他的肺活量的最大限度,然后由他继续把它唱下去,好似是其他歌手的回音一般,从而使这首抒情曲与复调多重唱相似。蒙古族民歌中还有一种短调,因风趣幽默、节奏明快、曲调活泼,又称其为诙谐歌曲。像土尔扈特蒙古的《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就是歌手即兴演唱的抒情长调,歌手反复用本嗓和假声演唱,歌词是歌手即兴吟成的,是对繁茂的伊犁河谷秋天的回忆。长调显然属于牧歌一类。察哈尔蒙古的《高山上的花》、《金纽扣》、《想念我的家乡》都属短调民歌。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民歌除牧歌外,还有赞歌、酒歌、情歌、婚礼歌等多种形式,如《西部可汗》、《可爱的暗褐色小马》、《我可爱的小雄鹿》、《额林哈毕尔噶山》等。由于马在卫拉特蒙古人生产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它也成了情歌重要描述的对象。对马的情景描写实际上是暗指情人,如《花色马》:“骑上我的花色马,一溜烟尘过大山。亲爱的哥哥讲的话,时刻铭记我心间”。还有《心爱的枣骝马》描写道:“乘上心爱的坐骑枣骝马,在无垠的草原上飞速驰骋。我热恋的心上人哟,喁喁的情话镌刻在我心中。”这种看似雷同的思路,往往是随手拈来,即兴吟唱,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都明了其意并不在马,而在于情。因感受、理解不同,同是对马的情景描写,各自成趣,毫不乏味。但是,在卫拉特蒙古人看来,骏马往往是和英雄相匹配的,于是有了那首歌唱土尔扈特人的英雄罗布桑察纳布及其骏马的民歌:
在白雪覆盖的高山之顶,
屹立着一所帐篷。
它白如白雪皑皑的山峰,
罗布桑察纳布在门口凝视着南方的地平线。
他的白色种马飞奔得比箭还快,
他骑上它追上了野鹿。
鹰靠强健的翅膀追捕野天鹅,
而罗布桑察纳布的敏捷胜过最强壮的鹰。
很多人都羡慕罗布桑察纳布,
但他们在战斗中才知道最伟大的要数黑色的鹰罗布桑察纳布。①
它在卫拉特蒙古诗歌中英雄史诗占有独特地位,《江格尔》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讲述的是蒙古族英雄江格尔及其十二“雄狮”、三十“虎将”、八千勇士与恶魔蟒古斯斗争的故事。《江格尔》由世代江格尔齐演唱、加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江格尔》属长篇巨制型英雄史诗,现在见到的是搜集整理出版的十五章托忒蒙古文本,还有十三章等汉译本。其实,民间流传的《江格尔》远比这长得多。据一些蒙古族老艺人回忆,有一种七十回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据蒙古族学者色道尔吉研究认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是土尔扈特人民集体的口头创作,是他们智慧和感情的生动反映,到明代,成了四卫拉特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后来通过江格尔齐的演唱和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国内外蒙古族人民聚居地区。《江格尔》歌颂的是蒙古人的理想乐园——宝木巴以及以江格尔为代表的宝木巴众多勇士,并揭露了奴隶制社会现实的丑恶。富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江格尔等人也成了反抗邪恶、铲除社会不公、创建和保卫宝木巴的象征,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推崇的英雄。《江格尔》在世代流传中也融进了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是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江格尔》中多处出现阿尔泰山、白头山、额什尔鄂拉山、额尔齐斯河、乌古伦河、奎屯河等山名、河名,这与卫拉特蒙古四部活动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毕竟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卫拉特蒙古在长期游牧生活中,或出于启迪教化的动机,或作为闲暇生活消遣的方式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和寓言故事、降妖伏魔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生活故事、讽刺幽默故事等。卫拉特蒙古的动物和寓言故事有解释动物外貌、习性特征的解释性故事,也有哲理性的有教化功能的寓言故事,还有图腾性的动物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征是:说是讲动物,实际在讲人;说是讲人,又明明是讲动物。基本上都属于以动物喻人,以动物事寓人事的故事。如《狐狸和熊》、《骆驼为啥在灰土上打滚》、《骑大红马的阿勒泰台吉》、《白雪和兔子》、《粮食全留给了青蛙和蜘蛛》等都属于以上三类动物故事。降妖伏魔故事大多是讲述民间流传的蒙古族的英雄故事,这些英雄都有降妖伏魔的神勇、神力,是百姓仰慕的对象。如《红脸勇士乌兰·哈茨尔》、《聪明的苏布松·都日勒格可汗》、《英雄布赫蒙贡·希克萨尔》等。还有些虽非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一些无助的孤儿、美貌的姑娘、年轻小伙、年长的老人等,但都是一些伸张正义、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人物,也成了这类故事的主人公。一些神话传说故事虽然都是幻想、想象的产物,但在这些神话世界中也有现世的影子,如用神话解释宇宙和各种自然现象起源,解释本民族始祖起源,解释诸如本民族风俗、伦理、器用、技术等的起源。《神女的恩惠》就是杜尔伯特蒙古人始祖的神话故事。讲述一个青年猎手和天女幽会生下一男孩,这位男孩长大后成了一名真正的勇士,也成了杜尔伯特人的祖先。这自然也是蒙古人天神崇拜观的反映,他们笃信,自己的祖先就是天上神女的后代。在卫拉特蒙古四部中更多的是世俗的生活故事和讽刺幽默故事。放牛娃、流浪女、放羊娃等都是一些善良、聪慧机智的人物,而章京、王爷、吝啬鬼、懒汉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讽刺、揄揶的对象。《聪慧的放牛娃》就是广泛流传于卫拉特蒙古四部的古老生活故事,是一系列单篇故事构成的组合故事。《阿尔格齐的故事》是机智人物故事,由《出丑》、《乞肉》、《懒汉》、《吹牛》、《戍马》等数十个系列故事组成,讽刺辛辣,妙语如珠,有极强的警策作用。①
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歌是哈萨克人的翅膀”,他们视民歌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实际上,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民歌,还有英雄叙事诗、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等,构成庞大的民间文学系统。哈萨克族的民歌大都可以列入习俗歌的范畴,可以这样说,是他们的习俗催生了这些民歌,这些民歌中也孕育了一定的习俗。这些习俗歌包括婚嫁歌、丧葬歌、日常生活歌、节日习俗歌、宗教习俗歌等。以哈萨克族的婚嫁歌为例,它分为“喜事序歌”、“萨仁”、“加尔—加尔”、“哭嫁歌”、“远嫁歌”、“劝嫁歌”、“揭面歌”等,是整个婚嫁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哈萨克族的婚礼是从提亲开始的,伴有订婚仪式、嫁娶仪式等。在整个过程中,婚嫁歌存在于自始至终,新娘用歌向亲人告别,亲人用歌劝嫁,男方用歌迎娶新娘,来宾歌唱助兴等。嫁女仪式中的“萨仁”歌原并非单指唱给新娘的歌,其他一些古老的有哲理性、劝喻性的古老民歌也称为“萨仁”。由于“萨仁”歌在嫁女仪式开始当天由男方的两位伴郎齐唱,唱给新娘听,往往唱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有“晓之以理”的意味,因此“萨仁”也就成了具有劝嫁内容的嫁女仪式歌。而“加尔—加尔”是男方劝嫁、女方哭嫁的对唱,往往是男方曲调欢快、轻松,而女方凄楚、悲凉。婚嫁歌透露的是婚嫁习俗原型的信息,通过演唱形式凸现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意识,同时,长期积淀的婚嫁原型为婚嫁歌奠定了雏形。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中民间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吉尔”的古歌代表着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的传统,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述英雄业绩的“英雄叙事诗”;一类是婚姻爱情叙事诗。而与“吉尔”相对应的是被称为“黑萨”的叙事诗。这部分大多是仿作和改铸之作,以外来故事素材进行再创作。它分为传奇叙事诗和宗教叙事诗两类。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歌颂的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如《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康巴尔》、《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等都以史诗性、古老性著称。婚姻爱情叙事诗则侧重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爱情命运,著名的有《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少女吉别克》、《萨丽哈与萨曼》等。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中,《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属长篇英雄叙事诗,由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单部叙事诗组成,歌颂了40位英雄反抗外侮的事迹。据说诗中的英雄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反映了自13~19世纪哈萨克族的历史和生活面貌,是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的集大成之作。
民间叙事诗是靠歌手演唱流传下来的,阿肯、吉尔齐都擅长叙事诗的演唱,但阿肯更长于即兴式的民歌对唱。只要有阿肯弹唱的地方准是在举行庆祝集会、重大祭奠、节日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盛典造就了阿肯,阿肯也使盛典热烈、欢快。阿肯单独吟唱固然能一举成名,但阿肯对唱更是智慧和才华的较量。阿肯对唱往往在两个氏族部落间举行,登场的虽是阿肯个人,但对唱的成败、胜负关系到本氏族、本部落的荣誉,所以阿肯在台上较劲演唱,台下的观众则为本氏族、本部落的阿肯呐喊助兴。如果说喜庆节日、盛大集会、祭奠仪式的阿肯对唱是由主持者或东道主有意为之的话,而以歌会友式的阿肯弹唱就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一种主动登门造访切磋技艺的有效形式。有的阿肯远途跋涉,不辞辛劳,从一个部落来到另一个部落探访有声望的阿肯进行对唱。哈萨克族著名的阿肯比尔江就曾骑垮了6匹乘骑,奔波半个月,慕名找到声望卓著的萨拉阿肯,与之对唱。阿肯的声望并不靠年龄、辈份、性别优势,而是造诣,看其是否有即兴赋歌吟唱的语言艺术功底。因此,阿肯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唱可以在男阿肯之间进行,也可以在男阿肯与女阿肯间举行,老年阿肯与少年阿肯间对唱也习以为常。年长的阿肯败在少年阿肯手下,男阿肯败在女阿肯手下并非鲜见。加纳克阿肯在哈萨克草原负有盛名,曾胜过无数阿肯,但败给一位少年阿肯。男阿肯隋因拜就在同女阿肯孔巴拉对唱时败北。阿肯对唱竞争十分激烈,采取淘汰制的办法。两名歌手一对一上场对唱,各自弹奏冬布拉或库布孜为自己伴奏,相互间对歌盘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尽浑身解数炫耀各自的才华,从气势上、语言技巧上,甚至才智、人品上压倒对方,当另一人自愧弗如、甘拜下风时,对唱就决出了高低。新老阿肯之间的对唱更是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似暴雨,如疾风,年长阿肯向新手展开猛烈进攻。一开口唱歌,年长阿肯就连珠炮似的猛攻,盘诘对方姓名、经历,继而自我炫耀,竭力嘲讽、戏谑新手,夸耀自己及氏族的荣耀,使对方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对于年长阿肯的“激怒”,新手不能恼怒,更不能发火,而只能不愠不火,靠自己的才智和语言技巧回敬对方。无论对唱多么激烈,但一旦对唱结束,双方都会以谦谦君子之风握手言欢。阿肯对唱中还不时穿插谜语、隐语等民间形式,增强对唱语言的艺术感染力。①
同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哈萨克族的神话与传说故事、世俗故事也是其民间文化宝库中的佼佼者。这些故事塑造了诸如迦萨甘这样的创世神话、动物传说,神箭手、机智人物、普通牧民,乃至牧主、强盗、统治者等个性鲜明、反差强烈的各种形象,表达着哈萨克族人民的思想、理念、情感以及价值观和审美走向。以《迦萨甘创世》为例,它解释的是宇宙创生模式:由混沌到初开,分为天、地、冥三界,其中天界以太阳与月亮为中心,地界的中心是生命树。宇宙混沌思维原型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混沌”实为“浑脱”,就是游牧民族装马奶的皮囊,所居圆形毡房古今不变,所以想象宇宙关系就如皮囊或毡房。而正是迦萨甘将天地、阴阳分开,出现了自然万物。神话中的生命树,又称宇宙树,它是通天的“天梯”,是人通神、神通天地的通道。生命树观念首先源自先民对宇宙的直观思维,构成天地层次观,其次源自宇宙中心观的确立。哈萨克族创世神话中的模式物——生命树,对他们的生死观、灵魂观以及各种人生礼仪都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
在草原文学中,古代突厥人和成吉思汗西征前操突厥语诸部落的民歌独树一帜,对后期草原诸民族的民歌也曾产生广泛影响。自6世纪80年代西突厥统辖阿勒泰以西广大地区后,突厥文化成了阿勒泰至伊犁草原地带最主要的草原游牧文化,而自9~13世纪则有诸如葛逻禄、炽俟、踏实力、样磨、乌古斯等操突厥语部落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突厥语大词典》中对各操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进行了介绍,并辑录了这些部落的民歌作为例证。这些民歌中很可能包括西突厥人的民歌,因为9世纪后的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不少就是从东西突厥汗国中分化出来的游牧部落。从大词典所记“伊犁”、“额尔齐斯”等地名、河名看,他们都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他们的民歌多与草原景物、狩猎活动以及生产生活习俗有关。一些狩猎民歌可能是古代突厥人的早期民歌,因为绝大部分草原游牧民族早期均是狩猎民族,而演进到游牧民族后,狩猎仍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大词典所录一首狩猎民歌为:
擎兔鹰,
跨骏马,
追逐盘羊,
放猎犬,
捕狐狸,
猎取黄羊。
活脱脱一幅紧张激烈的草原狩猎图。更有些狩猎民歌擅长描写猎犬捕狼时的打斗场面:
我的狗把它扑翻在地,
狠劲地撕咬它的毛皮。
把它的脑袋按在地上,
用利爪扼住了它的脖子。
这种描写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动感。也有些狩猎民歌是展示年轻猎手本领的:
带兔鹰去狩猎,纵猎犬去撕咬;
用石击狐狸野猪,
我们以本领自豪。
用石击都能捕获猎物,可见身手不凡。草原游牧民族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马,马是他们的坐骑,用于放牧、狩猎、迁徙,于是出现了大量以马为题材的民歌。有一首民歌是以驯马为题材的:
跨上烈马任它跳,
把那烈性驯服了;
让狗去追回猎物,
我们希望它猎到。
寥寥数语交代清楚驯马过程后,又叙写驯马与狩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在长期以马为伴的生活中,还积累了识马、相马的丰富经验,特别对疾驰如飞的骏马钟爱有加:“骏马在疾驰飞奔,马蹄下贱出火星;火星点燃了枯草,火焰在熊熊燃烧”。略嫌夸张的手法让人们领略到骏马如飞的身姿。同样,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十分熟悉所饲养的各种羊的习性,特别是公羊和母羊的分群、母羊和羊羔合群是能否挤奶的标志:“公羊公山羊分开了,母羊群会集起来了,乳汁统统地流出了,羊羔山羊羔合群了”。一般在夏季母羊与公羊分群,母羊合群后挤奶季节就开始了;而母羊和羊羔合群,由于哺乳羊羔,就不再挤奶了。他们经过严冬后对万物复苏的春天充满了喜悦:“山头被绿色笼罩,遮盖了隔年干草;湖泊盈溢着春天,公母牛哞哞欢叫。”这首民歌是春天的赞歌,满目葱绿,牲畜繁衍,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赏心悦目呢?①
应该说,蒙古人活动于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的历史并不短,从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起,到卫拉特蒙古四部,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了。但蒙元时期生活在阿力麻里一带蒙古人的民间文学状况怎样,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像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蒙古人对阿力麻里的征服,但不见有这一地区蒙古族民歌的只言片语记载。生于波斯的志费尼倒是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蒙古人征服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时的诗歌。这些诗歌多是对成吉思汗及诸子西征战绩的歌颂和征战场面的描写,但已非民歌范畴,而是被征服地的文人创作了。蒙古人的文学传统——包括民歌、英雄史诗、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文学形式经数百年的口头传承,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蒙古族民歌中最被称道的是长调民歌,这些长调常常是高低音同度一致的,但当两个或更多的蒙古人一起唱时,往往有出色的歌手唱出延长音,延长到他的肺活量的最大限度,然后由他继续把它唱下去,好似是其他歌手的回音一般,从而使这首抒情曲与复调多重唱相似。蒙古族民歌中还有一种短调,因风趣幽默、节奏明快、曲调活泼,又称其为诙谐歌曲。像土尔扈特蒙古的《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就是歌手即兴演唱的抒情长调,歌手反复用本嗓和假声演唱,歌词是歌手即兴吟成的,是对繁茂的伊犁河谷秋天的回忆。长调显然属于牧歌一类。察哈尔蒙古的《高山上的花》、《金纽扣》、《想念我的家乡》都属短调民歌。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民歌除牧歌外,还有赞歌、酒歌、情歌、婚礼歌等多种形式,如《西部可汗》、《可爱的暗褐色小马》、《我可爱的小雄鹿》、《额林哈毕尔噶山》等。由于马在卫拉特蒙古人生产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它也成了情歌重要描述的对象。对马的情景描写实际上是暗指情人,如《花色马》:“骑上我的花色马,一溜烟尘过大山。亲爱的哥哥讲的话,时刻铭记我心间”。还有《心爱的枣骝马》描写道:“乘上心爱的坐骑枣骝马,在无垠的草原上飞速驰骋。我热恋的心上人哟,喁喁的情话镌刻在我心中。”这种看似雷同的思路,往往是随手拈来,即兴吟唱,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都明了其意并不在马,而在于情。因感受、理解不同,同是对马的情景描写,各自成趣,毫不乏味。但是,在卫拉特蒙古人看来,骏马往往是和英雄相匹配的,于是有了那首歌唱土尔扈特人的英雄罗布桑察纳布及其骏马的民歌:
在白雪覆盖的高山之顶,
屹立着一所帐篷。
它白如白雪皑皑的山峰,
罗布桑察纳布在门口凝视着南方的地平线。
他的白色种马飞奔得比箭还快,
他骑上它追上了野鹿。
鹰靠强健的翅膀追捕野天鹅,
而罗布桑察纳布的敏捷胜过最强壮的鹰。
很多人都羡慕罗布桑察纳布,
但他们在战斗中才知道最伟大的要数黑色的鹰罗布桑察纳布。①
它在卫拉特蒙古诗歌中英雄史诗占有独特地位,《江格尔》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讲述的是蒙古族英雄江格尔及其十二“雄狮”、三十“虎将”、八千勇士与恶魔蟒古斯斗争的故事。《江格尔》由世代江格尔齐演唱、加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江格尔》属长篇巨制型英雄史诗,现在见到的是搜集整理出版的十五章托忒蒙古文本,还有十三章等汉译本。其实,民间流传的《江格尔》远比这长得多。据一些蒙古族老艺人回忆,有一种七十回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据蒙古族学者色道尔吉研究认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是土尔扈特人民集体的口头创作,是他们智慧和感情的生动反映,到明代,成了四卫拉特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后来通过江格尔齐的演唱和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国内外蒙古族人民聚居地区。《江格尔》歌颂的是蒙古人的理想乐园——宝木巴以及以江格尔为代表的宝木巴众多勇士,并揭露了奴隶制社会现实的丑恶。富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江格尔等人也成了反抗邪恶、铲除社会不公、创建和保卫宝木巴的象征,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推崇的英雄。《江格尔》在世代流传中也融进了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是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江格尔》中多处出现阿尔泰山、白头山、额什尔鄂拉山、额尔齐斯河、乌古伦河、奎屯河等山名、河名,这与卫拉特蒙古四部活动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毕竟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卫拉特蒙古在长期游牧生活中,或出于启迪教化的动机,或作为闲暇生活消遣的方式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和寓言故事、降妖伏魔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生活故事、讽刺幽默故事等。卫拉特蒙古的动物和寓言故事有解释动物外貌、习性特征的解释性故事,也有哲理性的有教化功能的寓言故事,还有图腾性的动物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征是:说是讲动物,实际在讲人;说是讲人,又明明是讲动物。基本上都属于以动物喻人,以动物事寓人事的故事。如《狐狸和熊》、《骆驼为啥在灰土上打滚》、《骑大红马的阿勒泰台吉》、《白雪和兔子》、《粮食全留给了青蛙和蜘蛛》等都属于以上三类动物故事。降妖伏魔故事大多是讲述民间流传的蒙古族的英雄故事,这些英雄都有降妖伏魔的神勇、神力,是百姓仰慕的对象。如《红脸勇士乌兰·哈茨尔》、《聪明的苏布松·都日勒格可汗》、《英雄布赫蒙贡·希克萨尔》等。还有些虽非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一些无助的孤儿、美貌的姑娘、年轻小伙、年长的老人等,但都是一些伸张正义、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人物,也成了这类故事的主人公。一些神话传说故事虽然都是幻想、想象的产物,但在这些神话世界中也有现世的影子,如用神话解释宇宙和各种自然现象起源,解释本民族始祖起源,解释诸如本民族风俗、伦理、器用、技术等的起源。《神女的恩惠》就是杜尔伯特蒙古人始祖的神话故事。讲述一个青年猎手和天女幽会生下一男孩,这位男孩长大后成了一名真正的勇士,也成了杜尔伯特人的祖先。这自然也是蒙古人天神崇拜观的反映,他们笃信,自己的祖先就是天上神女的后代。在卫拉特蒙古四部中更多的是世俗的生活故事和讽刺幽默故事。放牛娃、流浪女、放羊娃等都是一些善良、聪慧机智的人物,而章京、王爷、吝啬鬼、懒汉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讽刺、揄揶的对象。《聪慧的放牛娃》就是广泛流传于卫拉特蒙古四部的古老生活故事,是一系列单篇故事构成的组合故事。《阿尔格齐的故事》是机智人物故事,由《出丑》、《乞肉》、《懒汉》、《吹牛》、《戍马》等数十个系列故事组成,讽刺辛辣,妙语如珠,有极强的警策作用。①
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歌是哈萨克人的翅膀”,他们视民歌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实际上,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民歌,还有英雄叙事诗、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等,构成庞大的民间文学系统。哈萨克族的民歌大都可以列入习俗歌的范畴,可以这样说,是他们的习俗催生了这些民歌,这些民歌中也孕育了一定的习俗。这些习俗歌包括婚嫁歌、丧葬歌、日常生活歌、节日习俗歌、宗教习俗歌等。以哈萨克族的婚嫁歌为例,它分为“喜事序歌”、“萨仁”、“加尔—加尔”、“哭嫁歌”、“远嫁歌”、“劝嫁歌”、“揭面歌”等,是整个婚嫁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哈萨克族的婚礼是从提亲开始的,伴有订婚仪式、嫁娶仪式等。在整个过程中,婚嫁歌存在于自始至终,新娘用歌向亲人告别,亲人用歌劝嫁,男方用歌迎娶新娘,来宾歌唱助兴等。嫁女仪式中的“萨仁”歌原并非单指唱给新娘的歌,其他一些古老的有哲理性、劝喻性的古老民歌也称为“萨仁”。由于“萨仁”歌在嫁女仪式开始当天由男方的两位伴郎齐唱,唱给新娘听,往往唱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有“晓之以理”的意味,因此“萨仁”也就成了具有劝嫁内容的嫁女仪式歌。而“加尔—加尔”是男方劝嫁、女方哭嫁的对唱,往往是男方曲调欢快、轻松,而女方凄楚、悲凉。婚嫁歌透露的是婚嫁习俗原型的信息,通过演唱形式凸现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意识,同时,长期积淀的婚嫁原型为婚嫁歌奠定了雏形。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中民间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吉尔”的古歌代表着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的传统,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述英雄业绩的“英雄叙事诗”;一类是婚姻爱情叙事诗。而与“吉尔”相对应的是被称为“黑萨”的叙事诗。这部分大多是仿作和改铸之作,以外来故事素材进行再创作。它分为传奇叙事诗和宗教叙事诗两类。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歌颂的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如《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康巴尔》、《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等都以史诗性、古老性著称。婚姻爱情叙事诗则侧重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爱情命运,著名的有《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少女吉别克》、《萨丽哈与萨曼》等。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中,《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属长篇英雄叙事诗,由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单部叙事诗组成,歌颂了40位英雄反抗外侮的事迹。据说诗中的英雄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反映了自13~19世纪哈萨克族的历史和生活面貌,是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的集大成之作。
民间叙事诗是靠歌手演唱流传下来的,阿肯、吉尔齐都擅长叙事诗的演唱,但阿肯更长于即兴式的民歌对唱。只要有阿肯弹唱的地方准是在举行庆祝集会、重大祭奠、节日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盛典造就了阿肯,阿肯也使盛典热烈、欢快。阿肯单独吟唱固然能一举成名,但阿肯对唱更是智慧和才华的较量。阿肯对唱往往在两个氏族部落间举行,登场的虽是阿肯个人,但对唱的成败、胜负关系到本氏族、本部落的荣誉,所以阿肯在台上较劲演唱,台下的观众则为本氏族、本部落的阿肯呐喊助兴。如果说喜庆节日、盛大集会、祭奠仪式的阿肯对唱是由主持者或东道主有意为之的话,而以歌会友式的阿肯弹唱就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一种主动登门造访切磋技艺的有效形式。有的阿肯远途跋涉,不辞辛劳,从一个部落来到另一个部落探访有声望的阿肯进行对唱。哈萨克族著名的阿肯比尔江就曾骑垮了6匹乘骑,奔波半个月,慕名找到声望卓著的萨拉阿肯,与之对唱。阿肯的声望并不靠年龄、辈份、性别优势,而是造诣,看其是否有即兴赋歌吟唱的语言艺术功底。因此,阿肯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唱可以在男阿肯之间进行,也可以在男阿肯与女阿肯间举行,老年阿肯与少年阿肯间对唱也习以为常。年长的阿肯败在少年阿肯手下,男阿肯败在女阿肯手下并非鲜见。加纳克阿肯在哈萨克草原负有盛名,曾胜过无数阿肯,但败给一位少年阿肯。男阿肯隋因拜就在同女阿肯孔巴拉对唱时败北。阿肯对唱竞争十分激烈,采取淘汰制的办法。两名歌手一对一上场对唱,各自弹奏冬布拉或库布孜为自己伴奏,相互间对歌盘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尽浑身解数炫耀各自的才华,从气势上、语言技巧上,甚至才智、人品上压倒对方,当另一人自愧弗如、甘拜下风时,对唱就决出了高低。新老阿肯之间的对唱更是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似暴雨,如疾风,年长阿肯向新手展开猛烈进攻。一开口唱歌,年长阿肯就连珠炮似的猛攻,盘诘对方姓名、经历,继而自我炫耀,竭力嘲讽、戏谑新手,夸耀自己及氏族的荣耀,使对方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对于年长阿肯的“激怒”,新手不能恼怒,更不能发火,而只能不愠不火,靠自己的才智和语言技巧回敬对方。无论对唱多么激烈,但一旦对唱结束,双方都会以谦谦君子之风握手言欢。阿肯对唱中还不时穿插谜语、隐语等民间形式,增强对唱语言的艺术感染力。①
同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哈萨克族的神话与传说故事、世俗故事也是其民间文化宝库中的佼佼者。这些故事塑造了诸如迦萨甘这样的创世神话、动物传说,神箭手、机智人物、普通牧民,乃至牧主、强盗、统治者等个性鲜明、反差强烈的各种形象,表达着哈萨克族人民的思想、理念、情感以及价值观和审美走向。以《迦萨甘创世》为例,它解释的是宇宙创生模式:由混沌到初开,分为天、地、冥三界,其中天界以太阳与月亮为中心,地界的中心是生命树。宇宙混沌思维原型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混沌”实为“浑脱”,就是游牧民族装马奶的皮囊,所居圆形毡房古今不变,所以想象宇宙关系就如皮囊或毡房。而正是迦萨甘将天地、阴阳分开,出现了自然万物。神话中的生命树,又称宇宙树,它是通天的“天梯”,是人通神、神通天地的通道。生命树观念首先源自先民对宇宙的直观思维,构成天地层次观,其次源自宇宙中心观的确立。哈萨克族创世神话中的模式物——生命树,对他们的生死观、灵魂观以及各种人生礼仪都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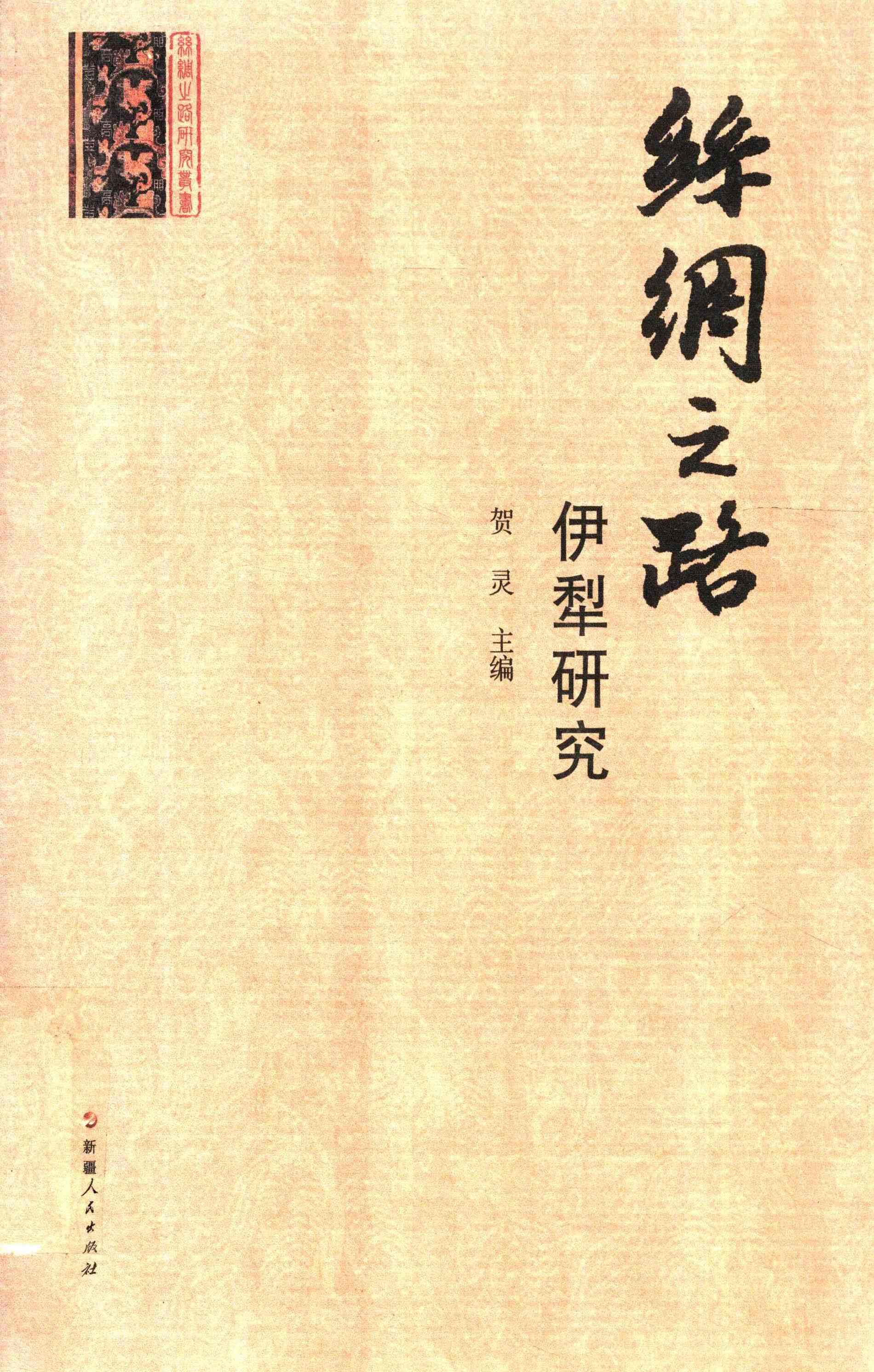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