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伊犁历代文学艺术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76 |
| 颗粒名称: | 第九章 伊犁历代文学艺术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23 |
| 页码: | 238-260 |
| 摘要: | 本章记述了伊犁历代文学艺术内容包括了,草原文学、屯垦文学、草原艺术、屯垦艺术等情况。 |
| 关键词: | 伊犁 历代文学 艺术 |
内容
第一节草原文学
吟咏歌唱近乎草原游牧民族的天性,于是产生了与他们生产生活及其习俗密切相关的草原民歌和传说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形式是构成草原文学的主流文学,特别是在早期更是这样,而书面文学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关于活动在伊犁、阿勒泰等草原地带早期民族的口头文学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这些充满草原气息的民间文学也随着这些民族的消亡而消失了。活动于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中的塞人、匈奴、呼揭、月氏、乌孙、铁勒等部族肯定都是富有口头文学传统的草原民族,如果不是汉文典籍偶有记载,人们对他们的民歌几乎一无所知。汉文文献存留了一首《匈奴歌》和另一首《敕勒歌》,前者是匈奴人痛失草原的绝唱:“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一泣一唱,一哭一回头,是多么的痛心疾首。后者被认为是铁勒(即敕勒)人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抒情味极浓的民歌,正如《诗薮》所言:“此歌成于信口,咸谓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无意发之,所以浑朴苍茫,使当时文士为之,便欲雕绘满眼。”天然无雕饰的民歌总是以清新、淳朴的秉性博得人们的青睐,远非文人创作能比。早期草原民族的吟唱中除淳朴、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外,还有一种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密不可分的萨满歌,即祷告歌。它是萨满在举行周期和非周期性祈祷仪式时的吟唱,属咒语一类的韵文。在献祭仪式、治病仪式、征战仪式中吟唱祝文是萨满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草原早期民族的战歌、情歌、摇篮曲、哀歌、婚礼颂歌等,在最初都是具有巫术、宗教的意义,带有咒语的性质。越是在早期,萨满在氏族部落中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萨满的祷告歌也无处无时不在,成为神圣的祈福禳灾的吟唱。
在草原文学中,古代突厥人和成吉思汗西征前操突厥语诸部落的民歌独树一帜,对后期草原诸民族的民歌也曾产生广泛影响。自6世纪80年代西突厥统辖阿勒泰以西广大地区后,突厥文化成了阿勒泰至伊犁草原地带最主要的草原游牧文化,而自9~13世纪则有诸如葛逻禄、炽俟、踏实力、样磨、乌古斯等操突厥语部落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突厥语大词典》中对各操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进行了介绍,并辑录了这些部落的民歌作为例证。这些民歌中很可能包括西突厥人的民歌,因为9世纪后的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不少就是从东西突厥汗国中分化出来的游牧部落。从大词典所记“伊犁”、“额尔齐斯”等地名、河名看,他们都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他们的民歌多与草原景物、狩猎活动以及生产生活习俗有关。一些狩猎民歌可能是古代突厥人的早期民歌,因为绝大部分草原游牧民族早期均是狩猎民族,而演进到游牧民族后,狩猎仍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大词典所录一首狩猎民歌为:
擎兔鹰,
跨骏马,
追逐盘羊,
放猎犬,
捕狐狸,
猎取黄羊。
活脱脱一幅紧张激烈的草原狩猎图。更有些狩猎民歌擅长描写猎犬捕狼时的打斗场面:
我的狗把它扑翻在地,
狠劲地撕咬它的毛皮。
把它的脑袋按在地上,
用利爪扼住了它的脖子。
这种描写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动感。也有些狩猎民歌是展示年轻猎手本领的:
带兔鹰去狩猎,纵猎犬去撕咬;
用石击狐狸野猪,
我们以本领自豪。
用石击都能捕获猎物,可见身手不凡。草原游牧民族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马,马是他们的坐骑,用于放牧、狩猎、迁徙,于是出现了大量以马为题材的民歌。有一首民歌是以驯马为题材的:
跨上烈马任它跳,
把那烈性驯服了;
让狗去追回猎物,
我们希望它猎到。
寥寥数语交代清楚驯马过程后,又叙写驯马与狩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在长期以马为伴的生活中,还积累了识马、相马的丰富经验,特别对疾驰如飞的骏马钟爱有加:“骏马在疾驰飞奔,马蹄下贱出火星;火星点燃了枯草,火焰在熊熊燃烧”。略嫌夸张的手法让人们领略到骏马如飞的身姿。同样,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十分熟悉所饲养的各种羊的习性,特别是公羊和母羊的分群、母羊和羊羔合群是能否挤奶的标志:“公羊公山羊分开了,母羊群会集起来了,乳汁统统地流出了,羊羔山羊羔合群了”。一般在夏季母羊与公羊分群,母羊合群后挤奶季节就开始了;而母羊和羊羔合群,由于哺乳羊羔,就不再挤奶了。他们经过严冬后对万物复苏的春天充满了喜悦:“山头被绿色笼罩,遮盖了隔年干草;湖泊盈溢着春天,公母牛哞哞欢叫。”这首民歌是春天的赞歌,满目葱绿,牲畜繁衍,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赏心悦目呢?①
应该说,蒙古人活动于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的历史并不短,从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起,到卫拉特蒙古四部,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了。但蒙元时期生活在阿力麻里一带蒙古人的民间文学状况怎样,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像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蒙古人对阿力麻里的征服,但不见有这一地区蒙古族民歌的只言片语记载。生于波斯的志费尼倒是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蒙古人征服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时的诗歌。这些诗歌多是对成吉思汗及诸子西征战绩的歌颂和征战场面的描写,但已非民歌范畴,而是被征服地的文人创作了。蒙古人的文学传统——包括民歌、英雄史诗、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文学形式经数百年的口头传承,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蒙古族民歌中最被称道的是长调民歌,这些长调常常是高低音同度一致的,但当两个或更多的蒙古人一起唱时,往往有出色的歌手唱出延长音,延长到他的肺活量的最大限度,然后由他继续把它唱下去,好似是其他歌手的回音一般,从而使这首抒情曲与复调多重唱相似。蒙古族民歌中还有一种短调,因风趣幽默、节奏明快、曲调活泼,又称其为诙谐歌曲。像土尔扈特蒙古的《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就是歌手即兴演唱的抒情长调,歌手反复用本嗓和假声演唱,歌词是歌手即兴吟成的,是对繁茂的伊犁河谷秋天的回忆。长调显然属于牧歌一类。察哈尔蒙古的《高山上的花》、《金纽扣》、《想念我的家乡》都属短调民歌。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民歌除牧歌外,还有赞歌、酒歌、情歌、婚礼歌等多种形式,如《西部可汗》、《可爱的暗褐色小马》、《我可爱的小雄鹿》、《额林哈毕尔噶山》等。由于马在卫拉特蒙古人生产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它也成了情歌重要描述的对象。对马的情景描写实际上是暗指情人,如《花色马》:“骑上我的花色马,一溜烟尘过大山。亲爱的哥哥讲的话,时刻铭记我心间”。还有《心爱的枣骝马》描写道:“乘上心爱的坐骑枣骝马,在无垠的草原上飞速驰骋。我热恋的心上人哟,喁喁的情话镌刻在我心中。”这种看似雷同
①所引民歌均见《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的思路,往往是随手拈来,即兴吟唱,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都明了其意并不在马,而在于情。因感受、理解不同,同是对马的情景描写,各自成趣,毫不乏味。但是,在卫拉特蒙古人看来,骏马往往是和英雄相匹配的,于是有了那首歌唱土尔扈特人的英雄罗布桑察纳布及其骏马的民歌:
在白雪覆盖的高山之顶,
屹立着一所帐篷。
它白如白雪皑皑的山峰,
罗布桑察纳布在门口凝视着南方的地平线。
他的白色种马飞奔得比箭还快,
他骑上它追上了野鹿。
鹰靠强健的翅膀追捕野天鹅,
而罗布桑察纳布的敏捷胜过最强壮的鹰。
很多人都羡慕罗布桑察纳布,
但他们在战斗中才知道最伟大的要数黑色的鹰罗布桑察纳布。①
它在卫拉特蒙古诗歌中英雄史诗占有独特地位,《江格尔》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讲述的是蒙古族英雄江格尔及其十二“雄狮”、三十“虎将”、八千勇士与恶魔蟒古斯斗争的故事。《江格尔》由世代江格尔齐演唱、加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江格尔》属长篇巨制型英雄史诗,现在见到的是搜集整理出版的十五章托忒蒙古文本,还有十三章等汉译本。其实,民间流传的《江格尔》远比这长得多。据一些蒙古族老艺人回忆,有一种七十回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据蒙古族学者色道尔吉研究认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是土尔扈特人民集体的口头创作,是他们智慧和感情的生动反映,到明代,成了四卫拉特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后来通过江格尔齐的演唱和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国内外蒙古族人民聚居地区。《江格尔》歌颂的是蒙古人的理想乐园——宝木巴以及以江格尔为代表的宝木巴众多勇士,并揭露了奴隶制社会现实的丑恶。富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江格尔等人也成了反抗邪恶、铲除社会不公、创建和保卫宝木巴的象征,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推崇的英雄。《江格尔》在世代流传中也融进了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是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江格尔》中多处出现阿尔泰山、白头山、额什尔鄂拉山、额尔齐斯河、乌古伦河、奎屯河等山名、河名,这与卫拉特蒙古四部活动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毕竟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卫拉特蒙古在长期游牧生活中,或出于启迪教化的动机,或作为闲暇生活消遣的方式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和寓言故事、降妖伏魔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生活故事、讽刺幽默故事等。卫拉特蒙古的动物和寓言故事有解释动物外貌、习性特征的解释性故事,也有哲理性的有教化功能的寓言故事,还有图腾性的动物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征是:说是讲动物,实际在讲人;说是讲人,又明明是讲动物。基本上都属于以动物喻人,以动物事寓人事的故事。如《狐狸和熊》、《骆驼为啥在灰土上打滚》、《骑大红马的阿勒泰台吉》、《白雪和兔子》、《粮食全留给了青蛙和蜘蛛》等都属于以上三类动物故事。降妖伏魔故事大多是讲述民间流传的蒙古族的英雄故事,这些英雄都有降妖伏魔的神勇、神力,是百姓仰慕的对象。如《红脸勇士乌兰·哈茨尔》、《聪明的苏布松·都日勒格可汗》、《英雄布赫蒙贡·希克萨尔》等。还有些虽非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一些无助的孤儿、美貌的姑娘、年轻小伙、年长的老人等,但都是一些伸张正义、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人物,也成了这类故事的主人公。一些神话传说故事虽然都是幻想、想象的产物,但在这些神话世界中也有现世的影子,如用神话解释宇宙和各种自然现象起源,解释本民族始祖起源,解释诸如本民族风俗、伦理、器用、技术等的起源。《神女的恩惠》就是杜尔伯特蒙古人始祖的神话故事。讲述一个青年猎手和天女幽会生下一男孩,这位男孩长大后成了一名真正的勇士,也成了杜尔伯特人的祖先。这自然也是蒙古人天神崇拜观的反映,他们笃信,自己的祖先就是天上神女的后代。在卫拉特蒙古四部中更多的是世俗的生活故事和讽刺幽默故事。放牛娃、流浪女、放羊娃等都是一些善良、聪慧机智的人物,而章京、王爷、吝啬鬼、懒汉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讽刺、揄揶的对象。《聪慧的放牛娃》就是广泛流传于卫拉特蒙古四部的古老生活故事,是一系列单篇故事构成的组合故事。《阿尔格齐的故事》是机智人物故事,由《出丑》、《乞肉》、《懒汉》、《吹牛》、《戍马》等数十个系列故事组成,讽刺辛辣,妙语如珠,有极强的警策作用。①
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歌是哈萨克人的翅膀”,他们视民歌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实际上,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民歌,还有英雄叙事诗、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等,构成庞大的民间文学系统。哈萨克族的民歌大都可以列入习俗歌的范畴,可以这样说,是他们的习俗催生了这些民歌,这些民歌中也孕育了一定的习俗。这些习俗歌包括婚嫁歌、丧葬歌、日常生活歌、节日习俗歌、宗教习俗歌等。以哈萨克族的婚嫁歌为例,它分为“喜事序歌”、“萨仁”、“加尔—加尔”、“哭嫁歌”、“远嫁歌”、“劝嫁歌”、“揭面歌”等,是整个婚嫁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哈萨克族的婚礼是从提亲开始的,伴有订婚仪式、嫁娶仪式等。在整个过程中,婚嫁歌存在于自始至终,新娘用歌向亲人告别,亲人用歌劝嫁,男方用歌迎娶新娘,来宾歌唱助兴等。嫁女仪式中的“萨仁”歌原并非单指唱给新娘的歌,其他一些古老的有哲理性、劝喻性的古老民歌也称为“萨仁”。由于“萨仁”歌在嫁女仪式开始当天由男方的两位伴郎齐唱,唱给新娘听,往往唱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有“晓之以理”的意味,因此“萨仁”也就成了具有劝嫁内容的嫁女仪式歌。而“加尔—加尔”是男方劝嫁、女方哭嫁的对唱,往往是男方曲调欢快、轻松,而女方凄楚、悲凉。婚嫁歌透露的是婚嫁习俗原型的信息,通过演唱形式凸现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意识,同时,长期积淀的婚嫁原型为婚嫁歌奠定了雏形。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中民间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吉尔”的古歌代表着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的传统,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述英雄业绩的“英雄叙事诗”;一类是婚姻爱情叙事诗。而与“吉尔”相对应的是被称为“黑萨”的叙事诗。这部分大多是仿作和改铸之作,以外来故事素材进行再创作。它分为传奇叙事诗和宗教叙事诗两类。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歌颂的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如《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康巴尔》、《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等都以史诗性、古老性著称。婚姻爱情叙事诗则侧重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爱情命运,著名的有《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少女吉别克》、《萨丽哈与萨曼》等。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中,《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属长篇英雄叙事诗,由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单部叙事诗组成,歌颂了40位英雄反抗外侮的事迹。据说诗中的英雄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反映了自13~19世纪哈萨克族的历史和生活面貌,是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的集大成之作。
民间叙事诗是靠歌手演唱流传下来的,阿肯、吉尔齐都擅长叙事诗的演唱,但阿肯更长于即兴式的民歌对唱。只要有阿肯弹唱的地方准是在举行庆祝集会、重大祭奠、节日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盛典造就了阿肯,阿肯也使盛典热烈、欢快。阿肯单独吟唱固然能一举成名,但阿肯对唱更是智慧和才华的较量。阿肯对唱往往在两个氏族部落间举行,登场的虽是阿肯个人,但对唱的成败、胜负关系到本氏族、本部落的荣誉,所以阿肯在台上较劲演唱,台下的观众则为本氏族、本部落的阿肯呐喊助兴。如果说喜庆节日、盛大集会、祭奠仪式的阿肯对唱是由主持者或东道主有意为之的话,而以歌会友式的阿肯弹唱就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一种主动登门造访切磋技艺的有效形式。有的阿肯远途跋涉,不辞辛劳,从一个部落来到另一个部落探访有声望的阿肯进行对唱。哈萨克族著名的阿肯比尔江就曾骑垮了6匹乘骑,奔波半个月,慕名找到声望卓著的萨拉阿肯,与之对唱。阿肯的声望并不靠年龄、辈份、性别优势,而是造诣,看其是否有即兴赋歌吟唱的语言艺术功底。因此,阿肯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唱可以在男阿肯之间进行,也可以在男阿肯与女阿肯间举行,老年阿肯与少年阿肯间对唱也习以为常。年长的阿肯败在少年阿肯手下,男阿肯败在女阿肯手下并非鲜见。加纳克阿肯在哈萨克草原负有盛名,曾胜过无数阿肯,但败给一位少年阿肯。男阿肯隋因拜就在同女阿肯孔巴拉对唱时败北。阿肯对唱竞争十分激烈,采取淘汰制的办法。两名歌手一对一上场对唱,各自弹奏冬布拉或库布孜为自己伴奏,相互间对歌盘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尽浑身解数炫耀各自的才华,从气势上、语言技巧上,甚至才智、人品上压倒对方,当另一人自愧弗如、甘拜下风时,对唱就决出了高低。新老阿肯之间的对唱更是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似暴雨,如疾风,年长阿肯向新手展开猛烈进攻。一开口唱歌,年长阿肯就连珠炮似的猛攻,盘诘对方姓名、经历,继而自我炫耀,竭力嘲讽、戏谑新手,夸耀自己及氏族的荣耀,使对方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对于年长阿肯的“激怒”,新手不能恼怒,更不能发火,而只能不愠不火,靠自己的才智和语言技巧回敬对方。无论对唱多么激烈,但一旦对唱结束,双方都会以谦谦君子之风握手言欢。阿肯对唱中还不时穿插谜语、隐语等民间形式,增强对唱语言的艺术感染力。①
同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哈萨克族的神话与传说故事、世俗故事也是其民间文化宝库中的佼佼者。这些故事塑造了诸如迦萨甘这样的创世神话、动物传说,神箭手、机智人物、普通牧民,乃至牧主、强盗、统治者等个性鲜明、反差强烈的各种形象,表达着哈萨克族人民的思想、理念、情感以及价值观和审美走向。以《迦萨甘创世》为例,它解释的是宇宙创生模式:由混沌到初开,分为天、地、冥三界,其中天界以太阳与月亮为中心,地界的中心是生命树。宇宙混沌思维原型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混沌”实为“浑脱”,就是游牧民族装马奶的皮囊,所居圆形毡房古今不变,所以想象宇宙关系就如皮囊或毡房。而正是迦萨甘将天地、阴阳分开,出现了自然万物。神话中的生命树,又称宇宙树,它是通天的“天梯”,是人通神、神通天地的通道。生命树观念首先源自先民对宇宙的直观思维,构成天地层次观,其次源自宇宙中心观的确立。哈萨克族创世神话中的模式物——生命树,对他们的生死观、灵魂观以及各种人生礼仪都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
第二节屯垦文学
历代的伊犁屯垦戍边造就了伊犁屯垦文学。这里所说的伊犁屯垦文学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历代在这片土地上屯垦戍边的各族军民的文学;二是以屯垦戍边为题材的文学。但从广义上讲,屯垦文学应指历代屯垦戍边的各族军民的文学。于是屯垦文学又可分为以西域边塞诗为主体的书面文学和弥漫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从一些文献记载看,清代形成了伊犁屯垦文学的高峰。伊犁边塞诗绝大多数出自获罪流放的流人之手,还有一些则出自屯垦戍边的各级官员之手。而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主要指扎根于伊犁河畔的锡伯等民族的民歌、民间故事等文学形态。
清代伊犁边塞诗作者众多,以伊犁屯田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诗作也不在少数,而且贯穿了整个清代。如果细细耙梳,代表性的有庄肇奎的《伊犁纪事二十首》、洪亮吉的《伊犁纪事四十二首》、舒其绍的《消夏吟并序二十五首》、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百首》、方士淦的《伊江杂诗十六首》、邓廷桢的《回疆凯歌十首》、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以及景廉等官员的诗作。①这些诗作基本代表了清代伊犁边塞诗的基调。当然,这些谪戍伊犁人士的诗作也有一些属宣泄失意情愫、应酬奉和、走马观花之作,但大多数人留滞伊犁一载或数载,往往能超然于个人荣辱之外,关注统一大业、屯垦戍边,并对边疆的民风民情有深入了解,即使是以风光为抒写对象,也往往充满激情。
在清代伊犁边塞诗中,诗人们吟咏最多的是伊犁的风土人情和屯田事业。庄肇奎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谪戍伊犁后,又在伊犁任职,前后在伊犁滞留8年之久,留有纪行诗、伊犁纪事诗等近70首,并以《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最为出色,作于离开伊犁前的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1789)。20首诗对伊犁景色、屯田成果、民族风情的描写别开生面。“戈壁滩头已驻兵,城中无水欲迁城。试传军令齐开井,掘处皆泉万斛清”。这是赞颂伊犁将军伊勒图掘井一举不仅保住了惠远城指挥中枢的地位,而且对屯田戍边意义重大的诗作。作者对伊犁充满热爱之情:“土膏肥沃雪泉香,尽有瓜蔬独少姜。最是早秋霜打后,菜根甘美胜吾乡。”伊犁土肥水美,瓜蔬丰饶,秋菜甘美胜似江南,足见物丰景美。作者对屯田带来的社会安定、物丰人喜有切身体会:“车载粮多未易行,六千回户岁收成。造舟运入仓箱满,大漠初闻欸乃声。”回屯是清代屯田形式之一,这些来自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在伊犁屯田后,粮食丰收,车载不及,乃设水运。可见屯田的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洪亮吉虽在伊犁流放仅有百日,但他的《伊犁纪事四十二首》在清代边塞诗中属精品一类。洪亮吉属学者型文人,虽命运多舛,但才气压不住,因此,伊犁纪事诗也就格高一调。他不是浮光掠影式地叙事状物,而往往注重风土人情所蕴含的深意,且能见常人不注意的细节之处。“五月天山雪水来,城门桥下响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却倩河流界画开。”这是伊犁屯田城镇常见的景色,每年4月引水入城后,曲池蓄之,到夏天用于灌溉园圃。这种城内蓄水城外用的情景在内地是不多见的。作者赞赏这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凿得冰梯向北开,阴崖白昼鬼徘徊。万丛磷火思偷渡,尽附牛羊角上来。”这是写维吾尔族农民开凿冰梯开通伊犁通往南疆冰达坂通道之事。年年如此,对当地人来说是司空见惯,而对洪亮吉来说却能写出新意,修路之难不说,便利行旅更重要。洪亮吉还在一些诗中表明自己虽遭流放,但不会因此而消沉,要永不气馁的心迹:“坐来八尺马如龙,演武堂高夹路松。谪吏一边三十六,尽排长载壮军容”。谪戍边陲,“壮军容”的精神永在。洪亮吉擅长状物写景,无论是“雪消齐露粉墙”的古庙,还是“杏子乍青桑葚紫”的果园景致,都写得有情有义。
舒其绍自清嘉庆二年(1797)以事戍伊犁长达8年,主要写有《消夏吟并序二十五首》,以状写伊犁等地屯田城镇、山川地理、历史掌故闻名。所写屯田城镇有塔勒奇城、霍尔果斯城、惠宁城、广仁城、锡伯营以及金顶寺、普化寺、无量寺、观音寺等寺庙建筑,山川地理写有红山嘴、皮里青、白杨沟、野马渡、果子沟、红柳湾、赛里木湖、固尔扎渡口、清水河、齐齐罕河、厄鲁特游牧场等。他的足迹踏遍伊犁的城乡、牧场、山山水水。舒其绍在《消夏吟》序中说,这些诗是“就素所知者,拈题分咏,藉消长夏”,但其意又不尽在消夏,而更是在话“升平”。作者在《芦草沟城》一诗中写道:“大野雪漫漫,孤城草际看,黄云痴不落,白日瘦生寒。鸡犬通秦语,貔貅列汉官。太平无一事,堠火报长安。”芦草沟城即广仁城。戍边虽艰苦,但这些来自陕甘的戍卒和商贾在保边疆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对伊犁的山川风光,往往也能抓住景物特征,写出各自特色。写果子沟是“云穿千嶂活,风曳百花香”,赛里木湖是“乱山围地起,一水点天流”,写齐齐罕河是“险隘葫芦口,当关水怒号”,厄鲁特游牧场是“夜猎霜飞血,晨炊雪压庐”。或许诗是浅白了点,但状物写景总是贴切、入味。
与舒其绍同时代的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也以写伊犁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著称,但更多了一些历史厚重感和责任感,这与他的学养深厚和撰写《伊犁总统事略》不无关系。他在《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名为《伊犁》的诗:“伊丽曾闻属定方,濛池碎叶路茫茫。投鞭直断西流水,始信当年我武扬。”这是借用唐朝平定西突厥建濛池都护府、碎叶州典故赞颂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之事。当时伊犁等地已在大唐版图内,对伊犁的这种述写充满自豪感。在《兵屯》、《卡伦》等诗中作者也不忘抒写清代屯田戍边的意义。《兵屯》写道:“细柳云屯剑气寒,貔貅百万势桓桓。列城棋布星罗日,阃外群尊大将云。”建伊犁九城,陈兵边塞,都是保民安边的重大举措,作者予以充分肯定。《卡伦》:“刁斗声残夜寂寥,龙沙极目雪花飘。守边一一皆飞将,生手何人敢射雕?”卡伦为清政府设于边地要隘守望并营税收之处。此诗是赞颂坚守卡伦将士的,寓指卡伦在边疆稳定中意义重大。祁韵士还写有《府茶》、《阿拉占》、《器乐》、《回布》等状写伊犁等地民俗文化的诗作,对边地淳朴的民风民俗充满赞誉之情。
方士淦于道光五年(1825)遣戍伊犁,道光八年释返。在伊犁期间写有《伊江杂诗十六首》,写历史,写风土,写山川,写交往,无所不包。他的诗有不少是对清乾隆朝在平定大小和卓和准噶尔叛乱中献身将士的追念和凭吊:
城外绿阴稠,
金堤百尺楼。
群峰环雪岭,
一水带沙流。
不有神明相,
谁令祀典修。
宗臣遗像在,
忠义凛千秋。
在惠远城南门外龙王庙前的望河楼为伊犁将军保宁建,其父纳穆札尔,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殉难。作者认为其父“忠义凛千秋”,值得人们缅怀。
林则徐和邓廷桢这两位禁烟中的英雄同被遣戍伊犁,在伊犁数年期间留下了不少咏物明志的诗作。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主要是描写新疆少数民族风俗的。因林则徐去南疆八城地区勘察水利,有了深入了解维吾尔族风俗的机会。在诗中对维吾尔族的农作节气、宗教信仰、服食起居、婚丧嫁娶、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描写。诗中大量借用维吾尔语,平淡中有诙谐,写实中富有诗意,如行云流水,畅晓上口,展示了清代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自乾隆年间开始,不少维吾尔族农民已以回屯方式在伊犁地区开荒垦种,对此,林则徐在伊犁期间已有所了解。像“城角高台广乐张”的维吾尔族音乐,像“爰伊谛会万人欢”的宗教节日庆典,又像“石粉团成满壁花”的建筑艺术和“新帕盖头扶上马”的婚礼,作者都有描写。林则徐在伊犁的诗作更多的是明志抒怀的。邓廷桢遣戍伊犁之初,心情郁闷,神情恍惚,随着滞留时间增长,对边疆的淳朴民风、富饶美丽有了切身感受,于是渐渐驱走了往日的愁思,写伊犁山川之雄浑,抒防俄固边的爱国忧思。《伊丽河上》就是其戍边诗中的代表作:
万里伊犁河,
西流不奈何。
驱车临断岸,
落木起层波。
远影群鸥没,
寒声独雁过。
河梁终古意,
击剑一长歌。
面对沙俄的虎视眈眈,邓廷桢感到塞防的重要,他以“击剑一长歌”表明心迹。
在此还应提一下清朝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的《伊犁杂咏》。这位伊犁将军仅在位54天就被伊犁起义的革命党人枪杀。虽然《伊犁杂咏》写于志锐任索伦营领队大臣时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但他的诗成了清代伊犁边塞诗终结的标志。《伊犁杂咏》由6首诗组成,即《抢羊》、《咏冰床》、《鸡卜》、《金银顶寺》、《贡马》等。诗是描写伊犁哈萨克等民族风俗的,后人王子钝先生评价《伊犁杂咏》是“数诗吟咏异俗,纯以平常语琢成,别有深味”。
与文人的边塞诗比较,伊犁屯垦文学中别开生面的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民间文学。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至伊犁的锡伯族因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较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形态。锡伯族的民间文学实际上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早在东北生活时期的民间文学;另一类是西迁至伊犁后新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民歌中的《狩猎歌》、《萨满歌》、《耶奇那》以及传说故事中的《喜利妈妈的传说》、《海尔堪玛法的传说》、《阿克敦的传说》、《人参故事》、《秃孩子》等早在农耕生活时代就产生了。有一首《狩猎歌》写道:“飘飘雪花如蝶飞,驰骋骏马共撒围。搜遍一山又一山,猎队满载凯歌回。”显然产生于锡伯族生活在东北绰尔河松噶里比拉、兴安岭一带的狩猎生活,描写的是猎手骑马围猎的场景。《萨满歌》也是源自锡伯族萨满跳神时所唱的祈祷词,由萨满独唱的正歌和众人合唱呼应的副歌组成。以后又与田间劳动相结合,成了有特定曲调和节奏感的民歌。《耶奇那》是锡伯族古老的民间长诗,是写一对穷苦夫妇战胜困难,创建新生活的经历。民歌唱出了一对夫妇的渔猎生活,每段一、三行均以“耶奇那”开头,形成内容相连而故事结构并不连贯的叙事模式,语言朴实、和谐,曲调明快、上口,因此在锡伯族民间广为传唱。《喜利妈妈的传说》来源于锡伯族系绳纪事的历史和家庭保护神的传说。由于喜利妈妈在锡伯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才演化出各类传统故事。《人参故事》也来自东北时的采药实践。在这类故事中,被锡伯族尊崇为百草之主的人参被赋予舍身救人的老人或小孩的性格,可见爱之深切。①
西迁伊犁后,锡伯族出现了一批新民歌、新传说,并产生了书面文学作品。一些以农耕生活为题材的田间歌、情歌、习俗歌都产生于此时,《一棵沙枣树》、《秃鹰》、《熟石皮》等传说故事更多了些伊犁的地域特色。在书面文学作品中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辉番卡伦来信》、佚名的《喀什噶尔之歌》、锡笔臣的《离乡曲》等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锡伯族最难忘怀的是西迁的历史,于是出现了以西迁为题材的民歌《告别盛京》、艺术诗《离乡曲》和民间叙事诗《西迁之歌》。
从创作时间看,《告别盛京》作为民歌,可能在锡伯族迁徙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不过在各个时期经过民间诗人的不断加工、改编出现了不同的变体,而最终形成书面手抄本,大约是在锡伯族西迁后的100年间。《离乡曲》是锡伯族文人锡笔臣用汉文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的七言诗。而管兴才根据民间流传的迁徙诗歌素材创作的《西迁之歌》则晚得多,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从篇幅看,《告别盛京》民歌抄本是240行,《离乡曲》是120行,而《西迁之歌》则长达500余行。行数形成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告别盛京》为民歌,变体多,民间诗人对其增减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离乡曲》是文人创作,严格恪守汉族古典诗歌的创作规律,又是文言诗,言简意赅是它的特色,它以简取胜。《西迁之歌》是在各种迁徙民歌和文人诗作的基础上创作的,要概括锡伯族的西迁以及西迁后屯垦戍边200年的历史轨迹,就有了史诗般的长度,它是以繁取胜。如果从诗体分类看,《告别盛京》是民歌,《离乡曲》是艺术诗,而《西迁之歌》属民间叙事诗。
以锡伯族大迁徙为题材的诗歌受其文化心理、思维定式和民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锡伯族民间有念说“朱伦”(即长篇故事)的传统,有些是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有些则是根据其他民族的传说故事改编和加工的,如《三国之歌》等。讲述者有用散文体的,也有用韵文体的。但是不论哪种故事都讲究首尾呼应,结构紧凑,情节完整,往往以时间为序安排结构。这种以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线性模式谋篇布局的传统方式无疑对锡伯族的迁徙诗歌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无一例外,3部西迁诗歌的叙述都与历史叙述同步亦趋,呈一种单线发展模式:迁徙缘由——迁徙之日骨肉离别场景——迁徙途中的艰辛——迁徙后的屯垦戍边。但这绝不等于说,3部西迁诗歌都雷同化,而在表现手法上是各有千秋。地方民歌《告别盛京》重过程,在结构上采取以不同地点、不同场景为单元的空间转换模式;《离乡曲》重历史氛围,善于在横断面上撷取若干细节渲染迁徙的艰难;《西迁之歌》重情感宣泄,场面烘托,在时令变化中揭示不同家庭的坎坷经历。①
锡伯族的西迁在诗化之前,必然有段史化的过程,这是由锡伯族的特殊社会结构决定的。锡伯族在西迁之后形成以牛录为核心的整体社会组织,但每个牛录又由若干个以父系血缘为标志的血缘共同体——“哈拉”组成,而哈拉则由数个莫昆,即同一个哈拉内自然形成的血缘分支组成,莫昆由数个家庭群体组成,其下即是单一的家庭。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西迁史起初是作为一个哈拉或一个莫昆或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由长辈讲给晚辈听的,讲述者多着眼于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千百个家庭以不同方式讲述同一段史实时,锡伯族民众就更多了些关注整个民族命运的悲壮感,要让整个民族牢记这段历史,于是在缺乏出现史书的特定历史环境中,锡伯族人民选择了扎根于本民族土壤、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歌,后来文人参与进来进行创作。民歌语言精练,富有韵律感,易于传唱,便于记忆,成了西迁史最好的载体。
清代屯垦民间文学中,以回屯方式在伊犁屯田定居的维吾尔族民歌也占有一席地位,虽然他们的生产方式未改变,其他民族称这些人为“塔兰奇”人(意为种地的人),仅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三十三年从南疆移居伊犁种地的就有6000余户,但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和与各民族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歌也出现了维汉合璧的现象。有一首广泛流传在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唱道:“伊犁的大道上有个截梁子,大河沿子是腰店子,开辟了伊犁大道的是,你我这样的好汉子。”“截梁子”、“腰店子”均属汉语中伊犁的村落、小镇名,“好汉子”更是汉语,维吾尔民歌是音译过去的。这类维汉合璧民歌的每段歌词的核心词均是以汉语表达的。还有些通晓汉语的维吾尔族歌手还能用汉语演唱民歌,如《沙里洪玛来》就属伊犁维吾尔族的汉语民歌:
问:哪里来的骆驼客?沙里洪玛来,
骆驼跟前啥东西?沙里洪玛来。
答:哈密来的骆驼客,沙里洪玛来,
花椒、胡椒、姜皮子,沙里洪玛来。
问:吐鲁番好吗哈密好?沙里洪玛来。
答:哪达有钱,哪达好,沙里洪玛来。
一问一答,诙谐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美丽的阿瓦尔古丽》也是当时流行于伊犁地区的一首维吾尔族情歌。
第三节草原艺术
我们很难在草原文学和艺术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是因为草原文学中的民歌、英雄史诗、叙事诗等实在属于歌者的范畴,都是靠演唱征服听众和流传下来的。但记录下来的书面形式——诗歌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故往往又划入文学范畴。关于草原民族的民歌、英雄史诗等已在《草原文学》一节中论及,在此不赘。在这一节中主要是论及被称为草原视觉艺术的岩画、石人、鹿石和民间工艺等。而现代人将岩画、石人、鹿石等视为造型艺术时,对史前先民来说,它们都是功能性的。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仅仅作为纯艺术看待,应看做是先民的心理、精神的产物,具有文化功能意义。如果离开这点,就与这些史前遗物制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伊犁、阿勒泰、塔城是新疆史前岩画、石人、鹿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在已发现的新疆150余处岩画中,伊、阿、塔三地区就占了80余处。这些岩画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是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也有少部分是有史时代的遗物。伊犁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伊宁县、巩留县、昭苏县、霍城县、特克斯县、新源县等地境内。阿尔泰山系岩画分布于阿勒泰市、青河县、富蕴县、布尔津县、福海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等地。塔城地区岩画分布于塔城市、裕民县、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岩画中,90%以上画面反映有洞角类、鹿科类、马科类等10多种动物形象。
从天山、阿尔泰山的这些岩画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野生动物,只有极少数如马、狗等为家养动物形象,而且出现的人形图像或与动物间有某种关联,或是象征人类生殖的组合图像。这表明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后期伴有少量畜牧业,即使在游牧社会,也不完全排除狩猎活动),人们最关注的是氏族人口的繁衍和猎取动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猎牧社会的文化也是一种狩猎文化,但是天灾人祸,很难保证人口的高存活率和每次都能猎获动物。在这样一个前科学时代,巫术思维的产生直接导致人们借助于运用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正如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所言:“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巫术的世界。开始,原始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力’。奇妙的‘力’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存在和石头的坚硬、水的湿润一样的确定无疑。这种‘力’仅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超自然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真实的和自然。”①人们在信奉神灵之前,是普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的。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②巫术思维导致的是巫术操作。岩画正是施法者实施巫术操作仪式的工具。这种巫术思维和巫术操作一直从旧石器时代起,经过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有史时代。西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都充满着这种巫术仪式。从已发现的天山、阿尔泰山岩画中不难得知,人与动物生殖“力”的传递形式有四种:一是感应式;二是接触式;三是相交式;四是距离交合式,都属于交感巫术范畴。已完成的岩画既可能是自足图像,又可能是非自足图像。
西域岩画中有一类在我国其他地方绝少有的洞窟彩绘岩画,它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其一是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乌孙山发现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岩画绘于阿克塔斯山高1850米处的岩洞内,洞高2.5~3米,洞口宽5米。岩画绘于洞口右面岩壁上,均用赭石绘制。画面由7只北山羊、2匹马和2组大小圆圈和一个“〉”形及“◎”形、“工”、“)”符号组成。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第一个岩洞在半山腰离地面25米处,洞窟高11.5米,宽20米,深11.8米。岩画绘于洞顶和正面、侧面岩壁上。画面由一组4个里外两层中间为圆圈的椭圆形图案和两个圆圈、手印以及被认为萨满帽、铜镜的图形组成,此外还有一组表意符号和所谓的人面像。唐巴勒塔斯2洞距离第一洞约60米,位于海拔1000米处,洞宽4.9米,高3.2米,深4米。画面由拿弓箭欲射的两人、脚印、两只野兽和叉腿、手臂平放或上举的4组人形图像组成。其三是阿勒泰市西北25公里处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洞窟在海拔1000米处,高1.31.5米,深浅不一,从1~4米左右。在二组50余道竖短杠组成的类似围栏内分别绘有一椭圆形图案和双腿叉开,高举双手的人形图像。此外还赭绘有牛、马、大角羊的图像。其四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乡的洞窟彩绘岩画,为两处,一处在杜阿特沟,另一处在松哈尔沟。杜阿特沟洞窟彩绘岩画又分5洞。第一洞海拔650米,洞高不过1米,宽也仅1.6米,赭石绘有牛和人物图像,人头部有“V”形饰物。第二洞在海拔605米处,洞高1~5米,宽1.7米,深1.3米。画面由一双手下垂、有尾饰的人物图像和牛形象以及一些表意符号组成,其中布满大而有规则的赭石圆形斑点。第三洞只绘有较粗的类似栅栏的竖道。第四洞是两个双腿叉开、双臂伸展的人物图像,有尾饰。第五洞仅有两只牛和一个人物图像。人像头部有两仰角物,尾饰特征显著。松哈尔沟洞窟彩绘岩画在一个高2.5米,宽8米,深4.5米的岩洞内的洞顶。在洞顶10余平方米的岩画上绘有人、动物和其他符号,实为一巨幅岩画。画面中心为一匹有赭石斑点的马,四周绘有羊、虎、牛等动物,人物图像形状与前述洞窟彩绘岩画相同,但与动物图像比较,人形都较小。此外,还绘有6个大手掌印,似栅栏的竖道,赭石实心圆以及虚线组成的不知名图形。从图像看,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多次使用的痕迹。伊犁、阿勒泰洞窟彩绘岩画完全可以根据狩猎文化中的典型动物祭祀仪式和与之有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来加以解释。①
在这些萨满岩画中保留了法力强大的萨满的最早形象。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为带角的拟人像,这一形象同样出现在杜阿特沟洞窟岩画中,而这些萨满形象无一例外都附有尾饰。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媒介者,他的任务就是沟通地上人类与天上神灵。早期的萨满本身就是巫师,装扮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角”。萨满在一种出神状态下,借助神灵的助佑者——鹿与神沟通。头上带角萨满岩画正是象征萨满的助佑神灵。羽毛状头饰、放射状头饰的功能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些人形身下的尾饰往往被误释为阳具,这是不了解早期萨满的装扮所致。从欧洲奥瑞纳文化时期史前岩画发现,岩画上的巫师(萨满)头上戴着鹿角,身上披着兽皮,臀部安有马毛,全身呈激烈跳动状,这就是原始萨满的典型形象。因此,洞窟岩画中萨满也应是头戴鹿角、披兽皮、安兽尾的形象。当然萨满也装扮成鸟的形象,羽毛状头饰即属此种。在阿勒泰洞窟岩画中还出现戴面具的萨满形象。对萨满的这种形象,朱狄先生解释为:“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做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西域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头戴兽冠、披着兽皮的萨满形象。在一个氏族里,萨满既是沟通人神者,也是保证氏族繁衍、狩猎成功的力的源泉。从这点看,萨满头戴象征神灵助佑者的鹿冠,身披兽皮正是在进行狩猎巫术仪式,它并不是出于单纯模仿的动机。萨满面具早期也是狩猎祭祀仪式的狩猎巫术面具。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神秘的“力”把物体的推动力转向另一物体。之后,面具成为萨满的固定道具,又附加了跳神(包括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供奉等多种功能。
石人和鹿石是草原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草原中段的伊犁、阿勒泰、塔城的草原地带也是石人、鹿石的集中分布地域。这些地区的石人最初产生于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6~9世纪达到兴盛期,衰落于11世纪左右。鹿石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以地域分类为伊犁石人、阿勒泰石人、塔城石人等;按族属分类为塞人石人、乌揭石人、突厥石人、铁勒石人、蒙古石人等,亦按设置情况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还可以按雕刻技法分类等。鹿石主要根据碑体形状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也有按族属、典型与否分类的。在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石人手持器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中古时期。手持器皿者分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右手持杯状物,另一种是双手抱罐、碗、瓶、钵之类器皿。其他还有手握刀、剑等兵器和手托鹰等形象。即使是手持杯的石人,其杯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如阿勒泰市境内阿克塔木墓地石人右臂屈至胸,手执一种角状杯;而温泉县境内阿尔卡特石人右臂屈,手执圆底罐形杯;内蒙古巴兰恩特利格突厥石人左手下垂,右手置于胸前执一筒状杯;吉尔吉斯草原发现石人右臂稍屈直,手托高足凸肚状杯,有的石人右臂屈,手执高脚杯。从青铜时代开始,右手执杯状物或双手抱罐、钵等器皿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对于这类墓地石人手持器皿的含义,学者们作过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认为是饮酒的酒杯;(2)神圣的器物;(3)丰产的象征物;(4)盛动物乳汁物的器皿。几种解释都无大错,问题是这些器皿是作为一般的饮器,还是另有它用?谁有资格使用这些器皿?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使用?这些答案还必须在萨满文化情境中寻解。手执器皿者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少这类形象往往在腰带上佩有条状装饰物,但它们既非刀剑之类,也非装物的皮袋,而是在垂条或垂绳上挂有垂饰。这在南西伯利亚、中国新疆、蒙古等地的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都十分常见。此外,石人与一些遗迹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有两种情况:一是石人竖立在祭祀石堆附近,石堆下面埋有牺牲的残余,有动物的骨骼、祭祀灰烬和各种器物,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6世纪的石人就属此类;二是南西伯利亚、中亚、内蒙古、新疆的确存在墓葬区的石人,齐木尔齐克石人墓的发掘证明墓地石人从青铜时代一直延至铁器时代。这些考古发现恰恰证明执器皿石人应是萨满形象,因为在后世萨满形象中的确能见到穿条状萨满服,腰带系垂绳挂铃、镜、挂饰、石球、动物骨关节等饰物的情景。萨满作法时这些物件叮当作响,目的是以响声传达人间与神界的信息,这些物件也是除邪镇魔的利器。结合遗迹关系分析,无论是祭祀堆石人还是墓葬区石人,均是萨满祭祀的形象,不管是祭祀祖先还是举行狩猎等仪式,都离不开萨满,他们总是这些仪式中的主角,不过祭祀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现在回到手持器皿的萨满形象上来。对于萨满来说,所用器皿是神圣的,同萨满神服、神帽、神具一同组成萨满的神物。阿契门尼德时期波斯的契形文字文献将塞人分为三大支:提格拉豪达塞克(尖帽塞克)、豪玛瓦尔格塞克(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和提艾伊·达拉伊雅塞克(近海塞克)。其中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极有可能是指其首领(也是萨满)是饮用豪麻汁的,即一种麻醉汁。据说萨满通神时必须处在一种迷狂、神志恍惚的“出神”状态,需要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因此,石人所持的也应是盛豪麻汁的器物。在充满萨满教信仰的氏族部落社会中,萨满最有资格持盛豪麻汁的器皿。在氏族、部落中萨满的神圣职能几乎囊括氏族、部落的所有活动,如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生产与生育、神判与记事等等。从近世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得知,萨满使用盛器见之于以下活动:一是治病时的喷术。起先治病时是喷气,后来是喷酒或水、药。在诸如得疮伤、骨折、长疖子、中风不语、口眼歪斜、错迷不醒等疾病时,往往用盛器盛水、酒或熬制的草药运气喷至病人身上,以达消炎、驱热之效。萨满常常在跳神治病仪式上向患者施之喷术,喷术功也成为萨满的内养功,平时要坚持练运内气、吹功。由此观之,立于祭台前的手执杯类器皿的石人应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上的施喷术的形象。二是与萨满教的神偶嗜血的灵魂观有关。“萨满教观念认为,血能育魂养魂,魂血相生互卫,所谓魂依血流,血行魂行,血凝魂止,则浮离体外,曰浮魂。魂依血养,魂凭血育,血旺魂壮,血热魄强,无敌天茬,鬼魔难当,曰养魂。神偶作为灵魂的依托体,其保持灵性和神性的奥秘在于常享祭物,尤以嗜血最益于养魂,使偶体内的灵魂常存。基于这种观念,萨满祭祀十分重视备牲、养牲、杀牲,无牲不祭成为萨满教不成文的规则。”①于是在萨满教祭祀仪式上,萨满常常是在神灵附体后,手持盛动物血的器皿喝血,也往往将器皿中的血弹或涂在祭祀的神偶身上。手持盛动物血器皿的石人也应是血祭诸如祖先、酋长、英雄等神偶的萨满形象。三是蒙古族的“行博”仪式也离不开容器。古代蒙古族凡进行渔猎、游牧、征战、治病、占卜、送葬、祈雨等仪式时都要请博(萨满)进行祈祷请神、附体求神、送神活动。在仪式中萨满常常在室外手持酒杯向诸神敬酒答谢,感谢神灵的庇佑。四是萨满为显通神的法力,常常要喝下圣水(可能是清水、酒或动物血等),目的是神灵会更显神力。在喝圣水时,萨满往往双手持碗等容器,以示虔诚。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对于索解手持盛器的草原石人之谜应是合乎情理的。
欧亚草原上的鹿石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此,仅探讨雕刻有鹿纹的典型鹿石。这些鹿石上的鹿形有如下特征:喙状头部前伸,嘴巴大张;两只枝状角仰向背部,一上一下(这说明与那种严整的动物侧影形不相符合);额部相应地有两处前突起;颈部和躯干前半部过长;前后腿相距甚近,一般都小而细得不合比例,有时仅有上半截,像被砍断一般。有时,当腿部全部雕刻出时,则呈弯曲状,前腿离于后腿,二者连接不严,中间留有空隙。蒙古——外贝加尔和中国新疆发现的鹿石都属此类带有图案化的鹿纹样的类型。雕刻这些鹿形图案的鹿石是一些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的石柱或石板。不过晚期的鹿石并非通体都是鹿的图案,而是雕刻成人形,这类鹿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鹿石是做什么用的?鹿形图案有象征意义吗?这不能不与欧亚草原民族的早期萨满教信仰联系起来考虑。在萨满教世界观中,高山、大树都是作为萨满通神的宇宙山、世界树出现的,而方柱体、圆柱体的鹿石也应是萨满通天通神的工具。萨满是一个送魂者,保证祖先或英雄的灵魂升天而不是人地狱的方式是在祭祀仪式中以巫术操作手段通过刻凿鹿石中的图像达到其目的。研究者认为,在萨满教中往往出现萨满庇护神:“每个萨满,肯定都有一个动物母亲或动物祖先。它通常被描绘成大角鹿,有时也是一头熊。这个动物自己生活,不与萨满在一起。大概,最好是把它设想成在大地上飞翔的,萨满那火一样的力量”①。不过从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材料发现,庇护和培育萨满的精灵常常是鹿、鹰、蛇等,其中鹿和鹰是萨满庇护神最具代表性和最权威的形象。鹿石上刻凿的鹰喙鹿身图案正是萨满庇护神的形象,天上飞翔的鹰与地上奔驰最快的鹿的组合已经成为普遍的萨满职业象征。特别是那些有人头形和鸟喙鹿身的鹿石是萨满正在实施巫术时的产物,刻凿过程也是巫术操作的过程。这是后代萨满通过这种巫术操作与前代萨满(祖先)的灵魂沟通。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鹿、鹰等萨满的庇护神或者是亡故的前代萨满,或者无异于萨满的配偶,抑或还是晚辈萨满的庇护者。因为萨满的灵魂均是由这些动物庇护神作为向导和保护者前往上界的。难怪有些鹿石上部刻凿有象征天界的圆圈、圆点和半月形纹饰,它们与人头形、鹰喙鹿身组成萨满灵魂升天的全景式图像。不过,鹿石雕凿展现的是萨满通神时巫术操作时的文化情境,而萨满服的缀饰变成了凝固的符号象征物,但它们在萨满教信仰中同样是神圣的。
在草原艺术造型中,动物纹样占有特殊地位。塞人、匈奴、大月氏、乌揭等早期部族的动物纹样来自于猎牧活动中的动物。常见的凶兽猛禽,如狮、虎、熊、鹰、狼、鹿、豺、野猪等,也有驯养的马、牛、羊、狗等形象。特别是一些野兽形象,多为啮咬、争斗状,形体往往扭曲变形。无论是塞人风格的动物纹样还是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绝对不是出于审美需求的艺术装饰,而具有功能意义。这些部族把动物形象装饰在牌、扣、钩、徽章、矛、剑、马具、带等须臾不离身的物件上是视其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塞人的狮神、吐火罗人的双马神(即龙神)、车师人的虎神、匈奴人的神兽、鲜卑人的瑞兽、蒙古人的“白海青”等,或来源于早期氏族图腾,或衍化成部落保护神。鲜卑人的带钩——犀比为瑞兽,即神兽,实际上鲜卑就是以“瑞兽”相称的部落。草原民族的这类动物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早期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以后在普遍存在的萨满教信仰中被信奉为部落保护神了。即使这样,功能性的动物纹样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草原民族个性和心灵世界的基本表现方式。
所谓草原民间工艺艺术是在传承中积淀凝聚民间智慧,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定型,富有民族普遍性并产生于日常生活能够真实反映草原民族心灵世界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弥漫于日常生活有普泛性。游牧民族的毡房、马具、服饰、毡毯都富有装饰性,特别是讲究以自然界的花草、动物角等抽象变形对称装饰,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搭配色彩。这种色彩搭配往往反差强烈,色泽艳丽。装饰用具、美化生活几乎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存在没有装饰的生活,也不存在离开生活的装饰。如果细细列举,诸如手帕、荷包、头巾、枕头、腰巾、围裙、毡帽、毛袜、领口、袖头、衣襟、裤角、被面、垫褥、罩单、帷帘、壁挂、壁围、花毡、织毯、草帘、编带、马褥、披肩等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恰到好处的纹样和色彩加以装饰美化。一些几何及植物纹样装饰图案的出现不能单纯归于某些游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后反对偶像崇拜所致。其实,这类装饰性图案起源很早,不亚于动物纹样。在塞人金银器中,匈奴织物中除动物纹样主题外,同样有花纹、三角形、圆形等装饰性图案,似乎都不是写实风格的。
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其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对象关系及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都直接联系着他们的文化艺术。他们在马背上吟唱着牧歌和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喜庆场合高唱婚礼歌、祝酒歌,并以歌舞相娱;他们的腰带上佩挂有镶嵌对兽猛禽图案的牌饰、带扣、短剑;他们在所迁徙之地雕琢了无数幅岩画;他们还在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座石人像、鹿石;他们还在毡毯上、服饰上飞针走线,留下了流光溢彩的精美图案..他们的艺术无处无时不在,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圆形毡房也富有艺术韵味。
第四节屯垦艺术
屯垦艺术的主流是清代汉、满、锡伯、维吾尔等民族的民间艺术形态。西域历史上的屯垦虽然兴于汉代,盛于唐代和清代,但汉唐时期伊犁屯垦艺术究竟如何,无论是典籍还是考古发现,都未能提供更充分的依据,但仍有遗迹可寻。西汉时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的随行人员中就有乐工等人,还带来中原乐器等。乌孙公主也曾一度“遣女至京师学鼓琴”,但范围有限,并未广泛流传。而在文化交流中,中原丝绸在乌孙王庭是流行的。乌孙国都赤谷城还建有汉族风格的宫室和房屋。这是汉族建筑艺术在天山以北地区的首次出现。唐代屯田和元代定居建筑,应该在伊犁地区广泛分布,但现在大多荡然无存。元代的阿力麻里城,意为“苹果城”,是元代西域地区的名城,但现已无城墙等遗迹。遗址曾出土元代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官窑特制的青瓷、白瓷盘、碗等文物。唐代丝织艺术品曾在昭苏县境内波马古墓中出土,属6世纪遗物。这三件丝织品分别是“富昌”文字锦、方纹绫、缀金珠绣织物。“富昌”锦以黄色为地,用红、绿、深褐色显现花纹,花纹为横向云气纹和不同形态的动物纹,间织“富”、“昌”等汉字铭文。汉锦是汉唐时期流行在西域的织锦,大多属吉祥文字锦,是为满足人们求吉祈福的心理需求。这类织锦均为汉地所产,但图案纹样明显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可能是为西域上层人物专织的。
当到了清代另一轮屯垦高潮来临时,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清代伊犁地区屯垦艺术的魅力,无论是世俗艺术,还是宗教艺术。清代伊犁屯垦艺术是满、汉、锡伯、维吾尔等屯垦民族的民间艺术。这些屯垦民族多杂居,特别是居住在城镇中,因此,在保持本民族艺术前提下,艺术交融也十分频繁。
伊犁、塔城等地区汉族的民间艺术往往与他们的民间信仰有关,也就是说,设祠供奉各种民间神祇的场所也就出现了庙会活动,这里集中着汉民族的诸多民间艺术形态。据民国初年到达新疆的谢彬在其所著《新疆游记》中记载,塔城汉城就建有财神庙、龙王庙、刘猛将军祠等。1908年所修《伊犁府乡土志》也记有伊犁九城广设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先农坛、祈谷坛、神祇坛、龙神祠、昭忠祠等。①惠远城也有津商商业区。按汉族习俗,庙会成为定例,如农历三月十八日的观音庙会、农历四月初八的药王庙会、农历六月六日的龙王庙会、农历六月十五日的八仙庙会等。庙会成了汉族居民的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散发着民间艺术气息。这里荟萃着全国各地的花鼓戏、闹龙灯、秦腔、眉户、高抬、跑旱船、舞狮子、高跷、中幡等多种民间表演艺术。艺术交融中莫过于新疆曲子戏对屯垦居民的影响大了。新疆曲子戏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甘肃民间艺人夏三通组织敦煌曲子戏进新疆演出,之后,它很快被新疆的汉、回、锡伯、满等民族接受,在城乡普及开来。新疆曲子戏是个博采众长、吸收融合各种音乐成分最杂最多的剧种。它最早是在陕西眉户剧音乐的基础上,在西渐的过程中融进兰州鼓子词、敦煌佛曲音乐等形成。流传到伊犁地区演变为新疆曲子戏的过程中,锡伯族的“秧歌调”几乎全被吸收融合。锡伯族的“秧歌调”分“平调”和“越调”两种,它是锡伯族吸收汉族“秧歌调”演变而成的一种戏曲音乐。新疆曲子戏音乐中的“天山令”还吸收了哈萨克族民间音乐成分。新疆曲子戏的白口完全是本地化的新疆汉语和方言俚语,还融进了维吾尔、俄罗斯等民族的词汇,全国各地方言俚语也夹杂其中,从语言上讲它成了新疆汉族或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都能听得懂的语汇。在伊犁,锡伯族每逢节庆婚嫁都演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以历史和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曲子戏,出现了诸如寿谦、恭金保、郑禄、安林、郭瑞、铁山、郭梅英等有名的艺人。他们所演曲子戏既有汉语的,也有锡伯语、汉语夹杂的戏。虽然新疆曲子戏原型脱胎于眉户剧,但在演进中已非原来的音乐,它一旦与新疆各民族音乐杂交后就显示了自身的优势,这要归功于清代大规模屯垦移民带来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勃兴。
清代伊犁的屯垦艺术中汉族或仿汉式建筑艺术也是十分典型的。伊犁九城是传统的汉式城市布局。它遵循的是“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的汉族传统建城原则。伊犁九城是以自然地形布局理论规划的,特别是惠远城因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故更讲究天材、地利诸因素。伊犁地区的喇嘛教寺庙除受藏族建筑艺术影响外,主要是受汉族建筑艺术影响,遍布于锡伯营八个牛录的关帝庙、娘娘庙等供奉民间神祇的庙宇也属仿汉式建筑。在这些寺庙建筑中规模较大的是锡伯族喇嘛教寺院——靖远寺。该寺占地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整个寺院是汉式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庭院式建筑。寺院坐北朝南,正南为砖雕影壁,进两侧山门为东西两小院,东为土地神庙,西是木栅栏小隔房,内立守门神塑像。正门两侧各有一石雕雄狮,进大门后依中轴线分别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世佛大殿。院内东西两侧还修有钟楼、鼓楼以及铁铸大香炉、木牌楼、偏殿等。三世佛大殿亦谓藏经楼,属木雕牌楼式两层飞檐建筑。大殿高尖屋脊,琉璃顶,翼角飞檐上挂12个铁铃。殿内供奉三世佛塑像,两侧为藏经阁。靖远寺已非单纯模仿汉式佛教或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它在充分吸收、融合汉藏建筑艺术的同时又渗透着锡伯族的审美观。无论是寺院大门上镌刻的锡伯文“靖远寺”金字,还是砖雕、木雕、彩绘、泥塑都显示了锡伯族工匠的高超技艺,融进了锡伯族人民的审美观。因此,靖远寺是屯垦民族建筑艺术完美融合的产物。
锡伯族民间装饰艺术不仅表现在庙宇等建筑中,主要的、大量的还是常见于日常生活中的艺术现象,如服饰的装饰以及门帘、墙饰、鞋、枕头、家具、荷包、烟袋、箭袋、首饰等无不充满艺术想像力。锡伯族的民间装饰图案主要是花卉、飞禽、走兽等植物、动物纹样图案,也有几何纹样、山水图案等。这些图案纹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牡丹、荷花、莲花、菊花、孔雀、凤凰、鹿、鸳鸯、蝴蝶、飞燕、仙鹤、龙、菱格形、方形、三角形等。选择的花卉和禽兽图案都表达着锡伯族人民求吉祈福、追求祥瑞平安的民族心理。色彩上以红、黄、绿、蓝为主色调,在图案布局上讲求对称。锡伯族男女婚嫁时,新房内往往有一种喜帐的挂饰物,它充满喜庆气氛。喜帐为大红绸缎或棉布料,最典型的是在正中绣有装饰性花卉图案,两侧绣有一对对称孔雀图案。帐下底边处绣有一排组合型喇叭花。孔雀上方有时还绣有祝福性的锡伯文。即使像婴儿吊床的装饰图案,一侧是对称性的弓箭组合图案,另一侧是以太阳纹为中心的对称飞龙舞凤图案,也折射着祈盼所生儿女成龙成凤的求吉心理。锡伯族家用的卧柜、竖柜、供桌、被橱等出现了较复杂的木雕技艺,圆雕、透雕、浅浮雕手法都常用,多数是宝瓶花卉对称图案。锡伯族女式绣花鞋就有无梁绣花鞋、双梁绣花鞋、单梁绣花鞋多种。绣花部位多在鞋头、鞋帮,常绣有牡丹、荷花、菊花等,亦有红底绿花、黑底红花多种。在此,对称是在整体布局中,以线条和色彩以及各种纹样图案之间的节奏、比例、复合、简繁、线条、色彩关系的和谐。在色彩上,锡伯族更多的是诉诸于感觉。从红色、黄色中感受到热烈、温暖;从蓝色、绿色中联想到凉爽或寒冷;黑色和白色从色度看,有明暗之别,因为这种性质归因于它的亮度,而不是它的色彩。锡伯族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深谙整体图案中,线条、图形、色彩互为关联,相互配合才能构成审美意义上的图案艺术。
在锡伯族宗教艺术中以萨满教神像、神歌、神舞三位为一体构成神圣世界。虽然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其造型和声态形式是功能性的,但所唱神歌、所跳萨满舞和所画神像蕴涵着艺术的种种因素。如:锡伯族的萨满画是萨满在举行祭祀祖先、上刀梯和跳神治病仪式时悬挂的神圣物,用毕即入匣收藏。萨满画按其绘画内容和功用大致分为三类:群体神像图、萨满画像和动物神灵图。20世纪初俄国人克洛特科夫在塔城发现锡伯族萨满神像图后,20世纪80年代锡伯族学者又在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现同一内容的群体神像图。这是布绘图像,其画面自上而下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最上一层画面为彩云、日月和“依兰恩杜里格格”(三位神姐)和“顾兴阿玛法”(男祖神)。这些祖神周围是虎、狼、狐狸、蛇、鹿等动物精灵。第二部分是各具神态的岱木林、阿玉鲁、额依嫩德德塔斯胡里、艾土罕、善琦、达玛法、阿里玛法、玛法默尔根、萨满玛法、着勒玛法等男女神灵形象。第三部分为合掌或单手祈祷及举杯为上刀梯者助威的近10位男女神灵,如张纳、着青额、纳松额、吴凌额、齐发罕珠、色楞芝等。第四部分为刀梯两侧的2位骑马萨满。第五部分画面最下端画有供桌,上置燃香的香炉。供桌右侧为3位手持神鼓萨满,左侧为一条白牛,后面为直入云端的刀梯,梯顶站立着萨满。这是一幅供上刀梯仪式时使用的画像。上刀梯仪式是锡伯族萨满教的独有仪式,举行这种象征仪式的动机据研究者认为:一是告诉人们通达神界并非易事,只有踏上实实在在的“刀梯”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并且暗示,不会人人都能做神界和人间的使者;二是显示萨满真有通达神界和治病救人的本事;三是为了区别有真“本事”萨满和无能萨满。画像中的众神灵既有萨满祖师、祖先神,也有瘟神、动物保护神等,甚至还出现了门神、灶神等。萨满在举行上刀梯、跳神治病等仪式时总是在其祷词中呼喊众位神灵,请神助佑其仪式成功。萨满画像是绘有萨满形象的图画。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幸福乡锡伯族民间发现的一幅萨满画像画面为:一位头戴三只鸟装饰神帽,身着萨满服的萨满坐于方凳上,左手高举绘有蛇形图案的萨满鼓,右手举至胸前微握,神像旁是一跪着的男子,面向萨满。萨满下面绘有水波纹,其上是一条飞龙。这类画像显然是哈拉姓氏或莫昆(家族)萨满祖神形象,是专供哈拉或莫昆后代萨满祭祀时使用的,有时在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悬挂,以便从祖神处求得神力。
动物神灵图是每一个萨满专用动物精灵的形象画像。动物精灵在锡伯语中称“巫出固”,实为萨满的动物保护神。每一个萨满均有自己的“巫出固,”有的是雕神,有的是虎神,有的是狼神。“巫出固”作为萨满的助手在跳神治病时助佑主人与病魔搏斗成功。在萨满“巫出固”中,虎神是女萨满保护神中的主神。
由于萨满画是功能性的,因此并不要求形似,也不可能形似。因为萨满画都出自民问画师之手,也有的是萨满本身绘制的,也就难免有很高的绘画技巧,而且作为仪式中的萨满画仅仅是个象征物,并不需要神形毕肖。由于萨满教仪式分为家祭仪式和公众集会仪式,萨满画也有所不同。家祭仪式中的萨满画可能是本族先辈萨满或祖先的形象,而像上刀梯仪式是一种广场式的公众集体仪式,所以悬挂的就是绘有众神的上刀梯图。萨满画中的人物服饰明显具有时代特征,一幅绘于清代的萨满画中的祖先神著的就是清代官服。
在屯垦艺术中,清乾隆年间以回屯身份屯田于伊犁的维吾尔族从世居的天山以南地区带去了他们的乐舞艺术,并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伊犁木卡姆和麦希莱甫,这是一种民间传播的方式。另一种是由木卡姆艺术家将其带到伊犁。据考证,清光绪十九年(1893),喀什著名的木卡姆艺术家穆罕默德·毛拉等人把喀什木卡姆带到伊犁,于是促成了伊犁木卡姆的形成。伊犁木卡姆同样由十二套组成,即1.拉克木卡姆;2.且比亚特木卡姆;3.木夏乌热克木卡姆;4.恰尔尕木卡姆;5.潘吉尕木卡姆;6.乌扎勒木卡姆;7.艾介姆木卡姆;8.乌夏克木卡姆;9.巴雅特木卡姆;10.纳瓦木卡姆;11.于孜哈尔木卡姆;12.玉赛因木卡姆。和喀什木卡姆比较,伊犁木卡姆没有“琼拉克曼”部分,只有“散序”、“达斯坦”和麦西莱甫,但结构相同,因此伊犁木卡姆应是喀什十二木卡姆的翻版,称为喀什木卡姆伊犁版更恰当。伊犁木卡姆在结构上除开始的散序外,在各曲之间还有过门和间奏。伊犁木卡姆调式与喀什木卡姆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布局上,常采用不同调式作对比并在调式转换时常常运用主音位置不变而变换调式的手法。伊犁木卡姆形成2/4、3/4、4/4、5/4、6/4、7/8、9/8七种基本节奏型。据一些田野调查资料披露,穆罕默德·毛拉精通十二木卡姆,他是将有72个达斯坦乃合曼(分别取材于不同的12部长诗)的达斯坦部分带入伊犁并广泛流传的艺术家。他在伊犁生活了40多年。他的弟子艾山弹拨儿、肉孜弹拨儿、玉赛音弹拨儿、巴拉提弹拨儿等人也对丰富和发展伊犁木卡姆有所建树。其后,还有则克力艾里帕塔搞出了一个含有一个序曲、一个太孜、六个达斯坦的糅合沙里木卡姆。这是富有伊犁特色的有创新意识的木卡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演的维吾尔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就采用了糅合沙里木卡姆中的达斯坦乐曲。
麦希莱甫是木卡姆大曲结束后的载歌载舞部分,有“集会”、“聚会”之意,是一种民间性的娱乐歌舞集会。麦希莱甫分“喜庆麦希莱甫”、“集体麦希来甫”、“邀请麦希莱甫”、“节日麦希莱甫”、“和解麦希莱甫”等不同形式。麦希莱甫因地域不同形成各异的民俗文化表征。伊犁麦希莱甫自然也充满了地区性的文化特征,如形成同龄人之间的冬季轮流麦希莱甫、河边野游麦希莱甫等。这与伊犁风光秀美,维吾尔族有野游的习俗有关,这时也成了举行麦希阿莱甫的最好时光。麦希莱甫除载歌载舞外,还穿插有各种民间游戏娱乐活动,如抢腰带、献茶唱歌、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惩罚”性游戏等。节庆婚嫁时的麦希莱甫以参加人数多、场面宏大、气氛热烈而著称。
吟咏歌唱近乎草原游牧民族的天性,于是产生了与他们生产生活及其习俗密切相关的草原民歌和传说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形式是构成草原文学的主流文学,特别是在早期更是这样,而书面文学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关于活动在伊犁、阿勒泰等草原地带早期民族的口头文学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这些充满草原气息的民间文学也随着这些民族的消亡而消失了。活动于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中的塞人、匈奴、呼揭、月氏、乌孙、铁勒等部族肯定都是富有口头文学传统的草原民族,如果不是汉文典籍偶有记载,人们对他们的民歌几乎一无所知。汉文文献存留了一首《匈奴歌》和另一首《敕勒歌》,前者是匈奴人痛失草原的绝唱:“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一泣一唱,一哭一回头,是多么的痛心疾首。后者被认为是铁勒(即敕勒)人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抒情味极浓的民歌,正如《诗薮》所言:“此歌成于信口,咸谓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无意发之,所以浑朴苍茫,使当时文士为之,便欲雕绘满眼。”天然无雕饰的民歌总是以清新、淳朴的秉性博得人们的青睐,远非文人创作能比。早期草原民族的吟唱中除淳朴、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外,还有一种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密不可分的萨满歌,即祷告歌。它是萨满在举行周期和非周期性祈祷仪式时的吟唱,属咒语一类的韵文。在献祭仪式、治病仪式、征战仪式中吟唱祝文是萨满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草原早期民族的战歌、情歌、摇篮曲、哀歌、婚礼颂歌等,在最初都是具有巫术、宗教的意义,带有咒语的性质。越是在早期,萨满在氏族部落中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萨满的祷告歌也无处无时不在,成为神圣的祈福禳灾的吟唱。
在草原文学中,古代突厥人和成吉思汗西征前操突厥语诸部落的民歌独树一帜,对后期草原诸民族的民歌也曾产生广泛影响。自6世纪80年代西突厥统辖阿勒泰以西广大地区后,突厥文化成了阿勒泰至伊犁草原地带最主要的草原游牧文化,而自9~13世纪则有诸如葛逻禄、炽俟、踏实力、样磨、乌古斯等操突厥语部落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突厥语大词典》中对各操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进行了介绍,并辑录了这些部落的民歌作为例证。这些民歌中很可能包括西突厥人的民歌,因为9世纪后的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不少就是从东西突厥汗国中分化出来的游牧部落。从大词典所记“伊犁”、“额尔齐斯”等地名、河名看,他们都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他们的民歌多与草原景物、狩猎活动以及生产生活习俗有关。一些狩猎民歌可能是古代突厥人的早期民歌,因为绝大部分草原游牧民族早期均是狩猎民族,而演进到游牧民族后,狩猎仍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大词典所录一首狩猎民歌为:
擎兔鹰,
跨骏马,
追逐盘羊,
放猎犬,
捕狐狸,
猎取黄羊。
活脱脱一幅紧张激烈的草原狩猎图。更有些狩猎民歌擅长描写猎犬捕狼时的打斗场面:
我的狗把它扑翻在地,
狠劲地撕咬它的毛皮。
把它的脑袋按在地上,
用利爪扼住了它的脖子。
这种描写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动感。也有些狩猎民歌是展示年轻猎手本领的:
带兔鹰去狩猎,纵猎犬去撕咬;
用石击狐狸野猪,
我们以本领自豪。
用石击都能捕获猎物,可见身手不凡。草原游牧民族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马,马是他们的坐骑,用于放牧、狩猎、迁徙,于是出现了大量以马为题材的民歌。有一首民歌是以驯马为题材的:
跨上烈马任它跳,
把那烈性驯服了;
让狗去追回猎物,
我们希望它猎到。
寥寥数语交代清楚驯马过程后,又叙写驯马与狩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在长期以马为伴的生活中,还积累了识马、相马的丰富经验,特别对疾驰如飞的骏马钟爱有加:“骏马在疾驰飞奔,马蹄下贱出火星;火星点燃了枯草,火焰在熊熊燃烧”。略嫌夸张的手法让人们领略到骏马如飞的身姿。同样,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十分熟悉所饲养的各种羊的习性,特别是公羊和母羊的分群、母羊和羊羔合群是能否挤奶的标志:“公羊公山羊分开了,母羊群会集起来了,乳汁统统地流出了,羊羔山羊羔合群了”。一般在夏季母羊与公羊分群,母羊合群后挤奶季节就开始了;而母羊和羊羔合群,由于哺乳羊羔,就不再挤奶了。他们经过严冬后对万物复苏的春天充满了喜悦:“山头被绿色笼罩,遮盖了隔年干草;湖泊盈溢着春天,公母牛哞哞欢叫。”这首民歌是春天的赞歌,满目葱绿,牲畜繁衍,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赏心悦目呢?①
应该说,蒙古人活动于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的历史并不短,从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起,到卫拉特蒙古四部,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了。但蒙元时期生活在阿力麻里一带蒙古人的民间文学状况怎样,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像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蒙古人对阿力麻里的征服,但不见有这一地区蒙古族民歌的只言片语记载。生于波斯的志费尼倒是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蒙古人征服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时的诗歌。这些诗歌多是对成吉思汗及诸子西征战绩的歌颂和征战场面的描写,但已非民歌范畴,而是被征服地的文人创作了。蒙古人的文学传统——包括民歌、英雄史诗、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文学形式经数百年的口头传承,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蒙古族民歌中最被称道的是长调民歌,这些长调常常是高低音同度一致的,但当两个或更多的蒙古人一起唱时,往往有出色的歌手唱出延长音,延长到他的肺活量的最大限度,然后由他继续把它唱下去,好似是其他歌手的回音一般,从而使这首抒情曲与复调多重唱相似。蒙古族民歌中还有一种短调,因风趣幽默、节奏明快、曲调活泼,又称其为诙谐歌曲。像土尔扈特蒙古的《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就是歌手即兴演唱的抒情长调,歌手反复用本嗓和假声演唱,歌词是歌手即兴吟成的,是对繁茂的伊犁河谷秋天的回忆。长调显然属于牧歌一类。察哈尔蒙古的《高山上的花》、《金纽扣》、《想念我的家乡》都属短调民歌。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民歌除牧歌外,还有赞歌、酒歌、情歌、婚礼歌等多种形式,如《西部可汗》、《可爱的暗褐色小马》、《我可爱的小雄鹿》、《额林哈毕尔噶山》等。由于马在卫拉特蒙古人生产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它也成了情歌重要描述的对象。对马的情景描写实际上是暗指情人,如《花色马》:“骑上我的花色马,一溜烟尘过大山。亲爱的哥哥讲的话,时刻铭记我心间”。还有《心爱的枣骝马》描写道:“乘上心爱的坐骑枣骝马,在无垠的草原上飞速驰骋。我热恋的心上人哟,喁喁的情话镌刻在我心中。”这种看似雷同
①所引民歌均见《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的思路,往往是随手拈来,即兴吟唱,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都明了其意并不在马,而在于情。因感受、理解不同,同是对马的情景描写,各自成趣,毫不乏味。但是,在卫拉特蒙古人看来,骏马往往是和英雄相匹配的,于是有了那首歌唱土尔扈特人的英雄罗布桑察纳布及其骏马的民歌:
在白雪覆盖的高山之顶,
屹立着一所帐篷。
它白如白雪皑皑的山峰,
罗布桑察纳布在门口凝视着南方的地平线。
他的白色种马飞奔得比箭还快,
他骑上它追上了野鹿。
鹰靠强健的翅膀追捕野天鹅,
而罗布桑察纳布的敏捷胜过最强壮的鹰。
很多人都羡慕罗布桑察纳布,
但他们在战斗中才知道最伟大的要数黑色的鹰罗布桑察纳布。①
它在卫拉特蒙古诗歌中英雄史诗占有独特地位,《江格尔》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讲述的是蒙古族英雄江格尔及其十二“雄狮”、三十“虎将”、八千勇士与恶魔蟒古斯斗争的故事。《江格尔》由世代江格尔齐演唱、加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江格尔》属长篇巨制型英雄史诗,现在见到的是搜集整理出版的十五章托忒蒙古文本,还有十三章等汉译本。其实,民间流传的《江格尔》远比这长得多。据一些蒙古族老艺人回忆,有一种七十回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据蒙古族学者色道尔吉研究认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是土尔扈特人民集体的口头创作,是他们智慧和感情的生动反映,到明代,成了四卫拉特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后来通过江格尔齐的演唱和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国内外蒙古族人民聚居地区。《江格尔》歌颂的是蒙古人的理想乐园——宝木巴以及以江格尔为代表的宝木巴众多勇士,并揭露了奴隶制社会现实的丑恶。富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江格尔等人也成了反抗邪恶、铲除社会不公、创建和保卫宝木巴的象征,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推崇的英雄。《江格尔》在世代流传中也融进了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是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江格尔》中多处出现阿尔泰山、白头山、额什尔鄂拉山、额尔齐斯河、乌古伦河、奎屯河等山名、河名,这与卫拉特蒙古四部活动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毕竟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卫拉特蒙古在长期游牧生活中,或出于启迪教化的动机,或作为闲暇生活消遣的方式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和寓言故事、降妖伏魔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生活故事、讽刺幽默故事等。卫拉特蒙古的动物和寓言故事有解释动物外貌、习性特征的解释性故事,也有哲理性的有教化功能的寓言故事,还有图腾性的动物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征是:说是讲动物,实际在讲人;说是讲人,又明明是讲动物。基本上都属于以动物喻人,以动物事寓人事的故事。如《狐狸和熊》、《骆驼为啥在灰土上打滚》、《骑大红马的阿勒泰台吉》、《白雪和兔子》、《粮食全留给了青蛙和蜘蛛》等都属于以上三类动物故事。降妖伏魔故事大多是讲述民间流传的蒙古族的英雄故事,这些英雄都有降妖伏魔的神勇、神力,是百姓仰慕的对象。如《红脸勇士乌兰·哈茨尔》、《聪明的苏布松·都日勒格可汗》、《英雄布赫蒙贡·希克萨尔》等。还有些虽非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一些无助的孤儿、美貌的姑娘、年轻小伙、年长的老人等,但都是一些伸张正义、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人物,也成了这类故事的主人公。一些神话传说故事虽然都是幻想、想象的产物,但在这些神话世界中也有现世的影子,如用神话解释宇宙和各种自然现象起源,解释本民族始祖起源,解释诸如本民族风俗、伦理、器用、技术等的起源。《神女的恩惠》就是杜尔伯特蒙古人始祖的神话故事。讲述一个青年猎手和天女幽会生下一男孩,这位男孩长大后成了一名真正的勇士,也成了杜尔伯特人的祖先。这自然也是蒙古人天神崇拜观的反映,他们笃信,自己的祖先就是天上神女的后代。在卫拉特蒙古四部中更多的是世俗的生活故事和讽刺幽默故事。放牛娃、流浪女、放羊娃等都是一些善良、聪慧机智的人物,而章京、王爷、吝啬鬼、懒汉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讽刺、揄揶的对象。《聪慧的放牛娃》就是广泛流传于卫拉特蒙古四部的古老生活故事,是一系列单篇故事构成的组合故事。《阿尔格齐的故事》是机智人物故事,由《出丑》、《乞肉》、《懒汉》、《吹牛》、《戍马》等数十个系列故事组成,讽刺辛辣,妙语如珠,有极强的警策作用。①
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歌是哈萨克人的翅膀”,他们视民歌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实际上,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民歌,还有英雄叙事诗、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等,构成庞大的民间文学系统。哈萨克族的民歌大都可以列入习俗歌的范畴,可以这样说,是他们的习俗催生了这些民歌,这些民歌中也孕育了一定的习俗。这些习俗歌包括婚嫁歌、丧葬歌、日常生活歌、节日习俗歌、宗教习俗歌等。以哈萨克族的婚嫁歌为例,它分为“喜事序歌”、“萨仁”、“加尔—加尔”、“哭嫁歌”、“远嫁歌”、“劝嫁歌”、“揭面歌”等,是整个婚嫁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哈萨克族的婚礼是从提亲开始的,伴有订婚仪式、嫁娶仪式等。在整个过程中,婚嫁歌存在于自始至终,新娘用歌向亲人告别,亲人用歌劝嫁,男方用歌迎娶新娘,来宾歌唱助兴等。嫁女仪式中的“萨仁”歌原并非单指唱给新娘的歌,其他一些古老的有哲理性、劝喻性的古老民歌也称为“萨仁”。由于“萨仁”歌在嫁女仪式开始当天由男方的两位伴郎齐唱,唱给新娘听,往往唱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有“晓之以理”的意味,因此“萨仁”也就成了具有劝嫁内容的嫁女仪式歌。而“加尔—加尔”是男方劝嫁、女方哭嫁的对唱,往往是男方曲调欢快、轻松,而女方凄楚、悲凉。婚嫁歌透露的是婚嫁习俗原型的信息,通过演唱形式凸现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意识,同时,长期积淀的婚嫁原型为婚嫁歌奠定了雏形。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中民间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吉尔”的古歌代表着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的传统,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述英雄业绩的“英雄叙事诗”;一类是婚姻爱情叙事诗。而与“吉尔”相对应的是被称为“黑萨”的叙事诗。这部分大多是仿作和改铸之作,以外来故事素材进行再创作。它分为传奇叙事诗和宗教叙事诗两类。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歌颂的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如《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康巴尔》、《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等都以史诗性、古老性著称。婚姻爱情叙事诗则侧重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爱情命运,著名的有《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少女吉别克》、《萨丽哈与萨曼》等。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中,《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属长篇英雄叙事诗,由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单部叙事诗组成,歌颂了40位英雄反抗外侮的事迹。据说诗中的英雄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反映了自13~19世纪哈萨克族的历史和生活面貌,是哈萨克族英雄叙事诗的集大成之作。
民间叙事诗是靠歌手演唱流传下来的,阿肯、吉尔齐都擅长叙事诗的演唱,但阿肯更长于即兴式的民歌对唱。只要有阿肯弹唱的地方准是在举行庆祝集会、重大祭奠、节日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盛典造就了阿肯,阿肯也使盛典热烈、欢快。阿肯单独吟唱固然能一举成名,但阿肯对唱更是智慧和才华的较量。阿肯对唱往往在两个氏族部落间举行,登场的虽是阿肯个人,但对唱的成败、胜负关系到本氏族、本部落的荣誉,所以阿肯在台上较劲演唱,台下的观众则为本氏族、本部落的阿肯呐喊助兴。如果说喜庆节日、盛大集会、祭奠仪式的阿肯对唱是由主持者或东道主有意为之的话,而以歌会友式的阿肯弹唱就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一种主动登门造访切磋技艺的有效形式。有的阿肯远途跋涉,不辞辛劳,从一个部落来到另一个部落探访有声望的阿肯进行对唱。哈萨克族著名的阿肯比尔江就曾骑垮了6匹乘骑,奔波半个月,慕名找到声望卓著的萨拉阿肯,与之对唱。阿肯的声望并不靠年龄、辈份、性别优势,而是造诣,看其是否有即兴赋歌吟唱的语言艺术功底。因此,阿肯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唱可以在男阿肯之间进行,也可以在男阿肯与女阿肯间举行,老年阿肯与少年阿肯间对唱也习以为常。年长的阿肯败在少年阿肯手下,男阿肯败在女阿肯手下并非鲜见。加纳克阿肯在哈萨克草原负有盛名,曾胜过无数阿肯,但败给一位少年阿肯。男阿肯隋因拜就在同女阿肯孔巴拉对唱时败北。阿肯对唱竞争十分激烈,采取淘汰制的办法。两名歌手一对一上场对唱,各自弹奏冬布拉或库布孜为自己伴奏,相互间对歌盘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尽浑身解数炫耀各自的才华,从气势上、语言技巧上,甚至才智、人品上压倒对方,当另一人自愧弗如、甘拜下风时,对唱就决出了高低。新老阿肯之间的对唱更是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似暴雨,如疾风,年长阿肯向新手展开猛烈进攻。一开口唱歌,年长阿肯就连珠炮似的猛攻,盘诘对方姓名、经历,继而自我炫耀,竭力嘲讽、戏谑新手,夸耀自己及氏族的荣耀,使对方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对于年长阿肯的“激怒”,新手不能恼怒,更不能发火,而只能不愠不火,靠自己的才智和语言技巧回敬对方。无论对唱多么激烈,但一旦对唱结束,双方都会以谦谦君子之风握手言欢。阿肯对唱中还不时穿插谜语、隐语等民间形式,增强对唱语言的艺术感染力。①
同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哈萨克族的神话与传说故事、世俗故事也是其民间文化宝库中的佼佼者。这些故事塑造了诸如迦萨甘这样的创世神话、动物传说,神箭手、机智人物、普通牧民,乃至牧主、强盗、统治者等个性鲜明、反差强烈的各种形象,表达着哈萨克族人民的思想、理念、情感以及价值观和审美走向。以《迦萨甘创世》为例,它解释的是宇宙创生模式:由混沌到初开,分为天、地、冥三界,其中天界以太阳与月亮为中心,地界的中心是生命树。宇宙混沌思维原型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混沌”实为“浑脱”,就是游牧民族装马奶的皮囊,所居圆形毡房古今不变,所以想象宇宙关系就如皮囊或毡房。而正是迦萨甘将天地、阴阳分开,出现了自然万物。神话中的生命树,又称宇宙树,它是通天的“天梯”,是人通神、神通天地的通道。生命树观念首先源自先民对宇宙的直观思维,构成天地层次观,其次源自宇宙中心观的确立。哈萨克族创世神话中的模式物——生命树,对他们的生死观、灵魂观以及各种人生礼仪都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
第二节屯垦文学
历代的伊犁屯垦戍边造就了伊犁屯垦文学。这里所说的伊犁屯垦文学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历代在这片土地上屯垦戍边的各族军民的文学;二是以屯垦戍边为题材的文学。但从广义上讲,屯垦文学应指历代屯垦戍边的各族军民的文学。于是屯垦文学又可分为以西域边塞诗为主体的书面文学和弥漫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从一些文献记载看,清代形成了伊犁屯垦文学的高峰。伊犁边塞诗绝大多数出自获罪流放的流人之手,还有一些则出自屯垦戍边的各级官员之手。而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主要指扎根于伊犁河畔的锡伯等民族的民歌、民间故事等文学形态。
清代伊犁边塞诗作者众多,以伊犁屯田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诗作也不在少数,而且贯穿了整个清代。如果细细耙梳,代表性的有庄肇奎的《伊犁纪事二十首》、洪亮吉的《伊犁纪事四十二首》、舒其绍的《消夏吟并序二十五首》、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百首》、方士淦的《伊江杂诗十六首》、邓廷桢的《回疆凯歌十首》、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以及景廉等官员的诗作。①这些诗作基本代表了清代伊犁边塞诗的基调。当然,这些谪戍伊犁人士的诗作也有一些属宣泄失意情愫、应酬奉和、走马观花之作,但大多数人留滞伊犁一载或数载,往往能超然于个人荣辱之外,关注统一大业、屯垦戍边,并对边疆的民风民情有深入了解,即使是以风光为抒写对象,也往往充满激情。
在清代伊犁边塞诗中,诗人们吟咏最多的是伊犁的风土人情和屯田事业。庄肇奎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谪戍伊犁后,又在伊犁任职,前后在伊犁滞留8年之久,留有纪行诗、伊犁纪事诗等近70首,并以《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最为出色,作于离开伊犁前的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1789)。20首诗对伊犁景色、屯田成果、民族风情的描写别开生面。“戈壁滩头已驻兵,城中无水欲迁城。试传军令齐开井,掘处皆泉万斛清”。这是赞颂伊犁将军伊勒图掘井一举不仅保住了惠远城指挥中枢的地位,而且对屯田戍边意义重大的诗作。作者对伊犁充满热爱之情:“土膏肥沃雪泉香,尽有瓜蔬独少姜。最是早秋霜打后,菜根甘美胜吾乡。”伊犁土肥水美,瓜蔬丰饶,秋菜甘美胜似江南,足见物丰景美。作者对屯田带来的社会安定、物丰人喜有切身体会:“车载粮多未易行,六千回户岁收成。造舟运入仓箱满,大漠初闻欸乃声。”回屯是清代屯田形式之一,这些来自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在伊犁屯田后,粮食丰收,车载不及,乃设水运。可见屯田的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洪亮吉虽在伊犁流放仅有百日,但他的《伊犁纪事四十二首》在清代边塞诗中属精品一类。洪亮吉属学者型文人,虽命运多舛,但才气压不住,因此,伊犁纪事诗也就格高一调。他不是浮光掠影式地叙事状物,而往往注重风土人情所蕴含的深意,且能见常人不注意的细节之处。“五月天山雪水来,城门桥下响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却倩河流界画开。”这是伊犁屯田城镇常见的景色,每年4月引水入城后,曲池蓄之,到夏天用于灌溉园圃。这种城内蓄水城外用的情景在内地是不多见的。作者赞赏这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凿得冰梯向北开,阴崖白昼鬼徘徊。万丛磷火思偷渡,尽附牛羊角上来。”这是写维吾尔族农民开凿冰梯开通伊犁通往南疆冰达坂通道之事。年年如此,对当地人来说是司空见惯,而对洪亮吉来说却能写出新意,修路之难不说,便利行旅更重要。洪亮吉还在一些诗中表明自己虽遭流放,但不会因此而消沉,要永不气馁的心迹:“坐来八尺马如龙,演武堂高夹路松。谪吏一边三十六,尽排长载壮军容”。谪戍边陲,“壮军容”的精神永在。洪亮吉擅长状物写景,无论是“雪消齐露粉墙”的古庙,还是“杏子乍青桑葚紫”的果园景致,都写得有情有义。
舒其绍自清嘉庆二年(1797)以事戍伊犁长达8年,主要写有《消夏吟并序二十五首》,以状写伊犁等地屯田城镇、山川地理、历史掌故闻名。所写屯田城镇有塔勒奇城、霍尔果斯城、惠宁城、广仁城、锡伯营以及金顶寺、普化寺、无量寺、观音寺等寺庙建筑,山川地理写有红山嘴、皮里青、白杨沟、野马渡、果子沟、红柳湾、赛里木湖、固尔扎渡口、清水河、齐齐罕河、厄鲁特游牧场等。他的足迹踏遍伊犁的城乡、牧场、山山水水。舒其绍在《消夏吟》序中说,这些诗是“就素所知者,拈题分咏,藉消长夏”,但其意又不尽在消夏,而更是在话“升平”。作者在《芦草沟城》一诗中写道:“大野雪漫漫,孤城草际看,黄云痴不落,白日瘦生寒。鸡犬通秦语,貔貅列汉官。太平无一事,堠火报长安。”芦草沟城即广仁城。戍边虽艰苦,但这些来自陕甘的戍卒和商贾在保边疆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对伊犁的山川风光,往往也能抓住景物特征,写出各自特色。写果子沟是“云穿千嶂活,风曳百花香”,赛里木湖是“乱山围地起,一水点天流”,写齐齐罕河是“险隘葫芦口,当关水怒号”,厄鲁特游牧场是“夜猎霜飞血,晨炊雪压庐”。或许诗是浅白了点,但状物写景总是贴切、入味。
与舒其绍同时代的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也以写伊犁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著称,但更多了一些历史厚重感和责任感,这与他的学养深厚和撰写《伊犁总统事略》不无关系。他在《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名为《伊犁》的诗:“伊丽曾闻属定方,濛池碎叶路茫茫。投鞭直断西流水,始信当年我武扬。”这是借用唐朝平定西突厥建濛池都护府、碎叶州典故赞颂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之事。当时伊犁等地已在大唐版图内,对伊犁的这种述写充满自豪感。在《兵屯》、《卡伦》等诗中作者也不忘抒写清代屯田戍边的意义。《兵屯》写道:“细柳云屯剑气寒,貔貅百万势桓桓。列城棋布星罗日,阃外群尊大将云。”建伊犁九城,陈兵边塞,都是保民安边的重大举措,作者予以充分肯定。《卡伦》:“刁斗声残夜寂寥,龙沙极目雪花飘。守边一一皆飞将,生手何人敢射雕?”卡伦为清政府设于边地要隘守望并营税收之处。此诗是赞颂坚守卡伦将士的,寓指卡伦在边疆稳定中意义重大。祁韵士还写有《府茶》、《阿拉占》、《器乐》、《回布》等状写伊犁等地民俗文化的诗作,对边地淳朴的民风民俗充满赞誉之情。
方士淦于道光五年(1825)遣戍伊犁,道光八年释返。在伊犁期间写有《伊江杂诗十六首》,写历史,写风土,写山川,写交往,无所不包。他的诗有不少是对清乾隆朝在平定大小和卓和准噶尔叛乱中献身将士的追念和凭吊:
城外绿阴稠,
金堤百尺楼。
群峰环雪岭,
一水带沙流。
不有神明相,
谁令祀典修。
宗臣遗像在,
忠义凛千秋。
在惠远城南门外龙王庙前的望河楼为伊犁将军保宁建,其父纳穆札尔,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殉难。作者认为其父“忠义凛千秋”,值得人们缅怀。
林则徐和邓廷桢这两位禁烟中的英雄同被遣戍伊犁,在伊犁数年期间留下了不少咏物明志的诗作。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主要是描写新疆少数民族风俗的。因林则徐去南疆八城地区勘察水利,有了深入了解维吾尔族风俗的机会。在诗中对维吾尔族的农作节气、宗教信仰、服食起居、婚丧嫁娶、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描写。诗中大量借用维吾尔语,平淡中有诙谐,写实中富有诗意,如行云流水,畅晓上口,展示了清代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自乾隆年间开始,不少维吾尔族农民已以回屯方式在伊犁地区开荒垦种,对此,林则徐在伊犁期间已有所了解。像“城角高台广乐张”的维吾尔族音乐,像“爰伊谛会万人欢”的宗教节日庆典,又像“石粉团成满壁花”的建筑艺术和“新帕盖头扶上马”的婚礼,作者都有描写。林则徐在伊犁的诗作更多的是明志抒怀的。邓廷桢遣戍伊犁之初,心情郁闷,神情恍惚,随着滞留时间增长,对边疆的淳朴民风、富饶美丽有了切身感受,于是渐渐驱走了往日的愁思,写伊犁山川之雄浑,抒防俄固边的爱国忧思。《伊丽河上》就是其戍边诗中的代表作:
万里伊犁河,
西流不奈何。
驱车临断岸,
落木起层波。
远影群鸥没,
寒声独雁过。
河梁终古意,
击剑一长歌。
面对沙俄的虎视眈眈,邓廷桢感到塞防的重要,他以“击剑一长歌”表明心迹。
在此还应提一下清朝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的《伊犁杂咏》。这位伊犁将军仅在位54天就被伊犁起义的革命党人枪杀。虽然《伊犁杂咏》写于志锐任索伦营领队大臣时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但他的诗成了清代伊犁边塞诗终结的标志。《伊犁杂咏》由6首诗组成,即《抢羊》、《咏冰床》、《鸡卜》、《金银顶寺》、《贡马》等。诗是描写伊犁哈萨克等民族风俗的,后人王子钝先生评价《伊犁杂咏》是“数诗吟咏异俗,纯以平常语琢成,别有深味”。
与文人的边塞诗比较,伊犁屯垦文学中别开生面的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民间文学。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至伊犁的锡伯族因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较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形态。锡伯族的民间文学实际上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早在东北生活时期的民间文学;另一类是西迁至伊犁后新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民歌中的《狩猎歌》、《萨满歌》、《耶奇那》以及传说故事中的《喜利妈妈的传说》、《海尔堪玛法的传说》、《阿克敦的传说》、《人参故事》、《秃孩子》等早在农耕生活时代就产生了。有一首《狩猎歌》写道:“飘飘雪花如蝶飞,驰骋骏马共撒围。搜遍一山又一山,猎队满载凯歌回。”显然产生于锡伯族生活在东北绰尔河松噶里比拉、兴安岭一带的狩猎生活,描写的是猎手骑马围猎的场景。《萨满歌》也是源自锡伯族萨满跳神时所唱的祈祷词,由萨满独唱的正歌和众人合唱呼应的副歌组成。以后又与田间劳动相结合,成了有特定曲调和节奏感的民歌。《耶奇那》是锡伯族古老的民间长诗,是写一对穷苦夫妇战胜困难,创建新生活的经历。民歌唱出了一对夫妇的渔猎生活,每段一、三行均以“耶奇那”开头,形成内容相连而故事结构并不连贯的叙事模式,语言朴实、和谐,曲调明快、上口,因此在锡伯族民间广为传唱。《喜利妈妈的传说》来源于锡伯族系绳纪事的历史和家庭保护神的传说。由于喜利妈妈在锡伯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才演化出各类传统故事。《人参故事》也来自东北时的采药实践。在这类故事中,被锡伯族尊崇为百草之主的人参被赋予舍身救人的老人或小孩的性格,可见爱之深切。①
西迁伊犁后,锡伯族出现了一批新民歌、新传说,并产生了书面文学作品。一些以农耕生活为题材的田间歌、情歌、习俗歌都产生于此时,《一棵沙枣树》、《秃鹰》、《熟石皮》等传说故事更多了些伊犁的地域特色。在书面文学作品中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辉番卡伦来信》、佚名的《喀什噶尔之歌》、锡笔臣的《离乡曲》等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锡伯族最难忘怀的是西迁的历史,于是出现了以西迁为题材的民歌《告别盛京》、艺术诗《离乡曲》和民间叙事诗《西迁之歌》。
从创作时间看,《告别盛京》作为民歌,可能在锡伯族迁徙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不过在各个时期经过民间诗人的不断加工、改编出现了不同的变体,而最终形成书面手抄本,大约是在锡伯族西迁后的100年间。《离乡曲》是锡伯族文人锡笔臣用汉文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的七言诗。而管兴才根据民间流传的迁徙诗歌素材创作的《西迁之歌》则晚得多,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从篇幅看,《告别盛京》民歌抄本是240行,《离乡曲》是120行,而《西迁之歌》则长达500余行。行数形成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告别盛京》为民歌,变体多,民间诗人对其增减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离乡曲》是文人创作,严格恪守汉族古典诗歌的创作规律,又是文言诗,言简意赅是它的特色,它以简取胜。《西迁之歌》是在各种迁徙民歌和文人诗作的基础上创作的,要概括锡伯族的西迁以及西迁后屯垦戍边200年的历史轨迹,就有了史诗般的长度,它是以繁取胜。如果从诗体分类看,《告别盛京》是民歌,《离乡曲》是艺术诗,而《西迁之歌》属民间叙事诗。
以锡伯族大迁徙为题材的诗歌受其文化心理、思维定式和民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锡伯族民间有念说“朱伦”(即长篇故事)的传统,有些是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有些则是根据其他民族的传说故事改编和加工的,如《三国之歌》等。讲述者有用散文体的,也有用韵文体的。但是不论哪种故事都讲究首尾呼应,结构紧凑,情节完整,往往以时间为序安排结构。这种以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线性模式谋篇布局的传统方式无疑对锡伯族的迁徙诗歌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无一例外,3部西迁诗歌的叙述都与历史叙述同步亦趋,呈一种单线发展模式:迁徙缘由——迁徙之日骨肉离别场景——迁徙途中的艰辛——迁徙后的屯垦戍边。但这绝不等于说,3部西迁诗歌都雷同化,而在表现手法上是各有千秋。地方民歌《告别盛京》重过程,在结构上采取以不同地点、不同场景为单元的空间转换模式;《离乡曲》重历史氛围,善于在横断面上撷取若干细节渲染迁徙的艰难;《西迁之歌》重情感宣泄,场面烘托,在时令变化中揭示不同家庭的坎坷经历。①
锡伯族的西迁在诗化之前,必然有段史化的过程,这是由锡伯族的特殊社会结构决定的。锡伯族在西迁之后形成以牛录为核心的整体社会组织,但每个牛录又由若干个以父系血缘为标志的血缘共同体——“哈拉”组成,而哈拉则由数个莫昆,即同一个哈拉内自然形成的血缘分支组成,莫昆由数个家庭群体组成,其下即是单一的家庭。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西迁史起初是作为一个哈拉或一个莫昆或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由长辈讲给晚辈听的,讲述者多着眼于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千百个家庭以不同方式讲述同一段史实时,锡伯族民众就更多了些关注整个民族命运的悲壮感,要让整个民族牢记这段历史,于是在缺乏出现史书的特定历史环境中,锡伯族人民选择了扎根于本民族土壤、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歌,后来文人参与进来进行创作。民歌语言精练,富有韵律感,易于传唱,便于记忆,成了西迁史最好的载体。
清代屯垦民间文学中,以回屯方式在伊犁屯田定居的维吾尔族民歌也占有一席地位,虽然他们的生产方式未改变,其他民族称这些人为“塔兰奇”人(意为种地的人),仅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三十三年从南疆移居伊犁种地的就有6000余户,但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和与各民族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歌也出现了维汉合璧的现象。有一首广泛流传在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唱道:“伊犁的大道上有个截梁子,大河沿子是腰店子,开辟了伊犁大道的是,你我这样的好汉子。”“截梁子”、“腰店子”均属汉语中伊犁的村落、小镇名,“好汉子”更是汉语,维吾尔民歌是音译过去的。这类维汉合璧民歌的每段歌词的核心词均是以汉语表达的。还有些通晓汉语的维吾尔族歌手还能用汉语演唱民歌,如《沙里洪玛来》就属伊犁维吾尔族的汉语民歌:
问:哪里来的骆驼客?沙里洪玛来,
骆驼跟前啥东西?沙里洪玛来。
答:哈密来的骆驼客,沙里洪玛来,
花椒、胡椒、姜皮子,沙里洪玛来。
问:吐鲁番好吗哈密好?沙里洪玛来。
答:哪达有钱,哪达好,沙里洪玛来。
一问一答,诙谐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美丽的阿瓦尔古丽》也是当时流行于伊犁地区的一首维吾尔族情歌。
第三节草原艺术
我们很难在草原文学和艺术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是因为草原文学中的民歌、英雄史诗、叙事诗等实在属于歌者的范畴,都是靠演唱征服听众和流传下来的。但记录下来的书面形式——诗歌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故往往又划入文学范畴。关于草原民族的民歌、英雄史诗等已在《草原文学》一节中论及,在此不赘。在这一节中主要是论及被称为草原视觉艺术的岩画、石人、鹿石和民间工艺等。而现代人将岩画、石人、鹿石等视为造型艺术时,对史前先民来说,它们都是功能性的。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仅仅作为纯艺术看待,应看做是先民的心理、精神的产物,具有文化功能意义。如果离开这点,就与这些史前遗物制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伊犁、阿勒泰、塔城是新疆史前岩画、石人、鹿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在已发现的新疆150余处岩画中,伊、阿、塔三地区就占了80余处。这些岩画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是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也有少部分是有史时代的遗物。伊犁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伊宁县、巩留县、昭苏县、霍城县、特克斯县、新源县等地境内。阿尔泰山系岩画分布于阿勒泰市、青河县、富蕴县、布尔津县、福海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等地。塔城地区岩画分布于塔城市、裕民县、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岩画中,90%以上画面反映有洞角类、鹿科类、马科类等10多种动物形象。
从天山、阿尔泰山的这些岩画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野生动物,只有极少数如马、狗等为家养动物形象,而且出现的人形图像或与动物间有某种关联,或是象征人类生殖的组合图像。这表明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后期伴有少量畜牧业,即使在游牧社会,也不完全排除狩猎活动),人们最关注的是氏族人口的繁衍和猎取动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猎牧社会的文化也是一种狩猎文化,但是天灾人祸,很难保证人口的高存活率和每次都能猎获动物。在这样一个前科学时代,巫术思维的产生直接导致人们借助于运用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正如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所言:“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巫术的世界。开始,原始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力’。奇妙的‘力’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存在和石头的坚硬、水的湿润一样的确定无疑。这种‘力’仅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超自然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真实的和自然。”①人们在信奉神灵之前,是普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的。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②巫术思维导致的是巫术操作。岩画正是施法者实施巫术操作仪式的工具。这种巫术思维和巫术操作一直从旧石器时代起,经过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有史时代。西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都充满着这种巫术仪式。从已发现的天山、阿尔泰山岩画中不难得知,人与动物生殖“力”的传递形式有四种:一是感应式;二是接触式;三是相交式;四是距离交合式,都属于交感巫术范畴。已完成的岩画既可能是自足图像,又可能是非自足图像。
西域岩画中有一类在我国其他地方绝少有的洞窟彩绘岩画,它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其一是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乌孙山发现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岩画绘于阿克塔斯山高1850米处的岩洞内,洞高2.5~3米,洞口宽5米。岩画绘于洞口右面岩壁上,均用赭石绘制。画面由7只北山羊、2匹马和2组大小圆圈和一个“〉”形及“◎”形、“工”、“)”符号组成。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第一个岩洞在半山腰离地面25米处,洞窟高11.5米,宽20米,深11.8米。岩画绘于洞顶和正面、侧面岩壁上。画面由一组4个里外两层中间为圆圈的椭圆形图案和两个圆圈、手印以及被认为萨满帽、铜镜的图形组成,此外还有一组表意符号和所谓的人面像。唐巴勒塔斯2洞距离第一洞约60米,位于海拔1000米处,洞宽4.9米,高3.2米,深4米。画面由拿弓箭欲射的两人、脚印、两只野兽和叉腿、手臂平放或上举的4组人形图像组成。其三是阿勒泰市西北25公里处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洞窟在海拔1000米处,高1.31.5米,深浅不一,从1~4米左右。在二组50余道竖短杠组成的类似围栏内分别绘有一椭圆形图案和双腿叉开,高举双手的人形图像。此外还赭绘有牛、马、大角羊的图像。其四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乡的洞窟彩绘岩画,为两处,一处在杜阿特沟,另一处在松哈尔沟。杜阿特沟洞窟彩绘岩画又分5洞。第一洞海拔650米,洞高不过1米,宽也仅1.6米,赭石绘有牛和人物图像,人头部有“V”形饰物。第二洞在海拔605米处,洞高1~5米,宽1.7米,深1.3米。画面由一双手下垂、有尾饰的人物图像和牛形象以及一些表意符号组成,其中布满大而有规则的赭石圆形斑点。第三洞只绘有较粗的类似栅栏的竖道。第四洞是两个双腿叉开、双臂伸展的人物图像,有尾饰。第五洞仅有两只牛和一个人物图像。人像头部有两仰角物,尾饰特征显著。松哈尔沟洞窟彩绘岩画在一个高2.5米,宽8米,深4.5米的岩洞内的洞顶。在洞顶10余平方米的岩画上绘有人、动物和其他符号,实为一巨幅岩画。画面中心为一匹有赭石斑点的马,四周绘有羊、虎、牛等动物,人物图像形状与前述洞窟彩绘岩画相同,但与动物图像比较,人形都较小。此外,还绘有6个大手掌印,似栅栏的竖道,赭石实心圆以及虚线组成的不知名图形。从图像看,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多次使用的痕迹。伊犁、阿勒泰洞窟彩绘岩画完全可以根据狩猎文化中的典型动物祭祀仪式和与之有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来加以解释。①
在这些萨满岩画中保留了法力强大的萨满的最早形象。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为带角的拟人像,这一形象同样出现在杜阿特沟洞窟岩画中,而这些萨满形象无一例外都附有尾饰。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媒介者,他的任务就是沟通地上人类与天上神灵。早期的萨满本身就是巫师,装扮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角”。萨满在一种出神状态下,借助神灵的助佑者——鹿与神沟通。头上带角萨满岩画正是象征萨满的助佑神灵。羽毛状头饰、放射状头饰的功能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些人形身下的尾饰往往被误释为阳具,这是不了解早期萨满的装扮所致。从欧洲奥瑞纳文化时期史前岩画发现,岩画上的巫师(萨满)头上戴着鹿角,身上披着兽皮,臀部安有马毛,全身呈激烈跳动状,这就是原始萨满的典型形象。因此,洞窟岩画中萨满也应是头戴鹿角、披兽皮、安兽尾的形象。当然萨满也装扮成鸟的形象,羽毛状头饰即属此种。在阿勒泰洞窟岩画中还出现戴面具的萨满形象。对萨满的这种形象,朱狄先生解释为:“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做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西域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头戴兽冠、披着兽皮的萨满形象。在一个氏族里,萨满既是沟通人神者,也是保证氏族繁衍、狩猎成功的力的源泉。从这点看,萨满头戴象征神灵助佑者的鹿冠,身披兽皮正是在进行狩猎巫术仪式,它并不是出于单纯模仿的动机。萨满面具早期也是狩猎祭祀仪式的狩猎巫术面具。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神秘的“力”把物体的推动力转向另一物体。之后,面具成为萨满的固定道具,又附加了跳神(包括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供奉等多种功能。
石人和鹿石是草原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草原中段的伊犁、阿勒泰、塔城的草原地带也是石人、鹿石的集中分布地域。这些地区的石人最初产生于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6~9世纪达到兴盛期,衰落于11世纪左右。鹿石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以地域分类为伊犁石人、阿勒泰石人、塔城石人等;按族属分类为塞人石人、乌揭石人、突厥石人、铁勒石人、蒙古石人等,亦按设置情况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还可以按雕刻技法分类等。鹿石主要根据碑体形状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也有按族属、典型与否分类的。在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石人手持器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中古时期。手持器皿者分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右手持杯状物,另一种是双手抱罐、碗、瓶、钵之类器皿。其他还有手握刀、剑等兵器和手托鹰等形象。即使是手持杯的石人,其杯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如阿勒泰市境内阿克塔木墓地石人右臂屈至胸,手执一种角状杯;而温泉县境内阿尔卡特石人右臂屈,手执圆底罐形杯;内蒙古巴兰恩特利格突厥石人左手下垂,右手置于胸前执一筒状杯;吉尔吉斯草原发现石人右臂稍屈直,手托高足凸肚状杯,有的石人右臂屈,手执高脚杯。从青铜时代开始,右手执杯状物或双手抱罐、钵等器皿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对于这类墓地石人手持器皿的含义,学者们作过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认为是饮酒的酒杯;(2)神圣的器物;(3)丰产的象征物;(4)盛动物乳汁物的器皿。几种解释都无大错,问题是这些器皿是作为一般的饮器,还是另有它用?谁有资格使用这些器皿?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使用?这些答案还必须在萨满文化情境中寻解。手执器皿者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少这类形象往往在腰带上佩有条状装饰物,但它们既非刀剑之类,也非装物的皮袋,而是在垂条或垂绳上挂有垂饰。这在南西伯利亚、中国新疆、蒙古等地的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都十分常见。此外,石人与一些遗迹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有两种情况:一是石人竖立在祭祀石堆附近,石堆下面埋有牺牲的残余,有动物的骨骼、祭祀灰烬和各种器物,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6世纪的石人就属此类;二是南西伯利亚、中亚、内蒙古、新疆的确存在墓葬区的石人,齐木尔齐克石人墓的发掘证明墓地石人从青铜时代一直延至铁器时代。这些考古发现恰恰证明执器皿石人应是萨满形象,因为在后世萨满形象中的确能见到穿条状萨满服,腰带系垂绳挂铃、镜、挂饰、石球、动物骨关节等饰物的情景。萨满作法时这些物件叮当作响,目的是以响声传达人间与神界的信息,这些物件也是除邪镇魔的利器。结合遗迹关系分析,无论是祭祀堆石人还是墓葬区石人,均是萨满祭祀的形象,不管是祭祀祖先还是举行狩猎等仪式,都离不开萨满,他们总是这些仪式中的主角,不过祭祀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现在回到手持器皿的萨满形象上来。对于萨满来说,所用器皿是神圣的,同萨满神服、神帽、神具一同组成萨满的神物。阿契门尼德时期波斯的契形文字文献将塞人分为三大支:提格拉豪达塞克(尖帽塞克)、豪玛瓦尔格塞克(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和提艾伊·达拉伊雅塞克(近海塞克)。其中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极有可能是指其首领(也是萨满)是饮用豪麻汁的,即一种麻醉汁。据说萨满通神时必须处在一种迷狂、神志恍惚的“出神”状态,需要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因此,石人所持的也应是盛豪麻汁的器物。在充满萨满教信仰的氏族部落社会中,萨满最有资格持盛豪麻汁的器皿。在氏族、部落中萨满的神圣职能几乎囊括氏族、部落的所有活动,如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生产与生育、神判与记事等等。从近世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得知,萨满使用盛器见之于以下活动:一是治病时的喷术。起先治病时是喷气,后来是喷酒或水、药。在诸如得疮伤、骨折、长疖子、中风不语、口眼歪斜、错迷不醒等疾病时,往往用盛器盛水、酒或熬制的草药运气喷至病人身上,以达消炎、驱热之效。萨满常常在跳神治病仪式上向患者施之喷术,喷术功也成为萨满的内养功,平时要坚持练运内气、吹功。由此观之,立于祭台前的手执杯类器皿的石人应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上的施喷术的形象。二是与萨满教的神偶嗜血的灵魂观有关。“萨满教观念认为,血能育魂养魂,魂血相生互卫,所谓魂依血流,血行魂行,血凝魂止,则浮离体外,曰浮魂。魂依血养,魂凭血育,血旺魂壮,血热魄强,无敌天茬,鬼魔难当,曰养魂。神偶作为灵魂的依托体,其保持灵性和神性的奥秘在于常享祭物,尤以嗜血最益于养魂,使偶体内的灵魂常存。基于这种观念,萨满祭祀十分重视备牲、养牲、杀牲,无牲不祭成为萨满教不成文的规则。”①于是在萨满教祭祀仪式上,萨满常常是在神灵附体后,手持盛动物血的器皿喝血,也往往将器皿中的血弹或涂在祭祀的神偶身上。手持盛动物血器皿的石人也应是血祭诸如祖先、酋长、英雄等神偶的萨满形象。三是蒙古族的“行博”仪式也离不开容器。古代蒙古族凡进行渔猎、游牧、征战、治病、占卜、送葬、祈雨等仪式时都要请博(萨满)进行祈祷请神、附体求神、送神活动。在仪式中萨满常常在室外手持酒杯向诸神敬酒答谢,感谢神灵的庇佑。四是萨满为显通神的法力,常常要喝下圣水(可能是清水、酒或动物血等),目的是神灵会更显神力。在喝圣水时,萨满往往双手持碗等容器,以示虔诚。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对于索解手持盛器的草原石人之谜应是合乎情理的。
欧亚草原上的鹿石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此,仅探讨雕刻有鹿纹的典型鹿石。这些鹿石上的鹿形有如下特征:喙状头部前伸,嘴巴大张;两只枝状角仰向背部,一上一下(这说明与那种严整的动物侧影形不相符合);额部相应地有两处前突起;颈部和躯干前半部过长;前后腿相距甚近,一般都小而细得不合比例,有时仅有上半截,像被砍断一般。有时,当腿部全部雕刻出时,则呈弯曲状,前腿离于后腿,二者连接不严,中间留有空隙。蒙古——外贝加尔和中国新疆发现的鹿石都属此类带有图案化的鹿纹样的类型。雕刻这些鹿形图案的鹿石是一些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的石柱或石板。不过晚期的鹿石并非通体都是鹿的图案,而是雕刻成人形,这类鹿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鹿石是做什么用的?鹿形图案有象征意义吗?这不能不与欧亚草原民族的早期萨满教信仰联系起来考虑。在萨满教世界观中,高山、大树都是作为萨满通神的宇宙山、世界树出现的,而方柱体、圆柱体的鹿石也应是萨满通天通神的工具。萨满是一个送魂者,保证祖先或英雄的灵魂升天而不是人地狱的方式是在祭祀仪式中以巫术操作手段通过刻凿鹿石中的图像达到其目的。研究者认为,在萨满教中往往出现萨满庇护神:“每个萨满,肯定都有一个动物母亲或动物祖先。它通常被描绘成大角鹿,有时也是一头熊。这个动物自己生活,不与萨满在一起。大概,最好是把它设想成在大地上飞翔的,萨满那火一样的力量”①。不过从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材料发现,庇护和培育萨满的精灵常常是鹿、鹰、蛇等,其中鹿和鹰是萨满庇护神最具代表性和最权威的形象。鹿石上刻凿的鹰喙鹿身图案正是萨满庇护神的形象,天上飞翔的鹰与地上奔驰最快的鹿的组合已经成为普遍的萨满职业象征。特别是那些有人头形和鸟喙鹿身的鹿石是萨满正在实施巫术时的产物,刻凿过程也是巫术操作的过程。这是后代萨满通过这种巫术操作与前代萨满(祖先)的灵魂沟通。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鹿、鹰等萨满的庇护神或者是亡故的前代萨满,或者无异于萨满的配偶,抑或还是晚辈萨满的庇护者。因为萨满的灵魂均是由这些动物庇护神作为向导和保护者前往上界的。难怪有些鹿石上部刻凿有象征天界的圆圈、圆点和半月形纹饰,它们与人头形、鹰喙鹿身组成萨满灵魂升天的全景式图像。不过,鹿石雕凿展现的是萨满通神时巫术操作时的文化情境,而萨满服的缀饰变成了凝固的符号象征物,但它们在萨满教信仰中同样是神圣的。
在草原艺术造型中,动物纹样占有特殊地位。塞人、匈奴、大月氏、乌揭等早期部族的动物纹样来自于猎牧活动中的动物。常见的凶兽猛禽,如狮、虎、熊、鹰、狼、鹿、豺、野猪等,也有驯养的马、牛、羊、狗等形象。特别是一些野兽形象,多为啮咬、争斗状,形体往往扭曲变形。无论是塞人风格的动物纹样还是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绝对不是出于审美需求的艺术装饰,而具有功能意义。这些部族把动物形象装饰在牌、扣、钩、徽章、矛、剑、马具、带等须臾不离身的物件上是视其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塞人的狮神、吐火罗人的双马神(即龙神)、车师人的虎神、匈奴人的神兽、鲜卑人的瑞兽、蒙古人的“白海青”等,或来源于早期氏族图腾,或衍化成部落保护神。鲜卑人的带钩——犀比为瑞兽,即神兽,实际上鲜卑就是以“瑞兽”相称的部落。草原民族的这类动物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早期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以后在普遍存在的萨满教信仰中被信奉为部落保护神了。即使这样,功能性的动物纹样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草原民族个性和心灵世界的基本表现方式。
所谓草原民间工艺艺术是在传承中积淀凝聚民间智慧,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定型,富有民族普遍性并产生于日常生活能够真实反映草原民族心灵世界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弥漫于日常生活有普泛性。游牧民族的毡房、马具、服饰、毡毯都富有装饰性,特别是讲究以自然界的花草、动物角等抽象变形对称装饰,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搭配色彩。这种色彩搭配往往反差强烈,色泽艳丽。装饰用具、美化生活几乎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存在没有装饰的生活,也不存在离开生活的装饰。如果细细列举,诸如手帕、荷包、头巾、枕头、腰巾、围裙、毡帽、毛袜、领口、袖头、衣襟、裤角、被面、垫褥、罩单、帷帘、壁挂、壁围、花毡、织毯、草帘、编带、马褥、披肩等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恰到好处的纹样和色彩加以装饰美化。一些几何及植物纹样装饰图案的出现不能单纯归于某些游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后反对偶像崇拜所致。其实,这类装饰性图案起源很早,不亚于动物纹样。在塞人金银器中,匈奴织物中除动物纹样主题外,同样有花纹、三角形、圆形等装饰性图案,似乎都不是写实风格的。
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其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对象关系及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都直接联系着他们的文化艺术。他们在马背上吟唱着牧歌和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喜庆场合高唱婚礼歌、祝酒歌,并以歌舞相娱;他们的腰带上佩挂有镶嵌对兽猛禽图案的牌饰、带扣、短剑;他们在所迁徙之地雕琢了无数幅岩画;他们还在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座石人像、鹿石;他们还在毡毯上、服饰上飞针走线,留下了流光溢彩的精美图案..他们的艺术无处无时不在,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圆形毡房也富有艺术韵味。
第四节屯垦艺术
屯垦艺术的主流是清代汉、满、锡伯、维吾尔等民族的民间艺术形态。西域历史上的屯垦虽然兴于汉代,盛于唐代和清代,但汉唐时期伊犁屯垦艺术究竟如何,无论是典籍还是考古发现,都未能提供更充分的依据,但仍有遗迹可寻。西汉时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的随行人员中就有乐工等人,还带来中原乐器等。乌孙公主也曾一度“遣女至京师学鼓琴”,但范围有限,并未广泛流传。而在文化交流中,中原丝绸在乌孙王庭是流行的。乌孙国都赤谷城还建有汉族风格的宫室和房屋。这是汉族建筑艺术在天山以北地区的首次出现。唐代屯田和元代定居建筑,应该在伊犁地区广泛分布,但现在大多荡然无存。元代的阿力麻里城,意为“苹果城”,是元代西域地区的名城,但现已无城墙等遗迹。遗址曾出土元代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官窑特制的青瓷、白瓷盘、碗等文物。唐代丝织艺术品曾在昭苏县境内波马古墓中出土,属6世纪遗物。这三件丝织品分别是“富昌”文字锦、方纹绫、缀金珠绣织物。“富昌”锦以黄色为地,用红、绿、深褐色显现花纹,花纹为横向云气纹和不同形态的动物纹,间织“富”、“昌”等汉字铭文。汉锦是汉唐时期流行在西域的织锦,大多属吉祥文字锦,是为满足人们求吉祈福的心理需求。这类织锦均为汉地所产,但图案纹样明显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可能是为西域上层人物专织的。
当到了清代另一轮屯垦高潮来临时,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清代伊犁地区屯垦艺术的魅力,无论是世俗艺术,还是宗教艺术。清代伊犁屯垦艺术是满、汉、锡伯、维吾尔等屯垦民族的民间艺术。这些屯垦民族多杂居,特别是居住在城镇中,因此,在保持本民族艺术前提下,艺术交融也十分频繁。
伊犁、塔城等地区汉族的民间艺术往往与他们的民间信仰有关,也就是说,设祠供奉各种民间神祇的场所也就出现了庙会活动,这里集中着汉民族的诸多民间艺术形态。据民国初年到达新疆的谢彬在其所著《新疆游记》中记载,塔城汉城就建有财神庙、龙王庙、刘猛将军祠等。1908年所修《伊犁府乡土志》也记有伊犁九城广设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先农坛、祈谷坛、神祇坛、龙神祠、昭忠祠等。①惠远城也有津商商业区。按汉族习俗,庙会成为定例,如农历三月十八日的观音庙会、农历四月初八的药王庙会、农历六月六日的龙王庙会、农历六月十五日的八仙庙会等。庙会成了汉族居民的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散发着民间艺术气息。这里荟萃着全国各地的花鼓戏、闹龙灯、秦腔、眉户、高抬、跑旱船、舞狮子、高跷、中幡等多种民间表演艺术。艺术交融中莫过于新疆曲子戏对屯垦居民的影响大了。新疆曲子戏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甘肃民间艺人夏三通组织敦煌曲子戏进新疆演出,之后,它很快被新疆的汉、回、锡伯、满等民族接受,在城乡普及开来。新疆曲子戏是个博采众长、吸收融合各种音乐成分最杂最多的剧种。它最早是在陕西眉户剧音乐的基础上,在西渐的过程中融进兰州鼓子词、敦煌佛曲音乐等形成。流传到伊犁地区演变为新疆曲子戏的过程中,锡伯族的“秧歌调”几乎全被吸收融合。锡伯族的“秧歌调”分“平调”和“越调”两种,它是锡伯族吸收汉族“秧歌调”演变而成的一种戏曲音乐。新疆曲子戏音乐中的“天山令”还吸收了哈萨克族民间音乐成分。新疆曲子戏的白口完全是本地化的新疆汉语和方言俚语,还融进了维吾尔、俄罗斯等民族的词汇,全国各地方言俚语也夹杂其中,从语言上讲它成了新疆汉族或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都能听得懂的语汇。在伊犁,锡伯族每逢节庆婚嫁都演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以历史和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曲子戏,出现了诸如寿谦、恭金保、郑禄、安林、郭瑞、铁山、郭梅英等有名的艺人。他们所演曲子戏既有汉语的,也有锡伯语、汉语夹杂的戏。虽然新疆曲子戏原型脱胎于眉户剧,但在演进中已非原来的音乐,它一旦与新疆各民族音乐杂交后就显示了自身的优势,这要归功于清代大规模屯垦移民带来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勃兴。
清代伊犁的屯垦艺术中汉族或仿汉式建筑艺术也是十分典型的。伊犁九城是传统的汉式城市布局。它遵循的是“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的汉族传统建城原则。伊犁九城是以自然地形布局理论规划的,特别是惠远城因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故更讲究天材、地利诸因素。伊犁地区的喇嘛教寺庙除受藏族建筑艺术影响外,主要是受汉族建筑艺术影响,遍布于锡伯营八个牛录的关帝庙、娘娘庙等供奉民间神祇的庙宇也属仿汉式建筑。在这些寺庙建筑中规模较大的是锡伯族喇嘛教寺院——靖远寺。该寺占地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整个寺院是汉式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庭院式建筑。寺院坐北朝南,正南为砖雕影壁,进两侧山门为东西两小院,东为土地神庙,西是木栅栏小隔房,内立守门神塑像。正门两侧各有一石雕雄狮,进大门后依中轴线分别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世佛大殿。院内东西两侧还修有钟楼、鼓楼以及铁铸大香炉、木牌楼、偏殿等。三世佛大殿亦谓藏经楼,属木雕牌楼式两层飞檐建筑。大殿高尖屋脊,琉璃顶,翼角飞檐上挂12个铁铃。殿内供奉三世佛塑像,两侧为藏经阁。靖远寺已非单纯模仿汉式佛教或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它在充分吸收、融合汉藏建筑艺术的同时又渗透着锡伯族的审美观。无论是寺院大门上镌刻的锡伯文“靖远寺”金字,还是砖雕、木雕、彩绘、泥塑都显示了锡伯族工匠的高超技艺,融进了锡伯族人民的审美观。因此,靖远寺是屯垦民族建筑艺术完美融合的产物。
锡伯族民间装饰艺术不仅表现在庙宇等建筑中,主要的、大量的还是常见于日常生活中的艺术现象,如服饰的装饰以及门帘、墙饰、鞋、枕头、家具、荷包、烟袋、箭袋、首饰等无不充满艺术想像力。锡伯族的民间装饰图案主要是花卉、飞禽、走兽等植物、动物纹样图案,也有几何纹样、山水图案等。这些图案纹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牡丹、荷花、莲花、菊花、孔雀、凤凰、鹿、鸳鸯、蝴蝶、飞燕、仙鹤、龙、菱格形、方形、三角形等。选择的花卉和禽兽图案都表达着锡伯族人民求吉祈福、追求祥瑞平安的民族心理。色彩上以红、黄、绿、蓝为主色调,在图案布局上讲求对称。锡伯族男女婚嫁时,新房内往往有一种喜帐的挂饰物,它充满喜庆气氛。喜帐为大红绸缎或棉布料,最典型的是在正中绣有装饰性花卉图案,两侧绣有一对对称孔雀图案。帐下底边处绣有一排组合型喇叭花。孔雀上方有时还绣有祝福性的锡伯文。即使像婴儿吊床的装饰图案,一侧是对称性的弓箭组合图案,另一侧是以太阳纹为中心的对称飞龙舞凤图案,也折射着祈盼所生儿女成龙成凤的求吉心理。锡伯族家用的卧柜、竖柜、供桌、被橱等出现了较复杂的木雕技艺,圆雕、透雕、浅浮雕手法都常用,多数是宝瓶花卉对称图案。锡伯族女式绣花鞋就有无梁绣花鞋、双梁绣花鞋、单梁绣花鞋多种。绣花部位多在鞋头、鞋帮,常绣有牡丹、荷花、菊花等,亦有红底绿花、黑底红花多种。在此,对称是在整体布局中,以线条和色彩以及各种纹样图案之间的节奏、比例、复合、简繁、线条、色彩关系的和谐。在色彩上,锡伯族更多的是诉诸于感觉。从红色、黄色中感受到热烈、温暖;从蓝色、绿色中联想到凉爽或寒冷;黑色和白色从色度看,有明暗之别,因为这种性质归因于它的亮度,而不是它的色彩。锡伯族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深谙整体图案中,线条、图形、色彩互为关联,相互配合才能构成审美意义上的图案艺术。
在锡伯族宗教艺术中以萨满教神像、神歌、神舞三位为一体构成神圣世界。虽然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其造型和声态形式是功能性的,但所唱神歌、所跳萨满舞和所画神像蕴涵着艺术的种种因素。如:锡伯族的萨满画是萨满在举行祭祀祖先、上刀梯和跳神治病仪式时悬挂的神圣物,用毕即入匣收藏。萨满画按其绘画内容和功用大致分为三类:群体神像图、萨满画像和动物神灵图。20世纪初俄国人克洛特科夫在塔城发现锡伯族萨满神像图后,20世纪80年代锡伯族学者又在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现同一内容的群体神像图。这是布绘图像,其画面自上而下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最上一层画面为彩云、日月和“依兰恩杜里格格”(三位神姐)和“顾兴阿玛法”(男祖神)。这些祖神周围是虎、狼、狐狸、蛇、鹿等动物精灵。第二部分是各具神态的岱木林、阿玉鲁、额依嫩德德塔斯胡里、艾土罕、善琦、达玛法、阿里玛法、玛法默尔根、萨满玛法、着勒玛法等男女神灵形象。第三部分为合掌或单手祈祷及举杯为上刀梯者助威的近10位男女神灵,如张纳、着青额、纳松额、吴凌额、齐发罕珠、色楞芝等。第四部分为刀梯两侧的2位骑马萨满。第五部分画面最下端画有供桌,上置燃香的香炉。供桌右侧为3位手持神鼓萨满,左侧为一条白牛,后面为直入云端的刀梯,梯顶站立着萨满。这是一幅供上刀梯仪式时使用的画像。上刀梯仪式是锡伯族萨满教的独有仪式,举行这种象征仪式的动机据研究者认为:一是告诉人们通达神界并非易事,只有踏上实实在在的“刀梯”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并且暗示,不会人人都能做神界和人间的使者;二是显示萨满真有通达神界和治病救人的本事;三是为了区别有真“本事”萨满和无能萨满。画像中的众神灵既有萨满祖师、祖先神,也有瘟神、动物保护神等,甚至还出现了门神、灶神等。萨满在举行上刀梯、跳神治病等仪式时总是在其祷词中呼喊众位神灵,请神助佑其仪式成功。萨满画像是绘有萨满形象的图画。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幸福乡锡伯族民间发现的一幅萨满画像画面为:一位头戴三只鸟装饰神帽,身着萨满服的萨满坐于方凳上,左手高举绘有蛇形图案的萨满鼓,右手举至胸前微握,神像旁是一跪着的男子,面向萨满。萨满下面绘有水波纹,其上是一条飞龙。这类画像显然是哈拉姓氏或莫昆(家族)萨满祖神形象,是专供哈拉或莫昆后代萨满祭祀时使用的,有时在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悬挂,以便从祖神处求得神力。
动物神灵图是每一个萨满专用动物精灵的形象画像。动物精灵在锡伯语中称“巫出固”,实为萨满的动物保护神。每一个萨满均有自己的“巫出固,”有的是雕神,有的是虎神,有的是狼神。“巫出固”作为萨满的助手在跳神治病时助佑主人与病魔搏斗成功。在萨满“巫出固”中,虎神是女萨满保护神中的主神。
由于萨满画是功能性的,因此并不要求形似,也不可能形似。因为萨满画都出自民问画师之手,也有的是萨满本身绘制的,也就难免有很高的绘画技巧,而且作为仪式中的萨满画仅仅是个象征物,并不需要神形毕肖。由于萨满教仪式分为家祭仪式和公众集会仪式,萨满画也有所不同。家祭仪式中的萨满画可能是本族先辈萨满或祖先的形象,而像上刀梯仪式是一种广场式的公众集体仪式,所以悬挂的就是绘有众神的上刀梯图。萨满画中的人物服饰明显具有时代特征,一幅绘于清代的萨满画中的祖先神著的就是清代官服。
在屯垦艺术中,清乾隆年间以回屯身份屯田于伊犁的维吾尔族从世居的天山以南地区带去了他们的乐舞艺术,并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伊犁木卡姆和麦希莱甫,这是一种民间传播的方式。另一种是由木卡姆艺术家将其带到伊犁。据考证,清光绪十九年(1893),喀什著名的木卡姆艺术家穆罕默德·毛拉等人把喀什木卡姆带到伊犁,于是促成了伊犁木卡姆的形成。伊犁木卡姆同样由十二套组成,即1.拉克木卡姆;2.且比亚特木卡姆;3.木夏乌热克木卡姆;4.恰尔尕木卡姆;5.潘吉尕木卡姆;6.乌扎勒木卡姆;7.艾介姆木卡姆;8.乌夏克木卡姆;9.巴雅特木卡姆;10.纳瓦木卡姆;11.于孜哈尔木卡姆;12.玉赛因木卡姆。和喀什木卡姆比较,伊犁木卡姆没有“琼拉克曼”部分,只有“散序”、“达斯坦”和麦西莱甫,但结构相同,因此伊犁木卡姆应是喀什十二木卡姆的翻版,称为喀什木卡姆伊犁版更恰当。伊犁木卡姆在结构上除开始的散序外,在各曲之间还有过门和间奏。伊犁木卡姆调式与喀什木卡姆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布局上,常采用不同调式作对比并在调式转换时常常运用主音位置不变而变换调式的手法。伊犁木卡姆形成2/4、3/4、4/4、5/4、6/4、7/8、9/8七种基本节奏型。据一些田野调查资料披露,穆罕默德·毛拉精通十二木卡姆,他是将有72个达斯坦乃合曼(分别取材于不同的12部长诗)的达斯坦部分带入伊犁并广泛流传的艺术家。他在伊犁生活了40多年。他的弟子艾山弹拨儿、肉孜弹拨儿、玉赛音弹拨儿、巴拉提弹拨儿等人也对丰富和发展伊犁木卡姆有所建树。其后,还有则克力艾里帕塔搞出了一个含有一个序曲、一个太孜、六个达斯坦的糅合沙里木卡姆。这是富有伊犁特色的有创新意识的木卡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演的维吾尔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就采用了糅合沙里木卡姆中的达斯坦乐曲。
麦希莱甫是木卡姆大曲结束后的载歌载舞部分,有“集会”、“聚会”之意,是一种民间性的娱乐歌舞集会。麦希莱甫分“喜庆麦希莱甫”、“集体麦希来甫”、“邀请麦希莱甫”、“节日麦希莱甫”、“和解麦希莱甫”等不同形式。麦希莱甫因地域不同形成各异的民俗文化表征。伊犁麦希莱甫自然也充满了地区性的文化特征,如形成同龄人之间的冬季轮流麦希莱甫、河边野游麦希莱甫等。这与伊犁风光秀美,维吾尔族有野游的习俗有关,这时也成了举行麦希阿莱甫的最好时光。麦希莱甫除载歌载舞外,还穿插有各种民间游戏娱乐活动,如抢腰带、献茶唱歌、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惩罚”性游戏等。节庆婚嫁时的麦希莱甫以参加人数多、场面宏大、气氛热烈而著称。
附注
①所引民歌均见《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
①〔丹麦〕亨宁·哈士纶:《蒙古人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95~196页。
①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均引自郝苏民选编《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①仲高著:《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国文库),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256~257页。
①星汉编著:《清代西域诗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①锡伯族民歌均引自关学宝主编《锡伯族民歌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①仲高:《西迁歌:锡伯族的精神家园》,《西域研究》,1996(3)。
①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326页。
②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84页。
①仲高:《西域萨满教岩画的文化阐释》,《西域研究》,2003(1)。
①淑云著:《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1页。
①《萨满教文化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21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342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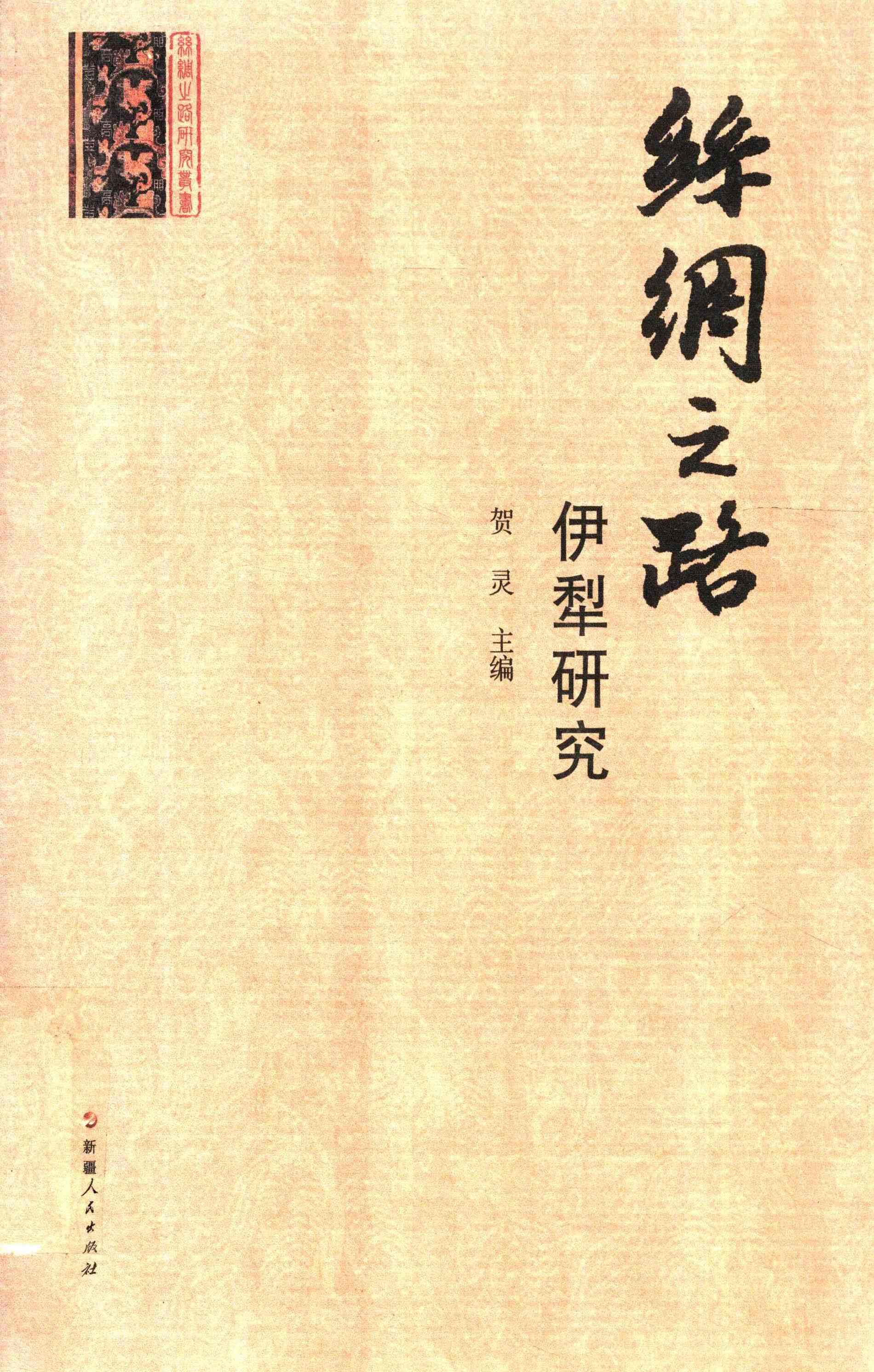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