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宗教文化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72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原始宗教文化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11 |
| 页码: | 202-212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伊犁地区是古代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 |
| 关键词: | 伊犁 宗教 宗教文化 |
内容
伊犁地区是古代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古代伊犁地区生活着众多的部落和居民,如塞种、匈奴、乌孙、大月氏、葛逻禄、突厥、契丹、蒙古、汉等。在宗教信仰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先后流传过原始崇拜、萨满教、祆教、佛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道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现在伊犁地区生活着哈萨克、汉、维吾尔、回、蒙古、锡伯等数十个民族成分,主要的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保留在民间的萨满教残余。这种长时期的多民族聚居、融合和多宗教的并存、交融,形成了伊犁地区丰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在新疆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萨满教是西域包括伊犁早期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对天、地、日、月、星辰、山、水、火、雷电等的崇拜以及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和萨满教的崇拜观念,曾经长期支配着伊犁先民的精神生活。
在自然崇拜中,对天的崇拜在诸游牧民族中有较为突出的地位。突厥语和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而这一名称的来源则为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语。可见匈奴人很早就有对苍天的崇拜。《汉书》记载:“匈奴俗,岁有云龙祠,祭天神”①。说明匈奴人早就把“腾格里”尊为天神,并设祭坛,受到匈奴人的特殊崇拜。匈奴酋长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即“腾格里”的不同汉译,“孤涂”为“子”,意即“苍天之子”。这与中原皇帝称“天子”是一个意思。匈奴冒顿单于自称是“天所立匈奴大子”,认为自己有上天佑护。公元前2世纪冒顿单于征服月氏及西域诸国时,就被看做是“以天之福”。汉武帝时,匈奴单于在马邑中计受伏,有汉朝尉史告密,得以逃脱。单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遂封尉史为“天王”①。有传说,“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②。这一传说足见匈奴人对于天献祭的重视。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除秋天的一次是为稽查人口增减和牲畜繁殖情况外,其余两次都是祭祀天神的集会。献祭天神多将祭品置于高台或高杆之上。突厥人在每年的5月中旬拜天献祭。《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记载有乌古斯可汗立12米高的木杆,杆顶挂鸡,杆下拴羊的祭天方式。乌孙人、康居人称天为“唐厄尔”或“苍唐厄尔”,也献祭拜天。突厥人十分崇拜天神,认为天神“腾格里”是主宰一切的神,在突厥鲁尼文的碑铭中,记载有“上天(腾格里)、女神(乌买)及神圣地水”,“蒙天之佑”(暾欲谷碑),“承上天之志”,“由天之意”(阙特勤碑),“承上天下地之福”(毗伽可汗碑)等语。《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里也经常提到“腾格里”。表达了对“腾格里”的崇拜和赞颂。
突厥部落阿史德氏崇拜天神,另一部落阿史那氏原来崇拜日神,两部世代联姻。后来,突厥人把崇拜天、日合而为一,日为神相,天为神名,形成敬天拜日的习俗,天神具有全智、全能的性质,并总是作为突厥人的保护神出现。祭祀时,只有朝着日出的东方跪拜,才能获得神的赐福。因此,突厥人的住所和墓地总是选择在高地,在空旷的草原上举行祭祀,需人工营建高台。据史载,突厥人祭天的风俗:“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之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③。据学者研究:“按勃登凝黎,实乃tengri的译音,其意非地神,而是天神,参稽其他史料,”这一在河畔山上祭拜天神的最盛大的节日乃五月八日④。
蒙古人有拜天之礼,天神“腾格里”是最主要的崇拜对象。史称蒙古人“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⑤天神在蒙古人的信仰中成为众多神灵中最高的神,以后又分出一些各司其职的诸天神,如马尼汗腾格里(主管狩猎)、吉雅其腾格里(主管牲畜)、巴特尔腾格里(给人以勇气和力量的英雄天神)、比斯满腾格里(主管财富)等等。
蒙古人崇奉地神,尊地神为“地母”。“彼等有神,名称纳赤该,谓是地神,而保佑其子女牲畜田麦者,大受礼敬。各置一神于家,用毡同布制作神像,并制神妻神子之像,位神妻于神左,神子之像全与神同。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神子之口,已而取肉羹散之家门外,谓神及神之家属由是得食”⑥。
古代塞人、乌孙人盛行太阳崇拜。在塞人崇拜的诸神之中,太阳神为最高之神。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作为牺牲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①。乌孙人把太阳尊为神来崇奉,每年都要宰马举行祭太阳的活动。在许多塞人生活过的地方都发现有祭马坑。他们还认为火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因此,对火的崇拜也就是对太阳的崇拜。
匈奴人还有拜月之俗:“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要看星月,月盛则议战,月亏则退兵②。蒙古人也崇拜月亮,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顾忌。见新月必拜“③。“秋出兵,春休兵,岁岁验中秋夜月明为利,即兴兵。若中秋夜风雨晦冥为不利,即不兴兵”④。哈萨克先民崇拜新月,每当新月初升时,女子要面向月亮下跪,男子面向月亮肃立,双臂伸直,手心向里,向月亮祈祷。哈萨克族杜拉特、阿尔根等部落的印记是太阳形圆圈,萨尔齐马尔万、艺格泰等部落的印记是半月形。在突厥人的神话传说中,月亮是第一个被天神创造出来的神,称月亮为Ayiata(月亮父亲)。星辰也为哈萨克先民所崇拜,相信星星代表着人的生命,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人。每当一颗流星陨落,便认为必也有一人殒命;把互相仇视的人称为“克星”。北斗七星和启明星(金星)格外受崇拜,被认为是神星。北斗星是“七个看守”,守护着两匹天马。或认为它们是七只天狼或天狗。金星被看作是夜间为人们指路的善神。
风雨雷电是神秘的自然现象之一,古人不能理解,既十分畏惧,又崇拜有加。每当第一声春雷轰鸣时,游牧人便认为是天神天恩的吉兆,老年妇女一边绕着毡房行走,一边用盛着牛奶或马奶酒的勺子敲打毡房,向天神祈祷。当下第一场春雨时,男人要摘下皮帽,光头淋雨,并祈祷天神降下喜雨,大地生长青草。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把遭雷劈看成是天神最严厉的惩罚。据史书记载,古代游牧人有“喜致雷霆”、“呼叫射天”之礼。即当第一声春雷轰鸣时,便以为是天神开恩,使春回大地,万物更新,牧民无不欢喜鼓舞。同时对这种威力巨大的雷霆,也十分畏惧。所以当发生雷击死人事件时,全部落都要举行呼叫射天之礼,并因此而集体迁徙避凶。到来年秋,仍须举行祓除仪式,以消灾避祸。古代游牧民族对雷电的敬畏与崇拜天神是一致的。雷鸣被认为是天神发怒的巨吼,“呼叫射天”的习俗,实际上也是对天神的祭祀。
在哈萨克语中,风神被称作“吉尔依耶”,是受天神派遣的诸神之一,但却是被当做恶的神灵来崇拜的。这是因为暴风雪和飓风对草原上的人畜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强烈的旋风常使游牧民的毡房被摧毁。因此,当旋风刮起的时候,人们便以为是天神所遣,十分惧怕。《周书》记载,突厥木杆可汗本来许婚于周,后又反悔,“会大风起,飘风坏其穹庐,旬月不止,俟斤(即木杆可汗)大惧,以为天遣,乃备礼送后”①。
山神、水神是古代游牧民崇拜的诸多自然神灵之一。伊犁多高山大川,巍峨壮丽的天山和阿尔泰山都被视为“腾格里山”加以膜拜。认为天山、阿尔泰山即为“腾格里”的化身或天神所居,所以对这些大山十分崇拜。
游牧民对水的崇拜来源于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突厥语称大河为“乌鲁克苏”,意为“伟大的水”,将水流湍急的河视为一种伟大的、超自然的力量而加以崇拜。泉水特别是温泉,尤其受到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崇拜,认为这种泉水是神水,可以治愈各种疾病。特别是有些泉水被认为与生殖有关,将泉视为女阴,被称为“圣泉”,如伊犁地区特克斯县和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的两处温泉,都被当做主管生育的圣泉而加以膜拜。
操伊朗语的古代塞种人认为,水是诸神创造的,诸神的活动多与水有关。表明生活在干旱沙漠地带的人们渴望获得洁净与充沛的水源。为此,塞人都定期向水献祭。祭品由牛乳和两种植物构成,代表水所滋养的动物和植物。家中的长者选择居所附近的河流、溪水或井水,一边祈祷,一边把祭品投入水中。每逢重大节日或典礼,则由祭司主持仪式祭水。②在游牧民中,对火的崇拜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突厥人认为,火是圣洁的,具有祛邪避灾的净化功能,是部落人畜的保护神。传说突厥始祖伊质泥师有四子,长子的部落居于高山,其地“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③。
火不但可以从严寒中给突厥人带来温暖,而且可以驱除外人带来的鬼祟。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进入西突厥境内,“有突厥人来言,能驱逐魔鬼,预阻不祥之兆,于是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取行李置众人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持香火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逐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尊敬
④。拜占庭历史学家狄奥菲拉特在其《历史》一书中记载:突厥人崇拜火,空气和水,颂扬大地和水,但仅奉天地唯一造物主为神,用马牛羊祭祀他,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⑤火被视为突厥部落和家庭的保护神。乌孙人、康居人则把火看做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
在塞人的游牧生活中,祭火是他们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平时向家居的炉膛之火献祭,每日三次,在晨祷、午祷、晚祷时进行。祭品也有三样:清洁的木柴、香料和一小块脂网。公元初年,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4~23)曾目睹波斯人祭火,“加入干燥、没有枝杈的木柴,把软化的脂油置于火上”⑥。
对火的崇拜,反映了古代先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向往光明、温暖的生活,驱走黑暗和寒冷;火是具有巨大神秘力量的神灵,可以祛除一切魔鬼和秽气,保证人畜不受猛兽、瘟疫的侵害,使人畜生存繁衍。人们精心保护火种,使其延续不断。
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动物崇拜极为盛行,还有许多动物被演化为氏族图腾举凡与游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如野兽类的狼、熊、狮、虎、豹、狐、鹿、野山羊等;家畜中的骆驼、马、牛、羊、狗;飞禽类的鹰、天鹅、乌鸦等,都被神化,认为这些动物各有其神通,具有灵异,从而加以崇拜。其中苍狼在突厥语诸部的动物崇拜中最具特殊地位,它被普遍认为与自己的祖先有某种血缘关系,并被视作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和图腾。狼是草原上最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具有凶猛、矫捷、顽强、诡谲等特点,而且常常群体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同时,狼也是草原上对人畜危害最大的动物,人们对它无能为力,进而产生敬畏,奉之若神,希望得到像狼一样的勇气和智慧,也祈求狼神保佑部落氏族人畜兴旺。
突厥语部落有许多关于“狼祖”、“狼生”的传说。乌孙人传说其祖先昆莫王是狼用奶水哺育长大的。《汉书》记载:“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①。另据乌孙昆莫乌就屠之子,第二代小昆莫名为“拊离”,而拊离即突厥语bori,狼之意狼被乌孙人追溯为母系的祖先而受到格外的崇拜。高车部则认为其祖先是一只公狼,狼祖传说也源自于此。
古代哈萨克、维吾尔族先民保持着狼图腾崇拜。《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是一头大公苍狼指引着乌古斯可汗在几次战斗中获得胜利。狼还是男子和英雄的代名词。《突厥语大词典》说,妇女若生了男孩,产婆便说生了狼,因男子英武、强健;若生了女孩,便说生了狐,因女子妩媚,讨人喜欢。②哈萨克族认为苍狼是保护祖先灵魂的神兽,能给予英雄、巫师特殊的神力。哈萨克巫师的诸神之一是狼,有些哈萨克部落的口号是狼,旗帜上也绘着狼像,英雄也被喻作狼。他们关于狼的传说,和突厥人“狼祖”的传说以及与狼相联系的古老信仰是十分相似的。
突厥人还有关于“鹿祖”和鹿图腾崇拜的传说。传说中,突厥阿史德氏祖先射摩舍利与海神婚配,海神女每日派金角白鹿迎送射摩入海。说明与其部祖先婚配的海神女为一个出自以白鹿为图腾的氏族。
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富蕴两县境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0多件“鹿石”。鹿石是一种石雕,古人先把石头做成长条形,在上面雕刻出鹿的图像,然后竖立在墓前。鹿石上鹿的图案姿态各异,造型十分优美。据专家考证,阿勒泰的鹿石为公元前1000年,即青铜时期古代塞人的遗物。这种鹿石与许多地方(如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十分相似,表明活动在阿尔泰山区的人还有崇拜鹿的习俗,以鹿为自己的图腾。在一些部落中,对山毛榉树尤为崇敬,把山毛榉奉为“圣树”。巫师念咒治病,举行祭祀,都要在山毛榉树旁进行。
古代游牧民族崇敬鹰鹫等勇鸷的猛禽,称鹰为神鹰,神鹰可以沟通天界,为人间与天神腾格里的使者。传说古代乌孙、康居的有些部落氏族是以猫头鹰为图腾的。猫头鹰的羽毛被哈萨克族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常佩缀在年轻女子的帽子上,婚嫁时装饰在新房的壁毯上,挂在婴儿的摇篮上,认为可以消邪取吉。赛马时也在马头、马尾饰以鹰羽,以祈马像鹰一样飞驰。有些突厥部落也把鹰作为图腾,如阙特勤碑上就雕刻有一只鹰。史诗《玛纳斯》中的柯尔克孜英雄玛纳斯,传说是其父梦见鹰落手中而使妻子怀孕,生下玛纳斯,少年玛纳斯称雏鹰,长大后称雄鹰;玛纳斯死后,他身边的鹰也飞走了。柯尔克孜人把自己的英雄祖先与神鹰联系在一起,具有雄鹰一般的勇猛和灵力,表现了鹰崇拜的信仰观念。
在哈萨克族有关族源名称的诸种传说中,就有一种传说认为哈萨克的始祖是白天鹅。传说,古时有一个叫卡勒夏哈德尔的首领,英勇无比,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他只好躺下来。眼看死神就要降临,这时,天空突然奇迹般地开了一个空隙,飞来一只白色雌天鹅,给他滴了一滴口涎,然后把他带到河边。他喝了水,体力逐渐得到了恢复,伤势也慢慢痊愈。这时,那只美丽无比的白天鹅变成一个举世无双的美丽少女。他喜出望外,与这位姑娘结为伉俪。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哈萨克”(kazak)。这个传说在哈萨克人中颇有影响,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①
此外,在天山、阿尔泰山的一些古代游牧人留下的岩画里,可以看到刻画在岩壁上的虎、豹、骏马、奔鹿、犬、山羊等动物的形象。这些都反映了西域古代游牧民族动物崇拜的内涵。
在古代游牧民族中,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都很盛行,这是与他们经历的从狩猎过渡到游牧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从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的原始社会体制分不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宗教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也必然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萨满教是新疆古代居民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之一,在古代游牧民族中十分盛行。伊犁现在的少数民族如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柯尔克孜、锡伯、满、达斡尔以及塔塔尔、乌孜别克族的祖先都曾信奉过萨满教。“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和对萨满巫师的崇拜长期支配着远古人们的思想,至今仍遗留下不少痕迹。这些民族后来又信仰了祆教、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阶级社会的宗教,但原始的萨满教观念习俗在这些民族中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萨满教的信仰十分广泛复杂,几乎包括了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崇拜的所有内容。萨满教原始的活动方式就是以频繁祭祀、降神附体、跳神驱鬼、卜问神灵、施展巫术来祈福免灾。巫师(即萨满)是神与人沟通的中介,是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据记载,匈奴、月氏等部族内早就存在着“胡巫”,即萨满术士,所用法术通常是祝诅咒语。胡巫在氏族部落的地位很高,对军事、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乌孙人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自己的巫师,萨满巫师的形象被刻画在洞岩上。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山里发现的康巴勒洞窟里面,画有人面形的神灵图。在阿勒泰市区旁一座将军山的岩画上,也刻画有与这种人面神形图完全一样的形象,戴着一顶尖形的帽子,与史书记载的“降神之巫曰萨麻,帽如兜銎,缘垂五色增条,长蔽面”①的萨满装束十分相似。
巫师不仅可以占卜,主持祭祀活动,使用巫术给病人看病,而且还有权对部族的习惯法作出解释。
柔然人信仰萨满教,其部内有女萨满巫师,也有男萨满。据《魏书》记载,蠕蠕(柔然)可汗所娶的一个妻室,就是豆浑地方的一个女巫:“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②。《梁书·芮芮传》记载:“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曀而不雨,问其故,以暖云”。巫师在柔然的地位很高,出则佐军,入则参政,女巫师妻尚可汗,进入宫廷,对柔然政治产生影响。
高车萨满巫师多为女性,“善用五十箸卜吉凶”③。祭祀天地、日月、星辰等,以狼祖为图腾,特别畏惧雷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④。女巫显然是母系氏族时代祭祀崇拜的遗留。突厥人信萨满教,“敬鬼神,信巫“⑤,“祭司预言未来之事”⑥,“祭司”即萨满巫师。突厥巫师以火占卜,预知未来之事。《萨满教今昔》一书中引用阿拉伯人对突厥人火卜的描述说:“突厥人的大统治者都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在这一天要为自己点一堆大火,要向火祭祀且祈祷。这火上有很大的火焰升起,火焰如果呈淡绿色,就预示将有充足的雨和好收成;如果火焰是红色的,预示着要发生战争;如果是黄色的,将有疾病和瘟疫;如果是黑色的,就说明统治者要死,或者到远处去旅行”。以羊肩胛骨占卜,也必经过在火上烘烤,才能烧出裂纹,观裂纹以卜凶吉。在突厥人中,萨满巫师地位很高。据传说,突厥先祖泥师都就是一位“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⑦的萨满。萨满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事,可汗都要听从萨满的意见,由萨满预卜凶吉,决定取舍进止。可汗登基,要由萨满充当神的使者,代表神意,授权新主。“其王初之,近侍、重臣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立乘马,以帛绞颈,使才不致绝,然后释,而急问曰:你能作九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①
新疆锡伯族、满族、达斡尔族的祖先都信奉萨满教。“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萨玛,巫觋也。其跳神法,萨玛击太平鼓作歌,病图92锡伯族萨满之一者亲族和之,词不甚了了,尾声似曰耶格耶,无分昼夜,声彻四邻。萨玛曰祖宗要马,则杀马以祭,要牛则椎牛以祭。至于骊萸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者。然续有人病,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萨玛之令,终不敢违”。②
“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跳一次,或季跳一次,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树丈余细木于墙院南隅,置斗其上,谓之曰竿,祭时着肉斗中,必有鸦来啄食之,谓之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妇,以铃击臀后,摇之作响,而手击鼓,鼓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而口致颂祷之词,词不可辨,祷毕跳跃旋转,有老虎回回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飞石黑阿峰。飞石黑阿峰者,粘谷米糕也,色黄如玉,质腻,掺以豆粉,蘸以蜜,跳毕,以此遍馈邻里亲族,而肉则拉人于家,食之以尽为度,不尽则为不祥”③。
萨满教在游牧民族中流行的时间相当久远,在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一直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所以其信仰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之间,长期支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生活。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萨满教信仰观念及其习俗,发祥于人类启蒙阶段,伴随人类的成长而成熟,成为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习俗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始的萨满教逐渐被兴起的人为宗教所取代。这些民族后来尽管信仰了其他宗教,但这种原生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一直深刻影响着并渗透于其他宗教里面,形成这些民族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
萨满巫师并没有因萨满教的衰落而消失,长期以来他们继续活跃在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中。不过名称已经从早期的“喀木,”演变为“巴合西”,哈萨克语称为“巴克思”,女巫师称“库什娜西”。遗留在维吾尔族民间的巫师,往往头戴一种白色或灰色的圆形或三角形毡帽,有的则留着披肩长发,作法时穿上妇女的裙子,女巫师梳着许多小辫,垂及耳侧脑后。哈萨克族巫师以天鹅皮制成神帽,插上猫头鹰羽毛,头上留一束头发。
在哈萨克族,“巴克思”被认为是博学之士、诗人、乐器演奏家、吟诵史诗的歌手、部落氏族的谋士。在跳神时,他们用库布兹琴伴奏歌唱,兴奋时即发表吉凶预言。在战争时,他们在军队首领身旁,演奏库布兹,歌颂英雄祖先,激励士气,并施巫术作法。平时则为人占卜、行医。有些巴克思也被称为“谢赫”(原意为伊斯兰教长老),他们身上都带着占卜用的40颗石子,有些谢赫终身不娶,以占卜、治病、跳神为生。有些巴克思称为“迪瓦纳”,他们身穿天鹅皮衣,骑白马,手持短矛或拐杖,人们认为他们是隐修者,追求萨满之路和真主之路的圣徒,可预知未来,神通广大,用手一指便能治愈患者,因而极受尊崇。同时,巴克思在传播和发展古代哈萨克诗歌、音乐、文学艺术、雕刻和杂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被认为是“哈萨克古代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①。
在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族民间都保留有大量的萨满教遗俗。这些遗俗被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例如清代文献记载的维吾尔族民间有祭天、祭山、祭祖的所谓三祭习俗;农村中盛行的麻扎朝拜;民间的求水祈雨仪式等,都可以看见萨满教的遗留。哈萨克族的求雨仪式名为“塔萨特克”,于干旱季节在河边举行。由聚集的人们捐献牲畜,向腾格里宰牲祭祀。祭祀时,大毛拉用白色大布将《古兰经》悬挂于一高木架上,然后站在《古兰经》下摊开双手,向腾格里和真主祈祷,念诵降雨的祷文。人们则按照对腾格里或真主的虔诚,凑一点作为布施的现金,然后分吃作为祭品宰杀的牲畜,向腾格里和真主叩头祷告,认为这样做便能降雨。还有表示祝福、祈求的“巴塔”仪式;为亡人点燃“四十支蜡烛”的驱魔仪式;诵唱咒语的“阿尔包”遗俗等等,都体现了原始萨满教在民间的遗俗。
在哈萨克族民间,巴克思充当着从前萨满的角色,预言未来,为病人念咒治病和进行跳神活动。他们到病人家或显贵人家跳神,多在夜间举行。先在毡房中央点燃一堆火,病人和阿吾勒(牧村)的人们来后,巴克思开始用冬不拉琴弹奏召唤鬼神的乐曲。这些乐曲是被称为巴克思之神的霍尔赫特遗传的最古老的乐曲,古时用库布兹琴演奏。巴克思一边弹冬不拉,一边唱歌。主要内容是祷告腾格里和召唤自己的鬼神。不久巴克思开始兴奋、焦躁、浑身颤抖,用臀部撑地移动身体,同时面色变得令人恐怖,这表示他的鬼神正在前来。稍后,巴克思从地上站起,这表示他的鬼神已经到来。巴克思从地上站起时,由其他人继续弹奏乐曲。这时巴克思一边围着火堆绕圈子,一边自言自语,呼唤鬼神之名。巴克思跳神时,还常用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持斧头砍自己的胸脯,伸舌头舔烧红的铁。有些巴克思跳神时,跳上毡房的天窗大发雷霆,或一边骑马绕毡房奔跑,一边大喊大叫。有些巴克思在跳神时异常兴奋,浑身颤抖,最后常疲惫至极,昏迷倒地。醒来后,便说自己如何与自己的鬼怪、精灵及神仙见面、交谈,并以它们的话向人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巴克思跳神治病,对重病患者则断定遭到了瘟疫,是由于瘟神报怨,魔鬼附体,灵魂不满所致。以前,哈萨克人认为,大巴克思跳神可祛病禳灾,驱赶凶神,甚至能在患者不觉的情况下打开患者的腹腔撵走疾病,故极力请他们来家里跳神。①
祖先崇拜是萨满教崇拜的重要内容,集中表现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西域古代游牧部族的葬仪葬式虽有所不同,但信仰灵魂不灭、崇拜祖先亡灵的宗教观念却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能够庇护子孙,福佑部落。崇拜共同的祖先,可以加强氏族部落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血缘关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和部族之间的纷争,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部落强盛繁荣、平安吉祥,人民勇敢尚武。
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游牧民族长久地保持着祖先崇拜的风俗。哈萨克族“灵魂不死”的观念有其特点,认为人虽死,但其灵魂不死。当人死亡时,其灵魂变成鸟或昆虫飞离肉体,如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灵魂是肉体的客人”。哈萨克人崇拜著名的部落头目、英雄、巫师、圣贤的亡灵,尤其崇拜本部落祖先之灵,认为办好丧葬仪式,亡灵便会满意,会时刻保佑后代和部落,否则亡灵便会发怒,后代就会遭逢不幸,或疾病蔓延,或牲畜死亡,或作战时会意志消沉遭到失败。哈萨克族人只要身陷困境、遭逢不幸,便向祖先之灵宰牲祭献,认为给死者
宰牲越多,其亡灵便越满意,从而大施恩德。没有生过孩子的妇女常在祖先的墓边过夜,祈求生孩子。在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中,英雄陷入困境时,便向祖先祷告,求祖先在其梦中出现并佑助,帮助英雄百战百胜。哈萨克族人认为,著名英雄和部落长老的亡灵能够佑助,故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部落和氏族,并把部落或氏族的旗帜当作祖先的旗帜,世代相传;若遭到侵犯,便去祖先之墓,插上旗帜,在那儿住宿,并宰牲祭献,全体痛哭,祈求援助。因有此信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部落把18世纪英雄贾尼别克的白色旗帜完好无损地保存至近代。①柯尔克孜族崇拜祖先,尤其是英雄祖先格外受崇拜。英雄史诗《玛纳斯》就是柯尔克孜族崇拜自己的英雄祖先玛纳斯及其八代英雄后代的古老传说。
这些习俗都是哈萨克族先民信仰萨满教时遗留下来的古俗,有些习俗保留至今。萨满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都有大量的遗留,反映了这种原始的宗教形态在新疆地区长期流行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萨满教逐渐让位,这是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过程。但是,由于萨满教的长期流行,特别是它是一种人们初始的、原生的宗教思想意识,许多观念和习俗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不会随着新的宗教的流行而完全消失。这些观念和习俗也必然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其他宗教里,形成地区化、民族化的特点。这是萨满教在许多少数民族中留存有大量遗迹的根源。
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萨满教是西域包括伊犁早期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对天、地、日、月、星辰、山、水、火、雷电等的崇拜以及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和萨满教的崇拜观念,曾经长期支配着伊犁先民的精神生活。
在自然崇拜中,对天的崇拜在诸游牧民族中有较为突出的地位。突厥语和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而这一名称的来源则为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语。可见匈奴人很早就有对苍天的崇拜。《汉书》记载:“匈奴俗,岁有云龙祠,祭天神”①。说明匈奴人早就把“腾格里”尊为天神,并设祭坛,受到匈奴人的特殊崇拜。匈奴酋长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即“腾格里”的不同汉译,“孤涂”为“子”,意即“苍天之子”。这与中原皇帝称“天子”是一个意思。匈奴冒顿单于自称是“天所立匈奴大子”,认为自己有上天佑护。公元前2世纪冒顿单于征服月氏及西域诸国时,就被看做是“以天之福”。汉武帝时,匈奴单于在马邑中计受伏,有汉朝尉史告密,得以逃脱。单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遂封尉史为“天王”①。有传说,“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②。这一传说足见匈奴人对于天献祭的重视。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除秋天的一次是为稽查人口增减和牲畜繁殖情况外,其余两次都是祭祀天神的集会。献祭天神多将祭品置于高台或高杆之上。突厥人在每年的5月中旬拜天献祭。《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记载有乌古斯可汗立12米高的木杆,杆顶挂鸡,杆下拴羊的祭天方式。乌孙人、康居人称天为“唐厄尔”或“苍唐厄尔”,也献祭拜天。突厥人十分崇拜天神,认为天神“腾格里”是主宰一切的神,在突厥鲁尼文的碑铭中,记载有“上天(腾格里)、女神(乌买)及神圣地水”,“蒙天之佑”(暾欲谷碑),“承上天之志”,“由天之意”(阙特勤碑),“承上天下地之福”(毗伽可汗碑)等语。《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里也经常提到“腾格里”。表达了对“腾格里”的崇拜和赞颂。
突厥部落阿史德氏崇拜天神,另一部落阿史那氏原来崇拜日神,两部世代联姻。后来,突厥人把崇拜天、日合而为一,日为神相,天为神名,形成敬天拜日的习俗,天神具有全智、全能的性质,并总是作为突厥人的保护神出现。祭祀时,只有朝着日出的东方跪拜,才能获得神的赐福。因此,突厥人的住所和墓地总是选择在高地,在空旷的草原上举行祭祀,需人工营建高台。据史载,突厥人祭天的风俗:“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之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③。据学者研究:“按勃登凝黎,实乃tengri的译音,其意非地神,而是天神,参稽其他史料,”这一在河畔山上祭拜天神的最盛大的节日乃五月八日④。
蒙古人有拜天之礼,天神“腾格里”是最主要的崇拜对象。史称蒙古人“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⑤天神在蒙古人的信仰中成为众多神灵中最高的神,以后又分出一些各司其职的诸天神,如马尼汗腾格里(主管狩猎)、吉雅其腾格里(主管牲畜)、巴特尔腾格里(给人以勇气和力量的英雄天神)、比斯满腾格里(主管财富)等等。
蒙古人崇奉地神,尊地神为“地母”。“彼等有神,名称纳赤该,谓是地神,而保佑其子女牲畜田麦者,大受礼敬。各置一神于家,用毡同布制作神像,并制神妻神子之像,位神妻于神左,神子之像全与神同。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神子之口,已而取肉羹散之家门外,谓神及神之家属由是得食”⑥。
古代塞人、乌孙人盛行太阳崇拜。在塞人崇拜的诸神之中,太阳神为最高之神。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作为牺牲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①。乌孙人把太阳尊为神来崇奉,每年都要宰马举行祭太阳的活动。在许多塞人生活过的地方都发现有祭马坑。他们还认为火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因此,对火的崇拜也就是对太阳的崇拜。
匈奴人还有拜月之俗:“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要看星月,月盛则议战,月亏则退兵②。蒙古人也崇拜月亮,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顾忌。见新月必拜“③。“秋出兵,春休兵,岁岁验中秋夜月明为利,即兴兵。若中秋夜风雨晦冥为不利,即不兴兵”④。哈萨克先民崇拜新月,每当新月初升时,女子要面向月亮下跪,男子面向月亮肃立,双臂伸直,手心向里,向月亮祈祷。哈萨克族杜拉特、阿尔根等部落的印记是太阳形圆圈,萨尔齐马尔万、艺格泰等部落的印记是半月形。在突厥人的神话传说中,月亮是第一个被天神创造出来的神,称月亮为Ayiata(月亮父亲)。星辰也为哈萨克先民所崇拜,相信星星代表着人的生命,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人。每当一颗流星陨落,便认为必也有一人殒命;把互相仇视的人称为“克星”。北斗七星和启明星(金星)格外受崇拜,被认为是神星。北斗星是“七个看守”,守护着两匹天马。或认为它们是七只天狼或天狗。金星被看作是夜间为人们指路的善神。
风雨雷电是神秘的自然现象之一,古人不能理解,既十分畏惧,又崇拜有加。每当第一声春雷轰鸣时,游牧人便认为是天神天恩的吉兆,老年妇女一边绕着毡房行走,一边用盛着牛奶或马奶酒的勺子敲打毡房,向天神祈祷。当下第一场春雨时,男人要摘下皮帽,光头淋雨,并祈祷天神降下喜雨,大地生长青草。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把遭雷劈看成是天神最严厉的惩罚。据史书记载,古代游牧人有“喜致雷霆”、“呼叫射天”之礼。即当第一声春雷轰鸣时,便以为是天神开恩,使春回大地,万物更新,牧民无不欢喜鼓舞。同时对这种威力巨大的雷霆,也十分畏惧。所以当发生雷击死人事件时,全部落都要举行呼叫射天之礼,并因此而集体迁徙避凶。到来年秋,仍须举行祓除仪式,以消灾避祸。古代游牧民族对雷电的敬畏与崇拜天神是一致的。雷鸣被认为是天神发怒的巨吼,“呼叫射天”的习俗,实际上也是对天神的祭祀。
在哈萨克语中,风神被称作“吉尔依耶”,是受天神派遣的诸神之一,但却是被当做恶的神灵来崇拜的。这是因为暴风雪和飓风对草原上的人畜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强烈的旋风常使游牧民的毡房被摧毁。因此,当旋风刮起的时候,人们便以为是天神所遣,十分惧怕。《周书》记载,突厥木杆可汗本来许婚于周,后又反悔,“会大风起,飘风坏其穹庐,旬月不止,俟斤(即木杆可汗)大惧,以为天遣,乃备礼送后”①。
山神、水神是古代游牧民崇拜的诸多自然神灵之一。伊犁多高山大川,巍峨壮丽的天山和阿尔泰山都被视为“腾格里山”加以膜拜。认为天山、阿尔泰山即为“腾格里”的化身或天神所居,所以对这些大山十分崇拜。
游牧民对水的崇拜来源于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突厥语称大河为“乌鲁克苏”,意为“伟大的水”,将水流湍急的河视为一种伟大的、超自然的力量而加以崇拜。泉水特别是温泉,尤其受到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崇拜,认为这种泉水是神水,可以治愈各种疾病。特别是有些泉水被认为与生殖有关,将泉视为女阴,被称为“圣泉”,如伊犁地区特克斯县和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的两处温泉,都被当做主管生育的圣泉而加以膜拜。
操伊朗语的古代塞种人认为,水是诸神创造的,诸神的活动多与水有关。表明生活在干旱沙漠地带的人们渴望获得洁净与充沛的水源。为此,塞人都定期向水献祭。祭品由牛乳和两种植物构成,代表水所滋养的动物和植物。家中的长者选择居所附近的河流、溪水或井水,一边祈祷,一边把祭品投入水中。每逢重大节日或典礼,则由祭司主持仪式祭水。②在游牧民中,对火的崇拜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突厥人认为,火是圣洁的,具有祛邪避灾的净化功能,是部落人畜的保护神。传说突厥始祖伊质泥师有四子,长子的部落居于高山,其地“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③。
火不但可以从严寒中给突厥人带来温暖,而且可以驱除外人带来的鬼祟。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进入西突厥境内,“有突厥人来言,能驱逐魔鬼,预阻不祥之兆,于是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取行李置众人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持香火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逐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尊敬
④。拜占庭历史学家狄奥菲拉特在其《历史》一书中记载:突厥人崇拜火,空气和水,颂扬大地和水,但仅奉天地唯一造物主为神,用马牛羊祭祀他,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⑤火被视为突厥部落和家庭的保护神。乌孙人、康居人则把火看做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
在塞人的游牧生活中,祭火是他们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平时向家居的炉膛之火献祭,每日三次,在晨祷、午祷、晚祷时进行。祭品也有三样:清洁的木柴、香料和一小块脂网。公元初年,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4~23)曾目睹波斯人祭火,“加入干燥、没有枝杈的木柴,把软化的脂油置于火上”⑥。
对火的崇拜,反映了古代先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向往光明、温暖的生活,驱走黑暗和寒冷;火是具有巨大神秘力量的神灵,可以祛除一切魔鬼和秽气,保证人畜不受猛兽、瘟疫的侵害,使人畜生存繁衍。人们精心保护火种,使其延续不断。
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动物崇拜极为盛行,还有许多动物被演化为氏族图腾举凡与游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如野兽类的狼、熊、狮、虎、豹、狐、鹿、野山羊等;家畜中的骆驼、马、牛、羊、狗;飞禽类的鹰、天鹅、乌鸦等,都被神化,认为这些动物各有其神通,具有灵异,从而加以崇拜。其中苍狼在突厥语诸部的动物崇拜中最具特殊地位,它被普遍认为与自己的祖先有某种血缘关系,并被视作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和图腾。狼是草原上最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具有凶猛、矫捷、顽强、诡谲等特点,而且常常群体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同时,狼也是草原上对人畜危害最大的动物,人们对它无能为力,进而产生敬畏,奉之若神,希望得到像狼一样的勇气和智慧,也祈求狼神保佑部落氏族人畜兴旺。
突厥语部落有许多关于“狼祖”、“狼生”的传说。乌孙人传说其祖先昆莫王是狼用奶水哺育长大的。《汉书》记载:“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①。另据乌孙昆莫乌就屠之子,第二代小昆莫名为“拊离”,而拊离即突厥语bori,狼之意狼被乌孙人追溯为母系的祖先而受到格外的崇拜。高车部则认为其祖先是一只公狼,狼祖传说也源自于此。
古代哈萨克、维吾尔族先民保持着狼图腾崇拜。《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是一头大公苍狼指引着乌古斯可汗在几次战斗中获得胜利。狼还是男子和英雄的代名词。《突厥语大词典》说,妇女若生了男孩,产婆便说生了狼,因男子英武、强健;若生了女孩,便说生了狐,因女子妩媚,讨人喜欢。②哈萨克族认为苍狼是保护祖先灵魂的神兽,能给予英雄、巫师特殊的神力。哈萨克巫师的诸神之一是狼,有些哈萨克部落的口号是狼,旗帜上也绘着狼像,英雄也被喻作狼。他们关于狼的传说,和突厥人“狼祖”的传说以及与狼相联系的古老信仰是十分相似的。
突厥人还有关于“鹿祖”和鹿图腾崇拜的传说。传说中,突厥阿史德氏祖先射摩舍利与海神婚配,海神女每日派金角白鹿迎送射摩入海。说明与其部祖先婚配的海神女为一个出自以白鹿为图腾的氏族。
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富蕴两县境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0多件“鹿石”。鹿石是一种石雕,古人先把石头做成长条形,在上面雕刻出鹿的图像,然后竖立在墓前。鹿石上鹿的图案姿态各异,造型十分优美。据专家考证,阿勒泰的鹿石为公元前1000年,即青铜时期古代塞人的遗物。这种鹿石与许多地方(如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十分相似,表明活动在阿尔泰山区的人还有崇拜鹿的习俗,以鹿为自己的图腾。在一些部落中,对山毛榉树尤为崇敬,把山毛榉奉为“圣树”。巫师念咒治病,举行祭祀,都要在山毛榉树旁进行。
古代游牧民族崇敬鹰鹫等勇鸷的猛禽,称鹰为神鹰,神鹰可以沟通天界,为人间与天神腾格里的使者。传说古代乌孙、康居的有些部落氏族是以猫头鹰为图腾的。猫头鹰的羽毛被哈萨克族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常佩缀在年轻女子的帽子上,婚嫁时装饰在新房的壁毯上,挂在婴儿的摇篮上,认为可以消邪取吉。赛马时也在马头、马尾饰以鹰羽,以祈马像鹰一样飞驰。有些突厥部落也把鹰作为图腾,如阙特勤碑上就雕刻有一只鹰。史诗《玛纳斯》中的柯尔克孜英雄玛纳斯,传说是其父梦见鹰落手中而使妻子怀孕,生下玛纳斯,少年玛纳斯称雏鹰,长大后称雄鹰;玛纳斯死后,他身边的鹰也飞走了。柯尔克孜人把自己的英雄祖先与神鹰联系在一起,具有雄鹰一般的勇猛和灵力,表现了鹰崇拜的信仰观念。
在哈萨克族有关族源名称的诸种传说中,就有一种传说认为哈萨克的始祖是白天鹅。传说,古时有一个叫卡勒夏哈德尔的首领,英勇无比,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他只好躺下来。眼看死神就要降临,这时,天空突然奇迹般地开了一个空隙,飞来一只白色雌天鹅,给他滴了一滴口涎,然后把他带到河边。他喝了水,体力逐渐得到了恢复,伤势也慢慢痊愈。这时,那只美丽无比的白天鹅变成一个举世无双的美丽少女。他喜出望外,与这位姑娘结为伉俪。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哈萨克”(kazak)。这个传说在哈萨克人中颇有影响,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①
此外,在天山、阿尔泰山的一些古代游牧人留下的岩画里,可以看到刻画在岩壁上的虎、豹、骏马、奔鹿、犬、山羊等动物的形象。这些都反映了西域古代游牧民族动物崇拜的内涵。
在古代游牧民族中,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都很盛行,这是与他们经历的从狩猎过渡到游牧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从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的原始社会体制分不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宗教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也必然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萨满教是新疆古代居民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之一,在古代游牧民族中十分盛行。伊犁现在的少数民族如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柯尔克孜、锡伯、满、达斡尔以及塔塔尔、乌孜别克族的祖先都曾信奉过萨满教。“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和对萨满巫师的崇拜长期支配着远古人们的思想,至今仍遗留下不少痕迹。这些民族后来又信仰了祆教、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阶级社会的宗教,但原始的萨满教观念习俗在这些民族中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萨满教的信仰十分广泛复杂,几乎包括了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崇拜的所有内容。萨满教原始的活动方式就是以频繁祭祀、降神附体、跳神驱鬼、卜问神灵、施展巫术来祈福免灾。巫师(即萨满)是神与人沟通的中介,是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据记载,匈奴、月氏等部族内早就存在着“胡巫”,即萨满术士,所用法术通常是祝诅咒语。胡巫在氏族部落的地位很高,对军事、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乌孙人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自己的巫师,萨满巫师的形象被刻画在洞岩上。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山里发现的康巴勒洞窟里面,画有人面形的神灵图。在阿勒泰市区旁一座将军山的岩画上,也刻画有与这种人面神形图完全一样的形象,戴着一顶尖形的帽子,与史书记载的“降神之巫曰萨麻,帽如兜銎,缘垂五色增条,长蔽面”①的萨满装束十分相似。
巫师不仅可以占卜,主持祭祀活动,使用巫术给病人看病,而且还有权对部族的习惯法作出解释。
柔然人信仰萨满教,其部内有女萨满巫师,也有男萨满。据《魏书》记载,蠕蠕(柔然)可汗所娶的一个妻室,就是豆浑地方的一个女巫:“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②。《梁书·芮芮传》记载:“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曀而不雨,问其故,以暖云”。巫师在柔然的地位很高,出则佐军,入则参政,女巫师妻尚可汗,进入宫廷,对柔然政治产生影响。
高车萨满巫师多为女性,“善用五十箸卜吉凶”③。祭祀天地、日月、星辰等,以狼祖为图腾,特别畏惧雷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④。女巫显然是母系氏族时代祭祀崇拜的遗留。突厥人信萨满教,“敬鬼神,信巫“⑤,“祭司预言未来之事”⑥,“祭司”即萨满巫师。突厥巫师以火占卜,预知未来之事。《萨满教今昔》一书中引用阿拉伯人对突厥人火卜的描述说:“突厥人的大统治者都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在这一天要为自己点一堆大火,要向火祭祀且祈祷。这火上有很大的火焰升起,火焰如果呈淡绿色,就预示将有充足的雨和好收成;如果火焰是红色的,预示着要发生战争;如果是黄色的,将有疾病和瘟疫;如果是黑色的,就说明统治者要死,或者到远处去旅行”。以羊肩胛骨占卜,也必经过在火上烘烤,才能烧出裂纹,观裂纹以卜凶吉。在突厥人中,萨满巫师地位很高。据传说,突厥先祖泥师都就是一位“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⑦的萨满。萨满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事,可汗都要听从萨满的意见,由萨满预卜凶吉,决定取舍进止。可汗登基,要由萨满充当神的使者,代表神意,授权新主。“其王初之,近侍、重臣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立乘马,以帛绞颈,使才不致绝,然后释,而急问曰:你能作九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①
新疆锡伯族、满族、达斡尔族的祖先都信奉萨满教。“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萨玛,巫觋也。其跳神法,萨玛击太平鼓作歌,病图92锡伯族萨满之一者亲族和之,词不甚了了,尾声似曰耶格耶,无分昼夜,声彻四邻。萨玛曰祖宗要马,则杀马以祭,要牛则椎牛以祭。至于骊萸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者。然续有人病,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萨玛之令,终不敢违”。②
“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跳一次,或季跳一次,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树丈余细木于墙院南隅,置斗其上,谓之曰竿,祭时着肉斗中,必有鸦来啄食之,谓之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妇,以铃击臀后,摇之作响,而手击鼓,鼓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而口致颂祷之词,词不可辨,祷毕跳跃旋转,有老虎回回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飞石黑阿峰。飞石黑阿峰者,粘谷米糕也,色黄如玉,质腻,掺以豆粉,蘸以蜜,跳毕,以此遍馈邻里亲族,而肉则拉人于家,食之以尽为度,不尽则为不祥”③。
萨满教在游牧民族中流行的时间相当久远,在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一直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所以其信仰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之间,长期支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生活。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萨满教信仰观念及其习俗,发祥于人类启蒙阶段,伴随人类的成长而成熟,成为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习俗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始的萨满教逐渐被兴起的人为宗教所取代。这些民族后来尽管信仰了其他宗教,但这种原生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一直深刻影响着并渗透于其他宗教里面,形成这些民族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
萨满巫师并没有因萨满教的衰落而消失,长期以来他们继续活跃在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中。不过名称已经从早期的“喀木,”演变为“巴合西”,哈萨克语称为“巴克思”,女巫师称“库什娜西”。遗留在维吾尔族民间的巫师,往往头戴一种白色或灰色的圆形或三角形毡帽,有的则留着披肩长发,作法时穿上妇女的裙子,女巫师梳着许多小辫,垂及耳侧脑后。哈萨克族巫师以天鹅皮制成神帽,插上猫头鹰羽毛,头上留一束头发。
在哈萨克族,“巴克思”被认为是博学之士、诗人、乐器演奏家、吟诵史诗的歌手、部落氏族的谋士。在跳神时,他们用库布兹琴伴奏歌唱,兴奋时即发表吉凶预言。在战争时,他们在军队首领身旁,演奏库布兹,歌颂英雄祖先,激励士气,并施巫术作法。平时则为人占卜、行医。有些巴克思也被称为“谢赫”(原意为伊斯兰教长老),他们身上都带着占卜用的40颗石子,有些谢赫终身不娶,以占卜、治病、跳神为生。有些巴克思称为“迪瓦纳”,他们身穿天鹅皮衣,骑白马,手持短矛或拐杖,人们认为他们是隐修者,追求萨满之路和真主之路的圣徒,可预知未来,神通广大,用手一指便能治愈患者,因而极受尊崇。同时,巴克思在传播和发展古代哈萨克诗歌、音乐、文学艺术、雕刻和杂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被认为是“哈萨克古代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①。
在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族民间都保留有大量的萨满教遗俗。这些遗俗被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例如清代文献记载的维吾尔族民间有祭天、祭山、祭祖的所谓三祭习俗;农村中盛行的麻扎朝拜;民间的求水祈雨仪式等,都可以看见萨满教的遗留。哈萨克族的求雨仪式名为“塔萨特克”,于干旱季节在河边举行。由聚集的人们捐献牲畜,向腾格里宰牲祭祀。祭祀时,大毛拉用白色大布将《古兰经》悬挂于一高木架上,然后站在《古兰经》下摊开双手,向腾格里和真主祈祷,念诵降雨的祷文。人们则按照对腾格里或真主的虔诚,凑一点作为布施的现金,然后分吃作为祭品宰杀的牲畜,向腾格里和真主叩头祷告,认为这样做便能降雨。还有表示祝福、祈求的“巴塔”仪式;为亡人点燃“四十支蜡烛”的驱魔仪式;诵唱咒语的“阿尔包”遗俗等等,都体现了原始萨满教在民间的遗俗。
在哈萨克族民间,巴克思充当着从前萨满的角色,预言未来,为病人念咒治病和进行跳神活动。他们到病人家或显贵人家跳神,多在夜间举行。先在毡房中央点燃一堆火,病人和阿吾勒(牧村)的人们来后,巴克思开始用冬不拉琴弹奏召唤鬼神的乐曲。这些乐曲是被称为巴克思之神的霍尔赫特遗传的最古老的乐曲,古时用库布兹琴演奏。巴克思一边弹冬不拉,一边唱歌。主要内容是祷告腾格里和召唤自己的鬼神。不久巴克思开始兴奋、焦躁、浑身颤抖,用臀部撑地移动身体,同时面色变得令人恐怖,这表示他的鬼神正在前来。稍后,巴克思从地上站起,这表示他的鬼神已经到来。巴克思从地上站起时,由其他人继续弹奏乐曲。这时巴克思一边围着火堆绕圈子,一边自言自语,呼唤鬼神之名。巴克思跳神时,还常用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持斧头砍自己的胸脯,伸舌头舔烧红的铁。有些巴克思跳神时,跳上毡房的天窗大发雷霆,或一边骑马绕毡房奔跑,一边大喊大叫。有些巴克思在跳神时异常兴奋,浑身颤抖,最后常疲惫至极,昏迷倒地。醒来后,便说自己如何与自己的鬼怪、精灵及神仙见面、交谈,并以它们的话向人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巴克思跳神治病,对重病患者则断定遭到了瘟疫,是由于瘟神报怨,魔鬼附体,灵魂不满所致。以前,哈萨克人认为,大巴克思跳神可祛病禳灾,驱赶凶神,甚至能在患者不觉的情况下打开患者的腹腔撵走疾病,故极力请他们来家里跳神。①
祖先崇拜是萨满教崇拜的重要内容,集中表现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西域古代游牧部族的葬仪葬式虽有所不同,但信仰灵魂不灭、崇拜祖先亡灵的宗教观念却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能够庇护子孙,福佑部落。崇拜共同的祖先,可以加强氏族部落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血缘关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和部族之间的纷争,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部落强盛繁荣、平安吉祥,人民勇敢尚武。
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游牧民族长久地保持着祖先崇拜的风俗。哈萨克族“灵魂不死”的观念有其特点,认为人虽死,但其灵魂不死。当人死亡时,其灵魂变成鸟或昆虫飞离肉体,如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灵魂是肉体的客人”。哈萨克人崇拜著名的部落头目、英雄、巫师、圣贤的亡灵,尤其崇拜本部落祖先之灵,认为办好丧葬仪式,亡灵便会满意,会时刻保佑后代和部落,否则亡灵便会发怒,后代就会遭逢不幸,或疾病蔓延,或牲畜死亡,或作战时会意志消沉遭到失败。哈萨克族人只要身陷困境、遭逢不幸,便向祖先之灵宰牲祭献,认为给死者
宰牲越多,其亡灵便越满意,从而大施恩德。没有生过孩子的妇女常在祖先的墓边过夜,祈求生孩子。在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中,英雄陷入困境时,便向祖先祷告,求祖先在其梦中出现并佑助,帮助英雄百战百胜。哈萨克族人认为,著名英雄和部落长老的亡灵能够佑助,故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部落和氏族,并把部落或氏族的旗帜当作祖先的旗帜,世代相传;若遭到侵犯,便去祖先之墓,插上旗帜,在那儿住宿,并宰牲祭献,全体痛哭,祈求援助。因有此信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部落把18世纪英雄贾尼别克的白色旗帜完好无损地保存至近代。①柯尔克孜族崇拜祖先,尤其是英雄祖先格外受崇拜。英雄史诗《玛纳斯》就是柯尔克孜族崇拜自己的英雄祖先玛纳斯及其八代英雄后代的古老传说。
这些习俗都是哈萨克族先民信仰萨满教时遗留下来的古俗,有些习俗保留至今。萨满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都有大量的遗留,反映了这种原始的宗教形态在新疆地区长期流行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萨满教逐渐让位,这是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过程。但是,由于萨满教的长期流行,特别是它是一种人们初始的、原生的宗教思想意识,许多观念和习俗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不会随着新的宗教的流行而完全消失。这些观念和习俗也必然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其他宗教里,形成地区化、民族化的特点。这是萨满教在许多少数民族中留存有大量遗迹的根源。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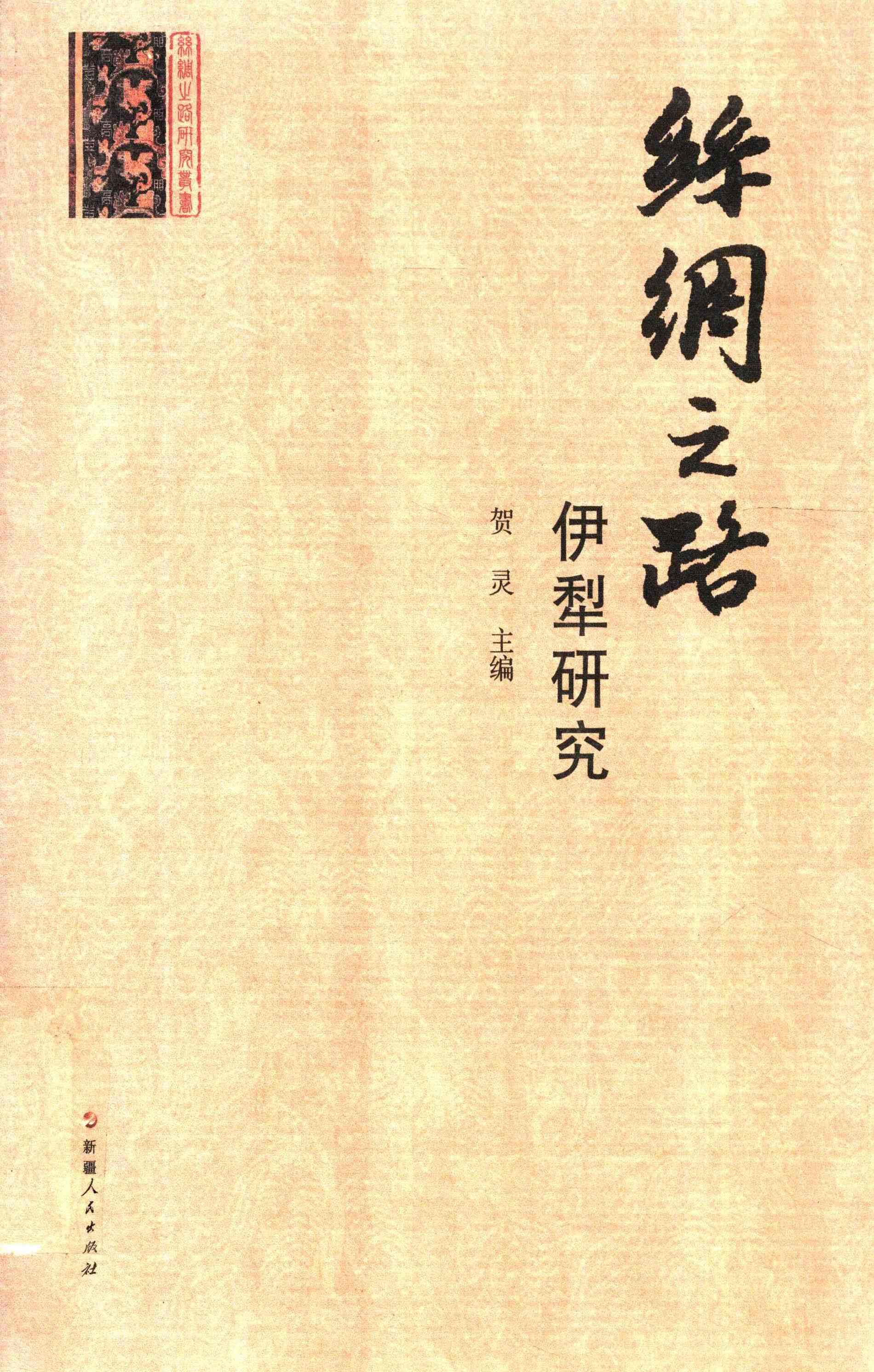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