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游牧文化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67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早期游牧文化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5 |
| 页码: | 181-185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伊犁民族文化内容包括了,欧亚草原中段的伊犁、阿尔泰大草原历来是众多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欧亚大草原依山脉的分隔形成三大块,即东起大兴安岭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至乌拉尔山和乌拉尔山至喀尔巴阡山三大区域。处于中段的伊犁、阿尔泰山地草原地带成了自东向西,自西向东迁徙的众多游牧民族的历史走廊和汇聚之地。公元前和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塞人、大月氏、乌孙、乌揭、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都驻足于此,跃马扬鞭自由驰骋。他们揖别了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走进了游牧文明时代,成了真正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铸就了早期的游牧文明,孕育了灿烂的草原文化。 |
| 关键词: | 伊犁 民族 游牧文化 |
内容
欧亚草原中段的伊犁、阿尔泰大草原历来是众多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欧亚大草原依山脉的分隔形成三大块,即东起大兴安岭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至乌拉尔山和乌拉尔山至喀尔巴阡山三大区域。处于中段的伊犁、阿尔泰山地草原地带成了自东向西,自西向东迁徙的众多游牧民族的历史走廊和汇聚之地。公元前和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塞人、大月氏、乌孙、乌揭、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都驻足于此,跃马扬鞭自由驰骋。他们揖别了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走进了游牧文明时代,成了真正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铸就了早期的游牧文明,孕育了灿烂的草原文化。
生活在伊犁、阿尔泰草原的早期游牧民族因地理生态、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相同,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表征。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马背民族的文化,因为他们逐水草而居、而牧、而行都离不开马。盘马弯弓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熟谙养马之术,精于骑射,养成骁勇善战、豪放不羁的品格。马鞍、马镫都是游牧民族发明的。早在战国时期,西域的游牧民族就有了马鞍,而最早的马镫是塞人用皮带环系在马肚带上的。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也开始使用这种马镫。到了阿尔泰的突厥时代,则出现了铜制、铁制马镫,至此马镫也基本定型。马鞍、马镫的出现是马具的一次革命,无论是对放牧的牧民,还是对骑兵,都意味着如虎添翼,在马背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活动在伊犁、阿勒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民族在丧葬习俗上也有许多共性:塞人、乌孙人的墓葬同为石(土)封堆,圆形,墓室均为竖穴,东西向,有殉动物的习俗。青铜牌饰、草原岩画、石人、鹿石上也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共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容易产生共同的思维定式和审美意识,于是在文化上的同质同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不会淹没在共性之中的,伊犁、阿勒泰地区早期游牧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也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民族特色的文化了。
塞人操东伊朗语,在伊犁河流域和西部天山一带活动的时间为公元前5~前3世纪,曾在这些地方建立游牧氏族部落政权,部落首领号称“塞王”,后在西迁的大月氏人的攻击下,塞人被迫南迁至天山以南地区和帕米尔高原。据希罗多德的描绘,塞人是头戴高尖顶帽的游牧部落。在新源县和巩留县均出土有戴尖顶帽的塞人青铜武士俑,均属公元前5~前3世纪文物,这与塞人在伊犁活动的时间相吻合。塞人妇女着长袍、披风,婚姻由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把马作为祭品奉献给太阳神,其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①塞人的这种信仰实际上就是火祆教。这从塞人活动的地名考证和考古发现也能得到证实。塞人把他们在中亚活动的花剌子模地区称之为“太阳的土地”,把索格底亚那称为“火地”。伊犁新源县曾出土过一件大型兽首吞蹄式足双耳青铜方盘,被学者们认为是塞人的祭祀台。在帕米尔高原发现的南迁后的塞人墓葬,有近一半是火葬墓,墓表也以太阳辐射状为标志。这些都表明,塞人有祭祀太阳神的习俗,献给太阳神的最重要祭品是马。献祭马和头戴尖顶帽,都旨在与天上的太阳神沟通。那么,太阳神和火神是否为同一神祇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于阗出土的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就是指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可见是同一神祇。因此,塞人信仰的巫教也就是火祆教。塞人还在他们的带饰、牌饰、衣饰、刀柄上塑造有啮咬状动物纹样,国外学者称之为“斯基泰”动物纹样艺术。这些纹样多是动物四肢被毁伤的形象,时常是一只野猫、熊、鹫,或一只鹰咬住了马或反刍动物的身子当作一副完全扭曲的内容。但是,这些动物纹样并不是作为艺术品出现的,它们具有巫术的目的。②牌饰上的一些凶兽猛禽是作为部落的保护神出现的,其作用也是功能性的。特别是一些有翼雪豹造型和狮子形象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用凸出的涡卷形象表示双翼,显然是通太阳神的动物保护神的形象,因为塞人早期的保护神就是狮身鹰头兽格立芬的形象。塞人迁徙到天山以西后,因常见雪豹之类猛兽,保护神也以雪豹为主了,当然也保留着狮身鹰头兽格立芬保护神的形象。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就出土过一件对翼兽铜项圈,就属塞人的翼兽保护神形象。塞人风俗中保留着原始骷髅崇拜,他们往往把死去亲人的头颅保存起来,并把头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在盛大的祭祀仪式上对祖先的头颅进行祭奠。③他们出于灵魂不灭的信仰,坚信死者灵魂就在头部,专心崇拜骷髅,就能通过巫术操作使祖先有生命的灵魂永续。
大月氏人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至伊犁河一带,赶跑了塞人,立足于伊犁草原。大月氏人西迁建立贵霜王朝后被称吐火罗人,而大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信奉佛教前是信仰多神教的氏族部落。但在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化中,吐火罗人开始独尊双马神。双马神就是吐火罗人的龙神,因此,汉文文献也将吐火罗人称为龙家,亦即龙部落。中亚吐火罗人墓地——“黄金之丘”出土的雕有龙神形象的耳坠、脚镯、短剑等物品表明,它就是吐火罗人早期信仰的双马神。吐火罗人在中亚建立贵霜帝国前曾广泛活动于天山南北地区,于是在这些地区也留下双马神信仰的踪迹。在巴里坤县八墙子村附近以及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中均发现有对马岩刻图。如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两组对马图案,其中一组对马的头、前腿和后腿,彼此联结,形成一个封闭的图案,马长头长颈,身材细瘦,尾垂于下,通体涂红。在吐鲁番艾丁湖畔也出土一件透雕对马青铜饰牌,是一对卧马,马背相连,头尾相衔。那么,双马神何以成了吐火罗人的龙神呢?《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人强盛时“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无论是游牧还是征战,吐火罗人非有良马不可,马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征战工具和最为珍视的财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马都可称为龙马。西域的汗血马应为龙马。由于吐火罗人与马的亲密关系,奉良马为龙神(即马神)就毫不奇怪了。《周礼》也认为:“马八尺以上为龙”。显然,那种疾跑如飞的骏马才能被称为“龙马”。吐火罗人早期就是以龙神(即马神)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吐火罗人用婆罗谜字母拼写的吐火罗语文书在西域曾流行过。吐火罗人还形成本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如在棺木上彩绘龙头,这与他们的龙神信仰是完全一致的。信仰佛教的吐火罗人在传播佛教文化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乌孙是在赶走大月氏人后立足于伊犁河流域的。从汉代文献记载看,乌孙有深目高鼻、赤发碧眼的印欧人种特征,但也混杂了蒙古人种的成分。乌孙人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其人口由10万余众增加到60余万,成为天山以北地区强大的游牧部落。作为游牧部落,乌孙人过着“穹庐为室毡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的生活,因此文化上也打上了游牧生活习俗的烙印。乌孙人的物质文化从伊犁河流域乌孙墓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出土文物有铁刀、铁铧、陶罐、陶盆、铜刀、铜碗以及各类金箔。这些出土的文物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一是他们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能铸冶、制造陶器和从事毛纺织等,也有酿马奶酒的技术。二是乌孙人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还有了一定的定居生活。昭苏县乌孙墓曾出土一件铁铧犁,就是有力的物证,但农耕定居文化并不占重要地位。对于乌孙人的制度文化所知甚少,但从一些文献的简略记载看,乌孙人在两汉时期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宗法社会。在政治上实行政治、军事一体的专制体制。乌孙王是最高统治者,称大昆莫(或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监、大吏、舍中大吏、骑君等各级官职。从丧葬习俗看,乌孙有严格的丧葬等级制度。现发现的乌孙墓葬封丘有大、中、小之分,而且随葬物也有厚薄之别。新源县巩乃斯草原上的乌孙特大墓冢高达20米,底周长350米,似为王一级的大墓。已发掘的乌孙墓中还见有狗骨架,昭苏县夏特墓葬中就曾有出土。因狗在游牧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与主人的亲密关系,封土殉狗是乌孙人的丧葬习俗之一。有学者认为:“墓室内葬狗,封土中殉狗(应该是祭祀的体现),也自然就是为死者作出的切合牧业生产需要的周到安排”①。由于乌孙与汉王朝和匈奴人的特殊关系,文化上也多受汉文化和匈奴文化的影响。对乌孙人的精神文化,几乎一无所知,这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但他们如同匈奴入一样,似也应有祭天、地、祖先、鬼神的习俗。
与塞人、大月氏人、乌孙人先后活动于伊犁河流域的同时,另一支游牧部落乌揭人则驰骋于阿尔泰山一带。乌揭人除在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外,又南下抵今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吐鲁番盆地一带活动。南下的这一支乌揭人被古代汉文文献称之为“姑师”或“车师”。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适应环境开始在绿洲农耕定居生活,称为车师前部,而奇台、吉木萨尔一带的车师人仍从事游牧业,称之为车师后部。阿尔泰山克尔木齐早期文化应是乌揭人的文化。从克尔木齐早期墓葬出土文物看,乌揭人有屈肢葬和殉葬制度,人殉、动物殉构成他们的丧葬文化。除殉葬奴隶外,主要是马殉。在阿尔泰山中部地区,原苏联考古学家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果发现在墓葬中都有马殉的遗迹,同时随葬的马匹都有马勒和马鞍。这些墓葬被确认为是公元前500年左右,恰与乌揭人在阿尔泰山的活动时间相吻合。与此相应的是,在阿拉沟车师贵族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马骨,最多的一座贵族墓中殉马就多达29匹,殉马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墓葬中的马骨如此之多和集中,那么只有一种解释:钟爱自己坐骑和以马匹多少衡量财富多寡的乌揭人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也有与爱骑相伴,并以殉马作为主人身份和拥有财富的象征。乌揭人及其南迁的车师人均是信仰虎神的部落,这可能与他们活动的阿尔泰地区多虎有关,故在车师人的墓葬中常见到金质、青铜质虎纹饰牌。吐鲁番腹地的苏贝希文化曾出土两件包金卧虎铜牌和一件虎纹金箔。包金卧虎铜牌外围边框饰一周圆点纹,中间铸成透雕状卧虎,虎右前腿高高扬起,回首张口,尾巴上翘,正面模压一层金箔。吐鲁番艾丁湖车师人墓葬中也出土有虎噬羊纹铜牌、虎纹圆金牌。吐鲁番地区并不产虎,将虎作为部落保护神,并在随身佩戴的饰牌等物件上圆雕虎纹,应是猎牧部落的乌揭人的遗俗。车师前部虽然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事农耕生产生活了,但早期的虎神信仰并未消失。虎神还可能是乌揭人萨满的动物精灵形象。作为通天的工具,每一个萨满都有若干动物神灵相助佑。萨满祭祀仪式中,虎纹饰牌也往往赋予巫术功能,借以沟通天、地、人。乌揭人的虎纹饰牌和塞人的狮纹饰牌、吐火罗人的双马纹饰牌在功能上都是相同的,均被赋予部落保护神的意义。
在伊犁、阿勒泰草原早期民族文化中匈奴文化占有一席地位。因为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并不似匆匆过客,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在较大范围内活动过。从文献记载看,匈奴有祭天习俗。《史记》记载,匈奴“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且有定期的春、秋两祭,祭祀仪式由萨满主持,献祭的祭品主要是肉和酒,祭祀完毕还举行大型飨宴,食其酒肉。祭祀的动机主要是祈盼牲畜繁衍,猎获丰多。匈奴右部曾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活动,伊犁、阿勒泰、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南郊、木垒等地都出土过匈奴人的铜鍑。新源县出土铜鍑为立耳、双附耳、镂空圈足。乌鲁木齐南郊出土铜鍑造型较特殊,在口沿处呈方形两竖上各附三个蘑菇形装饰。但所有的铜鍑都是深腹、双耳、喇叭形圈足。铜鍑并不是一般的煮食器皿,而是用于祭祀的礼器,祭祀祖先、天、地、鬼神无不用铜鍑。铜鍑的造型也是刻意象征“天圆”的,因为在匈奴人的神系中,天神——“撑犁”是最主要的神祇,祭天就是祭天神,天神在匈奴人的万神殿中处于主神的地位。匈奴人也在刀、匕、剑、饰牌、带钩、扣饰、头饰、佩饰上雕有动物纹样。学者们通常把以匈奴动物纹样为主的北方草原动物纹样通称为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①在匈奴人曾活动过的伊犁河流域、巴里坤、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南郊都曾出土过鄂尔多斯式野猪纹透雕铜牌、几何形透雕饰牌等,这与内蒙古匈奴墓出土的此类物件几乎无殊。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大多是鸟形、兽头形、伫立形、蹲踞形、弯曲兽形、群兽形以及人与动物组合型等,后期还出现以花草纹、自然景物纹衬托动物的纹样。与塞人动物纹样相较,鄂尔多斯动物纹样中像塞人的咬斗形动物纹样并不多。如果从造型特征看,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早期是饰在刀、剑柄的写实性的动物头纹样,到中期则出现图案化的双鸟纹,主要装饰在腰带上,特别强调鸟啄钩状特征。到了晚期,动物形象少了写实手法,家畜与自然景物相间成为流行纹样。工艺技法也由早期的圆雕逐渐向浮雕过渡,制作工艺也有镶嵌、抽丝等多种。②
伊犁河流域、阿尔泰草原这些早期游牧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在部落间的征战与和平交往中,文化间的互动十分频繁,这是推动早期草原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生活在伊犁、阿尔泰草原的早期游牧民族因地理生态、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相同,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表征。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马背民族的文化,因为他们逐水草而居、而牧、而行都离不开马。盘马弯弓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熟谙养马之术,精于骑射,养成骁勇善战、豪放不羁的品格。马鞍、马镫都是游牧民族发明的。早在战国时期,西域的游牧民族就有了马鞍,而最早的马镫是塞人用皮带环系在马肚带上的。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也开始使用这种马镫。到了阿尔泰的突厥时代,则出现了铜制、铁制马镫,至此马镫也基本定型。马鞍、马镫的出现是马具的一次革命,无论是对放牧的牧民,还是对骑兵,都意味着如虎添翼,在马背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活动在伊犁、阿勒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民族在丧葬习俗上也有许多共性:塞人、乌孙人的墓葬同为石(土)封堆,圆形,墓室均为竖穴,东西向,有殉动物的习俗。青铜牌饰、草原岩画、石人、鹿石上也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共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容易产生共同的思维定式和审美意识,于是在文化上的同质同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不会淹没在共性之中的,伊犁、阿勒泰地区早期游牧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也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民族特色的文化了。
塞人操东伊朗语,在伊犁河流域和西部天山一带活动的时间为公元前5~前3世纪,曾在这些地方建立游牧氏族部落政权,部落首领号称“塞王”,后在西迁的大月氏人的攻击下,塞人被迫南迁至天山以南地区和帕米尔高原。据希罗多德的描绘,塞人是头戴高尖顶帽的游牧部落。在新源县和巩留县均出土有戴尖顶帽的塞人青铜武士俑,均属公元前5~前3世纪文物,这与塞人在伊犁活动的时间相吻合。塞人妇女着长袍、披风,婚姻由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把马作为祭品奉献给太阳神,其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①塞人的这种信仰实际上就是火祆教。这从塞人活动的地名考证和考古发现也能得到证实。塞人把他们在中亚活动的花剌子模地区称之为“太阳的土地”,把索格底亚那称为“火地”。伊犁新源县曾出土过一件大型兽首吞蹄式足双耳青铜方盘,被学者们认为是塞人的祭祀台。在帕米尔高原发现的南迁后的塞人墓葬,有近一半是火葬墓,墓表也以太阳辐射状为标志。这些都表明,塞人有祭祀太阳神的习俗,献给太阳神的最重要祭品是马。献祭马和头戴尖顶帽,都旨在与天上的太阳神沟通。那么,太阳神和火神是否为同一神祇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于阗出土的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就是指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可见是同一神祇。因此,塞人信仰的巫教也就是火祆教。塞人还在他们的带饰、牌饰、衣饰、刀柄上塑造有啮咬状动物纹样,国外学者称之为“斯基泰”动物纹样艺术。这些纹样多是动物四肢被毁伤的形象,时常是一只野猫、熊、鹫,或一只鹰咬住了马或反刍动物的身子当作一副完全扭曲的内容。但是,这些动物纹样并不是作为艺术品出现的,它们具有巫术的目的。②牌饰上的一些凶兽猛禽是作为部落的保护神出现的,其作用也是功能性的。特别是一些有翼雪豹造型和狮子形象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用凸出的涡卷形象表示双翼,显然是通太阳神的动物保护神的形象,因为塞人早期的保护神就是狮身鹰头兽格立芬的形象。塞人迁徙到天山以西后,因常见雪豹之类猛兽,保护神也以雪豹为主了,当然也保留着狮身鹰头兽格立芬保护神的形象。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就出土过一件对翼兽铜项圈,就属塞人的翼兽保护神形象。塞人风俗中保留着原始骷髅崇拜,他们往往把死去亲人的头颅保存起来,并把头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在盛大的祭祀仪式上对祖先的头颅进行祭奠。③他们出于灵魂不灭的信仰,坚信死者灵魂就在头部,专心崇拜骷髅,就能通过巫术操作使祖先有生命的灵魂永续。
大月氏人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至伊犁河一带,赶跑了塞人,立足于伊犁草原。大月氏人西迁建立贵霜王朝后被称吐火罗人,而大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信奉佛教前是信仰多神教的氏族部落。但在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化中,吐火罗人开始独尊双马神。双马神就是吐火罗人的龙神,因此,汉文文献也将吐火罗人称为龙家,亦即龙部落。中亚吐火罗人墓地——“黄金之丘”出土的雕有龙神形象的耳坠、脚镯、短剑等物品表明,它就是吐火罗人早期信仰的双马神。吐火罗人在中亚建立贵霜帝国前曾广泛活动于天山南北地区,于是在这些地区也留下双马神信仰的踪迹。在巴里坤县八墙子村附近以及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中均发现有对马岩刻图。如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两组对马图案,其中一组对马的头、前腿和后腿,彼此联结,形成一个封闭的图案,马长头长颈,身材细瘦,尾垂于下,通体涂红。在吐鲁番艾丁湖畔也出土一件透雕对马青铜饰牌,是一对卧马,马背相连,头尾相衔。那么,双马神何以成了吐火罗人的龙神呢?《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人强盛时“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无论是游牧还是征战,吐火罗人非有良马不可,马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征战工具和最为珍视的财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马都可称为龙马。西域的汗血马应为龙马。由于吐火罗人与马的亲密关系,奉良马为龙神(即马神)就毫不奇怪了。《周礼》也认为:“马八尺以上为龙”。显然,那种疾跑如飞的骏马才能被称为“龙马”。吐火罗人早期就是以龙神(即马神)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吐火罗人用婆罗谜字母拼写的吐火罗语文书在西域曾流行过。吐火罗人还形成本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如在棺木上彩绘龙头,这与他们的龙神信仰是完全一致的。信仰佛教的吐火罗人在传播佛教文化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乌孙是在赶走大月氏人后立足于伊犁河流域的。从汉代文献记载看,乌孙有深目高鼻、赤发碧眼的印欧人种特征,但也混杂了蒙古人种的成分。乌孙人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其人口由10万余众增加到60余万,成为天山以北地区强大的游牧部落。作为游牧部落,乌孙人过着“穹庐为室毡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的生活,因此文化上也打上了游牧生活习俗的烙印。乌孙人的物质文化从伊犁河流域乌孙墓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出土文物有铁刀、铁铧、陶罐、陶盆、铜刀、铜碗以及各类金箔。这些出土的文物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一是他们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能铸冶、制造陶器和从事毛纺织等,也有酿马奶酒的技术。二是乌孙人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还有了一定的定居生活。昭苏县乌孙墓曾出土一件铁铧犁,就是有力的物证,但农耕定居文化并不占重要地位。对于乌孙人的制度文化所知甚少,但从一些文献的简略记载看,乌孙人在两汉时期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宗法社会。在政治上实行政治、军事一体的专制体制。乌孙王是最高统治者,称大昆莫(或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监、大吏、舍中大吏、骑君等各级官职。从丧葬习俗看,乌孙有严格的丧葬等级制度。现发现的乌孙墓葬封丘有大、中、小之分,而且随葬物也有厚薄之别。新源县巩乃斯草原上的乌孙特大墓冢高达20米,底周长350米,似为王一级的大墓。已发掘的乌孙墓中还见有狗骨架,昭苏县夏特墓葬中就曾有出土。因狗在游牧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与主人的亲密关系,封土殉狗是乌孙人的丧葬习俗之一。有学者认为:“墓室内葬狗,封土中殉狗(应该是祭祀的体现),也自然就是为死者作出的切合牧业生产需要的周到安排”①。由于乌孙与汉王朝和匈奴人的特殊关系,文化上也多受汉文化和匈奴文化的影响。对乌孙人的精神文化,几乎一无所知,这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但他们如同匈奴入一样,似也应有祭天、地、祖先、鬼神的习俗。
与塞人、大月氏人、乌孙人先后活动于伊犁河流域的同时,另一支游牧部落乌揭人则驰骋于阿尔泰山一带。乌揭人除在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外,又南下抵今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吐鲁番盆地一带活动。南下的这一支乌揭人被古代汉文文献称之为“姑师”或“车师”。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适应环境开始在绿洲农耕定居生活,称为车师前部,而奇台、吉木萨尔一带的车师人仍从事游牧业,称之为车师后部。阿尔泰山克尔木齐早期文化应是乌揭人的文化。从克尔木齐早期墓葬出土文物看,乌揭人有屈肢葬和殉葬制度,人殉、动物殉构成他们的丧葬文化。除殉葬奴隶外,主要是马殉。在阿尔泰山中部地区,原苏联考古学家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果发现在墓葬中都有马殉的遗迹,同时随葬的马匹都有马勒和马鞍。这些墓葬被确认为是公元前500年左右,恰与乌揭人在阿尔泰山的活动时间相吻合。与此相应的是,在阿拉沟车师贵族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马骨,最多的一座贵族墓中殉马就多达29匹,殉马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墓葬中的马骨如此之多和集中,那么只有一种解释:钟爱自己坐骑和以马匹多少衡量财富多寡的乌揭人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也有与爱骑相伴,并以殉马作为主人身份和拥有财富的象征。乌揭人及其南迁的车师人均是信仰虎神的部落,这可能与他们活动的阿尔泰地区多虎有关,故在车师人的墓葬中常见到金质、青铜质虎纹饰牌。吐鲁番腹地的苏贝希文化曾出土两件包金卧虎铜牌和一件虎纹金箔。包金卧虎铜牌外围边框饰一周圆点纹,中间铸成透雕状卧虎,虎右前腿高高扬起,回首张口,尾巴上翘,正面模压一层金箔。吐鲁番艾丁湖车师人墓葬中也出土有虎噬羊纹铜牌、虎纹圆金牌。吐鲁番地区并不产虎,将虎作为部落保护神,并在随身佩戴的饰牌等物件上圆雕虎纹,应是猎牧部落的乌揭人的遗俗。车师前部虽然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事农耕生产生活了,但早期的虎神信仰并未消失。虎神还可能是乌揭人萨满的动物精灵形象。作为通天的工具,每一个萨满都有若干动物神灵相助佑。萨满祭祀仪式中,虎纹饰牌也往往赋予巫术功能,借以沟通天、地、人。乌揭人的虎纹饰牌和塞人的狮纹饰牌、吐火罗人的双马纹饰牌在功能上都是相同的,均被赋予部落保护神的意义。
在伊犁、阿勒泰草原早期民族文化中匈奴文化占有一席地位。因为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并不似匆匆过客,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在较大范围内活动过。从文献记载看,匈奴有祭天习俗。《史记》记载,匈奴“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且有定期的春、秋两祭,祭祀仪式由萨满主持,献祭的祭品主要是肉和酒,祭祀完毕还举行大型飨宴,食其酒肉。祭祀的动机主要是祈盼牲畜繁衍,猎获丰多。匈奴右部曾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活动,伊犁、阿勒泰、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南郊、木垒等地都出土过匈奴人的铜鍑。新源县出土铜鍑为立耳、双附耳、镂空圈足。乌鲁木齐南郊出土铜鍑造型较特殊,在口沿处呈方形两竖上各附三个蘑菇形装饰。但所有的铜鍑都是深腹、双耳、喇叭形圈足。铜鍑并不是一般的煮食器皿,而是用于祭祀的礼器,祭祀祖先、天、地、鬼神无不用铜鍑。铜鍑的造型也是刻意象征“天圆”的,因为在匈奴人的神系中,天神——“撑犁”是最主要的神祇,祭天就是祭天神,天神在匈奴人的万神殿中处于主神的地位。匈奴人也在刀、匕、剑、饰牌、带钩、扣饰、头饰、佩饰上雕有动物纹样。学者们通常把以匈奴动物纹样为主的北方草原动物纹样通称为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①在匈奴人曾活动过的伊犁河流域、巴里坤、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南郊都曾出土过鄂尔多斯式野猪纹透雕铜牌、几何形透雕饰牌等,这与内蒙古匈奴墓出土的此类物件几乎无殊。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大多是鸟形、兽头形、伫立形、蹲踞形、弯曲兽形、群兽形以及人与动物组合型等,后期还出现以花草纹、自然景物纹衬托动物的纹样。与塞人动物纹样相较,鄂尔多斯动物纹样中像塞人的咬斗形动物纹样并不多。如果从造型特征看,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早期是饰在刀、剑柄的写实性的动物头纹样,到中期则出现图案化的双鸟纹,主要装饰在腰带上,特别强调鸟啄钩状特征。到了晚期,动物形象少了写实手法,家畜与自然景物相间成为流行纹样。工艺技法也由早期的圆雕逐渐向浮雕过渡,制作工艺也有镶嵌、抽丝等多种。②
伊犁河流域、阿尔泰草原这些早期游牧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在部落间的征战与和平交往中,文化间的互动十分频繁,这是推动早期草原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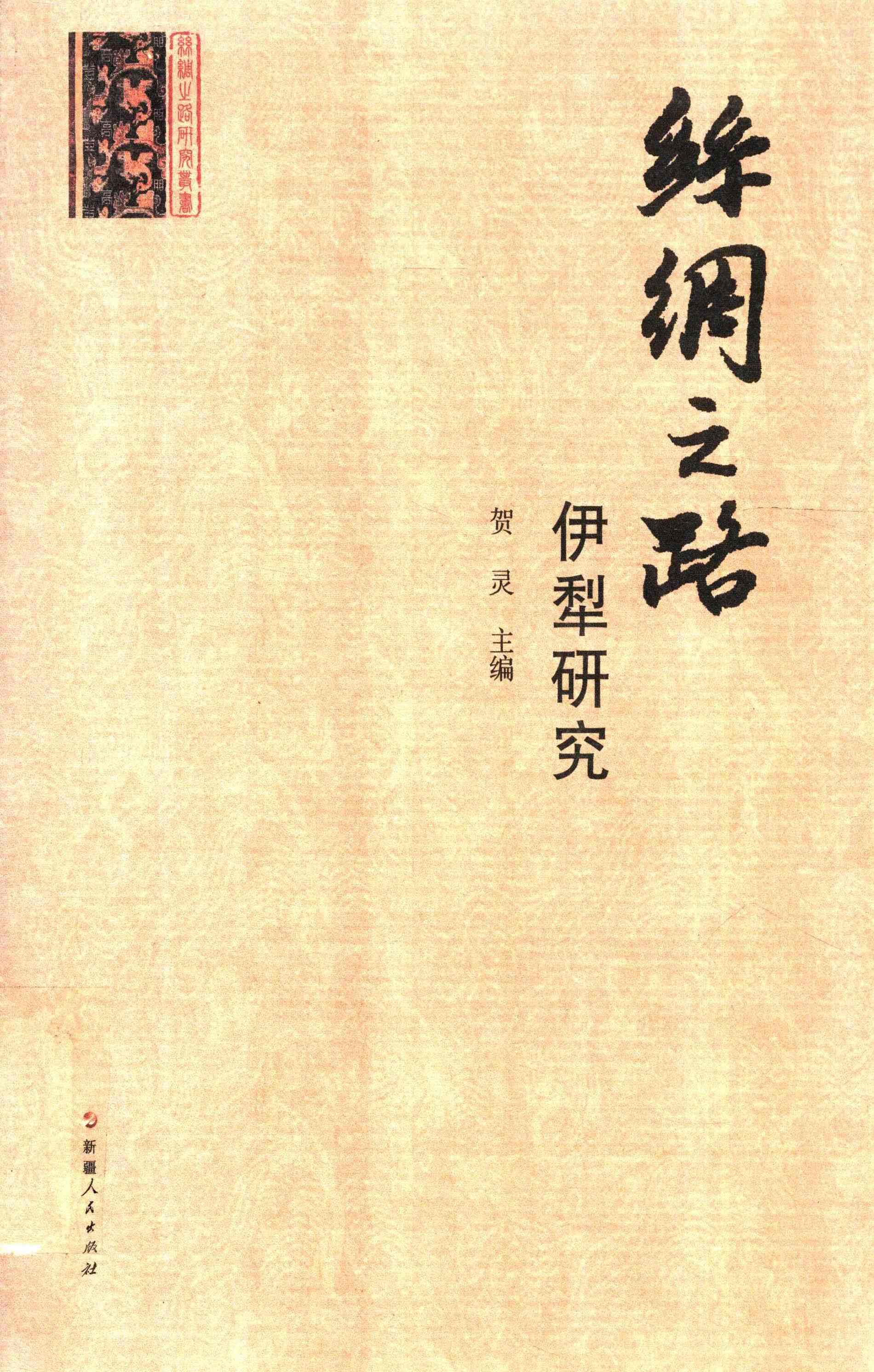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