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厄鲁特营八旗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53 |
| 颗粒名称: | 第六节 厄鲁特营八旗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9 |
| 页码: | 117-125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厄鲁特营八旗内容包括了,清代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厄鲁特营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投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其中大多数是原准噶尔二十一昂吉的达什达瓦部属。 |
| 关键词: | 伊犁 清代 厄鲁特营八旗 |
内容
清代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厄鲁特营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投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其中大多数是原准噶尔二十一昂吉的达什达瓦部属。1764年春,500名携眷之厄鲁特达什达瓦官兵奉命来到伊犁,被安置于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玛哈一带(今昭苏县境内)。1765年达什达瓦部众被编为一昂吉,为厄鲁特营左翼。二是清朝出兵准噶尔汗国时逃入哈萨克、布鲁特部游牧地后又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人,以及被清廷赎回的曾给维吾尔贵族当奴隶的准噶尔人。1760年后,少部分劫后余生的逃入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区等地的准噶尔人不堪为奴,陆续投靠清朝,对此,清廷实行了招抚和安置,1762年有6个佐领,次年置一昂吉,设置了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并颁发了关防印记。1765年此6个佐领编入厄鲁特营右翼。直到1772年投清的准噶尔入达1408人,其游牧区为崆吉斯河、哈什河及大小霍诺海等地,即现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及新源县境内。第三部分为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的沙比纳尔(门徒之意——作者)。据清代满文档案记载,其沙比纳尔有1200余户,被编为4个佐图66土尔扈特银印领,①归厄鲁特营右翼硕通管辖,其牧地为特克斯河下游(今特克斯县境内)。由此可见,准噶尔汗国灭亡以后,准噶尔牧民成了清朝管辖的属民,厄鲁特营的设立使“准噶尔”一词作为部落名已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一词。1767年7月,厄鲁特营按八旗编制,左翼被编为三旗,即镶黄、正黄、正蓝,称“上三旗”置6个佐领;右翼置5个旗,即镶白、正红、正白、镶红、镶蓝,称“下五旗”,有佐领8,个,1770年8个佐领扩编为10个佐领。加上沙比纳尔4个佐领,共有14个佐领。上三旗在特克斯河流域游牧,下五旗在诺海(即霍诺海)、空吉斯(即崆吉斯)一带游牧。
准噶尔部和察哈尔营一样实行的是总管旗制。左右两翼各设总管1员,上三旗设副总管1员,下五旗因佐领多,设副总管2员,又设沙比纳尔副总管职衔1员。总管、副总管办理八旗事务。每佐设佐领、骁骑校各1员,领催4人,管理军事、生产、诉讼各事,各翼还置空蓝翎(轮住卡伦)2~3人,额设挑补卡伦侍卫、委笔帖式(书记官)1~2人。厄鲁特营设领队大臣1员,总揽边防事务,大都由满族人担任。①另据《新疆识略》载,厄鲁特营还有世袭云骑尉1职,上三旗有2员,下五旗有3员。下五旗还有拜唐阿1员。
到道光年间,厄鲁特营兵额有了增加,据《伊犁略志》载,厄鲁特营有官员57名,兵3386名。厄鲁特营官兵家眷共22729名,其中兵3384名。
厄鲁特营各级官员及士兵的俸饷均由清朝政府发放。厄鲁特营等“四营”官兵的俸禄钱粮,实行与满营不同的形式,满营是有粮有银,而且月月食钱粮,而厄鲁特等营官兵则有银无粮,即只发俸银,不发口粮。在驻防伊犁的察哈尔、厄鲁特、索伦、锡伯四营中,厄鲁特营人数最多,在坐卡、巡边方面承担的差役最重,他们除驻巡本营辖境卡伦外,还要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等营驻巡卡伦,以及负责5座军台的文报传递。
厄鲁特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边疆,即驻卡巡边。他们除了驻守所辖区域外,还要驻守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他们平时驻卡巡边,定期操练,战时则上战场。
驻守卡伦。1763年,伊犁地区开始设置卡伦,“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
起初,厄鲁特营驻守格根、哈尔奇喇、特克斯色沁、根格色沁、都图岭等处卡伦,这些卡伦均设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与俄国接壤的边界线上。1788年又增设了察林河渡口等处卡伦。厄鲁特营所辖卡伦有32处,②其中常设卡伦4处:特克斯色沁、敦达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移设卡伦4处:特穆尔里克、乌弩古特、鄂博图渡口、昌曼;添撤卡伦24处:特穆尔里克渡口、雅巴尔布拉克、鄂博图、额尔格图、札拉图、库图勒、格根、鄂尔果珠勒、哈尔干图、齐齐罕图、垓尔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绰罗图(一作赤老图)、那(纳)喇特、博尔克阿满(曼)、巴噶塔木(巴噶喀木哈)、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铜厂外、沙里(喇)雅斯、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哈尔奇喇。
厄鲁特营除了驻守以上卡伦外,还派兵5~17名不等协助巴彦岱(惠宁)、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领队大臣驻守24座卡伦。18世纪20年代,沙俄加快了吞并中亚的步伐,不断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我国西北边疆开始出现危机。新疆地区同沙俄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伊犁地区卡伦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卡伦的驻防力量也有加强。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中叶,厄鲁特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9座,即鄂尔古朱勒卡(又译写成鄂尔果珠勒)、特木(穆)尔里克卡、格根卡、哈拉刻拉卡、沙拉(里)雅斯卡、那拉(喇)特卡、乌努(弩)古特卡、峨波土(鄂博图)卡、阿敦格尔布胡土卡;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即柏尔柯阿满(博尔克阿曼)、查干哈大、乌逊祜吉尔、特克斯边(可能是特克斯色沁)、巴汗塔马哈(巴噶喀木哈)、库土(图)勒、齐奇尔哈土(齐齐罕图)、哈尔干土(图)、通(铜)厂外、扎拉土(札拉图)、牙帕尔(雅巴尔)布拉克、特木(穆)尔里克桥、额尔各土(格图)、哈布哈克等巡防哨。
1864年10月7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清政府被迫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又订立了《中俄科布多界约》等三个勘界议定书,一共割去我国西部领土44万平方公里。其中斋桑湖往南,沙俄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七河流域,吹、塔拉斯河流域,使原来在鄂博(界牌)以内,卡伦以外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游牧地全被割去,进而侵吞了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等地方。随着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丢失。“厄鲁特营领队大臣所辖三十二卡,其明属俄国者二十三卡,其明属中国者仅一卡,其八卡佚考”。①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不但负责巡边,查看有无俄人越境之迹,还要防止私越和盗窃。新疆地区的卡伦最初设置时主要任务是内部防范,现在主要就是守卫边界了,所以厄鲁特等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
沙俄军队于1871年出兵侵占伊犁,又将该地区的数十处卡伦毁掉,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最后,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把包括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在内的新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了俄国的版图。《伊犁条约》划定自伊犁西南至伊犁东北一段边界,共立界碑鄂博33处。其中属于厄鲁特营牧地界内共有11处界碑。
中俄重新分界后,伊犁将军金顺在重要地段、隘口处重新安设卡伦,并派兵驻守。厄鲁特营新设卡伦10处,即那林哈勒噶卡、那林郭勒卡、胡苏木图卡、布胡图卡、特克斯噶塔尔干卡、莫霍托罗海卡、阿尔班苏木卡、格登山卡、沙图阿满卡、阿里干谷卡。由于其所属边界与俄境毗连,厄鲁特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
1763年,伊犁南路军台——伊犁至沙图阿满设有7处(由底台南行至阿克苏路),其中有5处军台由厄鲁特营军民驻坐:海努克台、索果尔台、博尔台、特克斯台、沙图阿满台,每座军台额设厄鲁特兵15户,马15匹,牛14头。驻守军台的官兵专管渡送折报公文等事。
厄鲁特营军民不仅驻守以上卡伦、台站,而且还到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驻守哨卡,向乌鲁木齐及内地运送军马等。自1766年始,厄鲁特营军民同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满洲、锡伯二年一换,每年换一半,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一年一换。厄鲁特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自1807年始又添兵10名。他们同其他营的换防兵一道“除分拨坐卡外,其余在城兵丁按期操演”①。1832年,由于经费等原因,停止了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厄鲁特等营官兵还要照看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地,其中厄鲁特营派佐领或骁骑校1员、兵4~15名不等前往驻防。
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游牧边界。吹、塔拉斯河流域原为西蒙古牧地,清朝统一新疆初,这一带暂作为“闲旷之地”,1763年始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塔拉斯地区稽查和巡逻,厄鲁特营官兵也随同前往。“每年夏天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布鲁特边界时,有两满营协领1员,大城(惠员)官2员..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计官10名,兵300名。每年秋季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哈萨克边界时,由两满营派协领1员,惠远城满营官2员,..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计官10名,兵300名”。②届时巡查官兵在边界上会哨,巡查边界,驱逐越界游牧者。
当时巡查分为两路,南路自伊塞克湖之南、巴尔珲岭到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今阿拉木图)到沙喇伯勒地方,在指定的地点彼此交换表报,互换信牌。这样边界地区就能全部查到。道光年间,随着沙俄对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逼近,巡查边防曾一度加强。1840年鸦片战争后,巡查变成巡边。主要任务是巡查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厄鲁特营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定期进行操练。清廷规定厄鲁特营等四营“各于屯所游牧处,随时操演鸟枪、骑射”。③
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厄鲁特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每年8月,将军带领各营官兵前往哈什河等地方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行围。届时厄鲁特营需派副总管1员、官12员、兵270名参加。这些兵丁都是从各旗挑选出来的。
维护内部的安定。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进行作乱。但很快都被平息了,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在镇压张格尔的暴乱中,新疆的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都作出了贡献。
厄鲁特军民也如此,奉命参加戡乱战斗。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面临300名清军覆灭于张格尔屠刀下及张格尔要大举进攻喀什噶尔的危机关头,又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厄鲁特、察哈尔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接着又攻克了喀什噶尔。在这场战役中,厄鲁特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了大功。1828年春节之际,张格尔第四次入卡作乱,被清军活捉,同年6月,张格尔被解送到北京处死。至此,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
1830年,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作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厄鲁特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厄鲁特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的围剿。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们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即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和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厄鲁特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战斗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厄鲁特营领催满吉、委领催巴图那逊、披甲哈拉黠讷莫库、鄂斯库等赏戴了六品蓝翎。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他们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面对倭里罕和卓一伙的进扰,各营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官兵1000余名,协领富珠哩等也带领兵1000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日解了巴楚之围,8月14日又解除了叶尔羌之围。9月21日,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①逃出卡外,清军跟踪追击,出卡进剿,倭里罕逃到了浩罕。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坐镇肃州(今甘肃酒泉)派刘锦棠率军进疆,驱逐侵略者。第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战斗中,厄鲁特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沙俄侵略者于1863年数次侵犯伊犁博罗胡吉尔等卡伦,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军分别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迫使沙俄撤回博罗胡吉尔一带。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厄鲁特军民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察哈尔、锡伯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英勇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在伊犁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10年期间,不仅在伊犁周围设要塞“各处把守,水泄不通”,而且沙俄在政治上也进行殖民奴役,他们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建制,撤换和驱除清政府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即沙俄突厥斯坦总督斜米列契省)直接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厄鲁特上三旗牧地被俄割占,其人口在俄境未回。后来经过交涉,其部众大都返回,但牧地却丧失了。
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他们以宁死不屈的精神,给侵略者一个响亮的回答。沙俄并不甘心,对各营兵丁进行敲诈勒索,趁机用发口粮等手段,诱迫各营军民归顺。但是,各营“兵民不从,亦不领粮”①,他们不畏强暴的坚强骨气再次挫败了沙俄的野心。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后,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伊犁最终未落入沙俄手中,这同厄鲁特蒙古等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
中国军民收复后的新疆,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地亩荒芜,人民离散,厄鲁特等营的情况也是惨不忍睹。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之后,着手伊犁重建工作,首先招集流离失所的厄鲁特、锡伯等营众,恢复厄鲁特、锡伯等营制。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决定将乌鲁木齐作为省会,自此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伊犁移至乌鲁木齐。伊犁仍设将军,但不再总统全疆军务,尽管伊塔边务。虽然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厄鲁特等营建制没有触动。营仍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8员。领队大臣仍受伊犁将军节制。由于厄鲁特营所属边界与俄境毗连,其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他们仍然是伊犁戍边的主要力量。清政府对厄鲁特等营作出了一些新的部署,厄鲁特营领队,移驻特克斯驻扎,以扼伊犁山南与俄接界之西面门户,兼扼冰岭。
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因“减兵加饷”,裁减各营官兵,裁减厄鲁特兵500名。所裁旗兵,每名授羊30只,令其牧放,仍属所在旗管辖。据《新疆图志》载,光绪末年厄鲁特营户口有:“职业职官100名,马步甲1236名,闲散10603名,孤25名”。①
新疆都督杨增新在不断裁减军队的同时,基于防边卫国,1914年1月24日,下令将厄鲁特营等四营领队大臣改为领队官,下属正副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均取消。虽然如此,厄鲁特营内部仍然沿用总管、副总管等旧制。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杨增新采取了停发厄鲁特等营薪饷,以挑兵为条件,免除一切赋税的措施,因此大部分官兵都解甲归田,卡伦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尽管如此,厄鲁特军民仍按旧制,巡防驻守各边界卡伦。
1938年厄鲁特营制被取消,均纳入地方行政编制。至此,长达170余年的厄鲁特营制取消。
游牧、狩猎的休养生息之地。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是兴办官牧厂。1760年,清政府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设立官营牧厂。伊犁牧厂有孳生马厂、孳生羊厂、驼厂、孳生牛厂。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牲畜除了部分羊和牛由维吾尔族牧放,部分马、牛由锡伯营牧放外,其余都由察哈尔、厄鲁特、索伦三营放养。骆驼厂全部由厄鲁特营经营。由于锡伯、索伦营兵丁不善畜牧,因此1773年后停止了索伦营经营马厂、牛厂以及锡伯营经营牛厂。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
以孳生厂为例,据1793年伊犁将军保宁奏,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7210匹,下五旗牧放9857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头,其中厄鲁特上三旗牧牛2483头,下五旗及沙毕纳尔四佐领牧牛4065头;羊厂,1772年共有孳生本牛140695只,厄鲁特营上三旗牧放羊29742只,下五旗及沙比纳尔四佐领牧羊56666只;1802年共收获孳生驼2665峰,上三旗牧驼1833峰,下五旗牧驼2343峰。②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孳生厂取孳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2636匹,下五旗牧马5242匹,牛厂有牛11573头,内上三旗牧牛2463头,下五旗牧牛4627头,羊厂存羊32187只,上三旗牧羊9500只,下五旗牧羊12112只。厄鲁特营仅牧放伊犁牧厂的牲畜就有十几万头。
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在特克斯河、察林河流域及塔马哈一带,下五旗在崆吉斯(今巩乃斯)、哈什河流域及霍诺海一带,以上草原都由高山环抱,其水草丰美,地域辽阔。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得膘肥体壮,孳生繁庶。伊犁将军伊勒图曾在1775~1781年连续5次查阅察哈尔、厄鲁特牧放的特穆尔牧厂时都很满意。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农民起义,浩罕阿古柏及沙俄乘机入侵,致使“全疆官厂荡然无存”,“伊犁乱后,牧厂悉停”,①厄鲁特营众的生计也非常艰难。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廷也无力再大规模地经营牧厂了。1896年,伊犁将军长庚为恢复生产,“筹办屯田耕种,以裕锡伯、索伦两营生计,筹办孳生牧畜,以裕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生计”②。伊犁牧厂恢复以后,察哈尔军民仍然同厄鲁特军民一道经营伊犁牧厂的牲畜。虽然牧厂恢复了,但由于牧厂荒废了几年,草场也不如从前了。
厄鲁特及察哈尔营众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伊犁官牧厂的马匹,主要是军马,用于拨补营缺、军台、卡伦、战事。羊为官兵食肉之主要来源,察哈尔营众牧放的羊只不仅自己食用,而且还供应满营官兵。据载,满营官兵6000员,每年每名可食羊6只,均有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孳生羊内拨给。牛为当时兵屯及铅、铜厂提供了重要工具。伊犁的厄鲁特蒙古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开发清代新疆畜牧业作出了贡献。
农业的开发。由于厄鲁特营的“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因此,其兵丁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厄鲁特营上三旗6个佐领屯田4处:敦达察罕乌苏、霍依图察罕乌苏、特尔莫土、哈牧哈;下五旗14个佐领屯田16处:昌满、哈什春稽布拉克、苏布台、浑多赖、衮佐特哈、库尔库类、呢勒哈、大济尔噶朗、算珠图、特勤克、特古斯塔柳、沙喇博果沁、巴哈拉克、弩楚衮。以上田地都位于河流域,因此都用河水灌溉。③
厄鲁特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屯田所获粮食,不仅自己食用,有时多获粮食还上缴官府,为当地驻防军提供军粮。
厄鲁特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再者牧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准噶尔部和察哈尔营一样实行的是总管旗制。左右两翼各设总管1员,上三旗设副总管1员,下五旗因佐领多,设副总管2员,又设沙比纳尔副总管职衔1员。总管、副总管办理八旗事务。每佐设佐领、骁骑校各1员,领催4人,管理军事、生产、诉讼各事,各翼还置空蓝翎(轮住卡伦)2~3人,额设挑补卡伦侍卫、委笔帖式(书记官)1~2人。厄鲁特营设领队大臣1员,总揽边防事务,大都由满族人担任。①另据《新疆识略》载,厄鲁特营还有世袭云骑尉1职,上三旗有2员,下五旗有3员。下五旗还有拜唐阿1员。
到道光年间,厄鲁特营兵额有了增加,据《伊犁略志》载,厄鲁特营有官员57名,兵3386名。厄鲁特营官兵家眷共22729名,其中兵3384名。
厄鲁特营各级官员及士兵的俸饷均由清朝政府发放。厄鲁特营等“四营”官兵的俸禄钱粮,实行与满营不同的形式,满营是有粮有银,而且月月食钱粮,而厄鲁特等营官兵则有银无粮,即只发俸银,不发口粮。在驻防伊犁的察哈尔、厄鲁特、索伦、锡伯四营中,厄鲁特营人数最多,在坐卡、巡边方面承担的差役最重,他们除驻巡本营辖境卡伦外,还要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等营驻巡卡伦,以及负责5座军台的文报传递。
厄鲁特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边疆,即驻卡巡边。他们除了驻守所辖区域外,还要驻守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他们平时驻卡巡边,定期操练,战时则上战场。
驻守卡伦。1763年,伊犁地区开始设置卡伦,“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
起初,厄鲁特营驻守格根、哈尔奇喇、特克斯色沁、根格色沁、都图岭等处卡伦,这些卡伦均设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与俄国接壤的边界线上。1788年又增设了察林河渡口等处卡伦。厄鲁特营所辖卡伦有32处,②其中常设卡伦4处:特克斯色沁、敦达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移设卡伦4处:特穆尔里克、乌弩古特、鄂博图渡口、昌曼;添撤卡伦24处:特穆尔里克渡口、雅巴尔布拉克、鄂博图、额尔格图、札拉图、库图勒、格根、鄂尔果珠勒、哈尔干图、齐齐罕图、垓尔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绰罗图(一作赤老图)、那(纳)喇特、博尔克阿满(曼)、巴噶塔木(巴噶喀木哈)、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铜厂外、沙里(喇)雅斯、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哈尔奇喇。
厄鲁特营除了驻守以上卡伦外,还派兵5~17名不等协助巴彦岱(惠宁)、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领队大臣驻守24座卡伦。18世纪20年代,沙俄加快了吞并中亚的步伐,不断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我国西北边疆开始出现危机。新疆地区同沙俄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伊犁地区卡伦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卡伦的驻防力量也有加强。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中叶,厄鲁特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9座,即鄂尔古朱勒卡(又译写成鄂尔果珠勒)、特木(穆)尔里克卡、格根卡、哈拉刻拉卡、沙拉(里)雅斯卡、那拉(喇)特卡、乌努(弩)古特卡、峨波土(鄂博图)卡、阿敦格尔布胡土卡;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即柏尔柯阿满(博尔克阿曼)、查干哈大、乌逊祜吉尔、特克斯边(可能是特克斯色沁)、巴汗塔马哈(巴噶喀木哈)、库土(图)勒、齐奇尔哈土(齐齐罕图)、哈尔干土(图)、通(铜)厂外、扎拉土(札拉图)、牙帕尔(雅巴尔)布拉克、特木(穆)尔里克桥、额尔各土(格图)、哈布哈克等巡防哨。
1864年10月7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清政府被迫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又订立了《中俄科布多界约》等三个勘界议定书,一共割去我国西部领土44万平方公里。其中斋桑湖往南,沙俄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七河流域,吹、塔拉斯河流域,使原来在鄂博(界牌)以内,卡伦以外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游牧地全被割去,进而侵吞了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等地方。随着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丢失。“厄鲁特营领队大臣所辖三十二卡,其明属俄国者二十三卡,其明属中国者仅一卡,其八卡佚考”。①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不但负责巡边,查看有无俄人越境之迹,还要防止私越和盗窃。新疆地区的卡伦最初设置时主要任务是内部防范,现在主要就是守卫边界了,所以厄鲁特等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
沙俄军队于1871年出兵侵占伊犁,又将该地区的数十处卡伦毁掉,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最后,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把包括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在内的新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了俄国的版图。《伊犁条约》划定自伊犁西南至伊犁东北一段边界,共立界碑鄂博33处。其中属于厄鲁特营牧地界内共有11处界碑。
中俄重新分界后,伊犁将军金顺在重要地段、隘口处重新安设卡伦,并派兵驻守。厄鲁特营新设卡伦10处,即那林哈勒噶卡、那林郭勒卡、胡苏木图卡、布胡图卡、特克斯噶塔尔干卡、莫霍托罗海卡、阿尔班苏木卡、格登山卡、沙图阿满卡、阿里干谷卡。由于其所属边界与俄境毗连,厄鲁特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
1763年,伊犁南路军台——伊犁至沙图阿满设有7处(由底台南行至阿克苏路),其中有5处军台由厄鲁特营军民驻坐:海努克台、索果尔台、博尔台、特克斯台、沙图阿满台,每座军台额设厄鲁特兵15户,马15匹,牛14头。驻守军台的官兵专管渡送折报公文等事。
厄鲁特营军民不仅驻守以上卡伦、台站,而且还到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驻守哨卡,向乌鲁木齐及内地运送军马等。自1766年始,厄鲁特营军民同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满洲、锡伯二年一换,每年换一半,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一年一换。厄鲁特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自1807年始又添兵10名。他们同其他营的换防兵一道“除分拨坐卡外,其余在城兵丁按期操演”①。1832年,由于经费等原因,停止了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厄鲁特等营官兵还要照看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地,其中厄鲁特营派佐领或骁骑校1员、兵4~15名不等前往驻防。
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游牧边界。吹、塔拉斯河流域原为西蒙古牧地,清朝统一新疆初,这一带暂作为“闲旷之地”,1763年始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塔拉斯地区稽查和巡逻,厄鲁特营官兵也随同前往。“每年夏天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布鲁特边界时,有两满营协领1员,大城(惠员)官2员..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计官10名,兵300名。每年秋季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哈萨克边界时,由两满营派协领1员,惠远城满营官2员,..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计官10名,兵300名”。②届时巡查官兵在边界上会哨,巡查边界,驱逐越界游牧者。
当时巡查分为两路,南路自伊塞克湖之南、巴尔珲岭到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今阿拉木图)到沙喇伯勒地方,在指定的地点彼此交换表报,互换信牌。这样边界地区就能全部查到。道光年间,随着沙俄对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逼近,巡查边防曾一度加强。1840年鸦片战争后,巡查变成巡边。主要任务是巡查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厄鲁特营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定期进行操练。清廷规定厄鲁特营等四营“各于屯所游牧处,随时操演鸟枪、骑射”。③
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厄鲁特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每年8月,将军带领各营官兵前往哈什河等地方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行围。届时厄鲁特营需派副总管1员、官12员、兵270名参加。这些兵丁都是从各旗挑选出来的。
维护内部的安定。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进行作乱。但很快都被平息了,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在镇压张格尔的暴乱中,新疆的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都作出了贡献。
厄鲁特军民也如此,奉命参加戡乱战斗。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面临300名清军覆灭于张格尔屠刀下及张格尔要大举进攻喀什噶尔的危机关头,又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厄鲁特、察哈尔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接着又攻克了喀什噶尔。在这场战役中,厄鲁特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了大功。1828年春节之际,张格尔第四次入卡作乱,被清军活捉,同年6月,张格尔被解送到北京处死。至此,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
1830年,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作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厄鲁特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厄鲁特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的围剿。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们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即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和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厄鲁特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战斗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厄鲁特营领催满吉、委领催巴图那逊、披甲哈拉黠讷莫库、鄂斯库等赏戴了六品蓝翎。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他们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面对倭里罕和卓一伙的进扰,各营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官兵1000余名,协领富珠哩等也带领兵1000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日解了巴楚之围,8月14日又解除了叶尔羌之围。9月21日,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①逃出卡外,清军跟踪追击,出卡进剿,倭里罕逃到了浩罕。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坐镇肃州(今甘肃酒泉)派刘锦棠率军进疆,驱逐侵略者。第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战斗中,厄鲁特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沙俄侵略者于1863年数次侵犯伊犁博罗胡吉尔等卡伦,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军分别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迫使沙俄撤回博罗胡吉尔一带。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厄鲁特军民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察哈尔、锡伯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英勇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在伊犁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10年期间,不仅在伊犁周围设要塞“各处把守,水泄不通”,而且沙俄在政治上也进行殖民奴役,他们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建制,撤换和驱除清政府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即沙俄突厥斯坦总督斜米列契省)直接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厄鲁特上三旗牧地被俄割占,其人口在俄境未回。后来经过交涉,其部众大都返回,但牧地却丧失了。
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他们以宁死不屈的精神,给侵略者一个响亮的回答。沙俄并不甘心,对各营兵丁进行敲诈勒索,趁机用发口粮等手段,诱迫各营军民归顺。但是,各营“兵民不从,亦不领粮”①,他们不畏强暴的坚强骨气再次挫败了沙俄的野心。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后,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伊犁最终未落入沙俄手中,这同厄鲁特蒙古等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
中国军民收复后的新疆,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地亩荒芜,人民离散,厄鲁特等营的情况也是惨不忍睹。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之后,着手伊犁重建工作,首先招集流离失所的厄鲁特、锡伯等营众,恢复厄鲁特、锡伯等营制。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决定将乌鲁木齐作为省会,自此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伊犁移至乌鲁木齐。伊犁仍设将军,但不再总统全疆军务,尽管伊塔边务。虽然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厄鲁特等营建制没有触动。营仍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8员。领队大臣仍受伊犁将军节制。由于厄鲁特营所属边界与俄境毗连,其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他们仍然是伊犁戍边的主要力量。清政府对厄鲁特等营作出了一些新的部署,厄鲁特营领队,移驻特克斯驻扎,以扼伊犁山南与俄接界之西面门户,兼扼冰岭。
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因“减兵加饷”,裁减各营官兵,裁减厄鲁特兵500名。所裁旗兵,每名授羊30只,令其牧放,仍属所在旗管辖。据《新疆图志》载,光绪末年厄鲁特营户口有:“职业职官100名,马步甲1236名,闲散10603名,孤25名”。①
新疆都督杨增新在不断裁减军队的同时,基于防边卫国,1914年1月24日,下令将厄鲁特营等四营领队大臣改为领队官,下属正副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均取消。虽然如此,厄鲁特营内部仍然沿用总管、副总管等旧制。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杨增新采取了停发厄鲁特等营薪饷,以挑兵为条件,免除一切赋税的措施,因此大部分官兵都解甲归田,卡伦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尽管如此,厄鲁特军民仍按旧制,巡防驻守各边界卡伦。
1938年厄鲁特营制被取消,均纳入地方行政编制。至此,长达170余年的厄鲁特营制取消。
游牧、狩猎的休养生息之地。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是兴办官牧厂。1760年,清政府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设立官营牧厂。伊犁牧厂有孳生马厂、孳生羊厂、驼厂、孳生牛厂。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牲畜除了部分羊和牛由维吾尔族牧放,部分马、牛由锡伯营牧放外,其余都由察哈尔、厄鲁特、索伦三营放养。骆驼厂全部由厄鲁特营经营。由于锡伯、索伦营兵丁不善畜牧,因此1773年后停止了索伦营经营马厂、牛厂以及锡伯营经营牛厂。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
以孳生厂为例,据1793年伊犁将军保宁奏,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7210匹,下五旗牧放9857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头,其中厄鲁特上三旗牧牛2483头,下五旗及沙毕纳尔四佐领牧牛4065头;羊厂,1772年共有孳生本牛140695只,厄鲁特营上三旗牧放羊29742只,下五旗及沙比纳尔四佐领牧羊56666只;1802年共收获孳生驼2665峰,上三旗牧驼1833峰,下五旗牧驼2343峰。②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孳生厂取孳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2636匹,下五旗牧马5242匹,牛厂有牛11573头,内上三旗牧牛2463头,下五旗牧牛4627头,羊厂存羊32187只,上三旗牧羊9500只,下五旗牧羊12112只。厄鲁特营仅牧放伊犁牧厂的牲畜就有十几万头。
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在特克斯河、察林河流域及塔马哈一带,下五旗在崆吉斯(今巩乃斯)、哈什河流域及霍诺海一带,以上草原都由高山环抱,其水草丰美,地域辽阔。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得膘肥体壮,孳生繁庶。伊犁将军伊勒图曾在1775~1781年连续5次查阅察哈尔、厄鲁特牧放的特穆尔牧厂时都很满意。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农民起义,浩罕阿古柏及沙俄乘机入侵,致使“全疆官厂荡然无存”,“伊犁乱后,牧厂悉停”,①厄鲁特营众的生计也非常艰难。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廷也无力再大规模地经营牧厂了。1896年,伊犁将军长庚为恢复生产,“筹办屯田耕种,以裕锡伯、索伦两营生计,筹办孳生牧畜,以裕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生计”②。伊犁牧厂恢复以后,察哈尔军民仍然同厄鲁特军民一道经营伊犁牧厂的牲畜。虽然牧厂恢复了,但由于牧厂荒废了几年,草场也不如从前了。
厄鲁特及察哈尔营众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伊犁官牧厂的马匹,主要是军马,用于拨补营缺、军台、卡伦、战事。羊为官兵食肉之主要来源,察哈尔营众牧放的羊只不仅自己食用,而且还供应满营官兵。据载,满营官兵6000员,每年每名可食羊6只,均有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孳生羊内拨给。牛为当时兵屯及铅、铜厂提供了重要工具。伊犁的厄鲁特蒙古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开发清代新疆畜牧业作出了贡献。
农业的开发。由于厄鲁特营的“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因此,其兵丁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厄鲁特营上三旗6个佐领屯田4处:敦达察罕乌苏、霍依图察罕乌苏、特尔莫土、哈牧哈;下五旗14个佐领屯田16处:昌满、哈什春稽布拉克、苏布台、浑多赖、衮佐特哈、库尔库类、呢勒哈、大济尔噶朗、算珠图、特勤克、特古斯塔柳、沙喇博果沁、巴哈拉克、弩楚衮。以上田地都位于河流域,因此都用河水灌溉。③
厄鲁特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屯田所获粮食,不仅自己食用,有时多获粮食还上缴官府,为当地驻防军提供军粮。
厄鲁特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再者牧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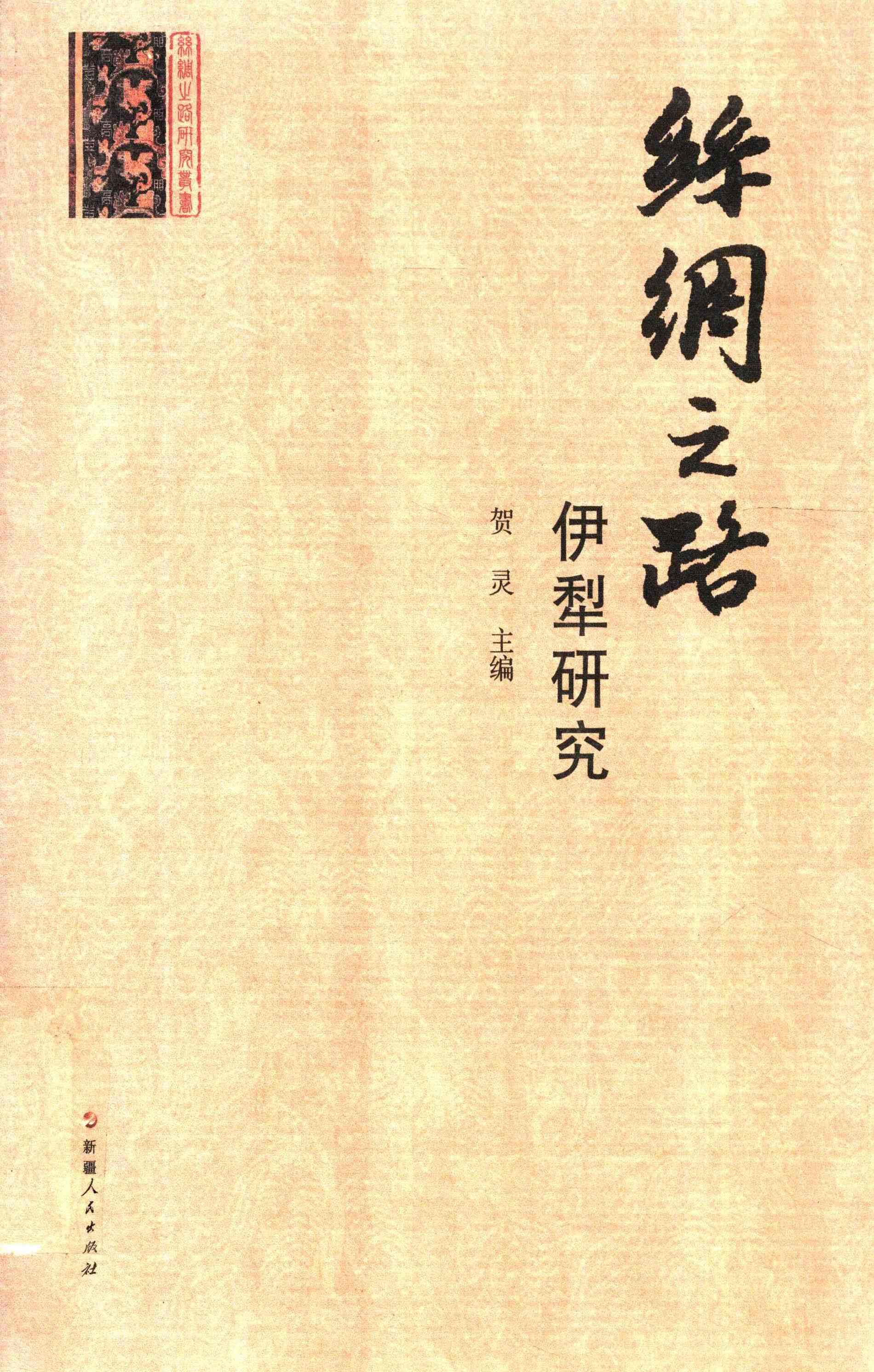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