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察哈尔营八旗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52 |
| 颗粒名称: | 第五节 察哈尔营八旗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9 |
| 页码: | 109-117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清廷统一新疆后,感到现有的兵力不足,不能驾驭目前的局势。伊犁作为新疆的重镇不能不派兵驻守。遂决定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迁入新疆。察哈尔八旗兵就是这些迁入新疆的八旗兵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批迁入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清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清廷决定派察哈尔官兵移驻伊犁。据满文档案记载,察哈尔蒙古是分两批西迁新疆的,分别是从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等地调遣的。 |
| 关键词: | 伊犁 清代 察哈尔营八旗 |
内容
清廷统一新疆后,感到现有的兵力不足,不能驾驭目前的局势。伊犁作为新疆的重镇不能不派兵驻守。遂决定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迁入新疆。察哈尔八旗兵就是这些迁入新疆的八旗兵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批迁入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清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清廷决定派察哈尔官兵移驻伊犁。据满文档案记载,察哈尔蒙古是分两批西迁新疆的,分别是从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等地调遣的。
1762年5月9日,第一批西迁官兵1000名汇集在察哈尔八旗中心,他们背负战箭,腰挎战刀,骑着战马,携带家眷,告别家乡,陆陆续续出发了。次年3月6日,1000名官兵陆续抵达乌鲁木齐。除留驻乌鲁木齐150名,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派驻50名外,派驻伊犁之官兵843人,自1763年初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于4月15日抵达赛里木湖。①据满文档案记载,在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八旗官兵内有200名厄鲁特人。②
第二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他们要解送大批牲畜到伊犁。兵丁分两队出发。前队500名官兵要解送4万只羊到伊犁,不携带家眷,家眷由后队携带。前队500名兵丁于1763年5月11日起程,花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到达伊犁;后队500名兵丁连同1000户家眷共2013人,于1763年6月8日起程,次年5月抵达伊犁。这批携眷移驻的1000名察哈尔兵,其中有厄鲁特兵丁34名,均作为披甲。两批察哈尔兵行走路线大致相同,都是越过蒙古高原。
两批西迁新疆的官兵总人数据《伊江汇览》载:移驻伊犁的察哈尔官兵1836户,5548人,③加上留在乌鲁木齐及移驻库尔喀喇乌苏的察哈尔官兵总计6090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此数。
驻防伊犁的1836户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一带。清政府之所以将其安置在博尔塔拉,主要是从战略地位及地理环境两方面考虑的。博尔塔拉地处西部边陲(当时只有北面与沙俄接壤),历来是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其次是博尔塔拉地域辽阔,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个天然的好牧场。虽然博尔塔拉在战略位置及地理环境上都很重要,却空旷无人,因此,清政府决定让作为游牧兵的察哈尔人驻守博尔塔拉,不仅适应自身的游牧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便开发和保卫这块西陲宝地。
察哈尔官兵的西迁,不仅使自身历史发生了变化,而且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察哈尔兵的胜利西迁,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即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察哈尔军民迁入博尔塔拉后,伊犁地区的军事防御呈南北西遥相呼应局面。
1763年,1800名察哈尔官兵先后编设2个昂吉(昂吉,蒙古语,意为分支,是准噶尔台吉下组织名称之一,清朝沿用),察哈尔营正式建立。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人为“旧昂吉”,第二批西迁的为“新昂吉”,1764年又设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蒙古人称米昂本)一员,总揽边防事务,平时定期召集各旗兵丁进行军训,战时则根据伊犁将军的调遣命令,负责动员、率领全营兵丁从征参战。领队大臣驻惠远城(1896年移驻博尔塔拉),归伊犁将军节制。
1767年6月确定新昂吉为右翼,旧昂吉为左翼,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2个苏木为1旗,即左翼4旗,右翼4旗,共计8旗。①
自此西迁的察哈尔兵正式以八旗组织建制起来。两翼各有官兵920名,并各附有厄鲁特闲散100名,各设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空蓝翎3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名。
伊犁将军还奉旨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以及八旗旗纛,其八旗的旗名同内地的察哈尔旗名一样,除全色的黄、白、红、蓝4色旗外,另4旗在原色旗上镶边,称镶蓝、镶白、镶黄、镶红。右翼(新昂吉)4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旧昂吉)4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自1764年始,察哈尔营内除原随迁的厄鲁特人外,又陆续安插了自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等地逃来投清的厄鲁特人,1767年共计有厄鲁特闲散兵200名,以后由厄鲁特闲散内又拨入察哈尔营420户。因此在察哈尔营有厄鲁特人600余户,千余人,多在旧昂吉。
察哈尔营官兵的俸饷同伊犁其他营一样均由清朝政府拨发,领队大臣岁支俸银700两,口粮4680斤;总管每人岁支俸银130两;副总管、佐领每人岁支银105两;骁骑校岁支银60两;领催岁支银24两;委笔帖式岁支银36两;空蓝翎月支盐菜银2两5钱,口粮60斤;披甲每名岁之钱粮银12两。察哈尔营官兵估需俸饷银26190余两。
清廷对于西迁的察哈尔部众推行的是总管旗制。总管旗设总管(满语称乌库尔代,察哈尔蒙古也习惯称乌库尔代,又尊称为昂本)、副总管(依日格代)各1人管辖。总管、副总管管理翼内各旗一切事务。总管、副总管主要由本旗内佐领升迁。总管旗制,一直延续到1938年才被废除。
察哈尔营八旗为军政合一的组织,凡蒙古族旗内的男性丁口,皆按规定18~60岁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其兵丁平时生产,战时从征。旗以下的社会组织是苏木(蒙古语,“箭”之意,就是满族的“牛录”汉语称为“佐”)。苏木是旗以下掌管兵役、行政的基层组织。察哈尔营每旗有2个苏,木,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清朝规定每150户组成1个苏木,其中50人为骁骑(即现役兵)兵,其余100人为闲散骁骑兵(即预备役兵),统称为箭丁。
每苏木设章京(章京为满语,察哈尔蒙古发音为占格,汉语佐领之意)1人,负责统辖全佐兵丁,审理编报丁册。章京以下,设昆都(骁骑校)、博硕克(领催)、转达(护军校)、梅伦(副佐领)等官吏。苏木以下每10户设“什长”1人,受章京管辖。
左右翼8个旗都以军旗色命名,即库外特夏尔(镶黄旗)、古勒夏尔(正黄旗)、库外特乌兰(镶红旗)、古勒乌兰(又称古勒郎,正红旗)、库外特察干(镶白旗)、古勒察干(正白旗)、库外特科克(又俗称依克科克,“大蓝之意”,镶蓝旗)、古勒科克(又俗称巴噶科克,“小蓝之意”,正蓝旗)。
驻守卡伦、台站。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主要任务是驻卡巡边。察哈尔营驻守21座卡伦,其中常设卡伦9座,添撤卡伦12座,无移设卡伦。常设卡伦为:乌兰布喇、扎克鄂博、哈布塔海、乌柯克、沁达兰、索达坂、冲库克、库库托木、达尔达木图卡伦。添撤卡伦12座:绰伦古尔、音德尔图、阿尔齐图哈玛尔、雅玛图、木鲁、沙喇布鲁克、硕博图、察奇木图呢盖、喀喇乌珠尔、察罕乌苏、鄂拓克赛里安达拉、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等。
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年间,察哈尔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6座,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①6座卡伦为:索达坂卡、沁达兰卡、哈布塔海卡、库克托木卡、许步土卡、绰伦古尔卡。14个巡防哨为:干楚汗布拉克、鄂拓克沙里、达尔大木土、扎克峨波、乌萨克、夏拉西里、殷德尔土、夏拉布拉克、木鲁、哈拉乌朱尔、雅玛图、查干乌苏、伊拉土哈木尔、察克尔图拉。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派兵5~15名协助巴彦岱(惠宁)领队大臣驻守其管辖的塔尔基卡及干楚汗卡。
1864年10月7日,随着沙俄入侵,我国大片国土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沙俄割占。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沿边卡伦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主要任务就是守卫边界。所以,察哈尔营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1876年,察哈尔营管辖的卡伦共设15个,即干珠罕、察罕郭勒、哈喇郭勒、哈喇乌珠尔、察罕乌苏、西里布拉克、库克托木、索达巴罕、沁达兰、哈布塔海、扎克鄂博、木鲁、察齐尔图呢盖、固尔班毕力齐尔、额肯西里,史称“旧21、新15”。光绪年间,国力日衰,清政府为节省军饷,将原察哈尔营左右两翼16佐领裁去4个,1903年初,察哈尔营左右两翼共有官兵1150名,仍按旧制巡逻和防守边界卡伦。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有驻守5座军台的任务。军台就是驻军防守的驿站,它负有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报文件,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物等职责。通常每个军台内额设兵14名,车2辆,马43匹,牛12头等。察哈尔营驻守的5座军台为:塔勒奇阿满台(俗称头台)、博勒齐尔台(塔勒齐尔台,即二台)、鄂尔哲图博木台(俗称三台)、呼苏图布鲁克台(俗称四台)、托和木图台(又称五台)。这5座军台都在伊犁通往库尔喀喇乌苏境(即东路)及博尔塔拉的交通要道上。
察哈尔营不仅驻守博尔塔拉,自1766年始,还同满、锡伯、索伦、厄鲁特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察哈尔、厄鲁特营一年一换。察哈尔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察哈尔兵还要监督土尔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
自1764年始,清朝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即吹河,今改名为楚河,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塔拉斯(因临塔拉斯河而得名,今为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地区稽查和巡逻,察哈尔官兵也随同前往。随着沙俄的入侵,巡查完全是巡边,主要任务是勘查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察哈尔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要定期进行操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察哈尔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据满文档案记载,总管2员每员战箭250枝,副总管、佐领18员,每员战箭200枝,骁骑校16员,每员战箭100枝,领催64名,每员战箭70枝。而且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员还要必配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马甲(即披甲)1736名,每员战箭50枝、撒袋1副、弓1张、腰刀1把,每2名兵,还配有长枪1杆,每5名兵,配有鸟枪1杆。察哈尔营的武器装备计有:撒袋1837副,弓1937张,腰刀1837把,长枪868杆,鸟枪347杆。②
察哈尔等营官兵当时素称“国家劲旅”。他们在新疆安内攘外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作乱。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清廷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由于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察哈尔、锡伯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在攻克喀什噶尔的战役中,察哈尔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1828年6月,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张格尔暴乱之所以能够很快被平息,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1830年初,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作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察哈尔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察哈尔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一次是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一次是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察哈尔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最终平定了叛乱,为维护南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在平定“七和卓之乱”的斗争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在英吉沙尔解围尤为出力人员折中察哈尔官兵有骁骑校鄂奇尔、佐领巴图鄂奇尔,均赏戴花翎,委官三音扣苏木雅擢升为骁骑校等,①还有其他战役中获奖的察哈尔营官兵。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官兵1000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14日先后解了巴楚、叶尔羌之围,接着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逃出卡外。倭里罕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同样对在本次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官兵给予奖赏,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以叶尔羌等处剿贼出力,被授予巴图鲁名号。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驱逐侵略者。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驱逐阿古柏的斗争中,察哈尔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这在史料中都有记载。
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察哈尔左翼总管博勒堆、右翼总管阿有等率领官兵于5月22日在霍尔果斯与沙俄军队打了一仗,沙俄入侵者兵败逃窜。6月26日,沙俄军队渡过霍尔果斯河,向驻守在阿克肯特至阿拉木图一带的伊犁军民进攻。广大伊犁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他们手持的兵器是弓箭和腰刀、鸟枪等,最终抵抗不过手持洋枪洋炮的侵略军,而节节败退。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察哈尔蒙古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厄鲁特、锡伯、柯尔克孜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侵占伊犁地区后实行军事殖民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长达10年。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伊犁各族军民并未被沙俄淫威所吓倒,“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精)河土尔扈特贝勒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①。察哈尔左右翼总管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均派人到塔尔巴哈台,向移住在那里的署伊犁将军荣全禀报伊犁情形,并纷纷要求派大军收复伊犁。由于沙俄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清朝政府决定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同时谕令军机大臣和驻守边疆的部队,加强防卫,防止沙俄入侵。
这一时期,沙俄还唆使原先从北疆各地潜逃伊犁,被沙俄收留的白彦虎(原陕西回民起义领袖,后降附于阿古柏)残余进犯伊犁边境,1879年春白彦虎残余又进而扰犯大河沿子及博尔塔拉一带,驻守博尔塔拉的部分察哈尔营兵,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协同作战,迅速歼灭了这帮残匪。
1878年2月16日清廷命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并率领察哈尔、锡伯兵在博尔塔拉屯垦。喀带领察哈尔、锡伯军民在大营盘(今博乐市)积极建造营房,兴修水利,屯种军粮,并获得好的收成,以实际行动支援抗俄斗争。喀尔莽阿因功绩卓越,而获得了清政府给予的“优叙”的奖励。在沙俄占领伊犁的10年间,察哈尔军民用各种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察哈尔营内涌现出了一些抗俄英雄,成绩卓著的都曾得到提升和嘉奖。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规定,1882年2月清军进驻伊犁,沙俄军队于1883年3月完全撤出伊犁。虽然伊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项不平等的条约给新疆造成了严重后果。
畜牧业的开发。西迁的察哈尔作为游牧兵丁,其主要任务除了驻卡巡边外,仍然是牧放牲畜。
伊犁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牧草丰茂。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经济开发活动是兴办官牧厂。伊犁牧厂始于1760年立孳生马厂,1761年立孳生羊厂、驼厂,1762年立孳生牛厂。
伊犁官办牧厂的部分牲畜是察哈尔蒙古从故乡带来的。察哈尔蒙古在家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牧放着官办牧厂的牲畜,据满文档案记载,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共带来了4万只羊,2050峰驼,5447匹马。①批牲畜不仅为伊犁牧厂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新疆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品种。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经营着伊犁官办牧厂的大部分牲畜,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自此,伊犁牧厂除了有少部分羊以及牛仍由维吾尔人牧放外,其余则全由察哈尔、厄鲁特营经营。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牧放的牲畜数也大为增加。以孳生厂为例,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马5743匹,右翼牧放马5759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牛2076只,右翼牧牛2088只;羊厂共有孳生本羊14069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羊28287只,右翼牧放羊26000只。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孳生厂取孳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察哈尔左翼牧马4878匹,察哈尔右翼牧马4881匹,牛厂有牛11573只,内察哈尔左翼牧牛2433只,察哈尔右翼牧牛2350只,羊厂存羊32187只,察哈尔左翼牧羊1430只。据满文档案记载,乾隆年间“察哈尔兵仅有1800名,牧放特穆尔牧厂及孳生牲畜共计10万余头,且又有各自私畜”。②
察哈尔营牧地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今博乐市境内)、赛里木湖一带,其牧地北、西、南面都为高山所环抱,东为戈壁平原及湖泊,中部则是辽阔的草原。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更何况,察哈尔蒙古在故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经营着官牧场牲畜,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也是有经验的。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得膘肥体壮,孳生繁庶。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廷也无力再大规模地经营牧厂了。
西迁的察哈尔蒙古一踏上祖国的西北,就开始一边戍边,一边牧放官牧厂的牲畜,他们同厄鲁特营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畜牧经验和牲畜,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的开发。察哈尔蒙古西迁北疆后,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因此,察哈尔蒙古西迁后“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时,当地田渠皆废,遍地是野草,但他们不畏艰难,在荒原上安家立业,开荒种地,没过两年,“察哈尔二昂吉自去年暂行移驻博罗塔拉以来,农牧皆得其利”。③博尔塔拉属于新疆盆地中西部山地干燥气候区,夏季炎热,降水少,冬季严寒,因此农业用水是河水。察哈尔军民灌溉用水主要是博尔塔拉河。博尔塔拉河是博尔塔拉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252公里,流域面积15928平方公里。博尔塔拉河两岸察哈尔人民基本上在沿河地带耕种农田。
嘉庆年间,松筠(察哈尔部人,后被编入蒙古八旗正蓝旗)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后,很重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博尔塔拉开凿了一条最大的水渠,名为“皇渠”察哈尔蒙古称为“相根布呼”意为“政府出资修的渠”水渠长逾10公里,后不断扩,修。1942年(民国31)长达35,公里,可灌溉13600亩地,。①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察哈尔营的屯田亩数扩大,大营盘(博乐市境)、小营盘、青得里、达勒特等地都成为其屯地,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共屯田3200亩。驻牧于今温泉县的察哈尔营左翼屯田于哈尔布呼、安格里格、查干屯格等地。
1879年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原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领导察哈尔及锡伯军民开挖“哈日布呼”(“黑渠”之意),该渠引入博尔塔拉河水,渠全长约25公里,这是温泉县最早的一条渠道工程。1879年在喀尔莽阿指挥下,蒙古族、锡伯族每户出一个劳动力修建了“夏日布呼”大渠(意为“黄渠”之意),长约10~15公里。
察哈尔营的旗屯收效是很大的,经济的发展又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也增加了。民国初年,察哈尔营人口总数为16023人。②
察哈尔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作为清朝统一新疆后第一批拓荒者,察哈尔军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为清代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屯垦戍边,肩负着驻守卡伦的重任。察哈尔军民驻守祖国西北前哨,昼夜巡卡守边,尽职尽责,最终未使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等地落入侵略者手里。他们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762年5月9日,第一批西迁官兵1000名汇集在察哈尔八旗中心,他们背负战箭,腰挎战刀,骑着战马,携带家眷,告别家乡,陆陆续续出发了。次年3月6日,1000名官兵陆续抵达乌鲁木齐。除留驻乌鲁木齐150名,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派驻50名外,派驻伊犁之官兵843人,自1763年初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于4月15日抵达赛里木湖。①据满文档案记载,在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八旗官兵内有200名厄鲁特人。②
第二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他们要解送大批牲畜到伊犁。兵丁分两队出发。前队500名官兵要解送4万只羊到伊犁,不携带家眷,家眷由后队携带。前队500名兵丁于1763年5月11日起程,花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到达伊犁;后队500名兵丁连同1000户家眷共2013人,于1763年6月8日起程,次年5月抵达伊犁。这批携眷移驻的1000名察哈尔兵,其中有厄鲁特兵丁34名,均作为披甲。两批察哈尔兵行走路线大致相同,都是越过蒙古高原。
两批西迁新疆的官兵总人数据《伊江汇览》载:移驻伊犁的察哈尔官兵1836户,5548人,③加上留在乌鲁木齐及移驻库尔喀喇乌苏的察哈尔官兵总计6090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此数。
驻防伊犁的1836户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一带。清政府之所以将其安置在博尔塔拉,主要是从战略地位及地理环境两方面考虑的。博尔塔拉地处西部边陲(当时只有北面与沙俄接壤),历来是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其次是博尔塔拉地域辽阔,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个天然的好牧场。虽然博尔塔拉在战略位置及地理环境上都很重要,却空旷无人,因此,清政府决定让作为游牧兵的察哈尔人驻守博尔塔拉,不仅适应自身的游牧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便开发和保卫这块西陲宝地。
察哈尔官兵的西迁,不仅使自身历史发生了变化,而且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察哈尔兵的胜利西迁,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即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察哈尔军民迁入博尔塔拉后,伊犁地区的军事防御呈南北西遥相呼应局面。
1763年,1800名察哈尔官兵先后编设2个昂吉(昂吉,蒙古语,意为分支,是准噶尔台吉下组织名称之一,清朝沿用),察哈尔营正式建立。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人为“旧昂吉”,第二批西迁的为“新昂吉”,1764年又设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蒙古人称米昂本)一员,总揽边防事务,平时定期召集各旗兵丁进行军训,战时则根据伊犁将军的调遣命令,负责动员、率领全营兵丁从征参战。领队大臣驻惠远城(1896年移驻博尔塔拉),归伊犁将军节制。
1767年6月确定新昂吉为右翼,旧昂吉为左翼,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2个苏木为1旗,即左翼4旗,右翼4旗,共计8旗。①
自此西迁的察哈尔兵正式以八旗组织建制起来。两翼各有官兵920名,并各附有厄鲁特闲散100名,各设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空蓝翎3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名。
伊犁将军还奉旨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以及八旗旗纛,其八旗的旗名同内地的察哈尔旗名一样,除全色的黄、白、红、蓝4色旗外,另4旗在原色旗上镶边,称镶蓝、镶白、镶黄、镶红。右翼(新昂吉)4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旧昂吉)4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自1764年始,察哈尔营内除原随迁的厄鲁特人外,又陆续安插了自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等地逃来投清的厄鲁特人,1767年共计有厄鲁特闲散兵200名,以后由厄鲁特闲散内又拨入察哈尔营420户。因此在察哈尔营有厄鲁特人600余户,千余人,多在旧昂吉。
察哈尔营官兵的俸饷同伊犁其他营一样均由清朝政府拨发,领队大臣岁支俸银700两,口粮4680斤;总管每人岁支俸银130两;副总管、佐领每人岁支银105两;骁骑校岁支银60两;领催岁支银24两;委笔帖式岁支银36两;空蓝翎月支盐菜银2两5钱,口粮60斤;披甲每名岁之钱粮银12两。察哈尔营官兵估需俸饷银26190余两。
清廷对于西迁的察哈尔部众推行的是总管旗制。总管旗设总管(满语称乌库尔代,察哈尔蒙古也习惯称乌库尔代,又尊称为昂本)、副总管(依日格代)各1人管辖。总管、副总管管理翼内各旗一切事务。总管、副总管主要由本旗内佐领升迁。总管旗制,一直延续到1938年才被废除。
察哈尔营八旗为军政合一的组织,凡蒙古族旗内的男性丁口,皆按规定18~60岁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其兵丁平时生产,战时从征。旗以下的社会组织是苏木(蒙古语,“箭”之意,就是满族的“牛录”汉语称为“佐”)。苏木是旗以下掌管兵役、行政的基层组织。察哈尔营每旗有2个苏,木,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清朝规定每150户组成1个苏木,其中50人为骁骑(即现役兵)兵,其余100人为闲散骁骑兵(即预备役兵),统称为箭丁。
每苏木设章京(章京为满语,察哈尔蒙古发音为占格,汉语佐领之意)1人,负责统辖全佐兵丁,审理编报丁册。章京以下,设昆都(骁骑校)、博硕克(领催)、转达(护军校)、梅伦(副佐领)等官吏。苏木以下每10户设“什长”1人,受章京管辖。
左右翼8个旗都以军旗色命名,即库外特夏尔(镶黄旗)、古勒夏尔(正黄旗)、库外特乌兰(镶红旗)、古勒乌兰(又称古勒郎,正红旗)、库外特察干(镶白旗)、古勒察干(正白旗)、库外特科克(又俗称依克科克,“大蓝之意”,镶蓝旗)、古勒科克(又俗称巴噶科克,“小蓝之意”,正蓝旗)。
驻守卡伦、台站。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主要任务是驻卡巡边。察哈尔营驻守21座卡伦,其中常设卡伦9座,添撤卡伦12座,无移设卡伦。常设卡伦为:乌兰布喇、扎克鄂博、哈布塔海、乌柯克、沁达兰、索达坂、冲库克、库库托木、达尔达木图卡伦。添撤卡伦12座:绰伦古尔、音德尔图、阿尔齐图哈玛尔、雅玛图、木鲁、沙喇布鲁克、硕博图、察奇木图呢盖、喀喇乌珠尔、察罕乌苏、鄂拓克赛里安达拉、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等。
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年间,察哈尔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6座,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①6座卡伦为:索达坂卡、沁达兰卡、哈布塔海卡、库克托木卡、许步土卡、绰伦古尔卡。14个巡防哨为:干楚汗布拉克、鄂拓克沙里、达尔大木土、扎克峨波、乌萨克、夏拉西里、殷德尔土、夏拉布拉克、木鲁、哈拉乌朱尔、雅玛图、查干乌苏、伊拉土哈木尔、察克尔图拉。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派兵5~15名协助巴彦岱(惠宁)领队大臣驻守其管辖的塔尔基卡及干楚汗卡。
1864年10月7日,随着沙俄入侵,我国大片国土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沙俄割占。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沿边卡伦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主要任务就是守卫边界。所以,察哈尔营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1876年,察哈尔营管辖的卡伦共设15个,即干珠罕、察罕郭勒、哈喇郭勒、哈喇乌珠尔、察罕乌苏、西里布拉克、库克托木、索达巴罕、沁达兰、哈布塔海、扎克鄂博、木鲁、察齐尔图呢盖、固尔班毕力齐尔、额肯西里,史称“旧21、新15”。光绪年间,国力日衰,清政府为节省军饷,将原察哈尔营左右两翼16佐领裁去4个,1903年初,察哈尔营左右两翼共有官兵1150名,仍按旧制巡逻和防守边界卡伦。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有驻守5座军台的任务。军台就是驻军防守的驿站,它负有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报文件,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物等职责。通常每个军台内额设兵14名,车2辆,马43匹,牛12头等。察哈尔营驻守的5座军台为:塔勒奇阿满台(俗称头台)、博勒齐尔台(塔勒齐尔台,即二台)、鄂尔哲图博木台(俗称三台)、呼苏图布鲁克台(俗称四台)、托和木图台(又称五台)。这5座军台都在伊犁通往库尔喀喇乌苏境(即东路)及博尔塔拉的交通要道上。
察哈尔营不仅驻守博尔塔拉,自1766年始,还同满、锡伯、索伦、厄鲁特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察哈尔、厄鲁特营一年一换。察哈尔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察哈尔兵还要监督土尔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
自1764年始,清朝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即吹河,今改名为楚河,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塔拉斯(因临塔拉斯河而得名,今为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地区稽查和巡逻,察哈尔官兵也随同前往。随着沙俄的入侵,巡查完全是巡边,主要任务是勘查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察哈尔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要定期进行操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察哈尔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据满文档案记载,总管2员每员战箭250枝,副总管、佐领18员,每员战箭200枝,骁骑校16员,每员战箭100枝,领催64名,每员战箭70枝。而且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员还要必配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马甲(即披甲)1736名,每员战箭50枝、撒袋1副、弓1张、腰刀1把,每2名兵,还配有长枪1杆,每5名兵,配有鸟枪1杆。察哈尔营的武器装备计有:撒袋1837副,弓1937张,腰刀1837把,长枪868杆,鸟枪347杆。②
察哈尔等营官兵当时素称“国家劲旅”。他们在新疆安内攘外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作乱。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清廷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由于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察哈尔、锡伯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在攻克喀什噶尔的战役中,察哈尔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1828年6月,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张格尔暴乱之所以能够很快被平息,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1830年初,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作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察哈尔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察哈尔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一次是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一次是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察哈尔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最终平定了叛乱,为维护南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在平定“七和卓之乱”的斗争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在英吉沙尔解围尤为出力人员折中察哈尔官兵有骁骑校鄂奇尔、佐领巴图鄂奇尔,均赏戴花翎,委官三音扣苏木雅擢升为骁骑校等,①还有其他战役中获奖的察哈尔营官兵。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官兵1000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14日先后解了巴楚、叶尔羌之围,接着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逃出卡外。倭里罕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同样对在本次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官兵给予奖赏,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以叶尔羌等处剿贼出力,被授予巴图鲁名号。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驱逐侵略者。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驱逐阿古柏的斗争中,察哈尔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这在史料中都有记载。
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察哈尔左翼总管博勒堆、右翼总管阿有等率领官兵于5月22日在霍尔果斯与沙俄军队打了一仗,沙俄入侵者兵败逃窜。6月26日,沙俄军队渡过霍尔果斯河,向驻守在阿克肯特至阿拉木图一带的伊犁军民进攻。广大伊犁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他们手持的兵器是弓箭和腰刀、鸟枪等,最终抵抗不过手持洋枪洋炮的侵略军,而节节败退。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察哈尔蒙古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厄鲁特、锡伯、柯尔克孜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侵占伊犁地区后实行军事殖民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长达10年。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伊犁各族军民并未被沙俄淫威所吓倒,“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精)河土尔扈特贝勒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①。察哈尔左右翼总管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均派人到塔尔巴哈台,向移住在那里的署伊犁将军荣全禀报伊犁情形,并纷纷要求派大军收复伊犁。由于沙俄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清朝政府决定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同时谕令军机大臣和驻守边疆的部队,加强防卫,防止沙俄入侵。
这一时期,沙俄还唆使原先从北疆各地潜逃伊犁,被沙俄收留的白彦虎(原陕西回民起义领袖,后降附于阿古柏)残余进犯伊犁边境,1879年春白彦虎残余又进而扰犯大河沿子及博尔塔拉一带,驻守博尔塔拉的部分察哈尔营兵,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协同作战,迅速歼灭了这帮残匪。
1878年2月16日清廷命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并率领察哈尔、锡伯兵在博尔塔拉屯垦。喀带领察哈尔、锡伯军民在大营盘(今博乐市)积极建造营房,兴修水利,屯种军粮,并获得好的收成,以实际行动支援抗俄斗争。喀尔莽阿因功绩卓越,而获得了清政府给予的“优叙”的奖励。在沙俄占领伊犁的10年间,察哈尔军民用各种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察哈尔营内涌现出了一些抗俄英雄,成绩卓著的都曾得到提升和嘉奖。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规定,1882年2月清军进驻伊犁,沙俄军队于1883年3月完全撤出伊犁。虽然伊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项不平等的条约给新疆造成了严重后果。
畜牧业的开发。西迁的察哈尔作为游牧兵丁,其主要任务除了驻卡巡边外,仍然是牧放牲畜。
伊犁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牧草丰茂。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经济开发活动是兴办官牧厂。伊犁牧厂始于1760年立孳生马厂,1761年立孳生羊厂、驼厂,1762年立孳生牛厂。
伊犁官办牧厂的部分牲畜是察哈尔蒙古从故乡带来的。察哈尔蒙古在家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牧放着官办牧厂的牲畜,据满文档案记载,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共带来了4万只羊,2050峰驼,5447匹马。①批牲畜不仅为伊犁牧厂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新疆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品种。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经营着伊犁官办牧厂的大部分牲畜,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自此,伊犁牧厂除了有少部分羊以及牛仍由维吾尔人牧放外,其余则全由察哈尔、厄鲁特营经营。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牧放的牲畜数也大为增加。以孳生厂为例,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马5743匹,右翼牧放马5759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牛2076只,右翼牧牛2088只;羊厂共有孳生本羊14069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羊28287只,右翼牧放羊26000只。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孳生厂取孳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察哈尔左翼牧马4878匹,察哈尔右翼牧马4881匹,牛厂有牛11573只,内察哈尔左翼牧牛2433只,察哈尔右翼牧牛2350只,羊厂存羊32187只,察哈尔左翼牧羊1430只。据满文档案记载,乾隆年间“察哈尔兵仅有1800名,牧放特穆尔牧厂及孳生牲畜共计10万余头,且又有各自私畜”。②
察哈尔营牧地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今博乐市境内)、赛里木湖一带,其牧地北、西、南面都为高山所环抱,东为戈壁平原及湖泊,中部则是辽阔的草原。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更何况,察哈尔蒙古在故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经营着官牧场牲畜,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也是有经验的。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得膘肥体壮,孳生繁庶。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廷也无力再大规模地经营牧厂了。
西迁的察哈尔蒙古一踏上祖国的西北,就开始一边戍边,一边牧放官牧厂的牲畜,他们同厄鲁特营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畜牧经验和牲畜,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的开发。察哈尔蒙古西迁北疆后,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因此,察哈尔蒙古西迁后“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时,当地田渠皆废,遍地是野草,但他们不畏艰难,在荒原上安家立业,开荒种地,没过两年,“察哈尔二昂吉自去年暂行移驻博罗塔拉以来,农牧皆得其利”。③博尔塔拉属于新疆盆地中西部山地干燥气候区,夏季炎热,降水少,冬季严寒,因此农业用水是河水。察哈尔军民灌溉用水主要是博尔塔拉河。博尔塔拉河是博尔塔拉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252公里,流域面积15928平方公里。博尔塔拉河两岸察哈尔人民基本上在沿河地带耕种农田。
嘉庆年间,松筠(察哈尔部人,后被编入蒙古八旗正蓝旗)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后,很重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博尔塔拉开凿了一条最大的水渠,名为“皇渠”察哈尔蒙古称为“相根布呼”意为“政府出资修的渠”水渠长逾10公里,后不断扩,修。1942年(民国31)长达35,公里,可灌溉13600亩地,。①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察哈尔营的屯田亩数扩大,大营盘(博乐市境)、小营盘、青得里、达勒特等地都成为其屯地,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共屯田3200亩。驻牧于今温泉县的察哈尔营左翼屯田于哈尔布呼、安格里格、查干屯格等地。
1879年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原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领导察哈尔及锡伯军民开挖“哈日布呼”(“黑渠”之意),该渠引入博尔塔拉河水,渠全长约25公里,这是温泉县最早的一条渠道工程。1879年在喀尔莽阿指挥下,蒙古族、锡伯族每户出一个劳动力修建了“夏日布呼”大渠(意为“黄渠”之意),长约10~15公里。
察哈尔营的旗屯收效是很大的,经济的发展又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也增加了。民国初年,察哈尔营人口总数为16023人。②
察哈尔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作为清朝统一新疆后第一批拓荒者,察哈尔军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为清代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屯垦戍边,肩负着驻守卡伦的重任。察哈尔军民驻守祖国西北前哨,昼夜巡卡守边,尽职尽责,最终未使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等地落入侵略者手里。他们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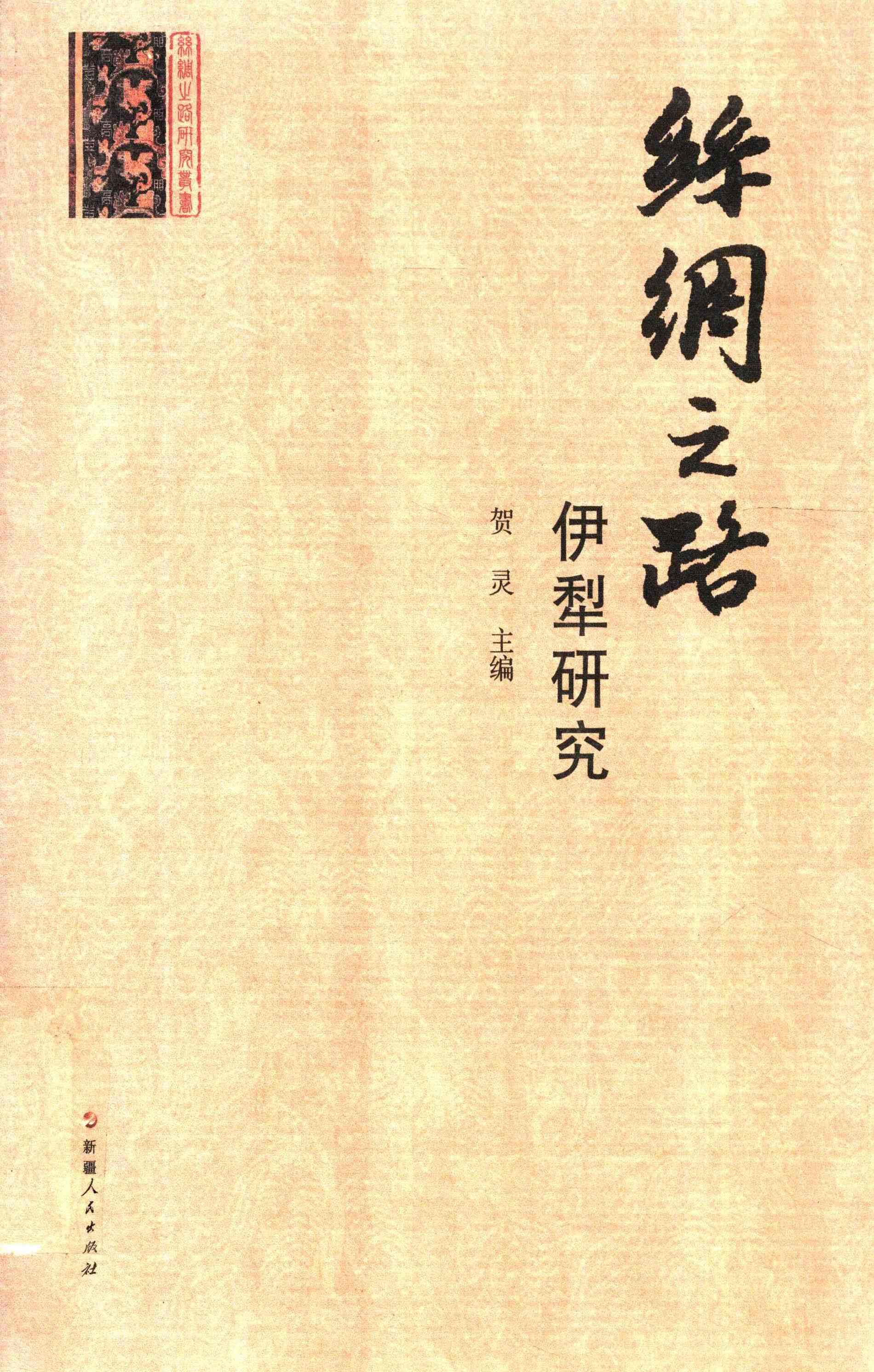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