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伊犁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741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 |
| 分类号: | K294.52 |
| 页数: | 7 |
| 页码: | 46-52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突厥(Turk)是继匈奴之后惊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马背部落新霸主。西魏废帝元年(552)突厥首领土门灭亡了柔然,建号伊利可汗,创立了突厥汗国。传至第三代君木杆可汗在位时期,不仅已完成了统一漠北的大业,而且率众西征,于586~587年间,灭亡了一度称雄中亚的大国■哒。自此,伊犁河东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今中亚七河流域和中国天山北麓地区,都已并入突厥汗国。它的崛起改写了整个北亚和中亚的历史。 |
| 关键词: | 伊犁 魏晋南北 突厥汗国 |
内容
突厥(Turk)是继匈奴之后惊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马背部落新霸主。西魏废帝元年(552)突厥首领土门灭亡了柔然,建号伊利可汗,创立了突厥汗国。传至第三代君木杆可汗在位时期,不仅已完成了统一漠北的大业,而且率众西征,于586~587年间,灭亡了一度称雄中亚的大国■哒。自此,伊犁河东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今中亚七河流域和中国天山北麓地区,都已并入突厥汗国。它的崛起改写了整个北亚和中亚的历史。
历史上的突厥部落有别于比较语言学上的突厥语族。它是以阿史那、阿史德二氏为核心,吸收庞杂的丁零、铁勒部落构成的古代游牧群体。阿史那氏是突厥历代国君所出的部落,阿史德氏则是历代王后所出的部落,发祥于阿尔泰山。突厥的兴起正是以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等部落为基本核心,逐渐融和与征服其周邻同操突厥语的丁零、铁勒部落而日益壮大。其中围绕阿史那氏、阿史德氏周围的核心部落,自称为蓝突厥,以区别于后来采用突厥共名的铁勒部落,这些部落被称为黑民,或作黑突厥,或异姓突厥。他们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突厥汗国建立在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的基础上,大可汗是突厥汗国政治统一体的最高国君,小可汗则相当于诸侯。大可汗先是建牙金山(今阿尔泰山),后来牙庭确定在漠北於都斤山,此外又设立了东面小可汗、北面小可汗和西面小可汗,分统重兵,拱卫四面,其中西面可汗就是曾随木杆可汗西征■哒的室点密可汗,主管葱岭东西、天山南北全部西域之地,伊犁河至碎叶川一带正是这一可汗统辖部落的主要游牧地区。室点密主持西域以后,于568年第一个突厥使臣来到拜占庭,谒见了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沙钵略可汗继任突厥中面大可汗,为了削弱西面可汗达头,在他的原有封疆之内又增置了阿波、贪汗、潘那等三个小可汗,以保持国内的政治平衡。传统的四部分国制度遂进一步演变为七部分国制度,其中仅突厥汗国的西部地区就存在着三个小可汗封地。这时,隋朝建立,不久中原一统,隋开皇二年(582)、开皇三年(583),沙钵略可汗两次征发突厥各小可汗联兵犯隋,都以失败告终。进一步激化了突厥内部大、小可汗间的固有矛盾,爆发了长达二十年的全面内战(开皇三年至仁寿三年,583~603)结果原为统一整体的突厥汗国不复存在,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出现了东突厥,与西突厥汗国两个互不相属、分疆而治的汗国。西突厥汗国并不是突厥汗国的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而是突厥全面内战中西突厥各派势力重新组合定型化的历史产物。西突厥汗国初期,仍然存在着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主要由室点密——达头与木杆—阿波可汗两大汗系及其所属东部咄陆、西部弩失毕等两厢、十姓部落组成。“姓”指小部落,如突骑施、胡禄屋等部,“厢”则指大部落。以伊犁河和碎叶川(今楚河)为界,以东称左厢咄陆诸部,其首领都称“啜”,以西称右厢弩失毕诸部,其首领都称“俟斤”。汗国的前两代国君泥利可汗、泥撅处罗可汗都出自阿波一系,至射匮可汗以后,开始转入统叶护可汗一系。一直传承到西突厥汗国的末代可汗泥伏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其间仅有个别可汗出自阿波汗系。
西突厥汗国建立初期,正当隋唐易代,初期的西突厥可汗同唐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统叶护可汗将可汗牙帐西移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楚河流域的阿克贝希姆遗址)为中心的千泉草原一带。不仅中亚河中粟特诸城邦都被其征服,而且领土扩张到今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今阿富汗)一带,与西亚强国波斯接界,东与建牙漠北的东突厥汗国争雄。唐初名僧玄奘西行求法,途经西突厥国境,翻越葱岭,过热海(今伊塞克湖),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即碎叶城)郊外,会见了统叶护可汗,受到了他的隆重礼遇。记载这位可汗身穿绿绫袍,辫发,坐在豪华的大帐中,帐外驼马不计其数,帐中贵族、达官侍坐,卫士执弓箭刀矛,威仪令人慑。可汗在大帐中举行了招待法师的宴会,席上珍馐杂陈,除酒肉外,还演奏了美妙的龟兹乐,为法师专备了素食,有石蜜、水果和美味的葡萄汁。临行,可汗还给予法师许多金帛资助,派兵护送到印度边境。玄奘西行求法的成功得益于可汗这一资助。统叶护可汗还曾与唐朝缔结了共同反对东突厥的政治同盟,唐朝还许诺了出嫁公主,结为和亲,因受东突厥阻挠,未能成功。其中与唐朝建国初期大体同时的西突厥名君统叶护在位时期进入西突厥汗国的武功盛世。
贞观六年(632)以后继任的西突厥君主如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利失可汗更进一步臣属于唐。只是到了贞观十三年(639)以武力夺取汗位的乙毗可汗(639~642)以后,开始推行反唐政策,导致唐朝开始用兵西域,始创安西都护府于高昌。贞观十六年(642)被推立为国君的乙毗射匮可汗是西突厥少有的出自阿波汗系的可汗,并曾经得到唐朝的册封,但继位后继续推行反唐政策,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648~649)唐朝再次出兵西域,将这一反唐可汗逐至碎叶川以西,占领了龟兹、焉耆,降服了于阗,葱岭以东西域诸国全部并入唐朝版图,基本上实现了新疆地区的政治统一。至高宗继位以后,又平定了原已降唐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以及退居葱岭西的乙毗射匮可汗之子乙毗射匮可汗,实现了西突厥两厢十姓全部归唐的伟业,西突厥汗国亡。
突厥语言在比较语言学谱系上与乌孙截然不同,与柔然同属阿尔泰语系,与铁勒和高车丁零、黠戛斯以及后来的回鹘、葛逻禄、样磨等则同属一个语族。尽管黠戛斯、铁勒、高车等的历史更为古老,但这一语族却是以突厥命名,足以说明这一古代部落影响巨大。
突厥属北方草原全辫发部落,既不同于剪发型的乌孙又不同于前髡后辫的柔然,而与高车、铁勒相同。衣装以毛、皮制品为主,最高级的是黑貂皮、灰鼠皮,次为狐皮,最下为羊皮,即所谓衣服裘褐。不分男女,一律衣开左衽。突厥人卑下对尊上行礼时,都要伏身吮尊上的靴鼻。突厥牧人都是穹庐而居,贵族豪酋则居住豪华大帐,到了西突厥汗国时期,上层贵族已改为城居。
突厥社会等级森严,最高首领称可汗,可汗之妻称可敦,可汗家族成员分别出任叶护、特勤等世袭显爵,王族阿史那氏、后族阿史德氏等居于统治的最高层的世袭贵族,都以蓝突厥自称。这同突厥人敬天拜日,牙帐东开的习俗有关。认为蓝是东方天空的颜色,最为高贵,蔑视黑色,被统治的异姓突厥部落被他们蔑称为黑突厥或黑民。突厥汗国建立后,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包括大、小可汗四部分国制;主要由蓝突厥贵族元老组成的国人会议制,分派吐屯(turtun)监督属国、属部制等,还设有达官一职,并不世袭,主要由粟特人承担,参赞帷幄,处理外交和商务活动。西突厥汗国继承了大、小可汗制度、吐屯、达官制度,新建了两厢、十姓制度,西突厥的叶护、设、特勤等蓝突厥世袭贵族都有统兵权,并册拜重要的异姓突厥首领出任啜、俟斤等本部落首领职务,协助蓝突厥贵族管理事务,从而保证了政治权力机构有效、有序地运行。突厥的军事力量主要以骑射为主的轻装骑兵组成,来去迅疾,战法灵活,是草原上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事力量。突厥人勇于作战,以劫掠为荣,杀一人就立一杀人石,立石越多越好,重战死,耻病终。战争的虏获物一般归自己,包括财物和奴隶。因此,突厥穷富的分野不仅依靠正常畜牧繁衍,而且依靠战争的掠夺物,战利品悉归私有,其中拥有奴隶的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成熟的奴隶制度。牧场公有,不同部落的马群都打上不同的马印,以羊马拥有的多少作为家族财产的标志。婚姻聘礼都以羊马支付。男女相悦为婚,婚前性自由,婚后保证家庭的巩固,法律简单明确,杀人偿命,淫人妻者割势腰斩,淫人女者则只需赔偿羊马。盗马绊者以杀人论处,以保护战马。实行收继婚制度,防止财产外流。突厥贵族间的婚姻则极重门第,蓝突厥绝不同异姓突厥通婚。王族阿史那氏的通婚对象更局限于后族阿史德氏,虽可纳妾,但妾生子女与嫡生后裔身份悬殊。例如作为西突厥两支汗系之一的阿波可汗由于母亲出身低贱,难于继承大统。突厥不像匈奴那样贵壮贱老,而是贵壮尊老,有利于本部文化的传承。早期使用粟特文和汉文作为书面语言,后东突厥汗国创制了突厥儒尼文,但在西突厥境内没有广泛使用。
畜牧业是突厥经济的基础,也存在着发达的手工业。突厥本身就善于冶铁,西突厥属部中还有许多精于手工业的部落、部族,其中粟特人尤为工巧。因此,西突厥的手工艺品不但较匈奴、柔然胜过许多,而且较东突厥也胜过许多。其中金银、玛瑙器皿、珠宝头饰、玻璃工艺、精巧毛织物等有的巧夺天工,尤善于在器皿上镂刻或浮雕动物图案。突厥早就对商业高度重视,其贸易伙伴南与中原,西与波斯,甚至远及东罗马,都有密切的往来。波斯史料中记载了两国间的丝绸贸易谈判,东罗马史料中记载了两国间的遣使,汉文史料中的有关记录更是不胜枚举。已发现的突厥墓葬中不仅有珍贵的毛皮,而且有中亚的器皿,汉地的织锦、丝绸、铜镜、带钩等。东罗马的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汉地的铜币同时在突厥境内通行,说明商品货币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文明发展程度也超过了漠北的同族。
突厥人自己并不从事商业,主要利用属下的粟特人进行经营。突厥人本身并不从事农业,但役使自身的农耕奴隶或治下的农耕民族种植粮食,因而普通突厥人虽仍以肉乳为食,而其贵族却吃肉和吃粮食。突厥人同乌孙一样,传统上喝马奶酒,至西突厥汗国时期,上层贵族更爱喝属部进贡的葡萄酒。
突厥丧礼的隆重更胜于婚礼,反映对人类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突厥实行二次葬法,第一次火葬,第二次土葬,相隔半年,且有嫠面、割耳、立标等特有的风俗。一般死后须停灵,杀羊马致祭,亲属行嫠面礼,就是用刀在脸上割出血来,形成血泪交流大悲大哀效果,割耳礼是划耳流血,剪短辫子也是一种志哀方式。然后择吉日火焚收其余灰,待时而葬。火焚只是丧礼的序曲,其亲属收其骨灰,藏于瓮中,半年后候草木一枯荣始可正式入葬,其思想内涵显然同灵魂的不灭及其再生观念有关。正式葬礼由部落头人主持,部众云集,蔚为盛会。突厥似乎还有人殉的风俗,被杀者主要是敌人。近年来,天山北麓丘陵地带发现了许多石冢墓,其特点是皆须建于较高的台地或丘陵上,墓上围以石块或卵石,奇台县曾发现有这种石冢,墓中并无棺椁,却见到了盛骨灰的陶瓮罐,且这种石冢墓群的分布总是同草原石人同一轨迹,似即突厥人的二次墓葬。
突厥人本来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敬天拜日,牙帐东开,其中日就是天神腾格里的形象化身,还崇拜生育之神乌玛尔,并相信祖先神灵的护佑,相信祖窟崇拜和圣山崇拜,相信火能祛邪。后来,在粟特及其他部落的影响下,也开始尊重佛教。唐朝高僧玄奘贞观初年取道高昌、焉耆、龟兹,而至碎叶,在那里受到了统叶护可汗的接见,给予了良好的款待和礼遇就是证明。但是西突厥贵族本身似乎并不真的崇信,不过是出于政治、文化、商业的实际需要。
史书记载突厥人“敬鬼神,信巫”,信仰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灵魂不灭的原始萨满教,却又不同于其他草原族群的萨满信仰,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1)敬天拜日,牙帐东开。这是由日神、天神崇拜衍变出来的风俗。由于日必出于东方,因而以东方为上。蓝突厥核心部落阿史那氏原来崇拜日神,另一核心部落阿史德氏则崇拜天神,二部世代联姻,形成突厥人以后,天、日合一,两种信仰相互融合,出现了“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的特殊风俗。日为神相,天为神名,天的突厥语名称是tangri,天神具有全智、全能的性质,并作为突厥的保护神出现。突厥儒尼碑文中多次出现对此神的赞颂。可汗则是天的儿子。只有东向跪拜才能瞻仰神的风采,获得神的赐福,这就是为什么突厥人的住所和墓地总是选择高地的缘故。至于在平坦的旷野上举行祭祀须人工营建高台,这一在河畔山上祭拜天神的最盛大节日乃五月八日。(2)乌玛伊生育女神崇拜。乌玛伊似即古阿史德氏始祖传说中的北海女神,射摩舍利之妻,乌玛伊女神既为海神,又是保佑可敦氏族的生育之神,地位仅次于天神Tangri,而凌居于其他诸神之上,享有很高的冥界权威。这正是突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的倒立反映。
(3)祖先崇拜。包括狼祖、狼徽的崇拜,祖先发祥圣山、洞窟的崇拜和家族近祖的崇拜等三项内容。狼在远古传说中是突厥的母系祖先,她是始祖阿史那的妻子,又是伊质泥师都的母亲,因而突厥牙帐前大旗上都饰有金狼头,叫做金狼纛,“盖本狼生,志不忘旧”。突厥人相信祖先灵的存在,他们总是冥冥地默佑自己的子孙,参与人间一切事务,祖先亡灵理想的住宅是高地最好是高山,因为那里较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出现了祭圣山、祭祖窟的习俗。普通平民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拜只能以竿祭的形式表达。将祖先的形象画在皮革或毡片上,系在帐前的木杆上四时祀祭。叫做竿祭。(4)火的崇拜:拜占庭史家狄奥菲拉特《历史》中明确记载:“突厥崇拜火,尊敬空气和水,颂扬大地和水。”突厥人的心目中火是圣洁的,具有吉祥祛邪的净化功能,传说中火不但从严寒中拯救了突厥始祖伊质泥师都,还驱走了外族带来的鬼祟。东罗马使臣进入突厥境,先引导绕火驱邪,才被准许入境。有人据此认为,突厥早期信仰过祆教,其实,突厥人的拜火与祆教徒的拜火异源殊趣,祆教崇拜祭坛上的不熄圣火,其旁且有鸡、犬、山羊等守护动物,突厥人所祭则乃无任何守护动物的穹庐之火,火仅仅是穹庐神或部落神,火神不但保护本部落的现世幸福,而且经过它的净化才可进入冥界。突厥的二次葬风俗就同相信火能驱邪的观念有关,焚尸的含义在于净化灵魂,且不允许单独焚烧躺着的尸体,必须连生平坐骑一起焚化,意味着突厥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依旧是一位勇敢的骑士。(5)萨满教把世界分割为人和亡灵的二重存在,人的死亡被称为“飞去”,只有鹰一类的猛禽才能看到它存在;并有专业巫师从事天人沟通,以羊胛骨进行占卜预言未来;相信人的癫狂境界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汗登基仪式就充满这种神秘氛围。国君坐在众臣共抬的毡座上向日旋转,制造神情瞀乱的境界以占卜神意。古突厥人有自身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认为物质世界由气、土、水、火四种元素构成,这四种元素各有其特有的颜色,所主的方位,其中气为蓝色,主东方,土为黑色,主北方,水为白色,主西方,火为红色,主南方。其中蓝色最尊贵,因为“气”就是“天”的构成元素,气的颜色也就是天的颜色。因此蓝突厥也就是“天”的子孙。从而赋予了这种朴素的四元素物质观以贵贱等级制的社会文化内涵。突厥早期本无文字,主要以汉文及粟特文记事,任命汉人及粟特人掌管文墨。突厥早期的《卜古特碑》就是用粟特文写成的。到了后东突厥汗国时期才出现了突厥儒尼文,出现了这一文字撰的《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翁金碑》等著名碑文,但这一文字在西突厥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西突厥汗国时代这一文字尚未创制,至唐朝册封的西突厥两厢可汗时期通行的文字已是汉文而非突厥儒尼文,直至目前仍未发现这一时期西域蓝突厥贵族撰写的儒尼文献。突厥存在着十二生肖纪年法。这种纪年法同汉土流行的纪年法非常类似,连十二种动物的排列顺序也完全相同,唯“龙”易为“鳄鱼”,《突厥语词典》中记有这一纪年法起源的传说,但该书时代较迟,其说未可视为信史,因为上述十二种动物中鸡、猪等都是罕见于草原而乃作为农耕的汉人惯养家畜,鼠是盛产粮食地区的伴生物,猴在漠北、西域均为稀见而乃生长在关东、关中、江南、巴蜀的茂密山林里,而同草原生活密切联系的动物如狼、鹰、驼、鹿等则一概阙如,可见这一纪年法应是由农耕地区扩散到草原上来的。事实上,汉式纪年法早在两汉时期已颁行于西域,漠北柔然汗国自受罗部真可汗予成以后也已采用汉式年号,突厥初本柔然锻奴,在文化上必然受其影响,至沙钵略可汗降隋以后,隋朝又于开皇六年正月庚午正式“颁历于突厥”进一步证实突厥的十二生肖历是中原汉历的改革和变通,汉历本是天干、地支相互配合,六十年一甲子循环,而突厥历则去其天干,唯留地支,十二年一循环。
关于佛教在突厥中的影响,史书中虽然早就记载从突厥汗国第三代君佗钵可汗时期就已传入漠北大衙,粟特文《卜古特碑》也明确记述asparqaγan发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这位Tasparqaγan显然就是佗钵可汗。西面可汗达头曾接待过天竺名僧波罗颇迦密,多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也曾隆礼善待唐朝高僧玄奘。但佛教教义与突厥的嗜肉好战的传统习俗根本矛盾。从建寺、礼佛的现象看,与其解释为真正的皈依佛门,不如理解为一种政治权术,旨的安抚治下众多信仰佛教的属民。只有远迁吐火罗一带的西突厥人才真正虔信三宝。突厥也有自己的歌舞,则天朝武延秀会唱突厥歌,归降突厥的武周大臣阎知微与突厥人一起在赵州城下联手踏歌《万岁乐》。《万岁乐》全名为《鸟歌万岁乐》,属坐部伎中第四首,特点是戴鸟冠,三人联手踏歌起舞,突厥人敬鹰,鸟冠实即鹰冠,以象征雄鹰猎物,舞姿刚健,是具有示威性的胜利凯旋舞。突厥有丰富的文娱、体育活动项目,赛射是突厥男性的重要比赛活动。分个人赛和集体赛两种形式。集体赛分为两队,个人赛的形式加多样,分射靶的,射走兽,射飞鸟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马球传自波斯,挑选骏马、骑手,亦分二朋,骑手各持击球棒一,飞驰击球,相互争夺,以攻入球门为胜。还有一种传自西域的游戏,介于棋与赌之间,称为“樗蒲”。突厥人早期无文字,主要以汉文及粟特文记事,任命汉人及粟特人掌管文墨,后来,才从后突厥汗国那里学会了儒尼文。
历史上的突厥部落有别于比较语言学上的突厥语族。它是以阿史那、阿史德二氏为核心,吸收庞杂的丁零、铁勒部落构成的古代游牧群体。阿史那氏是突厥历代国君所出的部落,阿史德氏则是历代王后所出的部落,发祥于阿尔泰山。突厥的兴起正是以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等部落为基本核心,逐渐融和与征服其周邻同操突厥语的丁零、铁勒部落而日益壮大。其中围绕阿史那氏、阿史德氏周围的核心部落,自称为蓝突厥,以区别于后来采用突厥共名的铁勒部落,这些部落被称为黑民,或作黑突厥,或异姓突厥。他们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突厥汗国建立在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的基础上,大可汗是突厥汗国政治统一体的最高国君,小可汗则相当于诸侯。大可汗先是建牙金山(今阿尔泰山),后来牙庭确定在漠北於都斤山,此外又设立了东面小可汗、北面小可汗和西面小可汗,分统重兵,拱卫四面,其中西面可汗就是曾随木杆可汗西征■哒的室点密可汗,主管葱岭东西、天山南北全部西域之地,伊犁河至碎叶川一带正是这一可汗统辖部落的主要游牧地区。室点密主持西域以后,于568年第一个突厥使臣来到拜占庭,谒见了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沙钵略可汗继任突厥中面大可汗,为了削弱西面可汗达头,在他的原有封疆之内又增置了阿波、贪汗、潘那等三个小可汗,以保持国内的政治平衡。传统的四部分国制度遂进一步演变为七部分国制度,其中仅突厥汗国的西部地区就存在着三个小可汗封地。这时,隋朝建立,不久中原一统,隋开皇二年(582)、开皇三年(583),沙钵略可汗两次征发突厥各小可汗联兵犯隋,都以失败告终。进一步激化了突厥内部大、小可汗间的固有矛盾,爆发了长达二十年的全面内战(开皇三年至仁寿三年,583~603)结果原为统一整体的突厥汗国不复存在,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出现了东突厥,与西突厥汗国两个互不相属、分疆而治的汗国。西突厥汗国并不是突厥汗国的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而是突厥全面内战中西突厥各派势力重新组合定型化的历史产物。西突厥汗国初期,仍然存在着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主要由室点密——达头与木杆—阿波可汗两大汗系及其所属东部咄陆、西部弩失毕等两厢、十姓部落组成。“姓”指小部落,如突骑施、胡禄屋等部,“厢”则指大部落。以伊犁河和碎叶川(今楚河)为界,以东称左厢咄陆诸部,其首领都称“啜”,以西称右厢弩失毕诸部,其首领都称“俟斤”。汗国的前两代国君泥利可汗、泥撅处罗可汗都出自阿波一系,至射匮可汗以后,开始转入统叶护可汗一系。一直传承到西突厥汗国的末代可汗泥伏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其间仅有个别可汗出自阿波汗系。
西突厥汗国建立初期,正当隋唐易代,初期的西突厥可汗同唐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统叶护可汗将可汗牙帐西移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楚河流域的阿克贝希姆遗址)为中心的千泉草原一带。不仅中亚河中粟特诸城邦都被其征服,而且领土扩张到今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今阿富汗)一带,与西亚强国波斯接界,东与建牙漠北的东突厥汗国争雄。唐初名僧玄奘西行求法,途经西突厥国境,翻越葱岭,过热海(今伊塞克湖),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即碎叶城)郊外,会见了统叶护可汗,受到了他的隆重礼遇。记载这位可汗身穿绿绫袍,辫发,坐在豪华的大帐中,帐外驼马不计其数,帐中贵族、达官侍坐,卫士执弓箭刀矛,威仪令人慑。可汗在大帐中举行了招待法师的宴会,席上珍馐杂陈,除酒肉外,还演奏了美妙的龟兹乐,为法师专备了素食,有石蜜、水果和美味的葡萄汁。临行,可汗还给予法师许多金帛资助,派兵护送到印度边境。玄奘西行求法的成功得益于可汗这一资助。统叶护可汗还曾与唐朝缔结了共同反对东突厥的政治同盟,唐朝还许诺了出嫁公主,结为和亲,因受东突厥阻挠,未能成功。其中与唐朝建国初期大体同时的西突厥名君统叶护在位时期进入西突厥汗国的武功盛世。
贞观六年(632)以后继任的西突厥君主如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利失可汗更进一步臣属于唐。只是到了贞观十三年(639)以武力夺取汗位的乙毗可汗(639~642)以后,开始推行反唐政策,导致唐朝开始用兵西域,始创安西都护府于高昌。贞观十六年(642)被推立为国君的乙毗射匮可汗是西突厥少有的出自阿波汗系的可汗,并曾经得到唐朝的册封,但继位后继续推行反唐政策,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648~649)唐朝再次出兵西域,将这一反唐可汗逐至碎叶川以西,占领了龟兹、焉耆,降服了于阗,葱岭以东西域诸国全部并入唐朝版图,基本上实现了新疆地区的政治统一。至高宗继位以后,又平定了原已降唐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以及退居葱岭西的乙毗射匮可汗之子乙毗射匮可汗,实现了西突厥两厢十姓全部归唐的伟业,西突厥汗国亡。
突厥语言在比较语言学谱系上与乌孙截然不同,与柔然同属阿尔泰语系,与铁勒和高车丁零、黠戛斯以及后来的回鹘、葛逻禄、样磨等则同属一个语族。尽管黠戛斯、铁勒、高车等的历史更为古老,但这一语族却是以突厥命名,足以说明这一古代部落影响巨大。
突厥属北方草原全辫发部落,既不同于剪发型的乌孙又不同于前髡后辫的柔然,而与高车、铁勒相同。衣装以毛、皮制品为主,最高级的是黑貂皮、灰鼠皮,次为狐皮,最下为羊皮,即所谓衣服裘褐。不分男女,一律衣开左衽。突厥人卑下对尊上行礼时,都要伏身吮尊上的靴鼻。突厥牧人都是穹庐而居,贵族豪酋则居住豪华大帐,到了西突厥汗国时期,上层贵族已改为城居。
突厥社会等级森严,最高首领称可汗,可汗之妻称可敦,可汗家族成员分别出任叶护、特勤等世袭显爵,王族阿史那氏、后族阿史德氏等居于统治的最高层的世袭贵族,都以蓝突厥自称。这同突厥人敬天拜日,牙帐东开的习俗有关。认为蓝是东方天空的颜色,最为高贵,蔑视黑色,被统治的异姓突厥部落被他们蔑称为黑突厥或黑民。突厥汗国建立后,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包括大、小可汗四部分国制;主要由蓝突厥贵族元老组成的国人会议制,分派吐屯(turtun)监督属国、属部制等,还设有达官一职,并不世袭,主要由粟特人承担,参赞帷幄,处理外交和商务活动。西突厥汗国继承了大、小可汗制度、吐屯、达官制度,新建了两厢、十姓制度,西突厥的叶护、设、特勤等蓝突厥世袭贵族都有统兵权,并册拜重要的异姓突厥首领出任啜、俟斤等本部落首领职务,协助蓝突厥贵族管理事务,从而保证了政治权力机构有效、有序地运行。突厥的军事力量主要以骑射为主的轻装骑兵组成,来去迅疾,战法灵活,是草原上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事力量。突厥人勇于作战,以劫掠为荣,杀一人就立一杀人石,立石越多越好,重战死,耻病终。战争的虏获物一般归自己,包括财物和奴隶。因此,突厥穷富的分野不仅依靠正常畜牧繁衍,而且依靠战争的掠夺物,战利品悉归私有,其中拥有奴隶的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成熟的奴隶制度。牧场公有,不同部落的马群都打上不同的马印,以羊马拥有的多少作为家族财产的标志。婚姻聘礼都以羊马支付。男女相悦为婚,婚前性自由,婚后保证家庭的巩固,法律简单明确,杀人偿命,淫人妻者割势腰斩,淫人女者则只需赔偿羊马。盗马绊者以杀人论处,以保护战马。实行收继婚制度,防止财产外流。突厥贵族间的婚姻则极重门第,蓝突厥绝不同异姓突厥通婚。王族阿史那氏的通婚对象更局限于后族阿史德氏,虽可纳妾,但妾生子女与嫡生后裔身份悬殊。例如作为西突厥两支汗系之一的阿波可汗由于母亲出身低贱,难于继承大统。突厥不像匈奴那样贵壮贱老,而是贵壮尊老,有利于本部文化的传承。早期使用粟特文和汉文作为书面语言,后东突厥汗国创制了突厥儒尼文,但在西突厥境内没有广泛使用。
畜牧业是突厥经济的基础,也存在着发达的手工业。突厥本身就善于冶铁,西突厥属部中还有许多精于手工业的部落、部族,其中粟特人尤为工巧。因此,西突厥的手工艺品不但较匈奴、柔然胜过许多,而且较东突厥也胜过许多。其中金银、玛瑙器皿、珠宝头饰、玻璃工艺、精巧毛织物等有的巧夺天工,尤善于在器皿上镂刻或浮雕动物图案。突厥早就对商业高度重视,其贸易伙伴南与中原,西与波斯,甚至远及东罗马,都有密切的往来。波斯史料中记载了两国间的丝绸贸易谈判,东罗马史料中记载了两国间的遣使,汉文史料中的有关记录更是不胜枚举。已发现的突厥墓葬中不仅有珍贵的毛皮,而且有中亚的器皿,汉地的织锦、丝绸、铜镜、带钩等。东罗马的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汉地的铜币同时在突厥境内通行,说明商品货币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文明发展程度也超过了漠北的同族。
突厥人自己并不从事商业,主要利用属下的粟特人进行经营。突厥人本身并不从事农业,但役使自身的农耕奴隶或治下的农耕民族种植粮食,因而普通突厥人虽仍以肉乳为食,而其贵族却吃肉和吃粮食。突厥人同乌孙一样,传统上喝马奶酒,至西突厥汗国时期,上层贵族更爱喝属部进贡的葡萄酒。
突厥丧礼的隆重更胜于婚礼,反映对人类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突厥实行二次葬法,第一次火葬,第二次土葬,相隔半年,且有嫠面、割耳、立标等特有的风俗。一般死后须停灵,杀羊马致祭,亲属行嫠面礼,就是用刀在脸上割出血来,形成血泪交流大悲大哀效果,割耳礼是划耳流血,剪短辫子也是一种志哀方式。然后择吉日火焚收其余灰,待时而葬。火焚只是丧礼的序曲,其亲属收其骨灰,藏于瓮中,半年后候草木一枯荣始可正式入葬,其思想内涵显然同灵魂的不灭及其再生观念有关。正式葬礼由部落头人主持,部众云集,蔚为盛会。突厥似乎还有人殉的风俗,被杀者主要是敌人。近年来,天山北麓丘陵地带发现了许多石冢墓,其特点是皆须建于较高的台地或丘陵上,墓上围以石块或卵石,奇台县曾发现有这种石冢,墓中并无棺椁,却见到了盛骨灰的陶瓮罐,且这种石冢墓群的分布总是同草原石人同一轨迹,似即突厥人的二次墓葬。
突厥人本来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敬天拜日,牙帐东开,其中日就是天神腾格里的形象化身,还崇拜生育之神乌玛尔,并相信祖先神灵的护佑,相信祖窟崇拜和圣山崇拜,相信火能祛邪。后来,在粟特及其他部落的影响下,也开始尊重佛教。唐朝高僧玄奘贞观初年取道高昌、焉耆、龟兹,而至碎叶,在那里受到了统叶护可汗的接见,给予了良好的款待和礼遇就是证明。但是西突厥贵族本身似乎并不真的崇信,不过是出于政治、文化、商业的实际需要。
史书记载突厥人“敬鬼神,信巫”,信仰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灵魂不灭的原始萨满教,却又不同于其他草原族群的萨满信仰,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1)敬天拜日,牙帐东开。这是由日神、天神崇拜衍变出来的风俗。由于日必出于东方,因而以东方为上。蓝突厥核心部落阿史那氏原来崇拜日神,另一核心部落阿史德氏则崇拜天神,二部世代联姻,形成突厥人以后,天、日合一,两种信仰相互融合,出现了“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的特殊风俗。日为神相,天为神名,天的突厥语名称是tangri,天神具有全智、全能的性质,并作为突厥的保护神出现。突厥儒尼碑文中多次出现对此神的赞颂。可汗则是天的儿子。只有东向跪拜才能瞻仰神的风采,获得神的赐福,这就是为什么突厥人的住所和墓地总是选择高地的缘故。至于在平坦的旷野上举行祭祀须人工营建高台,这一在河畔山上祭拜天神的最盛大节日乃五月八日。(2)乌玛伊生育女神崇拜。乌玛伊似即古阿史德氏始祖传说中的北海女神,射摩舍利之妻,乌玛伊女神既为海神,又是保佑可敦氏族的生育之神,地位仅次于天神Tangri,而凌居于其他诸神之上,享有很高的冥界权威。这正是突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的倒立反映。
(3)祖先崇拜。包括狼祖、狼徽的崇拜,祖先发祥圣山、洞窟的崇拜和家族近祖的崇拜等三项内容。狼在远古传说中是突厥的母系祖先,她是始祖阿史那的妻子,又是伊质泥师都的母亲,因而突厥牙帐前大旗上都饰有金狼头,叫做金狼纛,“盖本狼生,志不忘旧”。突厥人相信祖先灵的存在,他们总是冥冥地默佑自己的子孙,参与人间一切事务,祖先亡灵理想的住宅是高地最好是高山,因为那里较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出现了祭圣山、祭祖窟的习俗。普通平民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拜只能以竿祭的形式表达。将祖先的形象画在皮革或毡片上,系在帐前的木杆上四时祀祭。叫做竿祭。(4)火的崇拜:拜占庭史家狄奥菲拉特《历史》中明确记载:“突厥崇拜火,尊敬空气和水,颂扬大地和水。”突厥人的心目中火是圣洁的,具有吉祥祛邪的净化功能,传说中火不但从严寒中拯救了突厥始祖伊质泥师都,还驱走了外族带来的鬼祟。东罗马使臣进入突厥境,先引导绕火驱邪,才被准许入境。有人据此认为,突厥早期信仰过祆教,其实,突厥人的拜火与祆教徒的拜火异源殊趣,祆教崇拜祭坛上的不熄圣火,其旁且有鸡、犬、山羊等守护动物,突厥人所祭则乃无任何守护动物的穹庐之火,火仅仅是穹庐神或部落神,火神不但保护本部落的现世幸福,而且经过它的净化才可进入冥界。突厥的二次葬风俗就同相信火能驱邪的观念有关,焚尸的含义在于净化灵魂,且不允许单独焚烧躺着的尸体,必须连生平坐骑一起焚化,意味着突厥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依旧是一位勇敢的骑士。(5)萨满教把世界分割为人和亡灵的二重存在,人的死亡被称为“飞去”,只有鹰一类的猛禽才能看到它存在;并有专业巫师从事天人沟通,以羊胛骨进行占卜预言未来;相信人的癫狂境界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汗登基仪式就充满这种神秘氛围。国君坐在众臣共抬的毡座上向日旋转,制造神情瞀乱的境界以占卜神意。古突厥人有自身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认为物质世界由气、土、水、火四种元素构成,这四种元素各有其特有的颜色,所主的方位,其中气为蓝色,主东方,土为黑色,主北方,水为白色,主西方,火为红色,主南方。其中蓝色最尊贵,因为“气”就是“天”的构成元素,气的颜色也就是天的颜色。因此蓝突厥也就是“天”的子孙。从而赋予了这种朴素的四元素物质观以贵贱等级制的社会文化内涵。突厥早期本无文字,主要以汉文及粟特文记事,任命汉人及粟特人掌管文墨。突厥早期的《卜古特碑》就是用粟特文写成的。到了后东突厥汗国时期才出现了突厥儒尼文,出现了这一文字撰的《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翁金碑》等著名碑文,但这一文字在西突厥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西突厥汗国时代这一文字尚未创制,至唐朝册封的西突厥两厢可汗时期通行的文字已是汉文而非突厥儒尼文,直至目前仍未发现这一时期西域蓝突厥贵族撰写的儒尼文献。突厥存在着十二生肖纪年法。这种纪年法同汉土流行的纪年法非常类似,连十二种动物的排列顺序也完全相同,唯“龙”易为“鳄鱼”,《突厥语词典》中记有这一纪年法起源的传说,但该书时代较迟,其说未可视为信史,因为上述十二种动物中鸡、猪等都是罕见于草原而乃作为农耕的汉人惯养家畜,鼠是盛产粮食地区的伴生物,猴在漠北、西域均为稀见而乃生长在关东、关中、江南、巴蜀的茂密山林里,而同草原生活密切联系的动物如狼、鹰、驼、鹿等则一概阙如,可见这一纪年法应是由农耕地区扩散到草原上来的。事实上,汉式纪年法早在两汉时期已颁行于西域,漠北柔然汗国自受罗部真可汗予成以后也已采用汉式年号,突厥初本柔然锻奴,在文化上必然受其影响,至沙钵略可汗降隋以后,隋朝又于开皇六年正月庚午正式“颁历于突厥”进一步证实突厥的十二生肖历是中原汉历的改革和变通,汉历本是天干、地支相互配合,六十年一甲子循环,而突厥历则去其天干,唯留地支,十二年一循环。
关于佛教在突厥中的影响,史书中虽然早就记载从突厥汗国第三代君佗钵可汗时期就已传入漠北大衙,粟特文《卜古特碑》也明确记述asparqaγan发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这位Tasparqaγan显然就是佗钵可汗。西面可汗达头曾接待过天竺名僧波罗颇迦密,多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也曾隆礼善待唐朝高僧玄奘。但佛教教义与突厥的嗜肉好战的传统习俗根本矛盾。从建寺、礼佛的现象看,与其解释为真正的皈依佛门,不如理解为一种政治权术,旨的安抚治下众多信仰佛教的属民。只有远迁吐火罗一带的西突厥人才真正虔信三宝。突厥也有自己的歌舞,则天朝武延秀会唱突厥歌,归降突厥的武周大臣阎知微与突厥人一起在赵州城下联手踏歌《万岁乐》。《万岁乐》全名为《鸟歌万岁乐》,属坐部伎中第四首,特点是戴鸟冠,三人联手踏歌起舞,突厥人敬鹰,鸟冠实即鹰冠,以象征雄鹰猎物,舞姿刚健,是具有示威性的胜利凯旋舞。突厥有丰富的文娱、体育活动项目,赛射是突厥男性的重要比赛活动。分个人赛和集体赛两种形式。集体赛分为两队,个人赛的形式加多样,分射靶的,射走兽,射飞鸟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马球传自波斯,挑选骏马、骑手,亦分二朋,骑手各持击球棒一,飞驰击球,相互争夺,以攻入球门为胜。还有一种传自西域的游戏,介于棋与赌之间,称为“樗蒲”。突厥人早期无文字,主要以汉文及粟特文记事,任命汉人及粟特人掌管文墨,后来,才从后突厥汗国那里学会了儒尼文。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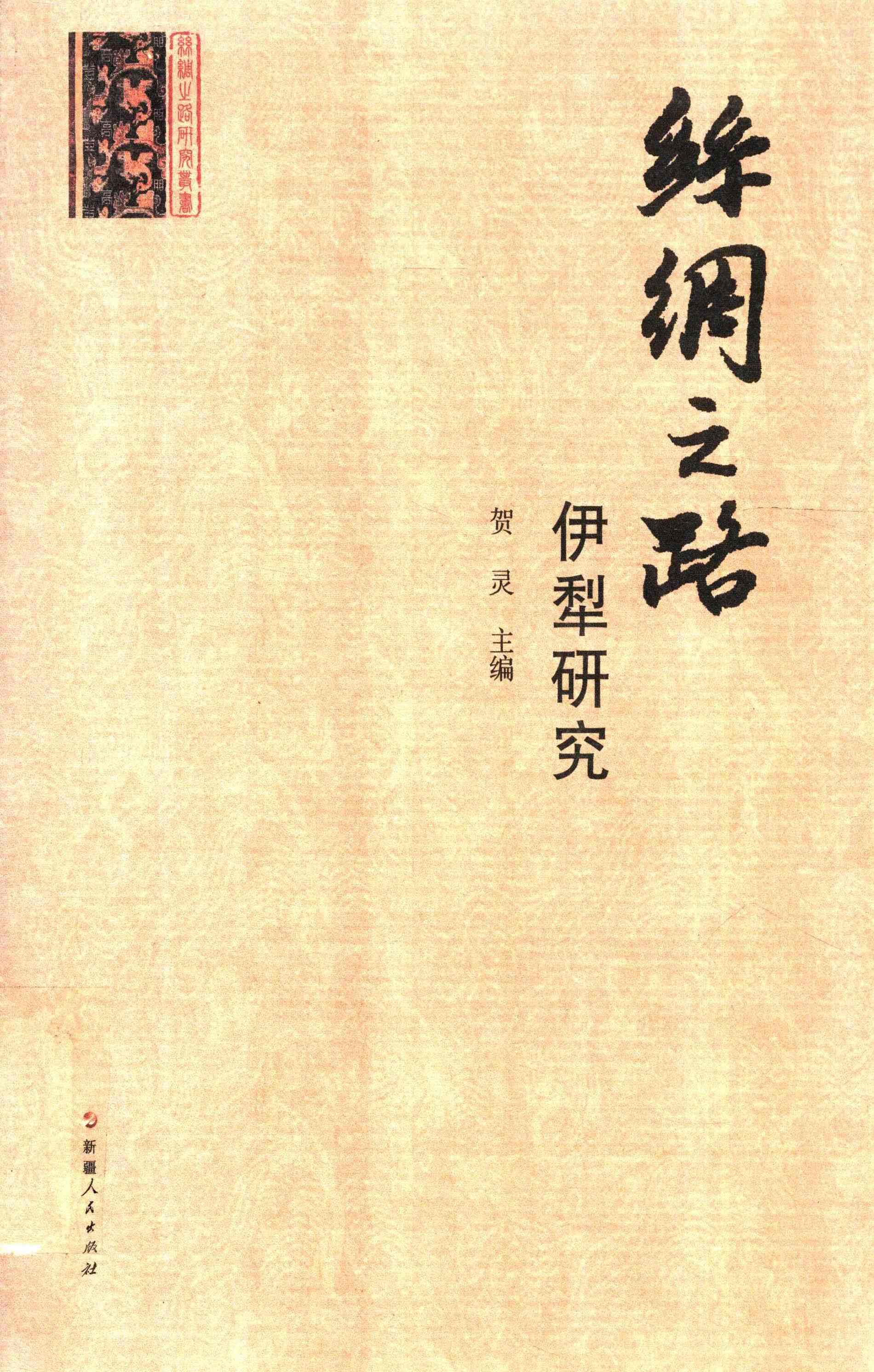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伊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