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北六国及其考古文化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北庭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647 |
| 颗粒名称: | 第二章 山北六国及其考古文化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26 |
| 页码: | 20-45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新疆地区山北六国及其考古文化的情况。 |
| 关键词: | 新疆地区 山北六国 考古文化 |
内容
天山北麓东段,是西域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巴里坤兰州湾子、木垒四道沟、吉木萨尔小西沟就是这一地区古代早期文化的代表。结合历史文献中所记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其雄霸天山北麓东段的时间远远早于以车师为盟主的车师六国,应当就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正是这一部落联盟奏响了天山北麓东段古代历史、文化的迎晨曲。
第一节兰州湾子、四道沟—小西沟文化
天山北麓东段的考古文化以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木垒四道沟遗址和吉木萨尔小西沟遗址为代表。前两个已知最古老的遗址同一渊源,小西沟遗址则是这一文化西播的历史产物。
兰州湾子原始聚落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东段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碳14测定距今约3000年左右。位于巴里坤湖东南的交通要冲地带的花园乡村,南距山根仅数百米。本为高出地表两米左右的两座土丘,相距很近,当地人称为 “鄂博” ①1958年挖土时发现,1984年发掘后发现有 1516米的长方形石围墙和直径约13米,的圆形石围墙,文化层厚约2米左右。出土了各种石器和细砂陶器,石器有有孔石器和石磨。陶色为红、褐和灰红双色,均为加细砂陶,其中褐色陶42块,红陶99件,灰红两色陶31块。能看出的器型为罐及钵。器耳均为宽带耳。有少量圈足底。还出现了上面绘有黑三角形图案的彩陶。出土了环首青铜刀一柄,长16.7厘米,环首,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征。还出土了一种巨型马鞍形磨谷器,长达1米余,遗址的文化层起码在1米以上。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又发现了面积约200平方米石结构居住遗址,分主附两室,室墙用巨石垒砌,残高近2米,厚2米。出土有人骨架17具,证明遗址曾多次居住,最后毁于大火。长期以来,新疆多种考古普查报告中都沿用内地通行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等传统分期法命名新疆古代遗址,根据我在奇台、昌吉等天山北麓从事考古调查的浅薄经验,纯正的石器时代在新疆似乎很少存在,过去命名的所谓石器时代遗址,几乎大都是金石并用时代的早期遗址,兰州湾子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东段最古老的遗址,也是石器与青铜器并存的事实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与此相联系的还有 14号信箱古墓地,位于木垒至哈密七角井的公路西南约 1公里14号信箱的院落内外,故名。古墓葬有十余座,地表封土已破坏,形制分石棺墓和竖穴积石墓两类。石棺木以厚0.06~0.07米的石板围成,棺内人骨散布较乱,属多人二次葬,随葬品有陶片和石珠。竖穴积石墓长170厘米,宽0.13米,尸骨上压有砾石,随葬品有陶罐和骨、铜、红玛瑙、海贝等所制饰件。无疑是天山北麓东段早期金石并用文化的主要代表。
木垒四道沟原始村落遗址的时间上限仅略晚于兰州湾子,碳14测定早期距今约2800年,晚期距今约2400年,位于木垒县城西南30余公里的东城乡四道沟村,过去老地名叫回回槽子。木垒县就是一座山中的县城,境内所有遗址都属于天山北麓坡前谷地。遗址就位于毗邻古河床的一座小丘上,南北狭长,东西南三面紧靠山丘。西距百米有一条干涸的古河床,一条南北向的水渠从遗址附近通过,依山傍水,地势形胜,当时是四道沟大队第二小学所在地,总面积约 1万平方米。 1976年秋,四道沟大队第二小学师生在操场修建跑道时发现许多石器。 1976年 10月和 1977年3月,自治区博物馆两次派人实地调查,发掘工作从 1977年5月起至 7月完成。共开探沟两条、探方 6个,发掘面积 200平方米。清理了 6座古墓葬,出土文物 150余件。发现有灰坑、灶址和柱洞等人类居住遗,由片状卵石砌成,说明已开始 定居,是新疆最早发现的古代村 落遗址 ①分为早、晚二期。早期出 土有石器、陶器、骨器及铜器。石 器80余件,大多是磨制品,有石 球、石锄、石锛、石纺轮、磨谷器、 刮削器、石杵等,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78%,其磨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打制和压制的石器占22%。骨器40余件,有骨针、骨梳、骨纺轮、骨饰件等。其中出土的骨针磨制加工极为精细,针孔透剔,针尖锋利,还出现了仿金属工具制成的三棱形单翼、扁平双翼倒勾形镞,说明骨器制造已达相当水平。陶器40余件,早期多为夹砂细陶,陶色多为赭色和赭红色,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平底钵、浅腹盆等,陶器为手制,有的器内壁留有泥条盘筑 痕迹。质地坚硬,火候较晚期高, 器形规整,陶色多为赭色和赭红 色。器耳为宽带式大耳,有的器 口戳孔,多圜底器。除彩陶外均 为素面,彩陶为黑彩。纹饰有网 纹、菱形纹、弧线和回形纹等,朱彩 纹饰,有垂帐纹、纵横条纹、长短条 纹。器型以圜底双耳罐为主。晚期陶器的陶质多为夹砂粗陶,陶色多褐色或褐红色,出现了单耳陶罐、双耳陶盆等不同的器型。其中一件残高约3厘米的陶狗,张嘴竖耳,似在狂吠,为早期陶器精品,说明四道沟文化时期,狼已被人类驯养为狗,成为狩猎、放牧的主要助手。出土铜器10余件,冶炼技术较高,其中有铜刀、铜笄、铜饰件。
以上出土文物分别属于不同时代遗物。其中石球是天山北麓东段广泛发现,在奇台、吉木萨尔等县都有广泛发现。使用方法是上系革带,围猎时掷出,以落地石球为支点,革带纵横交织,将被围野兽绊倒擒获。石纺轮则是织羊毛的一种工具。马、牛、羊、狗等畜类骨骼残骸与石锄、磨谷器等则已兆示着畜牧业与农业已同时并存,成为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遗址。
在这一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造型精致的石祖,是一种石雕的男根,质料为石英粗砂岩,通长16厘米,根部直径7厘米,顶端有3条竖形尿道,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却是一种精心磨制出来的圣物,反映在社会制上父系家长制的正式确立,这件石祖就是反映父系祖先崇拜的祭祀圣物,全国罕见。2号墓中还发现了十分鲜见的彩绘狩猎纹棺墓,属于晚期遗址。墓主人为老年男性。随葬品有弓、箭、镖、木碗、陶碗、铜、石饰件以及丝织品、皮靴、铁、木等残器物件共二十余件。木棺长2米,棺底、棺盖用长方形框制成,六块刨光木板同棺底、棺盖组成一个完整的木棺,彩绘狩猎图即绘在刨光板上。彩绘主要使用红色颜料,很少用黑色。图中有人物、动物、穹庐、符号等,人物有男有女,有孩子,或坐或立;动物以大角羊和鹿为主,均为奔跑状;画面原始粗犷,用笔简拙,类似岩画,内容是墓主人结婚、育子和正常的游牧生活。木棺底部的六根方衬上,平铺着一层有手指粗细的木棍,木棍上置尸体和随葬品。墓主人是一老年男性,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铁器、铜器、石器、皮制品、丝棉织品等,这是新疆发现的第一座彩绘狩猎纹棺墓。①比较以上兰州湾子一四道沟文化,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是以对钻方式磨制的带孔石器、褐红色陶胎上饰黑彩的圜底彩陶,绘紫红彩的倒三角形纹饰,发达的骨器、石器与特色铜器共存,其中三角纹是一种最常见的母体纹样,具有丰产符号的意义。四道沟遗址的出现反映了兰州湾子文化的向西扩散。它不仅是兰州湾子文化的正统继承,而且是它的成熟发展。
兰州湾子一四道沟文化不可能向东方扩散,向西方扩散则进入奇台、吉木萨尔境内。奇台县金石并用原始遗址有坎儿子、水磨河和半截沟遗址等,所出遗物都兼具游牧、农耕的双重特征,例如坎儿子遗址中具有游牧特征的黑陶圜底罐与大型马鞍形磨谷器共存,水磨河遗址中则围猎工具石球与石纺轮共存,其中半截沟尤具有代表性。位于半截沟乡所在山前地带的不远的一处南北向的土梁上,东侧有一小溪,西侧有一干涸河床,文化层厚约1米①,经发掘,出土石器皆为磨制,有锤斧、石锤,石环,都是中间穿孔,两面对钻,又有敲砸而成的小石臼、小石杵、石球以及金属器等。陶器都是手制夹砂陶,以素面、红褐色为主,灰陶较少;釜、罐类在颈部饰有一圈附加堆纹,其上再按成小窝,个别陶片有一乳突或透穿一小孔,器形主要有双耳釜、罐、盆、钵等,以圜底为主。在陶衣上以深红色或紫色彩描绘出倒三角加网状花纹,与四道沟属于同一文化类型。②在奇台与吉木萨尔两县交界的白杨河东岸,地理坐标:17′北纬43°02″今属奇台东经89°00″48′海拔1210米,县东湾乡白杨河村,面积约5000平方米,位,于山前冲积扇面,的一道西南一东北向的狭长低矮土梁上,西临白杨河。土梁北部已为农户王金全住宅,南为麦场,南端有一座石堆墓,直径约6米,石块多陷没于地。土梁中部东侧因农民挖土而成的剖面上发现了0.3~2米不等厚度的灰层,灰层中有红、灰陶片和牲畜碎骨,曾出土过石器,有石锄、石磨盘、石磨棒、戒石杵等。调查时采集到一些遗物,主要为手制的夹砂陶片,陶色多为红色,部分表红里灰,一些陶片上施夹红衣或有烟黑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绘有紫红彩的彩陶,纹饰虽稍模糊,仍可辨识有X形粗线纹,粗线左右加横点,具有浓厚的四道沟文化特征。又出现了为钻孔锄形器一件,略呈倒梯形状,中间钻孔,背面刃部有使用过的磨擦痕迹,正面刃部大面积的崩残,肩部两面皆崩裂,裂疤较大,残长 14厘米、宽1. 1厘米,最大厚度 4厘米,孔径 3. 9厘米。其中尤以钻孔石器最为突出。
吉木萨尔县境内的金石并用早期遗址,也是发祥于天山北麓的树木蓊郁、水草丰美的山前地带,以今位扼天山南北交通要冲的泉子街一带为中心向外辐射。
主要遗址有小西沟、乱葬岗、刘家槽子、白杨沟等。尤以小西沟遗址最为古老,时间仅次于巴里坤兰州湾子和木垒四道沟。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第三个最为古老的文化发祥地。
吉木萨尔小西沟遗址,当地人俗称贼疙疸梁,东临桦树沟,西临大龙沟支流长山渠,建于天山北坡一个谷间高地上,位于吉木萨尔县城以南 24公里,距泉子街乡西北约5公里,属泉子街镇西北小西沟村地界。地理坐标:东经89°40″48′,海拔1380米,文化层堆积07′北纬43°52″之厚,吉木萨尔境内诸古代遗址罕有其匹,,且有上下之别。早在60年代初,我在奇台中学任教时期就已注意到这座遗址,收集到一座黑陶烧制的陶灯(已遗失)。 1987年我与历史所陈志烈、司机刘同仁一起,专程赴吉木萨尔山前地带,考察了小西沟遗址,发现文化层堆积很厚,是一座十分鲜见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1983年以王炳华为领队的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组途经其地,发表了《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①198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主持了吉木萨尔县的文物普查,县文管所李功仁参加了这次普查。1988年公布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②,进一步肯定了“从现状以及遗物观察,该遗址有两种时间有早晚,文化内涵不同的遗存。其上层似为古城遗址,下层为彩陶与石器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并正式定名为小西沟遗址。 1990年6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地理研究所“西北地区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课题组阚耀平、阎顺二人到此做了详细地层分析,根据采集的孢粉和木炭碎屑,进行了碳 14测定。 1992年公布了考察成果《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③遗址土层
,表层厚约1米,二层为基本文化层(灰烬层与烘烤层),厚约30厘米,有些地点为二层,中间夹5~25厘米的黄土。三层为黄土,厚度 1. 1米。四层为棕黄色黏土,厚度 2米。五层由胶结不好的灰色砾石和砂组成,厚度大于 10米。上层为古城遗址,年代为 2039 ±104年 B、P,相当于西汉;下层为彩陶与金石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年代为2340±80年B、P,时间仅次于兰州湾子、四道沟两座文化遗址,位居第三。①说明该遗址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弃于东汉中期以后,在年代学上对小西沟遗址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小西沟遗址出土文物极为丰富,除当地文物局提供的大量文物之外,2004年冬,2005年初,我又两次赴这座遗址考察,尤以第二次在县委的大力支持和朱丹同志全程陪同下,深入到所在村庄调查访问,收获最巨。②出土物非常丰富,虽然时间上稍晚于巴里坤兰州湾子和木垒四道沟,其历史价值却远远超过了以上两座遗址,是全疆十分罕见的具有长期历史延续性的古代遗址。见《小西沟遗址出土文物表》。
小西沟遗址出土文物表
以上出土物中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种类有石磨、石球、石皿、石杵、石锄等,除石球一种属于围猎工具外,余皆为与农业有关的磨制石器,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其中大型磨谷器一件,长达0.58米,似为新疆已发现的同类磨谷器之最,又有石锄一件、有孔石器一件,都是生产工具,说明小西沟一带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当地居民也是兼用肉食、粮食,早已开始了半定居生活。出土陶器更多,手制、轮制俱全,根据烧制的火候和用料的不同,又出现了较为粗糙、火候不高的灰陶、灰红陶与陶器工艺较为发达的黑陶、红陶的区别,还有少量夹砂彩陶,多为罐类残片,特点是红衣黑彩,彩纹隐约可见几何形线条,这些都属较为早期的陶器,其中有一手制的夹砂灰陶,表面粗糙,口沿见一周小孔,耳坠在内,具有浓烈的木垒四道沟文化特征。器形已从圜底改为平底,已出现了钵、罐、瓮、杯的区别,以鼓腹、敞口、单耳为特征。黑陶的烧制已较为进步,尤以小西沟遗址北出土的一件小型红陶罐最为精致。①出土的石器中除石球一种属于围猎工具外,余皆为与农业有关的磨制石器,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参稽此前发表的有关考古报告,遗址中还出土了马、羊、骆驼等大量兽骨,说明当地居民已是粮食、肉食相兼,除经营农业外,还有发达的畜牧业。陶器工艺手制、轮制俱全,能烧制成黑、灰、青,灰红、红等各种颜色与瓮、罐、杯、盆、钵等各种器型。这些数量众多的陶器,显然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证实了这是一个具有长期延续的遗址。
除小西沟遗址之外,吉木萨尔境重要的金石并用时期原始遗址还有乱葬岗、榆树庄子、上套子沟台地和刘家槽子等古代遗址。
乱葬岗遗址,原定名为乱杂岗。②位于五塘沟口,似应正名为五塘沟口金石并用时期遗址,地理坐标:11′、北纬43°46′23″东经89°36″海拔 1490米。距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东南约4.5公里,公成村西约1公里处的一条,南北向的低矮黄土台地上。已被泉子街镇至公圣村委会的乡村公路横切为二,文化层剖面十分清楚。
1982年附近农民在此挖土又揭露出大面积的包含有陶片、石器、畜骨等遗物的灰层。厚度三五米不等,可粗略分为五层,含有夹砂红、褐色陶片、彩陶片、牲畜残骨、炭粒、白色碳化粉粒、石块、石核、石片等,2005年我与朱丹详细考察了这一遗址,发现不仅有石器,也有金属器,并采集了较为完整的石器数件。所发现的大型马鞍形磨谷器同小西沟遗址形制相似而略小,尚有双向钻孔的环形石器及马鞍形磨谷器等。陶片皆为手制,胎壁较薄,颈部有附加捏纹或链状纹,所烧制的灰红陶,火候不高,非常粗糙,也与小西沟的同类器形相同。地理位置也相距不远,分明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南距乱杂岗约1.5公里就是榆树庄子遗址。这次考察的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在距五塘沟不远的上套子沟河边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遗址,以薄胎彩陶为其文化的突出特点。以上三个遗址都分布在泉子街小西沟至五塘沟一带。
刘家槽子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公里处,二工学校东北刘家槽子北端。现为干涸的河滩,已辟为林带,宽约百米,其上游处河道分为东西二岔,遗址便坐落在二河交叉处的土梁上,遗址南北长约百米,宽20~30米不等,地表文化层石砾遍地,有石磨盘、磨棒残片和一些粗砂红、褐陶片和塌陷的灰坑。遗址西南对岸台地上也有粗砂质褐色陶片分布。此处距山前地带较远,应属小西沟古文化的远缘辐射范围。
吉木萨尔以西,虽然仍有散见金石共用时代遗址分布,但相对较少,且文化特征已属另一体系(例如阿拉沟)。可见天山北麓东段的古代文化最早发祥于巴里坤、木垒一带,后来逐渐向西扩散,吉木萨尔古文化代之而兴,成为这一地区古代文化的新兴中心。从巴里坤兰州湾子、木垒四道沟到吉木萨尔小西沟出土文物具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诸如大型磨谷器的出现反映早期农业的出现,大量畜骨说明家畜驯化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陶器烧制方法,尤其是粗红陶、灰红陶器具有惊人相似性,以单耳陶器为其共有器形,以及石器与青铜器的共存等,说明上述地区大体是在同一文化的覆盖之下,虽然仍存在着地方性的文化差别。
第二节山北六国及其盟主蒲类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解读洪荒之谜的双轨车,只有这两条通道完全并轨之后谜底才能破译。
西域进入信史时代的历史开端应溯源于张骞凿空和汉西域都护府的创立。在此之前,虽然西域早已升起文明的曙光,由于尚未创造文字,其历史面貌仍是一片混沌。汉开西域之后,才留下了翔实可信的文献记载。其中天山北麓东段出现了“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长期以来,这两个颇为近似的名称常被混淆,由此出现了总是将车师人视为东部天山最古老居民的历史误导。其实,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山北六国”之名出自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总序,所记录的应当是西汉史事,乃至更为古远的历史追溯;“车师六国”之名,则亘西汉王朝无闻,至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才首次出现。可见二者出现的时间不同,其中山北六国在先,车师六国在后。《圣武记》的作者清人魏源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至陶葆廉著《辛卯侍行记》已明确表态“车师六国与前汉所称山北六国不同”;岑仲勉也赞同这一结论①,却对车师前、后部是否包容在山北六国名单之中,仍有所犹豫;当代学者孟凡人认识更前进了一步,确定无疑地断言“西汉时期的‘山北六国’不包括车师前后王国”,但却将其主要区别界定为山北六国乃以地域为标准,车师六国则是以族属为标准。②在正确认识车师六国出现的时间是东汉的同时,却将山北六国出现的时间误断为西汉宣帝时期,仍未能找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仅就这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中就可发现,其涵盖的内容也完全不同。山北六国明确界定这一部落联盟的存在地域局限于天山北麓,而车师六国中的车师前部的居地并非山北,而是山南的吐鲁番盆地,其外延早已从“山北”进一步扩展至整个东部天山。可见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实乃前、后更代的不同时期、不同盟主领导的不同部落联盟。天山北麓东段最古老的居民绝非车师六国,而是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
令人困惑的是,《汉书·西域传》总序中虽然提出了“山北六国”之名,却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名单,而在其传文中所叙的国名却并非六国,而乃以下十国:即蒲类国、蒲类后国、卑陆前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乌贪訾离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劫国。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
蒲类后国,王治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
卑陆前国,王治天山东乾当谷,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
对此,我的理解是,西汉所记录的山北六国作为存在于天山北麓东段部落联盟名称其上限应更早于西汉初年,直至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的宣帝时期仍存,所反映的应是上起战国,下至西汉末年的漫长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匈奴西扩、西域归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一山北部落联盟必随之发生了复杂分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则由六国到十国乃是历史演变过程不断分化的结果。如果将它们重新合并,则汉初天山北麓的政治地图上,就会明确地出现蒲类、卑陆、郁立师、单桓、劫、且弥等六个清晰的国名,或部落名。这就是山北六国的原生形态,它们就是汉开西域之前,天山北麓东段原始的土著居民。
山北六国有大有小,强弱各异,而以后来被一分为三的蒲类显然最为强大。据此可知,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都是历史上存在的部落联盟名称,早在匈奴和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之前就已存在,而以蒲类为盟主。《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即“蒲类本大国也”。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谓。而进入东汉时期,蒲类已衰,可见其享有西域大国地位一段文字必为追溯时在西汉时期、乃至时间更早。同书又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可知蒲类人骁勇善战,拥有较高的文明,曾是西域大国。西域国名众多,而在史书上以大国相称者除汉与匈奴、乌孙、康居之外,为数无几。如《汉书·西域传》中列入大国名单者仅限于罽宾、乌弋山离、安息、莎车、于阗,名列《后汉书 ·西域传》中的大国仅有高附、东
离、蒲类等三国,以上诸国皆为拥众十余万,幅员千余里的强部,连疏勒、龟兹这样的城邦都不够“大国”的资格,独称蒲类是大国,可见在匈奴、汉朝相继进入西域之前,蒲类的赫赫声势。
蒲类,本为海名,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北麓东段,汉初属匈奴,《后汉书》卷77,注引《汉书音义》:“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我国汉、魏时期史书中所载方位常有所欹斜,“敦煌北”应指敦煌西北,今巴里坤湖正在这一位置。①《汉西域图考》云:“自奇台(指今老奇台)而东三十里,入山五百六十里,至肋巴泉塘,山势始开,又东二百六十里而复合,山环如城,中为巨浸,今为巴尔库淖尔,即古之蒲类海也。”此海在清宜禾县(今巴里坤县)北,道光钦定《新疆识略》记宜禾县“南为天山,即古祁连山,北为巴尔库淖尔,即古蒲类”。《新疆建置志》则称,巴里坤即蒲类之音译,其是巴里乃蒲类的对音,海之突厥语本为kul,蒙古人不明其原义,音译为坤,因于巴里坤后又后缀以“淖尔”(湖),转译为汉语时亦作巴里坤湖,以语言学角度言之,皆属多余。可知蒲类因蒲类海得名,必发祥于今巴里坤一带,与兰州湾子遗址所在位置完全相符。至《汉书·西域传》中,蒲类的牙庭已不在巴里坤,而是“天山西疏榆谷”了。天山是横断山脉,哪里来的“天山西”呢②,可见此处的天山,必指天山的支脉,说明移居天山西的蒲类国已迁至今木垒县境内,与今四道沟地望相符。与史书中所记“天山西疏榆谷”若相符契。很可能四道沟就是蒲类牙庭疏榆故址。唐代的榆慕谷似即这个“天山西疏榆谷”的千古遗音。③以此判断,蒲类的活动中心就在今巴里坤至木垒一带,古老的兰州湾子—四道沟文化应当就是蒲类人创造的。
蒲类之外,山北六国中还包括郁立师、卑陆、劫、单桓、且弥诸国,其相对位置比较清楚。可以参照古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大致可以确定其具体地望。其中郁立师在蒲类西、卑陆东,相当于今之奇台县,半截沟遗址似即此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内咄谷故址。其东境一直延伸到与吉木萨尔接境的白杨沟遗址。
卑陆国位置在郁立师国西,其政治中心绝非分化后位居“天山东”的卑陆前国,而应是位在卑陆后国牙庭番渠类谷,《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蒲类后国“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说明卑陆后国东接郁立师,西接劫国,松田寿男根据《汉书·西域传》所记里数推算,“大概卑陆国的西部,构成了靠近乌鲁木齐的别部,它被称为卑陆后国。”可见卑陆国的东界似应在今阜康县,西界已进入米泉县。卑陆人大约与蒲类人同族,其文化的诞生时间仅亚于蒲类。在车师后部到来之前今吉木萨尔县境的山北六国故部有所空缺,只是到了宣帝时期才出
现了有关金附国的记载,以此判断,金附国大约早就属于山北六国部落联盟之一。
劫国①,唐代丝路北道有俱六守捉之名,在今阜康县境,似即“劫”的古代遗音。以此判断,劫国所治天山东丹渠谷的位置应在今阜康县的山前地带。学术界早已公认,《汉书·西域传》中的方位有所倾斜,所谓“天山东”应指博格达峰东北,以此判断,丹渠谷的具体地望必在今天池东。其西则为单桓、且弥二国。
且弥,与唐代的处密同音,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唐之处密似存在东、西两支,东支活跃于凭洛水西,即今阜康、米泉、昌吉一带。西支已远在伊犁河流域,汉之且弥亦已分为东、西两支,其西支与乌孙接,至少已到达玛纳斯、呼图壁一带,其东支尚在单桓东,亦即阜康境内,但那里并未发现有价值的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原始遗址,发现的只是大批石堆墓和石棺墓,难以找到对应的遗址。
单桓是山北六国中唯一以城堡为牙庭的部族,位于东且弥西与西且弥东,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古代城堡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市东沟、阿拉沟水域,诸如东沟乡的东河坝西岸的破城子、苇子村烂城子和阿拉沟大桥一带发现的石建筑遗存。②后者更具有考古文化特色,也许这些石建筑在汉人看来就属于定居 “城堡 ”的一种,以此判断,阿拉沟大桥一带的古代石建筑遗存就是单桓城的所在地。
第三节岩画中的塞人图像
作为西域大国、山北六国盟主的蒲类人何以在天山北麓诸族中最先崛起,究竟出自什么人种?操何系语言?山中岩画大量图像和中外文献资料对我们的认识有所启迪。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天山北麓各地的岩画逐渐被发现并显现出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东起巴里坤、木垒西至呼图壁一带的天山北麓东段岩画明显多于以西岩画,且一律分布于北坡山前地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著名的岩画点有巴里坤的冰沟、塔勒德巴斯陶、八墙子、石人子乡、兰州湾子、大黑沟、阔克加尔;伊吾县的阔如勒、伊吾镇、大白杨沟;木垒县的芦塘沟、鸡心梁、旱沟、东地、水磨沟;吉木萨尔县的松树沟、甘沟塘;米泉县的独山子;阜康市的三工河、吉沿坚;昌吉市的阿什里;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阔克霍拉;玛纳斯县的沙拉乔克、苏鲁萨依等地,正属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故境。这些岩画虽然不能通过碳14测定,进行准确的时间断代,却具有众多的共同性。(1)从岩石的敲击方法和作画方法判断,绝大多数已使用了金属器。说明是金石并用时代的产物。(2)动物题材在岩画中居于压倒一切的数量优势。见于岩画的动物种类有羊、野马、野牛、野鹿、马鹿、野骆驼、熊、狼、狐狸、蛇,已经灭绝的新疆虎、鹰和狗,几乎食草、食肉、爬行、飞禽类动物无所不有。虽然绝大多数都是野生,但狗和骑者、羊圈画面的出现则已说明畜牧业已同狩猎业开始共存,同已知的兰州湾子一四道沟考古文化发现相一致。(3)人的图像资料虽然远较动物为少,但却鲜明地反映了当地居民的体质形态特征及其社会、精神活动,成为探讨天山北麓东段自然生态和古人生产、生活的重要图像资料,弥足珍贵。
在山北六国盟主蒲类发祥地的巴里坤、木垒,岩画开凿最多,而且多鸿篇巨制。兰州湾子岩画使用了凿刻、磨刻或凿磨兼施等技术。大都刻在平整砾石上,仅少数刻于岩壁。绘有行猎图12幅,包括单人猎、围猎、骑猎,使用的狩猎工具有弓箭、投枪、棒槌、绳索。猎画已开始与野生动物画平分秋色。①还有骑者图5幅,其中1幅长300厘米,高140厘米,刻有许多奔走的戴帽骑者,旁有鹿、大角羊等动物。说明蒲类人已开始驯化野马。巴里坤东北38公里的八墙子岩画画面多,群体画面尤多,且有文化重叠现象,时间延续最长,开始出现了狗,成为人类不可分离的伙伴。巴里坤大红柳峡东南小加山南麓塔勒德巴斯陶岩画共有数十幅,内容也大体相似。伊吾县吐葫芦乡大白杨沟村外山丘东壁岩画数十幅,集中凿刻在高3米、长约15米的岩壁上。所绘骑马者画面,昂首疾驰,形象极为生动,所骑的马很可能是正在驯服的野马。伊吾县盐池乡的热孜布拉克岩画分布在西、南山坡的花岗岩上。共有画面十余幅,内容除了狩猎、狼吃羊等画面以外,也出现了骑者的生动形象。在奇台北塔山阿艾提沟的野马岩画②绘于宽2.6米、高2.2米的一座红色峭壁上,壁上密集绘制有近20匹马的图像③,最大的一匹马宽60厘米,高4.4厘米,其中13匹马都为东向,独有一人骑在马上,西向而立,马无鞍,跃然欲立,人屈两臂,状若套马,马长17厘米,高20厘米,人高12厘米,宽15厘米,跃然欲活,其余野马,也情态各异,这种野马似乎就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沙俄探险家格鲁木尔的野马。由此推测,蒲类人之所以成为山北六国盟主,同率先驯服天山北麓野马有关。
羊的驯化为家畜和狼崽被驯化为狗,乃是考古学上重大事件。这在山北六国故境的天山北麓东段岩画中也有明确反映。这一地区羊的种类纷繁,包括大角山羊、盘羊、羚羊等。尤以大角羊数量最多,几乎每幅岩画都少不了它,为人类广泛放牧的肉用羊,应当就是这种大角羊驯化而来。木垒照壁乡学房村东的平顶山旱沟狩猎岩画中除了生动地雕刻出狩猎者张弓射箭的场面以外,其身旁还出现了蹲立的狗,似在待命出击,同四道沟出土的陶狗形象相似。
吉木萨尔的松树沟岩画地属大有乡广泉子村,共3幅。其中最重要的一幅刻于约70米一峭立的岩石上,上方为一骑马、牵马图。骑者头戴尖顶帽,一手持缰,一手叉腰,牵马者位于马头前,身体前倾,双腿一弓一蹬,反映社会已发生了身份分化。下方绘有羊的画面(图30),又绘有一有开口的圆圈,内有一有角动物,似为羊圈(图31),门前还绘有一无角动物,略带夸张,造型生动,似乎是狗。说明已进入畜牧社会。甘沟塘岩画位于泉子街镇北不远的山上,在松树沟之东,岩画共有3幅①(图32、图33),皆镌刻在散置的三块大岩石上,没有人物,阴雕浅刻,具有强烈的夸张色彩,刻画工具似为金属,说明是金石并用时期的遗物。其一形象漫漶不明,另一上绘大角羊,相当生动,最重要的一幅上绘大角鹿,一鹿角桠纷披,十分夸张。阜康市吉沿坚岩画位于天池东南约 18公里吉沿坚沟的台地砾石上。第一块
砾石上由30余只北山羊、两个人物、一头鹿、两条牧犬、一条狼组成一个画面:恶狼正袭击羊群,一男子张弓作欲射状;另一个人双臂张开,身体前倾,作驱赶状。第二块砾石画面侵蚀严重,仅数羊形象可辨。明显属于畜牧时代的岩画。岩画雕刻简洁,虽难以准确地反映当时人类的面貌特征,却几乎所有可以辨认的人物图像大都头戴尖顶帽,例如巴里坤兰州湾子岩画总有骑者图5幅,其中1幅长300厘米,高140厘米,就刻有头戴尖顶帽的骑者。巴里坤冰沟岩画中的一幅胯下为一倒置北山羊的狩猎图,骑者也似乎头戴这种帽子,伊吾镇岩画中清楚地绘有一位骑大山羊的猎者,头戴尖顶帽,前述吉木萨尔松树沟第四组岩画中的骑者也是头戴尖顶帽,学术界公认尖顶帽正是印欧人种的塞人的重要特征。奇台县西地乡发现的一具石雕人头像,明显具有印欧人种的体质特征,尤为最具说服力的雄辩物证。
塞人,又作塞种,《汉书》中多次提及这一古代族群,如卷96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鋥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同书卷97又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说明张骞初通西域时,塞人曾广泛分布于中亚内陆。“塞”字,即希腊文中之Sacae、古波斯语Saka的音译。乃古代中亚大族,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多次提到这一古族,记其分化为拥有不同名称的若干分支,如Smilian、Massagetae、Scythia①等。Smilian今译多作“西密利安人”,我以为应即《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访问过的“西膜”部落。这部出自晋汲郡古冢的先秦古籍详细记载了周穆王此次以联羌制戎为战略目标的西巡,周初诸王世与姜姓联姻,姜即羌,很可能兼通羌语,其沿途所访赤乌、曹奴、容成、甄韩、西王母、寿余、诸干、重罋、巨蒐诸国,都是直接交谈,惟访问西膜时乃以译语人为语言中介,说明西膜语言异于西域诸羌。可见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有一支塞人进入今新疆境内。在《历史》中Scythia与Massagetae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地域,却明确指出了
①说明二者同族。而同书又记:“波斯人是把所有的Scythia人都称为Sacae。”兆示着这些名称都是塞人的不同支脉。有学者研究,Massagetae可分解为Ma与Ssagetae两部分,该词的词头“Ma”在塞语中有大的涵义,词干部分的Ssagetae=Sacetae=Sacae,具有大塞种部落的涵义,为塞人中的主部。同书又记: “Massagetae(原译玛撒该塔伊人)据伊赛多涅斯人相对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 Scythia的一个族群。”Massagetae人穿着和Scythia相同的衣服,同样的生活方式;拥有骑兵、步兵、弓兵和矛兵,更有使用战斧的习惯。波斯王大流士贝希斯敦纪功碑铭文上塞人也分三支:SakaHaumavarga,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的叶子的Saka人;SakaTyaiytaradraya意为海那边或河那边的Saka人;SakaTigra~hauda,意为戴尖帽子的Saka人。其中戴尖帽子的塞人SakaTigrahauda尤同希罗多德所记Massagetae存在着众多共同点。大流士铭文记载SakaTigrahauda“住在海的那边,戴高高的尖顶帽”希罗多德:《历史》64节记:“属于Scythia人的Sacae(原译撒卡依人)人戴着一种高,帽子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的Scythia(原译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Sacae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Scythia(斯奇提亚)人都称为Sacae的。”②贝希斯敦铭文上方浮雕中表现的被俘的塞人,波斯波利斯浮雕中描写的向阿赫明尼德王朝朝贡的塞人,牵骆驼的巴克特里亚人以及南俄库尔奥巴(刻赤)和沃罗涅日发现的金银合金瓶画中的斯基泰人(Scythia)都是戴着护盖两耳的尖顶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综辑以上汉文、希腊文和波斯文献,所记塞人的共同特征都是戴尖顶帽的族群。1983年8月,在新源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件青铜塞人武士俑,造型端庄英俊,呈蹲跪姿,通高42厘米,空心,重4公斤,头戴尖顶带弯钩状圆帽,面目丰满,二目前视,双手环握执物。上身裸露,腰间围系着遮身物,赤足,两腿一跪一蹲③,女性帽上饰翎羽两支;面颊修长,大眼、高鼻、小嘴、长项、细腰、肥臀、隆胸、修腿,男子则大嘴、有髭,面部轮廓粗犷,康家石门子墓地中发现有骨器、天然金箔、直径约0.05米铜镜,以及妇女头上戴的银装饰物品,也印证是一处塞人墓。说明在匈奴和汉人相继到来之前,从巴里坤到呼图壁这一广阔地区古代居民就是印欧人种的塞人,而不是蒙古利亚种或混血型人种。具有高鼻、深目、多鬚的体质特征,戴尖顶高帽的塞人。蒲类的种族归属也应当属于塞人中的一个小分支。蒲类二字④复原古音,“蒲”为滂纽(P)虞韵(iu),类为来纽(1),灰(uai)、队(ai)二韵,上古虞入,鱼韵(a),灰、队皆入支韵(,e)蒲类的上古音值应读为“pali”,这一音读与中古波斯语中的pari一词完全相同,意,为仙女、美丽。⑤如果这一解读不错,那么,蒲类海的塞语本义就是美
丽的湖,仙女湖。进一步演变为蒲类人的族名自称。
麦高文在其名著《中亚古国史》①中强调塞人最大的贡献是骑射用于战争。《左传》中也印证虽然漠北的狄人早就习惯于骑马放牧,但在战争中却是“彼徒我车”,作战时仍是徒步对抗华夏人的战车,弓箭虽然早就用以狩猎,但大规模作战中却并未出现专业的弓箭手,塞人组建了专业的弓兵,引起了一场军事技术的革命。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当赵武灵王(前325~298年)时始模仿北方的蛮人,改采胡服骑射..我们从此不难看出此时北方的蛮人已经起了怎样大的变化,两世纪以前他们还是徒步生活,徒步作战的;其主要的攻击武器也许还是用剑而不用矢,那时他们有没有靴和裤,也还是一个疑问,但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却要从北方的蛮人传习‘胡服骑射’了。”②据此可知,匈奴的骑射之术也是渊源于塞人。希罗多德还记载,Massagagetae人“不播种任何种子”,逐水草,营游牧,食畜肉,习骑射,歃血为盟,以人头为饮器③,这些都对后世匈奴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节 匈奴与山北六国的衰落
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崛起及其西域霸权的确立,根本动摇了蒲类在山北诸国盟主的地位,至公元前2世纪的汉开西域时,蒲类已四分五裂,“西域大国 ”早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追溯。
匈奴是最先雄霸漠北、西域的草原游牧强族。“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扆(骆驼)驴、■、、騨。”④凭借这一雄厚的驯畜资源,建立了一支以骑射为主,兵牧合一的强大武装。早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期就已崛兴,以单于为王称,以阏氏为后妃之称,历代单于都出自王族挛鞮氏,太子常封为左屠耆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诸小王及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各级官员,“皆世官”。⑤秦朝统一中国前夕,多次出现于史册:周慎靓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周赧王四年(前311)又出现了“匈奴驱驰于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之下”⑥的记载。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遂筑长城,修驰道,遣将“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余里”。⑦在秦军的强大打击下,匈奴一度转衰,头曼单于在位时期,“东胡强而月氏盛”,被迫向东胡和月氏等两大强国各送质子,著名匈奴雄主冒顿单于就曾入质于月氏,后来逃回本国,以鸣镝训练部曲,射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①此岁正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太子扶苏被杀,“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国势逐渐复苏。但仍以甘言厚贡麻痹当时的漠北霸主东胡,任其来索千里马,美女,悉以奉贡,至汉高祖元年(冒顿单于四年)又诱其来索牧地瓯脱,故意激成众怒,及士气激奋,始率众出征,下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后汉书》卷90记东胡自为冒顿所破,“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此后又向月氏复仇,杀其王,迫使月氏举族西迁,匈奴大漠南北霸主的地位遂正式形成。《资治通鉴》记此役未提及匈奴,似应以《史记》记载为准。②汉高祖元年(前206,冒顿单于四年)灭东胡,以挛鞮氏为核心,吸收呼衍氏、须卜氏、兰氏诸大姓,正式创立了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河西、河曲诸小王纷纷加入了这一部落联盟,成为下属的异姓王。
匈奴的复兴正当楚汉相争的秦末乱世,不仅“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③,而且不断南侵汉边。汉高祖六年(冒顿单于九年,前201)汉军主力正与项羽楚军相峙,委韩王信守边。当年秋,匈奴围马邑,汉兵无力驰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兵逼晋阳。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十年,前200)高祖刘邦亲统大军北征,被围于白登,七日不食,迫使汉朝委曲求和,以美女、丝帛,无偿地奉献给匈奴,以换取边疆地区的苟安。并为吕后、文、景诸帝历代遵循,垂为定制。
冒顿单于在位长达36年,在此期间,汉与匈奴虽然名为“和亲”,实际上边境掠夺连年不断,图谋不轨的诸藩王也都密与通使,倚为后盾。文帝六年(前174)老上单于继立,英武骁悍不亚于冒顿,当年遣其右贤王统兵西征,迫使已经迁居西域的宿敌月氏再一次远徙妫水,致书吕后,声称:“以天之福..灭夷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④以上西域二十六国必定包括蒲类等山北六国在内,这是匈奴西域霸权正式确立的历史标志。委其二异姓王分治西域东、西,其中日逐王居西,“”建牙于 焉耆、危须、尉黎间 ⑤;呼衍王居东,建牙于“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⑥,将一切属国都视为奴隶,向各国都派出了僮仆校尉,即管理奴隶的官员,职能是向派出国征收贡物和监其国政。 “赋
税诸国,取富给焉。”①相当于后来突厥的吐屯、西辽的监国少师,清代的都统。有人认为匈奴的僮仆都尉似乎是类似于汉西域都护府那样的组织,有一个名为僮仆都尉府的建置存在。其实,匈奴统领西域的最高首领主要是呼衍王和日逐王,“僮仆都尉”只是此二王下辖分遣诸部的基层官员。
匈奴西域霸权的确立标志着蒲类山北盟主地位的动摇。在匈奴西征过程中,曾为西域大国和山北六国盟主的蒲类不可能不率众组织抵抗,必以失败告终,遭受重创,自此一衰不振。蒲类海本是蒲类国的发祥地,今已成为匈奴呼衍王的牙庭,蒲类牙庭被迫西徙天山西疏榆谷(今木垒四道沟)。蒲类的大国地位不利于匈奴的西域统治,分而治之是削弱这一大国的有效手段,在这一政策催化下,原来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蒲类统一体被肢解为若干小国。分化为蒲类国、蒲类后国、乌贪訾离国等三国。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2032人,荷戈壮男 799人;蒲类后国,拥众 1070人;又有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拥众 1700人,“元帝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则乌贪訾离也是蒲类中的一支,这三支蒲类人口加在一起,仍有 4802人,复据《后汉书 ·西域传》匈奴还曾 “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种种迹象表明,匈奴对蒲类的分化、肢解政策早已进行,至汉开西域之后,由于蒲类受制于匈奴呼衍王,又受到汉军的重击,这一历史进程更为加速。本始二年(前72)分遣五将军伐匈奴,“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 ”其中赵充国引人注目地领有“”
②,蒲类将军 名号,说明其主攻方向是蒲类海,“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 ”。③另遣 “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④东西夹击,斩获极众。可见此役遭受汉军打击的不仅是匈奴,蒲类也是其打击对象。此外,《后汉书》还出现了一个移支国名,记其 “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抄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无论从地域,还是风俗,这个移支国显然都是改换了国名的蒲类人。自此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落、部族联盟也面临解体的危机。蒲类衰落之后,匈奴与汉朝激烈争夺的对象转移到原居盐泽至吐鲁番盆地一带的车师。地节二年(前68)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在渠犁屯田的汉将郑吉捕捉这一有利时机,率领食饱财足、斗志旺盛的屯田将士,进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
复发兵攻车师王于丰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①。这座石城的位置在交河城北,不一定是天山之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石城即兜訾城。②车师腹背受敌,被迫降汉。郑吉遂开始在吐鲁番、鄯善一带经营屯田。“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③姑师、车师所居一直是吐鲁番盆地,不闻前、后部之别,至是始车师二王并立,这是车师分化为二王的历史开端。至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汉之后,郑吉乘胜率兵反攻车师,护送亲汉的车师王军宿还封交河,亲匈奴的车师王乌贵率众避迁天山北麓,车师前、后二部的分化更为定型化。车师后王徙居天山北麓,全力投倚匈奴,车师前部王则在汉军的全面控制之下。至前、后汉交替之际,在北匈奴的全力支持下,车师后王不仅成为车师二部的共主,而且取代了蒲类昔日的地位,成为天山北麓诸部及车师前部的共同盟主,自此,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部落、部族联盟正式形成。“山北六国”之名开始在史册中完全沉没。
在山北六国中卑陆是仅次于蒲类的天山北麓东段第二大国,这个曾经创立过辉煌小西沟文化的重要部族,至迟西汉宣帝时期似已离开了泉子街故牙,小西沟遗址的主人似已成为小金附国的牙庭。这个小金附国名既不见于山北六国名单,也不是车师六国的成员,其活动唯一见于史册乃地节二年(前68),其古音遗脉却自汉金蒲、唐金满,清济木萨传承至今,留待后论。
匈奴西域霸权确立同时又是匈奴加入西域多元族群行列的过程。主要居地也是天山北麓东段,虽然数量远较当地土著族群为少。
匈奴在野生动物驯化家畜方面的历史贡献极为突出。在匈奴经营的畜牧业中,不但有羊、马等后世为突厥、回鹘所继承的主畜之外,畜类品种之多,尤引人注目。不但举凡骆驼、驴、牛等被后世突厥等所称的“杂畜”一应俱全,还利用杂交技术培育出了“骡子”这一耐苦、耐长途行走的新畜种,用以拉车,以驼渡碛,以羊为食,为衣,以马为出征、畜牧的坐骑。其中马的培育尤为成功。平城之围中匈奴骑兵以毛色为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骆马(赤黄色)”④。令汉人惊骇,亦足反映匈奴各种毛色马的众多。单于招降汉使苏武时以整座山谷中的牛羊相许,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大将军卫青取“河南地”,获匈奴牛羊约百万头。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出高击败匈奴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万。①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单于,获其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②足以反映作为匈奴经济基础的游牧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狩猎已降为畜牧业的补充和骑射训练的一种手段。
前苏联学者在南西伯利亚匈奴墓的发掘和上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对漠南匈奴故境的考古调查、发掘,共同证实了匈奴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足以同汉朝抗衡。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后期匈奴墓出土的王冠由冠饰和饰带两部分组成,全为黄金打造,顶上立一展翅雄鹰,鹰头为绿宝石琢制③,极为精美。铁器已成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体。匈奴最有特色的兵器有鸣镝和径路,鸣镝即响箭,径路即马刀,诺颜山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发现的数百座匈奴墓葬中出土了这类铁制兵器,并发现了公元前2~公元1世纪时期的铁模、炼铁炉和铁渣,从而证实了《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和《东观汉记·邓遵传》所记邓遵缴获匈奴匕首三千、釜镬两千的真实性。出土的青铜制品中虽仍有少量铜镞、铜刀等武器,但更多的发现则乃铜针、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铃、铜环、铜马等生活用具④,以及带有野兽纹的铜饰件。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窟子⑤,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⑥都有类似的发现,透露出强烈的塞人文化影响。所发现的铜镜、铜鼎则显然是汉文化的影响。陶器乃日常生活的主要器皿,《汉书·苏武传》记单于弟於靬王赐武马畜、服匿、穹庐。其中服匿就是陶缶。其形如罂,小口,大腹,方底,用以装酒与乳浆。很有特色,曾传至南齐。匈奴善于“冶作弓矢”,出土了制造工艺相当复杂的合成弓,射程和穿透力都超过汉军。《汉书》卷94,记匈奴“车以材木为之,”“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⑦具有坚固耐用的特点。这种匈奴车在杨雄《长杨赋》中别记为轒輼。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汉军在常山、中山连败南单于,获此类穹庐及轒輼车多达千余辆。顺帝阳嘉三年(,134)在车师附近的阊吾陆谷汉军又大获匈奴车千余辆。⑧
匈奴衣皮革,被毡裘,《淮南子·齐俗训》记匈奴发式为“纵体施发”,陕西沣西客省庄匈奴墓出土的长方形透雕铜饰牌,画面上的两个人物皆披发。⑨可见“施发”就是披发。制革和毛纺织业似已成为家家精通的副业,出现了“匈奴出秽裘”⑩和“罽帐”11的记载,诺颜山苏珠克图山口的六号墓出土的毡毯上还绣制出牛、马、鹿头形和野兽互相搏斗画面。①匈奴服饰特征以左开衽、穿胡裤、穿革靴为特征。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匈奴官吏当户跪擎铜灯的铜俑,特征就是短衣直襟左衽,手有臂鞲,脚着长靴。②诺颜乌拉大型墓出土的匈奴服装都是用当地细毛线缝制而成,领、袖、下摆均镶边,做工十分精细。帽子为尖顶或椭圆形,带护耳,内蒙古的匈奴墓葬中还发现过铜制的小型甲片。
松田寿男据《汉书·常惠传》中以下一段文字:“是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认为匈奴也像汉朝一样在车师经营屯田。据我判断,“田车师”一句实同于“畋车师”,“畋”字的意思乃是狩猎,与耕田、屯田毫无关系。虽然史书上明确记载匈奴国中也有农业生产,《史记 ·卫青传》记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卫青军至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储存的大量粟米。《汉书 ·匈奴传》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秋,匈奴地区因为连续下雨数月,“谷稼不熟”。漠北匈奴墓葬中确已发现公元前3~前2世纪的“黑色的农作物种子”。③匈奴盛行奴隶制,连年犯边所掠汉人,都沦为匈奴奴隶。这些以黍米为特征的农作物显然是被掠至匈奴的汉人奴隶生产的。
匈奴信仰万物有灵的巫教,祭拜天地、日月星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④一年三集会,正月、五月、九月戊日为其集会时间,正月集会单于庭,举行祠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最为隆重。茏城,一作龙城⑤,非城堡名,似为神庙名。秋九月,大会蹛林,除重视外,还要进行人畜数字的核实工作。并有专业巫师,主持人神沟通和预
卜吉凶。《汉书·西域传》记:“匈奴使巫埋牛羊于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见使巫祝之。”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燕支山击败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重约 20斤,这就是匈奴人崇拜的偶像之一。 “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⑥
匈奴自身原无文字,自从中行说入匈奴,参赞帷幄以来,就一直使用汉文作为书面符号,出现了一批以汉文写成的匈奴文书。如汉惠帝三年(前 192)冒顿单于羞辱吕后书及征和四年(前89)匈奴狐鹿姑单于致书武帝书都直抒胸臆,无废言赘语,以直白为特色。如狐鹿姑书云: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匈奴语言风格非常明显。东汉时期还出现
了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密遣郭衡呈匈奴地图于汉使事件,说明匈奴国中还有汉人代绘的地图。①
匈奴有自身的乐器胡笳、鞞鼓。据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所记:“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胡笳为管鸣性的吹奏乐器,鞞鼓则乃膜鸣性的打击乐器。此外,匈奴还盛行“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②,陕西长安汉上林苑一座匈奴墓葬出土的两块长方形的透雕花纹铜牌上还存有摔跤场面。③在首领宴会中还有 “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 ”④的记载。
第一节兰州湾子、四道沟—小西沟文化
天山北麓东段的考古文化以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木垒四道沟遗址和吉木萨尔小西沟遗址为代表。前两个已知最古老的遗址同一渊源,小西沟遗址则是这一文化西播的历史产物。
兰州湾子原始聚落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东段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碳14测定距今约3000年左右。位于巴里坤湖东南的交通要冲地带的花园乡村,南距山根仅数百米。本为高出地表两米左右的两座土丘,相距很近,当地人称为 “鄂博” ①1958年挖土时发现,1984年发掘后发现有 1516米的长方形石围墙和直径约13米,的圆形石围墙,文化层厚约2米左右。出土了各种石器和细砂陶器,石器有有孔石器和石磨。陶色为红、褐和灰红双色,均为加细砂陶,其中褐色陶42块,红陶99件,灰红两色陶31块。能看出的器型为罐及钵。器耳均为宽带耳。有少量圈足底。还出现了上面绘有黑三角形图案的彩陶。出土了环首青铜刀一柄,长16.7厘米,环首,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征。还出土了一种巨型马鞍形磨谷器,长达1米余,遗址的文化层起码在1米以上。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又发现了面积约200平方米石结构居住遗址,分主附两室,室墙用巨石垒砌,残高近2米,厚2米。出土有人骨架17具,证明遗址曾多次居住,最后毁于大火。长期以来,新疆多种考古普查报告中都沿用内地通行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等传统分期法命名新疆古代遗址,根据我在奇台、昌吉等天山北麓从事考古调查的浅薄经验,纯正的石器时代在新疆似乎很少存在,过去命名的所谓石器时代遗址,几乎大都是金石并用时代的早期遗址,兰州湾子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东段最古老的遗址,也是石器与青铜器并存的事实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与此相联系的还有 14号信箱古墓地,位于木垒至哈密七角井的公路西南约 1公里14号信箱的院落内外,故名。古墓葬有十余座,地表封土已破坏,形制分石棺墓和竖穴积石墓两类。石棺木以厚0.06~0.07米的石板围成,棺内人骨散布较乱,属多人二次葬,随葬品有陶片和石珠。竖穴积石墓长170厘米,宽0.13米,尸骨上压有砾石,随葬品有陶罐和骨、铜、红玛瑙、海贝等所制饰件。无疑是天山北麓东段早期金石并用文化的主要代表。
木垒四道沟原始村落遗址的时间上限仅略晚于兰州湾子,碳14测定早期距今约2800年,晚期距今约2400年,位于木垒县城西南30余公里的东城乡四道沟村,过去老地名叫回回槽子。木垒县就是一座山中的县城,境内所有遗址都属于天山北麓坡前谷地。遗址就位于毗邻古河床的一座小丘上,南北狭长,东西南三面紧靠山丘。西距百米有一条干涸的古河床,一条南北向的水渠从遗址附近通过,依山傍水,地势形胜,当时是四道沟大队第二小学所在地,总面积约 1万平方米。 1976年秋,四道沟大队第二小学师生在操场修建跑道时发现许多石器。 1976年 10月和 1977年3月,自治区博物馆两次派人实地调查,发掘工作从 1977年5月起至 7月完成。共开探沟两条、探方 6个,发掘面积 200平方米。清理了 6座古墓葬,出土文物 150余件。发现有灰坑、灶址和柱洞等人类居住遗,由片状卵石砌成,说明已开始 定居,是新疆最早发现的古代村 落遗址 ①分为早、晚二期。早期出 土有石器、陶器、骨器及铜器。石 器80余件,大多是磨制品,有石 球、石锄、石锛、石纺轮、磨谷器、 刮削器、石杵等,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78%,其磨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打制和压制的石器占22%。骨器40余件,有骨针、骨梳、骨纺轮、骨饰件等。其中出土的骨针磨制加工极为精细,针孔透剔,针尖锋利,还出现了仿金属工具制成的三棱形单翼、扁平双翼倒勾形镞,说明骨器制造已达相当水平。陶器40余件,早期多为夹砂细陶,陶色多为赭色和赭红色,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平底钵、浅腹盆等,陶器为手制,有的器内壁留有泥条盘筑 痕迹。质地坚硬,火候较晚期高, 器形规整,陶色多为赭色和赭红 色。器耳为宽带式大耳,有的器 口戳孔,多圜底器。除彩陶外均 为素面,彩陶为黑彩。纹饰有网 纹、菱形纹、弧线和回形纹等,朱彩 纹饰,有垂帐纹、纵横条纹、长短条 纹。器型以圜底双耳罐为主。晚期陶器的陶质多为夹砂粗陶,陶色多褐色或褐红色,出现了单耳陶罐、双耳陶盆等不同的器型。其中一件残高约3厘米的陶狗,张嘴竖耳,似在狂吠,为早期陶器精品,说明四道沟文化时期,狼已被人类驯养为狗,成为狩猎、放牧的主要助手。出土铜器10余件,冶炼技术较高,其中有铜刀、铜笄、铜饰件。
以上出土文物分别属于不同时代遗物。其中石球是天山北麓东段广泛发现,在奇台、吉木萨尔等县都有广泛发现。使用方法是上系革带,围猎时掷出,以落地石球为支点,革带纵横交织,将被围野兽绊倒擒获。石纺轮则是织羊毛的一种工具。马、牛、羊、狗等畜类骨骼残骸与石锄、磨谷器等则已兆示着畜牧业与农业已同时并存,成为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遗址。
在这一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造型精致的石祖,是一种石雕的男根,质料为石英粗砂岩,通长16厘米,根部直径7厘米,顶端有3条竖形尿道,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却是一种精心磨制出来的圣物,反映在社会制上父系家长制的正式确立,这件石祖就是反映父系祖先崇拜的祭祀圣物,全国罕见。2号墓中还发现了十分鲜见的彩绘狩猎纹棺墓,属于晚期遗址。墓主人为老年男性。随葬品有弓、箭、镖、木碗、陶碗、铜、石饰件以及丝织品、皮靴、铁、木等残器物件共二十余件。木棺长2米,棺底、棺盖用长方形框制成,六块刨光木板同棺底、棺盖组成一个完整的木棺,彩绘狩猎图即绘在刨光板上。彩绘主要使用红色颜料,很少用黑色。图中有人物、动物、穹庐、符号等,人物有男有女,有孩子,或坐或立;动物以大角羊和鹿为主,均为奔跑状;画面原始粗犷,用笔简拙,类似岩画,内容是墓主人结婚、育子和正常的游牧生活。木棺底部的六根方衬上,平铺着一层有手指粗细的木棍,木棍上置尸体和随葬品。墓主人是一老年男性,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铁器、铜器、石器、皮制品、丝棉织品等,这是新疆发现的第一座彩绘狩猎纹棺墓。①比较以上兰州湾子一四道沟文化,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是以对钻方式磨制的带孔石器、褐红色陶胎上饰黑彩的圜底彩陶,绘紫红彩的倒三角形纹饰,发达的骨器、石器与特色铜器共存,其中三角纹是一种最常见的母体纹样,具有丰产符号的意义。四道沟遗址的出现反映了兰州湾子文化的向西扩散。它不仅是兰州湾子文化的正统继承,而且是它的成熟发展。
兰州湾子一四道沟文化不可能向东方扩散,向西方扩散则进入奇台、吉木萨尔境内。奇台县金石并用原始遗址有坎儿子、水磨河和半截沟遗址等,所出遗物都兼具游牧、农耕的双重特征,例如坎儿子遗址中具有游牧特征的黑陶圜底罐与大型马鞍形磨谷器共存,水磨河遗址中则围猎工具石球与石纺轮共存,其中半截沟尤具有代表性。位于半截沟乡所在山前地带的不远的一处南北向的土梁上,东侧有一小溪,西侧有一干涸河床,文化层厚约1米①,经发掘,出土石器皆为磨制,有锤斧、石锤,石环,都是中间穿孔,两面对钻,又有敲砸而成的小石臼、小石杵、石球以及金属器等。陶器都是手制夹砂陶,以素面、红褐色为主,灰陶较少;釜、罐类在颈部饰有一圈附加堆纹,其上再按成小窝,个别陶片有一乳突或透穿一小孔,器形主要有双耳釜、罐、盆、钵等,以圜底为主。在陶衣上以深红色或紫色彩描绘出倒三角加网状花纹,与四道沟属于同一文化类型。②在奇台与吉木萨尔两县交界的白杨河东岸,地理坐标:17′北纬43°02″今属奇台东经89°00″48′海拔1210米,县东湾乡白杨河村,面积约5000平方米,位,于山前冲积扇面,的一道西南一东北向的狭长低矮土梁上,西临白杨河。土梁北部已为农户王金全住宅,南为麦场,南端有一座石堆墓,直径约6米,石块多陷没于地。土梁中部东侧因农民挖土而成的剖面上发现了0.3~2米不等厚度的灰层,灰层中有红、灰陶片和牲畜碎骨,曾出土过石器,有石锄、石磨盘、石磨棒、戒石杵等。调查时采集到一些遗物,主要为手制的夹砂陶片,陶色多为红色,部分表红里灰,一些陶片上施夹红衣或有烟黑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绘有紫红彩的彩陶,纹饰虽稍模糊,仍可辨识有X形粗线纹,粗线左右加横点,具有浓厚的四道沟文化特征。又出现了为钻孔锄形器一件,略呈倒梯形状,中间钻孔,背面刃部有使用过的磨擦痕迹,正面刃部大面积的崩残,肩部两面皆崩裂,裂疤较大,残长 14厘米、宽1. 1厘米,最大厚度 4厘米,孔径 3. 9厘米。其中尤以钻孔石器最为突出。
吉木萨尔县境内的金石并用早期遗址,也是发祥于天山北麓的树木蓊郁、水草丰美的山前地带,以今位扼天山南北交通要冲的泉子街一带为中心向外辐射。
主要遗址有小西沟、乱葬岗、刘家槽子、白杨沟等。尤以小西沟遗址最为古老,时间仅次于巴里坤兰州湾子和木垒四道沟。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第三个最为古老的文化发祥地。
吉木萨尔小西沟遗址,当地人俗称贼疙疸梁,东临桦树沟,西临大龙沟支流长山渠,建于天山北坡一个谷间高地上,位于吉木萨尔县城以南 24公里,距泉子街乡西北约5公里,属泉子街镇西北小西沟村地界。地理坐标:东经89°40″48′,海拔1380米,文化层堆积07′北纬43°52″之厚,吉木萨尔境内诸古代遗址罕有其匹,,且有上下之别。早在60年代初,我在奇台中学任教时期就已注意到这座遗址,收集到一座黑陶烧制的陶灯(已遗失)。 1987年我与历史所陈志烈、司机刘同仁一起,专程赴吉木萨尔山前地带,考察了小西沟遗址,发现文化层堆积很厚,是一座十分鲜见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1983年以王炳华为领队的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组途经其地,发表了《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①198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主持了吉木萨尔县的文物普查,县文管所李功仁参加了这次普查。1988年公布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②,进一步肯定了“从现状以及遗物观察,该遗址有两种时间有早晚,文化内涵不同的遗存。其上层似为古城遗址,下层为彩陶与石器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并正式定名为小西沟遗址。 1990年6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地理研究所“西北地区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课题组阚耀平、阎顺二人到此做了详细地层分析,根据采集的孢粉和木炭碎屑,进行了碳 14测定。 1992年公布了考察成果《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③遗址土层
,表层厚约1米,二层为基本文化层(灰烬层与烘烤层),厚约30厘米,有些地点为二层,中间夹5~25厘米的黄土。三层为黄土,厚度 1. 1米。四层为棕黄色黏土,厚度 2米。五层由胶结不好的灰色砾石和砂组成,厚度大于 10米。上层为古城遗址,年代为 2039 ±104年 B、P,相当于西汉;下层为彩陶与金石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年代为2340±80年B、P,时间仅次于兰州湾子、四道沟两座文化遗址,位居第三。①说明该遗址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弃于东汉中期以后,在年代学上对小西沟遗址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小西沟遗址出土文物极为丰富,除当地文物局提供的大量文物之外,2004年冬,2005年初,我又两次赴这座遗址考察,尤以第二次在县委的大力支持和朱丹同志全程陪同下,深入到所在村庄调查访问,收获最巨。②出土物非常丰富,虽然时间上稍晚于巴里坤兰州湾子和木垒四道沟,其历史价值却远远超过了以上两座遗址,是全疆十分罕见的具有长期历史延续性的古代遗址。见《小西沟遗址出土文物表》。
小西沟遗址出土文物表
以上出土物中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种类有石磨、石球、石皿、石杵、石锄等,除石球一种属于围猎工具外,余皆为与农业有关的磨制石器,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其中大型磨谷器一件,长达0.58米,似为新疆已发现的同类磨谷器之最,又有石锄一件、有孔石器一件,都是生产工具,说明小西沟一带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当地居民也是兼用肉食、粮食,早已开始了半定居生活。出土陶器更多,手制、轮制俱全,根据烧制的火候和用料的不同,又出现了较为粗糙、火候不高的灰陶、灰红陶与陶器工艺较为发达的黑陶、红陶的区别,还有少量夹砂彩陶,多为罐类残片,特点是红衣黑彩,彩纹隐约可见几何形线条,这些都属较为早期的陶器,其中有一手制的夹砂灰陶,表面粗糙,口沿见一周小孔,耳坠在内,具有浓烈的木垒四道沟文化特征。器形已从圜底改为平底,已出现了钵、罐、瓮、杯的区别,以鼓腹、敞口、单耳为特征。黑陶的烧制已较为进步,尤以小西沟遗址北出土的一件小型红陶罐最为精致。①出土的石器中除石球一种属于围猎工具外,余皆为与农业有关的磨制石器,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参稽此前发表的有关考古报告,遗址中还出土了马、羊、骆驼等大量兽骨,说明当地居民已是粮食、肉食相兼,除经营农业外,还有发达的畜牧业。陶器工艺手制、轮制俱全,能烧制成黑、灰、青,灰红、红等各种颜色与瓮、罐、杯、盆、钵等各种器型。这些数量众多的陶器,显然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证实了这是一个具有长期延续的遗址。
除小西沟遗址之外,吉木萨尔境重要的金石并用时期原始遗址还有乱葬岗、榆树庄子、上套子沟台地和刘家槽子等古代遗址。
乱葬岗遗址,原定名为乱杂岗。②位于五塘沟口,似应正名为五塘沟口金石并用时期遗址,地理坐标:11′、北纬43°46′23″东经89°36″海拔 1490米。距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东南约4.5公里,公成村西约1公里处的一条,南北向的低矮黄土台地上。已被泉子街镇至公圣村委会的乡村公路横切为二,文化层剖面十分清楚。
1982年附近农民在此挖土又揭露出大面积的包含有陶片、石器、畜骨等遗物的灰层。厚度三五米不等,可粗略分为五层,含有夹砂红、褐色陶片、彩陶片、牲畜残骨、炭粒、白色碳化粉粒、石块、石核、石片等,2005年我与朱丹详细考察了这一遗址,发现不仅有石器,也有金属器,并采集了较为完整的石器数件。所发现的大型马鞍形磨谷器同小西沟遗址形制相似而略小,尚有双向钻孔的环形石器及马鞍形磨谷器等。陶片皆为手制,胎壁较薄,颈部有附加捏纹或链状纹,所烧制的灰红陶,火候不高,非常粗糙,也与小西沟的同类器形相同。地理位置也相距不远,分明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南距乱杂岗约1.5公里就是榆树庄子遗址。这次考察的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在距五塘沟不远的上套子沟河边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遗址,以薄胎彩陶为其文化的突出特点。以上三个遗址都分布在泉子街小西沟至五塘沟一带。
刘家槽子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公里处,二工学校东北刘家槽子北端。现为干涸的河滩,已辟为林带,宽约百米,其上游处河道分为东西二岔,遗址便坐落在二河交叉处的土梁上,遗址南北长约百米,宽20~30米不等,地表文化层石砾遍地,有石磨盘、磨棒残片和一些粗砂红、褐陶片和塌陷的灰坑。遗址西南对岸台地上也有粗砂质褐色陶片分布。此处距山前地带较远,应属小西沟古文化的远缘辐射范围。
吉木萨尔以西,虽然仍有散见金石共用时代遗址分布,但相对较少,且文化特征已属另一体系(例如阿拉沟)。可见天山北麓东段的古代文化最早发祥于巴里坤、木垒一带,后来逐渐向西扩散,吉木萨尔古文化代之而兴,成为这一地区古代文化的新兴中心。从巴里坤兰州湾子、木垒四道沟到吉木萨尔小西沟出土文物具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诸如大型磨谷器的出现反映早期农业的出现,大量畜骨说明家畜驯化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陶器烧制方法,尤其是粗红陶、灰红陶器具有惊人相似性,以单耳陶器为其共有器形,以及石器与青铜器的共存等,说明上述地区大体是在同一文化的覆盖之下,虽然仍存在着地方性的文化差别。
第二节山北六国及其盟主蒲类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解读洪荒之谜的双轨车,只有这两条通道完全并轨之后谜底才能破译。
西域进入信史时代的历史开端应溯源于张骞凿空和汉西域都护府的创立。在此之前,虽然西域早已升起文明的曙光,由于尚未创造文字,其历史面貌仍是一片混沌。汉开西域之后,才留下了翔实可信的文献记载。其中天山北麓东段出现了“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长期以来,这两个颇为近似的名称常被混淆,由此出现了总是将车师人视为东部天山最古老居民的历史误导。其实,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山北六国”之名出自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总序,所记录的应当是西汉史事,乃至更为古远的历史追溯;“车师六国”之名,则亘西汉王朝无闻,至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才首次出现。可见二者出现的时间不同,其中山北六国在先,车师六国在后。《圣武记》的作者清人魏源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至陶葆廉著《辛卯侍行记》已明确表态“车师六国与前汉所称山北六国不同”;岑仲勉也赞同这一结论①,却对车师前、后部是否包容在山北六国名单之中,仍有所犹豫;当代学者孟凡人认识更前进了一步,确定无疑地断言“西汉时期的‘山北六国’不包括车师前后王国”,但却将其主要区别界定为山北六国乃以地域为标准,车师六国则是以族属为标准。②在正确认识车师六国出现的时间是东汉的同时,却将山北六国出现的时间误断为西汉宣帝时期,仍未能找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仅就这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中就可发现,其涵盖的内容也完全不同。山北六国明确界定这一部落联盟的存在地域局限于天山北麓,而车师六国中的车师前部的居地并非山北,而是山南的吐鲁番盆地,其外延早已从“山北”进一步扩展至整个东部天山。可见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实乃前、后更代的不同时期、不同盟主领导的不同部落联盟。天山北麓东段最古老的居民绝非车师六国,而是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
令人困惑的是,《汉书·西域传》总序中虽然提出了“山北六国”之名,却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名单,而在其传文中所叙的国名却并非六国,而乃以下十国:即蒲类国、蒲类后国、卑陆前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乌贪訾离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劫国。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
蒲类后国,王治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
卑陆前国,王治天山东乾当谷,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
对此,我的理解是,西汉所记录的山北六国作为存在于天山北麓东段部落联盟名称其上限应更早于西汉初年,直至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的宣帝时期仍存,所反映的应是上起战国,下至西汉末年的漫长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匈奴西扩、西域归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一山北部落联盟必随之发生了复杂分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则由六国到十国乃是历史演变过程不断分化的结果。如果将它们重新合并,则汉初天山北麓的政治地图上,就会明确地出现蒲类、卑陆、郁立师、单桓、劫、且弥等六个清晰的国名,或部落名。这就是山北六国的原生形态,它们就是汉开西域之前,天山北麓东段原始的土著居民。
山北六国有大有小,强弱各异,而以后来被一分为三的蒲类显然最为强大。据此可知,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都是历史上存在的部落联盟名称,早在匈奴和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之前就已存在,而以蒲类为盟主。《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即“蒲类本大国也”。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谓。而进入东汉时期,蒲类已衰,可见其享有西域大国地位一段文字必为追溯时在西汉时期、乃至时间更早。同书又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可知蒲类人骁勇善战,拥有较高的文明,曾是西域大国。西域国名众多,而在史书上以大国相称者除汉与匈奴、乌孙、康居之外,为数无几。如《汉书·西域传》中列入大国名单者仅限于罽宾、乌弋山离、安息、莎车、于阗,名列《后汉书 ·西域传》中的大国仅有高附、东
离、蒲类等三国,以上诸国皆为拥众十余万,幅员千余里的强部,连疏勒、龟兹这样的城邦都不够“大国”的资格,独称蒲类是大国,可见在匈奴、汉朝相继进入西域之前,蒲类的赫赫声势。
蒲类,本为海名,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北麓东段,汉初属匈奴,《后汉书》卷77,注引《汉书音义》:“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我国汉、魏时期史书中所载方位常有所欹斜,“敦煌北”应指敦煌西北,今巴里坤湖正在这一位置。①《汉西域图考》云:“自奇台(指今老奇台)而东三十里,入山五百六十里,至肋巴泉塘,山势始开,又东二百六十里而复合,山环如城,中为巨浸,今为巴尔库淖尔,即古之蒲类海也。”此海在清宜禾县(今巴里坤县)北,道光钦定《新疆识略》记宜禾县“南为天山,即古祁连山,北为巴尔库淖尔,即古蒲类”。《新疆建置志》则称,巴里坤即蒲类之音译,其是巴里乃蒲类的对音,海之突厥语本为kul,蒙古人不明其原义,音译为坤,因于巴里坤后又后缀以“淖尔”(湖),转译为汉语时亦作巴里坤湖,以语言学角度言之,皆属多余。可知蒲类因蒲类海得名,必发祥于今巴里坤一带,与兰州湾子遗址所在位置完全相符。至《汉书·西域传》中,蒲类的牙庭已不在巴里坤,而是“天山西疏榆谷”了。天山是横断山脉,哪里来的“天山西”呢②,可见此处的天山,必指天山的支脉,说明移居天山西的蒲类国已迁至今木垒县境内,与今四道沟地望相符。与史书中所记“天山西疏榆谷”若相符契。很可能四道沟就是蒲类牙庭疏榆故址。唐代的榆慕谷似即这个“天山西疏榆谷”的千古遗音。③以此判断,蒲类的活动中心就在今巴里坤至木垒一带,古老的兰州湾子—四道沟文化应当就是蒲类人创造的。
蒲类之外,山北六国中还包括郁立师、卑陆、劫、单桓、且弥诸国,其相对位置比较清楚。可以参照古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大致可以确定其具体地望。其中郁立师在蒲类西、卑陆东,相当于今之奇台县,半截沟遗址似即此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内咄谷故址。其东境一直延伸到与吉木萨尔接境的白杨沟遗址。
卑陆国位置在郁立师国西,其政治中心绝非分化后位居“天山东”的卑陆前国,而应是位在卑陆后国牙庭番渠类谷,《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蒲类后国“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说明卑陆后国东接郁立师,西接劫国,松田寿男根据《汉书·西域传》所记里数推算,“大概卑陆国的西部,构成了靠近乌鲁木齐的别部,它被称为卑陆后国。”可见卑陆国的东界似应在今阜康县,西界已进入米泉县。卑陆人大约与蒲类人同族,其文化的诞生时间仅亚于蒲类。在车师后部到来之前今吉木萨尔县境的山北六国故部有所空缺,只是到了宣帝时期才出
现了有关金附国的记载,以此判断,金附国大约早就属于山北六国部落联盟之一。
劫国①,唐代丝路北道有俱六守捉之名,在今阜康县境,似即“劫”的古代遗音。以此判断,劫国所治天山东丹渠谷的位置应在今阜康县的山前地带。学术界早已公认,《汉书·西域传》中的方位有所倾斜,所谓“天山东”应指博格达峰东北,以此判断,丹渠谷的具体地望必在今天池东。其西则为单桓、且弥二国。
且弥,与唐代的处密同音,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唐之处密似存在东、西两支,东支活跃于凭洛水西,即今阜康、米泉、昌吉一带。西支已远在伊犁河流域,汉之且弥亦已分为东、西两支,其西支与乌孙接,至少已到达玛纳斯、呼图壁一带,其东支尚在单桓东,亦即阜康境内,但那里并未发现有价值的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原始遗址,发现的只是大批石堆墓和石棺墓,难以找到对应的遗址。
单桓是山北六国中唯一以城堡为牙庭的部族,位于东且弥西与西且弥东,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古代城堡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市东沟、阿拉沟水域,诸如东沟乡的东河坝西岸的破城子、苇子村烂城子和阿拉沟大桥一带发现的石建筑遗存。②后者更具有考古文化特色,也许这些石建筑在汉人看来就属于定居 “城堡 ”的一种,以此判断,阿拉沟大桥一带的古代石建筑遗存就是单桓城的所在地。
第三节岩画中的塞人图像
作为西域大国、山北六国盟主的蒲类人何以在天山北麓诸族中最先崛起,究竟出自什么人种?操何系语言?山中岩画大量图像和中外文献资料对我们的认识有所启迪。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天山北麓各地的岩画逐渐被发现并显现出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东起巴里坤、木垒西至呼图壁一带的天山北麓东段岩画明显多于以西岩画,且一律分布于北坡山前地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著名的岩画点有巴里坤的冰沟、塔勒德巴斯陶、八墙子、石人子乡、兰州湾子、大黑沟、阔克加尔;伊吾县的阔如勒、伊吾镇、大白杨沟;木垒县的芦塘沟、鸡心梁、旱沟、东地、水磨沟;吉木萨尔县的松树沟、甘沟塘;米泉县的独山子;阜康市的三工河、吉沿坚;昌吉市的阿什里;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阔克霍拉;玛纳斯县的沙拉乔克、苏鲁萨依等地,正属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故境。这些岩画虽然不能通过碳14测定,进行准确的时间断代,却具有众多的共同性。(1)从岩石的敲击方法和作画方法判断,绝大多数已使用了金属器。说明是金石并用时代的产物。(2)动物题材在岩画中居于压倒一切的数量优势。见于岩画的动物种类有羊、野马、野牛、野鹿、马鹿、野骆驼、熊、狼、狐狸、蛇,已经灭绝的新疆虎、鹰和狗,几乎食草、食肉、爬行、飞禽类动物无所不有。虽然绝大多数都是野生,但狗和骑者、羊圈画面的出现则已说明畜牧业已同狩猎业开始共存,同已知的兰州湾子一四道沟考古文化发现相一致。(3)人的图像资料虽然远较动物为少,但却鲜明地反映了当地居民的体质形态特征及其社会、精神活动,成为探讨天山北麓东段自然生态和古人生产、生活的重要图像资料,弥足珍贵。
在山北六国盟主蒲类发祥地的巴里坤、木垒,岩画开凿最多,而且多鸿篇巨制。兰州湾子岩画使用了凿刻、磨刻或凿磨兼施等技术。大都刻在平整砾石上,仅少数刻于岩壁。绘有行猎图12幅,包括单人猎、围猎、骑猎,使用的狩猎工具有弓箭、投枪、棒槌、绳索。猎画已开始与野生动物画平分秋色。①还有骑者图5幅,其中1幅长300厘米,高140厘米,刻有许多奔走的戴帽骑者,旁有鹿、大角羊等动物。说明蒲类人已开始驯化野马。巴里坤东北38公里的八墙子岩画画面多,群体画面尤多,且有文化重叠现象,时间延续最长,开始出现了狗,成为人类不可分离的伙伴。巴里坤大红柳峡东南小加山南麓塔勒德巴斯陶岩画共有数十幅,内容也大体相似。伊吾县吐葫芦乡大白杨沟村外山丘东壁岩画数十幅,集中凿刻在高3米、长约15米的岩壁上。所绘骑马者画面,昂首疾驰,形象极为生动,所骑的马很可能是正在驯服的野马。伊吾县盐池乡的热孜布拉克岩画分布在西、南山坡的花岗岩上。共有画面十余幅,内容除了狩猎、狼吃羊等画面以外,也出现了骑者的生动形象。在奇台北塔山阿艾提沟的野马岩画②绘于宽2.6米、高2.2米的一座红色峭壁上,壁上密集绘制有近20匹马的图像③,最大的一匹马宽60厘米,高4.4厘米,其中13匹马都为东向,独有一人骑在马上,西向而立,马无鞍,跃然欲立,人屈两臂,状若套马,马长17厘米,高20厘米,人高12厘米,宽15厘米,跃然欲活,其余野马,也情态各异,这种野马似乎就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沙俄探险家格鲁木尔的野马。由此推测,蒲类人之所以成为山北六国盟主,同率先驯服天山北麓野马有关。
羊的驯化为家畜和狼崽被驯化为狗,乃是考古学上重大事件。这在山北六国故境的天山北麓东段岩画中也有明确反映。这一地区羊的种类纷繁,包括大角山羊、盘羊、羚羊等。尤以大角羊数量最多,几乎每幅岩画都少不了它,为人类广泛放牧的肉用羊,应当就是这种大角羊驯化而来。木垒照壁乡学房村东的平顶山旱沟狩猎岩画中除了生动地雕刻出狩猎者张弓射箭的场面以外,其身旁还出现了蹲立的狗,似在待命出击,同四道沟出土的陶狗形象相似。
吉木萨尔的松树沟岩画地属大有乡广泉子村,共3幅。其中最重要的一幅刻于约70米一峭立的岩石上,上方为一骑马、牵马图。骑者头戴尖顶帽,一手持缰,一手叉腰,牵马者位于马头前,身体前倾,双腿一弓一蹬,反映社会已发生了身份分化。下方绘有羊的画面(图30),又绘有一有开口的圆圈,内有一有角动物,似为羊圈(图31),门前还绘有一无角动物,略带夸张,造型生动,似乎是狗。说明已进入畜牧社会。甘沟塘岩画位于泉子街镇北不远的山上,在松树沟之东,岩画共有3幅①(图32、图33),皆镌刻在散置的三块大岩石上,没有人物,阴雕浅刻,具有强烈的夸张色彩,刻画工具似为金属,说明是金石并用时期的遗物。其一形象漫漶不明,另一上绘大角羊,相当生动,最重要的一幅上绘大角鹿,一鹿角桠纷披,十分夸张。阜康市吉沿坚岩画位于天池东南约 18公里吉沿坚沟的台地砾石上。第一块
砾石上由30余只北山羊、两个人物、一头鹿、两条牧犬、一条狼组成一个画面:恶狼正袭击羊群,一男子张弓作欲射状;另一个人双臂张开,身体前倾,作驱赶状。第二块砾石画面侵蚀严重,仅数羊形象可辨。明显属于畜牧时代的岩画。岩画雕刻简洁,虽难以准确地反映当时人类的面貌特征,却几乎所有可以辨认的人物图像大都头戴尖顶帽,例如巴里坤兰州湾子岩画总有骑者图5幅,其中1幅长300厘米,高140厘米,就刻有头戴尖顶帽的骑者。巴里坤冰沟岩画中的一幅胯下为一倒置北山羊的狩猎图,骑者也似乎头戴这种帽子,伊吾镇岩画中清楚地绘有一位骑大山羊的猎者,头戴尖顶帽,前述吉木萨尔松树沟第四组岩画中的骑者也是头戴尖顶帽,学术界公认尖顶帽正是印欧人种的塞人的重要特征。奇台县西地乡发现的一具石雕人头像,明显具有印欧人种的体质特征,尤为最具说服力的雄辩物证。
塞人,又作塞种,《汉书》中多次提及这一古代族群,如卷96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鋥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同书卷97又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说明张骞初通西域时,塞人曾广泛分布于中亚内陆。“塞”字,即希腊文中之Sacae、古波斯语Saka的音译。乃古代中亚大族,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多次提到这一古族,记其分化为拥有不同名称的若干分支,如Smilian、Massagetae、Scythia①等。Smilian今译多作“西密利安人”,我以为应即《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访问过的“西膜”部落。这部出自晋汲郡古冢的先秦古籍详细记载了周穆王此次以联羌制戎为战略目标的西巡,周初诸王世与姜姓联姻,姜即羌,很可能兼通羌语,其沿途所访赤乌、曹奴、容成、甄韩、西王母、寿余、诸干、重罋、巨蒐诸国,都是直接交谈,惟访问西膜时乃以译语人为语言中介,说明西膜语言异于西域诸羌。可见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有一支塞人进入今新疆境内。在《历史》中Scythia与Massagetae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地域,却明确指出了
①说明二者同族。而同书又记:“波斯人是把所有的Scythia人都称为Sacae。”兆示着这些名称都是塞人的不同支脉。有学者研究,Massagetae可分解为Ma与Ssagetae两部分,该词的词头“Ma”在塞语中有大的涵义,词干部分的Ssagetae=Sacetae=Sacae,具有大塞种部落的涵义,为塞人中的主部。同书又记: “Massagetae(原译玛撒该塔伊人)据伊赛多涅斯人相对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 Scythia的一个族群。”Massagetae人穿着和Scythia相同的衣服,同样的生活方式;拥有骑兵、步兵、弓兵和矛兵,更有使用战斧的习惯。波斯王大流士贝希斯敦纪功碑铭文上塞人也分三支:SakaHaumavarga,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的叶子的Saka人;SakaTyaiytaradraya意为海那边或河那边的Saka人;SakaTigra~hauda,意为戴尖帽子的Saka人。其中戴尖帽子的塞人SakaTigrahauda尤同希罗多德所记Massagetae存在着众多共同点。大流士铭文记载SakaTigrahauda“住在海的那边,戴高高的尖顶帽”希罗多德:《历史》64节记:“属于Scythia人的Sacae(原译撒卡依人)人戴着一种高,帽子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的Scythia(原译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Sacae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Scythia(斯奇提亚)人都称为Sacae的。”②贝希斯敦铭文上方浮雕中表现的被俘的塞人,波斯波利斯浮雕中描写的向阿赫明尼德王朝朝贡的塞人,牵骆驼的巴克特里亚人以及南俄库尔奥巴(刻赤)和沃罗涅日发现的金银合金瓶画中的斯基泰人(Scythia)都是戴着护盖两耳的尖顶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综辑以上汉文、希腊文和波斯文献,所记塞人的共同特征都是戴尖顶帽的族群。1983年8月,在新源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件青铜塞人武士俑,造型端庄英俊,呈蹲跪姿,通高42厘米,空心,重4公斤,头戴尖顶带弯钩状圆帽,面目丰满,二目前视,双手环握执物。上身裸露,腰间围系着遮身物,赤足,两腿一跪一蹲③,女性帽上饰翎羽两支;面颊修长,大眼、高鼻、小嘴、长项、细腰、肥臀、隆胸、修腿,男子则大嘴、有髭,面部轮廓粗犷,康家石门子墓地中发现有骨器、天然金箔、直径约0.05米铜镜,以及妇女头上戴的银装饰物品,也印证是一处塞人墓。说明在匈奴和汉人相继到来之前,从巴里坤到呼图壁这一广阔地区古代居民就是印欧人种的塞人,而不是蒙古利亚种或混血型人种。具有高鼻、深目、多鬚的体质特征,戴尖顶高帽的塞人。蒲类的种族归属也应当属于塞人中的一个小分支。蒲类二字④复原古音,“蒲”为滂纽(P)虞韵(iu),类为来纽(1),灰(uai)、队(ai)二韵,上古虞入,鱼韵(a),灰、队皆入支韵(,e)蒲类的上古音值应读为“pali”,这一音读与中古波斯语中的pari一词完全相同,意,为仙女、美丽。⑤如果这一解读不错,那么,蒲类海的塞语本义就是美
丽的湖,仙女湖。进一步演变为蒲类人的族名自称。
麦高文在其名著《中亚古国史》①中强调塞人最大的贡献是骑射用于战争。《左传》中也印证虽然漠北的狄人早就习惯于骑马放牧,但在战争中却是“彼徒我车”,作战时仍是徒步对抗华夏人的战车,弓箭虽然早就用以狩猎,但大规模作战中却并未出现专业的弓箭手,塞人组建了专业的弓兵,引起了一场军事技术的革命。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当赵武灵王(前325~298年)时始模仿北方的蛮人,改采胡服骑射..我们从此不难看出此时北方的蛮人已经起了怎样大的变化,两世纪以前他们还是徒步生活,徒步作战的;其主要的攻击武器也许还是用剑而不用矢,那时他们有没有靴和裤,也还是一个疑问,但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却要从北方的蛮人传习‘胡服骑射’了。”②据此可知,匈奴的骑射之术也是渊源于塞人。希罗多德还记载,Massagagetae人“不播种任何种子”,逐水草,营游牧,食畜肉,习骑射,歃血为盟,以人头为饮器③,这些都对后世匈奴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节 匈奴与山北六国的衰落
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崛起及其西域霸权的确立,根本动摇了蒲类在山北诸国盟主的地位,至公元前2世纪的汉开西域时,蒲类已四分五裂,“西域大国 ”早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追溯。
匈奴是最先雄霸漠北、西域的草原游牧强族。“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扆(骆驼)驴、■、、騨。”④凭借这一雄厚的驯畜资源,建立了一支以骑射为主,兵牧合一的强大武装。早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期就已崛兴,以单于为王称,以阏氏为后妃之称,历代单于都出自王族挛鞮氏,太子常封为左屠耆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诸小王及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各级官员,“皆世官”。⑤秦朝统一中国前夕,多次出现于史册:周慎靓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周赧王四年(前311)又出现了“匈奴驱驰于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之下”⑥的记载。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遂筑长城,修驰道,遣将“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余里”。⑦在秦军的强大打击下,匈奴一度转衰,头曼单于在位时期,“东胡强而月氏盛”,被迫向东胡和月氏等两大强国各送质子,著名匈奴雄主冒顿单于就曾入质于月氏,后来逃回本国,以鸣镝训练部曲,射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①此岁正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太子扶苏被杀,“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国势逐渐复苏。但仍以甘言厚贡麻痹当时的漠北霸主东胡,任其来索千里马,美女,悉以奉贡,至汉高祖元年(冒顿单于四年)又诱其来索牧地瓯脱,故意激成众怒,及士气激奋,始率众出征,下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后汉书》卷90记东胡自为冒顿所破,“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此后又向月氏复仇,杀其王,迫使月氏举族西迁,匈奴大漠南北霸主的地位遂正式形成。《资治通鉴》记此役未提及匈奴,似应以《史记》记载为准。②汉高祖元年(前206,冒顿单于四年)灭东胡,以挛鞮氏为核心,吸收呼衍氏、须卜氏、兰氏诸大姓,正式创立了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河西、河曲诸小王纷纷加入了这一部落联盟,成为下属的异姓王。
匈奴的复兴正当楚汉相争的秦末乱世,不仅“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③,而且不断南侵汉边。汉高祖六年(冒顿单于九年,前201)汉军主力正与项羽楚军相峙,委韩王信守边。当年秋,匈奴围马邑,汉兵无力驰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兵逼晋阳。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十年,前200)高祖刘邦亲统大军北征,被围于白登,七日不食,迫使汉朝委曲求和,以美女、丝帛,无偿地奉献给匈奴,以换取边疆地区的苟安。并为吕后、文、景诸帝历代遵循,垂为定制。
冒顿单于在位长达36年,在此期间,汉与匈奴虽然名为“和亲”,实际上边境掠夺连年不断,图谋不轨的诸藩王也都密与通使,倚为后盾。文帝六年(前174)老上单于继立,英武骁悍不亚于冒顿,当年遣其右贤王统兵西征,迫使已经迁居西域的宿敌月氏再一次远徙妫水,致书吕后,声称:“以天之福..灭夷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④以上西域二十六国必定包括蒲类等山北六国在内,这是匈奴西域霸权正式确立的历史标志。委其二异姓王分治西域东、西,其中日逐王居西,“”建牙于 焉耆、危须、尉黎间 ⑤;呼衍王居东,建牙于“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⑥,将一切属国都视为奴隶,向各国都派出了僮仆校尉,即管理奴隶的官员,职能是向派出国征收贡物和监其国政。 “赋
税诸国,取富给焉。”①相当于后来突厥的吐屯、西辽的监国少师,清代的都统。有人认为匈奴的僮仆都尉似乎是类似于汉西域都护府那样的组织,有一个名为僮仆都尉府的建置存在。其实,匈奴统领西域的最高首领主要是呼衍王和日逐王,“僮仆都尉”只是此二王下辖分遣诸部的基层官员。
匈奴西域霸权的确立标志着蒲类山北盟主地位的动摇。在匈奴西征过程中,曾为西域大国和山北六国盟主的蒲类不可能不率众组织抵抗,必以失败告终,遭受重创,自此一衰不振。蒲类海本是蒲类国的发祥地,今已成为匈奴呼衍王的牙庭,蒲类牙庭被迫西徙天山西疏榆谷(今木垒四道沟)。蒲类的大国地位不利于匈奴的西域统治,分而治之是削弱这一大国的有效手段,在这一政策催化下,原来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蒲类统一体被肢解为若干小国。分化为蒲类国、蒲类后国、乌贪訾离国等三国。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2032人,荷戈壮男 799人;蒲类后国,拥众 1070人;又有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拥众 1700人,“元帝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则乌贪訾离也是蒲类中的一支,这三支蒲类人口加在一起,仍有 4802人,复据《后汉书 ·西域传》匈奴还曾 “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种种迹象表明,匈奴对蒲类的分化、肢解政策早已进行,至汉开西域之后,由于蒲类受制于匈奴呼衍王,又受到汉军的重击,这一历史进程更为加速。本始二年(前72)分遣五将军伐匈奴,“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 ”其中赵充国引人注目地领有“”
②,蒲类将军 名号,说明其主攻方向是蒲类海,“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 ”。③另遣 “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④东西夹击,斩获极众。可见此役遭受汉军打击的不仅是匈奴,蒲类也是其打击对象。此外,《后汉书》还出现了一个移支国名,记其 “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抄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无论从地域,还是风俗,这个移支国显然都是改换了国名的蒲类人。自此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落、部族联盟也面临解体的危机。蒲类衰落之后,匈奴与汉朝激烈争夺的对象转移到原居盐泽至吐鲁番盆地一带的车师。地节二年(前68)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在渠犁屯田的汉将郑吉捕捉这一有利时机,率领食饱财足、斗志旺盛的屯田将士,进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
复发兵攻车师王于丰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①。这座石城的位置在交河城北,不一定是天山之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石城即兜訾城。②车师腹背受敌,被迫降汉。郑吉遂开始在吐鲁番、鄯善一带经营屯田。“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③姑师、车师所居一直是吐鲁番盆地,不闻前、后部之别,至是始车师二王并立,这是车师分化为二王的历史开端。至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汉之后,郑吉乘胜率兵反攻车师,护送亲汉的车师王军宿还封交河,亲匈奴的车师王乌贵率众避迁天山北麓,车师前、后二部的分化更为定型化。车师后王徙居天山北麓,全力投倚匈奴,车师前部王则在汉军的全面控制之下。至前、后汉交替之际,在北匈奴的全力支持下,车师后王不仅成为车师二部的共主,而且取代了蒲类昔日的地位,成为天山北麓诸部及车师前部的共同盟主,自此,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部落、部族联盟正式形成。“山北六国”之名开始在史册中完全沉没。
在山北六国中卑陆是仅次于蒲类的天山北麓东段第二大国,这个曾经创立过辉煌小西沟文化的重要部族,至迟西汉宣帝时期似已离开了泉子街故牙,小西沟遗址的主人似已成为小金附国的牙庭。这个小金附国名既不见于山北六国名单,也不是车师六国的成员,其活动唯一见于史册乃地节二年(前68),其古音遗脉却自汉金蒲、唐金满,清济木萨传承至今,留待后论。
匈奴西域霸权确立同时又是匈奴加入西域多元族群行列的过程。主要居地也是天山北麓东段,虽然数量远较当地土著族群为少。
匈奴在野生动物驯化家畜方面的历史贡献极为突出。在匈奴经营的畜牧业中,不但有羊、马等后世为突厥、回鹘所继承的主畜之外,畜类品种之多,尤引人注目。不但举凡骆驼、驴、牛等被后世突厥等所称的“杂畜”一应俱全,还利用杂交技术培育出了“骡子”这一耐苦、耐长途行走的新畜种,用以拉车,以驼渡碛,以羊为食,为衣,以马为出征、畜牧的坐骑。其中马的培育尤为成功。平城之围中匈奴骑兵以毛色为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骆马(赤黄色)”④。令汉人惊骇,亦足反映匈奴各种毛色马的众多。单于招降汉使苏武时以整座山谷中的牛羊相许,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大将军卫青取“河南地”,获匈奴牛羊约百万头。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出高击败匈奴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万。①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单于,获其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②足以反映作为匈奴经济基础的游牧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狩猎已降为畜牧业的补充和骑射训练的一种手段。
前苏联学者在南西伯利亚匈奴墓的发掘和上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对漠南匈奴故境的考古调查、发掘,共同证实了匈奴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足以同汉朝抗衡。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后期匈奴墓出土的王冠由冠饰和饰带两部分组成,全为黄金打造,顶上立一展翅雄鹰,鹰头为绿宝石琢制③,极为精美。铁器已成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体。匈奴最有特色的兵器有鸣镝和径路,鸣镝即响箭,径路即马刀,诺颜山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发现的数百座匈奴墓葬中出土了这类铁制兵器,并发现了公元前2~公元1世纪时期的铁模、炼铁炉和铁渣,从而证实了《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和《东观汉记·邓遵传》所记邓遵缴获匈奴匕首三千、釜镬两千的真实性。出土的青铜制品中虽仍有少量铜镞、铜刀等武器,但更多的发现则乃铜针、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铃、铜环、铜马等生活用具④,以及带有野兽纹的铜饰件。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窟子⑤,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⑥都有类似的发现,透露出强烈的塞人文化影响。所发现的铜镜、铜鼎则显然是汉文化的影响。陶器乃日常生活的主要器皿,《汉书·苏武传》记单于弟於靬王赐武马畜、服匿、穹庐。其中服匿就是陶缶。其形如罂,小口,大腹,方底,用以装酒与乳浆。很有特色,曾传至南齐。匈奴善于“冶作弓矢”,出土了制造工艺相当复杂的合成弓,射程和穿透力都超过汉军。《汉书》卷94,记匈奴“车以材木为之,”“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⑦具有坚固耐用的特点。这种匈奴车在杨雄《长杨赋》中别记为轒輼。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汉军在常山、中山连败南单于,获此类穹庐及轒輼车多达千余辆。顺帝阳嘉三年(,134)在车师附近的阊吾陆谷汉军又大获匈奴车千余辆。⑧
匈奴衣皮革,被毡裘,《淮南子·齐俗训》记匈奴发式为“纵体施发”,陕西沣西客省庄匈奴墓出土的长方形透雕铜饰牌,画面上的两个人物皆披发。⑨可见“施发”就是披发。制革和毛纺织业似已成为家家精通的副业,出现了“匈奴出秽裘”⑩和“罽帐”11的记载,诺颜山苏珠克图山口的六号墓出土的毡毯上还绣制出牛、马、鹿头形和野兽互相搏斗画面。①匈奴服饰特征以左开衽、穿胡裤、穿革靴为特征。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匈奴官吏当户跪擎铜灯的铜俑,特征就是短衣直襟左衽,手有臂鞲,脚着长靴。②诺颜乌拉大型墓出土的匈奴服装都是用当地细毛线缝制而成,领、袖、下摆均镶边,做工十分精细。帽子为尖顶或椭圆形,带护耳,内蒙古的匈奴墓葬中还发现过铜制的小型甲片。
松田寿男据《汉书·常惠传》中以下一段文字:“是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认为匈奴也像汉朝一样在车师经营屯田。据我判断,“田车师”一句实同于“畋车师”,“畋”字的意思乃是狩猎,与耕田、屯田毫无关系。虽然史书上明确记载匈奴国中也有农业生产,《史记 ·卫青传》记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卫青军至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储存的大量粟米。《汉书 ·匈奴传》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秋,匈奴地区因为连续下雨数月,“谷稼不熟”。漠北匈奴墓葬中确已发现公元前3~前2世纪的“黑色的农作物种子”。③匈奴盛行奴隶制,连年犯边所掠汉人,都沦为匈奴奴隶。这些以黍米为特征的农作物显然是被掠至匈奴的汉人奴隶生产的。
匈奴信仰万物有灵的巫教,祭拜天地、日月星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④一年三集会,正月、五月、九月戊日为其集会时间,正月集会单于庭,举行祠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最为隆重。茏城,一作龙城⑤,非城堡名,似为神庙名。秋九月,大会蹛林,除重视外,还要进行人畜数字的核实工作。并有专业巫师,主持人神沟通和预
卜吉凶。《汉书·西域传》记:“匈奴使巫埋牛羊于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见使巫祝之。”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燕支山击败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重约 20斤,这就是匈奴人崇拜的偶像之一。 “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⑥
匈奴自身原无文字,自从中行说入匈奴,参赞帷幄以来,就一直使用汉文作为书面符号,出现了一批以汉文写成的匈奴文书。如汉惠帝三年(前 192)冒顿单于羞辱吕后书及征和四年(前89)匈奴狐鹿姑单于致书武帝书都直抒胸臆,无废言赘语,以直白为特色。如狐鹿姑书云: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匈奴语言风格非常明显。东汉时期还出现
了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密遣郭衡呈匈奴地图于汉使事件,说明匈奴国中还有汉人代绘的地图。①
匈奴有自身的乐器胡笳、鞞鼓。据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所记:“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胡笳为管鸣性的吹奏乐器,鞞鼓则乃膜鸣性的打击乐器。此外,匈奴还盛行“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②,陕西长安汉上林苑一座匈奴墓葬出土的两块长方形的透雕花纹铜牌上还存有摔跤场面。③在首领宴会中还有 “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 ”④的记载。
附注
①羊毅勇:《兰州湾子鄂博遗址》,《新疆日报》 1979年 4月 22日。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发掘报告》(羊毅勇执笔),载《考古》,1982年第2期。参阅羊毅勇《四道沟原始村落遗址》,《新疆日报》,1979年4月22日;戴良佐《四道沟氏族文化遗址》,载《庭州纵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①1黄小江:《木垒县彩绘狩猎纹棺墓》,《新疆日报》1979年4月22日。
①奇台文化馆文物专干徐文治最早接到当地报告,来到这座遗址,取回遗物,交我处理,我当时已调奇台师范任教,判断遗址的重要性非常,建议上报自治区博物馆派人发掘,主持这次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陈戈当时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工作,赴奇台发掘前曾专程赴奇台师范及我家,邀请我也参加这次发掘,我因尚有教学任务,自身又无法定文物千部身份,未参加此次发掘,但发掘前后详情,悉所周知。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奇台县半截沟新石器时代遗址》,陈戈执笔。《考古》,1981年,第6期。
①《新疆文物》,1987年,第 3期。
②《新疆文物》,1989年,第 3期。
③《新疆文物》,1992年,第 4期。
①《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新疆文物》,1992年,第 4期。
②小西沟古城所在的自然村汉、回杂居,经详细访问当地书记及70岁以上老人,该遗址遭受破坏主要发生于两个时间段:一是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的积肥运动。二是20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积肥热潮。出土文物主要集中于北城墙附近,破坏最大的也在这一地区,其他地区保护尚好,仍有出土文物的可能 c
①器形很小,胎薄,陶面极为光洁,制作精致,应为小西沟文化高度发展时的产物。原罐持有者在北城墙积肥时发现,我们登门拜访时主动捐献。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所记之乱杂岗实为乱葬岗的讹写。
①《汉书西城传地里校释 ·山北六国》,中华书局本。
②《北庭史地研究 ·山北六国》,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论距汉都长安里数》,见《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55页。
②《钦定皇舆西城图志》、岑仲勉《汉书西城传地里校释》皆误解传文中“天山西”一语,以为此二国位于今乌鲁木齐以西。倘如此,则与蒲类海相隔甚远,何以解释其国名由来?
③《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处月部即活动于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一带,歌逻,为东支葛逻禄的特殊写法,也是活动于阿尔泰山以南,木垒以北的突厥部落。
① “劫”古为入声字,后带辅音 k,古代翻译通例,皆以汉字带 k的入声字翻译 Iuk,lik等音,在古音学上与俱六、俱陆同音。
②《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 1期。
①邢开鼎:《巴里坤兰州湾子岩画》,《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②薛宗正:《奇台县北塔山岩画踏勘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③薛宗正:《奇台县北塔山岩画踏勘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①该岩画点此前未见任何报道,2005年我在朱丹陪同下勘察吉木萨尔山前地带无意中发现。领路者为甘沟塘村书记。在此选择使用了 2幅。
①王嘉隽译希罗多德著《历史》中译作斯奇提亚,有的译者译为西徐亚,今通用译名为斯基泰。
①〔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47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47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③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图录 90,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④有人以突厥系语言相附会,释蒲类为今哈萨克语中的 barikul,意为虎湖但巴里坤一带素不产虎,其释难通。
⑤ 1薛宗正:《唐蒲类诂名稽址》,《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①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273~27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③〔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273~27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④《集解》,徐广曰: “北狄骏马。”皆野马。
⑤《史记》,卷 110。
⑥《史记》,卷 110。
⑦《史记》,卷 110
①《史记》,卷110。
②周赧王四年(前311)为燕昭王问政郭隗事《说苑》卷一《君道》记此为燕昭王问政郭事,参阅《战国策·燕策》一,昭王收破燕后即位,为燕王哙九年,(前312)哙死后,故系此年。
③《汉书》,卷94。
④《汉书》,卷94。
⑤《汉书》,卷96。
⑥《资治通鉴》,卷50,孝安皇帝延光二年条。
①《汉书》,卷 96。
②《汉书》,卷 75。
③《汉书》,卷 94
④《汉书》,卷 94
①《汉书》,卷71:“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②《汉书》,卷71,汉宣帝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而传文中郑吉所破乃车师石城,以此得知,车师石城即车师兜訾城。
③《汉书》,卷95。
④《史记》,卷 110。
①《史记》,卷 111。
②《后汉书》,卷53
③《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④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合刊。
⑤李逸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6年,第6期。
⑥李逸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⑦《盐铁论 ·论功》。
⑧《史记》,卷 110。
⑨中科院考古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⑩《淮南子 ·原道训》。
11《后汉书》,卷80。
①林幹:《匈奴墓葬简介》,第二部分载《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80年版。
③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墓葬》,原载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的《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1956年第1期。转引自林幹《匈奴墓葬简介》第二部分。
④《史记》,卷110。
⑤《史记》,卷110,《索隐》引《汉书》,“龙城”,亦作“茏”字。又引《后汉书》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祭天神”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⑥《魏书》,,卷114。有学者据此断言,此金人即佛像,余太山撰文,不以为然。
①
匈奴有自身的乐器胡笳、鞞鼓。据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所记:“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胡笳为管鸣性的吹奏乐器,鞞鼓则乃膜鸣性的打击乐器。此外,匈奴还盛行“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②,陕西长安汉上林苑一座匈奴墓葬出土的两块长方形的透雕花纹铜牌上还存有摔跤场面。③在首领宴会中还有 “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 ”④的记载。
①《后汉书》,卷89。
②《东观汉记》,南匈奴单于传。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 10期。
④贾谊:《新书 ·匈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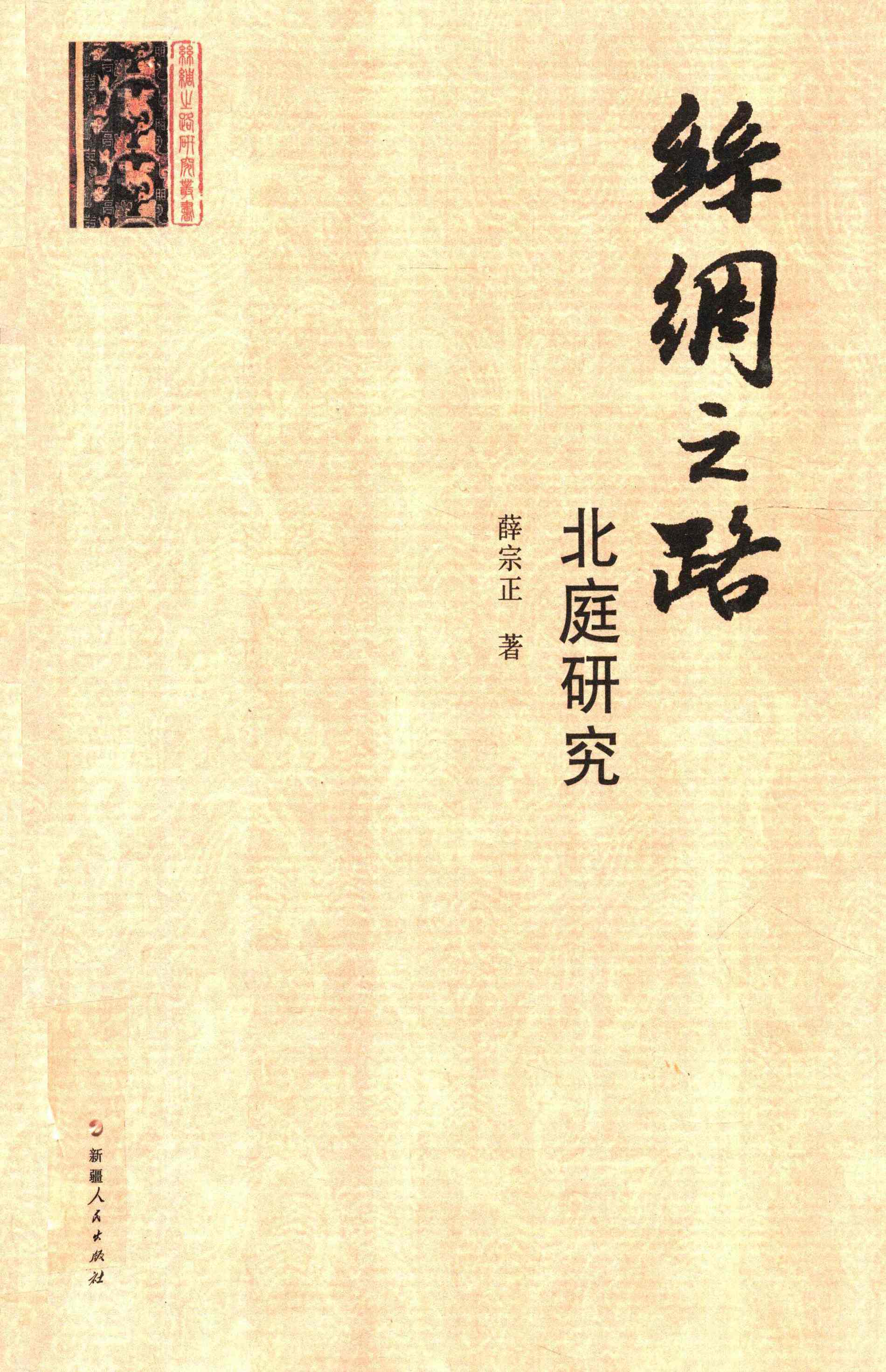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新疆地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