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庭古城的发现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北庭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644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北庭古城的发现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7 |
| 页码: | 1-7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新疆地区北庭研究历史回顾、北庭古城的发现的情况。 |
| 关键词: | 新疆地区 历史回顾 北庭古城 |
内容
北庭一别失八里古城自从明初开始荒废以来,曾经为世人淡忘。直至清朝重新统一西域之后,统治天山南北的军政中心已移至天山西段的伊犁将军府,再次驻兵屯垦,移民实边之后,它的历史辉煌才重新唤起人们尘封的记忆。
今吉木萨尔县清代名为济木萨,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已创设了济木萨巡检,起初主要主持当地绿营兵的军屯,后来随着民户的增多,也兼管当地民政。却直到清末建省前,才上升为县级规格,此前只是相邻奇台、阜康二县的属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始创镇西府,以原西路军大本营所在地巴尔库勒城(今巴里坤)为府治,实行郡县化。下辖宜禾、奇台两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创置了奇台、宜禾二县,同年又创置了迪化直隶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市汉城迪化,济木萨初归奇台县管辖。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阜康建县,昌吉、绥来、阜康等三县皆划归迪化直隶州,自此以后,济木萨又转隶阜康县管辖。由于这些新设诸府、州、县的汉人移民大都来自甘肃,在行政上初由甘肃省遥领,而又兼受驻守巩宁城的清军长官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事实上是双重管辖。随着乌鲁木齐都统权力的加重,后来,甘肃省的遥领形同虚设,乌鲁木齐都统逐渐全面接管了天山东段诸州县的管辖权。
乾隆三十三年秋七月至三十六年冬十月期间(1768~1771年),一代大名士纪晓岚获咎流放乌鲁木齐。纪晓岚(1724~1805年),名昀,字晓岚,以字行。又字春帆,晚号石生,《清史稿》卷320有传。原籍江苏省上元县(今南京市),明永乐年间移居北方,清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1724年8月3日)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河间府献县。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率真,幽默风趣,学识、文采都秀出群伦。曾主持纂修《大清会典》、清《三通》、《清高宗实录》等,参与《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诸书编写,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以手撰提要而名垂青史,出色地完成了我国文化史上这一空前伟业。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嘉庆十年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3月14日)以礼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高位病逝于北京。纪晓岚以其崇高声望,在戍期间,得到主政官员的高度礼遇。“乌鲁木齐”当时还不是一个城市名,而是一个地区名,所指乃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地区,即包括迪化州和镇西府全境,留有《乌鲁木齐赋》、《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资料。他在戍期间,曾亲临当时仍被称为护堡子破城子的北庭古城,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第11、第12卷《槐西杂志》中惊讶地记载了这座古城“周四十里”的宏大规模,比今天的范围要大得多。并根据史书所记将它正式确定即唐北庭古城,唐朝北庭大都护府治所。纪晓岚还细心地测量了城墙的厚度,留下了“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的原始记录。当时城内完整的建筑遗存似乎还不少,所见“旧瓦亦广尺余,长一尺五六寸”,城中还发现了一座佛寺,“寺已圮,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皆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唯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所出寺中铁钟,高过人头,足见寺院规模不小。现存古籍亦印证,庭州金满县境至少有三座规模宏大的佛寺,除悟空寄经的龙兴寺、宋使王延德憩足的高台寺外,北庭城中还有一座应运大宁寺,这座圮寺,是否就是该寺遗址?寺中所出连纪晓岚都不认识,类似八分书的铁钟铭文必非汉文,很可能是北庭回鹘时期流行的回鹘文。纪晓岚还记载:“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额鲁特云,此城皆以火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盖在准噶尔前矣。”史书中透露,东察合台歪思汗在位时期曾与新兴的准噶尔蒙古连年激战,他之所以西迁亦力把里,同战争失利有关。纪晓岚的这段记载,还可进一步印证别失八里的废弃,是一场恶战的结果。但是,纪晓岚的考察也不是没有失误。例如他说:“济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将北庭古城的兴建归功于“李卫公”,即唐贞观初年平定东突厥的大将李靖,显然是不对的,此人根本没有到过西域。
清朝管理天山东段的最高官员起初称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更名为乌鲁木齐都统,官位仅次于总管西域新疆的伊犁将军。所任命的首任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都是索诺木策凌。他是一个在旗蒙古人,兼通满、蒙、汉文字,非常能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率领部众始建满城巩宁,规模更大于汉城迪化,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竣工,成为满洲八旗及其随军家眷的驻地。乾隆三十八年更名乌鲁木齐都统,开辟了红山、水磨沟温泉等城市胜景,奠定了今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和风光旅游事业的基础。乌鲁木齐都统的管辖范围绝不止于今乌鲁木齐市,其职权有类于唐朝的北庭、伊西节度使,号令唐伊、西、庭三州故境,即包括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在内。索诺木策凌在任时期大有作为,常巡行所属各地,重视古迹保护更是他的特殊贡献。北庭古城属济木萨绿营兵屯垦区范围。据傅恒主持修纂,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古城中出土了古碑两方,当时正在古城(今奇台县城)巡视军务的索诺木策凌闻讯后,立即停止了军务视察,赶到出土地现场,最先辨认出上刻“金满县令”四字,嘱令当地妥善保存,这就是著名的《金满县碑》。也许是由于当地有文化的人太少,甚至连宣纸、墨拓也有问题,他并没有下令拓摹,也没有对此碑进一步考证。尽管如此,却是北庭古代文明重新被发现的历史前兆,索诺木策凌功不可没。此人仕宦经历初本一路顺风,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已升任伊犁将军,成为西域新疆最高军政官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又调任盛京将军,受命主政满族龙兴之地的今辽宁省,说明原本得到清朝很高的信任,不知是受到政敌的诬陷,还是确有个人污点,乾隆四十七年受控贪污,赐自尽,落了个悲惨结局。
乾隆四十一年(1776)济木萨由镇西府台县治下改隶于迪化州阜康县,同年撤巡检,设县丞,辅佐知县管理四十里井以东至白杨河、大泉之间地区的民政。其建置品阶升至副县级,已具备建县的雏形。进入嘉庆年间,又有大批名士、学人贬流西域,被称为我国西北史地之学的奠基人祁韵士与清代最大的西北史地学泰斗徐松都相继出关。而当时主政西陲,任伊犁将军的大员又是著名儒将松筠,正志在编写新疆地方志,双方合作,我国的西北史地学术之花遂绽开异蕾。松筠,蒙古正蓝旗人,语兼满、汉,学贯经史,为政突出文化建设,曾于嘉庆七年、嘉庆十四年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第二次任期较长,祁韵士、徐松都被收罗幕下,编成了《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识略》等开创性的西域学专著。而祁韵士戍边时,年岁已老,其成就局限于文献研究,徐松却正当盛年,重视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其名著《西域水道记》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当他来到尚未独立建县的济木萨之后,又完整地记录了金满残碑的大、小、形制及其残存碑文,内记:“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残碑碑石,裂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周仕珪等云中辇路,三行曰行户曹参军上柱国赵,四行曰□(阙一字)惠敬泰摄金满县令,五行曰姑藏(臧)府果毅都尉,六行曰乘帝师之,七行曰补迦;一石六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而为□承义郎,三行曰登仕郎摄录事,四行曰昭武校尉凉,五行□州退魏□,六行曰有准绳。”
这是北庭古城重新发现的重要记录。此碑现已荡然无存,吉木萨尔当地资深历史工作者王秉诚根据徐松的记载,参稽其他史料将金满县碑文复原如下表:
如果不是徐松留下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录,北庭古城也许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疑谜。但现在谜团已完全解开了。这是因为,唐北庭都护府、庭州、金满县衙,虽然在建置级别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却同治一城。足以说明护堡子破城废墟就是唐北庭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后来又成为北庭回鹘的夏都,改称别失八里,在《西域水道记》中我们又发现了如下记载:“护堡子破城有元造像碣石,上截作番字,下截刻僧像,疑是元时所造。”这件珍贵的造像碣石今天也早已不复存在了。但上面写的“番”字无疑就是古回鹘文,应是北庭回鹘到元代畏兀儿时期的遗物。至此,北庭古代文明的辉煌开始浮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徐松之后,另一部值得提及的名著是李光廷所著《汉西域图考》,总七卷。特点也是非常重视实地踏勘。他以两汉书《西域传》为基础,逐一与今山川、城镇地名相比对,明确指出济木萨,即金满古地名的历史继承,金满是济木萨的急读,济木萨是金满的缓读,他还指出汉、唐两金满地望不同,北庭古城是唐金满县的所在地,汉金满则在唐金满城南,临天山一带。从而为我们寻找汉金满城提供了可靠的航标。
道光、咸丰朝之后,清朝国势开始转衰,这时内优、外患频仍。主政西陲的官员忙于加强塞守,镇压叛乱,一度中断了寻觅古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流放到新疆,并曾到过济木萨的名士很多,诸如道光朝的林则徐,诗人史善长等,但大都是匆匆过客,虽有些诗文留影,对于北庭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并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至同治年间,又发生了内部动乱与阿古柏的武装入侵,清朝失去包括吉木萨尔在内的广大新疆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约十余年,其间战火纷飞,尸横遍地,千里为墟,北庭古城的历史辉煌又一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至左宗棠、刘锦棠挥戈出关,动乱结束,阿古柏入侵政权覆灭,沙俄交还伊犁,新疆建省之初,各地仍人口萧条,满目疮痍,元气仍未得到恢复。历任主政官吏的首要职责就在于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无暇顾及古代遗存和古代文物的保护,尽管这时,清朝正在边疆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改革,全面实行郡县化。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恺安城,改名孚远城,光绪二十八年(1902)县7丞升格为县,县治孚远城,遂以孚远为县名,隶于镇迪道迪化府,后来隶属于镇迪道。但初建县的孚远,文士奇缺。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编书局,下令全国各县,都要编写乡土志,已知新疆乡土志约30种(包括已刊清《新疆乡土志二十九种》及未刊之《奇台乡土志》手抄本一种,现藏甘肃图书馆),其中就包括光绪年间手抄本《孚远乡土志》。该书编写粗糙,无可称道,例如在历史沿革部分,竟云:“年代久远,沿革无征。”在政绩录部分又云:“官斯土者,前代..无文可考。”在耆旧录中再次强调“孚邑地方僻陋,既无大儒,亦无畸士”。这些明显有违史实。唯一留下的仍是有关护堡子破城的记载,但也不过短短数句:“县城之北三十里有破城,城垣残缺,形迹犹存。相传唐时征西,筑城故址。同治初元,尚有破铁钟在焉,半埋土中,半露地面,大唐年号,点画犹明,殆后被土人击碎入炉,铸为农器,销毁无存,此外别无古迹。”说明同治初年,古城中仍有铸有大唐年号的古钟出土,但已被毁,铸为农器。看来这位修志者,文化水平不高,前朝鸿儒纪晓岚、徐松的著作他都没有看到,并未认出这就是著名的北庭古城。这时素以史学称长于世的我国,却尽失所长,反映了历史的倒退。
与我国对古代文明的淡漠恰成鲜明对比,西方的来华探险热却正在此时兴起,新疆就是其中的重点。其中著名的人物不胜枚举,诸如率先到达喀什噶尔,著有《天山游记》的俄籍哈萨克人乔坎·瓦里汉诺夫(1835~1865年);楼兰古城的最早发现者、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年);多次来华,敦煌千佛洞的发现者和劫掠者、系统考察了和田、米兰、吐鲁番、库车等地文物古迹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年);曾造访敦煌、高昌、库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率先到达高昌、库车进行石窟寺考古的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寇克;以高昌考古为中心,兼及楼兰、库车研究的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年)、橘瑞超(1890~1968年)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入华来疆。这些外国探险家的活动,都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大批我国珍贵文物流失国外,固然是其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但正面影响也必须承认,恰恰是通过他们的“探险”活动,和田、库车、焉耆、楼兰、尼雅、高昌、敦煌等古代文明的地区性中心大都相继被发现;南疆地区,包括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以及河西走廊的古代辉煌已逐渐为世所知;而足以同以上地区性文明中心相媲美的北庭,却长期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外国探险家中到过吉木萨尔者早期主要是沙俄军官,最早到达天山北麓者乃沙俄参谋总部的陆军中校军官索斯诺夫斯基。他于光绪元年(1875)率领地图绘制师马图索夫斯基、摄影家波亚尔斯基等经哈密、巴里坤最后到古城,沿途绘制了地图。清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正在策划收复新疆,向俄国谈判购粮500万斤,自斋桑湖运至古城,生物地理学家彼甫佐夫率领了百名哥萨克士兵,押送第一批军粮到达古城,经吉木萨尔,于1876年7月1日到达古城。光绪三年(1877)沙俄总参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赴古城,虽为清朝当局所拒,却发现了活动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野马,为此前欧洲学者所未知,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俄人贝尔上校光绪十三年(1887)从北京出发,经兰州、安西、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到达喀什噶尔,光绪十四年(1888)沙俄格鲁木·格里施买罗弟兄探察队再次赴古城寻找这种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得到两个标本而归。以上数人仅仅是途中经行,并未认识到北庭的重要性;但日人橘瑞超和英人斯坦因则不然。橘瑞超(1890~1968年)乃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年)出资组成的大谷探险队主要成员,1908年6月,西本愿寺组成大谷中亚探险队,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进行第二次赴中亚探险。他们从日本先到北京,经张家口于7月底抵库伦(今乌兰巴托),为新疆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遂南下横穿蒙古草原,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阿尔泰山,越过大阿拉山口,进入准噶尔盆地。于10月7日抵达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北庭古城遗址。因预先通知了迪化布政使王树柟,得以对北庭古城测绘了最为原始的草图,对于今天认识遭严重破坏的北庭古城,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启迪作用。橘瑞超等人还雇用了当地20余民工,对古城进行了七八日的发掘。所获文物满满8筐,由毛驴驮往乌鲁木齐,野村荣三郎护送运往日本。其余部分留在旅顺,现由大连博物馆收藏。其正式公布的所获文物并不完全,主要有莲纹方砖、荷纹方砖、“开元通宝”、“乾元通宝”,还有陶盆、陶罐、陶俑等;其中还有在北庭古城盗走的一块碑石。 “碑后表面沙砾剥落严重,但‘唐中宗二年’几个字,字迹尚很清楚。是否是‘龙兴’、‘西寺’碑的遗物,目前尚不能肯定。”①有人认为此碑已流落到旅顺博物馆,尚有待证实。斯坦因是唯一到过吉木萨尔的西方探险家,1914年10月他先后经巴里坤、古城,到达吉木萨尔,考察了北庭古城遗址,斯坦因测定了城的方位,绘制了平面图(见图 1),并初步确定了城中重要的地点。
尽管此图仍较粗糙,“马面、敌台、角楼城门等部有缺失”,仍不失为北庭古城第一个科学的平面图,应当充分肯定其考察的价值。斯坦因在北庭曾进行发掘,虽然“在那里一无所获。残破的城墙上密布大小洞穴,说明附近的农民早已惯于取土作为肥料”,却正确地断定这里就是唐代北庭都护府。在其所著《亚洲腹地》一书中指出:“这是古代此地都会的故址。中国统治中亚的时候,历史所常见到的金满以及北庭,即是此地。”转道南下哈拉和卓,匆匆结束了北庭之行。斯坦因是来华探险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西方世界给予他高度的荣誉,称之为东方学之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国则斥之为窃宝大盗。在我看来,从他短短的未成功考察所得结论判断,不能不佩服其犀利的学术目光。应当在惋惜北庭文物流失的同时,充分肯定这次考察的重要意义。
今吉木萨尔县清代名为济木萨,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已创设了济木萨巡检,起初主要主持当地绿营兵的军屯,后来随着民户的增多,也兼管当地民政。却直到清末建省前,才上升为县级规格,此前只是相邻奇台、阜康二县的属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始创镇西府,以原西路军大本营所在地巴尔库勒城(今巴里坤)为府治,实行郡县化。下辖宜禾、奇台两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创置了奇台、宜禾二县,同年又创置了迪化直隶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市汉城迪化,济木萨初归奇台县管辖。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阜康建县,昌吉、绥来、阜康等三县皆划归迪化直隶州,自此以后,济木萨又转隶阜康县管辖。由于这些新设诸府、州、县的汉人移民大都来自甘肃,在行政上初由甘肃省遥领,而又兼受驻守巩宁城的清军长官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事实上是双重管辖。随着乌鲁木齐都统权力的加重,后来,甘肃省的遥领形同虚设,乌鲁木齐都统逐渐全面接管了天山东段诸州县的管辖权。
乾隆三十三年秋七月至三十六年冬十月期间(1768~1771年),一代大名士纪晓岚获咎流放乌鲁木齐。纪晓岚(1724~1805年),名昀,字晓岚,以字行。又字春帆,晚号石生,《清史稿》卷320有传。原籍江苏省上元县(今南京市),明永乐年间移居北方,清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1724年8月3日)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河间府献县。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率真,幽默风趣,学识、文采都秀出群伦。曾主持纂修《大清会典》、清《三通》、《清高宗实录》等,参与《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诸书编写,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以手撰提要而名垂青史,出色地完成了我国文化史上这一空前伟业。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嘉庆十年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3月14日)以礼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高位病逝于北京。纪晓岚以其崇高声望,在戍期间,得到主政官员的高度礼遇。“乌鲁木齐”当时还不是一个城市名,而是一个地区名,所指乃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地区,即包括迪化州和镇西府全境,留有《乌鲁木齐赋》、《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资料。他在戍期间,曾亲临当时仍被称为护堡子破城子的北庭古城,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第11、第12卷《槐西杂志》中惊讶地记载了这座古城“周四十里”的宏大规模,比今天的范围要大得多。并根据史书所记将它正式确定即唐北庭古城,唐朝北庭大都护府治所。纪晓岚还细心地测量了城墙的厚度,留下了“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的原始记录。当时城内完整的建筑遗存似乎还不少,所见“旧瓦亦广尺余,长一尺五六寸”,城中还发现了一座佛寺,“寺已圮,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皆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唯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所出寺中铁钟,高过人头,足见寺院规模不小。现存古籍亦印证,庭州金满县境至少有三座规模宏大的佛寺,除悟空寄经的龙兴寺、宋使王延德憩足的高台寺外,北庭城中还有一座应运大宁寺,这座圮寺,是否就是该寺遗址?寺中所出连纪晓岚都不认识,类似八分书的铁钟铭文必非汉文,很可能是北庭回鹘时期流行的回鹘文。纪晓岚还记载:“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额鲁特云,此城皆以火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盖在准噶尔前矣。”史书中透露,东察合台歪思汗在位时期曾与新兴的准噶尔蒙古连年激战,他之所以西迁亦力把里,同战争失利有关。纪晓岚的这段记载,还可进一步印证别失八里的废弃,是一场恶战的结果。但是,纪晓岚的考察也不是没有失误。例如他说:“济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将北庭古城的兴建归功于“李卫公”,即唐贞观初年平定东突厥的大将李靖,显然是不对的,此人根本没有到过西域。
清朝管理天山东段的最高官员起初称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更名为乌鲁木齐都统,官位仅次于总管西域新疆的伊犁将军。所任命的首任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都是索诺木策凌。他是一个在旗蒙古人,兼通满、蒙、汉文字,非常能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率领部众始建满城巩宁,规模更大于汉城迪化,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竣工,成为满洲八旗及其随军家眷的驻地。乾隆三十八年更名乌鲁木齐都统,开辟了红山、水磨沟温泉等城市胜景,奠定了今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和风光旅游事业的基础。乌鲁木齐都统的管辖范围绝不止于今乌鲁木齐市,其职权有类于唐朝的北庭、伊西节度使,号令唐伊、西、庭三州故境,即包括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在内。索诺木策凌在任时期大有作为,常巡行所属各地,重视古迹保护更是他的特殊贡献。北庭古城属济木萨绿营兵屯垦区范围。据傅恒主持修纂,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古城中出土了古碑两方,当时正在古城(今奇台县城)巡视军务的索诺木策凌闻讯后,立即停止了军务视察,赶到出土地现场,最先辨认出上刻“金满县令”四字,嘱令当地妥善保存,这就是著名的《金满县碑》。也许是由于当地有文化的人太少,甚至连宣纸、墨拓也有问题,他并没有下令拓摹,也没有对此碑进一步考证。尽管如此,却是北庭古代文明重新被发现的历史前兆,索诺木策凌功不可没。此人仕宦经历初本一路顺风,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已升任伊犁将军,成为西域新疆最高军政官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又调任盛京将军,受命主政满族龙兴之地的今辽宁省,说明原本得到清朝很高的信任,不知是受到政敌的诬陷,还是确有个人污点,乾隆四十七年受控贪污,赐自尽,落了个悲惨结局。
乾隆四十一年(1776)济木萨由镇西府台县治下改隶于迪化州阜康县,同年撤巡检,设县丞,辅佐知县管理四十里井以东至白杨河、大泉之间地区的民政。其建置品阶升至副县级,已具备建县的雏形。进入嘉庆年间,又有大批名士、学人贬流西域,被称为我国西北史地之学的奠基人祁韵士与清代最大的西北史地学泰斗徐松都相继出关。而当时主政西陲,任伊犁将军的大员又是著名儒将松筠,正志在编写新疆地方志,双方合作,我国的西北史地学术之花遂绽开异蕾。松筠,蒙古正蓝旗人,语兼满、汉,学贯经史,为政突出文化建设,曾于嘉庆七年、嘉庆十四年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第二次任期较长,祁韵士、徐松都被收罗幕下,编成了《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识略》等开创性的西域学专著。而祁韵士戍边时,年岁已老,其成就局限于文献研究,徐松却正当盛年,重视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其名著《西域水道记》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当他来到尚未独立建县的济木萨之后,又完整地记录了金满残碑的大、小、形制及其残存碑文,内记:“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残碑碑石,裂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周仕珪等云中辇路,三行曰行户曹参军上柱国赵,四行曰□(阙一字)惠敬泰摄金满县令,五行曰姑藏(臧)府果毅都尉,六行曰乘帝师之,七行曰补迦;一石六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而为□承义郎,三行曰登仕郎摄录事,四行曰昭武校尉凉,五行□州退魏□,六行曰有准绳。”
这是北庭古城重新发现的重要记录。此碑现已荡然无存,吉木萨尔当地资深历史工作者王秉诚根据徐松的记载,参稽其他史料将金满县碑文复原如下表:
如果不是徐松留下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录,北庭古城也许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疑谜。但现在谜团已完全解开了。这是因为,唐北庭都护府、庭州、金满县衙,虽然在建置级别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却同治一城。足以说明护堡子破城废墟就是唐北庭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后来又成为北庭回鹘的夏都,改称别失八里,在《西域水道记》中我们又发现了如下记载:“护堡子破城有元造像碣石,上截作番字,下截刻僧像,疑是元时所造。”这件珍贵的造像碣石今天也早已不复存在了。但上面写的“番”字无疑就是古回鹘文,应是北庭回鹘到元代畏兀儿时期的遗物。至此,北庭古代文明的辉煌开始浮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徐松之后,另一部值得提及的名著是李光廷所著《汉西域图考》,总七卷。特点也是非常重视实地踏勘。他以两汉书《西域传》为基础,逐一与今山川、城镇地名相比对,明确指出济木萨,即金满古地名的历史继承,金满是济木萨的急读,济木萨是金满的缓读,他还指出汉、唐两金满地望不同,北庭古城是唐金满县的所在地,汉金满则在唐金满城南,临天山一带。从而为我们寻找汉金满城提供了可靠的航标。
道光、咸丰朝之后,清朝国势开始转衰,这时内优、外患频仍。主政西陲的官员忙于加强塞守,镇压叛乱,一度中断了寻觅古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流放到新疆,并曾到过济木萨的名士很多,诸如道光朝的林则徐,诗人史善长等,但大都是匆匆过客,虽有些诗文留影,对于北庭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并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至同治年间,又发生了内部动乱与阿古柏的武装入侵,清朝失去包括吉木萨尔在内的广大新疆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约十余年,其间战火纷飞,尸横遍地,千里为墟,北庭古城的历史辉煌又一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至左宗棠、刘锦棠挥戈出关,动乱结束,阿古柏入侵政权覆灭,沙俄交还伊犁,新疆建省之初,各地仍人口萧条,满目疮痍,元气仍未得到恢复。历任主政官吏的首要职责就在于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无暇顾及古代遗存和古代文物的保护,尽管这时,清朝正在边疆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改革,全面实行郡县化。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恺安城,改名孚远城,光绪二十八年(1902)县7丞升格为县,县治孚远城,遂以孚远为县名,隶于镇迪道迪化府,后来隶属于镇迪道。但初建县的孚远,文士奇缺。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编书局,下令全国各县,都要编写乡土志,已知新疆乡土志约30种(包括已刊清《新疆乡土志二十九种》及未刊之《奇台乡土志》手抄本一种,现藏甘肃图书馆),其中就包括光绪年间手抄本《孚远乡土志》。该书编写粗糙,无可称道,例如在历史沿革部分,竟云:“年代久远,沿革无征。”在政绩录部分又云:“官斯土者,前代..无文可考。”在耆旧录中再次强调“孚邑地方僻陋,既无大儒,亦无畸士”。这些明显有违史实。唯一留下的仍是有关护堡子破城的记载,但也不过短短数句:“县城之北三十里有破城,城垣残缺,形迹犹存。相传唐时征西,筑城故址。同治初元,尚有破铁钟在焉,半埋土中,半露地面,大唐年号,点画犹明,殆后被土人击碎入炉,铸为农器,销毁无存,此外别无古迹。”说明同治初年,古城中仍有铸有大唐年号的古钟出土,但已被毁,铸为农器。看来这位修志者,文化水平不高,前朝鸿儒纪晓岚、徐松的著作他都没有看到,并未认出这就是著名的北庭古城。这时素以史学称长于世的我国,却尽失所长,反映了历史的倒退。
与我国对古代文明的淡漠恰成鲜明对比,西方的来华探险热却正在此时兴起,新疆就是其中的重点。其中著名的人物不胜枚举,诸如率先到达喀什噶尔,著有《天山游记》的俄籍哈萨克人乔坎·瓦里汉诺夫(1835~1865年);楼兰古城的最早发现者、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年);多次来华,敦煌千佛洞的发现者和劫掠者、系统考察了和田、米兰、吐鲁番、库车等地文物古迹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年);曾造访敦煌、高昌、库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率先到达高昌、库车进行石窟寺考古的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寇克;以高昌考古为中心,兼及楼兰、库车研究的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年)、橘瑞超(1890~1968年)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入华来疆。这些外国探险家的活动,都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大批我国珍贵文物流失国外,固然是其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但正面影响也必须承认,恰恰是通过他们的“探险”活动,和田、库车、焉耆、楼兰、尼雅、高昌、敦煌等古代文明的地区性中心大都相继被发现;南疆地区,包括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以及河西走廊的古代辉煌已逐渐为世所知;而足以同以上地区性文明中心相媲美的北庭,却长期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外国探险家中到过吉木萨尔者早期主要是沙俄军官,最早到达天山北麓者乃沙俄参谋总部的陆军中校军官索斯诺夫斯基。他于光绪元年(1875)率领地图绘制师马图索夫斯基、摄影家波亚尔斯基等经哈密、巴里坤最后到古城,沿途绘制了地图。清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正在策划收复新疆,向俄国谈判购粮500万斤,自斋桑湖运至古城,生物地理学家彼甫佐夫率领了百名哥萨克士兵,押送第一批军粮到达古城,经吉木萨尔,于1876年7月1日到达古城。光绪三年(1877)沙俄总参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赴古城,虽为清朝当局所拒,却发现了活动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野马,为此前欧洲学者所未知,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俄人贝尔上校光绪十三年(1887)从北京出发,经兰州、安西、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到达喀什噶尔,光绪十四年(1888)沙俄格鲁木·格里施买罗弟兄探察队再次赴古城寻找这种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得到两个标本而归。以上数人仅仅是途中经行,并未认识到北庭的重要性;但日人橘瑞超和英人斯坦因则不然。橘瑞超(1890~1968年)乃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年)出资组成的大谷探险队主要成员,1908年6月,西本愿寺组成大谷中亚探险队,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进行第二次赴中亚探险。他们从日本先到北京,经张家口于7月底抵库伦(今乌兰巴托),为新疆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遂南下横穿蒙古草原,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阿尔泰山,越过大阿拉山口,进入准噶尔盆地。于10月7日抵达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北庭古城遗址。因预先通知了迪化布政使王树柟,得以对北庭古城测绘了最为原始的草图,对于今天认识遭严重破坏的北庭古城,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启迪作用。橘瑞超等人还雇用了当地20余民工,对古城进行了七八日的发掘。所获文物满满8筐,由毛驴驮往乌鲁木齐,野村荣三郎护送运往日本。其余部分留在旅顺,现由大连博物馆收藏。其正式公布的所获文物并不完全,主要有莲纹方砖、荷纹方砖、“开元通宝”、“乾元通宝”,还有陶盆、陶罐、陶俑等;其中还有在北庭古城盗走的一块碑石。 “碑后表面沙砾剥落严重,但‘唐中宗二年’几个字,字迹尚很清楚。是否是‘龙兴’、‘西寺’碑的遗物,目前尚不能肯定。”①有人认为此碑已流落到旅顺博物馆,尚有待证实。斯坦因是唯一到过吉木萨尔的西方探险家,1914年10月他先后经巴里坤、古城,到达吉木萨尔,考察了北庭古城遗址,斯坦因测定了城的方位,绘制了平面图(见图 1),并初步确定了城中重要的地点。
尽管此图仍较粗糙,“马面、敌台、角楼城门等部有缺失”,仍不失为北庭古城第一个科学的平面图,应当充分肯定其考察的价值。斯坦因在北庭曾进行发掘,虽然“在那里一无所获。残破的城墙上密布大小洞穴,说明附近的农民早已惯于取土作为肥料”,却正确地断定这里就是唐代北庭都护府。在其所著《亚洲腹地》一书中指出:“这是古代此地都会的故址。中国统治中亚的时候,历史所常见到的金满以及北庭,即是此地。”转道南下哈拉和卓,匆匆结束了北庭之行。斯坦因是来华探险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西方世界给予他高度的荣誉,称之为东方学之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国则斥之为窃宝大盗。在我看来,从他短短的未成功考察所得结论判断,不能不佩服其犀利的学术目光。应当在惋惜北庭文物流失的同时,充分肯定这次考察的重要意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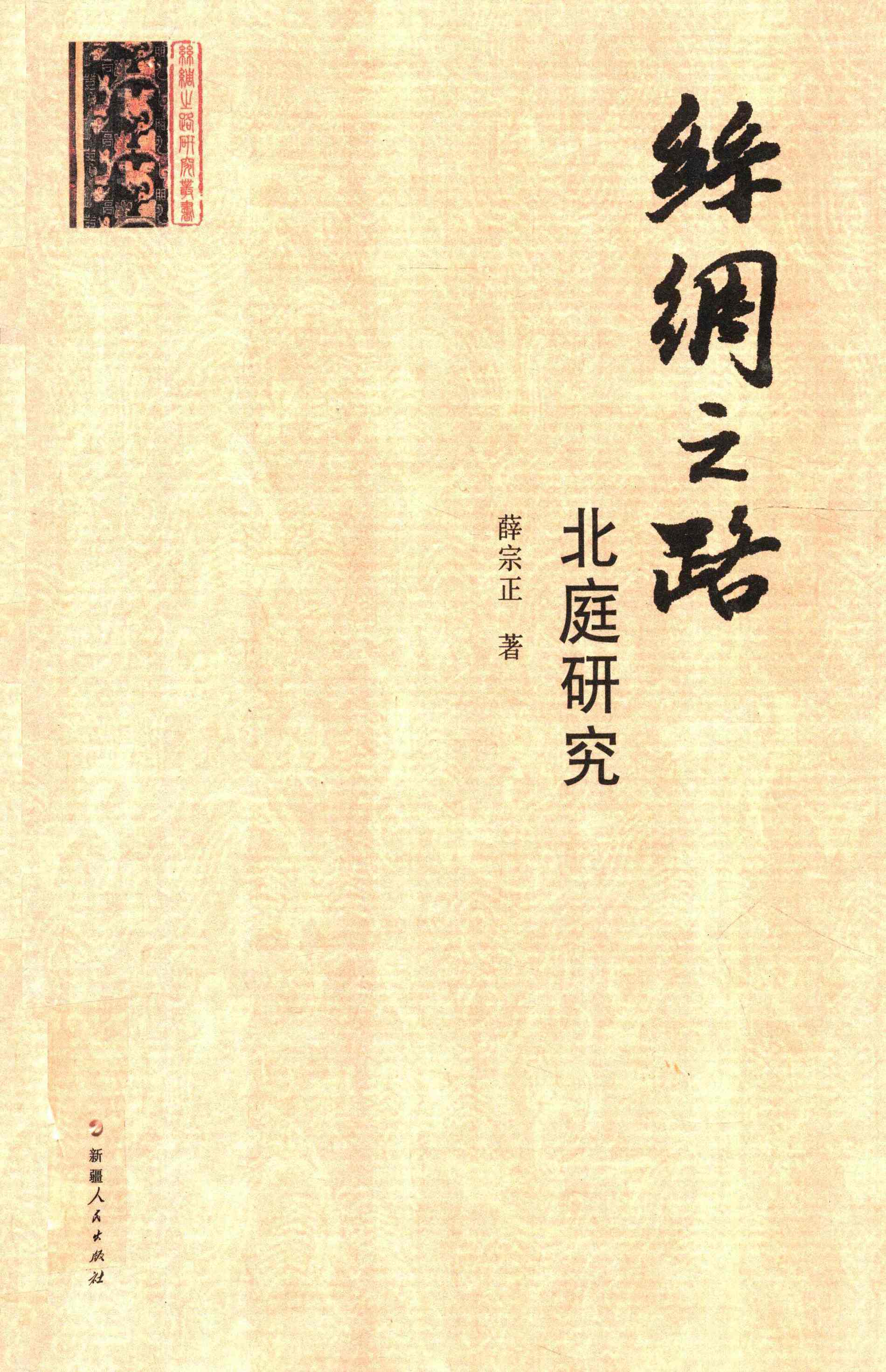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新疆地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