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艺术创新:交融与变异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58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交融与变异 |
| 分类号: | J209.45 |
| 页数: | 6 |
| 页码: | 299-304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在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绘画、雕塑艺术和乐舞艺术与异质艺术间的杂交可以采取移植和摹仿的不同方式,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均对异质艺术有吸纳性特征决定的。 |
| 关键词: | 艺术创新 艺术交融 艺术变异 |
内容
在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绘画、雕塑艺术和乐舞艺术与异质艺术间的杂交可以采取移植和摹仿的不同方式,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均对异质艺术有吸纳性特征决定的。但在异质艺术渗透时,本民族的艺术还保留有稳定性,也正是这种稳定性使本民族艺术保持了其“基本结构和特征”。无论是古代西域艺术,还是近代以来维吾尔等新疆各民族的艺术都是如此。但是吸纳异质艺术与保持本民族艺术的稳定性并不矛盾,吸纳异质文化艺术养分并不是失去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固有特色,而保持本民族文化艺术的“稳定性原则”,也并不意味着拒绝异质文化艺术的影响和渗透。在交融和变异中促成新质文化艺术的重建,这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艺术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交融和变异才能促成艺术创新,并进一步保持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基本结构和特征。
研究者习惯把丝绸之路上西域诸绿洲的佛教艺术分为于阗佛教艺术、龟兹佛教艺术、高昌佛教艺术和鄯善佛教艺术等,就是因为诸绿洲的佛教艺术在吸纳外来佛教艺术的过程中,经过交融和变异走向成熟,从而保持了艺术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缘故。这些绿洲的佛教艺术几乎都是在唐王朝统一西域期间走向成熟,7~8世纪也就成了西域佛教艺术成熟期的标志。以龟兹佛教为例,无论是佛教石窟建筑,还是佛教雕塑、壁画均摆脱了早期摹仿印度佛教艺术的痕迹,出现了龟兹式的佛教艺术。3~4世纪形成的龟兹石窟中的中心柱式洞窟都曾受到印度支提式洞窟和萨珊波斯建筑的影响,但到7世纪时,中心柱式洞窟的内部建筑结构和壁画布局都呈现出龟兹式特征:“部分洞窟内部空间扩大,主室券顶增高,正壁上部略向前倾,增加了正壁主尊的威严感。主室券顶与两壁连接处出现叠涩线与枭混结合的结构,有的洞窟在甬道顶部也使用了此种结构。后室相应扩大,设涅槃台和涅槃塑像的洞窟增多。主室正壁原来的山峦形的影塑为壁画所代替,整个中心柱式洞窟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布局紧凑密集,色调绚丽斑斓。”①这种充分考虑龟兹地区山体岩石酥松易于坍塌因素,又利于礼佛和观像等佛事活动方便的中心柱式洞窟形制较印度支提式洞窟发生了较大变异,反映的是龟兹式石窟建筑的基本结构和特征。
龟兹壁画艺术到了7世纪左右形成一种龟兹独有的菱形构图法,即在每一个菱形格内绘一个佛教故事。龟兹石窟中心柱式洞窟券顶就采用了菱形构图,这也成为龟兹佛教壁画的主要构图形式。成熟期的菱格构图在洞窟券顶一侧呈6层12列,有70余个画面单元,两壁总计140余个画面单元,每个单元绘制一个佛教故事,绝大部分为因缘故事,旨在弘扬佛的业力和神通。虽然在绘画技法上仍采用印度传过来的晕染法(即凹凸法),线条亦是“屈铁盘丝”技法,但到了龟兹,又有了创新,绘画技法发生重大变化。龟兹式晕染法有单面晕染和双面晕染等多种,由于晕染较夸张,立体感较强。成熟期的龟兹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出现身材修长、五官集中的本土化倾向,即使是壁画中的金刚力士、武士、龙王的服饰也采用了西域式样。龟兹壁画的变异还表现在出现了本地世俗供养人像,在隋唐时期,龟兹石窟壁画中出现了龟兹王及其王族供养人像。如果将成熟期的龟兹国王及王后供养像与龟兹早期佛传故事中的印度国王和王后像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异。克孜尔石窟第205窟中的龟兹国王和王后从服饰上看,国王上穿翻领对襟长大衣,下穿裹腿裤和尖头靴,右手握宝剑,左手持香炉,身后佩长剑;王后身穿翻领束腰短袖外套,双手持花珠链。国王头发从中间分开,长至耳下,王后头戴油帽。龟兹国王的这种服饰、发型与库车属7世纪昭怙厘寺出土的龟兹乐舞舍利盒中弹竖箜篌、凤首箜篌和击鼓男子的服饰、发型如出一辙,可见是龟兹本地男子的装束。而克孜尔石窟第22窟属4~5世纪的石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则是印度人,壁画亦是龟兹早期摹仿佛传故事之作。此壁画中的古印度国王阿阇世头戴三珠冠,有头光,后部有华盖。王后束高髻,上插三朵花,亦有头光。国王和王后均裸露上身,只是颈部、臂部、手腕部有装饰物。这与龟兹国王、王后的装饰打扮是完全不同的。印度佛教中常见裸体形象,与印度佛教主张通过极端的纵欲达到极端的出世和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有关,因此在佛教壁画和雕塑中性力崇拜、裸体表现一直很突出。佛教传入西域,这种表现方式仍然存在,但往往被加以改造。越到后期,裸体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尽管如压条、阴刻等键陀罗、秣菟罗雕塑技法仍在采用,但人物面部的平面化、服饰的繁褥化却是龟兹式的。
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壁画也反映了回鹘佛教艺术从摹仿到交融、变异的创新过程。回鹘西迁高昌后,在佛教艺术上深受晚唐汉传佛教艺术的影响,9~10世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回鹘王“非常体面地穿垂至脚面的宽大长袍,其袖子宽而长,必须卷起袖口才能露出双手。长衫的领子始终是圆形的。衣襟开在两侧,或者是以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开在前部,有时长袍的开襟于肋部亦直开到大腿之下。衣服始终是用带有几何图案或形象图案(云彩、花卉、飞禽)的华丽料子剪裁的”①。高昌地区自魏晋时期起就是河西汉族的聚居地,回鹘西迁前又属唐西州地区,主要居民仍是汉族,因此壁画中的回鹘王身着汉式长袍也极为正常。而随着蒙元时代的到来,汉族居民也逐渐被同化,佛教壁画中的供养人回鹘官员服饰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种身着蒙古服饰的官员形象。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壁画中的回鹘供养人穿着蒙古式服装,这是13世纪回鹘官员的形象。这种装束显然与蒙古人在畏兀儿地区推行蒙古制度文化有关。但是在一种摹仿艺术中仍能发现其发式是典型的回鹘式:“头发都披到肩后,束成光滑的一绺沿背部而下垂,常常是一直垂到腰带的高度,一绺头发有时是从耳朵前边出现,垂在面庞的两侧。这些上层人士全都留短须和相当细的下垂髭,大家在下巴之下还可以看到一种‘帝须’。一顶高高的挺直的三垂冠用两条窄窄的红带子拴在颌下。”①回鹘人的这种发式见于《五代史记》,其中记载:“(回鹘)其可汗常楼居,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文献证实,回鹘达官贵人才留这种发式。效仿唐文化和蒙古人推行蒙古化均未改变回鹘文化艺术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普通供养人无论是长相还是服饰都明显在体现一种回鹘风。高昌一座寺庙里的一群手持花束的供养人穿的是垂在膝盖的短袍,袍袖狭窄,裤子伸进长统靴中,靴口翻卷,腰部挂着各种物品,短髭短发,完全是回鹘式打扮了。仅从这些供养人壁画中,发现“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随着时间之推移,自然产生了融合混成之势。这种融合混成就是回鹘文化的特征”②。融合混成的结果产生的当然是回鹘文化艺术的新品种。
在乐舞艺术方面,同一地域的同一乐舞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反映的就是交融与变异造成的不同关系。《清书·音乐志》记载,隋初龟兹乐有三种,即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同是一种龟兹乐为何出现三种名称?这不能不从龟兹乐传入中原的不同时代特征谈起。西国龟兹指的是北周时从西面的龟兹传来的乐舞,它是随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下嫁北周武帝宇文邕传入的。突厥可汗是把龟兹乐队(包括舞伎、歌伎)作为陪嫁带到长安的。这是原汁原味的龟兹乐舞。而齐朝龟兹是北齐保存下来的龟兹乐舞,由于传入中原时间长,在传播中明显发生了重大变异。之前,首先是后梁吕光伐龟兹时将龟兹乐带入凉州,此后又杂以秦声,之后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占据河西后又将龟兹乐带入华北的平城。北魏分裂后,北齐的文宣帝也十分喜爱龟兹乐,《册府元龟》说他“每弹尝自击胡鼓和之”。总之,在隋朝建立前,龟兹乐已在河西和中原地区流传了200多年,龟兹乐自然也就受到北方鲜卑等游牧部落和汉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深刻影响。这样就大大改变了龟兹乐舞的本来面貌。土龟兹乐舞可能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可汗之女为皇后之前就存在于长安的龟兹乐舞了。从传入时间看,齐朝龟兹在中原流传时间最长,其源头可追溯到4世纪末吕光伐龟兹得龟兹乐,之后是土龟兹,它比北周武帝时的西国龟兹也早。从乐舞传入的文献记载看,北魏宣武帝时,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鼓、铜钹等龟兹乐器已出现在宫廷乐队中,铿锵的龟兹舞也深得王族喜爱。到北齐时,龟兹乐在中原出现繁盛景象,《隋书·音乐志》载:“杂乐西凉、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仅从龟兹乐器看,已从北魏时的五六种,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二十种,因为此时龟兹乐队的规模在二十人左右。龟兹乐舞东传的事实表明:一是任何一种异质艺术融入中原本土艺术都有所变形,即适应性变化,龟兹乐中“杂以秦声”就是乐舞艺术变形的结果,最终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乐舞发生交融;二是随时代的变迁,龟兹乐舞在交融变形中并未失去原色,鲜卑、汉等民族的乐舞的融入,只能是丰富了龟兹乐舞,而不是相反;三是龟兹乐舞等异质艺术、介入中原人的艺术审美系统,导致审美情趣的变化,从宫廷到民间,欣赏惯了中原的轻歌曼舞,而龟兹乐舞的豪放、激越,自然给予全新的视听感受。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艺术与中原艺术的交融是各民族审美意识交流、融合和渗透的结果。特别是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绿洲农耕社会和中原农业社会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是重社会、重伦理,这种农耕文化也是一种宗法文化,表现在审美意识上是伦理的、观念的、神性的。特别是唐统一西域以来,西域绿洲除流行佛教外,中原的道教和儒家文化也盛极一时,高昌、龟兹、于阗等绿洲居民同样视儒、道、佛为精神支柱。即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因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表现出审美意识的不同,但在唐代这样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农耕文化向游牧文化,西域文化向中原文化都大大靠近了,盛唐时出现的“华夷一家”的民族融洽氛围给艺术交融创造了条件。西域乐舞艺术那种粗犷、明快、激越的节奏给追求行云流水般韵律的中原乐舞无疑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时代精神的律动相协,同历史运行的步伐共振,和审美欣赏的需要相符,因此被中原广泛接受,继而吸收、融化。这也是汉族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在乐舞审美观念上的一次认同”①。西域艺术因地域、民族和时代发生的变异从更深层次上讲是由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决定的。处在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艺术,面对八方来风不能不对吸收的异质艺术作出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并非像对待一般事物那样只分出好与坏、优与劣那么简单,而是在考虑它的价值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价值判断所涉及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整体;它综合了这个艺术作品的各种积极侧面和消极侧面”②。西域佛教壁画吸收印度凹凸晕染法就是包含着对它的积极价值判断,因为这种技法较之平面着色,人物更有立体感,有强烈的表现力。龟兹乐舞中对外来乐器和昭武九姓舞蹈的吸收,也是由于这些乐器和乐舞丰富了龟兹乐舞的表现力和内涵,使之出现了质的飞跃。积极价值体现的是一种完美价值,“完美把艺术作品的和谐一致与它的价值模式、与它所具有的那些价值本身的深度联系在一起”③。审美判断是根据一个民族群体和个体的审美经验作出的。任何艺术都旨在激起受众的情感——在欣赏中产生愉悦感。在西域这个歌舞之乡,歌舞艺术不仅是欣赏的对象,而且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这种参与必然导致对外来歌舞艺术根据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作出筛选。柘枝舞、胡腾舞、胡旋舞就是根据龟兹人的审美经验经筛选后引进的,它们的韵律、节奏与本土艺术一拍即合。西域佛教雕塑、壁画艺术中一些本土化的人物形象和源自现实景物的天堂气象就是根据西域人物和景观,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做出的审美判断。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都会因空间和时间而发生变化。只有因地、因时作适宜性调整,才不至于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也才能在广泛的文化交融和变异中创造出新的艺术。
研究者习惯把丝绸之路上西域诸绿洲的佛教艺术分为于阗佛教艺术、龟兹佛教艺术、高昌佛教艺术和鄯善佛教艺术等,就是因为诸绿洲的佛教艺术在吸纳外来佛教艺术的过程中,经过交融和变异走向成熟,从而保持了艺术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缘故。这些绿洲的佛教艺术几乎都是在唐王朝统一西域期间走向成熟,7~8世纪也就成了西域佛教艺术成熟期的标志。以龟兹佛教为例,无论是佛教石窟建筑,还是佛教雕塑、壁画均摆脱了早期摹仿印度佛教艺术的痕迹,出现了龟兹式的佛教艺术。3~4世纪形成的龟兹石窟中的中心柱式洞窟都曾受到印度支提式洞窟和萨珊波斯建筑的影响,但到7世纪时,中心柱式洞窟的内部建筑结构和壁画布局都呈现出龟兹式特征:“部分洞窟内部空间扩大,主室券顶增高,正壁上部略向前倾,增加了正壁主尊的威严感。主室券顶与两壁连接处出现叠涩线与枭混结合的结构,有的洞窟在甬道顶部也使用了此种结构。后室相应扩大,设涅槃台和涅槃塑像的洞窟增多。主室正壁原来的山峦形的影塑为壁画所代替,整个中心柱式洞窟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布局紧凑密集,色调绚丽斑斓。”①这种充分考虑龟兹地区山体岩石酥松易于坍塌因素,又利于礼佛和观像等佛事活动方便的中心柱式洞窟形制较印度支提式洞窟发生了较大变异,反映的是龟兹式石窟建筑的基本结构和特征。
龟兹壁画艺术到了7世纪左右形成一种龟兹独有的菱形构图法,即在每一个菱形格内绘一个佛教故事。龟兹石窟中心柱式洞窟券顶就采用了菱形构图,这也成为龟兹佛教壁画的主要构图形式。成熟期的菱格构图在洞窟券顶一侧呈6层12列,有70余个画面单元,两壁总计140余个画面单元,每个单元绘制一个佛教故事,绝大部分为因缘故事,旨在弘扬佛的业力和神通。虽然在绘画技法上仍采用印度传过来的晕染法(即凹凸法),线条亦是“屈铁盘丝”技法,但到了龟兹,又有了创新,绘画技法发生重大变化。龟兹式晕染法有单面晕染和双面晕染等多种,由于晕染较夸张,立体感较强。成熟期的龟兹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出现身材修长、五官集中的本土化倾向,即使是壁画中的金刚力士、武士、龙王的服饰也采用了西域式样。龟兹壁画的变异还表现在出现了本地世俗供养人像,在隋唐时期,龟兹石窟壁画中出现了龟兹王及其王族供养人像。如果将成熟期的龟兹国王及王后供养像与龟兹早期佛传故事中的印度国王和王后像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异。克孜尔石窟第205窟中的龟兹国王和王后从服饰上看,国王上穿翻领对襟长大衣,下穿裹腿裤和尖头靴,右手握宝剑,左手持香炉,身后佩长剑;王后身穿翻领束腰短袖外套,双手持花珠链。国王头发从中间分开,长至耳下,王后头戴油帽。龟兹国王的这种服饰、发型与库车属7世纪昭怙厘寺出土的龟兹乐舞舍利盒中弹竖箜篌、凤首箜篌和击鼓男子的服饰、发型如出一辙,可见是龟兹本地男子的装束。而克孜尔石窟第22窟属4~5世纪的石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则是印度人,壁画亦是龟兹早期摹仿佛传故事之作。此壁画中的古印度国王阿阇世头戴三珠冠,有头光,后部有华盖。王后束高髻,上插三朵花,亦有头光。国王和王后均裸露上身,只是颈部、臂部、手腕部有装饰物。这与龟兹国王、王后的装饰打扮是完全不同的。印度佛教中常见裸体形象,与印度佛教主张通过极端的纵欲达到极端的出世和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有关,因此在佛教壁画和雕塑中性力崇拜、裸体表现一直很突出。佛教传入西域,这种表现方式仍然存在,但往往被加以改造。越到后期,裸体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尽管如压条、阴刻等键陀罗、秣菟罗雕塑技法仍在采用,但人物面部的平面化、服饰的繁褥化却是龟兹式的。
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壁画也反映了回鹘佛教艺术从摹仿到交融、变异的创新过程。回鹘西迁高昌后,在佛教艺术上深受晚唐汉传佛教艺术的影响,9~10世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回鹘王“非常体面地穿垂至脚面的宽大长袍,其袖子宽而长,必须卷起袖口才能露出双手。长衫的领子始终是圆形的。衣襟开在两侧,或者是以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开在前部,有时长袍的开襟于肋部亦直开到大腿之下。衣服始终是用带有几何图案或形象图案(云彩、花卉、飞禽)的华丽料子剪裁的”①。高昌地区自魏晋时期起就是河西汉族的聚居地,回鹘西迁前又属唐西州地区,主要居民仍是汉族,因此壁画中的回鹘王身着汉式长袍也极为正常。而随着蒙元时代的到来,汉族居民也逐渐被同化,佛教壁画中的供养人回鹘官员服饰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种身着蒙古服饰的官员形象。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壁画中的回鹘供养人穿着蒙古式服装,这是13世纪回鹘官员的形象。这种装束显然与蒙古人在畏兀儿地区推行蒙古制度文化有关。但是在一种摹仿艺术中仍能发现其发式是典型的回鹘式:“头发都披到肩后,束成光滑的一绺沿背部而下垂,常常是一直垂到腰带的高度,一绺头发有时是从耳朵前边出现,垂在面庞的两侧。这些上层人士全都留短须和相当细的下垂髭,大家在下巴之下还可以看到一种‘帝须’。一顶高高的挺直的三垂冠用两条窄窄的红带子拴在颌下。”①回鹘人的这种发式见于《五代史记》,其中记载:“(回鹘)其可汗常楼居,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文献证实,回鹘达官贵人才留这种发式。效仿唐文化和蒙古人推行蒙古化均未改变回鹘文化艺术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普通供养人无论是长相还是服饰都明显在体现一种回鹘风。高昌一座寺庙里的一群手持花束的供养人穿的是垂在膝盖的短袍,袍袖狭窄,裤子伸进长统靴中,靴口翻卷,腰部挂着各种物品,短髭短发,完全是回鹘式打扮了。仅从这些供养人壁画中,发现“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随着时间之推移,自然产生了融合混成之势。这种融合混成就是回鹘文化的特征”②。融合混成的结果产生的当然是回鹘文化艺术的新品种。
在乐舞艺术方面,同一地域的同一乐舞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反映的就是交融与变异造成的不同关系。《清书·音乐志》记载,隋初龟兹乐有三种,即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同是一种龟兹乐为何出现三种名称?这不能不从龟兹乐传入中原的不同时代特征谈起。西国龟兹指的是北周时从西面的龟兹传来的乐舞,它是随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下嫁北周武帝宇文邕传入的。突厥可汗是把龟兹乐队(包括舞伎、歌伎)作为陪嫁带到长安的。这是原汁原味的龟兹乐舞。而齐朝龟兹是北齐保存下来的龟兹乐舞,由于传入中原时间长,在传播中明显发生了重大变异。之前,首先是后梁吕光伐龟兹时将龟兹乐带入凉州,此后又杂以秦声,之后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占据河西后又将龟兹乐带入华北的平城。北魏分裂后,北齐的文宣帝也十分喜爱龟兹乐,《册府元龟》说他“每弹尝自击胡鼓和之”。总之,在隋朝建立前,龟兹乐已在河西和中原地区流传了200多年,龟兹乐自然也就受到北方鲜卑等游牧部落和汉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深刻影响。这样就大大改变了龟兹乐舞的本来面貌。土龟兹乐舞可能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可汗之女为皇后之前就存在于长安的龟兹乐舞了。从传入时间看,齐朝龟兹在中原流传时间最长,其源头可追溯到4世纪末吕光伐龟兹得龟兹乐,之后是土龟兹,它比北周武帝时的西国龟兹也早。从乐舞传入的文献记载看,北魏宣武帝时,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鼓、铜钹等龟兹乐器已出现在宫廷乐队中,铿锵的龟兹舞也深得王族喜爱。到北齐时,龟兹乐在中原出现繁盛景象,《隋书·音乐志》载:“杂乐西凉、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仅从龟兹乐器看,已从北魏时的五六种,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二十种,因为此时龟兹乐队的规模在二十人左右。龟兹乐舞东传的事实表明:一是任何一种异质艺术融入中原本土艺术都有所变形,即适应性变化,龟兹乐中“杂以秦声”就是乐舞艺术变形的结果,最终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乐舞发生交融;二是随时代的变迁,龟兹乐舞在交融变形中并未失去原色,鲜卑、汉等民族的乐舞的融入,只能是丰富了龟兹乐舞,而不是相反;三是龟兹乐舞等异质艺术、介入中原人的艺术审美系统,导致审美情趣的变化,从宫廷到民间,欣赏惯了中原的轻歌曼舞,而龟兹乐舞的豪放、激越,自然给予全新的视听感受。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艺术与中原艺术的交融是各民族审美意识交流、融合和渗透的结果。特别是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绿洲农耕社会和中原农业社会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是重社会、重伦理,这种农耕文化也是一种宗法文化,表现在审美意识上是伦理的、观念的、神性的。特别是唐统一西域以来,西域绿洲除流行佛教外,中原的道教和儒家文化也盛极一时,高昌、龟兹、于阗等绿洲居民同样视儒、道、佛为精神支柱。即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因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表现出审美意识的不同,但在唐代这样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农耕文化向游牧文化,西域文化向中原文化都大大靠近了,盛唐时出现的“华夷一家”的民族融洽氛围给艺术交融创造了条件。西域乐舞艺术那种粗犷、明快、激越的节奏给追求行云流水般韵律的中原乐舞无疑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时代精神的律动相协,同历史运行的步伐共振,和审美欣赏的需要相符,因此被中原广泛接受,继而吸收、融化。这也是汉族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在乐舞审美观念上的一次认同”①。西域艺术因地域、民族和时代发生的变异从更深层次上讲是由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决定的。处在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艺术,面对八方来风不能不对吸收的异质艺术作出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并非像对待一般事物那样只分出好与坏、优与劣那么简单,而是在考虑它的价值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价值判断所涉及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整体;它综合了这个艺术作品的各种积极侧面和消极侧面”②。西域佛教壁画吸收印度凹凸晕染法就是包含着对它的积极价值判断,因为这种技法较之平面着色,人物更有立体感,有强烈的表现力。龟兹乐舞中对外来乐器和昭武九姓舞蹈的吸收,也是由于这些乐器和乐舞丰富了龟兹乐舞的表现力和内涵,使之出现了质的飞跃。积极价值体现的是一种完美价值,“完美把艺术作品的和谐一致与它的价值模式、与它所具有的那些价值本身的深度联系在一起”③。审美判断是根据一个民族群体和个体的审美经验作出的。任何艺术都旨在激起受众的情感——在欣赏中产生愉悦感。在西域这个歌舞之乡,歌舞艺术不仅是欣赏的对象,而且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这种参与必然导致对外来歌舞艺术根据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作出筛选。柘枝舞、胡腾舞、胡旋舞就是根据龟兹人的审美经验经筛选后引进的,它们的韵律、节奏与本土艺术一拍即合。西域佛教雕塑、壁画艺术中一些本土化的人物形象和源自现实景物的天堂气象就是根据西域人物和景观,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做出的审美判断。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都会因空间和时间而发生变化。只有因地、因时作适宜性调整,才不至于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也才能在广泛的文化交融和变异中创造出新的艺术。
附注
①霍旭初.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109.
①〔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149.
①〔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149.
②〔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87.
①袁乐.古代舞蹈艺术的自觉.舞蹈艺术3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77.
②〔德〕莫里茨·盖格尔著.艾彦译.艺术的意味.华夏出版社,1999.204.
③〔德〕莫里茨·盖格尔著.艾彦译.艺术的意味.华夏出版社,1999.207.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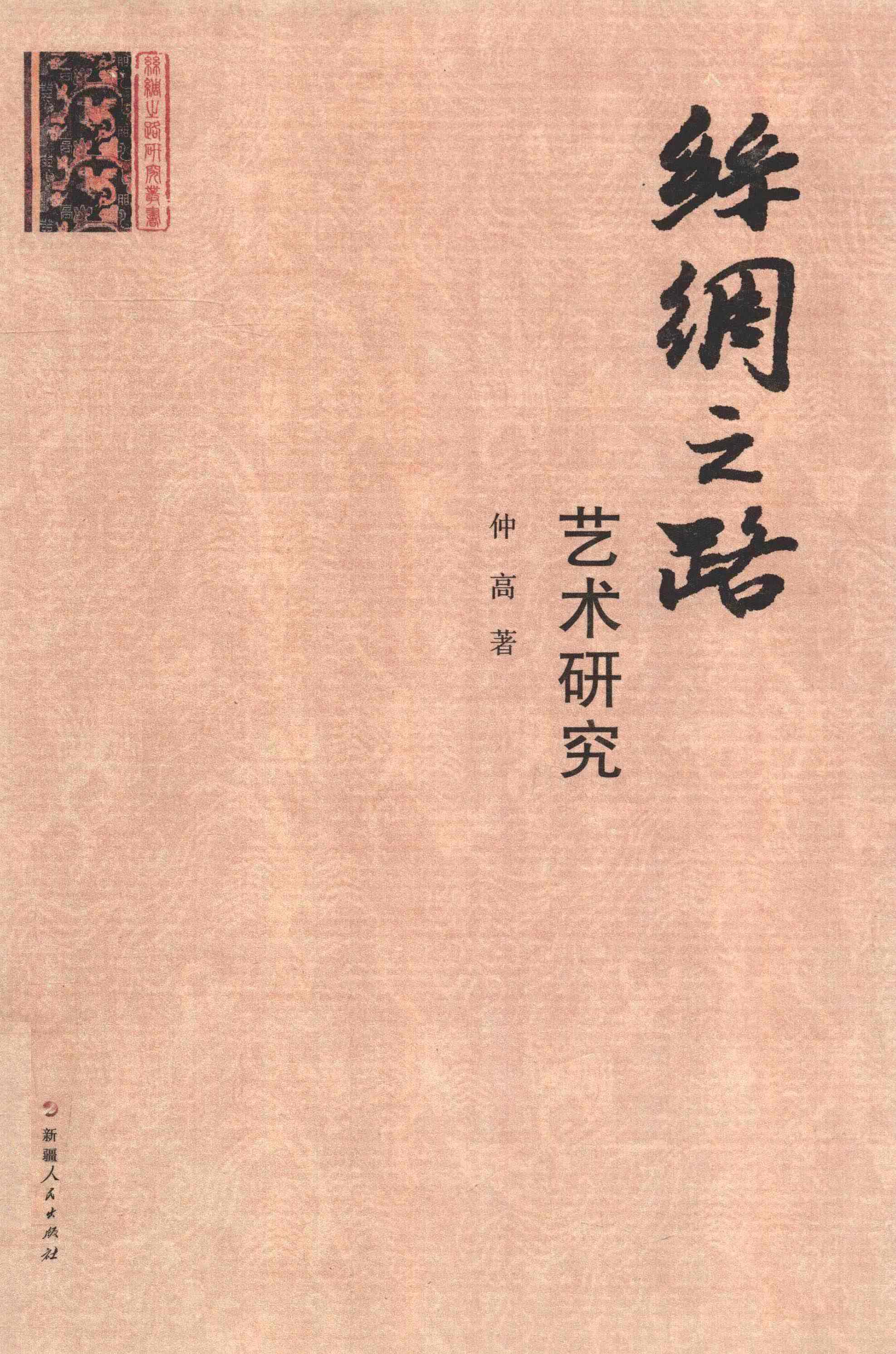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