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艺术借鉴:摹仿与嫁接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57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艺术借鉴:摹仿与嫁接 |
| 分类号: | J209.45 |
| 页数: | 6 |
| 页码: | 299-304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艺术借鉴:摹仿与嫁接情况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在与其他民族艺术接触中,先是摹仿与嫁接,而后是交融与变异,最后是往复与回授,经历了从艺术借鉴到艺术创新的发展历程。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艺术摹仿 艺术嫁接 |
内容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在与其他民族艺术接触中,先是摹仿与嫁接,而后是交融与变异,最后是往复与回授,经历了从艺术借鉴到艺术创新的发展历程。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众多民族的艺术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在西域,最易使不同质的艺术发生碰撞,起初艺术上的摹仿与嫁接就在所难免。面对外来的艺术,本土艺术先接受,后化解,才能谈得上艺术创新和发展。但是艺术上的摹仿和嫁接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摹仿、嫁接创造一种新艺术。西域各民族艺术间的摹仿与嫁接不仅出现在各绿洲农耕居民和各游牧民族之中,还出现在绿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以及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无论是在音乐舞蹈和绘画雕塑方面还是民间工艺方面概莫如此。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和审美意识都有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空间,都积淀了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对异质艺术的摹仿都要进行适应性嫁接,这种杂交成了由摹仿而进入创造的最好方式。
对于像塞人、大月氏、乌揭、匈奴、突厥、黠戛斯等游牧部落的动物纹样的相似性从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方面探讨是正确的,但也能明显看到这些动物纹样在流变中的摹仿、移植、嫁接关系。往往是后来的艺术对之前的艺术进行了合理吸收。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属6~8世纪的突厥人、黠戛斯人的带扣、饰牌、马具、刀具等金属器物和骨、角制品的纹样中有些是野兽纹样,而比较繁缛的纹饰如银质和青铜的辔上饰牌是植物形状。“通过研究这些花纹,发现其中很多是从斯基泰—西伯利亚时期的野兽纹发展而来的;野兽纹的某些因素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情节含意,变成植物形状的螺旋纹。直到现在,在哈萨克族特别是天山吉尔吉斯族的纹饰中,远古时代动物母题的这种演变过程也还在继续发展,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①。在欧亚草原中段的阿尔泰草原,历史上就是从东来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文化和西来的操东伊朗语塞人游牧文化碰撞汇聚之地,同质文化的移植、嫁接是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早期的动物纹样是功能性的,而以后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文化中。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群文化分三期,第一期距今3000年前,第二期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第三期为东汉至晋。前两期属狩猎、畜牧文化时代,而第三期则进入农耕文化时期。属于第三期文化的出土文物中有两件木雕动物纹样器物引人注目,一件是狼羊纹木盒,在长高各13.5厘米和5厘米的整木雕刻木盒两侧和底面雕有连体双首的狼纹,羊纹则刻于狼腹内。另一件羊鹿纹木筒高11.1厘米,口径8.1厘米,筒表面阴刻羊纹和鹿纹,漆黑漆。这些纹样显然脱胎于塞人动物纹样艺术,但在艺术借鉴中均有所变形,塞人的咬斗型动物纹样变成了狼吃羊纹样,这可能与绿洲农耕居民忧心狼患加害家畜家禽的现实遭遇有关。而羊鹿纹在塞人、匈奴等动物纹样艺术中也常见,但都出现在饰牌、带扣、刀柄等小型金属物件中,且有巫术功能,而扎滚鲁克的居民则把这类动物形象雕刻在木制器皿上,且造型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塞人、匈奴等游牧民族中马、羊、鹿等动物形象往往被雕绘成蜗牛形、蜷曲形的旋状,如匈奴长矛柄头上雕刻的牡鹿纹就是圆形凸起的。扎滚鲁克出土木筒中的阴刻羊鹿纹也能见到摹仿自早期动物纹样的痕迹,但在嫁接后纹样越来越抽象变形,在圆柱状的体面,羊和鹿成了首尾相接的图案,而且图案的装饰效果类似于剪纸。
除动物纹样外,一些主要的植物纹样、几何图形也成为摹仿对象,特别是后期的装饰效果往往抹去具象,变得越来越抽象,几乎成了所有日常用品中的主导装饰图案。在西域史前彩陶中常见一种菱格形图案,主要图形有菱格回纹、内填变形回纹、连续三角形变形的菱格纹以及饰斜带连续云雷纹等。连续云雷纹见于甘肃半山类型彩陶图案中,以黑红彩为主的装饰图案仍然是菱形纹。西域天山以南、以东地区彩陶与甘青地区和中亚北部草原的安德罗诺文化彩陶在纹样上的一致性,说明晚出的西域彩陶几乎是摹仿自这些地区彩陶的纹样,但安德罗诺彩陶文化晚于半山彩陶文化。不过,进入有史时代以来菱格形图案并未从绿洲农耕居民的生活中消失,反而在一些织物、舍利盒和佛教壁画中经常出现。尼雅属汉代墓葬中出土一件红蓝色菱格纹丝头巾在蓝地中显出红色菱格纹,另一件织锦覆面在白地中织出变体茱萸和菱形回纹,同时出土的还有漆奁和铜镜。丝织品可能直接来自中原地区,菱形纹样也成为本地居民钟爱的纹样。而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丘达依塔格佛寺遗址出土的两件舍利陶罐为本地产品,其中一件器身为土红色,在红色菱格形内绘有黑色圆圈纹,图案简洁、古朴;而另一件舍利陶罐器身为黑色,绘有白色菱格纹。菱格纹舍利盒与龟兹乐舞舍利盒属同一形制,均为唐代之物。菱格纹舍利盒在纹样上采取简约化的方式绘制,是对一些纹样的审美走向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从摹仿中蜕变而来的本土化纹样,或以简取胜,或以繁取胜,都旨在通过嫁接创造出一种新艺术。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格画又往往以繁取胜,属菱格纹图案有四方连续菱格图案、四方连续菱格嵌花纹样、二方连续折线自身复合式菱格形嵌花纹等。四方连续菱格图案是在菱格形内绘制本生故事、因缘故事或供养故事等。如一个本生故事,画在一个形似山峦的菱格纹内,往往是一个故事多以一个或两个典型画面表现,情节简单,但人物极富个性。因在券顶侧壁多绘制数列菱格,因此也就在一窟之内绘有数个本生故事。四方连续菱格嵌花给人以马赛克的感觉。二方连续折线复合式菱格嵌花纹样是在菱格纹内外都填充花卉纹。无论是填充人物的菱格纹还是填充花卉的菱格纹都繁而不乱,填充有序。这是龟兹艺匠在摹仿基础上的新创造。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摹仿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但是一些已程式化的形象如对汉族玄武形象和汉传佛教中人物形象的摹仿,就不能不附加上本土居民的审美趣味和主观标准了。黑格尔认为:“(摹仿)在选择对象并就对象分别美丑时,由于缺乏一个标准,可以适用于自然的无穷形式,主观趣味就成为最后的标准了,这种主观趣味的标准是既不能定为规律,又不能容许争辩的。”①和田布扎克古墓地出土彩棺属五代遗物,木制彩棺四面分别彩绘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方之神。其中青龙身躯弯曲,有鳞,口吐长舌;白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玄武则为蛇头,龟身,长尾,腿较长;朱雀两翅展开形似金翅鸟,尾部又似孔雀开屏。在楼兰古城以北墓葬出土的汉晋时期彩棺则只在木棺首尾两端彩绘朱雀和玄武。朱雀绘制在棺头端橘红色对角线交叉处的黄色圆内,朱雀两翅展开,尾巴较阔长且翘起。棺足端在对角线相交处的黄色圆内绘的玄武,形为青蛙,与和田出土彩棺上的龟蛇体玄武有所不同。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是汉族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青龙,又名苍龙,汉代画像石中的青龙亦为飞舞状,有足,无鳞,和田出土彩棺中的青龙略异于此。汉代画像石中的白虎身躯秀长,身有条状纹,而和田出土彩棺中呈啮斗状。玄武,《文选》注:“龟与蛇交为玄武。”洪兴祖在《楚辞·远游》补注中谓:“说者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汉代画像石中玄武为蛇头蛇尾,龟身,龟背有甲,和田出土彩棺中玄武与此相仿,只是四足稍长些而已。而楼兰彩棺中用蛙替代玄武,可能取蛙多子多产的象征意义,与玄武所代表的祈求长寿并不相悖。朱雀在汉代画像石是传说中的凤凰形象,但取象于孔雀是无疑的,和田和楼兰故城出土彩棺中的朱雀形象与汉代画像石中朱雀形象并无太大差别,仅仅在于画匠对形象的理解和绘画技巧的差异。从汉晋到五代,西域居民的丧葬中出现中原神话意象中的四方之神,显然系中原的翻版,在信仰上,崇拜长寿和追求生命永恒这点上,西域和中原居民是一致的。高昌回鹘佛教艺术中的壁画许多供养人像和藻井画均源自唐代中原以胖为美的人物形象和汉族藻井画,因为高昌毕竟是西域汉文化的发源地区之一。西迁的回鹘人起初在佛教绘画上的摹仿蓝本就是原来汉族壁画中的形象。
较之雕塑、绘画艺术,丝绸之路西域乐舞的艺术魅力更久远,正是不同民族乐舞间的相互摹仿、杂交、互渗才结出了各民族乐舞的硕果。因为在西域,乐舞并非是上层的专利,而是民间普遍的娱乐形式,无论是绿洲农耕居民,还是草原游牧民都是如此。入隋唐宫廷乐的龟兹乐舞在形成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粟特等定居民和草原部民的乐舞。从一些艺术形象资料看,龟兹舞中的健舞、软舞等与昭武九姓的《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十分相似。隋唐时期龟兹就有粟特人的聚落,这给乐舞摹仿创造了机会。龟兹、高昌流行的乞寒舞也源自中亚的康国,但在本土化过程中变成了龟兹、高昌的习俗舞。康国乐、安国乐等昭武九姓乐曲多为舞曲,亦随其舞蹈被龟兹乐舞摹仿、借鉴。龟兹乐舞中使用的不少乐器也并非完全是本土乐器,笛是羌人带入西域的,羯鼓本是游牧的大月氏人的乐器,后成了定居的龟兹人的乐器。龟兹乐舞早在汉代就曾摹仿、借鉴了汉族音乐。龟兹王绛宾就曾娶乌孙公主之女为夫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他本人也“乐汉衣服制度”“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从汉宣帝一直到汉哀帝,也就是从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1年,龟兹国一直在学习汉族音乐,甚至是完全摹仿。元康元年(即公元前65年),龟兹王还得到汉宣帝赠送的汉族音乐家数十人”。①龟兹乐舞向东传播时也成为诸如《西凉乐》摹仿的对象,《通典》就认为《西凉乐》是“变龟兹声为之”。西凉地处河西走廊,历史上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孔道,也是丝绸之路咽喉,《西凉乐》正是产生于后凉吕光统治时期。381年,前秦苻坚遣吕光攻占龟兹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晋书·吕光载记》),表明此时龟兹乐舞传入后凉。“由于西凉乐渊源于龟兹乐,所以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多的。即以乐器而论,两者所共有的乐器达十三种之多,即: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筚篥、檐鼓、齐鼓、腰鼓、铜钹、贝等”。①“变龟兹声为之”实际上是一个摹仿、杂交、融合、渗透的过程。“《西凉乐》是西凉人摹仿龟兹乐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音乐而创造的一种新品种的音乐,它是‘变’‘杂’也就是‘混合’的产物,是异质音乐文化杂交而生成的新质音乐文化”。②
清代以来形成的新疆各民族间由于大杂居、小聚居局面使各民族间交往更加频繁,乐舞艺术间的借鉴、摹仿更丰富了各民族的乐舞语汇。在天山以南的喀什等地,维吾尔族与乌孜别克族杂聚,形成许多共同的舞蹈语汇,如两个民族的舞蹈动作中都有“抖手”、“转手”、“晃手”、“弹指”的运用。而维吾尔执具舞《沙玛瓦尔舞》中的道具“沙玛瓦尔”来自俄罗斯,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锡伯、乌孜别克等民族也摹仿了俄罗斯族的踢踏舞。同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乐舞之间的摹仿发生频仍。新疆蒙古族的弹拨乐器“霍布修尔”非本民族传统乐器,而是根据哈萨克族的弹拨乐器“冬不拉”仿制的,而柯尔克孜族在历史上与蒙古族关系密切,因此舞蹈中吸收了蒙古舞的语汇。塔塔尔族与俄罗斯族的乐器、舞蹈间也呈现出相互摹仿、借鉴的痕迹,如两个民族的常用乐器均为手风琴、曼德林等,而舞步均以“踢踏步”为代表,手法上的“撩手”、“连手”、“双手交叉”、“击手”和舞步中的“云步”、“擦步”、“花点”等几乎完全相同。锡伯族历史上就与满族、蒙古族频繁交往,“动肩”、“挑腕”等舞蹈语汇,三个民族也是共同的。这种各民族间直接“拿来”式的摹仿,并不是使各民族的乐舞艺术只有共性而失去了个性,恰恰相反,各民族乐舞通过杂交相互渗透而产生了具有个性的新品位的各民族乐舞艺术。
清代,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中流行仿汉式建筑,其中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的靖远寺为典型一例。靖远寺为锡伯族喇嘛教寺庙,但建筑布局和风格是汉式的。这座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庙宇,由前殿、中殿、后殿、围墙、影壁和两侧小院组成,同汉式建筑一样坐北朝南。寺院正南为砖雕影壁,进两侧的门为东西两小院,东为土地神庙,西是木栅栏小隔房,内立守门神塑像。正门两侧各有一石雕雄狮,进大门后主殿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世佛大殿。院内东西各有钟楼、鼓楼,其他还有铁铸大香炉、木牌楼、偏殿等。寺院内的主体建筑是藏经楼(即三世佛大殿),为木雕牌楼式两层飞檐式建筑。大殿高尖屋脊、琉璃顶,异角飞檐上挂十二个铁铃。殿内供奉三世佛塑像,两侧即为藏经阁。清代遍及锡伯族各牛录的关帝庙、娘娘庙也完全是汉式的,连信奉的关帝也是汉族民间的神祗。汉式佛寺,近代以来主要由两组建筑构成:山门和天王殿为一组,合称“前殿”,大雄宝殿为一组,是佛寺的主体建筑。庭院布局为典型的四合院,虽是一个封闭性的建筑空间,但由于庭院开阔,使用上灵活多变。汉式宫殿、衙署、住宅、佛寺均采用这种布局形式。拿锡伯族的靖远寺与近代汉族佛寺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其摹仿的印记。由于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汉族建筑定型早,历史悠久,且在布局上以中轴线均衡对称,适应性强,又形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的特点,很容易为其他民族,特别是定居民族所接受,锡伯族寺庙的“人”字形屋顶建筑就属此类。
艺术上的摹仿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在于创新出新的艺术。如果是邯郸学步到连自己的路都不会走了,这种摹仿又有何意义呢?它只能是作茧自缚。
对于像塞人、大月氏、乌揭、匈奴、突厥、黠戛斯等游牧部落的动物纹样的相似性从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方面探讨是正确的,但也能明显看到这些动物纹样在流变中的摹仿、移植、嫁接关系。往往是后来的艺术对之前的艺术进行了合理吸收。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属6~8世纪的突厥人、黠戛斯人的带扣、饰牌、马具、刀具等金属器物和骨、角制品的纹样中有些是野兽纹样,而比较繁缛的纹饰如银质和青铜的辔上饰牌是植物形状。“通过研究这些花纹,发现其中很多是从斯基泰—西伯利亚时期的野兽纹发展而来的;野兽纹的某些因素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情节含意,变成植物形状的螺旋纹。直到现在,在哈萨克族特别是天山吉尔吉斯族的纹饰中,远古时代动物母题的这种演变过程也还在继续发展,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①。在欧亚草原中段的阿尔泰草原,历史上就是从东来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文化和西来的操东伊朗语塞人游牧文化碰撞汇聚之地,同质文化的移植、嫁接是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早期的动物纹样是功能性的,而以后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文化中。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群文化分三期,第一期距今3000年前,第二期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第三期为东汉至晋。前两期属狩猎、畜牧文化时代,而第三期则进入农耕文化时期。属于第三期文化的出土文物中有两件木雕动物纹样器物引人注目,一件是狼羊纹木盒,在长高各13.5厘米和5厘米的整木雕刻木盒两侧和底面雕有连体双首的狼纹,羊纹则刻于狼腹内。另一件羊鹿纹木筒高11.1厘米,口径8.1厘米,筒表面阴刻羊纹和鹿纹,漆黑漆。这些纹样显然脱胎于塞人动物纹样艺术,但在艺术借鉴中均有所变形,塞人的咬斗型动物纹样变成了狼吃羊纹样,这可能与绿洲农耕居民忧心狼患加害家畜家禽的现实遭遇有关。而羊鹿纹在塞人、匈奴等动物纹样艺术中也常见,但都出现在饰牌、带扣、刀柄等小型金属物件中,且有巫术功能,而扎滚鲁克的居民则把这类动物形象雕刻在木制器皿上,且造型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塞人、匈奴等游牧民族中马、羊、鹿等动物形象往往被雕绘成蜗牛形、蜷曲形的旋状,如匈奴长矛柄头上雕刻的牡鹿纹就是圆形凸起的。扎滚鲁克出土木筒中的阴刻羊鹿纹也能见到摹仿自早期动物纹样的痕迹,但在嫁接后纹样越来越抽象变形,在圆柱状的体面,羊和鹿成了首尾相接的图案,而且图案的装饰效果类似于剪纸。
除动物纹样外,一些主要的植物纹样、几何图形也成为摹仿对象,特别是后期的装饰效果往往抹去具象,变得越来越抽象,几乎成了所有日常用品中的主导装饰图案。在西域史前彩陶中常见一种菱格形图案,主要图形有菱格回纹、内填变形回纹、连续三角形变形的菱格纹以及饰斜带连续云雷纹等。连续云雷纹见于甘肃半山类型彩陶图案中,以黑红彩为主的装饰图案仍然是菱形纹。西域天山以南、以东地区彩陶与甘青地区和中亚北部草原的安德罗诺文化彩陶在纹样上的一致性,说明晚出的西域彩陶几乎是摹仿自这些地区彩陶的纹样,但安德罗诺彩陶文化晚于半山彩陶文化。不过,进入有史时代以来菱格形图案并未从绿洲农耕居民的生活中消失,反而在一些织物、舍利盒和佛教壁画中经常出现。尼雅属汉代墓葬中出土一件红蓝色菱格纹丝头巾在蓝地中显出红色菱格纹,另一件织锦覆面在白地中织出变体茱萸和菱形回纹,同时出土的还有漆奁和铜镜。丝织品可能直接来自中原地区,菱形纹样也成为本地居民钟爱的纹样。而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丘达依塔格佛寺遗址出土的两件舍利陶罐为本地产品,其中一件器身为土红色,在红色菱格形内绘有黑色圆圈纹,图案简洁、古朴;而另一件舍利陶罐器身为黑色,绘有白色菱格纹。菱格纹舍利盒与龟兹乐舞舍利盒属同一形制,均为唐代之物。菱格纹舍利盒在纹样上采取简约化的方式绘制,是对一些纹样的审美走向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从摹仿中蜕变而来的本土化纹样,或以简取胜,或以繁取胜,都旨在通过嫁接创造出一种新艺术。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格画又往往以繁取胜,属菱格纹图案有四方连续菱格图案、四方连续菱格嵌花纹样、二方连续折线自身复合式菱格形嵌花纹等。四方连续菱格图案是在菱格形内绘制本生故事、因缘故事或供养故事等。如一个本生故事,画在一个形似山峦的菱格纹内,往往是一个故事多以一个或两个典型画面表现,情节简单,但人物极富个性。因在券顶侧壁多绘制数列菱格,因此也就在一窟之内绘有数个本生故事。四方连续菱格嵌花给人以马赛克的感觉。二方连续折线复合式菱格嵌花纹样是在菱格纹内外都填充花卉纹。无论是填充人物的菱格纹还是填充花卉的菱格纹都繁而不乱,填充有序。这是龟兹艺匠在摹仿基础上的新创造。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摹仿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但是一些已程式化的形象如对汉族玄武形象和汉传佛教中人物形象的摹仿,就不能不附加上本土居民的审美趣味和主观标准了。黑格尔认为:“(摹仿)在选择对象并就对象分别美丑时,由于缺乏一个标准,可以适用于自然的无穷形式,主观趣味就成为最后的标准了,这种主观趣味的标准是既不能定为规律,又不能容许争辩的。”①和田布扎克古墓地出土彩棺属五代遗物,木制彩棺四面分别彩绘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方之神。其中青龙身躯弯曲,有鳞,口吐长舌;白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玄武则为蛇头,龟身,长尾,腿较长;朱雀两翅展开形似金翅鸟,尾部又似孔雀开屏。在楼兰古城以北墓葬出土的汉晋时期彩棺则只在木棺首尾两端彩绘朱雀和玄武。朱雀绘制在棺头端橘红色对角线交叉处的黄色圆内,朱雀两翅展开,尾巴较阔长且翘起。棺足端在对角线相交处的黄色圆内绘的玄武,形为青蛙,与和田出土彩棺上的龟蛇体玄武有所不同。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是汉族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青龙,又名苍龙,汉代画像石中的青龙亦为飞舞状,有足,无鳞,和田出土彩棺中的青龙略异于此。汉代画像石中的白虎身躯秀长,身有条状纹,而和田出土彩棺中呈啮斗状。玄武,《文选》注:“龟与蛇交为玄武。”洪兴祖在《楚辞·远游》补注中谓:“说者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汉代画像石中玄武为蛇头蛇尾,龟身,龟背有甲,和田出土彩棺中玄武与此相仿,只是四足稍长些而已。而楼兰彩棺中用蛙替代玄武,可能取蛙多子多产的象征意义,与玄武所代表的祈求长寿并不相悖。朱雀在汉代画像石是传说中的凤凰形象,但取象于孔雀是无疑的,和田和楼兰故城出土彩棺中的朱雀形象与汉代画像石中朱雀形象并无太大差别,仅仅在于画匠对形象的理解和绘画技巧的差异。从汉晋到五代,西域居民的丧葬中出现中原神话意象中的四方之神,显然系中原的翻版,在信仰上,崇拜长寿和追求生命永恒这点上,西域和中原居民是一致的。高昌回鹘佛教艺术中的壁画许多供养人像和藻井画均源自唐代中原以胖为美的人物形象和汉族藻井画,因为高昌毕竟是西域汉文化的发源地区之一。西迁的回鹘人起初在佛教绘画上的摹仿蓝本就是原来汉族壁画中的形象。
较之雕塑、绘画艺术,丝绸之路西域乐舞的艺术魅力更久远,正是不同民族乐舞间的相互摹仿、杂交、互渗才结出了各民族乐舞的硕果。因为在西域,乐舞并非是上层的专利,而是民间普遍的娱乐形式,无论是绿洲农耕居民,还是草原游牧民都是如此。入隋唐宫廷乐的龟兹乐舞在形成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粟特等定居民和草原部民的乐舞。从一些艺术形象资料看,龟兹舞中的健舞、软舞等与昭武九姓的《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十分相似。隋唐时期龟兹就有粟特人的聚落,这给乐舞摹仿创造了机会。龟兹、高昌流行的乞寒舞也源自中亚的康国,但在本土化过程中变成了龟兹、高昌的习俗舞。康国乐、安国乐等昭武九姓乐曲多为舞曲,亦随其舞蹈被龟兹乐舞摹仿、借鉴。龟兹乐舞中使用的不少乐器也并非完全是本土乐器,笛是羌人带入西域的,羯鼓本是游牧的大月氏人的乐器,后成了定居的龟兹人的乐器。龟兹乐舞早在汉代就曾摹仿、借鉴了汉族音乐。龟兹王绛宾就曾娶乌孙公主之女为夫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他本人也“乐汉衣服制度”“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从汉宣帝一直到汉哀帝,也就是从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1年,龟兹国一直在学习汉族音乐,甚至是完全摹仿。元康元年(即公元前65年),龟兹王还得到汉宣帝赠送的汉族音乐家数十人”。①龟兹乐舞向东传播时也成为诸如《西凉乐》摹仿的对象,《通典》就认为《西凉乐》是“变龟兹声为之”。西凉地处河西走廊,历史上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孔道,也是丝绸之路咽喉,《西凉乐》正是产生于后凉吕光统治时期。381年,前秦苻坚遣吕光攻占龟兹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晋书·吕光载记》),表明此时龟兹乐舞传入后凉。“由于西凉乐渊源于龟兹乐,所以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多的。即以乐器而论,两者所共有的乐器达十三种之多,即: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筚篥、檐鼓、齐鼓、腰鼓、铜钹、贝等”。①“变龟兹声为之”实际上是一个摹仿、杂交、融合、渗透的过程。“《西凉乐》是西凉人摹仿龟兹乐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音乐而创造的一种新品种的音乐,它是‘变’‘杂’也就是‘混合’的产物,是异质音乐文化杂交而生成的新质音乐文化”。②
清代以来形成的新疆各民族间由于大杂居、小聚居局面使各民族间交往更加频繁,乐舞艺术间的借鉴、摹仿更丰富了各民族的乐舞语汇。在天山以南的喀什等地,维吾尔族与乌孜别克族杂聚,形成许多共同的舞蹈语汇,如两个民族的舞蹈动作中都有“抖手”、“转手”、“晃手”、“弹指”的运用。而维吾尔执具舞《沙玛瓦尔舞》中的道具“沙玛瓦尔”来自俄罗斯,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锡伯、乌孜别克等民族也摹仿了俄罗斯族的踢踏舞。同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乐舞之间的摹仿发生频仍。新疆蒙古族的弹拨乐器“霍布修尔”非本民族传统乐器,而是根据哈萨克族的弹拨乐器“冬不拉”仿制的,而柯尔克孜族在历史上与蒙古族关系密切,因此舞蹈中吸收了蒙古舞的语汇。塔塔尔族与俄罗斯族的乐器、舞蹈间也呈现出相互摹仿、借鉴的痕迹,如两个民族的常用乐器均为手风琴、曼德林等,而舞步均以“踢踏步”为代表,手法上的“撩手”、“连手”、“双手交叉”、“击手”和舞步中的“云步”、“擦步”、“花点”等几乎完全相同。锡伯族历史上就与满族、蒙古族频繁交往,“动肩”、“挑腕”等舞蹈语汇,三个民族也是共同的。这种各民族间直接“拿来”式的摹仿,并不是使各民族的乐舞艺术只有共性而失去了个性,恰恰相反,各民族乐舞通过杂交相互渗透而产生了具有个性的新品位的各民族乐舞艺术。
清代,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中流行仿汉式建筑,其中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的靖远寺为典型一例。靖远寺为锡伯族喇嘛教寺庙,但建筑布局和风格是汉式的。这座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庙宇,由前殿、中殿、后殿、围墙、影壁和两侧小院组成,同汉式建筑一样坐北朝南。寺院正南为砖雕影壁,进两侧的门为东西两小院,东为土地神庙,西是木栅栏小隔房,内立守门神塑像。正门两侧各有一石雕雄狮,进大门后主殿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世佛大殿。院内东西各有钟楼、鼓楼,其他还有铁铸大香炉、木牌楼、偏殿等。寺院内的主体建筑是藏经楼(即三世佛大殿),为木雕牌楼式两层飞檐式建筑。大殿高尖屋脊、琉璃顶,异角飞檐上挂十二个铁铃。殿内供奉三世佛塑像,两侧即为藏经阁。清代遍及锡伯族各牛录的关帝庙、娘娘庙也完全是汉式的,连信奉的关帝也是汉族民间的神祗。汉式佛寺,近代以来主要由两组建筑构成:山门和天王殿为一组,合称“前殿”,大雄宝殿为一组,是佛寺的主体建筑。庭院布局为典型的四合院,虽是一个封闭性的建筑空间,但由于庭院开阔,使用上灵活多变。汉式宫殿、衙署、住宅、佛寺均采用这种布局形式。拿锡伯族的靖远寺与近代汉族佛寺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其摹仿的印记。由于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汉族建筑定型早,历史悠久,且在布局上以中轴线均衡对称,适应性强,又形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的特点,很容易为其他民族,特别是定居民族所接受,锡伯族寺庙的“人”字形屋顶建筑就属此类。
艺术上的摹仿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在于创新出新的艺术。如果是邯郸学步到连自己的路都不会走了,这种摹仿又有何意义呢?它只能是作茧自缚。
附注
①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铅印本.
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55.
①周菁葆.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187.
①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73.
②彭书麟.论中古时期民族审美意识的互渗.文艺研究.1995(.21)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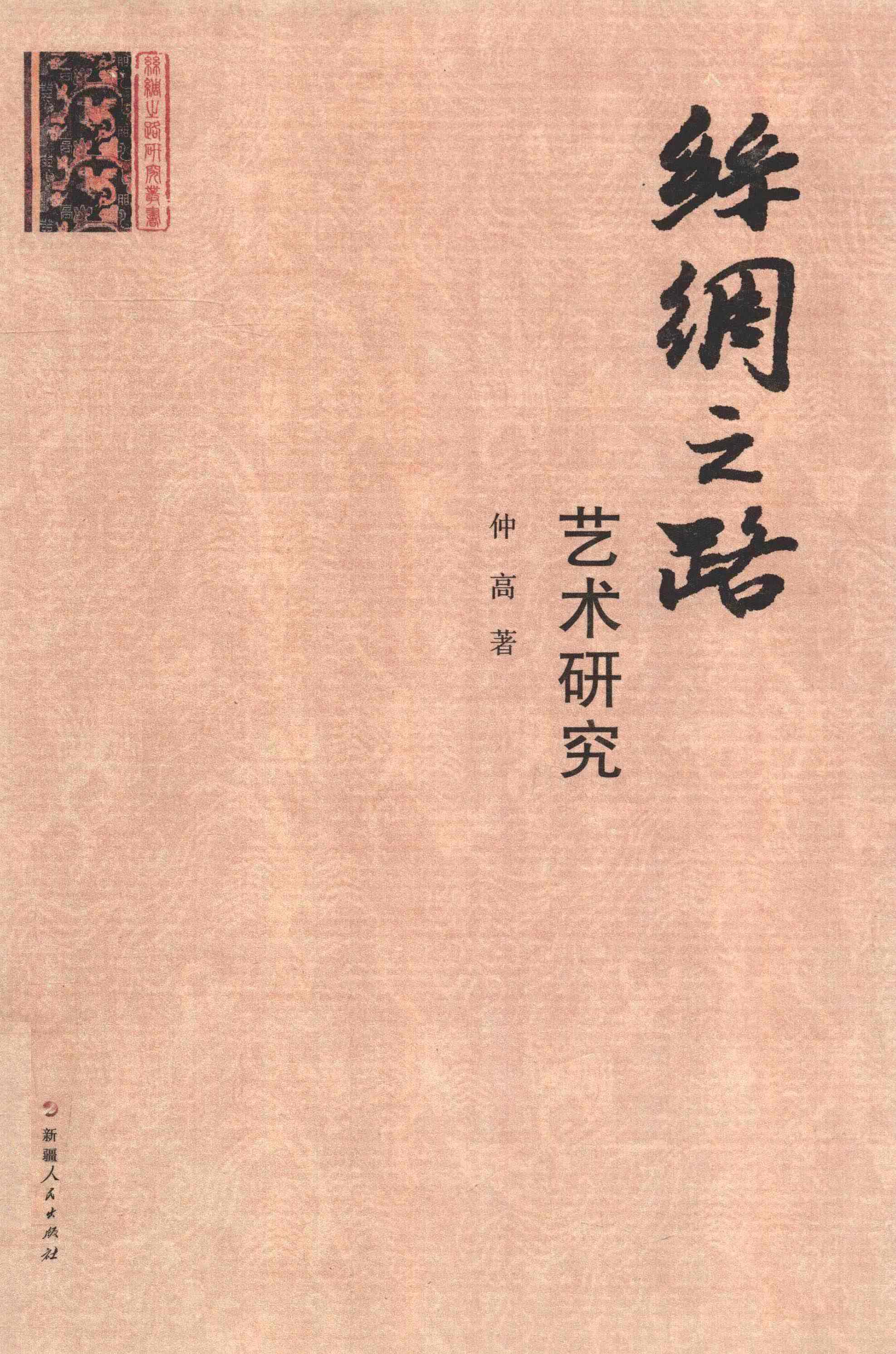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