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民族聚居与文化包容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56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多民族聚居与文化包容 |
| 分类号: | J209.45 |
| 页数: | 8 |
| 页码: | 292-299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有东西文化助动力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是内部各种文化互动的结果。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就是一个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复合型文化区域。从某一小范围来看,是某一民族在某一地区集中居住,但也杂居着其他民族,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特征。古代是这样,近代以来更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呢?主要原因是不断的民族迁徙。民族迁徙自古以来在西域这一方广袤土地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直接导致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使各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民族聚居 文化艺术 |
内容
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有东西文化助动力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是内部各种文化互动的结果。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就是一个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复合型文化区域。从某一小范围来看,是某一民族在某一地区集中居住,但也杂居着其他民族,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特征。古代是这样,近代以来更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呢?主要原因是不断的民族迁徙。民族迁徙自古以来在西域这一方广袤土地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直接导致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使各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
从考古发现得知,丝绸之路上中段西域最早迁徙的主要是塞人和羌人。操伊朗语的塞人从东南欧向黑海以北迁徙,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之后又迁移进入中亚、伊朗西部和印度,而中亚塞人的一支又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天山以南的塞人适应绿洲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农耕民,而天山以北地区的塞人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我国新疆南部的于阗地区,直至10世纪还存在着操和田塞语的民族。从现代学者的研究可知,和田塞语属于东伊朗语支,与粟特语、花剌子模语有近亲关系。这一支操印欧语的民族只能是从塔吉克斯坦或其以北地区迁入的。根据汉文资料记载,公元前3—前2世纪,今新疆相当大部分地区为塞种集团所占据”①。不仅于阗、帕米尔高原一带是操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地,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则是塞人的游牧地。春秋战国时期聚居于河西一带的强大的羌人集团曾先后向东、南、西三面迁徙,其中一支西迁进入天山以南地区,一直到两汉时期,若羌、楼兰(鄯善)、且末、于阗、蒲犁、龟兹等地都是羌人活动的地域。曾在今阿克苏地区的新和县于什格提(三道城)遗址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印背上的钮为卧羊形,表明羌人在龟兹地区的活动。羌人属汉藏语系的游牧部落。《说文解字》解释羌字为“西戎牧羊人也”。“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①。羌可能来自殷商人对他们的称呼。羌人西迁至昆仑山北麓后,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也从事了农业。在西域,羌人自东面的若羌至最西边的葱岭广泛分布。这种分布,在地域上往往又与塞人的分布相重合,表明东来的汉藏语系的羌人与西迁的东伊朗语族的塞人在天山以南地区相遇、接触并发生了融合。这是迄今所知的发生在西域的最早的民族融合。如果从文化习俗上区分,塞人是头戴尖顶帽的氏族集团,而羌人则是头戴羊角帽的氏族集团。中亚草原以及天山南北地区的墓葬中均出土有塞人的毡制尖顶帽。塞人早期是信仰太阳神的,这与他们的拜火教信仰是一致的。尖顶帽可能与他们信仰中沟通天界的宇宙山、生命树属同一个象征符号体系,久而久之,尖顶帽世俗化,成为塞人的文化标志。而羌人的羊角帽也有不同的文化表征,羌人戴羊角帽可能源自他们的图腾——羊,羌早期是一个以羊为图腾的氏族集团。在辛店文化中有羊角柱图案的彩陶出土,它就是羌族的图腾柱,在羊角纹上还绘有太阳纹。由于太阳能滋育畜群繁衍,故只有羊能配得上太阳,于是向太阳神献祭就以羊为主。“以羊象征太阳神,源出于羌戎族。羌族羊祭,图腾神以羊名,因以‘日’名‘太阳’即‘大羊’(样)”②。可见,羌人与塞人一样都是献祭太阳神的,只是祭品不同,羌人用羊献祭,而塞人则以跑得最快的马献祭。这两个古代部落在接触、混杂、连接的融合中,文化间的包容就在所难免了。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有史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主要有四次,即两汉时期、隋唐时期、蒙元时期和清代。这四个时期是西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最重要时期,每一个时期的统一都反映了更高层次上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汉代民族迁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向西迁徙。汉王朝屯田西域,进而统一西域,大月氏、乌孙、匈奴西迁至西域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大月氏、乌孙和匈奴为生存而争夺领地的战争连绵不断,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公元前2世纪左右居于河西的大月氏人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徙至伊犁河、楚河流域,月氏又打败了伊犁等地的塞人,使他们向更西的方向迁徙。原在河西地区与大月氏人为邻的乌孙人又联合匈奴打败刚刚迁徙至伊犁河流域不久的大月氏人,迫使其向西迁移。乌孙在汉王朝与匈奴的征战中时而与匈奴交好,时而又与汉王朝联姻,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汉王朝为对付匈奴,曾和大月氏、乌孙或联络或结盟过。大月氏、乌孙、匈奴均系游牧部落,因此在文化上大同小异,而西迁至西域后,有一部分在天山以南的农耕绿洲环境中转型成为定居的农耕民。从甲乙两种吐火罗语方言流行焉耆、龟兹等地的事实不难断定月氏人(即吐火罗人)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建绿洲城郭而定居,经济生活方式也变为以绿洲农业为主的印记。大月氏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与且末间所建立的小宛国也表明,在汉代至少有一部分大月氏人在此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原先的居民——塞人发生了接触。韩康信先生认为,形成乌孙部落的人类学类型的大人种基础是欧洲人种,其中有轻度蒙古人种的混杂。①魏晋以后,这些部落又融合到铁勒、突厥诸部落中去了。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后,汉族正式登上西域多民族的历史舞台。西汉政府先后在天山南北的轮台、楼兰、伊循、柳中、交河、伊吾、蒲类、金满、赤谷等地屯田,汉人在西域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成了连接农耕居民和游牧部落的纽带。车师人是秦汉之际生活在天山以东、以北的今吐鲁番、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一带的土著居民,汉代分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根据出土文物,车师前国地居吐鲁番绿洲,是以农业为主的绿洲城郭,而车师后国在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一带,仍以畜牧业为主。吐鲁番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民族迁徙的孔道,故车师人也带来了民族融合的特征。考古发现的车师人的头骨显示出了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如果说两汉时期西域的主要居民是操东伊朗语民族的话,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除汉族人口剧增和吐蕃进入西域外,突厥人的西迁,一下使突厥人口陡增。但是,东伊朗语族、汉藏语族和阿尔泰语系操突厥语族就人口而言,似乎是势均力敌。待到唐王朝统一西域时,西域形成了新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是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与唐朝推行‘华夷一家’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地,唐代的伊、西、庭三州也主要是汉族居民,汉族军民还广泛分布在天山南北屯田。5~6世纪,游牧的〓哒和柔然活动于天山南北地区,所居地区是塞人和大月氏人故地于阗、疏勒、姑墨、龟兹、焉耆一带,其势力还达准噶尔盆地一带。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哒、柔然又受到绿洲农耕居民文化的影响。灭柔然的突厥人在隋唐时期建立的横跨亚洲北部草原的突厥汗国因内外诸多因素而分裂为东西突厥汗国后,在西域建立政权的是西突厥。西突厥在唐王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归附和反唐统治的不同时期。虽然关系错综复杂,但西突厥的确加快了西域部分地区突厥化的进程。
西突厥曾在唐初控制了天山以南和准噶尔盆地以东;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南,至锡尔河以北;葱岭以西,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这些地区有些属于草原地带,突厥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而进入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后,突厥人与当地土著居民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即使像麴氏高昌王国这样的汉族政权因与突厥联姻在文化上相互影响,麴氏高昌王国的上层在服饰和头饰方面也出现仿效突厥人的时尚潮流。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古墓发现的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显然系突厥人的辫饰和服饰。高昌王麴伯雅还曾下令高昌国人“被发左衽”,这是典型的突厥习俗。突厥宗教信仰、官制、军制、历法以及婚丧习俗也与西域土著居民的习俗互为表里。西突厥本来就是由诸多部落形成的部落联盟,《唐书》指出:“(西突厥)杂有都陆、弩失毕、歌逻录、处月、处蜜、伊吾等诸种。”歌逻录即葛逻禄,此部自10世纪建立的喀喇汗王朝东部汗因皈依伊斯兰教,使喀什噶尔、于阗等地首先伊斯兰化。但是就民族融合而言,西突厥与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和费尔干纳盆地绿洲农耕居民比起来,人口毕竟是少数,很可能是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融合在操东伊朗语的定居民中了。
840年回鹘人被黠戛斯人打败之后,有一支西迁至高昌、北庭一带,建立回鹘汗国。回鹘居漠北时就与唐有密切关系,因唐王朝将宁国公主、咸安郡公主、太和公主先后下嫁回纥,回纥与唐王朝皇帝曾以甥舅相称,其时回纥又信仰汉传佛教。而在高昌建国的回鹘汗国所居之地先是阚氏、麴氏等河西汉人所在之地,后又是唐西州地区,故回鹘与汉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回鹘也正在此以后由游牧部落逐渐转变为农耕定居民。在高昌、北庭等地,回鹘人实际上与汉人处于杂居状态,不仅农耕技术是从汉族那儿学习来的,连最初的回鹘佛教寺院也是沿用了汉人的佛教寺院。从柏孜克里克回鹘佛教寺窟高昌回鹘王族服饰看,男子穿一种丝绸缝制的宽袖、下摆长的宽大衣服,腰间佩刀或短剑等,符合唐朝武官服饰制度。贵妇身着通裾大襦、领口呈桃形,饰有云纹图案,头施博髻冠也是汉族贵妇打扮。随着回鹘向龟兹等地的扩展,操突厥语的回鹘势力与喀喇汗王朝正对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操东伊朗语的定居民形成夹击之势,一场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期还有吐蕃人进入西域,虽然吐蕃还不足以影响西域民族融合的进程,但吐蕃文化在各方面的渗透也是不容忽视的。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是两个北方民族建立的中国封建王朝。这两个王朝在统一西域后,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元时期,游牧的蒙古人想用蒙古军政制度和习惯法统御西域,结果在一个操突厥语民族成分为主的西域,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区,蒙古人也放弃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接受了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再加之伊斯兰教东扩的影响,这部分蒙古人出现了“伊斯兰化”的趋势。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这些由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后裔建立的蒙古族政权根本无法抵挡操突厥语民族的融合力,蒙古人也就融入到这些民族中了,尽管这些政权还保留着蒙古人的军政制度称号。元朝出于统治需要,曾将吐鲁番等地的畏兀儿人调遣至内地为官、为文、经商和从事百工定居,这些人也渐渐汉化并融合到汉民族中。《明史》曰:“元时,回回遍天下。”正是指西域色目人遍及内地的情形。对这种盛况,后有学者慨叹:“元代来居中国之西域人,除上述武人、政客、商人外,尚有天文学家、宗教师、星相家、建筑师以及技艺百工之流,不胜枚举。”①元代是西域诸民族融合的高潮。清代,清朝政府为统一西域,一方面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向西域移民,基本上奠定了近代新疆各民族的格局。近代的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满、锡伯、达斡尔、塔吉克和沙俄入侵后迁来的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三个民族构成新疆的主要民族成分。这些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型分布。维吾尔族虽然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地区,但随着回屯向北扩展,他们也分布在伊犁等天山以北地区。柯尔克孜、塔吉克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一带。而哈萨克、准噶尔蒙古则分布于天山以北的伊犁等地区。锡伯、察哈尔蒙古、达斡尔是清乾隆年间被清政府征调西迁至伊犁、塔城等北疆地区的。为官为军的满族八旗则遍及天山南北。迁移来的汉族、回族居民分布在北疆、东疆一带,清代后期汉族、回族也在向天山以南地区分布。这种犬牙交错的民族分布恰恰有利于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局面的形成。
文化包容是一种文化互融互渗的族际文化共享现象。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形成了两个、多个乃至多数民族共同拥有一种文化的现象,正是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方面与不同民族的交叉,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民族的交叉,造成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入的交叉网络。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有汉族文化在各民族文化联系中的主线作用,各民族文化的交织、融合,使族际共享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总体共享”①。这种族际文化共享,一是由经济互补带来的,二是制度文化整合的结果,三是精神文化的交融导致的。在历史上,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之间在各个层面都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族际文化共享关系。自汉唐统一西域起,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越来越呈现出整合的态势,它反映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形成一种文化包容关系。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西汉统一西域,中原的物质文明远播到丝绸之路南北道诸地。在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都出土有锦、绮、罗、刺绣等丝织物。在以上三地出土不同纹样的汉锦有二十余种,颜色有宝蓝、藏青、绛红、葱绿、绛紫、深棕等十多种。这些汉锦上嵌织汉隶书,都是吉祥、富贵、长寿类文字,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世如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从着锦袍的死者看,大多是本地的王公贵族,但丝织物显然来自内地。以中原式的寿服埋葬死者,证明中原丧葬习俗中的观念、信仰也被西域各民族接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主要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这些丝织物样式、花色更丰富。锦、绮、纱、罗、刺绣、印花绢、绫均有出土。魏晋至唐时,高昌居民主要是河西迁来的汉民,因此在服饰上完全承袭了汉俗,但在与周边其他居民交往中,这些丝织物也打上了本土化的烙印。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物种、造纸术、铜镜、漆器等也随之传入西域。同样,西域的物质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自汉唐以降西域的胡瓜、胡蒜、胡萝卜、石榴、胡桃、葡萄以及种棉、酿葡萄酒技术传入内地,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得到提升。当然物质文明交流有一个拿来—模仿—借鉴—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的模仿到创新,都显示着族际文化共享的特征。中原地区的唐镜在中原、西域、中亚乃至南西伯利亚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唐镜往往都有民汉、中西合璧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唐镜的制作中其纹饰大量吸收了西域文化中的装饰艺术,其饰纹有瑞兽葡萄纹、有翼马纹、象纹、打马球纹等。以瑞兽葡萄纹铜镜为例,由葡萄纹与瑞兽(亦称海兽,原型为狮子)形成组合,从外在形式看是受西域文化影响所致,但反映的是中原人的传统观念:葡萄藤叶长长象征长寿,葡萄果实串串象征多子、富贵,瑞兽象征威武、吉祥。
从制度文化层面看,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也是一种族际共享关系。汉王朝统一西域后,在西域广泛推行中原制度文化,除委派西域都护,委任副校尉等职官外,还以册封、颁发印绶等方式加强管理。西汉时“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无论是职官名称还是管理方式,在制度文化方面既保留了西域职官特色,又置于中央统一管理下。唐朝在西域实行的政治管理制度是以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诸部的,其建制分州县制和都督府制。在东部地区,汉族居民相对集中的地方设州、县、乡、里,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则设都督府,任命本地人充任各级官职。职官有中原汉名,也有西域本土名称。清统一西域和新疆建省后,新疆的制度文化与中原制度文化日趋一致,特别是新疆建省后,实行了与内地统一的州县建制,标志着政治制度的统一。清代中国的制度文化本来就是以汉族制度文化为主,兼容了满等少数民族制度文化的受容体,而到了新疆又增添了一些地域制度文化特色,如在南疆实行的伯克制,在蒙古族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地区实行的扎萨克制。但清统一新疆后至新疆建省前的伯克制已非世袭制,而是由清廷任免,分3~7个品级。清代新疆的制度文化其实是汉、满制度文化与新疆各民族制度文化更广泛融合的产物。
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艺术更是在双向回授中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隋唐时期的龟兹乐舞、疏勒乐舞、高昌乐舞传入中原地区后形成了隋唐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这个时期还有于阗画派的尉迟乙僧父子驰名长安画坛,他们的凹凸晕染画法对中原画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龟兹、高昌等地的石窟艺术也是汉风、键陀罗风格与本土风格的互显,无论是雕塑还是壁画、建筑艺术都有各种流派、风格相互融合的特点。就连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出现的《福乐智慧》其思想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有学者认为,《福乐智慧》与中国汉民族的《治道集》、《九谏书》、《帝范臣轨》内容更为接近。①在元代民族大融合时期,西域不少色目人的知识分子在中原地区深受汉文化熏染,像马祖常、贯云石、偰玉立、萨都剌、薛昂夫等来自西域的文人均以汉文诗作、散曲蜚声中原,对中国诗歌发展有杰出贡献。流传中原至今的狮子舞也是从西域传到内地的,龟兹狮子舞又是从波斯传入的,而后又传入内地。民俗方面的相互渗透也是中原汉文化与西域诸民族文化族际共享的重要方面。和田地区出土两具晚唐五代时期的彩棺,属当地土著贵族棺椁,而棺盖内面则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其构图、题材、风格纯为中原汉风,而且属道教文化系统。道教玄武图所寓的生命永恒主题在遥远的于阗扎根,表明中华各民族在体认生命意识方面是相通的。清代以来,更是出现了各民族在艺术、饮食文化方面族际共享的新局面。
从考古发现得知,丝绸之路上中段西域最早迁徙的主要是塞人和羌人。操伊朗语的塞人从东南欧向黑海以北迁徙,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之后又迁移进入中亚、伊朗西部和印度,而中亚塞人的一支又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天山以南的塞人适应绿洲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农耕民,而天山以北地区的塞人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我国新疆南部的于阗地区,直至10世纪还存在着操和田塞语的民族。从现代学者的研究可知,和田塞语属于东伊朗语支,与粟特语、花剌子模语有近亲关系。这一支操印欧语的民族只能是从塔吉克斯坦或其以北地区迁入的。根据汉文资料记载,公元前3—前2世纪,今新疆相当大部分地区为塞种集团所占据”①。不仅于阗、帕米尔高原一带是操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地,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则是塞人的游牧地。春秋战国时期聚居于河西一带的强大的羌人集团曾先后向东、南、西三面迁徙,其中一支西迁进入天山以南地区,一直到两汉时期,若羌、楼兰(鄯善)、且末、于阗、蒲犁、龟兹等地都是羌人活动的地域。曾在今阿克苏地区的新和县于什格提(三道城)遗址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印背上的钮为卧羊形,表明羌人在龟兹地区的活动。羌人属汉藏语系的游牧部落。《说文解字》解释羌字为“西戎牧羊人也”。“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①。羌可能来自殷商人对他们的称呼。羌人西迁至昆仑山北麓后,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也从事了农业。在西域,羌人自东面的若羌至最西边的葱岭广泛分布。这种分布,在地域上往往又与塞人的分布相重合,表明东来的汉藏语系的羌人与西迁的东伊朗语族的塞人在天山以南地区相遇、接触并发生了融合。这是迄今所知的发生在西域的最早的民族融合。如果从文化习俗上区分,塞人是头戴尖顶帽的氏族集团,而羌人则是头戴羊角帽的氏族集团。中亚草原以及天山南北地区的墓葬中均出土有塞人的毡制尖顶帽。塞人早期是信仰太阳神的,这与他们的拜火教信仰是一致的。尖顶帽可能与他们信仰中沟通天界的宇宙山、生命树属同一个象征符号体系,久而久之,尖顶帽世俗化,成为塞人的文化标志。而羌人的羊角帽也有不同的文化表征,羌人戴羊角帽可能源自他们的图腾——羊,羌早期是一个以羊为图腾的氏族集团。在辛店文化中有羊角柱图案的彩陶出土,它就是羌族的图腾柱,在羊角纹上还绘有太阳纹。由于太阳能滋育畜群繁衍,故只有羊能配得上太阳,于是向太阳神献祭就以羊为主。“以羊象征太阳神,源出于羌戎族。羌族羊祭,图腾神以羊名,因以‘日’名‘太阳’即‘大羊’(样)”②。可见,羌人与塞人一样都是献祭太阳神的,只是祭品不同,羌人用羊献祭,而塞人则以跑得最快的马献祭。这两个古代部落在接触、混杂、连接的融合中,文化间的包容就在所难免了。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有史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主要有四次,即两汉时期、隋唐时期、蒙元时期和清代。这四个时期是西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最重要时期,每一个时期的统一都反映了更高层次上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汉代民族迁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向西迁徙。汉王朝屯田西域,进而统一西域,大月氏、乌孙、匈奴西迁至西域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大月氏、乌孙和匈奴为生存而争夺领地的战争连绵不断,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公元前2世纪左右居于河西的大月氏人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徙至伊犁河、楚河流域,月氏又打败了伊犁等地的塞人,使他们向更西的方向迁徙。原在河西地区与大月氏人为邻的乌孙人又联合匈奴打败刚刚迁徙至伊犁河流域不久的大月氏人,迫使其向西迁移。乌孙在汉王朝与匈奴的征战中时而与匈奴交好,时而又与汉王朝联姻,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汉王朝为对付匈奴,曾和大月氏、乌孙或联络或结盟过。大月氏、乌孙、匈奴均系游牧部落,因此在文化上大同小异,而西迁至西域后,有一部分在天山以南的农耕绿洲环境中转型成为定居的农耕民。从甲乙两种吐火罗语方言流行焉耆、龟兹等地的事实不难断定月氏人(即吐火罗人)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建绿洲城郭而定居,经济生活方式也变为以绿洲农业为主的印记。大月氏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与且末间所建立的小宛国也表明,在汉代至少有一部分大月氏人在此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原先的居民——塞人发生了接触。韩康信先生认为,形成乌孙部落的人类学类型的大人种基础是欧洲人种,其中有轻度蒙古人种的混杂。①魏晋以后,这些部落又融合到铁勒、突厥诸部落中去了。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后,汉族正式登上西域多民族的历史舞台。西汉政府先后在天山南北的轮台、楼兰、伊循、柳中、交河、伊吾、蒲类、金满、赤谷等地屯田,汉人在西域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成了连接农耕居民和游牧部落的纽带。车师人是秦汉之际生活在天山以东、以北的今吐鲁番、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一带的土著居民,汉代分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根据出土文物,车师前国地居吐鲁番绿洲,是以农业为主的绿洲城郭,而车师后国在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一带,仍以畜牧业为主。吐鲁番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民族迁徙的孔道,故车师人也带来了民族融合的特征。考古发现的车师人的头骨显示出了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如果说两汉时期西域的主要居民是操东伊朗语民族的话,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除汉族人口剧增和吐蕃进入西域外,突厥人的西迁,一下使突厥人口陡增。但是,东伊朗语族、汉藏语族和阿尔泰语系操突厥语族就人口而言,似乎是势均力敌。待到唐王朝统一西域时,西域形成了新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是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与唐朝推行‘华夷一家’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地,唐代的伊、西、庭三州也主要是汉族居民,汉族军民还广泛分布在天山南北屯田。5~6世纪,游牧的〓哒和柔然活动于天山南北地区,所居地区是塞人和大月氏人故地于阗、疏勒、姑墨、龟兹、焉耆一带,其势力还达准噶尔盆地一带。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哒、柔然又受到绿洲农耕居民文化的影响。灭柔然的突厥人在隋唐时期建立的横跨亚洲北部草原的突厥汗国因内外诸多因素而分裂为东西突厥汗国后,在西域建立政权的是西突厥。西突厥在唐王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归附和反唐统治的不同时期。虽然关系错综复杂,但西突厥的确加快了西域部分地区突厥化的进程。
西突厥曾在唐初控制了天山以南和准噶尔盆地以东;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南,至锡尔河以北;葱岭以西,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这些地区有些属于草原地带,突厥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而进入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后,突厥人与当地土著居民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即使像麴氏高昌王国这样的汉族政权因与突厥联姻在文化上相互影响,麴氏高昌王国的上层在服饰和头饰方面也出现仿效突厥人的时尚潮流。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古墓发现的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显然系突厥人的辫饰和服饰。高昌王麴伯雅还曾下令高昌国人“被发左衽”,这是典型的突厥习俗。突厥宗教信仰、官制、军制、历法以及婚丧习俗也与西域土著居民的习俗互为表里。西突厥本来就是由诸多部落形成的部落联盟,《唐书》指出:“(西突厥)杂有都陆、弩失毕、歌逻录、处月、处蜜、伊吾等诸种。”歌逻录即葛逻禄,此部自10世纪建立的喀喇汗王朝东部汗因皈依伊斯兰教,使喀什噶尔、于阗等地首先伊斯兰化。但是就民族融合而言,西突厥与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和费尔干纳盆地绿洲农耕居民比起来,人口毕竟是少数,很可能是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融合在操东伊朗语的定居民中了。
840年回鹘人被黠戛斯人打败之后,有一支西迁至高昌、北庭一带,建立回鹘汗国。回鹘居漠北时就与唐有密切关系,因唐王朝将宁国公主、咸安郡公主、太和公主先后下嫁回纥,回纥与唐王朝皇帝曾以甥舅相称,其时回纥又信仰汉传佛教。而在高昌建国的回鹘汗国所居之地先是阚氏、麴氏等河西汉人所在之地,后又是唐西州地区,故回鹘与汉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回鹘也正在此以后由游牧部落逐渐转变为农耕定居民。在高昌、北庭等地,回鹘人实际上与汉人处于杂居状态,不仅农耕技术是从汉族那儿学习来的,连最初的回鹘佛教寺院也是沿用了汉人的佛教寺院。从柏孜克里克回鹘佛教寺窟高昌回鹘王族服饰看,男子穿一种丝绸缝制的宽袖、下摆长的宽大衣服,腰间佩刀或短剑等,符合唐朝武官服饰制度。贵妇身着通裾大襦、领口呈桃形,饰有云纹图案,头施博髻冠也是汉族贵妇打扮。随着回鹘向龟兹等地的扩展,操突厥语的回鹘势力与喀喇汗王朝正对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操东伊朗语的定居民形成夹击之势,一场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期还有吐蕃人进入西域,虽然吐蕃还不足以影响西域民族融合的进程,但吐蕃文化在各方面的渗透也是不容忽视的。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是两个北方民族建立的中国封建王朝。这两个王朝在统一西域后,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元时期,游牧的蒙古人想用蒙古军政制度和习惯法统御西域,结果在一个操突厥语民族成分为主的西域,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区,蒙古人也放弃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接受了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再加之伊斯兰教东扩的影响,这部分蒙古人出现了“伊斯兰化”的趋势。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这些由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后裔建立的蒙古族政权根本无法抵挡操突厥语民族的融合力,蒙古人也就融入到这些民族中了,尽管这些政权还保留着蒙古人的军政制度称号。元朝出于统治需要,曾将吐鲁番等地的畏兀儿人调遣至内地为官、为文、经商和从事百工定居,这些人也渐渐汉化并融合到汉民族中。《明史》曰:“元时,回回遍天下。”正是指西域色目人遍及内地的情形。对这种盛况,后有学者慨叹:“元代来居中国之西域人,除上述武人、政客、商人外,尚有天文学家、宗教师、星相家、建筑师以及技艺百工之流,不胜枚举。”①元代是西域诸民族融合的高潮。清代,清朝政府为统一西域,一方面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向西域移民,基本上奠定了近代新疆各民族的格局。近代的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满、锡伯、达斡尔、塔吉克和沙俄入侵后迁来的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三个民族构成新疆的主要民族成分。这些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型分布。维吾尔族虽然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地区,但随着回屯向北扩展,他们也分布在伊犁等天山以北地区。柯尔克孜、塔吉克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一带。而哈萨克、准噶尔蒙古则分布于天山以北的伊犁等地区。锡伯、察哈尔蒙古、达斡尔是清乾隆年间被清政府征调西迁至伊犁、塔城等北疆地区的。为官为军的满族八旗则遍及天山南北。迁移来的汉族、回族居民分布在北疆、东疆一带,清代后期汉族、回族也在向天山以南地区分布。这种犬牙交错的民族分布恰恰有利于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局面的形成。
文化包容是一种文化互融互渗的族际文化共享现象。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形成了两个、多个乃至多数民族共同拥有一种文化的现象,正是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方面与不同民族的交叉,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民族的交叉,造成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入的交叉网络。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有汉族文化在各民族文化联系中的主线作用,各民族文化的交织、融合,使族际共享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总体共享”①。这种族际文化共享,一是由经济互补带来的,二是制度文化整合的结果,三是精神文化的交融导致的。在历史上,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之间在各个层面都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族际文化共享关系。自汉唐统一西域起,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越来越呈现出整合的态势,它反映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形成一种文化包容关系。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西汉统一西域,中原的物质文明远播到丝绸之路南北道诸地。在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都出土有锦、绮、罗、刺绣等丝织物。在以上三地出土不同纹样的汉锦有二十余种,颜色有宝蓝、藏青、绛红、葱绿、绛紫、深棕等十多种。这些汉锦上嵌织汉隶书,都是吉祥、富贵、长寿类文字,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世如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从着锦袍的死者看,大多是本地的王公贵族,但丝织物显然来自内地。以中原式的寿服埋葬死者,证明中原丧葬习俗中的观念、信仰也被西域各民族接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主要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这些丝织物样式、花色更丰富。锦、绮、纱、罗、刺绣、印花绢、绫均有出土。魏晋至唐时,高昌居民主要是河西迁来的汉民,因此在服饰上完全承袭了汉俗,但在与周边其他居民交往中,这些丝织物也打上了本土化的烙印。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物种、造纸术、铜镜、漆器等也随之传入西域。同样,西域的物质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自汉唐以降西域的胡瓜、胡蒜、胡萝卜、石榴、胡桃、葡萄以及种棉、酿葡萄酒技术传入内地,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得到提升。当然物质文明交流有一个拿来—模仿—借鉴—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的模仿到创新,都显示着族际文化共享的特征。中原地区的唐镜在中原、西域、中亚乃至南西伯利亚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唐镜往往都有民汉、中西合璧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唐镜的制作中其纹饰大量吸收了西域文化中的装饰艺术,其饰纹有瑞兽葡萄纹、有翼马纹、象纹、打马球纹等。以瑞兽葡萄纹铜镜为例,由葡萄纹与瑞兽(亦称海兽,原型为狮子)形成组合,从外在形式看是受西域文化影响所致,但反映的是中原人的传统观念:葡萄藤叶长长象征长寿,葡萄果实串串象征多子、富贵,瑞兽象征威武、吉祥。
从制度文化层面看,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也是一种族际共享关系。汉王朝统一西域后,在西域广泛推行中原制度文化,除委派西域都护,委任副校尉等职官外,还以册封、颁发印绶等方式加强管理。西汉时“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无论是职官名称还是管理方式,在制度文化方面既保留了西域职官特色,又置于中央统一管理下。唐朝在西域实行的政治管理制度是以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诸部的,其建制分州县制和都督府制。在东部地区,汉族居民相对集中的地方设州、县、乡、里,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则设都督府,任命本地人充任各级官职。职官有中原汉名,也有西域本土名称。清统一西域和新疆建省后,新疆的制度文化与中原制度文化日趋一致,特别是新疆建省后,实行了与内地统一的州县建制,标志着政治制度的统一。清代中国的制度文化本来就是以汉族制度文化为主,兼容了满等少数民族制度文化的受容体,而到了新疆又增添了一些地域制度文化特色,如在南疆实行的伯克制,在蒙古族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地区实行的扎萨克制。但清统一新疆后至新疆建省前的伯克制已非世袭制,而是由清廷任免,分3~7个品级。清代新疆的制度文化其实是汉、满制度文化与新疆各民族制度文化更广泛融合的产物。
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艺术更是在双向回授中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隋唐时期的龟兹乐舞、疏勒乐舞、高昌乐舞传入中原地区后形成了隋唐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这个时期还有于阗画派的尉迟乙僧父子驰名长安画坛,他们的凹凸晕染画法对中原画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龟兹、高昌等地的石窟艺术也是汉风、键陀罗风格与本土风格的互显,无论是雕塑还是壁画、建筑艺术都有各种流派、风格相互融合的特点。就连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出现的《福乐智慧》其思想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有学者认为,《福乐智慧》与中国汉民族的《治道集》、《九谏书》、《帝范臣轨》内容更为接近。①在元代民族大融合时期,西域不少色目人的知识分子在中原地区深受汉文化熏染,像马祖常、贯云石、偰玉立、萨都剌、薛昂夫等来自西域的文人均以汉文诗作、散曲蜚声中原,对中国诗歌发展有杰出贡献。流传中原至今的狮子舞也是从西域传到内地的,龟兹狮子舞又是从波斯传入的,而后又传入内地。民俗方面的相互渗透也是中原汉文化与西域诸民族文化族际共享的重要方面。和田地区出土两具晚唐五代时期的彩棺,属当地土著贵族棺椁,而棺盖内面则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其构图、题材、风格纯为中原汉风,而且属道教文化系统。道教玄武图所寓的生命永恒主题在遥远的于阗扎根,表明中华各民族在体认生命意识方面是相通的。清代以来,更是出现了各民族在艺术、饮食文化方面族际共享的新局面。
附注
①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1.
①于省吾.释羌、苟、敬、美.吉林大学学报.1963(1).
②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152.
①韩康信.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1992(2).
②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横排本).新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刊印,1986.243.
①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6.
①陈恒富.《福乐智慧》与祖国文化传统.《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集(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50.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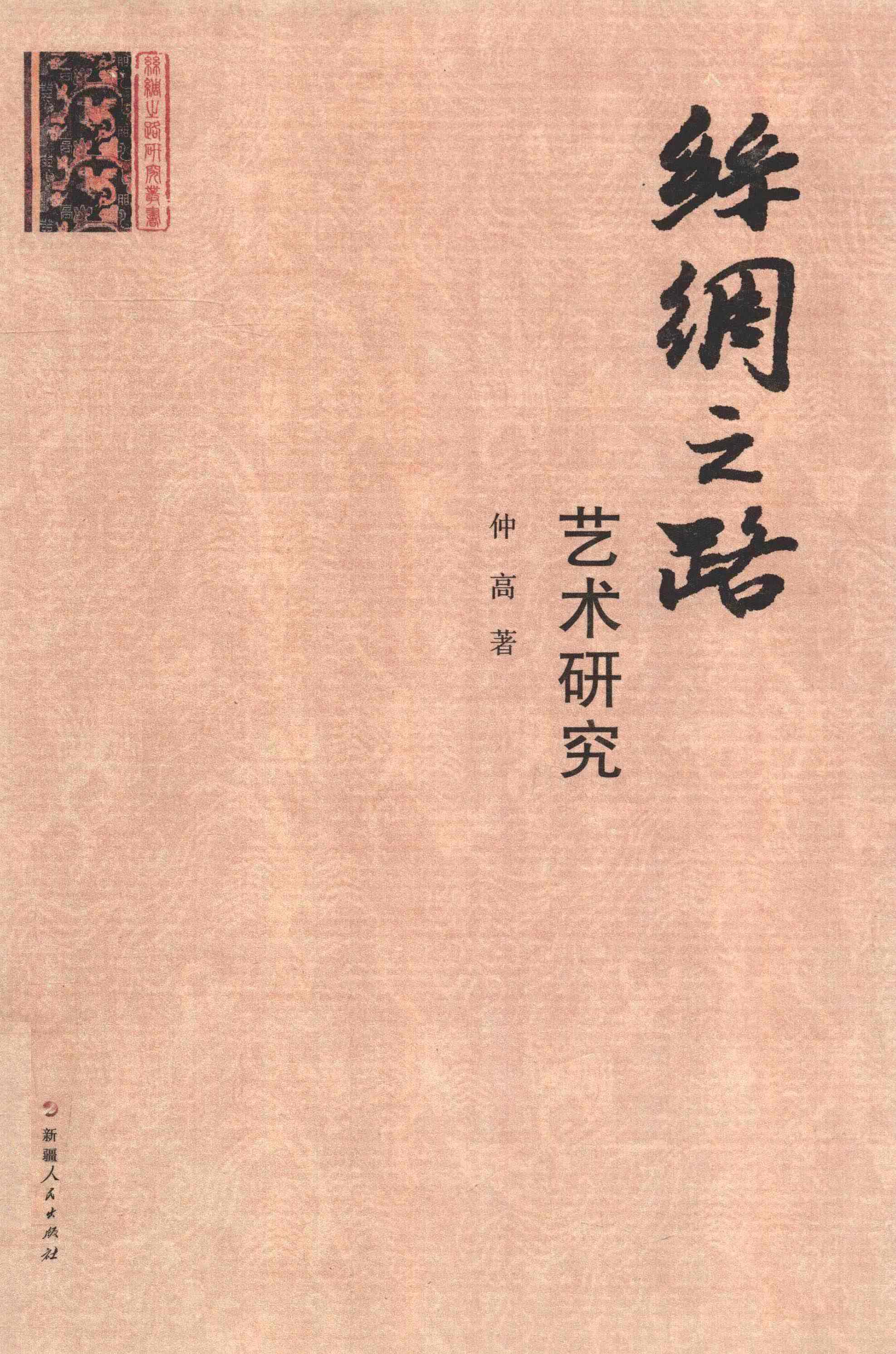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