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粟特:文化艺术的中介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53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粟特:文化艺术的中介 |
| 分类号: | K879.45 |
| 页数: | 8 |
| 页码: | 272-278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粟特:文化艺术的中介情况包括粟特文化是绿洲农耕型定居文化,因九姓胡诸国人多经商,故筑城而居,形成商业性的城邦文化。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波斯文化 艺术文化 |
内容
粟特,这个中亚绿洲的古老居民,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汉籍中,汉代称其为粟弋,唐代谓之窣利、九姓昭武。虽然名称不同,但均指中亚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粟特人地居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泽拉夫尚河为中心的绿洲地区。这个地区就是古代的索格底亚那,意为火地,很可能与粟特人信奉拜火教有关。唐时,粟特分成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九国,故以国名冠以“九姓”。于是,唐人习惯称九姓胡为杂种胡。③粟特所居之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得地理之便,依托丝绸之路,粟特人成了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胡贩客”,并建立以康国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诸多城邦国,有“千城之国”之称。因为粟特人“善商贾”近乎天性,所以也就“以得利多为善”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丝绸之路上到处都有粟特商人的足迹了。粟特人“兴生贩货,无远不至”的秉性,使他们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旅,同时也扮演了文化中介的角色。粟特人肩负着经商贸易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功能,而后者正是由前者引发的。
粟特文化是绿洲农耕型定居文化,因九姓胡诸国人多经商,故筑城而居,形成商业性的城邦文化。粟特人是如何筑城而居的,从现存距撒马尔罕以东60公里处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不难看出,在中古时期它就是粟特人属“都”一级的城邦。该城建成于5世纪,8世纪初毁于阿拉伯人的入侵。这是粟特的经济、文化的全盛期。《新唐书》曾描绘此城是: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绘突厥、婆罗门,西绘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这至少表明粟特在文化上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夹在诸大国之间,也只能以一种变通的方式左右逢源了。事实上,粟特曾受突厥监摄,也曾作为唐朝的羁縻州存在过,但是仍有粟特人自己的统辖系统。这种蕃、汉、胡的多重政治结构自然也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因此,可以说粟特文化是有极强适应性的文化。古代中亚城市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供统治者居住的内城和由贵族宅第、市场组成并筑有城墙的本城以及城市的外围。片治肯特古城则包括环绕城墙的本城,西边山丘上的设防卫城,城外东边的建筑群和东南边的墓地。建筑材料为大型砖坯和切割成大块的黏土制件。考古发掘出该城两座神庙,并排坐落在城中广场西面。每座神庙由各式房间和正方形院落组成。每一座神庙的中心建筑居于高台之上,东边为立有几根圆柱的门厅,与四柱大厅连为一体,大厅的西面为封闭的圣殿和环绕大厅的回廊。神庙正面朝东,为粟特人早期崇拜太阳神密特拉的反映。门厅用黏土质彩绘浮雕装饰,可能源于贵霜艺术传统。门厅和大厅装饰有壁画,大厅深处门口立有大型塑像。南面神庙壁画是人和众神的《哭哀图》。神庙应为粟特本土化的多神教庙宇。城中贵族住宅区的每个住宅单元由10~15个房间组成,有两层或三层的,分别有大客厅、拱顶房、走廊、储藏室等。客厅的梁木、柱头、柱身、墙壁上的木质缘饰均有几何纹、植物纹以及神、人和动物形象的雕刻装饰。客厅墙壁有含某种故事情节的装饰性壁画,正面墙上绘有中心人物,其他墙面绘有征战功绩,有庆功的宴会或隆重的接见场面。粟特贵族宅第以叙事性故事壁画进行装饰十分普遍,除装饰性外,主要和某段历史或主人公的经历有关,还有的则是史诗故事和寓言等,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片治肯特的内城除平房或二层楼住宅区外,街区店铺、作坊十分密集,金银器作坊、铁作坊、陶器作坊、织布作坊、制革作坊和玻璃作坊均有分布。这与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所反映的“邦民”情况是一致的。这些城邦是以邦民社会为主体的等级社会,“邦民下层包括:从事金银作、铁作和陶作的工匠,以及做小本生意的各类商贩。在水渠劳作的浇水工,也属庶民。邦民上层是一群僧俗显贵:祆主、商队主和钱庄老板。此外,还有一系列与内陆性商业城邦适应的官吏、税吏、马监、主簿、驿站长和河渠官,等等”①。城市的扩增,发达的手工业和日益增长的商业贸易刺激了工艺艺术的发展。粟特金银器皿、陶器、纺织等工艺制作业日益成为粟特人最重要的手工业。粟特金银器因19世纪末阿姆河宝藏的发现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各地的出土,其面貌逐渐清晰起来。这些金银制作的带柄壶、带柄杯、盘、碗等器皿多以动、植物纹样装饰,武士、有翼骆驼等神话意象常出现在金银器装饰中。在构图上常以中心饰物,周围留空布局,其工艺为浮雕式。“在阿姆河宝藏中还有一件金质提壶,金壶明显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下部近似一个球体,表面有楞条状装饰,上部近似一个喇叭口,表面无纹饰,口部有流,略似鸟头形,其下无圈足。最有特色的是金壶有一半环状把手,把手下端接于金壶中部,上端为一精美的狮头造型,狮口正好衔住金壶口沿”①。粟特提壶的基本特征也就成了低或无圈足,短颈粗腰,把手为动物造型,且直接接于沿口,壶体表面无复杂装饰等。这与萨珊波斯高圈足,壶把手按在壶体上部,壶体表面图案装饰复杂有明显区别。武士决斗题材的粟特镀金银盘属7世纪器皿,表现的是一个拿长矛的武士同另一个持弓箭的武士进行决斗的过程。两位武士全身披甲,身旁弃置圆锤、剑、斧等武器,可能在用这些武器长时间决斗不分胜负后才决定用长矛和弓箭决一雌雄。另一件7世纪饰有双翼骆驼形象的镀金银壶,题材类似于瓦拉赫沙宫殿中一个大厅中的壁画。所以有翼骆驼形象应来源于粟特人古老的神话意象是无疑的。
粟特诸城邦国中制陶业也成为主要的手工业。早在希腊化时期,粟特人就因制作小型陶塑像出名,特别是出现诸如自然女神、家庭保护神、幸福女神塑像。起初是陶制半裸女神像,后又演变为身着宽大外裙和斗篷、衣褶垂直且神态庄重的女神像,一般为端庄的正面像,大脑袋与程式化手臂姿势不相称。这些女神像相貌、冠帽有地域性,但直垂衣褶则为希腊式。几乎所有的女神像都有象征意义,被称为“大女神”的陶像是丰产的大地的象征,而梅尔夫出土的立式女神像手持象征太阳或命运的标志,与粟特人信仰的拜火教中的神祗有关。撒马尔罕出土的女神像手持郁金香和石榴,是春天和多子多产的象征。布哈拉出土的有贵妇气质的陶像则是城市保护女神。6~8世纪,粟特由于与唐朝、突厥、波斯、印度等频繁的文化交往,制陶业处在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粟特陶器“也有采用在泥质陶器的表面敷施一层云母的方法。显然,这是为了表现金属艺术品的加工工艺。大量的陶器都是塑成各种造型,器表和形制粗糙者极少见,有的还用蓖子饰以简单的图案”②。赤陶塑像主要是骑马、骑象、骑公羊的骑手形象和一些怪异动物,再有就是尸骨瓮上的浮雕像。其中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出土的一件尸骨瓮浮雕中有四个拱门,每个门前为一立式人像,可能象征火、水、土、气四大元素。从人物造像和构图不难发现模仿萨珊人物画的迹象,起码粟特的制陶工匠对萨珊波斯的制陶工艺是十分熟悉的。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中亚后,粟特陶器中非偶像化的几何、植物图案装饰成了主流。上釉陶器上棕榈叶的各种式样和波浪形嫩枝、几何图形轮廓线与弧线相交后用石榴、郁金香、玫瑰等作为装饰纹样取代了人物、动物纹样,陶器的色彩也由起初的淡绿、淡黄、淡棕色变成浓重的深褐色、灰绿色、紫色等。12世纪后粟特陶器艺术走向终结。
“为了最大限度地适应国际贸易,粟特的织工们常常以萨珊伊朗的、中国的和拜占庭的图案风格装饰自己的产品”①。但是在中古时期这样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影响总是相互的。唐代那种花纹布满全幅的织锦中出现了中亚、西亚盛行的忍冬纹、葡萄纹等,甚至连波斯式、粟特式的联珠对兽、对鸟纹也在唐朝盛行;中国风格的花鸟纹锦也流行在粟特、萨珊波斯。唐锦、波斯锦、拜占庭锦和粟特锦在中古时期的丝织品工艺中各领风骚。穆格山出土的粟特织物就有丝织品、毛织品、棉织品等,纹样也分格纹、联珠纹、联花纹、梅花纹、联星纹、平纹素织等多种。在丝织品中以布哈拉赞达纳出土的织锦为代表,被称为“赞达涅奇”。这是一种联珠对兽、对鸟的纹样,较多受到此类波斯织锦的影响。比利时尤伊城教堂所收藏的一件属7世纪的有粟特文题记的对羊织锦中间为站在天平上的装饰性对羊,四周为联珠纹,被确认为是“赞达涅奇”风格的丝织品,纹样似有买卖公平的寓意。另一件发现于高加索的属6~7世纪的织锦“圆框一周有以荷花组成的饰带,这是对典型的拜占庭织物图案的模仿,圆框之中则是祭祀亚伯拉罕的场面,它源于拜占庭时期埃及科普特人的织物,不过在这里变成了两个相对的形象”①。粟特织锦上对称装饰的方法成了其最显著的特征,同时纹饰也受丝绸之路周边地区的影响。
粟特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唐诗和唐代文献中常见的胡腾舞、柘枝舞、胡旋舞均出自九姓昭武国。李端在《胡腾儿》一诗中描写胡腾舞是“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欲月”。无名氏的《柘枝词》序文中将柘枝舞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往往是“对舞相占”。胡旋舞,当然是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描写最贴切:“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遥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粟特人的这三种舞蹈因强健有力、刚柔相济,俗有“健舞”之称。粟特人的乐舞被西域诸民吸收,同时也成为唐代长安流行的乐舞,这给安于轻歌曼舞的唐代中原文化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强烈的劲歌狂舞形成新的视听冲击。
那么,粟特人是如何充当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旅和文化中介的呢?汉唐之际,随着粟特人向东进行的贸易扩展,开始大批移民,粟特聚落形成了,“在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都有他们的移民聚落,散布十分广泛。他们经商、善战、信奉祆教、能歌善舞等特性,对中古中国的政治进程、‘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传播、音乐舞蹈的繁荣昌盛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荣新江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考证了粟特向东移民的迁徙路线:“他们经过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疏勒、据史德、温宿、拨换、龟兹、焉耆、吐鲁番,或于阗、且末、楼兰,到达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的常乐、酒泉、张掖、武威东行,经固原,到唐朝的都城长安或东都洛阳,从洛阳东行北上,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或者从灵武东行,经六胡州、太原、雁门(代县)、蔚州(灵丘),也可以到达河北重镇幽州,在中国北境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而且大多数地点都有粟特人的聚落。”③“粟特人随处而居,形成聚落,一部分人再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宝(又作萨保、萨甫,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把萨宝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当中,作为视流外官,专门授予胡人首领,以控制胡人聚落”④。到了唐代,唐政府把实行州县制地区的粟特聚落改为乡里,如唐西州的崇化乡安乐里,而唐帝国周边地区的粟特人聚落仍保持原有形态,如唐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粟特人东居的聚落——石城镇。居住在乡里的粟特人也逐渐融入到汉等民族中,较独立的粟特聚落还保留着粟特人筑城而居的传统。正是这些粟特移民和后来的定居民,由于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媒介。粟特艺术品在我国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北方等地的发现,正是粟特文化艺术东渐的结果。
粟特人向东移民筑城而居的聚落,虽不像中亚粟特人的城市那样分内城、本城和外围三部分,但也是筑城而居的。康艳典移民鄯善所筑之城有旧城、新城之别,如原住石城镇,后又重筑有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蒲桃城就因城内广种葡萄而得名。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城池的具体形制,但从一些出土文献中知悉,其中均建有祆教寺院,且建在城的中心,寺内供奉着绘有祆教神祗的素画,画有祆教诸神阿胡拉·玛兹达、祖尔万、韦施帕卡、密特拉、娜娜女神等。有些地方还形成每年举行“赛祆”活动的习俗。敦煌出土的白画祆神图可能就是举行赛祆活动时悬挂在沙州城东祆祠当中的。①“赛祆”应是粟特人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悬挂祆教素画主要是用于信徒观瞻和膜拜。
如果将粟特和萨珊波斯的金银器相比较,会发现许多异同点。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与操西伊朗语的波斯人就有亲缘关系,更何况通过丝绸之路的相互联系和沟通,语言、宗教等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在所难免。但他们又是生活在不同地域,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表现在金银器制作工艺和艺术审美走向上的差异。在西域和中原等地出土的粟特金银器地点与粟特人聚落分布地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有粟特文铭记的金银器就更易于判定为粟特金银器了。新疆发现的粟特七鸵纹银盘出土于焉耆锡克沁乡,而被称为“颇罗”的银酒杯在库车、焉耆均有出土。七鸵纹银盘为圆底盘,“此盘内饰有七只鸵鸟,底心一只,周围六只,皆为单线平錾,阴文内涂金。鸵鸟之蓬松下垂的尾羽和分二趾并带有肉垫的足部刻画得很忠实,头部的造型也很逼真。七只鸵鸟的身姿既有变化又有重复,其中两只昂首的和两只俯首的各自相像,似乎用的是同一底样;两只用嘴叼腿的也相接近,但一只叼左腿,另一只叼右腿,小有分别;只有回首剔翅上翎毛的那只是单独出现的”①。它与萨珊猎驼纹银盘属两种不同的风格。与七鸵纹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银碗,碗沿刻有粟特铭文,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根据林梅村所提供银碗摹文解读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staters)”②。威氏还将得悉神确认为粟特人的神祗,而且是女神,由此可见此银碗是祭祀器皿——酒器无疑。《隋书·西域传》曹国条记载:“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以千人食之不尽。”用“金破罗”祭祀得悉神是昭武九姓诸国的普遍风俗。在此所说“金破罗”亦即“叵罗”、“颇罗”,同音异字而已,指同一器物。那么,颇罗就是浅口酒杯,属敞口的浅杯之类,有金银之分。粟特文的Patro即为杯状银碗。焉耆出土的银颇罗口径20.5厘米,高7.4厘米,除碗沿的铭文外,碗外壁用直棱划分成细瓣,内壁素面。在库车龟兹故城内西南出土的银颇罗为敞口,直径14厘米,高3.5厘米,容器内“中部錾有月、兔图案,月为弯月牙(新月),月牙两尖形成的‘阙’中包含一白兔。白兔背躬,长耳,尾上翘,作欲奔走状”③。自南北朝以降,粟特人祭神的颇罗就成为宫廷酒宴中的酒具了。唐代诗人岑参在其《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中云:“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可见,作为酒具的颇罗也风行于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在隋唐时期亦曾有过粟特聚落。唐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鹿纹十二瓣银颇罗,其上铭文被西姆斯·威廉姆斯释读为粟特文的“祖尔万神之奴仆”。祖尔万神是祆教中的重要神祗,粟特人亦信奉此神。粟特金银器不仅发现于西安、洛阳等地,而且出现在北方草原地区,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有银带柄壶、银带柄杯、银椭圆形杯、银盘、银勺等。这些银器年代为唐代,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是粟特银器:“李家营子的带柄壶、带柄杯、椭圆形杯、盘,加上未发表图的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用具,而且是输入品。它们的原产地应是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更大。其年代为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④银盘中心饰动物、周围留空白的做法是粟特人独有的,库车出土银颇罗也与此类似。如果李家营子的粟特银器果真是输入品,充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商旅的也正是粟特人。
向东移民的粟特人归化之后,其文化艺术和习俗也发生了适应性变化。在丧葬习俗上已采用土葬,中土屏风式石棺床已出现,但浮雕图像还多少保留了骨瓮的形式,祆教和粟特歌舞的踪影还依稀可见,实际上它是以祆教画像石的艺术形态出现的。甘肃天水属隋代的石屏风画像石、河南安阳石屏风画像石、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西安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太原隋代虞弘墓屏式画像石几乎全是中土九屏式彩色浮雕画。这些浮雕画题材多与主人生前参加节日庆典、狩猎、宴饮等活动有关,有的还与粟特人神话中的意象不无关系。粟特绘画中的“曹衣出水”和汉代天阙图像也证明归化后的粟特艺术越来越中国化。不过从宁夏盐池属隋唐时期的M6号墓石门上的两个舞者形象的浮雕中,人们似乎看到了粟特胡旋舞的韵致,它与虞弘墓浮雕中的舞者形象和片治肯特出土的骨瓮上的舞蹈者均属一个系统,即源远流长的粟特乐舞传统。
粟特文化是绿洲农耕型定居文化,因九姓胡诸国人多经商,故筑城而居,形成商业性的城邦文化。粟特人是如何筑城而居的,从现存距撒马尔罕以东60公里处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不难看出,在中古时期它就是粟特人属“都”一级的城邦。该城建成于5世纪,8世纪初毁于阿拉伯人的入侵。这是粟特的经济、文化的全盛期。《新唐书》曾描绘此城是: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绘突厥、婆罗门,西绘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这至少表明粟特在文化上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夹在诸大国之间,也只能以一种变通的方式左右逢源了。事实上,粟特曾受突厥监摄,也曾作为唐朝的羁縻州存在过,但是仍有粟特人自己的统辖系统。这种蕃、汉、胡的多重政治结构自然也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因此,可以说粟特文化是有极强适应性的文化。古代中亚城市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供统治者居住的内城和由贵族宅第、市场组成并筑有城墙的本城以及城市的外围。片治肯特古城则包括环绕城墙的本城,西边山丘上的设防卫城,城外东边的建筑群和东南边的墓地。建筑材料为大型砖坯和切割成大块的黏土制件。考古发掘出该城两座神庙,并排坐落在城中广场西面。每座神庙由各式房间和正方形院落组成。每一座神庙的中心建筑居于高台之上,东边为立有几根圆柱的门厅,与四柱大厅连为一体,大厅的西面为封闭的圣殿和环绕大厅的回廊。神庙正面朝东,为粟特人早期崇拜太阳神密特拉的反映。门厅用黏土质彩绘浮雕装饰,可能源于贵霜艺术传统。门厅和大厅装饰有壁画,大厅深处门口立有大型塑像。南面神庙壁画是人和众神的《哭哀图》。神庙应为粟特本土化的多神教庙宇。城中贵族住宅区的每个住宅单元由10~15个房间组成,有两层或三层的,分别有大客厅、拱顶房、走廊、储藏室等。客厅的梁木、柱头、柱身、墙壁上的木质缘饰均有几何纹、植物纹以及神、人和动物形象的雕刻装饰。客厅墙壁有含某种故事情节的装饰性壁画,正面墙上绘有中心人物,其他墙面绘有征战功绩,有庆功的宴会或隆重的接见场面。粟特贵族宅第以叙事性故事壁画进行装饰十分普遍,除装饰性外,主要和某段历史或主人公的经历有关,还有的则是史诗故事和寓言等,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片治肯特的内城除平房或二层楼住宅区外,街区店铺、作坊十分密集,金银器作坊、铁作坊、陶器作坊、织布作坊、制革作坊和玻璃作坊均有分布。这与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所反映的“邦民”情况是一致的。这些城邦是以邦民社会为主体的等级社会,“邦民下层包括:从事金银作、铁作和陶作的工匠,以及做小本生意的各类商贩。在水渠劳作的浇水工,也属庶民。邦民上层是一群僧俗显贵:祆主、商队主和钱庄老板。此外,还有一系列与内陆性商业城邦适应的官吏、税吏、马监、主簿、驿站长和河渠官,等等”①。城市的扩增,发达的手工业和日益增长的商业贸易刺激了工艺艺术的发展。粟特金银器皿、陶器、纺织等工艺制作业日益成为粟特人最重要的手工业。粟特金银器因19世纪末阿姆河宝藏的发现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各地的出土,其面貌逐渐清晰起来。这些金银制作的带柄壶、带柄杯、盘、碗等器皿多以动、植物纹样装饰,武士、有翼骆驼等神话意象常出现在金银器装饰中。在构图上常以中心饰物,周围留空布局,其工艺为浮雕式。“在阿姆河宝藏中还有一件金质提壶,金壶明显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下部近似一个球体,表面有楞条状装饰,上部近似一个喇叭口,表面无纹饰,口部有流,略似鸟头形,其下无圈足。最有特色的是金壶有一半环状把手,把手下端接于金壶中部,上端为一精美的狮头造型,狮口正好衔住金壶口沿”①。粟特提壶的基本特征也就成了低或无圈足,短颈粗腰,把手为动物造型,且直接接于沿口,壶体表面无复杂装饰等。这与萨珊波斯高圈足,壶把手按在壶体上部,壶体表面图案装饰复杂有明显区别。武士决斗题材的粟特镀金银盘属7世纪器皿,表现的是一个拿长矛的武士同另一个持弓箭的武士进行决斗的过程。两位武士全身披甲,身旁弃置圆锤、剑、斧等武器,可能在用这些武器长时间决斗不分胜负后才决定用长矛和弓箭决一雌雄。另一件7世纪饰有双翼骆驼形象的镀金银壶,题材类似于瓦拉赫沙宫殿中一个大厅中的壁画。所以有翼骆驼形象应来源于粟特人古老的神话意象是无疑的。
粟特诸城邦国中制陶业也成为主要的手工业。早在希腊化时期,粟特人就因制作小型陶塑像出名,特别是出现诸如自然女神、家庭保护神、幸福女神塑像。起初是陶制半裸女神像,后又演变为身着宽大外裙和斗篷、衣褶垂直且神态庄重的女神像,一般为端庄的正面像,大脑袋与程式化手臂姿势不相称。这些女神像相貌、冠帽有地域性,但直垂衣褶则为希腊式。几乎所有的女神像都有象征意义,被称为“大女神”的陶像是丰产的大地的象征,而梅尔夫出土的立式女神像手持象征太阳或命运的标志,与粟特人信仰的拜火教中的神祗有关。撒马尔罕出土的女神像手持郁金香和石榴,是春天和多子多产的象征。布哈拉出土的有贵妇气质的陶像则是城市保护女神。6~8世纪,粟特由于与唐朝、突厥、波斯、印度等频繁的文化交往,制陶业处在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粟特陶器“也有采用在泥质陶器的表面敷施一层云母的方法。显然,这是为了表现金属艺术品的加工工艺。大量的陶器都是塑成各种造型,器表和形制粗糙者极少见,有的还用蓖子饰以简单的图案”②。赤陶塑像主要是骑马、骑象、骑公羊的骑手形象和一些怪异动物,再有就是尸骨瓮上的浮雕像。其中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出土的一件尸骨瓮浮雕中有四个拱门,每个门前为一立式人像,可能象征火、水、土、气四大元素。从人物造像和构图不难发现模仿萨珊人物画的迹象,起码粟特的制陶工匠对萨珊波斯的制陶工艺是十分熟悉的。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中亚后,粟特陶器中非偶像化的几何、植物图案装饰成了主流。上釉陶器上棕榈叶的各种式样和波浪形嫩枝、几何图形轮廓线与弧线相交后用石榴、郁金香、玫瑰等作为装饰纹样取代了人物、动物纹样,陶器的色彩也由起初的淡绿、淡黄、淡棕色变成浓重的深褐色、灰绿色、紫色等。12世纪后粟特陶器艺术走向终结。
“为了最大限度地适应国际贸易,粟特的织工们常常以萨珊伊朗的、中国的和拜占庭的图案风格装饰自己的产品”①。但是在中古时期这样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影响总是相互的。唐代那种花纹布满全幅的织锦中出现了中亚、西亚盛行的忍冬纹、葡萄纹等,甚至连波斯式、粟特式的联珠对兽、对鸟纹也在唐朝盛行;中国风格的花鸟纹锦也流行在粟特、萨珊波斯。唐锦、波斯锦、拜占庭锦和粟特锦在中古时期的丝织品工艺中各领风骚。穆格山出土的粟特织物就有丝织品、毛织品、棉织品等,纹样也分格纹、联珠纹、联花纹、梅花纹、联星纹、平纹素织等多种。在丝织品中以布哈拉赞达纳出土的织锦为代表,被称为“赞达涅奇”。这是一种联珠对兽、对鸟的纹样,较多受到此类波斯织锦的影响。比利时尤伊城教堂所收藏的一件属7世纪的有粟特文题记的对羊织锦中间为站在天平上的装饰性对羊,四周为联珠纹,被确认为是“赞达涅奇”风格的丝织品,纹样似有买卖公平的寓意。另一件发现于高加索的属6~7世纪的织锦“圆框一周有以荷花组成的饰带,这是对典型的拜占庭织物图案的模仿,圆框之中则是祭祀亚伯拉罕的场面,它源于拜占庭时期埃及科普特人的织物,不过在这里变成了两个相对的形象”①。粟特织锦上对称装饰的方法成了其最显著的特征,同时纹饰也受丝绸之路周边地区的影响。
粟特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唐诗和唐代文献中常见的胡腾舞、柘枝舞、胡旋舞均出自九姓昭武国。李端在《胡腾儿》一诗中描写胡腾舞是“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欲月”。无名氏的《柘枝词》序文中将柘枝舞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往往是“对舞相占”。胡旋舞,当然是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描写最贴切:“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遥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粟特人的这三种舞蹈因强健有力、刚柔相济,俗有“健舞”之称。粟特人的乐舞被西域诸民吸收,同时也成为唐代长安流行的乐舞,这给安于轻歌曼舞的唐代中原文化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强烈的劲歌狂舞形成新的视听冲击。
那么,粟特人是如何充当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旅和文化中介的呢?汉唐之际,随着粟特人向东进行的贸易扩展,开始大批移民,粟特聚落形成了,“在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都有他们的移民聚落,散布十分广泛。他们经商、善战、信奉祆教、能歌善舞等特性,对中古中国的政治进程、‘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传播、音乐舞蹈的繁荣昌盛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荣新江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考证了粟特向东移民的迁徙路线:“他们经过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疏勒、据史德、温宿、拨换、龟兹、焉耆、吐鲁番,或于阗、且末、楼兰,到达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的常乐、酒泉、张掖、武威东行,经固原,到唐朝的都城长安或东都洛阳,从洛阳东行北上,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或者从灵武东行,经六胡州、太原、雁门(代县)、蔚州(灵丘),也可以到达河北重镇幽州,在中国北境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而且大多数地点都有粟特人的聚落。”③“粟特人随处而居,形成聚落,一部分人再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宝(又作萨保、萨甫,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把萨宝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当中,作为视流外官,专门授予胡人首领,以控制胡人聚落”④。到了唐代,唐政府把实行州县制地区的粟特聚落改为乡里,如唐西州的崇化乡安乐里,而唐帝国周边地区的粟特人聚落仍保持原有形态,如唐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粟特人东居的聚落——石城镇。居住在乡里的粟特人也逐渐融入到汉等民族中,较独立的粟特聚落还保留着粟特人筑城而居的传统。正是这些粟特移民和后来的定居民,由于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媒介。粟特艺术品在我国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北方等地的发现,正是粟特文化艺术东渐的结果。
粟特人向东移民筑城而居的聚落,虽不像中亚粟特人的城市那样分内城、本城和外围三部分,但也是筑城而居的。康艳典移民鄯善所筑之城有旧城、新城之别,如原住石城镇,后又重筑有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蒲桃城就因城内广种葡萄而得名。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城池的具体形制,但从一些出土文献中知悉,其中均建有祆教寺院,且建在城的中心,寺内供奉着绘有祆教神祗的素画,画有祆教诸神阿胡拉·玛兹达、祖尔万、韦施帕卡、密特拉、娜娜女神等。有些地方还形成每年举行“赛祆”活动的习俗。敦煌出土的白画祆神图可能就是举行赛祆活动时悬挂在沙州城东祆祠当中的。①“赛祆”应是粟特人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悬挂祆教素画主要是用于信徒观瞻和膜拜。
如果将粟特和萨珊波斯的金银器相比较,会发现许多异同点。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与操西伊朗语的波斯人就有亲缘关系,更何况通过丝绸之路的相互联系和沟通,语言、宗教等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在所难免。但他们又是生活在不同地域,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表现在金银器制作工艺和艺术审美走向上的差异。在西域和中原等地出土的粟特金银器地点与粟特人聚落分布地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有粟特文铭记的金银器就更易于判定为粟特金银器了。新疆发现的粟特七鸵纹银盘出土于焉耆锡克沁乡,而被称为“颇罗”的银酒杯在库车、焉耆均有出土。七鸵纹银盘为圆底盘,“此盘内饰有七只鸵鸟,底心一只,周围六只,皆为单线平錾,阴文内涂金。鸵鸟之蓬松下垂的尾羽和分二趾并带有肉垫的足部刻画得很忠实,头部的造型也很逼真。七只鸵鸟的身姿既有变化又有重复,其中两只昂首的和两只俯首的各自相像,似乎用的是同一底样;两只用嘴叼腿的也相接近,但一只叼左腿,另一只叼右腿,小有分别;只有回首剔翅上翎毛的那只是单独出现的”①。它与萨珊猎驼纹银盘属两种不同的风格。与七鸵纹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银碗,碗沿刻有粟特铭文,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根据林梅村所提供银碗摹文解读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staters)”②。威氏还将得悉神确认为粟特人的神祗,而且是女神,由此可见此银碗是祭祀器皿——酒器无疑。《隋书·西域传》曹国条记载:“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以千人食之不尽。”用“金破罗”祭祀得悉神是昭武九姓诸国的普遍风俗。在此所说“金破罗”亦即“叵罗”、“颇罗”,同音异字而已,指同一器物。那么,颇罗就是浅口酒杯,属敞口的浅杯之类,有金银之分。粟特文的Patro即为杯状银碗。焉耆出土的银颇罗口径20.5厘米,高7.4厘米,除碗沿的铭文外,碗外壁用直棱划分成细瓣,内壁素面。在库车龟兹故城内西南出土的银颇罗为敞口,直径14厘米,高3.5厘米,容器内“中部錾有月、兔图案,月为弯月牙(新月),月牙两尖形成的‘阙’中包含一白兔。白兔背躬,长耳,尾上翘,作欲奔走状”③。自南北朝以降,粟特人祭神的颇罗就成为宫廷酒宴中的酒具了。唐代诗人岑参在其《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中云:“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可见,作为酒具的颇罗也风行于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在隋唐时期亦曾有过粟特聚落。唐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鹿纹十二瓣银颇罗,其上铭文被西姆斯·威廉姆斯释读为粟特文的“祖尔万神之奴仆”。祖尔万神是祆教中的重要神祗,粟特人亦信奉此神。粟特金银器不仅发现于西安、洛阳等地,而且出现在北方草原地区,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有银带柄壶、银带柄杯、银椭圆形杯、银盘、银勺等。这些银器年代为唐代,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是粟特银器:“李家营子的带柄壶、带柄杯、椭圆形杯、盘,加上未发表图的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用具,而且是输入品。它们的原产地应是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更大。其年代为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④银盘中心饰动物、周围留空白的做法是粟特人独有的,库车出土银颇罗也与此类似。如果李家营子的粟特银器果真是输入品,充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商旅的也正是粟特人。
向东移民的粟特人归化之后,其文化艺术和习俗也发生了适应性变化。在丧葬习俗上已采用土葬,中土屏风式石棺床已出现,但浮雕图像还多少保留了骨瓮的形式,祆教和粟特歌舞的踪影还依稀可见,实际上它是以祆教画像石的艺术形态出现的。甘肃天水属隋代的石屏风画像石、河南安阳石屏风画像石、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西安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太原隋代虞弘墓屏式画像石几乎全是中土九屏式彩色浮雕画。这些浮雕画题材多与主人生前参加节日庆典、狩猎、宴饮等活动有关,有的还与粟特人神话中的意象不无关系。粟特绘画中的“曹衣出水”和汉代天阙图像也证明归化后的粟特艺术越来越中国化。不过从宁夏盐池属隋唐时期的M6号墓石门上的两个舞者形象的浮雕中,人们似乎看到了粟特胡旋舞的韵致,它与虞弘墓浮雕中的舞者形象和片治肯特出土的骨瓮上的舞蹈者均属一个系统,即源远流长的粟特乐舞传统。
附注
③陈寅格.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2.
①别列尼茨基等.中世纪中亚城市.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5.
①陈海涛.阿姆河宝藏及其反映的早期粟特文化.西域研究.2001(2).
②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97.
①1Б.Я.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119.
①Б.Я.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119~120.
②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20.
③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111~112.
④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112~113.
①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1997.第3卷.
①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57.
②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161.
③刘松柏,郭慧林.库车发现的银颇罗考.西域研究.1999(1)
④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学报.1992(2).大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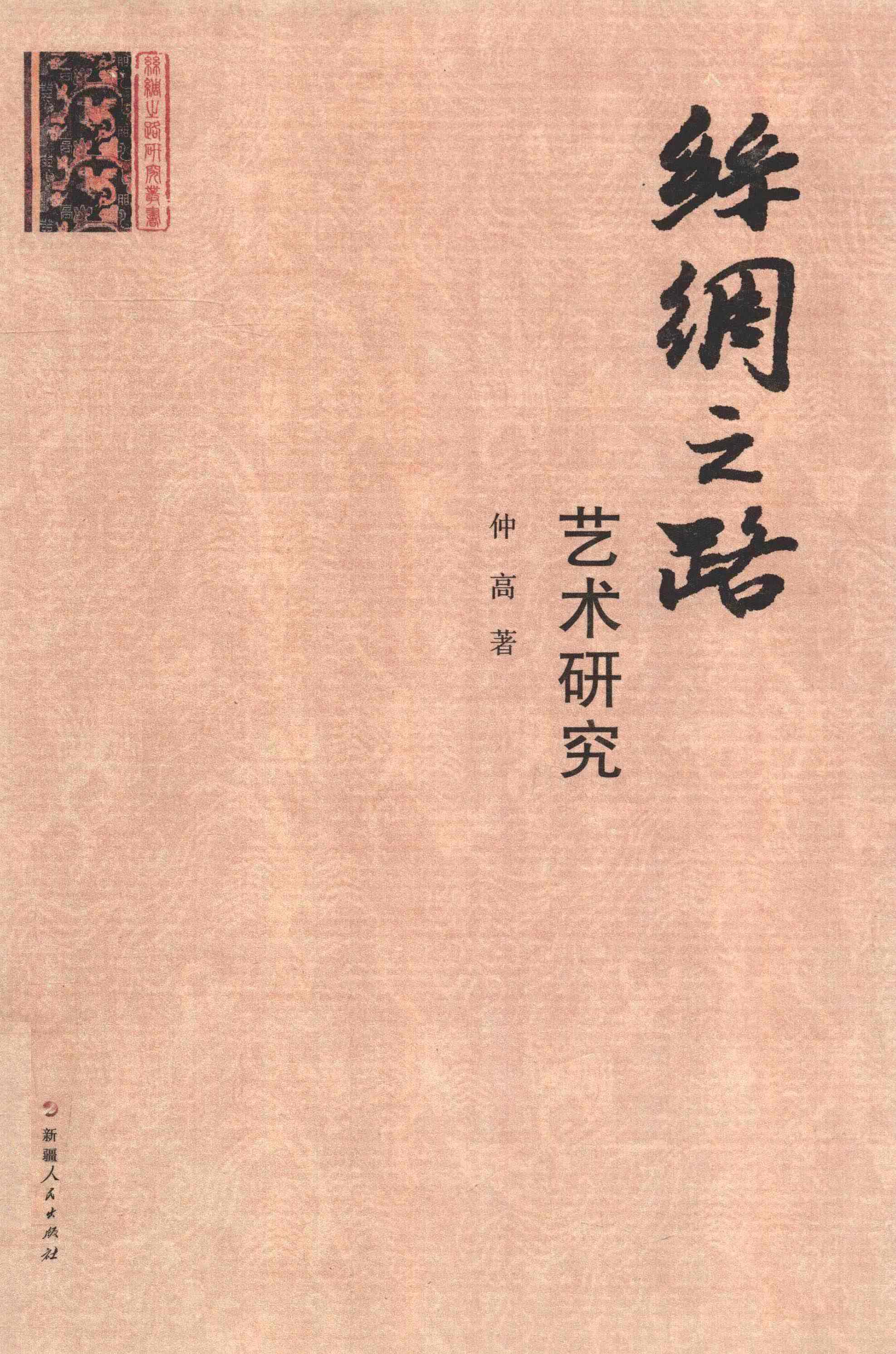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