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波斯文化与艺术张力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52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波斯文化与艺术张力 |
| 分类号: | J809.3 |
| 页数: | 7 |
| 页码: | 272-278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波斯文化与艺术张力情况包括波斯人在信仰伊斯兰教建立萨曼王朝之前,曾建立过强大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和萨珊王朝、波斯丝织品是由中国丝绸工艺沿丝绸之路西传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艺等。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波斯文化 艺术文化 |
内容
波斯人在信仰伊斯兰教建立萨曼王朝之前,曾建立过强大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和萨珊王朝。但是这两个王朝并不是连续的文明,而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亚历山大希腊人打败之后就进入了希腊化时代,只有自226年起建立的萨珊王朝才续上了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香火。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波斯人建立的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强大帝国。自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期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由居鲁士称波斯王起到大流士皇帝一世时,其疆域西至地中海和埃及,北至黑海、里海和高加索,南至波斯湾和阿拉比亚,东至中亚的锡尔河,它还征服了西北印度的大片地方。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是“在吸收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古代的波斯文化”③。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将势力扩大到中亚南部和印度西北部,所以对这些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波斯人早期曾借用两河流域的楔形符号书写波斯语,后来借用阿拉美字母拼写波斯语。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采用阿拉美文发布命令和用于其他公务,于是阿拉美文也传到波斯帝国治下的中亚和印度。后来的粟特文和佉卢文都源于阿拉美文。这两种文字都曾在西域使用过。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间也是祆教向东传播的时期。这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新教,自公元前6世纪末出现之后就在波斯帝国统治的西亚、中亚、南亚诸地兴盛起来。传入中亚不久又传入西域诸绿洲和草原游牧诸民中。祆教东扩的结果是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因祆教是传入西域的最早外来宗教,往往又与本地的原始崇拜相契合,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迄今还能在新疆的不少民族中见到祆教的遗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成就还表现在建筑和雕塑方面。波斯波利斯卫城阿帕达那是由106级台阶和排列两侧的武士、王公浮雕像和大流士宫以及薛西斯宫组成的宏大建筑群。大流士宫被称为“百柱大殿”,即使较小的薛西斯柱殿也有72根圆柱,每根都高达80英尺,柱头上均有雕刻。在建筑形制和艺术上,显然仿效和借鉴了埃及和亚述建筑艺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雕刻艺术除建筑群的薄浮雕和柱头雕刻,主要还是宗教雕刻。祆教神像是以古老题材创造出的新式样。阿胡拉·玛兹达的造像是:头戴形似软帽的低宝冠,着衣袖宽大的衣服,衣服上的襞褶暗合着背景上巨大羽翼的线条。背景除羽翼外还有日轮和涡纹。这正是被祆教奉为“智慧之主”的最高神祗阿胡拉·玛兹达的形象,他是光明、清净、创造和生的象征。
自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称波斯王到公元前330年大流士被杀,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历时220年,之后就被马其顿亚历山大所灭,文化上还没有来得及有更大的建树就进入了希腊化时期。而另一轮更大规模的波斯文化兴起和产生深远影响时,则到了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在经历了80多年的希腊化时期后,终于有了波斯人自己的王朝——安息人的王朝,它成了萨珊波斯王朝的前奏。萨珊波斯王朝从226年立国,到642年灭亡,历时400余年,但其文化艺术的生命力超越了王朝存在的年代,一直到9世纪在丝绸之路各地还有余绪可寻。波斯人建立的安息王国统治时间并不短,自公元前250年到公元234年止,共480余年,但统治阶层的“希腊化”和整个社会流行的希腊习俗,似乎使波斯文明处在冬眠之中。这固然是征服东方的希腊文化过于强盛的缘故,但也与安息王朝上层毫无复兴波斯文化的坚定信念不无关系。故阿萨西斯安息王朝被波斯萨珊王朝推翻也就不足为怪了。萨珊王朝从一开始就打着复兴波斯文化的旗号,它西拒罗马帝国和以后的拜占庭帝国,东御〓哒和突厥人。萨珊王朝在东西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开始了恢复包括波斯宗教、君主政治和波斯文化在内的复兴历程。萨珊王朝的文化在霍斯罗一世(531~579)、二世(590~628)时达到巅峰。这个时期不仅继承了波斯文化的传统,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总能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风格。这与萨珊王朝鼓励艺术创作和发展丝绸业、金属工艺以及广纳国外艺术人才有直接关系。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织锦、波斯金银器艺术几乎成了萨珊艺术的代名词。
波斯丝织品是由中国丝绸工艺沿丝绸之路西传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艺。波斯锦织法不同于汉锦,它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纬线起花,夹经常用双线。在图案花纹上用联珠圆圈分隔成各个花纹单元。其形式是联珠对兽对鸟纹,常见的有对鸭、对狮、对羊、对雁等图案。波斯联珠纹图案艺术也成了自北魏到唐代中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主流图案艺术。这种图案除见于织锦外,还出现在佛教壁画、雕塑、陶瓷工艺中。在克孜尔石窟中就能见到联珠纹鸟兽图样的壁画,甚至敦煌莫高窟属中唐的第361窟中也有联珠对雁纹藻井图案。克孜尔石窟麒麟窟佛像的座石石雕也是联珠纹麒麟,这成了融合汉地神兽和波斯纹样艺术的典范。波斯织锦中还有一种以大圆团花为主体,四周连接着无数小圆装饰的式样,这或许是吸收了中国团花图案艺术的结果。对称是波斯锦追求的完美形式,即使以人物为主的狩猎题材的织锦也十分讲究构图上的对称。有一块波斯锦上织有两个正在追杀母狮的国王骑在双翼马背上手高举幼狮的形象,构成了完美的对称图案。
萨珊波斯的金银器艺术成就也很突出,它曾对中国的金银器及瓷器工艺产生过影响。萨珊的金银器多是统治阶层用的盘、壶、杯、碗、罐等生活器皿和流通的金银币。这些金银器因其造型、雕刻工艺精湛,形成了当时流行的萨珊波斯风格,而且在工艺上常常出现圆雕、錾花和“敲花”等技艺。萨珊波斯金银器艺术从题材上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世俗题材的宫廷艺术,另一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宗教题材艺术。但这是出现纪念性艺术时的早期情况,而到后期,其界线也就没有那么分明了。所谓“纪念性艺术”是指萨珊王朝沿袭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时以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和恶神安格拉·曼纽斗争图像来象征国王和敌人作战的传统形式。这种图像大多雕刻在崖壁上,但也用以作为金银器皿、钱币、印章的装饰。这类宗教题材的金银器艺术以后逐渐让位于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国王肖像了,这就是屡屡能见到的“王中之王”、达官显贵或高级祭司人物的肖像。其中一件出土于格鲁吉亚的饰有萨珊国王瓦拉兰二世及全家人的肖像的银杯,国王的姿态和手势是表现“君权神授”这一特定主题的规范形式。“同类肖像不仅装饰在银器上,而且更多地表现于金银货币及摩崖浮雕中。这件浮雕在银杯圆光中的国王肖像,就是一种以货币肖像为基础的修正形式。而且把国王及其嫡系亲属铭刻在器物上,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公开宣扬其世袭王位的合法性。每当萨珊宫廷举行盛大庆典或宴会时,通常使用这种银杯饮酒,同时把它作为赏赐高官或功臣的礼物。..萨珊银器中的国王肖像,实质上就是对君权神授思想加以图像化和人格化的结果”①。甚者神话中的太阳神密特立骑马狩猎图像也变成了王权的象征。不过在萨珊王朝金银器中的国王狩猎图中国王追击的野兽往往是成对出现,或两只或四只,一只被击倒,另一只仍在顽抗。这实际上是以图像化的方式象征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强调国王的勇敢精神。这种构图布局在艺术上是为了保持画面的平衡感。有一件表现萨珊国王瓦拉兰五世猎鸵的银盘,虽然工艺精湛,但也明显地在向程式化方向发展,这几乎成了这类狩猎纹银盘的传统模式:“盘上之人和马的姿势前后经过多少代始终无多大改动,连盘上那些动物的样子也不够灵活;..它们(指鸵鸟)的腿太靠后,显得很不自然,头部也嫌太大,招展的两翼十分造作,与七鸵纹判然有别。”②而七鸵纹银盘是在新疆焉耆出土的粟特银器。银盘中单线平錾的七只鸵鸟呈错综有序的布局,使整个图案充满韵律感。粟特系操东伊朗语的民族,隋唐时期被汉文史籍称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的国家与萨珊波斯基本上以临近阿姆河一带为界。由于粟特与唐朝的特殊关系,萨珊波斯文化艺术是通过粟特这个中介才影响到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基于这个原因,有时粟特和萨珊波斯金银器艺术往往被一些学者误认为是同一种艺术,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将饰有塞穆鲁纹的萨珊波斯银壶和饰有有翼骆驼的粟特银壶作一比较,差异是明显的。塞穆鲁纹是在萨珊波斯织锦和金银器中常出现的纹饰形象,它的头和前半身似犬,后半身则像鸟,这种由犬与鸟组合的神兽是帝王权威和国势兴隆的象征。而这种纹饰在粟特织物和金银器中几乎不见,粟特银壶中的图案则是由有翼骆驼替代了。粟特人善于经商,在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上有其无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他们崇敬有翼骆驼为胜利之神也就不奇怪了。当己骑马征战的浮雕留在了崖壁上。在塔克—阿—波斯达的霍斯罗的雕像是他全副盔甲,骑着“漆黑似夜”骏马的岩雕艺术品,在一种装饰美中透出强烈的生命韵律。不过,一些主要的建筑和浮雕艺术并不是波斯人的发明,是从邻国引进的,拱廊、壁龛、壁柱和圆拱都是叙利亚建筑的形式,源头可追溯到古代巴比伦。但是经萨珊波斯“引进”之后,再经本土化“改造”,“作为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穹庐和拱形已经被认为是萨珊建筑的典型”①。西域的克孜尔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建筑除券顶中心柱窟外,还有一种方形穹隆顶窟,这种形制不见于印度传入的建筑艺术,而在萨珊波斯建筑中常见。这类建筑形制在西域摩尼教寺和佛寺中时常见到。高昌故城K遗址,被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描述为是由四个拱顶房组成的一组建筑,其中被认为是“藏书室”的“那件穹隆顶房间为正方形,位于长廊西侧,它的前室还有些断垣残壁,它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还可以看到拱形转角”②。因在此出土有摩尼教经书,被确认是摩尼寺。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后被萨珊波斯王朝的沙波尔一世尊为国教。沙波尔一世死后,继位国王宣布取缔摩尼教,大批受迫害的摩尼教徒逃往中亚阿姆河一带。粟特人信奉摩尼教后于6世纪将摩尼教传入高昌境内。此后,萨珊波斯方形穹隆顶摩尼寺也开始兴起。这种建筑形制还见于克孜尔石窟,如9号窟、135号窟等12窟都属方形穹隆顶窟。克孜尔石窟形制分为一、二、三期。第一期以中心柱窟(又称支提窟)为主,源自印度佛教石窟;第二期则以方形窟居多,数量超过中心柱窟,其中穹隆顶石窟应属萨珊波斯方形窟穹隆寺建筑风格;第三期是新型和改建洞窟,窟形和绘塑都呈简单化趋势,且新增小型窟,可能是本土化的结果。方形窟也不尽然都是穹隆顶,它分拱券顶、穹隆顶、平顶和套斗顶等。在这些形制中“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券顶最早,其次为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穹隆顶,再次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平棋顶、套斗顶和仿橡一面坡顶”③。在此,我们不难发现西域建筑艺术在不同阶段与不同建筑艺术融合的轨迹。
萨珊波斯的绘画作品在其本土几乎不存,但是从中亚佛教壁画和西域摩尼教绘画中都能见到波斯绘画的影响,不过是经粟特人转手之后传入而已。波斯绘画实际上是上承摩尼教的宗教绘画,下接伊斯兰教时期波斯细密画的绘画艺术。格鲁塞认为,巴米扬壁画中除印度画风和犍陀罗流派的壁画外,还有一种波斯风的壁画,这些穿着宽边长袍、其一在腰间系着一条窄带子,并拿着长剑和矛的人物形象壁画上,“将那无疑的是沙浦尔(今译沙波尔)、巴拉姆和喀斯鲁(今译霍斯罗)的王者典型和我们可称之为‘克孜尔骑士’的典型并列,证明了这些伊朗风格的绘画,无论是佛教的还是摩尼教的——我们以后将发现此教盛行于7至9世纪的中亚,自库车至吐鲁番——实际上正如我们所假定,都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启示,或者更可说这乃是伊朗绘画的一个地方性的,或外围的支派”①。格鲁塞的这个假设完全被在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高昌王国摩尼教寺院壁画和克孜尔石窟画师洞、海马洞壁画中的人物都是用白描线画,一些装饰性花纹也全是白色。这种随摩尼教传入的白描画起源于萨珊波斯是无疑的。勒柯克等人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发现了多幅早期当地各族居民礼佛的画像,有叙利亚人、吐火罗人、波斯人和突厥王子等像,作合掌致敬状;其中波斯人像,不仅衣冠带有波斯风格,而且相貌神态也都像波斯人”②。斯坦因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属8世纪的《波斯菩萨》木板画,虽被一些学者辨认为是佛教造像中的护法像或明王像,而不是如斯坦因所言“伊朗菩萨”,但人物脸长而红,双眼圆睁,浓密的络腮胡,头戴金色王冠,细长的腰身,穿一身绿色锦缎外衣,腰间皮带上悬挂一柄弯形短剑,脚穿长靴,完全是波斯王者的形象。足见波斯绘画对佛教艺术影响之深,在西域波斯艺术风格和印度佛教艺术呈现一种完美结合的趋势。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波斯人建立的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强大帝国。自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期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由居鲁士称波斯王起到大流士皇帝一世时,其疆域西至地中海和埃及,北至黑海、里海和高加索,南至波斯湾和阿拉比亚,东至中亚的锡尔河,它还征服了西北印度的大片地方。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是“在吸收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古代的波斯文化”③。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将势力扩大到中亚南部和印度西北部,所以对这些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波斯人早期曾借用两河流域的楔形符号书写波斯语,后来借用阿拉美字母拼写波斯语。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采用阿拉美文发布命令和用于其他公务,于是阿拉美文也传到波斯帝国治下的中亚和印度。后来的粟特文和佉卢文都源于阿拉美文。这两种文字都曾在西域使用过。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间也是祆教向东传播的时期。这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新教,自公元前6世纪末出现之后就在波斯帝国统治的西亚、中亚、南亚诸地兴盛起来。传入中亚不久又传入西域诸绿洲和草原游牧诸民中。祆教东扩的结果是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因祆教是传入西域的最早外来宗教,往往又与本地的原始崇拜相契合,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迄今还能在新疆的不少民族中见到祆教的遗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成就还表现在建筑和雕塑方面。波斯波利斯卫城阿帕达那是由106级台阶和排列两侧的武士、王公浮雕像和大流士宫以及薛西斯宫组成的宏大建筑群。大流士宫被称为“百柱大殿”,即使较小的薛西斯柱殿也有72根圆柱,每根都高达80英尺,柱头上均有雕刻。在建筑形制和艺术上,显然仿效和借鉴了埃及和亚述建筑艺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雕刻艺术除建筑群的薄浮雕和柱头雕刻,主要还是宗教雕刻。祆教神像是以古老题材创造出的新式样。阿胡拉·玛兹达的造像是:头戴形似软帽的低宝冠,着衣袖宽大的衣服,衣服上的襞褶暗合着背景上巨大羽翼的线条。背景除羽翼外还有日轮和涡纹。这正是被祆教奉为“智慧之主”的最高神祗阿胡拉·玛兹达的形象,他是光明、清净、创造和生的象征。
自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称波斯王到公元前330年大流士被杀,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历时220年,之后就被马其顿亚历山大所灭,文化上还没有来得及有更大的建树就进入了希腊化时期。而另一轮更大规模的波斯文化兴起和产生深远影响时,则到了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在经历了80多年的希腊化时期后,终于有了波斯人自己的王朝——安息人的王朝,它成了萨珊波斯王朝的前奏。萨珊波斯王朝从226年立国,到642年灭亡,历时400余年,但其文化艺术的生命力超越了王朝存在的年代,一直到9世纪在丝绸之路各地还有余绪可寻。波斯人建立的安息王国统治时间并不短,自公元前250年到公元234年止,共480余年,但统治阶层的“希腊化”和整个社会流行的希腊习俗,似乎使波斯文明处在冬眠之中。这固然是征服东方的希腊文化过于强盛的缘故,但也与安息王朝上层毫无复兴波斯文化的坚定信念不无关系。故阿萨西斯安息王朝被波斯萨珊王朝推翻也就不足为怪了。萨珊王朝从一开始就打着复兴波斯文化的旗号,它西拒罗马帝国和以后的拜占庭帝国,东御〓哒和突厥人。萨珊王朝在东西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开始了恢复包括波斯宗教、君主政治和波斯文化在内的复兴历程。萨珊王朝的文化在霍斯罗一世(531~579)、二世(590~628)时达到巅峰。这个时期不仅继承了波斯文化的传统,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总能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风格。这与萨珊王朝鼓励艺术创作和发展丝绸业、金属工艺以及广纳国外艺术人才有直接关系。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织锦、波斯金银器艺术几乎成了萨珊艺术的代名词。
波斯丝织品是由中国丝绸工艺沿丝绸之路西传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艺。波斯锦织法不同于汉锦,它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纬线起花,夹经常用双线。在图案花纹上用联珠圆圈分隔成各个花纹单元。其形式是联珠对兽对鸟纹,常见的有对鸭、对狮、对羊、对雁等图案。波斯联珠纹图案艺术也成了自北魏到唐代中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主流图案艺术。这种图案除见于织锦外,还出现在佛教壁画、雕塑、陶瓷工艺中。在克孜尔石窟中就能见到联珠纹鸟兽图样的壁画,甚至敦煌莫高窟属中唐的第361窟中也有联珠对雁纹藻井图案。克孜尔石窟麒麟窟佛像的座石石雕也是联珠纹麒麟,这成了融合汉地神兽和波斯纹样艺术的典范。波斯织锦中还有一种以大圆团花为主体,四周连接着无数小圆装饰的式样,这或许是吸收了中国团花图案艺术的结果。对称是波斯锦追求的完美形式,即使以人物为主的狩猎题材的织锦也十分讲究构图上的对称。有一块波斯锦上织有两个正在追杀母狮的国王骑在双翼马背上手高举幼狮的形象,构成了完美的对称图案。
萨珊波斯的金银器艺术成就也很突出,它曾对中国的金银器及瓷器工艺产生过影响。萨珊的金银器多是统治阶层用的盘、壶、杯、碗、罐等生活器皿和流通的金银币。这些金银器因其造型、雕刻工艺精湛,形成了当时流行的萨珊波斯风格,而且在工艺上常常出现圆雕、錾花和“敲花”等技艺。萨珊波斯金银器艺术从题材上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世俗题材的宫廷艺术,另一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宗教题材艺术。但这是出现纪念性艺术时的早期情况,而到后期,其界线也就没有那么分明了。所谓“纪念性艺术”是指萨珊王朝沿袭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时以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和恶神安格拉·曼纽斗争图像来象征国王和敌人作战的传统形式。这种图像大多雕刻在崖壁上,但也用以作为金银器皿、钱币、印章的装饰。这类宗教题材的金银器艺术以后逐渐让位于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国王肖像了,这就是屡屡能见到的“王中之王”、达官显贵或高级祭司人物的肖像。其中一件出土于格鲁吉亚的饰有萨珊国王瓦拉兰二世及全家人的肖像的银杯,国王的姿态和手势是表现“君权神授”这一特定主题的规范形式。“同类肖像不仅装饰在银器上,而且更多地表现于金银货币及摩崖浮雕中。这件浮雕在银杯圆光中的国王肖像,就是一种以货币肖像为基础的修正形式。而且把国王及其嫡系亲属铭刻在器物上,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公开宣扬其世袭王位的合法性。每当萨珊宫廷举行盛大庆典或宴会时,通常使用这种银杯饮酒,同时把它作为赏赐高官或功臣的礼物。..萨珊银器中的国王肖像,实质上就是对君权神授思想加以图像化和人格化的结果”①。甚者神话中的太阳神密特立骑马狩猎图像也变成了王权的象征。不过在萨珊王朝金银器中的国王狩猎图中国王追击的野兽往往是成对出现,或两只或四只,一只被击倒,另一只仍在顽抗。这实际上是以图像化的方式象征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强调国王的勇敢精神。这种构图布局在艺术上是为了保持画面的平衡感。有一件表现萨珊国王瓦拉兰五世猎鸵的银盘,虽然工艺精湛,但也明显地在向程式化方向发展,这几乎成了这类狩猎纹银盘的传统模式:“盘上之人和马的姿势前后经过多少代始终无多大改动,连盘上那些动物的样子也不够灵活;..它们(指鸵鸟)的腿太靠后,显得很不自然,头部也嫌太大,招展的两翼十分造作,与七鸵纹判然有别。”②而七鸵纹银盘是在新疆焉耆出土的粟特银器。银盘中单线平錾的七只鸵鸟呈错综有序的布局,使整个图案充满韵律感。粟特系操东伊朗语的民族,隋唐时期被汉文史籍称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的国家与萨珊波斯基本上以临近阿姆河一带为界。由于粟特与唐朝的特殊关系,萨珊波斯文化艺术是通过粟特这个中介才影响到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基于这个原因,有时粟特和萨珊波斯金银器艺术往往被一些学者误认为是同一种艺术,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将饰有塞穆鲁纹的萨珊波斯银壶和饰有有翼骆驼的粟特银壶作一比较,差异是明显的。塞穆鲁纹是在萨珊波斯织锦和金银器中常出现的纹饰形象,它的头和前半身似犬,后半身则像鸟,这种由犬与鸟组合的神兽是帝王权威和国势兴隆的象征。而这种纹饰在粟特织物和金银器中几乎不见,粟特银壶中的图案则是由有翼骆驼替代了。粟特人善于经商,在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上有其无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他们崇敬有翼骆驼为胜利之神也就不奇怪了。当己骑马征战的浮雕留在了崖壁上。在塔克—阿—波斯达的霍斯罗的雕像是他全副盔甲,骑着“漆黑似夜”骏马的岩雕艺术品,在一种装饰美中透出强烈的生命韵律。不过,一些主要的建筑和浮雕艺术并不是波斯人的发明,是从邻国引进的,拱廊、壁龛、壁柱和圆拱都是叙利亚建筑的形式,源头可追溯到古代巴比伦。但是经萨珊波斯“引进”之后,再经本土化“改造”,“作为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穹庐和拱形已经被认为是萨珊建筑的典型”①。西域的克孜尔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建筑除券顶中心柱窟外,还有一种方形穹隆顶窟,这种形制不见于印度传入的建筑艺术,而在萨珊波斯建筑中常见。这类建筑形制在西域摩尼教寺和佛寺中时常见到。高昌故城K遗址,被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描述为是由四个拱顶房组成的一组建筑,其中被认为是“藏书室”的“那件穹隆顶房间为正方形,位于长廊西侧,它的前室还有些断垣残壁,它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还可以看到拱形转角”②。因在此出土有摩尼教经书,被确认是摩尼寺。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后被萨珊波斯王朝的沙波尔一世尊为国教。沙波尔一世死后,继位国王宣布取缔摩尼教,大批受迫害的摩尼教徒逃往中亚阿姆河一带。粟特人信奉摩尼教后于6世纪将摩尼教传入高昌境内。此后,萨珊波斯方形穹隆顶摩尼寺也开始兴起。这种建筑形制还见于克孜尔石窟,如9号窟、135号窟等12窟都属方形穹隆顶窟。克孜尔石窟形制分为一、二、三期。第一期以中心柱窟(又称支提窟)为主,源自印度佛教石窟;第二期则以方形窟居多,数量超过中心柱窟,其中穹隆顶石窟应属萨珊波斯方形窟穹隆寺建筑风格;第三期是新型和改建洞窟,窟形和绘塑都呈简单化趋势,且新增小型窟,可能是本土化的结果。方形窟也不尽然都是穹隆顶,它分拱券顶、穹隆顶、平顶和套斗顶等。在这些形制中“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券顶最早,其次为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穹隆顶,再次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平棋顶、套斗顶和仿橡一面坡顶”③。在此,我们不难发现西域建筑艺术在不同阶段与不同建筑艺术融合的轨迹。
萨珊波斯的绘画作品在其本土几乎不存,但是从中亚佛教壁画和西域摩尼教绘画中都能见到波斯绘画的影响,不过是经粟特人转手之后传入而已。波斯绘画实际上是上承摩尼教的宗教绘画,下接伊斯兰教时期波斯细密画的绘画艺术。格鲁塞认为,巴米扬壁画中除印度画风和犍陀罗流派的壁画外,还有一种波斯风的壁画,这些穿着宽边长袍、其一在腰间系着一条窄带子,并拿着长剑和矛的人物形象壁画上,“将那无疑的是沙浦尔(今译沙波尔)、巴拉姆和喀斯鲁(今译霍斯罗)的王者典型和我们可称之为‘克孜尔骑士’的典型并列,证明了这些伊朗风格的绘画,无论是佛教的还是摩尼教的——我们以后将发现此教盛行于7至9世纪的中亚,自库车至吐鲁番——实际上正如我们所假定,都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启示,或者更可说这乃是伊朗绘画的一个地方性的,或外围的支派”①。格鲁塞的这个假设完全被在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高昌王国摩尼教寺院壁画和克孜尔石窟画师洞、海马洞壁画中的人物都是用白描线画,一些装饰性花纹也全是白色。这种随摩尼教传入的白描画起源于萨珊波斯是无疑的。勒柯克等人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发现了多幅早期当地各族居民礼佛的画像,有叙利亚人、吐火罗人、波斯人和突厥王子等像,作合掌致敬状;其中波斯人像,不仅衣冠带有波斯风格,而且相貌神态也都像波斯人”②。斯坦因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属8世纪的《波斯菩萨》木板画,虽被一些学者辨认为是佛教造像中的护法像或明王像,而不是如斯坦因所言“伊朗菩萨”,但人物脸长而红,双眼圆睁,浓密的络腮胡,头戴金色王冠,细长的腰身,穿一身绿色锦缎外衣,腰间皮带上悬挂一柄弯形短剑,脚穿长靴,完全是波斯王者的形象。足见波斯绘画对佛教艺术影响之深,在西域波斯艺术风格和印度佛教艺术呈现一种完美结合的趋势。
附注
③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47.
①王明增编译.丝路遗宝(一).美术史论.1987(4).
①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62.
①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67.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9.
③毛君炎.古代伊朗艺术.美术史论.1987(4).
①奥斯卡·路德.萨珊建筑.转引自尚衍斌.西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6.
②〔德〕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7.
③克孜尔石窟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7.
①〔法〕雷奈·格鲁塞著.常任侠等译.东方的文明.中华书局,1999.85.
②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65~66.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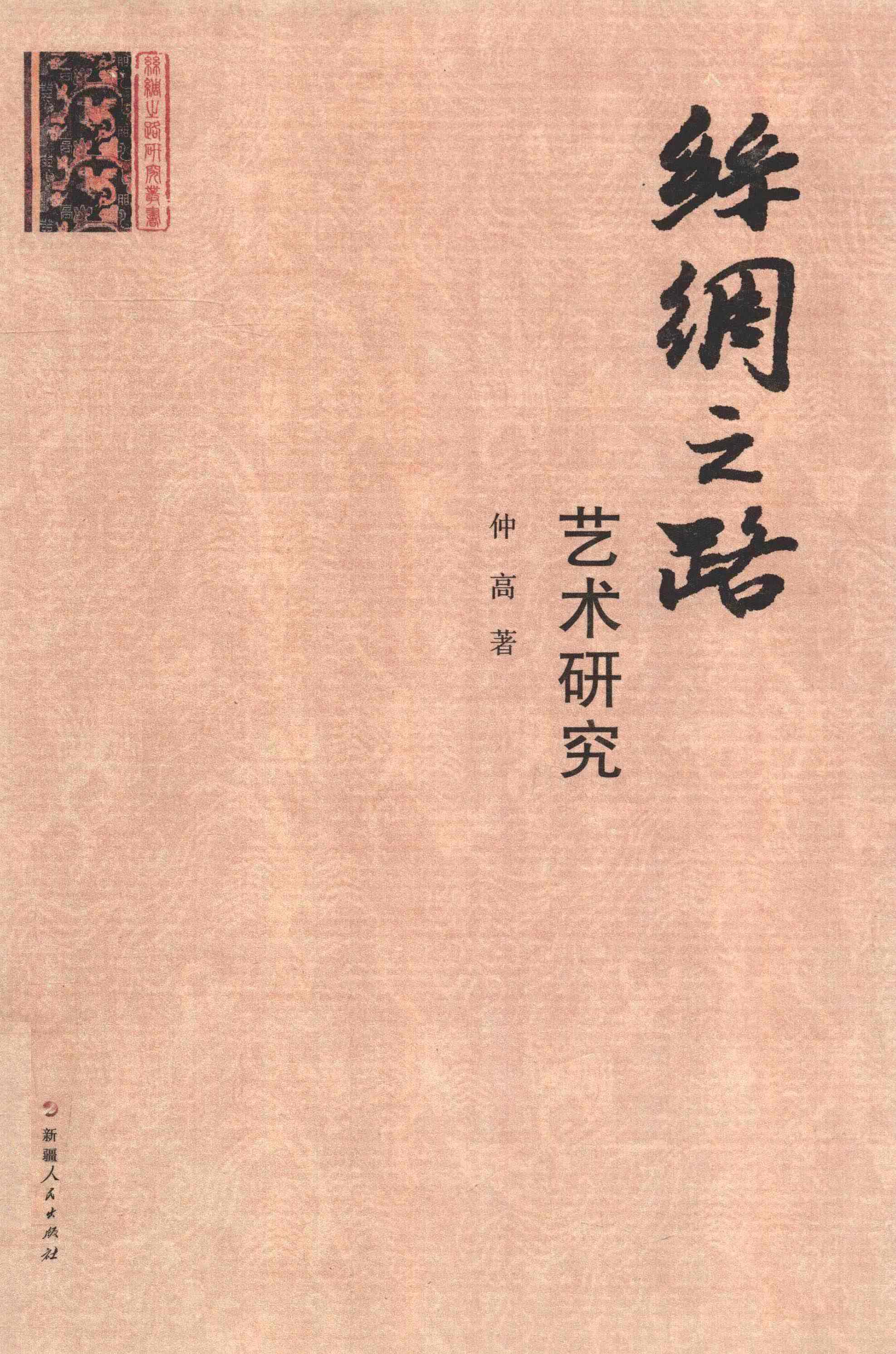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