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丝绸之路西域佛教艺术(二)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47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丝绸之路西域佛教艺术(二) |
| 分类号: | J196.2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41-250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佛教艺术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是多元的,不仅存在本土化的诸如于阗、鄯善、龟兹、高昌等区域性佛教艺术,还存在汉传佛教艺术、藏传佛教艺术等形态。其实,印度佛教在东渐中就在不断变异,这是一个外来文化不断被改造、吸收、融合的过程。汉传佛教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整合熔铸成中国式佛教的过程。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西域 佛教艺术 |
内容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佛教艺术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是多元的,不仅存在本土化的诸如于阗、鄯善、龟兹、高昌等区域性佛教艺术,还存在汉传佛教艺术、藏传佛教艺术等形态。其实,印度佛教在东渐中就在不断变异,这是一个外来文化不断被改造、吸收、融合的过程。汉传佛教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整合熔铸成中国式佛教的过程。汤用彤先生在论及中国隋唐佛教时认为:“隋唐佛教,承汉魏以来数百年发展之结果,五花八门,演为宗派,且理解渐精,能融合印度之学说,自立门户,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为纯粹之中国佛教也。”②汉传佛教艺术也是与中国传统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相融合的产物。汉传佛教艺术以其巨大的能量足以在西域的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的第一站当是甘肃河西地区,这是印度佛教、西域佛教东渐演化为汉传佛教后,与西域佛教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十六国后期沮渠蒙逊在河西走廊建立北凉政权,北凉被北魏灭后,其后裔在高昌建立政权,于是,河西地区的汉传佛教也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唐代在西域建安西、北庭两都护府,随着内地汉民来到西域,碛西三州、四镇地区再次传入汉传佛教。高昌回鹘汗国的回鹘人接受的也是汉传佛教。清代更出现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并立的局面。尽管我们在汉传佛教艺术中都能见到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渊源关系,但北凉沮渠蒙逊则是运用雕刻、窣堵波、壁画表现佛徒王权的始作俑者。“在蒙逊的保护之下,挖掘了很多石窟如敦煌石窟,并用许多雕刻和壁画表现他的政治(思想),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的目的还翻译了很多大乘佛经”③。这也是河西汉传佛教艺术勃兴的时期。作为汉传佛教艺术审美标准的最高境界是:“以静态人体的大致轮廓,表达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景仰的对象和理想。”④尽管在此说的是宗教雕塑,但它同样适用于一切佛教造型艺术。北凉裔部在高昌的佛教石窟最类似于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268、272、275窟的是吐峪沟44窟,洞窟形制、壁画布局、人物造型、绘画技艺及佛教信仰方面都有共同之处:
吐峪沟44窟与莫高窟272、275窟均为单室,窟平面呈方形,吐44窟为平顶,中间筑拱为穹隆顶,也和莫高窟272窟相似。在壁画布局方面,吐44窟正(东)壁和两侧(南北)的画面与莫高窟272、275窟相同,均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和272窟的南北壁相似,中间是一佛二菩萨的说法图,其余是禅定千佛。中段绘一排佛本生故事,与275窟南北两壁相似。从壁画的题材内容来看,吐44窟中段所绘佛本生故事和莫高窟相同,均以最富特色的一个或两个情节来表现主题。说法图中的主尊可能是弥勒佛,两侧协侍菩萨侍立,窟内四壁满绘千佛,这均与上述莫高窟的壁画题材有共同之处。壁画中的人物面型、服饰与上述莫高窟一样,都是面型浑圆,额宽颐丰,肩宽而腰细,佛内穿僧祗支,外披袒右式通肩袈裟。菩萨头戴三髻珠宝冠,头发披两肩,袒上身披帛,着裙。在图案装饰方面,吐44窟穹隆顶和四壁下端的三角形垂帐纹,也和莫高窟272、275相同。引人注意的是,我国传统的线描,用粗犷有力的线条勾勒轮廓,纤细的铁线描绘眼嘴和衣纹等细部,再用烘染法表现物体内部、人物或服色及所采用的“凹凸晕染法”,尤其是人物面部的晕染,两地十分近似。①
从北凉到高昌王国时期流行“弥勒”题材的壁画看,北凉政权及其裔部都试图借弥勒降生在转轮王的国土这一传说,以转轮王作为自己的理想,以使统治稳固长久。“佛徒王权”才是绘制这些壁画的真正动机。
唐统一西域后汉传佛教盛行于西域的直接结果是一批佛教汉寺窟的出现。唐北庭都护府治庭州先后出现了应运太宁寺、龙兴寺、高台寺,龟兹作为唐安西都护府治,也有大云寺、龙兴寺,疏勒的汉寺是大云寺,于阗地区也建有龙兴寺等。寺主都是内地来的汉僧。唐西州的柏孜克里克
石窟寺、吐峪沟石窟寺都成为伊、西、庭三州的佛教圣地。龟兹地区的库木吐喇石窟寺也是汉传佛教的窟寺。所有这些汉寺窟的僧人同内地一样信奉大乘佛学。在这些佛教寺窟中代表唐文化的佛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应运而生,成为盛唐气象的标志。
汉传佛教雕塑“到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和精神性不同,唐代雕塑代之以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接近世间,帮助人们”①。“壁画的转变遵循了同样的方向。不但同一题材的人物形象有了变化,..而且题材和主题本身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里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山林荒野,没有老虎野鹿。有的是华贵绚烂的色调,圆润流利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氛围。衣襟飘动的舞蹈美替代了动作强烈的运动美,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绚烂华丽代替了粗犷狂放”②。不过,由于历代战乱和人为毁损,西域汉传佛教的雕塑艺术品遗存极少,现能见到的是20世纪初被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喇石窟掠走的两具佛教人头像。其中一尊泥塑菩萨头像束发高髻,脸略长,弯眉,端鼻,朱唇,有蝌蚪状胡须,似中原男子形象。而另一尊菩萨头像为女性,亦是束发高髻,但脸部丰满圆润,弯眉,杏眼,朱唇小嘴,其形象更接近唐代雍容、慈祥的仕女。这些菩萨的造型显然取材于唐代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因此更具世俗意味。库木吐喇石窟留存较多的是佛教壁画,特别是45窟壁画是来自中原的画师所绘。这些壁画汉文榜书是晋以来中原流行的“左图右史”的传统样式,人物头饰、衣着及形象均为画家所熟悉并精于表现的汉民族形象,脸为唐之“胖胖型”,技法上重线淡彩,单纯清雅,利用留白,善用唐时劲健流畅的吴派线描。①彩绘大型经变故事壁画是库木吐喇汉风窟的最主要特征。这些经变画往往是一部佛经绘成一幅画,且构图宏大,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场面宏阔。“库木吐喇石窟的经变画与敦煌莫高窟经变画十分相似,只是库木吐喇洞窟空间比较狭小,经变画相应缩小,缺少敦煌大型经变画那种恢宏的气势”②。库木吐喇石窟现存汉风经变画主要有《见无量寿经变》、《药师净土变》、《阿弥陀经变》、《大灌顶经变》等。第11、14窟的正壁绘有《阿弥陀经变》,其中第14窟“阿弥陀佛坐中央,两侧胁侍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佛和菩萨上方的华盖上摩尼珠闪烁,‘重宝璎珞’,‘珍妙宝网罗覆其上’,‘七宝诸树周遍世界’。..虚空中,天花乱坠,各方诸佛端坐莲中前来赴会,楼阁飘住蓝天,彩云烘托着飞天持花盘供养,悬挂在两侧的日、月失去了光辉。下方,众菩萨、天人和阿修罗、夜叉、龙王、罗睺罗等天龙八部围绕”③。它是唐代中原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净土变的题材。中原佛教石窟窟顶还满绘千佛壁画,这种汉风壁画也出现在库木吐喇汉风窟中。第14窟纵券顶中脊绘有莲花、云头纹图案,中脊两侧各绘有千佛12排,也与莫高窟的千佛完全相同。如果从洞窟的装饰图案看,其纹样如团花、云纹、石榴卷草纹等也是中原地区常见的装饰图案。
1999年5月在库车县阿艾乡发现的佛教石窟是典型的汉风窟,因发现地命名为“阿艾石窟”。虽然佛教塑像早已不存,但可贵的是残存在正壁的壁画和汉文榜题。由榜题得知,该石窟是盛唐时期由汉人开凿修建的。正壁的壁画是一幅《观无量寿经变图》,中央是长方形的中堂式佛法会图。阿艾石窟的壁画正是中原大乘佛教净土思想的反映。如果和莫高窟《观无量寿经变图》相比较,无论构图、人物造型、技法、用色都如出一辙:一是总体构图为汉式中堂配左右条幅式。这是中国传统的构图方式,出现在敦煌、龟兹佛教壁画中,有首创性。二是壁画中的人物造型特别贴近唐代社会现实,“以比例适度、面相丰腴、体态健美、庄严沉静为造型风格特点”①。阿艾石窟中的菩萨与莫高窟中的菩萨形象一样,原本无性别,现在成了个个高盘发髻、面部丰腴、婀娜多姿、体态绰约、佩带钏饰、身着罗裙的丽人形象。三是技法均属中国传统的线描技法,人物面部五官、身材、衣着线描流畅、洒脱。四是用色基调偏于淡雅,主色调是石绿和白色,主要敷于佛和菩萨的头光,而帔帛等衣着用淡石青色,裙裤则有时用赭石色勾勒。用色上还使用了莫高窟常见的叠晕法。
笔者把回鹘人信仰的佛教艺术归入汉传佛教艺术范畴是有缘由的:一是回鹘于840年西迁前就在漠北接受了佛教,主要传播途径是中原的汉传佛教;二是西迁后回鹘所居之地基本是唐伊、庭、西三州地区,此三地又是唐代汉传佛教盛行之地;三是回鹘佛教同汉传佛教一样均为大乘佛教。回鹘佛教艺术也可以说是唐代汉传佛教艺术在西域的延续。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的佛寺主要集中在高昌、北庭等地,龟兹也有回鹘佛寺,这三地也就成了回鹘王国的佛教中心。回鹘人西迁后,所用的寺院原本就是汉传佛教寺院,有些则是改建、重建的。回鹘佛教艺术主要也是佛寺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故城佛寺遗址、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佛寺遗址、库车库木吐喇晚期石窟都留下了回鹘佛教艺术的遗迹,其中佛教壁画最具艺术品位。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现存的40多个洞窟中,就有37个洞窟为回鹘王国时期的,其中的壁画主要是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佛本行经变。所绘人物往往在佛像周围,有天部、菩萨、金刚、比丘以及国王、王后、贵族、平民等供养人形象,有些还在佛头两侧画有城池、宫殿、寺院、塔庙等。除佛本行经变壁画外,还有各种净土变壁画、佛本生故事壁画等。这些壁画中的人物,既有盛唐大菩萨(神)、小供养人的画面,亦有晚唐五代出现的小菩萨(神)、大供养人的画面,同时社会生活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壁画中,“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②。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供养礼佛图壁画正中立者为说法传教的大立佛,而右侧两位单腿跪地的供养人大小仅及立佛的三分之一,手持金花盘中各放装物的七个袋子。而吉木萨尔北庭回鹘寺中“王者出行图”壁画的中心人物是交脚坐于白象背上的王者形象。王者前后左右簇拥着身着铠甲、腰间佩剑、弓箭,手持长伞、旌旗的骑士。这与唐五代敦煌壁画中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属同一题材,此幅壁画以张仪潮为中心,战马成行,旌旗飘扬,鼓乐齐鸣,文武官员并列。这种相似绝非偶然,这个时期的壁画都在从虚幻颂歌走向世俗,于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3窟的众人奏乐图本为外道婆罗门听说佛涅槃后欢庆场面的奏乐情景,但壁画中琵琶、横笛、铙、鼓等西域乐器均源于现实生活。同一窟中的举哀图中的散花童子飞天以及戴通天冠的帝王,突厥、吐蕃、回鹘等十六国王子完全是汉人形象。而且在众多壁画人物形象中出现了汉、回(鹘)合璧的现象。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贵妇礼佛图中的贵妇人体态丰腴,脸为“胖胖型”,完全是唐代中原贵妇的形象,但服装、头饰却有回鹘人的特征。这种现象表明,回鹘佛教壁画的人物造型标准完全与中原地区相同,只是在衣著等方面有民族化特征。绘画本身也说明,画师是以汉传佛教的人物形象和回鹘人扮饰共同糅合在一起作为取象的参照系的。就壁画人物形象而言,其身材不再是印度传来的“一折三波”的“S”形的三道弯式身姿,而具有回鹘人体魄健壮的特点。
回鹘壁画同中原佛教壁画技法一样,重视用线条——屈铁盘丝法刻画人物。“他们以密集的线条表现衣服的褶襞,既有质感,又显出躯体的健壮。他们重视解剖,突出人物骨骼,也以线条表示。用线条勾个圆圈,表现人物肘膝关节,突出圆浑的肢体。又用线条勾成钉子式样的骨骼,显得人物粗壮有力”①。在色彩运用上,回鹘佛教壁画也不似龟兹壁画以冷色调为主,而大胆采用暖色,喜用红、黄、赭石、茜等色彩。一般,佛和菩萨的袈裟均为红色,甚至回鹘王族等供养人的服色也全是红色,给人以热烈、温暖的视觉冲击。在回鹘壁画中常常出现富有表现力的装饰图案,如忍冬蔓草、茶花、宝相花等中原地区的花草和水波、云纹、火焰都有极强的装饰性。在图案装饰中回鹘壁画特别注重纹饰间的巧妙搭配,如在蔓藤卷叶纹中配以茶花纹边饰,宝相花纹图案与白色圆圈的搭配都颇具匠心,甚至一些经变故事画也被绘在由白云构成的圆形图案中,这是回鹘壁画的独创。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传入西域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随吐蕃人支援于阗国对付喀喇汗王朝的战争传入于阗等地区。回鹘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于11~13世纪在与吐蕃人的接触中对藏传佛教有了了解和认识。和田出土的“欢喜佛”、高昌回鹘壁画中的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像都证明藏传佛教的确传入了西域。第二个时期是在13世纪的蒙元时代,随着蒙古人皈依佛教和西征,藏传佛教也很快在西域的蒙古人、畏兀人中间传播开来。但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与佛教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第三个时期是明末到整个清代,信仰藏传佛教的卫拉特蒙古进入天山以北地区,藏传佛教流布于西蒙古人中。清代以后西域的满族、锡伯族、察哈尔蒙古、达斡尔族也普遍信仰藏传佛教。17世纪后西蒙古正式确立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在蒙古人中的正统地位,自此,黄教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普遍信仰。卫拉特是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结成的联盟,但互不统属。
在格鲁派形成之前,藏传佛教的主要派别有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创立于15世纪初,创始人为宗喀巴。该派僧人因穿戴黄色僧衣僧帽、庙宇为黄色而通称为黄教。藏传佛教艺术是以庙宇为中心的内供佛像雕塑、壁画、法器以及举行佛事时奏法乐为一体的宗教艺术。黄教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处于全盛期,在蒙古草原和西域卫拉特蒙古聚居地黄庙林立,成了黄教迅速发展的标志。但是,早期的黄庙并非固定的土木结构寺庙,而是帐篷式的庙宇。晚至20世纪20年代,这种帐篷式的黄教庙宇仍在游牧于裕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人中盛行:“这个土尔扈特游牧部落最神圣的宗教境地拥有7座布尔汗斡耳朵这个名字,而7座庙宇的祭坛都是专供祭祀喇嘛教的最高诸神灵(布尔汗)和这些神灵所代表的各个‘黄教’分支派别的。一座庙专供占星术(珠尔哈),另一座庙专供医药(曼巴),而第三座则专供密宗(玉特),这些庙宇叫作珠尔哈音斡耳朵、厄姆音斡耳朵和玉特音斡耳朵。..另一个庙篷叫作‘格根殿’,这个帐篷的喇嘛照管祭坛的香火,总是伴僧钦旅行。在这座庙的诸神中的主神是弥勒,他是未来的救世主,是土尔扈特统治者高度尊敬的一尊神。..帐篷里面悬挂着蓝色和红色的丝绸,从顶上垂着庙旗,旗子上面有‘凶煞’(dokshit)令人害怕的相貌,以保护祭坛上比较文静的诸神灵。巨大的祭祀银质物品,在油灯摇晃的光亮中闪闪发光,在昏暗的帐篷里面,强烈引人注目的色彩,产生了一种亚洲式的辉煌和把秘密视为神圣的浓缩效果。”①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昼夜响彻着法号、海螺和击鼓的声音。音响与辉煌的帐篷庙宇以及弥勒佛像和诸多银质法器构成了黄教的艺术世界。帐篷式的庙宇显然是游牧民族出于游移迁徙方便原因而设计的,蒙古语称为“库伦”。但在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则出现了固定的土木结构的黄庙寺院建筑。
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蒙古是西域最早信仰黄教并修建土木结构黄教庙宇的西蒙古部落。准噶尔部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就曾出现土木结构的寺庙,噶尔丹时期还修建了特尔尼、拉马木、沙丹巴三座寺庙。准噶尔蒙古势力强大时,以伊犁作为进行黄教活动的会宗地,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于1717年后先后在伊犁河南北岸修建了固尔扎庙(俗称金顶寺)和海努克庙(俗称银顶寺)。金顶寺庙顶以盘羊角形状装饰,蒙古语称为固尔扎都纲(意为盘羊庙);银顶寺庙顶形似巨大的牦牛角,蒙古语称为海努克都纲(意为牦牛庙)。这两座堪称黄教艺术之冠的建筑毁于战火,现在所能见到的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承德仿照金顶寺建的安远庙。其后,清政府又在伊犁兴建兴教寺、普化寺等寺庙。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又先后在蒙古族聚居地修建了一系列土木结构的寺庙,如巴伦台的黄庙、尼勒克的喇嘛召、昭苏的圣佑庙、乌苏的黄庙、和布克赛尔的喇嘛庙、和硕的红庙等。哈密、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等地也大建庙宇。在这些黄庙建筑中,现存较完整的是昭苏的圣佑庙,俗称昭苏喇嘛庙。该庙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四年才建成。现存寺院建筑8座,2000平方米。“八座建筑沿着中轴线错落有致,除照壁、山门、前殿、大殿、后殿按中轴建筑外,左右还有硬山顶配殿和八角形双层檐亭阁。大雄宝殿为古庙的主体建筑,殿宽17米,七开间,平面正方形,大出檐,高举析,陡屋顶,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式。大殿前悬挂汉文书写的‘敕建圣佑庙’金字匾额。大殿工程精细,鎏金沥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巨柱擎起的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猛虎雄狮,金鹿麒麟,凤凰弥猴,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大殿的正壁还绘有二龙戏珠、凤凰比翼、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我国传统的壁画”①。从建筑样式和壁画题材看,完全属汉式风格,但在佛殿内又置蒙古包庙宇,内设各种神像和祭奠用的金银祖鲁杯,又体现着西藏、蒙古混合型艺术风格。至于二龙戏珠、凤凰比翼等汉族吉祥图案和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汉族世俗故事壁画的出现证明,越到后期,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庙越是融进了汉文化艺术的因素。绝大多数黄庙建筑并不是纯粹的西藏风格,而是融进了满汉建筑文化的元素。
察哈尔蒙古西迁至塔尔巴哈台等地驻防屯田也建有察哈尔喇嘛庙,较著名的有今博乐市的镇远寺,俗称“依克苏木大庙”,今温泉县的积福寺,俗称“查干苏木”,即白庙,塔尔巴哈台的绥靖寺等。镇远寺建筑从山门到大殿呈对称格局。大殿坐北朝南,为三大间的建筑,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屋面为两面坡式,双层挑檐,四角飞翘。山门屋面覆瓦,亦为两面坡式,双层挑檐,主脊与垂脊处理和大殿相近。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对称配殿。大殿建于七级台阶的高台上,高台四周用有动物、花卉图形构件镶嵌装饰。大殿、配殿、山门构成镇远寺的主体建筑。积福寺则为藏式建筑,除三大间的经堂大殿外,最有特色的是庙前的白色宝瓶状喇嘛塔。方形塔座和四周的回廊构成塔的底部,廊基顶部为宝塔的须弥座,呈八面形,每面均有浮雕花纹的佛龛。须弥座上为宝瓶形塔身,塔顶为一圆柱形塔柱,柱顶有华盖,尖顶。整座塔高约30米。察哈尔蒙古喇嘛庙大殿内都供有佛陀、弥勒、宗喀巴诸神的金、银、铜像,还绘有众多的壁画、布墙画等,供奉用的酥油灯、佛铃、钵、香炉、盏等也为金、银、铜质。
藏传佛教的所有雕塑和壁画的制作都要遵循严格的轨仪,不能随心所欲。“这些造像根据佛陀所现的三身分为三类:一是法身,用诸如坛城、法轮、佛塔和‘擦擦’袖珍小佛像雕塑等等的法物表示;二是受用身,用一些带有法结、丝饰衣袍的各种身饰、头饰的神灵造像表示;三是变化身,用没有佩戴饰物的神灵形象表示。..就宗教绘画来说,除了与神佛的主体身像直接相关的细节外,艺术家还要考虑主体以外的整个装饰背景。这包括风景、画面活动的生物以及一些装饰物品,诸如太阳、月亮、星辰一类的天体以及其他能使观众产生愉悦的装饰”①。当然,创作这些雕塑和绘画的目的是为了使广大信徒通过佛教艺术造像进入善业功德之中。信徒通过膜拜这些象征物获取善业功德是最根本的,只是佛教艺术家们所塑造、绘制的诸多神灵、天堂等虚幻景象往往又以现实的世俗社会为依据,无论创作者有多么超凡的想象力,总不能摆脱感性经验的窠臼,因为宗教艺术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有七情六欲的人。
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的第一站当是甘肃河西地区,这是印度佛教、西域佛教东渐演化为汉传佛教后,与西域佛教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十六国后期沮渠蒙逊在河西走廊建立北凉政权,北凉被北魏灭后,其后裔在高昌建立政权,于是,河西地区的汉传佛教也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唐代在西域建安西、北庭两都护府,随着内地汉民来到西域,碛西三州、四镇地区再次传入汉传佛教。高昌回鹘汗国的回鹘人接受的也是汉传佛教。清代更出现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并立的局面。尽管我们在汉传佛教艺术中都能见到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渊源关系,但北凉沮渠蒙逊则是运用雕刻、窣堵波、壁画表现佛徒王权的始作俑者。“在蒙逊的保护之下,挖掘了很多石窟如敦煌石窟,并用许多雕刻和壁画表现他的政治(思想),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的目的还翻译了很多大乘佛经”③。这也是河西汉传佛教艺术勃兴的时期。作为汉传佛教艺术审美标准的最高境界是:“以静态人体的大致轮廓,表达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景仰的对象和理想。”④尽管在此说的是宗教雕塑,但它同样适用于一切佛教造型艺术。北凉裔部在高昌的佛教石窟最类似于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268、272、275窟的是吐峪沟44窟,洞窟形制、壁画布局、人物造型、绘画技艺及佛教信仰方面都有共同之处:
吐峪沟44窟与莫高窟272、275窟均为单室,窟平面呈方形,吐44窟为平顶,中间筑拱为穹隆顶,也和莫高窟272窟相似。在壁画布局方面,吐44窟正(东)壁和两侧(南北)的画面与莫高窟272、275窟相同,均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和272窟的南北壁相似,中间是一佛二菩萨的说法图,其余是禅定千佛。中段绘一排佛本生故事,与275窟南北两壁相似。从壁画的题材内容来看,吐44窟中段所绘佛本生故事和莫高窟相同,均以最富特色的一个或两个情节来表现主题。说法图中的主尊可能是弥勒佛,两侧协侍菩萨侍立,窟内四壁满绘千佛,这均与上述莫高窟的壁画题材有共同之处。壁画中的人物面型、服饰与上述莫高窟一样,都是面型浑圆,额宽颐丰,肩宽而腰细,佛内穿僧祗支,外披袒右式通肩袈裟。菩萨头戴三髻珠宝冠,头发披两肩,袒上身披帛,着裙。在图案装饰方面,吐44窟穹隆顶和四壁下端的三角形垂帐纹,也和莫高窟272、275相同。引人注意的是,我国传统的线描,用粗犷有力的线条勾勒轮廓,纤细的铁线描绘眼嘴和衣纹等细部,再用烘染法表现物体内部、人物或服色及所采用的“凹凸晕染法”,尤其是人物面部的晕染,两地十分近似。①
从北凉到高昌王国时期流行“弥勒”题材的壁画看,北凉政权及其裔部都试图借弥勒降生在转轮王的国土这一传说,以转轮王作为自己的理想,以使统治稳固长久。“佛徒王权”才是绘制这些壁画的真正动机。
唐统一西域后汉传佛教盛行于西域的直接结果是一批佛教汉寺窟的出现。唐北庭都护府治庭州先后出现了应运太宁寺、龙兴寺、高台寺,龟兹作为唐安西都护府治,也有大云寺、龙兴寺,疏勒的汉寺是大云寺,于阗地区也建有龙兴寺等。寺主都是内地来的汉僧。唐西州的柏孜克里克
石窟寺、吐峪沟石窟寺都成为伊、西、庭三州的佛教圣地。龟兹地区的库木吐喇石窟寺也是汉传佛教的窟寺。所有这些汉寺窟的僧人同内地一样信奉大乘佛学。在这些佛教寺窟中代表唐文化的佛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应运而生,成为盛唐气象的标志。
汉传佛教雕塑“到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和精神性不同,唐代雕塑代之以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接近世间,帮助人们”①。“壁画的转变遵循了同样的方向。不但同一题材的人物形象有了变化,..而且题材和主题本身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里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山林荒野,没有老虎野鹿。有的是华贵绚烂的色调,圆润流利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氛围。衣襟飘动的舞蹈美替代了动作强烈的运动美,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绚烂华丽代替了粗犷狂放”②。不过,由于历代战乱和人为毁损,西域汉传佛教的雕塑艺术品遗存极少,现能见到的是20世纪初被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喇石窟掠走的两具佛教人头像。其中一尊泥塑菩萨头像束发高髻,脸略长,弯眉,端鼻,朱唇,有蝌蚪状胡须,似中原男子形象。而另一尊菩萨头像为女性,亦是束发高髻,但脸部丰满圆润,弯眉,杏眼,朱唇小嘴,其形象更接近唐代雍容、慈祥的仕女。这些菩萨的造型显然取材于唐代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因此更具世俗意味。库木吐喇石窟留存较多的是佛教壁画,特别是45窟壁画是来自中原的画师所绘。这些壁画汉文榜书是晋以来中原流行的“左图右史”的传统样式,人物头饰、衣着及形象均为画家所熟悉并精于表现的汉民族形象,脸为唐之“胖胖型”,技法上重线淡彩,单纯清雅,利用留白,善用唐时劲健流畅的吴派线描。①彩绘大型经变故事壁画是库木吐喇汉风窟的最主要特征。这些经变画往往是一部佛经绘成一幅画,且构图宏大,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场面宏阔。“库木吐喇石窟的经变画与敦煌莫高窟经变画十分相似,只是库木吐喇洞窟空间比较狭小,经变画相应缩小,缺少敦煌大型经变画那种恢宏的气势”②。库木吐喇石窟现存汉风经变画主要有《见无量寿经变》、《药师净土变》、《阿弥陀经变》、《大灌顶经变》等。第11、14窟的正壁绘有《阿弥陀经变》,其中第14窟“阿弥陀佛坐中央,两侧胁侍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佛和菩萨上方的华盖上摩尼珠闪烁,‘重宝璎珞’,‘珍妙宝网罗覆其上’,‘七宝诸树周遍世界’。..虚空中,天花乱坠,各方诸佛端坐莲中前来赴会,楼阁飘住蓝天,彩云烘托着飞天持花盘供养,悬挂在两侧的日、月失去了光辉。下方,众菩萨、天人和阿修罗、夜叉、龙王、罗睺罗等天龙八部围绕”③。它是唐代中原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净土变的题材。中原佛教石窟窟顶还满绘千佛壁画,这种汉风壁画也出现在库木吐喇汉风窟中。第14窟纵券顶中脊绘有莲花、云头纹图案,中脊两侧各绘有千佛12排,也与莫高窟的千佛完全相同。如果从洞窟的装饰图案看,其纹样如团花、云纹、石榴卷草纹等也是中原地区常见的装饰图案。
1999年5月在库车县阿艾乡发现的佛教石窟是典型的汉风窟,因发现地命名为“阿艾石窟”。虽然佛教塑像早已不存,但可贵的是残存在正壁的壁画和汉文榜题。由榜题得知,该石窟是盛唐时期由汉人开凿修建的。正壁的壁画是一幅《观无量寿经变图》,中央是长方形的中堂式佛法会图。阿艾石窟的壁画正是中原大乘佛教净土思想的反映。如果和莫高窟《观无量寿经变图》相比较,无论构图、人物造型、技法、用色都如出一辙:一是总体构图为汉式中堂配左右条幅式。这是中国传统的构图方式,出现在敦煌、龟兹佛教壁画中,有首创性。二是壁画中的人物造型特别贴近唐代社会现实,“以比例适度、面相丰腴、体态健美、庄严沉静为造型风格特点”①。阿艾石窟中的菩萨与莫高窟中的菩萨形象一样,原本无性别,现在成了个个高盘发髻、面部丰腴、婀娜多姿、体态绰约、佩带钏饰、身着罗裙的丽人形象。三是技法均属中国传统的线描技法,人物面部五官、身材、衣着线描流畅、洒脱。四是用色基调偏于淡雅,主色调是石绿和白色,主要敷于佛和菩萨的头光,而帔帛等衣着用淡石青色,裙裤则有时用赭石色勾勒。用色上还使用了莫高窟常见的叠晕法。
笔者把回鹘人信仰的佛教艺术归入汉传佛教艺术范畴是有缘由的:一是回鹘于840年西迁前就在漠北接受了佛教,主要传播途径是中原的汉传佛教;二是西迁后回鹘所居之地基本是唐伊、庭、西三州地区,此三地又是唐代汉传佛教盛行之地;三是回鹘佛教同汉传佛教一样均为大乘佛教。回鹘佛教艺术也可以说是唐代汉传佛教艺术在西域的延续。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的佛寺主要集中在高昌、北庭等地,龟兹也有回鹘佛寺,这三地也就成了回鹘王国的佛教中心。回鹘人西迁后,所用的寺院原本就是汉传佛教寺院,有些则是改建、重建的。回鹘佛教艺术主要也是佛寺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故城佛寺遗址、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佛寺遗址、库车库木吐喇晚期石窟都留下了回鹘佛教艺术的遗迹,其中佛教壁画最具艺术品位。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现存的40多个洞窟中,就有37个洞窟为回鹘王国时期的,其中的壁画主要是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佛本行经变。所绘人物往往在佛像周围,有天部、菩萨、金刚、比丘以及国王、王后、贵族、平民等供养人形象,有些还在佛头两侧画有城池、宫殿、寺院、塔庙等。除佛本行经变壁画外,还有各种净土变壁画、佛本生故事壁画等。这些壁画中的人物,既有盛唐大菩萨(神)、小供养人的画面,亦有晚唐五代出现的小菩萨(神)、大供养人的画面,同时社会生活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壁画中,“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②。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供养礼佛图壁画正中立者为说法传教的大立佛,而右侧两位单腿跪地的供养人大小仅及立佛的三分之一,手持金花盘中各放装物的七个袋子。而吉木萨尔北庭回鹘寺中“王者出行图”壁画的中心人物是交脚坐于白象背上的王者形象。王者前后左右簇拥着身着铠甲、腰间佩剑、弓箭,手持长伞、旌旗的骑士。这与唐五代敦煌壁画中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属同一题材,此幅壁画以张仪潮为中心,战马成行,旌旗飘扬,鼓乐齐鸣,文武官员并列。这种相似绝非偶然,这个时期的壁画都在从虚幻颂歌走向世俗,于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3窟的众人奏乐图本为外道婆罗门听说佛涅槃后欢庆场面的奏乐情景,但壁画中琵琶、横笛、铙、鼓等西域乐器均源于现实生活。同一窟中的举哀图中的散花童子飞天以及戴通天冠的帝王,突厥、吐蕃、回鹘等十六国王子完全是汉人形象。而且在众多壁画人物形象中出现了汉、回(鹘)合璧的现象。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贵妇礼佛图中的贵妇人体态丰腴,脸为“胖胖型”,完全是唐代中原贵妇的形象,但服装、头饰却有回鹘人的特征。这种现象表明,回鹘佛教壁画的人物造型标准完全与中原地区相同,只是在衣著等方面有民族化特征。绘画本身也说明,画师是以汉传佛教的人物形象和回鹘人扮饰共同糅合在一起作为取象的参照系的。就壁画人物形象而言,其身材不再是印度传来的“一折三波”的“S”形的三道弯式身姿,而具有回鹘人体魄健壮的特点。
回鹘壁画同中原佛教壁画技法一样,重视用线条——屈铁盘丝法刻画人物。“他们以密集的线条表现衣服的褶襞,既有质感,又显出躯体的健壮。他们重视解剖,突出人物骨骼,也以线条表示。用线条勾个圆圈,表现人物肘膝关节,突出圆浑的肢体。又用线条勾成钉子式样的骨骼,显得人物粗壮有力”①。在色彩运用上,回鹘佛教壁画也不似龟兹壁画以冷色调为主,而大胆采用暖色,喜用红、黄、赭石、茜等色彩。一般,佛和菩萨的袈裟均为红色,甚至回鹘王族等供养人的服色也全是红色,给人以热烈、温暖的视觉冲击。在回鹘壁画中常常出现富有表现力的装饰图案,如忍冬蔓草、茶花、宝相花等中原地区的花草和水波、云纹、火焰都有极强的装饰性。在图案装饰中回鹘壁画特别注重纹饰间的巧妙搭配,如在蔓藤卷叶纹中配以茶花纹边饰,宝相花纹图案与白色圆圈的搭配都颇具匠心,甚至一些经变故事画也被绘在由白云构成的圆形图案中,这是回鹘壁画的独创。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传入西域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随吐蕃人支援于阗国对付喀喇汗王朝的战争传入于阗等地区。回鹘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于11~13世纪在与吐蕃人的接触中对藏传佛教有了了解和认识。和田出土的“欢喜佛”、高昌回鹘壁画中的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像都证明藏传佛教的确传入了西域。第二个时期是在13世纪的蒙元时代,随着蒙古人皈依佛教和西征,藏传佛教也很快在西域的蒙古人、畏兀人中间传播开来。但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与佛教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第三个时期是明末到整个清代,信仰藏传佛教的卫拉特蒙古进入天山以北地区,藏传佛教流布于西蒙古人中。清代以后西域的满族、锡伯族、察哈尔蒙古、达斡尔族也普遍信仰藏传佛教。17世纪后西蒙古正式确立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在蒙古人中的正统地位,自此,黄教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普遍信仰。卫拉特是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结成的联盟,但互不统属。
在格鲁派形成之前,藏传佛教的主要派别有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创立于15世纪初,创始人为宗喀巴。该派僧人因穿戴黄色僧衣僧帽、庙宇为黄色而通称为黄教。藏传佛教艺术是以庙宇为中心的内供佛像雕塑、壁画、法器以及举行佛事时奏法乐为一体的宗教艺术。黄教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处于全盛期,在蒙古草原和西域卫拉特蒙古聚居地黄庙林立,成了黄教迅速发展的标志。但是,早期的黄庙并非固定的土木结构寺庙,而是帐篷式的庙宇。晚至20世纪20年代,这种帐篷式的黄教庙宇仍在游牧于裕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人中盛行:“这个土尔扈特游牧部落最神圣的宗教境地拥有7座布尔汗斡耳朵这个名字,而7座庙宇的祭坛都是专供祭祀喇嘛教的最高诸神灵(布尔汗)和这些神灵所代表的各个‘黄教’分支派别的。一座庙专供占星术(珠尔哈),另一座庙专供医药(曼巴),而第三座则专供密宗(玉特),这些庙宇叫作珠尔哈音斡耳朵、厄姆音斡耳朵和玉特音斡耳朵。..另一个庙篷叫作‘格根殿’,这个帐篷的喇嘛照管祭坛的香火,总是伴僧钦旅行。在这座庙的诸神中的主神是弥勒,他是未来的救世主,是土尔扈特统治者高度尊敬的一尊神。..帐篷里面悬挂着蓝色和红色的丝绸,从顶上垂着庙旗,旗子上面有‘凶煞’(dokshit)令人害怕的相貌,以保护祭坛上比较文静的诸神灵。巨大的祭祀银质物品,在油灯摇晃的光亮中闪闪发光,在昏暗的帐篷里面,强烈引人注目的色彩,产生了一种亚洲式的辉煌和把秘密视为神圣的浓缩效果。”①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昼夜响彻着法号、海螺和击鼓的声音。音响与辉煌的帐篷庙宇以及弥勒佛像和诸多银质法器构成了黄教的艺术世界。帐篷式的庙宇显然是游牧民族出于游移迁徙方便原因而设计的,蒙古语称为“库伦”。但在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则出现了固定的土木结构的黄庙寺院建筑。
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蒙古是西域最早信仰黄教并修建土木结构黄教庙宇的西蒙古部落。准噶尔部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就曾出现土木结构的寺庙,噶尔丹时期还修建了特尔尼、拉马木、沙丹巴三座寺庙。准噶尔蒙古势力强大时,以伊犁作为进行黄教活动的会宗地,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于1717年后先后在伊犁河南北岸修建了固尔扎庙(俗称金顶寺)和海努克庙(俗称银顶寺)。金顶寺庙顶以盘羊角形状装饰,蒙古语称为固尔扎都纲(意为盘羊庙);银顶寺庙顶形似巨大的牦牛角,蒙古语称为海努克都纲(意为牦牛庙)。这两座堪称黄教艺术之冠的建筑毁于战火,现在所能见到的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承德仿照金顶寺建的安远庙。其后,清政府又在伊犁兴建兴教寺、普化寺等寺庙。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又先后在蒙古族聚居地修建了一系列土木结构的寺庙,如巴伦台的黄庙、尼勒克的喇嘛召、昭苏的圣佑庙、乌苏的黄庙、和布克赛尔的喇嘛庙、和硕的红庙等。哈密、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等地也大建庙宇。在这些黄庙建筑中,现存较完整的是昭苏的圣佑庙,俗称昭苏喇嘛庙。该庙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四年才建成。现存寺院建筑8座,2000平方米。“八座建筑沿着中轴线错落有致,除照壁、山门、前殿、大殿、后殿按中轴建筑外,左右还有硬山顶配殿和八角形双层檐亭阁。大雄宝殿为古庙的主体建筑,殿宽17米,七开间,平面正方形,大出檐,高举析,陡屋顶,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式。大殿前悬挂汉文书写的‘敕建圣佑庙’金字匾额。大殿工程精细,鎏金沥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巨柱擎起的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猛虎雄狮,金鹿麒麟,凤凰弥猴,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大殿的正壁还绘有二龙戏珠、凤凰比翼、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我国传统的壁画”①。从建筑样式和壁画题材看,完全属汉式风格,但在佛殿内又置蒙古包庙宇,内设各种神像和祭奠用的金银祖鲁杯,又体现着西藏、蒙古混合型艺术风格。至于二龙戏珠、凤凰比翼等汉族吉祥图案和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汉族世俗故事壁画的出现证明,越到后期,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庙越是融进了汉文化艺术的因素。绝大多数黄庙建筑并不是纯粹的西藏风格,而是融进了满汉建筑文化的元素。
察哈尔蒙古西迁至塔尔巴哈台等地驻防屯田也建有察哈尔喇嘛庙,较著名的有今博乐市的镇远寺,俗称“依克苏木大庙”,今温泉县的积福寺,俗称“查干苏木”,即白庙,塔尔巴哈台的绥靖寺等。镇远寺建筑从山门到大殿呈对称格局。大殿坐北朝南,为三大间的建筑,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屋面为两面坡式,双层挑檐,四角飞翘。山门屋面覆瓦,亦为两面坡式,双层挑檐,主脊与垂脊处理和大殿相近。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对称配殿。大殿建于七级台阶的高台上,高台四周用有动物、花卉图形构件镶嵌装饰。大殿、配殿、山门构成镇远寺的主体建筑。积福寺则为藏式建筑,除三大间的经堂大殿外,最有特色的是庙前的白色宝瓶状喇嘛塔。方形塔座和四周的回廊构成塔的底部,廊基顶部为宝塔的须弥座,呈八面形,每面均有浮雕花纹的佛龛。须弥座上为宝瓶形塔身,塔顶为一圆柱形塔柱,柱顶有华盖,尖顶。整座塔高约30米。察哈尔蒙古喇嘛庙大殿内都供有佛陀、弥勒、宗喀巴诸神的金、银、铜像,还绘有众多的壁画、布墙画等,供奉用的酥油灯、佛铃、钵、香炉、盏等也为金、银、铜质。
藏传佛教的所有雕塑和壁画的制作都要遵循严格的轨仪,不能随心所欲。“这些造像根据佛陀所现的三身分为三类:一是法身,用诸如坛城、法轮、佛塔和‘擦擦’袖珍小佛像雕塑等等的法物表示;二是受用身,用一些带有法结、丝饰衣袍的各种身饰、头饰的神灵造像表示;三是变化身,用没有佩戴饰物的神灵形象表示。..就宗教绘画来说,除了与神佛的主体身像直接相关的细节外,艺术家还要考虑主体以外的整个装饰背景。这包括风景、画面活动的生物以及一些装饰物品,诸如太阳、月亮、星辰一类的天体以及其他能使观众产生愉悦的装饰”①。当然,创作这些雕塑和绘画的目的是为了使广大信徒通过佛教艺术造像进入善业功德之中。信徒通过膜拜这些象征物获取善业功德是最根本的,只是佛教艺术家们所塑造、绘制的诸多神灵、天堂等虚幻景象往往又以现实的世俗社会为依据,无论创作者有多么超凡的想象力,总不能摆脱感性经验的窠臼,因为宗教艺术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有七情六欲的人。
附注
①祁志祥.以“圆”为美——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之一.文史哲.2003(1).
②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2~3.
③〔新加坡〕古正美.中国的佛教:过去和现在.汤一介.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00.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22.
①杜斗城.试论北凉佛教对高昌的影响.西域研究.1991(4).
①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14.
②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16~117.
①刘增祺.库木吐喇45窟壁画浅析.新疆社会科学.1988(1).
②霍旭初.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117~118.
③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326.
①段文杰.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86.
②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19.
①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502.
①〔丹麦〕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253~254.
①魏长洪等著.西域佛教史.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234.
①扎雅·诺丹西绕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52、54.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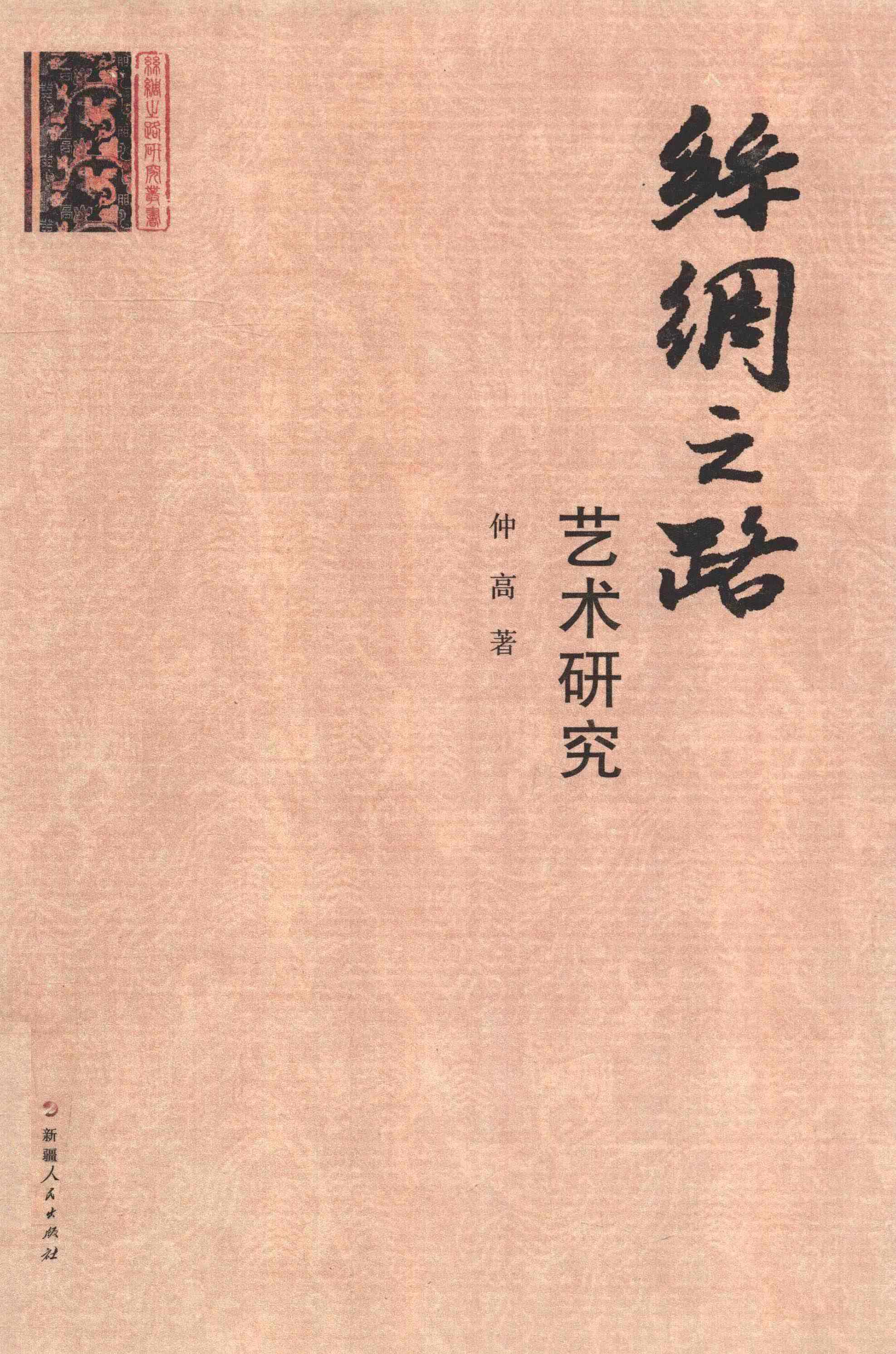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