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祆教、摩尼教、景教艺术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45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祆教、摩尼教、景教艺术 |
| 分类号: | J196.9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21-230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祆教艺术、摩尼教艺术、景教艺术情况。 |
| 关键词: | 祆教 摩尼教 景教艺术 |
内容
一、祆教艺术
祆教是唐代汉语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因祆教崇拜火,也称为“拜火教”、“火祆教”等。据说,祆教于公元前4世纪传入西域,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于阗都已成为传播的中心。
祆教于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立,之后传入中亚地区,再从中亚地区传入于阗、疏勒、高昌等地,这些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的交汇处。祆教的经典是《河维斯塔》,其含义有“智识”、“经典”、“谕令”之意,内容分三部分,即天国的知识(伽萨尼克),人间的知识(达迪克),天国和人间的联系(哈塔克·曼斯里克)。祆教有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祆祠,内有大小火炉,为祭拜太阳神(火神)之物,也可能有神主画像或塑像。祆教的教义是善恶二元论,代表光明、清净、创造、生的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而代表黑暗、不净、破坏、死的是恶神安格拉·曼纽。善恶二神不断斗争,最后是善神战胜恶神。根据祆教教义,人的一生不断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死后受到马兹达的“末日审判”,以决定该人是进天堂还是入地狱。祆教尊崇太阳神与火神,故汉文献称之为“火祆教”。对“火祆”二字,陈垣先生的解释是:“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①
祆教同其他宗教一样,“精神化是伟大的理想的目标;但形体化是必要的手段。真理必须有形化才能被认识;它必须具体化才会被理解。历史上所有有影响的、受欢迎的宗教运动都离不开丰富的形象”②。被称为祆教艺术的祆祠、画像、雕塑、丧葬器物等以物化的象征物和祭祀乐舞构成吸引感官的基本形式。从出土文物看,祆教早期的造型物是十分简单的,特别像塞人拜火处所和圣坛更是如此。举行祭火仪式的处所不过是“火之屋”(阿洛乌霍纳),孔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地表是太阳辐射状的象征物;祭坛是铜制方盘,这可能与塞人是居无定所的狩猎游牧部落有关。在阿拉沟和伊犁河流域出土的青铜盘被认为是塞人的拜火祭坛。阿拉沟古墓出土的高方座承兽铜盘上为方盘,宽平折沿,中央立狮形双兽,下为方体喇叭状高圈足。在伊犁河北岸古墓出土的兽首吞蹄式足双耳铜方盘亦为方盘,平底,口沿平折,两侧有双环状横耳,四条驼蹄形足上部以人面为饰。两件方铜盘均为公元前5世纪~前1世纪之间文物,与祆教传入西域时间相吻合。由此“塞人将火祆教传入中国的史实再次为考古材料证明”。④除塞人外,3世纪萨珊波斯王朝将祆教奉为国教,随后粟特人将祆教继塞人后又一次传入西域,高昌、于阗、焉耆、疏勒等西域诸城郭之国的祆教信仰再次兴盛起来,祆祠、祆教壁画、雕塑和骨瓮等成了祆教艺术的主要载体。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亚祆祠遗迹是属5~8世纪粟特人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中已发掘的两座并排的神庙:“它们坐落在城市大广场的西面,而且在布局的基本原则上,两座神庙十分接近:每座神庙都由一个被围墙和各种房间环绕着的正方形院子,及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中心建筑物构成。每一神庙的中心建筑,东边都有立着6根圆柱的门厅,它与没有东墙的四柱大厅连为一体,大厅的西面是封闭的圣殿和从南、西、北三面环绕大厅和圣殿并与门厅相连的回廊(或一排房间)。
门厅的东面是台阶或斜坡道与院子相连。”①片治肯特的神庙建筑面向东方,发掘后发现彩绘浮雕、塑像和壁画的残迹,其中被称为《哭丧图》的壁画正是粟特人祭祀男女神祗的场面。从形象看,男神为祆教中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而女神则是娜娜,她原为波斯人万神殿中的大地之神,后阿胡拉·马兹达升格为祆教主神,而娜娜的地位却降为天神之女。②粟特人祆教壁画和木板画中的这种“素”画被称为白画或素画,在和田的丹丹乌里克和敦煌都有发现。“1992年,莫德(MarkusMode)发表《远离故土的粟特神祗——近年粟特地区考古发现所印证的一些和田出土的粟特图像》一文,判断出和田出土的一些木板画上,绘制的不是佛教的形象,而是粟特系统的祆教神谱,特别是编号为D.X.3的木板正面,是三个一组的神像,从左到右依次绘制的是阿胡拉·马兹达、娜娜女神和风神。另外,还有一些木板画上的形象,也可以认定是属于祆教的”。③但是D.X.3木板画正面是祆神形象,而背面则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不能排除在一个多神信仰的社会中,佛教信仰和祆教信仰并不互相排斥,它们的神祗可共居于一座寺庙中,当然这与于阗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聚落不无关系。敦煌P.4518(24)号白画中,右面女神有光轮,高冠,后两臂一手执日,一手执月;前两臂一手执蛇,一手执蝎,身后一犬伸舌。对此,姜伯勤先生综合一些学者的研究后认为:“那些手执日月的女神或与阿尔迈提有关,而阿尔迈提在《阿维斯塔》中亦是一行使天神使命的重要神祗。加上祆教又是主张杀蛇的,因此,我们认为敦煌白画中的手持日月蛇蝎的女神,与粟特人信仰的四臂女神有关,亦与祆教有关。”④粟特人民间信仰中的诸多神祗也成为祆教神祗的情形屡见不鲜。
文献所记高昌国“俗事天神”之事,至今学者们意见纷争,但从出土文物看,高昌居民也曾信仰祆教。在高昌故城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这些钱币的固定模式是,正面为发行该货币的国王头像,头冠上有三个雉形饰物,象征祆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北面中间为拜火祭坛,两边各立一个祭司或其他神职人员,火坛上方的火焰之上,有阿胡拉·马兹达的侧面像。”①高昌王国并不流通波斯银币,而恰恰在一个用煤精制成的黑色方盒内装有一组10枚银币。对此,荣新江先生认为:“它们很可能是供奉给祆祠的,因为信奉祆教的粟特人是当时波斯银币的主要持有者。”②此说不无道理。
祆教徒死后的丧葬习俗是盛骨瓮葬,王室用金瓮:“‘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民间则用陶质骨瓮,花拉子模(即九姓胡的“火寻”)地区常有发现。”③这种“盛骨瓮”在新疆也有出土。1959年在伊犁地区出土的外壁装饰忍冬花纹的陶瓮可能是5世纪之盛骨瓮,其形状如游牧部落的毡房,极有可能是〓哒人的盛骨瓮。与中亚楚河流域出土的7~8世纪突厥人的盛骨瓮比较,“不难看出伊犁出土的这个佚失其盖的陶瓮实际上就是中亚火祆教徒使用的那种盛骨瓮”。④楚河流域出土的毡房式盛骨瓮瓮壁装饰有双手在胸前相交祈祷的立人像和太阳纹图案,上方镂空,象征毡房的骨架。整个盛骨瓮的装饰采用浮雕式手法,有强烈的立体效果。毡房式盛骨瓮应看作是祆教传入游牧部落后适应本土化的一种变异。其实祆教的丧葬习俗在东渐中不断发生变异,在中原地区采用汉式石棺床土葬,而且出现双阙型石棺床画像石、石椁型石棺床画像石和石屏风型石棺床画像石,但内容与祆教信仰有关,如祭火坛等。可以说“中国祆教画像石,融合了中国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和外来的波斯及中亚的祆教美术的艺术风格”。⑤从一些祆教壁画和盛骨瓮图像看,祆教祭祀仪式中是有娱神乐舞的。
二、摩尼教艺术
摩尼教因其教主名摩尼而得名,曾于3~15世纪流行于亚洲、欧洲和非洲。摩尼教以融祆教、佛教、基督教精华于一炉自诩。摩尼教的经典是摩尼所著七部书,即《彻尽万法根源智经》、《争命宝藏经》、《律藏经》、《证明过去教经》、《大力士经》、《赞愿经》等,但均遗失,未能保存下来。摩尼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二宗”为光明和黑暗、善与恶,显然吸取了祆教教义的内容。“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现在、未来,“二宗”始终在“三际”中斗争,但以“中际”的斗争最为激烈。摩尼教的最高神祗是大明神,他是光明王国的主宰,大明神的光明是太阳和月亮,故进行摩尼教仪式活动的摩尼寺绘有象征大明神形象的日月等壁画。摩尼教有其自身的戒律,即“三封”、“十戒”。“三封”指口封、手封、胸封,多是劝诫教徒不说谎、不做坏事、禁淫欲等内容;“十戒”包括不拜偶像、不说谎、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诈伪、不行邪术、不二心、不惰等。但分属五个教界的教职人员和信徒,对“三封”、“十戒”的要求是不同的。摩尼教教徒每天进行四次祈祷,还要实行斋戒和忏悔、追悼亡者等活动都以诗歌方式礼赞,《摩尼教下部赞》就是这类诗歌集。
摩尼教是在丝绸之路流行时间较长的宗教之一,估计在6世纪左右传入西域。从各种迹象看,摩尼教是经粟特人传入西域的,于阗、高昌等都是传入之地。国外学者认为:“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天山南路之西域,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前。..在东方从事传播摩尼教的不仅有粟特人,也有吐火罗人。”②但是摩尼教在西域这样一个佛教发达的地区,为了本教的生存不得不随时改形,而且还往往依托佛教求生存不可,甚至连教义也从佛教教义中吸收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分。
在西域较早信仰摩尼教的是回鹘人,曾在8世纪中叶西迁前就放弃佛教而改宗摩尼教,840年西迁至高昌一带后仍信奉摩尼教,高昌也就成了摩尼教的传播中心。20世纪所发现的与摩尼教艺术有关的窟寺、壁画也主要是回鹘汗国时期的。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发掘,是有关摩尼教寺院遗址和古代写本的首次发现。1904年由勒柯克等人组成的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有关摩尼教文物包括高昌城K遗址、摩尼寺和摩尼教壁画残片、摩尼教画幡、摩尼教绢画、摩尼教纸画和有突厥文题记的摩尼教细密画残片等。
高昌城K遗址由北部的一组拱顶小房、东部的藏书室、中部的几个大厅和西部的拱顶大房组成。有关摩尼教的写本、壁画、画幡、绢、纸画和细密画都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因此确认它是一座摩尼寺。晁华山先生曾对吐鲁番胜金口摩尼教的北寺、南寺石窟寺院作过考察:“北寺规模宏大,左右宽约40米,上下高约12米,从寺前地面到最高处窟顶共有五层平台。下起第3层是主要平台,这层平台的正壁建有5个洞窟,中心是环形道的礼拜窟(第3窟),南邻窟(第4窟)是大窟,主室三壁开有旁室,其正壁上方半圆面画生命树与死亡树交会图,两侧壁画宝树果园图,树下有斋讲高师。大礼拜窟北邻窟(第2窟)正壁有龛,龛外两侧壁画宝树果园图,券腹画葡萄树。..南寺规模较小,上下有五层整斋的平台,洞窟建于下起第1、2层平台。”①这两寺后均被改作佛教寺院。按敦煌遗书文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摩尼寺院应由五种殿堂组成,每种各有一座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和病僧堂。高昌故城K遗址和胜金口北寺、南寺恰恰与摩尼寺院的布局、分类相似。K遗址中的拱顶大屋和胜金口北寺的主室均应为摩尼教寺院的斋讲堂。
胜金口北寺斋讲堂壁画题材主要有:(1)生命树与死亡树交会图;(2)七重宝树明使图;(3)宝树果园图;(4)日月宫图;(5)高师斋讲图;(6)行者观想图;(7)阴阳人图;(8)断爱欲图等。在所有已发现的摩尼教壁画中以K遗址中的大型壁画最为引人注目:
我们发现了一幅用水彩画的壁画,这是一位摩尼教的高级教士,他穿着专用的教士服装,周围被穿着白色僧侣服饰的教徒所包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一些摩尼教的细密画中,经常出现摩尼教徒们用穿不同的僧服来区别他们在宗教上的不同级别。这个高级教士的画像,在整个壁画的所有人物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尺寸比真人还大。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在胸部位置有一块矩形刺绣图案,左肩也绣有这么一块,也许在右肩上也绣有一块,可惜已毁坏了。在他的头上,戴有一顶高高的白帽子,有金线装饰,用一根黑色的带子扎在下腭处。脸呈椭圆形,鼻梁弯曲,眼睛虽然不大,但却布局合理,非常有神,使人想起中国艺术家们在给欧洲人画肖像时所表现出的特点。画像身后的光轮是由新月和太阳组合而成的。太阳的圆盘被画成淡淡的胭脂色,然而那月牙则被画成金黄色,就画在代表太阳的圆圈中。从这一与众不同的光轮或可推测,我们面前的这幅摩尼教大士像也许就是摩尼本人。①
由于该壁画已残缺,壁画上部的生命树与死亡树交会图已看不到。但从胜金口北寺正壁壁画分析,这两幅壁画应属同一题材,表达同一主题,系同一来源。壁画中的太阳与月亮的光芒显然是大明神的象征,突出的人物形象为明尊——摩尼,其他为明尊周围的诸使者,即明使。斋讲堂的这些大型壁画的用途应与摩尼教的仪式联系起来考虑,斋讲堂正是教士讲授、信徒诵习七部大经之处,观想代表七部大经的宝树和明尊、明使,也就具有超度自己和求得解脱的作用。K遗址出土的摩尼教画幡中的男女白衣人形象也应是摩尼教中的男女明使形象。在摩尼教三际论的中际阶段,大明尊曾先后三次召唤男女诸明使,以制服暗魔,穿白衣的男女明使当与此有关。高昌故城K遗址出土的摩尼教典籍中还在红、黑两色书写的回鹘文经卷旁绘有盛开花朵的长藤正是《下部赞》中的常荣树:“..一切诸佛(明使)花间出,一切智慧果中生。”其寓意是诸明使“展转相生,化身无量”,助明尊战胜暗魔。在和田约特干遗址还出土一件棕地摩尼宝珠纹锦巾,出土时佩于死者身上。图案是,在盛开的莲花之上是宝珠放射光芒的纹饰。死者应是位摩尼教徒,锦巾图案正是教徒所追求的光明王国的象征,宝石、珍珠意象在摩尼教壁画中一再出现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摩尼教教义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壁画中屡屡出现明尊、明使的形象,这与其教义有悖。教徒“观想”这些壁画中的形象不能说没有崇敬心理,这或许与佛教、基督教偶像崇拜对摩尼教不无影响相关。
三、景教艺术
景教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传入中国后的称呼,因创始人的名字聂斯脱里而得名,又称波斯经教、秦教等。景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物证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在长安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为汉字,背面左右两侧和下面是用叙利亚文刻的七十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教职。碑文由序文和颂词组成。碑的序文概括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和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据文献记载,景教是7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唐朝都城长安的。传入丝绸之路中段西域的时间可能在6世纪,而在唐代至元朝达到鼎盛期。
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创立于5世纪上半叶,创始者聂斯脱里是叙利亚人。他于428~431年期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当时君士坦丁堡教会对耶稣之母玛利亚是人还是神产生分歧,且争论不休。而聂斯脱里认为“神之母”的说法违背“耶稣”使徒的教诲,也未经过教会授权,他针对尖锐的意见分歧提出一个折中的说法,称玛利亚为“基督之母”。但他的说法遭到亚历山大城大主教西利勒的强烈反对,聂斯脱里遂被流放,客死埃及,“神之母”说取得胜利。之后,聂斯脱里的信徒将其说教向东发展,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直到中亚,从我国的新疆再到长安以及沿海等地逐渐扩大势力,管辖着25个主教教区,到14世纪末才被蒙古人所瓦解。我国的唐代长安和新疆高昌地区都是景教的中心。景教总主教伊尔亚三世(1176~1190)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建立了总教区,时至西辽时期,其教区范围包括喀什噶尔、于阗及七河流域地区。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也是经上述总教区传入长安后译写又传到敦煌地区抄写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共有七件,即《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其中第一件中的“三威”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尊严,《尊经》是向三位一体、圣徒和诸经的礼赞,其他还包括景教的“十愿”及赞词等内容。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景教文献以吐鲁番出土文书较丰,基本是用四种文字书写的,即粟特文、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和回鹘文。景教在喀什噶尔及周边地区传播的情况见诸于《马可波罗行纪》:“此地(指喀什噶尔)有不少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有其本教教堂。”①又说:“鸭儿看(今莎车)乃是一州,广五日程。居民遵守摩诃末教法,然亦有聂思脱里派同雅各派之基督教徒。”②辽金至蒙元时代,北方草原以及金山一带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和阿里麻里地区的哈剌鲁部也曾信奉景教。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任何成果都“无法与那个时代的绘画、雕刻以及教堂建筑所具有的宗教品质相媲美”①,予以基督教艺术高度评价。作为基督教分支的聂斯托里教派的绘画、雕刻和教堂建筑的宗教造型艺术在西域肯定也是盛极一时,但遗存却是凤毛麟角。我们现在可以凭借的还是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高昌故城遗址的发现。被确认为景教教堂的遗址早已被洗劫一空,“就所保存下来的部分看,此庙有三个大厅。大厅前边东南侧上,有一个后建的、安装了门的小侧室。在东、西两侧的大厅里,出于某种改建的目的,建造了新墙。在东厅中,此新墙建在南墙与北墙的内侧,西厅则建在南墙内侧”②。证明这是景教教堂的证据是在东厅北墙所绘骑士形象左肩扛着的旗杆尖端为十字架,更重要的发现是西厅Y处的一幅壁画,勒柯克等人没有定名,现在刊布的资料中也仅仅称为“高昌景教壁画”。对此,勒柯克描述道:
画面左侧,..站着一高大的、不寻常的男人,他的黑色卷发,使人想起晚期希腊艺术的绘画。他身穿一件直达脚面的绿色长衫,上身还披一件有皱褶的宽大红外套。..他左手提着一个金黄(黄)色的香炉,此种形式的香炉,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壁画与细密画上,都没有出现过。用一束向上飘浮的波浪状线条表示烟雾,升至高处变成螺旋形烟云。右手捧着一个黑色的碗状物体,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圣水钵。他面前站着三个人,其中前两个人看来是男人,靠右边的第三人是女人,每个人都举着一根有叶子的树枝。他们的服装很奇特,..它是很长的单色长衫,最前边那个人穿棕色的,第二个人穿青灰色的,看来没有系腰带。..最后看右边那个女人形象:她身穿一件绿色长袖短上衣,只达上半身的一半;下身系一条很长的裙子,遮盖了两脚;肩头轻披一件棕色的披肩或围巾,从右肩直垂到大腿中部,从左肩飘到胸前。③
勒柯克还描述了男子的棕色帽子与女子的圆球形发式和挽的发髻。因这些人物并非像摩尼教徒一样身穿白衣,可以确认为是景教徒。勒柯克的描述虽然显得有些琐碎,但对理解此幅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不无裨益。壁画表现的是基督教徒在“圣枝节”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情景。前面身材高大者为牧师,其余男女均为信徒。“圣枝节”也称“圣枝主日”,它源于耶稣受难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手执棕枝的众信徒欢迎的故事。以后以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纪念活动。基督教教堂也多以棕枝作装饰,有时教徒也持棕枝绕教堂一周以示纪念。高昌故城的这幅壁画明显具有拜占庭艺术风格。拜占庭(东罗马)艺术是继承早期基督教艺术和吸收西亚、中亚艺术的宫廷基督教艺术,这种东西方艺术融合的踪迹在高昌景教壁画中也能看到。景教的信物发现不多,见于刊布的是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和田约特干收集到的一枚铜制十字架,以及伊犁河流域景教徒墓碑。由于景教遗址、文物发现极少,因此对景教艺术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遗憾,这种遗憾只能有待今后更多文物的发现来弥补了。
祆教是唐代汉语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因祆教崇拜火,也称为“拜火教”、“火祆教”等。据说,祆教于公元前4世纪传入西域,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于阗都已成为传播的中心。
祆教于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立,之后传入中亚地区,再从中亚地区传入于阗、疏勒、高昌等地,这些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的交汇处。祆教的经典是《河维斯塔》,其含义有“智识”、“经典”、“谕令”之意,内容分三部分,即天国的知识(伽萨尼克),人间的知识(达迪克),天国和人间的联系(哈塔克·曼斯里克)。祆教有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祆祠,内有大小火炉,为祭拜太阳神(火神)之物,也可能有神主画像或塑像。祆教的教义是善恶二元论,代表光明、清净、创造、生的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而代表黑暗、不净、破坏、死的是恶神安格拉·曼纽。善恶二神不断斗争,最后是善神战胜恶神。根据祆教教义,人的一生不断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死后受到马兹达的“末日审判”,以决定该人是进天堂还是入地狱。祆教尊崇太阳神与火神,故汉文献称之为“火祆教”。对“火祆”二字,陈垣先生的解释是:“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①
祆教同其他宗教一样,“精神化是伟大的理想的目标;但形体化是必要的手段。真理必须有形化才能被认识;它必须具体化才会被理解。历史上所有有影响的、受欢迎的宗教运动都离不开丰富的形象”②。被称为祆教艺术的祆祠、画像、雕塑、丧葬器物等以物化的象征物和祭祀乐舞构成吸引感官的基本形式。从出土文物看,祆教早期的造型物是十分简单的,特别像塞人拜火处所和圣坛更是如此。举行祭火仪式的处所不过是“火之屋”(阿洛乌霍纳),孔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地表是太阳辐射状的象征物;祭坛是铜制方盘,这可能与塞人是居无定所的狩猎游牧部落有关。在阿拉沟和伊犁河流域出土的青铜盘被认为是塞人的拜火祭坛。阿拉沟古墓出土的高方座承兽铜盘上为方盘,宽平折沿,中央立狮形双兽,下为方体喇叭状高圈足。在伊犁河北岸古墓出土的兽首吞蹄式足双耳铜方盘亦为方盘,平底,口沿平折,两侧有双环状横耳,四条驼蹄形足上部以人面为饰。两件方铜盘均为公元前5世纪~前1世纪之间文物,与祆教传入西域时间相吻合。由此“塞人将火祆教传入中国的史实再次为考古材料证明”。④除塞人外,3世纪萨珊波斯王朝将祆教奉为国教,随后粟特人将祆教继塞人后又一次传入西域,高昌、于阗、焉耆、疏勒等西域诸城郭之国的祆教信仰再次兴盛起来,祆祠、祆教壁画、雕塑和骨瓮等成了祆教艺术的主要载体。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亚祆祠遗迹是属5~8世纪粟特人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中已发掘的两座并排的神庙:“它们坐落在城市大广场的西面,而且在布局的基本原则上,两座神庙十分接近:每座神庙都由一个被围墙和各种房间环绕着的正方形院子,及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中心建筑物构成。每一神庙的中心建筑,东边都有立着6根圆柱的门厅,它与没有东墙的四柱大厅连为一体,大厅的西面是封闭的圣殿和从南、西、北三面环绕大厅和圣殿并与门厅相连的回廊(或一排房间)。
门厅的东面是台阶或斜坡道与院子相连。”①片治肯特的神庙建筑面向东方,发掘后发现彩绘浮雕、塑像和壁画的残迹,其中被称为《哭丧图》的壁画正是粟特人祭祀男女神祗的场面。从形象看,男神为祆教中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而女神则是娜娜,她原为波斯人万神殿中的大地之神,后阿胡拉·马兹达升格为祆教主神,而娜娜的地位却降为天神之女。②粟特人祆教壁画和木板画中的这种“素”画被称为白画或素画,在和田的丹丹乌里克和敦煌都有发现。“1992年,莫德(MarkusMode)发表《远离故土的粟特神祗——近年粟特地区考古发现所印证的一些和田出土的粟特图像》一文,判断出和田出土的一些木板画上,绘制的不是佛教的形象,而是粟特系统的祆教神谱,特别是编号为D.X.3的木板正面,是三个一组的神像,从左到右依次绘制的是阿胡拉·马兹达、娜娜女神和风神。另外,还有一些木板画上的形象,也可以认定是属于祆教的”。③但是D.X.3木板画正面是祆神形象,而背面则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不能排除在一个多神信仰的社会中,佛教信仰和祆教信仰并不互相排斥,它们的神祗可共居于一座寺庙中,当然这与于阗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聚落不无关系。敦煌P.4518(24)号白画中,右面女神有光轮,高冠,后两臂一手执日,一手执月;前两臂一手执蛇,一手执蝎,身后一犬伸舌。对此,姜伯勤先生综合一些学者的研究后认为:“那些手执日月的女神或与阿尔迈提有关,而阿尔迈提在《阿维斯塔》中亦是一行使天神使命的重要神祗。加上祆教又是主张杀蛇的,因此,我们认为敦煌白画中的手持日月蛇蝎的女神,与粟特人信仰的四臂女神有关,亦与祆教有关。”④粟特人民间信仰中的诸多神祗也成为祆教神祗的情形屡见不鲜。
文献所记高昌国“俗事天神”之事,至今学者们意见纷争,但从出土文物看,高昌居民也曾信仰祆教。在高昌故城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这些钱币的固定模式是,正面为发行该货币的国王头像,头冠上有三个雉形饰物,象征祆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北面中间为拜火祭坛,两边各立一个祭司或其他神职人员,火坛上方的火焰之上,有阿胡拉·马兹达的侧面像。”①高昌王国并不流通波斯银币,而恰恰在一个用煤精制成的黑色方盒内装有一组10枚银币。对此,荣新江先生认为:“它们很可能是供奉给祆祠的,因为信奉祆教的粟特人是当时波斯银币的主要持有者。”②此说不无道理。
祆教徒死后的丧葬习俗是盛骨瓮葬,王室用金瓮:“‘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民间则用陶质骨瓮,花拉子模(即九姓胡的“火寻”)地区常有发现。”③这种“盛骨瓮”在新疆也有出土。1959年在伊犁地区出土的外壁装饰忍冬花纹的陶瓮可能是5世纪之盛骨瓮,其形状如游牧部落的毡房,极有可能是〓哒人的盛骨瓮。与中亚楚河流域出土的7~8世纪突厥人的盛骨瓮比较,“不难看出伊犁出土的这个佚失其盖的陶瓮实际上就是中亚火祆教徒使用的那种盛骨瓮”。④楚河流域出土的毡房式盛骨瓮瓮壁装饰有双手在胸前相交祈祷的立人像和太阳纹图案,上方镂空,象征毡房的骨架。整个盛骨瓮的装饰采用浮雕式手法,有强烈的立体效果。毡房式盛骨瓮应看作是祆教传入游牧部落后适应本土化的一种变异。其实祆教的丧葬习俗在东渐中不断发生变异,在中原地区采用汉式石棺床土葬,而且出现双阙型石棺床画像石、石椁型石棺床画像石和石屏风型石棺床画像石,但内容与祆教信仰有关,如祭火坛等。可以说“中国祆教画像石,融合了中国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和外来的波斯及中亚的祆教美术的艺术风格”。⑤从一些祆教壁画和盛骨瓮图像看,祆教祭祀仪式中是有娱神乐舞的。
二、摩尼教艺术
摩尼教因其教主名摩尼而得名,曾于3~15世纪流行于亚洲、欧洲和非洲。摩尼教以融祆教、佛教、基督教精华于一炉自诩。摩尼教的经典是摩尼所著七部书,即《彻尽万法根源智经》、《争命宝藏经》、《律藏经》、《证明过去教经》、《大力士经》、《赞愿经》等,但均遗失,未能保存下来。摩尼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二宗”为光明和黑暗、善与恶,显然吸取了祆教教义的内容。“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现在、未来,“二宗”始终在“三际”中斗争,但以“中际”的斗争最为激烈。摩尼教的最高神祗是大明神,他是光明王国的主宰,大明神的光明是太阳和月亮,故进行摩尼教仪式活动的摩尼寺绘有象征大明神形象的日月等壁画。摩尼教有其自身的戒律,即“三封”、“十戒”。“三封”指口封、手封、胸封,多是劝诫教徒不说谎、不做坏事、禁淫欲等内容;“十戒”包括不拜偶像、不说谎、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诈伪、不行邪术、不二心、不惰等。但分属五个教界的教职人员和信徒,对“三封”、“十戒”的要求是不同的。摩尼教教徒每天进行四次祈祷,还要实行斋戒和忏悔、追悼亡者等活动都以诗歌方式礼赞,《摩尼教下部赞》就是这类诗歌集。
摩尼教是在丝绸之路流行时间较长的宗教之一,估计在6世纪左右传入西域。从各种迹象看,摩尼教是经粟特人传入西域的,于阗、高昌等都是传入之地。国外学者认为:“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天山南路之西域,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前。..在东方从事传播摩尼教的不仅有粟特人,也有吐火罗人。”②但是摩尼教在西域这样一个佛教发达的地区,为了本教的生存不得不随时改形,而且还往往依托佛教求生存不可,甚至连教义也从佛教教义中吸收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分。
在西域较早信仰摩尼教的是回鹘人,曾在8世纪中叶西迁前就放弃佛教而改宗摩尼教,840年西迁至高昌一带后仍信奉摩尼教,高昌也就成了摩尼教的传播中心。20世纪所发现的与摩尼教艺术有关的窟寺、壁画也主要是回鹘汗国时期的。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发掘,是有关摩尼教寺院遗址和古代写本的首次发现。1904年由勒柯克等人组成的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有关摩尼教文物包括高昌城K遗址、摩尼寺和摩尼教壁画残片、摩尼教画幡、摩尼教绢画、摩尼教纸画和有突厥文题记的摩尼教细密画残片等。
高昌城K遗址由北部的一组拱顶小房、东部的藏书室、中部的几个大厅和西部的拱顶大房组成。有关摩尼教的写本、壁画、画幡、绢、纸画和细密画都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因此确认它是一座摩尼寺。晁华山先生曾对吐鲁番胜金口摩尼教的北寺、南寺石窟寺院作过考察:“北寺规模宏大,左右宽约40米,上下高约12米,从寺前地面到最高处窟顶共有五层平台。下起第3层是主要平台,这层平台的正壁建有5个洞窟,中心是环形道的礼拜窟(第3窟),南邻窟(第4窟)是大窟,主室三壁开有旁室,其正壁上方半圆面画生命树与死亡树交会图,两侧壁画宝树果园图,树下有斋讲高师。大礼拜窟北邻窟(第2窟)正壁有龛,龛外两侧壁画宝树果园图,券腹画葡萄树。..南寺规模较小,上下有五层整斋的平台,洞窟建于下起第1、2层平台。”①这两寺后均被改作佛教寺院。按敦煌遗书文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摩尼寺院应由五种殿堂组成,每种各有一座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和病僧堂。高昌故城K遗址和胜金口北寺、南寺恰恰与摩尼寺院的布局、分类相似。K遗址中的拱顶大屋和胜金口北寺的主室均应为摩尼教寺院的斋讲堂。
胜金口北寺斋讲堂壁画题材主要有:(1)生命树与死亡树交会图;(2)七重宝树明使图;(3)宝树果园图;(4)日月宫图;(5)高师斋讲图;(6)行者观想图;(7)阴阳人图;(8)断爱欲图等。在所有已发现的摩尼教壁画中以K遗址中的大型壁画最为引人注目:
我们发现了一幅用水彩画的壁画,这是一位摩尼教的高级教士,他穿着专用的教士服装,周围被穿着白色僧侣服饰的教徒所包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一些摩尼教的细密画中,经常出现摩尼教徒们用穿不同的僧服来区别他们在宗教上的不同级别。这个高级教士的画像,在整个壁画的所有人物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尺寸比真人还大。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在胸部位置有一块矩形刺绣图案,左肩也绣有这么一块,也许在右肩上也绣有一块,可惜已毁坏了。在他的头上,戴有一顶高高的白帽子,有金线装饰,用一根黑色的带子扎在下腭处。脸呈椭圆形,鼻梁弯曲,眼睛虽然不大,但却布局合理,非常有神,使人想起中国艺术家们在给欧洲人画肖像时所表现出的特点。画像身后的光轮是由新月和太阳组合而成的。太阳的圆盘被画成淡淡的胭脂色,然而那月牙则被画成金黄色,就画在代表太阳的圆圈中。从这一与众不同的光轮或可推测,我们面前的这幅摩尼教大士像也许就是摩尼本人。①
由于该壁画已残缺,壁画上部的生命树与死亡树交会图已看不到。但从胜金口北寺正壁壁画分析,这两幅壁画应属同一题材,表达同一主题,系同一来源。壁画中的太阳与月亮的光芒显然是大明神的象征,突出的人物形象为明尊——摩尼,其他为明尊周围的诸使者,即明使。斋讲堂的这些大型壁画的用途应与摩尼教的仪式联系起来考虑,斋讲堂正是教士讲授、信徒诵习七部大经之处,观想代表七部大经的宝树和明尊、明使,也就具有超度自己和求得解脱的作用。K遗址出土的摩尼教画幡中的男女白衣人形象也应是摩尼教中的男女明使形象。在摩尼教三际论的中际阶段,大明尊曾先后三次召唤男女诸明使,以制服暗魔,穿白衣的男女明使当与此有关。高昌故城K遗址出土的摩尼教典籍中还在红、黑两色书写的回鹘文经卷旁绘有盛开花朵的长藤正是《下部赞》中的常荣树:“..一切诸佛(明使)花间出,一切智慧果中生。”其寓意是诸明使“展转相生,化身无量”,助明尊战胜暗魔。在和田约特干遗址还出土一件棕地摩尼宝珠纹锦巾,出土时佩于死者身上。图案是,在盛开的莲花之上是宝珠放射光芒的纹饰。死者应是位摩尼教徒,锦巾图案正是教徒所追求的光明王国的象征,宝石、珍珠意象在摩尼教壁画中一再出现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摩尼教教义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壁画中屡屡出现明尊、明使的形象,这与其教义有悖。教徒“观想”这些壁画中的形象不能说没有崇敬心理,这或许与佛教、基督教偶像崇拜对摩尼教不无影响相关。
三、景教艺术
景教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传入中国后的称呼,因创始人的名字聂斯脱里而得名,又称波斯经教、秦教等。景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物证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在长安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为汉字,背面左右两侧和下面是用叙利亚文刻的七十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教职。碑文由序文和颂词组成。碑的序文概括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和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据文献记载,景教是7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唐朝都城长安的。传入丝绸之路中段西域的时间可能在6世纪,而在唐代至元朝达到鼎盛期。
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创立于5世纪上半叶,创始者聂斯脱里是叙利亚人。他于428~431年期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当时君士坦丁堡教会对耶稣之母玛利亚是人还是神产生分歧,且争论不休。而聂斯脱里认为“神之母”的说法违背“耶稣”使徒的教诲,也未经过教会授权,他针对尖锐的意见分歧提出一个折中的说法,称玛利亚为“基督之母”。但他的说法遭到亚历山大城大主教西利勒的强烈反对,聂斯脱里遂被流放,客死埃及,“神之母”说取得胜利。之后,聂斯脱里的信徒将其说教向东发展,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直到中亚,从我国的新疆再到长安以及沿海等地逐渐扩大势力,管辖着25个主教教区,到14世纪末才被蒙古人所瓦解。我国的唐代长安和新疆高昌地区都是景教的中心。景教总主教伊尔亚三世(1176~1190)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建立了总教区,时至西辽时期,其教区范围包括喀什噶尔、于阗及七河流域地区。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也是经上述总教区传入长安后译写又传到敦煌地区抄写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共有七件,即《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其中第一件中的“三威”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尊严,《尊经》是向三位一体、圣徒和诸经的礼赞,其他还包括景教的“十愿”及赞词等内容。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景教文献以吐鲁番出土文书较丰,基本是用四种文字书写的,即粟特文、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和回鹘文。景教在喀什噶尔及周边地区传播的情况见诸于《马可波罗行纪》:“此地(指喀什噶尔)有不少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有其本教教堂。”①又说:“鸭儿看(今莎车)乃是一州,广五日程。居民遵守摩诃末教法,然亦有聂思脱里派同雅各派之基督教徒。”②辽金至蒙元时代,北方草原以及金山一带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和阿里麻里地区的哈剌鲁部也曾信奉景教。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任何成果都“无法与那个时代的绘画、雕刻以及教堂建筑所具有的宗教品质相媲美”①,予以基督教艺术高度评价。作为基督教分支的聂斯托里教派的绘画、雕刻和教堂建筑的宗教造型艺术在西域肯定也是盛极一时,但遗存却是凤毛麟角。我们现在可以凭借的还是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高昌故城遗址的发现。被确认为景教教堂的遗址早已被洗劫一空,“就所保存下来的部分看,此庙有三个大厅。大厅前边东南侧上,有一个后建的、安装了门的小侧室。在东、西两侧的大厅里,出于某种改建的目的,建造了新墙。在东厅中,此新墙建在南墙与北墙的内侧,西厅则建在南墙内侧”②。证明这是景教教堂的证据是在东厅北墙所绘骑士形象左肩扛着的旗杆尖端为十字架,更重要的发现是西厅Y处的一幅壁画,勒柯克等人没有定名,现在刊布的资料中也仅仅称为“高昌景教壁画”。对此,勒柯克描述道:
画面左侧,..站着一高大的、不寻常的男人,他的黑色卷发,使人想起晚期希腊艺术的绘画。他身穿一件直达脚面的绿色长衫,上身还披一件有皱褶的宽大红外套。..他左手提着一个金黄(黄)色的香炉,此种形式的香炉,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壁画与细密画上,都没有出现过。用一束向上飘浮的波浪状线条表示烟雾,升至高处变成螺旋形烟云。右手捧着一个黑色的碗状物体,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圣水钵。他面前站着三个人,其中前两个人看来是男人,靠右边的第三人是女人,每个人都举着一根有叶子的树枝。他们的服装很奇特,..它是很长的单色长衫,最前边那个人穿棕色的,第二个人穿青灰色的,看来没有系腰带。..最后看右边那个女人形象:她身穿一件绿色长袖短上衣,只达上半身的一半;下身系一条很长的裙子,遮盖了两脚;肩头轻披一件棕色的披肩或围巾,从右肩直垂到大腿中部,从左肩飘到胸前。③
勒柯克还描述了男子的棕色帽子与女子的圆球形发式和挽的发髻。因这些人物并非像摩尼教徒一样身穿白衣,可以确认为是景教徒。勒柯克的描述虽然显得有些琐碎,但对理解此幅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不无裨益。壁画表现的是基督教徒在“圣枝节”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情景。前面身材高大者为牧师,其余男女均为信徒。“圣枝节”也称“圣枝主日”,它源于耶稣受难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手执棕枝的众信徒欢迎的故事。以后以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纪念活动。基督教教堂也多以棕枝作装饰,有时教徒也持棕枝绕教堂一周以示纪念。高昌故城的这幅壁画明显具有拜占庭艺术风格。拜占庭(东罗马)艺术是继承早期基督教艺术和吸收西亚、中亚艺术的宫廷基督教艺术,这种东西方艺术融合的踪迹在高昌景教壁画中也能看到。景教的信物发现不多,见于刊布的是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和田约特干收集到的一枚铜制十字架,以及伊犁河流域景教徒墓碑。由于景教遗址、文物发现极少,因此对景教艺术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遗憾,这种遗憾只能有待今后更多文物的发现来弥补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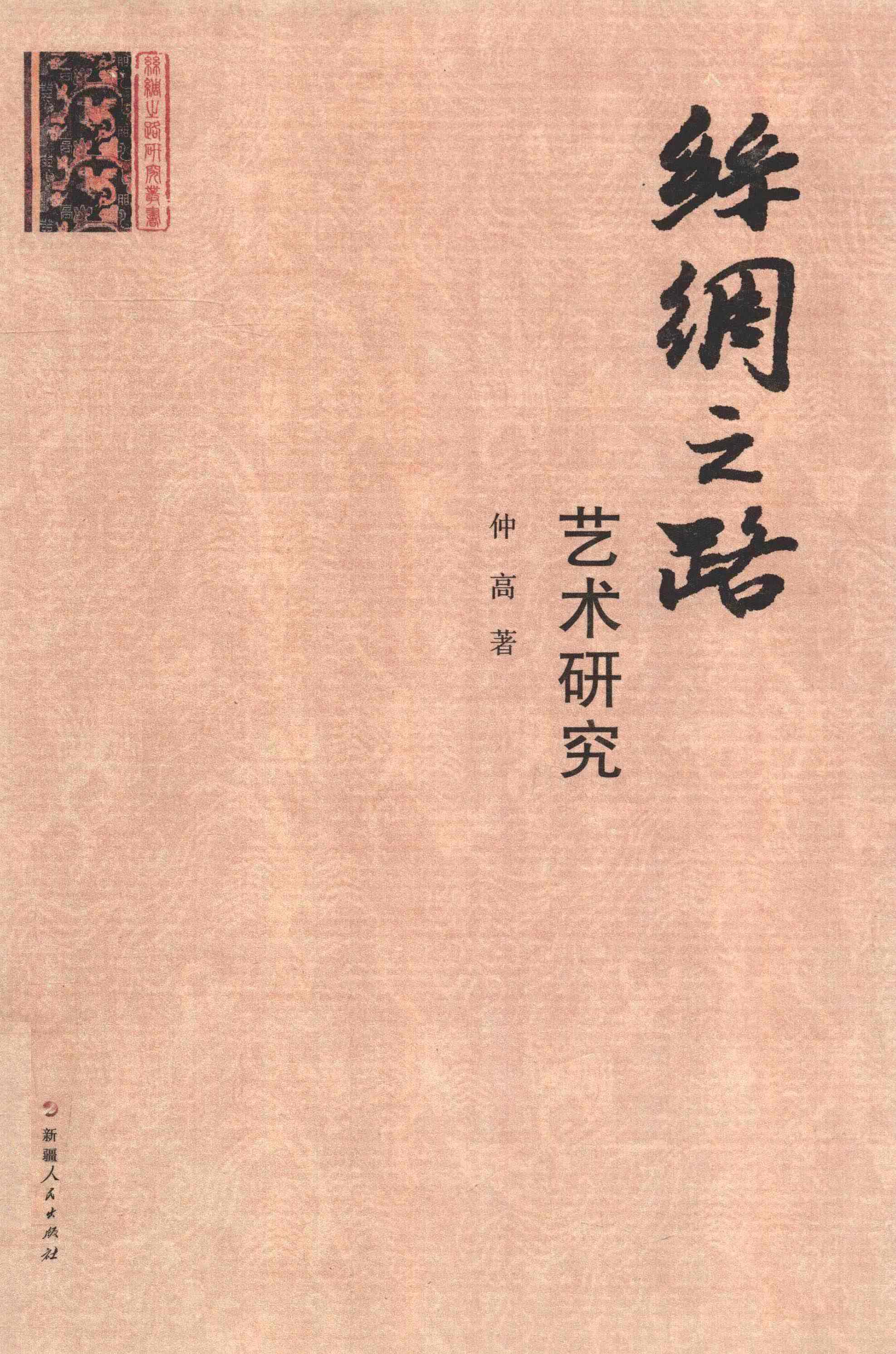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