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萨满教艺术的审美迷狂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44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萨满教艺术的审美迷狂 |
| 分类号: | J196.9 |
| 页数: | 9 |
| 页码: | 213-221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情况。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萨满教 文化艺术 |
内容
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满—通古斯语中将通神的巫〓称为萨满,按性别有男、女萨满之分。突厥语中将萨满称为“卡姆”,以后也称“奥云”和“巴克西”。在蒙古语中,对男女萨满有不同称谓,男萨满称为“博”,女萨满称为“渥德根”,但“博”和“渥德根”仅指施萨满巫术治病的萨满。一般认为,萨满产生于以人类的灵魂和祖先崇拜、自然和灵物崇拜为标志的原始宗教的晚期阶段。如果和人为宗教相比较,萨满教有其自身特征:一是它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如寺院、教堂等,而是与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系进行信仰活动;二是萨满教的信仰是一种自发的传承观念,没有创教始祖和教主,因此也就不存在神授的经文;三是萨满教的信仰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因此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分化出任何固定的信仰组织;四是萨满有韵的祷词——神歌或是程式化或是即兴式的,没有固定的范本;五是表演仪式是象征性的,没有经典、系统的信仰依据,萨满教的造型也是象征性的,它反映的是萨满的思维、观念和意识。
在萨满教信仰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萨满,他既是天神的代言人,又是精灵的化身;他既是人,也是神;他既能代表人们向神许下心愿,又能用巫术为人们消病解灾。萨满是在一种癫狂状态下,用萨满巫术支配着世界的各个方面——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萨满世界按其宇宙观分为三界:上界为天界,是诸神的住所;中界为人间,是人、动物的栖息地;下界为地狱,为魔鬼所居。
萨满教的三界既是由天、地构成的实在的物质世界,又是由神祗、精灵、魂鬼组成的超验的精神世界。因此,萨满的世界观是一种二元世界观。萨满教的观念体系是灵魂观、神灵观和神性观,其核心是对神的信仰,因此,萨满的职能也就成了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其通神的手段是巫术。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作为“行巫术”的仪式性表演,它类似于戏剧表演,有道具、服饰、动作、声音。萨满的道具是他的法器,如萨满鼓、神杖、铃铛、铜镜、神偶、画像等;萨满服饰包括萨满服、萨满帽、萨满裙等;萨满在仪式表演中的形体动作,后被称为萨满舞;而萨满在鼓乐声中唱念祝祷词的有声系统则被赋予萨满歌的称谓。萨满所有这些用于通神的道具、服饰、动作、声音都可归纳为两类,即造型类和声态类,但萨满都对它们赋予了神性,它们都具有象征特征。萨满本身从来不把这些当作艺术,在萨满的仪式性表演活动中只有神圣可言,绝无“戏言”。而研究者则发现,萨满教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萨满教的活动,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既戏剧表演、舞蹈和造型艺术”。①但是,无论是对萨满本身而言,还是就仪式性表演来讲,萨满教的所有造型和声态都是功能性的,有象征意义。把萨满教视为“各种艺术的综合体”仅仅是我们的见解,而不是萨满的看法。不可否认,萨满教的仪式性表演不可能脱离静态的造型形式和动态的声态形式而存在,而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就其造型和声态形式而言,的确蕴涵着艺术发生的种种因素。
笔者在前面若干章节中探讨了与萨满教造型有关的岩画、石人、鹿石的功用问题,在此不再赘述。现在仅讨论萨满在仪式性表演中使用的画像、神偶、服饰、法器等造型和声态系统的问题,因为这些造型和萨满神歌抄本还在锡伯族民间有所遗存,这也就成了最有力的实物例证。锡伯族萨满教延续时间最长,20世纪50年代前仍有萨满的仪式性表演活动,而最后一个女萨满则到20世纪70年代才去世。
锡伯族的萨满画是萨满在举行祭祀祖先、上刀梯和跳神治病仪式时悬挂的神圣物,用毕即入匣收藏。萨满画按其绘画内容和功用大致分为三类:群体神像图、萨满画像和动物神灵图。自20世纪初俄国人克洛特科夫在塔城发现锡伯族萨满神像图后,20世纪80年代锡伯族学者又在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现同一内容的群体神像图。这是一种布绘图像,其画面自上而下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最上一层画面为彩云、日月和“依兰恩杜里格格”(三位神姐)和“顾兴阿玛法”(男祖神)。这些祖神周围是虎、狼、狐狸、蛇、鹿等动物精灵。第二部分是各具神态的岱木林、阿玉鲁、额依嫩德德祟神、艾土罕、善琦、达玛法、阿里玛法、玛法默尔根、萨满玛法、着勒玛法等男女神灵形象。第三部分为合掌或单手祈祷及举杯为上刀梯者助威的近10位男女神灵,如张纳、着青额、纳松额、吴凌额、齐发罕珠、色楞芝等。第四部分为刀梯两侧的两位骑马萨满。第五部分画面最下端绘有供桌,上置燃香的香炉。供桌右侧为三位手持神鼓的萨满,左侧为一条白牛,后面为直入云端的刀梯,梯顶站立着萨满。这是一幅供上刀梯仪式时使用的画像。上刀梯仪式是锡伯族萨满教的独有仪式,举行这种象征仪式的动机是:“一是告诉人们通达神界并非易事,只有踏上实实在在的‘刀梯’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并且暗示,不会人人都能做神界和人间的使者;二是显示萨满真有通达神界和治病救人的本事;三是为了区别有真‘本事’萨满和无能萨满。”①画像中的众神灵既有萨满祖师、祖先神,也有瘟神、动物保护神等,甚至还出现了门神、灶神等。萨满在举行上刀梯、跳神治病等仪式时总是在其祷词中呼喊众位神灵,请神助佑其仪式成功。萨满画像是绘有萨满形象的图画。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幸福乡锡伯族民间发现的一幅萨满画像画面为:一位头戴三只鸟装饰神帽、身着萨满服的萨满坐于方凳上,左手高举绘有蛇形图案的萨满鼓,右手举至胸前微握,神像旁是一跪着的男子,面向萨满。萨满下面绘有水波纹,其上是一条飞龙。这类画像显然是哈拉(姓氏)或莫昆(家族)萨满祖神形象,是专供哈拉或莫昆后代萨满祭祀时使用的,有时在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悬挂,以便从祖神处求得神力。
动物神灵图是每一个萨满专用动物精灵的形象画像。动物精灵在锡伯语中称“巫出固”,实为萨满的动物保护神,每一个萨满均有自己的“巫出固”,有的是雕神,有的是虎神,有的是狼神。“巫出固”作为萨满的助手在跳神治病时助佑主人与病魔搏斗成功。在萨满“巫出固”中,虎神是女萨满保护神中的主神。由于萨满画是功能性的,因此并不要求形似,也不可能形似。因为萨满画都出自民间画师之手,也有的是萨满本身绘制的,就难有很高的绘画技巧,而且作为仪式中的萨满画仅仅是个象征物,并不需要神形毕肖。由于萨满教仪式分为家祭仪式和公众集会仪式,萨满画也有所不同,家祭仪式中的萨满画可能是本族先辈萨满或祖先的形象,而像上刀梯仪式是一种广场式的公众集体仪式,所以悬挂的就是绘有众神的上刀梯图。萨满画中的人物服饰明显有时代特征,如一幅绘于清代的萨满画中的祖先神著的是清代官服。
作为萨满教中的祖神和动物精灵形象不仅出现在画像中,也以神偶等雕塑或缝制形式出现,而且还有些是幻想中得来的怪异形象。在锡伯族民间时常可以见到本族祖先神偶,多为布帛制成的群体神偶。
一般是用布帛剪出人形,内填充棉花等物,再绘出五官。有的还著衣装,或用布裹住全身,只露头部。祖先神偶有单个的,也有夫妻双偶,还有三人以上的群偶,虽然人数不等,但姓氏祖先神偶的形制大体相似。人形偶也有皮制、木雕、金属等材质。有些人形偶的五官特征并不突出,只是在脸部嵌上两个纽扣表示眼睛,与人物实像相去甚远。动物神偶有些是以现实中的动物形象进行造型,多为雕塑,如木雕、金属雕塑等,但也有些是怪诞的形象,用布或皮制作的这些怪诞神鹰之类是萨满心中的“镜像”。动物神偶是萨满的助佑精灵,也可能是氏族的保护神。锡伯族萨满曾使用一种铜质的鹰形动物神偶,是栖息式鹰的形象,用两半鹰形范模合在一起浇铸而成。其背部和腹部均有挂钩,背部挂钩用以系绳,腹部挂钩挂一块红布,在萨满跳神治病等仪式中挂在供桌前,以便治病时助佑萨满发挥神力以达疗效。萨满教中神偶的产生和神形的确立,都与萨满本身的生理、心理特质有关。在一般人看来,萨满都是一些与常人不同的人。成为萨满的先决条件,不是小时经常生病,就是成年后突然出现癫狂之症,或者是好动、爱激动者。特别是患癫狂之症很重要,是存在生理缺陷者。就心理因素而言,萨满的神圣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幻像的产物,因此这些神圣形象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创造者的信仰,特别是那些怪诞的神偶尤其如此。而“神偶中一些怪异形体的形成多源于梦,并非萨满任意而为。一般认为,萨满在梦中见偶体,梦中引偶降世,然后依梦中所得幻体,遵其形谨制偶体,不得疏漏、简率。萨满教观念认为,梦与灵魂密不可分,做梦即浮魂的外游,‘无魂无梦,无梦无形’。其实质是心理幻像的产物”。①一般人都可能在梦境中和记忆中出现一些视觉形象,萨满不过是在千百次的“修炼”中使心理形象更加“完形”而已。
萨满神服、神帽和法器都是萨满化形体为神圣的象征。萨满神服和神帽都是萨满形体重要的组合部分,它们的共同功能有二:一是在萨满的祭神驱邪神物中,神服和神帽是核心的祭祀象征,本身就代表特定的神祗;二是它们又是每个萨满自身的宗教崇拜和信仰的传承物,汇聚了为他服务的超世神祗、精灵和被他征服后甘心为其效力的恶魔精灵,全附栖在神服和神帽内。①但是在使用中神服和神帽又有其各自的特殊功能。由于萨满神服既是神祗的象征,同时又是某些神祗的形体寓所,所以它是法力和凝聚体的综合象征;萨满神帽则是萨满感应信息的主要渠道,它相当于神树。锡伯族萨满早期神服、神帽的实物资料阙如,现在能见到的是百年左右的遗物。男萨满神服由短衣和裙组成。短衣为对襟,高领,布纽扣,多选黄、蓝等颜色布料制作,下摆开衩,前襟、下摆、袖中处补缀有花边;而神裙则由内衬围裙、中层多根麻绳和外包的各色布条缝制而成,布条组成的飘带上绣有各种动物、花草纹饰,裙下摆有垂穗,飘带片数有21条、23条、27条等之分,这与萨满教对宇宙天地的分层观有关。实际上,每个哈拉的萨满神服是各不相同的,而且越是经历多次神祭的神服越是法力无穷。神服的制作、使用、收藏都有严格的规仪,甚至成了萨满的专利,一般人不能染指。萨满服早期是皮制的或干脆是披兽皮,而过渡到布帛制神服不会很早。现在在新疆伊犁锡伯族民间保存下来的神帽由铁制帽圈、帽边、帽顶、铜镜、帽穗及衬里组成。帽圈为圆形,帽边由上到下成十字形交叉,卷成半圆形,四头用铁皮固定在帽圈上。帽顶由3块交叉铜片组成,固定于帽边顶部。因帽顶铜片六边向上翻卷成半圆形,形似莲花,锡伯语称为“伊尔哈”(花)。花边装饰有4个铜铃,帽前嵌有小铜镜。帽后垂穗为5根或10根,是红、蓝、黄、绿等色组成的布制飘带。曾在辽宁锦州市义县罗家屯乡锡伯族民间发现一顶铁制神帽,铁制帽梁上拥成的信息树上顶端为鹰的形象,锡伯语称“安切兰”,是萨满的动物精灵之一。鹰鸟神帽是锡伯族萨满较典型的神帽。对萨满而言,“只要有神祗或其他异兆出现,就马上通过神帽传递于萨满神帽上的精灵和肩鸟,迅传萨满感应,使萨满永立不败之地”。②申帽对萨满来说,更易于与神相交,也就比神服更有特殊地位。
锡伯族萨满的法器多是发光、发声或激击器,有多重功能。“哈准”是萨满挂于腰间的铜镜,为圆形、光面,镜背有铜钮,穿皮绳用。一个萨满的“哈准”多达18个,举行萨满仪式时发光和丁当作响。“托里”是护心镜,佩于胸前,正面光洁鉴人,相当于“照妖镜”。萨满鼓,锡伯语称“伊木秦”,为圆形单面皮鼓,面上绘有动物、植物等纹饰。每个萨满都有三面神鼓,一面自己使用,另两面由副手使用,跳神时用以控制跳动舞步的节奏。神矛、神鞭也是萨满仪式中的器具。神矛柄为木制,矛头为铁制,矛头与柄结合部系有红、黄等色布飘带,并系有若干小铜铃。神鞭,杆为木制,鞭为牛皮编制。所有这些法器发出的响声和光亮以及进击在萨满跳神治病仪式中都是象征性的,萨满一方面在铜镜撞击和击鼓声中有节奏地舞之蹈之,增强跳神效果;另一方面以响声、光亮和进击动作吓退病魔,以达疗效。当然护心镜也象征萨满得到神祗护佑,以保证神力有效。由于萨满仪式常常在夜间举行,于是“萨满服饰和法器的设计实际上也是为了去加强视觉的心理幻想的产生”。①
作为萨满教声态系统的萨满歌和萨满舞都是萨满通神的手段之一,也是萨满神力的表现。就其特征而言,对萨满仪式来说,“舞蹈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要通过高度兴奋的动作的忘形失神去恢复与神秘力量的联系;装饰往往有护符的意义,其功效不在于美而在于防止巫术的伤害;歌唱则与咒语相关,因此重要的是记住歌词而不是懂得歌词真正的意义,意义就在声音里面。”②但是随着萨满的消亡,萨满舞成了程式化的民间舞形态,萨满歌也成了凝固的文本,而萨满仪式性表演中的歌舞文化情境再也不可复现了,锡伯族的萨满舞、萨满歌也是如此。所谓的萨满舞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中的处在迷狂状态的激烈跳动动作。最早描述阿尔泰语系民族萨满跳神治病仪式中萨满舞的是拉德洛夫,时间是1860年7月。他描述的是哈萨克族的巴克西跳神治病的情形:“巴克西一般以单调的伴唱拉琴表演(哈萨克巴克西的表演不起任何作用)。然后拿起棍子挥动着乱跳乱吵。在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巴克西一起跳,一个拉琴,一个又是挥棍又是跳。也有的巴克西跳神什么器具都不用。跳神的时候,巴克西也和萨满一样会神智昏迷,所以也得由几个人护守以避免发生意外,因为巴克西在民众中不再有什么伦理基础,所以看来巴克西比萨满更努力以自己的举动引起大家的恐惧感。所以他跳得非常疯狂,可怕地转动眼睛,咬牙,如疯似狂蹦跳奔跑、踢脚。他们入神之后所耍的把戏,使哈萨克人每每提及无不惊讶不止。”①巴克西至多是巫医,并非真正的萨满,他们的动作也不过是模拟萨满的动作,但它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萨满舞的基本形体动作特征,这比现在民间表演中的“萨满舞”多少有些真实感。从一些资料分析,早期的萨满舞可能是狩猎巫舞。因为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中,身着神服,头戴神帽,一手持神鼓,一手拿神矛,在腰束铜镜丁当响声伴奏下忽而在院内横冲直撞,忽而跳出窗户,忽而又在房顶举目远眺,然后又跳下来,握紧短矛不断猛刺,并从口中发出“哈嘎,哈嘎”的喊声,越跳越兴奋,又发起狂来,最后昏迷过去,以示与妖魔搏斗成功。它的原型显然是原始的狩猎巫舞。
萨满歌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是伴以各种舞步动作的,也就是说,萨满歌与萨满舞是歌舞为一体的。我们现在所见的锡伯族萨满歌是尔喜萨满于光绪十年十一月(1884)手抄的,是神歌的手抄文本,无从窥知其曲调,因此也就只能依据文本进行分析了。手抄本的《萨满歌》分为两册,第一册为《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第二册是《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由九部分构成,即《学萨满时的祷告神歌》、《祈请托里神歌》、《祈请金刀梯神歌》、《萨满端坐凳子之上哀求神歌》、《萨满立在门前祈祷神歌》、《萨满为治病事求告神歌》、《萨满设坛呼唤山羊之神歌》、《请神歌时二神呼唤神歌》和《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神歌》。《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影》有一副标题为《萨满为治病事送三个白色巫尔虎之神歌》,显然是萨满跳神治病时按跳神治病仪式的顺序唱的神歌。从《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的九个部分内容看,均是萨满徒弟学萨满的范本,内涵十分丰富。一向是口耳相传、秘不示人的神歌,露出了它的真容,也可以使人们体味其原始意蕴。萨满歌非一时一世之作,是众多萨满在长期的积累中不断加工的结果,虽然神歌内容都有不同时代的烙印,但原始文化形态的踪影仍能窥见。如第九部分《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神歌》有这样的内容:
行行复行行,
走到第二道门前,
有一只凶猛的公虎,
挡住这大门,
不让进去。
如何进去呀?
师傅道:
在九重天外的祟神们呀,
把这属龙的孙儿,
〔第二道门〕引进里边吧!①
这里的公虎挡道是源自古代氏族萨满顺应人们防范老虎威胁树立虎神,用祈祷方式避祸的心理需求的反映。在萨满神话观中,天是多层的,萨满要与天神沟通,必须越过7道或9道障碍。“在萨满神话中每层天就有1道障碍,5、7、9的障碍数和天的5、7、9层数显然是一致的”。②而“卡伦”是根据清代所设台站、哨卡创作的意象,有“关卡”之意。《祈告、祝赞、祷告之神歌》和《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囊括了锡伯族萨满文化的全部内涵:诸多神祗、精灵,上刀梯、跳神治病仪式,萨满神帽神服和法器等物化形式,甚至还涵盖天文地理、疗术机制和神话观等,因此神歌也可以称之为锡伯族萨满文化的综合体。从演唱形式看,既有萨满本人的独吟,也有师徒俩之间的对唱,还有领唱助唱等形式。如第一册中的《萨满立在门前祈祷神歌》是萨满本人挨家挨户跳神宣喻的独自吟唱;而《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神歌》则是两人间的对唱;《萨满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是由萨满领唱,众人应合的形式,类似有领唱的合唱。在“合唱”中,每一句有实际意义的歌词由萨满本人吟唱,众人以衬词应合:
在方正的屋子里呀环—达里,
有环绕的声息呀伊纳昆—达里,
侧耳倾听呀环—达里,
不是环绕的声息伊纳昆—达里,
是威武的萨满们的环—达里,
霍硕特尔之声呀伊纳昆—达里。
在每一句中前为萨满有意义的吟唱,后为众人无意义的和声衬词。在跳神治病神歌中,尽管每一节中萨满吟唱的歌词是按跳神治病顺序进行的,但衬词都是相同的,即在各节中重复出现。这样,不仅增加了演唱的节奏感,而且在一种助唱的“强声”氛围中祛除病魔,以达到神奇的疗效。早期或一些萨满歌并无歌词,“乐谱极其简单,由一个一再重复的短乐句构成。此短乐句几次重复之后,萨满突然停止歌声,并发出连续的拖长的歇斯底里的叹气,此种叹气声好像‘啊,呀,卡,呀,卡!’之后,他又重新歌唱起来,为此,他要尽力地深呼吸,以便肺部有更多的空气,并使第一个音符最长”。①萨满歌舞同萨满画、萨满神偶、萨满服饰、法器一样均被萨满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萨满神歌的神语神音只在祭祀、跳神等仪式中吟咏,萨满之间是口耳相传的,并且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萨满歌的曲调、旋律也是经过多代萨满吟唱逐渐完善的。萨满神歌的歌词是由萨满背下来的,也有些是即兴演唱的歌词,“这意味着萨满虽谙熟传统的曲调和旋律,但还必须在其能召请之神的帮助下创作诗歌文本。在节日场合使用诗歌文本,不仅将祭祀氛围提高到日常状态之上,而且允许参加者参与这种艺术体验”。②无论是萨满本人,还是广大参与者都能各得其所,这正是萨满歌的存在价值所在。
在萨满教信仰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萨满,他既是天神的代言人,又是精灵的化身;他既是人,也是神;他既能代表人们向神许下心愿,又能用巫术为人们消病解灾。萨满是在一种癫狂状态下,用萨满巫术支配着世界的各个方面——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萨满世界按其宇宙观分为三界:上界为天界,是诸神的住所;中界为人间,是人、动物的栖息地;下界为地狱,为魔鬼所居。
萨满教的三界既是由天、地构成的实在的物质世界,又是由神祗、精灵、魂鬼组成的超验的精神世界。因此,萨满的世界观是一种二元世界观。萨满教的观念体系是灵魂观、神灵观和神性观,其核心是对神的信仰,因此,萨满的职能也就成了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其通神的手段是巫术。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作为“行巫术”的仪式性表演,它类似于戏剧表演,有道具、服饰、动作、声音。萨满的道具是他的法器,如萨满鼓、神杖、铃铛、铜镜、神偶、画像等;萨满服饰包括萨满服、萨满帽、萨满裙等;萨满在仪式表演中的形体动作,后被称为萨满舞;而萨满在鼓乐声中唱念祝祷词的有声系统则被赋予萨满歌的称谓。萨满所有这些用于通神的道具、服饰、动作、声音都可归纳为两类,即造型类和声态类,但萨满都对它们赋予了神性,它们都具有象征特征。萨满本身从来不把这些当作艺术,在萨满的仪式性表演活动中只有神圣可言,绝无“戏言”。而研究者则发现,萨满教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萨满教的活动,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既戏剧表演、舞蹈和造型艺术”。①但是,无论是对萨满本身而言,还是就仪式性表演来讲,萨满教的所有造型和声态都是功能性的,有象征意义。把萨满教视为“各种艺术的综合体”仅仅是我们的见解,而不是萨满的看法。不可否认,萨满教的仪式性表演不可能脱离静态的造型形式和动态的声态形式而存在,而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就其造型和声态形式而言,的确蕴涵着艺术发生的种种因素。
笔者在前面若干章节中探讨了与萨满教造型有关的岩画、石人、鹿石的功用问题,在此不再赘述。现在仅讨论萨满在仪式性表演中使用的画像、神偶、服饰、法器等造型和声态系统的问题,因为这些造型和萨满神歌抄本还在锡伯族民间有所遗存,这也就成了最有力的实物例证。锡伯族萨满教延续时间最长,20世纪50年代前仍有萨满的仪式性表演活动,而最后一个女萨满则到20世纪70年代才去世。
锡伯族的萨满画是萨满在举行祭祀祖先、上刀梯和跳神治病仪式时悬挂的神圣物,用毕即入匣收藏。萨满画按其绘画内容和功用大致分为三类:群体神像图、萨满画像和动物神灵图。自20世纪初俄国人克洛特科夫在塔城发现锡伯族萨满神像图后,20世纪80年代锡伯族学者又在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现同一内容的群体神像图。这是一种布绘图像,其画面自上而下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最上一层画面为彩云、日月和“依兰恩杜里格格”(三位神姐)和“顾兴阿玛法”(男祖神)。这些祖神周围是虎、狼、狐狸、蛇、鹿等动物精灵。第二部分是各具神态的岱木林、阿玉鲁、额依嫩德德祟神、艾土罕、善琦、达玛法、阿里玛法、玛法默尔根、萨满玛法、着勒玛法等男女神灵形象。第三部分为合掌或单手祈祷及举杯为上刀梯者助威的近10位男女神灵,如张纳、着青额、纳松额、吴凌额、齐发罕珠、色楞芝等。第四部分为刀梯两侧的两位骑马萨满。第五部分画面最下端绘有供桌,上置燃香的香炉。供桌右侧为三位手持神鼓的萨满,左侧为一条白牛,后面为直入云端的刀梯,梯顶站立着萨满。这是一幅供上刀梯仪式时使用的画像。上刀梯仪式是锡伯族萨满教的独有仪式,举行这种象征仪式的动机是:“一是告诉人们通达神界并非易事,只有踏上实实在在的‘刀梯’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并且暗示,不会人人都能做神界和人间的使者;二是显示萨满真有通达神界和治病救人的本事;三是为了区别有真‘本事’萨满和无能萨满。”①画像中的众神灵既有萨满祖师、祖先神,也有瘟神、动物保护神等,甚至还出现了门神、灶神等。萨满在举行上刀梯、跳神治病等仪式时总是在其祷词中呼喊众位神灵,请神助佑其仪式成功。萨满画像是绘有萨满形象的图画。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幸福乡锡伯族民间发现的一幅萨满画像画面为:一位头戴三只鸟装饰神帽、身着萨满服的萨满坐于方凳上,左手高举绘有蛇形图案的萨满鼓,右手举至胸前微握,神像旁是一跪着的男子,面向萨满。萨满下面绘有水波纹,其上是一条飞龙。这类画像显然是哈拉(姓氏)或莫昆(家族)萨满祖神形象,是专供哈拉或莫昆后代萨满祭祀时使用的,有时在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悬挂,以便从祖神处求得神力。
动物神灵图是每一个萨满专用动物精灵的形象画像。动物精灵在锡伯语中称“巫出固”,实为萨满的动物保护神,每一个萨满均有自己的“巫出固”,有的是雕神,有的是虎神,有的是狼神。“巫出固”作为萨满的助手在跳神治病时助佑主人与病魔搏斗成功。在萨满“巫出固”中,虎神是女萨满保护神中的主神。由于萨满画是功能性的,因此并不要求形似,也不可能形似。因为萨满画都出自民间画师之手,也有的是萨满本身绘制的,就难有很高的绘画技巧,而且作为仪式中的萨满画仅仅是个象征物,并不需要神形毕肖。由于萨满教仪式分为家祭仪式和公众集会仪式,萨满画也有所不同,家祭仪式中的萨满画可能是本族先辈萨满或祖先的形象,而像上刀梯仪式是一种广场式的公众集体仪式,所以悬挂的就是绘有众神的上刀梯图。萨满画中的人物服饰明显有时代特征,如一幅绘于清代的萨满画中的祖先神著的是清代官服。
作为萨满教中的祖神和动物精灵形象不仅出现在画像中,也以神偶等雕塑或缝制形式出现,而且还有些是幻想中得来的怪异形象。在锡伯族民间时常可以见到本族祖先神偶,多为布帛制成的群体神偶。
一般是用布帛剪出人形,内填充棉花等物,再绘出五官。有的还著衣装,或用布裹住全身,只露头部。祖先神偶有单个的,也有夫妻双偶,还有三人以上的群偶,虽然人数不等,但姓氏祖先神偶的形制大体相似。人形偶也有皮制、木雕、金属等材质。有些人形偶的五官特征并不突出,只是在脸部嵌上两个纽扣表示眼睛,与人物实像相去甚远。动物神偶有些是以现实中的动物形象进行造型,多为雕塑,如木雕、金属雕塑等,但也有些是怪诞的形象,用布或皮制作的这些怪诞神鹰之类是萨满心中的“镜像”。动物神偶是萨满的助佑精灵,也可能是氏族的保护神。锡伯族萨满曾使用一种铜质的鹰形动物神偶,是栖息式鹰的形象,用两半鹰形范模合在一起浇铸而成。其背部和腹部均有挂钩,背部挂钩用以系绳,腹部挂钩挂一块红布,在萨满跳神治病等仪式中挂在供桌前,以便治病时助佑萨满发挥神力以达疗效。萨满教中神偶的产生和神形的确立,都与萨满本身的生理、心理特质有关。在一般人看来,萨满都是一些与常人不同的人。成为萨满的先决条件,不是小时经常生病,就是成年后突然出现癫狂之症,或者是好动、爱激动者。特别是患癫狂之症很重要,是存在生理缺陷者。就心理因素而言,萨满的神圣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幻像的产物,因此这些神圣形象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创造者的信仰,特别是那些怪诞的神偶尤其如此。而“神偶中一些怪异形体的形成多源于梦,并非萨满任意而为。一般认为,萨满在梦中见偶体,梦中引偶降世,然后依梦中所得幻体,遵其形谨制偶体,不得疏漏、简率。萨满教观念认为,梦与灵魂密不可分,做梦即浮魂的外游,‘无魂无梦,无梦无形’。其实质是心理幻像的产物”。①一般人都可能在梦境中和记忆中出现一些视觉形象,萨满不过是在千百次的“修炼”中使心理形象更加“完形”而已。
萨满神服、神帽和法器都是萨满化形体为神圣的象征。萨满神服和神帽都是萨满形体重要的组合部分,它们的共同功能有二:一是在萨满的祭神驱邪神物中,神服和神帽是核心的祭祀象征,本身就代表特定的神祗;二是它们又是每个萨满自身的宗教崇拜和信仰的传承物,汇聚了为他服务的超世神祗、精灵和被他征服后甘心为其效力的恶魔精灵,全附栖在神服和神帽内。①但是在使用中神服和神帽又有其各自的特殊功能。由于萨满神服既是神祗的象征,同时又是某些神祗的形体寓所,所以它是法力和凝聚体的综合象征;萨满神帽则是萨满感应信息的主要渠道,它相当于神树。锡伯族萨满早期神服、神帽的实物资料阙如,现在能见到的是百年左右的遗物。男萨满神服由短衣和裙组成。短衣为对襟,高领,布纽扣,多选黄、蓝等颜色布料制作,下摆开衩,前襟、下摆、袖中处补缀有花边;而神裙则由内衬围裙、中层多根麻绳和外包的各色布条缝制而成,布条组成的飘带上绣有各种动物、花草纹饰,裙下摆有垂穗,飘带片数有21条、23条、27条等之分,这与萨满教对宇宙天地的分层观有关。实际上,每个哈拉的萨满神服是各不相同的,而且越是经历多次神祭的神服越是法力无穷。神服的制作、使用、收藏都有严格的规仪,甚至成了萨满的专利,一般人不能染指。萨满服早期是皮制的或干脆是披兽皮,而过渡到布帛制神服不会很早。现在在新疆伊犁锡伯族民间保存下来的神帽由铁制帽圈、帽边、帽顶、铜镜、帽穗及衬里组成。帽圈为圆形,帽边由上到下成十字形交叉,卷成半圆形,四头用铁皮固定在帽圈上。帽顶由3块交叉铜片组成,固定于帽边顶部。因帽顶铜片六边向上翻卷成半圆形,形似莲花,锡伯语称为“伊尔哈”(花)。花边装饰有4个铜铃,帽前嵌有小铜镜。帽后垂穗为5根或10根,是红、蓝、黄、绿等色组成的布制飘带。曾在辽宁锦州市义县罗家屯乡锡伯族民间发现一顶铁制神帽,铁制帽梁上拥成的信息树上顶端为鹰的形象,锡伯语称“安切兰”,是萨满的动物精灵之一。鹰鸟神帽是锡伯族萨满较典型的神帽。对萨满而言,“只要有神祗或其他异兆出现,就马上通过神帽传递于萨满神帽上的精灵和肩鸟,迅传萨满感应,使萨满永立不败之地”。②申帽对萨满来说,更易于与神相交,也就比神服更有特殊地位。
锡伯族萨满的法器多是发光、发声或激击器,有多重功能。“哈准”是萨满挂于腰间的铜镜,为圆形、光面,镜背有铜钮,穿皮绳用。一个萨满的“哈准”多达18个,举行萨满仪式时发光和丁当作响。“托里”是护心镜,佩于胸前,正面光洁鉴人,相当于“照妖镜”。萨满鼓,锡伯语称“伊木秦”,为圆形单面皮鼓,面上绘有动物、植物等纹饰。每个萨满都有三面神鼓,一面自己使用,另两面由副手使用,跳神时用以控制跳动舞步的节奏。神矛、神鞭也是萨满仪式中的器具。神矛柄为木制,矛头为铁制,矛头与柄结合部系有红、黄等色布飘带,并系有若干小铜铃。神鞭,杆为木制,鞭为牛皮编制。所有这些法器发出的响声和光亮以及进击在萨满跳神治病仪式中都是象征性的,萨满一方面在铜镜撞击和击鼓声中有节奏地舞之蹈之,增强跳神效果;另一方面以响声、光亮和进击动作吓退病魔,以达疗效。当然护心镜也象征萨满得到神祗护佑,以保证神力有效。由于萨满仪式常常在夜间举行,于是“萨满服饰和法器的设计实际上也是为了去加强视觉的心理幻想的产生”。①
作为萨满教声态系统的萨满歌和萨满舞都是萨满通神的手段之一,也是萨满神力的表现。就其特征而言,对萨满仪式来说,“舞蹈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要通过高度兴奋的动作的忘形失神去恢复与神秘力量的联系;装饰往往有护符的意义,其功效不在于美而在于防止巫术的伤害;歌唱则与咒语相关,因此重要的是记住歌词而不是懂得歌词真正的意义,意义就在声音里面。”②但是随着萨满的消亡,萨满舞成了程式化的民间舞形态,萨满歌也成了凝固的文本,而萨满仪式性表演中的歌舞文化情境再也不可复现了,锡伯族的萨满舞、萨满歌也是如此。所谓的萨满舞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中的处在迷狂状态的激烈跳动动作。最早描述阿尔泰语系民族萨满跳神治病仪式中萨满舞的是拉德洛夫,时间是1860年7月。他描述的是哈萨克族的巴克西跳神治病的情形:“巴克西一般以单调的伴唱拉琴表演(哈萨克巴克西的表演不起任何作用)。然后拿起棍子挥动着乱跳乱吵。在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巴克西一起跳,一个拉琴,一个又是挥棍又是跳。也有的巴克西跳神什么器具都不用。跳神的时候,巴克西也和萨满一样会神智昏迷,所以也得由几个人护守以避免发生意外,因为巴克西在民众中不再有什么伦理基础,所以看来巴克西比萨满更努力以自己的举动引起大家的恐惧感。所以他跳得非常疯狂,可怕地转动眼睛,咬牙,如疯似狂蹦跳奔跑、踢脚。他们入神之后所耍的把戏,使哈萨克人每每提及无不惊讶不止。”①巴克西至多是巫医,并非真正的萨满,他们的动作也不过是模拟萨满的动作,但它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萨满舞的基本形体动作特征,这比现在民间表演中的“萨满舞”多少有些真实感。从一些资料分析,早期的萨满舞可能是狩猎巫舞。因为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中,身着神服,头戴神帽,一手持神鼓,一手拿神矛,在腰束铜镜丁当响声伴奏下忽而在院内横冲直撞,忽而跳出窗户,忽而又在房顶举目远眺,然后又跳下来,握紧短矛不断猛刺,并从口中发出“哈嘎,哈嘎”的喊声,越跳越兴奋,又发起狂来,最后昏迷过去,以示与妖魔搏斗成功。它的原型显然是原始的狩猎巫舞。
萨满歌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是伴以各种舞步动作的,也就是说,萨满歌与萨满舞是歌舞为一体的。我们现在所见的锡伯族萨满歌是尔喜萨满于光绪十年十一月(1884)手抄的,是神歌的手抄文本,无从窥知其曲调,因此也就只能依据文本进行分析了。手抄本的《萨满歌》分为两册,第一册为《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第二册是《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由九部分构成,即《学萨满时的祷告神歌》、《祈请托里神歌》、《祈请金刀梯神歌》、《萨满端坐凳子之上哀求神歌》、《萨满立在门前祈祷神歌》、《萨满为治病事求告神歌》、《萨满设坛呼唤山羊之神歌》、《请神歌时二神呼唤神歌》和《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神歌》。《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影》有一副标题为《萨满为治病事送三个白色巫尔虎之神歌》,显然是萨满跳神治病时按跳神治病仪式的顺序唱的神歌。从《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的九个部分内容看,均是萨满徒弟学萨满的范本,内涵十分丰富。一向是口耳相传、秘不示人的神歌,露出了它的真容,也可以使人们体味其原始意蕴。萨满歌非一时一世之作,是众多萨满在长期的积累中不断加工的结果,虽然神歌内容都有不同时代的烙印,但原始文化形态的踪影仍能窥见。如第九部分《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神歌》有这样的内容:
行行复行行,
走到第二道门前,
有一只凶猛的公虎,
挡住这大门,
不让进去。
如何进去呀?
师傅道:
在九重天外的祟神们呀,
把这属龙的孙儿,
〔第二道门〕引进里边吧!①
这里的公虎挡道是源自古代氏族萨满顺应人们防范老虎威胁树立虎神,用祈祷方式避祸的心理需求的反映。在萨满神话观中,天是多层的,萨满要与天神沟通,必须越过7道或9道障碍。“在萨满神话中每层天就有1道障碍,5、7、9的障碍数和天的5、7、9层数显然是一致的”。②而“卡伦”是根据清代所设台站、哨卡创作的意象,有“关卡”之意。《祈告、祝赞、祷告之神歌》和《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囊括了锡伯族萨满文化的全部内涵:诸多神祗、精灵,上刀梯、跳神治病仪式,萨满神帽神服和法器等物化形式,甚至还涵盖天文地理、疗术机制和神话观等,因此神歌也可以称之为锡伯族萨满文化的综合体。从演唱形式看,既有萨满本人的独吟,也有师徒俩之间的对唱,还有领唱助唱等形式。如第一册中的《萨满立在门前祈祷神歌》是萨满本人挨家挨户跳神宣喻的独自吟唱;而《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神歌》则是两人间的对唱;《萨满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是由萨满领唱,众人应合的形式,类似有领唱的合唱。在“合唱”中,每一句有实际意义的歌词由萨满本人吟唱,众人以衬词应合:
在方正的屋子里呀环—达里,
有环绕的声息呀伊纳昆—达里,
侧耳倾听呀环—达里,
不是环绕的声息伊纳昆—达里,
是威武的萨满们的环—达里,
霍硕特尔之声呀伊纳昆—达里。
在每一句中前为萨满有意义的吟唱,后为众人无意义的和声衬词。在跳神治病神歌中,尽管每一节中萨满吟唱的歌词是按跳神治病顺序进行的,但衬词都是相同的,即在各节中重复出现。这样,不仅增加了演唱的节奏感,而且在一种助唱的“强声”氛围中祛除病魔,以达到神奇的疗效。早期或一些萨满歌并无歌词,“乐谱极其简单,由一个一再重复的短乐句构成。此短乐句几次重复之后,萨满突然停止歌声,并发出连续的拖长的歇斯底里的叹气,此种叹气声好像‘啊,呀,卡,呀,卡!’之后,他又重新歌唱起来,为此,他要尽力地深呼吸,以便肺部有更多的空气,并使第一个音符最长”。①萨满歌舞同萨满画、萨满神偶、萨满服饰、法器一样均被萨满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萨满神歌的神语神音只在祭祀、跳神等仪式中吟咏,萨满之间是口耳相传的,并且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萨满歌的曲调、旋律也是经过多代萨满吟唱逐渐完善的。萨满神歌的歌词是由萨满背下来的,也有些是即兴演唱的歌词,“这意味着萨满虽谙熟传统的曲调和旋律,但还必须在其能召请之神的帮助下创作诗歌文本。在节日场合使用诗歌文本,不仅将祭祀氛围提高到日常状态之上,而且允许参加者参与这种艺术体验”。②无论是萨满本人,还是广大参与者都能各得其所,这正是萨满歌的存在价值所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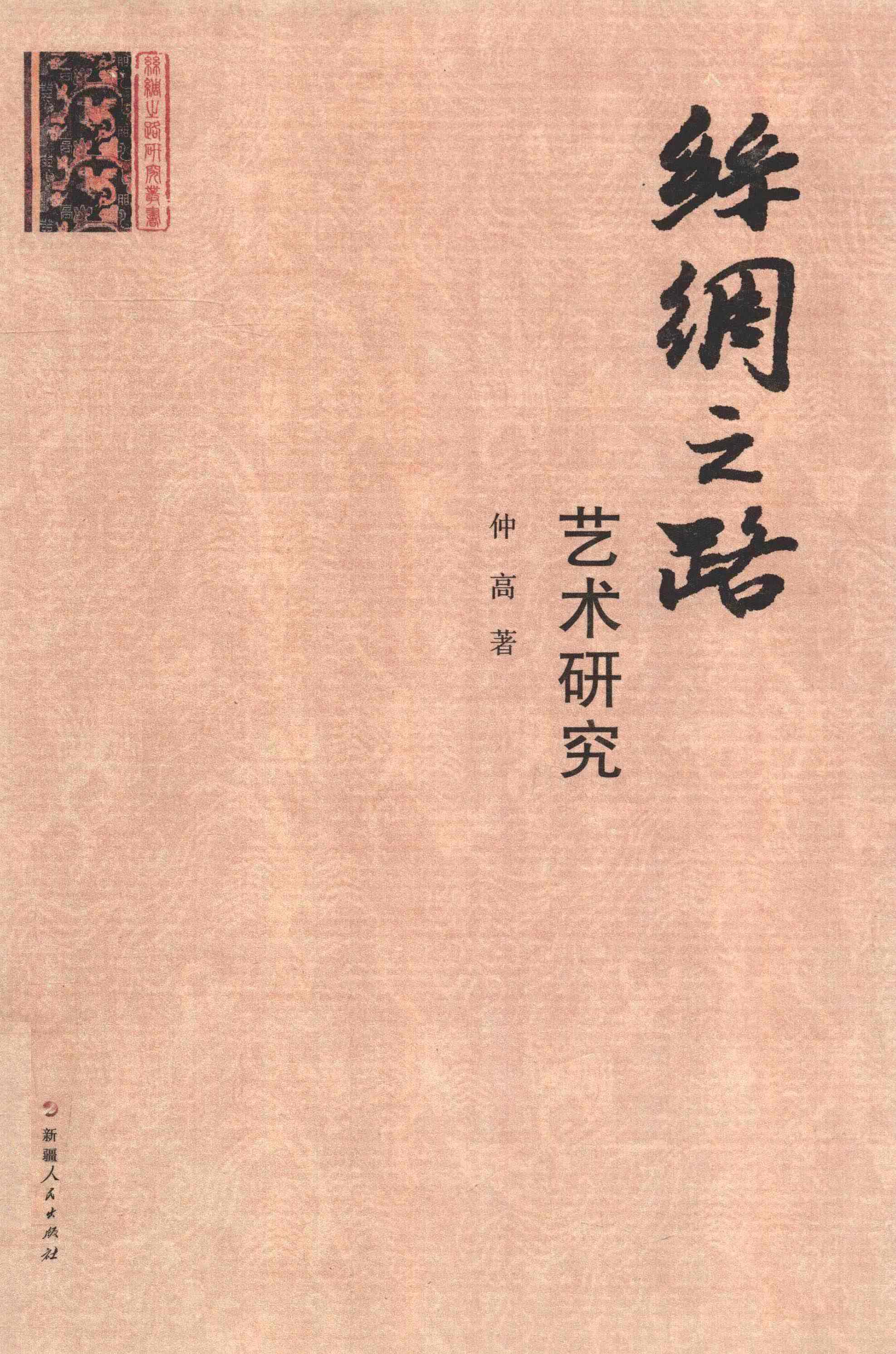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