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锦唐绢的艺术品格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40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汉锦唐绢的艺术品格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8 |
| 页码: | 192-199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汉锦唐绢的艺术品格情况包括丝织物的保存与丝织物颜色;丝织物刺绣等。 |
| 关键词: | 汉锦 唐绢 艺术品格 |
内容
尽管人们把古代贯通欧亚的陆路通道冠名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等,但这些名称远不如“丝绸之路”久负盛名。这条自我国长安起始,途经西域广大地区,曾远达罗马、叙利亚的陆路丝绸贸易通道虽然存在了一千多年,但作为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专用名称——丝绸之路,则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外学者不仅把丝绸之路看作是古代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而且还把它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不争的事实是,各种文化的传播、交流、辐射,最初的确来自丝绸贸易,中国的丝绸成了不同文化背景民族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它早已超脱了其有形的物质形态,而深入到丝绸之路周缘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诸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升着整个人类的文明程度,因此,丝绸之路也具备了文化符号的功能。历史学家把古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叙利亚总督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败在安息人手下的原因归罪于安息人那令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斓的军旗上,安息人的军旗正是用中国的丝绸制作的。古罗马人正是在卡尔莱战役中初次接触到中国的丝绸:“丝绸比先前所有的纺织品都更加绚丽多彩,因而很快为罗马社会所熟悉。叙利亚战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织物,它可能是在几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到手的。卡尔莱战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恺撒在罗马祝捷的时候,借机向罗马臣民显示夸耀各地所展现的奢侈品,即为他的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奉献的一批丝绸织物。因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惊诧赞叹。..在卡尔莱战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①被西方人称为“赛里斯”的中国丝绸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仍然还是欧洲妇女追求的时尚,妇女们一改十五六世纪追求单色呢绒料的时尚,“而到了十七世纪,又掀起了抢购‘草原式图案’缎纹织物和‘印度之花’织物、‘土耳其式’的塔夫绸、‘米兰式图案’织物的风潮。到了十八世纪,丝绸工业又受到了追求大幅图案为时髦之风潮的刺激,这种图案形成了一幅幅真正的图画(其设计图纸是被当作绝密资料加以保护的),带有裙环的那种宽大裙子的式样需要特别宽幅的丝绸布。..终于在欧洲首次出现了汉人式的图案:如佛塔、竹桥、人像等等。”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丝②绸服饰的款式、图案形成不同的审美追求,但丝绸文化的魅力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
丝绸,这种令古罗马人目瞪口呆、惊诧赞叹的织物几乎不进入艺术史家的视野,虽然用丝绸缝制的服饰,人们宠爱有加,但它不如青铜器、瓷器那样成为学者们眼中的艺术研究对象。像格鲁塞的《东方的文明》、巴赞的《艺术史》这样的艺术史名著也只字未提丝绸工艺、图案艺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其实“纺织物品通常经过某种加工以增进它的美感,..在布料的装饰方面由世界各民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风格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习惯。例如,主题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象征性的,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往往来自他的信仰和理想”。③新疆出土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汉唐时期的丝织品或许可以大开人们的眼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梦幻般的汉锦唐绢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判断。
由于丝绸织物不宜保存,在世界各地极少有出土,只是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由于干旱少雨,才在汉代以来的墓葬中发现了品类众多的丝织物。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无论是丝织物的品类、织法、纹样、色彩,还是主题、题材、装饰手法都印证着东西文化交融、互渗这一事实。人们发现,中国丝绸西传的结果,竟派生出波斯锦、粟特锦、叙利亚丝织品以及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的织物等。这种东传西渐的踪迹在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及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汉唐丝织品中都能寻觅到。
新疆出土的汉代至唐代的丝织物与丝绸之路走向吻合,也与汉族居民在西域的分布合拍。汉唐丝织品的出土地点几乎全集中于丝绸之路的南北道。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发现了包括锦、绮、罗、各色绢、缣及刺绣等汉代丝织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则出土了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这里是麴氏等汉族政权高昌国和唐西州的所在地,丝绸生产和贸易都曾盛极一时,仅出土的丝织品就有锦、绢、绮、绫、〓、染缬、刺绣等。在某一区域出土品类各异、色彩缤纷的众多丝织物,非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莫属。仅从这些丝绸织品东西合璧的图案纹样就不难窥见这座古代丝绸博物馆的风采。如果从主题着眼,我们可以将汉唐时期的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分为吉祥图案和祥禽瑞兽图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汉锦主题基本属于吉祥文字纹锦,在满幅变幻莫测的动植物纹样中,嵌织有隶书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韩仁绣文宏吉子孙万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长乐明光”、“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这与人们普遍存在的“祈福赐祥”心理不无关系。祥禽瑞兽纹锦常见的有“龙凤纹锦”、“鱼禽纹锦”、“对鸟对羊树纹锦”、“飞风蛱蝶团花锦”、“联珠对鸡纹锦”、“联珠鸾鸟纹锦”、“联珠鹿纹锦”等,联珠纹主题的纹锦多见于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高昌地区。假如从题材去分析,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文字纹都久盛不衰。据研究者统计,仅楼兰、尼雅所出的东汉锦纹样就有二十余种。①其实,自汉至唐代西域丝织品的纹样远比这要多得多。假如从构图思路看,汉唐时期西域丝织物的纹样严格遵循着对称平衡的原则,这几乎是装饰工艺的不二法则。但对称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布局的变化,上下对称、左右对称、中心对称、边缘对称等旨在追求严谨中的变化。动物纹样、植物纹样、文字纹样、几何纹样之间的有机搭配,也在追求一种各纹样间的对称平衡效果。如果着眼于色彩、工艺,就能发现其色彩的绚丽和编织技巧的娴熟。汉代锦、绮、绣等丝织品的色彩就有藏青、宝蓝、天青、海蓝、湖蓝、墨绿、葱绿、粉绿、绛紫、绛红、褪红、深棕、沉香、驼色、白色、绯红、黑色等多种。北朝至唐代高昌(西州)的锦、绮、绫、印花绢、缦、缣、纱、罗等的色彩有褪红、朱红、海蓝、绢黄、藏青、海蓝、天青、葱绿、湖绿、草绿、叶绿、绛红、橙红、银红、棕色、白色等。在色彩上汉唐之间有承袭关系,但也明显有创新,如唐代织锦除沿袭汉代以深色为地外,大多以白色或浅色为地,用绛、绿、青、黄等色显花,花纹间色彩互换富有变化。丝绸品的工艺从平织、平纹重组织、显花起绒圈重组织、经线显花、纬线显花、刺绣到印花法都出现,仅印花,唐代就有蜡染法和绞缬法。汉唐西域丝绸品就纹样而言,纵向流变和横向融合都呈现出创新和互渗的特征。“花纹方面,汉代那种宽带式花纹布局,到了唐代改为孤立的花纹元素散布全幅。花纹母题则西方式植物纹盛行,包括忍冬纹、葡萄纹等。波斯萨珊朝式的那种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唐代很是盛行”。①联珠圆圈内是对鸟、对兽图案。但这种合璧并非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而是各种文化在长期接触中,从冲突、碰撞走向融合的结果,它虽脱胎于原来的文化,但并非原来的模样,一经消化吸收和文化整合后,成了本土化的艺术品种。盛唐气象就是指其化解东西文化的大气,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岂能例外。
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是汉锦的主要发现地。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1980年在楼兰城郊古墓群孤台墓地就出土汉锦53件;1995年在尼雅遗址编号为95MNIM8号的墓地出土的汉锦织物10多件,其中就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1983~1995年在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中,出土包括织锦、绢类丝织物33件。汉锦上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是纹样构成的基本特征。楼兰出土的一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褐色地,黄、蓝二色里花,经锦。变体云纹和攀枝叶蔓中夹瑞兽,瑞兽间织隶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吉祥语”。②而另一件1995年出土于尼雅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重平纹经锦,平挺厚实,图案题材新颖,有虎、龙、避邪、仙鹤、孔雀、瑞兽图案,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③山普拉出土的丝绸物多为死者的帽、衣、裤、护颌罩等服饰类,有锦、绢、缦、绮等。其中织锦有两件,一件蓝地,显黄色菱格、曲线、点纹;另一件有幅边,绛色为地,宝蓝、米黄、粉绿和白色五种颜色显花。①营盘出土的属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织锦是以“吉祥云纹、祥禽瑞兽为主体的图案。有夹织立禽和隶书‘登高’、‘寿’、‘右’等文字锦,也有图案横向排列的卷草纹锦和方格纹内相同的瑞兽纹锦”。②西域以织锦为代表的汉代丝织品,“其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纹饰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现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其间穿插种种吉祥用语”,③具有汉文化特征。许多祥禽瑞兽是有象征寓意的,如对鸭图案中的鸭子意取“压子”;老鼠象征长寿;独角兽——避邪有祛邪除凶的寓意;龙凤象征吉祥等等。汉代丝织品中出现的这类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纹饰是一个时代思想与信仰的折射。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更现实,也更务实,“显然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世俗化,成为一种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就是追求生命的永生。而现实生活中的‘富贵’与子孙的‘繁衍’,却成了更现实的生活中‘幸福’,人们的渴求日益现实,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字样就是明证,人们日益实用的生活观念正是在这里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④当汉朝统一西域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思想、信仰上的趋同性已深深扎根于西域各地居民的心中,所以才会在那么多墓葬中出土如此众多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的丝绸织物——生用死殉,追求着生命的永生和一生的“富贵”,并期望“幸福”庇荫子孙后代。就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些我国古代星占术上的占辞用语也出现在织锦上,也可以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祈语,反映了西域各地居民同中原汉民族同样追求吉祥昌盛的良好祈愿和朴素的感情。
从北朝到唐代,西域丝织物的产地主要在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含西州)等地,但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物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工艺技术和图案风格。在众多出土的丝织品中织锦和绢(染缬)最为普遍。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的织锦是有差异的。6世纪前的织锦图案单位直行排列,作横幅相间的祥瑞兽纹,形成瑞兽纹锦、狮纹锦等,图案内容和布局与汉锦相似,但动物形态或立或卧,都比较稳定,是汉锦风格的继续;而到了唐代,有两类图案的织锦居于主导地位:一为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图案,二为联珠对禽对兽图案。⑤植物纹样图案织锦品类多,纹样多变,其中的“宝相花斜纹经锦”的纹饰图案是唐代汉地的主流图案。魏晋以来,中原曾盛行在金银器、铜镜上镶嵌珠宝类花,在中心花蕊及花蕊和花瓣交接的地方镶嵌以珍珠和宝石,图案上用佛教艺术的退晕色方法,以放射对称的格式,组成盛开、半开、含苞的花与花叶等富丽堂皇的团花,谓之“宝相花”。到了唐代,宝相花图案又出现在织锦图案中。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件唐云头锦鞋,其鞋面就是宝相花图案:“系用宝蓝、墨绿、橘黄、深棕四色在白地上织簇八中心放射状图案花纹的斜纹经锦,以中心部分,为六个花瓣组成的圆形朵花,围绕着中心朵花则是簇八放射对称的如意勾藤,在对称如意的地方,缀以花蕊及花叶。”从花的图案看,似是雪花的变形。宝.①“相花斜纹经锦”可能就是唐代的“瑞锦”,有“瑞雪兆丰年”、“雪花献瑞”的象征寓意。
阿斯塔那出土最多的是联珠对禽、对鸡、对兽图案的织锦,统称为联珠纹样织锦。联珠纹样是萨珊波斯的传统图案。3世纪兴起的萨珊波斯王朝流行一种装饰性程式化倾向的纹章艺术,出现在织物和金银工艺品中。“其上即根据此种风格表现着为求装饰效果而多少予以程式化的幻想怪物:头和前爪似猫而翼和尾部如‘开屏’孔雀的‘龙孔雀’;或武士骑在半狮半鹫的‘格力芬’或带翼的狮的背上,和其他‘格力芬’作战;或完全对称的成对野羊或雄狮,各举一前足对面而立;或如迦勒底—亚述所喜好的题材,即程式化的狸形野兽吞食着同样程式化的鹿类动物”。②在这些织物中,往往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圆圈内常填以对马纹、对鸟纹和对鸭纹,也有填以波斯式的猪头纹和立鸟纹。③但是吐鲁番出土的联珠纹锦并不是波斯的工艺品,而是根据西域商人订货需求由汉人织作的织锦,其产地是蜀地,因此,这类织锦也称为蜀锦。“联珠禽兽纹斜纹纬锦有组织细密的精品,如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也有像联珠戴胜鸾鸟纹锦那样组织粗松的制品。这种联珠禽兽纹斜纬纹锦是这个时期墓葬中最常见的纹锦,发现的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显然,这意味着它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另外,我们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其他间接资料也可以知道这种有别于传统的图案,当时在我国内地已较为流行”。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件联珠“胡王”锦。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织锦采用倒置循环提花法织成上下对称的图案,米黄色地上有橘红、绛红色显花,在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手执长鞭,深目高鼻,花环之间饰以复合忍冬四叶纹。它显然是萨珊波斯式的联珠动物纹样织锦,但所织“胡王”汉字表明它确系汉地产品,估计是为九姓昭武或萨珊波斯王族专织的。在丝绸之路中端的高昌出现,可能是商品交易的结果。植物纹锦中的忍冬纹、葡萄纹也是西来的产物,但也很快被唐代织锦所接受。
唐代高昌、西州丝织物以绢类为大宗。绢也称“素”,本为一般平纹织物,经纬密度大致相等,除本色外,染成大红、粉红、墨绿、叶绿、鹅黄、绛紫、茄紫、翠蓝、湖蓝、藕荷等颜色图案的称为染缬,其染织方法又有绞缬、夹缬之分。当然,染缬也用于缦、缣、纱、罗、棉布等工艺上,这些染织物也统称印花丝织物。绢类丝绸物的绞缬法有两种:一种是将谷粒大致匀称地包在织物上,用线扎紧,染色,晾干后,拆去扎线,即现出遍地大小相等的菱形圈花纹;另一种是将织物折成连皱,用针线穿过,然后将线抽紧钉牢,染色后晾干,拆去穿线,即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①夹缬的方法是将织物绷紧,夹于镂花夹板中间,涂以蜡,再解去夹板,染后晾干,剥去蜡即成,因涂蜡处未吸收染色,即显出花纹。②夹缬法就是通常所称的蜡染法。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染缬织物看,主要以盛唐为主。墓葬出土的数件夹缬绢,一染绛地花云,一染棕地散花,一染土黄地花云,都绘制工致,浸染均匀,是唐代蜡缬的精品。③唐代流行的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纹样就与这种染缬工艺有关。夹缬法不仅适宜于染制植物花卉图案,还可以印染较复杂的人物、动物、山石树木在内的组合纹样。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狩猎纹印花绢片就属此种。此为平纹印花绢织物,纹样内容为,在深绿地上显出粉绿的狩猎图案:骑马的猎手飞马张弓射狮,猎犬逐兔,猎鹰追飞鸟,天上流云,地下山石树木,图案呈上下对称,有强烈动感。唐代夹缬绢上的狩猎图案与5世纪的骑士(狩猎者)对兽纹锦图案可能有渊源关系。另一件纹锦同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纹锦黄地,以深青、浅蓝、浅黄色显花,以数个相切的圆环为图案骨架,其内饰狩猎者射鹿、对象、对狮、对驼等纹样。圆环之间填对马和忍冬纹样,圆环相切处又以仰莲相缀。除联珠纹鸟兽纹样流行于高昌等地外,还有一种人像、动物、树木等组合式纹样同样流行,不过它的主题是骑士、狩猎者等英雄形象与狩猎对象关系的表现。这些纹样是九姓昭武和萨珊波斯常见的纹样。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类题材还源自西域游牧民族的狩猎生活,虽然高昌、西州作为农耕民的汉族居民并不狩猎或根本无猎可狩,但与其关系密切的突厥人确实是典型的狩猎、游牧民族。不过,其主要影响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和萨珊波斯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萨珊波斯艺术的生命力超过了王朝生存的年代,直到九世纪在中国北方还有余绪可见。..由于进入中国新疆的一些画师来自伊朗东部或吐火罗地区,所以在画风上也必然带来波斯绘画的格调”。①高昌地区就有粟特人的聚落。汉锦唐绢正是在吸收、化解各种艺术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品格,这是它的大气,也是它的力量所在,这正是流光溢彩的中国气派,西域的汉族居民也受惠于此。
丝绸,这种令古罗马人目瞪口呆、惊诧赞叹的织物几乎不进入艺术史家的视野,虽然用丝绸缝制的服饰,人们宠爱有加,但它不如青铜器、瓷器那样成为学者们眼中的艺术研究对象。像格鲁塞的《东方的文明》、巴赞的《艺术史》这样的艺术史名著也只字未提丝绸工艺、图案艺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其实“纺织物品通常经过某种加工以增进它的美感,..在布料的装饰方面由世界各民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风格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习惯。例如,主题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象征性的,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往往来自他的信仰和理想”。③新疆出土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汉唐时期的丝织品或许可以大开人们的眼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梦幻般的汉锦唐绢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判断。
由于丝绸织物不宜保存,在世界各地极少有出土,只是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由于干旱少雨,才在汉代以来的墓葬中发现了品类众多的丝织物。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无论是丝织物的品类、织法、纹样、色彩,还是主题、题材、装饰手法都印证着东西文化交融、互渗这一事实。人们发现,中国丝绸西传的结果,竟派生出波斯锦、粟特锦、叙利亚丝织品以及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的织物等。这种东传西渐的踪迹在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及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汉唐丝织品中都能寻觅到。
新疆出土的汉代至唐代的丝织物与丝绸之路走向吻合,也与汉族居民在西域的分布合拍。汉唐丝织品的出土地点几乎全集中于丝绸之路的南北道。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发现了包括锦、绮、罗、各色绢、缣及刺绣等汉代丝织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则出土了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这里是麴氏等汉族政权高昌国和唐西州的所在地,丝绸生产和贸易都曾盛极一时,仅出土的丝织品就有锦、绢、绮、绫、〓、染缬、刺绣等。在某一区域出土品类各异、色彩缤纷的众多丝织物,非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莫属。仅从这些丝绸织品东西合璧的图案纹样就不难窥见这座古代丝绸博物馆的风采。如果从主题着眼,我们可以将汉唐时期的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分为吉祥图案和祥禽瑞兽图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汉锦主题基本属于吉祥文字纹锦,在满幅变幻莫测的动植物纹样中,嵌织有隶书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韩仁绣文宏吉子孙万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长乐明光”、“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这与人们普遍存在的“祈福赐祥”心理不无关系。祥禽瑞兽纹锦常见的有“龙凤纹锦”、“鱼禽纹锦”、“对鸟对羊树纹锦”、“飞风蛱蝶团花锦”、“联珠对鸡纹锦”、“联珠鸾鸟纹锦”、“联珠鹿纹锦”等,联珠纹主题的纹锦多见于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高昌地区。假如从题材去分析,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文字纹都久盛不衰。据研究者统计,仅楼兰、尼雅所出的东汉锦纹样就有二十余种。①其实,自汉至唐代西域丝织品的纹样远比这要多得多。假如从构图思路看,汉唐时期西域丝织物的纹样严格遵循着对称平衡的原则,这几乎是装饰工艺的不二法则。但对称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布局的变化,上下对称、左右对称、中心对称、边缘对称等旨在追求严谨中的变化。动物纹样、植物纹样、文字纹样、几何纹样之间的有机搭配,也在追求一种各纹样间的对称平衡效果。如果着眼于色彩、工艺,就能发现其色彩的绚丽和编织技巧的娴熟。汉代锦、绮、绣等丝织品的色彩就有藏青、宝蓝、天青、海蓝、湖蓝、墨绿、葱绿、粉绿、绛紫、绛红、褪红、深棕、沉香、驼色、白色、绯红、黑色等多种。北朝至唐代高昌(西州)的锦、绮、绫、印花绢、缦、缣、纱、罗等的色彩有褪红、朱红、海蓝、绢黄、藏青、海蓝、天青、葱绿、湖绿、草绿、叶绿、绛红、橙红、银红、棕色、白色等。在色彩上汉唐之间有承袭关系,但也明显有创新,如唐代织锦除沿袭汉代以深色为地外,大多以白色或浅色为地,用绛、绿、青、黄等色显花,花纹间色彩互换富有变化。丝绸品的工艺从平织、平纹重组织、显花起绒圈重组织、经线显花、纬线显花、刺绣到印花法都出现,仅印花,唐代就有蜡染法和绞缬法。汉唐西域丝绸品就纹样而言,纵向流变和横向融合都呈现出创新和互渗的特征。“花纹方面,汉代那种宽带式花纹布局,到了唐代改为孤立的花纹元素散布全幅。花纹母题则西方式植物纹盛行,包括忍冬纹、葡萄纹等。波斯萨珊朝式的那种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唐代很是盛行”。①联珠圆圈内是对鸟、对兽图案。但这种合璧并非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而是各种文化在长期接触中,从冲突、碰撞走向融合的结果,它虽脱胎于原来的文化,但并非原来的模样,一经消化吸收和文化整合后,成了本土化的艺术品种。盛唐气象就是指其化解东西文化的大气,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岂能例外。
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是汉锦的主要发现地。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1980年在楼兰城郊古墓群孤台墓地就出土汉锦53件;1995年在尼雅遗址编号为95MNIM8号的墓地出土的汉锦织物10多件,其中就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1983~1995年在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中,出土包括织锦、绢类丝织物33件。汉锦上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是纹样构成的基本特征。楼兰出土的一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褐色地,黄、蓝二色里花,经锦。变体云纹和攀枝叶蔓中夹瑞兽,瑞兽间织隶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吉祥语”。②而另一件1995年出土于尼雅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重平纹经锦,平挺厚实,图案题材新颖,有虎、龙、避邪、仙鹤、孔雀、瑞兽图案,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③山普拉出土的丝绸物多为死者的帽、衣、裤、护颌罩等服饰类,有锦、绢、缦、绮等。其中织锦有两件,一件蓝地,显黄色菱格、曲线、点纹;另一件有幅边,绛色为地,宝蓝、米黄、粉绿和白色五种颜色显花。①营盘出土的属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织锦是以“吉祥云纹、祥禽瑞兽为主体的图案。有夹织立禽和隶书‘登高’、‘寿’、‘右’等文字锦,也有图案横向排列的卷草纹锦和方格纹内相同的瑞兽纹锦”。②西域以织锦为代表的汉代丝织品,“其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纹饰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现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其间穿插种种吉祥用语”,③具有汉文化特征。许多祥禽瑞兽是有象征寓意的,如对鸭图案中的鸭子意取“压子”;老鼠象征长寿;独角兽——避邪有祛邪除凶的寓意;龙凤象征吉祥等等。汉代丝织品中出现的这类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纹饰是一个时代思想与信仰的折射。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更现实,也更务实,“显然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世俗化,成为一种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就是追求生命的永生。而现实生活中的‘富贵’与子孙的‘繁衍’,却成了更现实的生活中‘幸福’,人们的渴求日益现实,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字样就是明证,人们日益实用的生活观念正是在这里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④当汉朝统一西域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思想、信仰上的趋同性已深深扎根于西域各地居民的心中,所以才会在那么多墓葬中出土如此众多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的丝绸织物——生用死殉,追求着生命的永生和一生的“富贵”,并期望“幸福”庇荫子孙后代。就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些我国古代星占术上的占辞用语也出现在织锦上,也可以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祈语,反映了西域各地居民同中原汉民族同样追求吉祥昌盛的良好祈愿和朴素的感情。
从北朝到唐代,西域丝织物的产地主要在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含西州)等地,但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物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工艺技术和图案风格。在众多出土的丝织品中织锦和绢(染缬)最为普遍。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的织锦是有差异的。6世纪前的织锦图案单位直行排列,作横幅相间的祥瑞兽纹,形成瑞兽纹锦、狮纹锦等,图案内容和布局与汉锦相似,但动物形态或立或卧,都比较稳定,是汉锦风格的继续;而到了唐代,有两类图案的织锦居于主导地位:一为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图案,二为联珠对禽对兽图案。⑤植物纹样图案织锦品类多,纹样多变,其中的“宝相花斜纹经锦”的纹饰图案是唐代汉地的主流图案。魏晋以来,中原曾盛行在金银器、铜镜上镶嵌珠宝类花,在中心花蕊及花蕊和花瓣交接的地方镶嵌以珍珠和宝石,图案上用佛教艺术的退晕色方法,以放射对称的格式,组成盛开、半开、含苞的花与花叶等富丽堂皇的团花,谓之“宝相花”。到了唐代,宝相花图案又出现在织锦图案中。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件唐云头锦鞋,其鞋面就是宝相花图案:“系用宝蓝、墨绿、橘黄、深棕四色在白地上织簇八中心放射状图案花纹的斜纹经锦,以中心部分,为六个花瓣组成的圆形朵花,围绕着中心朵花则是簇八放射对称的如意勾藤,在对称如意的地方,缀以花蕊及花叶。”从花的图案看,似是雪花的变形。宝.①“相花斜纹经锦”可能就是唐代的“瑞锦”,有“瑞雪兆丰年”、“雪花献瑞”的象征寓意。
阿斯塔那出土最多的是联珠对禽、对鸡、对兽图案的织锦,统称为联珠纹样织锦。联珠纹样是萨珊波斯的传统图案。3世纪兴起的萨珊波斯王朝流行一种装饰性程式化倾向的纹章艺术,出现在织物和金银工艺品中。“其上即根据此种风格表现着为求装饰效果而多少予以程式化的幻想怪物:头和前爪似猫而翼和尾部如‘开屏’孔雀的‘龙孔雀’;或武士骑在半狮半鹫的‘格力芬’或带翼的狮的背上,和其他‘格力芬’作战;或完全对称的成对野羊或雄狮,各举一前足对面而立;或如迦勒底—亚述所喜好的题材,即程式化的狸形野兽吞食着同样程式化的鹿类动物”。②在这些织物中,往往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圆圈内常填以对马纹、对鸟纹和对鸭纹,也有填以波斯式的猪头纹和立鸟纹。③但是吐鲁番出土的联珠纹锦并不是波斯的工艺品,而是根据西域商人订货需求由汉人织作的织锦,其产地是蜀地,因此,这类织锦也称为蜀锦。“联珠禽兽纹斜纹纬锦有组织细密的精品,如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也有像联珠戴胜鸾鸟纹锦那样组织粗松的制品。这种联珠禽兽纹斜纬纹锦是这个时期墓葬中最常见的纹锦,发现的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显然,这意味着它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另外,我们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其他间接资料也可以知道这种有别于传统的图案,当时在我国内地已较为流行”。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件联珠“胡王”锦。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织锦采用倒置循环提花法织成上下对称的图案,米黄色地上有橘红、绛红色显花,在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手执长鞭,深目高鼻,花环之间饰以复合忍冬四叶纹。它显然是萨珊波斯式的联珠动物纹样织锦,但所织“胡王”汉字表明它确系汉地产品,估计是为九姓昭武或萨珊波斯王族专织的。在丝绸之路中端的高昌出现,可能是商品交易的结果。植物纹锦中的忍冬纹、葡萄纹也是西来的产物,但也很快被唐代织锦所接受。
唐代高昌、西州丝织物以绢类为大宗。绢也称“素”,本为一般平纹织物,经纬密度大致相等,除本色外,染成大红、粉红、墨绿、叶绿、鹅黄、绛紫、茄紫、翠蓝、湖蓝、藕荷等颜色图案的称为染缬,其染织方法又有绞缬、夹缬之分。当然,染缬也用于缦、缣、纱、罗、棉布等工艺上,这些染织物也统称印花丝织物。绢类丝绸物的绞缬法有两种:一种是将谷粒大致匀称地包在织物上,用线扎紧,染色,晾干后,拆去扎线,即现出遍地大小相等的菱形圈花纹;另一种是将织物折成连皱,用针线穿过,然后将线抽紧钉牢,染色后晾干,拆去穿线,即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①夹缬的方法是将织物绷紧,夹于镂花夹板中间,涂以蜡,再解去夹板,染后晾干,剥去蜡即成,因涂蜡处未吸收染色,即显出花纹。②夹缬法就是通常所称的蜡染法。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染缬织物看,主要以盛唐为主。墓葬出土的数件夹缬绢,一染绛地花云,一染棕地散花,一染土黄地花云,都绘制工致,浸染均匀,是唐代蜡缬的精品。③唐代流行的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纹样就与这种染缬工艺有关。夹缬法不仅适宜于染制植物花卉图案,还可以印染较复杂的人物、动物、山石树木在内的组合纹样。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狩猎纹印花绢片就属此种。此为平纹印花绢织物,纹样内容为,在深绿地上显出粉绿的狩猎图案:骑马的猎手飞马张弓射狮,猎犬逐兔,猎鹰追飞鸟,天上流云,地下山石树木,图案呈上下对称,有强烈动感。唐代夹缬绢上的狩猎图案与5世纪的骑士(狩猎者)对兽纹锦图案可能有渊源关系。另一件纹锦同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纹锦黄地,以深青、浅蓝、浅黄色显花,以数个相切的圆环为图案骨架,其内饰狩猎者射鹿、对象、对狮、对驼等纹样。圆环之间填对马和忍冬纹样,圆环相切处又以仰莲相缀。除联珠纹鸟兽纹样流行于高昌等地外,还有一种人像、动物、树木等组合式纹样同样流行,不过它的主题是骑士、狩猎者等英雄形象与狩猎对象关系的表现。这些纹样是九姓昭武和萨珊波斯常见的纹样。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类题材还源自西域游牧民族的狩猎生活,虽然高昌、西州作为农耕民的汉族居民并不狩猎或根本无猎可狩,但与其关系密切的突厥人确实是典型的狩猎、游牧民族。不过,其主要影响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和萨珊波斯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萨珊波斯艺术的生命力超过了王朝生存的年代,直到九世纪在中国北方还有余绪可见。..由于进入中国新疆的一些画师来自伊朗东部或吐火罗地区,所以在画风上也必然带来波斯绘画的格调”。①高昌地区就有粟特人的聚落。汉锦唐绢正是在吸收、化解各种艺术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品格,这是它的大气,也是它的力量所在,这正是流光溢彩的中国气派,西域的汉族居民也受惠于此。
附注
①〔法〕L.布尔努瓦.耿昇译.丝绸之路·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3.
②〔法〕L.布尔努瓦.耿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251.
③〔美〕玛里琳·霍恩.乐竟泓等译.服饰:人的第二皮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0.
①武敏.新疆出土汉至唐丝织物概说.文博.1991(1).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67~69.
②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349.
③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IM8概况及初步研究.西域研究.1997(1).
①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39~41.
②周金玲.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群考古述论.西域研究.1999(3).
③穆舜英.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100.
④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38.
⑤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7、8).
①陈娟娟.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文物.1979(2).
②〔法〕雷奈·格鲁塞著.常任侠等译.东方的文明上册.中华书局,1999.87~88.
③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69.
④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3).
①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7、8).
②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1972(2)考古.
③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考古.1972(2).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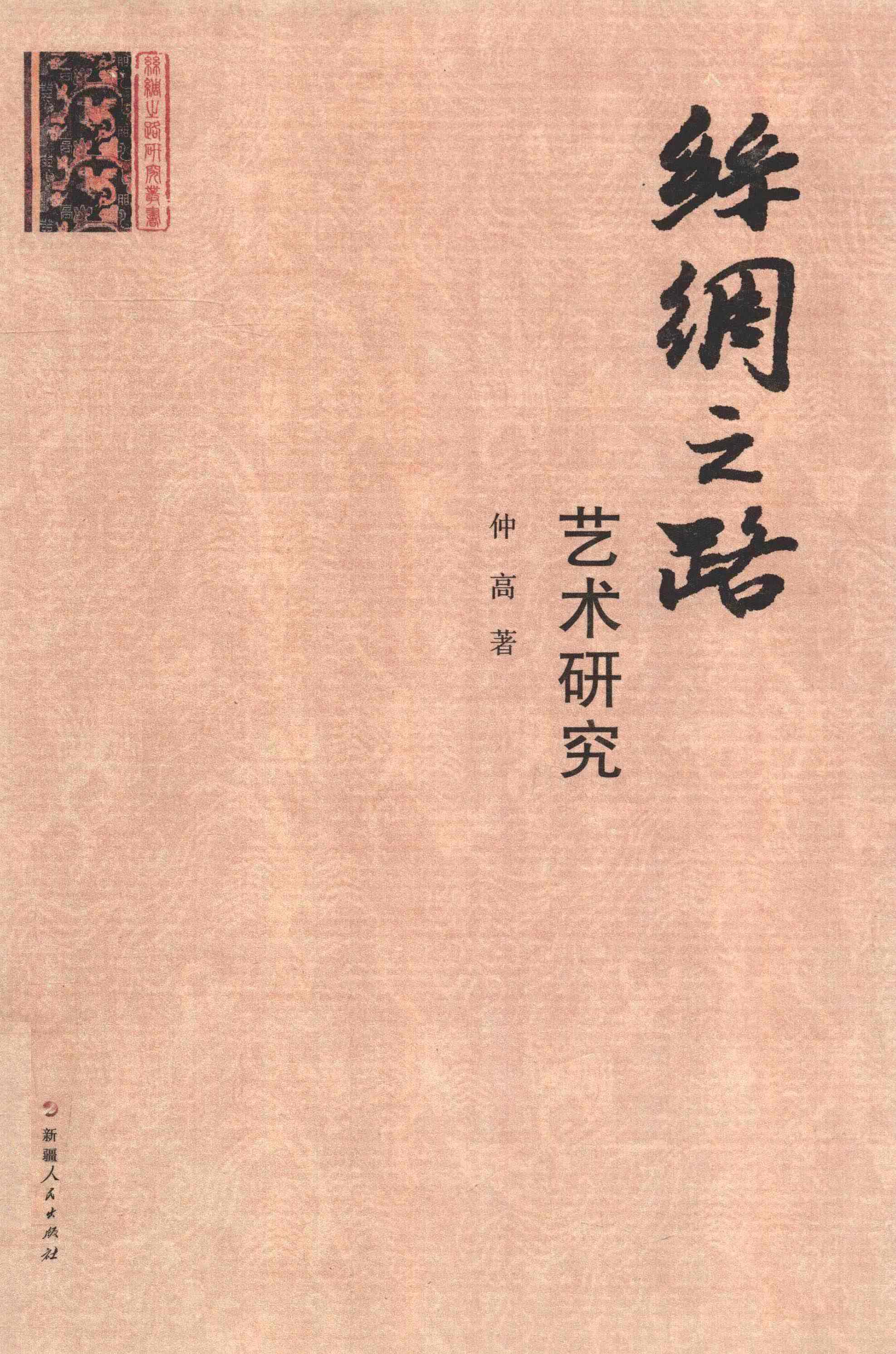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