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雕塑艺术:神圣与世俗之间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39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雕塑艺术:神圣与世俗之间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8 |
| 页码: | 185-192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汉民族文化中雕塑艺术:神圣与世俗之间情况。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神话 风格 |
内容
在丝绸之路汉民族文化中,他们的神话、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总是神圣的;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则是世俗的。
“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将神圣事物简单地理解成那些被称为神或精灵的人格存在;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泓泉水,一枚卵石,一段木头,一座房子,简言之,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圣的事物。”①那些雕塑的偶像及其膜拜仪式当然是神圣的,而再现墓主人生前世俗生活的人俑、动物俑、镇墓兽之类的明器也是神圣的吗?按理,无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多么高贵,但他们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再凡俗不过了。只是当他们离开人世间时,所进行的隆重葬礼连同象征生前生活的明器均被神圣化,凡俗之物成了神圣之物。
俑与神偶尽管制作材料相差无几,但功能大相径庭。神偶,往往以造型的形式被看作是神圣存在的代表,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俑虽然也以造型形式出现,但并不是膜拜的对象,而只是人们幻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的观念的反映。在以人俑、动物俑随葬之前,曾出现过人殉和动物殉。“父系氏族兴起以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的现象,随葬品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种类增加了,有生产工具、陶器、装饰、牲畜和奴隶,另一方面出现了随葬品多少不一的现象。”②富有者,如氏族酋长等,随葬时往往有大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牲畜,甚至以奴隶殉葬。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新型个体家庭的兴起,活殉的情况就有了改变,俑葬出现了。但是俑不是作为现实中人和物的替代品出现的,而是在展示墓主人的阴间生活。在中国丧葬文化中,俑本专指俑人,但以后把动物形象也包括进去了。“这些俑是要在阴间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人并且所有的俑都必将发挥其实效”。③因此,俑是显示墓主人社会地位的,它的实效也表明其功能和职责是最重要的。
西域汉族墓葬中的俑集中于7~9世纪,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时期,出土俑又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为多。按题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侍奉墓主的俑人和动物俑;二是保护墓主的避邪压胜之神物,如镇墓兽、十二生辰、天王俑之属。④这与中原墓葬中的随葬俑人习俗毫无二致。西域汉俑与中原俑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制作材料和某些人物造型上,它显示的是汉文化一统中的地域特色。阿斯塔那古墓中的俑为彩绘泥俑和木俑,绝少有中原的陶俑,且制作材料和方法有地域性。彩绘泥俑一般采用模型和捏塑方法,以木或草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木俑采用刻、削、琢、旋、磨等工艺,成型后再施以彩绘。俑人和动物俑除唐代常见的仕女俑、吏俑、乐舞俑、武士俑、胡人俑、生育俑、天王俑、家畜、家禽俑等以外,还有反映高昌、西州汉人现实生活的劳作俑、杂技俑、牛车俑等。
自汉代以来,西域就陆续有中原的汉族居民迁入,于是像高昌这样一些汉族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社区社会。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得知,从高昌王国到唐西州的400多年中,该地区曾先后有麴、张、马、阚、索、唐、曹、赵、郭、孙、范、巳、傅、董、牛、李、史、焦等姓氏的家族。“家族,在当时的高昌社会中,是一支不可以低估的社会力量,普通百姓人家,要依靠同姓同族的扶持、照应,以求得安身立命之地;权贵之家,也利用血缘、家族的关系,作为维护统治权益、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家族的、血缘的关系,成了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有力手段。生前,人人都感受到形如蛛网的家族的系联;死后,也自不能脱离这一家族关系的束缚。因此,以一个个大家族为单元,营建自己的墓地,成了一种习俗。”①我国汉族的丧葬习俗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丧葬之礼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进行的。孔子就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仅以隋唐时期的随葬制度而言,就形成以陶俑为主的随葬习俗。俑的形象多为出行时的仪卫队列和家居时的奴婢侍者,乐舞俑、游戏俑、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种动物模型也十分普遍。武周后,以黄、白、绿三彩为主的“唐三彩”陶俑为主,镇墓兽也演变为有头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兽。但是并非所有的墓葬的随葬品都如此丰厚,只有帝王、王公贵族及官宦人家依定制可有丰厚或较丰厚的随葬品。这种厚丧的丧葬习俗也被高昌王族或某个家族中的富有者所承袭。麴氏高昌王室是西域汉族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其墓葬规模也算得上宏大了。其中编号为60TAM336的王室墓的“墓室地表曾经建有一座四棱形佛塔,墓道长达29米,墓底深入地下约9米,墓室前部有象征前厅的甬道,左右有象征厢房的龛室,更前为天井,象征着居室的庭院。天井地面以小块砾石铺砌,不同寻常。墓葬随葬品,主要是大量俑像,品类既繁,数量也多。大型镇墓兽、泥塑马、驼、文吏、武士以及舞乐百戏,还有家畜、井、灶等一应俱全”。②按照“事死如事生”原则指导下的俑人、动物俑和镇墓兽都不是随意塑造的,而是按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和生活经历精心选择的,这些随葬物也应是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物。
高昌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普通百姓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作式生活,而是由政事、社交、宴饮娱乐等活动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俑人也大多与他们的上层生活情景有关。仕女俑可能就是他们阴间生活中妻妾、歌舞伎等形象;而一些男俑,特别是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也应是他们处理军政事务的手下的形象;还有些胡人俑很可能是与之交往地区部民首领派来使者的形象;更有些昆仑奴的戏俑、舞蹈俑、舞狮俑、杂技马舞俑等也是供上层人物娱乐时的百戏乐舞者的形象。始作俑者当然是活着的亲人,他们希望通过诸如此类的丧葬手段,力图让死者在阴间拥有同生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死者如同生前一样享尽荣华富贵。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AM206的张雄夫妻合葬墓的两件仕女俑代表了麴氏高昌王国彩绘泥塑的艺术水准。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麴、张二姓是头等豪门,麴氏为王,张氏为将相,又形成联姻关系。张雄的祖父曾任高昌王国左卫将军、绾曹郎中,其父任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张雄的姑母是高昌王麴伯雅的王妃,而他本人则任高昌王国左卫大将军,其二子张定和、张怀寂曾在唐西州、甘州任官。出土的这两件仕女俑只是张雄夫妇合葬墓中木俑的极少一部分,从他们的墓中清理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70多件,还有木马残腿、木俑手脚200余件。两件仕女俑均为立俑,高发髻、白襦衫,一件是绛色长裙,另一件为彩条长裙。仕女俑头部与躯体用木雕刻而成,脸部打磨施彩,表情温静安祥。仕女的手及长裙用衬纸做成,其一仕女俑双手交叠腹前,另一仕女俑为长袖善舞状。这两件仕女俑高36厘米左右,不及麴氏王族陵墓中的高54厘米的仕女俑。可见王族与非王族的俑人在高低大小上是有定制的。王陵仕女俑用整端木头雕成,后施彩绘。因色彩剥落,已无法窥知其艳丽,但仕女俑形象仍栩栩如生。仕女发束“惊鹄髻”,宽衣大袖,休态丰腴,为典型的贵妇形象,似为王室女眷。与仕女体态端庄、神情温顺、安详形象不同的是一些乐舞俑。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这批绢衣木俑制作特殊,形象、表情、装饰都不同于常见的殉葬俑人。男女俑原来均以木雕头部、彩绘面貌,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这种纸臂绢衣的木俑,既便于表现各种舞蹈动作,而又衣着真实,宛若真人”。①用什么材料制作,受条件制约,其他俑人,如仕女俑也用木、纸等材料,关键是人物动作、神态,这些绢衣木俑,男的(实为女扮男装)“滑稽戏调”,女的“秾华窈窕”,完全不似仕女俑肃穆端庄。“十七个绢衣彩绘女俑,不是一般的舞俑。这些女俑不但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而且还有女扮男装的。..这类木偶不直接雕绘成男角,而要刻画成女扮男装,正是当时演出就有由女优扮演男角的缘故。这反映当时男女倡优尚不同台演出,而女扮男装木偶的发现,则用实例证明初唐已有女优装扮生、旦角色演出‘合生’了”。②这些表现歌舞戏弄木俑的出土表明唐统一西域后,西域汉族居民中也流行中原地区的乐舞戏弄。汉唐时期上层人物丧葬中用傀儡表演歌舞伎乐的习俗,很可能也被高昌、西州汉族上层所采用,或者王族等也有私家乐舞队。唐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就认为:“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故高昌王公贵族墓中会出现如此多的乐舞俑。
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等是作为死者阴间的侍从、下属、左右等形象出现的。文官俑和武士俑有站立式塑像和骑马式塑像。骑马式武士俑似为仪仗俑的一部分。张雄夫妇墓出土的骑马武士木俑有三具,全身着铠甲,头戴软盔,骑于马上都呈同一姿势的执兵器状。应是仪仗卫队中的卫士。马身与马腿是两个部件隼接而成,可能受材料的限制,马腿显得僵直,未表现出动感。而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另一具骑马武士泥俑则不同。虽然也是仪仗兵马俑之一,但从装束看,似为将军。此俑因用软泥塑造而成,故线条流畅,无木俑的僵直感。将军头戴尖顶软盔(与兵士有别),穿深褐色长袍,外罩软甲,端坐马上,左手持缰绳,右手作提鞭状(与兵士持兵器不同),马为黑色,体形高大健壮。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审美效果,骑马武士泥俑都堪称这类俑人中的精品,虽然人与马处于相对静态,但人马比例、马的形体塑造以及着色等艺术水准都远在三尊骑马武士木俑之上。高昌(西州)的民间艺人在雕塑俑人时很能把握不同人物的瞬间状态,雕塑出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具文吏俑,其形象为右手握笔,左肋挟文卷,头梳发髻,身着长袍的彩绘泥塑。文吏俑表情谦恭,目光直视,嘴上的两撇胡子有动感。整个神态表明他正在毕恭毕敬地聆听上司的旨意,以便随时起草文告。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汉族居民墓葬中出土的动物俑主要是和他们生活关系密切的骆驼俑、马俑、牛俑、鸭俑等,人身兽头的十二生肖俑也应归入动物俑中。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有一具单峰驼俑,实属罕见。因为古代新疆、中亚等地的骆驼为双峰驼,而单峰驼只生活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等地。吐鲁番出土单峰驼俑,表明此地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这具单峰驼俑,研究者往往给予很高评价:“这件泥塑造型洗炼,决不‘谨毛而失貌’。选择的是静止的一瞬间,使‘一纵即逝’的东西‘获得一种持久性’。它留驻的是整体的神形态势,不容许无谓的枝节存在,又没有漏过有生命的细节——如点睛传神。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形,是服从于神、态、势的形,而不是真驼外形的摹仿,从而在局部与整体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神、形、态、势的统一,它发挥了雕塑艺术体积的深度、厚度、体面变化无穷的特长,发挥了雕塑艺术可以多角度欣赏而不失其生动完整、容纳丰富内涵的优势,克服了造型艺术的有限性,超越了时间,启发人进入驰骋想象马镫的无限性,达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具单峰驼俑成了我国发现的三件单峰驼俑中的极品,它的体面结构与淡淡的色调,真正是浑然一体。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两件大型十二生肖俑——鸡首人身俑和猪首人身俑。前者高80厘米,彩绘泥塑,造型上为鸡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绿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后者高75厘米,上为猪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橙蓼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如此大的生肖俑,实属罕见,且鸡首、猪首毕肖,衣着华丽,宽袖、长裙下垂,舒展自然。人死后以生肖俑作为随葬品,自隋代以来就成为汉民族丧葬习俗之一。对于这种葬俗的流播地区、时间及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十二生肖俑,南方最早见于隋墓,西安见于盛唐前期墓葬,吐鲁番地区见于盛唐后期墓葬。西安唐墓是受了南方的影响,而吐鲁番唐墓当是受了西安唐墓的影响。”②
在西域汉民族俑塑中有一种非人非兽、似人似兽的特殊形象——镇墓兽。这是汉民族想象中的神物,放在墓中是为了避邪镇墓,防止魍魉破坏尸体。据民间传说,有一种叫魍魉的怪兽专吃死人肝脑,而它最怕魌头、方相。《周礼》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大丧,先〓,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相、魌头本是山神的造像,作为镇墓兽出现于战国时期,为双头兽形象,每个头上各插一对鹿角,也有单头兽,插一对长鹿角。汉代的镇墓兽多为四蹄、四爪蹬开,低头用长角作前牴状或蹲伏昂首作守望状。而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镇墓兽多为蹲踞状,有的是兽身人头,有的则是兽身兽头。还有一种人身兽头兽爪,为人立姿,其形象介于人兽之间,类似降魔变中的天王,显然来源于佛教艺术形象。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镇墓兽也多为蹲踞形,有的是人头兽身,有的是兽头兽身。立式镇墓兽是天王踏小鬼的形象。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镇墓兽,通高超过70厘米,泥塑淡彩,狮头兽身,头生双角,长有四只偶蹄;坚如岩石的前额和胸肋,张嘴翘舌,口裂深大,鼻翼和眉头像拧在一起的鹅卵石;深陷的眼窝,夸张地努凸出来的一对眼睛,好似在喷火。这些又同阔胸细腹、肋骨成条排的凹凸明显的斜沟相呼应,给人以吼声震耳的威慑感。①如果从造型看,阿斯塔那的这类镇墓兽完全与中原地区自战国以来镇墓兽长鹿角、偶蹄的传统相符。自战国至唐代,墓葬中放镇墓兽的习俗自长江流域传到中原地区,再辐射到各地,西域也是其远披之地。
阿斯塔那古墓所出土的人首豹身类镇墓兽,高86厘米,为彩绘泥塑像。此镇墓兽头为人头形,头戴兜鍪如武士,面目威严,身躯似豹,足似马蹄,尾部细长如蛇紧贴身后。全身作蹲踞状。这种镇墓兽实际上是人和豹、马等动物的组合形象。武士的威严、豹身的敏捷、马蹄的快疾组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拼凑,而是想象力和现实的结合,创造出这一怪诞的形象才能防止魍魉毁坏墓主人的尸体,这正是镇墓兽的功能所在。
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彩绘天王踏鬼木俑,从其形象看,也应是镇墓兽之类,不过是在形象上借用了佛教传入后的天王形象。它非传统的镇墓兽,而应是镇墓天王,来自于佛教传说,因此,这类形象更有地域色彩,也更人性化。佛教传说中的四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实为守护四方之神。佛教传入中原、西域后,往往在佛寺内塑造四天王像: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持国天王著白色服饰,持琵琶;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缠一龙;多闻天王着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阿斯塔那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由30余块分别雕刻套接后成形。天王高髻束带,身着铠甲,右手上举,左手臂弯曲前伸,穿红花裤,系扶腿,足蹬靴,右足下踏一小鬼(可能就是魍魉)。虽然天王衣著依现实生活中武士打扮造型,有世俗化意味,但双目怒视,龇牙咧嘴,的确有威严感,其形象足以震慑魍魉之类。天王用于镇墓,是西域汉族居民依据现实生活和佛教信仰的创作,它不拘泥于传统的镇墓兽形象,采用更人性化的创新思维,大胆把佛教传说形象用于墓葬。由此可以证明,一些神圣事物完全可以用于现实目的。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俑人中有一种特殊的形象——黑人形象,有研究者称之为黑人与戏俑,也有人说是昆仑奴形象。这一俑人为彩绘泥塑,上身赤裸,下身着橘红色短裤,赤足,皮肤施黑彩,短卷发,嘴唇较厚,双手正握棒舞弄,此俑人高仅12.5厘米。该俑与西安南郊嘉里村唐裴氏墓出土的陶俑如出一辙,不过阿斯塔那的彩绘泥塑俑人出土于王族墓中而已。孙机先生认为,这类“黑人”俑不应定为昆仑俑,而是所谓的僧祗,昆仑俑是南海昆仑国人被夸张强化所致的形象,而作为“黑人”形象的僧祗是大食自东非掠买的黑人,与大食有外交事务关系的唐朝高官也养成家养黑奴的恶俗。所以这类黑人俑应是僧祗的形象。①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鞠氏王族或唐西州高官有养黑奴的恶俗,但黑人俑的出土至少说明西域汉族上层人物对唐长安高官人家养黑奴是仰慕的,故以这类俑人随葬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罢了。
“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将神圣事物简单地理解成那些被称为神或精灵的人格存在;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泓泉水,一枚卵石,一段木头,一座房子,简言之,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圣的事物。”①那些雕塑的偶像及其膜拜仪式当然是神圣的,而再现墓主人生前世俗生活的人俑、动物俑、镇墓兽之类的明器也是神圣的吗?按理,无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多么高贵,但他们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再凡俗不过了。只是当他们离开人世间时,所进行的隆重葬礼连同象征生前生活的明器均被神圣化,凡俗之物成了神圣之物。
俑与神偶尽管制作材料相差无几,但功能大相径庭。神偶,往往以造型的形式被看作是神圣存在的代表,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俑虽然也以造型形式出现,但并不是膜拜的对象,而只是人们幻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的观念的反映。在以人俑、动物俑随葬之前,曾出现过人殉和动物殉。“父系氏族兴起以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的现象,随葬品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种类增加了,有生产工具、陶器、装饰、牲畜和奴隶,另一方面出现了随葬品多少不一的现象。”②富有者,如氏族酋长等,随葬时往往有大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牲畜,甚至以奴隶殉葬。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新型个体家庭的兴起,活殉的情况就有了改变,俑葬出现了。但是俑不是作为现实中人和物的替代品出现的,而是在展示墓主人的阴间生活。在中国丧葬文化中,俑本专指俑人,但以后把动物形象也包括进去了。“这些俑是要在阴间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人并且所有的俑都必将发挥其实效”。③因此,俑是显示墓主人社会地位的,它的实效也表明其功能和职责是最重要的。
西域汉族墓葬中的俑集中于7~9世纪,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时期,出土俑又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为多。按题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侍奉墓主的俑人和动物俑;二是保护墓主的避邪压胜之神物,如镇墓兽、十二生辰、天王俑之属。④这与中原墓葬中的随葬俑人习俗毫无二致。西域汉俑与中原俑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制作材料和某些人物造型上,它显示的是汉文化一统中的地域特色。阿斯塔那古墓中的俑为彩绘泥俑和木俑,绝少有中原的陶俑,且制作材料和方法有地域性。彩绘泥俑一般采用模型和捏塑方法,以木或草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木俑采用刻、削、琢、旋、磨等工艺,成型后再施以彩绘。俑人和动物俑除唐代常见的仕女俑、吏俑、乐舞俑、武士俑、胡人俑、生育俑、天王俑、家畜、家禽俑等以外,还有反映高昌、西州汉人现实生活的劳作俑、杂技俑、牛车俑等。
自汉代以来,西域就陆续有中原的汉族居民迁入,于是像高昌这样一些汉族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社区社会。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得知,从高昌王国到唐西州的400多年中,该地区曾先后有麴、张、马、阚、索、唐、曹、赵、郭、孙、范、巳、傅、董、牛、李、史、焦等姓氏的家族。“家族,在当时的高昌社会中,是一支不可以低估的社会力量,普通百姓人家,要依靠同姓同族的扶持、照应,以求得安身立命之地;权贵之家,也利用血缘、家族的关系,作为维护统治权益、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家族的、血缘的关系,成了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有力手段。生前,人人都感受到形如蛛网的家族的系联;死后,也自不能脱离这一家族关系的束缚。因此,以一个个大家族为单元,营建自己的墓地,成了一种习俗。”①我国汉族的丧葬习俗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丧葬之礼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进行的。孔子就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仅以隋唐时期的随葬制度而言,就形成以陶俑为主的随葬习俗。俑的形象多为出行时的仪卫队列和家居时的奴婢侍者,乐舞俑、游戏俑、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种动物模型也十分普遍。武周后,以黄、白、绿三彩为主的“唐三彩”陶俑为主,镇墓兽也演变为有头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兽。但是并非所有的墓葬的随葬品都如此丰厚,只有帝王、王公贵族及官宦人家依定制可有丰厚或较丰厚的随葬品。这种厚丧的丧葬习俗也被高昌王族或某个家族中的富有者所承袭。麴氏高昌王室是西域汉族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其墓葬规模也算得上宏大了。其中编号为60TAM336的王室墓的“墓室地表曾经建有一座四棱形佛塔,墓道长达29米,墓底深入地下约9米,墓室前部有象征前厅的甬道,左右有象征厢房的龛室,更前为天井,象征着居室的庭院。天井地面以小块砾石铺砌,不同寻常。墓葬随葬品,主要是大量俑像,品类既繁,数量也多。大型镇墓兽、泥塑马、驼、文吏、武士以及舞乐百戏,还有家畜、井、灶等一应俱全”。②按照“事死如事生”原则指导下的俑人、动物俑和镇墓兽都不是随意塑造的,而是按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和生活经历精心选择的,这些随葬物也应是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物。
高昌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普通百姓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作式生活,而是由政事、社交、宴饮娱乐等活动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俑人也大多与他们的上层生活情景有关。仕女俑可能就是他们阴间生活中妻妾、歌舞伎等形象;而一些男俑,特别是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也应是他们处理军政事务的手下的形象;还有些胡人俑很可能是与之交往地区部民首领派来使者的形象;更有些昆仑奴的戏俑、舞蹈俑、舞狮俑、杂技马舞俑等也是供上层人物娱乐时的百戏乐舞者的形象。始作俑者当然是活着的亲人,他们希望通过诸如此类的丧葬手段,力图让死者在阴间拥有同生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死者如同生前一样享尽荣华富贵。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AM206的张雄夫妻合葬墓的两件仕女俑代表了麴氏高昌王国彩绘泥塑的艺术水准。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麴、张二姓是头等豪门,麴氏为王,张氏为将相,又形成联姻关系。张雄的祖父曾任高昌王国左卫将军、绾曹郎中,其父任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张雄的姑母是高昌王麴伯雅的王妃,而他本人则任高昌王国左卫大将军,其二子张定和、张怀寂曾在唐西州、甘州任官。出土的这两件仕女俑只是张雄夫妇合葬墓中木俑的极少一部分,从他们的墓中清理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70多件,还有木马残腿、木俑手脚200余件。两件仕女俑均为立俑,高发髻、白襦衫,一件是绛色长裙,另一件为彩条长裙。仕女俑头部与躯体用木雕刻而成,脸部打磨施彩,表情温静安祥。仕女的手及长裙用衬纸做成,其一仕女俑双手交叠腹前,另一仕女俑为长袖善舞状。这两件仕女俑高36厘米左右,不及麴氏王族陵墓中的高54厘米的仕女俑。可见王族与非王族的俑人在高低大小上是有定制的。王陵仕女俑用整端木头雕成,后施彩绘。因色彩剥落,已无法窥知其艳丽,但仕女俑形象仍栩栩如生。仕女发束“惊鹄髻”,宽衣大袖,休态丰腴,为典型的贵妇形象,似为王室女眷。与仕女体态端庄、神情温顺、安详形象不同的是一些乐舞俑。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这批绢衣木俑制作特殊,形象、表情、装饰都不同于常见的殉葬俑人。男女俑原来均以木雕头部、彩绘面貌,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这种纸臂绢衣的木俑,既便于表现各种舞蹈动作,而又衣着真实,宛若真人”。①用什么材料制作,受条件制约,其他俑人,如仕女俑也用木、纸等材料,关键是人物动作、神态,这些绢衣木俑,男的(实为女扮男装)“滑稽戏调”,女的“秾华窈窕”,完全不似仕女俑肃穆端庄。“十七个绢衣彩绘女俑,不是一般的舞俑。这些女俑不但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而且还有女扮男装的。..这类木偶不直接雕绘成男角,而要刻画成女扮男装,正是当时演出就有由女优扮演男角的缘故。这反映当时男女倡优尚不同台演出,而女扮男装木偶的发现,则用实例证明初唐已有女优装扮生、旦角色演出‘合生’了”。②这些表现歌舞戏弄木俑的出土表明唐统一西域后,西域汉族居民中也流行中原地区的乐舞戏弄。汉唐时期上层人物丧葬中用傀儡表演歌舞伎乐的习俗,很可能也被高昌、西州汉族上层所采用,或者王族等也有私家乐舞队。唐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就认为:“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故高昌王公贵族墓中会出现如此多的乐舞俑。
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等是作为死者阴间的侍从、下属、左右等形象出现的。文官俑和武士俑有站立式塑像和骑马式塑像。骑马式武士俑似为仪仗俑的一部分。张雄夫妇墓出土的骑马武士木俑有三具,全身着铠甲,头戴软盔,骑于马上都呈同一姿势的执兵器状。应是仪仗卫队中的卫士。马身与马腿是两个部件隼接而成,可能受材料的限制,马腿显得僵直,未表现出动感。而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另一具骑马武士泥俑则不同。虽然也是仪仗兵马俑之一,但从装束看,似为将军。此俑因用软泥塑造而成,故线条流畅,无木俑的僵直感。将军头戴尖顶软盔(与兵士有别),穿深褐色长袍,外罩软甲,端坐马上,左手持缰绳,右手作提鞭状(与兵士持兵器不同),马为黑色,体形高大健壮。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审美效果,骑马武士泥俑都堪称这类俑人中的精品,虽然人与马处于相对静态,但人马比例、马的形体塑造以及着色等艺术水准都远在三尊骑马武士木俑之上。高昌(西州)的民间艺人在雕塑俑人时很能把握不同人物的瞬间状态,雕塑出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具文吏俑,其形象为右手握笔,左肋挟文卷,头梳发髻,身着长袍的彩绘泥塑。文吏俑表情谦恭,目光直视,嘴上的两撇胡子有动感。整个神态表明他正在毕恭毕敬地聆听上司的旨意,以便随时起草文告。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汉族居民墓葬中出土的动物俑主要是和他们生活关系密切的骆驼俑、马俑、牛俑、鸭俑等,人身兽头的十二生肖俑也应归入动物俑中。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有一具单峰驼俑,实属罕见。因为古代新疆、中亚等地的骆驼为双峰驼,而单峰驼只生活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等地。吐鲁番出土单峰驼俑,表明此地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这具单峰驼俑,研究者往往给予很高评价:“这件泥塑造型洗炼,决不‘谨毛而失貌’。选择的是静止的一瞬间,使‘一纵即逝’的东西‘获得一种持久性’。它留驻的是整体的神形态势,不容许无谓的枝节存在,又没有漏过有生命的细节——如点睛传神。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形,是服从于神、态、势的形,而不是真驼外形的摹仿,从而在局部与整体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神、形、态、势的统一,它发挥了雕塑艺术体积的深度、厚度、体面变化无穷的特长,发挥了雕塑艺术可以多角度欣赏而不失其生动完整、容纳丰富内涵的优势,克服了造型艺术的有限性,超越了时间,启发人进入驰骋想象马镫的无限性,达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具单峰驼俑成了我国发现的三件单峰驼俑中的极品,它的体面结构与淡淡的色调,真正是浑然一体。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两件大型十二生肖俑——鸡首人身俑和猪首人身俑。前者高80厘米,彩绘泥塑,造型上为鸡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绿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后者高75厘米,上为猪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橙蓼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如此大的生肖俑,实属罕见,且鸡首、猪首毕肖,衣着华丽,宽袖、长裙下垂,舒展自然。人死后以生肖俑作为随葬品,自隋代以来就成为汉民族丧葬习俗之一。对于这种葬俗的流播地区、时间及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十二生肖俑,南方最早见于隋墓,西安见于盛唐前期墓葬,吐鲁番地区见于盛唐后期墓葬。西安唐墓是受了南方的影响,而吐鲁番唐墓当是受了西安唐墓的影响。”②
在西域汉民族俑塑中有一种非人非兽、似人似兽的特殊形象——镇墓兽。这是汉民族想象中的神物,放在墓中是为了避邪镇墓,防止魍魉破坏尸体。据民间传说,有一种叫魍魉的怪兽专吃死人肝脑,而它最怕魌头、方相。《周礼》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大丧,先〓,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相、魌头本是山神的造像,作为镇墓兽出现于战国时期,为双头兽形象,每个头上各插一对鹿角,也有单头兽,插一对长鹿角。汉代的镇墓兽多为四蹄、四爪蹬开,低头用长角作前牴状或蹲伏昂首作守望状。而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镇墓兽多为蹲踞状,有的是兽身人头,有的则是兽身兽头。还有一种人身兽头兽爪,为人立姿,其形象介于人兽之间,类似降魔变中的天王,显然来源于佛教艺术形象。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镇墓兽也多为蹲踞形,有的是人头兽身,有的是兽头兽身。立式镇墓兽是天王踏小鬼的形象。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镇墓兽,通高超过70厘米,泥塑淡彩,狮头兽身,头生双角,长有四只偶蹄;坚如岩石的前额和胸肋,张嘴翘舌,口裂深大,鼻翼和眉头像拧在一起的鹅卵石;深陷的眼窝,夸张地努凸出来的一对眼睛,好似在喷火。这些又同阔胸细腹、肋骨成条排的凹凸明显的斜沟相呼应,给人以吼声震耳的威慑感。①如果从造型看,阿斯塔那的这类镇墓兽完全与中原地区自战国以来镇墓兽长鹿角、偶蹄的传统相符。自战国至唐代,墓葬中放镇墓兽的习俗自长江流域传到中原地区,再辐射到各地,西域也是其远披之地。
阿斯塔那古墓所出土的人首豹身类镇墓兽,高86厘米,为彩绘泥塑像。此镇墓兽头为人头形,头戴兜鍪如武士,面目威严,身躯似豹,足似马蹄,尾部细长如蛇紧贴身后。全身作蹲踞状。这种镇墓兽实际上是人和豹、马等动物的组合形象。武士的威严、豹身的敏捷、马蹄的快疾组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拼凑,而是想象力和现实的结合,创造出这一怪诞的形象才能防止魍魉毁坏墓主人的尸体,这正是镇墓兽的功能所在。
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彩绘天王踏鬼木俑,从其形象看,也应是镇墓兽之类,不过是在形象上借用了佛教传入后的天王形象。它非传统的镇墓兽,而应是镇墓天王,来自于佛教传说,因此,这类形象更有地域色彩,也更人性化。佛教传说中的四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实为守护四方之神。佛教传入中原、西域后,往往在佛寺内塑造四天王像: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持国天王著白色服饰,持琵琶;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缠一龙;多闻天王着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阿斯塔那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由30余块分别雕刻套接后成形。天王高髻束带,身着铠甲,右手上举,左手臂弯曲前伸,穿红花裤,系扶腿,足蹬靴,右足下踏一小鬼(可能就是魍魉)。虽然天王衣著依现实生活中武士打扮造型,有世俗化意味,但双目怒视,龇牙咧嘴,的确有威严感,其形象足以震慑魍魉之类。天王用于镇墓,是西域汉族居民依据现实生活和佛教信仰的创作,它不拘泥于传统的镇墓兽形象,采用更人性化的创新思维,大胆把佛教传说形象用于墓葬。由此可以证明,一些神圣事物完全可以用于现实目的。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俑人中有一种特殊的形象——黑人形象,有研究者称之为黑人与戏俑,也有人说是昆仑奴形象。这一俑人为彩绘泥塑,上身赤裸,下身着橘红色短裤,赤足,皮肤施黑彩,短卷发,嘴唇较厚,双手正握棒舞弄,此俑人高仅12.5厘米。该俑与西安南郊嘉里村唐裴氏墓出土的陶俑如出一辙,不过阿斯塔那的彩绘泥塑俑人出土于王族墓中而已。孙机先生认为,这类“黑人”俑不应定为昆仑俑,而是所谓的僧祗,昆仑俑是南海昆仑国人被夸张强化所致的形象,而作为“黑人”形象的僧祗是大食自东非掠买的黑人,与大食有外交事务关系的唐朝高官也养成家养黑奴的恶俗。所以这类黑人俑应是僧祗的形象。①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鞠氏王族或唐西州高官有养黑奴的恶俗,但黑人俑的出土至少说明西域汉族上层人物对唐长安高官人家养黑奴是仰慕的,故以这类俑人随葬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罢了。
附注
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51.
②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52.
③刘文锁.新疆历史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135.
①爱弥尔·涂尔干.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3.
②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482.
③〔英〕罗森.孙心菲等译.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2.
④谭树桐.阿斯塔那唐墓俑塑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08.
①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78.
②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201.
①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文物.1976(12).
②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文物.1976(12).
①谭树桐.阿斯塔那唐墓俑塑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10~111.
②陈安利.古文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博.1982(2).
①谭树桐.阿斯塔那唐墓俑塑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17.
①孙机.唐俑中的昆仑和僧祗.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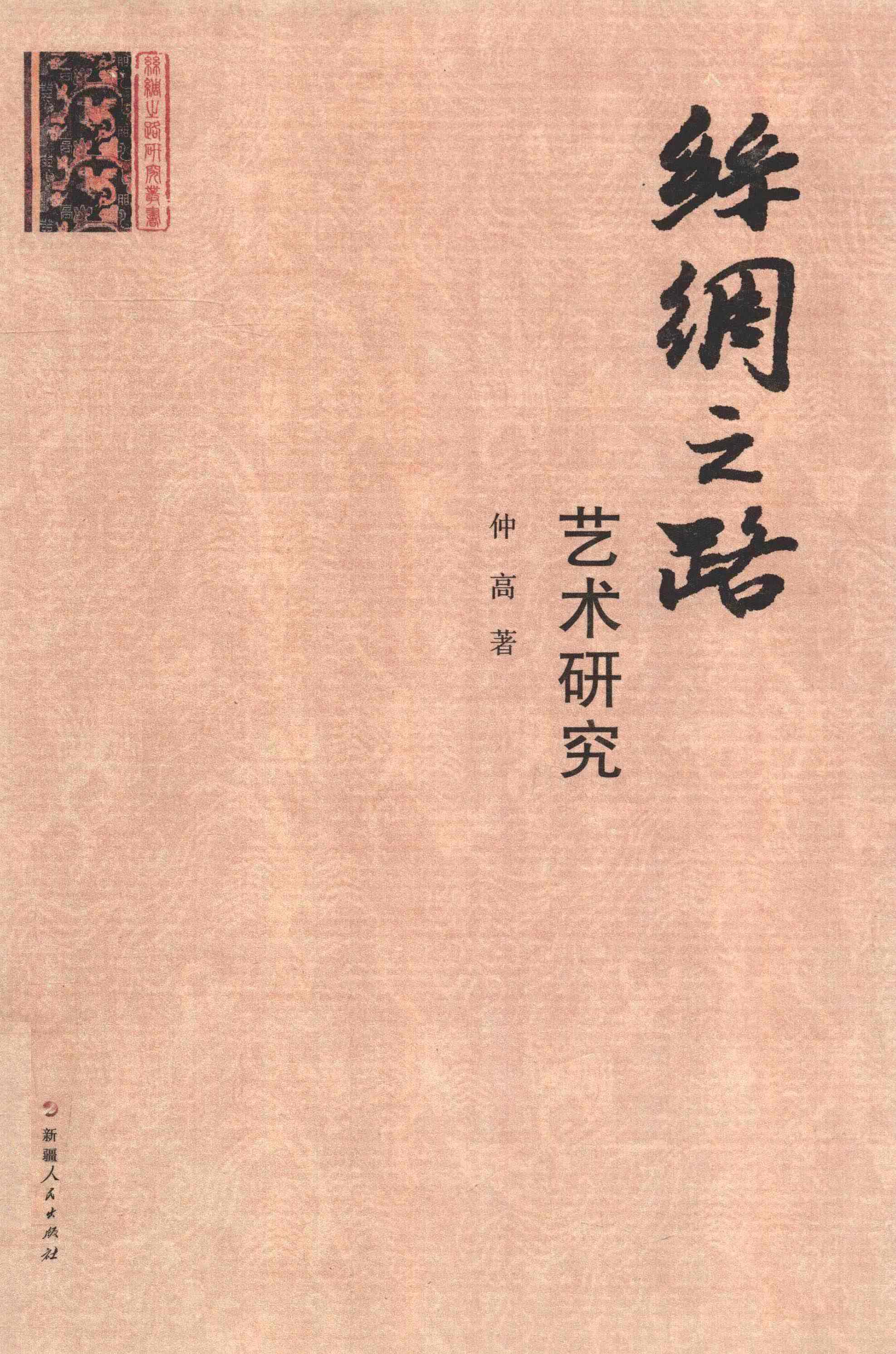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