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丝绸之路汉文化艺术之链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37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丝绸之路汉文化艺术之链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35 |
| 页码: | 178-212 |
| 摘要: | 本章记述的是丝绸之路汉文化艺术之链情况包括从神话意象到写实风格、汉锦唐绢的艺术品格、建筑艺术的绝响、汉唐遗风与屯垦艺术等。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西域 文化艺术 |
内容
第一节 从神话意象到写实风格
如果将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汉文化与西域其他诸民的文化相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文化仅仅比塞人文化晚扎根于兹,而与匈奴、月氏、乌孙等部落文化出现在西域的时间相当,且早于突厥、回鹘、〓哒、蒙古等的文化扎根于西域。以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为标志,汉民族定居于西域已有二千多年时间了。按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某种文化在某区域生存了两千多年,就可归入原居住民族文化;少于两千年但多于五百年,则归为古代移民文化;不到五百年,则归为近代移民文化。①由此看来,西域汉文化无可争议是西域的原居住民族文化。其实,西域与汉文化的联系在上古时期就已存在。“新石器时代中国黄河流域的陶鬲,出现在中亚、西亚的古地层中;制作于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代马头刀、马具等,明显地带有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用白玉雕成的人像和玉片、玉瑗出现在不产白玉的甘肃灵台西周墓葬和河西史前遗址中,而这种玉又极似和田所产;只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珠饰,于新疆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群中发现..。”②先秦时就已存在的丝绸之路,又将这种文化交往推向极致。《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上古文献的记载也反映了中原汉民族对西域的了解和认识。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为汉民族自汉代及其以后定居西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两汉入居西域的主要是军屯的将士、家属以及被征募和自愿来西域的屯田者,其他还有以政治联姻方式入居西域者和被匈奴贵族等掠夺转卖来的汉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汉人的主要来源是驻军屯田的将士和从河西等地迁至高昌等地的居民。即使在蒙古人统治的蒙元时期,自中原地区移居西域屯田的汉军、农民、工匠等日益增多。清代更以兵屯、民屯、遣屯、旗屯等屯田方式奠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汉文化格局。从西域、高昌、交河、柳中、金满、西州、天山、安西、北庭等汉语地名也能领略到汉民族作为西域原居住民族文化的客观存在。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汉文化属农耕定居文化型,源自中原汉文化。到了西域,汉文化又与不同时期的其他民族文化接触、碰撞、吸纳、整合变成了有地域特色的汉文化——西域汉文化。如果从经济形态着眼,西域汉文化可以分为屯垦文化型和城镇商业文化型;从汉民族人员来源还可分为流入文化型、移民文化型等;从地域分布看,有两汉时期罗布泊等地的军屯文化型以及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高昌汉文化型和清代的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奇台等地区的汉文化型。西域汉文化若从精神文化层面看,构成这样一些观念文化形态:(一)儒、释、道三元汇一的宗教文化形态;(二)以边塞诗为代表的汉文学形态;(三)以绘画、雕塑、戏剧、庙会、演出等方式出现的民间艺术形态;(四)以各种民俗出现的民间文化形态;(五)以汉语为主的交际、教育体系等。虽然西域汉文化的源头是中原的汉文化,但在两千多年的演进中已经基本西域化了,成了既有中原文化共性,又有西域地域特色的个性化的一个文化单元。所以,笔者把西域文化分为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屯垦文化三大类型意义也正在此。
丝绸之路汉文化之所以成为一方地域独特的文化单元,这是因为他们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林林总总,其中只有那些体现着普遍模式的事象才是民俗。第一,这些事象是模式化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形成、它们的结构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被人们完整地在生活中重复。第二,它们在社区生活中,在特定的群体中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群体中是共知共识,共同遵循的。”①在时空上显示为固定的民俗模式,如婚丧、起居、休养生息等民俗生活构成了西域汉民族人生活动的基础。一种模式化的、普遍的生活文化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就会发生发酵式的膨胀效应,无论题材、背景、表现有多么不同,但作为文化传承的结构模式是相同的。从魏晋时期到唐代,汉民族聚居的高昌地区的绘画艺术正呈现这种态势。
汉代,高昌就是西域屯田地区之一;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唐初,这里是阚氏、麴氏等汉族政权的统治地区;唐灭麴氏高昌国后,在此设立郡县,成立西州,与伊州、庭州一起成为汉族聚居的三州地区。于是,这些地区也就成了古代最能显现西域汉文化艺术特征的地区。从神话意象的伏羲女娲像到写实风格的墓主人生前生活图的绘画都出土于此。
西域汉族神话绘画材料出土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的绢画伏羲女娲图;二是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壁画龙腾图;三是楼兰、和田等地出土的彩棺上的玄武图;四是月宫桂树、玉兔图。其中大量的是伏羲女娲图。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11月的一年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发掘的四十座墓葬中,“十之六七都发现有伏羲女娲像的绢画。..大约一共有二三十幅之多。它们在墓室中,一般都是画面朝下,用木钉钉在墓顶上。”①这还不算20世纪初被西方探险者掠走的数量。高昌汉民族的伏羲女娲像首先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盛唐时期,这比中原晚了200多年。伏羲女娲像在中原盛行是在东汉时期,魏晋时已成余韵,而在西域,似香火相续,衔接中原而出现伏羲女娲像,其余绪绵延数百载。这不能不说是植根于汉民族民间的民俗信仰有强大的生命力,共同的丧葬习俗和精神信仰成了高昌汉族的共知共识,世代重复着以伏羲女娲神为核心的丧葬习俗。
最早发现的伏羲女娲绢画现存英国大英博物馆,20世纪初为外国探险者斯坦因所得。其画面为:伏羲女娲手执规矩,上身相拥,下身化作蛇尾缠绕。整个画面以深蓝色为底,并用红、黄、白三色描绘日月及人物蜿蜒缠绕的身躯。伏羲女娲粗眉、圆眼、钩鼻、朱唇。为7世纪之绢画。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也在吐鲁番得到一幅伏羲女娲绢画:“上绘二人像,左男右女,互相拥抱。两手扬起手执物,下部作两蛇相绞形。上绘一日形,日中有三足鸟,下绘一月形,月中有树兔和蟾蜍。周围有大小不一的彩色圆点,或是星宿。”②黄先生认为是7世纪上半期以后的绘画。晚近一幅伏羲女娲绢画出土于20世纪60年代,“男头戴幞头,女束高髻,两腮涂朱,眉间贴金。男举矩和墨斗,女执规。上身相拥,均着对襟直领宽袖朱衣,腰相连,共穿一花裙,下尾相交。画上部绘红心圆轮象征日形,下部以黑色圆形示月形。背景以小圆显示星辰”。③此为7世纪中期作品。审视这些画像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只存在绘画技法、着色、人物位置、服饰等方面的差异,而题材、内容则基本相同:伏羲、女娲均呈交缠之式。如果追根溯源,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形象有一种普遍现象,即作交尾状。山东武梁祠石刻:伏羲、女娲侧身相对,男戴方冠,衣缘领长袖,执曲尺,女衣同男,执规,下身蛇尾相交。南阳画像中,伏羲、女娲虽然不执规矩,下龙躯,但仍为尾相交状。
伏羲、女娲神话源自汉民族繁衍人类的始祖神信仰,到了战国时见于文献记载,而伏羲女娲交尾的绘画或雕像则晚至西汉末东汉初才大量出现。对于伏羲女娲的这种交尾式画像所含的意蕴,学者们的见解各不相同。闻一多先生认为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最基本的轮廓。①常任侠先生认为,他们既是人类的祖神,又是人类死后的保护神,“因此都雕刻在棺前或墓室享堂的前方,以保护死者,使他可以安享地下的快乐”。②吕微先生认为:“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的双蛇交尾形象除了反映出他们之间的血缘对偶关系,同时还是一种洪水创世意象。”③何新先生认为,中国远古神话中对太阳神加月亮神的二元崇拜,是中国哲学中极为重要的阴阳二元观念的始源,它是参照着男女两性的交合模型而产生的,这种两性交合的观念,转化为神话意象,也就是伏羲女娲的合体形象。④伏羲女娲绢画出现于偏于一隅的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汉民族的墓葬中,就不能不考虑其丧葬习俗及信仰之间的关系。伏羲女娲绢画是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的,死者直接面对绢画(死者无棺椁入殓,只是放在尸架或席上)。在这类墓葬中,不仅伏羲女娲绢画中绘有日、月、星辰等天象,日中多绘三足鸟,月中绘有玉兔、蟾蜍、桂树等,而且一些墓的顶部、四壁上部均以白点绘出二十八宿,每群星点间的线相连,表示一个星座。东北壁以红色绘出太阳,内有金鸟;西南壁以白色绘出月亮,内有桂树和玉兔捣月等图形。这些天象图与伏羲女娲像组合在一起,实际象征的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交而变化起”(《荀子礼治》)的观念。信仰上反映的是高昌、西州汉族祈求祖神保佑群体并希冀墓主死后升仙的思想。自汉代以来,中国道教的这种仙乡神话深深扎根于汉民族丧葬习俗中。由于太阳神——伏羲和月神——女娲结合化生万物神话信仰根深蒂固,于是伏羲女娲这对“育化人类”的文化英雄也成了祖神、生殖神等文化起源的象征,这是今世的需求。而与月神神话密切相关的月中有不死之药的神话,正是汉民族由天文现象进一步演化而成的新神话。如果死者能“死而复生”,那是人们对来世的祈求,但是其条件必须是成仙升天才能保证灵魂不死。于是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绢画和天象图有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引魂升天的多重意义。这也说明,即使汉民族中的一个不大的群体远离文化中心,其习俗信仰也会持续数百年而不衰。
楼兰古城以北墓葬出土的属汉晋时期的彩棺和和田出土的属晚唐五代时期的两具彩棺上均发现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这是最具价值的神话学材料。玄武是“龟蛇合体”的怪物形象,文献多有载,《后汉书·王梁传》李贤注说:“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有学者认为:“中国道教崇拜玄武大帝,民间盛行以玄武为吉祥长寿之物,证明玄武乃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一棵树,它的花果,正展示着中国文化一个方面的特色。”①楼兰古城以北墓葬、和田出土的彩棺所绘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守护神,和田“此二棺的彩画,从风格构图、题材上看,纯为汉族风格,连棺材造型都是汉族风格”。②从文化传播角度讲,这表明楼兰和于阗地区确实传入了中原道教,玄武大帝崇拜在楼兰和于阗民间存在是不成问题的。但楼兰和于阗人为何接受汉族的玄武信仰呢?这不能不归结到人类在追求生命永恒上是相通的:“玄武有两个属性,其一他的原形为龟,龟是寿的象征,..其二他占居北方水位,为水神。而在人类的潜意识中,水是生命的起始,也是生命的归宿。”③楼兰和于阗玄武图其意义在于长寿崇拜,玄武帝正充当了增寿赐福的职能,即使人死后,因灵魂不死,故在阴间也能享尽富贵。无论是生或死,玄武之神都能保佑他们长生永存。由此看来,玄武神在楼兰和于阗本土文化中的扎根,或者说崇拜玄武神,正是楼兰人和于阗人同汉民族一样体认生命意识的表现。
对人类而言,今世和来世总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西域汉民族也不例外。他们在祈求死后“羽化成仙”来世的同时,也十分眷恋今世,于是死者的墓葬中不仅存在伏羲女娲绢画,也多有反映今世生活的写实风格的绘画。这类绘画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再现死者生前生活情景的绘画,其动机是祝愿死者如生前一样享尽荣华富贵;二是死者生前的绘画藏品,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反映,但乃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三是带有伦理说教意味的历史故事题材六屏壁画。
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绘画出土有两幅。一幅是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墓中属3~4世纪的长条形壁画。壁画的中心人物是在帷幔下头戴巾帻,身穿大袖袍衫,双手作揖的庄园主的形象,身后有妻妾相随。左侧所画厨房内,厨娘们正炊烧和磨面。右侧是耕地、葡萄园、桑园、酿酒房、鞍马、牛车、工匠等庄园景色。另一幅是出土于吐鲁番的属7~9世纪的画有庄园主宴饮作乐的纸画。主人和客人正席地而坐,观赏两个舞女翩翩起舞,旁有吹箫、击鼓者,画面下部绘有厨具和炊烧的厨娘,还有牛车等。两幅画均为单线勾勒,平涂填色,内容基本相同。但比较这两幅不同时期的绘画也不难发现其不同之处。前一幅为长条形的组合式画面,由主人的宅外生活画面依次构成主人的主要家庭成员、财产(土地、果木、作坊、工具等)以及饮食等日常生活场景,类似出游图,绘画拙朴,不似出自专业画师之手。而后一幅则不同,描绘墓主人生前生活中的一个特定场景(内宅生活),笔法流畅圆润,构图简洁,画面有较强平衡感,人物比例也得当。如果将吐鲁番出土的这些世俗绘画与西安唐墓壁画相比较,布局和画法几无差别。①这就不难发现西域汉文化艺术与中原汉文化艺术之间的源流关系。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一批属7~9世纪的唐风绢画,大部分为仕女和侍女图,如仕女弈棋图、盛装仕女图、托盏侍女图、舞伎图等,此外还有侍马图、童子图等。这些画极有可能是唐代文人仕女图的摹本或以此类仕女图为蓝本绘制的。人物均属唐代妇女的丰美形象,圆润的脸上涂朱,眼睛细长,朱唇小嘴,梳高髻或平髻,衣着华贵,衣褶线条流畅。其中一幅仕女弈棋图是唐风仕女图。画中妇女为一贵妇,发束高髻,阔眉,额间描心形花钿,身着绯衣绿裙,披帛,贵妇表情凝重、安详,正若有所思,右手执子,呈举棋不定状。这类仕女题材的人物画是盛唐到中唐时长安流行的画风,代表人物是张萱、周昉等文人画家。《唐朝名画录》评价张萱的画是“尝画贵公子、鞍马、屏障、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宣和画谱》所载张萱画迹四十七卷中竟有三十卷为仕女图,多是描绘贵妇的世俗生活,如整妆、鼓琴、弈棋、烹菜、赏雪、出游、七夕祈巧等。其人物体态都以丰满见长,整个画面都是工笔重彩,有雍容华贵的“盛唐气象”。中唐的周昉也曾有“画仕女,为古今绝冠”的盛誉。他的留世代表作为《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周昉笔下的仕女也多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之态。这正是唐代妇女的时尚。“比较张萱、周昉的作品,其共同之处不仅在于世俗的倾向和宫廷的趣味,也不仅在于色彩的浓郁和笔触的细腻,还在于他们都善于动中取静,追求一种雍容典雅、仪态万方的气度,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的‘高贵单纯,静穆的伟大’。”①如果参照库木吐喇石窟中8世纪汉风飞天形象和吐鲁番出土的7~9世纪墓主人生活图纸画中的贵妇形象不难看出,这些人物都是体态丰腴,仪态万方,足以证明唐代西域的汉族贵妇亦以长安贵妇的浓艳丰满作为追求的审美时尚。盛唐气象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胡风汉化一起来,长安的胡风,西域的汉风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是各种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盛唐文化有强大辐射功能和极强吸纳力的表现。西域的汉族贵妇们同样追求长安上层流行的“以胖为美”的时尚,并形成一种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无论是唐代的长安还是西域的西州,“现实世间生活以自己多样化的真实,展现在、反映在文艺的面貌中,构成这个时代的艺术风神”。②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唐代墓葬还有一些屏风式壁画,一般为六屏式,有的绘有花卉禽鸟、山水人物、舞乐伎等,而有的则是连环画式的伦理说教图。有一幅“六屏式鉴诫图”的壁画为六条挂屏式布局。画面从左至右依次为:最左侧绘有一种名为“欹”的容器,形似倒挂的钟,横贯于一根木杆上。壁画中间四屏上各绘有“金人”、“石人”、“玉人”等形象,其前胸或后背题有“金人”、“石人”、“玉人”等字样。最右端的一屏上绘有生刍、素丝和扑满。屏风画的形式,“为三国以来南北朝隋唐时期常画的形式。到唐代有六曲、四曲的屏风,这形式曾经传至日本,为封建上层社会室内装饰的必备之物”。①在墓室中绘制屏风式壁画可能在汉代已出现,唐代亦盛行,特别是六屏式屏风画和墓葬壁画是唐代流行的形式,往往都蕴含有历史故事。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另一幅唐代六屏式壁画《树下人物图》,所画都是树下人物,人物或交谈,或聆听,或指点,或对话。常任侠先生认为:“若果用历史人物来比附的话,第一条可能是王羲之;第三条可能是谢安;第二条借双陆进谏,陈说利害的,可能是狄仁杰的故事;第五条手捧卷轴的可能就是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这些都是在唐人的记载中就很驰名的。第四条人物的臂上,架有一鹰,这与开元天宝时期李隆基爱好鹰鹘有些关系。”②常先生并对这幅六屏式壁画的内容进行了考证,理由也是说得通的。常先生可能未见那幅“六屏式鉴诫图”,故也未提及。但它所反映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也是西域汉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为人处世之道。因为这幅“六屏式鉴诫图”是以形象的画面在劝诫人们应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自己。每当“欹”这种容器内空或盛满水时,容器就会倾斜或翻倒,只有盛水适中时,才能保持平衡,这是在形象地劝谕人们要谦虚,勿自满。“金人”、“石人”、“玉人”是将儒家列圣做人的鉴诫宣示以形象:“金人”,是教人凡事要“三缄其口”,谦虚谨慎,勿骄勿躁;“石人”,是主张为人要有所作为,要有正义感,匡正时弊;“玉人”,是劝告人们要节制物欲,修身养性。③右端所绘生刍、素丝和扑满,是在告诫人们为人端正质朴,为事由微至著,为官清正廉明。所画形象可能既是对死者一生道德品格的赞誉,又对后辈有劝诫警示作用。
从丝绸之路汉民族神话意象的绘画到写实作风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唐艺术精神永远是西域汉文化的灵魂,因为这种艺术精神本身就是和汉文化血肉相连的。从阿斯塔那墓室的布局发现,墓主人居于由伏羲女娲画组成的“天上”和墓壁四周描绘生活情景的壁画构成的“地上”这样相联结的空间中,恰恰象征的是以“天、地、人”为基本结构的宇宙模式。墓主人将生活在地下的永远的家安置在宇宙的背景下,他虽然死亡了,但也寄托了生的愿望,他或她将在伏羲、女娲两位天神的指引下,灵魂升天,自己也将成为这个永恒乐土的成员。
第二节 雕塑艺术:神圣与世俗之间
在丝绸之路汉民族文化中,他们的神话、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总是神圣的;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则是世俗的。
“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将神圣事物简单地理解成那些被称为神或精灵的人格存在;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泓泉水,一枚卵石,一段木头,一座房子,简言之,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圣的事物。”①那些雕塑的偶像及其膜拜仪式当然是神圣的,而再现墓主人生前世俗生活的人俑、动物俑、镇墓兽之类的明器也是神圣的吗?按理,无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多么高贵,但他们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再凡俗不过了。只是当他们离开人世间时,所进行的隆重葬礼连同象征生前生活的明器均被神圣化,凡俗之物成了神圣之物。
俑与神偶尽管制作材料相差无几,但功能大相径庭。神偶,往往以造型的形式被看作是神圣存在的代表,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俑虽然也以造型形式出现,但并不是膜拜的对象,而只是人们幻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的观念的反映。在以人俑、动物俑随葬之前,曾出现过人殉和动物殉。“父系氏族兴起以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的现象,随葬品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种类增加了,有生产工具、陶器、装饰、牲畜和奴隶,另一方面出现了随葬品多少不一的现象。”②富有者,如氏族酋长等,随葬时往往有大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牲畜,甚至以奴隶殉葬。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新型个体家庭的兴起,活殉的情况就有了改变,俑葬出现了。但是俑不是作为现实中人和物的替代品出现的,而是在展示墓主人的阴间生活。在中国丧葬文化中,俑本专指俑人,但以后把动物形象也包括进去了。“这些俑是要在阴间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人并且所有的俑都必将发挥其实效”。③因此,俑是显示墓主人社会地位的,它的实效也表明其功能和职责是最重要的。
西域汉族墓葬中的俑集中于7~9世纪,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时期,出土俑又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为多。按题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侍奉墓主的俑人和动物俑;二是保护墓主的避邪压胜之神物,如镇墓兽、十二生辰、天王俑之属。④这与中原墓葬中的随葬俑人习俗毫无二致。西域汉俑与中原俑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制作材料和某些人物造型上,它显示的是汉文化一统中的地域特色。阿斯塔那古墓中的俑为彩绘泥俑和木俑,绝少有中原的陶俑,且制作材料和方法有地域性。彩绘泥俑一般采用模型和捏塑方法,以木或草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木俑采用刻、削、琢、旋、磨等工艺,成型后再施以彩绘。俑人和动物俑除唐代常见的仕女俑、吏俑、乐舞俑、武士俑、胡人俑、生育俑、天王俑、家畜、家禽俑等以外,还有反映高昌、西州汉人现实生活的劳作俑、杂技俑、牛车俑等。
自汉代以来,西域就陆续有中原的汉族居民迁入,于是像高昌这样一些汉族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社区社会。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得知,从高昌王国到唐西州的400多年中,该地区曾先后有麴、张、马、阚、索、唐、曹、赵、郭、孙、范、巳、傅、董、牛、李、史、焦等姓氏的家族。“家族,在当时的高昌社会中,是一支不可以低估的社会力量,普通百姓人家,要依靠同姓同族的扶持、照应,以求得安身立命之地;权贵之家,也利用血缘、家族的关系,作为维护统治权益、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家族的、血缘的关系,成了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有力手段。生前,人人都感受到形如蛛网的家族的系联;死后,也自不能脱离这一家族关系的束缚。因此,以一个个大家族为单元,营建自己的墓地,成了一种习俗。”①我国汉族的丧葬习俗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丧葬之礼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进行的。孔子就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仅以隋唐时期的随葬制度而言,就形成以陶俑为主的随葬习俗。俑的形象多为出行时的仪卫队列和家居时的奴婢侍者,乐舞俑、游戏俑、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种动物模型也十分普遍。武周后,以黄、白、绿三彩为主的“唐三彩”陶俑为主,镇墓兽也演变为有头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兽。但是并非所有的墓葬的随葬品都如此丰厚,只有帝王、王公贵族及官宦人家依定制可有丰厚或较丰厚的随葬品。这种厚丧的丧葬习俗也被高昌王族或某个家族中的富有者所承袭。麴氏高昌王室是西域汉族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其墓葬规模也算得上宏大了。其中编号为60TAM336的王室墓的“墓室地表曾经建有一座四棱形佛塔,墓道长达29米,墓底深入地下约9米,墓室前部有象征前厅的甬道,左右有象征厢房的龛室,更前为天井,象征着居室的庭院。天井地面以小块砾石铺砌,不同寻常。墓葬随葬品,主要是大量俑像,品类既繁,数量也多。大型镇墓兽、泥塑马、驼、文吏、武士以及舞乐百戏,还有家畜、井、灶等一应俱全”。②按照“事死如事生”原则指导下的俑人、动物俑和镇墓兽都不是随意塑造的,而是按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和生活经历精心选择的,这些随葬物也应是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物。
高昌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普通百姓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作式生活,而是由政事、社交、宴饮娱乐等活动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俑人也大多与他们的上层生活情景有关。仕女俑可能就是他们阴间生活中妻妾、歌舞伎等形象;而一些男俑,特别是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也应是他们处理军政事务的手下的形象;还有些胡人俑很可能是与之交往地区部民首领派来使者的形象;更有些昆仑奴的戏俑、舞蹈俑、舞狮俑、杂技马舞俑等也是供上层人物娱乐时的百戏乐舞者的形象。始作俑者当然是活着的亲人,他们希望通过诸如此类的丧葬手段,力图让死者在阴间拥有同生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死者如同生前一样享尽荣华富贵。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AM206的张雄夫妻合葬墓的两件仕女俑代表了麴氏高昌王国彩绘泥塑的艺术水准。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麴、张二姓是头等豪门,麴氏为王,张氏为将相,又形成联姻关系。张雄的祖父曾任高昌王国左卫将军、绾曹郎中,其父任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张雄的姑母是高昌王麴伯雅的王妃,而他本人则任高昌王国左卫大将军,其二子张定和、张怀寂曾在唐西州、甘州任官。出土的这两件仕女俑只是张雄夫妇合葬墓中木俑的极少一部分,从他们的墓中清理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70多件,还有木马残腿、木俑手脚200余件。两件仕女俑均为立俑,高发髻、白襦衫,一件是绛色长裙,另一件为彩条长裙。仕女俑头部与躯体用木雕刻而成,脸部打磨施彩,表情温静安祥。仕女的手及长裙用衬纸做成,其一仕女俑双手交叠腹前,另一仕女俑为长袖善舞状。这两件仕女俑高36厘米左右,不及麴氏王族陵墓中的高54厘米的仕女俑。可见王族与非王族的俑人在高低大小上是有定制的。王陵仕女俑用整端木头雕成,后施彩绘。因色彩剥落,已无法窥知其艳丽,但仕女俑形象仍栩栩如生。仕女发束“惊鹄髻”,宽衣大袖,休态丰腴,为典型的贵妇形象,似为王室女眷。与仕女体态端庄、神情温顺、安详形象不同的是一些乐舞俑。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这批绢衣木俑制作特殊,形象、表情、装饰都不同于常见的殉葬俑人。男女俑原来均以木雕头部、彩绘面貌,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这种纸臂绢衣的木俑,既便于表现各种舞蹈动作,而又衣着真实,宛若真人”。①用什么材料制作,受条件制约,其他俑人,如仕女俑也用木、纸等材料,关键是人物动作、神态,这些绢衣木俑,男的(实为女扮男装)“滑稽戏调”,女的“秾华窈窕”,完全不似仕女俑肃穆端庄。“十七个绢衣彩绘女俑,不是一般的舞俑。这些女俑不但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而且还有女扮男装的。..这类木偶不直接雕绘成男角,而要刻画成女扮男装,正是当时演出就有由女优扮演男角的缘故。这反映当时男女倡优尚不同台演出,而女扮男装木偶的发现,则用实例证明初唐已有女优装扮生、旦角色演出‘合生’了”。②这些表现歌舞戏弄木俑的出土表明唐统一西域后,西域汉族居民中也流行中原地区的乐舞戏弄。汉唐时期上层人物丧葬中用傀儡表演歌舞伎乐的习俗,很可能也被高昌、西州汉族上层所采用,或者王族等也有私家乐舞队。唐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就认为:“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故高昌王公贵族墓中会出现如此多的乐舞俑。
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等是作为死者阴间的侍从、下属、左右等形象出现的。文官俑和武士俑有站立式塑像和骑马式塑像。骑马式武士俑似为仪仗俑的一部分。张雄夫妇墓出土的骑马武士木俑有三具,全身着铠甲,头戴软盔,骑于马上都呈同一姿势的执兵器状。应是仪仗卫队中的卫士。马身与马腿是两个部件隼接而成,可能受材料的限制,马腿显得僵直,未表现出动感。而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另一具骑马武士泥俑则不同。虽然也是仪仗兵马俑之一,但从装束看,似为将军。此俑因用软泥塑造而成,故线条流畅,无木俑的僵直感。将军头戴尖顶软盔(与兵士有别),穿深褐色长袍,外罩软甲,端坐马上,左手持缰绳,右手作提鞭状(与兵士持兵器不同),马为黑色,体形高大健壮。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审美效果,骑马武士泥俑都堪称这类俑人中的精品,虽然人与马处于相对静态,但人马比例、马的形体塑造以及着色等艺术水准都远在三尊骑马武士木俑之上。高昌(西州)的民间艺人在雕塑俑人时很能把握不同人物的瞬间状态,雕塑出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具文吏俑,其形象为右手握笔,左肋挟文卷,头梳发髻,身着长袍的彩绘泥塑。文吏俑表情谦恭,目光直视,嘴上的两撇胡子有动感。整个神态表明他正在毕恭毕敬地聆听上司的旨意,以便随时起草文告。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汉族居民墓葬中出土的动物俑主要是和他们生活关系密切的骆驼俑、马俑、牛俑、鸭俑等,人身兽头的十二生肖俑也应归入动物俑中。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有一具单峰驼俑,实属罕见。因为古代新疆、中亚等地的骆驼为双峰驼,而单峰驼只生活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等地。吐鲁番出土单峰驼俑,表明此地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这具单峰驼俑,研究者往往给予很高评价:“这件泥塑造型洗炼,决不‘谨毛而失貌’。选择的是静止的一瞬间,使‘一纵即逝’的东西‘获得一种持久性’。它留驻的是整体的神形态势,不容许无谓的枝节存在,又没有漏过有生命的细节——如点睛传神。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形,是服从于神、态、势的形,而不是真驼外形的摹仿,从而在局部与整体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神、形、态、势的统一,它发挥了雕塑艺术体积的深度、厚度、体面变化无穷的特长,发挥了雕塑艺术可以多角度欣赏而不失其生动完整、容纳丰富内涵的优势,克服了造型艺术的有限性,超越了时间,启发人进入驰骋想象马镫的无限性,达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具单峰驼俑成了我国发现的三件单峰驼俑中的极品,它的体面结构与淡淡的色调,真正是浑然一体。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两件大型十二生肖俑——鸡首人身俑和猪首人身俑。前者高80厘米,彩绘泥塑,造型上为鸡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绿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后者高75厘米,上为猪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橙蓼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如此大的生肖俑,实属罕见,且鸡首、猪首毕肖,衣着华丽,宽袖、长裙下垂,舒展自然。人死后以生肖俑作为随葬品,自隋代以来就成为汉民族丧葬习俗之一。对于这种葬俗的流播地区、时间及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十二生肖俑,南方最早见于隋墓,西安见于盛唐前期墓葬,吐鲁番地区见于盛唐后期墓葬。西安唐墓是受了南方的影响,而吐鲁番唐墓当是受了西安唐墓的影响。”②
在西域汉民族俑塑中有一种非人非兽、似人似兽的特殊形象——镇墓兽。这是汉民族想象中的神物,放在墓中是为了避邪镇墓,防止魍魉破坏尸体。据民间传说,有一种叫魍魉的怪兽专吃死人肝脑,而它最怕魌头、方相。《周礼》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大丧,先〓,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相、魌头本是山神的造像,作为镇墓兽出现于战国时期,为双头兽形象,每个头上各插一对鹿角,也有单头兽,插一对长鹿角。汉代的镇墓兽多为四蹄、四爪蹬开,低头用长角作前牴状或蹲伏昂首作守望状。而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镇墓兽多为蹲踞状,有的是兽身人头,有的则是兽身兽头。还有一种人身兽头兽爪,为人立姿,其形象介于人兽之间,类似降魔变中的天王,显然来源于佛教艺术形象。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镇墓兽也多为蹲踞形,有的是人头兽身,有的是兽头兽身。立式镇墓兽是天王踏小鬼的形象。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镇墓兽,通高超过70厘米,泥塑淡彩,狮头兽身,头生双角,长有四只偶蹄;坚如岩石的前额和胸肋,张嘴翘舌,口裂深大,鼻翼和眉头像拧在一起的鹅卵石;深陷的眼窝,夸张地努凸出来的一对眼睛,好似在喷火。这些又同阔胸细腹、肋骨成条排的凹凸明显的斜沟相呼应,给人以吼声震耳的威慑感。①如果从造型看,阿斯塔那的这类镇墓兽完全与中原地区自战国以来镇墓兽长鹿角、偶蹄的传统相符。自战国至唐代,墓葬中放镇墓兽的习俗自长江流域传到中原地区,再辐射到各地,西域也是其远披之地。
阿斯塔那古墓所出土的人首豹身类镇墓兽,高86厘米,为彩绘泥塑像。此镇墓兽头为人头形,头戴兜鍪如武士,面目威严,身躯似豹,足似马蹄,尾部细长如蛇紧贴身后。全身作蹲踞状。这种镇墓兽实际上是人和豹、马等动物的组合形象。武士的威严、豹身的敏捷、马蹄的快疾组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拼凑,而是想象力和现实的结合,创造出这一怪诞的形象才能防止魍魉毁坏墓主人的尸体,这正是镇墓兽的功能所在。
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彩绘天王踏鬼木俑,从其形象看,也应是镇墓兽之类,不过是在形象上借用了佛教传入后的天王形象。它非传统的镇墓兽,而应是镇墓天王,来自于佛教传说,因此,这类形象更有地域色彩,也更人性化。佛教传说中的四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实为守护四方之神。佛教传入中原、西域后,往往在佛寺内塑造四天王像: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持国天王著白色服饰,持琵琶;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缠一龙;多闻天王着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阿斯塔那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由30余块分别雕刻套接后成形。天王高髻束带,身着铠甲,右手上举,左手臂弯曲前伸,穿红花裤,系扶腿,足蹬靴,右足下踏一小鬼(可能就是魍魉)。虽然天王衣著依现实生活中武士打扮造型,有世俗化意味,但双目怒视,龇牙咧嘴,的确有威严感,其形象足以震慑魍魉之类。天王用于镇墓,是西域汉族居民依据现实生活和佛教信仰的创作,它不拘泥于传统的镇墓兽形象,采用更人性化的创新思维,大胆把佛教传说形象用于墓葬。由此可以证明,一些神圣事物完全可以用于现实目的。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俑人中有一种特殊的形象——黑人形象,有研究者称之为黑人与戏俑,也有人说是昆仑奴形象。这一俑人为彩绘泥塑,上身赤裸,下身着橘红色短裤,赤足,皮肤施黑彩,短卷发,嘴唇较厚,双手正握棒舞弄,此俑人高仅12.5厘米。该俑与西安南郊嘉里村唐裴氏墓出土的陶俑如出一辙,不过阿斯塔那的彩绘泥塑俑人出土于王族墓中而已。孙机先生认为,这类“黑人”俑不应定为昆仑俑,而是所谓的僧祗,昆仑俑是南海昆仑国人被夸张强化所致的形象,而作为“黑人”形象的僧祗是大食自东非掠买的黑人,与大食有外交事务关系的唐朝高官也养成家养黑奴的恶俗。所以这类黑人俑应是僧祗的形象。①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鞠氏王族或唐西州高官有养黑奴的恶俗,但黑人俑的出土至少说明西域汉族上层人物对唐长安高官人家养黑奴是仰慕的,故以这类俑人随葬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罢了。
第三节 汉锦唐绢的艺术品格
尽管人们把古代贯通欧亚的陆路通道冠名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等,但这些名称远不如“丝绸之路”久负盛名。这条自我国长安起始,途经西域广大地区,曾远达罗马、叙利亚的陆路丝绸贸易通道虽然存在了一千多年,但作为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专用名称——丝绸之路,则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外学者不仅把丝绸之路看作是古代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而且还把它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不争的事实是,各种文化的传播、交流、辐射,最初的确来自丝绸贸易,中国的丝绸成了不同文化背景民族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它早已超脱了其有形的物质形态,而深入到丝绸之路周缘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诸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升着整个人类的文明程度,因此,丝绸之路也具备了文化符号的功能。历史学家把古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叙利亚总督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败在安息人手下的原因归罪于安息人那令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斓的军旗上,安息人的军旗正是用中国的丝绸制作的。古罗马人正是在卡尔莱战役中初次接触到中国的丝绸:“丝绸比先前所有的纺织品都更加绚丽多彩,因而很快为罗马社会所熟悉。叙利亚战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织物,它可能是在几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到手的。卡尔莱战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恺撒在罗马祝捷的时候,借机向罗马臣民显示夸耀各地所展现的奢侈品,即为他的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奉献的一批丝绸织物。因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惊诧赞叹。..在卡尔莱战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①被西方人称为“赛里斯”的中国丝绸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仍然还是欧洲妇女追求的时尚,妇女们一改十五六世纪追求单色呢绒料的时尚,“而到了十七世纪,又掀起了抢购‘草原式图案’缎纹织物和‘印度之花’织物、‘土耳其式’的塔夫绸、‘米兰式图案’织物的风潮。到了十八世纪,丝绸工业又受到了追求大幅图案为时髦之风潮的刺激,这种图案形成了一幅幅真正的图画(其设计图纸是被当作绝密资料加以保护的),带有裙环的那种宽大裙子的式样需要特别宽幅的丝绸布。..终于在欧洲首次出现了汉人式的图案:如佛塔、竹桥、人像等等。”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丝②绸服饰的款式、图案形成不同的审美追求,但丝绸文化的魅力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
丝绸,这种令古罗马人目瞪口呆、惊诧赞叹的织物几乎不进入艺术史家的视野,虽然用丝绸缝制的服饰,人们宠爱有加,但它不如青铜器、瓷器那样成为学者们眼中的艺术研究对象。像格鲁塞的《东方的文明》、巴赞的《艺术史》这样的艺术史名著也只字未提丝绸工艺、图案艺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其实“纺织物品通常经过某种加工以增进它的美感,..在布料的装饰方面由世界各民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风格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习惯。例如,主题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象征性的,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往往来自他的信仰和理想”。③新疆出土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汉唐时期的丝织品或许可以大开人们的眼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梦幻般的汉锦唐绢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判断。
由于丝绸织物不宜保存,在世界各地极少有出土,只是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由于干旱少雨,才在汉代以来的墓葬中发现了品类众多的丝织物。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无论是丝织物的品类、织法、纹样、色彩,还是主题、题材、装饰手法都印证着东西文化交融、互渗这一事实。人们发现,中国丝绸西传的结果,竟派生出波斯锦、粟特锦、叙利亚丝织品以及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的织物等。这种东传西渐的踪迹在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及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汉唐丝织品中都能寻觅到。
新疆出土的汉代至唐代的丝织物与丝绸之路走向吻合,也与汉族居民在西域的分布合拍。汉唐丝织品的出土地点几乎全集中于丝绸之路的南北道。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发现了包括锦、绮、罗、各色绢、缣及刺绣等汉代丝织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则出土了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这里是麴氏等汉族政权高昌国和唐西州的所在地,丝绸生产和贸易都曾盛极一时,仅出土的丝织品就有锦、绢、绮、绫、〓、染缬、刺绣等。在某一区域出土品类各异、色彩缤纷的众多丝织物,非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莫属。仅从这些丝绸织品东西合璧的图案纹样就不难窥见这座古代丝绸博物馆的风采。如果从主题着眼,我们可以将汉唐时期的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分为吉祥图案和祥禽瑞兽图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汉锦主题基本属于吉祥文字纹锦,在满幅变幻莫测的动植物纹样中,嵌织有隶书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韩仁绣文宏吉子孙万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长乐明光”、“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这与人们普遍存在的“祈福赐祥”心理不无关系。祥禽瑞兽纹锦常见的有“龙凤纹锦”、“鱼禽纹锦”、“对鸟对羊树纹锦”、“飞风蛱蝶团花锦”、“联珠对鸡纹锦”、“联珠鸾鸟纹锦”、“联珠鹿纹锦”等,联珠纹主题的纹锦多见于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高昌地区。假如从题材去分析,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文字纹都久盛不衰。据研究者统计,仅楼兰、尼雅所出的东汉锦纹样就有二十余种。①其实,自汉至唐代西域丝织品的纹样远比这要多得多。假如从构图思路看,汉唐时期西域丝织物的纹样严格遵循着对称平衡的原则,这几乎是装饰工艺的不二法则。但对称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布局的变化,上下对称、左右对称、中心对称、边缘对称等旨在追求严谨中的变化。动物纹样、植物纹样、文字纹样、几何纹样之间的有机搭配,也在追求一种各纹样间的对称平衡效果。如果着眼于色彩、工艺,就能发现其色彩的绚丽和编织技巧的娴熟。汉代锦、绮、绣等丝织品的色彩就有藏青、宝蓝、天青、海蓝、湖蓝、墨绿、葱绿、粉绿、绛紫、绛红、褪红、深棕、沉香、驼色、白色、绯红、黑色等多种。北朝至唐代高昌(西州)的锦、绮、绫、印花绢、缦、缣、纱、罗等的色彩有褪红、朱红、海蓝、绢黄、藏青、海蓝、天青、葱绿、湖绿、草绿、叶绿、绛红、橙红、银红、棕色、白色等。在色彩上汉唐之间有承袭关系,但也明显有创新,如唐代织锦除沿袭汉代以深色为地外,大多以白色或浅色为地,用绛、绿、青、黄等色显花,花纹间色彩互换富有变化。丝绸品的工艺从平织、平纹重组织、显花起绒圈重组织、经线显花、纬线显花、刺绣到印花法都出现,仅印花,唐代就有蜡染法和绞缬法。汉唐西域丝绸品就纹样而言,纵向流变和横向融合都呈现出创新和互渗的特征。“花纹方面,汉代那种宽带式花纹布局,到了唐代改为孤立的花纹元素散布全幅。花纹母题则西方式植物纹盛行,包括忍冬纹、葡萄纹等。波斯萨珊朝式的那种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唐代很是盛行”。①联珠圆圈内是对鸟、对兽图案。但这种合璧并非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而是各种文化在长期接触中,从冲突、碰撞走向融合的结果,它虽脱胎于原来的文化,但并非原来的模样,一经消化吸收和文化整合后,成了本土化的艺术品种。盛唐气象就是指其化解东西文化的大气,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岂能例外。
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是汉锦的主要发现地。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1980年在楼兰城郊古墓群孤台墓地就出土汉锦53件;1995年在尼雅遗址编号为95MNIM8号的墓地出土的汉锦织物10多件,其中就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1983~1995年在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中,出土包括织锦、绢类丝织物33件。汉锦上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是纹样构成的基本特征。楼兰出土的一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褐色地,黄、蓝二色里花,经锦。变体云纹和攀枝叶蔓中夹瑞兽,瑞兽间织隶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吉祥语”。②而另一件1995年出土于尼雅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重平纹经锦,平挺厚实,图案题材新颖,有虎、龙、避邪、仙鹤、孔雀、瑞兽图案,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③山普拉出土的丝绸物多为死者的帽、衣、裤、护颌罩等服饰类,有锦、绢、缦、绮等。其中织锦有两件,一件蓝地,显黄色菱格、曲线、点纹;另一件有幅边,绛色为地,宝蓝、米黄、粉绿和白色五种颜色显花。①营盘出土的属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织锦是以“吉祥云纹、祥禽瑞兽为主体的图案。有夹织立禽和隶书‘登高’、‘寿’、‘右’等文字锦,也有图案横向排列的卷草纹锦和方格纹内相同的瑞兽纹锦”。②西域以织锦为代表的汉代丝织品,“其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纹饰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现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其间穿插种种吉祥用语”,③具有汉文化特征。许多祥禽瑞兽是有象征寓意的,如对鸭图案中的鸭子意取“压子”;老鼠象征长寿;独角兽——避邪有祛邪除凶的寓意;龙凤象征吉祥等等。汉代丝织品中出现的这类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纹饰是一个时代思想与信仰的折射。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更现实,也更务实,“显然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世俗化,成为一种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就是追求生命的永生。而现实生活中的‘富贵’与子孙的‘繁衍’,却成了更现实的生活中‘幸福’,人们的渴求日益现实,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字样就是明证,人们日益实用的生活观念正是在这里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④当汉朝统一西域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思想、信仰上的趋同性已深深扎根于西域各地居民的心中,所以才会在那么多墓葬中出土如此众多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的丝绸织物——生用死殉,追求着生命的永生和一生的“富贵”,并期望“幸福”庇荫子孙后代。就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些我国古代星占术上的占辞用语也出现在织锦上,也可以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祈语,反映了西域各地居民同中原汉民族同样追求吉祥昌盛的良好祈愿和朴素的感情。
从北朝到唐代,西域丝织物的产地主要在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含西州)等地,但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物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工艺技术和图案风格。在众多出土的丝织品中织锦和绢(染缬)最为普遍。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的织锦是有差异的。6世纪前的织锦图案单位直行排列,作横幅相间的祥瑞兽纹,形成瑞兽纹锦、狮纹锦等,图案内容和布局与汉锦相似,但动物形态或立或卧,都比较稳定,是汉锦风格的继续;而到了唐代,有两类图案的织锦居于主导地位:一为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图案,二为联珠对禽对兽图案。⑤植物纹样图案织锦品类多,纹样多变,其中的“宝相花斜纹经锦”的纹饰图案是唐代汉地的主流图案。魏晋以来,中原曾盛行在金银器、铜镜上镶嵌珠宝类花,在中心花蕊及花蕊和花瓣交接的地方镶嵌以珍珠和宝石,图案上用佛教艺术的退晕色方法,以放射对称的格式,组成盛开、半开、含苞的花与花叶等富丽堂皇的团花,谓之“宝相花”。到了唐代,宝相花图案又出现在织锦图案中。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件唐云头锦鞋,其鞋面就是宝相花图案:“系用宝蓝、墨绿、橘黄、深棕四色在白地上织簇八中心放射状图案花纹的斜纹经锦,以中心部分,为六个花瓣组成的圆形朵花,围绕着中心朵花则是簇八放射对称的如意勾藤,在对称如意的地方,缀以花蕊及花叶。”从花的图案看,似是雪花的变形。宝.①“相花斜纹经锦”可能就是唐代的“瑞锦”,有“瑞雪兆丰年”、“雪花献瑞”的象征寓意。
阿斯塔那出土最多的是联珠对禽、对鸡、对兽图案的织锦,统称为联珠纹样织锦。联珠纹样是萨珊波斯的传统图案。3世纪兴起的萨珊波斯王朝流行一种装饰性程式化倾向的纹章艺术,出现在织物和金银工艺品中。“其上即根据此种风格表现着为求装饰效果而多少予以程式化的幻想怪物:头和前爪似猫而翼和尾部如‘开屏’孔雀的‘龙孔雀’;或武士骑在半狮半鹫的‘格力芬’或带翼的狮的背上,和其他‘格力芬’作战;或完全对称的成对野羊或雄狮,各举一前足对面而立;或如迦勒底—亚述所喜好的题材,即程式化的狸形野兽吞食着同样程式化的鹿类动物”。②在这些织物中,往往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圆圈内常填以对马纹、对鸟纹和对鸭纹,也有填以波斯式的猪头纹和立鸟纹。③但是吐鲁番出土的联珠纹锦并不是波斯的工艺品,而是根据西域商人订货需求由汉人织作的织锦,其产地是蜀地,因此,这类织锦也称为蜀锦。“联珠禽兽纹斜纹纬锦有组织细密的精品,如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也有像联珠戴胜鸾鸟纹锦那样组织粗松的制品。这种联珠禽兽纹斜纬纹锦是这个时期墓葬中最常见的纹锦,发现的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显然,这意味着它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另外,我们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其他间接资料也可以知道这种有别于传统的图案,当时在我国内地已较为流行”。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件联珠“胡王”锦。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织锦采用倒置循环提花法织成上下对称的图案,米黄色地上有橘红、绛红色显花,在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手执长鞭,深目高鼻,花环之间饰以复合忍冬四叶纹。它显然是萨珊波斯式的联珠动物纹样织锦,但所织“胡王”汉字表明它确系汉地产品,估计是为九姓昭武或萨珊波斯王族专织的。在丝绸之路中端的高昌出现,可能是商品交易的结果。植物纹锦中的忍冬纹、葡萄纹也是西来的产物,但也很快被唐代织锦所接受。
唐代高昌、西州丝织物以绢类为大宗。绢也称“素”,本为一般平纹织物,经纬密度大致相等,除本色外,染成大红、粉红、墨绿、叶绿、鹅黄、绛紫、茄紫、翠蓝、湖蓝、藕荷等颜色图案的称为染缬,其染织方法又有绞缬、夹缬之分。当然,染缬也用于缦、缣、纱、罗、棉布等工艺上,这些染织物也统称印花丝织物。绢类丝绸物的绞缬法有两种:一种是将谷粒大致匀称地包在织物上,用线扎紧,染色,晾干后,拆去扎线,即现出遍地大小相等的菱形圈花纹;另一种是将织物折成连皱,用针线穿过,然后将线抽紧钉牢,染色后晾干,拆去穿线,即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①夹缬的方法是将织物绷紧,夹于镂花夹板中间,涂以蜡,再解去夹板,染后晾干,剥去蜡即成,因涂蜡处未吸收染色,即显出花纹。②夹缬法就是通常所称的蜡染法。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染缬织物看,主要以盛唐为主。墓葬出土的数件夹缬绢,一染绛地花云,一染棕地散花,一染土黄地花云,都绘制工致,浸染均匀,是唐代蜡缬的精品。③唐代流行的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纹样就与这种染缬工艺有关。夹缬法不仅适宜于染制植物花卉图案,还可以印染较复杂的人物、动物、山石树木在内的组合纹样。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狩猎纹印花绢片就属此种。此为平纹印花绢织物,纹样内容为,在深绿地上显出粉绿的狩猎图案:骑马的猎手飞马张弓射狮,猎犬逐兔,猎鹰追飞鸟,天上流云,地下山石树木,图案呈上下对称,有强烈动感。唐代夹缬绢上的狩猎图案与5世纪的骑士(狩猎者)对兽纹锦图案可能有渊源关系。另一件纹锦同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纹锦黄地,以深青、浅蓝、浅黄色显花,以数个相切的圆环为图案骨架,其内饰狩猎者射鹿、对象、对狮、对驼等纹样。圆环之间填对马和忍冬纹样,圆环相切处又以仰莲相缀。除联珠纹鸟兽纹样流行于高昌等地外,还有一种人像、动物、树木等组合式纹样同样流行,不过它的主题是骑士、狩猎者等英雄形象与狩猎对象关系的表现。这些纹样是九姓昭武和萨珊波斯常见的纹样。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类题材还源自西域游牧民族的狩猎生活,虽然高昌、西州作为农耕民的汉族居民并不狩猎或根本无猎可狩,但与其关系密切的突厥人确实是典型的狩猎、游牧民族。不过,其主要影响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和萨珊波斯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萨珊波斯艺术的生命力超过了王朝生存的年代,直到九世纪在中国北方还有余绪可见。..由于进入中国新疆的一些画师来自伊朗东部或吐火罗地区,所以在画风上也必然带来波斯绘画的格调”。①高昌地区就有粟特人的聚落。汉锦唐绢正是在吸收、化解各种艺术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品格,这是它的大气,也是它的力量所在,这正是流光溢彩的中国气派,西域的汉族居民也受惠于此。
第四节 建筑艺术的绝响
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建筑按其功能可分为世俗建筑和宗教建筑。世俗建筑包括城市建筑、城堡建筑及民居等地表建筑,墓葬属地下建筑。宗教建筑主要是寺庙建筑、石窟建筑和塔类建筑。在此,仅探讨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世俗建筑的问题,而宗教建筑将在宗教艺术章节里涉及。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汉式世俗建筑自汉代屯田时已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高昌国和唐安西、北庭都护府期间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格局和城镇、城堡建筑。清代则是汉式建筑的极盛时期。汉至唐代的汉式世俗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建筑,即生土夯筑、地表下挖和土坯垒砌三种类型,这是适宜于西域气候、材料和施工特点的建筑,无需像烧砖瓦那样费力费时。当然修建这类土木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囿于建筑材料,生土是最便捷、最廉价的建筑材料。唐代已将砖、瓦用于建筑中,而在清代,砖木结构的世俗建筑就不仅仅是城市商号、官邸府衙了,会馆、民居也开始有了一砖到顶或半砖半土式建筑,园林式建筑此时也已经出现。
两汉时期的西域汉式建筑已不可寻,即使像两汉都护府遗址的确切位置也成了历史悬案,有待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更遑论一些完整的地表建筑了。现在也只能从遗存的几段残垣断壁、几座烽燧和零星的文献记载去推测了。西汉政府曾在伊循、楼兰、轮台、焉耆、姑墨等十余处屯田,东汉时伊吾庐、金满、柳中、高昌壁、疏勒等多处屯田也史有明载,这种屯垦延续到魏晋时期。这些屯田地区也是汉族军民的聚居地,有城堡、城镇等建筑。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起,就对古城的性质文讼不断,考古学家孟凡人先生认为它是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并有完整的行政机构。①这个时期屯田的楼兰城是以衙署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城镇建筑:“城中布局,从现存遗迹依我们发现的古水道为轴线,古水道由城西北向城东南流贯,大致可分两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可能是佛寺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外,西部和南部还有大小院落..西南区的残存遗迹,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间房址,整个建筑呈〓形,正中是用土块垒砌的三间房。..三间房东西两厢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②从考古发现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些建筑的材料是西域传统的土坯垒外墙,木料搭顶,以红柳枝作夹条抹草泥的内隔墙结构,至于屋顶是西域传统的平顶屋还是汉式的人字形屋顶,已无法得知,更不用说整个建筑的装饰工艺了。楼兰古城的整体布局是一个东面城垣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的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城址。③两汉以来这种用本地材料构筑的汉式建筑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筑城而居的定居模式,是中原传统与西域特色的完美结合,它对唐代的西域汉式建筑影响极大。
两汉时期西域屯田之处所还属于城堡、城镇型建筑,还不具备古代城市的功能,即使像高昌、交河在两汉时期也是筑城而居的屯田地,其建筑只具有军事城堡的性质。既屯田又要打仗,面临匈奴的威胁,这些屯田城堡应是易守难攻的。真正意义上的西域汉族古代城市当然要属高昌,它是在两汉时期屯田城堡高昌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凉时置高昌郡,从北朝时期麴氏王国的都城到唐代的西州时期,高昌城是西域汉族最具规模的城市建筑。9世纪后又成为回鹘王国的亦都护所在地,但总体上还是北朝到唐代高昌城的基本格局。现存高昌城遗址城三重,是不同时期的遗存,外城方形,周长5公里,内城居外城中部,宫城居北,外城西南角为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佛寺遗迹。高昌城门外面为曲折的瓮城。高昌城的外城墙高达12米,每面有2~3座城门,分别冠名为“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内城北面的王宫遗址还可辨认宫城为长方形,正中偏北为一小城堡,堡内西北有高台,台上有一个高达15米用土坯砌成的高耸建筑,似为唐以前高昌王的王宫遗址之一。与“城堡内建筑物”相对的中轴线上,还有四层殿的基址。殿基以东存遗址七处,殿基西有四处。可能是不同时期王宫建筑的组成部分。外城东南和西南是寺院建筑和工商业作坊。寺院由山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建筑组成。在寺院遗址外的东南和东北是“坊”的遗址,东南的坊有两排整齐的建筑遗址,在南北两排相对的房屋建筑之前为广场,南排房屋后又有一个广场。坊的四角,都有巷口式通道,通向坊外。据文献记载,高昌的作坊、商行已形成规模,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果子行、彩帛行、瓦器行、铛釜行、菜子行等,①手工业工匠有木匠、铁匠、缝匠、皮匠、甲匠、石匠、泥匠等。建筑遗存也证实存在各种作坊和商行。高昌城的平面布局“宫城在北,内城在南,有大面的高大建筑物,与唐代长安城的宫城、皇城的位置相同,应是高昌最高统治集团的驻在地。至于外城东南和西南的寺院和工商业的坊市遗址,又与唐长安外郭城,或一般城市的布局相类似,应当是一般市民的居住区。总之,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的平面布局是相当接近的”。②
交河故城是完全不同于高昌故城的古代城市建筑。它早期是车师前部的王廷,自西汉末年起,曾先后是屯田常驻地和高昌王国的交河郡、交河县所在地,9世纪中叶之后,又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交河州,一直到14世纪因战乱等原因被弃置。交河故城并非中原传统意义上的汉式地面建筑,它并没有用砖、石等建筑材料堆砌而成,而是在一块长1650米、宽300米的台地上向下挖凿而成,这是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观。当街道、房屋等建筑向下挖一定深度的土方后,再将挖出土方夯筑其上,免去土方拉运它地之役。现存的交河故城是唐代汉族居民修筑的遗址。贯穿全城南北的一条大街把居民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北端是规模宏大的以寺院为中心的寺院区,东区南部是官署区,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就设在此处。因全城四周崖岸壁立,并不需要城墙防守,故城东、城南各留一个城门,供居民出入。故城的大街小巷、民居平房、佛寺佛塔、手工作坊、两层官署都是在原生土中掏挖而成。故城的不少建筑下为窟洞,上为平房,两层乃至多层。这种建筑构造样式被称为“陶复”式的地窟,其特征是:(一)上半截“累土”,下半截“凿地”,作半地下室式;(二)窟顶中央“开口其上”,名为“中露”;(三)通体作圆形,故称为“环堵”(“圜环墙”)。最初的“陶复”式地窟,只有一个出入口,即“中雷”。人们进出窟室都必须通过窟中央柱形梯子经“中雷”上出下入。以后,这种“陶复”式地窟在设计和建筑上有了发展,人们在南壁或东壁基部挖开一个洞口,作为“户”(门户),并在户外挖出一道斜坡梯形的“门道”。这样,窟中人便可以通过这门户和门道上登到地表上来。①壁门在不同季节还有空气对流、御寒、增加阳光照射的作用。交河故城的这种“陶复”式建筑显然是因地制宜,夏避暑冬御寒的理想居所。交河城的寺院占地面积为5000多平方米,虽不及高昌城寺院面积大,但建筑布局和风格均异于高昌寺院。交河城的寺院也是掏挖原生土而成,由山门、大殿、僧房、庭院等建筑组成,城北是一组壮观的佛塔群,以中央大佛塔为主,四角各有25个小塔,形成纵横各5个方阵,共计101个。佛塔的这种形制是当时汉族居民中佛教密宗信仰的反映。
唐代曾在伊州、西州、焉耆、乌垒、于阗、疏勒、庭州、轮台、清海、碎叶等处屯田,并建有伊州、西州、庭州和四镇。郡县制设立后的州、县所在地都形成了一定的城市、城镇规模。巴里坤县的大河古城和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均分别为唐代屯田驻军的伊吾军和庭州城的遗迹。从出土的莲花纹砖和瓦当看,这些城堡、城市建筑已用砖、瓦等建筑材料,建筑样式和风格也一如内地唐代汉式建筑。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城市建筑、宗教建筑、宫殿建筑和四合院民居及园林建筑始终占主导地位。清代西域进入大统一、大移民、大融合时期,也是西域汉式传统建筑的辉煌时期。乾隆年间的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建省后以绥定为伊犁府治城),新疆建省后的省会——乌鲁木齐(时称迪化)都是以汉族传统建筑理念建城的。它们与喀什噶尔形成清代新疆的三大城市格局。坐落在现伊宁市西30多公里处的惠远古城初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后扩建,城周5公里,城高5米,是新疆建省前清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一座商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城市。通常将清代惠远和绥定、宁远、拱辰、广仁、瞻德、塔勒奇、惠宁、熙春称为伊犁九城。惠远旧城1871年毁,1883年又在其北修建惠远新城。新城周长近5公里,城垣高约5米。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以直通四大城门的四条大街构成城市基本布局。四条大街上还有48条小巷,组成商业和居民区。钟鼓楼是一座中国传统风格的三层三檐歇山顶的砖木结构建筑,雕梁画栋。屋檐铺有琉璃瓦,每层12根檐柱绘有花卉等图案,每层檐角均吊有小铜铃。钟鼓楼正东不远处是伊犁将军府旧址,现存府门、石狮、金库、厢房、凉亭等建筑。伊犁将军府的庭院花园古木参天,亭台布于其间。仿江南园林的花园曲径通幽,给人幽逸、明净之感。伊犁将军府花园是迄今所知的新疆最早的汉式园林建筑。
中国传统城市都是按照自然地形布局理论规划的。《管子》认为,建城的原则是“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原则也在乌鲁木齐建城原则中体现出来。早在汉唐之际,乌鲁木齐附近就有屯田的城堡,但还不是传统的城市,从清乾隆年间到光绪年间才逐渐形成城市规模。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土城基础上,又于二十八年(1763)添加四门建迪化城,为雏形期。乾隆三十年(1765)在旧城之北另建新城,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始建巩宁城(俗称老满城),为扩展期。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迪化为省会,光绪十二年(1886)扩建筑城,城周5.5公里,有惠孚门(东门)、丰庆门(西门)、肇阜门(南门)、景惠门(北门)四个正门和小南门、小东门、小西门3个偏门组成城市基本结构,为定型期。乌鲁木齐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其东、南两侧是天山山脉,西、北两侧为平原地带,城依乌鲁木齐河而建,雅玛里克山(俗称妖魔山)与红山南北对峙。因依山势、水势而建,乌鲁木齐城郭是不合规矩,道路是不中准绳的,但与古人提倡的建城原则不相悖。对于老迪化城,清代文人椿园七十一在其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撰《新疆纪略》中写道,迪化城“字号商店,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这还是建省前的情景。清代是乌鲁木齐传统城市建筑形成和定型的时期。1884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作为省会,以大、小十字(街)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大十字是以老“津商八大家”永裕德、同盛和、复泉涌等和新“津商八大家”永盛西、裕昌原、庆和春等为代表的商业街,店面鳞次栉比,商号林立;小十字一带则是戏院、国药店、清真饭馆、老君庙等云集。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后,在南门外的南梁地带由俄国开设了吉祥涌、天兴行、德盛行、吉利行等俄商洋行八大家,形成洋行街。20世纪20年代后,南关一带则是少数民族商人经营的商业中心。乌鲁木齐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于是内地各省的民间文化也就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形成以木架结构为主体的寺庙、商店、会馆、四合院等汉式建筑风格。红山一带是玉皇阁、大佛寺、地藏寺、北斗宫、龙王庙等;西九家湾一带是关帝庙、仙姑庙;建国路是观音阁、娘娘庙;东风路是定湘王庙、两湖会馆、左公祠;中山路是城隍庙、龙王庙、山西庙、陕西会馆等;其他各处还分别有文武庙、积骨寺、八仙庙、财神楼子、药王庙、马王庙、火神庙等。因乌鲁木齐河将乌鲁木齐分成河东河西两部分,故城东、城西就由桥来连接,原名“虹桥”、“巩宁桥”的西大桥成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这种依山傍水而建的移民城市无内地传统城市建筑以中轴线贯穿其中坐北朝南的严格布局,因为它只能依地形走势而建。其建筑风格也不是一元的,而呈多元化发展,因为内地南北各省移民带来了不同风格的建筑艺术,且因功能而异的建筑又形成不同风格。外来文化的冲击,城市建筑又呈现出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二元结构,这正与新疆近代文化特征相契合。
西域汉族民居建筑除高昌交河的“陶复”式的特殊形式外,基本上是上栋下宇型的居住样式。但因天山南北的气候、降水量差异,又分为平顶形和两流水形(即“人”字形)民居建筑。天山以南地区干早少雨,其民居基本为一面形的平顶屋。这种民居用土坯砌墙,平顶,住房多在北面,房内设土炕,自成一家一户院落,院落呈正方形。而天山以北地区因气候寒冷,雨雪多,民居多用砖石砌成,屋顶呈“人”字形,房间一般为一明两暗式,坐北朝南,也有坐西朝东的。从近代新疆的汉式民居看,农村与城市有所不同。农村建筑是前庭后园式,即正房前是庭院,侧为厢房,往往是库房、牲畜圈等,而正房后面是菜园、果园等。城市民居最典型的是北方四合院式建筑。自清代乌鲁木齐兴起津商八大商行后,就在大十字商业区周围出现了北方四合院式民居。大十字一带的八条东西巷、藩台巷子、三角地、满城、北梁一带是四合院最集中的地带。乌鲁木齐标准的四合院是清代末期民国初期天津杨柳青商人刘贵铭建在藩台巷子的四合院住宅。“这个四合院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前面的高台阶上有两扇黑大门,门槛高约30厘米,是活的插板式,可以拿下来,门槛的前两侧各有一块方石凳子,大门过道宽约2.5米,接着是黄油漆的木质二道门。院子为正方形,约15米见方,用青色大方砖铺地。有南、北住房各三大间,东西住房各三小间,四幢住房相对称,前廊后厦,布局合理。另外还有厨房、炭房、厕所、水井和渗水井等设施。所有房屋均为木质框架结构,一砖到顶。南、北房的中间屋为堂屋,两侧是卧室,室内是小方砖铺地,有火炕取暖,火炕的一端有放置被褥的长立柜(俗称被搭子),炕沿的上方和两侧有雕刻的木质隔扇。全院房间的门窗,均以古式花木格子装饰。院落中间砌着花坛,每到夏天牵牛花顺四面花架爬上屋顶,花红叶绿,整个院落显得古朴静谧”。①四合院式建筑体现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封闭空间的自闭性和不张扬性,并使建筑及装饰更富有层次性和虚实变化。同时“如果家族人丁兴旺,有财有势,家宅可以向其四周无限扩展。..这种住宅形制,符合我国古代的家族型制及其发展”。②
西域汉族建筑文化在形成地域化的过程中,与西域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之间是一种族际文化共享关系。汉族建筑文化不仅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也吸收了汉族的建筑文化。清代是汉民族与满族、锡伯族之间族际文化共享频繁的时期。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至伊犁屯垦戍边的锡伯族被清政府组成八个牛录,各牛录建筑虽属清朝八旗制的军民兼用型,但城堡及官署、民居均是汉式建筑。每个牛录的城堡由高大夯实的正方形城墙组成,城墙上有垛口,并在东西南北砖砌四个城门,城墙周长七八里至十里不等。城内是“牛录”办事机构、胡同式民居以及粮库、兵器库和监牢等。这种城堡式建筑和古代汉式能防易守的城堡建筑从形制、布局和功能上都相同。甚至官署、关帝庙、娘娘庙和民宅也是汉式的。清末民国初年伊犁地区锡伯族的“人”字形大屋顶房本身就是汉式结构的宅屋。这种房屋也是木质框架结构,包括支撑柱和房顶,然后用新疆传统的土坯砌墙,再抹细泥并用白灰粉刷,后期也有砖砌墙的。房顶为双流水型,有伸展出的廊檐,门窗是小木格式的。窗户都很大,用于充分采光。“人”字形大屋通常为一明两暗的三间式,门窗工艺精细,雕刻、绘画显其富丽、典雅。住房与庭院组成典型的锡伯族民居。有人认为这种房屋造型是从满族民居学来的。的确,东北的汉族、满族等均居住一种被称为“东北大院”的民宅,但此类建筑的起源则来自北方的汉式四合院,因此是汉化的产物,锡伯族“人”字形大屋顶房当然也不例外。现存清代锡伯族的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为汉式寺院建筑类型,大殿中梁上彩绘二龙戏珠等也完全是汉族民间传统图案艺术。这种体现在建筑上的文化融合现象正反映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精神。
尽管丝绸之路上的许多汉式建筑随着岁月的剥蚀已成为历史的绝响,但永驻人们心中的是那神圣的精神殿堂,它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辉煌。
第五节 汉唐遗风与屯垦艺术
兴于两汉,盛于唐代的西域汉文化艺术总不免使后人产生怀古之情思,但这绝不是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情,而是一种通过对汉唐遗风的追念,发扬光大汉文化艺术的精神追求。在西域这块热土上,汉唐将士们演绎了多少屯垦戍边的壮举,所以清代诗人总是凭吊这段历史:“至今扪古碣,血渍土花班”(李銮宣《巴里坤城北寻汉永和二年碑》),“摩挲残碣在,唐汉未销兵”(史善长:《到巴里坤》)。抚摸汉唐古碑,深感统一西域责任重大,弘扬汉文化意义深远。清代屯垦戍边、统一西域的举措,将西域汉文化艺术推向新的高度。
清代西域的汉文化艺术总体上讲也是一种秉承汉唐精神的屯垦艺术。往事越千年,清代的屯垦艺术无论是规模、类型、层面、内涵都超过了汉唐。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就开始大规模屯垦,从乾嘉年间开始,新疆建省后又有大批内地移民来到新疆屯垦。清乾嘉年间的屯垦主要是兵屯、回屯、民屯、旗屯、遣屯等形式,屯田地区主要在天山以北以东地区,其中,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昌吉等地已形成相当规模。据乾隆四十年(1775)统计,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之间,这些地区屯垦人数达七万余人,屯田亩数已逾二十八万亩。新疆建省后,新疆巡抚刘锦棠等人制定《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军民屯垦,于是内地汉民“携眷承垦络绎相属”。据《刘襄勤公奏稿》卷一二载,清光绪十二年(1886),仅迪化、奇台、昌吉、阜康、绥来、济木萨尔、呼图壁等地又安插屯垦移民一千九百户。屯垦的目的当然是扩大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但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内地各省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化艺术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族的年节习俗、饮食服饰、南北戏剧、庙会社火、诗词说唱、婚丧礼仪、剪纸年画等都成了屯垦区的耀眼的文化景观。以汉族艺术为载体的汉文化与屯垦规模、移民人数成正比,对整个清代新疆的多民族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近代新疆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翼。
清代新疆的屯垦艺术类型比汉唐时期更加丰富,而且增添了许多新品种。戏剧演出在清代至民国期间的新疆汉族艺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纪昀在其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返京途中所写《乌鲁木齐杂诗》中吟咏乌鲁木齐戏剧演出的盛况:“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并自注曰:“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就连楚调也往往是“低徊唱煞红绫袴,四座衣裳涴酒痕”。显然,自清乾隆年间屯田驻军、内地移民和谪戍遣犯日益增多,南曲北戏艺术也在边城乌鲁木齐兴盛起来,京剧、昆曲、秦腔、越剧、楚调、曲子戏争相纷呈。左宗棠率十万湖湘子弟下天山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时天津杨柳青商贩“赶大营”的出现以及更大规模移民潮的到来,关内各地方剧种在乌鲁木齐等地扎下了根。到19世纪末,乌鲁木齐已有了唱花鼓戏的“清华班”、唱秦腔的“新盛班”、唱河北梆子的“吉利班”等戏班。湖南花鼓戏原是随军的花鼓自乐班在乌鲁木齐登台演出,之后组成“清华班”专业戏班,除唱堂会外,主要在庙会或节日进行演出。秦腔艺人吴占鳌组织的“新盛班”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首次在红山庙会上清唱演出。光绪十七年(1891)以菜农为主体的河北人也组成演唱河北梆子的“吉利班”参加到红山庙会演出的行列中,主要还是清唱。刘锦棠任新疆巡抚期间在乌鲁木齐修建了“定湘王”庙,从内地购置新戏箱,供该庙会演出之用。1917年,由陕西会馆出面,联合陕、晋、甘等地流入新疆的秦腔艺人组成“三合班”,开始在乌鲁木齐及北疆各县演出连台本戏。曲子戏清末出现于陕、甘、宁、青移民聚居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鲁木齐等地出现秦腔、京剧、花鼓戏、河北梆子、曲子戏竞相演出的场面。与内地地方戏演出不同的是,新疆的汉族戏剧出现了“民汉合璧”的现象。维吾尔族京剧花脸演员达吾提、维吾尔族曲子戏演员卡帕尔,回族、满族、锡伯族曲子戏演员等都曾名噪一时。只有在新疆这样的多元文化氛围中才会出现这种族际文化共享的盛况。新疆曲子戏成为新疆地方剧种之一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甘肃民间艺人夏三通组织敦煌曲子戏进新疆演出,之后,它很快被新疆汉、回、锡伯等民族接受,在城乡普及开来。新疆曲子戏是个博采众长、吸收融合各种音乐成分最杂最多的剧种。最早是在陕西眉户剧音乐的基础上,在西进的过程中融进兰州鼓子词、青海平弦、敦煌佛曲音乐等形成。在西渐到新疆演变成新疆曲子戏的过程中,锡伯族的“秧歌调”几乎全被新疆曲子戏吸收融合。“秧歌调”分“平调”和“越调”两种,它是锡伯族西迁前吸收汉族“秧歌调”演变而成的一种戏曲音乐。新疆曲子戏音乐中的“天山令”还吸取了哈萨克族音乐成分。①新疆曲子戏的白口,完全是本地化的新疆汉语和方言俚语,不少还融进了维吾尔、俄罗斯等民族词汇,全国各地方言俚语也夹杂其中,从语言上讲它成了新疆汉族或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都能听得懂的语汇。虽然,新疆曲子戏原型脱胎于眉户剧,但在演进中已非原来的音乐,它一旦与新疆各民族音乐杂交后就显出了自身的优势,这要归功于清代大规模屯垦移民带来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勃兴。清代还有说书艺术流行于民间。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描写了一位名叫孙七的说唱艺术家。因为孙七说书技艺高超,听众“且唤诙谐柳敬亭”。虽然说书内容都是野史小说故事,但农户人家都爱听。
清代西域屯垦艺术类型中民间造型艺术虽不登大雅之堂,但为汉民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钟爱——剪纸和年画。西域可考的汉族剪纸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其后还有唐代剪纸,这正是高昌汉族王朝和西州时期的遗物。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剪纸有四幅:对鹿团花剪纸、对猴团花剪纸、对蝶团花剪纸和几何纹团花剪纸;唐代一幅;剪出连续七个纸人的代人形剪纸。从剪纸图案看,对兽图案、团花图案是当地汉族中流行的主流纹样,各种丝织物上都有这类纹样。这些剪纸的“表现方法是用象征、表号、谐音的方法和折叠形式,选取有关的动植物,巧妙地组合成托物寄意的寓意图案”。①这个时期的剪纸主要是作为随葬品,南北朝剪纸中出现莲花、鹿、猴等动植物和光环、宝塔形纹样,应与高昌汉人的佛教信仰有关,祈愿佛法保佑死者的灵魂升天。清代西域屯垦汉族移民带来的内地剪纸艺术己经超越了丧葬和宗教范畴,它既是一种民间活动,又是一种有喜庆内涵的民间艺术形式。“新疆汉族剪纸,主要是年节喜庆用于装饰的窗花、喜花、礼花及绣花等。其风格是丰富多彩的。有的粗犷简练,有的浑厚朴实,有的工巧纤细,..新疆汉族剪纸的基本特点还是淳朴、粗犷、厚实、明朗。属于西北的风格”。②这些民间剪纸大致分为用具纹、植物纹、动物纹、自然纹、几何纹、文字纹等,其中古钱、牡丹、梅花、鱼、羊、星月、水波、圆形、方形、三角形、雪花、喜字、寿字等纹样出现频率最高;构图法有平衡式、对称式、辐射式、填充式等,其中花中套花、果中套花、动物体上剪花等填充式构图法最常见。剪纸中的“喜花”多用于结婚等喜庆场合,窗户、室内墙上、各种陪嫁妆奁上都贴上喜庆吉祥的剪纸,如“龙凤呈祥”、“状元及第”、“麒麟送子”、“莲生贵子”、“榴开百生”等。过春节时贴窗花,糕点、供果上放喜花,也成为当时的年节习俗之一。共同的审美情趣使新疆的汉族和回族、锡伯族、满族的剪纸中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主题、题材和风格。剪纸图案中大量使用牡丹花、荷花、梅花、石榴花、蝴蝶、孔雀、凤凰等纹样,表达的吉祥、喜庆、福寿等寓意都是相同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剪纸并非用纸剪出图案,而是以剪纸方式装饰建筑、服饰、毡毯、刺绣等,以植物纹样、几何图形为主要图案。游牧民族还以动物角等为装饰图案。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剪纸图案中也常见汉族喜爱的牡丹、梅花、荷花等;而新疆汉族剪纸中也常有少数民族的巴旦木花、石榴花等图案。这种现象只有在清代以来形成的以屯垦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才会出现,从这点讲,是清代的屯垦文化催生了屯垦艺术,屯垦文化是屯垦艺术的母体。
汉族古老的民间木版年画有三大画派: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杨家埠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而在清代新疆汉民族中流行的是天津杨柳青年画,这与天津杨柳青人随左宗棠大军“赶大营”有直接关系。杨柳青年画的波及面不仅仅是新疆汉族,也影响到了锡伯、满等民族的习俗和审美趋向。“赶大营”的结果是,几乎年年有杨柳青人落户于乌鲁木齐西河坝一带,形成颇有津味特色的“杨柳青村”。到了20世纪40年代,把天津杨柳青人开设商号、居住较集中的大、小十字一带也曾称为“小杨柳青”。乌鲁木齐汉城的早期居民是以天津杨柳青人为主是无疑的。于是,思乡心切的乌鲁木齐杨柳青商人常购进杨柳青年画,以供年节张挂之用。凭借津商八大商行的势力和信誉,乌鲁木齐成了杨柳青年画的批发站,经这儿再销售到全疆各地。据说乌鲁木齐等城市在春节前夕卖年画的地摊一家挨一家。杨柳青年画题材多为“连年有余”、“万象更新”、“五谷丰登”的四季耕作图,还有“恭喜发财,四季平安”为内容的财神、门神、福禄寿三星高照图,也有表示喜庆的“双喜登梅图”和由谷穗、花瓶、鹌鹑组合的“岁岁平安图”等。总之,它迎合了当时人们除旧迎新、吉祥如意的心理需求。杨柳青年画具有形式多样、色彩艳丽的装饰美特点,故张贴年画成为当时边城乌鲁木齐等地过春节的流行时尚。它又与民间流行的迎财神、送灶神、贴门神等习俗结合起来,不仅为新疆各地的各省来的汉族居民所喜爱,也为接受汉族年节习俗的满、锡伯等民族钟情。杨柳青年画中还有一种称作“详林”的品类,“画的是亭台楼阁,没有人物,颇似穆斯林建筑,还有一种是画瓶花壶盘、博古文物,称作‘格景’,..很受新疆穆斯林民众的欢迎”。
清代西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屯垦文化艺术中莫过于传统的庙会和会馆社火因参众广、影响大、时间长而最为闻名,也成了展示全国各地民间文化艺术和风俗的最佳场合。从清代到民国期间,庙会文化和会馆文化是整个新疆汉文化的两大支柱,也是一种强势民间文化。
汉民族传统庙会是以寺庙为活动场所进行的全民性娱神、娱人民间文化活动,以戏剧歌舞表演祭祀为主要内容。在传统汉族社会中,几乎是到了有庙必有会的程度。汉民族传统的祭祀活动早在史前就产生了,春秋时已有定期祭神庆典类的狂欢活动,功能齐全的庙会大致起于隋唐时期。以戏剧、歌舞之类的狂欢活动也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从乐身到乐心的飞跃。这种情形越到后期越明显,参与者已并不在乎去祭祀什么样的神祗了,而是在这种全民性的民间狂欢艺术节中感受到了身心的愉悦。自清乾隆年间始,随着内地汉族移民增多,供奉各种神祗的庙宇也多起来,特别是乌鲁木齐红山嘴子更是大小庙宇林立。自乾隆十四年(1749)修建玉皇阁后,相继修建有大佛寺、地藏庙、北斗宫、三皇庙等。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释迦牟尼诞辰和四月十五日的玉皇阁庙会,红山嘴子庙会持续半月有余,庙会也成了乌鲁木齐汉族居民最重要的民间娱乐活动。庙会中不仅有“清华班”、“新盛班”、“吉利班”等的花鼓戏、秦腔、河北梆子等剧种搭台演出,而且以后还加进了京剧、新疆曲子戏的演出,而且变戏法、耍中幡,乃至少数民族的赛马等活动也参与其中。对于红山嘴子庙会的盛况曾有一段民间说唱反映了它的真实情景:
红山嘴子妖魔山,两个塔对得端。乌鲁木齐河水凉又甜,绿树成荫在岸边。庙会过了十来天,大人娃娃挤成山。西安人敲梆子唱乱弹,天津人又唱又敲拉洋片。河南人耍猴卖药围圈圈,拳把式耍的刀枪矛子三节鞭。吹唢呐鼓敲的欢,喀什噶尔的踩弯绳太惊险。耍把戏的空中取水变鸡蛋,对台戏唱的真好看。看了桄桄子(秦腔)看梆子,又看京戏小曲子。小四儿唱的盘肠战,张胡子唱的走雪山。兰州红、王小旦,二人唱的是小姑贤。看戏吃喝都方便,就怕你手里没有钱。回族人手端洋盘子卖凉面,维族人卖的是烤肉烤包子油抓饭。忠义馆三成园,搭起席棚子把酒席办。过油肉、溜三片、清蒸鸭子带海鲜,盖碗茶往上端,保你吃好、唱好、玩好满心喜欢。①
从说唱的语气及用词看,可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乌鲁木齐民间的顺口溜,口语化,还显点粗俗,但多少道出了乌鲁木齐庙会的盛况。但乌鲁木齐的庙会不仅仅限于红山嘴子的农历四月初八和十五日,还有农历三月十八日的观音阁庙会、农历六月十五日的八仙庙会、老君庙会、农历七月十五日的城隍庙会、农历六月六日的龙王庙会、三官庙会、定湘王庙会、农历四月初八的药王庙会等,有的则成为行业性的庙会。一切庙会活动自然是取悦于神祗的动机,但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参与是群体性的,如秧歌、小调等歌舞就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并不像舞台演出那样演员和观众判然有别。“从深层来看,这类活动在传统社会中起着调节器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平日单调生活、辛苦劳作的调节器;另一方面,也是平日传统礼教束缚下人们被压抑心理的调节器(尽管人们自己往往也未曾觉察这种心理)。更进一步看,这样一种调节器又起到了社会控制中的安全阀的作用”。①各类庙会是以生活在新疆的所有汉族居民群体参与为特征的,参加者并不特别重视东西南北移民身份的个体性差异,因此它所展示的民间文艺活动更有普泛性,这也是吸引所有汉民族集体参与的重要原因。就这点而言,它不同于各会馆的民间文艺花会——社火活动。
新疆的汉族会馆社火是节日期间各地民间举行的各种乡土性娱乐活动。社火分地面和高台两类,地面社火多在晚上举行,而高台社火则在白天。据说社火源自汉代百戏,而汉代百戏又与西域乐舞、杂技有关联,清代内地社火在新疆的流行也可以说是重归故里。新疆会馆是清代屯垦移民的产物,会馆是一种维护同乡利益,以松散型的乡缘、业缘为主的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机构。清代设在乌鲁木齐的主要是七大会馆:两湖会馆、山西会馆、甘肃会馆、陕西会馆、云贵川会馆、江浙会馆、中州会馆。各会馆都有本乡本土特色的社火活动,个性化特征十分突出,两湖会馆的花鼓戏、闹龙灯,陕西会馆的秦腔、眉户、高抬,甘肃会馆的跑早船,中州会馆的舞狮子,山西会馆的汾阳花鼓,直隶公所的高跷、中幡都属地方性的民间文艺形式。两湖会馆的龙灯夜间在街头表演,龙身的每节都点有蜡烛,舞龙时随行进上下翻动,似火龙飞舞。山西会馆的花鼓表演是男背腰鼓,女持小铜锣,边舞边敲,队形富于变换。甘肃会馆的跑早船,亦称灯船之戏,行进表演时,演员口唱小曲,用手划动船桨,以步履表现船荡漾前行,入夜,“船”上装有灯笼,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直隶公所的高跷表演者双脚踩木跷,表演以传统戏曲为内容的舞蹈,动作有扑、捉、闪、滚、爬、劈叉等多种,在锣鼓声中或行或走、或演或唱都有一定程式。陕西会馆的高抬亦叫铁芯子社火,铁芯子是4人肩扛的有基座的高约5米的铁杆,并根据画面造型焊接成脚手架,其上由扮演各种角色的八九岁儿童进行表演,表演的多是传统戏曲内容,往往一抬一个内容,如《黛玉葬花》、《游西湖》等,陕西会馆在春节前后都组织20余台高抬上街表演。各会馆的社火表演虽然有强烈的乡土情结,且产生于较封闭的一方地域,但它一旦融入到清代新疆这样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开放社会中,就不单单是一省或一地移民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活动,而是一种为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大众文艺了。因为社火都是以街头表演形式出现的,受众不分东西南北,也不分汉族或少数民族,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欣赏习惯各取所需,各有所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乌鲁木齐总商会组织的社火表演中的秧歌队,扭秧歌者可能是来自各地的东北人、山东人,而吹唢呐者又是维吾尔人。观赏者则更不分民汉了。因此,从一隅封闭乡间走出来的社火文艺活动一旦到了新疆这样八方移民汇聚、四面文化相融的开放空间中,民间艺术往往也就成了全方位的开放系统。
当人们审视清代的屯垦文化及其艺术现象时,不能不感到它前承汉唐遗风、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兵团文化的承袭关系。虽然各自都打上了不同时代的深深烙印,但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屯垦文化艺术的精髓早已植根于丝绸之路上西域这块沃土,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如果将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汉文化与西域其他诸民的文化相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文化仅仅比塞人文化晚扎根于兹,而与匈奴、月氏、乌孙等部落文化出现在西域的时间相当,且早于突厥、回鹘、〓哒、蒙古等的文化扎根于西域。以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为标志,汉民族定居于西域已有二千多年时间了。按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某种文化在某区域生存了两千多年,就可归入原居住民族文化;少于两千年但多于五百年,则归为古代移民文化;不到五百年,则归为近代移民文化。①由此看来,西域汉文化无可争议是西域的原居住民族文化。其实,西域与汉文化的联系在上古时期就已存在。“新石器时代中国黄河流域的陶鬲,出现在中亚、西亚的古地层中;制作于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代马头刀、马具等,明显地带有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用白玉雕成的人像和玉片、玉瑗出现在不产白玉的甘肃灵台西周墓葬和河西史前遗址中,而这种玉又极似和田所产;只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珠饰,于新疆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群中发现..。”②先秦时就已存在的丝绸之路,又将这种文化交往推向极致。《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上古文献的记载也反映了中原汉民族对西域的了解和认识。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为汉民族自汉代及其以后定居西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两汉入居西域的主要是军屯的将士、家属以及被征募和自愿来西域的屯田者,其他还有以政治联姻方式入居西域者和被匈奴贵族等掠夺转卖来的汉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汉人的主要来源是驻军屯田的将士和从河西等地迁至高昌等地的居民。即使在蒙古人统治的蒙元时期,自中原地区移居西域屯田的汉军、农民、工匠等日益增多。清代更以兵屯、民屯、遣屯、旗屯等屯田方式奠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汉文化格局。从西域、高昌、交河、柳中、金满、西州、天山、安西、北庭等汉语地名也能领略到汉民族作为西域原居住民族文化的客观存在。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汉文化属农耕定居文化型,源自中原汉文化。到了西域,汉文化又与不同时期的其他民族文化接触、碰撞、吸纳、整合变成了有地域特色的汉文化——西域汉文化。如果从经济形态着眼,西域汉文化可以分为屯垦文化型和城镇商业文化型;从汉民族人员来源还可分为流入文化型、移民文化型等;从地域分布看,有两汉时期罗布泊等地的军屯文化型以及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高昌汉文化型和清代的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奇台等地区的汉文化型。西域汉文化若从精神文化层面看,构成这样一些观念文化形态:(一)儒、释、道三元汇一的宗教文化形态;(二)以边塞诗为代表的汉文学形态;(三)以绘画、雕塑、戏剧、庙会、演出等方式出现的民间艺术形态;(四)以各种民俗出现的民间文化形态;(五)以汉语为主的交际、教育体系等。虽然西域汉文化的源头是中原的汉文化,但在两千多年的演进中已经基本西域化了,成了既有中原文化共性,又有西域地域特色的个性化的一个文化单元。所以,笔者把西域文化分为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屯垦文化三大类型意义也正在此。
丝绸之路汉文化之所以成为一方地域独特的文化单元,这是因为他们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林林总总,其中只有那些体现着普遍模式的事象才是民俗。第一,这些事象是模式化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形成、它们的结构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被人们完整地在生活中重复。第二,它们在社区生活中,在特定的群体中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群体中是共知共识,共同遵循的。”①在时空上显示为固定的民俗模式,如婚丧、起居、休养生息等民俗生活构成了西域汉民族人生活动的基础。一种模式化的、普遍的生活文化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就会发生发酵式的膨胀效应,无论题材、背景、表现有多么不同,但作为文化传承的结构模式是相同的。从魏晋时期到唐代,汉民族聚居的高昌地区的绘画艺术正呈现这种态势。
汉代,高昌就是西域屯田地区之一;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唐初,这里是阚氏、麴氏等汉族政权的统治地区;唐灭麴氏高昌国后,在此设立郡县,成立西州,与伊州、庭州一起成为汉族聚居的三州地区。于是,这些地区也就成了古代最能显现西域汉文化艺术特征的地区。从神话意象的伏羲女娲像到写实风格的墓主人生前生活图的绘画都出土于此。
西域汉族神话绘画材料出土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的绢画伏羲女娲图;二是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壁画龙腾图;三是楼兰、和田等地出土的彩棺上的玄武图;四是月宫桂树、玉兔图。其中大量的是伏羲女娲图。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11月的一年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发掘的四十座墓葬中,“十之六七都发现有伏羲女娲像的绢画。..大约一共有二三十幅之多。它们在墓室中,一般都是画面朝下,用木钉钉在墓顶上。”①这还不算20世纪初被西方探险者掠走的数量。高昌汉民族的伏羲女娲像首先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盛唐时期,这比中原晚了200多年。伏羲女娲像在中原盛行是在东汉时期,魏晋时已成余韵,而在西域,似香火相续,衔接中原而出现伏羲女娲像,其余绪绵延数百载。这不能不说是植根于汉民族民间的民俗信仰有强大的生命力,共同的丧葬习俗和精神信仰成了高昌汉族的共知共识,世代重复着以伏羲女娲神为核心的丧葬习俗。
最早发现的伏羲女娲绢画现存英国大英博物馆,20世纪初为外国探险者斯坦因所得。其画面为:伏羲女娲手执规矩,上身相拥,下身化作蛇尾缠绕。整个画面以深蓝色为底,并用红、黄、白三色描绘日月及人物蜿蜒缠绕的身躯。伏羲女娲粗眉、圆眼、钩鼻、朱唇。为7世纪之绢画。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也在吐鲁番得到一幅伏羲女娲绢画:“上绘二人像,左男右女,互相拥抱。两手扬起手执物,下部作两蛇相绞形。上绘一日形,日中有三足鸟,下绘一月形,月中有树兔和蟾蜍。周围有大小不一的彩色圆点,或是星宿。”②黄先生认为是7世纪上半期以后的绘画。晚近一幅伏羲女娲绢画出土于20世纪60年代,“男头戴幞头,女束高髻,两腮涂朱,眉间贴金。男举矩和墨斗,女执规。上身相拥,均着对襟直领宽袖朱衣,腰相连,共穿一花裙,下尾相交。画上部绘红心圆轮象征日形,下部以黑色圆形示月形。背景以小圆显示星辰”。③此为7世纪中期作品。审视这些画像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只存在绘画技法、着色、人物位置、服饰等方面的差异,而题材、内容则基本相同:伏羲、女娲均呈交缠之式。如果追根溯源,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形象有一种普遍现象,即作交尾状。山东武梁祠石刻:伏羲、女娲侧身相对,男戴方冠,衣缘领长袖,执曲尺,女衣同男,执规,下身蛇尾相交。南阳画像中,伏羲、女娲虽然不执规矩,下龙躯,但仍为尾相交状。
伏羲、女娲神话源自汉民族繁衍人类的始祖神信仰,到了战国时见于文献记载,而伏羲女娲交尾的绘画或雕像则晚至西汉末东汉初才大量出现。对于伏羲女娲的这种交尾式画像所含的意蕴,学者们的见解各不相同。闻一多先生认为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最基本的轮廓。①常任侠先生认为,他们既是人类的祖神,又是人类死后的保护神,“因此都雕刻在棺前或墓室享堂的前方,以保护死者,使他可以安享地下的快乐”。②吕微先生认为:“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的双蛇交尾形象除了反映出他们之间的血缘对偶关系,同时还是一种洪水创世意象。”③何新先生认为,中国远古神话中对太阳神加月亮神的二元崇拜,是中国哲学中极为重要的阴阳二元观念的始源,它是参照着男女两性的交合模型而产生的,这种两性交合的观念,转化为神话意象,也就是伏羲女娲的合体形象。④伏羲女娲绢画出现于偏于一隅的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汉民族的墓葬中,就不能不考虑其丧葬习俗及信仰之间的关系。伏羲女娲绢画是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的,死者直接面对绢画(死者无棺椁入殓,只是放在尸架或席上)。在这类墓葬中,不仅伏羲女娲绢画中绘有日、月、星辰等天象,日中多绘三足鸟,月中绘有玉兔、蟾蜍、桂树等,而且一些墓的顶部、四壁上部均以白点绘出二十八宿,每群星点间的线相连,表示一个星座。东北壁以红色绘出太阳,内有金鸟;西南壁以白色绘出月亮,内有桂树和玉兔捣月等图形。这些天象图与伏羲女娲像组合在一起,实际象征的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交而变化起”(《荀子礼治》)的观念。信仰上反映的是高昌、西州汉族祈求祖神保佑群体并希冀墓主死后升仙的思想。自汉代以来,中国道教的这种仙乡神话深深扎根于汉民族丧葬习俗中。由于太阳神——伏羲和月神——女娲结合化生万物神话信仰根深蒂固,于是伏羲女娲这对“育化人类”的文化英雄也成了祖神、生殖神等文化起源的象征,这是今世的需求。而与月神神话密切相关的月中有不死之药的神话,正是汉民族由天文现象进一步演化而成的新神话。如果死者能“死而复生”,那是人们对来世的祈求,但是其条件必须是成仙升天才能保证灵魂不死。于是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绢画和天象图有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引魂升天的多重意义。这也说明,即使汉民族中的一个不大的群体远离文化中心,其习俗信仰也会持续数百年而不衰。
楼兰古城以北墓葬出土的属汉晋时期的彩棺和和田出土的属晚唐五代时期的两具彩棺上均发现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这是最具价值的神话学材料。玄武是“龟蛇合体”的怪物形象,文献多有载,《后汉书·王梁传》李贤注说:“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有学者认为:“中国道教崇拜玄武大帝,民间盛行以玄武为吉祥长寿之物,证明玄武乃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一棵树,它的花果,正展示着中国文化一个方面的特色。”①楼兰古城以北墓葬、和田出土的彩棺所绘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守护神,和田“此二棺的彩画,从风格构图、题材上看,纯为汉族风格,连棺材造型都是汉族风格”。②从文化传播角度讲,这表明楼兰和于阗地区确实传入了中原道教,玄武大帝崇拜在楼兰和于阗民间存在是不成问题的。但楼兰和于阗人为何接受汉族的玄武信仰呢?这不能不归结到人类在追求生命永恒上是相通的:“玄武有两个属性,其一他的原形为龟,龟是寿的象征,..其二他占居北方水位,为水神。而在人类的潜意识中,水是生命的起始,也是生命的归宿。”③楼兰和于阗玄武图其意义在于长寿崇拜,玄武帝正充当了增寿赐福的职能,即使人死后,因灵魂不死,故在阴间也能享尽富贵。无论是生或死,玄武之神都能保佑他们长生永存。由此看来,玄武神在楼兰和于阗本土文化中的扎根,或者说崇拜玄武神,正是楼兰人和于阗人同汉民族一样体认生命意识的表现。
对人类而言,今世和来世总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西域汉民族也不例外。他们在祈求死后“羽化成仙”来世的同时,也十分眷恋今世,于是死者的墓葬中不仅存在伏羲女娲绢画,也多有反映今世生活的写实风格的绘画。这类绘画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再现死者生前生活情景的绘画,其动机是祝愿死者如生前一样享尽荣华富贵;二是死者生前的绘画藏品,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反映,但乃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三是带有伦理说教意味的历史故事题材六屏壁画。
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绘画出土有两幅。一幅是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墓中属3~4世纪的长条形壁画。壁画的中心人物是在帷幔下头戴巾帻,身穿大袖袍衫,双手作揖的庄园主的形象,身后有妻妾相随。左侧所画厨房内,厨娘们正炊烧和磨面。右侧是耕地、葡萄园、桑园、酿酒房、鞍马、牛车、工匠等庄园景色。另一幅是出土于吐鲁番的属7~9世纪的画有庄园主宴饮作乐的纸画。主人和客人正席地而坐,观赏两个舞女翩翩起舞,旁有吹箫、击鼓者,画面下部绘有厨具和炊烧的厨娘,还有牛车等。两幅画均为单线勾勒,平涂填色,内容基本相同。但比较这两幅不同时期的绘画也不难发现其不同之处。前一幅为长条形的组合式画面,由主人的宅外生活画面依次构成主人的主要家庭成员、财产(土地、果木、作坊、工具等)以及饮食等日常生活场景,类似出游图,绘画拙朴,不似出自专业画师之手。而后一幅则不同,描绘墓主人生前生活中的一个特定场景(内宅生活),笔法流畅圆润,构图简洁,画面有较强平衡感,人物比例也得当。如果将吐鲁番出土的这些世俗绘画与西安唐墓壁画相比较,布局和画法几无差别。①这就不难发现西域汉文化艺术与中原汉文化艺术之间的源流关系。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一批属7~9世纪的唐风绢画,大部分为仕女和侍女图,如仕女弈棋图、盛装仕女图、托盏侍女图、舞伎图等,此外还有侍马图、童子图等。这些画极有可能是唐代文人仕女图的摹本或以此类仕女图为蓝本绘制的。人物均属唐代妇女的丰美形象,圆润的脸上涂朱,眼睛细长,朱唇小嘴,梳高髻或平髻,衣着华贵,衣褶线条流畅。其中一幅仕女弈棋图是唐风仕女图。画中妇女为一贵妇,发束高髻,阔眉,额间描心形花钿,身着绯衣绿裙,披帛,贵妇表情凝重、安详,正若有所思,右手执子,呈举棋不定状。这类仕女题材的人物画是盛唐到中唐时长安流行的画风,代表人物是张萱、周昉等文人画家。《唐朝名画录》评价张萱的画是“尝画贵公子、鞍马、屏障、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宣和画谱》所载张萱画迹四十七卷中竟有三十卷为仕女图,多是描绘贵妇的世俗生活,如整妆、鼓琴、弈棋、烹菜、赏雪、出游、七夕祈巧等。其人物体态都以丰满见长,整个画面都是工笔重彩,有雍容华贵的“盛唐气象”。中唐的周昉也曾有“画仕女,为古今绝冠”的盛誉。他的留世代表作为《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周昉笔下的仕女也多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之态。这正是唐代妇女的时尚。“比较张萱、周昉的作品,其共同之处不仅在于世俗的倾向和宫廷的趣味,也不仅在于色彩的浓郁和笔触的细腻,还在于他们都善于动中取静,追求一种雍容典雅、仪态万方的气度,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的‘高贵单纯,静穆的伟大’。”①如果参照库木吐喇石窟中8世纪汉风飞天形象和吐鲁番出土的7~9世纪墓主人生活图纸画中的贵妇形象不难看出,这些人物都是体态丰腴,仪态万方,足以证明唐代西域的汉族贵妇亦以长安贵妇的浓艳丰满作为追求的审美时尚。盛唐气象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胡风汉化一起来,长安的胡风,西域的汉风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是各种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盛唐文化有强大辐射功能和极强吸纳力的表现。西域的汉族贵妇们同样追求长安上层流行的“以胖为美”的时尚,并形成一种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无论是唐代的长安还是西域的西州,“现实世间生活以自己多样化的真实,展现在、反映在文艺的面貌中,构成这个时代的艺术风神”。②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唐代墓葬还有一些屏风式壁画,一般为六屏式,有的绘有花卉禽鸟、山水人物、舞乐伎等,而有的则是连环画式的伦理说教图。有一幅“六屏式鉴诫图”的壁画为六条挂屏式布局。画面从左至右依次为:最左侧绘有一种名为“欹”的容器,形似倒挂的钟,横贯于一根木杆上。壁画中间四屏上各绘有“金人”、“石人”、“玉人”等形象,其前胸或后背题有“金人”、“石人”、“玉人”等字样。最右端的一屏上绘有生刍、素丝和扑满。屏风画的形式,“为三国以来南北朝隋唐时期常画的形式。到唐代有六曲、四曲的屏风,这形式曾经传至日本,为封建上层社会室内装饰的必备之物”。①在墓室中绘制屏风式壁画可能在汉代已出现,唐代亦盛行,特别是六屏式屏风画和墓葬壁画是唐代流行的形式,往往都蕴含有历史故事。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另一幅唐代六屏式壁画《树下人物图》,所画都是树下人物,人物或交谈,或聆听,或指点,或对话。常任侠先生认为:“若果用历史人物来比附的话,第一条可能是王羲之;第三条可能是谢安;第二条借双陆进谏,陈说利害的,可能是狄仁杰的故事;第五条手捧卷轴的可能就是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这些都是在唐人的记载中就很驰名的。第四条人物的臂上,架有一鹰,这与开元天宝时期李隆基爱好鹰鹘有些关系。”②常先生并对这幅六屏式壁画的内容进行了考证,理由也是说得通的。常先生可能未见那幅“六屏式鉴诫图”,故也未提及。但它所反映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也是西域汉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为人处世之道。因为这幅“六屏式鉴诫图”是以形象的画面在劝诫人们应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自己。每当“欹”这种容器内空或盛满水时,容器就会倾斜或翻倒,只有盛水适中时,才能保持平衡,这是在形象地劝谕人们要谦虚,勿自满。“金人”、“石人”、“玉人”是将儒家列圣做人的鉴诫宣示以形象:“金人”,是教人凡事要“三缄其口”,谦虚谨慎,勿骄勿躁;“石人”,是主张为人要有所作为,要有正义感,匡正时弊;“玉人”,是劝告人们要节制物欲,修身养性。③右端所绘生刍、素丝和扑满,是在告诫人们为人端正质朴,为事由微至著,为官清正廉明。所画形象可能既是对死者一生道德品格的赞誉,又对后辈有劝诫警示作用。
从丝绸之路汉民族神话意象的绘画到写实作风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唐艺术精神永远是西域汉文化的灵魂,因为这种艺术精神本身就是和汉文化血肉相连的。从阿斯塔那墓室的布局发现,墓主人居于由伏羲女娲画组成的“天上”和墓壁四周描绘生活情景的壁画构成的“地上”这样相联结的空间中,恰恰象征的是以“天、地、人”为基本结构的宇宙模式。墓主人将生活在地下的永远的家安置在宇宙的背景下,他虽然死亡了,但也寄托了生的愿望,他或她将在伏羲、女娲两位天神的指引下,灵魂升天,自己也将成为这个永恒乐土的成员。
第二节 雕塑艺术:神圣与世俗之间
在丝绸之路汉民族文化中,他们的神话、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总是神圣的;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则是世俗的。
“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将神圣事物简单地理解成那些被称为神或精灵的人格存在;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泓泉水,一枚卵石,一段木头,一座房子,简言之,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圣的事物。”①那些雕塑的偶像及其膜拜仪式当然是神圣的,而再现墓主人生前世俗生活的人俑、动物俑、镇墓兽之类的明器也是神圣的吗?按理,无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多么高贵,但他们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再凡俗不过了。只是当他们离开人世间时,所进行的隆重葬礼连同象征生前生活的明器均被神圣化,凡俗之物成了神圣之物。
俑与神偶尽管制作材料相差无几,但功能大相径庭。神偶,往往以造型的形式被看作是神圣存在的代表,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俑虽然也以造型形式出现,但并不是膜拜的对象,而只是人们幻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的观念的反映。在以人俑、动物俑随葬之前,曾出现过人殉和动物殉。“父系氏族兴起以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的现象,随葬品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种类增加了,有生产工具、陶器、装饰、牲畜和奴隶,另一方面出现了随葬品多少不一的现象。”②富有者,如氏族酋长等,随葬时往往有大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牲畜,甚至以奴隶殉葬。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新型个体家庭的兴起,活殉的情况就有了改变,俑葬出现了。但是俑不是作为现实中人和物的替代品出现的,而是在展示墓主人的阴间生活。在中国丧葬文化中,俑本专指俑人,但以后把动物形象也包括进去了。“这些俑是要在阴间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人并且所有的俑都必将发挥其实效”。③因此,俑是显示墓主人社会地位的,它的实效也表明其功能和职责是最重要的。
西域汉族墓葬中的俑集中于7~9世纪,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时期,出土俑又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为多。按题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侍奉墓主的俑人和动物俑;二是保护墓主的避邪压胜之神物,如镇墓兽、十二生辰、天王俑之属。④这与中原墓葬中的随葬俑人习俗毫无二致。西域汉俑与中原俑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制作材料和某些人物造型上,它显示的是汉文化一统中的地域特色。阿斯塔那古墓中的俑为彩绘泥俑和木俑,绝少有中原的陶俑,且制作材料和方法有地域性。彩绘泥俑一般采用模型和捏塑方法,以木或草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木俑采用刻、削、琢、旋、磨等工艺,成型后再施以彩绘。俑人和动物俑除唐代常见的仕女俑、吏俑、乐舞俑、武士俑、胡人俑、生育俑、天王俑、家畜、家禽俑等以外,还有反映高昌、西州汉人现实生活的劳作俑、杂技俑、牛车俑等。
自汉代以来,西域就陆续有中原的汉族居民迁入,于是像高昌这样一些汉族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社区社会。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得知,从高昌王国到唐西州的400多年中,该地区曾先后有麴、张、马、阚、索、唐、曹、赵、郭、孙、范、巳、傅、董、牛、李、史、焦等姓氏的家族。“家族,在当时的高昌社会中,是一支不可以低估的社会力量,普通百姓人家,要依靠同姓同族的扶持、照应,以求得安身立命之地;权贵之家,也利用血缘、家族的关系,作为维护统治权益、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家族的、血缘的关系,成了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有力手段。生前,人人都感受到形如蛛网的家族的系联;死后,也自不能脱离这一家族关系的束缚。因此,以一个个大家族为单元,营建自己的墓地,成了一种习俗。”①我国汉族的丧葬习俗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丧葬之礼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进行的。孔子就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仅以隋唐时期的随葬制度而言,就形成以陶俑为主的随葬习俗。俑的形象多为出行时的仪卫队列和家居时的奴婢侍者,乐舞俑、游戏俑、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种动物模型也十分普遍。武周后,以黄、白、绿三彩为主的“唐三彩”陶俑为主,镇墓兽也演变为有头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兽。但是并非所有的墓葬的随葬品都如此丰厚,只有帝王、王公贵族及官宦人家依定制可有丰厚或较丰厚的随葬品。这种厚丧的丧葬习俗也被高昌王族或某个家族中的富有者所承袭。麴氏高昌王室是西域汉族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其墓葬规模也算得上宏大了。其中编号为60TAM336的王室墓的“墓室地表曾经建有一座四棱形佛塔,墓道长达29米,墓底深入地下约9米,墓室前部有象征前厅的甬道,左右有象征厢房的龛室,更前为天井,象征着居室的庭院。天井地面以小块砾石铺砌,不同寻常。墓葬随葬品,主要是大量俑像,品类既繁,数量也多。大型镇墓兽、泥塑马、驼、文吏、武士以及舞乐百戏,还有家畜、井、灶等一应俱全”。②按照“事死如事生”原则指导下的俑人、动物俑和镇墓兽都不是随意塑造的,而是按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和生活经历精心选择的,这些随葬物也应是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物。
高昌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普通百姓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作式生活,而是由政事、社交、宴饮娱乐等活动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俑人也大多与他们的上层生活情景有关。仕女俑可能就是他们阴间生活中妻妾、歌舞伎等形象;而一些男俑,特别是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也应是他们处理军政事务的手下的形象;还有些胡人俑很可能是与之交往地区部民首领派来使者的形象;更有些昆仑奴的戏俑、舞蹈俑、舞狮俑、杂技马舞俑等也是供上层人物娱乐时的百戏乐舞者的形象。始作俑者当然是活着的亲人,他们希望通过诸如此类的丧葬手段,力图让死者在阴间拥有同生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死者如同生前一样享尽荣华富贵。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AM206的张雄夫妻合葬墓的两件仕女俑代表了麴氏高昌王国彩绘泥塑的艺术水准。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麴、张二姓是头等豪门,麴氏为王,张氏为将相,又形成联姻关系。张雄的祖父曾任高昌王国左卫将军、绾曹郎中,其父任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张雄的姑母是高昌王麴伯雅的王妃,而他本人则任高昌王国左卫大将军,其二子张定和、张怀寂曾在唐西州、甘州任官。出土的这两件仕女俑只是张雄夫妇合葬墓中木俑的极少一部分,从他们的墓中清理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70多件,还有木马残腿、木俑手脚200余件。两件仕女俑均为立俑,高发髻、白襦衫,一件是绛色长裙,另一件为彩条长裙。仕女俑头部与躯体用木雕刻而成,脸部打磨施彩,表情温静安祥。仕女的手及长裙用衬纸做成,其一仕女俑双手交叠腹前,另一仕女俑为长袖善舞状。这两件仕女俑高36厘米左右,不及麴氏王族陵墓中的高54厘米的仕女俑。可见王族与非王族的俑人在高低大小上是有定制的。王陵仕女俑用整端木头雕成,后施彩绘。因色彩剥落,已无法窥知其艳丽,但仕女俑形象仍栩栩如生。仕女发束“惊鹄髻”,宽衣大袖,休态丰腴,为典型的贵妇形象,似为王室女眷。与仕女体态端庄、神情温顺、安详形象不同的是一些乐舞俑。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这批绢衣木俑制作特殊,形象、表情、装饰都不同于常见的殉葬俑人。男女俑原来均以木雕头部、彩绘面貌,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这种纸臂绢衣的木俑,既便于表现各种舞蹈动作,而又衣着真实,宛若真人”。①用什么材料制作,受条件制约,其他俑人,如仕女俑也用木、纸等材料,关键是人物动作、神态,这些绢衣木俑,男的(实为女扮男装)“滑稽戏调”,女的“秾华窈窕”,完全不似仕女俑肃穆端庄。“十七个绢衣彩绘女俑,不是一般的舞俑。这些女俑不但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而且还有女扮男装的。..这类木偶不直接雕绘成男角,而要刻画成女扮男装,正是当时演出就有由女优扮演男角的缘故。这反映当时男女倡优尚不同台演出,而女扮男装木偶的发现,则用实例证明初唐已有女优装扮生、旦角色演出‘合生’了”。②这些表现歌舞戏弄木俑的出土表明唐统一西域后,西域汉族居民中也流行中原地区的乐舞戏弄。汉唐时期上层人物丧葬中用傀儡表演歌舞伎乐的习俗,很可能也被高昌、西州汉族上层所采用,或者王族等也有私家乐舞队。唐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就认为:“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故高昌王公贵族墓中会出现如此多的乐舞俑。
武士俑、官宦俑、文吏俑等是作为死者阴间的侍从、下属、左右等形象出现的。文官俑和武士俑有站立式塑像和骑马式塑像。骑马式武士俑似为仪仗俑的一部分。张雄夫妇墓出土的骑马武士木俑有三具,全身着铠甲,头戴软盔,骑于马上都呈同一姿势的执兵器状。应是仪仗卫队中的卫士。马身与马腿是两个部件隼接而成,可能受材料的限制,马腿显得僵直,未表现出动感。而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另一具骑马武士泥俑则不同。虽然也是仪仗兵马俑之一,但从装束看,似为将军。此俑因用软泥塑造而成,故线条流畅,无木俑的僵直感。将军头戴尖顶软盔(与兵士有别),穿深褐色长袍,外罩软甲,端坐马上,左手持缰绳,右手作提鞭状(与兵士持兵器不同),马为黑色,体形高大健壮。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审美效果,骑马武士泥俑都堪称这类俑人中的精品,虽然人与马处于相对静态,但人马比例、马的形体塑造以及着色等艺术水准都远在三尊骑马武士木俑之上。高昌(西州)的民间艺人在雕塑俑人时很能把握不同人物的瞬间状态,雕塑出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具文吏俑,其形象为右手握笔,左肋挟文卷,头梳发髻,身着长袍的彩绘泥塑。文吏俑表情谦恭,目光直视,嘴上的两撇胡子有动感。整个神态表明他正在毕恭毕敬地聆听上司的旨意,以便随时起草文告。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汉族居民墓葬中出土的动物俑主要是和他们生活关系密切的骆驼俑、马俑、牛俑、鸭俑等,人身兽头的十二生肖俑也应归入动物俑中。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有一具单峰驼俑,实属罕见。因为古代新疆、中亚等地的骆驼为双峰驼,而单峰驼只生活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等地。吐鲁番出土单峰驼俑,表明此地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这具单峰驼俑,研究者往往给予很高评价:“这件泥塑造型洗炼,决不‘谨毛而失貌’。选择的是静止的一瞬间,使‘一纵即逝’的东西‘获得一种持久性’。它留驻的是整体的神形态势,不容许无谓的枝节存在,又没有漏过有生命的细节——如点睛传神。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形,是服从于神、态、势的形,而不是真驼外形的摹仿,从而在局部与整体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神、形、态、势的统一,它发挥了雕塑艺术体积的深度、厚度、体面变化无穷的特长,发挥了雕塑艺术可以多角度欣赏而不失其生动完整、容纳丰富内涵的优势,克服了造型艺术的有限性,超越了时间,启发人进入驰骋想象马镫的无限性,达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具单峰驼俑成了我国发现的三件单峰驼俑中的极品,它的体面结构与淡淡的色调,真正是浑然一体。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两件大型十二生肖俑——鸡首人身俑和猪首人身俑。前者高80厘米,彩绘泥塑,造型上为鸡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绿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后者高75厘米,上为猪首,自脖颈以下为人身,着橙蓼色无领大襟宽袖衫,喇叭式长裙,双手相握,笼在袖中。如此大的生肖俑,实属罕见,且鸡首、猪首毕肖,衣着华丽,宽袖、长裙下垂,舒展自然。人死后以生肖俑作为随葬品,自隋代以来就成为汉民族丧葬习俗之一。对于这种葬俗的流播地区、时间及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十二生肖俑,南方最早见于隋墓,西安见于盛唐前期墓葬,吐鲁番地区见于盛唐后期墓葬。西安唐墓是受了南方的影响,而吐鲁番唐墓当是受了西安唐墓的影响。”②
在西域汉民族俑塑中有一种非人非兽、似人似兽的特殊形象——镇墓兽。这是汉民族想象中的神物,放在墓中是为了避邪镇墓,防止魍魉破坏尸体。据民间传说,有一种叫魍魉的怪兽专吃死人肝脑,而它最怕魌头、方相。《周礼》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大丧,先〓,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相、魌头本是山神的造像,作为镇墓兽出现于战国时期,为双头兽形象,每个头上各插一对鹿角,也有单头兽,插一对长鹿角。汉代的镇墓兽多为四蹄、四爪蹬开,低头用长角作前牴状或蹲伏昂首作守望状。而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镇墓兽多为蹲踞状,有的是兽身人头,有的则是兽身兽头。还有一种人身兽头兽爪,为人立姿,其形象介于人兽之间,类似降魔变中的天王,显然来源于佛教艺术形象。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镇墓兽也多为蹲踞形,有的是人头兽身,有的是兽头兽身。立式镇墓兽是天王踏小鬼的形象。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镇墓兽,通高超过70厘米,泥塑淡彩,狮头兽身,头生双角,长有四只偶蹄;坚如岩石的前额和胸肋,张嘴翘舌,口裂深大,鼻翼和眉头像拧在一起的鹅卵石;深陷的眼窝,夸张地努凸出来的一对眼睛,好似在喷火。这些又同阔胸细腹、肋骨成条排的凹凸明显的斜沟相呼应,给人以吼声震耳的威慑感。①如果从造型看,阿斯塔那的这类镇墓兽完全与中原地区自战国以来镇墓兽长鹿角、偶蹄的传统相符。自战国至唐代,墓葬中放镇墓兽的习俗自长江流域传到中原地区,再辐射到各地,西域也是其远披之地。
阿斯塔那古墓所出土的人首豹身类镇墓兽,高86厘米,为彩绘泥塑像。此镇墓兽头为人头形,头戴兜鍪如武士,面目威严,身躯似豹,足似马蹄,尾部细长如蛇紧贴身后。全身作蹲踞状。这种镇墓兽实际上是人和豹、马等动物的组合形象。武士的威严、豹身的敏捷、马蹄的快疾组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拼凑,而是想象力和现实的结合,创造出这一怪诞的形象才能防止魍魉毁坏墓主人的尸体,这正是镇墓兽的功能所在。
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有彩绘天王踏鬼木俑,从其形象看,也应是镇墓兽之类,不过是在形象上借用了佛教传入后的天王形象。它非传统的镇墓兽,而应是镇墓天王,来自于佛教传说,因此,这类形象更有地域色彩,也更人性化。佛教传说中的四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实为守护四方之神。佛教传入中原、西域后,往往在佛寺内塑造四天王像: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持国天王著白色服饰,持琵琶;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缠一龙;多闻天王着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阿斯塔那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由30余块分别雕刻套接后成形。天王高髻束带,身着铠甲,右手上举,左手臂弯曲前伸,穿红花裤,系扶腿,足蹬靴,右足下踏一小鬼(可能就是魍魉)。虽然天王衣著依现实生活中武士打扮造型,有世俗化意味,但双目怒视,龇牙咧嘴,的确有威严感,其形象足以震慑魍魉之类。天王用于镇墓,是西域汉族居民依据现实生活和佛教信仰的创作,它不拘泥于传统的镇墓兽形象,采用更人性化的创新思维,大胆把佛教传说形象用于墓葬。由此可以证明,一些神圣事物完全可以用于现实目的。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俑人中有一种特殊的形象——黑人形象,有研究者称之为黑人与戏俑,也有人说是昆仑奴形象。这一俑人为彩绘泥塑,上身赤裸,下身着橘红色短裤,赤足,皮肤施黑彩,短卷发,嘴唇较厚,双手正握棒舞弄,此俑人高仅12.5厘米。该俑与西安南郊嘉里村唐裴氏墓出土的陶俑如出一辙,不过阿斯塔那的彩绘泥塑俑人出土于王族墓中而已。孙机先生认为,这类“黑人”俑不应定为昆仑俑,而是所谓的僧祗,昆仑俑是南海昆仑国人被夸张强化所致的形象,而作为“黑人”形象的僧祗是大食自东非掠买的黑人,与大食有外交事务关系的唐朝高官也养成家养黑奴的恶俗。所以这类黑人俑应是僧祗的形象。①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鞠氏王族或唐西州高官有养黑奴的恶俗,但黑人俑的出土至少说明西域汉族上层人物对唐长安高官人家养黑奴是仰慕的,故以这类俑人随葬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罢了。
第三节 汉锦唐绢的艺术品格
尽管人们把古代贯通欧亚的陆路通道冠名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等,但这些名称远不如“丝绸之路”久负盛名。这条自我国长安起始,途经西域广大地区,曾远达罗马、叙利亚的陆路丝绸贸易通道虽然存在了一千多年,但作为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专用名称——丝绸之路,则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外学者不仅把丝绸之路看作是古代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而且还把它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不争的事实是,各种文化的传播、交流、辐射,最初的确来自丝绸贸易,中国的丝绸成了不同文化背景民族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它早已超脱了其有形的物质形态,而深入到丝绸之路周缘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诸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升着整个人类的文明程度,因此,丝绸之路也具备了文化符号的功能。历史学家把古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叙利亚总督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败在安息人手下的原因归罪于安息人那令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斓的军旗上,安息人的军旗正是用中国的丝绸制作的。古罗马人正是在卡尔莱战役中初次接触到中国的丝绸:“丝绸比先前所有的纺织品都更加绚丽多彩,因而很快为罗马社会所熟悉。叙利亚战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织物,它可能是在几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到手的。卡尔莱战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恺撒在罗马祝捷的时候,借机向罗马臣民显示夸耀各地所展现的奢侈品,即为他的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奉献的一批丝绸织物。因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惊诧赞叹。..在卡尔莱战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①被西方人称为“赛里斯”的中国丝绸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仍然还是欧洲妇女追求的时尚,妇女们一改十五六世纪追求单色呢绒料的时尚,“而到了十七世纪,又掀起了抢购‘草原式图案’缎纹织物和‘印度之花’织物、‘土耳其式’的塔夫绸、‘米兰式图案’织物的风潮。到了十八世纪,丝绸工业又受到了追求大幅图案为时髦之风潮的刺激,这种图案形成了一幅幅真正的图画(其设计图纸是被当作绝密资料加以保护的),带有裙环的那种宽大裙子的式样需要特别宽幅的丝绸布。..终于在欧洲首次出现了汉人式的图案:如佛塔、竹桥、人像等等。”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丝②绸服饰的款式、图案形成不同的审美追求,但丝绸文化的魅力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
丝绸,这种令古罗马人目瞪口呆、惊诧赞叹的织物几乎不进入艺术史家的视野,虽然用丝绸缝制的服饰,人们宠爱有加,但它不如青铜器、瓷器那样成为学者们眼中的艺术研究对象。像格鲁塞的《东方的文明》、巴赞的《艺术史》这样的艺术史名著也只字未提丝绸工艺、图案艺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其实“纺织物品通常经过某种加工以增进它的美感,..在布料的装饰方面由世界各民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风格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习惯。例如,主题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象征性的,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往往来自他的信仰和理想”。③新疆出土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汉唐时期的丝织品或许可以大开人们的眼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梦幻般的汉锦唐绢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判断。
由于丝绸织物不宜保存,在世界各地极少有出土,只是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由于干旱少雨,才在汉代以来的墓葬中发现了品类众多的丝织物。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无论是丝织物的品类、织法、纹样、色彩,还是主题、题材、装饰手法都印证着东西文化交融、互渗这一事实。人们发现,中国丝绸西传的结果,竟派生出波斯锦、粟特锦、叙利亚丝织品以及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的织物等。这种东传西渐的踪迹在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及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汉唐丝织品中都能寻觅到。
新疆出土的汉代至唐代的丝织物与丝绸之路走向吻合,也与汉族居民在西域的分布合拍。汉唐丝织品的出土地点几乎全集中于丝绸之路的南北道。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发现了包括锦、绮、罗、各色绢、缣及刺绣等汉代丝织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则出土了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这里是麴氏等汉族政权高昌国和唐西州的所在地,丝绸生产和贸易都曾盛极一时,仅出土的丝织品就有锦、绢、绮、绫、〓、染缬、刺绣等。在某一区域出土品类各异、色彩缤纷的众多丝织物,非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莫属。仅从这些丝绸织品东西合璧的图案纹样就不难窥见这座古代丝绸博物馆的风采。如果从主题着眼,我们可以将汉唐时期的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分为吉祥图案和祥禽瑞兽图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汉锦主题基本属于吉祥文字纹锦,在满幅变幻莫测的动植物纹样中,嵌织有隶书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韩仁绣文宏吉子孙万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长乐明光”、“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这与人们普遍存在的“祈福赐祥”心理不无关系。祥禽瑞兽纹锦常见的有“龙凤纹锦”、“鱼禽纹锦”、“对鸟对羊树纹锦”、“飞风蛱蝶团花锦”、“联珠对鸡纹锦”、“联珠鸾鸟纹锦”、“联珠鹿纹锦”等,联珠纹主题的纹锦多见于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高昌地区。假如从题材去分析,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文字纹都久盛不衰。据研究者统计,仅楼兰、尼雅所出的东汉锦纹样就有二十余种。①其实,自汉至唐代西域丝织品的纹样远比这要多得多。假如从构图思路看,汉唐时期西域丝织物的纹样严格遵循着对称平衡的原则,这几乎是装饰工艺的不二法则。但对称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布局的变化,上下对称、左右对称、中心对称、边缘对称等旨在追求严谨中的变化。动物纹样、植物纹样、文字纹样、几何纹样之间的有机搭配,也在追求一种各纹样间的对称平衡效果。如果着眼于色彩、工艺,就能发现其色彩的绚丽和编织技巧的娴熟。汉代锦、绮、绣等丝织品的色彩就有藏青、宝蓝、天青、海蓝、湖蓝、墨绿、葱绿、粉绿、绛紫、绛红、褪红、深棕、沉香、驼色、白色、绯红、黑色等多种。北朝至唐代高昌(西州)的锦、绮、绫、印花绢、缦、缣、纱、罗等的色彩有褪红、朱红、海蓝、绢黄、藏青、海蓝、天青、葱绿、湖绿、草绿、叶绿、绛红、橙红、银红、棕色、白色等。在色彩上汉唐之间有承袭关系,但也明显有创新,如唐代织锦除沿袭汉代以深色为地外,大多以白色或浅色为地,用绛、绿、青、黄等色显花,花纹间色彩互换富有变化。丝绸品的工艺从平织、平纹重组织、显花起绒圈重组织、经线显花、纬线显花、刺绣到印花法都出现,仅印花,唐代就有蜡染法和绞缬法。汉唐西域丝绸品就纹样而言,纵向流变和横向融合都呈现出创新和互渗的特征。“花纹方面,汉代那种宽带式花纹布局,到了唐代改为孤立的花纹元素散布全幅。花纹母题则西方式植物纹盛行,包括忍冬纹、葡萄纹等。波斯萨珊朝式的那种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唐代很是盛行”。①联珠圆圈内是对鸟、对兽图案。但这种合璧并非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而是各种文化在长期接触中,从冲突、碰撞走向融合的结果,它虽脱胎于原来的文化,但并非原来的模样,一经消化吸收和文化整合后,成了本土化的艺术品种。盛唐气象就是指其化解东西文化的大气,西域丝织物图案纹样岂能例外。
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是汉锦的主要发现地。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1980年在楼兰城郊古墓群孤台墓地就出土汉锦53件;1995年在尼雅遗址编号为95MNIM8号的墓地出土的汉锦织物10多件,其中就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1983~1995年在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中,出土包括织锦、绢类丝织物33件。汉锦上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是纹样构成的基本特征。楼兰出土的一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褐色地,黄、蓝二色里花,经锦。变体云纹和攀枝叶蔓中夹瑞兽,瑞兽间织隶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吉祥语”。②而另一件1995年出土于尼雅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重平纹经锦,平挺厚实,图案题材新颖,有虎、龙、避邪、仙鹤、孔雀、瑞兽图案,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③山普拉出土的丝绸物多为死者的帽、衣、裤、护颌罩等服饰类,有锦、绢、缦、绮等。其中织锦有两件,一件蓝地,显黄色菱格、曲线、点纹;另一件有幅边,绛色为地,宝蓝、米黄、粉绿和白色五种颜色显花。①营盘出土的属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织锦是以“吉祥云纹、祥禽瑞兽为主体的图案。有夹织立禽和隶书‘登高’、‘寿’、‘右’等文字锦,也有图案横向排列的卷草纹锦和方格纹内相同的瑞兽纹锦”。②西域以织锦为代表的汉代丝织品,“其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纹饰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现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其间穿插种种吉祥用语”,③具有汉文化特征。许多祥禽瑞兽是有象征寓意的,如对鸭图案中的鸭子意取“压子”;老鼠象征长寿;独角兽——避邪有祛邪除凶的寓意;龙凤象征吉祥等等。汉代丝织品中出现的这类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纹饰是一个时代思想与信仰的折射。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更现实,也更务实,“显然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世俗化,成为一种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就是追求生命的永生。而现实生活中的‘富贵’与子孙的‘繁衍’,却成了更现实的生活中‘幸福’,人们的渴求日益现实,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字样就是明证,人们日益实用的生活观念正是在这里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④当汉朝统一西域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思想、信仰上的趋同性已深深扎根于西域各地居民的心中,所以才会在那么多墓葬中出土如此众多的吉祥文字、祥禽瑞兽图案的丝绸织物——生用死殉,追求着生命的永生和一生的“富贵”,并期望“幸福”庇荫子孙后代。就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些我国古代星占术上的占辞用语也出现在织锦上,也可以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祈语,反映了西域各地居民同中原汉民族同样追求吉祥昌盛的良好祈愿和朴素的感情。
从北朝到唐代,西域丝织物的产地主要在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含西州)等地,但以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物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工艺技术和图案风格。在众多出土的丝织品中织锦和绢(染缬)最为普遍。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的织锦是有差异的。6世纪前的织锦图案单位直行排列,作横幅相间的祥瑞兽纹,形成瑞兽纹锦、狮纹锦等,图案内容和布局与汉锦相似,但动物形态或立或卧,都比较稳定,是汉锦风格的继续;而到了唐代,有两类图案的织锦居于主导地位:一为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图案,二为联珠对禽对兽图案。⑤植物纹样图案织锦品类多,纹样多变,其中的“宝相花斜纹经锦”的纹饰图案是唐代汉地的主流图案。魏晋以来,中原曾盛行在金银器、铜镜上镶嵌珠宝类花,在中心花蕊及花蕊和花瓣交接的地方镶嵌以珍珠和宝石,图案上用佛教艺术的退晕色方法,以放射对称的格式,组成盛开、半开、含苞的花与花叶等富丽堂皇的团花,谓之“宝相花”。到了唐代,宝相花图案又出现在织锦图案中。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件唐云头锦鞋,其鞋面就是宝相花图案:“系用宝蓝、墨绿、橘黄、深棕四色在白地上织簇八中心放射状图案花纹的斜纹经锦,以中心部分,为六个花瓣组成的圆形朵花,围绕着中心朵花则是簇八放射对称的如意勾藤,在对称如意的地方,缀以花蕊及花叶。”从花的图案看,似是雪花的变形。宝.①“相花斜纹经锦”可能就是唐代的“瑞锦”,有“瑞雪兆丰年”、“雪花献瑞”的象征寓意。
阿斯塔那出土最多的是联珠对禽、对鸡、对兽图案的织锦,统称为联珠纹样织锦。联珠纹样是萨珊波斯的传统图案。3世纪兴起的萨珊波斯王朝流行一种装饰性程式化倾向的纹章艺术,出现在织物和金银工艺品中。“其上即根据此种风格表现着为求装饰效果而多少予以程式化的幻想怪物:头和前爪似猫而翼和尾部如‘开屏’孔雀的‘龙孔雀’;或武士骑在半狮半鹫的‘格力芬’或带翼的狮的背上,和其他‘格力芬’作战;或完全对称的成对野羊或雄狮,各举一前足对面而立;或如迦勒底—亚述所喜好的题材,即程式化的狸形野兽吞食着同样程式化的鹿类动物”。②在这些织物中,往往以联珠缀成的圆圈作为主纹的边缘,圆圈内常填以对马纹、对鸟纹和对鸭纹,也有填以波斯式的猪头纹和立鸟纹。③但是吐鲁番出土的联珠纹锦并不是波斯的工艺品,而是根据西域商人订货需求由汉人织作的织锦,其产地是蜀地,因此,这类织锦也称为蜀锦。“联珠禽兽纹斜纹纬锦有组织细密的精品,如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也有像联珠戴胜鸾鸟纹锦那样组织粗松的制品。这种联珠禽兽纹斜纬纹锦是这个时期墓葬中最常见的纹锦,发现的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显然,这意味着它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另外,我们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其他间接资料也可以知道这种有别于传统的图案,当时在我国内地已较为流行”。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件联珠“胡王”锦。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织锦采用倒置循环提花法织成上下对称的图案,米黄色地上有橘红、绛红色显花,在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手执长鞭,深目高鼻,花环之间饰以复合忍冬四叶纹。它显然是萨珊波斯式的联珠动物纹样织锦,但所织“胡王”汉字表明它确系汉地产品,估计是为九姓昭武或萨珊波斯王族专织的。在丝绸之路中端的高昌出现,可能是商品交易的结果。植物纹锦中的忍冬纹、葡萄纹也是西来的产物,但也很快被唐代织锦所接受。
唐代高昌、西州丝织物以绢类为大宗。绢也称“素”,本为一般平纹织物,经纬密度大致相等,除本色外,染成大红、粉红、墨绿、叶绿、鹅黄、绛紫、茄紫、翠蓝、湖蓝、藕荷等颜色图案的称为染缬,其染织方法又有绞缬、夹缬之分。当然,染缬也用于缦、缣、纱、罗、棉布等工艺上,这些染织物也统称印花丝织物。绢类丝绸物的绞缬法有两种:一种是将谷粒大致匀称地包在织物上,用线扎紧,染色,晾干后,拆去扎线,即现出遍地大小相等的菱形圈花纹;另一种是将织物折成连皱,用针线穿过,然后将线抽紧钉牢,染色后晾干,拆去穿线,即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①夹缬的方法是将织物绷紧,夹于镂花夹板中间,涂以蜡,再解去夹板,染后晾干,剥去蜡即成,因涂蜡处未吸收染色,即显出花纹。②夹缬法就是通常所称的蜡染法。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染缬织物看,主要以盛唐为主。墓葬出土的数件夹缬绢,一染绛地花云,一染棕地散花,一染土黄地花云,都绘制工致,浸染均匀,是唐代蜡缬的精品。③唐代流行的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和植物纹样就与这种染缬工艺有关。夹缬法不仅适宜于染制植物花卉图案,还可以印染较复杂的人物、动物、山石树木在内的组合纹样。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狩猎纹印花绢片就属此种。此为平纹印花绢织物,纹样内容为,在深绿地上显出粉绿的狩猎图案:骑马的猎手飞马张弓射狮,猎犬逐兔,猎鹰追飞鸟,天上流云,地下山石树木,图案呈上下对称,有强烈动感。唐代夹缬绢上的狩猎图案与5世纪的骑士(狩猎者)对兽纹锦图案可能有渊源关系。另一件纹锦同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纹锦黄地,以深青、浅蓝、浅黄色显花,以数个相切的圆环为图案骨架,其内饰狩猎者射鹿、对象、对狮、对驼等纹样。圆环之间填对马和忍冬纹样,圆环相切处又以仰莲相缀。除联珠纹鸟兽纹样流行于高昌等地外,还有一种人像、动物、树木等组合式纹样同样流行,不过它的主题是骑士、狩猎者等英雄形象与狩猎对象关系的表现。这些纹样是九姓昭武和萨珊波斯常见的纹样。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类题材还源自西域游牧民族的狩猎生活,虽然高昌、西州作为农耕民的汉族居民并不狩猎或根本无猎可狩,但与其关系密切的突厥人确实是典型的狩猎、游牧民族。不过,其主要影响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和萨珊波斯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萨珊波斯艺术的生命力超过了王朝生存的年代,直到九世纪在中国北方还有余绪可见。..由于进入中国新疆的一些画师来自伊朗东部或吐火罗地区,所以在画风上也必然带来波斯绘画的格调”。①高昌地区就有粟特人的聚落。汉锦唐绢正是在吸收、化解各种艺术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品格,这是它的大气,也是它的力量所在,这正是流光溢彩的中国气派,西域的汉族居民也受惠于此。
第四节 建筑艺术的绝响
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建筑按其功能可分为世俗建筑和宗教建筑。世俗建筑包括城市建筑、城堡建筑及民居等地表建筑,墓葬属地下建筑。宗教建筑主要是寺庙建筑、石窟建筑和塔类建筑。在此,仅探讨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世俗建筑的问题,而宗教建筑将在宗教艺术章节里涉及。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汉式世俗建筑自汉代屯田时已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高昌国和唐安西、北庭都护府期间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格局和城镇、城堡建筑。清代则是汉式建筑的极盛时期。汉至唐代的汉式世俗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建筑,即生土夯筑、地表下挖和土坯垒砌三种类型,这是适宜于西域气候、材料和施工特点的建筑,无需像烧砖瓦那样费力费时。当然修建这类土木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囿于建筑材料,生土是最便捷、最廉价的建筑材料。唐代已将砖、瓦用于建筑中,而在清代,砖木结构的世俗建筑就不仅仅是城市商号、官邸府衙了,会馆、民居也开始有了一砖到顶或半砖半土式建筑,园林式建筑此时也已经出现。
两汉时期的西域汉式建筑已不可寻,即使像两汉都护府遗址的确切位置也成了历史悬案,有待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更遑论一些完整的地表建筑了。现在也只能从遗存的几段残垣断壁、几座烽燧和零星的文献记载去推测了。西汉政府曾在伊循、楼兰、轮台、焉耆、姑墨等十余处屯田,东汉时伊吾庐、金满、柳中、高昌壁、疏勒等多处屯田也史有明载,这种屯垦延续到魏晋时期。这些屯田地区也是汉族军民的聚居地,有城堡、城镇等建筑。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起,就对古城的性质文讼不断,考古学家孟凡人先生认为它是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并有完整的行政机构。①这个时期屯田的楼兰城是以衙署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城镇建筑:“城中布局,从现存遗迹依我们发现的古水道为轴线,古水道由城西北向城东南流贯,大致可分两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可能是佛寺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外,西部和南部还有大小院落..西南区的残存遗迹,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间房址,整个建筑呈〓形,正中是用土块垒砌的三间房。..三间房东西两厢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②从考古发现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些建筑的材料是西域传统的土坯垒外墙,木料搭顶,以红柳枝作夹条抹草泥的内隔墙结构,至于屋顶是西域传统的平顶屋还是汉式的人字形屋顶,已无法得知,更不用说整个建筑的装饰工艺了。楼兰古城的整体布局是一个东面城垣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的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城址。③两汉以来这种用本地材料构筑的汉式建筑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筑城而居的定居模式,是中原传统与西域特色的完美结合,它对唐代的西域汉式建筑影响极大。
两汉时期西域屯田之处所还属于城堡、城镇型建筑,还不具备古代城市的功能,即使像高昌、交河在两汉时期也是筑城而居的屯田地,其建筑只具有军事城堡的性质。既屯田又要打仗,面临匈奴的威胁,这些屯田城堡应是易守难攻的。真正意义上的西域汉族古代城市当然要属高昌,它是在两汉时期屯田城堡高昌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凉时置高昌郡,从北朝时期麴氏王国的都城到唐代的西州时期,高昌城是西域汉族最具规模的城市建筑。9世纪后又成为回鹘王国的亦都护所在地,但总体上还是北朝到唐代高昌城的基本格局。现存高昌城遗址城三重,是不同时期的遗存,外城方形,周长5公里,内城居外城中部,宫城居北,外城西南角为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佛寺遗迹。高昌城门外面为曲折的瓮城。高昌城的外城墙高达12米,每面有2~3座城门,分别冠名为“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内城北面的王宫遗址还可辨认宫城为长方形,正中偏北为一小城堡,堡内西北有高台,台上有一个高达15米用土坯砌成的高耸建筑,似为唐以前高昌王的王宫遗址之一。与“城堡内建筑物”相对的中轴线上,还有四层殿的基址。殿基以东存遗址七处,殿基西有四处。可能是不同时期王宫建筑的组成部分。外城东南和西南是寺院建筑和工商业作坊。寺院由山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建筑组成。在寺院遗址外的东南和东北是“坊”的遗址,东南的坊有两排整齐的建筑遗址,在南北两排相对的房屋建筑之前为广场,南排房屋后又有一个广场。坊的四角,都有巷口式通道,通向坊外。据文献记载,高昌的作坊、商行已形成规模,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果子行、彩帛行、瓦器行、铛釜行、菜子行等,①手工业工匠有木匠、铁匠、缝匠、皮匠、甲匠、石匠、泥匠等。建筑遗存也证实存在各种作坊和商行。高昌城的平面布局“宫城在北,内城在南,有大面的高大建筑物,与唐代长安城的宫城、皇城的位置相同,应是高昌最高统治集团的驻在地。至于外城东南和西南的寺院和工商业的坊市遗址,又与唐长安外郭城,或一般城市的布局相类似,应当是一般市民的居住区。总之,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的平面布局是相当接近的”。②
交河故城是完全不同于高昌故城的古代城市建筑。它早期是车师前部的王廷,自西汉末年起,曾先后是屯田常驻地和高昌王国的交河郡、交河县所在地,9世纪中叶之后,又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交河州,一直到14世纪因战乱等原因被弃置。交河故城并非中原传统意义上的汉式地面建筑,它并没有用砖、石等建筑材料堆砌而成,而是在一块长1650米、宽300米的台地上向下挖凿而成,这是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观。当街道、房屋等建筑向下挖一定深度的土方后,再将挖出土方夯筑其上,免去土方拉运它地之役。现存的交河故城是唐代汉族居民修筑的遗址。贯穿全城南北的一条大街把居民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北端是规模宏大的以寺院为中心的寺院区,东区南部是官署区,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就设在此处。因全城四周崖岸壁立,并不需要城墙防守,故城东、城南各留一个城门,供居民出入。故城的大街小巷、民居平房、佛寺佛塔、手工作坊、两层官署都是在原生土中掏挖而成。故城的不少建筑下为窟洞,上为平房,两层乃至多层。这种建筑构造样式被称为“陶复”式的地窟,其特征是:(一)上半截“累土”,下半截“凿地”,作半地下室式;(二)窟顶中央“开口其上”,名为“中露”;(三)通体作圆形,故称为“环堵”(“圜环墙”)。最初的“陶复”式地窟,只有一个出入口,即“中雷”。人们进出窟室都必须通过窟中央柱形梯子经“中雷”上出下入。以后,这种“陶复”式地窟在设计和建筑上有了发展,人们在南壁或东壁基部挖开一个洞口,作为“户”(门户),并在户外挖出一道斜坡梯形的“门道”。这样,窟中人便可以通过这门户和门道上登到地表上来。①壁门在不同季节还有空气对流、御寒、增加阳光照射的作用。交河故城的这种“陶复”式建筑显然是因地制宜,夏避暑冬御寒的理想居所。交河城的寺院占地面积为5000多平方米,虽不及高昌城寺院面积大,但建筑布局和风格均异于高昌寺院。交河城的寺院也是掏挖原生土而成,由山门、大殿、僧房、庭院等建筑组成,城北是一组壮观的佛塔群,以中央大佛塔为主,四角各有25个小塔,形成纵横各5个方阵,共计101个。佛塔的这种形制是当时汉族居民中佛教密宗信仰的反映。
唐代曾在伊州、西州、焉耆、乌垒、于阗、疏勒、庭州、轮台、清海、碎叶等处屯田,并建有伊州、西州、庭州和四镇。郡县制设立后的州、县所在地都形成了一定的城市、城镇规模。巴里坤县的大河古城和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均分别为唐代屯田驻军的伊吾军和庭州城的遗迹。从出土的莲花纹砖和瓦当看,这些城堡、城市建筑已用砖、瓦等建筑材料,建筑样式和风格也一如内地唐代汉式建筑。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城市建筑、宗教建筑、宫殿建筑和四合院民居及园林建筑始终占主导地位。清代西域进入大统一、大移民、大融合时期,也是西域汉式传统建筑的辉煌时期。乾隆年间的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建省后以绥定为伊犁府治城),新疆建省后的省会——乌鲁木齐(时称迪化)都是以汉族传统建筑理念建城的。它们与喀什噶尔形成清代新疆的三大城市格局。坐落在现伊宁市西30多公里处的惠远古城初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后扩建,城周5公里,城高5米,是新疆建省前清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一座商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城市。通常将清代惠远和绥定、宁远、拱辰、广仁、瞻德、塔勒奇、惠宁、熙春称为伊犁九城。惠远旧城1871年毁,1883年又在其北修建惠远新城。新城周长近5公里,城垣高约5米。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以直通四大城门的四条大街构成城市基本布局。四条大街上还有48条小巷,组成商业和居民区。钟鼓楼是一座中国传统风格的三层三檐歇山顶的砖木结构建筑,雕梁画栋。屋檐铺有琉璃瓦,每层12根檐柱绘有花卉等图案,每层檐角均吊有小铜铃。钟鼓楼正东不远处是伊犁将军府旧址,现存府门、石狮、金库、厢房、凉亭等建筑。伊犁将军府的庭院花园古木参天,亭台布于其间。仿江南园林的花园曲径通幽,给人幽逸、明净之感。伊犁将军府花园是迄今所知的新疆最早的汉式园林建筑。
中国传统城市都是按照自然地形布局理论规划的。《管子》认为,建城的原则是“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原则也在乌鲁木齐建城原则中体现出来。早在汉唐之际,乌鲁木齐附近就有屯田的城堡,但还不是传统的城市,从清乾隆年间到光绪年间才逐渐形成城市规模。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土城基础上,又于二十八年(1763)添加四门建迪化城,为雏形期。乾隆三十年(1765)在旧城之北另建新城,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始建巩宁城(俗称老满城),为扩展期。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迪化为省会,光绪十二年(1886)扩建筑城,城周5.5公里,有惠孚门(东门)、丰庆门(西门)、肇阜门(南门)、景惠门(北门)四个正门和小南门、小东门、小西门3个偏门组成城市基本结构,为定型期。乌鲁木齐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其东、南两侧是天山山脉,西、北两侧为平原地带,城依乌鲁木齐河而建,雅玛里克山(俗称妖魔山)与红山南北对峙。因依山势、水势而建,乌鲁木齐城郭是不合规矩,道路是不中准绳的,但与古人提倡的建城原则不相悖。对于老迪化城,清代文人椿园七十一在其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撰《新疆纪略》中写道,迪化城“字号商店,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这还是建省前的情景。清代是乌鲁木齐传统城市建筑形成和定型的时期。1884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作为省会,以大、小十字(街)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大十字是以老“津商八大家”永裕德、同盛和、复泉涌等和新“津商八大家”永盛西、裕昌原、庆和春等为代表的商业街,店面鳞次栉比,商号林立;小十字一带则是戏院、国药店、清真饭馆、老君庙等云集。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后,在南门外的南梁地带由俄国开设了吉祥涌、天兴行、德盛行、吉利行等俄商洋行八大家,形成洋行街。20世纪20年代后,南关一带则是少数民族商人经营的商业中心。乌鲁木齐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于是内地各省的民间文化也就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形成以木架结构为主体的寺庙、商店、会馆、四合院等汉式建筑风格。红山一带是玉皇阁、大佛寺、地藏寺、北斗宫、龙王庙等;西九家湾一带是关帝庙、仙姑庙;建国路是观音阁、娘娘庙;东风路是定湘王庙、两湖会馆、左公祠;中山路是城隍庙、龙王庙、山西庙、陕西会馆等;其他各处还分别有文武庙、积骨寺、八仙庙、财神楼子、药王庙、马王庙、火神庙等。因乌鲁木齐河将乌鲁木齐分成河东河西两部分,故城东、城西就由桥来连接,原名“虹桥”、“巩宁桥”的西大桥成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这种依山傍水而建的移民城市无内地传统城市建筑以中轴线贯穿其中坐北朝南的严格布局,因为它只能依地形走势而建。其建筑风格也不是一元的,而呈多元化发展,因为内地南北各省移民带来了不同风格的建筑艺术,且因功能而异的建筑又形成不同风格。外来文化的冲击,城市建筑又呈现出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二元结构,这正与新疆近代文化特征相契合。
西域汉族民居建筑除高昌交河的“陶复”式的特殊形式外,基本上是上栋下宇型的居住样式。但因天山南北的气候、降水量差异,又分为平顶形和两流水形(即“人”字形)民居建筑。天山以南地区干早少雨,其民居基本为一面形的平顶屋。这种民居用土坯砌墙,平顶,住房多在北面,房内设土炕,自成一家一户院落,院落呈正方形。而天山以北地区因气候寒冷,雨雪多,民居多用砖石砌成,屋顶呈“人”字形,房间一般为一明两暗式,坐北朝南,也有坐西朝东的。从近代新疆的汉式民居看,农村与城市有所不同。农村建筑是前庭后园式,即正房前是庭院,侧为厢房,往往是库房、牲畜圈等,而正房后面是菜园、果园等。城市民居最典型的是北方四合院式建筑。自清代乌鲁木齐兴起津商八大商行后,就在大十字商业区周围出现了北方四合院式民居。大十字一带的八条东西巷、藩台巷子、三角地、满城、北梁一带是四合院最集中的地带。乌鲁木齐标准的四合院是清代末期民国初期天津杨柳青商人刘贵铭建在藩台巷子的四合院住宅。“这个四合院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前面的高台阶上有两扇黑大门,门槛高约30厘米,是活的插板式,可以拿下来,门槛的前两侧各有一块方石凳子,大门过道宽约2.5米,接着是黄油漆的木质二道门。院子为正方形,约15米见方,用青色大方砖铺地。有南、北住房各三大间,东西住房各三小间,四幢住房相对称,前廊后厦,布局合理。另外还有厨房、炭房、厕所、水井和渗水井等设施。所有房屋均为木质框架结构,一砖到顶。南、北房的中间屋为堂屋,两侧是卧室,室内是小方砖铺地,有火炕取暖,火炕的一端有放置被褥的长立柜(俗称被搭子),炕沿的上方和两侧有雕刻的木质隔扇。全院房间的门窗,均以古式花木格子装饰。院落中间砌着花坛,每到夏天牵牛花顺四面花架爬上屋顶,花红叶绿,整个院落显得古朴静谧”。①四合院式建筑体现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封闭空间的自闭性和不张扬性,并使建筑及装饰更富有层次性和虚实变化。同时“如果家族人丁兴旺,有财有势,家宅可以向其四周无限扩展。..这种住宅形制,符合我国古代的家族型制及其发展”。②
西域汉族建筑文化在形成地域化的过程中,与西域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之间是一种族际文化共享关系。汉族建筑文化不仅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也吸收了汉族的建筑文化。清代是汉民族与满族、锡伯族之间族际文化共享频繁的时期。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至伊犁屯垦戍边的锡伯族被清政府组成八个牛录,各牛录建筑虽属清朝八旗制的军民兼用型,但城堡及官署、民居均是汉式建筑。每个牛录的城堡由高大夯实的正方形城墙组成,城墙上有垛口,并在东西南北砖砌四个城门,城墙周长七八里至十里不等。城内是“牛录”办事机构、胡同式民居以及粮库、兵器库和监牢等。这种城堡式建筑和古代汉式能防易守的城堡建筑从形制、布局和功能上都相同。甚至官署、关帝庙、娘娘庙和民宅也是汉式的。清末民国初年伊犁地区锡伯族的“人”字形大屋顶房本身就是汉式结构的宅屋。这种房屋也是木质框架结构,包括支撑柱和房顶,然后用新疆传统的土坯砌墙,再抹细泥并用白灰粉刷,后期也有砖砌墙的。房顶为双流水型,有伸展出的廊檐,门窗是小木格式的。窗户都很大,用于充分采光。“人”字形大屋通常为一明两暗的三间式,门窗工艺精细,雕刻、绘画显其富丽、典雅。住房与庭院组成典型的锡伯族民居。有人认为这种房屋造型是从满族民居学来的。的确,东北的汉族、满族等均居住一种被称为“东北大院”的民宅,但此类建筑的起源则来自北方的汉式四合院,因此是汉化的产物,锡伯族“人”字形大屋顶房当然也不例外。现存清代锡伯族的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为汉式寺院建筑类型,大殿中梁上彩绘二龙戏珠等也完全是汉族民间传统图案艺术。这种体现在建筑上的文化融合现象正反映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精神。
尽管丝绸之路上的许多汉式建筑随着岁月的剥蚀已成为历史的绝响,但永驻人们心中的是那神圣的精神殿堂,它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辉煌。
第五节 汉唐遗风与屯垦艺术
兴于两汉,盛于唐代的西域汉文化艺术总不免使后人产生怀古之情思,但这绝不是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情,而是一种通过对汉唐遗风的追念,发扬光大汉文化艺术的精神追求。在西域这块热土上,汉唐将士们演绎了多少屯垦戍边的壮举,所以清代诗人总是凭吊这段历史:“至今扪古碣,血渍土花班”(李銮宣《巴里坤城北寻汉永和二年碑》),“摩挲残碣在,唐汉未销兵”(史善长:《到巴里坤》)。抚摸汉唐古碑,深感统一西域责任重大,弘扬汉文化意义深远。清代屯垦戍边、统一西域的举措,将西域汉文化艺术推向新的高度。
清代西域的汉文化艺术总体上讲也是一种秉承汉唐精神的屯垦艺术。往事越千年,清代的屯垦艺术无论是规模、类型、层面、内涵都超过了汉唐。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就开始大规模屯垦,从乾嘉年间开始,新疆建省后又有大批内地移民来到新疆屯垦。清乾嘉年间的屯垦主要是兵屯、回屯、民屯、旗屯、遣屯等形式,屯田地区主要在天山以北以东地区,其中,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昌吉等地已形成相当规模。据乾隆四十年(1775)统计,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之间,这些地区屯垦人数达七万余人,屯田亩数已逾二十八万亩。新疆建省后,新疆巡抚刘锦棠等人制定《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军民屯垦,于是内地汉民“携眷承垦络绎相属”。据《刘襄勤公奏稿》卷一二载,清光绪十二年(1886),仅迪化、奇台、昌吉、阜康、绥来、济木萨尔、呼图壁等地又安插屯垦移民一千九百户。屯垦的目的当然是扩大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但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内地各省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化艺术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族的年节习俗、饮食服饰、南北戏剧、庙会社火、诗词说唱、婚丧礼仪、剪纸年画等都成了屯垦区的耀眼的文化景观。以汉族艺术为载体的汉文化与屯垦规模、移民人数成正比,对整个清代新疆的多民族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近代新疆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翼。
清代新疆的屯垦艺术类型比汉唐时期更加丰富,而且增添了许多新品种。戏剧演出在清代至民国期间的新疆汉族艺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纪昀在其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返京途中所写《乌鲁木齐杂诗》中吟咏乌鲁木齐戏剧演出的盛况:“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并自注曰:“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就连楚调也往往是“低徊唱煞红绫袴,四座衣裳涴酒痕”。显然,自清乾隆年间屯田驻军、内地移民和谪戍遣犯日益增多,南曲北戏艺术也在边城乌鲁木齐兴盛起来,京剧、昆曲、秦腔、越剧、楚调、曲子戏争相纷呈。左宗棠率十万湖湘子弟下天山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时天津杨柳青商贩“赶大营”的出现以及更大规模移民潮的到来,关内各地方剧种在乌鲁木齐等地扎下了根。到19世纪末,乌鲁木齐已有了唱花鼓戏的“清华班”、唱秦腔的“新盛班”、唱河北梆子的“吉利班”等戏班。湖南花鼓戏原是随军的花鼓自乐班在乌鲁木齐登台演出,之后组成“清华班”专业戏班,除唱堂会外,主要在庙会或节日进行演出。秦腔艺人吴占鳌组织的“新盛班”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首次在红山庙会上清唱演出。光绪十七年(1891)以菜农为主体的河北人也组成演唱河北梆子的“吉利班”参加到红山庙会演出的行列中,主要还是清唱。刘锦棠任新疆巡抚期间在乌鲁木齐修建了“定湘王”庙,从内地购置新戏箱,供该庙会演出之用。1917年,由陕西会馆出面,联合陕、晋、甘等地流入新疆的秦腔艺人组成“三合班”,开始在乌鲁木齐及北疆各县演出连台本戏。曲子戏清末出现于陕、甘、宁、青移民聚居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鲁木齐等地出现秦腔、京剧、花鼓戏、河北梆子、曲子戏竞相演出的场面。与内地地方戏演出不同的是,新疆的汉族戏剧出现了“民汉合璧”的现象。维吾尔族京剧花脸演员达吾提、维吾尔族曲子戏演员卡帕尔,回族、满族、锡伯族曲子戏演员等都曾名噪一时。只有在新疆这样的多元文化氛围中才会出现这种族际文化共享的盛况。新疆曲子戏成为新疆地方剧种之一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甘肃民间艺人夏三通组织敦煌曲子戏进新疆演出,之后,它很快被新疆汉、回、锡伯等民族接受,在城乡普及开来。新疆曲子戏是个博采众长、吸收融合各种音乐成分最杂最多的剧种。最早是在陕西眉户剧音乐的基础上,在西进的过程中融进兰州鼓子词、青海平弦、敦煌佛曲音乐等形成。在西渐到新疆演变成新疆曲子戏的过程中,锡伯族的“秧歌调”几乎全被新疆曲子戏吸收融合。“秧歌调”分“平调”和“越调”两种,它是锡伯族西迁前吸收汉族“秧歌调”演变而成的一种戏曲音乐。新疆曲子戏音乐中的“天山令”还吸取了哈萨克族音乐成分。①新疆曲子戏的白口,完全是本地化的新疆汉语和方言俚语,不少还融进了维吾尔、俄罗斯等民族词汇,全国各地方言俚语也夹杂其中,从语言上讲它成了新疆汉族或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都能听得懂的语汇。虽然,新疆曲子戏原型脱胎于眉户剧,但在演进中已非原来的音乐,它一旦与新疆各民族音乐杂交后就显出了自身的优势,这要归功于清代大规模屯垦移民带来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勃兴。清代还有说书艺术流行于民间。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描写了一位名叫孙七的说唱艺术家。因为孙七说书技艺高超,听众“且唤诙谐柳敬亭”。虽然说书内容都是野史小说故事,但农户人家都爱听。
清代西域屯垦艺术类型中民间造型艺术虽不登大雅之堂,但为汉民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钟爱——剪纸和年画。西域可考的汉族剪纸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其后还有唐代剪纸,这正是高昌汉族王朝和西州时期的遗物。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剪纸有四幅:对鹿团花剪纸、对猴团花剪纸、对蝶团花剪纸和几何纹团花剪纸;唐代一幅;剪出连续七个纸人的代人形剪纸。从剪纸图案看,对兽图案、团花图案是当地汉族中流行的主流纹样,各种丝织物上都有这类纹样。这些剪纸的“表现方法是用象征、表号、谐音的方法和折叠形式,选取有关的动植物,巧妙地组合成托物寄意的寓意图案”。①这个时期的剪纸主要是作为随葬品,南北朝剪纸中出现莲花、鹿、猴等动植物和光环、宝塔形纹样,应与高昌汉人的佛教信仰有关,祈愿佛法保佑死者的灵魂升天。清代西域屯垦汉族移民带来的内地剪纸艺术己经超越了丧葬和宗教范畴,它既是一种民间活动,又是一种有喜庆内涵的民间艺术形式。“新疆汉族剪纸,主要是年节喜庆用于装饰的窗花、喜花、礼花及绣花等。其风格是丰富多彩的。有的粗犷简练,有的浑厚朴实,有的工巧纤细,..新疆汉族剪纸的基本特点还是淳朴、粗犷、厚实、明朗。属于西北的风格”。②这些民间剪纸大致分为用具纹、植物纹、动物纹、自然纹、几何纹、文字纹等,其中古钱、牡丹、梅花、鱼、羊、星月、水波、圆形、方形、三角形、雪花、喜字、寿字等纹样出现频率最高;构图法有平衡式、对称式、辐射式、填充式等,其中花中套花、果中套花、动物体上剪花等填充式构图法最常见。剪纸中的“喜花”多用于结婚等喜庆场合,窗户、室内墙上、各种陪嫁妆奁上都贴上喜庆吉祥的剪纸,如“龙凤呈祥”、“状元及第”、“麒麟送子”、“莲生贵子”、“榴开百生”等。过春节时贴窗花,糕点、供果上放喜花,也成为当时的年节习俗之一。共同的审美情趣使新疆的汉族和回族、锡伯族、满族的剪纸中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主题、题材和风格。剪纸图案中大量使用牡丹花、荷花、梅花、石榴花、蝴蝶、孔雀、凤凰等纹样,表达的吉祥、喜庆、福寿等寓意都是相同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剪纸并非用纸剪出图案,而是以剪纸方式装饰建筑、服饰、毡毯、刺绣等,以植物纹样、几何图形为主要图案。游牧民族还以动物角等为装饰图案。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剪纸图案中也常见汉族喜爱的牡丹、梅花、荷花等;而新疆汉族剪纸中也常有少数民族的巴旦木花、石榴花等图案。这种现象只有在清代以来形成的以屯垦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才会出现,从这点讲,是清代的屯垦文化催生了屯垦艺术,屯垦文化是屯垦艺术的母体。
汉族古老的民间木版年画有三大画派: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杨家埠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而在清代新疆汉民族中流行的是天津杨柳青年画,这与天津杨柳青人随左宗棠大军“赶大营”有直接关系。杨柳青年画的波及面不仅仅是新疆汉族,也影响到了锡伯、满等民族的习俗和审美趋向。“赶大营”的结果是,几乎年年有杨柳青人落户于乌鲁木齐西河坝一带,形成颇有津味特色的“杨柳青村”。到了20世纪40年代,把天津杨柳青人开设商号、居住较集中的大、小十字一带也曾称为“小杨柳青”。乌鲁木齐汉城的早期居民是以天津杨柳青人为主是无疑的。于是,思乡心切的乌鲁木齐杨柳青商人常购进杨柳青年画,以供年节张挂之用。凭借津商八大商行的势力和信誉,乌鲁木齐成了杨柳青年画的批发站,经这儿再销售到全疆各地。据说乌鲁木齐等城市在春节前夕卖年画的地摊一家挨一家。杨柳青年画题材多为“连年有余”、“万象更新”、“五谷丰登”的四季耕作图,还有“恭喜发财,四季平安”为内容的财神、门神、福禄寿三星高照图,也有表示喜庆的“双喜登梅图”和由谷穗、花瓶、鹌鹑组合的“岁岁平安图”等。总之,它迎合了当时人们除旧迎新、吉祥如意的心理需求。杨柳青年画具有形式多样、色彩艳丽的装饰美特点,故张贴年画成为当时边城乌鲁木齐等地过春节的流行时尚。它又与民间流行的迎财神、送灶神、贴门神等习俗结合起来,不仅为新疆各地的各省来的汉族居民所喜爱,也为接受汉族年节习俗的满、锡伯等民族钟情。杨柳青年画中还有一种称作“详林”的品类,“画的是亭台楼阁,没有人物,颇似穆斯林建筑,还有一种是画瓶花壶盘、博古文物,称作‘格景’,..很受新疆穆斯林民众的欢迎”。
清代西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屯垦文化艺术中莫过于传统的庙会和会馆社火因参众广、影响大、时间长而最为闻名,也成了展示全国各地民间文化艺术和风俗的最佳场合。从清代到民国期间,庙会文化和会馆文化是整个新疆汉文化的两大支柱,也是一种强势民间文化。
汉民族传统庙会是以寺庙为活动场所进行的全民性娱神、娱人民间文化活动,以戏剧歌舞表演祭祀为主要内容。在传统汉族社会中,几乎是到了有庙必有会的程度。汉民族传统的祭祀活动早在史前就产生了,春秋时已有定期祭神庆典类的狂欢活动,功能齐全的庙会大致起于隋唐时期。以戏剧、歌舞之类的狂欢活动也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从乐身到乐心的飞跃。这种情形越到后期越明显,参与者已并不在乎去祭祀什么样的神祗了,而是在这种全民性的民间狂欢艺术节中感受到了身心的愉悦。自清乾隆年间始,随着内地汉族移民增多,供奉各种神祗的庙宇也多起来,特别是乌鲁木齐红山嘴子更是大小庙宇林立。自乾隆十四年(1749)修建玉皇阁后,相继修建有大佛寺、地藏庙、北斗宫、三皇庙等。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释迦牟尼诞辰和四月十五日的玉皇阁庙会,红山嘴子庙会持续半月有余,庙会也成了乌鲁木齐汉族居民最重要的民间娱乐活动。庙会中不仅有“清华班”、“新盛班”、“吉利班”等的花鼓戏、秦腔、河北梆子等剧种搭台演出,而且以后还加进了京剧、新疆曲子戏的演出,而且变戏法、耍中幡,乃至少数民族的赛马等活动也参与其中。对于红山嘴子庙会的盛况曾有一段民间说唱反映了它的真实情景:
红山嘴子妖魔山,两个塔对得端。乌鲁木齐河水凉又甜,绿树成荫在岸边。庙会过了十来天,大人娃娃挤成山。西安人敲梆子唱乱弹,天津人又唱又敲拉洋片。河南人耍猴卖药围圈圈,拳把式耍的刀枪矛子三节鞭。吹唢呐鼓敲的欢,喀什噶尔的踩弯绳太惊险。耍把戏的空中取水变鸡蛋,对台戏唱的真好看。看了桄桄子(秦腔)看梆子,又看京戏小曲子。小四儿唱的盘肠战,张胡子唱的走雪山。兰州红、王小旦,二人唱的是小姑贤。看戏吃喝都方便,就怕你手里没有钱。回族人手端洋盘子卖凉面,维族人卖的是烤肉烤包子油抓饭。忠义馆三成园,搭起席棚子把酒席办。过油肉、溜三片、清蒸鸭子带海鲜,盖碗茶往上端,保你吃好、唱好、玩好满心喜欢。①
从说唱的语气及用词看,可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乌鲁木齐民间的顺口溜,口语化,还显点粗俗,但多少道出了乌鲁木齐庙会的盛况。但乌鲁木齐的庙会不仅仅限于红山嘴子的农历四月初八和十五日,还有农历三月十八日的观音阁庙会、农历六月十五日的八仙庙会、老君庙会、农历七月十五日的城隍庙会、农历六月六日的龙王庙会、三官庙会、定湘王庙会、农历四月初八的药王庙会等,有的则成为行业性的庙会。一切庙会活动自然是取悦于神祗的动机,但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参与是群体性的,如秧歌、小调等歌舞就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并不像舞台演出那样演员和观众判然有别。“从深层来看,这类活动在传统社会中起着调节器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平日单调生活、辛苦劳作的调节器;另一方面,也是平日传统礼教束缚下人们被压抑心理的调节器(尽管人们自己往往也未曾觉察这种心理)。更进一步看,这样一种调节器又起到了社会控制中的安全阀的作用”。①各类庙会是以生活在新疆的所有汉族居民群体参与为特征的,参加者并不特别重视东西南北移民身份的个体性差异,因此它所展示的民间文艺活动更有普泛性,这也是吸引所有汉民族集体参与的重要原因。就这点而言,它不同于各会馆的民间文艺花会——社火活动。
新疆的汉族会馆社火是节日期间各地民间举行的各种乡土性娱乐活动。社火分地面和高台两类,地面社火多在晚上举行,而高台社火则在白天。据说社火源自汉代百戏,而汉代百戏又与西域乐舞、杂技有关联,清代内地社火在新疆的流行也可以说是重归故里。新疆会馆是清代屯垦移民的产物,会馆是一种维护同乡利益,以松散型的乡缘、业缘为主的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机构。清代设在乌鲁木齐的主要是七大会馆:两湖会馆、山西会馆、甘肃会馆、陕西会馆、云贵川会馆、江浙会馆、中州会馆。各会馆都有本乡本土特色的社火活动,个性化特征十分突出,两湖会馆的花鼓戏、闹龙灯,陕西会馆的秦腔、眉户、高抬,甘肃会馆的跑早船,中州会馆的舞狮子,山西会馆的汾阳花鼓,直隶公所的高跷、中幡都属地方性的民间文艺形式。两湖会馆的龙灯夜间在街头表演,龙身的每节都点有蜡烛,舞龙时随行进上下翻动,似火龙飞舞。山西会馆的花鼓表演是男背腰鼓,女持小铜锣,边舞边敲,队形富于变换。甘肃会馆的跑早船,亦称灯船之戏,行进表演时,演员口唱小曲,用手划动船桨,以步履表现船荡漾前行,入夜,“船”上装有灯笼,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直隶公所的高跷表演者双脚踩木跷,表演以传统戏曲为内容的舞蹈,动作有扑、捉、闪、滚、爬、劈叉等多种,在锣鼓声中或行或走、或演或唱都有一定程式。陕西会馆的高抬亦叫铁芯子社火,铁芯子是4人肩扛的有基座的高约5米的铁杆,并根据画面造型焊接成脚手架,其上由扮演各种角色的八九岁儿童进行表演,表演的多是传统戏曲内容,往往一抬一个内容,如《黛玉葬花》、《游西湖》等,陕西会馆在春节前后都组织20余台高抬上街表演。各会馆的社火表演虽然有强烈的乡土情结,且产生于较封闭的一方地域,但它一旦融入到清代新疆这样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开放社会中,就不单单是一省或一地移民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活动,而是一种为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大众文艺了。因为社火都是以街头表演形式出现的,受众不分东西南北,也不分汉族或少数民族,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欣赏习惯各取所需,各有所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乌鲁木齐总商会组织的社火表演中的秧歌队,扭秧歌者可能是来自各地的东北人、山东人,而吹唢呐者又是维吾尔人。观赏者则更不分民汉了。因此,从一隅封闭乡间走出来的社火文艺活动一旦到了新疆这样八方移民汇聚、四面文化相融的开放空间中,民间艺术往往也就成了全方位的开放系统。
当人们审视清代的屯垦文化及其艺术现象时,不能不感到它前承汉唐遗风、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兵团文化的承袭关系。虽然各自都打上了不同时代的深深烙印,但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屯垦文化艺术的精髓早已植根于丝绸之路上西域这块沃土,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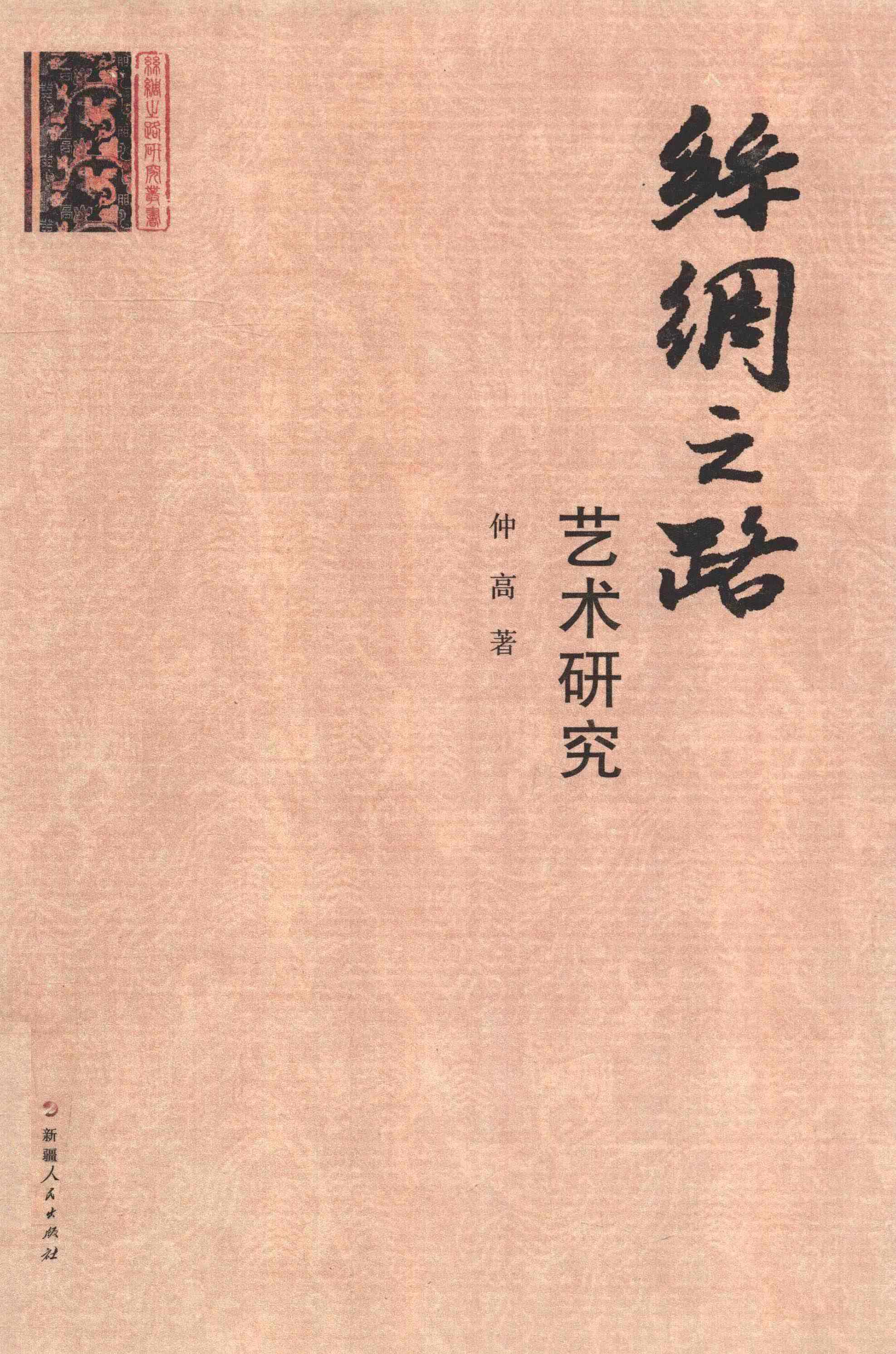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