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草原咏叹调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35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草原咏叹调 |
| 分类号: | J642.213.6 |
| 页数: | 9 |
| 页码: | 162-170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草原民族风情情况包括草原咏叹调、萨满击鼓、阿肯弹唱等。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草原 咏叹调 |
内容
哈萨克族谚语云:“歌是哈萨克人民的翅膀。”岂止是哈萨克族,所有的草原民族都是这样,他们自古以来就视歌为生活的一部分。只是由于口头流传,为史籍所载的游牧民族的民歌寥寥无几。作为匈奴民歌流传下来的也只有一首《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首现存最早的游牧部民的哀歌成了他们痛失草原故土的绝唱,一泣一唱,一哭一回头,是多么痛心疾首。过了五六百年,又有一首名为《敕勒歌》的草原部民的民歌载于史籍:“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抒情意味极浓的牧歌,它“于明快激越中见迂曲,自然浑朴,跌宕多姿。它所表现的感情幅度是宽广的,表现的热爱乡土的激情是真挚的”。①正如《诗薮》所言:“此歌成于信口,咸谓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无意发之,所以浑朴苍茫,使当时文士为之,便欲雕绘满眼。”这的确是肺腑之言,天然无雕饰的民歌总是以清新、纯朴的秉性博得人们的青睐,这一点,远非文人创作可比。但这些古老民歌的曲调、韵律、节拍已无从知晓,有关草原音乐传入中原的记载也是凤毛麟角。《魏书·乐志》载:“复通西域,有以悦般鼓舞设于乐署。”《北史》记:“悦般国,在乌孙西北,..乃诏有司以某鼓舞之节,施于乐府。”至于5世纪传入中原的西域草原悦般乐舞的形态概未提及,从字里行间揣摸,可能是应鼓点起舞的乐舞,是否有唱词,不得而知。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的最早的吟唱应属于与萨满教密不可分的祷告歌,即萨满歌。“无论是什么肤色的巫师,他的咒语总是韵文。战歌、情歌、摇篮曲、哀歌以及婚礼颂歌,无疑在最初都是具有巫术、宗教的意义,带有咒文的性质。”②萨满在氏族部落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常举行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各种仪式,如萨满的“行巫术”——“萨满昏迷”仪式,献祭祭祀仪式,以及群体发生危难、个人或群体遭遇病疫、天灾、征战时举行的仪式等。这些仪式均由萨满主持,其中吟唱祝文是重要内容。19世纪60年代中亚学者拉德洛夫曾对阿尔泰山区的哈萨克族萨满教遗迹进行过田野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记录了萨满教祭祀仪式的全过程,并记录下萨满歌。在仪式的请神、降神、送神过程中,萨满都在吟唱一种带韵味的祝文。让我们看一段拉德洛夫有关哈萨克族萨满召唤神灵的记录:这时,萨满左手持神鼓,并用烟熏。然后萨满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慢慢地用木槌击鼓,并以激昂的声音呼唤神灵。每位被召唤的神灵应都对萨满回答:“啊!卡木,哎!”萨满便将它们收入神鼓中。萨满每完成召唤一位神灵的过程,都得用相应的动作将神鼓倾斜一下。首先呼唤的是海之神——亚依克汗,然后是开拉汗,以后是派金汗,还有好多好多,最后是亚伯尔汗。最后的呼唤以如下的词语结束:
请您听听我的祈念,
并请满足我的祈求!
请给予永久的平安吧!
请给予长夜的睡梦!
请给予浓厚的马鬃!
请给予夜晚的平静!
请给予千家的平安!
请给予万户的平和!
请到我右手边玩一玩!
我的右手击打着木槌在召唤!①
哈萨克族的萨满歌实际是歌舞为一体的,萨满击鼓、吟唱往往是在有节奏的节拍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动作和曲调。在萨满歌中保持着古老而优美的叠句。叠句有时用的是无意义的词,如哈萨克族萨满追捉祭牲魂灵时就大声吟唱:
拿起金绳子!
嗨,嗨,嗨!
快快摇起缰绳
!嗨,嗨,嗨!
套上金笼头!
嗨,嗨,嗨!②
实际上是以“嗨,嗨,嗨”等叠词加强气势。有时也用拟声词,如萨满在呼唤天鹅精灵时往往反复模仿鹅的“嘎克、嘎克”的叫声。在萨满追捉祭牲灵魂吟唱时,众人还大声呼喊“哎嗨,哎嗨”,形成一种合声效果。如果追根溯源,萨满歌“从民间音乐和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当中广泛地吸取材料,特别是吸取了大量的神话材料;同时,这些歌往往有丰富的想象,运用语言灵活、大胆,它也反过来给了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以很大影响”,①在草原游牧民族的民歌中,萨满歌现在是作为宗教习俗歌出现的。
由于民间音乐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近半个世纪以来调查、发掘、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民歌已取得可喜成就,使人们有幸一睹草原游牧民族传唱不息的民歌的芳容。蒙古族长调短调、哈萨克族阿肯弹唱、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演唱以及所有草原游牧民族共有的不同类型的习俗歌、情歌等构成了流淌在广袤草原的咏叹调。
蒙古族长调“节奏缓慢,曲调高亢豪放,真假声并用,气息宽广,字少腔长,以辽阔、宽广而著称。结构一般以上下句组成乐段。有触景生情、即兴编唱的特点。分单声部长调和带持续低音长调两类”。②长调产生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故有牧歌、思乡曲、赞歌、宴歌、婚礼歌等多种形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晓蒙古语的丹麦人亨宁·哈士纶在其《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中收录了不少采集自西蒙古的民歌曲调(他实际录制了60首蒙古民歌),其中一些显然是长调。其中有土尔扈特民歌《西部可汗》、《可爱的暗褐色小马》、《我可爱的小雄鹿》、《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额林哈毕尔噶山》以及察哈尔蒙古的《博尔塔拉乌拉》等。其中一些属赞歌,另一些则是牧歌。哈士纶认为,这些长调“常常是高低音同度一致的,但当两个或更多的蒙古人在一起唱时,唱得最好的喜欢唱出延音,延长到他的肺活量的最大限度。然后他继续把这首歌曲唱下去,好像是其他歌手的回音一般,从而使得这首抒情曲和复调多重唱相似”。③其中《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显然是歌手即兴演唱的抒情长调,“歌手反复用本嗓和假声演唱着,山上的回音中又掺和着他自己清脆嘹亮的嗓音,构成了一首向灿烂的早晨问候的交响乐曲。..歌词是歌手眼下自己即兴吟成的。歌词描绘了对繁茂的伊犁河谷的秋天的幸福回忆,在那儿,茁壮的牲畜和肌肉发达的马儿站在高齐马肚的新鲜多汁的黄草中”。④歌手的长调显然属于牧歌一类。短调民歌在土尔扈特等厄鲁特和察哈尔蒙古诸部中都流行,“短调民歌大多风趣幽默,节奏明快,曲调活泼,故又称诙谐歌曲。..察哈尔短调民歌富有风趣幽默,曲调极为活泼,节奏强烈明快,每一位歌者都进发出炽烈如火、浓烈如酒般的热情”。①《高山上的花》、《金纽》、《想念我的家乡》、《摇篮曲》等都是新疆察哈尔蒙古久唱不衰的短调民歌。其中《摇篮曲》则取材于民间传说,本身就在叙述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情节逐步展开,但不是连续不断的叙事,而是像戏剧一样显现一系列小场面带有频繁的重复,这些都是真正叙事曲形式的特征,即使没有叠句,也是如此”。②
在哈萨克族民歌演唱中有一种有问有答的对唱形式,分为阿肯对唱和群众性对唱。成熟阿肯参加的只能是高层次的、规范的被称为“苏列的对唱”。人们说哈萨克人有两件宝:一是骏马,一是歌喉。哈萨克人是歌唱的天才,从小孩到老人,从男子到妇女都能一展歌喉唱上一曲,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冠以“阿肯”的尊衔。能唱多种民歌的民间歌手不是阿肯,擅长即兴做诗的民间诗人也不能称其为阿肯。阿肯必须是既能即兴做诗,又能自弹自唱,兼有诗人、歌手双重艺术才能的演唱诗人,但他们是在群众性的“吐列”对唱中成熟起来的。阿肯在哈萨克族中威望崇高,阿肯弹唱是哈萨克草原的盛典。
几乎所有的阿肯都是即兴创作,他们才思敏捷,能触景生情,脱口成章演唱,手中伴奏的乐器也不过是一把东布拉琴。
阿肯是草原之子,是哈萨克草原托起了他。哈萨克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场、接羔、扎帐、放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需要用动人的歌声驱散疲劳、孤独。一个人放牧形单影只,弹起东布拉深情地唱起来,一切寂寞都会烟消云散;放牧归来,燃起篝火,听着阿肯的即兴对唱,草原就充满了生机。阿肯是草原的骄傲,他们对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前文字时期出现的长诗、民歌,主要是靠阿肯、吉拉乌、吉尔其等民间歌手一代一代传唱保存、流传下来的,因为他们能编善唱,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化又多半由他们去总结、发展。阿肯、吉拉乌、吉尔其等民间歌手是哈萨克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10卷《哈萨克叙事长诗选》中的《阔布兰德》、《英雄塔尔根》、《阿勒帕梅斯》等众多的长诗都是靠民间歌手得以流传下来的。阿肯、吉拉乌、吉尔其都擅长长叙事诗的演唱,但阿肯则长于即兴演唱短歌,尽管也有演唱长叙事诗者,但在改编加工方面有很大灵活性,主要形式还是对唱。
草原是阿肯弹唱的舞台,只要有阿肯弹唱的地方准是在举行庆祝集会、重大祭典、节日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盛典造就了阿肯,阿肯也使盛典更显气氛热烈、欢快。阿肯单独吟唱固然能一举成名,但阿肯对唱更是智慧和才华的较量。阿肯对唱往往在两个氏族或部落间举行,登场的虽是阿肯个人,但对唱的成功、胜负关系到本氏族、本部落的荣誉,所以阿肯在台上较劲演唱,台下的观众则为本氏族、本部落的阿肯呐喊助兴。每年的八九月的夏牧场,蓝天白云,碧草青山,阿肯引吭高歌,构成哈萨克草原的风俗画卷。
如果说节日喜庆、盛大集会、祭典仪式的阿肯对唱是由主持者或东道主有意为之的话,而以歌会友式的阿肯弹唱就更具有喜剧性。这是一种主动登门造访切磋技艺的有效形式。有些阿肯远途跋涉,不辞辛劳,从一个部落来到另一个部落探访有声望的阿肯进行对唱。哈萨克族著名的阿肯比尔江就曾骑垮了六匹乘骑,奔波半个月,慕名找到名望卓著的萨拉阿肯,与之对唱。
阿肯的声望并不靠年龄、辈分、性别优势,而是造诣,看其是否有即兴赋歌吟唱的语言艺术功底。阿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阿肯对唱可以在男阿肯与男阿肯间进行,也可以在男阿肯与女阿肯间举行,老年阿肯与少年阿肯间对唱也习以为常。年长的阿肯败在少年阿肯手下,男阿肯败在女阿肯手下也并非鲜见。加纳克是哈萨克草原负有盛名的阿肯,曾胜过无数的阿肯,却败给一位少年阿肯。男阿肯隋因拜就在同女阿肯孔巴拉对唱时败北。阿肯对唱竞争十分激烈,采取淘汰制的办法。两名歌手一对一上场对唱,各自弹奏东布拉或库布孜为自己伴奏,相互间对歌盘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尽浑身解数炫耀各自的才华,从气势上,从语言技巧上,甚至从才智、人品上压倒对方,当另一位自愧弗如、甘拜下风时,对唱就决出了高低。新老阿肯之间的对唱更是充满剑拔弩张般的紧张气氛,似暴雨,像疾风,年长阿肯向新手展开猛烈进攻。一开口唱歌,年长阿肯就连珠炮似地猛攻,盘诘姓名、经历,继而自我炫耀,竭力嘲讽、戏谑新手,夸耀自己及氏族的荣耀,使对方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对于年长阿肯的“激怒”,新手不能恼怒,更不能发火,而只能不愠不火,靠自己的才智和语言技巧回敬对方。无论对唱多么激烈,但一旦对唱结束,双方都会以谦谦君子之风握手言欢。阿肯对唱中还不时穿插谜语、隐语等民间形式,增强对唱语言的艺术感染力。
“谎言歌”对唱是阿肯对唱的奇葩。它犹如汉语的“颠倒歌”、“扯谎歌,”以丰富的想象力,展开联想,编造出荒诞离奇的情节,富有机智和幽默感。但是,对唱者一再郑重其事地声明“绝不说谎”,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谎言歌”尽管是作为娱乐歌使人在笑声中产生愉悦的对唱形式,但它也是哈萨克人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认识和了解事物的方式,面对生活、社会,也有笑看人生的意味,在旧时,尤其是这样。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谎言歌”是《秃小子的四十句谎言歌》。在阿肯对唱中,“谎言歌”是可以无休止地连续编唱下去的。
阿肯弹唱走过了它的昨天,再也用不着用低沉、如泣如诉的吟唱述说那优伤、沉重的苦难生活;阿肯弹唱走到了今天,阿肯们也焕发了青春,用欢快、明亮的歌喉讴歌他们的新生活;阿肯弹唱这朵盛开在草原的民间艺术之花,它的明天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在丝绸之路草原演唱艺术中有一种鸿篇巨制型的英雄史诗演唱,它们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演唱。英雄史诗的演唱是语言技巧、音调、旋律、形体语言等相互作用、和谐完美的艺术综合体。柯尔克孜族称《玛纳斯》演唱者是“玛纳斯奇”,蒙古族则将《江格尔》的演唱者称为“江格尔齐”。无论是“玛纳斯奇”还是“江格尔齐”都是一些具有超凡记忆力、娴熟演唱口才和技巧的民间艺术家。但在众多“玛纳斯奇”和“江格尔齐”中称得上演唱大师者则寥若晨星。柯尔克孜族的居素普·玛玛依就是一位大师级的“玛纳斯奇”,人们称誉他为当代的“荷马”。但是荷马史诗包括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合起来不足3万行,而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整理出来的就有8部21万余行,他能连续演唱8部《玛纳斯》。
居素普·玛玛依才智过人,记忆力超群,8岁就开始背诵《玛纳斯》,到16岁时便把他哥哥整理、记录的《玛纳斯》8部全都背诵下来了。但是他绝不是简单承袭了他哥哥搜集、整理的《玛纳斯》,而是在几十年的演唱中不断充实和丰富它,因此他演唱的《玛纳斯》也称为居素普·玛玛依变体。居素普·玛玛依在他晚年时这样回忆自己演唱《玛纳斯》的经历:“我所演唱的史诗可以说是我哥哥巴勒瓦依所演唱的继承和发扬。..‘玛纳斯奇’日夜思考史诗情节,一心一意为演唱好史诗而努力,史诗的情节和人物怎么可能不进入梦乡呢?但是说某人凭着神功,一夜之间便能演唱这么庞大的史诗,成为‘玛纳斯奇’这是毫无根据的。”①居素普·玛玛依与八方聚来的“玛纳斯奇”切磋演唱技艺,虚心听取广大听众的意见,对史诗中的人物、情节以及演唱技巧精心加工、雕琢,使之演唱日臻成熟、完美。
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8部20余万行《玛纳斯》以其人物众多、情节起伏跌宕、结构繁复而著称。8部以柯尔克孜族古代传说中的英雄玛纳斯为核心组成了一百多个人物的艺术群像。在情节安排上,单是宏阔的战斗场面就有数十次之多。参加战斗的英雄性格、脾气迥异,有各自的智谋、武功,用不同的武器,穿不同的盔甲、服饰;战斗号角长鸣,铠甲寒光逼人,交战触目惊心;战斗环境或在沙漠,或在河滨,或在草原,或在山坡;勇士们与对手每次交战打法也截然不同。《玛纳斯》是以玛纳斯及其四十英雄为结构中心的史诗,所有情节、事件都是围绕玛纳斯及其子孙八代英雄的活动展开的。史诗的各部既可以各自独立,每一部都描写一位玛纳斯家族的英雄,又有统一的结构关系,即全部史诗组成了玛纳斯及其家族英雄的壮丽画卷。《玛纳斯》具有相同的基本模式,每部都由英雄的身世——征战——和平时期的生活三大结构构成。对民间歌手来说,这种模式易于驾驭史诗的复杂结构,演唱可以在某一部分结束时停下来;对听众而言,线索清晰,情节系于人物命运,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居素普·玛玛依作为演唱大师能够征服千万人的心还在于演唱的技艺超群。居素普·玛玛依演唱时的语言技巧、音调、旋律风格和手势变化自成一派,成了“玛纳斯奇”中的佼佼者。他演唱时语言简洁流畅,准确生动,在塑造英雄形象、描写征战场面、展现风俗生活时都是那样恰如其分,和谐完美。字斟句酌,丰富的柯尔克孜族语汇造就了居素普·玛玛依的语言才能。音调和旋律的准确把握让听众产生强烈共鸣。根据不同场景、不同人物、不同情节,音调时而轻松自如,时而高昂激越,时而细腻,时而粗犷,构成不同的旋律。在演唱时,居素普·玛玛依用各种多变的手势作为辅助手段,与史诗内容和演唱音调相配合,更增强了演唱效果。心、口、手和谐配合,这就是居素普·玛玛依的演唱经久不衰的动力。
在卫拉特蒙古演唱艺术中,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演唱有独特地位。《江格尔》于14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之后成了卫拉特蒙古四部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江格尔》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基础上,经过世代江格尔齐演唱、加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江格尔》属鸿篇巨制型英雄史诗,已经整理出版的是七十章托忒蒙古文本以及资料本,还有汉文选译本等,汉文全译本六卷也陆续出版。其实,民间流传的《江格尔》远比这长得多。据一些蒙古族艺人回忆,民间有一种七十回的手抄本。据托忒蒙古文文献记载,17世纪的江格尔齐托尔·巴依尔就会演唱许多篇章。《江格尔》中以富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勇士成了反抗邪恶、铲除社会不公,创建和保卫宝日本巴的象征,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推崇的英雄。《江格尔》在世代口头流传中融进了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
《江格尔》的演唱既是卫拉特蒙古的娱乐活动,又是公众性的民间演唱艺术的展示和欣赏。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上层的王爷、活佛、王公、大喇嘛等往往从农历正月初一拜年后开始就请江格尔齐演唱《江格尔》,一直到正月月底。他们认为江格尔是众佛的化身,把他请进来,可以驱魔逐怪。但是《江格尔》的演唱范围最广、声势最大的是在民间举行的。节庆、婚礼、祭祀等盛大活动,都有演唱《江格尔》的活动。只要有《江格尔》演唱,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蜂拥而至,因此《江格尔》演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江格尔》的演唱艺术而言,是分为演唱和平说的。演唱又有伴奏演唱和无伴奏演唱之分;平说,属讲述故事性质。名声远播的江格尔齐都是能连续演唱多至十几、几十章的著名民间演唱艺术家。演唱的《江格尔》属韵文,有严格的格律。在节奏上,《江格尔》基本可分为与字数有关的因素和与音韵有关的因素两类。前者是指在一个诗段中或有对仗关系的各行的音节数总是相等或基本相等,这是为了演唱时增强节奏感。后者是指在一个诗段中往往押头韵、脚韵、腰韵和全韵等。《江格尔》除在一个诗段中有这种韵律结构外,在诗段与诗段之间也有一定的韵律关系。由于江格尔齐阅历、传承不尽相同,因此《江格尔》的演唱也因人而异,给每个江格尔齐以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更大空间。《江格尔》演唱是融语言口才、韵律节奏和记忆天赋为一体的。
草原民族的民歌大都可以列入习俗歌的范畴,它包括婚嫁歌、丧葬歌、生产生活歌、节日习俗歌、宗教习俗歌等。是一个民族的习俗催生了习俗歌的诞生,还是习俗歌孕育了一定的习俗,对此,有学者认为:
在历史长河中,民俗意象原型,一般作为民俗圈内民族和地区民众大型社会群体心理意识的超稳定结构层——风俗、信仰等民俗形态紧附在民众的生活和思维之中的。这些民俗意象原型,本质上原是初民对自然万物变化的一种群体心理意识的共同感,是一定条件、环境下从事共同活动的人群具有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在人类社会中它不仅以口头,更多的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思考观察问题的原逻辑形态出现,呈现为一种群体共同的信息规范和行为规范、制约个体采取与群体一致的意愿和行动。民众在集体创作表达共同心愿的艺术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规范的影响。此外,民俗意象原型,借助于民俗特有的群体性和传承性,以超时空的状态在一定地区人群中存在和发展,具有独特的稳定性,以致产生它的母体社会发生了变化,仍可以原有的群体意识,左右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内容。①
以哈萨克族婚嫁歌为例,它显然是人生仪式中的一部分,是伴随婚嫁仪式程序所唱的相应歌,它分为“喜事序歌”、“萨仁”、“加尔—加尔”、“哭嫁歌”、“远嫁歌”、“劝嫁歌”、“揭面纱歌”等,是整个婚嫁仪式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类社会在婚姻上从血婚走向族外婚,又从对偶婚走向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习俗随社会变迁而演变。哈萨克族婚姻实行的是男婚女嫁,妻从夫居。按照习俗约定,七代以内是至亲,不得通婚,同时,缔姻双方家庭的居地应该有七水之隔,意思是要相距遥远,以避免彼此间可能有的任何一种“血缘”联系。①哈萨克族的婚礼是从提亲开始的,还有订婚仪式、嫁娶仪式等。在整个过程中,婚嫁歌存在于自始至终,新娘用歌向亲人告别,亲人用歌劝嫁,男方用歌迎娶新娘,来宾歌唱助兴等。婚嫁歌透露的是婚嫁习俗原型的信息,通过演唱形式凸现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意识,同时,长期积淀的婚嫁原型为婚嫁歌的创作奠定了雏形。
哈萨克族的婚嫁歌有不同的曲调和演唱形式,如“加尔—加尔”是男方劝嫁,女方哭嫁时对唱的歌。往往是男方的劝嫁歌曲调欢快、轻松,而女方哭嫁歌凄楚、悲凉。当男方在歌唱中呼唤“加尔—加尔”时,而女方歌唱时则呼唤“碧克依”,或在句末有衬词。“加尔”在哈萨克语中是“情侣”、“恋人”之意,而女方的哭嫁歌—“森瑟玛”是“伤心地长哭”、“哭出来的歌”的意思。难怪“加尔—加尔”总是欢愉、温情,而“森瑟玛”则悲苦、委屈,曲调显得低沉、抑郁。在演唱形式上,“加尔—加尔”是新郎新娘的对唱,但常常有伴娘的唱和。在对唱里,“加尔—加尔”的呼唤增强了曲调的节奏感。在哈萨克族婚嫁歌中,独唱、对唱、齐唱、和唱等形式单独或交替出现。如在嫁女仪式开场时的喜事序歌是民间歌手的独唱,之后,当天演唱的“萨仁”是两个小伙子的齐唱,而到了“加尔—加尔”又成了新郎、新娘的对唱。离家远嫁时,新娘以独唱方式向亲人依依惜别,在过门后的揭面纱仪式上,则由一位善唱的青年歌手唱诙谐、轻松、热烈的揭面纱歌。在喜庆的婚礼场面,来宾们也往往即兴和唱表示祝贺。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的最早的吟唱应属于与萨满教密不可分的祷告歌,即萨满歌。“无论是什么肤色的巫师,他的咒语总是韵文。战歌、情歌、摇篮曲、哀歌以及婚礼颂歌,无疑在最初都是具有巫术、宗教的意义,带有咒文的性质。”②萨满在氏族部落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常举行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各种仪式,如萨满的“行巫术”——“萨满昏迷”仪式,献祭祭祀仪式,以及群体发生危难、个人或群体遭遇病疫、天灾、征战时举行的仪式等。这些仪式均由萨满主持,其中吟唱祝文是重要内容。19世纪60年代中亚学者拉德洛夫曾对阿尔泰山区的哈萨克族萨满教遗迹进行过田野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记录了萨满教祭祀仪式的全过程,并记录下萨满歌。在仪式的请神、降神、送神过程中,萨满都在吟唱一种带韵味的祝文。让我们看一段拉德洛夫有关哈萨克族萨满召唤神灵的记录:这时,萨满左手持神鼓,并用烟熏。然后萨满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慢慢地用木槌击鼓,并以激昂的声音呼唤神灵。每位被召唤的神灵应都对萨满回答:“啊!卡木,哎!”萨满便将它们收入神鼓中。萨满每完成召唤一位神灵的过程,都得用相应的动作将神鼓倾斜一下。首先呼唤的是海之神——亚依克汗,然后是开拉汗,以后是派金汗,还有好多好多,最后是亚伯尔汗。最后的呼唤以如下的词语结束:
请您听听我的祈念,
并请满足我的祈求!
请给予永久的平安吧!
请给予长夜的睡梦!
请给予浓厚的马鬃!
请给予夜晚的平静!
请给予千家的平安!
请给予万户的平和!
请到我右手边玩一玩!
我的右手击打着木槌在召唤!①
哈萨克族的萨满歌实际是歌舞为一体的,萨满击鼓、吟唱往往是在有节奏的节拍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动作和曲调。在萨满歌中保持着古老而优美的叠句。叠句有时用的是无意义的词,如哈萨克族萨满追捉祭牲魂灵时就大声吟唱:
拿起金绳子!
嗨,嗨,嗨!
快快摇起缰绳
!嗨,嗨,嗨!
套上金笼头!
嗨,嗨,嗨!②
实际上是以“嗨,嗨,嗨”等叠词加强气势。有时也用拟声词,如萨满在呼唤天鹅精灵时往往反复模仿鹅的“嘎克、嘎克”的叫声。在萨满追捉祭牲灵魂吟唱时,众人还大声呼喊“哎嗨,哎嗨”,形成一种合声效果。如果追根溯源,萨满歌“从民间音乐和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当中广泛地吸取材料,特别是吸取了大量的神话材料;同时,这些歌往往有丰富的想象,运用语言灵活、大胆,它也反过来给了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以很大影响”,①在草原游牧民族的民歌中,萨满歌现在是作为宗教习俗歌出现的。
由于民间音乐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近半个世纪以来调查、发掘、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民歌已取得可喜成就,使人们有幸一睹草原游牧民族传唱不息的民歌的芳容。蒙古族长调短调、哈萨克族阿肯弹唱、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演唱以及所有草原游牧民族共有的不同类型的习俗歌、情歌等构成了流淌在广袤草原的咏叹调。
蒙古族长调“节奏缓慢,曲调高亢豪放,真假声并用,气息宽广,字少腔长,以辽阔、宽广而著称。结构一般以上下句组成乐段。有触景生情、即兴编唱的特点。分单声部长调和带持续低音长调两类”。②长调产生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故有牧歌、思乡曲、赞歌、宴歌、婚礼歌等多种形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晓蒙古语的丹麦人亨宁·哈士纶在其《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中收录了不少采集自西蒙古的民歌曲调(他实际录制了60首蒙古民歌),其中一些显然是长调。其中有土尔扈特民歌《西部可汗》、《可爱的暗褐色小马》、《我可爱的小雄鹿》、《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额林哈毕尔噶山》以及察哈尔蒙古的《博尔塔拉乌拉》等。其中一些属赞歌,另一些则是牧歌。哈士纶认为,这些长调“常常是高低音同度一致的,但当两个或更多的蒙古人在一起唱时,唱得最好的喜欢唱出延音,延长到他的肺活量的最大限度。然后他继续把这首歌曲唱下去,好像是其他歌手的回音一般,从而使得这首抒情曲和复调多重唱相似”。③其中《伊犁河金色草原之歌》显然是歌手即兴演唱的抒情长调,“歌手反复用本嗓和假声演唱着,山上的回音中又掺和着他自己清脆嘹亮的嗓音,构成了一首向灿烂的早晨问候的交响乐曲。..歌词是歌手眼下自己即兴吟成的。歌词描绘了对繁茂的伊犁河谷的秋天的幸福回忆,在那儿,茁壮的牲畜和肌肉发达的马儿站在高齐马肚的新鲜多汁的黄草中”。④歌手的长调显然属于牧歌一类。短调民歌在土尔扈特等厄鲁特和察哈尔蒙古诸部中都流行,“短调民歌大多风趣幽默,节奏明快,曲调活泼,故又称诙谐歌曲。..察哈尔短调民歌富有风趣幽默,曲调极为活泼,节奏强烈明快,每一位歌者都进发出炽烈如火、浓烈如酒般的热情”。①《高山上的花》、《金纽》、《想念我的家乡》、《摇篮曲》等都是新疆察哈尔蒙古久唱不衰的短调民歌。其中《摇篮曲》则取材于民间传说,本身就在叙述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情节逐步展开,但不是连续不断的叙事,而是像戏剧一样显现一系列小场面带有频繁的重复,这些都是真正叙事曲形式的特征,即使没有叠句,也是如此”。②
在哈萨克族民歌演唱中有一种有问有答的对唱形式,分为阿肯对唱和群众性对唱。成熟阿肯参加的只能是高层次的、规范的被称为“苏列的对唱”。人们说哈萨克人有两件宝:一是骏马,一是歌喉。哈萨克人是歌唱的天才,从小孩到老人,从男子到妇女都能一展歌喉唱上一曲,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冠以“阿肯”的尊衔。能唱多种民歌的民间歌手不是阿肯,擅长即兴做诗的民间诗人也不能称其为阿肯。阿肯必须是既能即兴做诗,又能自弹自唱,兼有诗人、歌手双重艺术才能的演唱诗人,但他们是在群众性的“吐列”对唱中成熟起来的。阿肯在哈萨克族中威望崇高,阿肯弹唱是哈萨克草原的盛典。
几乎所有的阿肯都是即兴创作,他们才思敏捷,能触景生情,脱口成章演唱,手中伴奏的乐器也不过是一把东布拉琴。
阿肯是草原之子,是哈萨克草原托起了他。哈萨克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场、接羔、扎帐、放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需要用动人的歌声驱散疲劳、孤独。一个人放牧形单影只,弹起东布拉深情地唱起来,一切寂寞都会烟消云散;放牧归来,燃起篝火,听着阿肯的即兴对唱,草原就充满了生机。阿肯是草原的骄傲,他们对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前文字时期出现的长诗、民歌,主要是靠阿肯、吉拉乌、吉尔其等民间歌手一代一代传唱保存、流传下来的,因为他们能编善唱,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化又多半由他们去总结、发展。阿肯、吉拉乌、吉尔其等民间歌手是哈萨克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10卷《哈萨克叙事长诗选》中的《阔布兰德》、《英雄塔尔根》、《阿勒帕梅斯》等众多的长诗都是靠民间歌手得以流传下来的。阿肯、吉拉乌、吉尔其都擅长长叙事诗的演唱,但阿肯则长于即兴演唱短歌,尽管也有演唱长叙事诗者,但在改编加工方面有很大灵活性,主要形式还是对唱。
草原是阿肯弹唱的舞台,只要有阿肯弹唱的地方准是在举行庆祝集会、重大祭典、节日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盛典造就了阿肯,阿肯也使盛典更显气氛热烈、欢快。阿肯单独吟唱固然能一举成名,但阿肯对唱更是智慧和才华的较量。阿肯对唱往往在两个氏族或部落间举行,登场的虽是阿肯个人,但对唱的成功、胜负关系到本氏族、本部落的荣誉,所以阿肯在台上较劲演唱,台下的观众则为本氏族、本部落的阿肯呐喊助兴。每年的八九月的夏牧场,蓝天白云,碧草青山,阿肯引吭高歌,构成哈萨克草原的风俗画卷。
如果说节日喜庆、盛大集会、祭典仪式的阿肯对唱是由主持者或东道主有意为之的话,而以歌会友式的阿肯弹唱就更具有喜剧性。这是一种主动登门造访切磋技艺的有效形式。有些阿肯远途跋涉,不辞辛劳,从一个部落来到另一个部落探访有声望的阿肯进行对唱。哈萨克族著名的阿肯比尔江就曾骑垮了六匹乘骑,奔波半个月,慕名找到名望卓著的萨拉阿肯,与之对唱。
阿肯的声望并不靠年龄、辈分、性别优势,而是造诣,看其是否有即兴赋歌吟唱的语言艺术功底。阿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阿肯对唱可以在男阿肯与男阿肯间进行,也可以在男阿肯与女阿肯间举行,老年阿肯与少年阿肯间对唱也习以为常。年长的阿肯败在少年阿肯手下,男阿肯败在女阿肯手下也并非鲜见。加纳克是哈萨克草原负有盛名的阿肯,曾胜过无数的阿肯,却败给一位少年阿肯。男阿肯隋因拜就在同女阿肯孔巴拉对唱时败北。阿肯对唱竞争十分激烈,采取淘汰制的办法。两名歌手一对一上场对唱,各自弹奏东布拉或库布孜为自己伴奏,相互间对歌盘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尽浑身解数炫耀各自的才华,从气势上,从语言技巧上,甚至从才智、人品上压倒对方,当另一位自愧弗如、甘拜下风时,对唱就决出了高低。新老阿肯之间的对唱更是充满剑拔弩张般的紧张气氛,似暴雨,像疾风,年长阿肯向新手展开猛烈进攻。一开口唱歌,年长阿肯就连珠炮似地猛攻,盘诘姓名、经历,继而自我炫耀,竭力嘲讽、戏谑新手,夸耀自己及氏族的荣耀,使对方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对于年长阿肯的“激怒”,新手不能恼怒,更不能发火,而只能不愠不火,靠自己的才智和语言技巧回敬对方。无论对唱多么激烈,但一旦对唱结束,双方都会以谦谦君子之风握手言欢。阿肯对唱中还不时穿插谜语、隐语等民间形式,增强对唱语言的艺术感染力。
“谎言歌”对唱是阿肯对唱的奇葩。它犹如汉语的“颠倒歌”、“扯谎歌,”以丰富的想象力,展开联想,编造出荒诞离奇的情节,富有机智和幽默感。但是,对唱者一再郑重其事地声明“绝不说谎”,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谎言歌”尽管是作为娱乐歌使人在笑声中产生愉悦的对唱形式,但它也是哈萨克人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认识和了解事物的方式,面对生活、社会,也有笑看人生的意味,在旧时,尤其是这样。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谎言歌”是《秃小子的四十句谎言歌》。在阿肯对唱中,“谎言歌”是可以无休止地连续编唱下去的。
阿肯弹唱走过了它的昨天,再也用不着用低沉、如泣如诉的吟唱述说那优伤、沉重的苦难生活;阿肯弹唱走到了今天,阿肯们也焕发了青春,用欢快、明亮的歌喉讴歌他们的新生活;阿肯弹唱这朵盛开在草原的民间艺术之花,它的明天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在丝绸之路草原演唱艺术中有一种鸿篇巨制型的英雄史诗演唱,它们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演唱。英雄史诗的演唱是语言技巧、音调、旋律、形体语言等相互作用、和谐完美的艺术综合体。柯尔克孜族称《玛纳斯》演唱者是“玛纳斯奇”,蒙古族则将《江格尔》的演唱者称为“江格尔齐”。无论是“玛纳斯奇”还是“江格尔齐”都是一些具有超凡记忆力、娴熟演唱口才和技巧的民间艺术家。但在众多“玛纳斯奇”和“江格尔齐”中称得上演唱大师者则寥若晨星。柯尔克孜族的居素普·玛玛依就是一位大师级的“玛纳斯奇”,人们称誉他为当代的“荷马”。但是荷马史诗包括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合起来不足3万行,而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整理出来的就有8部21万余行,他能连续演唱8部《玛纳斯》。
居素普·玛玛依才智过人,记忆力超群,8岁就开始背诵《玛纳斯》,到16岁时便把他哥哥整理、记录的《玛纳斯》8部全都背诵下来了。但是他绝不是简单承袭了他哥哥搜集、整理的《玛纳斯》,而是在几十年的演唱中不断充实和丰富它,因此他演唱的《玛纳斯》也称为居素普·玛玛依变体。居素普·玛玛依在他晚年时这样回忆自己演唱《玛纳斯》的经历:“我所演唱的史诗可以说是我哥哥巴勒瓦依所演唱的继承和发扬。..‘玛纳斯奇’日夜思考史诗情节,一心一意为演唱好史诗而努力,史诗的情节和人物怎么可能不进入梦乡呢?但是说某人凭着神功,一夜之间便能演唱这么庞大的史诗,成为‘玛纳斯奇’这是毫无根据的。”①居素普·玛玛依与八方聚来的“玛纳斯奇”切磋演唱技艺,虚心听取广大听众的意见,对史诗中的人物、情节以及演唱技巧精心加工、雕琢,使之演唱日臻成熟、完美。
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8部20余万行《玛纳斯》以其人物众多、情节起伏跌宕、结构繁复而著称。8部以柯尔克孜族古代传说中的英雄玛纳斯为核心组成了一百多个人物的艺术群像。在情节安排上,单是宏阔的战斗场面就有数十次之多。参加战斗的英雄性格、脾气迥异,有各自的智谋、武功,用不同的武器,穿不同的盔甲、服饰;战斗号角长鸣,铠甲寒光逼人,交战触目惊心;战斗环境或在沙漠,或在河滨,或在草原,或在山坡;勇士们与对手每次交战打法也截然不同。《玛纳斯》是以玛纳斯及其四十英雄为结构中心的史诗,所有情节、事件都是围绕玛纳斯及其子孙八代英雄的活动展开的。史诗的各部既可以各自独立,每一部都描写一位玛纳斯家族的英雄,又有统一的结构关系,即全部史诗组成了玛纳斯及其家族英雄的壮丽画卷。《玛纳斯》具有相同的基本模式,每部都由英雄的身世——征战——和平时期的生活三大结构构成。对民间歌手来说,这种模式易于驾驭史诗的复杂结构,演唱可以在某一部分结束时停下来;对听众而言,线索清晰,情节系于人物命运,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居素普·玛玛依作为演唱大师能够征服千万人的心还在于演唱的技艺超群。居素普·玛玛依演唱时的语言技巧、音调、旋律风格和手势变化自成一派,成了“玛纳斯奇”中的佼佼者。他演唱时语言简洁流畅,准确生动,在塑造英雄形象、描写征战场面、展现风俗生活时都是那样恰如其分,和谐完美。字斟句酌,丰富的柯尔克孜族语汇造就了居素普·玛玛依的语言才能。音调和旋律的准确把握让听众产生强烈共鸣。根据不同场景、不同人物、不同情节,音调时而轻松自如,时而高昂激越,时而细腻,时而粗犷,构成不同的旋律。在演唱时,居素普·玛玛依用各种多变的手势作为辅助手段,与史诗内容和演唱音调相配合,更增强了演唱效果。心、口、手和谐配合,这就是居素普·玛玛依的演唱经久不衰的动力。
在卫拉特蒙古演唱艺术中,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演唱有独特地位。《江格尔》于14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之后成了卫拉特蒙古四部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江格尔》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基础上,经过世代江格尔齐演唱、加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江格尔》属鸿篇巨制型英雄史诗,已经整理出版的是七十章托忒蒙古文本以及资料本,还有汉文选译本等,汉文全译本六卷也陆续出版。其实,民间流传的《江格尔》远比这长得多。据一些蒙古族艺人回忆,民间有一种七十回的手抄本。据托忒蒙古文文献记载,17世纪的江格尔齐托尔·巴依尔就会演唱许多篇章。《江格尔》中以富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勇士成了反抗邪恶、铲除社会不公,创建和保卫宝日本巴的象征,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推崇的英雄。《江格尔》在世代口头流传中融进了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
《江格尔》的演唱既是卫拉特蒙古的娱乐活动,又是公众性的民间演唱艺术的展示和欣赏。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上层的王爷、活佛、王公、大喇嘛等往往从农历正月初一拜年后开始就请江格尔齐演唱《江格尔》,一直到正月月底。他们认为江格尔是众佛的化身,把他请进来,可以驱魔逐怪。但是《江格尔》的演唱范围最广、声势最大的是在民间举行的。节庆、婚礼、祭祀等盛大活动,都有演唱《江格尔》的活动。只要有《江格尔》演唱,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蜂拥而至,因此《江格尔》演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江格尔》的演唱艺术而言,是分为演唱和平说的。演唱又有伴奏演唱和无伴奏演唱之分;平说,属讲述故事性质。名声远播的江格尔齐都是能连续演唱多至十几、几十章的著名民间演唱艺术家。演唱的《江格尔》属韵文,有严格的格律。在节奏上,《江格尔》基本可分为与字数有关的因素和与音韵有关的因素两类。前者是指在一个诗段中或有对仗关系的各行的音节数总是相等或基本相等,这是为了演唱时增强节奏感。后者是指在一个诗段中往往押头韵、脚韵、腰韵和全韵等。《江格尔》除在一个诗段中有这种韵律结构外,在诗段与诗段之间也有一定的韵律关系。由于江格尔齐阅历、传承不尽相同,因此《江格尔》的演唱也因人而异,给每个江格尔齐以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更大空间。《江格尔》演唱是融语言口才、韵律节奏和记忆天赋为一体的。
草原民族的民歌大都可以列入习俗歌的范畴,它包括婚嫁歌、丧葬歌、生产生活歌、节日习俗歌、宗教习俗歌等。是一个民族的习俗催生了习俗歌的诞生,还是习俗歌孕育了一定的习俗,对此,有学者认为:
在历史长河中,民俗意象原型,一般作为民俗圈内民族和地区民众大型社会群体心理意识的超稳定结构层——风俗、信仰等民俗形态紧附在民众的生活和思维之中的。这些民俗意象原型,本质上原是初民对自然万物变化的一种群体心理意识的共同感,是一定条件、环境下从事共同活动的人群具有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在人类社会中它不仅以口头,更多的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思考观察问题的原逻辑形态出现,呈现为一种群体共同的信息规范和行为规范、制约个体采取与群体一致的意愿和行动。民众在集体创作表达共同心愿的艺术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规范的影响。此外,民俗意象原型,借助于民俗特有的群体性和传承性,以超时空的状态在一定地区人群中存在和发展,具有独特的稳定性,以致产生它的母体社会发生了变化,仍可以原有的群体意识,左右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内容。①
以哈萨克族婚嫁歌为例,它显然是人生仪式中的一部分,是伴随婚嫁仪式程序所唱的相应歌,它分为“喜事序歌”、“萨仁”、“加尔—加尔”、“哭嫁歌”、“远嫁歌”、“劝嫁歌”、“揭面纱歌”等,是整个婚嫁仪式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类社会在婚姻上从血婚走向族外婚,又从对偶婚走向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习俗随社会变迁而演变。哈萨克族婚姻实行的是男婚女嫁,妻从夫居。按照习俗约定,七代以内是至亲,不得通婚,同时,缔姻双方家庭的居地应该有七水之隔,意思是要相距遥远,以避免彼此间可能有的任何一种“血缘”联系。①哈萨克族的婚礼是从提亲开始的,还有订婚仪式、嫁娶仪式等。在整个过程中,婚嫁歌存在于自始至终,新娘用歌向亲人告别,亲人用歌劝嫁,男方用歌迎娶新娘,来宾歌唱助兴等。婚嫁歌透露的是婚嫁习俗原型的信息,通过演唱形式凸现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意识,同时,长期积淀的婚嫁原型为婚嫁歌的创作奠定了雏形。
哈萨克族的婚嫁歌有不同的曲调和演唱形式,如“加尔—加尔”是男方劝嫁,女方哭嫁时对唱的歌。往往是男方的劝嫁歌曲调欢快、轻松,而女方哭嫁歌凄楚、悲凉。当男方在歌唱中呼唤“加尔—加尔”时,而女方歌唱时则呼唤“碧克依”,或在句末有衬词。“加尔”在哈萨克语中是“情侣”、“恋人”之意,而女方的哭嫁歌—“森瑟玛”是“伤心地长哭”、“哭出来的歌”的意思。难怪“加尔—加尔”总是欢愉、温情,而“森瑟玛”则悲苦、委屈,曲调显得低沉、抑郁。在演唱形式上,“加尔—加尔”是新郎新娘的对唱,但常常有伴娘的唱和。在对唱里,“加尔—加尔”的呼唤增强了曲调的节奏感。在哈萨克族婚嫁歌中,独唱、对唱、齐唱、和唱等形式单独或交替出现。如在嫁女仪式开场时的喜事序歌是民间歌手的独唱,之后,当天演唱的“萨仁”是两个小伙子的齐唱,而到了“加尔—加尔”又成了新郎、新娘的对唱。离家远嫁时,新娘以独唱方式向亲人依依惜别,在过门后的揭面纱仪式上,则由一位善唱的青年歌手唱诙谐、轻松、热烈的揭面纱歌。在喜庆的婚礼场面,来宾们也往往即兴和唱表示祝贺。
附注
①王曙光.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新疆社会科学.1984(4).
②〔英〕查·索·博尔尼著.程德祺等译.民俗学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20.
①拉德洛夫.哈萨克族的萨满教遗迹.转引自姜崇仑主编.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245~246.
②拉德洛夫.哈萨克族的萨满教遗迹.转引自姜崇仑主编.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240.
①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280.
②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66.
③〔丹麦〕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212.
④〔丹麦〕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244~245.
①加·奥其尔巴特,吐娜.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218.
②〔英〕查·索·博尔尼著.程德祺等译.民俗学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22~223.
①居素普·玛玛依.我是怎样开始演唱《玛纳斯》史诗的.玛纳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34.
①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290~291.
①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247~248.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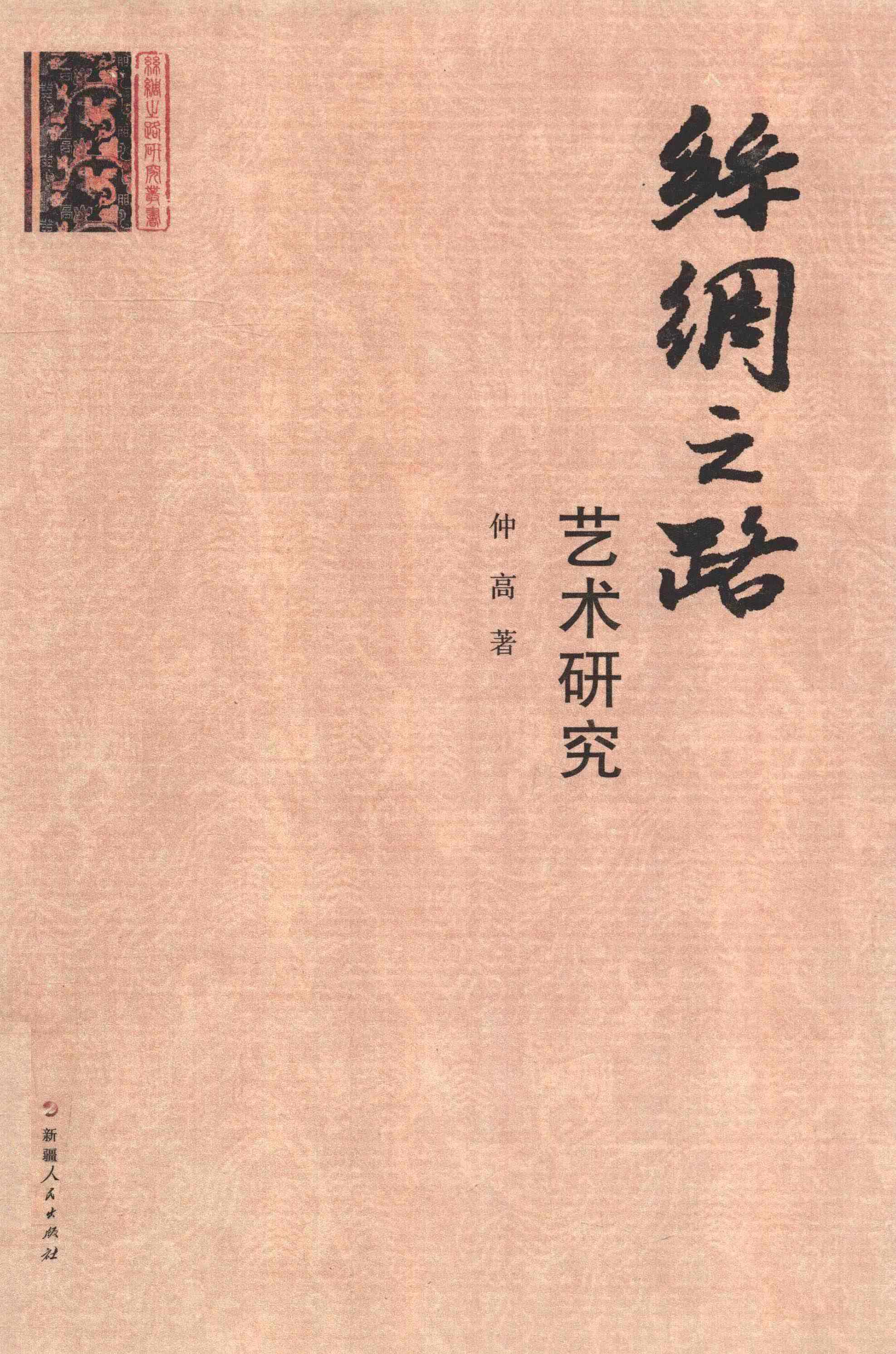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