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动物纹样的角色转换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33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动物纹样的角色转换 |
| 分类号: | K876.41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43-152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青铜器、金银器的早期主人是塞人、匈奴人、鲜卑人、乌孙人、大月氏人等诸多游牧部落,其后以装饰性突出的突厥、蒙古等的金银器则是草原动物纹样的余韵。虽然突厥等中古游牧部落仍使用古老的金、铜等金属饰品,但通天工具的作用在逐渐消解,而代之以一种新的装饰审美时尚,对突厥贵族来说,黄金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动物纹样 角色转换 |
内容
在丝绸之路上,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曾在文明形成之初的青铜时代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青铜文化,但是对同样掌握冶炼青铜甚至于炼铁技术的游牧民族,还有学者仍以“野蛮”民族相称,否认游牧民族是“文明民族”,这是不公允的。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进入青铜时代后,已肇始他们的文明进程正在加快。从发展进程纵向比较:中国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使用青铜器不会迟于公元前2000年,①而且延续了1500年;而中亚北部草原地区以安德罗诺沃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也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②即使以中国西部为例,甘肃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也在公元前2200~1600年之间;③西域(主要指新疆)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④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商初(距今3500年左右)已出现。⑤由此可见,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和农耕文化几乎在同一起点上,从时间发展上难分伯仲。从器形纹样和功能横向比较: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青铜器以重器为主,包括礼器、乐器以及兵器、服御器等;游牧民族的青铜器除鍑、盘等大器外,几乎全为小型器物,兵器类的剑、刀、矛、镞以及腰带、饰牌,马具类的装饰物等。就青铜器的纹样而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竟不谋而合地均采用动物纹样,只是中原的动物纹样是一种饕餮纹样以及以它为主的青铜器,给人以狞厉神秘之感,而欧亚草原以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为代表则从早期的野兽猛禽的咬斗、蜷曲、螺旋形纹样向马、牛、羊、驼等家畜对称纹样发展。无论是中原农耕民族,还是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民族,其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均是巫觋(萨满)的通天工具之一,都是功能性的,尽管它们不是通天的惟一工具。张光直先生认为:“在原始民族的萨满教里,动物是通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的牺牲身上体现出来。这里有两种表现:一是动物本身作牺牲,它的魂灵就是巫的助手,往来于天地之间;另一是青铜器上面的动物,巫师希望以动物来排除通天过程中的障碍。”⑥中国九鼎传说源自夏代,以后历代王朝都视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九鼎,就是因为九鼎独占通天手段的象征。⑦早期草原的氏族部落首领须臾不离身的剑、刀、牌饰、带钩以及马具等上的动物纹样也是如此,首领即是萨满,他们以各种动物为助手精灵,以达到通天的目的。青铜器连同动物纹样都是王者权力的象征。
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青铜器、金银器的早期主人是塞人、匈奴人、鲜卑人、乌孙人、大月氏人等诸多游牧部落,其后以装饰性突出的突厥、蒙古等的金银器则是草原动物纹样的余韵。虽然突厥等中古游牧部落仍使用古老的金、铜等金属饰品,但通天工具的作用在逐渐消解,而代之以一种新的装饰审美时尚,对突厥贵族来说,黄金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
中亚草原最早的游牧部落无疑是中国汉代史籍译为“塞”,而古波斯文献称之为“萨迦”的塞人,他们自公元前7世纪就在中亚草原活动,并渗入绿洲地区。“萨迦”在古音中读为“sak”,因此,“塞克”、“萨迦”、“塞”不过是它的不同音译。塞人在西域草原地带的活动主要在公元前5~前3世纪之间,他们分布于伊犁河流域、西天山、东天山及帕米尔高原一带,为典型的游牧部落。塞人公元前1世纪进入印度,公元前后在塔里木盆地以及和田绿洲定居下来,公元5世纪又扩展至塔里木盆地东缘的鄯善。这部分定居的塞人因生产方式的改变,成为绿洲农耕民,但他们仍保留着游牧部落的文化传统。塞人是否就是古代的游牧部落斯基泰人呢?学者的意见是相左的。所谓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是指分布于欧亚草原上从喀尔巴阡山往东至顿河,以至更东的游牧人(又译为西徐亚人)。希罗多德坚持说:“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迦人的。”①“由此可见萨迦人与斯基泰人,名虽不同,其实则一”。②这个提法为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的学者普遍接受。塞人或塞克实际上就是希罗多德等希腊学者所指称的亚洲斯基泰人,主要是游牧于亚洲草原地带的氏族部落,以别于欧洲斯基泰人。③西方学者也把这部分斯基泰人称之为斯基泰塞人。④他们从哈萨克草原到天山北部及阿尔泰山一带广泛分布。这样,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西方学者所谓斯基泰式动物纹样冠之于塞人动物纹样了。正当塞人呈自西向东的流向时,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则在自东向西流动。“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统一大漠南北的全部地区,并建立起国家政权——匈奴单于国的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活动了约三百年。东汉初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于汉,入居塞内,北匈奴不久(公元91年)因战败西迁中亚和欧洲”。⑤早在秦汉时,匈奴就沿丝绸之路南道、北道、中道抵达西域南北部,于公元91年,被汉朝打败后逃遁。匈奴自秦汉之际在西域活动起至东汉时西迁,其文化与曾和正在活动于西域草原地带的塞人、乌孙、月氏、乌揭等游牧文化发生交融互渗。特别是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终于有机会在天山、阿尔泰山草原地带相遇了。
不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延续时间要长得多,经历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铁器时代。⑥鄂尔多斯动物纹样起始于商代晚期,而盛于战国时期,这是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的繁盛期。就与周边文化关系而言,早在公元前1000年纪,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与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关系密切,尤其是卡拉苏剑首的动物造型与鄂尔多斯的非常相似。①也就是说在商周时期,这两种文化就有密切接触了。到了塔加尔文化时期,东西两个方向的动物纹样开始融合。
塞人的动物纹样是黄金饰品,对此,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认为:“塞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黄金饰品成为塞人生用死殉的最主要用品,这可能和他们的太阳神信仰有关。如果从类型看几乎全是饰牌、带钩、饰片及刀、马具上的装饰等,而且以动物纹样圆形金牌为多。考古学家曾对天山阿拉沟塞人的4座竖穴木椁墓进行发掘,发现无墓不见金器。仅第三十号墓就出土虎纹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带4件,狮形金箔1件,菱形花金饰片3件,较大圆形金泡饰片33片,以及柳叶形、螺旋形等金饰片、金串饰130多件,合计在200件以上。因这些墓均被盗扰,所见金器不过是盗墓后的劫余。②这里所说的虎纹圆金牌可能是猫科动物中的雪豹纹样圆金牌。塞人金牌中的动物纹样主要是狮、豹、熊、狼、鹫、雄山羊、鹿、鸟翼等凶兽猛禽形象。伊塞克古墓曾出土四千多件器物,其中有156件是金质动物纹样牌饰类,也是塞人的动物纹样器物。国外学者对伊塞克古墓出土的塞人动物纹样的造型和风格有过细致研究,几乎涉及所有的动物纹样。以雪豹牌饰为例:“雪豹形象都是侧面像,伊塞克雪豹侧面像的脸、嘴全部不相上下,圆脑袋,扁状眼睛,旋贝状三角耳,龇牙咧嘴。颧骨渲染成一道凹进的宽弧形,肩胛骨以涡卷纹表示。尾巴卷成圆圈。表示肋骨的是一排突出的弧。大腿由双行线构成,腹下、肋部和从背到脚的部位也遍布这种线条。”③有翼的雪豹牌饰上的雪豹后爪蹬着模拟山行的踞齿缘,拧着前半身,仿佛要扬起前爪搏击一般,动物躯体强壮而柔韧,着重表现了野兽的狂暴和凶猛,狰狞地龇着牙,咧着嘴,肩部是以凸出的涡纹标出,从那里伸出模拟翅膀的突芽。①虽是个例,但它凸现出塞人动物纹样造型的所有特征。塞人的动物纹样几乎全是野兽咬啮状和蜷曲形,以牌饰为主的动物纹样虽然器形小,但乾坤大。塞人善于在有限的形式——牌饰等小型物件中拓展无限想象马镫的空间,善于利用空间巧妙地处理动物题材。以圆雕为主的工艺娴熟,纹样轮廓简洁、醒目,内容充实而完美,手法写实而夸张。苏联研究早期游牧文化的学者格拉科夫的论述不无精当:
这种风格,大多描绘某些企图击倒对方的猛兽和善于反搏对方袭击的灵敏家畜,同时突出表现这两类动物的攻击器官和感觉器官。这些动物,口内长满了巨大的牙齿,嘴和足的表现尤为明确具体。十分夸张耳朵、鼻孔和眼睛,蹄宽大而趾尖锐。..通过对于猛兽趾爪、牙齿、蹄子、翅膀以及灵活敏锐的鼻子、耳朵等各种器官的表现,使动物的全身尤其肩部及腰部充满一种强劲的力量,而且,对于这些最能显示攻击能力及灵敏感觉的器官本身,则特别提到显要部位加以充分塑造。②
活动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也有较大型的青铜器物——方座承兽铜盘。天山阿拉沟方座承兽铜盘,器身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鬣毛卷曲成穿孔,似翼。①1983年在伊犁巩乃斯河岸也出土同一类型的铜盘。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两件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和双飞兽相对圆环。②于是这种幻想式的动物纹样成了塞人这类动物造型的标志,也显然是它的特征。
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主要出现在刀、匕、剑、饰牌、带钩、扣饰、头饰、佩饰等器物中。动物形象包括家畜,如马、牛、羊、驼等和野生动物鹿、虎、豹、狼、鸟等,以鹿、虎、鸟的形象多见。“这些动物纹大体可归纳为鸟形、兽头形、宁立形、蹲踞形、弯曲兽形、群兽形、动物咬斗形和人与动物结合组成的反映社会生活场面的各种造型等”。③不过,与塞人动物纹样相比较,动物咬斗形纹样发现的并不多。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早期(商周时期)多以圆雕技法将动物兽头形象装饰在青铜短剑、刀的柄端。到春秋时动物纹样以图案化的双鸟纹盛行,且主要装饰在腰带上。鸟喙特别强调钩状特征。战国时期是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的繁盛期,以圆雕、浮雕技法表现的动物纹样,有较强的写实性。动物形象除个体外,还有不同动物的组合形象。工艺已达到精工娴熟程度,制作工艺也日趋复杂,有镶嵌、锤鍱、抽丝及错金银等工艺。两汉时期,诸如兽头形、宁立形、蹲踞形等动物纹样基本不见,动物形象刻画也少了纯写实手法,大型饰牌往往在卧羊等家畜周围衬托花草纹,以自然景物,如山、树等相衬托的动物纹样成为普遍流行装饰。④
在匈奴右部曾活动的哈密、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南郊、木垒、阿勒泰等中心地区,都曾出土有匈奴的动物纹样器物,大至青铜鍑小到饰牌都有发现。乌鲁木齐南山出土的铜鍑底座为喇叭形,一对提手有蘑菇状造型,鍑的外壁是装饰形花纹。就其花纹而言,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西汉式纹样。这些地点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野猪纹透雕铜牌、几何形透雕饰牌都与内蒙古匈奴墓出土的此类物件几乎无殊。无论从造型、技法、题材看,都可以断定是匈奴的动物纹样。
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有极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也反映在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的卡拉苏克、塔加尔文化的动物纹样中。塔加尔人把诸如熊、鹿、雪豹、虎、山羊等动物形象雕刻在带扣、刀柄、短剑、饰牌、坠饰等铜器上。这些动物形象装饰为立像、奔驰像、蜷曲形和猛禽头像等。对于塔加尔动物纹样同周边文化的关系,吉谢列夫认为:“鄂尔多斯和蒙古的形象同塔加尔形象极为相似,但也有其特点——起伏比较柔和,躯体的表现同北方扬诺博尔——格利亚登诺沃风格的熊的姿势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熊的立像在鄂尔多斯和蒙古并不是惟一的,甚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母题。野猪和猫科动物(雪豹和虎)的形象也常有发现。这些无疑是在北方草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之下创造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具有另一种风格,同中国圆雕的联系较为密切。”①其实比塔加尔文化更早的卡拉苏克文化也因东边丁零等部族在此地域的活动,其动物纹样的铜刀、短剑和铜牌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华北这三个地区经常出现。②无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两端的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游牧文化就在阿尔泰山区发生了融合,因此出现了一种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动物纹样,它对诸如匈奴、鲜卑、月氏、乌孙、乌揭乃至突厥、蒙古等部族和民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从东西两个方向互动的动物纹样的汇合处。
对干草原动物纹样的起源趋同性特征,学者们试图做出各种解释,有代表性的是格鲁塞的解释: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人民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他们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儿马忒人或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集处所,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只是表现在衣冠上、金首饰上,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已。这些物件:——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用说像在诺音——乌拉的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而以至于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人民,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或突厥—蒙古人种如匈奴,都是在马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从事于追逐反刍动物或野驴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在追逐着野羊。这是很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爱奢侈的个性,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在于徽章图形铜牌方面的考究和动物斗争图的风格。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在草原上的这些猎狩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有其巫术的目的,这是如同我们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们雕刻的骨头上的图画一样。③
雕刻在带扣、刀柄、短剑、饰牌、坠饰等铜器上。这些动物形象装饰为立像、奔驰像、蜷曲形和猛禽头像等。对于塔加尔动物纹样同周边文化的关系,吉谢列夫认为:“鄂尔多斯和蒙古的形象同塔加尔形象极为相似,但也有其特点——起伏比较柔和,躯体的表现同北方扬诺博尔——格利亚登诺沃风格的熊的姿势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熊的立像在鄂尔多斯和蒙古并不是惟一的,甚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母题。野猪和猫科动物(雪豹和虎)的形象也常有发现。这些无疑是在北方草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之下创造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具有另一种风格,同中国圆雕的联系较为密切。”①其实比塔加尔文化更早的卡拉苏克文化也因东边丁零等部族在此地域的活动,其动物纹样的铜刀、短剑和铜牌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华北这三个地区经常出现。②无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两端的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游牧文化就在阿尔泰山区发生了融合,因此出现了一种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动物纹样,它对诸如匈奴、鲜卑、月氏、乌孙、乌揭乃至突厥、蒙古等部族和民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从东西两个方向互动的动物纹样的汇合处。
对干草原动物纹样的起源趋同性特征,学者们试图做出各种解释,有代表性的是格鲁塞的解释: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人民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他们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儿马忒人或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集处所,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只是表现在衣冠上、金首饰上,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已。这些物件:——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用说像在诺音——乌拉的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而以至于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人民,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或突厥—蒙古人种如匈奴,都是在马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从事于追逐反刍动物或野驴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在追逐着野羊。这是很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爱奢侈的个性,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在于徽章图形铜牌方面的考究和动物斗争图的风格。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在草原上的这些猎狩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有其巫术的目的,这是如同我们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们雕刻的骨头上的图画一样。③
共同的生产方式,相同的生活习俗当然是动物纹样共生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充其量是外在因素,而对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却只用“有巫术目的”一笔带过。在此,我们不能不涉及动物纹样起源的深层结构。就生产、生活方式等外在因素而言,它只讲清了人与物(动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没有阐明“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①“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②
草原动物纹样是出现在史前文化中的,它们在“原始文化中总要联系着某种观念,满足着某种需要,实现着某种价值,产生着某种影响。亦即是说,原始艺术品终归要发挥它的文化功能”。③从根本上讲,动物纹样的创作者正是一些深谙“天—地—人”三元统一者。因此,动物纹样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投入作品”。④创作者与动物纹样的关系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猎牧民的“天—地—人”三元统一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试图以这种纯然的统一性来解释世界。能够予以解释的只有在欧亚草原自史前就存在的萨满教信仰。萨满世界就是一个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是天神的居所,地是动物的栖所,人是短暂者。这三者的沟通者只能是萨满,于是他成了“天—地—人”之间的媒介,也就是海德格尔“四元论”中的神圣者。神圣者是神性召唤的信使,从隐秘的力量中,神圣者显现为其所是,它使自身远离任何与现身者的相比。⑤在一个充斥着萨满世界观的文化情境中,动物纹样如同岩画、鹿石一样,只有功能意义,而不具备纯形式分类的意义。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的结构模式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它由上界、中界、地界构成:“上界就是天界,是各路天神住的地方,也就是上述的天上国;下界就是地界,是各种凶恶魔鬼栖止的地方,也就是地下国;中界就是人界,是人类和人类的朋友——甚至认为是和人同类的动物共同生息的地方。在这三界中,天和地都被看作是多层的所在。”⑥它是一个对应于“天—地—人”的三元模式。沟通天地的是萨满及其动物精灵。艾利亚德认为:“萨满们还有一批专属他们自己的精灵,其他人和献祭的人对此毫不知晓..这些作为伙伴,充当助手的精灵多作动物状。在西伯利亚和阿尔泰人中间,他们有熊、狼、雄鹿、兔,所有种类的鸟(尤其是雁、鹰、鸮、乌鸦等),各种大虫子,此外还有幽灵、树的精灵、泥土的精灵、灶神等等。”①召唤动物精灵的通行办法是萨满在出神状态下(实际上是进入迷幻状态,中亚的早期萨满是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的),击鼓并舞之蹈之召唤的,其行为仪式是以这些动物作为牺牲,使之从自己的躯体中解脱和升华出来。在一个充满巫术思维的萨满世界中,“表象”和真实是同一的,萨满控制了动物纹样实际上就占有了这些动物本身。尽管这些氏族、部落萨满的动物精灵各有不同,而且动物纹样形状各异,如咬啮状、蜷曲状、成双成对等等,但功能是相同的:“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形象。”②对于经常游移迁徙的猎牧民来说,随身携带的动物纹样牌饰、带钩、武器等更便捷,沟通“天—地—人”的巫术功能也更灵验,更何况氏族或部落萨满要借助于动物纹样经常性实施巫术以确保本氏族、部落的繁衍和猎获动物的成功。
草原动物纹样青铜器、金银器经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后,由于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渐进式变化,器形及纹样的功能性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非功能性的实用工艺性,也就是说,一种以审美为主的器型和纹样出现了。突厥人的金银器就属此类。“自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曾作为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当其盛时,版图东抵兴安岭,西达铁门关,‘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被史家称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大地的突厥’”。在6世纪80年代,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以阿尔泰山为界,其东为东突厥汗国,其西为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的疆域包括西域广大地区,其盛时势力远抵阿姆河以北的铁门。突厥也是个信仰萨满教的部族,但其信仰远不能和塞人、匈奴人相比了,自信仰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可能信仰佛教后,萨满教也只是残余了。于是金银器无论从形制和纹样都发生了变化:“广泛习见于匈奴、塞族的青铜制品,如浮雕或透雕的动物纹的腰带扣不见了,而代之以双首月体的铜带扣,鸭形壶也是远古草原青铜艺术中所不见。..有些题材,虽然承袭了下来,但在形制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④突厥曾是柔然的“锻奴”,擅长金属器物的制作,包括金银、红铜、铁等制品,尤其是突厥金银器在他们的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厥金银器主要以生活器皿、用具和首饰品为主,有金罐、银壶、金银盘、金银杯、银马具、金带柄剑、步摇、手镯、戒指、耳环等。突厥金银器中有一种折肩的罐、杯等物。这类器皿在阿尔泰、内蒙古等地都有出土,它有素面和錾花折肩器之分。在阿尔泰地区库赖草原和乌尔河沿岸,突厥大墓出土的两件银罐“侈口鼓腹,腹上侧装单环状把手,在器肩处有一圈明显的折棱”,①素面,故名为折肩罐。而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出土的两件折肩式金罐,其中一件器身满布缠枝卷草,在颈部和腹部以枝蔓簇结成两排类似“开光”的莲瓣形,莲瓣之内填以凤衔绶带。②折肩杯与折肩罐相较,体型较小,无把手,但器形与折肩罐相同。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2号墓中和陕西礼泉郑仁泰墓中都曾出土过金银盘,其中有的在中心的圆框外环绕一圈桃形花结的图案,通常称为宝相花。1997年10月曾在新疆昭苏县境内的西突厥墓中出土有70余件金银器等遗物,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面具、镶嵌红宝石虎柄金杯、镶嵌红宝石包金剑鞘和缀金珠饰织物、金戒指等。特别是“镶嵌红宝石带盖金罐盖上模压出7朵宝相花纹,花心部及盖周缘镶嵌宝石”,③与其他地方出土的突厥金银盘中的宝相花纹如出一辙。从这些突厥金银器中不难发现,一些金银罐、杯是作为饮器使用的,而其他一些器物也是实用器物或首饰类。其纹样也不似塞人、匈奴人的动物纹样,而出现了以装饰性花卉对称出现的纹样。制作技术以錾、镶嵌、金珠鱼子纹细工、焊接、锤鍱、模压、抛光等工艺为主。
从动物纹样的功能性到实用装饰性的角色转换,意味着草原金银铜器无论是形制还是纹样都兆示,它们揖别了复功用性,而进入了生活审美领域的实用工艺阶段。诸如突厥金银器的造型、色彩、纹样都证明工匠们是一些“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美的法则,诸如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稳定与轻巧、直线与曲线、比例与尺度、多样与统一”④的高手,虽然这些实用工艺品并非纯艺术品,但它比纯艺术品毫不逊色。
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青铜器、金银器的早期主人是塞人、匈奴人、鲜卑人、乌孙人、大月氏人等诸多游牧部落,其后以装饰性突出的突厥、蒙古等的金银器则是草原动物纹样的余韵。虽然突厥等中古游牧部落仍使用古老的金、铜等金属饰品,但通天工具的作用在逐渐消解,而代之以一种新的装饰审美时尚,对突厥贵族来说,黄金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
中亚草原最早的游牧部落无疑是中国汉代史籍译为“塞”,而古波斯文献称之为“萨迦”的塞人,他们自公元前7世纪就在中亚草原活动,并渗入绿洲地区。“萨迦”在古音中读为“sak”,因此,“塞克”、“萨迦”、“塞”不过是它的不同音译。塞人在西域草原地带的活动主要在公元前5~前3世纪之间,他们分布于伊犁河流域、西天山、东天山及帕米尔高原一带,为典型的游牧部落。塞人公元前1世纪进入印度,公元前后在塔里木盆地以及和田绿洲定居下来,公元5世纪又扩展至塔里木盆地东缘的鄯善。这部分定居的塞人因生产方式的改变,成为绿洲农耕民,但他们仍保留着游牧部落的文化传统。塞人是否就是古代的游牧部落斯基泰人呢?学者的意见是相左的。所谓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是指分布于欧亚草原上从喀尔巴阡山往东至顿河,以至更东的游牧人(又译为西徐亚人)。希罗多德坚持说:“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迦人的。”①“由此可见萨迦人与斯基泰人,名虽不同,其实则一”。②这个提法为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的学者普遍接受。塞人或塞克实际上就是希罗多德等希腊学者所指称的亚洲斯基泰人,主要是游牧于亚洲草原地带的氏族部落,以别于欧洲斯基泰人。③西方学者也把这部分斯基泰人称之为斯基泰塞人。④他们从哈萨克草原到天山北部及阿尔泰山一带广泛分布。这样,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西方学者所谓斯基泰式动物纹样冠之于塞人动物纹样了。正当塞人呈自西向东的流向时,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则在自东向西流动。“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统一大漠南北的全部地区,并建立起国家政权——匈奴单于国的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活动了约三百年。东汉初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于汉,入居塞内,北匈奴不久(公元91年)因战败西迁中亚和欧洲”。⑤早在秦汉时,匈奴就沿丝绸之路南道、北道、中道抵达西域南北部,于公元91年,被汉朝打败后逃遁。匈奴自秦汉之际在西域活动起至东汉时西迁,其文化与曾和正在活动于西域草原地带的塞人、乌孙、月氏、乌揭等游牧文化发生交融互渗。特别是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终于有机会在天山、阿尔泰山草原地带相遇了。
不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延续时间要长得多,经历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铁器时代。⑥鄂尔多斯动物纹样起始于商代晚期,而盛于战国时期,这是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的繁盛期。就与周边文化关系而言,早在公元前1000年纪,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与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关系密切,尤其是卡拉苏剑首的动物造型与鄂尔多斯的非常相似。①也就是说在商周时期,这两种文化就有密切接触了。到了塔加尔文化时期,东西两个方向的动物纹样开始融合。
塞人的动物纹样是黄金饰品,对此,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认为:“塞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黄金饰品成为塞人生用死殉的最主要用品,这可能和他们的太阳神信仰有关。如果从类型看几乎全是饰牌、带钩、饰片及刀、马具上的装饰等,而且以动物纹样圆形金牌为多。考古学家曾对天山阿拉沟塞人的4座竖穴木椁墓进行发掘,发现无墓不见金器。仅第三十号墓就出土虎纹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带4件,狮形金箔1件,菱形花金饰片3件,较大圆形金泡饰片33片,以及柳叶形、螺旋形等金饰片、金串饰130多件,合计在200件以上。因这些墓均被盗扰,所见金器不过是盗墓后的劫余。②这里所说的虎纹圆金牌可能是猫科动物中的雪豹纹样圆金牌。塞人金牌中的动物纹样主要是狮、豹、熊、狼、鹫、雄山羊、鹿、鸟翼等凶兽猛禽形象。伊塞克古墓曾出土四千多件器物,其中有156件是金质动物纹样牌饰类,也是塞人的动物纹样器物。国外学者对伊塞克古墓出土的塞人动物纹样的造型和风格有过细致研究,几乎涉及所有的动物纹样。以雪豹牌饰为例:“雪豹形象都是侧面像,伊塞克雪豹侧面像的脸、嘴全部不相上下,圆脑袋,扁状眼睛,旋贝状三角耳,龇牙咧嘴。颧骨渲染成一道凹进的宽弧形,肩胛骨以涡卷纹表示。尾巴卷成圆圈。表示肋骨的是一排突出的弧。大腿由双行线构成,腹下、肋部和从背到脚的部位也遍布这种线条。”③有翼的雪豹牌饰上的雪豹后爪蹬着模拟山行的踞齿缘,拧着前半身,仿佛要扬起前爪搏击一般,动物躯体强壮而柔韧,着重表现了野兽的狂暴和凶猛,狰狞地龇着牙,咧着嘴,肩部是以凸出的涡纹标出,从那里伸出模拟翅膀的突芽。①虽是个例,但它凸现出塞人动物纹样造型的所有特征。塞人的动物纹样几乎全是野兽咬啮状和蜷曲形,以牌饰为主的动物纹样虽然器形小,但乾坤大。塞人善于在有限的形式——牌饰等小型物件中拓展无限想象马镫的空间,善于利用空间巧妙地处理动物题材。以圆雕为主的工艺娴熟,纹样轮廓简洁、醒目,内容充实而完美,手法写实而夸张。苏联研究早期游牧文化的学者格拉科夫的论述不无精当:
这种风格,大多描绘某些企图击倒对方的猛兽和善于反搏对方袭击的灵敏家畜,同时突出表现这两类动物的攻击器官和感觉器官。这些动物,口内长满了巨大的牙齿,嘴和足的表现尤为明确具体。十分夸张耳朵、鼻孔和眼睛,蹄宽大而趾尖锐。..通过对于猛兽趾爪、牙齿、蹄子、翅膀以及灵活敏锐的鼻子、耳朵等各种器官的表现,使动物的全身尤其肩部及腰部充满一种强劲的力量,而且,对于这些最能显示攻击能力及灵敏感觉的器官本身,则特别提到显要部位加以充分塑造。②
活动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也有较大型的青铜器物——方座承兽铜盘。天山阿拉沟方座承兽铜盘,器身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鬣毛卷曲成穿孔,似翼。①1983年在伊犁巩乃斯河岸也出土同一类型的铜盘。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两件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和双飞兽相对圆环。②于是这种幻想式的动物纹样成了塞人这类动物造型的标志,也显然是它的特征。
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主要出现在刀、匕、剑、饰牌、带钩、扣饰、头饰、佩饰等器物中。动物形象包括家畜,如马、牛、羊、驼等和野生动物鹿、虎、豹、狼、鸟等,以鹿、虎、鸟的形象多见。“这些动物纹大体可归纳为鸟形、兽头形、宁立形、蹲踞形、弯曲兽形、群兽形、动物咬斗形和人与动物结合组成的反映社会生活场面的各种造型等”。③不过,与塞人动物纹样相比较,动物咬斗形纹样发现的并不多。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早期(商周时期)多以圆雕技法将动物兽头形象装饰在青铜短剑、刀的柄端。到春秋时动物纹样以图案化的双鸟纹盛行,且主要装饰在腰带上。鸟喙特别强调钩状特征。战国时期是鄂尔多斯动物纹样的繁盛期,以圆雕、浮雕技法表现的动物纹样,有较强的写实性。动物形象除个体外,还有不同动物的组合形象。工艺已达到精工娴熟程度,制作工艺也日趋复杂,有镶嵌、锤鍱、抽丝及错金银等工艺。两汉时期,诸如兽头形、宁立形、蹲踞形等动物纹样基本不见,动物形象刻画也少了纯写实手法,大型饰牌往往在卧羊等家畜周围衬托花草纹,以自然景物,如山、树等相衬托的动物纹样成为普遍流行装饰。④
在匈奴右部曾活动的哈密、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南郊、木垒、阿勒泰等中心地区,都曾出土有匈奴的动物纹样器物,大至青铜鍑小到饰牌都有发现。乌鲁木齐南山出土的铜鍑底座为喇叭形,一对提手有蘑菇状造型,鍑的外壁是装饰形花纹。就其花纹而言,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西汉式纹样。这些地点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野猪纹透雕铜牌、几何形透雕饰牌都与内蒙古匈奴墓出土的此类物件几乎无殊。无论从造型、技法、题材看,都可以断定是匈奴的动物纹样。
塞人动物纹样和鄂尔多斯动物纹样有极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也反映在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的卡拉苏克、塔加尔文化的动物纹样中。塔加尔人把诸如熊、鹿、雪豹、虎、山羊等动物形象雕刻在带扣、刀柄、短剑、饰牌、坠饰等铜器上。这些动物形象装饰为立像、奔驰像、蜷曲形和猛禽头像等。对于塔加尔动物纹样同周边文化的关系,吉谢列夫认为:“鄂尔多斯和蒙古的形象同塔加尔形象极为相似,但也有其特点——起伏比较柔和,躯体的表现同北方扬诺博尔——格利亚登诺沃风格的熊的姿势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熊的立像在鄂尔多斯和蒙古并不是惟一的,甚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母题。野猪和猫科动物(雪豹和虎)的形象也常有发现。这些无疑是在北方草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之下创造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具有另一种风格,同中国圆雕的联系较为密切。”①其实比塔加尔文化更早的卡拉苏克文化也因东边丁零等部族在此地域的活动,其动物纹样的铜刀、短剑和铜牌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华北这三个地区经常出现。②无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两端的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游牧文化就在阿尔泰山区发生了融合,因此出现了一种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动物纹样,它对诸如匈奴、鲜卑、月氏、乌孙、乌揭乃至突厥、蒙古等部族和民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从东西两个方向互动的动物纹样的汇合处。
对干草原动物纹样的起源趋同性特征,学者们试图做出各种解释,有代表性的是格鲁塞的解释: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人民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他们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儿马忒人或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集处所,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只是表现在衣冠上、金首饰上,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已。这些物件:——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用说像在诺音——乌拉的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而以至于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人民,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或突厥—蒙古人种如匈奴,都是在马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从事于追逐反刍动物或野驴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在追逐着野羊。这是很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爱奢侈的个性,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在于徽章图形铜牌方面的考究和动物斗争图的风格。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在草原上的这些猎狩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有其巫术的目的,这是如同我们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们雕刻的骨头上的图画一样。③
雕刻在带扣、刀柄、短剑、饰牌、坠饰等铜器上。这些动物形象装饰为立像、奔驰像、蜷曲形和猛禽头像等。对于塔加尔动物纹样同周边文化的关系,吉谢列夫认为:“鄂尔多斯和蒙古的形象同塔加尔形象极为相似,但也有其特点——起伏比较柔和,躯体的表现同北方扬诺博尔——格利亚登诺沃风格的熊的姿势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熊的立像在鄂尔多斯和蒙古并不是惟一的,甚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母题。野猪和猫科动物(雪豹和虎)的形象也常有发现。这些无疑是在北方草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之下创造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具有另一种风格,同中国圆雕的联系较为密切。”①其实比塔加尔文化更早的卡拉苏克文化也因东边丁零等部族在此地域的活动,其动物纹样的铜刀、短剑和铜牌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华北这三个地区经常出现。②无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两端的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游牧文化就在阿尔泰山区发生了融合,因此出现了一种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动物纹样,它对诸如匈奴、鲜卑、月氏、乌孙、乌揭乃至突厥、蒙古等部族和民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从东西两个方向互动的动物纹样的汇合处。
对干草原动物纹样的起源趋同性特征,学者们试图做出各种解释,有代表性的是格鲁塞的解释: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人民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他们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儿马忒人或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集处所,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只是表现在衣冠上、金首饰上,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已。这些物件:——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用说像在诺音——乌拉的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而以至于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人民,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或突厥—蒙古人种如匈奴,都是在马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从事于追逐反刍动物或野驴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在追逐着野羊。这是很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爱奢侈的个性,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在于徽章图形铜牌方面的考究和动物斗争图的风格。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在草原上的这些猎狩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有其巫术的目的,这是如同我们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们雕刻的骨头上的图画一样。③
共同的生产方式,相同的生活习俗当然是动物纹样共生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充其量是外在因素,而对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却只用“有巫术目的”一笔带过。在此,我们不能不涉及动物纹样起源的深层结构。就生产、生活方式等外在因素而言,它只讲清了人与物(动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没有阐明“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①“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②
草原动物纹样是出现在史前文化中的,它们在“原始文化中总要联系着某种观念,满足着某种需要,实现着某种价值,产生着某种影响。亦即是说,原始艺术品终归要发挥它的文化功能”。③从根本上讲,动物纹样的创作者正是一些深谙“天—地—人”三元统一者。因此,动物纹样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投入作品”。④创作者与动物纹样的关系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猎牧民的“天—地—人”三元统一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试图以这种纯然的统一性来解释世界。能够予以解释的只有在欧亚草原自史前就存在的萨满教信仰。萨满世界就是一个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是天神的居所,地是动物的栖所,人是短暂者。这三者的沟通者只能是萨满,于是他成了“天—地—人”之间的媒介,也就是海德格尔“四元论”中的神圣者。神圣者是神性召唤的信使,从隐秘的力量中,神圣者显现为其所是,它使自身远离任何与现身者的相比。⑤在一个充斥着萨满世界观的文化情境中,动物纹样如同岩画、鹿石一样,只有功能意义,而不具备纯形式分类的意义。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的结构模式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它由上界、中界、地界构成:“上界就是天界,是各路天神住的地方,也就是上述的天上国;下界就是地界,是各种凶恶魔鬼栖止的地方,也就是地下国;中界就是人界,是人类和人类的朋友——甚至认为是和人同类的动物共同生息的地方。在这三界中,天和地都被看作是多层的所在。”⑥它是一个对应于“天—地—人”的三元模式。沟通天地的是萨满及其动物精灵。艾利亚德认为:“萨满们还有一批专属他们自己的精灵,其他人和献祭的人对此毫不知晓..这些作为伙伴,充当助手的精灵多作动物状。在西伯利亚和阿尔泰人中间,他们有熊、狼、雄鹿、兔,所有种类的鸟(尤其是雁、鹰、鸮、乌鸦等),各种大虫子,此外还有幽灵、树的精灵、泥土的精灵、灶神等等。”①召唤动物精灵的通行办法是萨满在出神状态下(实际上是进入迷幻状态,中亚的早期萨满是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的),击鼓并舞之蹈之召唤的,其行为仪式是以这些动物作为牺牲,使之从自己的躯体中解脱和升华出来。在一个充满巫术思维的萨满世界中,“表象”和真实是同一的,萨满控制了动物纹样实际上就占有了这些动物本身。尽管这些氏族、部落萨满的动物精灵各有不同,而且动物纹样形状各异,如咬啮状、蜷曲状、成双成对等等,但功能是相同的:“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形象。”②对于经常游移迁徙的猎牧民来说,随身携带的动物纹样牌饰、带钩、武器等更便捷,沟通“天—地—人”的巫术功能也更灵验,更何况氏族或部落萨满要借助于动物纹样经常性实施巫术以确保本氏族、部落的繁衍和猎获动物的成功。
草原动物纹样青铜器、金银器经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后,由于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渐进式变化,器形及纹样的功能性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非功能性的实用工艺性,也就是说,一种以审美为主的器型和纹样出现了。突厥人的金银器就属此类。“自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曾作为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当其盛时,版图东抵兴安岭,西达铁门关,‘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被史家称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大地的突厥’”。在6世纪80年代,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以阿尔泰山为界,其东为东突厥汗国,其西为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的疆域包括西域广大地区,其盛时势力远抵阿姆河以北的铁门。突厥也是个信仰萨满教的部族,但其信仰远不能和塞人、匈奴人相比了,自信仰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可能信仰佛教后,萨满教也只是残余了。于是金银器无论从形制和纹样都发生了变化:“广泛习见于匈奴、塞族的青铜制品,如浮雕或透雕的动物纹的腰带扣不见了,而代之以双首月体的铜带扣,鸭形壶也是远古草原青铜艺术中所不见。..有些题材,虽然承袭了下来,但在形制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④突厥曾是柔然的“锻奴”,擅长金属器物的制作,包括金银、红铜、铁等制品,尤其是突厥金银器在他们的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厥金银器主要以生活器皿、用具和首饰品为主,有金罐、银壶、金银盘、金银杯、银马具、金带柄剑、步摇、手镯、戒指、耳环等。突厥金银器中有一种折肩的罐、杯等物。这类器皿在阿尔泰、内蒙古等地都有出土,它有素面和錾花折肩器之分。在阿尔泰地区库赖草原和乌尔河沿岸,突厥大墓出土的两件银罐“侈口鼓腹,腹上侧装单环状把手,在器肩处有一圈明显的折棱”,①素面,故名为折肩罐。而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出土的两件折肩式金罐,其中一件器身满布缠枝卷草,在颈部和腹部以枝蔓簇结成两排类似“开光”的莲瓣形,莲瓣之内填以凤衔绶带。②折肩杯与折肩罐相较,体型较小,无把手,但器形与折肩罐相同。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2号墓中和陕西礼泉郑仁泰墓中都曾出土过金银盘,其中有的在中心的圆框外环绕一圈桃形花结的图案,通常称为宝相花。1997年10月曾在新疆昭苏县境内的西突厥墓中出土有70余件金银器等遗物,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面具、镶嵌红宝石虎柄金杯、镶嵌红宝石包金剑鞘和缀金珠饰织物、金戒指等。特别是“镶嵌红宝石带盖金罐盖上模压出7朵宝相花纹,花心部及盖周缘镶嵌宝石”,③与其他地方出土的突厥金银盘中的宝相花纹如出一辙。从这些突厥金银器中不难发现,一些金银罐、杯是作为饮器使用的,而其他一些器物也是实用器物或首饰类。其纹样也不似塞人、匈奴人的动物纹样,而出现了以装饰性花卉对称出现的纹样。制作技术以錾、镶嵌、金珠鱼子纹细工、焊接、锤鍱、模压、抛光等工艺为主。
从动物纹样的功能性到实用装饰性的角色转换,意味着草原金银铜器无论是形制还是纹样都兆示,它们揖别了复功用性,而进入了生活审美领域的实用工艺阶段。诸如突厥金银器的造型、色彩、纹样都证明工匠们是一些“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美的法则,诸如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稳定与轻巧、直线与曲线、比例与尺度、多样与统一”④的高手,虽然这些实用工艺品并非纯艺术品,但它比纯艺术品毫不逊色。
附注
①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2.
②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14.
③安志敏.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38.
④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14.
⑤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185.
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478.
⑦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480.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660.
②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8.
③〔苏〕阿基舍夫著.吴妍春译.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克艺术.新疆文物.1995(2).
④〔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26.
⑤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5.
⑥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185.
①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191.
②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21.
③〔苏〕阿基舍夫著.吴妍春译.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克艺术.新疆文物.1995(2).
①〔苏〕阿基舍夫著.吴妍春译.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克艺术.新疆文物.1995(2).
②王明增编译.丝路遗宝(一).美术史论.1987(4).
①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人民出版社,1993.213.
②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16.
③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162.
④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
①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铅印本.123.
②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铅印本.62.
③〔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31.
①王晓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新整体论文艺学论纲.学术月刊.2002(7).
②王晓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新整体论文艺学论纲.学术月刊.2002(7).
③牛克诚.原始艺术品在巫术中的使用与操作(下).美术史论.1991(2)
④〔德〕M.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
⑤〔德〕M.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57.·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7.
⑥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2.
①转引自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48.
②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46.
③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260.
④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250.
①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261.
②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262~263.
③于志勇.新疆昭苏西突厥黄金宝藏.文物天地.2000(2).
④李心峰.艺术类型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303.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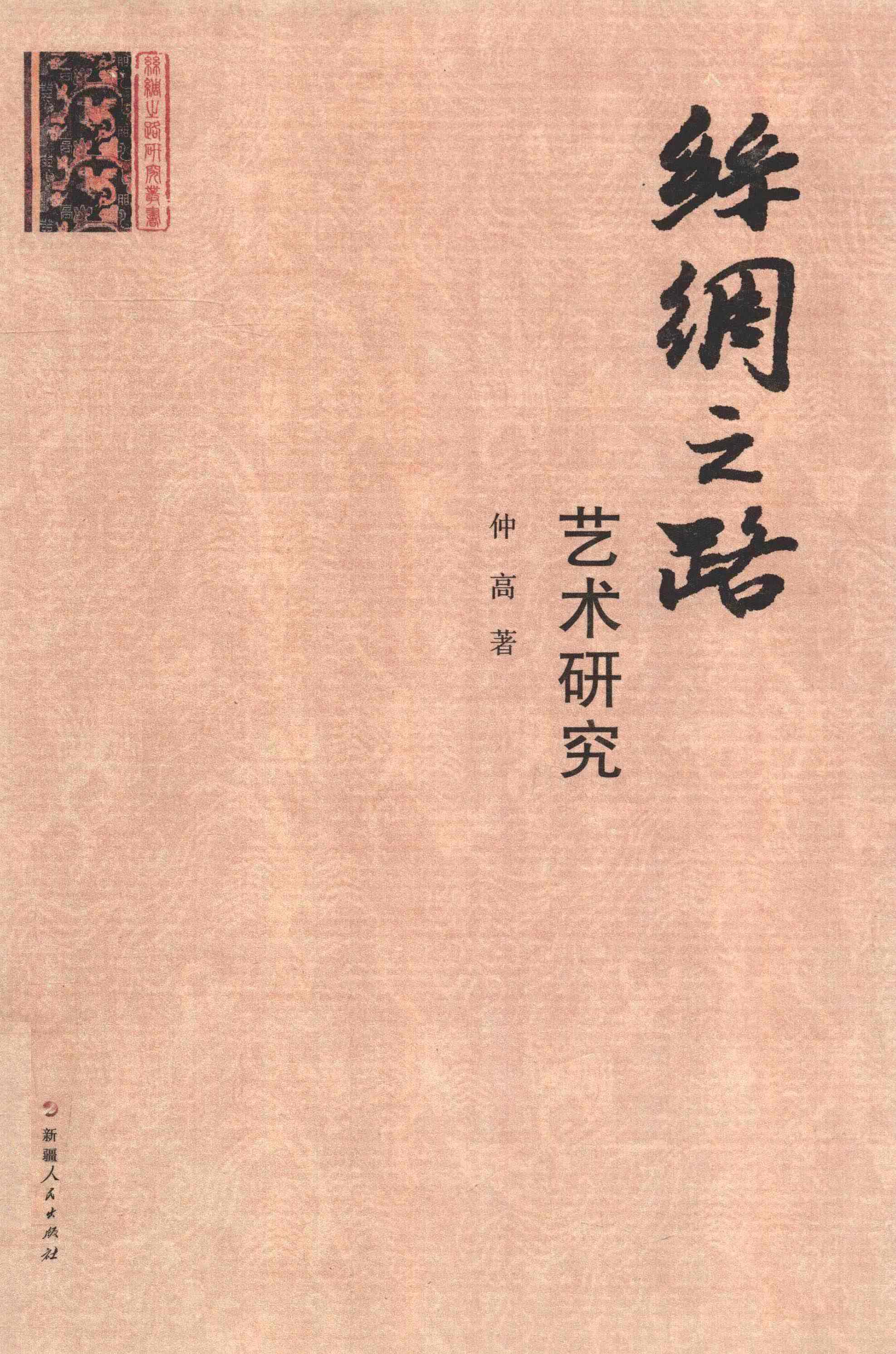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