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背民族的艺术摇篮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32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马背民族的艺术摇篮 |
| 分类号: | K879.45 |
| 页数: | 8 |
| 页码: | 136-143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马背民族的艺术摇篮情况包括游牧部落是古代的匈奴、鲜卑、呼揭、乌孙、柔然、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契丹、蒙古以及近代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马背民族 艺术摇篮 |
内容
如果说绿洲是丝绸之路农耕民族的生命线,那么,草原就是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摇篮。绿洲“居国”和草原“行国”显然属不同的文化类型。当绿洲的农民守土躬耕时,草原上的游牧民则在自由驰骋。这些游牧部落把欧亚大草原当作活动的大舞台。欧亚草原是如此广阔,游牧部落是如此众多,文化艺术是如此丰富多彩。欧亚山地草原地带依山脉的分隔形成三大块,即东起大兴安岭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至乌拉尔山和乌拉尔山至喀尔巴阡山三大区域。这儿有辽阔的草原牧场,也有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尽管一座座高山绵亘,但它们并不能阻止游牧民族的游移、迁徙。除早期的塞人外,丝绸之路草原部落的基本流向是自东向西。“印欧人种的居住空间呈现萎缩倾向,亚洲人种的语言和血缘则是扩张态势。苦瘠的蒙古高原无法容纳增长的人口,地域辽阔且水草茂盛的俄罗斯南部草原更是‘马背上的人们’所向往的。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几乎是这一人类流动的无穷无尽的源泉”①。人们惊奇地发现,印欧语系的塞人和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都曾游牧于此。阿尔泰语系的这些游牧部落是古代的匈奴、鲜卑、呼揭、乌孙、柔然、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契丹、蒙古以及近代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而且他们主要来自蒙古高原,证明其流向是自东向西的。
活动于西域北部草原的这些游牧部落具有与绿洲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绿洲农耕民族无论是凿渠引水,还是开荒垦殖,始终把自己放在征服自然的位置上。而草原游牧民则不然,他们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水草牧场给游牧民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不动产”,而放牧于兹的马、羊、牛则是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他们的“动产”。游牧民族与大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所以“游牧民族尽管其种族、肤色、语言有差别,但其劳动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却都相同。这种共性本质,就在于游牧社会都是在:水草牧场〓牲畜〓游牧劳动——这三种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无论是游牧父权氏族社会、游牧奴隶制和游牧封建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畜牧业生产,都是在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生成发展的,只是这些不同阶段的对象性关系的性质和对象化活动形式不同罢了”①。这三种对象性关系看似简单,其实含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冬夏牧场的选择,草原对牲畜的负荷量,牲畜的繁殖、放牧、驯养,奶制品、日常生活器皿的制作及毡房的搭建,冬夏服装的缝织,人生和节日礼仪、文化娱乐生活等行为仪式和精神追求等等莫不如此。这里,往往是经济动机和文化意识纠葛在一起,游牧生活充满文化意味,而文化意味则在展示他们的审美感觉、艺术想象和表现形式及创作思维。
在游牧生产、生活活动中举足轻重的是坐骑——马。游牧民族之所以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和马联系在一起。整个游牧社会是依赖马在维系,马是坐骑,马是交通工具和征战工具,迁徙游牧、四方征战、闲暇游戏,马以人为主,人以马当伴。在游牧民族眼里,马是有灵性、通人性的,于是赋予马以各种人文含义。当然,马背民族对马的钟爱是从驯马开始的。欧亚大草原正是人类第一次驯服马的摇篮:“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之间,生活在亚洲大草原边缘上的某个民族或者某几个民族,在已经掌握了牛和羊的习性的基础上,培养出第一批家养马的品种。”②自此,马与游牧民族之间便存在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人类学家们已经在设法复现马在这些最早的马背文化中的作用。我们研究过诸如雅库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这样的中亚游牧民族,他们直到最近还保持着祖先的很多生活方式。这些游牧者的整个生存都依赖于马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把马作为食物,而且还因为马使他们在大草原为他们提供的稀疏的自然牧场上放牧牛羊成为可能。在那个风多树少的环境中,他们惟一的生存之路就是使牛羊散布在方圆数百里的地方,让它们不停地寻找水草。在靠近欧洲的西部,雨量充沛,牧草比较丰美,马背游牧民养的牛比羊多。而在靠近蒙古的东部,半沙漠的环境比较普遍,那里的牧民养的羊比牛多。在这两种情况下,马的贡献都在于它的流动性,它使其主人能够照料广泛散布的畜群,它可以迅速移动以抵御来自那些专好偷窃别人牲畜的敌对邻邦的威胁。”①从一定意义上说,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马背民族的文化。盘马弯弓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熟谙养马之术,精于骑射,养成骁勇善战、豪放不羁的品格。哈萨克人将马称为“百畜之王”,认为“马是人的翅膀”。他们在长期的养马实践中对马的毛色、品种、禀性、体态、姿势等特征了如指掌,并形成丰富的相马经验。曾有哈萨克族学者对有关马的各方面特征的词汇作过统计:
哈萨克过去的语言中,有关马的毛色的名称(词汇)有350种之多——从大的方面虽然分为Baran(深色)和qelang(浅色)两种,然而从小的方面却分得异常精细,例如,枣骝类有23种;棕黄色22种;黑马32种;黄色28种;灰白色15种。还有吉祥和非吉祥的颜色名称。吉祥的有:黑耳朵马、白鼻子马、花白腿马、白腿马等等;非吉祥的有:灰眼睛马、白头马、月形白鼻梁、白嘴马等等。仅用于形容马走的姿势的词汇就有30多个,而有关骏马标志的形容词则有约100个,比如,用于说明马的年龄的专有名词就有25个;而有关马的性别的词有15个;有关马群的特点的词汇有10个;有关母马的各种禀性的词汇有17个,而根据母马的产奶情况而对此加以说明的词汇有11种;而将母马的乳房特点分为14类并且用不同的专有名词加以说明;根据产奶量来为马进行分类的词汇有7个;用于形容马的神态的词有6个;刚配群的3岁马分为36种,并用36种词加以说明;公马分为13种;骟马分为7种;离群的马分为12种(有12种名称);小马驹有16种名称;根据马的牙的特点分为17类;而用于说明母马、公马和一般骟马的“中性”词则有约30种;用于说明马的属性的词汇有100个左右;仅用于说明马走和跑的姿势特征的词有30种。而用于马的有关性别、年龄、体形、性等方面的特征和形象的词汇(专有名词)有600多个。②
由马及人、及物,在哈萨克族中还有不少部落名称、地名、人名也是与马有关的,如果一一列举,简直就是一本马文化辞典。
相马、养马不仅构成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与他们的政治、军事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蒙古人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西征,靠的就是兵民合一的部落兵制:“为了弥补长期战争的人员消耗,蒙古统治者将15岁以下的儿童编成‘渐丁军’(意思是‘渐长成丁军’),作为蒙古军队的后备力量。
孩子到3岁时,就将他直接‘索维’在马鞍上,让他手里拿着器械,骑马任意奔驰,四五岁时就在马上练习弓箭,再大一点便经常参加狩猎。十五六岁便参加正式作战。北方民族在战争期间广泛实行自备鞍马粮草兵器的兵役制度。”①从小与马为伍,以马为友,焉能不与马产生感情?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背就是他们的家,马背承负着整个民族的荣辱兴衰。游牧民族一旦离了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马鞍、马镫的发明更使他们如虎添翼。
世界上最早的马鞍、马镫诞生于何时何地,已无实物可考,但在新疆鄯善县属战国时期的苏贝希墓群1号墓地出土了包括马鞍在内的一系列马具。这套马具包括马鞍、马络、绞具、衔、镳、肚带。马鞍用毡皮合制。鞍两侧的四角各有数条皮绳,做捆扎猎物之用。桃形、S形骨带扣用来固定前、后鞧的革带。②这是现知的我国最早的马鞍具。苏贝希文明是从狩猎采集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畜牧业生活过渡的文明,因此,苏贝希1号墓地出土的马鞍绝不是西域游牧民族马具的上限,更早的马具只是还有待于考古实物的发现。当然,苏贝希出土的马鞍还较简单,它的外形像两个合并而成的用皮革做的枕套,套内填塞羊毛,更像垫。这种鞍垫不用时可以折叠。从一些出土文物看,大约在西汉末年出现了有鞍桥的马鞍,这才解决了骑手身体在马奔驰跳跃时前后滑动的问题,而苏贝希马鞍还不具备此种功能。自此,马鞍才开始走向定型。此后的马鞍尽管有高鞍桥马鞍、彩绘木马鞍、包银鎏金马鞍等,但马鞍的基本形态并无多大改变。而马镫则完全不同了,它的出现被认为是马具的一次革命,尤其对骑兵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有了马鞍之后,乘骑时不至于前后滑动,但由于没有马镫还不能在马背上自如地进击。“随着马鞍和马镫的发明,士兵们必须学会跨骑在他们的坐骑上挥枪弄剑”①,自此,他们弯弓射箭、挥刀进击更加游刃有余了。早期的马镫为单镫,或是用皮革制成,或是薄薄一片,只作上马时使用。双镫,底部有较宽的镫板,才使马镫具有了更高的使用价值。最早的马镫是斯基泰人用皮革环系在马肚带上的马镫,匈奴人的马镫在公元前3世纪已存在。②见于考古发现的马镫是7~8世纪突厥人的,阿尔泰地区曾出土这类马镫:“马镫有三种。最流行的是8字形马镫,下部较宽,安有平整的踏板;上部较小,是系带的环。——第二种马镫最为简单,呈弧形,上部打平,并凿有系皮带的孔。——第三种类型的阿尔泰马镫最复杂。穿系皮带的眼开在一块铁片上,铁片安在弧形铁顶端专门的‘脚’上,有的铁片相当长。”③这些马镫既有青铜制作的,也有铁制的。有些马镫有镂孔花纹,有的有银嵌纹样。但是有证据表明,在南西伯利亚,早在3世纪的塔施提克时期马镫就普遍使用,这与一些学者认为的“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马镫在各种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中都开始大量出现”④的论断是吻合的。事实证明,以马鞍、马镫等马具为主的游牧文明出现之后,世界文明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革。自此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形成鼎足之势。游牧文明不仅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使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冲突、碰撞中沟通。
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其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及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都直接联系着他们的文化艺术。他们在马背上吟唱着牧歌和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喜庆场合高唱婚礼歌、祝酒歌,并以歌舞相娱;他们的腰带上佩挂有镶嵌对兽猛禽图案的牌饰、带扣、短剑;他们在所迁徙之地雕凿有无数幅岩画;他们还在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座石人像、鹿石;他们还在毡毯上、服饰上飞针走线,留下了流光溢彩的精美图案..他们的艺术无处无时不在,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圆形毡房也富有艺术韵味。
游牧民族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把他们的艺术理念、艺术内容、艺术形式与自然完美地统一起来,他们师法自然,从自然中获得灵感,把对自然的感觉、想象完整地表现在对艺术的理解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最根本的特征。
首先,草原造型艺术都是复功用性的。所谓复功用性是指这些造型绝非“纯艺术”,“而是具有明显程度不同的实用功能的行为—礼仪——巫术功能,或者实践——认识功能,抑或符号——交际功能”。①欧亚草原上的动物纹样,从塞人(西方学者称之为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样到鄂尔多斯风格动物纹样,从岩画到石人无一不是复功用性的。也就是说,这些造型并不是作为纯艺术形象出现的,它们明显具有“行为—礼仪—巫术”功能,这些造型物长久以来并没有从非艺术成分中分离出来。所谓塞人的动物纹样主要表现在衣冠、金首饰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人们把以匈奴为代表的腰带上的金牌饰、马具上的铜钩、钮和长矛柄头牝鹿形象的动物题材统称为鄂尔多斯艺术。但是“按照青铜器艺术品的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和艺术风格,从东至西,大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区系类型:东胡系、山戎系、匈奴系和西戎系等四个青铜器艺术类型”②。其实,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还包括大月氏、乌揭、车师人的此类纹样。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主要来自猎牧民猎牧活动中常见的凶兽猛禽,如狮、虎、熊、鹰、狼、鹿、豺、野猪等,也有驯养的马、牛、羊、狗等形象。特别是一些野兽形象,多为啮咬、争斗状,形体往往扭曲变形。无论是塞人风格的动物纹样还是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绝对不是出于审美需求的艺术装饰,而具有功能意义。他们把动物形象装饰在牌、扣、钩、徽章、矛、剑、马具、带等须臾不离身的物件上是视其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的。塞人的狮神、吐火罗人的双马神(即龙神)、车师人的虎神、匈奴人的神兽、鲜卑人的瑞兽、蒙古人的“白海青”等,或来源于早期氏族图腾,或衍化成部落保护神。鲜卑人的带钩——犀比为瑞兽,即神兽,实际上鲜卑就是以“瑞兽”相称的部落。这种瑞兽,据文献记载是一种像狐狸大小的五爪虎,汉文为区,“因为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的名称;同时把它的形象用在金属带钩上,以自别于其他部落的人民”③。
犀毗、犀比、胥比、师比等都是鲜卑的汉语的不同译音,原意是“神兽”,“最初以之作为带钩型样和装饰母题是很可能的(后来的带钩除部分为几何形外,绝大多数以动物形体造型,尚保持其图腾装饰传统)”。①草原部民的这类动物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早期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以后在普遍存在的萨满教信仰中被信奉为部落保护神了。即使这样,复功用性的动物纹样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草原民族个性和心灵世界的基本表现方式。岩画、石人也是如此。
其次,草原艺术的民间性是它的基本特征。一些最主要的艺术形态,如造型艺术、装饰艺术、歌舞艺术“在传承中积淀凝聚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创作,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定型,它更富于民族普遍性;尤其它产生于现实生活,因而更真实地反映了民族心灵世界、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②我们把草原艺术的这种民间性可称之为民间艺术。这种艺术因弥漫于日常生活中而具有普泛性。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是吟唱诗人和民歌手。蒙古族的长调、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都是全民族性的;这里几乎没有演唱者和听众之分。有时看似是某个歌手、阿肯、玛纳斯奇、江格尔齐在演唱,但是以全民族参与为前提的,从创作到演唱都无法把歌者和听众分开。创作和演唱都与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口承文化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民族中,只有全民性的参与,才能产生这些艺术诸形式。草原民族的民歌演唱更是如此,如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婚礼歌、酒歌、丧葬歌、牧歌、情歌等,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放牧炊饮..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择时择地地演唱不同的民歌,而且不少是即兴演唱。我们还不难发现,游牧民族的毡房、马具、服饰、毡毯都富有装饰性,特别是讲究以自然界的花草、动物角等抽象变形对称装饰,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搭配色彩,这种色彩搭配往往反差强烈,色泽艳丽。装饰用具、美化生活几乎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存在没有装饰的生活,也不存在离开生活的装饰。如果细细列举,诸如手帕、荷包、头巾、枕头、腰巾、围裙、毡帽、毛袜、领口、袖头、衣襟、裤角、被面、垫褥、罩单、帷帘、壁挂、壁围、花毡、织毯、草帘、编带、马褥、披肩等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恰到好处的纹样和色彩加以装饰美化。一些几何及植物纹样装饰图案的出现不能单纯归因于某些游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致。其实,这类装饰性图案起源很早,不亚于动物纹样。在塞人金银器中,汉代匈奴织物中除动物纹样主题外,同样有花纹、三角形、圆形等装饰性图案,似乎都不是写实风格的。
最后,草原艺术中的一些类型是出于象征的、代表的意义创造的。象征起源很古老。先民总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人类的祸福,故经常观察会不会出现反常的物象,又进而预测是否有什么征兆。象征中的那些具象大于观念的意象除留有先民们的图腾逻辑和泛灵论的印记外,还可以从具象产生的现实土壤中寻求答案。游牧民族几乎天天处在高山、河流、草原之中,所见到的几乎全是野兽和他们放牧的马、牛、羊,以及山川、天地、草木,于是草原艺术家从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中取象,因物触感,因象生意,故他们的艺术充满了象征意味。艺术至少在四种不同途径上是符号性的:一是艺术在它直接转达意思时可以具有符号性;二是艺术的符号性还体现在它们是情感和意义的反映;三是符号层次可以在艺术所反映的某种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等等原则中见到;四是艺术的符号是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更深的变化过程有关的。①马里安界定的艺术的符号性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象征意味是十分明显的。譬如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往往采用复式结构,以字少腔长的方式表达一种深沉、悲壮、雄浑、沉郁的情感。马头琴等乐器的配合演奏“则暗示着特定的物质或情感现象,甚至乐音特殊组合的选择也可以而且确实象征了存在物的特定状态”。②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中还常见一种模仿性舞蹈,如《斗熊舞》、《鹰舞》、《擀毡舞》、《挤奶舞》、《走马舞》等不能仅仅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还表达了某种态度和情感。草原民族的音乐、舞蹈有时在揭示意义上是隐喻性和含蓄的。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之为隐喻性象征和暗示性象征。
草原是游牧文化的广阔舞台,骏马和歌喉是游牧民族的双翼,它们铸就了草原之子豪放之气和豁达性格。所有的草原艺术因此而发生、发展、演进。只要草原存在,马背民族的艺术就会生生不息。
活动于西域北部草原的这些游牧部落具有与绿洲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绿洲农耕民族无论是凿渠引水,还是开荒垦殖,始终把自己放在征服自然的位置上。而草原游牧民则不然,他们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水草牧场给游牧民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不动产”,而放牧于兹的马、羊、牛则是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他们的“动产”。游牧民族与大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所以“游牧民族尽管其种族、肤色、语言有差别,但其劳动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却都相同。这种共性本质,就在于游牧社会都是在:水草牧场〓牲畜〓游牧劳动——这三种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无论是游牧父权氏族社会、游牧奴隶制和游牧封建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畜牧业生产,都是在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生成发展的,只是这些不同阶段的对象性关系的性质和对象化活动形式不同罢了”①。这三种对象性关系看似简单,其实含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冬夏牧场的选择,草原对牲畜的负荷量,牲畜的繁殖、放牧、驯养,奶制品、日常生活器皿的制作及毡房的搭建,冬夏服装的缝织,人生和节日礼仪、文化娱乐生活等行为仪式和精神追求等等莫不如此。这里,往往是经济动机和文化意识纠葛在一起,游牧生活充满文化意味,而文化意味则在展示他们的审美感觉、艺术想象和表现形式及创作思维。
在游牧生产、生活活动中举足轻重的是坐骑——马。游牧民族之所以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和马联系在一起。整个游牧社会是依赖马在维系,马是坐骑,马是交通工具和征战工具,迁徙游牧、四方征战、闲暇游戏,马以人为主,人以马当伴。在游牧民族眼里,马是有灵性、通人性的,于是赋予马以各种人文含义。当然,马背民族对马的钟爱是从驯马开始的。欧亚大草原正是人类第一次驯服马的摇篮:“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之间,生活在亚洲大草原边缘上的某个民族或者某几个民族,在已经掌握了牛和羊的习性的基础上,培养出第一批家养马的品种。”②自此,马与游牧民族之间便存在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人类学家们已经在设法复现马在这些最早的马背文化中的作用。我们研究过诸如雅库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这样的中亚游牧民族,他们直到最近还保持着祖先的很多生活方式。这些游牧者的整个生存都依赖于马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把马作为食物,而且还因为马使他们在大草原为他们提供的稀疏的自然牧场上放牧牛羊成为可能。在那个风多树少的环境中,他们惟一的生存之路就是使牛羊散布在方圆数百里的地方,让它们不停地寻找水草。在靠近欧洲的西部,雨量充沛,牧草比较丰美,马背游牧民养的牛比羊多。而在靠近蒙古的东部,半沙漠的环境比较普遍,那里的牧民养的羊比牛多。在这两种情况下,马的贡献都在于它的流动性,它使其主人能够照料广泛散布的畜群,它可以迅速移动以抵御来自那些专好偷窃别人牲畜的敌对邻邦的威胁。”①从一定意义上说,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马背民族的文化。盘马弯弓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熟谙养马之术,精于骑射,养成骁勇善战、豪放不羁的品格。哈萨克人将马称为“百畜之王”,认为“马是人的翅膀”。他们在长期的养马实践中对马的毛色、品种、禀性、体态、姿势等特征了如指掌,并形成丰富的相马经验。曾有哈萨克族学者对有关马的各方面特征的词汇作过统计:
哈萨克过去的语言中,有关马的毛色的名称(词汇)有350种之多——从大的方面虽然分为Baran(深色)和qelang(浅色)两种,然而从小的方面却分得异常精细,例如,枣骝类有23种;棕黄色22种;黑马32种;黄色28种;灰白色15种。还有吉祥和非吉祥的颜色名称。吉祥的有:黑耳朵马、白鼻子马、花白腿马、白腿马等等;非吉祥的有:灰眼睛马、白头马、月形白鼻梁、白嘴马等等。仅用于形容马走的姿势的词汇就有30多个,而有关骏马标志的形容词则有约100个,比如,用于说明马的年龄的专有名词就有25个;而有关马的性别的词有15个;有关马群的特点的词汇有10个;有关母马的各种禀性的词汇有17个,而根据母马的产奶情况而对此加以说明的词汇有11种;而将母马的乳房特点分为14类并且用不同的专有名词加以说明;根据产奶量来为马进行分类的词汇有7个;用于形容马的神态的词有6个;刚配群的3岁马分为36种,并用36种词加以说明;公马分为13种;骟马分为7种;离群的马分为12种(有12种名称);小马驹有16种名称;根据马的牙的特点分为17类;而用于说明母马、公马和一般骟马的“中性”词则有约30种;用于说明马的属性的词汇有100个左右;仅用于说明马走和跑的姿势特征的词有30种。而用于马的有关性别、年龄、体形、性等方面的特征和形象的词汇(专有名词)有600多个。②
由马及人、及物,在哈萨克族中还有不少部落名称、地名、人名也是与马有关的,如果一一列举,简直就是一本马文化辞典。
相马、养马不仅构成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与他们的政治、军事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蒙古人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西征,靠的就是兵民合一的部落兵制:“为了弥补长期战争的人员消耗,蒙古统治者将15岁以下的儿童编成‘渐丁军’(意思是‘渐长成丁军’),作为蒙古军队的后备力量。
孩子到3岁时,就将他直接‘索维’在马鞍上,让他手里拿着器械,骑马任意奔驰,四五岁时就在马上练习弓箭,再大一点便经常参加狩猎。十五六岁便参加正式作战。北方民族在战争期间广泛实行自备鞍马粮草兵器的兵役制度。”①从小与马为伍,以马为友,焉能不与马产生感情?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背就是他们的家,马背承负着整个民族的荣辱兴衰。游牧民族一旦离了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马鞍、马镫的发明更使他们如虎添翼。
世界上最早的马鞍、马镫诞生于何时何地,已无实物可考,但在新疆鄯善县属战国时期的苏贝希墓群1号墓地出土了包括马鞍在内的一系列马具。这套马具包括马鞍、马络、绞具、衔、镳、肚带。马鞍用毡皮合制。鞍两侧的四角各有数条皮绳,做捆扎猎物之用。桃形、S形骨带扣用来固定前、后鞧的革带。②这是现知的我国最早的马鞍具。苏贝希文明是从狩猎采集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畜牧业生活过渡的文明,因此,苏贝希1号墓地出土的马鞍绝不是西域游牧民族马具的上限,更早的马具只是还有待于考古实物的发现。当然,苏贝希出土的马鞍还较简单,它的外形像两个合并而成的用皮革做的枕套,套内填塞羊毛,更像垫。这种鞍垫不用时可以折叠。从一些出土文物看,大约在西汉末年出现了有鞍桥的马鞍,这才解决了骑手身体在马奔驰跳跃时前后滑动的问题,而苏贝希马鞍还不具备此种功能。自此,马鞍才开始走向定型。此后的马鞍尽管有高鞍桥马鞍、彩绘木马鞍、包银鎏金马鞍等,但马鞍的基本形态并无多大改变。而马镫则完全不同了,它的出现被认为是马具的一次革命,尤其对骑兵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有了马鞍之后,乘骑时不至于前后滑动,但由于没有马镫还不能在马背上自如地进击。“随着马鞍和马镫的发明,士兵们必须学会跨骑在他们的坐骑上挥枪弄剑”①,自此,他们弯弓射箭、挥刀进击更加游刃有余了。早期的马镫为单镫,或是用皮革制成,或是薄薄一片,只作上马时使用。双镫,底部有较宽的镫板,才使马镫具有了更高的使用价值。最早的马镫是斯基泰人用皮革环系在马肚带上的马镫,匈奴人的马镫在公元前3世纪已存在。②见于考古发现的马镫是7~8世纪突厥人的,阿尔泰地区曾出土这类马镫:“马镫有三种。最流行的是8字形马镫,下部较宽,安有平整的踏板;上部较小,是系带的环。——第二种马镫最为简单,呈弧形,上部打平,并凿有系皮带的孔。——第三种类型的阿尔泰马镫最复杂。穿系皮带的眼开在一块铁片上,铁片安在弧形铁顶端专门的‘脚’上,有的铁片相当长。”③这些马镫既有青铜制作的,也有铁制的。有些马镫有镂孔花纹,有的有银嵌纹样。但是有证据表明,在南西伯利亚,早在3世纪的塔施提克时期马镫就普遍使用,这与一些学者认为的“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马镫在各种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中都开始大量出现”④的论断是吻合的。事实证明,以马鞍、马镫等马具为主的游牧文明出现之后,世界文明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革。自此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形成鼎足之势。游牧文明不仅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使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冲突、碰撞中沟通。
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其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及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都直接联系着他们的文化艺术。他们在马背上吟唱着牧歌和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喜庆场合高唱婚礼歌、祝酒歌,并以歌舞相娱;他们的腰带上佩挂有镶嵌对兽猛禽图案的牌饰、带扣、短剑;他们在所迁徙之地雕凿有无数幅岩画;他们还在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座石人像、鹿石;他们还在毡毯上、服饰上飞针走线,留下了流光溢彩的精美图案..他们的艺术无处无时不在,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圆形毡房也富有艺术韵味。
游牧民族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把他们的艺术理念、艺术内容、艺术形式与自然完美地统一起来,他们师法自然,从自然中获得灵感,把对自然的感觉、想象完整地表现在对艺术的理解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最根本的特征。
首先,草原造型艺术都是复功用性的。所谓复功用性是指这些造型绝非“纯艺术”,“而是具有明显程度不同的实用功能的行为—礼仪——巫术功能,或者实践——认识功能,抑或符号——交际功能”。①欧亚草原上的动物纹样,从塞人(西方学者称之为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样到鄂尔多斯风格动物纹样,从岩画到石人无一不是复功用性的。也就是说,这些造型并不是作为纯艺术形象出现的,它们明显具有“行为—礼仪—巫术”功能,这些造型物长久以来并没有从非艺术成分中分离出来。所谓塞人的动物纹样主要表现在衣冠、金首饰及驾具和马具上的附属物等方面。而人们把以匈奴为代表的腰带上的金牌饰、马具上的铜钩、钮和长矛柄头牝鹿形象的动物题材统称为鄂尔多斯艺术。但是“按照青铜器艺术品的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和艺术风格,从东至西,大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区系类型:东胡系、山戎系、匈奴系和西戎系等四个青铜器艺术类型”②。其实,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还包括大月氏、乌揭、车师人的此类纹样。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样主要来自猎牧民猎牧活动中常见的凶兽猛禽,如狮、虎、熊、鹰、狼、鹿、豺、野猪等,也有驯养的马、牛、羊、狗等形象。特别是一些野兽形象,多为啮咬、争斗状,形体往往扭曲变形。无论是塞人风格的动物纹样还是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绝对不是出于审美需求的艺术装饰,而具有功能意义。他们把动物形象装饰在牌、扣、钩、徽章、矛、剑、马具、带等须臾不离身的物件上是视其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的。塞人的狮神、吐火罗人的双马神(即龙神)、车师人的虎神、匈奴人的神兽、鲜卑人的瑞兽、蒙古人的“白海青”等,或来源于早期氏族图腾,或衍化成部落保护神。鲜卑人的带钩——犀比为瑞兽,即神兽,实际上鲜卑就是以“瑞兽”相称的部落。这种瑞兽,据文献记载是一种像狐狸大小的五爪虎,汉文为区,“因为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的名称;同时把它的形象用在金属带钩上,以自别于其他部落的人民”③。
犀毗、犀比、胥比、师比等都是鲜卑的汉语的不同译音,原意是“神兽”,“最初以之作为带钩型样和装饰母题是很可能的(后来的带钩除部分为几何形外,绝大多数以动物形体造型,尚保持其图腾装饰传统)”。①草原部民的这类动物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早期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以后在普遍存在的萨满教信仰中被信奉为部落保护神了。即使这样,复功用性的动物纹样仍不失其艺术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草原民族个性和心灵世界的基本表现方式。岩画、石人也是如此。
其次,草原艺术的民间性是它的基本特征。一些最主要的艺术形态,如造型艺术、装饰艺术、歌舞艺术“在传承中积淀凝聚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创作,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定型,它更富于民族普遍性;尤其它产生于现实生活,因而更真实地反映了民族心灵世界、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②我们把草原艺术的这种民间性可称之为民间艺术。这种艺术因弥漫于日常生活中而具有普泛性。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是吟唱诗人和民歌手。蒙古族的长调、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都是全民族性的;这里几乎没有演唱者和听众之分。有时看似是某个歌手、阿肯、玛纳斯奇、江格尔齐在演唱,但是以全民族参与为前提的,从创作到演唱都无法把歌者和听众分开。创作和演唱都与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口承文化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民族中,只有全民性的参与,才能产生这些艺术诸形式。草原民族的民歌演唱更是如此,如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婚礼歌、酒歌、丧葬歌、牧歌、情歌等,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放牧炊饮..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择时择地地演唱不同的民歌,而且不少是即兴演唱。我们还不难发现,游牧民族的毡房、马具、服饰、毡毯都富有装饰性,特别是讲究以自然界的花草、动物角等抽象变形对称装饰,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搭配色彩,这种色彩搭配往往反差强烈,色泽艳丽。装饰用具、美化生活几乎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存在没有装饰的生活,也不存在离开生活的装饰。如果细细列举,诸如手帕、荷包、头巾、枕头、腰巾、围裙、毡帽、毛袜、领口、袖头、衣襟、裤角、被面、垫褥、罩单、帷帘、壁挂、壁围、花毡、织毯、草帘、编带、马褥、披肩等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恰到好处的纹样和色彩加以装饰美化。一些几何及植物纹样装饰图案的出现不能单纯归因于某些游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致。其实,这类装饰性图案起源很早,不亚于动物纹样。在塞人金银器中,汉代匈奴织物中除动物纹样主题外,同样有花纹、三角形、圆形等装饰性图案,似乎都不是写实风格的。
最后,草原艺术中的一些类型是出于象征的、代表的意义创造的。象征起源很古老。先民总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人类的祸福,故经常观察会不会出现反常的物象,又进而预测是否有什么征兆。象征中的那些具象大于观念的意象除留有先民们的图腾逻辑和泛灵论的印记外,还可以从具象产生的现实土壤中寻求答案。游牧民族几乎天天处在高山、河流、草原之中,所见到的几乎全是野兽和他们放牧的马、牛、羊,以及山川、天地、草木,于是草原艺术家从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中取象,因物触感,因象生意,故他们的艺术充满了象征意味。艺术至少在四种不同途径上是符号性的:一是艺术在它直接转达意思时可以具有符号性;二是艺术的符号性还体现在它们是情感和意义的反映;三是符号层次可以在艺术所反映的某种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等等原则中见到;四是艺术的符号是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更深的变化过程有关的。①马里安界定的艺术的符号性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象征意味是十分明显的。譬如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往往采用复式结构,以字少腔长的方式表达一种深沉、悲壮、雄浑、沉郁的情感。马头琴等乐器的配合演奏“则暗示着特定的物质或情感现象,甚至乐音特殊组合的选择也可以而且确实象征了存在物的特定状态”。②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中还常见一种模仿性舞蹈,如《斗熊舞》、《鹰舞》、《擀毡舞》、《挤奶舞》、《走马舞》等不能仅仅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还表达了某种态度和情感。草原民族的音乐、舞蹈有时在揭示意义上是隐喻性和含蓄的。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之为隐喻性象征和暗示性象征。
草原是游牧文化的广阔舞台,骏马和歌喉是游牧民族的双翼,它们铸就了草原之子豪放之气和豁达性格。所有的草原艺术因此而发生、发展、演进。只要草原存在,马背民族的艺术就会生生不息。
附注
①〔美〕朱学渊.论欧亚草原上的通古斯族.世界民族.1999(4).
①满都夫.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文艺研究.1998(1)
②〔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东画报出版社,2001.96.
①〔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96~97.
②卡哈尔曼·穆汗.哈萨克历史文化中马的形象.西域研究.1998(2).
①杭侃.草原民族的马背生活.文物天地.2002(2)
②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鄯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3善.(4).
①〔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00.
②〔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25页.
③〔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铅印本.98.
④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96.
①莫·卡冈著.凌继光等译.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190.
②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380.
③包尔汉,冯家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历史研究.1956(10).
①肖兵.犀比·鲜卑·西伯利亚——从《楚辞·二招》描写的带钩谈到古代文化交流.人文杂志.1981(1).
②满都夫.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文艺研究.1998(1).
①〔美〕阿兰·P.马里安.艺术与人类学.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1~303.
②〔美〕阿兰·P.马里安.艺术与人类学.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2.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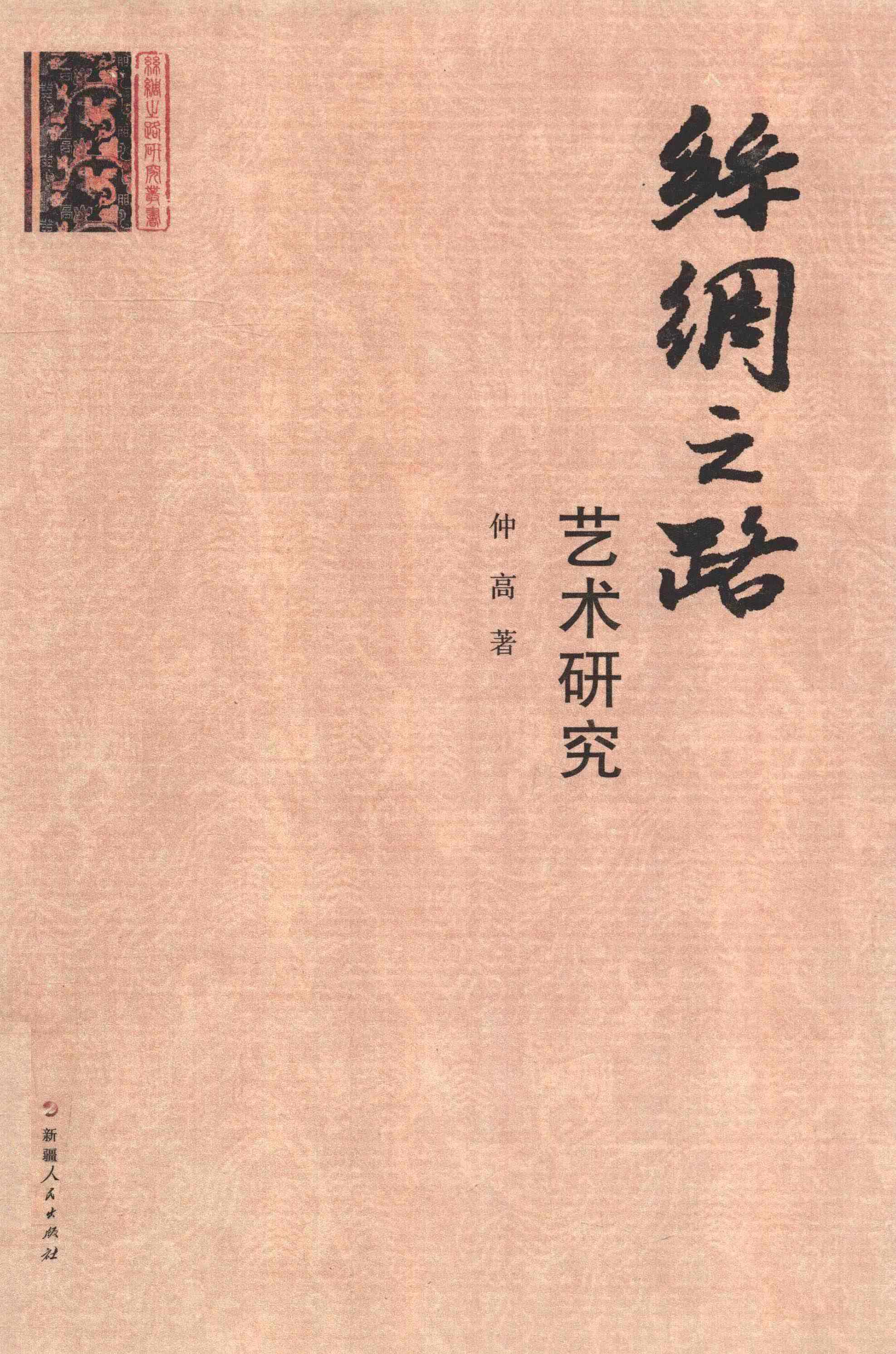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