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丝绸之路艺术人文初曦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20 |
| 颗粒名称: | 第三章 丝绸之路艺术人文初曦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33 |
| 页码: | 71-103 |
| 摘要: | 本章记述的是丝绸之路艺术人文初曦情况包括人体装饰与原始审美意识、彩陶:有意味的形式、女性雕像的地母情结等。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艺术 初曦 |
内容
第一节 人体装饰与原始审美意识
人类何时开始进行人体装饰,已无案可稽,人类学家往往根据现代原始部落民的人体装饰推演人类早期的人体装饰,由此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有人认为:“原始民族的画身(即绘身),主要目的是为美观。”①也有人认为人体装饰就是装饰艺术中最重要、最普遍也最能揭示装饰艺术本质规定性的一种。②虽然审美观念在改进和发展人体装饰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审美观念不是发生人体装饰的原始动机。人体装饰的起源是先民出于功利性目的,也就是说,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并非像现代人那样纯粹是非功利性的艺术审美行为,而是基于原始思维的功能性活动,往往伴随着巫术操作过程。
从考古发现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提供的证据看,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分绘身、文身和人体饰物三大类,而人体饰物则又有头饰、发饰、颈饰、胸饰、手饰、腰饰、脚饰等数种。史前先民人体装饰的动机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形式,如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装置鼻饰时,在西域史前先民中则不存在这类装饰。西域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主要见于考古发现。由于西域干早少雨,一些古尸保存相当完好,能看到人体上的绘身和文身。人体装饰物出土较多,天山以南、以北地区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1)头饰、发式,有发辫、发网、冠饰、发笄等;(2)颈饰,有石、玉、骨、铜、金、琉璃、玛瑙、象牙、草果、珊瑚质串珠;(3)耳饰,骨、铜、金、银质耳环、耳坠;(4)眼饰,眼皮金箔和描眉;(5)胸饰,衣服上片饰、坠饰等;(6)手饰,骨、铜、金、银戒指和手镯以及手指甲涂红等;(7)腰饰,腰际环绕骨管等;(8)脚饰,脚趾甲涂红、脚环等。人体装饰物出土的墓葬大约距今4000~2000年不等。文化人类学家把人体装饰按其性质分为两大类:“(一)固定的:即各种的永久性的戕贼身体的妆饰,如瘢纹、黥涅及安置耳鼻唇饰等。(二)不固定的:即以物暂时附系于身体上的妆饰,如悬挂〓带条环等。另有‘绘身’,一种似乎介于两者的中间,且像是最早的妆饰。”①绘身、文身是在西域史前先民中常见的人体装饰;“黥涅”,即黥刺也就是文身,见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中:“扎滚鲁克墓地一些干尸胳膊上见有黥刺文身者,纹样呈不规则三角纹等。”②见于晚期文献的是关于突厥人“以刀〓面”习俗的记载,《周书·突厥传》载,突厥人在亲人死去后往往“以刀〓面,且哭,血泪俱流”。这种“〓面”自然与“美观”无关,只是以自戕的极端手段沉痛悼念死去亲人的方式而已,也不过是用刀留下“瘢痕”,而非文身。
笔者赞同林惠祥先生关于绘身是最早装饰的说法。由于绘身(即画身)易于褪落,才有了文身这种留于身上耐久不灭的方式。绘身不同于文身,绘身是用各种涂料,如植物、矿物染料,泥土、血液、油脂等在裸露的体表涂抹或描绘,“画身(即绘身)的习惯,在低级文化中最为普遍”③。而文身,即先刺文,然后“是用研细的炭粉,渗入皮下,等到发炎过后,那嵌入的花纹就显出一种永不褪落的深蓝颜色”④。绘身中用的最多的是红色。从新疆出土的干尸中很容易区别什么是绘身,什么是文身。扎滚鲁克2号墓“共葬四个个体,一男三女,男尸为侧身屈肢,身着毛织布上衣,..圆脸高鼻,从脸部看似有文身,其图案似羊角状,头发半白,编成两根辫子,..辫梢加有红毛线;脚穿毛毡长袜,外套白鹿皮长靴。三具女尸,两具已不完整。一具女尸身着过膝的棕红色套裙,也有文身,其纹饰也似大盘羊角状,辫发四根..”⑤该文在此所说“文身”实为绘身。另一则绘身的干尸出土于鄯善县的苏贝希墓葬:“M2中出土一个男性干头颅,面部饰有彩绘,前额正中两竖道,两颊分别有两横道。说明彩纹是在死者埋葬前临时画上的,在实施过程中,应举行过某种宗教仪式。”①苏贝希墓葬被认为是车师人的墓葬,距今约2500年左右,稍晚于扎滚鲁克。尉犁县营盘遗址墓葬的古尸中也有绘面现象。而文身,考古发现不多,仅在洛浦县山普拉M01号墓葬和哈密五堡墓地中发现文身:“个体的肢体已分离,性别不清。山普拉为刺青在带干皮肉的拇指指背上,蓝色,图案有点像人形。”②M01号墓的年代距今约2000年,又晚于苏贝希墓葬的年代。哈密五堡墓葬中的手文见于右手手背、腕部,黥有蓝色花纹。③距今3000年左右。至于用什么颜料绘身,可以从苏贝希一号墓中的眉石去求证。眉石实际上是将矿石磨成粉末,并将粉末用于绘面的用具。眉石见于一女性身旁的一小皮袋内,“同一个皮袋中还装有角梳,黑、红、白三种矿物染料,染料缺口有磨出的沟槽,其作用非常明白,当为化妆用具。以眉石将矿石磨成粉末,如需要可分别涂抹在眉毛、脸颊和面部,起到与眉笔、胭脂、粉相同的作用”④。阿尔泰距今2500年左右的巴泽雷克一、二号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也有文身、绘身现象。一号墓男主人身上刺着家猫一样的动物,有翅,另一动物则为鹿身鸟嘴猫尾。二号墓男主人的手、胸、背和脚上都绘有真实和幻想的动物形象。⑤这些绘身、文身究竟有什么含义?综合各种文化人类学、民族志材料,绘身现象常见于以下活动和行为方面:A.举行入社、成丁礼时;B.作为氏族或集团的图腾标志时;C.参加舞蹈、庆典类活动时;D.作战、血亲复仇时;E.祛邪禳灾时;F.丧葬、举哀仪礼时;G.美观装饰,以期艳丽入时。⑥
文身现象则见于如下活动和行为:A.进行入社、成丁仪礼时;B.作为氏族或集团图腾标志,表示氏族差异,表现群体敌我时;C.显示社会或阶级分层,即等级、地位、身份是否显赫、尊贵时;D.在重大活动,如作战、血亲复仇等前后昭彰坚毅与勇武、耐力与无畏时;E.祛邪禳灾,消蠲祸患时;F.丧葬、举哀仪礼时;G.展示美艳丽姿,追求雄健魁伟时。⑦
在所有这些解释中,追求美观说是最便捷和最不费力的,但也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因为这类假说往往以现代人的审美观去审视史前先民的绘身、文身,使人不得要领。其他若干项解释都有合理的理由,但作为临时性的绘身和永久性的文身可能有不同的功能。诸如入社、成丁礼、庆典、葬仪等仪式中常以绘身方式隐喻一种象征意义,而作为永久性的文身,大概与图腾标志、等级、身份、地位有关,而等级、身份、地位标志是后起的因素。
从扎滚鲁克、苏贝希、营盘、巴泽雷克等墓葬干尸的绘身看,有一些共同现象。一是绘身主要在面部,颜色以红色为主,即为赭石颜料。这种赭石的作用“用以象征鲜血,因而也象征生命,尤其是死者的生命”①。以赭石为颜料涂饰墓穴、绘身的习俗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相当普遍,而且在洞穴壁画中也广泛使用。何以赭石色绘于面部象征死者的生命,勒鲁瓦·古昂解释道:“在格里曼底的卡维荣发现的墓葬独特奇异,是个绝无仅有的实例:一条长18厘米的皱痕涂上赭石颜料,由口鼻部向外延伸。由此到将赭石颜料比作生命的气息或说话的声调,仅一步之差,尤其是因为在马格德林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中,好些动物也画有这种从口鼻部延伸的线条,并被看成是呼吸的表现,所以这一步就更加诱人跨越了。”②无论是扎滚鲁克干尸面部的羊角纹,还是苏贝希干尸面部的横、竖道都从口鼻部延伸到颧骨两颊和闭合的眼目等面部的各个部位,似乎都与呼吸表现有关,应是死者灵魂不灭、生命永续的象征。二是这些绘身均是在人死后临时绘于面部的,显然与丧葬习俗有关。实施绘身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巫术操作,这种巫术主要实施于头部,因为史前先民“在人造的祖先像外,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也作为含有‘灵魂力量’之物而受到崇拜”③,在此,“死去的灵魂”和“活人的灵魂”不能等同,所以绘面只有在人死后才实施,先民相信这种用赭石绘面的巫术是可以安抚死者灵魂的。新疆古代墓葬中的干尸文身仅见于手部、腕部,显然都是生前黥刺的。究竟是成丁礼时文上的,还是获取战功后文上的或是作为等级、地位、身份的标志绘上的,现在还不好妄下断语,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巴泽雷克墓葬中男主人所绘、所文的飞禽走兽组合形象或许就是萨满通神的动物精灵。虽然新疆、中亚地区发现的绘身、文身晚出,但它的起源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史前先民的各种人体装饰物是最容易使人产生“原始艺术”的遐想的。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大量的发现表明贝壳充当了饰品的构件,镶嵌在头饰或颈饰以及手镯或脚镯上”④。不过新疆出土的人体饰物最早为新石器时代,晚至铁器时代。按其年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石、草果、骨、角、牙等为主;第二个阶段以玉、琉璃、玛瑙珠、珊瑚等为主;第三个阶段以铜、金、银为主。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晚期的墓葬中除铜、金、银人体饰物外,同样有石、骨、玉、草果等饰物出土。但早期的遗址中不见铜、金、银等饰物,只有石质饰物。吐鲁番阿斯塔那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物主要是石器和彩陶,其中出土的两件穿孔砾石坠是新疆发现的最早人体饰物了。第一个阶段表明雕、磨、刻、琢等加工技术日益成熟,而到第三个阶段的铜器时代,金属的锻、铸等工艺使铜、金、银等饰物更加精致、精巧化。西域的这些饰物无外乎头部(头发、额前、眼、耳、唇、颈)、腰部(兼及胸部)和四肢(主要是手腕和脚腕)这三个部位。
头饰包括发饰、眼饰、耳饰、颈饰等活动装饰。头部,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尊崇的,只是在人类的狩猎采集阶段,由于头发随意生长,常披到额前挡住视线,很不便于追逐猎物和采集果实,所以只好随便捆扎或辫起了,这完全是一种迫切的实际需要。有了修剪工具和氏族图腾的出现,才赋予头饰更多的含义,甚至与巫术有关,以后又演变成以头饰为主的习俗,后者当然是一种审美需求。发辫是西域史前先民常见的头饰,有单辫、双辫、多辫之分。阿拉沟竖穴木棺墓为战国—西汉时期墓葬,女主人黑褐色头发,“其辫式是先将头发分成若干股(此辫为25股),用5股辫成一辫,然后将辫好的5辫,又相辫成一大辫”①,此为多股单辫,与苏贝希死者发型相同。扎滚鲁克墓葬2号墓中墓主为一老年妇女,头发灰白,两条发辫从耳后垂下,系有红毛线头绳,有描眉、绘前额痕迹。墓葬距今3000年左右。②民丰东汉墓为男女合葬墓,女尸头发为多辫。这种辫发习俗可能和年龄有关,现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婚前往往依年龄梳成同等数量的辫发,而婚后则为单辫或双辫。史载,突厥等游牧部族“其俗被发左衽”,其实“被发”、“披发”、“编发”通指“辫发”。西域史前先民的辫发之俗对后世民族肯定是有影响的。与发式相伴的是发饰,常见的是发网和冠饰。苏贝希3号墓地距今2500年左右,“M6:B女性老年,仰身屈肢..头戴黑毡卷成的牛角状冠饰,头发盘卷其上,外套圆盘形发网,以黑色毛线织成,头顶中间栽植一高帽状毡棒,下端较粗,用毛绳系于颅上,外面也套以黑发网,耸立于颅顶中央,甚为别致”③。M8:A成年女性也同样以双辫盘于头顶,用黑发网罩和冠饰。西域先民的辫发之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孔雀河下游北岸距今3800年前的古墓葬中出土的木制女俑,其头饰为梳短辫,垂于颈后。④该墓葬中男性死者头戴尖顶毡帽,上插禽鸟翎羽。苏贝希墓葬中头部牛角状冠饰与孔雀河古墓中死者头戴尖顶帽是否有同样含义,值得探究。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奇异的圆锥形盖头物,长期以来起过神秘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已失去尊严的意义,而获得了魔术的意义。”①越是在史前,发饰同帽子一样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巫术性’物品”②。“人体装饰不仅见于眼、眉、耳等头部,而且还见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孔雀河古墓沟死者“腕、腰、颈部,见玉、骨、珠饰”“颈、腕部围饰骨、玉质串珠,腰际环绕骨管”,③在此之后的墓葬中屡屡出土这,类人体装饰品。木垒县距今3000年的古墓葬死者耳佩铜耳环,颈戴石串珠;焉不拉克古墓葬中出土多件石、骨、铜串珠和金耳坠,此墓葬距今3000年左右;察吾乎沟口1号和4号墓被认为是距今3000~2500年间的墓葬,人体装饰物质地为石、骨、铜、金等饰品,装饰在女性的颈、手、耳等部位,多者一串骨珠有100多个,还有三个金耳环,5号墓出土牙饰,可能是以动物牙穿孔而成的项链;在发掘的距今2500年前的帕米尔高原40座古墓中出土有石串珠、骨串珠、玛瑙珠和铜、金质饰物,有手镯、耳环、戒指等,特别是铜质饰物有镂孔片饰、梯形片饰、羊角形饰、凹字形饰等;伊犁河流域古墓葬也多出土骨珠、骨环、铜耳环、铜笄、石串珠等。这些人体装饰物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地区跨越4000~2000年间的各类墓葬中,且以头部装饰物居多,如耳坠、耳环、项链等,而且均是女性,只有眼部装饰物发现于男性死者的眼、眉部。民丰县东汉墓葬中男性死者的“右眉和右眼皮上,各放着一小块金片。金片很不规则,也不像是完整的器物”,而女性死者颈戴项珠,为珊瑚石和琉璃质地。④从随葬物看,墓主人是地位显赫者,应属当地贵族。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眼睛以上部位的装饰更多的是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功绩相联系,并更多的具有宗教和巫术的意义的话,那么,眼睛以下各部位,包括耳、鼻、唇、颈、胸、腰的装饰,就更多地是出于性吸引和性选择的动机。”⑤这种论断可能有简单化之嫌。
腰饰、胸饰和四肢装饰虽不及头饰普遍,但也是人体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先民的腰饰早期是腰际环绕骨管,以孔雀河古墓沟墓葬为早期发现,之后在塞人等游牧部落的墓葬中出土铜、金、银质带扣、带钩,也是腰饰之一种。几乎所有的古代游牧部落均使用这种带钩,而最早使用带钩的是塞人,之后,鲜卑、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使用,全都雕饰有动物纹样,前者被称为“斯基泰艺术”,而后者则称之为“鄂尔多斯”风格。对于两者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匈奴式、鲜卑式乃至战国式带钩的形制可能来自异域,纹样武饰也接受了一定外来影响,但是其母题和基本构思却主要是独立的,自成体系和别具传统的。”①鲜卑人的“郭洛带”就是“瑞兽之带”,他们以源自氏族图腾的“神兽”铸镂带钩之上,塞人、匈奴、东胡等游牧部落的兽形带钩也与此同,“绝大多数以动物体造型,尚保持其图腾装饰传统”②,后演变为部落保护神。胸饰多坠挂于衣物上,距今3000年左右的木垒县古墓葬“墓主身穿皮、毛类衣服,胸前挂海贝、串珠,背后、手臂服装上缝有扣形和锥形卷饰件”③。苏贝希3号墓地M25:A墓主为“男性成年,仰身直肢,头戴有护耳的毡帽,..上衣羊皮袄,腰系皮带,上挂药袋、刀鞘等物,无内衣,胸口戴一梯形皮质护身符,其上绘火焰纹和穷曲纹”④,其年代稍晚于木垒县古墓葬。从年代和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这两处均为车师人的墓葬,胸饰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特征。新疆近代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都有佩戴胸饰的习俗,如柯尔克孜族青年女子的坎肩就缀有银质饰物及胸花等,有的缀有几排银币或银扣子,有的还佩戴铸有花纹的圆银片。⑤对于近代游牧民族的胸饰功能,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装饰美或吸引异性注意,也有人认为是炫耀财富。不过古代先民的胸饰总免不了某种宗教含义——往往成为祛魔避邪的护身符。正如汉文文献所言,君子佩玉是为了“以示不祥”、“在宝石或玉成为人类的装饰品以前,是被作为信仰的对象而用来做护身符用的”。⑥大概西域先民的胸饰、颈饰、腰饰、脚饰、手饰等都有这种功能,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装饰物材料质地发生了变化。但戒指、手镯等首饰原初的功能也并非如现代一样是爱情的信物,它们同胸饰等一样起着护身符的作用。这些人体饰物向装饰、审美发展,才逐渐脱离了功利性目的。
史前的这些人体装饰是否也折射着先民的原始审美心理呢?答案是肯定的。“乍一看,原始艺术品从未为审美原因而制造和使用,而是为了宗教和魔法的目的。..然而,恰恰相反,..原始艺术的这种情形要比它初看时复杂得多,通过更详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那种认为原始艺术品的制造和使用行为中完全不存在审美因素的说法存在不少疑窦”①,情形也正如此。绘身所用的赭石固然因其红色有象征生命的意义,但红色也给人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因为红色比较容易从矿物中获取,又特别鲜亮、明快,用红色绘身,客观上有装饰作用,深受史前先民喜爱,也反映着他们在色彩选择上的审美意识。先前先民还注意选取满足视觉、听觉等感官需要的各类材料作为人体装饰物。首先,如耳饰、腰、胸饰、四肢装饰都是一些发出悦耳响声的材料,有石珠、琉璃、玛瑙、骨环、金属饰物等。即使从避邪功能而言,丁当作响的饰物也足以吓退妖魔等恶精灵。其次是闪闪发光的,“在原始人的眼光中,再没有比发光的物件更有装饰价值的了”②。石珠、琉璃珠、玉珠、金、银、铜耳环、戒指、项饰、胸饰都是闪闪发光的。对闪光材料的选择绝不是不经意的,而是充满了审美意识,即使佩戴这些闪光饰物的女性出于吸引异性的目的,也总比非闪光饰物更有诱惑力。最后,除绘身以红色为主外,许多人体装饰物都是色彩绚丽的,而且多半是黑、白、红、黄、蓝、绿等原色,如黑色和白色的石珠,白色的兽牙、项链,红色的玛瑙珠,黄色的金饰,白色和绿色的玉饰等。但是,“我们赋予某种颜色象征性的特殊意义,和原始人的看法完全不同”③,无疑,对现代人来说,色彩是能够表现感情的,进而认为色彩的情感表现是靠人的联想得到的:“红色之所以具有刺激性,那是因为它能使人联想到火焰、流血和革命;绿色的表现性则来自于它所唤起的对大自然的清新感觉;蓝色的表现性来自于它使人想到水的冰凉”④,不过在原始审美中,那种色彩越鲜艳、色感越强烈、对比越明显就越好的意识是肯定存在的,只是某些颜色用于吸引异性注意,而另一些颜色则恐吓恶精灵,以求驱邪罢了。原始审美心理中还不乏对形式的追求,几乎所有的人体装饰物都是圆形的,如项珠、耳环、手镯、骨管,且讲求对称和节奏原则。这是由于“身体的对称形式,使他们不能不作对称的装饰”⑤。史前先民将兽牙、石珠、果实整齐地排成串子,讲求的自然是一种节奏美。铜器时代的梯形、羊角形、凹字形饰物都是呈几何形的对称图形,这反映了史前先民审美实践中更富有变化的对称和节奏原则。在所有人体装饰中,圆形仍然是主导形状,史前先民何以选择圆形,这不能不说与他们的圆形思维密切相关:“这种圆形思维的特质当和新石器时代那些诞生生命而又复活生命的陶器不无关系,它很可能来源于彩陶文化的精神遗传,即生命的生与再生在一代一代人的心目中积淀为一种思维定势。”①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物和另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彩陶就思维和审美心理而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 彩陶:有意味的形式
彩陶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诞生于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出现以后,因此它也成了农业定居文明的标志。在中国,彩陶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不过80年时间,源自仰韶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这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端。近十几年来,彩陶研究则是方兴未艾,真有“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趋势。文化人类学者、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神话学者、美学家..从来没有如此多学科的学者把研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这一神秘的史前遗物,以期对彩陶的制作、器形、纹饰、功能等做出种种解释。但囿于各自的专业所长和思维定势,往往各顾一端,各执一词。考古学家注重年代、材料、器形等基础性工作,艺术史家和美学家则倾心于造型艺术的纯形式分类、表现手法和审美心理等,而文化人类学家则重视其“文化功能”,还有些学者很难划分他是哪一类,欲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中探究彩陶的诸多“干什么”、“怎样使用”和“为什么这样用”等深层次问题,这毕竟比只是回答“是什么”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也时常冒着不能自圆其说的风险,但探索的勇气令人钦佩。彩陶制造者遇到的“怎么样”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现代人也同样会遇到,诸如怎样把一抔泥土捏成器形、怎样绘彩、怎样烧焙以及为什么会制成这种器形,为什么要绘上不同的纹饰,为什么要生用死殉等,或许对史前先民来说,这是举手之劳之事,而对现代诠释者来说,进入先民的原初情境则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诸如彩陶等“原始物品在我们眼中,具有纯形式分类的意义,而在当时制作者和使用者眼里,则具有功能分类的意义”②,故我们必须重构和复原彩陶制作的文化情境。史前先民为什么要制作纹饰各异的彩陶,有没有功能意义,这本身就有文化意味,充满了他们的精神活动。而捏成葫芦等各种器形,又绘以各种精致的纹饰,同样是充满想象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对称、圆形、动物纹样、各种几何图形,除工艺娴熟和丰富的想象力外,还与审美心理相关,这也是一种文化情境。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现代的初学制陶者在陶坊中还不足以制出各种完美的器形呢!对先民来说,彩陶的制作过程和目的是功能性的,也是史前先民审美心理的物化形式。
中国彩陶文化的发生距今已8000多年,延续了4000多年。中国彩陶文化向西传进西域时,几乎晚了3500多年,西域彩陶文化最早起始于距今3500年前,又晚至距今2000年左右时还存在,它成了中国彩陶文化在西部的最后余韵。即使如此,姗姗来迟的西域彩陶文化并没有因中原彩陶文化的终结而衰退,它又以旺盛的生命力存续了1500年左右,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
丝绸之路中段最早的农耕区多在天山南北麓的绿洲区,依次可分为天山东麓区、天山南麓区、天山北麓区和昆仑山北麓区,这些农耕区也是西域彩陶文化孕育和发生的文化区。天山东麓的彩陶分布在哈密、伊吾、巴里坤、鄯善、吐鲁番等地,出土地点有哈密的三堡、焉不拉克、四堡拉甫乔克、五堡克孜尔确卡、庙尔库、喀拉敦等遗址,以及伊吾的盐池土尔衮遗址、巴里坤的石人子、兰州湾子、南湾遗址和鄯善的苏贝希遗址、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阿斯塔那、胜金口、雅尔湖等遗址。天山南麓的彩陶分布在和静、阿克苏、沙雅、库车、焉耆等地,出土地点有和静的察吾乎沟遗址,和硕的新塔拉遗址、曲惠遗址,库车的哈拉墩遗址,阿克苏市附近遗址和喀拉玉尔衮遗址,疏附县的阿克塔拉遗址等。天山北麓的彩陶分布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水库、阿拉沟以及木垒、奇台半截沟、吉木萨尔、伊宁、昭苏、阿勒泰等地,出土地点有木垒河东岸台地遗址、昭苏夏特遗址、四道沟遗址、克尔木齐遗址等。昆仑山北麓区彩陶分布在罗布泊、且末柯那沙尔、扎滚鲁克、洛浦的山普拉等遗址。如果从中国彩陶的西进路线看,最早是天山以东地区和罗布泊流域,然后才向天山以南、以北地区发展。据考古工作者对这些地点出土的彩陶进行碳十四测定,也恰好吻合。哈拉和卓、阿斯塔那、柴窝堡、辛格尔和罗布泊等遗址被认为是距今4000~3500年前的遗址,均零星出土有彩陶。在目前考古还未发掘出更早年代的彩陶之前,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彩陶无疑成了西域最早的彩陶。天山南北麓地区的彩陶大多晚于天山东麓地区,大都盛于铁器时代。
对西域彩陶的质地、制法、器形、纹饰和功用等形式方面,考古学家曾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这对我们进一步探讨彩陶物化的精神,即复原其“文化情境”提供了可资比较的物证。天山以东地区的彩陶以早期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遗址的彩陶(新石器时期晚期)和稍晚的焉不拉克文化(早期铁器时代)以及苏贝希的彩陶具有代表性。阿斯塔那的彩陶多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饰为粗细线条、网状纹等。哈拉和卓的彩陶亦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饰主要有倒三角、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由倒三角向下延长的平行竖条纹等。①两处遗址彩陶器形主要为缸、瓮、壶、钵、碗、碟等。分布于哈密市西部的三堡、四堡和五堡一带的焉不拉克文化“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少数是夹砂灰陶和黑陶,手制;彩陶较多,基本是红衣黑彩,花纹主要有曲线纹、锯齿纹、水波纹、S形纹、倒三角纹、十字双钩纹、竖线纹等;器形主要是单耳罐、单耳钵、单耳杯、单耳豆、腹耳壶,钵和杯的底部一般都穿有小孔,口部往往被切割后又重新打磨光平”①。善苏贝希遗址由编号为1~5号墓地的不同时期的百余座墓葬组成,其中3号墓地就包括30座墓葬。3号墓出土彩陶基本为夹砂红陶,为通体彩,以内饰平行线的涡纹为主,还有网纹和竖条纹,常见的器形有釜、双耳罐、单耳罐、罐形杯、筒形杯、豆等。苏贝希3号墓距今2500年左右。从使用功能看,都相当一致,大多数彩陶作为炊具使用,这些彩陶下腹部和底部都有烟炱痕迹,也有一些与内地彩陶一样作为盛具使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焉不拉克、苏贝希的彩陶绝大多数都出土于墓葬,是将实用器皿作为明器使用的彩陶器皿内都放有祭祀的食物,如小米、羊肉、羊头等。天山南麓区的彩陶以和静察吾呼沟口文化为代表,从距今3000年到2500年不等,先后挖掘编号为1~5号墓地,墓葬密集,考古工作者发掘了600余座墓葬,其中彩陶就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察吾乎沟口彩陶文化由发生、发展、成熟到衰败的演进规律。察吾乎沟彩陶按质地、制法、器形、纹饰、使用功能可分为四期:
一期,A型墓。陶器形体肥胖,假圈足凸底器较流行,口沿下常见一周凸弦纹。彩陶线条粗细不匀,纹样以简单的网格纹和云雷纹为主。主要是局部颈带彩和腹斜带彩。
二期,B型墓。陶器器形向瘦高发展。一期中流行的假圈凸底器和口沿下凸弦纹已消失,颈部常见锥刺纹。此期是彩陶的昌盛时期,纹样精美,处处显示出一种对传统艺术的突破和创新。除局部颈带彩和腹斜带彩外,出现许多结构严谨规整的通体彩。其中的棋盘格纹似给整个彩陶艺术输入一种稳定、统一的因素。
三期,C型墓。陶器器形比较瘦高。单耳带流杯的流嘴上挺,彩陶衰落。颈带彩、腹斜带彩和通体彩不见,兴起的是简单的局部沿下彩。主要为井点纹。
四期,D型墓。陶器腹多下垂。带流杯的流嘴已变成朝天流。彩陶数量不多,纹样为极简单的竖条纹。②
察吾乎沟口文化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手制,器形多平底,带流器形占近一半,主要有单耳带流罐、双耳罐、单耳杯、釜、钵等,器表多饰红色陶衣,暗红色或黑色纹样,纹样以棋盘格、网格、菱形格、三角、云纹等几何图形和动、植物纹构成通体彩或局部彩。彩陶多作为随葬品入葬,多置于死者头前或头侧,器内放有小麦、大麦和粟、肉类等食物,釜等彩陶有烟炱痕迹,是作为炊具使用的。天山北麓彩陶分木垒、奇台和伊犁河流域以及阿勒泰等地出土,其质地、制作、器形、纹饰、功用各有异同。木垒河东岸台地上出土彩陶为夹砂红褐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样主要为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和其他网格纹,器形多为罐类。奇台半截沟彩陶为夹砂陶质,手制,外表均打磨光滑,大部分涂粉色陶衣,个别的是黄白色或白色。在陶衣上以深红色或紫色彩描绘花纹。花纹图案主要是倒三角和网纹,有些倒三角边上有斜刺。最常见的是罐类的口沿至颈部绘两排或三排倒三角,倒三角下面接绘网纹,布满整个腹部,器形基本为罐类,有些表面有烟炱,作为炊具使用,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①伊犁昭苏墓葬出土的两件彩陶壶,均鼓腹,圆底,夹砂褐陶,手制,橙黄色陶衣,红色彩绘,花纹比较复杂,其中一件在口沿处绘一圈倒三角,颈部绘棋盘格纹,整个腹部用粗细折线组成重叠的倒三角,口沿里壁有一圈宽条带;另一条在肩部绘一圈倒三角,三角下接绘网纹或三四个同心半圆纹,口沿里壁亦有一圈宽条带。②昆仑山北麓区以罗布泊地区为主的彩陶均系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饰主要为倒三角纹、水波纹、竖条纹等,器形多是单耳和双耳罐。且末县柯那沙尔出土一件完整彩陶壶,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颈部绘网纹,颈肩相接处是水波纹,腹部绘内填平行竖线的变形三角,三角之间有平行竖线,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三角之间有平行竖线,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器形为细颈、鼓腹、双耳、小平底。①
西域彩陶从整体上讲是“大同小异”、“同中有异”,但总体趋势是明显的趋同性,“小异”只是反映了时间流变和空间分布上的区域性特征。从质地、制法、器形、纹饰和功用看,至少有以下一些趋同性:(1)质地基本上都是夹砂红陶或红褐陶,不见细泥陶;(2)均为手制,多是泥条盘筑法,不见轮制彩陶;(3)器形主要是罐、盆、壶、钵、把杯等,又以单耳罐、双耳罐、把杯为普遍,且以圆底鼓腹细颈式罐居多;(4)陶衣主要是红色,还有橙黄色和白色,彩绘主要是黑色,也有红色和紫色,纹饰母题主要是实体、大倒三角、其他三角以及由三角演化而来的涡纹、竖条纹等,其他还有网纹、棋盘格纹、水波纹、平行弧线和各种短线等,纹饰不仅绘于器表,还绘于口沿里壁;(5)相当一部分彩陶作为炊具使用,也作为随葬中的盛器,往往盛有粮食、肉类等。西域彩陶的异主要表现在:与内地(主要是甘肃、青海)相比,与这些地区毗邻的天山以东、昆仑山以北区的彩陶都是红衣黑彩,器形基本是单耳、双耳罐,纹饰主要是各种短线、三角纹、水波纹、竖纹等。天山北麓彩陶则多红、橙黄、白色陶衣,红色或紫色彩绘。天山南麓区彩陶是红衣黑或红彩,器形以单耳鼓腹罐为主,纹饰以三角纹、竖条纹、涡纹为主。西域彩陶究竟与甘青彩陶的哪种文化联系更为密切?“新疆的彩陶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马厂类型、火烧沟类型文化及沙井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它们共有的单耳罐、小把杯及彩绘花纹中的三角纹、竖条纹等方面隐显出来”②。这是中原农耕文化西披的直接证明,越靠近东部,这种特征越加明显。但西域彩陶所受的文化影响绝对不是单线和一个方向的影响,否则它就不能称为西域文化了。有些学者根据西域不同地区青铜文化的构成提出了多源文化因素说,包括东来文化因素、北来文化因素、西来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越靠西部、北部,西来文化、北来文化影响越大,而东进过程中又与东来文化汇合,形成一种以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包容其他文化的多元格局。西域彩陶在东部地区主要受甘、青彩陶文化的影响,而“伊犁河流域以铁木里克墓地遗存为代表的这种青铜文化,是中部天山及七河地区相同年代的青铜文化不断向东迁移分布的产物。这种青铜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产生,应与中亚地区稍早阶段广泛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较密切的渊源关系”③。在天山东麓彩陶文化中“还存在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塔加尔文化的某些成分”①。出现这种情况是极为正常的。
尽管考古学家对彩陶进行了田野发掘、层位确定、器形分类、年代测定、纹饰描绘、区域分布等基础性的工作,但留下的还只是发掘和记录,人们仍无法去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精神内涵,“为了有效地回返到彩陶所由产生的石器时代的精神氛围,体悟当时社会的信仰、观念和行为,自然有必要借鉴人类学已有的文化重构方法,把制陶的技术生产活动和农耕文化的整体联系起来考察”②,这不失为一条揭开彩陶文化之谜的有效途径。
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化,被考古学家称为“农业革命”,这是完全不同于采集—狩猎文化的新时代。“在农业革命之前,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觅下一顿的食物,除非他们在狩猎成功后能饱餐一顿。因为人类学会了生产食物——而不是采集、狩猎或收集食物——把食物贮藏在粮仓里和牲圈里,他们不得不而且也有能力大批地定居下来。人类的能量一旦解放出来并且投入到许多新的工作中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专门的非农业的工艺的发展。因而,像诸多如基本机械原理的发现,纺织、犁耕、轮作制陶以及冶金术等许多发明的迅速出现,就决非偶然”③。在农耕文化阶段产生的女神崇拜观念及其活动是普遍的,这与先民把大地视为大地母亲的观念有密切关系。“植物每年死亡和复活,原是在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每一阶段中现成地表现出来的观念;这种不断的衰谢和再生规模巨大,人的生存又紧密地依靠它,两者合起来就使它成了一年中自然界给人印象最深的现象,至少在温带如此。毫不奇怪,这么重要、这么惊人、这么广大的一个现象,它必然会用提出类似观念的办法使许多地方产生类似的仪式”④,而人类神话中最重要的生死母题就是植根于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之中的。彩陶生产的象征意义,如使用的材料黏土、器形、纹饰,无不可以从地母神话或生育巫术仪式之法器的象征功能方面去求解。人类在经历狩猎文化阶段,揖别狩猎巫术后精心选择了大地母神信仰为核心的生殖巫术,彩陶成了生殖巫术的法器,与地母观念有了生生不息的关联:
她反映了人类关于生育与死亡、生存与消亡的基本经验。她是赋予生命的母亲,但同时也是地母,人们死后都要回到她的怀抱里。好些表现这种基本经验的象征都伴随着她:以增、圆、缺三种形象出现的月亮,..还有罐子,这个相当于腹部的容器,新的生命就来自这里。同样,她用来蓄积食物和保存食物的这个罐子,又会变成人们——就像隐藏在母腹中那样——重又回到那里去的墓穴。这是一个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受到局限,可以通观,因为“母亲的王国往往就来自这个世界”。生与死在她身上同时并存,尚未遭到罪孽经验、惩罚经验与异化经验的分裂。①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制作彩陶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产过程,它还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彩陶之谜也必须进入其精神世界进行探索。
晚于陕、甘、青诞生的西域彩陶造型有“依样画葫芦”之感,完全是葫芦形的仿制。从罐、杯、釜、钵、盆、碗、豆、壶等主要器形看,无不是取样于葫芦形,只不过不同器形是横剖葫芦不同截面的组合。早期与晚期器形的不同点并不在其腹部形状的改变,只是颈部长短、粗细和底部(圆底、平底)、带流等的变化。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西域也是普遍生长葫芦的地域,“世界上凡是远古曾生产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容器之前,曾先使用过天然的容器葫芦;而葫芦容器也就是陶容器的现成模型。葫芦的特点之一,是它在青嫩时可作为食物(苦葫芦除外),到成熟晒干后就成为硬壳的干葫芦——外凸光滑,腹空能容物”②。史前先民以葫芦来仿制彩陶器形,“正是因为史前思维将葫芦认作植物所从出的母体和子宫,而且根据这种思维的类比与认同原则,人与地母的子宫也是这种形状,三者同形,功能也相同,可以相互串位和替代,因而陶器依葫芦而造型,所象征的既是植物生殖的母体,也是人与地母的母体子宫”③。西域仿葫芦制作的彩陶主要器形为食具、饮器和炊具,同时也作为葬具,因为葫芦腹大多子,这其中“暗含的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巫术信仰,即通过葫芦状的饮食器皿的使用而将其旺盛的繁殖力传递和生长于人类身上。因为远古的食就是性,性也就是食”④。西域彩陶时代的墓葬中的彩陶中都盛有农作物、种子,或许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死去的亲人完全可以像农作物种子一样死而复生,这种方式大概是希望将地母旺盛的繁殖力、生命力传递给人类本身。因此,活着的人用陶器“吃喝”,并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吃喝本身也有生殖意义,是一种传递生殖力的巫术行为。彩陶取像均为圆形,这种圆形还来源于史前先民的圆形思维,它的功能也是一个圆。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先民的圆形思维来自于农作物依四季死而复生的启发,在此,时间无所谓有始,也无所谓有终,一粒种子埋入土中,生长、开花、结果,然后又循环往复,始就是终,终也是始。这种圆形时间观又类推到人的生死,瓮罐葬、屈肢葬、彩陶盛粮食种子随葬,都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圆,人死后埋葬并不是死亡,只是回到大地母亲的子宫,是完全可以死而复生的。女性制作彩陶的仪式,以彩陶为盛具吃喝的仪食,以瓮罐、屈肢、圆形墓堆的丧葬仪式都是史前先民源于圆形思维的巫术仪式,它充满了生殖(包括人的繁衍和食物的生产)巫术信仰和行为的旺盛生命力。
在彩陶文化情境中,最不可索解的是纹饰,人们往往以艺术审美的眼光诠释这些纹样,无论是动植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于是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如“观物取象”、“抽象变形”、“模拟自然”等。但人们似乎忽视了彩陶纹饰同彩陶的选料、制作、器形一样是具有功能意义的,“彩陶纹饰则严格地与器形(还有质料)一起联合表意,整体地充当巫术施法的工具”①,它们共同表达一种“力”的观念,在彩陶产生的时代还有比生殖力更重要的东西吗?西域彩陶中反复出现的主导性纹样——三角形,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西亚、中亚、北非、希腊彩陶纹饰中都有这种三角形图案,中国彩陶文化的各种类型中也是所谓的蛙纹、鸟纹、鱼纹与三角形等几何纹样伴生。从整体上看,彩陶的主导纹样均与生殖母题相关,“生殖崇拜是统摄了彩陶艺术创作的一个主导性观念”②。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作比照。该岩画被认为是西域猎牧部族的岩刻作品,与西域农耕文化中的彩陶属同期。康家石门子岩画的主体是裸体的男女群像,他们的身体造型,尤其是上身躯体无一例外全是倒三角形,一些单人、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的人体造型,除头部外,自上而下完全是倒三角形,分不出上身和下身的区别。这完全与西域彩陶中的倒三角形纹样不谋而合,这绝非偶然,都是一种生殖力的张扬。不过,史前猎牧先民选择如此僻静、肃穆、万木茂盛的天山深处举行神圣的生殖巫术仪式时,农耕先民则选择了来自地母的彩陶进行这种生殖巫术仪式,这只能说是殊途同归。事情远不止如此,在罗布泊地区小河5号墓地出土的“许多箭杆上面雕刻有横向排列的三角纹,三角形内部涂以红色,花纹呈条带形排列,每一条带包括两组相向排列的三角形”中诸如三角纹、水波纹、涡漩纹、网纹等是先民装饰艺术的变形结果,我倒相信这样的结论:“(先民)在陶器腹部每绘制一根线条、每涂上一种色彩,都是在进行一种巫术操作。在巫术的意义上,陶器尤其是彩陶可以说是集天下生殖力之大成:它的质料来自大地母亲的血肉——黏土,它的造型取像于大地母亲的子宫,它的器腹上又绘满各种具有生殖感应能力的纹饰,难怪它在远古先民心目中有崇高与神圣的地位呢!”①卫聚贤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多有三角形如‘▽’的花纹,即是崇拜女性生殖器的象征。”②
当我们以一种艺术眼光审视彩陶文化时,谁也不能否认在彩陶的线条和色块中所具有的节奏、韵律、对称、均衡、连续、间隔、重叠、粗细、疏密、交叉、错综、一致、变化、统一等形式规律表明史前先民审美心理机制的客观存在。浑然天成的圆形,神态毕肖的人物、动物造型,错落有致的对称纹饰,带流的完美形态,诚如博厄斯所言:“在图画中和造型艺术中对对称、节奏之类的形式的强调并非像进化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是艺术渐进过程中的产物,而在于双手运动的对称性以及对人和动物左右两侧都是对称的观察而得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节奏的反复循环常出现在处于水平线的带状事物中。如树木、山、云、腿、身体、翅膀等都处在水平状态中。节奏的形式和技巧过程的关系最密切。..最简单的技巧过程总是产生简单的同一运动的重复。与此同时,愈来愈复杂的技巧则构成艺术鉴赏的尺度。鉴赏力愈发展,复杂的节奏就愈易于出现”③。千百次的重复,循环往复,或许就是这种最初的审美机制发生的缘由。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彩陶的制作是出于审美的动机,因为即使像彩陶的这种装饰“却并不具有它自身的目的,它只是为了强化巫术工具的力量。这样,也就很难说它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动机,因为即使存在着有审美价值的纹饰,它的单纯的巫术工具性质就排除了审美的动机”④,我们万不可把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强加于史前先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先民制作彩陶的原初动机。
第三节 女性雕像的地母情结
人类在母系社会阶段,女性是一切的主宰,农耕是靠女性发展起来,彩陶的制作者也是女性:“农业的发明是妇女的功绩,不仅因为妇女是主要的采集者,其后又成为初期农业的发明者;还因为初期农业主要是由妇女们承担和领导的。北美印第安人如易洛魁人、祖尼人、亥达沙人,非洲东南部的许多部落,以及新几内亚的巴拿罗人等,在农业活动上就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由妇女们选出一个年长而精力充沛的管理人领导农耕工作,而这个管理人还可以选择一两个人作自己的助手。随着锄耕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男子变成为农业方面的主要劳动者了。”①在这样一个母权制的社会中,妇女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农事、制陶、生育,这些主要由妇女从事的工作都被赋予一种神圣意义,女性自然也就成了受崇拜的偶像,女性雕像也应运而生。新石器时代的女性雕像(无论是象征丰产的还是生育的)都可以追溯到她的原型——大母神,尽管她有不同称谓,如原母神、大母、大女神等,但含义是相同的,“特指起源于父系社会之前的最大神灵,是狩猎的史前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原始信仰中最早出现的神”②。它起源于先民的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想象:“在这种原始状态里,人的意识和自我还很弱小,尚未发展。作为初始的、对立面容纳于其间的象征,乌罗伯洛斯是‘大圆’(the‘GreatRound’),正面和负面,男性和女性,意识因素、与意识对立的因素和无意识因素,在其间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乌罗伯洛斯也是混沌、无意识和心理整体未分化状态的象征,而这种状况,被自我经验为一种不确定的两可状况。”③在任何一个自我意识弱小、未经发展而无意识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都能见到女性的基本特征:大圆、大容器的形态,它包容万物,而万物又产生于它。“假如我们把初民未定形的身体—世界等式同女性基本特征的等式女人=身体=容器结合在一起,我们便为人类远古时代得出了一个普遍的象征公式:女人=身体=容器=世界。这是母权阶段的基本公式,在这个人类发展阶段里,女性支配男性,无意识支配自我和意识”④。这完全为考古学材料所证明。有学者对已知的石器时代的雕像进行了性别统计,发现女性雕像是50件,而男性雕像仅有5件,且这几件男性雕像不合定型而且技巧拙劣。⑤文些女性雕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矮胖,肚腹和乳房、臀部往往畸大,它们的主要象征意义都是圆形容器;而另一类是细长而纤弱,身材修长,只是突出乳房、阴部等女性特征。“这些无定形的大母神塑像是孕育的生育女神的造型,在全世界,它都被当作怀孕和生育的女神,而且作为不仅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崇拜对象,它也被视为生育力的原型象征,遮蔽、保护和滋养的基本特征的原型象征”⑥。人类认识自身生产、种族繁衍的奥秘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物生人,人是由某动植物或无生物生出来的,这一阶段虽然缺乏物征,但神话中有大量资料可以回答人的来源;第二阶段是感生,人是由母亲生的,母亲又是受感应而生的,感生神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父权制确立后,出现新的生育观念,概称性生,即通过男女交合而生育后代。①在母系社会阶段,先民始终认为人类的生育是一种孤雌繁殖,这种孤雌繁殖是将女性创造生命认同于大地创生万物的结果,“在多产和生殖中,并不是妇女为土地树立了榜样,而是土地为妇女树立了榜样”。②从这个意义上讲,生育信仰也是一种地母信仰,女性和地母是同义语,具有相同的繁殖(生产)功能,在一个孤雌繁殖信仰相当普遍的社会,达到生殖目的的有效手段就是生殖巫术。
丝绸之路西域最早的女性雕像发现于孔雀河下游被称作小河墓地的地方。维吾尔人奥尔德克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罗布荒原上神秘地方的人,时间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奥尔德克做向导,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到了小河墓地并首先向世人披露了他在小河墓地的发现,引述如下:
这个经过长时间寻觅的墓地距“小河”岸4公里,位于一个浑圆的小山包上。..小山的表面,特别是在山坡上,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弯曲的厚木板,不论走到哪里,脚下都会绊到久经岁月摧蚀的人骨、被肢解了的木乃伊和厚毛织物碎片。..在小山的西端,有一道略呈曲线排列的木栅栏,栅栏的木杆比较细,且不很直。在小山顶部稍靠东一些,又有一道木栅栏,这道栅栏的木杆较粗,其顶部都在同一高度上。..在大栅栏正东侧的自由木杆相互挨得很近,几乎全部都非常高,平均高度达4.25米,杆子的直径都大致相同,约25厘米。它们全部是多棱柱,具有7~13个表面。将柱基部的沙移走后,可见其表面曾被涂成红色。杆子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颜色已消失殆尽。看来这座“死神的立柱殿堂”曾经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红色之中。..制作颜料的材料是红赭石。..这里的一个有趣特征,是桨形纪念物,它们许多还矗立在原位,另一些已全部埋入沙中,另有15个落在了山坡下。..桨片的下方通常有一条由数道经向刻线组成的装饰带,装饰带也曾被涂成红色。..小山的最东部近乎平坦,而且只有一根直立的木杆。这是唯一的一根具有经向沟槽的木杆,沟槽宽约1厘米,槽与槽等距。..整个小山的北坡、东坡和南坡,散落着各种尺寸的棺材板、倒下的木杆、木桩和桨形纪念物。..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所有的棺木都是同样的结构(亦被后人称为的船形棺——笔者)。①
这是距今近4000年的西域早期氏族墓葬群。遥想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庄严仪典?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神秘气氛的地方出土了西域最早的女性雕像。在贝格曼之前,斯坦因曾在楼兰附近的墓葬中发现过一些小型女性雕像,其中一具木质女性雕像,高70厘米,无腿,面部呈平面,用红赭石粉绘制出五官,另一具女性石像仅高10厘米。贝格曼发现的雕像为三具,其中一具为男性,两具女性雕像,分别高134厘米和158厘米,但是贝氏并未对这两具女性雕像的特征作过多的描述,只对一具保存较完整的雕像描述道:“女性雕像面部为椭圆形平面,上面可能曾经绘有五官。双臂极细,几乎不成比例。腿部雕刻完整,小腿极粗,可分辨出球形的膝部。”②参照贝格曼所拍摄的照片,发现这两具女性雕像的性器特征是明显夸张变形。小河墓地的女性雕像并非个例,孔雀河古墓沟、哈密焉不拉克文化等都出土有距今4000~3000年前的女性雕像。考古工作者在孔雀河古墓沟发现的距今近4000年的石质女性雕像仅高27.5厘米,用白石雕刻而成,方头,眉、眼、嘴、鼻均用黑色竖横线表示,颈部阴刻三道弧线表示服饰领口,胸部突出女性乳房特征,束腰系带,下肢简略。同一地点出土的木质女性雕像,属距今3000年左右的物品,雕像用整木雕刻,头戴圆帽,未雕五官,身体扁平,乳房下垂。另两件男女木雕像则出土于哈密焉不拉克,距今3000年,用原木雕刻。男女面部的嘴、眼等五官用阴刻方式表现,四肢刻划具备,但雕刻僵直刻板。从身体轮廓看,女性显粗壮、高大,男性纤细、矮小。男女性器均夸张变形。发现女性雕像的墓葬中均出土有麦粒、谷粒等农作物,是西域农耕文明发祥的地方,也是西域彩陶文化的发源地。巴里坤县甲山沙墓葬中出土两件铜石并用时代的青铜器女性雕像,其形象是大腹丰乳,我们看到了身体=容器的原型等式。
小河墓地足以让我们对罗布泊地区史前先民遗物——那高大的红色多棱柱和桨形物,无底的船形棺;那雕刻粗糙,连脸部五官都不清,但性器特征十分明显的并非艺术品的女性木雕像...产生无穷的联想。特别是神秘的雕刻有蛇形的木桩:“这是一根直木桩,上面的刻纹描绘出一条蛇正在吞食一根线轴形木桩。蛇背用密布的小菱形表示,菱形内涂以红色,肚皮间刻横线和成排的小三角。这些刻纹意欲代表蛇鳞和蛇身图案。...(另一根类似的蛇纹木桩)的中部附近有一小孔,可能用来拴悬挂的线绳。”①箭、梳子、小木梳上反复出现的众多三角形纹饰;红色是这个世界永恒的色彩。这些究竟寓示着什么?对此,我们不能不从罗布泊地区的史前文明说起,整个孔雀河下游地区既是畜牧和农耕兼营的地区,也是西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一地区“农业是存在的,墓区发现的小麦粒,是一个直接的说明。...孔雀河谷可得灌溉之便,少量的农业经营是完全可能的。...而小麦,最早可能在新疆种植。...除畜牧业、少量的农业生产外,渔猎是人们生活的补充”②。从这较有保留性的估计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完全不同于采集—狩猎文化的畜牧—农耕文化已经出现了,人们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与他们生死相依的土地。早在4000年前罗布泊地区就属于干早、半干旱区,沿河、沿湖分布有绿洲。“现有的资料表明,通常是那些半干早的地区..有较丰富的但绝不过多的可采集的食物资源,往往是栽培与驯化发生的最重要的中心”③,西域早期的畜牧—农耕文明都是这样产生的。要揭开发生在畜牧—农耕文明诞生时期的小河墓地红色多棱柱、船形棺、木桨、蛇形木桩、女性雕像、三角符号等千古之谜,非得触摸史前先民的思维、信仰、观念、心理等深层文化机制的脉搏不可。较之采集—狩猎文化时期,畜牧—农耕时代先民的思维、信仰、观念、心理,即精神文化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大大扩充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范围。对舒适的定居生活和有规律的岁月循环的习惯、农业收成作长期耐心等待的必要性(加之农业收成还会遭到各种灾害,如天灾和兽害等),根据天象精确地计算时间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使得农人们对天、地、日、月、雨、雹等自然力空前地关注,他们把这些自然力崇拜为神,很多事情现在都得依赖这些自然力的作用。伴随着这种泛灵观念的发展,还大大加强了对丰产和繁殖的崇拜,对女神的崇拜(可能是对地母的崇拜),这种女神的石像和泥塑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发现。农人们对“阴世”生活也采取了新的态度。看来,对丰产和一年一度的枯(结果)荣(发芽)的崇拜,产生了关于死者可以复生的观念。因此,葬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①
这个时期先民的精神领域的变化主要是:(1)农业巫术代替了狩猎巫术。在一个粮食并不丰裕的社会,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歉收时,就必须实施巫术,保证粮食足以果腹,因此农业巫术也是一种丰产巫术。(2)根据先民类比和认同的原则,大地生长出谷物是有周期性的(生长、枯荣),就有了将女性与大地认同的巫术信仰。将大地丰产和女性生殖的认同,正是母系社会的普遍信仰,在一个“知母不知父”的社会,女性是所有生产活动的主宰。在此,地母与女性是一种同义认同。(3)人是可以死而复生的观念的形成。人“死”后入土为安,实际上意味着回到了大地母亲的子宫,他们像农作物枯荣那样是可以再生的,这同样是一种圆形思维。由女性主持的神圣葬仪也就成了一种生命回归的庄严仪典。(4)从新石器到铜石并用时代,史前先民的生育信仰经历了由大地生人到两性交媾生人的转化,西域出土的性器夸张变形的男、女木雕像是最有力的证据。
一些学者把女性的基本特征分为正面基本特征和负面基本特征。女性的正面基本特征的中心是容器,它既是女性性质的属性,也是女性性质的象征。在那个“真实生活”也是“象征生活”的母系社会中,鼓腹的彩陶、丰乳肥臀的女性雕像、蛇、隆起的地乳..都与容器有关,是代表丰产和生育的地母的象征。于阗,梵文称为“瞿萨旦那”,意为地乳,其建国传说显然源于早期的地母崇拜。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小河墓地乃至焉不拉克出土的女性雕像,几乎都没有五官标记,或只有用横竖线条表示,但夸大了乳房、臀部、性器等特征。这些女性中五官经常缺失的基本特征的意义在于:“丰足性是人的正面原始经验之一,是他对女性作为提供营养的容器的经验的一部分,因此乳房得到了强调。”②至于贝格曼在小河墓地发现的蛇纹木桩,他小心谨慎地认为:“此二蛇形物的确切用途尚无法确定,我们仅知通常巫术及医药界都崇拜蛇。像青蛙是雨的象征一样,蛇被一些权威认为是促进生育的原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蛇也经常被作为阴茎的象征。”①贝格曼已经踏进了揭开这个千古之谜的门槛,却裹足不前了。蛇与生育的关系都源自那个诡秘的“乌罗伯洛斯”——衔尾环蛇,是初始原始状态心理状况的象征。“由于它的乌罗伯洛斯混成性,蛇象征也可以表现为女性。因为女性容器是创造性的,子宫是神圣的部位,在身体象征系统中具有真正神秘的特色,而且像每一种神秘事物一样,它是情感矛盾、意义暖昧的。蛇以附属的角色与之相关,就像男人和阴茎因素,它成为女性的一部分,或作为其伴侣”②。作为代表生育力的地蛇,它是地母的一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讲蛇是女性的象征,也是生育力的象征,小河墓地的蛇形木桩很可能就是实施生殖巫术的工具。
女性的负面基本特征也是在女性意象中被感知:“往往表现为死亡和毁灭,危险与困难,饥饿和无防备,在黑暗恐怖母神面前表现为无助。”③“这样,大地子宫变成了地下致命的、吞噬的大口,等同于受孕的子宫、防护的地洞与山洞、地狱的深渊、深藏的暗穴、坟墓和死亡吞噬的子宫,没有光明,一片空虚。正是这个产生生命和世间一切众生的女人使他们返回到她自身,她追捕着她的牺牲品,用她的陷阱和罗网抓住他们。疾病、饥饿、艰难困苦,再加上战争,都是她的帮手,而在一切人群中间,战争和狩猎女神都表达了生命乃女性之血的人生经验。这位恐怖母神是饥渴的土地,它吞食自己的孩子们,用他们的尸体来增强自己的肥沃;它是老虎和兀鹰,兀鹰和棺材,是饕餮地舔尽人与兽的血精的食肉石棺,然后,再次孕育、滋养生命,使它重获新生,再不断地将它们抛入死亡的深渊”④。面对死亡、恐惧、痛苦,人们并非无能为力,直觉使人们相信,通过痛苦和死亡、献祭和肉体与灵魂的泯灭而能达到更新、再生和不朽,也就是说死亡是回归母亲容器,这是变形物完全溶入女性的原则,这些容器不论是骨灰坛、棺材、洞穴,还是船、土、水等。这些容器与其他一些物件象征地关联在一起,出于先民“无所不包”的心理真实,先民是将整套关于女性生命的心理象征投射于现实世界,变成了笃信不疑的巫术仪式。在小河墓地地表矗立着的近200根高达4米多、直径在25~50厘米的红色多棱柱和30多个红色桨形物,以及同样是红色的木栅栏究竟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在一个可能是几代人使用的氏族公共墓地,如此兴师动众,费力费时树立这些“纪念物”绝不是史前罗布泊人的一时冲动所致,而仍然出于把容器视为女性基本特征的象征。容器的“掩蔽结构”赋予冥界的住宅——坟墓以形式,正如它赋予地上的住所房屋和天上诸神的居所圣殿以形式一样,在利西亚和小亚细亚,房屋是“这个古代母权国度的废墟上发现的坟墓和圣殿的精确副本”①。由于在母系社会,房屋的设计和建筑是女性的特权,于是房屋、坟墓、圣殿、房屋的支柱、栅栏、围墙都是大母神的象征。从考古发现得知,最初的氏族公社聚落、房屋都是一个大圆,它源于大圆巫术思维,像子宫、中心或世界一样,显示出女性的特征。在一个容器象征的“掩蔽结构”的冥界,还能有例外吗?母系社会早期一些卫护女性分娩场所的原始围栏(栅栏)等变成了圣地的标志,而生育过程也变成了再生过程,在以后的神秘仪典中,人要新生(再生)必须经历冥界危险的旅行。在经过多重栅栏、巨型多棱柱和桨形物组成的多重门后,死者才能再生,获得新生。红色在女性基本特征中总是担任双重角色:它不仅是代表生育力的积极颜色,也是灾难、罪恶、流血和死亡的颜色,同栅栏、木柱、大门等一样都是女性大地——子宫的象征。小河墓地显然是史前先民进行这种再生巫术仪典的神圣场所。墓葬中的无底船形棺、草篓中的麦粒、粟米、几捆麻黄枝、绘有红色的三角形图案的物件等墓中物品同地表物件一样都属于生育祭奠的范畴,有死而复生的巫术意义。特别是船形棺也与女性象征有关:“因此古代的船只常常是‘怀孕的女性’,也因此它们的命名强调女性的拯救功能”②。“作为诞生之地,作为拯救之路,作为死者之船,船是开端、中间和终结之木。它是作为命运女主人的三合一女神,也是树母神,她庇护着人的生命并引导他从地到地,从木到木,最终返回到她自身”③。否则,史前的罗布泊人就不会在墓地上制造如此多的多棱柱、栅栏、桨形物、船形棺。
生育与死亡、白天与黑夜、大地与上天、房屋与墓穴、太阳与月亮、欢欣与恐惧..这种正面与负面的两极因素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二重性。在母系氏族社会,它源于对自然界出生、成长和死亡的复杂节律的朴素认识,形成一种圆形思维,由于这种宇宙性意义和女性的生育力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以“大圆”为象征的原型单位。西域的史前女性雕像及其诞生地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地母丰富多彩的形式的原型心理世界,它也构成了母系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岩画与巫术
正当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东部、南部绿洲发生农耕民的彩陶文化时,其北部、西部沿天山、阿尔泰山地带则开始兴起猎牧民的岩画文化。发生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这一幕绝不是偶然的。在史前,先民在这些造型、绘刻形象中蕴涵的是精神指向,岩画和彩陶一样,是一种精神象征,而不只是一些物化形态。要探究这些岩画的奥秘,仍然要像索解彩陶一样,进行一番精神寻根。
尽管诸如岩画等原始图像在我们眼中有形式分类的意义,但在史前先民眼中则具有功能分类的意义。我们曾先入为主,对岩画进行着违背史前先民意愿的纯形式分类,于是仅仅根据图像,简单、率直地把它们分为舞蹈图、狩猎图、放牧图、杂技图、车辆图、动物图、印记图等,甚至还认为某些岩画是裸体艺术、人体艺术等。这种形式分类或许可以走一条捷径,但望图生义的结果离岩画刻绘者的初衷则相差十万八千里,就会更加远离岩画的文化情境。
在众多的西域岩画中,的确存在一些有史时代,甚至近现代的创作,但剔除那些有意无意的仿作外,其贯穿的巫术信仰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几乎都是巫术思维的产物。其实在古代,巫术思维并不是史前先民的专利,它的精神嫡传一直泽被于后世。英国学者基思·托马斯在《巫术的兴衰》一书中分析的就是16、17世纪英国盛兴的妖术、占星术、占卜术及形形色色的大众巫术,以求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迄今在新疆一些偏远地区还存有治疗、求子、取名、祈雨、防厄等巫术的遗迹。在一个充满巫术思维的史前社会中,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制陶、农耕、狩猎、生殖、雕刻女性像、人体装饰、绘刻岩画又怎能离开巫术思维呢!这些制作、劳作、绘刻的过程就是巫术操作的过程,都与生殖(人口的繁衍、动植物的丰产)有关。因此,西域史前和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岩画都与生殖巫术或狩猎巫术有关,其中不少还渗透着萨满教的信仰。只是由于西域众多岩画无法像出土文物那样易于断代,其中的一些难解之谜还有待时日进一步破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岩画精神实质的剖解和诠释。
考察西域岩画就会发现,它是沿西域南北草原带分布的,这个草原带是欧亚草原的中间地带。在这样一个广袤的草原地带,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里海,北起西伯利亚,南至昆仑,又形成若干岩画区域,如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阿尔泰山岩画、天山岩画、昆仑山岩画、西伯利亚岩画等。这个岩画带虽然只是世界性岩画(世界各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发现岩画)的一个单元,但它在世界岩画和中国岩画系列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在内的草原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狩猎、畜牧文化,要研究史前狩猎、畜牧文化,非在这些地区寻觅踪迹不可。新疆境内沿阿尔泰山系、天山山系和昆仑山系发现的岩画多达150多处,且这还不是最终的数字。如果要在欧亚草原带选若干代表性的岩画点进行研究,新疆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因为猎牧先民的游移性,新疆的天山岩画、阿尔泰山岩画、昆仑山岩画与阴山岩画、西伯利亚岩画、中亚岩画、西藏岩画之间都有一种天然联系,这为对这些不同地区的岩画进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对岩画的微观透视和宏观把握并不相悖,在微观剖析中把握宏观意义,或以宏观神野对一系列岩画图像进行精道的缕分条析,两者的旨向是相通的:进入猎牧先民绘刻的真实世界。但是一些研究者往往误认为微观分析就是按现成思路对岩画的类型、图像、分布地点等作简单的陈述,却极少进入岩画绘刻者的精神世界作深度探索;而一些宏大理论也因为大而无当,或干脆照搬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留下了无可挽回的硬伤。如果我们旨在通过岩画“复原”或“重构”史前先民的文化情境,那么宏观与微观结合就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一种正确、合理的方法往往成了打开岩画之谜大门的一把钥匙,我们在研究中就会游刃有余,否则不是浅陋就是误入歧途。
什么是岩画,迄今并无公认的定论,也没有周密的界定,有些学者侧重于艺术角度,认为岩画是一种在洞窟、崖壁、岩床、巨石上绘、刻、雕刻的艺术品;①也有学者认为是刻或画在岩石表面的图画;②还有学者从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婚姻形态界定岩画,认为是部落先民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③如果从凸现岩画的本质特征而言,第三种界定较为合理,尽管并非十全十美。岩画可以分为洞穴岩画、崖壁岩画和单个大石岩画,制作图像的方法有涂绘、刻画、凿刻等手法。从性质上看,岩画应界定为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无论因岩画空间分布和时间跨度有多么悬殊,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认定它是岩画,这可以排除一些人为因素,使岩画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那么西域有哪些岩画是属于“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呢?据已经发现的岩画,除某些个别为后人的游戏之作外,绝大部分都在这个范畴内,无论是史前的还是有史以来的。阿尔泰山系岩画分布于阿勒泰、青河、富蕴、布尔津、福海、哈巴河、吉木乃一市六县辖区内,④90%以上画面反映有动物形体。⑤这些岩画中刻绘的动物形象有洞角类、鹿科类、犬科类、豹类、马科类、骆驼科类、野猪科类、象科类等,多达数十种,其中如亚洲象、麋鹿、野牛等动物早已灭绝。阿尔泰山系岩画中最常见的动物形象是洞角类的盘羊、北山羊、岩羊、羚羊以及鹿科的梅花鹿、马鹿、驼鹿、驯鹿、麋鹿等。阿尔泰山系岩画中还见有洞窟岩画,富蕴县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被认为是男女交媾生育和萨满教信仰岩画。阿勒泰市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亦属此类型,不过是增添了动物形象而已。其他还有别列泽克河上游的洞窟彩绘岩画,均用赭石绘制。天山岩画按分布区域大致可分为东部岩画、北部岩画和南部岩画。天山东部岩画分布在巴里坤、伊吾、哈密等市县境内。巴里坤以兰州湾子、李家湾子、大小夹山、卡墙子、塔斯托贝、小柳沟、阿希哈赖山等处的动物(北山羊)岩画、狩猎巫术岩画以及刻绘符号居多。伊吾也是东天山岩画分布较集中的地区,现发现的岩画点有乌勒盖、白杨沟、科托果勒、卡塔布齐、白芨等地。这些地方岩画中的动物图像有北山羊、盘羊、鹿、骆驼、马等,还有反映狩猎巫术的岩画以及一些刻绘符号。哈密市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其东北沁城区白山上,属凿刻型岩画。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数百幅岩羊、大角羊、鹿、骆驼、牛等动物图像岩画和狩猎巫术的岩画。天山北部岩画自东向西沿天山北麓分布,岩画主要分布在昌吉州的木垒县水磨沟、芦塘沟、奇台县北塔山、米泉市白杨河、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等地,塔城地区的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托里县的玛依山喀拉曲克牧场,博尔塔拉地区的温泉县苏鲁北津,伊犁地区伊宁县的卡约鲁克沟、巩留县的萨尔布津、昭苏县的阿克牙孜沟、特克斯县的唐姆洛克塔什、库克苏河水电站、科克苏、阿克塔什和尼勒克县的塔特郎、却米克拜、新源县的喀拉汉德沟、克孜勒塔斯等处。天山北部岩画除与阿尔泰山和天山东部岩画常见的动物岩画、狩猎巫术岩画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被学者们称为生殖崇拜的岩画,如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大型生殖崇拜岩画、裕民县巴尔达库尔生殖崇拜岩画、木垒县博斯坦牧场狩猎巫术岩画等。天山以南的岩画有托克逊县科普加衣岩画、温宿县岩画等,均以动物图像和符号为主。昆仑山系岩画发现不多,主要有和田地区的桑株岩画、克依刻图孜岩画、康阿孜岩画和且末县莫勒恰河山口岩画等,也以动物图像,如北山羊、黄羊、盘羊、野牛、骆驼、牦牛、鹿、羚羊、野驴、马等为主,同时也伴有刻绘的人物形象和符号标记。有些人物形象被似是而非的命名为舞蹈图和杂技图等,这是完全不了解猎牧民刻绘这些图像的意图所致。那么,这些史前猎牧民究竟通过刻绘岩画要表达什么意图呢?或者说,这些史前猎牧民为什么要绘刻这些岩画呢?
从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的这些岩画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野生动物形象,只有极少数如马、狗等为家养动物形象,而且出现的人形图像或与动物间有某种关系,或是象征人类生殖的组合图像。这表明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后期伴有少量畜牧业,即使在游牧社会,也不完全排除狩猎活动),人们最关注的是氏族人口的繁衍和猎取动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猎牧社会的文化也是一种产食文化,但是天灾人祸并不能完全保证人口的高存活率和每次都能猎获动物。在这样一个前科学时代,巫术思维的产生直接导致人们借助于运用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巫术的世界。开始,原始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力’。奇妙的‘力’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存在和石头的坚硬、水的湿润一样的确定无疑,和现代物理学上‘以太’一样的普遍。这种‘力’仅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超自然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真实的和自然的”①。人们在信奉神灵之前,是普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的。正如弗雷泽所言:“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②巫术思维导致的是巫术操作。岩画正是施法者实施巫术操作仪式的工具。这种巫术思维和巫术操作一直从旧石器时代起,经过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有史时代。西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都充满着这种巫术仪式。
弗雷泽认为,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和物体相互接触后中断接触可相互作用,他把前者称为“相似律”,后者称为“接触律”。由此,基于相似律的巫术叫作“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的巫术叫作“接触巫术”。而这两种巫术都归于“交感巫术”。“因为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③。猎牧社会的狩猎巫术、生殖巫术都是一种交感巫术。岩画作为实施巫术的工具,其制作的图像有自足图像和非自足图像之分。所谓自足图像是“施法者(人)在图像中并未出现,但是,只要动物图像和施法工具同时出现在同一画面上,也可以将这种图像称为自足型图像,因为画面本身中出现的因素已经足以构成一个施法动作和巫术事件了”④。自足图像是把施法者的施法动作(绘刻)保留在图像画面上。有些岩画图像有动物叠压、覆盖的痕迹,反映的正是自足图像制作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巫术操作过程,即造型过程与巫术过程合一。这种过程已无法复原,人们只能根据图像本身残存的痕迹进行观察分析了。一般来说,一次巫术仪式要使用一次图像。所谓非自足图像是指“施法动作要由现实中的人来完成,..一般来讲,非自足图像的巫术事件要由图像中的要素和现实中人的动作要素一起才能实现”⑤。非自足图像是施法者在已完成的图像上施动作于图像,才构成一个巫术操作过程,于是,发现一些岩画中有重刻(绘)或多次刻画的痕迹,表明施法动作在原已绘刻好的图像上进行。从已发现的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岩画中不难得知,人与动物生殖“力”的传递形式有四种:一是感应式;二是接触式;三是相交式;四是距离交合式,都属于交感巫术范畴。已完成的岩画图像既可能是自足图像,又可能是非自足图像。
西域岩画中有一类在我国其他地方绝少有的洞窟彩绘岩画。它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其一是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乌孙山发现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岩画绘于阿克塔斯山高1850米处的岩洞内,洞高2.5~3米,洞口宽5米。岩画绘于洞口右面岩画上,均用赭石绘制。画面由七只北山羊、两匹马和两组大小圆圈和一个“〉”形及“◎”形、“工”、“)”符号组成。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第一个岩洞在半山腰离地面25米处,洞窟高11.5米,宽20米,深11.8米。岩画绘于洞顶和正面、侧面岩壁上。画面由一组四个里外两层、中间为圆圈的椭圆形图案和两个圆圈、手印以及被认为萨满帽、铜镜的图形组成,此外还有一组表意符号和所谓的人面像。唐巴勒塔斯二洞距离第一洞约60米,位于海拔1000米处,洞宽4.9米,高3.2米,深4米。画面由拿弓箭欲射的两人、脚印、两只野兽和叉腿、手臂平放或上举的四组人形图像组成。其三是阿勒泰市西北25公里处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洞窟在海拔1000米处,高1.3~1.5米,深浅不一,从一米多到四米左右。在三组五十余道竖短杠组成的类似围栏内分别绘有一椭圆形图案和双腿叉开、高举双手的人物图像。此外还赭绘有牛、马、大角羊的图像。其四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乡的洞窟彩绘岩画,为两处,一处在杜阿特沟,另一处在松哈尔沟。杜阿特沟洞窟彩绘岩画又分5洞。第一洞海拔650米,洞高不过1米,宽也仅1.6米,赭石绘有牛和人物图像,人头部有.“〓”形饰物。第二洞在海拔605米处,洞高1~5米,宽1.7米,深1.3米。画面由一双手下垂、有尾饰的人物图像和牛形象以及一些表意符号组成,其中布满大而有规则的赭石圆形斑点。第三洞只绘有较粗的类似栅栏的竖道。第四洞是两个双腿叉开、双臂伸展的人物图像,有尾巴。第五洞仅有两只牛和一个人物图像。人像头部有两仰角物,尾饰特征显著。松哈尔沟洞窟彩绘岩画在一个高2.5米,宽8米,深4.5米的岩洞内的洞顶。在洞顶十余平方米的岩画上绘有人、动物和其他符号,实为一巨幅岩画。画面中心为一匹有赭石斑点的马,四周绘有羊、虎、牛等动物,人物图像形状与前述洞窟彩绘岩画相同,但与动物图像比较,人形都较小。此外,还绘有六个大手掌印,似栅栏的竖道,赭石实心圆以及虚线组成的不知名图形。从图像看,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多次使用的痕迹。
如果我们将伊犁、阿勒泰地区的洞窟彩绘岩画与广泛分布于西伯利亚的岩画比较,就会发现许多共同点。西伯利亚岩画上的主要图像是萨满形象:(1)鸟头(舞蹈的鸟形人);(2)带有阳具的人形;(3)带角的拟人形;(4)带有牛羊角和鹿角面具;(5)带鼓的萨满。①萨满教曾自公元前2000年后广泛分布于包括西伯利亚、阿尔泰等在内的亚洲北部(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广大地区。伊犁、阿勒泰洞窟彩绘岩画完全可以根据狩猎文化中的典型动物祭祀仪式和与之有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来加以解释:
..各种抽象的模式和形象、人像以及性象征表明:我们不能仅仅用纯粹的和简单的狩猎巫术来解释岩画。性、生殖以及动物世界的繁殖的观念肯定是这种艺术之意义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与狩猎巫术的观念并不矛盾,相反,这是对它的一个重要补充,这表明创作岩画的动机是复杂的,正是这种复杂的动机推动着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狩猎者完成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一切活动,并且通过使用与之有关的图像、图案和仪式来完成这些活动。②萨满教是在氏族生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中,一般称氏族为“昆”(Mukun),“其含义就是一个共同血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男女群团,既是血亲关系的共同体,又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共同体”①。萨满正是在氏族这一特殊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萨满教神灵观念支配下的北方诸民族各姓氏,都有一座数千年来永无休止地精心筑造着的辉煌圣殿。每一座圣殿都是一个氏族的化身”②。萨满岩画的内容题材是多产多育和祭祀祖先。③于是一些僻静、神秘的山洞成了萨满举行生殖、祭祀仪式最理想的场所。山洞中绘制的各种图像和符号正是萨满为本氏族兴旺祈求生育、多猎获动物举行巫术仪式的遗存。虽然举行萨满仪式的情境已不可复现,但这些图像和符号中仍然保留了远古萨满活动的信息。
在西域萨满岩画中保留了法力强大的萨满的最早形象。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为带角的拟人像,这一形象同样出现在杜阿特沟洞窟岩画中,而这些萨满形象无一例外都附有尾巴。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媒介者,他的任务就是沟通地上人类与天上神灵。早期的萨满本身就是巫师,装扮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角”。萨满在一种出神状态下,借助神灵的助佑者——鹿或其他动物精灵与神沟通。头上带角萨满岩画正是象征萨满的助佑神灵。羽毛状头饰、放射状头饰的功能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些人形身下的尾巴往往被误释为阳具,这是不了解早期萨满的装扮所致。从欧洲奥瑞纳文化时期史前岩画发现,岩画上的巫师(萨满)头上戴着鹿角,身上披着兽皮,臀部安有马尾,全身呈激烈跳动状,这就是原始萨满的典型形象。因此,西域洞窟岩画中萨满也应是头戴鹿角、披兽皮、安兽尾的形象。当然萨满也装扮成鸟的形象,羽毛状头饰即属此种。在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还出现戴面具的萨满形象。对萨满的这种形象也有其他解释:“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作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④西域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头戴兽冠、披着兽皮的萨满的形象。在一个氏族里,萨满既是沟通人神者,也是保证氏族繁衍、狩猎成功的力的源泉。从这点看,萨满头戴象征神灵助佑者的鹿冠,身披兽皮正是在进行狩猎巫术仪式,它并不是出于单纯模仿的动机。萨满面具早期也是狩猎祭祀仪式的狩猎巫术面具。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物体的推动力转向另一物体。”⑤之后,面具成为萨满的固定道具,又附加了跳神(包括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供奉等多种功能。
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出现许多图饰符号,与萨满形象绘在同一岩面上,常见的有圆圈形、圆点形、竖道形、手掌形以及由点组成的各种不知名图形等。长期研究萨满教文化的富育光先生认为:
萨满身饰、神器以及任何经过萨满亲自创造的独立图饰,不是随意产生出来的。多数是经过萨满祭祀、祈神之后,从梦幻中、迷痴行为后眼前突显出来的清晰或似真非真、似虚非虚的跳动式曲线,而且持续长时间不见变幻,或通过自己意念促其消逝和冲散,仍然原形跳跃不乱不改,或者经过二至三次梦幻、迷痴行为后仍大致展现如前者,便视为神示信息符号。萨满按其型绘制成雕刻出来,其神示信息符号含义惟萨满所知。因为萨满在求得某种神秘符号之先,依据自己的意念做了祝祷。符号依萨满祝愿而孕生。这是萨满教观念中重要的规训:惟萨满心知,绝忌外泄。认为只有如此虔心,形态迥异的符号图形才具有指点迷津、开导众智、逢凶化吉的神力。①
绘于岩石上的这些表意符号同样是具有巫术效力的,将这种神秘力传递给图符的是萨满。尽管因地域、氏族不同,萨满符号也千差万别,但在成千上万符号中有没有一些同向思维规律的痕迹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原始思维中的共性现象证明了这点。如萨满教用菱形或椭圆形象征女性,用粗直线或箭头形象征男性,用若干竖道表示是同一氏族,若干赭石红粗点表示氏族兴旺、力量,倒“U”形表示天,圆点为不受欢迎,菱形头人形表示女萨满,粗线形头人形表示男萨满,群人联手表示友爱、互助、求援。这些符号虽为明末建州女真所发现的东海当地土人刻在树上的象形符号,但一些符号起源很早,对于理解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的萨满符号也不无意义。
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和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岩画一直被学者公认为是史前的生殖崇拜岩画。这两地岩画的确有许多共性:(1)男女交媾图像;(2)阳具特征明显的群体对人、单人图像;(3)对马图像(仅见于康家石门子岩画);(4)持弓矢人与动物的组合图像;(5)头上的角状物。当然也有图45康家石门子岩画(局部)差异,康家石门子岩画以人物图像为主,主要形体是上身呈倒三角的人物图像,而巴尔达库尔岩画则是人与动物的组合图像,尤其是成对正面相对人物图像在西域岩画中极为罕见。但是这些岩画是生殖巫术岩画还是生殖崇拜岩画,学者们是有分歧的。不过,像康家石门子岩画中“人物形象有不少互相叠压,即在早期刻像的基础上,稍予处理,又重新刻凿”①,这提醒人们,这类岩画是生殖巫术岩画。图像互相叠压或重刻(绘)都是巫术的一个动作,每次刻(绘)也就成了巫术仪式的一部分,刻绘过程亦即是实现人的生殖“力”与动物的繁殖力的传通和交感了。在狩猎文化中,弓箭具有狩猎工具和性象征物的双重意义。岩画中阳具突出的人持弓射动物阴部或持弓箭射动物,甚至干脆就刻一张待射的弓箭,都象征着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殖力的传递和互渗。弓箭、阳具是一种认同原则,刻绘这些图像的目的是为了用巫术操作增殖动物。对马、对人图像(为雄性和男性)都是雄性或男性的象征,刻绘这些图像本身就是求育的生殖巫术。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许多人物图像头部有角状物,下身阳具突出,臀后有尾。这与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的戴鹿头、有兽尾的萨满形象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在生殖巫术中萨满是保证巫术成功的主角,史前先民相信,萨满本身有保证氏族和动物多产多育的神秘力量——巫术。但是人们(较为精明者)发现巫术操作并不能每次都达到预期结果,也不能时时处处都能保证生殖巫术应验,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左右某些自然力。于是“由巫术向宗教的缓慢过渡开始了,生殖巫术开始演变为生殖崇拜,前者是以人的施法动作直接影响,指令生殖,后者是向超验和超人的神去祈求生殖,人类的巫术操作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人类第一次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控制力让给了异己的、超人的图像、符号或神”②。本来是一些生殖巫术的图像,后又成了生殖崇拜的凝固化的永久安抚人心的偶像,在这个过程中,萨满巫术也逐渐让位于乞求神灵的神职功能,图像也越来越向符号化、程式化、类 型化和凝固化发展了。巫术时代结束了,但巫术远未尽绝。
人类何时开始进行人体装饰,已无案可稽,人类学家往往根据现代原始部落民的人体装饰推演人类早期的人体装饰,由此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有人认为:“原始民族的画身(即绘身),主要目的是为美观。”①也有人认为人体装饰就是装饰艺术中最重要、最普遍也最能揭示装饰艺术本质规定性的一种。②虽然审美观念在改进和发展人体装饰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审美观念不是发生人体装饰的原始动机。人体装饰的起源是先民出于功利性目的,也就是说,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并非像现代人那样纯粹是非功利性的艺术审美行为,而是基于原始思维的功能性活动,往往伴随着巫术操作过程。
从考古发现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提供的证据看,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分绘身、文身和人体饰物三大类,而人体饰物则又有头饰、发饰、颈饰、胸饰、手饰、腰饰、脚饰等数种。史前先民人体装饰的动机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形式,如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装置鼻饰时,在西域史前先民中则不存在这类装饰。西域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主要见于考古发现。由于西域干早少雨,一些古尸保存相当完好,能看到人体上的绘身和文身。人体装饰物出土较多,天山以南、以北地区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1)头饰、发式,有发辫、发网、冠饰、发笄等;(2)颈饰,有石、玉、骨、铜、金、琉璃、玛瑙、象牙、草果、珊瑚质串珠;(3)耳饰,骨、铜、金、银质耳环、耳坠;(4)眼饰,眼皮金箔和描眉;(5)胸饰,衣服上片饰、坠饰等;(6)手饰,骨、铜、金、银戒指和手镯以及手指甲涂红等;(7)腰饰,腰际环绕骨管等;(8)脚饰,脚趾甲涂红、脚环等。人体装饰物出土的墓葬大约距今4000~2000年不等。文化人类学家把人体装饰按其性质分为两大类:“(一)固定的:即各种的永久性的戕贼身体的妆饰,如瘢纹、黥涅及安置耳鼻唇饰等。(二)不固定的:即以物暂时附系于身体上的妆饰,如悬挂〓带条环等。另有‘绘身’,一种似乎介于两者的中间,且像是最早的妆饰。”①绘身、文身是在西域史前先民中常见的人体装饰;“黥涅”,即黥刺也就是文身,见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中:“扎滚鲁克墓地一些干尸胳膊上见有黥刺文身者,纹样呈不规则三角纹等。”②见于晚期文献的是关于突厥人“以刀〓面”习俗的记载,《周书·突厥传》载,突厥人在亲人死去后往往“以刀〓面,且哭,血泪俱流”。这种“〓面”自然与“美观”无关,只是以自戕的极端手段沉痛悼念死去亲人的方式而已,也不过是用刀留下“瘢痕”,而非文身。
笔者赞同林惠祥先生关于绘身是最早装饰的说法。由于绘身(即画身)易于褪落,才有了文身这种留于身上耐久不灭的方式。绘身不同于文身,绘身是用各种涂料,如植物、矿物染料,泥土、血液、油脂等在裸露的体表涂抹或描绘,“画身(即绘身)的习惯,在低级文化中最为普遍”③。而文身,即先刺文,然后“是用研细的炭粉,渗入皮下,等到发炎过后,那嵌入的花纹就显出一种永不褪落的深蓝颜色”④。绘身中用的最多的是红色。从新疆出土的干尸中很容易区别什么是绘身,什么是文身。扎滚鲁克2号墓“共葬四个个体,一男三女,男尸为侧身屈肢,身着毛织布上衣,..圆脸高鼻,从脸部看似有文身,其图案似羊角状,头发半白,编成两根辫子,..辫梢加有红毛线;脚穿毛毡长袜,外套白鹿皮长靴。三具女尸,两具已不完整。一具女尸身着过膝的棕红色套裙,也有文身,其纹饰也似大盘羊角状,辫发四根..”⑤该文在此所说“文身”实为绘身。另一则绘身的干尸出土于鄯善县的苏贝希墓葬:“M2中出土一个男性干头颅,面部饰有彩绘,前额正中两竖道,两颊分别有两横道。说明彩纹是在死者埋葬前临时画上的,在实施过程中,应举行过某种宗教仪式。”①苏贝希墓葬被认为是车师人的墓葬,距今约2500年左右,稍晚于扎滚鲁克。尉犁县营盘遗址墓葬的古尸中也有绘面现象。而文身,考古发现不多,仅在洛浦县山普拉M01号墓葬和哈密五堡墓地中发现文身:“个体的肢体已分离,性别不清。山普拉为刺青在带干皮肉的拇指指背上,蓝色,图案有点像人形。”②M01号墓的年代距今约2000年,又晚于苏贝希墓葬的年代。哈密五堡墓葬中的手文见于右手手背、腕部,黥有蓝色花纹。③距今3000年左右。至于用什么颜料绘身,可以从苏贝希一号墓中的眉石去求证。眉石实际上是将矿石磨成粉末,并将粉末用于绘面的用具。眉石见于一女性身旁的一小皮袋内,“同一个皮袋中还装有角梳,黑、红、白三种矿物染料,染料缺口有磨出的沟槽,其作用非常明白,当为化妆用具。以眉石将矿石磨成粉末,如需要可分别涂抹在眉毛、脸颊和面部,起到与眉笔、胭脂、粉相同的作用”④。阿尔泰距今2500年左右的巴泽雷克一、二号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也有文身、绘身现象。一号墓男主人身上刺着家猫一样的动物,有翅,另一动物则为鹿身鸟嘴猫尾。二号墓男主人的手、胸、背和脚上都绘有真实和幻想的动物形象。⑤这些绘身、文身究竟有什么含义?综合各种文化人类学、民族志材料,绘身现象常见于以下活动和行为方面:A.举行入社、成丁礼时;B.作为氏族或集团的图腾标志时;C.参加舞蹈、庆典类活动时;D.作战、血亲复仇时;E.祛邪禳灾时;F.丧葬、举哀仪礼时;G.美观装饰,以期艳丽入时。⑥
文身现象则见于如下活动和行为:A.进行入社、成丁仪礼时;B.作为氏族或集团图腾标志,表示氏族差异,表现群体敌我时;C.显示社会或阶级分层,即等级、地位、身份是否显赫、尊贵时;D.在重大活动,如作战、血亲复仇等前后昭彰坚毅与勇武、耐力与无畏时;E.祛邪禳灾,消蠲祸患时;F.丧葬、举哀仪礼时;G.展示美艳丽姿,追求雄健魁伟时。⑦
在所有这些解释中,追求美观说是最便捷和最不费力的,但也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因为这类假说往往以现代人的审美观去审视史前先民的绘身、文身,使人不得要领。其他若干项解释都有合理的理由,但作为临时性的绘身和永久性的文身可能有不同的功能。诸如入社、成丁礼、庆典、葬仪等仪式中常以绘身方式隐喻一种象征意义,而作为永久性的文身,大概与图腾标志、等级、身份、地位有关,而等级、身份、地位标志是后起的因素。
从扎滚鲁克、苏贝希、营盘、巴泽雷克等墓葬干尸的绘身看,有一些共同现象。一是绘身主要在面部,颜色以红色为主,即为赭石颜料。这种赭石的作用“用以象征鲜血,因而也象征生命,尤其是死者的生命”①。以赭石为颜料涂饰墓穴、绘身的习俗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相当普遍,而且在洞穴壁画中也广泛使用。何以赭石色绘于面部象征死者的生命,勒鲁瓦·古昂解释道:“在格里曼底的卡维荣发现的墓葬独特奇异,是个绝无仅有的实例:一条长18厘米的皱痕涂上赭石颜料,由口鼻部向外延伸。由此到将赭石颜料比作生命的气息或说话的声调,仅一步之差,尤其是因为在马格德林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中,好些动物也画有这种从口鼻部延伸的线条,并被看成是呼吸的表现,所以这一步就更加诱人跨越了。”②无论是扎滚鲁克干尸面部的羊角纹,还是苏贝希干尸面部的横、竖道都从口鼻部延伸到颧骨两颊和闭合的眼目等面部的各个部位,似乎都与呼吸表现有关,应是死者灵魂不灭、生命永续的象征。二是这些绘身均是在人死后临时绘于面部的,显然与丧葬习俗有关。实施绘身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巫术操作,这种巫术主要实施于头部,因为史前先民“在人造的祖先像外,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也作为含有‘灵魂力量’之物而受到崇拜”③,在此,“死去的灵魂”和“活人的灵魂”不能等同,所以绘面只有在人死后才实施,先民相信这种用赭石绘面的巫术是可以安抚死者灵魂的。新疆古代墓葬中的干尸文身仅见于手部、腕部,显然都是生前黥刺的。究竟是成丁礼时文上的,还是获取战功后文上的或是作为等级、地位、身份的标志绘上的,现在还不好妄下断语,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巴泽雷克墓葬中男主人所绘、所文的飞禽走兽组合形象或许就是萨满通神的动物精灵。虽然新疆、中亚地区发现的绘身、文身晚出,但它的起源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史前先民的各种人体装饰物是最容易使人产生“原始艺术”的遐想的。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大量的发现表明贝壳充当了饰品的构件,镶嵌在头饰或颈饰以及手镯或脚镯上”④。不过新疆出土的人体饰物最早为新石器时代,晚至铁器时代。按其年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石、草果、骨、角、牙等为主;第二个阶段以玉、琉璃、玛瑙珠、珊瑚等为主;第三个阶段以铜、金、银为主。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晚期的墓葬中除铜、金、银人体饰物外,同样有石、骨、玉、草果等饰物出土。但早期的遗址中不见铜、金、银等饰物,只有石质饰物。吐鲁番阿斯塔那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物主要是石器和彩陶,其中出土的两件穿孔砾石坠是新疆发现的最早人体饰物了。第一个阶段表明雕、磨、刻、琢等加工技术日益成熟,而到第三个阶段的铜器时代,金属的锻、铸等工艺使铜、金、银等饰物更加精致、精巧化。西域的这些饰物无外乎头部(头发、额前、眼、耳、唇、颈)、腰部(兼及胸部)和四肢(主要是手腕和脚腕)这三个部位。
头饰包括发饰、眼饰、耳饰、颈饰等活动装饰。头部,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尊崇的,只是在人类的狩猎采集阶段,由于头发随意生长,常披到额前挡住视线,很不便于追逐猎物和采集果实,所以只好随便捆扎或辫起了,这完全是一种迫切的实际需要。有了修剪工具和氏族图腾的出现,才赋予头饰更多的含义,甚至与巫术有关,以后又演变成以头饰为主的习俗,后者当然是一种审美需求。发辫是西域史前先民常见的头饰,有单辫、双辫、多辫之分。阿拉沟竖穴木棺墓为战国—西汉时期墓葬,女主人黑褐色头发,“其辫式是先将头发分成若干股(此辫为25股),用5股辫成一辫,然后将辫好的5辫,又相辫成一大辫”①,此为多股单辫,与苏贝希死者发型相同。扎滚鲁克墓葬2号墓中墓主为一老年妇女,头发灰白,两条发辫从耳后垂下,系有红毛线头绳,有描眉、绘前额痕迹。墓葬距今3000年左右。②民丰东汉墓为男女合葬墓,女尸头发为多辫。这种辫发习俗可能和年龄有关,现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婚前往往依年龄梳成同等数量的辫发,而婚后则为单辫或双辫。史载,突厥等游牧部族“其俗被发左衽”,其实“被发”、“披发”、“编发”通指“辫发”。西域史前先民的辫发之俗对后世民族肯定是有影响的。与发式相伴的是发饰,常见的是发网和冠饰。苏贝希3号墓地距今2500年左右,“M6:B女性老年,仰身屈肢..头戴黑毡卷成的牛角状冠饰,头发盘卷其上,外套圆盘形发网,以黑色毛线织成,头顶中间栽植一高帽状毡棒,下端较粗,用毛绳系于颅上,外面也套以黑发网,耸立于颅顶中央,甚为别致”③。M8:A成年女性也同样以双辫盘于头顶,用黑发网罩和冠饰。西域先民的辫发之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孔雀河下游北岸距今3800年前的古墓葬中出土的木制女俑,其头饰为梳短辫,垂于颈后。④该墓葬中男性死者头戴尖顶毡帽,上插禽鸟翎羽。苏贝希墓葬中头部牛角状冠饰与孔雀河古墓中死者头戴尖顶帽是否有同样含义,值得探究。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奇异的圆锥形盖头物,长期以来起过神秘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已失去尊严的意义,而获得了魔术的意义。”①越是在史前,发饰同帽子一样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巫术性’物品”②。“人体装饰不仅见于眼、眉、耳等头部,而且还见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孔雀河古墓沟死者“腕、腰、颈部,见玉、骨、珠饰”“颈、腕部围饰骨、玉质串珠,腰际环绕骨管”,③在此之后的墓葬中屡屡出土这,类人体装饰品。木垒县距今3000年的古墓葬死者耳佩铜耳环,颈戴石串珠;焉不拉克古墓葬中出土多件石、骨、铜串珠和金耳坠,此墓葬距今3000年左右;察吾乎沟口1号和4号墓被认为是距今3000~2500年间的墓葬,人体装饰物质地为石、骨、铜、金等饰品,装饰在女性的颈、手、耳等部位,多者一串骨珠有100多个,还有三个金耳环,5号墓出土牙饰,可能是以动物牙穿孔而成的项链;在发掘的距今2500年前的帕米尔高原40座古墓中出土有石串珠、骨串珠、玛瑙珠和铜、金质饰物,有手镯、耳环、戒指等,特别是铜质饰物有镂孔片饰、梯形片饰、羊角形饰、凹字形饰等;伊犁河流域古墓葬也多出土骨珠、骨环、铜耳环、铜笄、石串珠等。这些人体装饰物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地区跨越4000~2000年间的各类墓葬中,且以头部装饰物居多,如耳坠、耳环、项链等,而且均是女性,只有眼部装饰物发现于男性死者的眼、眉部。民丰县东汉墓葬中男性死者的“右眉和右眼皮上,各放着一小块金片。金片很不规则,也不像是完整的器物”,而女性死者颈戴项珠,为珊瑚石和琉璃质地。④从随葬物看,墓主人是地位显赫者,应属当地贵族。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眼睛以上部位的装饰更多的是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功绩相联系,并更多的具有宗教和巫术的意义的话,那么,眼睛以下各部位,包括耳、鼻、唇、颈、胸、腰的装饰,就更多地是出于性吸引和性选择的动机。”⑤这种论断可能有简单化之嫌。
腰饰、胸饰和四肢装饰虽不及头饰普遍,但也是人体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先民的腰饰早期是腰际环绕骨管,以孔雀河古墓沟墓葬为早期发现,之后在塞人等游牧部落的墓葬中出土铜、金、银质带扣、带钩,也是腰饰之一种。几乎所有的古代游牧部落均使用这种带钩,而最早使用带钩的是塞人,之后,鲜卑、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使用,全都雕饰有动物纹样,前者被称为“斯基泰艺术”,而后者则称之为“鄂尔多斯”风格。对于两者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匈奴式、鲜卑式乃至战国式带钩的形制可能来自异域,纹样武饰也接受了一定外来影响,但是其母题和基本构思却主要是独立的,自成体系和别具传统的。”①鲜卑人的“郭洛带”就是“瑞兽之带”,他们以源自氏族图腾的“神兽”铸镂带钩之上,塞人、匈奴、东胡等游牧部落的兽形带钩也与此同,“绝大多数以动物体造型,尚保持其图腾装饰传统”②,后演变为部落保护神。胸饰多坠挂于衣物上,距今3000年左右的木垒县古墓葬“墓主身穿皮、毛类衣服,胸前挂海贝、串珠,背后、手臂服装上缝有扣形和锥形卷饰件”③。苏贝希3号墓地M25:A墓主为“男性成年,仰身直肢,头戴有护耳的毡帽,..上衣羊皮袄,腰系皮带,上挂药袋、刀鞘等物,无内衣,胸口戴一梯形皮质护身符,其上绘火焰纹和穷曲纹”④,其年代稍晚于木垒县古墓葬。从年代和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这两处均为车师人的墓葬,胸饰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特征。新疆近代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都有佩戴胸饰的习俗,如柯尔克孜族青年女子的坎肩就缀有银质饰物及胸花等,有的缀有几排银币或银扣子,有的还佩戴铸有花纹的圆银片。⑤对于近代游牧民族的胸饰功能,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装饰美或吸引异性注意,也有人认为是炫耀财富。不过古代先民的胸饰总免不了某种宗教含义——往往成为祛魔避邪的护身符。正如汉文文献所言,君子佩玉是为了“以示不祥”、“在宝石或玉成为人类的装饰品以前,是被作为信仰的对象而用来做护身符用的”。⑥大概西域先民的胸饰、颈饰、腰饰、脚饰、手饰等都有这种功能,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装饰物材料质地发生了变化。但戒指、手镯等首饰原初的功能也并非如现代一样是爱情的信物,它们同胸饰等一样起着护身符的作用。这些人体饰物向装饰、审美发展,才逐渐脱离了功利性目的。
史前的这些人体装饰是否也折射着先民的原始审美心理呢?答案是肯定的。“乍一看,原始艺术品从未为审美原因而制造和使用,而是为了宗教和魔法的目的。..然而,恰恰相反,..原始艺术的这种情形要比它初看时复杂得多,通过更详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那种认为原始艺术品的制造和使用行为中完全不存在审美因素的说法存在不少疑窦”①,情形也正如此。绘身所用的赭石固然因其红色有象征生命的意义,但红色也给人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因为红色比较容易从矿物中获取,又特别鲜亮、明快,用红色绘身,客观上有装饰作用,深受史前先民喜爱,也反映着他们在色彩选择上的审美意识。先前先民还注意选取满足视觉、听觉等感官需要的各类材料作为人体装饰物。首先,如耳饰、腰、胸饰、四肢装饰都是一些发出悦耳响声的材料,有石珠、琉璃、玛瑙、骨环、金属饰物等。即使从避邪功能而言,丁当作响的饰物也足以吓退妖魔等恶精灵。其次是闪闪发光的,“在原始人的眼光中,再没有比发光的物件更有装饰价值的了”②。石珠、琉璃珠、玉珠、金、银、铜耳环、戒指、项饰、胸饰都是闪闪发光的。对闪光材料的选择绝不是不经意的,而是充满了审美意识,即使佩戴这些闪光饰物的女性出于吸引异性的目的,也总比非闪光饰物更有诱惑力。最后,除绘身以红色为主外,许多人体装饰物都是色彩绚丽的,而且多半是黑、白、红、黄、蓝、绿等原色,如黑色和白色的石珠,白色的兽牙、项链,红色的玛瑙珠,黄色的金饰,白色和绿色的玉饰等。但是,“我们赋予某种颜色象征性的特殊意义,和原始人的看法完全不同”③,无疑,对现代人来说,色彩是能够表现感情的,进而认为色彩的情感表现是靠人的联想得到的:“红色之所以具有刺激性,那是因为它能使人联想到火焰、流血和革命;绿色的表现性则来自于它所唤起的对大自然的清新感觉;蓝色的表现性来自于它使人想到水的冰凉”④,不过在原始审美中,那种色彩越鲜艳、色感越强烈、对比越明显就越好的意识是肯定存在的,只是某些颜色用于吸引异性注意,而另一些颜色则恐吓恶精灵,以求驱邪罢了。原始审美心理中还不乏对形式的追求,几乎所有的人体装饰物都是圆形的,如项珠、耳环、手镯、骨管,且讲求对称和节奏原则。这是由于“身体的对称形式,使他们不能不作对称的装饰”⑤。史前先民将兽牙、石珠、果实整齐地排成串子,讲求的自然是一种节奏美。铜器时代的梯形、羊角形、凹字形饰物都是呈几何形的对称图形,这反映了史前先民审美实践中更富有变化的对称和节奏原则。在所有人体装饰中,圆形仍然是主导形状,史前先民何以选择圆形,这不能不说与他们的圆形思维密切相关:“这种圆形思维的特质当和新石器时代那些诞生生命而又复活生命的陶器不无关系,它很可能来源于彩陶文化的精神遗传,即生命的生与再生在一代一代人的心目中积淀为一种思维定势。”①史前先民的人体装饰物和另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彩陶就思维和审美心理而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 彩陶:有意味的形式
彩陶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诞生于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出现以后,因此它也成了农业定居文明的标志。在中国,彩陶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不过80年时间,源自仰韶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这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端。近十几年来,彩陶研究则是方兴未艾,真有“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趋势。文化人类学者、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神话学者、美学家..从来没有如此多学科的学者把研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这一神秘的史前遗物,以期对彩陶的制作、器形、纹饰、功能等做出种种解释。但囿于各自的专业所长和思维定势,往往各顾一端,各执一词。考古学家注重年代、材料、器形等基础性工作,艺术史家和美学家则倾心于造型艺术的纯形式分类、表现手法和审美心理等,而文化人类学家则重视其“文化功能”,还有些学者很难划分他是哪一类,欲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中探究彩陶的诸多“干什么”、“怎样使用”和“为什么这样用”等深层次问题,这毕竟比只是回答“是什么”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也时常冒着不能自圆其说的风险,但探索的勇气令人钦佩。彩陶制造者遇到的“怎么样”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现代人也同样会遇到,诸如怎样把一抔泥土捏成器形、怎样绘彩、怎样烧焙以及为什么会制成这种器形,为什么要绘上不同的纹饰,为什么要生用死殉等,或许对史前先民来说,这是举手之劳之事,而对现代诠释者来说,进入先民的原初情境则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诸如彩陶等“原始物品在我们眼中,具有纯形式分类的意义,而在当时制作者和使用者眼里,则具有功能分类的意义”②,故我们必须重构和复原彩陶制作的文化情境。史前先民为什么要制作纹饰各异的彩陶,有没有功能意义,这本身就有文化意味,充满了他们的精神活动。而捏成葫芦等各种器形,又绘以各种精致的纹饰,同样是充满想象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对称、圆形、动物纹样、各种几何图形,除工艺娴熟和丰富的想象力外,还与审美心理相关,这也是一种文化情境。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现代的初学制陶者在陶坊中还不足以制出各种完美的器形呢!对先民来说,彩陶的制作过程和目的是功能性的,也是史前先民审美心理的物化形式。
中国彩陶文化的发生距今已8000多年,延续了4000多年。中国彩陶文化向西传进西域时,几乎晚了3500多年,西域彩陶文化最早起始于距今3500年前,又晚至距今2000年左右时还存在,它成了中国彩陶文化在西部的最后余韵。即使如此,姗姗来迟的西域彩陶文化并没有因中原彩陶文化的终结而衰退,它又以旺盛的生命力存续了1500年左右,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
丝绸之路中段最早的农耕区多在天山南北麓的绿洲区,依次可分为天山东麓区、天山南麓区、天山北麓区和昆仑山北麓区,这些农耕区也是西域彩陶文化孕育和发生的文化区。天山东麓的彩陶分布在哈密、伊吾、巴里坤、鄯善、吐鲁番等地,出土地点有哈密的三堡、焉不拉克、四堡拉甫乔克、五堡克孜尔确卡、庙尔库、喀拉敦等遗址,以及伊吾的盐池土尔衮遗址、巴里坤的石人子、兰州湾子、南湾遗址和鄯善的苏贝希遗址、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阿斯塔那、胜金口、雅尔湖等遗址。天山南麓的彩陶分布在和静、阿克苏、沙雅、库车、焉耆等地,出土地点有和静的察吾乎沟遗址,和硕的新塔拉遗址、曲惠遗址,库车的哈拉墩遗址,阿克苏市附近遗址和喀拉玉尔衮遗址,疏附县的阿克塔拉遗址等。天山北麓的彩陶分布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水库、阿拉沟以及木垒、奇台半截沟、吉木萨尔、伊宁、昭苏、阿勒泰等地,出土地点有木垒河东岸台地遗址、昭苏夏特遗址、四道沟遗址、克尔木齐遗址等。昆仑山北麓区彩陶分布在罗布泊、且末柯那沙尔、扎滚鲁克、洛浦的山普拉等遗址。如果从中国彩陶的西进路线看,最早是天山以东地区和罗布泊流域,然后才向天山以南、以北地区发展。据考古工作者对这些地点出土的彩陶进行碳十四测定,也恰好吻合。哈拉和卓、阿斯塔那、柴窝堡、辛格尔和罗布泊等遗址被认为是距今4000~3500年前的遗址,均零星出土有彩陶。在目前考古还未发掘出更早年代的彩陶之前,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彩陶无疑成了西域最早的彩陶。天山南北麓地区的彩陶大多晚于天山东麓地区,大都盛于铁器时代。
对西域彩陶的质地、制法、器形、纹饰和功用等形式方面,考古学家曾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这对我们进一步探讨彩陶物化的精神,即复原其“文化情境”提供了可资比较的物证。天山以东地区的彩陶以早期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遗址的彩陶(新石器时期晚期)和稍晚的焉不拉克文化(早期铁器时代)以及苏贝希的彩陶具有代表性。阿斯塔那的彩陶多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饰为粗细线条、网状纹等。哈拉和卓的彩陶亦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饰主要有倒三角、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由倒三角向下延长的平行竖条纹等。①两处遗址彩陶器形主要为缸、瓮、壶、钵、碗、碟等。分布于哈密市西部的三堡、四堡和五堡一带的焉不拉克文化“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少数是夹砂灰陶和黑陶,手制;彩陶较多,基本是红衣黑彩,花纹主要有曲线纹、锯齿纹、水波纹、S形纹、倒三角纹、十字双钩纹、竖线纹等;器形主要是单耳罐、单耳钵、单耳杯、单耳豆、腹耳壶,钵和杯的底部一般都穿有小孔,口部往往被切割后又重新打磨光平”①。善苏贝希遗址由编号为1~5号墓地的不同时期的百余座墓葬组成,其中3号墓地就包括30座墓葬。3号墓出土彩陶基本为夹砂红陶,为通体彩,以内饰平行线的涡纹为主,还有网纹和竖条纹,常见的器形有釜、双耳罐、单耳罐、罐形杯、筒形杯、豆等。苏贝希3号墓距今2500年左右。从使用功能看,都相当一致,大多数彩陶作为炊具使用,这些彩陶下腹部和底部都有烟炱痕迹,也有一些与内地彩陶一样作为盛具使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焉不拉克、苏贝希的彩陶绝大多数都出土于墓葬,是将实用器皿作为明器使用的彩陶器皿内都放有祭祀的食物,如小米、羊肉、羊头等。天山南麓区的彩陶以和静察吾呼沟口文化为代表,从距今3000年到2500年不等,先后挖掘编号为1~5号墓地,墓葬密集,考古工作者发掘了600余座墓葬,其中彩陶就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察吾乎沟口彩陶文化由发生、发展、成熟到衰败的演进规律。察吾乎沟彩陶按质地、制法、器形、纹饰、使用功能可分为四期:
一期,A型墓。陶器形体肥胖,假圈足凸底器较流行,口沿下常见一周凸弦纹。彩陶线条粗细不匀,纹样以简单的网格纹和云雷纹为主。主要是局部颈带彩和腹斜带彩。
二期,B型墓。陶器器形向瘦高发展。一期中流行的假圈凸底器和口沿下凸弦纹已消失,颈部常见锥刺纹。此期是彩陶的昌盛时期,纹样精美,处处显示出一种对传统艺术的突破和创新。除局部颈带彩和腹斜带彩外,出现许多结构严谨规整的通体彩。其中的棋盘格纹似给整个彩陶艺术输入一种稳定、统一的因素。
三期,C型墓。陶器器形比较瘦高。单耳带流杯的流嘴上挺,彩陶衰落。颈带彩、腹斜带彩和通体彩不见,兴起的是简单的局部沿下彩。主要为井点纹。
四期,D型墓。陶器腹多下垂。带流杯的流嘴已变成朝天流。彩陶数量不多,纹样为极简单的竖条纹。②
察吾乎沟口文化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手制,器形多平底,带流器形占近一半,主要有单耳带流罐、双耳罐、单耳杯、釜、钵等,器表多饰红色陶衣,暗红色或黑色纹样,纹样以棋盘格、网格、菱形格、三角、云纹等几何图形和动、植物纹构成通体彩或局部彩。彩陶多作为随葬品入葬,多置于死者头前或头侧,器内放有小麦、大麦和粟、肉类等食物,釜等彩陶有烟炱痕迹,是作为炊具使用的。天山北麓彩陶分木垒、奇台和伊犁河流域以及阿勒泰等地出土,其质地、制作、器形、纹饰、功用各有异同。木垒河东岸台地上出土彩陶为夹砂红褐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样主要为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和其他网格纹,器形多为罐类。奇台半截沟彩陶为夹砂陶质,手制,外表均打磨光滑,大部分涂粉色陶衣,个别的是黄白色或白色。在陶衣上以深红色或紫色彩描绘花纹。花纹图案主要是倒三角和网纹,有些倒三角边上有斜刺。最常见的是罐类的口沿至颈部绘两排或三排倒三角,倒三角下面接绘网纹,布满整个腹部,器形基本为罐类,有些表面有烟炱,作为炊具使用,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①伊犁昭苏墓葬出土的两件彩陶壶,均鼓腹,圆底,夹砂褐陶,手制,橙黄色陶衣,红色彩绘,花纹比较复杂,其中一件在口沿处绘一圈倒三角,颈部绘棋盘格纹,整个腹部用粗细折线组成重叠的倒三角,口沿里壁有一圈宽条带;另一条在肩部绘一圈倒三角,三角下接绘网纹或三四个同心半圆纹,口沿里壁亦有一圈宽条带。②昆仑山北麓区以罗布泊地区为主的彩陶均系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纹饰主要为倒三角纹、水波纹、竖条纹等,器形多是单耳和双耳罐。且末县柯那沙尔出土一件完整彩陶壶,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黑色彩绘,颈部绘网纹,颈肩相接处是水波纹,腹部绘内填平行竖线的变形三角,三角之间有平行竖线,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三角之间有平行竖线,口沿里壁绘一圈倒三角,器形为细颈、鼓腹、双耳、小平底。①
西域彩陶从整体上讲是“大同小异”、“同中有异”,但总体趋势是明显的趋同性,“小异”只是反映了时间流变和空间分布上的区域性特征。从质地、制法、器形、纹饰和功用看,至少有以下一些趋同性:(1)质地基本上都是夹砂红陶或红褐陶,不见细泥陶;(2)均为手制,多是泥条盘筑法,不见轮制彩陶;(3)器形主要是罐、盆、壶、钵、把杯等,又以单耳罐、双耳罐、把杯为普遍,且以圆底鼓腹细颈式罐居多;(4)陶衣主要是红色,还有橙黄色和白色,彩绘主要是黑色,也有红色和紫色,纹饰母题主要是实体、大倒三角、其他三角以及由三角演化而来的涡纹、竖条纹等,其他还有网纹、棋盘格纹、水波纹、平行弧线和各种短线等,纹饰不仅绘于器表,还绘于口沿里壁;(5)相当一部分彩陶作为炊具使用,也作为随葬中的盛器,往往盛有粮食、肉类等。西域彩陶的异主要表现在:与内地(主要是甘肃、青海)相比,与这些地区毗邻的天山以东、昆仑山以北区的彩陶都是红衣黑彩,器形基本是单耳、双耳罐,纹饰主要是各种短线、三角纹、水波纹、竖纹等。天山北麓彩陶则多红、橙黄、白色陶衣,红色或紫色彩绘。天山南麓区彩陶是红衣黑或红彩,器形以单耳鼓腹罐为主,纹饰以三角纹、竖条纹、涡纹为主。西域彩陶究竟与甘青彩陶的哪种文化联系更为密切?“新疆的彩陶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马厂类型、火烧沟类型文化及沙井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它们共有的单耳罐、小把杯及彩绘花纹中的三角纹、竖条纹等方面隐显出来”②。这是中原农耕文化西披的直接证明,越靠近东部,这种特征越加明显。但西域彩陶所受的文化影响绝对不是单线和一个方向的影响,否则它就不能称为西域文化了。有些学者根据西域不同地区青铜文化的构成提出了多源文化因素说,包括东来文化因素、北来文化因素、西来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越靠西部、北部,西来文化、北来文化影响越大,而东进过程中又与东来文化汇合,形成一种以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包容其他文化的多元格局。西域彩陶在东部地区主要受甘、青彩陶文化的影响,而“伊犁河流域以铁木里克墓地遗存为代表的这种青铜文化,是中部天山及七河地区相同年代的青铜文化不断向东迁移分布的产物。这种青铜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产生,应与中亚地区稍早阶段广泛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较密切的渊源关系”③。在天山东麓彩陶文化中“还存在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塔加尔文化的某些成分”①。出现这种情况是极为正常的。
尽管考古学家对彩陶进行了田野发掘、层位确定、器形分类、年代测定、纹饰描绘、区域分布等基础性的工作,但留下的还只是发掘和记录,人们仍无法去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精神内涵,“为了有效地回返到彩陶所由产生的石器时代的精神氛围,体悟当时社会的信仰、观念和行为,自然有必要借鉴人类学已有的文化重构方法,把制陶的技术生产活动和农耕文化的整体联系起来考察”②,这不失为一条揭开彩陶文化之谜的有效途径。
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化,被考古学家称为“农业革命”,这是完全不同于采集—狩猎文化的新时代。“在农业革命之前,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觅下一顿的食物,除非他们在狩猎成功后能饱餐一顿。因为人类学会了生产食物——而不是采集、狩猎或收集食物——把食物贮藏在粮仓里和牲圈里,他们不得不而且也有能力大批地定居下来。人类的能量一旦解放出来并且投入到许多新的工作中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专门的非农业的工艺的发展。因而,像诸多如基本机械原理的发现,纺织、犁耕、轮作制陶以及冶金术等许多发明的迅速出现,就决非偶然”③。在农耕文化阶段产生的女神崇拜观念及其活动是普遍的,这与先民把大地视为大地母亲的观念有密切关系。“植物每年死亡和复活,原是在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每一阶段中现成地表现出来的观念;这种不断的衰谢和再生规模巨大,人的生存又紧密地依靠它,两者合起来就使它成了一年中自然界给人印象最深的现象,至少在温带如此。毫不奇怪,这么重要、这么惊人、这么广大的一个现象,它必然会用提出类似观念的办法使许多地方产生类似的仪式”④,而人类神话中最重要的生死母题就是植根于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之中的。彩陶生产的象征意义,如使用的材料黏土、器形、纹饰,无不可以从地母神话或生育巫术仪式之法器的象征功能方面去求解。人类在经历狩猎文化阶段,揖别狩猎巫术后精心选择了大地母神信仰为核心的生殖巫术,彩陶成了生殖巫术的法器,与地母观念有了生生不息的关联:
她反映了人类关于生育与死亡、生存与消亡的基本经验。她是赋予生命的母亲,但同时也是地母,人们死后都要回到她的怀抱里。好些表现这种基本经验的象征都伴随着她:以增、圆、缺三种形象出现的月亮,..还有罐子,这个相当于腹部的容器,新的生命就来自这里。同样,她用来蓄积食物和保存食物的这个罐子,又会变成人们——就像隐藏在母腹中那样——重又回到那里去的墓穴。这是一个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受到局限,可以通观,因为“母亲的王国往往就来自这个世界”。生与死在她身上同时并存,尚未遭到罪孽经验、惩罚经验与异化经验的分裂。①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制作彩陶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产过程,它还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彩陶之谜也必须进入其精神世界进行探索。
晚于陕、甘、青诞生的西域彩陶造型有“依样画葫芦”之感,完全是葫芦形的仿制。从罐、杯、釜、钵、盆、碗、豆、壶等主要器形看,无不是取样于葫芦形,只不过不同器形是横剖葫芦不同截面的组合。早期与晚期器形的不同点并不在其腹部形状的改变,只是颈部长短、粗细和底部(圆底、平底)、带流等的变化。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西域也是普遍生长葫芦的地域,“世界上凡是远古曾生产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容器之前,曾先使用过天然的容器葫芦;而葫芦容器也就是陶容器的现成模型。葫芦的特点之一,是它在青嫩时可作为食物(苦葫芦除外),到成熟晒干后就成为硬壳的干葫芦——外凸光滑,腹空能容物”②。史前先民以葫芦来仿制彩陶器形,“正是因为史前思维将葫芦认作植物所从出的母体和子宫,而且根据这种思维的类比与认同原则,人与地母的子宫也是这种形状,三者同形,功能也相同,可以相互串位和替代,因而陶器依葫芦而造型,所象征的既是植物生殖的母体,也是人与地母的母体子宫”③。西域仿葫芦制作的彩陶主要器形为食具、饮器和炊具,同时也作为葬具,因为葫芦腹大多子,这其中“暗含的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巫术信仰,即通过葫芦状的饮食器皿的使用而将其旺盛的繁殖力传递和生长于人类身上。因为远古的食就是性,性也就是食”④。西域彩陶时代的墓葬中的彩陶中都盛有农作物、种子,或许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死去的亲人完全可以像农作物种子一样死而复生,这种方式大概是希望将地母旺盛的繁殖力、生命力传递给人类本身。因此,活着的人用陶器“吃喝”,并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吃喝本身也有生殖意义,是一种传递生殖力的巫术行为。彩陶取像均为圆形,这种圆形还来源于史前先民的圆形思维,它的功能也是一个圆。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先民的圆形思维来自于农作物依四季死而复生的启发,在此,时间无所谓有始,也无所谓有终,一粒种子埋入土中,生长、开花、结果,然后又循环往复,始就是终,终也是始。这种圆形时间观又类推到人的生死,瓮罐葬、屈肢葬、彩陶盛粮食种子随葬,都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圆,人死后埋葬并不是死亡,只是回到大地母亲的子宫,是完全可以死而复生的。女性制作彩陶的仪式,以彩陶为盛具吃喝的仪食,以瓮罐、屈肢、圆形墓堆的丧葬仪式都是史前先民源于圆形思维的巫术仪式,它充满了生殖(包括人的繁衍和食物的生产)巫术信仰和行为的旺盛生命力。
在彩陶文化情境中,最不可索解的是纹饰,人们往往以艺术审美的眼光诠释这些纹样,无论是动植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于是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如“观物取象”、“抽象变形”、“模拟自然”等。但人们似乎忽视了彩陶纹饰同彩陶的选料、制作、器形一样是具有功能意义的,“彩陶纹饰则严格地与器形(还有质料)一起联合表意,整体地充当巫术施法的工具”①,它们共同表达一种“力”的观念,在彩陶产生的时代还有比生殖力更重要的东西吗?西域彩陶中反复出现的主导性纹样——三角形,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西亚、中亚、北非、希腊彩陶纹饰中都有这种三角形图案,中国彩陶文化的各种类型中也是所谓的蛙纹、鸟纹、鱼纹与三角形等几何纹样伴生。从整体上看,彩陶的主导纹样均与生殖母题相关,“生殖崇拜是统摄了彩陶艺术创作的一个主导性观念”②。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作比照。该岩画被认为是西域猎牧部族的岩刻作品,与西域农耕文化中的彩陶属同期。康家石门子岩画的主体是裸体的男女群像,他们的身体造型,尤其是上身躯体无一例外全是倒三角形,一些单人、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的人体造型,除头部外,自上而下完全是倒三角形,分不出上身和下身的区别。这完全与西域彩陶中的倒三角形纹样不谋而合,这绝非偶然,都是一种生殖力的张扬。不过,史前猎牧先民选择如此僻静、肃穆、万木茂盛的天山深处举行神圣的生殖巫术仪式时,农耕先民则选择了来自地母的彩陶进行这种生殖巫术仪式,这只能说是殊途同归。事情远不止如此,在罗布泊地区小河5号墓地出土的“许多箭杆上面雕刻有横向排列的三角纹,三角形内部涂以红色,花纹呈条带形排列,每一条带包括两组相向排列的三角形”中诸如三角纹、水波纹、涡漩纹、网纹等是先民装饰艺术的变形结果,我倒相信这样的结论:“(先民)在陶器腹部每绘制一根线条、每涂上一种色彩,都是在进行一种巫术操作。在巫术的意义上,陶器尤其是彩陶可以说是集天下生殖力之大成:它的质料来自大地母亲的血肉——黏土,它的造型取像于大地母亲的子宫,它的器腹上又绘满各种具有生殖感应能力的纹饰,难怪它在远古先民心目中有崇高与神圣的地位呢!”①卫聚贤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多有三角形如‘▽’的花纹,即是崇拜女性生殖器的象征。”②
当我们以一种艺术眼光审视彩陶文化时,谁也不能否认在彩陶的线条和色块中所具有的节奏、韵律、对称、均衡、连续、间隔、重叠、粗细、疏密、交叉、错综、一致、变化、统一等形式规律表明史前先民审美心理机制的客观存在。浑然天成的圆形,神态毕肖的人物、动物造型,错落有致的对称纹饰,带流的完美形态,诚如博厄斯所言:“在图画中和造型艺术中对对称、节奏之类的形式的强调并非像进化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是艺术渐进过程中的产物,而在于双手运动的对称性以及对人和动物左右两侧都是对称的观察而得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节奏的反复循环常出现在处于水平线的带状事物中。如树木、山、云、腿、身体、翅膀等都处在水平状态中。节奏的形式和技巧过程的关系最密切。..最简单的技巧过程总是产生简单的同一运动的重复。与此同时,愈来愈复杂的技巧则构成艺术鉴赏的尺度。鉴赏力愈发展,复杂的节奏就愈易于出现”③。千百次的重复,循环往复,或许就是这种最初的审美机制发生的缘由。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彩陶的制作是出于审美的动机,因为即使像彩陶的这种装饰“却并不具有它自身的目的,它只是为了强化巫术工具的力量。这样,也就很难说它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动机,因为即使存在着有审美价值的纹饰,它的单纯的巫术工具性质就排除了审美的动机”④,我们万不可把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强加于史前先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先民制作彩陶的原初动机。
第三节 女性雕像的地母情结
人类在母系社会阶段,女性是一切的主宰,农耕是靠女性发展起来,彩陶的制作者也是女性:“农业的发明是妇女的功绩,不仅因为妇女是主要的采集者,其后又成为初期农业的发明者;还因为初期农业主要是由妇女们承担和领导的。北美印第安人如易洛魁人、祖尼人、亥达沙人,非洲东南部的许多部落,以及新几内亚的巴拿罗人等,在农业活动上就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由妇女们选出一个年长而精力充沛的管理人领导农耕工作,而这个管理人还可以选择一两个人作自己的助手。随着锄耕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男子变成为农业方面的主要劳动者了。”①在这样一个母权制的社会中,妇女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农事、制陶、生育,这些主要由妇女从事的工作都被赋予一种神圣意义,女性自然也就成了受崇拜的偶像,女性雕像也应运而生。新石器时代的女性雕像(无论是象征丰产的还是生育的)都可以追溯到她的原型——大母神,尽管她有不同称谓,如原母神、大母、大女神等,但含义是相同的,“特指起源于父系社会之前的最大神灵,是狩猎的史前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原始信仰中最早出现的神”②。它起源于先民的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想象:“在这种原始状态里,人的意识和自我还很弱小,尚未发展。作为初始的、对立面容纳于其间的象征,乌罗伯洛斯是‘大圆’(the‘GreatRound’),正面和负面,男性和女性,意识因素、与意识对立的因素和无意识因素,在其间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乌罗伯洛斯也是混沌、无意识和心理整体未分化状态的象征,而这种状况,被自我经验为一种不确定的两可状况。”③在任何一个自我意识弱小、未经发展而无意识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都能见到女性的基本特征:大圆、大容器的形态,它包容万物,而万物又产生于它。“假如我们把初民未定形的身体—世界等式同女性基本特征的等式女人=身体=容器结合在一起,我们便为人类远古时代得出了一个普遍的象征公式:女人=身体=容器=世界。这是母权阶段的基本公式,在这个人类发展阶段里,女性支配男性,无意识支配自我和意识”④。这完全为考古学材料所证明。有学者对已知的石器时代的雕像进行了性别统计,发现女性雕像是50件,而男性雕像仅有5件,且这几件男性雕像不合定型而且技巧拙劣。⑤文些女性雕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矮胖,肚腹和乳房、臀部往往畸大,它们的主要象征意义都是圆形容器;而另一类是细长而纤弱,身材修长,只是突出乳房、阴部等女性特征。“这些无定形的大母神塑像是孕育的生育女神的造型,在全世界,它都被当作怀孕和生育的女神,而且作为不仅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崇拜对象,它也被视为生育力的原型象征,遮蔽、保护和滋养的基本特征的原型象征”⑥。人类认识自身生产、种族繁衍的奥秘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物生人,人是由某动植物或无生物生出来的,这一阶段虽然缺乏物征,但神话中有大量资料可以回答人的来源;第二阶段是感生,人是由母亲生的,母亲又是受感应而生的,感生神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父权制确立后,出现新的生育观念,概称性生,即通过男女交合而生育后代。①在母系社会阶段,先民始终认为人类的生育是一种孤雌繁殖,这种孤雌繁殖是将女性创造生命认同于大地创生万物的结果,“在多产和生殖中,并不是妇女为土地树立了榜样,而是土地为妇女树立了榜样”。②从这个意义上讲,生育信仰也是一种地母信仰,女性和地母是同义语,具有相同的繁殖(生产)功能,在一个孤雌繁殖信仰相当普遍的社会,达到生殖目的的有效手段就是生殖巫术。
丝绸之路西域最早的女性雕像发现于孔雀河下游被称作小河墓地的地方。维吾尔人奥尔德克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罗布荒原上神秘地方的人,时间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奥尔德克做向导,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到了小河墓地并首先向世人披露了他在小河墓地的发现,引述如下:
这个经过长时间寻觅的墓地距“小河”岸4公里,位于一个浑圆的小山包上。..小山的表面,特别是在山坡上,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弯曲的厚木板,不论走到哪里,脚下都会绊到久经岁月摧蚀的人骨、被肢解了的木乃伊和厚毛织物碎片。..在小山的西端,有一道略呈曲线排列的木栅栏,栅栏的木杆比较细,且不很直。在小山顶部稍靠东一些,又有一道木栅栏,这道栅栏的木杆较粗,其顶部都在同一高度上。..在大栅栏正东侧的自由木杆相互挨得很近,几乎全部都非常高,平均高度达4.25米,杆子的直径都大致相同,约25厘米。它们全部是多棱柱,具有7~13个表面。将柱基部的沙移走后,可见其表面曾被涂成红色。杆子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颜色已消失殆尽。看来这座“死神的立柱殿堂”曾经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红色之中。..制作颜料的材料是红赭石。..这里的一个有趣特征,是桨形纪念物,它们许多还矗立在原位,另一些已全部埋入沙中,另有15个落在了山坡下。..桨片的下方通常有一条由数道经向刻线组成的装饰带,装饰带也曾被涂成红色。..小山的最东部近乎平坦,而且只有一根直立的木杆。这是唯一的一根具有经向沟槽的木杆,沟槽宽约1厘米,槽与槽等距。..整个小山的北坡、东坡和南坡,散落着各种尺寸的棺材板、倒下的木杆、木桩和桨形纪念物。..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所有的棺木都是同样的结构(亦被后人称为的船形棺——笔者)。①
这是距今近4000年的西域早期氏族墓葬群。遥想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庄严仪典?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神秘气氛的地方出土了西域最早的女性雕像。在贝格曼之前,斯坦因曾在楼兰附近的墓葬中发现过一些小型女性雕像,其中一具木质女性雕像,高70厘米,无腿,面部呈平面,用红赭石粉绘制出五官,另一具女性石像仅高10厘米。贝格曼发现的雕像为三具,其中一具为男性,两具女性雕像,分别高134厘米和158厘米,但是贝氏并未对这两具女性雕像的特征作过多的描述,只对一具保存较完整的雕像描述道:“女性雕像面部为椭圆形平面,上面可能曾经绘有五官。双臂极细,几乎不成比例。腿部雕刻完整,小腿极粗,可分辨出球形的膝部。”②参照贝格曼所拍摄的照片,发现这两具女性雕像的性器特征是明显夸张变形。小河墓地的女性雕像并非个例,孔雀河古墓沟、哈密焉不拉克文化等都出土有距今4000~3000年前的女性雕像。考古工作者在孔雀河古墓沟发现的距今近4000年的石质女性雕像仅高27.5厘米,用白石雕刻而成,方头,眉、眼、嘴、鼻均用黑色竖横线表示,颈部阴刻三道弧线表示服饰领口,胸部突出女性乳房特征,束腰系带,下肢简略。同一地点出土的木质女性雕像,属距今3000年左右的物品,雕像用整木雕刻,头戴圆帽,未雕五官,身体扁平,乳房下垂。另两件男女木雕像则出土于哈密焉不拉克,距今3000年,用原木雕刻。男女面部的嘴、眼等五官用阴刻方式表现,四肢刻划具备,但雕刻僵直刻板。从身体轮廓看,女性显粗壮、高大,男性纤细、矮小。男女性器均夸张变形。发现女性雕像的墓葬中均出土有麦粒、谷粒等农作物,是西域农耕文明发祥的地方,也是西域彩陶文化的发源地。巴里坤县甲山沙墓葬中出土两件铜石并用时代的青铜器女性雕像,其形象是大腹丰乳,我们看到了身体=容器的原型等式。
小河墓地足以让我们对罗布泊地区史前先民遗物——那高大的红色多棱柱和桨形物,无底的船形棺;那雕刻粗糙,连脸部五官都不清,但性器特征十分明显的并非艺术品的女性木雕像...产生无穷的联想。特别是神秘的雕刻有蛇形的木桩:“这是一根直木桩,上面的刻纹描绘出一条蛇正在吞食一根线轴形木桩。蛇背用密布的小菱形表示,菱形内涂以红色,肚皮间刻横线和成排的小三角。这些刻纹意欲代表蛇鳞和蛇身图案。...(另一根类似的蛇纹木桩)的中部附近有一小孔,可能用来拴悬挂的线绳。”①箭、梳子、小木梳上反复出现的众多三角形纹饰;红色是这个世界永恒的色彩。这些究竟寓示着什么?对此,我们不能不从罗布泊地区的史前文明说起,整个孔雀河下游地区既是畜牧和农耕兼营的地区,也是西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一地区“农业是存在的,墓区发现的小麦粒,是一个直接的说明。...孔雀河谷可得灌溉之便,少量的农业经营是完全可能的。...而小麦,最早可能在新疆种植。...除畜牧业、少量的农业生产外,渔猎是人们生活的补充”②。从这较有保留性的估计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完全不同于采集—狩猎文化的畜牧—农耕文化已经出现了,人们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与他们生死相依的土地。早在4000年前罗布泊地区就属于干早、半干旱区,沿河、沿湖分布有绿洲。“现有的资料表明,通常是那些半干早的地区..有较丰富的但绝不过多的可采集的食物资源,往往是栽培与驯化发生的最重要的中心”③,西域早期的畜牧—农耕文明都是这样产生的。要揭开发生在畜牧—农耕文明诞生时期的小河墓地红色多棱柱、船形棺、木桨、蛇形木桩、女性雕像、三角符号等千古之谜,非得触摸史前先民的思维、信仰、观念、心理等深层文化机制的脉搏不可。较之采集—狩猎文化时期,畜牧—农耕时代先民的思维、信仰、观念、心理,即精神文化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大大扩充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范围。对舒适的定居生活和有规律的岁月循环的习惯、农业收成作长期耐心等待的必要性(加之农业收成还会遭到各种灾害,如天灾和兽害等),根据天象精确地计算时间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使得农人们对天、地、日、月、雨、雹等自然力空前地关注,他们把这些自然力崇拜为神,很多事情现在都得依赖这些自然力的作用。伴随着这种泛灵观念的发展,还大大加强了对丰产和繁殖的崇拜,对女神的崇拜(可能是对地母的崇拜),这种女神的石像和泥塑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发现。农人们对“阴世”生活也采取了新的态度。看来,对丰产和一年一度的枯(结果)荣(发芽)的崇拜,产生了关于死者可以复生的观念。因此,葬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①
这个时期先民的精神领域的变化主要是:(1)农业巫术代替了狩猎巫术。在一个粮食并不丰裕的社会,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歉收时,就必须实施巫术,保证粮食足以果腹,因此农业巫术也是一种丰产巫术。(2)根据先民类比和认同的原则,大地生长出谷物是有周期性的(生长、枯荣),就有了将女性与大地认同的巫术信仰。将大地丰产和女性生殖的认同,正是母系社会的普遍信仰,在一个“知母不知父”的社会,女性是所有生产活动的主宰。在此,地母与女性是一种同义认同。(3)人是可以死而复生的观念的形成。人“死”后入土为安,实际上意味着回到了大地母亲的子宫,他们像农作物枯荣那样是可以再生的,这同样是一种圆形思维。由女性主持的神圣葬仪也就成了一种生命回归的庄严仪典。(4)从新石器到铜石并用时代,史前先民的生育信仰经历了由大地生人到两性交媾生人的转化,西域出土的性器夸张变形的男、女木雕像是最有力的证据。
一些学者把女性的基本特征分为正面基本特征和负面基本特征。女性的正面基本特征的中心是容器,它既是女性性质的属性,也是女性性质的象征。在那个“真实生活”也是“象征生活”的母系社会中,鼓腹的彩陶、丰乳肥臀的女性雕像、蛇、隆起的地乳..都与容器有关,是代表丰产和生育的地母的象征。于阗,梵文称为“瞿萨旦那”,意为地乳,其建国传说显然源于早期的地母崇拜。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小河墓地乃至焉不拉克出土的女性雕像,几乎都没有五官标记,或只有用横竖线条表示,但夸大了乳房、臀部、性器等特征。这些女性中五官经常缺失的基本特征的意义在于:“丰足性是人的正面原始经验之一,是他对女性作为提供营养的容器的经验的一部分,因此乳房得到了强调。”②至于贝格曼在小河墓地发现的蛇纹木桩,他小心谨慎地认为:“此二蛇形物的确切用途尚无法确定,我们仅知通常巫术及医药界都崇拜蛇。像青蛙是雨的象征一样,蛇被一些权威认为是促进生育的原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蛇也经常被作为阴茎的象征。”①贝格曼已经踏进了揭开这个千古之谜的门槛,却裹足不前了。蛇与生育的关系都源自那个诡秘的“乌罗伯洛斯”——衔尾环蛇,是初始原始状态心理状况的象征。“由于它的乌罗伯洛斯混成性,蛇象征也可以表现为女性。因为女性容器是创造性的,子宫是神圣的部位,在身体象征系统中具有真正神秘的特色,而且像每一种神秘事物一样,它是情感矛盾、意义暖昧的。蛇以附属的角色与之相关,就像男人和阴茎因素,它成为女性的一部分,或作为其伴侣”②。作为代表生育力的地蛇,它是地母的一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讲蛇是女性的象征,也是生育力的象征,小河墓地的蛇形木桩很可能就是实施生殖巫术的工具。
女性的负面基本特征也是在女性意象中被感知:“往往表现为死亡和毁灭,危险与困难,饥饿和无防备,在黑暗恐怖母神面前表现为无助。”③“这样,大地子宫变成了地下致命的、吞噬的大口,等同于受孕的子宫、防护的地洞与山洞、地狱的深渊、深藏的暗穴、坟墓和死亡吞噬的子宫,没有光明,一片空虚。正是这个产生生命和世间一切众生的女人使他们返回到她自身,她追捕着她的牺牲品,用她的陷阱和罗网抓住他们。疾病、饥饿、艰难困苦,再加上战争,都是她的帮手,而在一切人群中间,战争和狩猎女神都表达了生命乃女性之血的人生经验。这位恐怖母神是饥渴的土地,它吞食自己的孩子们,用他们的尸体来增强自己的肥沃;它是老虎和兀鹰,兀鹰和棺材,是饕餮地舔尽人与兽的血精的食肉石棺,然后,再次孕育、滋养生命,使它重获新生,再不断地将它们抛入死亡的深渊”④。面对死亡、恐惧、痛苦,人们并非无能为力,直觉使人们相信,通过痛苦和死亡、献祭和肉体与灵魂的泯灭而能达到更新、再生和不朽,也就是说死亡是回归母亲容器,这是变形物完全溶入女性的原则,这些容器不论是骨灰坛、棺材、洞穴,还是船、土、水等。这些容器与其他一些物件象征地关联在一起,出于先民“无所不包”的心理真实,先民是将整套关于女性生命的心理象征投射于现实世界,变成了笃信不疑的巫术仪式。在小河墓地地表矗立着的近200根高达4米多、直径在25~50厘米的红色多棱柱和30多个红色桨形物,以及同样是红色的木栅栏究竟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在一个可能是几代人使用的氏族公共墓地,如此兴师动众,费力费时树立这些“纪念物”绝不是史前罗布泊人的一时冲动所致,而仍然出于把容器视为女性基本特征的象征。容器的“掩蔽结构”赋予冥界的住宅——坟墓以形式,正如它赋予地上的住所房屋和天上诸神的居所圣殿以形式一样,在利西亚和小亚细亚,房屋是“这个古代母权国度的废墟上发现的坟墓和圣殿的精确副本”①。由于在母系社会,房屋的设计和建筑是女性的特权,于是房屋、坟墓、圣殿、房屋的支柱、栅栏、围墙都是大母神的象征。从考古发现得知,最初的氏族公社聚落、房屋都是一个大圆,它源于大圆巫术思维,像子宫、中心或世界一样,显示出女性的特征。在一个容器象征的“掩蔽结构”的冥界,还能有例外吗?母系社会早期一些卫护女性分娩场所的原始围栏(栅栏)等变成了圣地的标志,而生育过程也变成了再生过程,在以后的神秘仪典中,人要新生(再生)必须经历冥界危险的旅行。在经过多重栅栏、巨型多棱柱和桨形物组成的多重门后,死者才能再生,获得新生。红色在女性基本特征中总是担任双重角色:它不仅是代表生育力的积极颜色,也是灾难、罪恶、流血和死亡的颜色,同栅栏、木柱、大门等一样都是女性大地——子宫的象征。小河墓地显然是史前先民进行这种再生巫术仪典的神圣场所。墓葬中的无底船形棺、草篓中的麦粒、粟米、几捆麻黄枝、绘有红色的三角形图案的物件等墓中物品同地表物件一样都属于生育祭奠的范畴,有死而复生的巫术意义。特别是船形棺也与女性象征有关:“因此古代的船只常常是‘怀孕的女性’,也因此它们的命名强调女性的拯救功能”②。“作为诞生之地,作为拯救之路,作为死者之船,船是开端、中间和终结之木。它是作为命运女主人的三合一女神,也是树母神,她庇护着人的生命并引导他从地到地,从木到木,最终返回到她自身”③。否则,史前的罗布泊人就不会在墓地上制造如此多的多棱柱、栅栏、桨形物、船形棺。
生育与死亡、白天与黑夜、大地与上天、房屋与墓穴、太阳与月亮、欢欣与恐惧..这种正面与负面的两极因素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二重性。在母系氏族社会,它源于对自然界出生、成长和死亡的复杂节律的朴素认识,形成一种圆形思维,由于这种宇宙性意义和女性的生育力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以“大圆”为象征的原型单位。西域的史前女性雕像及其诞生地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地母丰富多彩的形式的原型心理世界,它也构成了母系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岩画与巫术
正当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东部、南部绿洲发生农耕民的彩陶文化时,其北部、西部沿天山、阿尔泰山地带则开始兴起猎牧民的岩画文化。发生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这一幕绝不是偶然的。在史前,先民在这些造型、绘刻形象中蕴涵的是精神指向,岩画和彩陶一样,是一种精神象征,而不只是一些物化形态。要探究这些岩画的奥秘,仍然要像索解彩陶一样,进行一番精神寻根。
尽管诸如岩画等原始图像在我们眼中有形式分类的意义,但在史前先民眼中则具有功能分类的意义。我们曾先入为主,对岩画进行着违背史前先民意愿的纯形式分类,于是仅仅根据图像,简单、率直地把它们分为舞蹈图、狩猎图、放牧图、杂技图、车辆图、动物图、印记图等,甚至还认为某些岩画是裸体艺术、人体艺术等。这种形式分类或许可以走一条捷径,但望图生义的结果离岩画刻绘者的初衷则相差十万八千里,就会更加远离岩画的文化情境。
在众多的西域岩画中,的确存在一些有史时代,甚至近现代的创作,但剔除那些有意无意的仿作外,其贯穿的巫术信仰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几乎都是巫术思维的产物。其实在古代,巫术思维并不是史前先民的专利,它的精神嫡传一直泽被于后世。英国学者基思·托马斯在《巫术的兴衰》一书中分析的就是16、17世纪英国盛兴的妖术、占星术、占卜术及形形色色的大众巫术,以求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迄今在新疆一些偏远地区还存有治疗、求子、取名、祈雨、防厄等巫术的遗迹。在一个充满巫术思维的史前社会中,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制陶、农耕、狩猎、生殖、雕刻女性像、人体装饰、绘刻岩画又怎能离开巫术思维呢!这些制作、劳作、绘刻的过程就是巫术操作的过程,都与生殖(人口的繁衍、动植物的丰产)有关。因此,西域史前和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岩画都与生殖巫术或狩猎巫术有关,其中不少还渗透着萨满教的信仰。只是由于西域众多岩画无法像出土文物那样易于断代,其中的一些难解之谜还有待时日进一步破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岩画精神实质的剖解和诠释。
考察西域岩画就会发现,它是沿西域南北草原带分布的,这个草原带是欧亚草原的中间地带。在这样一个广袤的草原地带,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里海,北起西伯利亚,南至昆仑,又形成若干岩画区域,如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阿尔泰山岩画、天山岩画、昆仑山岩画、西伯利亚岩画等。这个岩画带虽然只是世界性岩画(世界各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发现岩画)的一个单元,但它在世界岩画和中国岩画系列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在内的草原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狩猎、畜牧文化,要研究史前狩猎、畜牧文化,非在这些地区寻觅踪迹不可。新疆境内沿阿尔泰山系、天山山系和昆仑山系发现的岩画多达150多处,且这还不是最终的数字。如果要在欧亚草原带选若干代表性的岩画点进行研究,新疆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因为猎牧先民的游移性,新疆的天山岩画、阿尔泰山岩画、昆仑山岩画与阴山岩画、西伯利亚岩画、中亚岩画、西藏岩画之间都有一种天然联系,这为对这些不同地区的岩画进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对岩画的微观透视和宏观把握并不相悖,在微观剖析中把握宏观意义,或以宏观神野对一系列岩画图像进行精道的缕分条析,两者的旨向是相通的:进入猎牧先民绘刻的真实世界。但是一些研究者往往误认为微观分析就是按现成思路对岩画的类型、图像、分布地点等作简单的陈述,却极少进入岩画绘刻者的精神世界作深度探索;而一些宏大理论也因为大而无当,或干脆照搬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留下了无可挽回的硬伤。如果我们旨在通过岩画“复原”或“重构”史前先民的文化情境,那么宏观与微观结合就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一种正确、合理的方法往往成了打开岩画之谜大门的一把钥匙,我们在研究中就会游刃有余,否则不是浅陋就是误入歧途。
什么是岩画,迄今并无公认的定论,也没有周密的界定,有些学者侧重于艺术角度,认为岩画是一种在洞窟、崖壁、岩床、巨石上绘、刻、雕刻的艺术品;①也有学者认为是刻或画在岩石表面的图画;②还有学者从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婚姻形态界定岩画,认为是部落先民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③如果从凸现岩画的本质特征而言,第三种界定较为合理,尽管并非十全十美。岩画可以分为洞穴岩画、崖壁岩画和单个大石岩画,制作图像的方法有涂绘、刻画、凿刻等手法。从性质上看,岩画应界定为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无论因岩画空间分布和时间跨度有多么悬殊,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认定它是岩画,这可以排除一些人为因素,使岩画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那么西域有哪些岩画是属于“在岩石上记录原始意识的遗存”呢?据已经发现的岩画,除某些个别为后人的游戏之作外,绝大部分都在这个范畴内,无论是史前的还是有史以来的。阿尔泰山系岩画分布于阿勒泰、青河、富蕴、布尔津、福海、哈巴河、吉木乃一市六县辖区内,④90%以上画面反映有动物形体。⑤这些岩画中刻绘的动物形象有洞角类、鹿科类、犬科类、豹类、马科类、骆驼科类、野猪科类、象科类等,多达数十种,其中如亚洲象、麋鹿、野牛等动物早已灭绝。阿尔泰山系岩画中最常见的动物形象是洞角类的盘羊、北山羊、岩羊、羚羊以及鹿科的梅花鹿、马鹿、驼鹿、驯鹿、麋鹿等。阿尔泰山系岩画中还见有洞窟岩画,富蕴县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被认为是男女交媾生育和萨满教信仰岩画。阿勒泰市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亦属此类型,不过是增添了动物形象而已。其他还有别列泽克河上游的洞窟彩绘岩画,均用赭石绘制。天山岩画按分布区域大致可分为东部岩画、北部岩画和南部岩画。天山东部岩画分布在巴里坤、伊吾、哈密等市县境内。巴里坤以兰州湾子、李家湾子、大小夹山、卡墙子、塔斯托贝、小柳沟、阿希哈赖山等处的动物(北山羊)岩画、狩猎巫术岩画以及刻绘符号居多。伊吾也是东天山岩画分布较集中的地区,现发现的岩画点有乌勒盖、白杨沟、科托果勒、卡塔布齐、白芨等地。这些地方岩画中的动物图像有北山羊、盘羊、鹿、骆驼、马等,还有反映狩猎巫术的岩画以及一些刻绘符号。哈密市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其东北沁城区白山上,属凿刻型岩画。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数百幅岩羊、大角羊、鹿、骆驼、牛等动物图像岩画和狩猎巫术的岩画。天山北部岩画自东向西沿天山北麓分布,岩画主要分布在昌吉州的木垒县水磨沟、芦塘沟、奇台县北塔山、米泉市白杨河、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等地,塔城地区的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托里县的玛依山喀拉曲克牧场,博尔塔拉地区的温泉县苏鲁北津,伊犁地区伊宁县的卡约鲁克沟、巩留县的萨尔布津、昭苏县的阿克牙孜沟、特克斯县的唐姆洛克塔什、库克苏河水电站、科克苏、阿克塔什和尼勒克县的塔特郎、却米克拜、新源县的喀拉汉德沟、克孜勒塔斯等处。天山北部岩画除与阿尔泰山和天山东部岩画常见的动物岩画、狩猎巫术岩画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被学者们称为生殖崇拜的岩画,如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大型生殖崇拜岩画、裕民县巴尔达库尔生殖崇拜岩画、木垒县博斯坦牧场狩猎巫术岩画等。天山以南的岩画有托克逊县科普加衣岩画、温宿县岩画等,均以动物图像和符号为主。昆仑山系岩画发现不多,主要有和田地区的桑株岩画、克依刻图孜岩画、康阿孜岩画和且末县莫勒恰河山口岩画等,也以动物图像,如北山羊、黄羊、盘羊、野牛、骆驼、牦牛、鹿、羚羊、野驴、马等为主,同时也伴有刻绘的人物形象和符号标记。有些人物形象被似是而非的命名为舞蹈图和杂技图等,这是完全不了解猎牧民刻绘这些图像的意图所致。那么,这些史前猎牧民究竟通过刻绘岩画要表达什么意图呢?或者说,这些史前猎牧民为什么要绘刻这些岩画呢?
从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的这些岩画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野生动物形象,只有极少数如马、狗等为家养动物形象,而且出现的人形图像或与动物间有某种关系,或是象征人类生殖的组合图像。这表明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后期伴有少量畜牧业,即使在游牧社会,也不完全排除狩猎活动),人们最关注的是氏族人口的繁衍和猎取动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猎牧社会的文化也是一种产食文化,但是天灾人祸并不能完全保证人口的高存活率和每次都能猎获动物。在这样一个前科学时代,巫术思维的产生直接导致人们借助于运用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巫术的世界。开始,原始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力’。奇妙的‘力’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存在和石头的坚硬、水的湿润一样的确定无疑,和现代物理学上‘以太’一样的普遍。这种‘力’仅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超自然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真实的和自然的”①。人们在信奉神灵之前,是普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的。正如弗雷泽所言:“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②巫术思维导致的是巫术操作。岩画正是施法者实施巫术操作仪式的工具。这种巫术思维和巫术操作一直从旧石器时代起,经过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有史时代。西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都充满着这种巫术仪式。
弗雷泽认为,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和物体相互接触后中断接触可相互作用,他把前者称为“相似律”,后者称为“接触律”。由此,基于相似律的巫术叫作“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的巫术叫作“接触巫术”。而这两种巫术都归于“交感巫术”。“因为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③。猎牧社会的狩猎巫术、生殖巫术都是一种交感巫术。岩画作为实施巫术的工具,其制作的图像有自足图像和非自足图像之分。所谓自足图像是“施法者(人)在图像中并未出现,但是,只要动物图像和施法工具同时出现在同一画面上,也可以将这种图像称为自足型图像,因为画面本身中出现的因素已经足以构成一个施法动作和巫术事件了”④。自足图像是把施法者的施法动作(绘刻)保留在图像画面上。有些岩画图像有动物叠压、覆盖的痕迹,反映的正是自足图像制作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巫术操作过程,即造型过程与巫术过程合一。这种过程已无法复原,人们只能根据图像本身残存的痕迹进行观察分析了。一般来说,一次巫术仪式要使用一次图像。所谓非自足图像是指“施法动作要由现实中的人来完成,..一般来讲,非自足图像的巫术事件要由图像中的要素和现实中人的动作要素一起才能实现”⑤。非自足图像是施法者在已完成的图像上施动作于图像,才构成一个巫术操作过程,于是,发现一些岩画中有重刻(绘)或多次刻画的痕迹,表明施法动作在原已绘刻好的图像上进行。从已发现的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岩画中不难得知,人与动物生殖“力”的传递形式有四种:一是感应式;二是接触式;三是相交式;四是距离交合式,都属于交感巫术范畴。已完成的岩画图像既可能是自足图像,又可能是非自足图像。
西域岩画中有一类在我国其他地方绝少有的洞窟彩绘岩画。它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其一是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乌孙山发现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岩画绘于阿克塔斯山高1850米处的岩洞内,洞高2.5~3米,洞口宽5米。岩画绘于洞口右面岩画上,均用赭石绘制。画面由七只北山羊、两匹马和两组大小圆圈和一个“〉”形及“◎”形、“工”、“)”符号组成。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绘岩画。第一个岩洞在半山腰离地面25米处,洞窟高11.5米,宽20米,深11.8米。岩画绘于洞顶和正面、侧面岩壁上。画面由一组四个里外两层、中间为圆圈的椭圆形图案和两个圆圈、手印以及被认为萨满帽、铜镜的图形组成,此外还有一组表意符号和所谓的人面像。唐巴勒塔斯二洞距离第一洞约60米,位于海拔1000米处,洞宽4.9米,高3.2米,深4米。画面由拿弓箭欲射的两人、脚印、两只野兽和叉腿、手臂平放或上举的四组人形图像组成。其三是阿勒泰市西北25公里处的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洞窟在海拔1000米处,高1.3~1.5米,深浅不一,从一米多到四米左右。在三组五十余道竖短杠组成的类似围栏内分别绘有一椭圆形图案和双腿叉开、高举双手的人物图像。此外还赭绘有牛、马、大角羊的图像。其四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乡的洞窟彩绘岩画,为两处,一处在杜阿特沟,另一处在松哈尔沟。杜阿特沟洞窟彩绘岩画又分5洞。第一洞海拔650米,洞高不过1米,宽也仅1.6米,赭石绘有牛和人物图像,人头部有.“〓”形饰物。第二洞在海拔605米处,洞高1~5米,宽1.7米,深1.3米。画面由一双手下垂、有尾饰的人物图像和牛形象以及一些表意符号组成,其中布满大而有规则的赭石圆形斑点。第三洞只绘有较粗的类似栅栏的竖道。第四洞是两个双腿叉开、双臂伸展的人物图像,有尾巴。第五洞仅有两只牛和一个人物图像。人像头部有两仰角物,尾饰特征显著。松哈尔沟洞窟彩绘岩画在一个高2.5米,宽8米,深4.5米的岩洞内的洞顶。在洞顶十余平方米的岩画上绘有人、动物和其他符号,实为一巨幅岩画。画面中心为一匹有赭石斑点的马,四周绘有羊、虎、牛等动物,人物图像形状与前述洞窟彩绘岩画相同,但与动物图像比较,人形都较小。此外,还绘有六个大手掌印,似栅栏的竖道,赭石实心圆以及虚线组成的不知名图形。从图像看,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多次使用的痕迹。
如果我们将伊犁、阿勒泰地区的洞窟彩绘岩画与广泛分布于西伯利亚的岩画比较,就会发现许多共同点。西伯利亚岩画上的主要图像是萨满形象:(1)鸟头(舞蹈的鸟形人);(2)带有阳具的人形;(3)带角的拟人形;(4)带有牛羊角和鹿角面具;(5)带鼓的萨满。①萨满教曾自公元前2000年后广泛分布于包括西伯利亚、阿尔泰等在内的亚洲北部(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广大地区。伊犁、阿勒泰洞窟彩绘岩画完全可以根据狩猎文化中的典型动物祭祀仪式和与之有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来加以解释:
..各种抽象的模式和形象、人像以及性象征表明:我们不能仅仅用纯粹的和简单的狩猎巫术来解释岩画。性、生殖以及动物世界的繁殖的观念肯定是这种艺术之意义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与狩猎巫术的观念并不矛盾,相反,这是对它的一个重要补充,这表明创作岩画的动机是复杂的,正是这种复杂的动机推动着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狩猎者完成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一切活动,并且通过使用与之有关的图像、图案和仪式来完成这些活动。②萨满教是在氏族生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中,一般称氏族为“昆”(Mukun),“其含义就是一个共同血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男女群团,既是血亲关系的共同体,又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共同体”①。萨满正是在氏族这一特殊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萨满教神灵观念支配下的北方诸民族各姓氏,都有一座数千年来永无休止地精心筑造着的辉煌圣殿。每一座圣殿都是一个氏族的化身”②。萨满岩画的内容题材是多产多育和祭祀祖先。③于是一些僻静、神秘的山洞成了萨满举行生殖、祭祀仪式最理想的场所。山洞中绘制的各种图像和符号正是萨满为本氏族兴旺祈求生育、多猎获动物举行巫术仪式的遗存。虽然举行萨满仪式的情境已不可复现,但这些图像和符号中仍然保留了远古萨满活动的信息。
在西域萨满岩画中保留了法力强大的萨满的最早形象。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为带角的拟人像,这一形象同样出现在杜阿特沟洞窟岩画中,而这些萨满形象无一例外都附有尾巴。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媒介者,他的任务就是沟通地上人类与天上神灵。早期的萨满本身就是巫师,装扮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角”。萨满在一种出神状态下,借助神灵的助佑者——鹿或其他动物精灵与神沟通。头上带角萨满岩画正是象征萨满的助佑神灵。羽毛状头饰、放射状头饰的功能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些人形身下的尾巴往往被误释为阳具,这是不了解早期萨满的装扮所致。从欧洲奥瑞纳文化时期史前岩画发现,岩画上的巫师(萨满)头上戴着鹿角,身上披着兽皮,臀部安有马尾,全身呈激烈跳动状,这就是原始萨满的典型形象。因此,西域洞窟岩画中萨满也应是头戴鹿角、披兽皮、安兽尾的形象。当然萨满也装扮成鸟的形象,羽毛状头饰即属此种。在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还出现戴面具的萨满形象。对萨满的这种形象也有其他解释:“披上兽皮所获得的良好狩猎效果使原始人误以为在兽皮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于是交感巫术中的模仿律和接触律就自然而然地从中产生出来。..戴上兽冠,披上兽皮被看作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④西域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头戴兽冠、披着兽皮的萨满的形象。在一个氏族里,萨满既是沟通人神者,也是保证氏族繁衍、狩猎成功的力的源泉。从这点看,萨满头戴象征神灵助佑者的鹿冠,身披兽皮正是在进行狩猎巫术仪式,它并不是出于单纯模仿的动机。萨满面具早期也是狩猎祭祀仪式的狩猎巫术面具。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物体的推动力转向另一物体。”⑤之后,面具成为萨满的固定道具,又附加了跳神(包括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供奉等多种功能。
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出现许多图饰符号,与萨满形象绘在同一岩面上,常见的有圆圈形、圆点形、竖道形、手掌形以及由点组成的各种不知名图形等。长期研究萨满教文化的富育光先生认为:
萨满身饰、神器以及任何经过萨满亲自创造的独立图饰,不是随意产生出来的。多数是经过萨满祭祀、祈神之后,从梦幻中、迷痴行为后眼前突显出来的清晰或似真非真、似虚非虚的跳动式曲线,而且持续长时间不见变幻,或通过自己意念促其消逝和冲散,仍然原形跳跃不乱不改,或者经过二至三次梦幻、迷痴行为后仍大致展现如前者,便视为神示信息符号。萨满按其型绘制成雕刻出来,其神示信息符号含义惟萨满所知。因为萨满在求得某种神秘符号之先,依据自己的意念做了祝祷。符号依萨满祝愿而孕生。这是萨满教观念中重要的规训:惟萨满心知,绝忌外泄。认为只有如此虔心,形态迥异的符号图形才具有指点迷津、开导众智、逢凶化吉的神力。①
绘于岩石上的这些表意符号同样是具有巫术效力的,将这种神秘力传递给图符的是萨满。尽管因地域、氏族不同,萨满符号也千差万别,但在成千上万符号中有没有一些同向思维规律的痕迹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原始思维中的共性现象证明了这点。如萨满教用菱形或椭圆形象征女性,用粗直线或箭头形象征男性,用若干竖道表示是同一氏族,若干赭石红粗点表示氏族兴旺、力量,倒“U”形表示天,圆点为不受欢迎,菱形头人形表示女萨满,粗线形头人形表示男萨满,群人联手表示友爱、互助、求援。这些符号虽为明末建州女真所发现的东海当地土人刻在树上的象形符号,但一些符号起源很早,对于理解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的萨满符号也不无意义。
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和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岩画一直被学者公认为是史前的生殖崇拜岩画。这两地岩画的确有许多共性:(1)男女交媾图像;(2)阳具特征明显的群体对人、单人图像;(3)对马图像(仅见于康家石门子岩画);(4)持弓矢人与动物的组合图像;(5)头上的角状物。当然也有图45康家石门子岩画(局部)差异,康家石门子岩画以人物图像为主,主要形体是上身呈倒三角的人物图像,而巴尔达库尔岩画则是人与动物的组合图像,尤其是成对正面相对人物图像在西域岩画中极为罕见。但是这些岩画是生殖巫术岩画还是生殖崇拜岩画,学者们是有分歧的。不过,像康家石门子岩画中“人物形象有不少互相叠压,即在早期刻像的基础上,稍予处理,又重新刻凿”①,这提醒人们,这类岩画是生殖巫术岩画。图像互相叠压或重刻(绘)都是巫术的一个动作,每次刻(绘)也就成了巫术仪式的一部分,刻绘过程亦即是实现人的生殖“力”与动物的繁殖力的传通和交感了。在狩猎文化中,弓箭具有狩猎工具和性象征物的双重意义。岩画中阳具突出的人持弓射动物阴部或持弓箭射动物,甚至干脆就刻一张待射的弓箭,都象征着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殖力的传递和互渗。弓箭、阳具是一种认同原则,刻绘这些图像的目的是为了用巫术操作增殖动物。对马、对人图像(为雄性和男性)都是雄性或男性的象征,刻绘这些图像本身就是求育的生殖巫术。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许多人物图像头部有角状物,下身阳具突出,臀后有尾。这与阿尔泰山洞窟岩画中的戴鹿头、有兽尾的萨满形象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在生殖巫术中萨满是保证巫术成功的主角,史前先民相信,萨满本身有保证氏族和动物多产多育的神秘力量——巫术。但是人们(较为精明者)发现巫术操作并不能每次都达到预期结果,也不能时时处处都能保证生殖巫术应验,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左右某些自然力。于是“由巫术向宗教的缓慢过渡开始了,生殖巫术开始演变为生殖崇拜,前者是以人的施法动作直接影响,指令生殖,后者是向超验和超人的神去祈求生殖,人类的巫术操作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人类第一次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控制力让给了异己的、超人的图像、符号或神”②。本来是一些生殖巫术的图像,后又成了生殖崇拜的凝固化的永久安抚人心的偶像,在这个过程中,萨满巫术也逐渐让位于乞求神灵的神职功能,图像也越来越向符号化、程式化、类 型化和凝固化发展了。巫术时代结束了,但巫术远未尽绝。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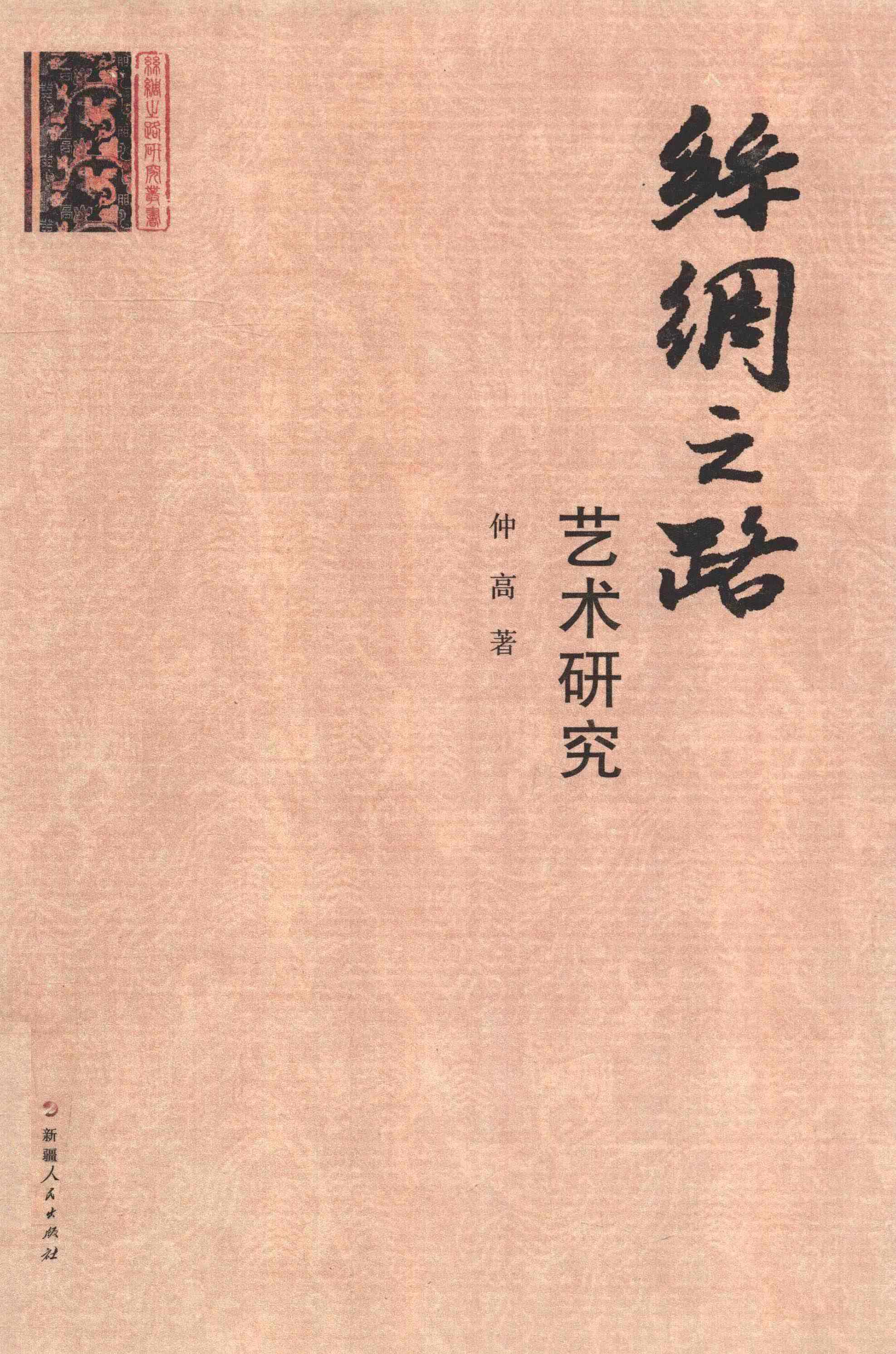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