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早期民族文化与艺术传统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19 |
| 颗粒名称: | 第五节 早期民族文化与艺术传统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9 |
| 页码: | 62-70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上西域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演进始终是两大主流——宗教文化艺术和世俗文化艺术齐头并进,前者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神圣事物与风俗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表达了世俗事物之间以及世俗事物与风俗事物之间的关系情况。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民族文化 艺术传统 |
内容
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丝绸之路上西域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演进始终是两大主流——宗教文化艺术和世俗文化艺术齐头并进,前者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神圣事物与风俗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表达了世俗事物之间以及世俗事物与风俗事物之间的关系。后者的这种关系体现为一种文化与艺术关系时,我们往往把它们称之为一种民俗文化与艺术传统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丝绸之路民族文化艺术都源自民间文化或与其有关,即使是宗教文化艺术也不仅仅是神祗或上层人物的专利,它同样扎根于民间文化的沃土中。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上层文化(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中层文化(城市市民文化)以及下层文化的总称。下层文化亦称民间文化,主体是广大农牧民。在西域,“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地位,他们的文化特点,大都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基本生活)密切地相贴着。像生产技术、民间医药、建筑物、工艺品、劳动歌、实用艺术以及各种民众娱乐等都是例子”①。民间文化因其稳定性、口承性、集体性、模式性等特征,较完整地保留了“文化遗留物”,成为民间文化学(或称为民俗文化学、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它也深深吸引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学者,把“文化遗留物”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民间文化中自然蕴涵作为精神民俗的民间艺术,它至少涵盖民间工艺、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游艺、竞技、民歌等口承艺术。由于这些民间艺术诸形式在长期流变中世代相袭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也就被民俗学家划入民俗文艺的范围中。“在民俗文艺中,民俗与艺术之间,有一种往返无穷的运动模式,即习俗催化艺术,艺术改造习俗。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修补,使民俗文艺保持永久的魅力”②。这多少道出了民间文化与艺术传统之间的关系。
民间文化是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的主流,由于民间文化底蕴丰厚,有强大的辐射功能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世代相传,所以,丝绸之路民族文化主要应指其民间文化。虽然我们把西域古代居民划分为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但在其早期,生活在天山以南、以东地区的居民则是农业与畜牧业兼营的,之后才演变为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民。而天山以北地区也是如此,早期居民亦是农业与畜牧业兼营,而后才发展成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为适应生存,传统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出现交叉、叠加态势,也就是说,天山以北的传统游牧区也出现了定居从事农业的农耕民,而天山以南地区的山前草原地带也存在以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或者说,当地的有些农民在牧民化,而有些牧民也在农民化,甚至有些民族为生存需求整体性转化。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错综复杂关系也直接影响到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乃至艺术传统。
丝绸之路西域早期居民,据现在所知主要有塞人、羌人、车师人、乌揭人、楼兰人、吐火罗人(其先谓月氏)、乌孙人、匈奴人、汉人等。如果按地域分布看,塞人分布最广,主要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及西部天山、吐鲁番盆地、天山南部喀什、和田和帕米尔高原,其活动年代为公元前5~前3世纪。公元前3世纪之后先后有月氏、乌孙等部落占据伊犁河流域。而阿尔泰山一带活动的是乌揭(亦称呼揭)人,《史记·匈奴列传》载有匈奴冒顿单于于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写给汉朝皇帝的信,其中有“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等语,又据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等地发掘的属公元前5~前3世纪巨冢都说明该地区的游牧部落与乌揭人有关。车师人也被认为是乌揭人的分支。①两汉时期原居河西的羌人部分迁徙至天山以南地区,活动范围包括塔里木盆地东部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至帕米尔等地,曾建有婼羌、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等国。有学者根据楼兰人的专有名词特别是名词源出“楼兰语”词汇,多至千余,而源自伊朗语者非常少这一事实,认定楼兰人是塔里木盆地东缘的最早居民,与龟兹、焉耆、高昌操“吐火罗语”的人不同。②吐火罗人是月氏人西迁至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建立贵霜帝国后的称谓,迁徙途中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焉耆、高昌以及伊犁河流域都留有遗民,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西支。吐火罗人的文字为婆罗谜字母斜体书写的文字,焉耆、龟兹一带通行的吐火罗语称为焉耆—龟兹语。早期活动于西域的绝大多数都是游牧部落,有些则是猎牧部落,还有部分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或主营农业兼营牧业。
这些部落尽管因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相同或相似,文化上大同小异,但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却各有不同。现就活动最广泛的塞人、吐火罗人、乌揭人(含其分支车师人)的文化与艺术传统关系作一番探讨。
塞人文化现知不多,且常与匈奴、月氏、乌孙人的文化相混,因为这些民族先后都在西域活动过,尤其在其活动的主要流域—伊犁河流域单从墓葬还难以分辨。如果从时间推算,塞人在西域活动最早,但被兵败于匈奴的月氏人击败,而月氏人又被联合匈奴的乌孙人打败。塞人、月氏、乌孙等同属游牧(猎牧)部落,文化相通,如墓葬,据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塞人、乌孙墓葬同为石(土)封堆,圆形,墓室均为竖穴,东西向,不过从习俗及艺术的细微差别去入手辨析各自文化特征不失为一条途径。塞人从信仰上讲是崇拜太阳与火的,特别是信奉拜火教后,一切文化都打上了崇拜太阳与火的烙印。在阿拉沟塞人墓葬中出土有高方座承兽铜盘,方盘中伫立二兽,在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塞人墓葬中也出土有这种方盘,为兽首吞蹄式足双耳方盘,此种风格的方盘在中亚地区塞人文化遗址中也曾出土。新源县出土的方盘长宽为76厘米,应为大型青铜器。关于方盘的用途,国外考古者往往语焉不详,苏联学者认为是祭祀台,与宗教崇拜、宗教祭祀活动有关。(①但与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有关,祭祀什么神祗,都未加说明。有学者研究了塞人后裔的于阗人“其俗信巫”的情况,认为:“于阗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urmaysde即祆教主神ahnramazda(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中用来翻译印度女神〓rī(吉祥天女)及梵语佛经的mahādevī(大天女)的词〓andrāmatā源于《阿维斯塔》神祗spantaārmaiti〓。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harā或haraiti等翻译梵语佛典中的sumeru(须弥山)。所以,于阗人在信仰佛教之前所崇祀的巫教必为火祆教。”②出土方盘是塞人祭祀太阳神、火神时供放牺牲之用具。塞人的拜火习俗还可从塔什库尔干河谷西岸二台地上的香宝宝四十座墓葬得到印证:“四十座墓葬中,计有火葬墓十九座、土葬墓二十一座。除地表堆石或围以石垣以为标志,墓室作长圆形或不规则圆形为两类墓葬同时具备的特征外,在其他更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墓口盖木、有无葬具、埋葬方式(火葬或土葬)、有无殉物或殉葬文物种类、组合等,都明显具有不同的特点。”③由此观之,拜火习俗已渗透到塞人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考古发现可知,塞人有铜器、金银器加工、木器制作、毛纺织、制陶等手工业。塞人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牌饰、带饰、衣饰一向被认为是塞人动物纹样中的精华。乌鲁木齐南山矿区、天山阿拉沟东口墓葬“出土文物中,金器量多,..大多当为带饰、衣饰。计虎纹圆金牌八块,图案为老虎形象:头微昂、前腿跃起、躯体卷曲成半圆。或左向,或右向,对虎纹金箔带四件,图案为相向踞伏的对虎。另外,还有作奔跃咬啮状的狮形金箔一件。他如兽面纹金饰片、六角形花金饰片、菱形花金饰片、圆形、柳叶式、矩形、树叶形、双十字形、螺旋形金饰片等,品种不少,数量很多,当为衣饰无疑。..银牌,共见七块。有方形、矩形、盾形之别。均模压兽面纹图案,似猫科类野兽形象”④。在此,某些墓葬出土的虎纹圆金牌被错认为是塞人的遗物,其实是车师人的,它们与塞人奔跃咬啮状的狮形纹样是不同的。塞人的动物纹样也异于亚述、阿赫美尼德人和中国中原的青铜器动物形象。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在一个简单和清晰的布景内他们在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而“(塞人)刻绘内容则尤多倾向于动物四肢的被毁伤,时常把一只野猫、熊、鹫,或一个鹰咬住了马或反刍动物的身子当作一副完全扭曲的艺术内容”①。塞人的这些啮咬状动物纹样带饰、牌饰、衣饰从金银质材料的选择到动物形象的塑造有很明显的巫术目的。塞人作为猎牧部民,他们不可能像古埃及人把包有铜或金箔的石头放在金字塔顶,以象征太阳神,让人们领受太阳神的恩泽;也不像玛雅金字塔上的太阳神。塞人对太阳神与火神的崇拜表现在带饰、牌饰、衣饰纹样,他们坚信,只有这样,这些神祗才能时时护佑他们。《吠陀》中把有形象的太阳神比喻为金色的,②黄金在人们的形象思维领域里“总是被用来形容那些奇异神妙、辉煌灿烂的东西”③,于是在佛教文化中也出现了金身的佛陀造像。塞人以黄金饰品作为保护神意图是明显的,徽章图形化的饰物制作以宰杀为题材是有巫术操作性质的,其动机是对太阳神的崇拜。塞人的动物纹样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被中国北方游牧部落造型艺术所吸收,形成鄂尔多斯动物纹样。
吐火罗人的文化也常常和塞人文化相混,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动物纹样,但渊源、主题、题材、风格都有差异性。吐火罗人是大月氏人西迁后的自称,因操吐火罗语,学术界也以吐火罗人指称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亚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并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吐火罗人在信奉佛教前是信仰多神教的部落,后才信奉一神教,早期的部落神是龙神,所以汉文文献将吐火罗人称为“龙部落”,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图经》就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焉耆的吐火罗人王族也以龙为姓氏。那么吐火罗人的龙神是什么呢?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吐火罗人的古代宗教是某种龙神崇拜,先秦文献称之为‘请龙’。中亚大月氏墓地所出以龙为题材的艺术品表明,吐火罗人龙神的艺术原型实乃印欧人原始宗教的双马神。这和先秦文献将中亚马称作‘龙’是一致的。这个认识还得到语言学证据的支持。”④在此,笔者只旨在探究吐火罗人龙文化及其在艺术上的表现。无疑,在吐火罗人曾活动和居住过的龟兹、焉耆、高昌等地,仍能觅得龙文化的踪迹。林梅村先生考证后认为大月氏人的故乡在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⑤如果考证不误,巴里坤发现的双马神岩画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对马图像均为吐火罗人的杰作。巴里坤双马神岩画因发现于该县八墙子村附近,故又称“八墙子岩刻”,其中“一幅‘对马图’,二马四蹄相对”。⑥康家石门子岩画中“两组对马图案,一组位于右起的第三与第四人之间。两马的头、前腿和后腿,彼此联结,形成一个封闭的图案。马长头长颈,身体细瘦。尾垂于下,通体涂朱。另一组对马,位于右起第六与第七人之间。形体特征基本同前,只是突出刻画了雄性的生殖器官,未涂颜色”①。内蒙古、宁夏发现的双马神岩画也可能出自活动范围极广的吐火罗系统游牧人之手。双马神本为印欧人共同信奉的神祗,由于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化,吐火罗人开始独尊双马神。吐火罗人何以在岩壁上刻绘红色对马图像?“岩画应该是对当年这片土地上也曾流行过的、通过马祠可以得子的原始生命信仰的艺术反映”②。吐火罗人同塞人一样把他们尊奉的神祗装饰在带饰、牌饰、衣饰上,不过只是神祗不同,塞人起先以狮身鹰头的格里芬为神灵,信仰拜火教后又以太阳神为主神,而吐火罗人的主神则是双马神。新疆出土的双马神牌饰、带饰有两例:“其一,近年新疆轮台县琼巴克古墓出土了一件双马神牌饰,据碳14年代测定,这批墓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00前400年间;其二,1980年新疆吐鲁番艾丁湖畔发现一处汉代墓地,其中出有紫铜质‘带扣动物纹饰牌1件(80TADM0:13)。长8.2厘米,宽4.5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透雕状一对卧马,马背相联,头尾相衔,背面有三个环纽,位于三个角部’。”③这两件牌饰中的双马神图像不同于呼图壁岩画中的图像,前者是两马头上下反向相对图形,而后者是两马从头至尾的正对向图形。在阿富汗西北边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的被称为黄金之丘的墓地遗址3号墓还出土双马头背向金头饰。黄金之丘墓地的墓主人被认为是公元前175年从敦煌西迁至中亚的大月氏人。但是是否任何一类马都是吐火罗人的龙神呢?不是。按周人的标准,“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西域的天马,也就是汉代所称的汗血马。这些疾跑如飞的高头马就是传说中的龙。汉代《汉郊祀歌·天马》中盛赞天马为:“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逝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可见天马就是龙马。从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铜奔马中就能体味到天马一跃千里的气势。无论是“龙为友”,还是“龙之媒”,均是以名马——天马为原型,双马神形象也是马,但现实中不存在的龙和实有的马如何合而为一变成了吐火罗人的信仰并融入到他们的民俗文化中的呢?考古学家在吐火罗人生活的迪利雅特佩发现一件“二龙与女神像”的金质文物,中间是展开双臂的女神(其形象显然受印度、希腊文化影响),与女神为中心,两侧是一对马首(有火焰般马鬃)和龙身的龙马神。它出现在吐火罗人已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信仰佛教之后,足见其民间的龙马神信仰仍扎根于他们的文化土壤之中。当中原人以鳄鱼等爬行动物为原型塑造龙的形象时,吐火罗人则选择了他们最钟爱并须臾不能离开的天马作为龙的原型。这不能不说与吐火罗人作为游牧部落且东征西战片刻都离不开马有关。吐火罗人在西迁抵达阿姆河流域时,“拥有10万至20万骑兵”①。《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可为证。如此庞大的骑兵且长途征战非有良马不可,“人们喂养马是为了它在战争白热化时所表现的迅猛、耐力和稳当,而不是为了它的肉或奶”②。马是所有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征战工具和最值得珍视的财产。从马被驯化起,像诸如月氏人这样的游牧部落就被称为龙部落,龙神(即马神)成为其艺术表现的主题,也成为一种传统艺术。
当吐火罗人信仰龙神(双马神)时,活动于阿尔泰山内外的乌揭人却在流行食马肉的习俗。活动于阿尔泰山的乌揭人有一支曾南下生活在吐鲁番盆地以及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等地,他们先被称为姑师,后又改称车师。乌揭人生活年代大致同于塞人、吐火罗人活动年代。作为阿尔泰游牧部落的乌揭人南迁一支的车师,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迁。天山北部的车师人仍以畜牧业为主,其中食马肉和殉马习俗构成游牧车师人的主要文化成分。“阿拉沟的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马骨,可见车师人是牧马和食用马肉的部族”“从发掘的几座早期车师贵族墓葬看,殉马是普遍的现象,最多的一座墓,殉,马多达29匹,这是其他古代民族中少有的现象”①。如果是游牧生活和征战中食物短缺,迫不得已食用马肉本不足为怪,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蒙古人在征战中缺乏食物或饮水时,往往杀食战马,紧急情况下,还割断马脖子上的血管,饮马血自救。车师人食马肉可以排除这种意外,因为墓葬中的马骨是如此之多和集中。那么只有一种解释,车师人的贵族有食马肉、殉马的时尚和嗜好:“他们以善待自己的坐骑著称;他们在爱情歌曲中歌唱他们的坐骑,他们从不粗暴地鞭挞任何一只坐骑。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杀掉肥硕的母马为英雄们和‘大人物’举行盛宴,也不妨碍他们用滚烫的马头和马肉香肠款待婚礼上的嘉宾。”②殉马当然是主人身份的象征,否则就不好解释车师人有羊、牛等丰富的肉食来源,为何又去食用他们钟爱的坐骑。吐鲁番盆地以农业为主的车师人的主要生活器皿是陶器和木器,而陶器中以彩陶为主,这既是车师人定居生活的标志,也是农耕车师人审美心理的折射。考古学家对车师人的彩陶作了如下描述:
..这批(车师人的)墓葬中出土大量彩陶器皿。有时,一座墓葬中,这类陶器就有十几件、20件之多,杯、罐、盆、钵、豆,造型不同,彩色图案却没有大的差别。绝大部分都是在陶胎外表刷一层红色陶衣,上面绘制黑色纹彩。正、倒的三角形、涡漩纹、垂幛纹、菱形网格纹等,都是当年流行的图案。陶器制作,说不上十分精致,陶土中,几乎都夹砂;烧制的温度也不太高;纹饰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已显得浅淡。而且,这些精心绘制的陶器,竟然也直接放在烟火上熏烧,..这些特点,与以精美著称的甘肃、河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差异,表现了新疆地区彩陶器的个性特点。它们流行的时代,比起邻近的甘肃、青海地区,也要晚得多。③
车师人的彩陶同他们的木质盆、盘、杯一样既是饮食器皿也是祭器。从墓葬出土的这些器皿中都放有肉块、粟米、黑豆、胡麻籽等祭品,随死者埋入土里的这些动物肉和粮食种子难道也是一种由种子的入土——死亡——新生引起的同向思维所造成的巫术仪式吗?的确是,“土葬的目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埋葬死者,而在于利用这种反本复始的手段促使死者再生,它的本义在于向生而死!在这里,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将生殖巫术的内涵大大扩大了,因为它的整体实践己经表明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使生者(人、动物和植物)生,生得更多或更好,而且还在于让死者生,使其死而复生”④!这不正代表大地的丰产、人畜的兴旺吗?车师人的这种思维显然源于他们的生产方式。车师人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分为前后二部,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为前部,从事农业生产,天山以北的车师人为后部,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分野也决定了文化的走向。车师前部文化呈现的是绿洲农耕文化的特征,而车师后部仍保留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不过处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部吐鲁番的车师人的文化总是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部落。火焰山腹地的苏贝希文化属车师前部的农耕文化,出土有大量彩陶和木器,但同样出土有具有欧亚草原文化特征的动物纹样牌饰。所出土金属物件中有二件包金卧虎铜牌和一件虎纹金箔。前者为长形卧虎铜牌,外围边框饰一周圆点纹,中间铸成透雕状的一只卧虎,右前腿高高扬起,回首张口,尾巴上翘,形象生动,正面模压一层金箔;后者为圆形,中间是一只站立的老虎,尾巴上翘,回首长啸,金箔很薄,应该也是模压在一圆形虎纹铜牌上的。①另两件牌饰,一为虎噬羊铜牌,出土于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第二件为虎纹圆金牌和金饰带,出土于阿拉沟古墓,都为车师人的墓葬。木垒县城东也出土有铜虎、虎形扣饰,虎纹牌饰为车师人动物纹样是不成问题的。车师人以生产方式的转变分为前后车师后,其文化艺术传统一直保留着一致性。这种动物纹样传统一直可追溯到游牧于阿尔泰山的乌揭人的文化中。苏贝希墓葬中的石棺墓丧葬习俗同样存在于阿尔泰乌揭人的克尔木齐墓葬文化中,“故苏贝希文化中所见的这类墓葬形制有可能是受克尔木齐墓葬的影响”②。
丝绸之路西域早期民族文化及其艺术传统对后世绿洲农耕文化艺术和草原游牧文化艺术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各民族艺术,诸如造型艺术、民间工艺、乐舞艺术、民歌艺术、竞技游艺等均与前期有承袭关系。在承袭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过是消解了巫术意义,走向了非功利性艺术而已。从绿洲农耕文化中的于阗艺术、龟兹艺术、鄯善艺术、高昌艺术和草原游牧文化中的塞人的艺术、突厥人的艺术、蒙古人的艺术中都能找到前后继承关系的踪迹,只是各民族在艺术中互渗互补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并形成各自的艺术传统而已(关于此将在丝绸之路绿洲艺术、草原艺术和汉文化艺术等章节中展开论述)。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上层文化(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中层文化(城市市民文化)以及下层文化的总称。下层文化亦称民间文化,主体是广大农牧民。在西域,“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地位,他们的文化特点,大都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基本生活)密切地相贴着。像生产技术、民间医药、建筑物、工艺品、劳动歌、实用艺术以及各种民众娱乐等都是例子”①。民间文化因其稳定性、口承性、集体性、模式性等特征,较完整地保留了“文化遗留物”,成为民间文化学(或称为民俗文化学、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它也深深吸引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学者,把“文化遗留物”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民间文化中自然蕴涵作为精神民俗的民间艺术,它至少涵盖民间工艺、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游艺、竞技、民歌等口承艺术。由于这些民间艺术诸形式在长期流变中世代相袭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也就被民俗学家划入民俗文艺的范围中。“在民俗文艺中,民俗与艺术之间,有一种往返无穷的运动模式,即习俗催化艺术,艺术改造习俗。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修补,使民俗文艺保持永久的魅力”②。这多少道出了民间文化与艺术传统之间的关系。
民间文化是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的主流,由于民间文化底蕴丰厚,有强大的辐射功能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世代相传,所以,丝绸之路民族文化主要应指其民间文化。虽然我们把西域古代居民划分为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但在其早期,生活在天山以南、以东地区的居民则是农业与畜牧业兼营的,之后才演变为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民。而天山以北地区也是如此,早期居民亦是农业与畜牧业兼营,而后才发展成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为适应生存,传统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出现交叉、叠加态势,也就是说,天山以北的传统游牧区也出现了定居从事农业的农耕民,而天山以南地区的山前草原地带也存在以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或者说,当地的有些农民在牧民化,而有些牧民也在农民化,甚至有些民族为生存需求整体性转化。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错综复杂关系也直接影响到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乃至艺术传统。
丝绸之路西域早期居民,据现在所知主要有塞人、羌人、车师人、乌揭人、楼兰人、吐火罗人(其先谓月氏)、乌孙人、匈奴人、汉人等。如果按地域分布看,塞人分布最广,主要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及西部天山、吐鲁番盆地、天山南部喀什、和田和帕米尔高原,其活动年代为公元前5~前3世纪。公元前3世纪之后先后有月氏、乌孙等部落占据伊犁河流域。而阿尔泰山一带活动的是乌揭(亦称呼揭)人,《史记·匈奴列传》载有匈奴冒顿单于于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写给汉朝皇帝的信,其中有“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等语,又据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等地发掘的属公元前5~前3世纪巨冢都说明该地区的游牧部落与乌揭人有关。车师人也被认为是乌揭人的分支。①两汉时期原居河西的羌人部分迁徙至天山以南地区,活动范围包括塔里木盆地东部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至帕米尔等地,曾建有婼羌、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等国。有学者根据楼兰人的专有名词特别是名词源出“楼兰语”词汇,多至千余,而源自伊朗语者非常少这一事实,认定楼兰人是塔里木盆地东缘的最早居民,与龟兹、焉耆、高昌操“吐火罗语”的人不同。②吐火罗人是月氏人西迁至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建立贵霜帝国后的称谓,迁徙途中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焉耆、高昌以及伊犁河流域都留有遗民,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西支。吐火罗人的文字为婆罗谜字母斜体书写的文字,焉耆、龟兹一带通行的吐火罗语称为焉耆—龟兹语。早期活动于西域的绝大多数都是游牧部落,有些则是猎牧部落,还有部分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或主营农业兼营牧业。
这些部落尽管因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相同或相似,文化上大同小异,但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却各有不同。现就活动最广泛的塞人、吐火罗人、乌揭人(含其分支车师人)的文化与艺术传统关系作一番探讨。
塞人文化现知不多,且常与匈奴、月氏、乌孙人的文化相混,因为这些民族先后都在西域活动过,尤其在其活动的主要流域—伊犁河流域单从墓葬还难以分辨。如果从时间推算,塞人在西域活动最早,但被兵败于匈奴的月氏人击败,而月氏人又被联合匈奴的乌孙人打败。塞人、月氏、乌孙等同属游牧(猎牧)部落,文化相通,如墓葬,据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塞人、乌孙墓葬同为石(土)封堆,圆形,墓室均为竖穴,东西向,不过从习俗及艺术的细微差别去入手辨析各自文化特征不失为一条途径。塞人从信仰上讲是崇拜太阳与火的,特别是信奉拜火教后,一切文化都打上了崇拜太阳与火的烙印。在阿拉沟塞人墓葬中出土有高方座承兽铜盘,方盘中伫立二兽,在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塞人墓葬中也出土有这种方盘,为兽首吞蹄式足双耳方盘,此种风格的方盘在中亚地区塞人文化遗址中也曾出土。新源县出土的方盘长宽为76厘米,应为大型青铜器。关于方盘的用途,国外考古者往往语焉不详,苏联学者认为是祭祀台,与宗教崇拜、宗教祭祀活动有关。(①但与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有关,祭祀什么神祗,都未加说明。有学者研究了塞人后裔的于阗人“其俗信巫”的情况,认为:“于阗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urmaysde即祆教主神ahnramazda(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中用来翻译印度女神〓rī(吉祥天女)及梵语佛经的mahādevī(大天女)的词〓andrāmatā源于《阿维斯塔》神祗spantaārmaiti〓。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harā或haraiti等翻译梵语佛典中的sumeru(须弥山)。所以,于阗人在信仰佛教之前所崇祀的巫教必为火祆教。”②出土方盘是塞人祭祀太阳神、火神时供放牺牲之用具。塞人的拜火习俗还可从塔什库尔干河谷西岸二台地上的香宝宝四十座墓葬得到印证:“四十座墓葬中,计有火葬墓十九座、土葬墓二十一座。除地表堆石或围以石垣以为标志,墓室作长圆形或不规则圆形为两类墓葬同时具备的特征外,在其他更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墓口盖木、有无葬具、埋葬方式(火葬或土葬)、有无殉物或殉葬文物种类、组合等,都明显具有不同的特点。”③由此观之,拜火习俗已渗透到塞人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考古发现可知,塞人有铜器、金银器加工、木器制作、毛纺织、制陶等手工业。塞人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牌饰、带饰、衣饰一向被认为是塞人动物纹样中的精华。乌鲁木齐南山矿区、天山阿拉沟东口墓葬“出土文物中,金器量多,..大多当为带饰、衣饰。计虎纹圆金牌八块,图案为老虎形象:头微昂、前腿跃起、躯体卷曲成半圆。或左向,或右向,对虎纹金箔带四件,图案为相向踞伏的对虎。另外,还有作奔跃咬啮状的狮形金箔一件。他如兽面纹金饰片、六角形花金饰片、菱形花金饰片、圆形、柳叶式、矩形、树叶形、双十字形、螺旋形金饰片等,品种不少,数量很多,当为衣饰无疑。..银牌,共见七块。有方形、矩形、盾形之别。均模压兽面纹图案,似猫科类野兽形象”④。在此,某些墓葬出土的虎纹圆金牌被错认为是塞人的遗物,其实是车师人的,它们与塞人奔跃咬啮状的狮形纹样是不同的。塞人的动物纹样也异于亚述、阿赫美尼德人和中国中原的青铜器动物形象。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在一个简单和清晰的布景内他们在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而“(塞人)刻绘内容则尤多倾向于动物四肢的被毁伤,时常把一只野猫、熊、鹫,或一个鹰咬住了马或反刍动物的身子当作一副完全扭曲的艺术内容”①。塞人的这些啮咬状动物纹样带饰、牌饰、衣饰从金银质材料的选择到动物形象的塑造有很明显的巫术目的。塞人作为猎牧部民,他们不可能像古埃及人把包有铜或金箔的石头放在金字塔顶,以象征太阳神,让人们领受太阳神的恩泽;也不像玛雅金字塔上的太阳神。塞人对太阳神与火神的崇拜表现在带饰、牌饰、衣饰纹样,他们坚信,只有这样,这些神祗才能时时护佑他们。《吠陀》中把有形象的太阳神比喻为金色的,②黄金在人们的形象思维领域里“总是被用来形容那些奇异神妙、辉煌灿烂的东西”③,于是在佛教文化中也出现了金身的佛陀造像。塞人以黄金饰品作为保护神意图是明显的,徽章图形化的饰物制作以宰杀为题材是有巫术操作性质的,其动机是对太阳神的崇拜。塞人的动物纹样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被中国北方游牧部落造型艺术所吸收,形成鄂尔多斯动物纹样。
吐火罗人的文化也常常和塞人文化相混,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动物纹样,但渊源、主题、题材、风格都有差异性。吐火罗人是大月氏人西迁后的自称,因操吐火罗语,学术界也以吐火罗人指称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亚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并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吐火罗人在信奉佛教前是信仰多神教的部落,后才信奉一神教,早期的部落神是龙神,所以汉文文献将吐火罗人称为“龙部落”,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图经》就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焉耆的吐火罗人王族也以龙为姓氏。那么吐火罗人的龙神是什么呢?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吐火罗人的古代宗教是某种龙神崇拜,先秦文献称之为‘请龙’。中亚大月氏墓地所出以龙为题材的艺术品表明,吐火罗人龙神的艺术原型实乃印欧人原始宗教的双马神。这和先秦文献将中亚马称作‘龙’是一致的。这个认识还得到语言学证据的支持。”④在此,笔者只旨在探究吐火罗人龙文化及其在艺术上的表现。无疑,在吐火罗人曾活动和居住过的龟兹、焉耆、高昌等地,仍能觅得龙文化的踪迹。林梅村先生考证后认为大月氏人的故乡在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⑤如果考证不误,巴里坤发现的双马神岩画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对马图像均为吐火罗人的杰作。巴里坤双马神岩画因发现于该县八墙子村附近,故又称“八墙子岩刻”,其中“一幅‘对马图’,二马四蹄相对”。⑥康家石门子岩画中“两组对马图案,一组位于右起的第三与第四人之间。两马的头、前腿和后腿,彼此联结,形成一个封闭的图案。马长头长颈,身体细瘦。尾垂于下,通体涂朱。另一组对马,位于右起第六与第七人之间。形体特征基本同前,只是突出刻画了雄性的生殖器官,未涂颜色”①。内蒙古、宁夏发现的双马神岩画也可能出自活动范围极广的吐火罗系统游牧人之手。双马神本为印欧人共同信奉的神祗,由于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化,吐火罗人开始独尊双马神。吐火罗人何以在岩壁上刻绘红色对马图像?“岩画应该是对当年这片土地上也曾流行过的、通过马祠可以得子的原始生命信仰的艺术反映”②。吐火罗人同塞人一样把他们尊奉的神祗装饰在带饰、牌饰、衣饰上,不过只是神祗不同,塞人起先以狮身鹰头的格里芬为神灵,信仰拜火教后又以太阳神为主神,而吐火罗人的主神则是双马神。新疆出土的双马神牌饰、带饰有两例:“其一,近年新疆轮台县琼巴克古墓出土了一件双马神牌饰,据碳14年代测定,这批墓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00前400年间;其二,1980年新疆吐鲁番艾丁湖畔发现一处汉代墓地,其中出有紫铜质‘带扣动物纹饰牌1件(80TADM0:13)。长8.2厘米,宽4.5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透雕状一对卧马,马背相联,头尾相衔,背面有三个环纽,位于三个角部’。”③这两件牌饰中的双马神图像不同于呼图壁岩画中的图像,前者是两马头上下反向相对图形,而后者是两马从头至尾的正对向图形。在阿富汗西北边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的被称为黄金之丘的墓地遗址3号墓还出土双马头背向金头饰。黄金之丘墓地的墓主人被认为是公元前175年从敦煌西迁至中亚的大月氏人。但是是否任何一类马都是吐火罗人的龙神呢?不是。按周人的标准,“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西域的天马,也就是汉代所称的汗血马。这些疾跑如飞的高头马就是传说中的龙。汉代《汉郊祀歌·天马》中盛赞天马为:“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逝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可见天马就是龙马。从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铜奔马中就能体味到天马一跃千里的气势。无论是“龙为友”,还是“龙之媒”,均是以名马——天马为原型,双马神形象也是马,但现实中不存在的龙和实有的马如何合而为一变成了吐火罗人的信仰并融入到他们的民俗文化中的呢?考古学家在吐火罗人生活的迪利雅特佩发现一件“二龙与女神像”的金质文物,中间是展开双臂的女神(其形象显然受印度、希腊文化影响),与女神为中心,两侧是一对马首(有火焰般马鬃)和龙身的龙马神。它出现在吐火罗人已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信仰佛教之后,足见其民间的龙马神信仰仍扎根于他们的文化土壤之中。当中原人以鳄鱼等爬行动物为原型塑造龙的形象时,吐火罗人则选择了他们最钟爱并须臾不能离开的天马作为龙的原型。这不能不说与吐火罗人作为游牧部落且东征西战片刻都离不开马有关。吐火罗人在西迁抵达阿姆河流域时,“拥有10万至20万骑兵”①。《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可为证。如此庞大的骑兵且长途征战非有良马不可,“人们喂养马是为了它在战争白热化时所表现的迅猛、耐力和稳当,而不是为了它的肉或奶”②。马是所有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征战工具和最值得珍视的财产。从马被驯化起,像诸如月氏人这样的游牧部落就被称为龙部落,龙神(即马神)成为其艺术表现的主题,也成为一种传统艺术。
当吐火罗人信仰龙神(双马神)时,活动于阿尔泰山内外的乌揭人却在流行食马肉的习俗。活动于阿尔泰山的乌揭人有一支曾南下生活在吐鲁番盆地以及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等地,他们先被称为姑师,后又改称车师。乌揭人生活年代大致同于塞人、吐火罗人活动年代。作为阿尔泰游牧部落的乌揭人南迁一支的车师,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迁。天山北部的车师人仍以畜牧业为主,其中食马肉和殉马习俗构成游牧车师人的主要文化成分。“阿拉沟的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马骨,可见车师人是牧马和食用马肉的部族”“从发掘的几座早期车师贵族墓葬看,殉马是普遍的现象,最多的一座墓,殉,马多达29匹,这是其他古代民族中少有的现象”①。如果是游牧生活和征战中食物短缺,迫不得已食用马肉本不足为怪,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蒙古人在征战中缺乏食物或饮水时,往往杀食战马,紧急情况下,还割断马脖子上的血管,饮马血自救。车师人食马肉可以排除这种意外,因为墓葬中的马骨是如此之多和集中。那么只有一种解释,车师人的贵族有食马肉、殉马的时尚和嗜好:“他们以善待自己的坐骑著称;他们在爱情歌曲中歌唱他们的坐骑,他们从不粗暴地鞭挞任何一只坐骑。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杀掉肥硕的母马为英雄们和‘大人物’举行盛宴,也不妨碍他们用滚烫的马头和马肉香肠款待婚礼上的嘉宾。”②殉马当然是主人身份的象征,否则就不好解释车师人有羊、牛等丰富的肉食来源,为何又去食用他们钟爱的坐骑。吐鲁番盆地以农业为主的车师人的主要生活器皿是陶器和木器,而陶器中以彩陶为主,这既是车师人定居生活的标志,也是农耕车师人审美心理的折射。考古学家对车师人的彩陶作了如下描述:
..这批(车师人的)墓葬中出土大量彩陶器皿。有时,一座墓葬中,这类陶器就有十几件、20件之多,杯、罐、盆、钵、豆,造型不同,彩色图案却没有大的差别。绝大部分都是在陶胎外表刷一层红色陶衣,上面绘制黑色纹彩。正、倒的三角形、涡漩纹、垂幛纹、菱形网格纹等,都是当年流行的图案。陶器制作,说不上十分精致,陶土中,几乎都夹砂;烧制的温度也不太高;纹饰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已显得浅淡。而且,这些精心绘制的陶器,竟然也直接放在烟火上熏烧,..这些特点,与以精美著称的甘肃、河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差异,表现了新疆地区彩陶器的个性特点。它们流行的时代,比起邻近的甘肃、青海地区,也要晚得多。③
车师人的彩陶同他们的木质盆、盘、杯一样既是饮食器皿也是祭器。从墓葬出土的这些器皿中都放有肉块、粟米、黑豆、胡麻籽等祭品,随死者埋入土里的这些动物肉和粮食种子难道也是一种由种子的入土——死亡——新生引起的同向思维所造成的巫术仪式吗?的确是,“土葬的目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埋葬死者,而在于利用这种反本复始的手段促使死者再生,它的本义在于向生而死!在这里,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将生殖巫术的内涵大大扩大了,因为它的整体实践己经表明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使生者(人、动物和植物)生,生得更多或更好,而且还在于让死者生,使其死而复生”④!这不正代表大地的丰产、人畜的兴旺吗?车师人的这种思维显然源于他们的生产方式。车师人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分为前后二部,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为前部,从事农业生产,天山以北的车师人为后部,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分野也决定了文化的走向。车师前部文化呈现的是绿洲农耕文化的特征,而车师后部仍保留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不过处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部吐鲁番的车师人的文化总是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部落。火焰山腹地的苏贝希文化属车师前部的农耕文化,出土有大量彩陶和木器,但同样出土有具有欧亚草原文化特征的动物纹样牌饰。所出土金属物件中有二件包金卧虎铜牌和一件虎纹金箔。前者为长形卧虎铜牌,外围边框饰一周圆点纹,中间铸成透雕状的一只卧虎,右前腿高高扬起,回首张口,尾巴上翘,形象生动,正面模压一层金箔;后者为圆形,中间是一只站立的老虎,尾巴上翘,回首长啸,金箔很薄,应该也是模压在一圆形虎纹铜牌上的。①另两件牌饰,一为虎噬羊铜牌,出土于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第二件为虎纹圆金牌和金饰带,出土于阿拉沟古墓,都为车师人的墓葬。木垒县城东也出土有铜虎、虎形扣饰,虎纹牌饰为车师人动物纹样是不成问题的。车师人以生产方式的转变分为前后车师后,其文化艺术传统一直保留着一致性。这种动物纹样传统一直可追溯到游牧于阿尔泰山的乌揭人的文化中。苏贝希墓葬中的石棺墓丧葬习俗同样存在于阿尔泰乌揭人的克尔木齐墓葬文化中,“故苏贝希文化中所见的这类墓葬形制有可能是受克尔木齐墓葬的影响”②。
丝绸之路西域早期民族文化及其艺术传统对后世绿洲农耕文化艺术和草原游牧文化艺术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各民族艺术,诸如造型艺术、民间工艺、乐舞艺术、民歌艺术、竞技游艺等均与前期有承袭关系。在承袭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过是消解了巫术意义,走向了非功利性艺术而已。从绿洲农耕文化中的于阗艺术、龟兹艺术、鄯善艺术、高昌艺术和草原游牧文化中的塞人的艺术、突厥人的艺术、蒙古人的艺术中都能找到前后继承关系的踪迹,只是各民族在艺术中互渗互补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并形成各自的艺术传统而已(关于此将在丝绸之路绿洲艺术、草原艺术和汉文化艺术等章节中展开论述)。
附注
①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41.
②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82.
①钱伯泉.乌揭——阿尔泰历史和草原丝路的早期主人.西域研究.2000(4).
②黄盛璋.塔里木盆地东缘的早期居民.西域研究.1992(1).
①H.贝尔什塔姆.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基本阶段.苏联考古学.1949(11).
②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105.
③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1).
④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1).
①〔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32~33.
②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8.8.
③〔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51.
④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32.
⑤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74.
⑥哈密风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40.
①王炳华.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7.
②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203.
③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31.
①榎一雄,科舍伦科,海达里.月氏人及其迁移.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27.
②〔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00.
①钱伯泉.乌揭——阿尔泰历史和草原丝路的早期主人.西域研究.2000(4).
②〔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97.
③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54.
④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17.
①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鄯善县苏巴什(即苏贝希)古墓群的新发现.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01.
②陈戈.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2).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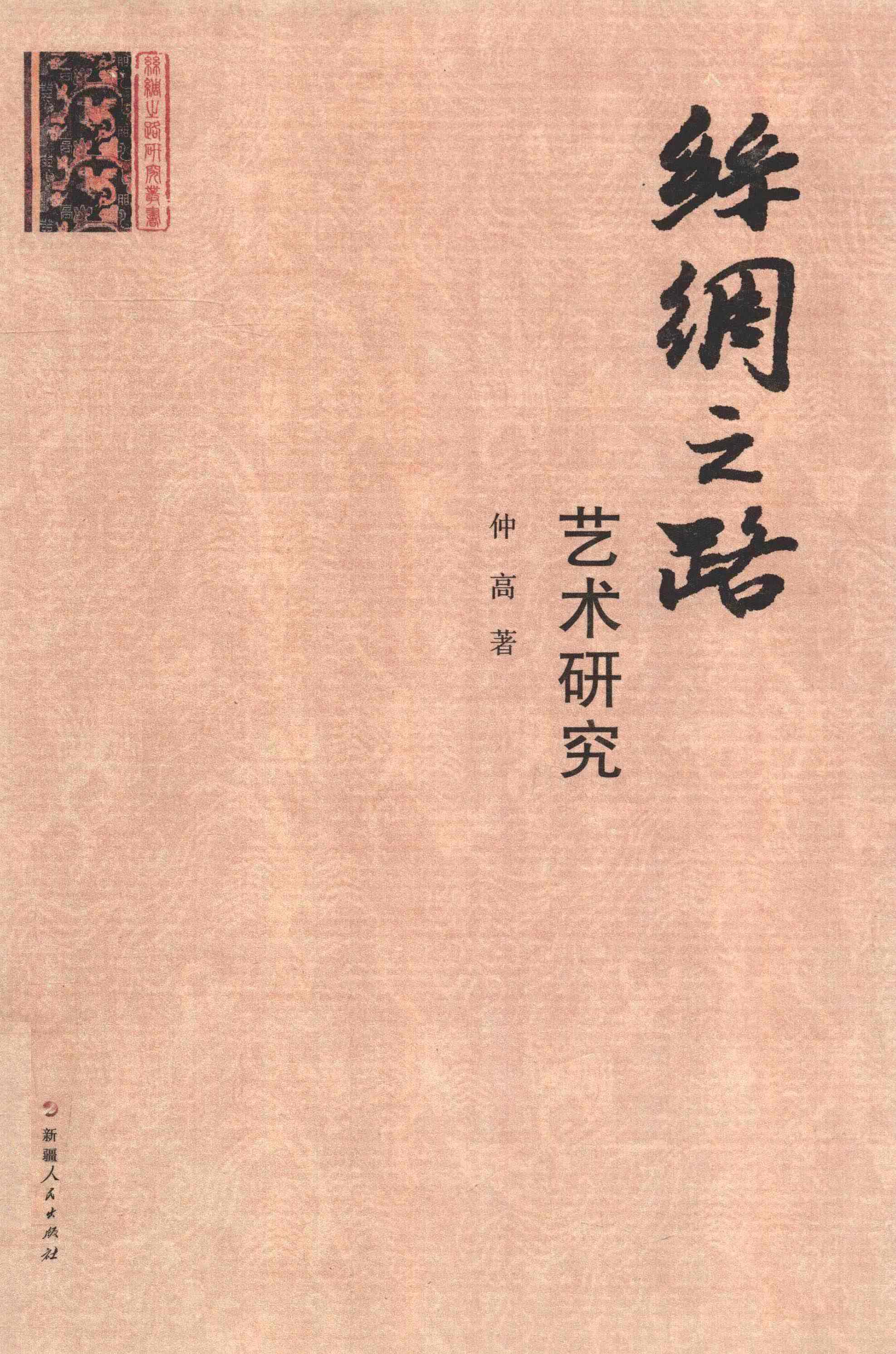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