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信仰、仪式与文化精神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13 |
| 颗粒名称: | 第五节 信仰、仪式与文化精神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9 |
| 页码: | 27-35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信仰、仪式与文化精神情况包括信仰和仪式是宗教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先民图腾信仰及其原始仪式的情况等。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信阳仪式 文化精神 |
内容
信仰和仪式是宗教构成的基本要素:“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群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每个集体成员都能够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信念团结起来。集体成员不仅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有关神圣世界及其与风俗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把这些共同观念转变成为共同的实践,从而构成了社会,即人们所谓的社会。”①无论是初级的宗教形式还是高级的宗教形式概莫如此。图腾信仰及其仪式、自然神信仰及其仪式、人格神信仰及其仪式都旨在“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于是就产生了仪典。”②对丝绸之路西域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的信仰、仪式都可以作如是观。在此,“宗教信仰就是各种表现,它们不仅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性质,也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神圣事物与风俗事物之间的关系”③,而“仪式是各种行为准则,它们规定了人们在神圣对象面前应该具有怎样的行为举止”。④
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先民图腾信仰及其原始仪式的情况,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资凭借的资料,因而不得不从一些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去索解,这些记载几乎都有孤证的性质。其一是关于突厥人先祖“狼生”的传说,《周书·突厥传》有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中一曰伊质泥斯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痴愚,国遂被灭。泥斯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小妻之子也。”其二是有关突厥“狼头纛”的记载,有数则:《通典·突厥传》:“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其旧。”《隋书·北狄传》:“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日唐书·刘武周传》:“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除去后世润色、附会痕迹外,这数则记载传达了如下信息:突厥始祖是以狼为图腾的氏族;狼作为图腾物神由母系世代相传,并同婚姻制度相连;突厥人在他们的旗帜上所绘狼头,正是他们图腾动物的形态,是氏族的标志。
突厥人以牝狼作为祖先图腾的观念显然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是在图腾亲属观念之后产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祖先是人,而是把某种与氏族关系密切的动物(也有植物)当作氏族图腾——自己的祖先了。“在属于同一部落图腾下的所有男人和妇人都深信自己系源自于相同的祖先并且具有共同的血缘,他们之间由于一种共同的义务和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①。“所谓‘一孕而生四男’,当即一个胞族分为四个氏族,并非无稽之谈”②。人类学田野调查证明,胞族是借助特殊的兄弟关系的纽带联合起来的一个氏族群,几乎所有的胞族,只要它有一个含义确定的名字,就会是一种动物的名字,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图腾。③突厥部落的“狼头纛”源于氏族图腾标记。当然古代各氏族的图腾标志各不相同,有动物,也有植物,但主要是动物。它与图腾中心的所在位置密切相关。图腾中心一般都位于山脉、峡谷、河流、泉水处,因为这里是被群体当作图腾的动物大量聚集的地方,突厥始祖的图腾动物——狼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关于这点,从有关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古代突厥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称为“狼山”。唐朝灭突厥后,亦尝因突厥地名,于安北都护府设置狼山州。④突厥人还“每岁五月八日相聚祭神,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⑤就图腾标记的功能而言,大致有这么几种:(1)标记用作召集中心;(2)借助表达其内在状态的记号,进行沟通,形成群体意识,标记成为一种象征;(3)每一个氏族群体都需要一个区别其他群体或流入该群体的标志,有区分群体的功能。与图腾信仰相伴而生的是图腾仪式和禁忌。一般认为图腾仪式分为三种,即入社仪式、生殖仪式和祭祖仪式。西域史前先民的某些图腾仪式从一些晚期的生殖岩画中还能寻其踪迹。
西域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各种图腾逐渐被神化,演化为某一部落、地域的保护神,于是原来被奉为图腾的各种动物、植物乃至天地等自然万物和自然现象被神化和人格化,它们被赋予神性、神职,并随之形成各种专门的祭祀仪式。这种现象在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后不是被弱化,而是强化了。农业居民和游牧民在其信仰的自然神系统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形成各类繁杂的仪式。自然神信仰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观念:“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落的特点,它从此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于高度的现代文化之中。”①万物有灵论论者认为,其理论可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种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于是对它们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说必不可免地导致对它们的实际崇拜或希望得到它们的怜悯。”②由这种信仰引发的仪式大概可分为消极膜拜仪式和积极膜拜仪式。其实,消极膜拜仪式“不需要规定某些特定的信仰行为,而只限于禁止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因此,它们全部采用了禁忌的形式”③。积极膜拜仪式包括祭祀仪式、模仿仪式、表现仪式、纪念仪式、禳解仪式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么都在满怀信心、欢乐以至狂热的状态下举行,要么是为了迎接一场灾难和为了纪念或痛悼这场灾难。④
西域先民的崇拜对象早期涉及万事万物,但出于功利性需求,越来越集中于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天及天神、火及火神、地及地母诸方面。
在西域诸民族中,天崇拜及天神信仰包括天神观念、名称、形象、祭所、神话、仪式等要素。生活和活动在西域的古代部落都曾经历过这一阶段。按天神观念,它有神性、神职,是护佑部落的,故都在固定地点、固定日期以固定仪式进行祭拜。曾活动于西域的匈奴人将天神称为“撑犁”,而突厥人和蒙古人等则称为“腾格里”。不过,匈奴人的“撑犁”既指物质的天,也指精神意义上的天,即天神,而突厥人在指称物质之天时用“盔克”,只有用指天神时才以“腾格里”相称。至于他们信奉的天神是否具体有形——偶像,现无法定论,但有学者认为汉代为霍去病所获匈奴“金人”,即为匈奴人的天神偶像。⑤无独有偶,蒙古人往往“各人置牌位一方于房壁高处,牌上写一名,代表最高天帝”⑥。显然所写名为天帝形象。所有的祭祀场所都是举行神圣仪式的地方,特意选定,成为祭天神的圣地。《史记》及《汉书》记,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天、地等,秋天,马肥,“大会蹛林”。《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无论是西汉时匈奴人的“龙城”,还是东汉时南匈奴人的“龙祠”,都指祭天的场所。大会蹛林,是绕林木而祭。匈奴人或在自然林木,或在树枝的堆竖之处举行祭天仪式,为祈请天神,需绕林木而进行。其祭天神时间又分为冬、春、秋三季。虽然文献未载祭祀、牺牲为何物,但根据后世民俗学材料得知,中国西北、北方游牧民族祭天神主要以牲畜为牺牲,“因而推测匈奴的龙城大祭上,马牛羊之家畜,特别是白马,也为重要之牺牲”①,三季祈愿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在春之大会上,祈愿慈雨滋润、牧草繁茂、家畜兴旺;在冬之大会上,祈求祸害家畜的风雪稀少、狩获丰多。此外,部民之安宁与首(酋)长之康泰,必定是春、秋共同的祈愿”②。突厥人也有祭天神仪式,《通典·突厥传》载:“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祭天神”,“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所记应是突厥人的春祭,他人水是特意选定的地点,以羊马等畜为牺牲。古代突厥部落十分强悍,曾建立过突厥汗国。突厥人的天神观可以概括为:汗权天授的观念、兵事天佑的观念和畏惧天谴的观念。③在游牧民族中所信奉的天神,很有可能是至上神。匈奴人认为天神是至高无上的,他主宰一切,故匈奴单于又自称“撑犁孤涂单于”,④意为“天之子”。同样,突厥人也认为天神统辖天上诸神,其可汗也被认为是天所生,人畜兴旺,征战胜利,都认为是天神所赐。古代蒙古人“把天放在各种神之上,第二流神只不过是天意的工具,或天的各种力量,天以各种目的使用这些力量”⑤。他们在缔结盟约、告天、起誓、打赌时往往都对天发誓。这种情况在近代的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中广泛存在。
对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绿洲农耕民来说,土地是生命之源,由此而形成的土地神观念及其仪式更为实际,他们把土地神奉为丰产之神、保护神。在西域农耕民族中,土地神往往以地母形象出现。古代于阗人有一则建国传说,《大唐西域记》有载:“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吸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地乳所育,因为国号。”⑥这个传说虽然被玄奘戴上佛教的光环,但分明透露着于阗人早期地母信仰的信息。于阗建国传说的“地乳说”是大地与母神崇拜的产物。这是因为“神圣的大地是神所创造的,由于大地上生长农作物和其他万物的事实,在原始的农耕社会里,大地的丰饶性与女性的生殖性往往互相结合而有把大地与子宫连接在一起的信仰倾向,因此大地也常常被当作原始的母神”①。有学者认为于阗国名“地乳”的传说来自朴素的民间传说,经过佛教润色后变成了建国传说。②于阗被梵文称作“瞿萨旦那”(kus-tana),“ku”为“地”意,而“Stana”为妇女乳房之意,地乳传说自然是母神信仰的遗存。在原始农耕阶段,妇女是农业生产的发明者,耕作实践都与女性有关,女性也成了丰产的象征。另一方面,人口的繁衍,先民们认为也主要靠女性。丰产女神与生育女神崇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于阗建国传说拂去佛教的迷雾,当是和田先民早期信仰的表现,这种信仰是有祭祀仪式的,就是设神祀祭拜。当于阗人崇祀地母时,魏晋时期高昌王国的汉人却在祭祀一种“丁谷天”的神祗。吐鲁番出土文书记有此事:
章和五年乙卯正月口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辰英羊一口,供始耕。合二口。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驹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二十四日,康祺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二十八日,取白姚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此七月十四日,取康酉儿牛一头,供谷里祀。③
据考证,“丁谷”即为现吐鲁番地区的吐峪沟,丁谷天,亦非祆教中的胡天神,极有可能就是汉民族民间信仰中的天神。因为高昌国的居民以农业为主,而且属灌溉农业,加之高昌地区干旱少雨,风沙大,常常对农业造成威胁,故在祭天神时连同风神、树神、石神、清山神一起进行祭祀。祭品是牛、羊,是按户丁摊派祭品的。其祭祀活动从农历的正月至七月均举行。祭始耕,可能是农事的准备阶段,如准备农具、种子、农畜等,三月份是农耕播种,六七月份为收获季节,几乎所有的农事活动都设祀祭奠,以求五谷丰登。在表现人与神关系的祭祀仪式中,常见的有瘗埋祭、血祭、牲祭、焚香祭、酒祭、奶祭等多种。不过,其间并无严格区分,往往是各种献祭手段共同使用,以求奏效。近代锡伯族的祭地仪式就属此例。如:每年春耕前,各家各户都选一头肥猪,牵到后园设的祭坛上,用清水浇猪以示沐浴,一家之长亲手点香,在猪身上晃三下,跪向西天念祝词,以求地神和天神赐给丰年,确保五谷丰登。然后杀猪,猪血洒在地上,鬃毛埋进土里。如果祭祀的当天或隔一天下雨,兆示着丰年,再把猪头煮到半生不熟时供到供桌上,过三天再吃;如果刮大风,意味着灾年,再到祈年树下去祭祀地神和天神,以求消灾赐福。另外,在选地盖房前或开垦新地时,还要举行特殊的祭地仪式。①
所有的土地神献祭仪式都是厚祭,表示尊敬的意味浓厚,而不像薄祭,只有象征意义。这种厚祭暗含的寓意是,用“献祭的方法来与一切神祗分享丰富的食物,便等于与一切神祗分享这天意的嘉惠了。因此,原始社会里面献祭的根本,乃在送礼的心理;送礼便是分享丰足的意思”②。
丝绸之路西域诸民的火神信仰及祭火仪式,尽管名称时有转换,其实均为火神崇拜,火神充当了保护部落、农作物、牲畜平安的保护神角色。而当人们无法抗拒天灾人祸时,又往往点燃净火以驱魔避邪,形成一系列神圣仪式。即使是丧葬仪式也是如此。在西域先民观念中,太阳与火是同义语,太阳神与火神同为一种神祗,有同等功效。学者们曾对古代西突厥的弓月城(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名称进行过考证,认为它“来自古突厥语kün(日,太阳)和〓rt(火,火焰)组成的一个合成词,其意为‘日火’或‘太阳之为’”③。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也证明:“一切火的崇拜都起源于太阳崇拜,..火时常是太阳的代表。”④不过,圣火观念和其祭献仪式各有不同。古代突厥人的火神信仰从其名称中也能觅其踪迹:“据突厥学家分析,‘突厥’一名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T?P+K。第二部分K可还原为常见词尾r〓H、〓是从单词r〓〓〓〓‘KHHi、KHi(妻)变来的。第一部分Tp//Tp的主要含义是炉灶要地’,其,音变形为T〓c//T〓c~T?3,即前述的‘托司’指‘原始神灵’并有‘偶像’、‘神偶’、‘荣席’、‘帐内禁地’诸义”⑤。显然,突厥人的,火神信仰源自,母系氏族社会,灶神即为火神。但祭灶神的木材不是随意捡来的,而是经过精心选定的,因为只有洁净之木才能产生净火。印欧人种的人生火的两块雌雄木片要纯洁,这样才能保证相互摩擦所生之火——“阿格尼”的洁净。蒙古人的火神——乌特娘娘传说是两座神山上生长的榆木制成的。突厥人“把火视为神物,进而连能产生火的木头都不敢亵渎,不用木头做交椅,认为坐在木头上是对火的不敬”⑥。对此,文献史料也可以佐证:“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①宗教既然是一种与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那么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牺牲举行祭火仪式就至关重要。一切民族的祭火仪式都是一种驱魔避邪的净火仪式。东罗马使臣出使西突厥时就亲眼目睹了突厥人的这种净火仪式:“..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逐者。咒既诘毕,乃请蔡马库斯(东罗马使臣)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②主持这种仪式的显然是通神的萨满巫师。净火仪式是有季节性的,游牧民族多在草木枯黄、火灾易发的秋季举行。阿尔泰乌梁海人“祭火一般是相邻的若干户合祭。祭火必须杀黄羊或黄头白身绵羊,在空旷处烧一堆火,点火用黄山羊油或柏叶香,祭祀时以牺牲供于火堆前,并往火里撒些祭品,然后叩头跪拜三次”③。用黄羊或白羊祭火,仍是一种积极的巫术行为,在此,太阳与火的白光或黄色火苗在现实中被黄羊或白羊置换了。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也认为火是光明的象征,能祛除一切妖魔,畜群发生疫情时用火熏畜圈,转场时,畜群从两堆火之间通过。当然,“点燃的篝火不是创造性手段,而是清洗性手段,它通过烧掉或消除可以导致疾病和死亡,威胁一切生物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有害因素,而净化人和牲畜与作物”④。据考古发现,西域史前的“群巴克和香宝宝墓葬实行火葬,或者将火化之后的骨灰撒埋墓室之中,或者在墓室中直接焚烧再掩埋之”⑤,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的距今4000年前的模拟太阳辐射状的墓葬地表列木表明这是先民精心选择的安抚灵魂的神圣祭火仪式。在此,焚尸不是死亡,而是火神给予人死而复生,是生命永恒的祭礼;墓葬地表的太阳徽记,旨在表明惟有辉煌的太阳巫术仪式才能使人类“已临一转机,生命于此复得延续”⑥。当死者的肉体沐浴着太阳的光芒,在火中升腾为灵魂时,祭祀者深信,灵魂永生,生命在延续。
禳解仪式弥漫于西域民间文化中,公共哀悼、歉收、干旱、疾病等成为举行禳解仪式的理由。因为“所有不幸,所有凶兆,所有能够带来悲伤和恐惧情感的事物,都使禳解成为必要,因此才称之为禳解。所以,用这个词来指称那些在不安或悲伤的状态下所奉行的仪式是非常贴切的”⑦。19世纪,在新疆南部地区传教的瑞典传教团曾在喀什、莎车、和田等地区进行过人类学田野调查,包括这些地区的民间信仰、仪式、习俗等三大体系。报告认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存在鬼神信仰、麻扎崇拜,因此也就形成祭麻扎仪式、疾病的巫术治疗仪式、求雨、止涝、求风、占验术等禳解仪式。朝拜麻扎者的动机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为了解脱痛苦,得到圣人的帮助;有些无子女的妇女是期盼圣人赐予儿女,等等。其仪式有群体和个体之分。有些求子心切的妇女,特别是想要男孩的妇女往往在麻扎前放把弓,待很长时间,有的长达四十天,并不断诵读《古兰经》。许多麻扎周围小树或高竿上拴上五颜六色的布条。显然,麻扎崇拜渊源于祖先崇拜和萨满教信仰。疾病的禳解仪式因病征不同,仪式也大相径庭。如头痛病的治疗仪式是:“患者准备好6尺棉布和21只面包(应为——引者注),请巫师带着他的41只用棉布包着的木制鸽子和一只黄狗的头。巫师把黄狗的头固定在咽喉处并念咒语,之后在患者头上吹口气,表示病魔已转移到黄狗的头里。随后就把狗头埋在屋外的十字路口上,面包和六尺棉布作为酬谢送给巫师。”①巫师,实为萨满,维吾尔族称其为“巴克西”。因新疆南部干旱,求雨仪式成为解决紧急事务的最重要的禳解仪式,这些仪式都有巫术操作性质。该报告对求雨仪式进行了这样描述:
求雨的过程是这样的:巫师把一块从动物肠中找到的石头放进有被宰牲的动物血的碗中,用一柳枝不停搅动,并念诵着经文。如果在规定的时间还没有下雨,那意味着坏人作祟,此时巫师要求付更多的钱。如果求雨最终失败或雨下得过多引起了水灾,农民们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就要惩罚这些巫师,把他送到地方法庭,接受一百皮鞭的皮肉之苦并锁在木枷中几个星期。②
这种公共性的集体禳解仪式倾注了农民的全部情感和道德准则,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伊斯兰教色彩。
禳解仪式并不总是充满悲伤气氛和危急意识,即使十分庄重的虔诚仪式也并不排斥活泼、欢乐的成分。积极仪式也成为一种狂欢活动,体现出一种狂欢精神。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两大佛教中心于阗和龟兹最大的佛教盛典是行像仪式。《法显传》描述了于阗国行像仪式的全过程:“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法显传》记载于阗国有十四座大型佛教寺院,按“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恰好是十四日。于阗国、龟兹国的行像仪式几乎是全国出动,因此形成了全国性的盛大宗教节日。从全城出动、扫洒道路、易著新衣、散华烧香等项内容看,除庄重气氛外,又多了节日的狂欢气息。《法显传》虽未说有乐舞相伴,但从于阗乐、龟兹乐的普及情况看,这类仪式是应有乐舞的。因为乐舞娱神一直是沟通人神两界的重要手段。在此,其膜拜对像——佛陀是人还是神已无关宏旨。狂欢仪式及其衍生的狂欢精神一般以非理性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他庆典活动中,在庙会中尤为典型。清代乌鲁木齐以会馆为中心的社火、庙会活动的内容主要是祭神祭祀和民间娱乐活动。两湖会馆的龙灯、四川会馆的狮子、甘肃会馆的旱船、山西会馆的汾阳花鼓、直隶公所的高跷、陕西会馆的高抬,新年期间竟连日演出,长达十几天。甚至连一些与农事有关的祭祀活动仍在城市中流行。按汉族习俗,为消灾祈求农业丰收,农村均有祭祀“农神”的庙宇,所供者为传说中消除蝗灾的“虫王”——刘猛将军。清末在乌鲁木齐市满城东街修有刘猛庙,民国后又在福寿山(今雅玛里克山)上修八蜡庙,于是“虫王”、“农神”庙会成为城乡百姓的秋收节,杀牲祭祀,娱神演戏,盛况空前。本来这些会馆就人神驳杂,两湖会馆建有禹王庙、湘王庙;晋陕会馆建有关帝庙;云贵川会馆建有文昌庙;甘肃会馆供奉伏羲氏,举行各种酬神、娱神仪式,其中戏曲歌舞表演是主要方式。秦腔、眉户剧、小曲子、汉剧、花鼓戏、京剧、河北梆子等也从娱神向娱人转化。庙会及娱神活动是全民性活动,包括社会的各阶层,“这类活动无疑会加强不同等级的社区内部、家族或宗族内部以及行业内部乃至性别群体内部的凝聚力”①,这是庙会狂欢仪式的良性社会功能。
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仪式从总体上讲呈现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律背反,但其人文性和人间性是主要特征。“这种人文实践的理性化,并不企图消解一切神圣性,礼乐文化在理性化的脱巫的同时,珍视地保留着神圣性与神圣感,使人对神圣性的需要在文明、教养、礼仪中仍得到体现”②,这种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由中央王朝向边疆地区的统合力增强而逐步形成。③
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先民图腾信仰及其原始仪式的情况,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资凭借的资料,因而不得不从一些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去索解,这些记载几乎都有孤证的性质。其一是关于突厥人先祖“狼生”的传说,《周书·突厥传》有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中一曰伊质泥斯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痴愚,国遂被灭。泥斯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小妻之子也。”其二是有关突厥“狼头纛”的记载,有数则:《通典·突厥传》:“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其旧。”《隋书·北狄传》:“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日唐书·刘武周传》:“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除去后世润色、附会痕迹外,这数则记载传达了如下信息:突厥始祖是以狼为图腾的氏族;狼作为图腾物神由母系世代相传,并同婚姻制度相连;突厥人在他们的旗帜上所绘狼头,正是他们图腾动物的形态,是氏族的标志。
突厥人以牝狼作为祖先图腾的观念显然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是在图腾亲属观念之后产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祖先是人,而是把某种与氏族关系密切的动物(也有植物)当作氏族图腾——自己的祖先了。“在属于同一部落图腾下的所有男人和妇人都深信自己系源自于相同的祖先并且具有共同的血缘,他们之间由于一种共同的义务和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①。“所谓‘一孕而生四男’,当即一个胞族分为四个氏族,并非无稽之谈”②。人类学田野调查证明,胞族是借助特殊的兄弟关系的纽带联合起来的一个氏族群,几乎所有的胞族,只要它有一个含义确定的名字,就会是一种动物的名字,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图腾。③突厥部落的“狼头纛”源于氏族图腾标记。当然古代各氏族的图腾标志各不相同,有动物,也有植物,但主要是动物。它与图腾中心的所在位置密切相关。图腾中心一般都位于山脉、峡谷、河流、泉水处,因为这里是被群体当作图腾的动物大量聚集的地方,突厥始祖的图腾动物——狼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关于这点,从有关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古代突厥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称为“狼山”。唐朝灭突厥后,亦尝因突厥地名,于安北都护府设置狼山州。④突厥人还“每岁五月八日相聚祭神,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⑤就图腾标记的功能而言,大致有这么几种:(1)标记用作召集中心;(2)借助表达其内在状态的记号,进行沟通,形成群体意识,标记成为一种象征;(3)每一个氏族群体都需要一个区别其他群体或流入该群体的标志,有区分群体的功能。与图腾信仰相伴而生的是图腾仪式和禁忌。一般认为图腾仪式分为三种,即入社仪式、生殖仪式和祭祖仪式。西域史前先民的某些图腾仪式从一些晚期的生殖岩画中还能寻其踪迹。
西域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各种图腾逐渐被神化,演化为某一部落、地域的保护神,于是原来被奉为图腾的各种动物、植物乃至天地等自然万物和自然现象被神化和人格化,它们被赋予神性、神职,并随之形成各种专门的祭祀仪式。这种现象在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后不是被弱化,而是强化了。农业居民和游牧民在其信仰的自然神系统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形成各类繁杂的仪式。自然神信仰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观念:“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落的特点,它从此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于高度的现代文化之中。”①万物有灵论论者认为,其理论可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种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于是对它们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说必不可免地导致对它们的实际崇拜或希望得到它们的怜悯。”②由这种信仰引发的仪式大概可分为消极膜拜仪式和积极膜拜仪式。其实,消极膜拜仪式“不需要规定某些特定的信仰行为,而只限于禁止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因此,它们全部采用了禁忌的形式”③。积极膜拜仪式包括祭祀仪式、模仿仪式、表现仪式、纪念仪式、禳解仪式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么都在满怀信心、欢乐以至狂热的状态下举行,要么是为了迎接一场灾难和为了纪念或痛悼这场灾难。④
西域先民的崇拜对象早期涉及万事万物,但出于功利性需求,越来越集中于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天及天神、火及火神、地及地母诸方面。
在西域诸民族中,天崇拜及天神信仰包括天神观念、名称、形象、祭所、神话、仪式等要素。生活和活动在西域的古代部落都曾经历过这一阶段。按天神观念,它有神性、神职,是护佑部落的,故都在固定地点、固定日期以固定仪式进行祭拜。曾活动于西域的匈奴人将天神称为“撑犁”,而突厥人和蒙古人等则称为“腾格里”。不过,匈奴人的“撑犁”既指物质的天,也指精神意义上的天,即天神,而突厥人在指称物质之天时用“盔克”,只有用指天神时才以“腾格里”相称。至于他们信奉的天神是否具体有形——偶像,现无法定论,但有学者认为汉代为霍去病所获匈奴“金人”,即为匈奴人的天神偶像。⑤无独有偶,蒙古人往往“各人置牌位一方于房壁高处,牌上写一名,代表最高天帝”⑥。显然所写名为天帝形象。所有的祭祀场所都是举行神圣仪式的地方,特意选定,成为祭天神的圣地。《史记》及《汉书》记,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天、地等,秋天,马肥,“大会蹛林”。《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无论是西汉时匈奴人的“龙城”,还是东汉时南匈奴人的“龙祠”,都指祭天的场所。大会蹛林,是绕林木而祭。匈奴人或在自然林木,或在树枝的堆竖之处举行祭天仪式,为祈请天神,需绕林木而进行。其祭天神时间又分为冬、春、秋三季。虽然文献未载祭祀、牺牲为何物,但根据后世民俗学材料得知,中国西北、北方游牧民族祭天神主要以牲畜为牺牲,“因而推测匈奴的龙城大祭上,马牛羊之家畜,特别是白马,也为重要之牺牲”①,三季祈愿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在春之大会上,祈愿慈雨滋润、牧草繁茂、家畜兴旺;在冬之大会上,祈求祸害家畜的风雪稀少、狩获丰多。此外,部民之安宁与首(酋)长之康泰,必定是春、秋共同的祈愿”②。突厥人也有祭天神仪式,《通典·突厥传》载:“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祭天神”,“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所记应是突厥人的春祭,他人水是特意选定的地点,以羊马等畜为牺牲。古代突厥部落十分强悍,曾建立过突厥汗国。突厥人的天神观可以概括为:汗权天授的观念、兵事天佑的观念和畏惧天谴的观念。③在游牧民族中所信奉的天神,很有可能是至上神。匈奴人认为天神是至高无上的,他主宰一切,故匈奴单于又自称“撑犁孤涂单于”,④意为“天之子”。同样,突厥人也认为天神统辖天上诸神,其可汗也被认为是天所生,人畜兴旺,征战胜利,都认为是天神所赐。古代蒙古人“把天放在各种神之上,第二流神只不过是天意的工具,或天的各种力量,天以各种目的使用这些力量”⑤。他们在缔结盟约、告天、起誓、打赌时往往都对天发誓。这种情况在近代的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中广泛存在。
对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绿洲农耕民来说,土地是生命之源,由此而形成的土地神观念及其仪式更为实际,他们把土地神奉为丰产之神、保护神。在西域农耕民族中,土地神往往以地母形象出现。古代于阗人有一则建国传说,《大唐西域记》有载:“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吸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地乳所育,因为国号。”⑥这个传说虽然被玄奘戴上佛教的光环,但分明透露着于阗人早期地母信仰的信息。于阗建国传说的“地乳说”是大地与母神崇拜的产物。这是因为“神圣的大地是神所创造的,由于大地上生长农作物和其他万物的事实,在原始的农耕社会里,大地的丰饶性与女性的生殖性往往互相结合而有把大地与子宫连接在一起的信仰倾向,因此大地也常常被当作原始的母神”①。有学者认为于阗国名“地乳”的传说来自朴素的民间传说,经过佛教润色后变成了建国传说。②于阗被梵文称作“瞿萨旦那”(kus-tana),“ku”为“地”意,而“Stana”为妇女乳房之意,地乳传说自然是母神信仰的遗存。在原始农耕阶段,妇女是农业生产的发明者,耕作实践都与女性有关,女性也成了丰产的象征。另一方面,人口的繁衍,先民们认为也主要靠女性。丰产女神与生育女神崇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于阗建国传说拂去佛教的迷雾,当是和田先民早期信仰的表现,这种信仰是有祭祀仪式的,就是设神祀祭拜。当于阗人崇祀地母时,魏晋时期高昌王国的汉人却在祭祀一种“丁谷天”的神祗。吐鲁番出土文书记有此事:
章和五年乙卯正月口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辰英羊一口,供始耕。合二口。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驹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二十四日,康祺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二十八日,取白姚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此七月十四日,取康酉儿牛一头,供谷里祀。③
据考证,“丁谷”即为现吐鲁番地区的吐峪沟,丁谷天,亦非祆教中的胡天神,极有可能就是汉民族民间信仰中的天神。因为高昌国的居民以农业为主,而且属灌溉农业,加之高昌地区干旱少雨,风沙大,常常对农业造成威胁,故在祭天神时连同风神、树神、石神、清山神一起进行祭祀。祭品是牛、羊,是按户丁摊派祭品的。其祭祀活动从农历的正月至七月均举行。祭始耕,可能是农事的准备阶段,如准备农具、种子、农畜等,三月份是农耕播种,六七月份为收获季节,几乎所有的农事活动都设祀祭奠,以求五谷丰登。在表现人与神关系的祭祀仪式中,常见的有瘗埋祭、血祭、牲祭、焚香祭、酒祭、奶祭等多种。不过,其间并无严格区分,往往是各种献祭手段共同使用,以求奏效。近代锡伯族的祭地仪式就属此例。如:每年春耕前,各家各户都选一头肥猪,牵到后园设的祭坛上,用清水浇猪以示沐浴,一家之长亲手点香,在猪身上晃三下,跪向西天念祝词,以求地神和天神赐给丰年,确保五谷丰登。然后杀猪,猪血洒在地上,鬃毛埋进土里。如果祭祀的当天或隔一天下雨,兆示着丰年,再把猪头煮到半生不熟时供到供桌上,过三天再吃;如果刮大风,意味着灾年,再到祈年树下去祭祀地神和天神,以求消灾赐福。另外,在选地盖房前或开垦新地时,还要举行特殊的祭地仪式。①
所有的土地神献祭仪式都是厚祭,表示尊敬的意味浓厚,而不像薄祭,只有象征意义。这种厚祭暗含的寓意是,用“献祭的方法来与一切神祗分享丰富的食物,便等于与一切神祗分享这天意的嘉惠了。因此,原始社会里面献祭的根本,乃在送礼的心理;送礼便是分享丰足的意思”②。
丝绸之路西域诸民的火神信仰及祭火仪式,尽管名称时有转换,其实均为火神崇拜,火神充当了保护部落、农作物、牲畜平安的保护神角色。而当人们无法抗拒天灾人祸时,又往往点燃净火以驱魔避邪,形成一系列神圣仪式。即使是丧葬仪式也是如此。在西域先民观念中,太阳与火是同义语,太阳神与火神同为一种神祗,有同等功效。学者们曾对古代西突厥的弓月城(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名称进行过考证,认为它“来自古突厥语kün(日,太阳)和〓rt(火,火焰)组成的一个合成词,其意为‘日火’或‘太阳之为’”③。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也证明:“一切火的崇拜都起源于太阳崇拜,..火时常是太阳的代表。”④不过,圣火观念和其祭献仪式各有不同。古代突厥人的火神信仰从其名称中也能觅其踪迹:“据突厥学家分析,‘突厥’一名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T?P+K。第二部分K可还原为常见词尾r〓H、〓是从单词r〓〓〓〓‘KHHi、KHi(妻)变来的。第一部分Tp//Tp的主要含义是炉灶要地’,其,音变形为T〓c//T〓c~T?3,即前述的‘托司’指‘原始神灵’并有‘偶像’、‘神偶’、‘荣席’、‘帐内禁地’诸义”⑤。显然,突厥人的,火神信仰源自,母系氏族社会,灶神即为火神。但祭灶神的木材不是随意捡来的,而是经过精心选定的,因为只有洁净之木才能产生净火。印欧人种的人生火的两块雌雄木片要纯洁,这样才能保证相互摩擦所生之火——“阿格尼”的洁净。蒙古人的火神——乌特娘娘传说是两座神山上生长的榆木制成的。突厥人“把火视为神物,进而连能产生火的木头都不敢亵渎,不用木头做交椅,认为坐在木头上是对火的不敬”⑥。对此,文献史料也可以佐证:“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①宗教既然是一种与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那么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牺牲举行祭火仪式就至关重要。一切民族的祭火仪式都是一种驱魔避邪的净火仪式。东罗马使臣出使西突厥时就亲眼目睹了突厥人的这种净火仪式:“..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逐者。咒既诘毕,乃请蔡马库斯(东罗马使臣)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②主持这种仪式的显然是通神的萨满巫师。净火仪式是有季节性的,游牧民族多在草木枯黄、火灾易发的秋季举行。阿尔泰乌梁海人“祭火一般是相邻的若干户合祭。祭火必须杀黄羊或黄头白身绵羊,在空旷处烧一堆火,点火用黄山羊油或柏叶香,祭祀时以牺牲供于火堆前,并往火里撒些祭品,然后叩头跪拜三次”③。用黄羊或白羊祭火,仍是一种积极的巫术行为,在此,太阳与火的白光或黄色火苗在现实中被黄羊或白羊置换了。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也认为火是光明的象征,能祛除一切妖魔,畜群发生疫情时用火熏畜圈,转场时,畜群从两堆火之间通过。当然,“点燃的篝火不是创造性手段,而是清洗性手段,它通过烧掉或消除可以导致疾病和死亡,威胁一切生物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有害因素,而净化人和牲畜与作物”④。据考古发现,西域史前的“群巴克和香宝宝墓葬实行火葬,或者将火化之后的骨灰撒埋墓室之中,或者在墓室中直接焚烧再掩埋之”⑤,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的距今4000年前的模拟太阳辐射状的墓葬地表列木表明这是先民精心选择的安抚灵魂的神圣祭火仪式。在此,焚尸不是死亡,而是火神给予人死而复生,是生命永恒的祭礼;墓葬地表的太阳徽记,旨在表明惟有辉煌的太阳巫术仪式才能使人类“已临一转机,生命于此复得延续”⑥。当死者的肉体沐浴着太阳的光芒,在火中升腾为灵魂时,祭祀者深信,灵魂永生,生命在延续。
禳解仪式弥漫于西域民间文化中,公共哀悼、歉收、干旱、疾病等成为举行禳解仪式的理由。因为“所有不幸,所有凶兆,所有能够带来悲伤和恐惧情感的事物,都使禳解成为必要,因此才称之为禳解。所以,用这个词来指称那些在不安或悲伤的状态下所奉行的仪式是非常贴切的”⑦。19世纪,在新疆南部地区传教的瑞典传教团曾在喀什、莎车、和田等地区进行过人类学田野调查,包括这些地区的民间信仰、仪式、习俗等三大体系。报告认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存在鬼神信仰、麻扎崇拜,因此也就形成祭麻扎仪式、疾病的巫术治疗仪式、求雨、止涝、求风、占验术等禳解仪式。朝拜麻扎者的动机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为了解脱痛苦,得到圣人的帮助;有些无子女的妇女是期盼圣人赐予儿女,等等。其仪式有群体和个体之分。有些求子心切的妇女,特别是想要男孩的妇女往往在麻扎前放把弓,待很长时间,有的长达四十天,并不断诵读《古兰经》。许多麻扎周围小树或高竿上拴上五颜六色的布条。显然,麻扎崇拜渊源于祖先崇拜和萨满教信仰。疾病的禳解仪式因病征不同,仪式也大相径庭。如头痛病的治疗仪式是:“患者准备好6尺棉布和21只面包(应为——引者注),请巫师带着他的41只用棉布包着的木制鸽子和一只黄狗的头。巫师把黄狗的头固定在咽喉处并念咒语,之后在患者头上吹口气,表示病魔已转移到黄狗的头里。随后就把狗头埋在屋外的十字路口上,面包和六尺棉布作为酬谢送给巫师。”①巫师,实为萨满,维吾尔族称其为“巴克西”。因新疆南部干旱,求雨仪式成为解决紧急事务的最重要的禳解仪式,这些仪式都有巫术操作性质。该报告对求雨仪式进行了这样描述:
求雨的过程是这样的:巫师把一块从动物肠中找到的石头放进有被宰牲的动物血的碗中,用一柳枝不停搅动,并念诵着经文。如果在规定的时间还没有下雨,那意味着坏人作祟,此时巫师要求付更多的钱。如果求雨最终失败或雨下得过多引起了水灾,农民们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就要惩罚这些巫师,把他送到地方法庭,接受一百皮鞭的皮肉之苦并锁在木枷中几个星期。②
这种公共性的集体禳解仪式倾注了农民的全部情感和道德准则,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伊斯兰教色彩。
禳解仪式并不总是充满悲伤气氛和危急意识,即使十分庄重的虔诚仪式也并不排斥活泼、欢乐的成分。积极仪式也成为一种狂欢活动,体现出一种狂欢精神。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两大佛教中心于阗和龟兹最大的佛教盛典是行像仪式。《法显传》描述了于阗国行像仪式的全过程:“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法显传》记载于阗国有十四座大型佛教寺院,按“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恰好是十四日。于阗国、龟兹国的行像仪式几乎是全国出动,因此形成了全国性的盛大宗教节日。从全城出动、扫洒道路、易著新衣、散华烧香等项内容看,除庄重气氛外,又多了节日的狂欢气息。《法显传》虽未说有乐舞相伴,但从于阗乐、龟兹乐的普及情况看,这类仪式是应有乐舞的。因为乐舞娱神一直是沟通人神两界的重要手段。在此,其膜拜对像——佛陀是人还是神已无关宏旨。狂欢仪式及其衍生的狂欢精神一般以非理性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他庆典活动中,在庙会中尤为典型。清代乌鲁木齐以会馆为中心的社火、庙会活动的内容主要是祭神祭祀和民间娱乐活动。两湖会馆的龙灯、四川会馆的狮子、甘肃会馆的旱船、山西会馆的汾阳花鼓、直隶公所的高跷、陕西会馆的高抬,新年期间竟连日演出,长达十几天。甚至连一些与农事有关的祭祀活动仍在城市中流行。按汉族习俗,为消灾祈求农业丰收,农村均有祭祀“农神”的庙宇,所供者为传说中消除蝗灾的“虫王”——刘猛将军。清末在乌鲁木齐市满城东街修有刘猛庙,民国后又在福寿山(今雅玛里克山)上修八蜡庙,于是“虫王”、“农神”庙会成为城乡百姓的秋收节,杀牲祭祀,娱神演戏,盛况空前。本来这些会馆就人神驳杂,两湖会馆建有禹王庙、湘王庙;晋陕会馆建有关帝庙;云贵川会馆建有文昌庙;甘肃会馆供奉伏羲氏,举行各种酬神、娱神仪式,其中戏曲歌舞表演是主要方式。秦腔、眉户剧、小曲子、汉剧、花鼓戏、京剧、河北梆子等也从娱神向娱人转化。庙会及娱神活动是全民性活动,包括社会的各阶层,“这类活动无疑会加强不同等级的社区内部、家族或宗族内部以及行业内部乃至性别群体内部的凝聚力”①,这是庙会狂欢仪式的良性社会功能。
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仪式从总体上讲呈现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律背反,但其人文性和人间性是主要特征。“这种人文实践的理性化,并不企图消解一切神圣性,礼乐文化在理性化的脱巫的同时,珍视地保留着神圣性与神圣感,使人对神圣性的需要在文明、教养、礼仪中仍得到体现”②,这种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由中央王朝向边疆地区的统合力增强而逐步形成。③
附注
①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0.
②爱弥尔·涂尔千著,渠东,汲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62.
③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7.
④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7.
①张岩著.图腾制与原始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42.
②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13.
③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7.
④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14.
⑤隋书·突厥传.
①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414.
②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414.
③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96.
④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14.
⑤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69.
⑥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389.
①〔日〕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13.
②〔日〕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13.
③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137~138.
④汉书·匈奴传上.
⑤道尔吉·班扎罗夫.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7辑.
⑥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1008.
①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作家出版社,1991.171~172.
②〔日〕山崎元一著.荣新江译.于阗建国传说成立的背景.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4).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帐.文物出版社,1981.39.
①佟克力编.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177.
②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等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26.
③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④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328~329.
⑤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133.
⑥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20.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②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7.285~286.
③何星亮.阿尔泰乌梁海人的宗教信仰初探.民族研究.1986(1).
④弗雷泽著.徐育新译.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915.
⑤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42.
⑥雷奈·格鲁塞.印度的文明.商务印书馆,1965.9.
⑦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14~515.
①贡纳尔·雅林.瑞典传教团南疆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木拉提等.了解近代维吾尔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资料.西域研究.1999(4).
②贡纳尔·雅林.瑞典传教团南疆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转引自木拉提等.了解近代维吾尔民间文化的重要资料.西域研究.1999(4).
①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1).
②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1996.12.
③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1996.7.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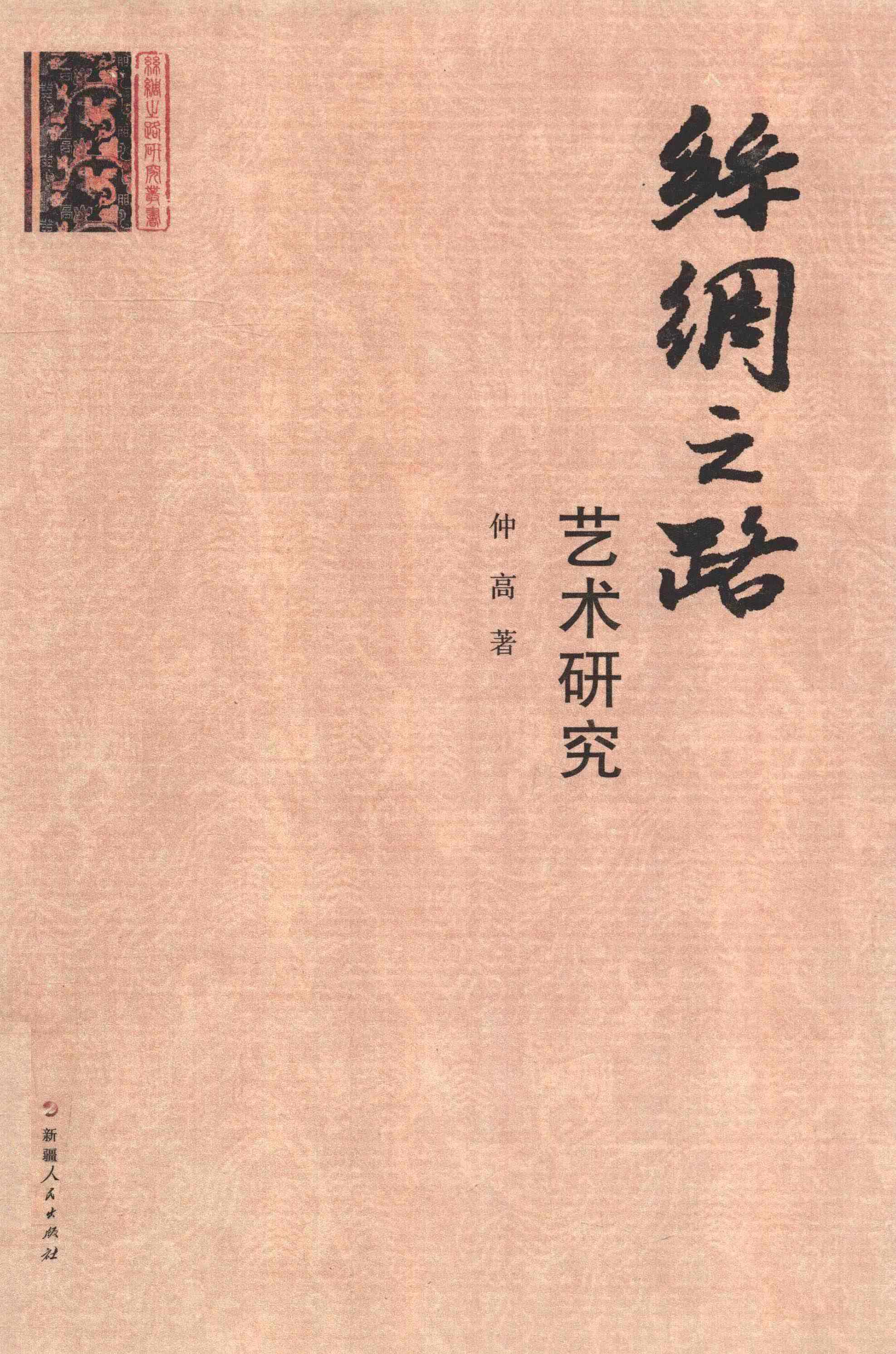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