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区域社会与文化变迁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411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区域社会与文化变迁 |
| 分类号: | J110.9 |
| 页数: | 9 |
| 页码: | 13-21 |
| 摘要: | 本节记述的是丝绸之路区域社会与文化变迁情况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变更引起的文化变迁、外来文化引起的文化变迁。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区域社会 文化变迁 |
内容
“变迁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是恒定的,虽然变迁的速度及其表现形式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①。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文化自发生之时起,就处在一种“恒定”的文化变迁中,其中既有缓慢式的文化渐变,也有结构性的文化突变。文化变迁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总体上是随着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其中有这么几种因素是十分重要的:(一)文化变迁的内因是一个文化集团内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正是这种变更导致各种社会现象的变更,从而自增加或减少文化形态开始,最终引起文化变迁;(二)文化变迁的外因是一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撞和影响,从而引起文化变迁;(三)文化的冲突和分化是文化变迁的又一个原因。②西域自史前以来的各种氏族集团、部落、部族以及民族构成的社会文化大体都遵循着这种种动因而变迁着。
一、社会生产方式变更引起的文化变迁
西域旧石器和细石器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狩猎和采集,但是随着氏族集团人口的增多,猎获动物数量的减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西域出现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这是一个渐变的文化变迁过程,两种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剥离,也就是说无论是天山以南还是以北地区,在此阶段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同时还存在狩猎生产方式。这个时期的西域史前先民从游移迁徙走向定居,使用金属工具,家养牲畜,耕种农作物并使用陶器等日用器皿,衣食质量也大为提高。这种定居聚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广泛分布。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遗址主要有东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北疆的柴窝堡、南疆的辛格尔、乌帕尔及罗布泊一带。青铜时代的定居聚落则有东疆巴里坤的南湾、兰州湾子及伊吾县的军马场、卡尔桑遗址和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遗址、南疆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和小河附近的5号墓地、和硕的新塔拉遗址、库车的哈拉墩遗址、疏附的阿克塔拉遗址以及北疆塔城卫生学校遗址等。
让我们剖析一个以畜牧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个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孔雀河古墓沟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表明,罗布泊地区曾生活着以畜牧业为主体、兼营农业的氏族集团。从所发掘的42座古墓葬可以认定,这是距今3800年前的定居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有牛羊角、毛织品(毛布、毛毯、尖顶毡帽等)、皮革制品、木雕、铜制品、骨制品、角制品、小麦粒、草编制品等,但不见陶器。从有环列木桩和无环形列木的墓表特征及随葬品看,此处已形成一种有特色的地方性葬俗。据此,“发掘资料具体表明,当时古墓沟人的生产以畜牧业为主体,主要饲养羊、牛,羊有山羊、绵羊。在一座墓葬中,随殉的牛、羊角多达26支,说明已有相当规模的牲畜积累。鞋、帽、包覆身体的毛布或毛毯,也都取自羊绒、皮张,主要依靠畜牧业。足以说明,畜牧业是当时人民生活的衣、食之源,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是存在的,墓区发现的小麦粒,是一个直接的说明。但出土数量,从总体看,只占很小比例。孔雀河谷可得灌溉之便,少量的农业经营是完全可能存在的。”①但是古墓沟定居文化是以墓葬发掘推论定居聚落的,还未及对定居点遗址进行发掘,而木垒四道沟遗址则被认为是西域原始社会晚期的遗址之一。四道沟定居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是发现圆形房屋的遗址,有柱洞和灶址;二是出土有彩陶、夹砂陶,可分为容器、炊具、工具、玩具等;三是出土有磨盘、石锄、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及铜刀等。遗址分早晚二期,可以明显看出在生产方式上由采集狩猎过渡到相对定居的聚落生活。②晚期,显然是农业和畜牧业占有同等重要地位,并伴有狩猎活动。
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引起物质文化的变迁,同样引起信仰习俗的嬗变。从自然和灵物崇拜到灵魂和祖先崇拜,都反映着西域先民原始信仰种种复杂的精神活动。新疆出土的女神偶像、男性石祖,揭示了从女性祖先到男性祖先信仰的渐变过程。原始信仰形成一套行为仪式。
考古学家认为,西域早期铁器时代是畜牧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重要标志,自此之后,形成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文化和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格局,这种格局延续至今并无多大变化。不过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混融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对这两种生产方式分离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西域境内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影响的北疆宜于畜牧业而南疆适合农业的经济形态格局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早期铁器时代即已开始形成了。”①哈密的焉不拉克文化和和静的察吾乎沟口文化是这一时期由生产方式变更引发的文化变迁的典型例证。这两个文化的共同点是:一是大量陶器的出现,彩陶较多,可分为带流罐、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单耳豆、腹耳壶、钵等,此外还有盘、碗、勺、桶、铣、耜、锥、纺轮等木器,器皿增多表明农耕定居生活进入新阶段。二是铁器出现,前者出土物为刀、剑等武器和戒指等,不见铁制农具;而后者除武器外,还有铁镰等农具。三是两处文化遗址均有谷物,如小麦、青稞、小米饼出土,又见马、牛、羊骨和大量毛织物。四是形成二次葬、合葬、屈肢葬及祭祀等葬俗。五是手工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工艺技术日臻完善。种种物证表明,焉不拉克、察吾乎沟口等属于以农耕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氏族社会文化。“而在北疆区的大部分遗址或墓葬中所见到的多是马、牛、羊骨和与畜牧经济有关的小工具,却很少或不见农业的踪迹,北疆区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畜牧业”②。北疆地区草原游牧业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家马的出现。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西域的游牧部落于何时何地驯服了马,但“马的贡献都在于它的流动性,它使其主人能够照料广泛散布的畜群,它可以迅速移动以抵御来自那些专好偷窃别人牲畜的敌对邻邦的威胁”③。
天山以南绿洲城郭诸国和天山以北草原游牧行国的出现,标志着西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按不同轨迹发展,并按生产方式的不同,发生着迥异的文化变迁。汉文文献所载西域三十六国,按生产方式不同,出现了以农耕为主的精绝、扜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等国,还有些属仰谷寄田的绿洲诸国。这些绿洲城郭诸国主要沿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周缘分布。绿洲城郭诸国以农耕为主后,虽然居民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千百年来文化变迁的历程不断在进行。《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这从生活、生产方式上说清楚了农耕、游牧文化内涵的不同。自两汉以后(至少从此时起是这样),绿洲诸农耕国是筑城而居的,较大的绿洲城郭诸国还有都城,如龟兹国的都城为三重。现存汉晋龟兹都城遗址为方形,周长约7公里。绿洲城郭诸国因生产工具、技术、农作物的改进而出现文化提升。犁耕技术至少在西汉时已出现,魏晋时,罗布泊、楼兰、龟兹等地已推广牛耕技术。犁耕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绿洲农耕文化的进程。自汉、魏晋以后,农作物也不仅仅以粮食,如小麦为主,还出现了经济作物,如棉花、葡萄等瓜果种植、菜蔬和养蚕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到隋唐时已达相当规模。在绿洲农耕社会中,铸冶业、纺织业、轮作制陶业、木器业、酿酒业、建筑业等手工业相当普遍,逐渐向专业分工化发展。这表明“人类的能量一旦解放出来并且投入到许多新的工作中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专门的非农业的工艺的发展。因而,像诸多如基本机械原理的发现,纺织、犁耕、轮作制陶以及冶金等许多发明的迅速出现,就决非偶然”①。农耕社会新的发明改变着绿洲农耕文化的旧面貌并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西域文化的历史。
天山以北草原游牧文化形成后,它就沿着与绿洲农耕文化不同的轨迹变迁着。自公元前7世纪之后,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先后迁徙和生活过塞种、月氏、乌揭、匈奴、乌孙、〓哒、柔然、突厥、蒙古等不同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因生产、生活方式大同小异,故文化上有许多趋同性。较之绿洲农耕文化而言,草原游牧文化至少因如下因素的不同,发生了较大的文化变迁:一是生产方式不同。游牧部落基本上是逐水草而放牧牲畜,而农耕则以土地为中心从事稼穑,即使有少量的家畜,但并不随季节变化转换草场,只是家庭畜养。这种分化早在塞人时期就出现了。塞人在西方文献中被分为带着崇拜的植物叶子、戴尖顶帽的和海那边或河那边的三个集团,可能第一种是定居农耕的集团,和田绿洲的早期居民即属此种,而第二种是游牧的塞人集团,他们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及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汉书·西域传》对乌孙等游牧部落的社会经济特点归结为“不田作种树(植),随畜逐水草”。二是衡量财富标准不同。绿洲农耕居民往往以土地、粮食、房产的多寡衡量财富,而游牧部落则以牲畜多少区分贫富,这还关系到部落的兴衰,《旧唐书》所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正是此意。游牧民族从根本上说是马背民族,马既是迁徙、游牧时的坐骑,又是征战的战骑。《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多马,其富人至四五千匹。”而羊、牛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生存。月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征战几乎全是骑兵。三是生活方式不同。农耕居民以村落定居方式生活,而游牧部落则是“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可拆可装的活动毡帐,随迁徙移动的羊群、牛群都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求。由此,南北不同经济社会,其风俗也各殊。
二、外来文化引起的文化变迁
外来文化和西域本土文化的碰撞从未间断过,这是由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和文化特质决定的,但引起文化变迁的主要是外来的宗教文化,而其中又主要是古代的三种宗教,即祆教、佛教、伊斯兰教。这种变迁反映在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
祆教原名琐罗亚斯德教,因崇拜天神、火神,又称为拜火教,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波斯东部,由琐罗亚斯德创立。其主要经典称为《河维斯塔》,其教义是善恶二元论。祆教于公元前4世纪传入西域,之后迅速在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地的绿洲居民中传播开来,此后,又有突厥等游牧部落信仰。祆教遗风至今还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近代游牧民族中能寻觅到。祆教为什么能在西域流传并历经一千多年兴盛不衰呢?这不能不从西域居民的早期信仰谈起。西域原始宗教中的膜拜对象是自然万物,形成自然和灵物信仰,还存在灵魂和祖先信仰,其中膜拜对象就有天地等神祗,进而西域居民中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中出现了天神观念。祆教的教义与这些原始宗教信仰一拍即合,为其传播找到了生存空间。但祆教的传播究竟怎样使西域文化发生变迁的呢?首先,祆教作为人为宗教,西域第一次出现以设祠、经典、教徒等有形方式的祭拜活动。西域各地,特别是南部、东部绿洲广设祆祠,供神主崇拜,教徒自上层人物至下层百姓均有。吐鲁番的祆祠遗址,阿拉沟、伊犁等地出土的祆教祭祀台,即为明证。其次,祆教信仰与日常习俗密切结合,改变着西域居民的信仰系统。祆教因对火、太阳的神圣信仰,故不进行水葬、火葬、土葬,而实行天葬,但到了西域,则变成火葬(以瓮罐收埋骨灰),这被认为是伊朗东部两种葬式——天葬与火葬合流的结果。①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就普遍实行过天葬。塔吉克人自称为太阳神的子孙,《大唐西域记》称其为“汉日天种”,留下了祆教崇拜的遗迹。柯尔克孜族新郎、新娘的跳火仪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新娘祭火时向火堆投放动物脂油的仪式都是祈福祛灾的信念所致,也反映出由早期的尊崇火神向祆教信仰的嬗变。最后,由于信奉祆教,引起制度性文化变迁。隋唐时期,曾建立过奉祀胡天的机构,谓之萨宝(府),其中管理祆教事务的职官即为萨宝。吐鲁番文书中就有“萨薄”(即萨宝)的记载,说明西域各绿洲城郭诸国中也同样存在负责管理祆教事务的机构并设有职官。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西域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受到萨满教、祆教信仰的本土居民的抵制,但由于上层统治者大力支持并将佛教奉为国教,结果导致萨满教、祆教受到压制乃至被取缔。不过作为一种长期植根于民间的信仰习俗,最后也渐渐融入到佛教信仰习俗中,如思想、仪式、神祗等。那么,佛教传入之后在西域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怎样的文化变迁呢?一是信仰上出现大乘教、小乘教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佛教文化中心,即于阗大乘佛教文化中心、龟兹小乘佛教文化中心、鄯善和高昌佛教文化中心。魏晋时期于阗佛教进入全盛期,僧众多时达数万人,有十四个最大的寺院,有盛大的行像仪式,而且连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于阗的译经僧。龟兹先奉大乘佛教,后改宗小乘,除兴建雀梨大寺等佛寺外,还形成以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等为中心的佛教石窟群。每年一度的全国性法事活动盛大,龟兹还出现了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译经僧。鄯善佛教与于阗、龟兹佛教有所不同,几乎是全民信仰佛教,并且形成不同的僧团,僧人可以结婚。鄯善佛教文化因汉代屯田,汉文化传统影响很深。高昌佛教曾经历麴氏高昌、唐西州、高昌回鹘等时期,高昌城建有佛寺,在吐峪沟开凿石窟,不同时期的佛教文化出现了汉风和回鹘风。二是因这些地区“俗重佛法”,从上层到民间的信仰系统和习俗都在发生巨大嬗变。佛教的法事成为生活的中心内容,形成行像、浴佛等盛大宗教活动。丧葬方式也发生变化,“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于阗国甚至出现“家家门前皆起小塔”的盛况。音乐也多是法曲,人们常常以法乐相娱,行像也是“金银雕莹”。从上层开始,追求一种奢糜、豪华的时尚,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发生着改变。三是因民族不同,佛教传入西域后发生重大变异。高昌汉人政权和唐西州时期,儒释道合一,形成有特色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随着吐蕃人援助于阗对喀喇汗朝的战争传入于阗,之后又传入高昌回鹘中。蒙元时期蒙古人已皈依藏传佛教,明清之际,厄鲁特蒙古中流行藏传佛教。清代新疆佛教信仰情况更复杂,“除了新疆原来的准噶尔部、乌梁海三部(即图瓦人)信仰格鲁派外,为防守边疆从东北、内蒙等地调来的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察哈尔部的士兵也都信仰格鲁派。满族、汉族士兵及商人、农民、官吏等也大批来到新疆各地。满族虽信仰格鲁派,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汉族的宗教信仰本来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人所信佛教为内地佛教。这样,新疆的佛教就表现为:既有原保存下来的,又有新近传入的;既有藏传佛教,又有内地佛教;即便在同一格鲁派中,也因民族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不同特点”①。
祆教、佛教等外来宗教是以和平方式传入西域的,而伊斯兰教初传之时就以武力征服了于阗。首先接受伊斯兰教的是喀喇汗朝的首领萨图克·博格拉汗。博格拉汗死后其子木萨继位,随即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喀什噶尔地区随之伊斯兰化。10世纪70年代,喀喇汗朝开始了征服于阗的“圣战”。伊斯兰教势力用武力攻城掠地,对几乎所有的佛教建筑采取了焦土政策。《突厥语大词典》中一首诗歌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势猛如山洪,攻陷他们座座城,佛堂庙宇全毁掉,菩萨身上屙一泡。”②实际情况也正如此,于阗现存佛教遗址中,均有被火焚烧过的痕迹,有些木质结构建筑一片焦黑,被烧掉的还有大量佛教经典。难怪在于阗出土的文书中难以见到一篇完整的佛教文献,反而较多保留在敦煌和吐蕃文书中。
于阗与喀喇汗朝之间的战争,既是争夺统治于阗政治权力的战争,也是一场捍卫信仰的较量,是涉及固守原有的佛教信仰还是改宗伊斯兰教信仰的重大问题。说伊斯兰势力征服于阗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年、二十四年都无大错,但彻底改变于阗人的信仰,绝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延续一个乃至几个世纪,都有可能。因为战争只能解决政权归属问题,决不可能马上解决信仰改宗问题,特别是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即使在伊斯兰教征服于阗后,于阗本土文化也在以各种方式顽强地生存着。
喀喇汗朝征服于阗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于阗居民为免遭改宗伊斯兰教,有一部分人逃到青海和西藏,与信仰佛教的吐蕃人融合了。据《皇宋十朝纲要》载:“王原至鄯州(今西宁),伪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及酋豪李阿温率回纥、于阗诸族开门出降。”可能李姓阿温就是于阗王族,随其逃到青海的于阗人不在少数。伊斯兰文化对于于阗人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不是以平等交流方式被于阗文化整合的,而是以一种“圣战”方式强行推行的。其结果是,推行之初就受到强有力抵制,一时很难融入本土文化中。于是,这种异质文化为避免过激的文化冲突,就以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色彩浸入民间文化,以图从文化根基上动摇本土文化。其中伴随“圣战”而来的是穆斯林志书《四伊玛目传》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在于阗地区流传的《四伊玛目传》有各种手抄本传世,其神话成分不能单纯看作是民间以讹传讹的产物,被“圣化”、“神化”的四个伊玛目无论其经历被编造得多么离奇,多么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他们均负有强迫于阗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使命。对此,伊玛目们说得很明白:要使此地(于阗)人也成为穆斯林,异教徒必须投降,否则将对异教徒大者杀,小者俘,城市毁灭不留。”①伊玛目们派人滥杀无辜之事,在《四伊玛目传》中也多有描写。《四伊玛目传》神化伊玛目们,归根结底是想用伊斯兰教信仰替代于阗人的佛教信仰,至于方式,只要达到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伊斯兰教文化自11世纪以来逐渐改变着于阗文化的原有风貌,它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方面使于阗文化急剧转型。
首先是作为佛教文化标志的佛寺、佛塔、佛像、佛教壁画被抹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阿拉伯建筑式样。清真寺建有“尖拱或圆拱式高大正门,主体建筑为底部方体,顶部为穹隆式圆拱形式,由于呼唤礼拜的需要,一般在大门或主体建筑两侧建有邦克楼(又称唤礼塔)”。②麻扎、经文学校甚至民居也呈阿拉伯建筑风格,装饰也被非偶像崇拜的花卉、几何图案代替。和田地区现还存有清代礼拜寺,如和田市区内的加满清真寺、皮山大清真寺、策勒加帕尔特合兰清真寺,距今约120~200年左右,均为伊斯兰风格建筑。而众多的麻扎,如洛浦的巴格达提麻扎、伊玛目阿斯木麻扎、玉吉曼麻扎、民丰县的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等,都是伊斯兰教传入于阗后的产物。不过,元、明以前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现几乎不存,更不用说是喀喇汗朝时代的建筑了。
从丧葬物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对于阗物质文化的深刻影响。北魏时宋云抵达于阗,还见到此地葬俗是按佛教葬仪进行的:“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但伊斯兰教传入后葬式一律改为土葬,葬具用抬尸床,白布裹尸,土坯起造坟墓,并请阿訇念经、祈祷。从丧葬用品、葬具制式及葬法看,于阗人在信仰佛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前后不同时期均有天壤之别。
其次是伊斯兰制度文化,如阿拉伯的经书、契约文书替代了于阗文本土文书。但在于阗出土的阿拉伯文书极为罕见,而与之相邻的莎车却出土了不少阿拉伯文文书。有记载的是“马继业还从和田获得属于喀喇汗朝时期的4件阿拉伯(其中有两件分别标明回历401年/公元1010~1011年和回历501年/公元1107年)和24件回鹘文文书”③。从其中一件莎车出土的阿拉伯文法律诉讼文书看,行文上有一套按伊斯兰教宗旨规定的固定式样,如开头是对安拉的赞颂,法官以安拉的名义以及对汗王的歌颂等,行文中间事实及结尾判决部分也穿插“向至高无上的真主乞求帮助”①等内容。随着伊斯兰教传入的还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这是穆斯林必诵的经典。因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一直被伊斯兰教神学家宣扬为安拉用阿拉伯语颁降的‘天启’经典,因此用以诵读和书写《古兰经》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允许信徒翻译的。不管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不管操何种语言、使用何种文字,只要是穆斯林,就只能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诵读和书写《古兰经》经文”②。从上面阿拉伯文法律诉讼文书看,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已成了喀喇汗朝的官方语文,同时审判制度也沿用了伊斯兰教裁判制度。
阿拉伯语言、文字的使用,导致于阗等地区的本土语言、文字发生转型,且不说本地语言中杂糅了许多阿拉伯语词汇,以后流行于喀什、于阗地区的察合台文也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最后是文学艺术和民俗也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到蒙元时期,于阗地区完全伊斯兰化,而且伊斯兰教呈自南向北发展趋势。对此,马可·波罗记道:“(忽炭)居民崇拜摩诃末(即穆罕默德)。”③自喀喇汗朝之后,用阿拉伯文创作和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回鹘语的作品层出不穷,模仿阿拉伯伊斯兰作品的格式也成了一种时髦。一般文学作品都有赞颂安拉、先知、圣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开篇形式,然后再转入正文。当时流行于喀喇汗朝时期的《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均采用这种结构。和田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初期的文学创作情况无案可查,现在可考的是18世纪的和田诗人努比提·马赫逊和墨玉诗人艾合买提·喀拉喀什、毛拉·萨里赫的作品。努比提曾系统学习过波斯语,而艾合买提·喀拉喀什则在喀什噶尔的伊斯兰经学院修业十年。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免不了在开头部分循着时尚有“颂”(Munajat)的内容,格律上也开始出现模仿体,但像努比提的诗歌创作,如《格则勒》、《柔巴依》显然还受到中亚诗歌的影响,不过所写《和田礼赞》等更世俗化,充满作者的故土情结。
伊斯兰教对于阗本土世俗习俗的影响主要是迫使居民不得不放弃与伊斯兰教教规相牴牾的一些风俗习惯,于阗人的婚丧嫁娶、成人、命名、节庆等仪式都充满了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婚礼上的尼卡仪式、割礼、取名宗教化,世俗节日被宗教节日代替,都是文化转型期内由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变迁。于阗人中尽管还保留着自然崇拜的痕迹,但信仰完全由非偶像崇拜代替了多神信仰。这种现象越到后来,如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时期及清代就越普遍。明清时期,苏非派诗歌等在新疆南部绿洲地区广为传播,其中推波助澜的是苏非派传教士。
一、社会生产方式变更引起的文化变迁
西域旧石器和细石器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狩猎和采集,但是随着氏族集团人口的增多,猎获动物数量的减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西域出现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这是一个渐变的文化变迁过程,两种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剥离,也就是说无论是天山以南还是以北地区,在此阶段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同时还存在狩猎生产方式。这个时期的西域史前先民从游移迁徙走向定居,使用金属工具,家养牲畜,耕种农作物并使用陶器等日用器皿,衣食质量也大为提高。这种定居聚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广泛分布。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遗址主要有东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北疆的柴窝堡、南疆的辛格尔、乌帕尔及罗布泊一带。青铜时代的定居聚落则有东疆巴里坤的南湾、兰州湾子及伊吾县的军马场、卡尔桑遗址和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遗址、南疆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和小河附近的5号墓地、和硕的新塔拉遗址、库车的哈拉墩遗址、疏附的阿克塔拉遗址以及北疆塔城卫生学校遗址等。
让我们剖析一个以畜牧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个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孔雀河古墓沟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表明,罗布泊地区曾生活着以畜牧业为主体、兼营农业的氏族集团。从所发掘的42座古墓葬可以认定,这是距今3800年前的定居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有牛羊角、毛织品(毛布、毛毯、尖顶毡帽等)、皮革制品、木雕、铜制品、骨制品、角制品、小麦粒、草编制品等,但不见陶器。从有环列木桩和无环形列木的墓表特征及随葬品看,此处已形成一种有特色的地方性葬俗。据此,“发掘资料具体表明,当时古墓沟人的生产以畜牧业为主体,主要饲养羊、牛,羊有山羊、绵羊。在一座墓葬中,随殉的牛、羊角多达26支,说明已有相当规模的牲畜积累。鞋、帽、包覆身体的毛布或毛毯,也都取自羊绒、皮张,主要依靠畜牧业。足以说明,畜牧业是当时人民生活的衣、食之源,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是存在的,墓区发现的小麦粒,是一个直接的说明。但出土数量,从总体看,只占很小比例。孔雀河谷可得灌溉之便,少量的农业经营是完全可能存在的。”①但是古墓沟定居文化是以墓葬发掘推论定居聚落的,还未及对定居点遗址进行发掘,而木垒四道沟遗址则被认为是西域原始社会晚期的遗址之一。四道沟定居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是发现圆形房屋的遗址,有柱洞和灶址;二是出土有彩陶、夹砂陶,可分为容器、炊具、工具、玩具等;三是出土有磨盘、石锄、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及铜刀等。遗址分早晚二期,可以明显看出在生产方式上由采集狩猎过渡到相对定居的聚落生活。②晚期,显然是农业和畜牧业占有同等重要地位,并伴有狩猎活动。
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引起物质文化的变迁,同样引起信仰习俗的嬗变。从自然和灵物崇拜到灵魂和祖先崇拜,都反映着西域先民原始信仰种种复杂的精神活动。新疆出土的女神偶像、男性石祖,揭示了从女性祖先到男性祖先信仰的渐变过程。原始信仰形成一套行为仪式。
考古学家认为,西域早期铁器时代是畜牧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重要标志,自此之后,形成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文化和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格局,这种格局延续至今并无多大变化。不过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混融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对这两种生产方式分离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西域境内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影响的北疆宜于畜牧业而南疆适合农业的经济形态格局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早期铁器时代即已开始形成了。”①哈密的焉不拉克文化和和静的察吾乎沟口文化是这一时期由生产方式变更引发的文化变迁的典型例证。这两个文化的共同点是:一是大量陶器的出现,彩陶较多,可分为带流罐、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单耳豆、腹耳壶、钵等,此外还有盘、碗、勺、桶、铣、耜、锥、纺轮等木器,器皿增多表明农耕定居生活进入新阶段。二是铁器出现,前者出土物为刀、剑等武器和戒指等,不见铁制农具;而后者除武器外,还有铁镰等农具。三是两处文化遗址均有谷物,如小麦、青稞、小米饼出土,又见马、牛、羊骨和大量毛织物。四是形成二次葬、合葬、屈肢葬及祭祀等葬俗。五是手工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工艺技术日臻完善。种种物证表明,焉不拉克、察吾乎沟口等属于以农耕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氏族社会文化。“而在北疆区的大部分遗址或墓葬中所见到的多是马、牛、羊骨和与畜牧经济有关的小工具,却很少或不见农业的踪迹,北疆区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畜牧业”②。北疆地区草原游牧业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家马的出现。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西域的游牧部落于何时何地驯服了马,但“马的贡献都在于它的流动性,它使其主人能够照料广泛散布的畜群,它可以迅速移动以抵御来自那些专好偷窃别人牲畜的敌对邻邦的威胁”③。
天山以南绿洲城郭诸国和天山以北草原游牧行国的出现,标志着西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按不同轨迹发展,并按生产方式的不同,发生着迥异的文化变迁。汉文文献所载西域三十六国,按生产方式不同,出现了以农耕为主的精绝、扜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等国,还有些属仰谷寄田的绿洲诸国。这些绿洲城郭诸国主要沿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周缘分布。绿洲城郭诸国以农耕为主后,虽然居民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千百年来文化变迁的历程不断在进行。《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这从生活、生产方式上说清楚了农耕、游牧文化内涵的不同。自两汉以后(至少从此时起是这样),绿洲诸农耕国是筑城而居的,较大的绿洲城郭诸国还有都城,如龟兹国的都城为三重。现存汉晋龟兹都城遗址为方形,周长约7公里。绿洲城郭诸国因生产工具、技术、农作物的改进而出现文化提升。犁耕技术至少在西汉时已出现,魏晋时,罗布泊、楼兰、龟兹等地已推广牛耕技术。犁耕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绿洲农耕文化的进程。自汉、魏晋以后,农作物也不仅仅以粮食,如小麦为主,还出现了经济作物,如棉花、葡萄等瓜果种植、菜蔬和养蚕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到隋唐时已达相当规模。在绿洲农耕社会中,铸冶业、纺织业、轮作制陶业、木器业、酿酒业、建筑业等手工业相当普遍,逐渐向专业分工化发展。这表明“人类的能量一旦解放出来并且投入到许多新的工作中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专门的非农业的工艺的发展。因而,像诸多如基本机械原理的发现,纺织、犁耕、轮作制陶以及冶金等许多发明的迅速出现,就决非偶然”①。农耕社会新的发明改变着绿洲农耕文化的旧面貌并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西域文化的历史。
天山以北草原游牧文化形成后,它就沿着与绿洲农耕文化不同的轨迹变迁着。自公元前7世纪之后,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先后迁徙和生活过塞种、月氏、乌揭、匈奴、乌孙、〓哒、柔然、突厥、蒙古等不同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因生产、生活方式大同小异,故文化上有许多趋同性。较之绿洲农耕文化而言,草原游牧文化至少因如下因素的不同,发生了较大的文化变迁:一是生产方式不同。游牧部落基本上是逐水草而放牧牲畜,而农耕则以土地为中心从事稼穑,即使有少量的家畜,但并不随季节变化转换草场,只是家庭畜养。这种分化早在塞人时期就出现了。塞人在西方文献中被分为带着崇拜的植物叶子、戴尖顶帽的和海那边或河那边的三个集团,可能第一种是定居农耕的集团,和田绿洲的早期居民即属此种,而第二种是游牧的塞人集团,他们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及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汉书·西域传》对乌孙等游牧部落的社会经济特点归结为“不田作种树(植),随畜逐水草”。二是衡量财富标准不同。绿洲农耕居民往往以土地、粮食、房产的多寡衡量财富,而游牧部落则以牲畜多少区分贫富,这还关系到部落的兴衰,《旧唐书》所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正是此意。游牧民族从根本上说是马背民族,马既是迁徙、游牧时的坐骑,又是征战的战骑。《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多马,其富人至四五千匹。”而羊、牛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生存。月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征战几乎全是骑兵。三是生活方式不同。农耕居民以村落定居方式生活,而游牧部落则是“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可拆可装的活动毡帐,随迁徙移动的羊群、牛群都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求。由此,南北不同经济社会,其风俗也各殊。
二、外来文化引起的文化变迁
外来文化和西域本土文化的碰撞从未间断过,这是由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和文化特质决定的,但引起文化变迁的主要是外来的宗教文化,而其中又主要是古代的三种宗教,即祆教、佛教、伊斯兰教。这种变迁反映在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
祆教原名琐罗亚斯德教,因崇拜天神、火神,又称为拜火教,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波斯东部,由琐罗亚斯德创立。其主要经典称为《河维斯塔》,其教义是善恶二元论。祆教于公元前4世纪传入西域,之后迅速在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地的绿洲居民中传播开来,此后,又有突厥等游牧部落信仰。祆教遗风至今还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近代游牧民族中能寻觅到。祆教为什么能在西域流传并历经一千多年兴盛不衰呢?这不能不从西域居民的早期信仰谈起。西域原始宗教中的膜拜对象是自然万物,形成自然和灵物信仰,还存在灵魂和祖先信仰,其中膜拜对象就有天地等神祗,进而西域居民中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中出现了天神观念。祆教的教义与这些原始宗教信仰一拍即合,为其传播找到了生存空间。但祆教的传播究竟怎样使西域文化发生变迁的呢?首先,祆教作为人为宗教,西域第一次出现以设祠、经典、教徒等有形方式的祭拜活动。西域各地,特别是南部、东部绿洲广设祆祠,供神主崇拜,教徒自上层人物至下层百姓均有。吐鲁番的祆祠遗址,阿拉沟、伊犁等地出土的祆教祭祀台,即为明证。其次,祆教信仰与日常习俗密切结合,改变着西域居民的信仰系统。祆教因对火、太阳的神圣信仰,故不进行水葬、火葬、土葬,而实行天葬,但到了西域,则变成火葬(以瓮罐收埋骨灰),这被认为是伊朗东部两种葬式——天葬与火葬合流的结果。①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就普遍实行过天葬。塔吉克人自称为太阳神的子孙,《大唐西域记》称其为“汉日天种”,留下了祆教崇拜的遗迹。柯尔克孜族新郎、新娘的跳火仪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新娘祭火时向火堆投放动物脂油的仪式都是祈福祛灾的信念所致,也反映出由早期的尊崇火神向祆教信仰的嬗变。最后,由于信奉祆教,引起制度性文化变迁。隋唐时期,曾建立过奉祀胡天的机构,谓之萨宝(府),其中管理祆教事务的职官即为萨宝。吐鲁番文书中就有“萨薄”(即萨宝)的记载,说明西域各绿洲城郭诸国中也同样存在负责管理祆教事务的机构并设有职官。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西域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受到萨满教、祆教信仰的本土居民的抵制,但由于上层统治者大力支持并将佛教奉为国教,结果导致萨满教、祆教受到压制乃至被取缔。不过作为一种长期植根于民间的信仰习俗,最后也渐渐融入到佛教信仰习俗中,如思想、仪式、神祗等。那么,佛教传入之后在西域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怎样的文化变迁呢?一是信仰上出现大乘教、小乘教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佛教文化中心,即于阗大乘佛教文化中心、龟兹小乘佛教文化中心、鄯善和高昌佛教文化中心。魏晋时期于阗佛教进入全盛期,僧众多时达数万人,有十四个最大的寺院,有盛大的行像仪式,而且连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于阗的译经僧。龟兹先奉大乘佛教,后改宗小乘,除兴建雀梨大寺等佛寺外,还形成以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等为中心的佛教石窟群。每年一度的全国性法事活动盛大,龟兹还出现了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译经僧。鄯善佛教与于阗、龟兹佛教有所不同,几乎是全民信仰佛教,并且形成不同的僧团,僧人可以结婚。鄯善佛教文化因汉代屯田,汉文化传统影响很深。高昌佛教曾经历麴氏高昌、唐西州、高昌回鹘等时期,高昌城建有佛寺,在吐峪沟开凿石窟,不同时期的佛教文化出现了汉风和回鹘风。二是因这些地区“俗重佛法”,从上层到民间的信仰系统和习俗都在发生巨大嬗变。佛教的法事成为生活的中心内容,形成行像、浴佛等盛大宗教活动。丧葬方式也发生变化,“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于阗国甚至出现“家家门前皆起小塔”的盛况。音乐也多是法曲,人们常常以法乐相娱,行像也是“金银雕莹”。从上层开始,追求一种奢糜、豪华的时尚,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发生着改变。三是因民族不同,佛教传入西域后发生重大变异。高昌汉人政权和唐西州时期,儒释道合一,形成有特色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随着吐蕃人援助于阗对喀喇汗朝的战争传入于阗,之后又传入高昌回鹘中。蒙元时期蒙古人已皈依藏传佛教,明清之际,厄鲁特蒙古中流行藏传佛教。清代新疆佛教信仰情况更复杂,“除了新疆原来的准噶尔部、乌梁海三部(即图瓦人)信仰格鲁派外,为防守边疆从东北、内蒙等地调来的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察哈尔部的士兵也都信仰格鲁派。满族、汉族士兵及商人、农民、官吏等也大批来到新疆各地。满族虽信仰格鲁派,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汉族的宗教信仰本来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人所信佛教为内地佛教。这样,新疆的佛教就表现为:既有原保存下来的,又有新近传入的;既有藏传佛教,又有内地佛教;即便在同一格鲁派中,也因民族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不同特点”①。
祆教、佛教等外来宗教是以和平方式传入西域的,而伊斯兰教初传之时就以武力征服了于阗。首先接受伊斯兰教的是喀喇汗朝的首领萨图克·博格拉汗。博格拉汗死后其子木萨继位,随即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喀什噶尔地区随之伊斯兰化。10世纪70年代,喀喇汗朝开始了征服于阗的“圣战”。伊斯兰教势力用武力攻城掠地,对几乎所有的佛教建筑采取了焦土政策。《突厥语大词典》中一首诗歌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势猛如山洪,攻陷他们座座城,佛堂庙宇全毁掉,菩萨身上屙一泡。”②实际情况也正如此,于阗现存佛教遗址中,均有被火焚烧过的痕迹,有些木质结构建筑一片焦黑,被烧掉的还有大量佛教经典。难怪在于阗出土的文书中难以见到一篇完整的佛教文献,反而较多保留在敦煌和吐蕃文书中。
于阗与喀喇汗朝之间的战争,既是争夺统治于阗政治权力的战争,也是一场捍卫信仰的较量,是涉及固守原有的佛教信仰还是改宗伊斯兰教信仰的重大问题。说伊斯兰势力征服于阗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年、二十四年都无大错,但彻底改变于阗人的信仰,绝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延续一个乃至几个世纪,都有可能。因为战争只能解决政权归属问题,决不可能马上解决信仰改宗问题,特别是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即使在伊斯兰教征服于阗后,于阗本土文化也在以各种方式顽强地生存着。
喀喇汗朝征服于阗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于阗居民为免遭改宗伊斯兰教,有一部分人逃到青海和西藏,与信仰佛教的吐蕃人融合了。据《皇宋十朝纲要》载:“王原至鄯州(今西宁),伪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及酋豪李阿温率回纥、于阗诸族开门出降。”可能李姓阿温就是于阗王族,随其逃到青海的于阗人不在少数。伊斯兰文化对于于阗人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不是以平等交流方式被于阗文化整合的,而是以一种“圣战”方式强行推行的。其结果是,推行之初就受到强有力抵制,一时很难融入本土文化中。于是,这种异质文化为避免过激的文化冲突,就以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色彩浸入民间文化,以图从文化根基上动摇本土文化。其中伴随“圣战”而来的是穆斯林志书《四伊玛目传》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在于阗地区流传的《四伊玛目传》有各种手抄本传世,其神话成分不能单纯看作是民间以讹传讹的产物,被“圣化”、“神化”的四个伊玛目无论其经历被编造得多么离奇,多么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他们均负有强迫于阗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使命。对此,伊玛目们说得很明白:要使此地(于阗)人也成为穆斯林,异教徒必须投降,否则将对异教徒大者杀,小者俘,城市毁灭不留。”①伊玛目们派人滥杀无辜之事,在《四伊玛目传》中也多有描写。《四伊玛目传》神化伊玛目们,归根结底是想用伊斯兰教信仰替代于阗人的佛教信仰,至于方式,只要达到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伊斯兰教文化自11世纪以来逐渐改变着于阗文化的原有风貌,它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方面使于阗文化急剧转型。
首先是作为佛教文化标志的佛寺、佛塔、佛像、佛教壁画被抹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阿拉伯建筑式样。清真寺建有“尖拱或圆拱式高大正门,主体建筑为底部方体,顶部为穹隆式圆拱形式,由于呼唤礼拜的需要,一般在大门或主体建筑两侧建有邦克楼(又称唤礼塔)”。②麻扎、经文学校甚至民居也呈阿拉伯建筑风格,装饰也被非偶像崇拜的花卉、几何图案代替。和田地区现还存有清代礼拜寺,如和田市区内的加满清真寺、皮山大清真寺、策勒加帕尔特合兰清真寺,距今约120~200年左右,均为伊斯兰风格建筑。而众多的麻扎,如洛浦的巴格达提麻扎、伊玛目阿斯木麻扎、玉吉曼麻扎、民丰县的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等,都是伊斯兰教传入于阗后的产物。不过,元、明以前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现几乎不存,更不用说是喀喇汗朝时代的建筑了。
从丧葬物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对于阗物质文化的深刻影响。北魏时宋云抵达于阗,还见到此地葬俗是按佛教葬仪进行的:“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但伊斯兰教传入后葬式一律改为土葬,葬具用抬尸床,白布裹尸,土坯起造坟墓,并请阿訇念经、祈祷。从丧葬用品、葬具制式及葬法看,于阗人在信仰佛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前后不同时期均有天壤之别。
其次是伊斯兰制度文化,如阿拉伯的经书、契约文书替代了于阗文本土文书。但在于阗出土的阿拉伯文书极为罕见,而与之相邻的莎车却出土了不少阿拉伯文文书。有记载的是“马继业还从和田获得属于喀喇汗朝时期的4件阿拉伯(其中有两件分别标明回历401年/公元1010~1011年和回历501年/公元1107年)和24件回鹘文文书”③。从其中一件莎车出土的阿拉伯文法律诉讼文书看,行文上有一套按伊斯兰教宗旨规定的固定式样,如开头是对安拉的赞颂,法官以安拉的名义以及对汗王的歌颂等,行文中间事实及结尾判决部分也穿插“向至高无上的真主乞求帮助”①等内容。随着伊斯兰教传入的还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这是穆斯林必诵的经典。因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一直被伊斯兰教神学家宣扬为安拉用阿拉伯语颁降的‘天启’经典,因此用以诵读和书写《古兰经》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允许信徒翻译的。不管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不管操何种语言、使用何种文字,只要是穆斯林,就只能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诵读和书写《古兰经》经文”②。从上面阿拉伯文法律诉讼文书看,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已成了喀喇汗朝的官方语文,同时审判制度也沿用了伊斯兰教裁判制度。
阿拉伯语言、文字的使用,导致于阗等地区的本土语言、文字发生转型,且不说本地语言中杂糅了许多阿拉伯语词汇,以后流行于喀什、于阗地区的察合台文也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最后是文学艺术和民俗也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到蒙元时期,于阗地区完全伊斯兰化,而且伊斯兰教呈自南向北发展趋势。对此,马可·波罗记道:“(忽炭)居民崇拜摩诃末(即穆罕默德)。”③自喀喇汗朝之后,用阿拉伯文创作和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回鹘语的作品层出不穷,模仿阿拉伯伊斯兰作品的格式也成了一种时髦。一般文学作品都有赞颂安拉、先知、圣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开篇形式,然后再转入正文。当时流行于喀喇汗朝时期的《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均采用这种结构。和田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初期的文学创作情况无案可查,现在可考的是18世纪的和田诗人努比提·马赫逊和墨玉诗人艾合买提·喀拉喀什、毛拉·萨里赫的作品。努比提曾系统学习过波斯语,而艾合买提·喀拉喀什则在喀什噶尔的伊斯兰经学院修业十年。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免不了在开头部分循着时尚有“颂”(Munajat)的内容,格律上也开始出现模仿体,但像努比提的诗歌创作,如《格则勒》、《柔巴依》显然还受到中亚诗歌的影响,不过所写《和田礼赞》等更世俗化,充满作者的故土情结。
伊斯兰教对于阗本土世俗习俗的影响主要是迫使居民不得不放弃与伊斯兰教教规相牴牾的一些风俗习惯,于阗人的婚丧嫁娶、成人、命名、节庆等仪式都充满了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婚礼上的尼卡仪式、割礼、取名宗教化,世俗节日被宗教节日代替,都是文化转型期内由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变迁。于阗人中尽管还保留着自然崇拜的痕迹,但信仰完全由非偶像崇拜代替了多神信仰。这种现象越到后来,如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时期及清代就越普遍。明清时期,苏非派诗歌等在新疆南部绿洲地区广为传播,其中推波助澜的是苏非派传教士。
附注
①〔美〕克莱德·伍兹著,施惟达,胡华生.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21~22.
②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78~179.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95.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发掘报告.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人民出版社,1995.127.
①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30.
②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9~30.
③〔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96~97.
①〔美〕罗伯特·J.布雷伍德.农业革命.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62~263.
①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106.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77~78.
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汉译本.民族出版社,2002.363.
①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176.
②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115.
③牛汝极.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西域研究.1999(3).
①牛汝极.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西域研究.1999(3).
②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115.
③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63.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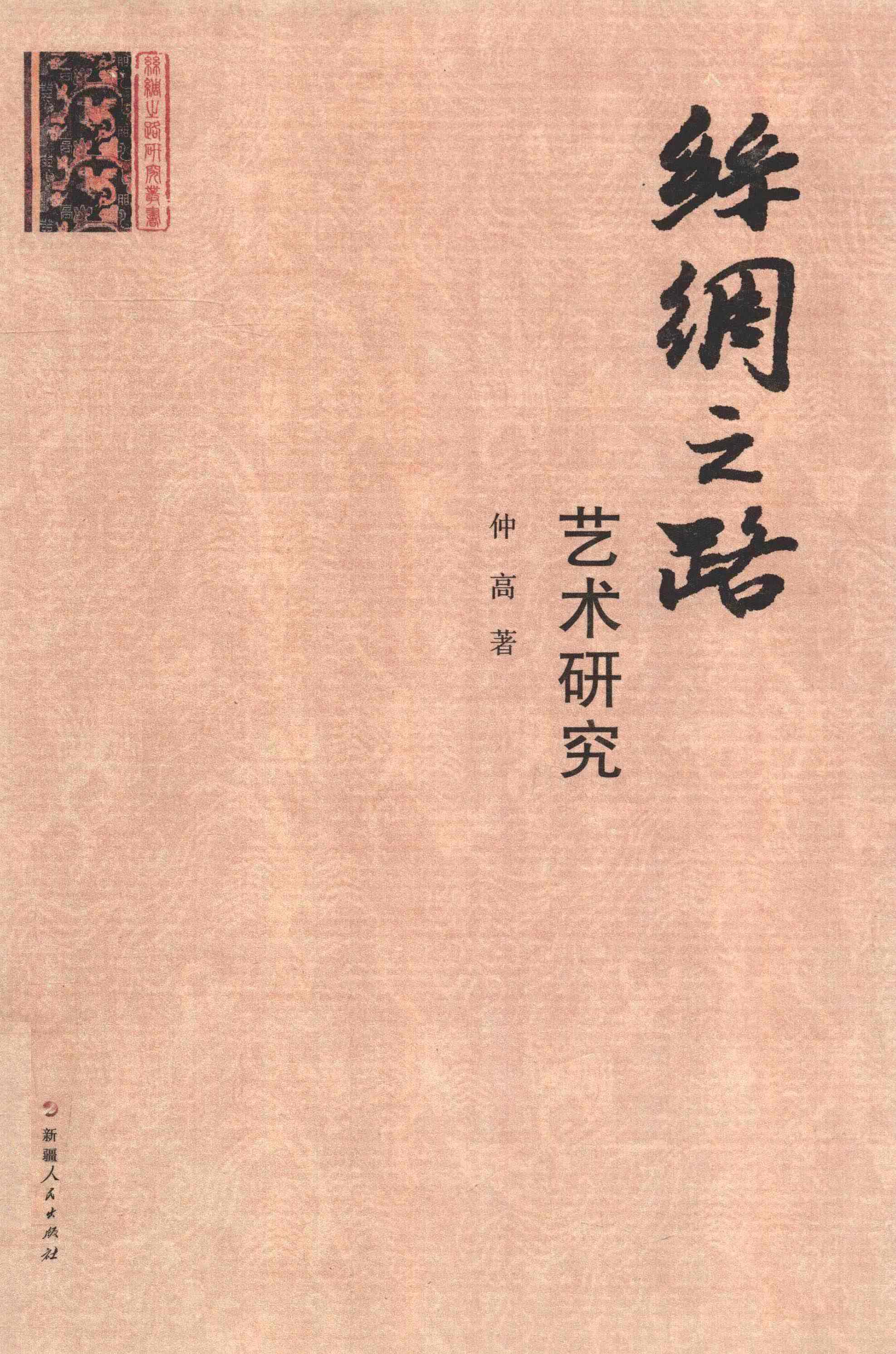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文记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