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歌的涵义和分类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297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丝绸之路民族民歌的涵义和分类 |
| 分类号: | I207.72 |
| 页数: | 8 |
| 页码: | 164-17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丝绸之路民族民歌的涵义和分类的情况。其中包括古歌、劳动歌、习俗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宗教礼仪歌等。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民族民歌 涵义 |
内容
丝绸之路民歌,是指流传在古代西域各民族中间的一种形式短小、多样,具有丰富内容和独特形式、韵律的韵文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丝绸之路民歌从各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西域各民族劳动、习俗、爱情婚姻、宗教仪式等社会生活内容。数量众多的丝绸之路民歌,以其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歌形象,真实而艺术地投射出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特征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在丝绸之路民间文学艺苑中占据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一席之地。
丝绸之路民歌在西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少民族成员,从婴儿诞生来到人间直至最后逝世丧葬,在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都伴随着民歌的演唱。这正如哈萨克族俗语所说,“哈萨克伴随着歌声来到人世,伴随着歌声死去”。创作和演唱民歌,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歌不仅记录着各民族成员的人生历程,而且还程度不同地成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各个民族在他们自己民歌的花坛上,演唱着自己民族的兴衰变化,表演着自己民族的生活礼仪,共识和认同着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
西域各民族似乎都有较为深厚的诗歌传统。但是民歌,它带着与生俱来的特质与后来同属于诗歌范畴的史诗、叙事诗等相比较,在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上,在形式的多样化上,在演唱的形式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其中,载歌载舞,又说又唱,恐怕是最显著的区分之一。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对唱”,达斡尔族“大奥”的载歌载舞,回族的“花儿”演唱,锡伯族的“舞春”等,都带有强烈的歌舞性。这些民歌的演唱,大约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艺术、服饰造型艺术等为一体,呈现出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与民间艺术活动相济相生的动人情景。
丝绸之路民歌内容丰富广泛,分类庞杂。据现有研究资料,有的学者以民族分类,如维吾尔族民歌、哈萨克族民歌、塔吉克族民歌、乌孜别克族民歌等等;有的学者以流传地域分类,如伊犁民歌、库车民歌、喀什民歌、昌吉民歌等;有的学者以内容分类,如古歌、劳动歌、仪式歌、风俗歌、迁徙歌、颂歌、情歌、儿歌、宗教歌等;还有的学者以演唱表现形式分类,如哈萨克族民歌中的“吐列对唱”和“苏列对唱”,回族民歌中的“花儿”和“宴席曲”,达斡尔族民歌中的“大奥”、“扎恩达勒”、“舞春”、“舞词”、“祝词和赞词”等。为便于叙述,我们拟将丝绸之路各民族民歌分为六类:古歌、劳动歌、习俗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宗教礼仪歌及其他歌。
古歌
古歌,是丝绸之路各民族口头创作和流传的古史歌,又称“根的歌”。这类民歌其内容大多是创世和族源传说,具有奇特想象和大胆夸张,幻想成分浓重,可以说是民歌形式的民族神话传说。古歌在丝绸之路民歌中数量不多,但影响甚大,它直接影响到神话、传说、史诗、民间叙事诗等的创作和流传。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从散见的其他民间文学形式中窥见丝绸之路民族古歌的一些蛛丝马迹。如,哈萨克族记述先祖的一些古歌,在韵散相间的《先祖阔尔库特书》各篇章中还可看到。阔尔库特,是流传在哈萨克民间的一位神话般的著名人物,他是哈萨克人心目中一位圣人、贤哲、无所不知的预言者和智慧的化身。关于此,在《阔尔库特之歌》中这样唱道:
在古时,
在太阳升起的东方,
在大名鼎鼎的阿尔泰山之阳,
曾经生活过一位阔尔库特老人,
他是圣明的先哲,
他见多识广。
在这部韵散相间,带有浓重哈萨克先人古代英雄歌谣印痕的作品中,含有丰富的同哈萨克族源有关的古代突厥部族的英雄传说和英雄歌谣的内容。虽经后人的复合、加工、扩充与缀连,但其中古歌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古歌部分以鲜活的口头文学特色形成了哈萨克族民间说唱文学的源头之一,就是对后来的《阿勒帕梅斯》、《阿勒克·蔑尔干》等著名作品也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劳动歌
这类反映西域各族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歌在丝绸之路民歌中数量较多,极为丰富。无论是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还是农耕为主的维吾尔族、回族,以及狩猎为主的锡伯族、塔吉克族等,都流传有大量的反映他们劳动过程、生产经验和在劳动中表现出某种真情实感、劳动场面情景的民歌。如,哈萨克族的“畜牧生产歌”,以马、驼、羊、牛四种牲畜为题,具体描述了这些牲畜的习性,如何饲养放牧管理,强烈地表现出哈萨克民族增殖牲畜、发展生产的愿望和对牲畜的珍爱之情。又如,锡伯族的“猎歌”、蒙古族的“接羔歌”、柯尔克孜族的“牧马歌”、塔吉克族的“牧羊歌”、乌孜别克族的“割麦歌”、回族的“犁地歌”、维吾尔族的“麦收歌”等等,都是以歌谣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丝绸之路各民族在特殊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为求取生存、发展而走过的生产劳动的足迹。此外,在这些民歌中还涌动着丝绸之路西域民族独特的思维心理、宗教感情,从而构成作品特有的旋律、韵味和节奏,读来别具风味。如在柯尔克孜族中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守圈歌》。这首被称为“别克别凯依”的古老的劳动歌,大多在夏夜为牧民看守羊圈的妇女所传唱。歌中开头一段是这么唱的:
我把针尖弄弯了呀!哎,哎,哎依!
今天我看守羊圈,哎,哎,哎依!
我又把针尖弄直了呀!哎,哎,哎依!
怕丢羊,我才来守圈。哎,哎,哎依!
棍子是坚硬的楂木做的啊!
豺狼、小偷休想靠边!
若有小偷来,就擒住他,
我们要把他头打烂。哎,哎,哎依!
圈旁有条小道,
但愿我的羊群平安!
姑娘、媳妇们看守羊圈,
这是自古传下来的习惯。
整首民歌有领唱、对昌、合唱,在通宵达旦的演唱中流露出柯尔克孜族妇女对自然,对畜群,对部落和对别克别凯依神的特殊感情。
习俗仪式歌
丝绸之路各民族中流传盛行的习俗仪式类民歌,它是在各民族民间礼俗和礼典仪式上吟诵和歌唱的。在丝绸之路各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华彩乐章。根据各民族习俗和仪式的要求,这类民歌在内容上有着相对集中的题材,在形式上有着较为固定的格式,并以固定的民间曲调吟唱。哈萨克族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哈萨克族人从生到死的每个人生历程中都随时伴响着这种习俗礼仪民歌的吟唱。如,婴儿生下时,要为婴儿举行三个晚上的“诞生歌”歌唱活动;女儿长大成人举行婚礼,有名目繁多的“婚礼歌”(主要包括“婚序歌”、“劝嫁歌”、“哭嫁歌”、“揭面纱歌”等),亲友去世有“报丧歌”、“挽歌”。此外,还有不少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告别歌”、“摇篮歌”、“戒律歌”等民歌。在丝绸之路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大量的习俗仪式民歌。维吾尔族在过“白雪节”时要吟唱传送祝福平安的“信歌”,肉孜节时要演唱“祝福歌”,女儿出嫁时母亲要唱“送嫁歌”,婚后新郎去拜谒岳父岳母要唱“婚礼歌”等,蒙古族卫拉特人在酒宴上除了豪饮外还要纵情高歌“宴歌”。在他们看来“没有歌声的喜宴不算喜宴,不唱酒歌的宴席没有欢乐”,至于像“那达慕”这样的喜庆节日更是歌不离口了;在塔吉克族中,男婚女嫁、欢迎宾客、祝贺节日、贺生送葬等礼仪场合都要吟唱礼俗歌。如欢度一年一度的“乞脱乞迪尔爱脱节”时,除了大扫除,向墙上撒面粉,妇女给来宾在肩上撒面粉等传统礼仪外,全村还要公推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依次到各家吟唱祝贺新春和丰收的颂歌;在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等民族中也流传着丰富的习俗礼仪民歌。尤其是在婚丧嫁娶活动中,这类民歌更是无处不有,无时不有。
值得指出的是,这类习俗礼仪民歌由于它特殊的社会作用,在传统文化强有力的影响下,从内容到形式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套式。尽管由于某些场合的特殊要求,在个别词句上有些增减,但通常都尽量保存其产生和流传中的口语形式和原始状态,一般不允许即兴式的创作。因为这种礼俗民歌的演唱,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演唱,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融化为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在民族精神、心理的深处,从而转化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延续传递给后代。例如,我们上述提到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婚礼歌,都是伴随婚礼每一套完整的仪式而出现相应的具有固定套式的“劝嫁”、“哭嫁”、“揭面纱”等婚礼歌内容,在形式上(衬字衬词、换韵、曲调节奏等)更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演唱这类婚礼歌,已超出一般观赏创作民间文艺的意义,在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气氛中,你会身不由己地全身心投入到一种民族习俗文化活动中去而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些礼俗民歌,随着丝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会不断地发生着某些变化。有些随同原来依附的仪式一齐消亡,有些仪式虽然废除,但仪式歌却保存延续下来,成为民族习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外,丝绸之路民族习俗仪式类民歌因受民族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伴有一定的祈祷目的(祈年,禳灾,告祖,求福等)。如在乌孜别克族中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求雨歌》。歌中唱道:
下雨吧,女婆,
让小麦丰收吧,女婆,
让人们吃饱吧,女婆,
女婆,苏丹女婆!
让收成丰盛,女婆,
让谷物堆满农家,女婆,
让说谎话的人家里空空,女婆,
女婆,苏丹女婆!
这首著名的《求雨歌》,一方面反映出乌孜别克族祈求降雨的风习:祈雨者把两根木棍对着捆起来,裹上妇女衣服,头顶面纱,扮成妇女样举着偶像逐门挨户求雨唱《求雨歌》,集中地表现了人们祈雨渴望丰收的愿望;另一方面这首民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乌孜别克人对“苏丹女婆”神的敬畏和崇拜,希望能得到她的保护,弥漫着浓重的原始宗教气息。
情歌
在丝路民族中,情歌大约是传唱最多、最为丰富多彩具有魅力的一种民歌种类了。与汉族相比,青年男女之间较为自由的择偶,其方式大多又用歌唱来表情达意,加之融入民族习俗中的歌唱传统,这些为丝绸之路民族情歌的创作和流传造成了一定的条件。丝路民族情歌主要以歌唱爱情为主。青年男女从相识、初恋到相互结合,在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情歌来表达男女之间热烈而复杂的感情。当爱情萌生建立时,他们有初识歌、结交歌、赞美歌、迷恋歌、相思歌等;当爱情受到挫折时,他们又有苦情歌、起誓歌、反抗歌、逃婚歌等。这些情歌以朴实、真切、优美、健康的风格表现出丝路各民族青年男女忠于爱情、追求自由幸福,反抗恶势力的爱情观。通过情歌这一窗口,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民族借对爱情生活的吟唱来表现对严酷不合理的现实生活的态度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同时,这些情歌也直率袒露出丝绸之路民族独特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习惯,以及令人着迷的婚姻习俗。
在丝绸之路各民族中都流传着大量的蕴涵着民族特色和涌动着民族情感的情歌。如在哈萨克族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情歌:《百灵鸟啊,你不要叫了》:
百灵鸟啊,你不要叫了,
姑娘的心啊,够乱的了;
晚霞啊,你不要照了,
姑娘的脸啊,够红的了!
牧羊的人儿啊,不要唱了,
你的心事啊,姑娘早知道了;
月亮啊快出来,快出来吧,
姑娘的心啊,早就等急了!
这首情歌用朴素生动的语言、反复咏叹和巧妙的比喻,形象地表现出哈萨克族姑娘赴约前羞涩、焦急、埋怨的复杂心情。又如塔塔尔族著名的情歌《弯弯的镰刀》:
我挥动着弯月般的镰刀,
镰刀上明媚的阳光闪耀;
为了把镰刀磨得更锋利,
我来到有泉水的山坳。
我在泉边磨着弯弯镰刀,
眼睛望着远处那座小桥;
是谁挥手帕向我召唤,
迎着我在不停地奔跑。
我的心止不住地乱跳,
不留神没有抓住镰刀,
唉哟,镰刀割破了右手,
只痛得我又喊又叫。
唉,年轻的小伙子哟,
看见我疼得又喊又叫
举着我的手唉声叹气,
急得他不住地跺脚。
情歌中把年轻的塔塔尔族姑娘急切见到情人以及会面时那种慌乱的心情描绘得惟妙惟肖,十分传神。结尾又细腻地描摹了塔塔尔族小伙子的神情动作,加深了这首情歌的感染力。
生活歌
丝绸之路少数民族民歌中的生活歌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从民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这个角度讲,凡是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歌谣都可称为生活歌,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劳动歌、习俗仪式歌、情歌等大体都包括在内。这里我们主要是指它的狭义,即指反映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家庭状况的歌谣,具体为流传在劳动人民中数量众多的田歌、牧歌、渔歌、猎歌以及妇女、孤儿、流浪汉等的歌谣。这些生活歌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各行各业、各种不同遭遇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唱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其中,《苦歌》、《怨歌》占有相当数量。如柯尔克孜族的《牧羊人的怨歌》:
我当了多少年牧工,
从小就受尽了欺凌,
肚子里饿得难以忍受,
我还得为牧主卖命。
脚上裹脚的布子已经磨碎,
脚板上的茧儿已变得更硬,
难道我就这样死去吗?
成天在山顶上奔命。
我就是哭泣啊,
也没人倾听我的哀苦;
在这吸血的年代里,
受尽折磨的穷苦牧工。
作品低沉忧郁,集中地代表了丝绸之路各民族劳动人民对黑暗残忍血腥统治的旧社会恶势力的控诉!在这些《苦歌》中,也有一些历史上传下来的吟唱整个民族和部落苦难的歌谣,这些苦歌在这类生活歌中分外引人注目。例如,18世纪准噶尔人骚扰哈萨克族部落时哈萨克族流传下来的歌《我的民族》,至今几乎每个哈萨克人都会吟唱。歌的大意是:
落难逃荒翻越那峻岭高山,
一步一险多留下孤驼哭唤;
背井离乡难丢弃故土家园,
满目凄凉忍不住泪珠涟涟。
当今世道何如此生路竭蹶,
幸福安康从身边倏然离却,
一行长阵惊搅起滚滚烟尘,
蔽天遮日更胜似严寒风雪。
当今世道何如此风云突变,
往日幸福可能够重归身边?
故土家乡已经是荒凉废墟,
我洒凄泪汇聚成汪洋一片。
有压迫就有反抗。丝绸之路各族劳动人民将心中的不平与愤懑化作《苦歌》倾泻出来的同时,对当时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异族的侵略也凝结成一首首《反抗歌》从心底爆发出来,在民间迅速流传。如维吾尔族的《流浪汉之歌》、《悲壮歌》,塔吉克族的《保爹保娘保家乡》,柯尔克孜族的《女英雄阿依库孜汗》,等等。
宗教礼仪歌
宗教礼仪类民歌主要是指同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习俗相关连的反映他们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歌谣,具体表现在宗教祭祀活动、祛病禳灾的民间习俗和宗教节日等活动中。萨满原始宗教和伊斯兰近现代宗教在丝绸之路民族精神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宗教礼仪性民歌也主要是围绕这两种宗教进行的。如哈萨克族中流传的关于萨满教巫师“巴克瑟”的歌。巫师巴克瑟在用语言和歌声创造的恐怖神秘的气氛中呼唤自己的灵魂来与神沟通,以用于驱除邪祟,为人、畜治病。与此相似的有锡伯族的“萨满舞春”。锡伯族在历史上长期尊奉原始的萨满教,巫师萨满在“萨满舞春”的词曲中跳神祛邪,进行宗教活动。另外,在一些宗教节日活动中,丝绸之路各民族都在一定神职人员主持下进行宗教仪式民歌的演唱。如维吾尔族在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时要吟诵诗句,以感谢真主的恩赐,求取平安幸福;哈萨克族在伊斯兰教的肉孜节的夜晚要唱《加拉帕赞》歌,向人们祝福;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乌孜别克族、蒙古族等,都要在自己民族宗教节日时演唱带有浓重宗教气息的歌谣,以颂扬神的伟大,求取福佑民族的安宁和发展。
丝绸之路民歌除以上六类外,还有儿歌、游戏歌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丝绸之路民歌在西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少民族成员,从婴儿诞生来到人间直至最后逝世丧葬,在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都伴随着民歌的演唱。这正如哈萨克族俗语所说,“哈萨克伴随着歌声来到人世,伴随着歌声死去”。创作和演唱民歌,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歌不仅记录着各民族成员的人生历程,而且还程度不同地成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各个民族在他们自己民歌的花坛上,演唱着自己民族的兴衰变化,表演着自己民族的生活礼仪,共识和认同着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
西域各民族似乎都有较为深厚的诗歌传统。但是民歌,它带着与生俱来的特质与后来同属于诗歌范畴的史诗、叙事诗等相比较,在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上,在形式的多样化上,在演唱的形式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其中,载歌载舞,又说又唱,恐怕是最显著的区分之一。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对唱”,达斡尔族“大奥”的载歌载舞,回族的“花儿”演唱,锡伯族的“舞春”等,都带有强烈的歌舞性。这些民歌的演唱,大约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艺术、服饰造型艺术等为一体,呈现出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与民间艺术活动相济相生的动人情景。
丝绸之路民歌内容丰富广泛,分类庞杂。据现有研究资料,有的学者以民族分类,如维吾尔族民歌、哈萨克族民歌、塔吉克族民歌、乌孜别克族民歌等等;有的学者以流传地域分类,如伊犁民歌、库车民歌、喀什民歌、昌吉民歌等;有的学者以内容分类,如古歌、劳动歌、仪式歌、风俗歌、迁徙歌、颂歌、情歌、儿歌、宗教歌等;还有的学者以演唱表现形式分类,如哈萨克族民歌中的“吐列对唱”和“苏列对唱”,回族民歌中的“花儿”和“宴席曲”,达斡尔族民歌中的“大奥”、“扎恩达勒”、“舞春”、“舞词”、“祝词和赞词”等。为便于叙述,我们拟将丝绸之路各民族民歌分为六类:古歌、劳动歌、习俗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宗教礼仪歌及其他歌。
古歌
古歌,是丝绸之路各民族口头创作和流传的古史歌,又称“根的歌”。这类民歌其内容大多是创世和族源传说,具有奇特想象和大胆夸张,幻想成分浓重,可以说是民歌形式的民族神话传说。古歌在丝绸之路民歌中数量不多,但影响甚大,它直接影响到神话、传说、史诗、民间叙事诗等的创作和流传。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从散见的其他民间文学形式中窥见丝绸之路民族古歌的一些蛛丝马迹。如,哈萨克族记述先祖的一些古歌,在韵散相间的《先祖阔尔库特书》各篇章中还可看到。阔尔库特,是流传在哈萨克民间的一位神话般的著名人物,他是哈萨克人心目中一位圣人、贤哲、无所不知的预言者和智慧的化身。关于此,在《阔尔库特之歌》中这样唱道:
在古时,
在太阳升起的东方,
在大名鼎鼎的阿尔泰山之阳,
曾经生活过一位阔尔库特老人,
他是圣明的先哲,
他见多识广。
在这部韵散相间,带有浓重哈萨克先人古代英雄歌谣印痕的作品中,含有丰富的同哈萨克族源有关的古代突厥部族的英雄传说和英雄歌谣的内容。虽经后人的复合、加工、扩充与缀连,但其中古歌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古歌部分以鲜活的口头文学特色形成了哈萨克族民间说唱文学的源头之一,就是对后来的《阿勒帕梅斯》、《阿勒克·蔑尔干》等著名作品也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劳动歌
这类反映西域各族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歌在丝绸之路民歌中数量较多,极为丰富。无论是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还是农耕为主的维吾尔族、回族,以及狩猎为主的锡伯族、塔吉克族等,都流传有大量的反映他们劳动过程、生产经验和在劳动中表现出某种真情实感、劳动场面情景的民歌。如,哈萨克族的“畜牧生产歌”,以马、驼、羊、牛四种牲畜为题,具体描述了这些牲畜的习性,如何饲养放牧管理,强烈地表现出哈萨克民族增殖牲畜、发展生产的愿望和对牲畜的珍爱之情。又如,锡伯族的“猎歌”、蒙古族的“接羔歌”、柯尔克孜族的“牧马歌”、塔吉克族的“牧羊歌”、乌孜别克族的“割麦歌”、回族的“犁地歌”、维吾尔族的“麦收歌”等等,都是以歌谣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丝绸之路各民族在特殊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为求取生存、发展而走过的生产劳动的足迹。此外,在这些民歌中还涌动着丝绸之路西域民族独特的思维心理、宗教感情,从而构成作品特有的旋律、韵味和节奏,读来别具风味。如在柯尔克孜族中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守圈歌》。这首被称为“别克别凯依”的古老的劳动歌,大多在夏夜为牧民看守羊圈的妇女所传唱。歌中开头一段是这么唱的:
我把针尖弄弯了呀!哎,哎,哎依!
今天我看守羊圈,哎,哎,哎依!
我又把针尖弄直了呀!哎,哎,哎依!
怕丢羊,我才来守圈。哎,哎,哎依!
棍子是坚硬的楂木做的啊!
豺狼、小偷休想靠边!
若有小偷来,就擒住他,
我们要把他头打烂。哎,哎,哎依!
圈旁有条小道,
但愿我的羊群平安!
姑娘、媳妇们看守羊圈,
这是自古传下来的习惯。
整首民歌有领唱、对昌、合唱,在通宵达旦的演唱中流露出柯尔克孜族妇女对自然,对畜群,对部落和对别克别凯依神的特殊感情。
习俗仪式歌
丝绸之路各民族中流传盛行的习俗仪式类民歌,它是在各民族民间礼俗和礼典仪式上吟诵和歌唱的。在丝绸之路各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华彩乐章。根据各民族习俗和仪式的要求,这类民歌在内容上有着相对集中的题材,在形式上有着较为固定的格式,并以固定的民间曲调吟唱。哈萨克族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哈萨克族人从生到死的每个人生历程中都随时伴响着这种习俗礼仪民歌的吟唱。如,婴儿生下时,要为婴儿举行三个晚上的“诞生歌”歌唱活动;女儿长大成人举行婚礼,有名目繁多的“婚礼歌”(主要包括“婚序歌”、“劝嫁歌”、“哭嫁歌”、“揭面纱歌”等),亲友去世有“报丧歌”、“挽歌”。此外,还有不少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告别歌”、“摇篮歌”、“戒律歌”等民歌。在丝绸之路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大量的习俗仪式民歌。维吾尔族在过“白雪节”时要吟唱传送祝福平安的“信歌”,肉孜节时要演唱“祝福歌”,女儿出嫁时母亲要唱“送嫁歌”,婚后新郎去拜谒岳父岳母要唱“婚礼歌”等,蒙古族卫拉特人在酒宴上除了豪饮外还要纵情高歌“宴歌”。在他们看来“没有歌声的喜宴不算喜宴,不唱酒歌的宴席没有欢乐”,至于像“那达慕”这样的喜庆节日更是歌不离口了;在塔吉克族中,男婚女嫁、欢迎宾客、祝贺节日、贺生送葬等礼仪场合都要吟唱礼俗歌。如欢度一年一度的“乞脱乞迪尔爱脱节”时,除了大扫除,向墙上撒面粉,妇女给来宾在肩上撒面粉等传统礼仪外,全村还要公推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依次到各家吟唱祝贺新春和丰收的颂歌;在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等民族中也流传着丰富的习俗礼仪民歌。尤其是在婚丧嫁娶活动中,这类民歌更是无处不有,无时不有。
值得指出的是,这类习俗礼仪民歌由于它特殊的社会作用,在传统文化强有力的影响下,从内容到形式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套式。尽管由于某些场合的特殊要求,在个别词句上有些增减,但通常都尽量保存其产生和流传中的口语形式和原始状态,一般不允许即兴式的创作。因为这种礼俗民歌的演唱,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演唱,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融化为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在民族精神、心理的深处,从而转化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延续传递给后代。例如,我们上述提到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婚礼歌,都是伴随婚礼每一套完整的仪式而出现相应的具有固定套式的“劝嫁”、“哭嫁”、“揭面纱”等婚礼歌内容,在形式上(衬字衬词、换韵、曲调节奏等)更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演唱这类婚礼歌,已超出一般观赏创作民间文艺的意义,在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气氛中,你会身不由己地全身心投入到一种民族习俗文化活动中去而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些礼俗民歌,随着丝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会不断地发生着某些变化。有些随同原来依附的仪式一齐消亡,有些仪式虽然废除,但仪式歌却保存延续下来,成为民族习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外,丝绸之路民族习俗仪式类民歌因受民族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伴有一定的祈祷目的(祈年,禳灾,告祖,求福等)。如在乌孜别克族中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求雨歌》。歌中唱道:
下雨吧,女婆,
让小麦丰收吧,女婆,
让人们吃饱吧,女婆,
女婆,苏丹女婆!
让收成丰盛,女婆,
让谷物堆满农家,女婆,
让说谎话的人家里空空,女婆,
女婆,苏丹女婆!
这首著名的《求雨歌》,一方面反映出乌孜别克族祈求降雨的风习:祈雨者把两根木棍对着捆起来,裹上妇女衣服,头顶面纱,扮成妇女样举着偶像逐门挨户求雨唱《求雨歌》,集中地表现了人们祈雨渴望丰收的愿望;另一方面这首民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乌孜别克人对“苏丹女婆”神的敬畏和崇拜,希望能得到她的保护,弥漫着浓重的原始宗教气息。
情歌
在丝路民族中,情歌大约是传唱最多、最为丰富多彩具有魅力的一种民歌种类了。与汉族相比,青年男女之间较为自由的择偶,其方式大多又用歌唱来表情达意,加之融入民族习俗中的歌唱传统,这些为丝绸之路民族情歌的创作和流传造成了一定的条件。丝路民族情歌主要以歌唱爱情为主。青年男女从相识、初恋到相互结合,在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情歌来表达男女之间热烈而复杂的感情。当爱情萌生建立时,他们有初识歌、结交歌、赞美歌、迷恋歌、相思歌等;当爱情受到挫折时,他们又有苦情歌、起誓歌、反抗歌、逃婚歌等。这些情歌以朴实、真切、优美、健康的风格表现出丝路各民族青年男女忠于爱情、追求自由幸福,反抗恶势力的爱情观。通过情歌这一窗口,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民族借对爱情生活的吟唱来表现对严酷不合理的现实生活的态度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同时,这些情歌也直率袒露出丝绸之路民族独特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习惯,以及令人着迷的婚姻习俗。
在丝绸之路各民族中都流传着大量的蕴涵着民族特色和涌动着民族情感的情歌。如在哈萨克族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情歌:《百灵鸟啊,你不要叫了》:
百灵鸟啊,你不要叫了,
姑娘的心啊,够乱的了;
晚霞啊,你不要照了,
姑娘的脸啊,够红的了!
牧羊的人儿啊,不要唱了,
你的心事啊,姑娘早知道了;
月亮啊快出来,快出来吧,
姑娘的心啊,早就等急了!
这首情歌用朴素生动的语言、反复咏叹和巧妙的比喻,形象地表现出哈萨克族姑娘赴约前羞涩、焦急、埋怨的复杂心情。又如塔塔尔族著名的情歌《弯弯的镰刀》:
我挥动着弯月般的镰刀,
镰刀上明媚的阳光闪耀;
为了把镰刀磨得更锋利,
我来到有泉水的山坳。
我在泉边磨着弯弯镰刀,
眼睛望着远处那座小桥;
是谁挥手帕向我召唤,
迎着我在不停地奔跑。
我的心止不住地乱跳,
不留神没有抓住镰刀,
唉哟,镰刀割破了右手,
只痛得我又喊又叫。
唉,年轻的小伙子哟,
看见我疼得又喊又叫
举着我的手唉声叹气,
急得他不住地跺脚。
情歌中把年轻的塔塔尔族姑娘急切见到情人以及会面时那种慌乱的心情描绘得惟妙惟肖,十分传神。结尾又细腻地描摹了塔塔尔族小伙子的神情动作,加深了这首情歌的感染力。
生活歌
丝绸之路少数民族民歌中的生活歌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从民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这个角度讲,凡是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歌谣都可称为生活歌,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劳动歌、习俗仪式歌、情歌等大体都包括在内。这里我们主要是指它的狭义,即指反映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家庭状况的歌谣,具体为流传在劳动人民中数量众多的田歌、牧歌、渔歌、猎歌以及妇女、孤儿、流浪汉等的歌谣。这些生活歌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各行各业、各种不同遭遇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唱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其中,《苦歌》、《怨歌》占有相当数量。如柯尔克孜族的《牧羊人的怨歌》:
我当了多少年牧工,
从小就受尽了欺凌,
肚子里饿得难以忍受,
我还得为牧主卖命。
脚上裹脚的布子已经磨碎,
脚板上的茧儿已变得更硬,
难道我就这样死去吗?
成天在山顶上奔命。
我就是哭泣啊,
也没人倾听我的哀苦;
在这吸血的年代里,
受尽折磨的穷苦牧工。
作品低沉忧郁,集中地代表了丝绸之路各民族劳动人民对黑暗残忍血腥统治的旧社会恶势力的控诉!在这些《苦歌》中,也有一些历史上传下来的吟唱整个民族和部落苦难的歌谣,这些苦歌在这类生活歌中分外引人注目。例如,18世纪准噶尔人骚扰哈萨克族部落时哈萨克族流传下来的歌《我的民族》,至今几乎每个哈萨克人都会吟唱。歌的大意是:
落难逃荒翻越那峻岭高山,
一步一险多留下孤驼哭唤;
背井离乡难丢弃故土家园,
满目凄凉忍不住泪珠涟涟。
当今世道何如此生路竭蹶,
幸福安康从身边倏然离却,
一行长阵惊搅起滚滚烟尘,
蔽天遮日更胜似严寒风雪。
当今世道何如此风云突变,
往日幸福可能够重归身边?
故土家乡已经是荒凉废墟,
我洒凄泪汇聚成汪洋一片。
有压迫就有反抗。丝绸之路各族劳动人民将心中的不平与愤懑化作《苦歌》倾泻出来的同时,对当时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异族的侵略也凝结成一首首《反抗歌》从心底爆发出来,在民间迅速流传。如维吾尔族的《流浪汉之歌》、《悲壮歌》,塔吉克族的《保爹保娘保家乡》,柯尔克孜族的《女英雄阿依库孜汗》,等等。
宗教礼仪歌
宗教礼仪类民歌主要是指同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习俗相关连的反映他们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歌谣,具体表现在宗教祭祀活动、祛病禳灾的民间习俗和宗教节日等活动中。萨满原始宗教和伊斯兰近现代宗教在丝绸之路民族精神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宗教礼仪性民歌也主要是围绕这两种宗教进行的。如哈萨克族中流传的关于萨满教巫师“巴克瑟”的歌。巫师巴克瑟在用语言和歌声创造的恐怖神秘的气氛中呼唤自己的灵魂来与神沟通,以用于驱除邪祟,为人、畜治病。与此相似的有锡伯族的“萨满舞春”。锡伯族在历史上长期尊奉原始的萨满教,巫师萨满在“萨满舞春”的词曲中跳神祛邪,进行宗教活动。另外,在一些宗教节日活动中,丝绸之路各民族都在一定神职人员主持下进行宗教仪式民歌的演唱。如维吾尔族在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时要吟诵诗句,以感谢真主的恩赐,求取平安幸福;哈萨克族在伊斯兰教的肉孜节的夜晚要唱《加拉帕赞》歌,向人们祝福;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乌孜别克族、蒙古族等,都要在自己民族宗教节日时演唱带有浓重宗教气息的歌谣,以颂扬神的伟大,求取福佑民族的安宁和发展。
丝绸之路民歌除以上六类外,还有儿歌、游戏歌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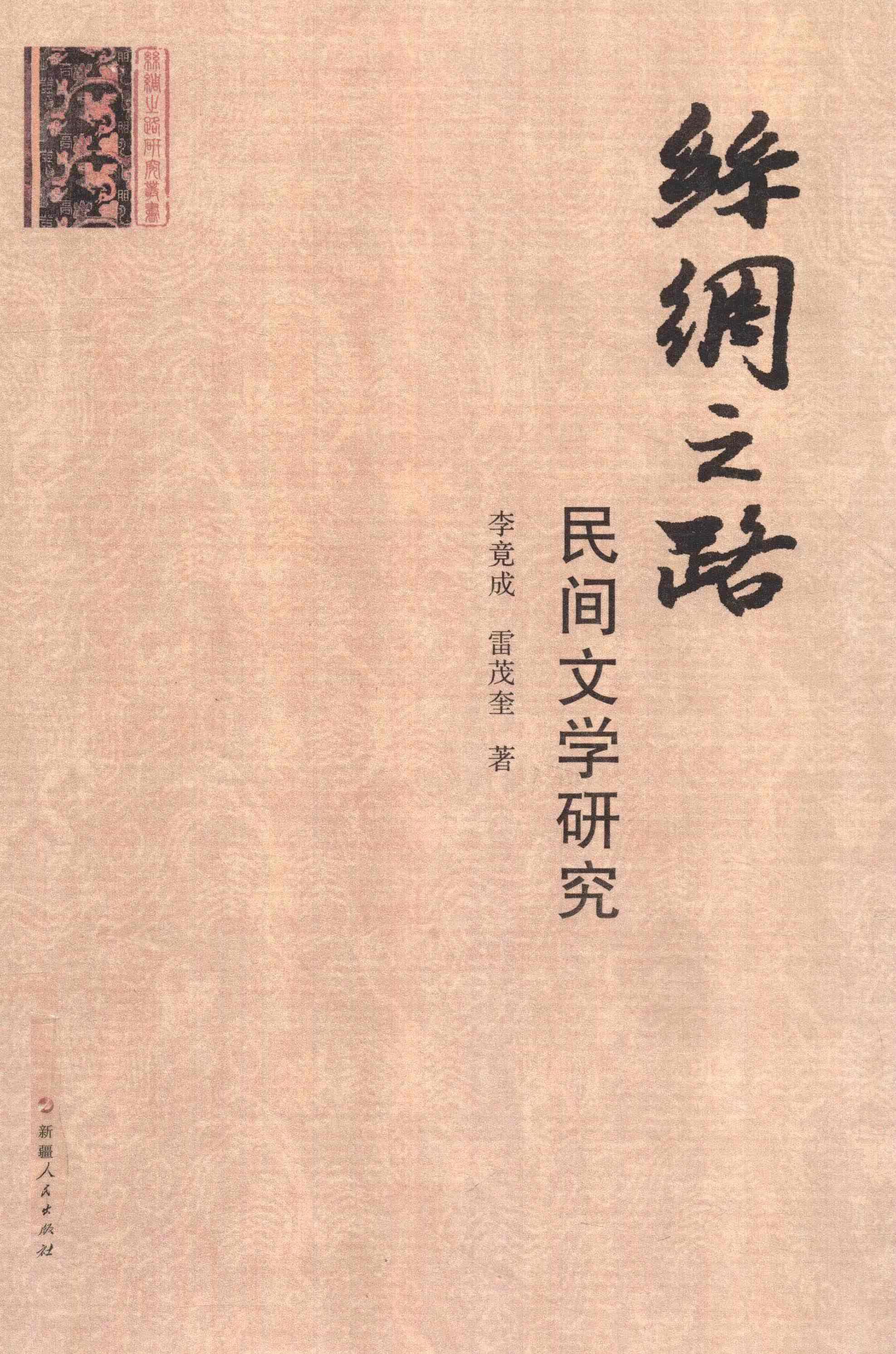
《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民族神话、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丝绸之路民族英雄史诗、丝绸之路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丝绸之路民族民歌、丝绸之路民族民间谚语和谜语等。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