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丝路神话构成了我国昆仑神话的主要构架。一方面,它具有神话所存有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与中原神话和南方各少数民族神话相比较,它又显示出自己独到的特性。现将丝路西域神话特征归纳分述如下:
其一,原始性和神祗的体系性
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认识的反映。在丝路神话中,这种反映主要表现为丝路各民族先民对自然万物、人类与自然力矛盾的混沌认识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哲学观念,这就形成了丝路神话的原始性。例如,在哈萨克族神话中占有显著地位的创世神话:宇宙从漆黑中分离诞生出新的世界;从滚沸的混合体中产生水、土、日、星;从泥土中诞生初人;此外,还有九重天的人间,七层地底下的生命世界,十八层天里的神仙;用一只犄角顶着地球的巨大天牛,顶着海水的蓝鲸,能喝光江河湖海的怪物等等。从这些神话可以看出,哈萨克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对宇宙形成、人类起源的幼稚而独特的看法。这些自然生成和社会现象与他们的游牧生活、原始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又如,在柯尔克孜族中流传的《鹿妈妈》①的族源神话。传说,古代柯尔克孜人曾遭到一次突发的空前规模的战争洗劫,使得整个民族濒于灭绝。当时幸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进山采野,才幸免于难。当他们出山看到家乡惨状时,不禁绝望地恸哭起来。这时,一只母鹿过来将他们带回山里,用鹿奶养育他们长大成人。后来这对男女结为夫妻,繁衍了后代。现在柯尔克孜人中还有叫“布古”(鹿)的大部落,据说就是他们的后代。这篇神话明白无误地向今人表明,柯尔克孜人对“鹿”崇拜的原始动物图腾观念。其实柯尔克孜人的祖先并非是鹿,在我国史书《史记》最早记载中称其为“坚昆”等氏族部落。当时主要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由于被漠北匈奴所迫,迁至天山周围,到公元2世纪时建立了柯尔克孜汗国。这些族源神话放射出的原始神秘色彩,使柯尔克孜初民确信自己的族母是“鹿妈妈”,时至今日,在柯尔克孜族民间还盛行着崇敬鹿,将鹿视为圣物的习俗。
丝路神话原始性特征还集中表现在神话的承传方式上。众所周知,丝路民族神话主要在本民族中靠口头承传和保存。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种种原因,在丝路一些边远闭塞的民族中,几千年来,神话一直被当作本民族的历史而传唱、讲述着。即使在今天,诸如哈萨克族中的“阿肯弹唱”,满族中的“萨满口传神谕”等承传形式,也仍盛行不衰。这种口传艺术,由于较少有文人的加工雕琢,因而继续保持着民间文学固有的口语化、生活化的特色,使得丝路神话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艺术的特征。就目前接触到的神话资料来看,丝路神话比较完好地保存着它的原始面貌。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丝路各民族原始的社会生活、民族历史和文化以及原始的思维活动等方面,无疑具有极为可贵的参考价值。
神祗体系的形成,是神话发展到后期的产物。它标志着原始人类对宇宙万物认识的成熟和完成,他们开始脱离野蛮状态,向有序的文明社会过渡。从神话发展的角度看,一旦神祗体系出现之后,神话发展也就趋向成熟,并相对处于停滞状态。在中国,古老的汉族神话虽然多见于古籍记载,但由于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统治和“不语怪力乱神”,加之历代文人篡改,将神话历史化,使得原来丰富的汉族神话大部分失传。至今残存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著作中的神话资料,实属肢体不全。其中虽也存有各类神祗,但神祗体系不甚完整。甚至显示不出神祗体系的基本面貌。相反,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尤其是在丝路民族神话中,我们却不难发现神祗的独特体系。这完全可以和古埃及神祗体系、巴比伦神祗体系,甚至古希腊神祗体系相媲美。
在丝路神话中,神祗体系大都有一个主神(至高无上的神)统帅着其他诸神。与此相对立的,还有一套冥府鬼怪诸神。这种神祗体系在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满族等丝路少数民族神话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以哈萨克族为例。在哈萨克族神话的神祗体系中,迦萨甘是创世之神,至高无上;腾格里是天神,主宰着世界万物。在这之下有诸多掌管各部门的神灵,如保护妇女的乌弥女神,主宰雷电的阿加哈依神,摄取亡魂的阿尔达西神,为人们带来福运的克德尔神,行动神速的捷勒阿亚克神,飞禽之神萨木勒克,体大如山力大无穷的巨人达吾,以及马神康木巴尔阿塔和神马匹拉克,牛神赞格巴巴和用犄角顶地球的天牛,山羊神谢克谢克阿塔,绵羊神绍潘阿塔和骆驼神奥依斯尔哈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与神作对的妖魔鬼怪。如魔王佩里、魔鬼捷兹特尔纳克、独眼巨人以及阴险毒辣的老妖婆等。
又如柯尔克孜族神话。柯尔克孜人自古以来依山而居,逐水而游,过着狩猎和放牧的生活。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劳动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独有的心理和习俗,也就决定了在他们的神话中神祗体系的特殊种属。天上有宇宙神、火神(太阳)、冷神(月亮)、北斗神、三羊星神、七星神、月亮中的巫婆等;人世间有幸运之神库特、力神玛勒斯、风神科依卡卜、冬神琪勒黛卡尔特、雪神阿克阿坦、婴儿保护神吾玛叶涅、神鸟阿勒普、鹰神布达依克、骆驼神奥依索勒阿塔、马神康巴尔阿塔、羊神巧力潘阿塔、牛神乌依桑巴巴、狗神库麻依克;与以上诸神相对立的还有聚集在“妖魔世界”中的狰狞可怖的妖魔阿勒巴尔斯特,“臭妖”沙色克阿勒巴尔斯特等。
其二,复杂性及其宗教的衍变性
丝路民族神话既古老又复杂。这里除了诸多民族神话异彩纷呈的不同面貌外,更为主要的是“神话”的特殊涵义赋予了丝路各民族神话迥异的质的规定性。即它是丝路原始人类萌芽状态的宗教、历史、哲学、法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观念的反映。由于神话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丝路各民族神话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色彩。如哈萨克神话多为“草原神话”,维吾尔神话多为“绿洲神话”,而塔吉克神话则多为“冰山神话”(关于此,下面将有专门论述)。
自有西域初民之后,丝路神话在不断的产生和承传中,除了自身的发展变异外,还不时夹杂带入一些时代、阶级、种族和多种不断衍变的宗教等观念,使之在丰富多样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丝路各民族的图腾、崇拜、信仰等宗教情感和形式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丝路各民族的童年时期,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如萨满教在当时各部落氏族中盛行)。这是一种自发的全民信仰,常常以多神崇拜的图腾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柯尔克孜人古老宗教信仰中存在着多种崇拜形式,有星宿崇拜、大地崇拜、山崇拜、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气崇拜、狼崇拜、鹰崇拜、骆驼崇拜、龙崇拜、虎崇拜、猫崇拜、喜鹊崇拜、灵魂崇拜、坟墓崇拜、女性崇拜、白色崇拜、红色崇拜等。总之,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都认为具有神的意味,皆崇拜之。这种以多神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是丝路各民族初民统一意志、团结氏族部落以抗衡自然力的精神动力,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在这种原始宗教的统攝下,丝路初民的原始神话呈现出一种单纯而神秘的多神崇拜的特色。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多神宗教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浓烈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宗教(当然,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衍变过程)。一神崇拜宗教是一种人为的宗教。为了宣扬教义,这种宗教不断利用和改造丝路神话中的神祗,由多神崇拜衍变为一神信仰,在不少神话情节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样,在丝路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迫使丝路神话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除去其他因素外,单就因宗教信仰的衍变导致丝路神话在内容诸方面发生变化,这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以及锡伯族等丝路民族中极为普遍。
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隶属阿尔泰突厥语系的维吾尔族先民曾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这以前,也曾有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前宗教形式)。多桑《蒙古史》中说:“畏吾儿先人奉之宗教为珊蛮教,与亚洲北方诸部落同。其教之巫师曰珊蛮(cames),即此粗野宗教之教师也。”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因诸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称巫师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的宗教特点。萨满教在教义和观念上将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和若干层次:上界为天堂,下界为地狱,中界系人世地面;奉“腾格里”为尊神,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具有多神偶像崇拜的特点。维吾尔先民信仰萨满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之前居住在漠北时期,以后长期保留着萨满教的残余影响(如至今在维吾尔族民间还有“巴合西”,即“萨满”)。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祆教(原名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传人西域。据《梁书》、《魏书》、《隋书》、《唐书》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域各地居民“俗事天神”,各国“其国事天神火神”①,可见祆教在当时流行情况。祆教以《波斯古经》为经典,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要求人们以善避恶,弃暗投明,教徒要在“麻葛”(祭师)的指导下通过专门的仪式,礼拜“圣火”。唐以后,祆教在西域逐渐衰落,伊斯兰教传入后便销声匿迹,但其遗风仍然存在于维吾尔族民间。如现今民间习俗,在迎亲回来的路上,新郎、新娘要跳过或绕过一堆火,以表示幸福吉祥。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道教已在西域高昌的维吾尔先民中传播。到唐朝时,道教颇为兴盛,在伊州(今新疆哈密地区)等地修建多处道观,并有阴阳、巫觋、道人、咒师等道教的职业人员。此种状况到宋元时期才趋于衰微。在公元6~7世纪,摩尼教开始输入到当时居住在漠北的回鹘部落中,并于公元763年之后成为回鹘的国教。近代中外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寺院遗址和文献,即为证明。后伊斯兰教传入,摩尼教才在回鹘中逐渐消亡。摩尼教原是伊朗的古代宗教之一,它在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思想材料而形成自己的独特信仰。摩尼教崇拜“四大尊严”(即大明神、神的光明、神的威力及神的智慧),以大明神为尊神,根本教义为“二宗三际”(“二宗”为明暗两极,“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摩尼教在西域,尤其在高昌回鹘王国影响深远,对后世西域文明(如历法)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公元6世纪,景教(即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教派)传入西域喀什噶尔等地,在那里发展到十分兴盛的地步,后来在今吐鲁番地区形成了景教的中心。景教在西域流传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在民间的影响仅次于佛教和伊斯兰教,成为西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大约于公元2世纪前后传入西域于阗,后来沿着丝绸古道的南北两路依次传布。公元2~3世纪,佛教已遍布西域各地,公元4~5世纪日趋隆盛。隋唐时期已非常发达,形成了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高昌(今吐鲁番)四大佛教中心。公元840年,从鄂尔浑河流域迁到西域的回鹘部落接受了佛教,并渗透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他们的主要宗教。当时的龟兹、于阗、高昌等地已是佛教活动的中心。高僧云集,具有完善的组织和法事仪式,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典籍,兴建寺院,创造了辉煌的佛教石窟艺术文化。
维吾尔族先民虽曾信奉过上述的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但最终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早在唐代伊斯兰教即已开始输入西域,但大规模传布,则是在公元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萨图克·布拉格汗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公元960年,阿尔斯兰汗木萨统治时期,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接受伊斯兰教,标志着喀喇汗王朝实行了伊斯兰教国教化。此后,随着蒙古军队征服中亚,西域伊斯兰教发展一度停滞。14世纪,秃黑鲁帖木儿登上东察合台汗国宝座成为伊斯兰教信徒后,伊斯兰教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15世纪后期,吐鲁番等地改信伊斯兰教后,伊斯兰教终于取代了历史上的种种宗教,使得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中成为唯一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徒绝大多数属于正统主义的逊尼派。该派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遵循“逊奈”(圣行),坚信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天经、信使者、信末日),承认安拉的前定,履行天命五功(念、礼、斋、课、朝),以穆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承认“四大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此外,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还有苏非派、什叶派、瓦哈比派等。
综上所述,这种由多神崇拜到一神信仰的历史宗教事实,使得维吾尔族神话相应出现了复杂的状态。这在它的一些经典著作,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阿赫马德·本·穆罕默德·玉克乃克的《真理的入门》等中,对多种衍变以及神话传说都有过记载。例如,有大量的维吾尔先民在萨满崇拜原始宗教时流传的狼神话、树神话和《乌古斯传》;有在佛教盛行时期在各个“千佛洞”壁画上记载的佛教神话传说;更有伊斯兰教统辖后流传着的诸如《女天神造亚当》、《拉布胡兹故事集》这样富于浓郁伊斯兰教色彩的神话故事。
另外,多种宗教的更迭衍变使得维吾尔族神话中的一些重要神祗的涵义也相应发生着某种变化,并多次被赋以新意。例如,“腾格里”(在突厥语中的读音是tangri),原指“苍天”、“上天”之意。维吾尔初民在信仰萨满教时期,把“腾格里”视为“天之主宰”、“神祗之统称”,是“上界”、“天堂”;在信奉祆教时,被用以称呼该教的至高神阿胡拉·玛慈达为“艾兹罗阿腾格里”;到了信奉佛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佛祖”为“波尔汗腾格里”;在改宗伊斯兰教后,它又被用以称呼伊斯兰教的尊神“安拉”、“真主”;在近现代,“腾格里”一语在历史文献中已被阿拉伯语的“安拉”和波斯语的“胡大”代替了。
其三,审美价值——艺术形象的怪诞美
丝路神话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它作为一种艺术美,集中反映了西域原始初民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就是,以幻想的方式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反映出既朦胧混沌,又严肃认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出种种鬼斧神工的神话来。这些神话以虚幻为真实,以险异为雄奇,以荒诞为瑰丽,以蒙昧为睿智,表现出丝路各民族文学在童年时期所特有的天真和稚气,具有一种疏简朴野、离奇怪诞的美学风貌。
丝路神话的这种美学价值,主要是通过神话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怪诞美表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原始初民对时空限制的逾越上。
在丝路远古神话中,原始初民以天地万物变化无常的现实为基础,借助想像的翅膀,飞腾跳跃,打破了物质世界的固有时空,创造出许多解释自然、征服自然的美丽的神话传说,艺术地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界以及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大多为荒诞不经,但由于所表现思想感情的真挚,编织艺术时空的神奇,使人迷醉不疑。丝路神话的这种超越现实荒诞离奇的美学特征,往往获得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例如,柯尔克孜族的创世神话《大青牛的传说》。①相传大地分为七层,由地下一头巨大的青牛用两只角轮换支撑。当它的一只角疲劳时,便改用另一只角支撑。每到此时,便山摇地动,发生地震。人们惹恼青牛就会有灾难降临,而青牛若失去良心,大地将陷入无底深渊。这则神话表明,在古代柯尔克孜人眼中,人的命运是与大自然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自然界中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左右着人的命运。这里不乏展示出柯尔克孜人丰富神奇的想象力,但更多流露出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渴求获取身心自由的忧虑。二是表现在丝路神话中,人、神、兽浑为一体,尤其是那些顶天立地的神话英雄形象更是亦人亦神亦兽,放射出一种怪诞美的异彩。这是因为原始人类在很长时期内不能自觉地把自己区别于动物,与百兽相与群居;另外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脆弱,他们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原始宗教幻化出来的神祗和有奇异功能的怪鸟异兽身上,以实现和放大人的价值。如,维吾尔族英雄神话《乌古斯传》。乌古斯一生下来就吃生肉、喝酒,四十天后会走路、玩耍。英雄乌古斯的形象在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他的腿像公牛的腿,腰像狼的腰,肩像黑貂的肩,胸像熊的胸,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②这种半人半兽怪诞的乌古斯英雄形象,正是要把维吾尔族先民几个核心氏族的图腾集中于乌古斯可汗一身。它反映了由氏族而联合为部落的过程,乌古斯可汗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丝路神话艺术形象的这种怪诞美,既符合艺术美的普遍原则,又兼有自然美、社会美的一般特点,它以神奇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征服着一代又一代人。
其四,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丝路神话中,民族性和地方特色表现得最为明显。丝路各民族总是将各民族不同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方式、心理特征等包容在优美神奇的神话传说中,构成情调各异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表现出在一定的历史宗教背景下异质的文化形态,从中渗透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为例。
从宏观上看,这三个民族的神话因融入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特征等因素,使得各自的神话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如哈萨克神话,在创世和族源神话中,迦萨甘都被视为创世主,创造出天地万物;天鹅女被视为民族的始祖母,苍狼被看作与苍天有关的神物,成为哈萨克原始部落的标志;在自然和英雄神话中,出现了众多的与畜牧有关的动物保护神祗和四方征战、保卫家乡牧场的英雄。这一切,都与哈萨克人部落联盟的历史有关,与他们特殊的游牧生活有关,反映出哈萨克先民强烈的部落意识,从本质上呈现出一种“草原文化”的特质。又如维吾尔族神话,在多种宗教漫长的更迭衍变中,适合于精神统治和农耕文化的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它的神话有别于其他民族神话。在《女天神造亚当》、《龙妻索夫》等神话中,明显看到“真主赐给泥人以灵魂”、“因河水断流,农作物无法耕种”等情节,反映出伊斯兰教和农耕文化对神话的影响。在整体上,维吾尔族神话呈现出一种“农耕文化”或“绿洲文化”的形态。再如塔吉克族神话。塔吉克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雄伟神奇的慕士塔格山下,特殊的自然环境赋予塔吉克神话所独具的冰山式的神奇魅力。慕士塔格山,不仅是座闻名于世的冰峰,还是一尊超自然的主宰塔吉克人的神灵。在它的统摄下,神鹰飞翔,鹰笛悠扬,英雄鲁斯塔木惩治邪恶,建功立业。塔吉克族神话是真正的冰山神话,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冰山文化”的特质。
从微观上看,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吉克的神话中,诸如图腾崇拜、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使其在民族性和地方特色上大相径庭。例如在族源神话中,这些民族因图腾崇拜物不一样,因而鲜明地体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哈萨克族《天鹅女》和关于“苍狼”的神话中,图腾物是天鹅和狼;在维吾尔族《狼的后代》、《树生子》、《神树母》等神话中,图腾物是狼和树;而在塔吉克族神话《慕士塔格的传说》和《鹰笛》中,更多的是对冰山和鹰的图腾崇拜。这些民族各自不同的原始崇拜对象,使得他们的民族渊源、精神品格和宗教文化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最终在行动模式和文化模式上产生出鲜明迥异的民族性。
另外,在代代沿袭的民族习俗方面,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吉克这三个民族的神话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差异。例如,在对“火”和“火的观念”上。哈萨克神话中出现有“火娘娘”奥特阿娜的形象。哈萨克人崇拜火,认为火是家庭的恩人、明灯,具有生命、灵性和某种神奇的力量。他们在婚礼上有“拜火”、“向火倒油”的习俗,在丧葬中有“四十支蜡烛”点灯守灵的习俗;在塔吉克神话《光明与黑暗》、《祖哈克与魔鬼》等中,有不少关于“火”的记叙,从中可以看到在早期塔吉克人中拜火教的痕迹。在塔吉克族生活中也有不少关于“火”的习俗。如他们每年回历八月中旬举办的传统节日“皮里克节”(灯节),实际上是赞美崇拜火,借火求福。在发生日食、月食时,婴儿降生时,畜群转移时,埋葬死者时,“火”在这其中都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由于劳动生产方式比较接近,哈萨克与塔吉克在对“火”的观念上比较相似,他们大都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在神话和习俗中把“火”放在重要地位。与此相比,维吾尔族却略有不同。在维吾尔神话中少有“火崇拜”的传说,尽管生活习俗中也存有迎亲归来“跳火”的遗风和“奥特拉西”驱鬼祛病的迷信活动,但这些大都属祆教的遗迹,并无多少功利色彩。维吾尔族对“火”的重视,远远不如对太阳、月亮、星星,甚至植物和盐的崇拜。
以上我们对丝路神话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丝路神话所呈现出来的原始性和神祗的体系性、复杂性和宗教的衍变性,艺术形象的怪诞美所产生的审美价值以及鲜明而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凡此种种,盖源于丝路各民族原始初民特殊的心理和思维,这就是神话思维。
神话思维,是丝路各民族童年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原始思维,它在西域原始初民的思维世界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丝路神话,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文学艺术作品,从中体验到更多的是一种洪荒时代的原始美;而对于西域原始初民,则是一种巫术中介。通过它,使原始人类体验到朦胧、混沌的生命存在的一种神秘,从而达到实用的功利目的。众所周知,原始人类在远古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知识极贫乏,对大千世界无所知晓,对宇宙奥秘深感莫测。猛兽的袭击,疾病的传染以及自然灾害等,无时不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因此,面对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和宇宙万物,他们便产生出一种恐惧感,觉得在那些威慑人们的种种现象背后还有着特殊的物体存在。这便在他们头脑中显现出一种“神的幻影”。与此同时,原始人类又对天地万物寄寓着希望,幻想着有一种超人的神奇力量助人一臂之力,使人安宁度日,带给人间以幸福。于是,人们的心中又升起一尊尊崇拜偶像,这便是“自然崇拜”。这些形成了原始宗教的思想基础,集中地体现在“自然神”的“万物有灵”的思维观念上。后来,原始人的劳动生活环境逐渐趋于固定,人们开始在自己生存的那一特定环境里选择某一自然物,作为崇拜的对象,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原始人在人与崇拜物之间特殊的关联中,寻觅体验着一种神秘而迷妄的信念。或祈求保佑,消灾除害;或占卜吉凶,预祝丰收。虚幻的巫术活动开始了。原始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人们产生了“灵魂不灭”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和躯体是可以分离的,并能单独存在。灵魂可以化作无形的“神灵”,以一种神奇的威力对在世的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由此,生者对死者的灵魂产生惊恐而加以崇拜,祭祀鬼神的活动便由此开始。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充满了“神秘”的因素。“神”的观念形成,支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想。这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那样:“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以至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神话的创造,正是原始人以这种意识形态去认识和理解自然界,表达他们渴望“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的产物。以上我们对神话思维的神秘性加以论述旨在说明,丝路神话依然是在西域各民族原始初民神话思维的支配下,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神秘意识,弥漫着一抹斑斓的神秘色彩。丝路神话的这种神秘性,一方面表明西域初民的无知,同时又说明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是与社会、自我存在的功利作用相关联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自身无能的情况下,便寄希望于“神”的身上。这在丝路神话中的创世神话、族源神话和自然神话中尤为突出。
意大利历史哲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柯,他把人类的心理功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最初只有感受而不能知觉,接着用一种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①在产生神话的原始社会中,原始人是凭着感官作为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的,西域初民亦不例外。在那个朦胧混沌的洪荒时代,他们还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还限于感性方面。他们对于宇宙奥秘的探索,在不知而求知中是通过感官,根据直接的直觉,去探索,去认识,去解释和行动的,从而在记忆中获得了对客观事物的某些形象。西域原始初民的神话创作,便是描述他们所获得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将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形象的“表象”加以再现。这种神话思维的感官性,在西域初民创造的丝路神话中具体表现为模仿性和拟人性。如在达斡尔族神话中,“洞穴神话”颇引人注目。在他们先民的生活经历中,曾经有过栖息洞穴、树丛的生活。在他们的思维意识深处,认为奇特的山峰、山洞和古树,是神灵栖息之处。通过感官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加之出自本能的再现性模仿,在达斡尔人的思维中,“洞穴”等就成为联系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的媒介,于是产生了《嘎西讷洞神话》和《车齐热讷洞神话》。又如哈萨克族神话《月亮藏身》。太阳和月亮这对孪生美女,因相互嫉妒,彼此交恶。最后太阳抓破了月亮的脸,月亮出现了黑斑,不得已经常躲着太阳。这则颇具情趣的神话反映出哈萨克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具有的一种类似儿童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思维世界里,主体与客体还混为一体,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在原始的思想中,日与月大都是活的东西,而且有人性”。②在这种“以己度物”、“以物拟人”的思维支配下,他们不自觉地将万物拟人化,描绘出人与日月情深意厚,亲如一家的情景。从中也可看出,哈萨克先民思维河床中流淌着丰富不竭的原始想象的河水。
丝路神话是西域原始初民神话思维作用的结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一切似乎只是一种梦幻般的存在。但是,丝路神话作为西域早期文化象征性的标记,其中蕴涵着各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风俗、艺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它是丝路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丝路神话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种文化实体。它具有独特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如果我们将丝路神话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的结构功能大体可分为表层和深层两部分。表层部分又由两个层面构成,即由神话的语音、文字所组成的语句层面和由神话的语句集合构成的语义层面构成;深层部分主要指神话的深层结构所蕴涵的文化隐义层面。这一层面构成了对神话的真正解释。
从表层结构功能看,丝路神话至少具有以下三种价值功能:其一,解释性功能。丝路神话是西域原始初民的“哲学”和“科学”。他们的认识感知方式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是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①。丝路各民族先民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世界宇宙的形成,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解释他们自身的来源,解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这种解释性功能在我们前面所表述的丝路创世神话、自然神话、族源神话以及英雄神话中显示得再充分不过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丝路神话的解释性功能“是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论述神话的产生时指出:“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使人类“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②。丝路神话是西域原始初民的精神产物,他们凭借特殊形式的想象——幻想,把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彼时的现实生活和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交错组合,巧妙编织,形象地展现出一个“幻想世界”。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不断创造出一个个衍化发展着的神话形象。通过种种神话形象,生动具体“形象化”地体现出他们对主观化了的外部世界的种种神奇的解释。
在西域的丝路神话中,出现有千姿百态的神话形象。如果根据它们的外形特征和纵向的发展,我们大体可将此分为三种类型和三个阶段。一是象形型神话形象,这是最原始的形象,也是最低层次的形象;二是复合型神话形象,这是在象形型神话形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神话形象发展中级阶段的产物;三是人型或符号型神话形象,这是神话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如果用简明的方式来表示,即:
在我国丝路神话中,象形型神话形象最为丰富,复合型神话形象次之,人型形象又次之,而符号型则更少。这里一方面表明丝路民族神话与国内中原神话及西方外国神话相比,具有更浓厚的原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丝路神话中的解释性功能呈现出由低级趋向高级,由实用功利性逐渐发展为审美、非物态化状态。
在丝路神话中,存在有大量的象形型神话形象。这类形象大多没有经过“作者”和流传者更多的综合和加工,其形象本身就是客观世界的某一物体,或者突出和夸张这个实体的某种特征。丝路原始初民正是借助这类形象解释和寄寓着自己最原始的观念。例如太阳,在丝路创世神话和自然神话中,它既不是“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太阳帝,也不是希腊神话中那个弹奏着七弦琴的裸体少年阿波罗,而是发着光和热的圆球形的太阳本身。类似“太阳”这种象形型的神话形象在丝路神话中还有很多,如用犄角顶起地球的公牛、生下五个儿子的树神、引导军队前进的苍狼、开口说人话的神鹰、奔驰如飞的神驹、能幻化成美女的白天鹅等等。这类神话形象大都具有直观性和物态化的特征,在西域初民原始思维的制约下,用幻想代替现实,以解释和说明自然现象、种族来源等。
随着西域原始初民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开始学会运用直观的综合方法去创造神话形象。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能够运用现实生活中所感知的某种具体事物作为神话里的形象,而且能进一步运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种种表象,在幻想中复合构造某个新的神话形象,这样就产生出复合型的神话形象。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复合型神话形象在我国丝路神话中也较丰富。它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几种动物的复合体,一类是半人半兽形,以后者居多。如维吾尔神话中亦人亦兽的“乌古斯”、“人熊”库尔班;哈萨克神话中的人头鸟身的飞禽之神“萨木勒克”等。在以半人半兽为主的复合型神话形象中,其特征还未摆脱物态化的象形型神话形象的影响。它的解释性功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由图腾崇拜转向祖先崇拜的社会历史内容。远古时期,在我国辽阔的西域土地上氏族部落林立。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神话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氏族部落的战争和迁徙流动中,各个氏族部落不断地兼并融合形成新的氏族部落。而代表这些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神话形象也随之而进行着横向的综合,产生了代表新的更高层次的部落群体的图腾标志或神话形象。例如在维吾尔族神话《乌古斯传》中,“乌古斯”这个神话形象是由“公牛”、“狼”,“黑貂”、“熊”的形象综合构成。它形象地反映出维吾尔族是由牛图腾、狼图腾、貂图腾以及熊图腾等众多氏族联合为一个部落的过程。在乌古斯这个由众多动物图腾集于一身的神话形象中,已经突出地显露出“人”的形象来,即形成半人半兽形的神话形象。这里,一方面表明了杰出人物的作用,显示了乌古斯代表着维吾尔人的祖先,具有了祖先崇拜的历史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在神话形象中掺入具体的动物形象,以表明区别不同氏族的作用和使命还未完全消失(如果单用人形就不能识别),显示出维吾尔先民在人类初期的动物偶像崇拜意识。
当神话形象由复合型发展到人型(或者是符号型)时,神话已经开始迈进文明时代的门槛,从而进入了高级阶段。在丝路神话中,神话形象的物态化程度减低到最低限度,形象的表象已经摆脱了怪异多样的形态,渐进为匀称协调的“人”的面目。例如,在塔吉克神话《公主堡》中,美丽的汉族公主和骑着神驹的英俊男子太阳神均为人的形象。在维吾尔神话中有降伏神龙的龟兹王的形象,塔塔尔族神话中有银须皓发仙人赫秩儿的形象。这些神话形象均具有“人”的面目、语言和思想感情,已经完全看不到早期神话中丑陋怪异的动物的踪影了。丝路的人型神话表明,西域原始先民到此时视野已经扩大,对不同种族,不同民情风俗的部落和自然社会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原始思维已经开始解体。神话的解释性功能开始失去实用功利性质,神话“作者”的审美主体逐渐形成,开始作为“艺术品”的丝路神话,“神”性消退,而“人”性正在萌发。
其二,礼仪性功能。丝路神话在远古先民那里并不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而是具有实用性的礼仪规范和价值规范的效力。例如在丝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存有宗教祭祀崇拜活动,而丝路神话正是为这种活动提供了根据和保证。在大量的丝路宗教神话中(包括原始宗教神话),先民们把某种宗教的起源推向荒古,奉为神祖恩赐的法宝,使全体参加祭祀者坚信不疑,并视为求生和发展的根本方法。
原始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①,其基本内涵是用虚妄的认识和行动来满足求食和增殖的需要。神话,正是在原始意识支配下,透过宗教的礼仪来实现原始初民求食和增殖的感情愿望的一种精神纽带。在丝路神话中,这种宗教礼仪主要体现在对诸多神祗的崇拜上。
例如对自然神的崇拜。自然是宗教最原始的对象。在丝路自然神话中,那种原始初民与自然之间既恐惧又依赖的特殊关系,促使西域原始初民根据自身的主观需要来幻化创造出众多的自然神祗,出现了太阳神、月亮神、星辰神、山神、水神、风神、雪神、火神、树神等繁多的崇拜对象。这种对自然神的幻化和崇拜,来自功利的需要,即把自身恐惧和依赖的感情寄托在对人类生活关系重大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身上。对“火”的崇拜,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火,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可以把生食变成熟食,可以防止野兽的袭击,而火的明灭,火焰的曳动,又最容易激起人们的神秘感。依赖感和神秘感相结合,乃把火现为具有特殊力量的神,并因此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崇拜仪式和礼俗。在哈萨克神话、柯尔克孜神话、塔吉克神话中,多处可见“拜火”的遗迹。其目的是用火来保护人类的安全。如,转场时烧两堆火,让畜群从火堆中间穿过,火的熄灭会带来人畜的大量死亡等。这正如希腊语中,“火的熄灭”与“氏族的灭亡”属同一词语一样。
又如对图腾物和始祖神的崇拜。在丝路民族神话中,苍狼崇拜、天鹅崇拜、树崇拜、鹿崇拜、鹰崇拜、冰山崇拜等皆属于此类。丝路原始初民通过对这些动植物图腾物的崇拜,来显示本氏族与某一动植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以解释氏族的来源。如维吾尔族神话,在后世汉文史书的有关记载中,多处有“拜狼纛”、“树狼头纛”、“施金狼头”的记述。这种以动植物为图腾物的始祖崇拜,发展到后来即成为某个氏族民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受到该氏族部落的信仰和膜拜,直至今天,这些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仍成为某些民族坚韧的精神象征。
除此之外,在丝路神话中还有对生殖的崇拜和对英雄神祗及鬼魂的崇拜,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宗教礼仪构成了丝路神话的重要内容和功能。没有对神的崇拜,就没有神话。丝路神话在对神的宗教仪式中产生、流传、发展。没有神的祭坛,便没有丝路的文坛。
丝路神话除了具有神的礼仪性功能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某种法规作用。在西域,远古时期并无法律,也没有专设的法律执行机构。而神话往往在人们发生诉讼时,由神祗来法定曲直,起到一种法规作用。另外,那时的原始初民也不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价值观念,以神的名义起誓,就是行为的最高约束力量。这样,丝路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对建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规范行为准则,保护氏族部落神主的尊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力。最后,丝路神话还具有加强西域各氏族部落内部凝聚力,组成有力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突出作用。
其三,操作性功能。从本质上讲,丝路神话在西域原始初民手中显示出一种巫术的实践力量。在洪水、干早、地震、瘟疫等灾害面前,他们根据神话的启示,祈求神灵保佑,以消灾除难。例如,哈萨克神话中记述的求雨仪式“塔萨特克”。干早季节在河边,人们聚集在一起,向腾格里宰牲祭祀,祈求雨神降雨。后来哈萨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掺入了悬挂《古兰经》,大毛拉念诵求雨的祷文,众人向腾格里和真主叩头祷告等内容。求神驱病的“巴克思跳神”。在哈萨克神话中,萨满教巫师巴克思应邀到病人或显贵人家跳神。巴克思一边弹奏着召唤鬼神的乐曲,一边歌唱祷告腾格里的歌曲;不久,巴克思神情恐怖恍惚,浑身颤抖,围绕火堆边呼唤鬼神之名,边作出和魔鬼搏斗的动作,甚至跳上毡房天窗,或骑马绕毡房奔跑,大喊大叫,最后昏迷倒地;巴克思醒来后向人们诉说自己与神灵见面交谈的经过,以预言未来和消除附依在人身上的鬼怪魂魄。在维吾尔族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情景,如杀羊祭祀雨神亚合提汗、驱鬼祛病的“奥特拉西”等。在塔吉克神话中有祈求神牛,以防地震不测等。在丝路英雄神话中,这种占卜求卦、祭祀神灵的情节更是比比皆是。氏族部落的英雄们,每逢战时高呼神灵的名字,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每逢重大事件之前,他们要观测天气,祭祀神灵,选择吉日,以趋避凶神。综上所述,丝路神话以神灵的神秘力量为中介,调整着原始初民与客观世界的种种不和谐关系,体现着原始艺术所固有的以实用功利为目的的操作性功能。
以上我们对丝路神话的表层功能进行了简明的叙述。从丝路神话在整个丝路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丝路民间文学其他形式的影响角度来看,丝路神话的深层结构功能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大约更为重要。在丝路原始先民的文化中,神话并不是一种单纯想象的虚构物,也不是一些荒谬有趣的故事,而是以原始初民的真实感和神圣感为基础的渗透着独特神话思维的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文化。丝路神话,作为丝路各民族精神植株上开放的第一朵奇葩,它在原始初民心目中的地位虽不及在今天文学艺术园地里那样芳香袭人,但是,在人类艺术漫漫长夜中,它却是露出的第一线曙光。丝路神话以其鲜活瑰丽的原始意象,积淀在后世丝路文化和丝路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深刻地体现出丝路各民族的早期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在长期的承传中,它转化为一系列神话原型和文学母题,形成了丝路各民族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和左右着丝路民族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如果我们展开丝路神话长卷,就会醒目地看到一系列光彩夺目的神话篇章:神奇的迦萨甘创造了天地万物;美丽的天鹅女与年轻的勇士结为伉俪,繁衍了哈萨克部落;英武的乌古斯可汗在苍狼的引导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白雪皑皑的慕士塔格冰峰上,神鹰飞翔,鲁斯塔木之弓化作美丽的彩虹,横跨在天上;顶地球的公牛,稍不留神便山摇地动;太阳与月亮两姐妹在天上相互追逐,戏谑玩耍..透过这种种神话的万花筒,我们不仅观察到丝路各民族的童年,更为重要的是向我们今人提供了一把研究他们现状和未来的金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对丝路神话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纯文学性的研究,乃是对丝路各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的研究——对一种民族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探索。
其一,原始性和神祗的体系性
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认识的反映。在丝路神话中,这种反映主要表现为丝路各民族先民对自然万物、人类与自然力矛盾的混沌认识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哲学观念,这就形成了丝路神话的原始性。例如,在哈萨克族神话中占有显著地位的创世神话:宇宙从漆黑中分离诞生出新的世界;从滚沸的混合体中产生水、土、日、星;从泥土中诞生初人;此外,还有九重天的人间,七层地底下的生命世界,十八层天里的神仙;用一只犄角顶着地球的巨大天牛,顶着海水的蓝鲸,能喝光江河湖海的怪物等等。从这些神话可以看出,哈萨克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对宇宙形成、人类起源的幼稚而独特的看法。这些自然生成和社会现象与他们的游牧生活、原始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又如,在柯尔克孜族中流传的《鹿妈妈》①的族源神话。传说,古代柯尔克孜人曾遭到一次突发的空前规模的战争洗劫,使得整个民族濒于灭绝。当时幸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进山采野,才幸免于难。当他们出山看到家乡惨状时,不禁绝望地恸哭起来。这时,一只母鹿过来将他们带回山里,用鹿奶养育他们长大成人。后来这对男女结为夫妻,繁衍了后代。现在柯尔克孜人中还有叫“布古”(鹿)的大部落,据说就是他们的后代。这篇神话明白无误地向今人表明,柯尔克孜人对“鹿”崇拜的原始动物图腾观念。其实柯尔克孜人的祖先并非是鹿,在我国史书《史记》最早记载中称其为“坚昆”等氏族部落。当时主要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由于被漠北匈奴所迫,迁至天山周围,到公元2世纪时建立了柯尔克孜汗国。这些族源神话放射出的原始神秘色彩,使柯尔克孜初民确信自己的族母是“鹿妈妈”,时至今日,在柯尔克孜族民间还盛行着崇敬鹿,将鹿视为圣物的习俗。
丝路神话原始性特征还集中表现在神话的承传方式上。众所周知,丝路民族神话主要在本民族中靠口头承传和保存。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种种原因,在丝路一些边远闭塞的民族中,几千年来,神话一直被当作本民族的历史而传唱、讲述着。即使在今天,诸如哈萨克族中的“阿肯弹唱”,满族中的“萨满口传神谕”等承传形式,也仍盛行不衰。这种口传艺术,由于较少有文人的加工雕琢,因而继续保持着民间文学固有的口语化、生活化的特色,使得丝路神话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艺术的特征。就目前接触到的神话资料来看,丝路神话比较完好地保存着它的原始面貌。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丝路各民族原始的社会生活、民族历史和文化以及原始的思维活动等方面,无疑具有极为可贵的参考价值。
神祗体系的形成,是神话发展到后期的产物。它标志着原始人类对宇宙万物认识的成熟和完成,他们开始脱离野蛮状态,向有序的文明社会过渡。从神话发展的角度看,一旦神祗体系出现之后,神话发展也就趋向成熟,并相对处于停滞状态。在中国,古老的汉族神话虽然多见于古籍记载,但由于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统治和“不语怪力乱神”,加之历代文人篡改,将神话历史化,使得原来丰富的汉族神话大部分失传。至今残存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著作中的神话资料,实属肢体不全。其中虽也存有各类神祗,但神祗体系不甚完整。甚至显示不出神祗体系的基本面貌。相反,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尤其是在丝路民族神话中,我们却不难发现神祗的独特体系。这完全可以和古埃及神祗体系、巴比伦神祗体系,甚至古希腊神祗体系相媲美。
在丝路神话中,神祗体系大都有一个主神(至高无上的神)统帅着其他诸神。与此相对立的,还有一套冥府鬼怪诸神。这种神祗体系在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满族等丝路少数民族神话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以哈萨克族为例。在哈萨克族神话的神祗体系中,迦萨甘是创世之神,至高无上;腾格里是天神,主宰着世界万物。在这之下有诸多掌管各部门的神灵,如保护妇女的乌弥女神,主宰雷电的阿加哈依神,摄取亡魂的阿尔达西神,为人们带来福运的克德尔神,行动神速的捷勒阿亚克神,飞禽之神萨木勒克,体大如山力大无穷的巨人达吾,以及马神康木巴尔阿塔和神马匹拉克,牛神赞格巴巴和用犄角顶地球的天牛,山羊神谢克谢克阿塔,绵羊神绍潘阿塔和骆驼神奥依斯尔哈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与神作对的妖魔鬼怪。如魔王佩里、魔鬼捷兹特尔纳克、独眼巨人以及阴险毒辣的老妖婆等。
又如柯尔克孜族神话。柯尔克孜人自古以来依山而居,逐水而游,过着狩猎和放牧的生活。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劳动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独有的心理和习俗,也就决定了在他们的神话中神祗体系的特殊种属。天上有宇宙神、火神(太阳)、冷神(月亮)、北斗神、三羊星神、七星神、月亮中的巫婆等;人世间有幸运之神库特、力神玛勒斯、风神科依卡卜、冬神琪勒黛卡尔特、雪神阿克阿坦、婴儿保护神吾玛叶涅、神鸟阿勒普、鹰神布达依克、骆驼神奥依索勒阿塔、马神康巴尔阿塔、羊神巧力潘阿塔、牛神乌依桑巴巴、狗神库麻依克;与以上诸神相对立的还有聚集在“妖魔世界”中的狰狞可怖的妖魔阿勒巴尔斯特,“臭妖”沙色克阿勒巴尔斯特等。
其二,复杂性及其宗教的衍变性
丝路民族神话既古老又复杂。这里除了诸多民族神话异彩纷呈的不同面貌外,更为主要的是“神话”的特殊涵义赋予了丝路各民族神话迥异的质的规定性。即它是丝路原始人类萌芽状态的宗教、历史、哲学、法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观念的反映。由于神话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丝路各民族神话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色彩。如哈萨克神话多为“草原神话”,维吾尔神话多为“绿洲神话”,而塔吉克神话则多为“冰山神话”(关于此,下面将有专门论述)。
自有西域初民之后,丝路神话在不断的产生和承传中,除了自身的发展变异外,还不时夹杂带入一些时代、阶级、种族和多种不断衍变的宗教等观念,使之在丰富多样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丝路各民族的图腾、崇拜、信仰等宗教情感和形式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丝路各民族的童年时期,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如萨满教在当时各部落氏族中盛行)。这是一种自发的全民信仰,常常以多神崇拜的图腾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柯尔克孜人古老宗教信仰中存在着多种崇拜形式,有星宿崇拜、大地崇拜、山崇拜、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气崇拜、狼崇拜、鹰崇拜、骆驼崇拜、龙崇拜、虎崇拜、猫崇拜、喜鹊崇拜、灵魂崇拜、坟墓崇拜、女性崇拜、白色崇拜、红色崇拜等。总之,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都认为具有神的意味,皆崇拜之。这种以多神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是丝路各民族初民统一意志、团结氏族部落以抗衡自然力的精神动力,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在这种原始宗教的统攝下,丝路初民的原始神话呈现出一种单纯而神秘的多神崇拜的特色。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多神宗教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浓烈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宗教(当然,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衍变过程)。一神崇拜宗教是一种人为的宗教。为了宣扬教义,这种宗教不断利用和改造丝路神话中的神祗,由多神崇拜衍变为一神信仰,在不少神话情节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样,在丝路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迫使丝路神话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除去其他因素外,单就因宗教信仰的衍变导致丝路神话在内容诸方面发生变化,这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以及锡伯族等丝路民族中极为普遍。
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隶属阿尔泰突厥语系的维吾尔族先民曾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这以前,也曾有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前宗教形式)。多桑《蒙古史》中说:“畏吾儿先人奉之宗教为珊蛮教,与亚洲北方诸部落同。其教之巫师曰珊蛮(cames),即此粗野宗教之教师也。”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因诸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称巫师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的宗教特点。萨满教在教义和观念上将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和若干层次:上界为天堂,下界为地狱,中界系人世地面;奉“腾格里”为尊神,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具有多神偶像崇拜的特点。维吾尔先民信仰萨满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之前居住在漠北时期,以后长期保留着萨满教的残余影响(如至今在维吾尔族民间还有“巴合西”,即“萨满”)。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祆教(原名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传人西域。据《梁书》、《魏书》、《隋书》、《唐书》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域各地居民“俗事天神”,各国“其国事天神火神”①,可见祆教在当时流行情况。祆教以《波斯古经》为经典,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要求人们以善避恶,弃暗投明,教徒要在“麻葛”(祭师)的指导下通过专门的仪式,礼拜“圣火”。唐以后,祆教在西域逐渐衰落,伊斯兰教传入后便销声匿迹,但其遗风仍然存在于维吾尔族民间。如现今民间习俗,在迎亲回来的路上,新郎、新娘要跳过或绕过一堆火,以表示幸福吉祥。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道教已在西域高昌的维吾尔先民中传播。到唐朝时,道教颇为兴盛,在伊州(今新疆哈密地区)等地修建多处道观,并有阴阳、巫觋、道人、咒师等道教的职业人员。此种状况到宋元时期才趋于衰微。在公元6~7世纪,摩尼教开始输入到当时居住在漠北的回鹘部落中,并于公元763年之后成为回鹘的国教。近代中外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寺院遗址和文献,即为证明。后伊斯兰教传入,摩尼教才在回鹘中逐渐消亡。摩尼教原是伊朗的古代宗教之一,它在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思想材料而形成自己的独特信仰。摩尼教崇拜“四大尊严”(即大明神、神的光明、神的威力及神的智慧),以大明神为尊神,根本教义为“二宗三际”(“二宗”为明暗两极,“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摩尼教在西域,尤其在高昌回鹘王国影响深远,对后世西域文明(如历法)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公元6世纪,景教(即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教派)传入西域喀什噶尔等地,在那里发展到十分兴盛的地步,后来在今吐鲁番地区形成了景教的中心。景教在西域流传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在民间的影响仅次于佛教和伊斯兰教,成为西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大约于公元2世纪前后传入西域于阗,后来沿着丝绸古道的南北两路依次传布。公元2~3世纪,佛教已遍布西域各地,公元4~5世纪日趋隆盛。隋唐时期已非常发达,形成了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高昌(今吐鲁番)四大佛教中心。公元840年,从鄂尔浑河流域迁到西域的回鹘部落接受了佛教,并渗透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他们的主要宗教。当时的龟兹、于阗、高昌等地已是佛教活动的中心。高僧云集,具有完善的组织和法事仪式,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典籍,兴建寺院,创造了辉煌的佛教石窟艺术文化。
维吾尔族先民虽曾信奉过上述的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但最终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早在唐代伊斯兰教即已开始输入西域,但大规模传布,则是在公元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萨图克·布拉格汗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公元960年,阿尔斯兰汗木萨统治时期,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接受伊斯兰教,标志着喀喇汗王朝实行了伊斯兰教国教化。此后,随着蒙古军队征服中亚,西域伊斯兰教发展一度停滞。14世纪,秃黑鲁帖木儿登上东察合台汗国宝座成为伊斯兰教信徒后,伊斯兰教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15世纪后期,吐鲁番等地改信伊斯兰教后,伊斯兰教终于取代了历史上的种种宗教,使得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中成为唯一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徒绝大多数属于正统主义的逊尼派。该派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遵循“逊奈”(圣行),坚信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天经、信使者、信末日),承认安拉的前定,履行天命五功(念、礼、斋、课、朝),以穆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承认“四大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此外,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还有苏非派、什叶派、瓦哈比派等。
综上所述,这种由多神崇拜到一神信仰的历史宗教事实,使得维吾尔族神话相应出现了复杂的状态。这在它的一些经典著作,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阿赫马德·本·穆罕默德·玉克乃克的《真理的入门》等中,对多种衍变以及神话传说都有过记载。例如,有大量的维吾尔先民在萨满崇拜原始宗教时流传的狼神话、树神话和《乌古斯传》;有在佛教盛行时期在各个“千佛洞”壁画上记载的佛教神话传说;更有伊斯兰教统辖后流传着的诸如《女天神造亚当》、《拉布胡兹故事集》这样富于浓郁伊斯兰教色彩的神话故事。
另外,多种宗教的更迭衍变使得维吾尔族神话中的一些重要神祗的涵义也相应发生着某种变化,并多次被赋以新意。例如,“腾格里”(在突厥语中的读音是tangri),原指“苍天”、“上天”之意。维吾尔初民在信仰萨满教时期,把“腾格里”视为“天之主宰”、“神祗之统称”,是“上界”、“天堂”;在信奉祆教时,被用以称呼该教的至高神阿胡拉·玛慈达为“艾兹罗阿腾格里”;到了信奉佛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佛祖”为“波尔汗腾格里”;在改宗伊斯兰教后,它又被用以称呼伊斯兰教的尊神“安拉”、“真主”;在近现代,“腾格里”一语在历史文献中已被阿拉伯语的“安拉”和波斯语的“胡大”代替了。
其三,审美价值——艺术形象的怪诞美
丝路神话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它作为一种艺术美,集中反映了西域原始初民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就是,以幻想的方式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反映出既朦胧混沌,又严肃认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出种种鬼斧神工的神话来。这些神话以虚幻为真实,以险异为雄奇,以荒诞为瑰丽,以蒙昧为睿智,表现出丝路各民族文学在童年时期所特有的天真和稚气,具有一种疏简朴野、离奇怪诞的美学风貌。
丝路神话的这种美学价值,主要是通过神话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怪诞美表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原始初民对时空限制的逾越上。
在丝路远古神话中,原始初民以天地万物变化无常的现实为基础,借助想像的翅膀,飞腾跳跃,打破了物质世界的固有时空,创造出许多解释自然、征服自然的美丽的神话传说,艺术地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界以及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大多为荒诞不经,但由于所表现思想感情的真挚,编织艺术时空的神奇,使人迷醉不疑。丝路神话的这种超越现实荒诞离奇的美学特征,往往获得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例如,柯尔克孜族的创世神话《大青牛的传说》。①相传大地分为七层,由地下一头巨大的青牛用两只角轮换支撑。当它的一只角疲劳时,便改用另一只角支撑。每到此时,便山摇地动,发生地震。人们惹恼青牛就会有灾难降临,而青牛若失去良心,大地将陷入无底深渊。这则神话表明,在古代柯尔克孜人眼中,人的命运是与大自然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自然界中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左右着人的命运。这里不乏展示出柯尔克孜人丰富神奇的想象力,但更多流露出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渴求获取身心自由的忧虑。二是表现在丝路神话中,人、神、兽浑为一体,尤其是那些顶天立地的神话英雄形象更是亦人亦神亦兽,放射出一种怪诞美的异彩。这是因为原始人类在很长时期内不能自觉地把自己区别于动物,与百兽相与群居;另外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脆弱,他们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原始宗教幻化出来的神祗和有奇异功能的怪鸟异兽身上,以实现和放大人的价值。如,维吾尔族英雄神话《乌古斯传》。乌古斯一生下来就吃生肉、喝酒,四十天后会走路、玩耍。英雄乌古斯的形象在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他的腿像公牛的腿,腰像狼的腰,肩像黑貂的肩,胸像熊的胸,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②这种半人半兽怪诞的乌古斯英雄形象,正是要把维吾尔族先民几个核心氏族的图腾集中于乌古斯可汗一身。它反映了由氏族而联合为部落的过程,乌古斯可汗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丝路神话艺术形象的这种怪诞美,既符合艺术美的普遍原则,又兼有自然美、社会美的一般特点,它以神奇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征服着一代又一代人。
其四,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丝路神话中,民族性和地方特色表现得最为明显。丝路各民族总是将各民族不同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方式、心理特征等包容在优美神奇的神话传说中,构成情调各异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表现出在一定的历史宗教背景下异质的文化形态,从中渗透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为例。
从宏观上看,这三个民族的神话因融入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特征等因素,使得各自的神话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如哈萨克神话,在创世和族源神话中,迦萨甘都被视为创世主,创造出天地万物;天鹅女被视为民族的始祖母,苍狼被看作与苍天有关的神物,成为哈萨克原始部落的标志;在自然和英雄神话中,出现了众多的与畜牧有关的动物保护神祗和四方征战、保卫家乡牧场的英雄。这一切,都与哈萨克人部落联盟的历史有关,与他们特殊的游牧生活有关,反映出哈萨克先民强烈的部落意识,从本质上呈现出一种“草原文化”的特质。又如维吾尔族神话,在多种宗教漫长的更迭衍变中,适合于精神统治和农耕文化的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它的神话有别于其他民族神话。在《女天神造亚当》、《龙妻索夫》等神话中,明显看到“真主赐给泥人以灵魂”、“因河水断流,农作物无法耕种”等情节,反映出伊斯兰教和农耕文化对神话的影响。在整体上,维吾尔族神话呈现出一种“农耕文化”或“绿洲文化”的形态。再如塔吉克族神话。塔吉克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雄伟神奇的慕士塔格山下,特殊的自然环境赋予塔吉克神话所独具的冰山式的神奇魅力。慕士塔格山,不仅是座闻名于世的冰峰,还是一尊超自然的主宰塔吉克人的神灵。在它的统摄下,神鹰飞翔,鹰笛悠扬,英雄鲁斯塔木惩治邪恶,建功立业。塔吉克族神话是真正的冰山神话,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冰山文化”的特质。
从微观上看,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吉克的神话中,诸如图腾崇拜、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使其在民族性和地方特色上大相径庭。例如在族源神话中,这些民族因图腾崇拜物不一样,因而鲜明地体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哈萨克族《天鹅女》和关于“苍狼”的神话中,图腾物是天鹅和狼;在维吾尔族《狼的后代》、《树生子》、《神树母》等神话中,图腾物是狼和树;而在塔吉克族神话《慕士塔格的传说》和《鹰笛》中,更多的是对冰山和鹰的图腾崇拜。这些民族各自不同的原始崇拜对象,使得他们的民族渊源、精神品格和宗教文化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最终在行动模式和文化模式上产生出鲜明迥异的民族性。
另外,在代代沿袭的民族习俗方面,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吉克这三个民族的神话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差异。例如,在对“火”和“火的观念”上。哈萨克神话中出现有“火娘娘”奥特阿娜的形象。哈萨克人崇拜火,认为火是家庭的恩人、明灯,具有生命、灵性和某种神奇的力量。他们在婚礼上有“拜火”、“向火倒油”的习俗,在丧葬中有“四十支蜡烛”点灯守灵的习俗;在塔吉克神话《光明与黑暗》、《祖哈克与魔鬼》等中,有不少关于“火”的记叙,从中可以看到在早期塔吉克人中拜火教的痕迹。在塔吉克族生活中也有不少关于“火”的习俗。如他们每年回历八月中旬举办的传统节日“皮里克节”(灯节),实际上是赞美崇拜火,借火求福。在发生日食、月食时,婴儿降生时,畜群转移时,埋葬死者时,“火”在这其中都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由于劳动生产方式比较接近,哈萨克与塔吉克在对“火”的观念上比较相似,他们大都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在神话和习俗中把“火”放在重要地位。与此相比,维吾尔族却略有不同。在维吾尔神话中少有“火崇拜”的传说,尽管生活习俗中也存有迎亲归来“跳火”的遗风和“奥特拉西”驱鬼祛病的迷信活动,但这些大都属祆教的遗迹,并无多少功利色彩。维吾尔族对“火”的重视,远远不如对太阳、月亮、星星,甚至植物和盐的崇拜。
以上我们对丝路神话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丝路神话所呈现出来的原始性和神祗的体系性、复杂性和宗教的衍变性,艺术形象的怪诞美所产生的审美价值以及鲜明而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凡此种种,盖源于丝路各民族原始初民特殊的心理和思维,这就是神话思维。
神话思维,是丝路各民族童年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原始思维,它在西域原始初民的思维世界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丝路神话,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文学艺术作品,从中体验到更多的是一种洪荒时代的原始美;而对于西域原始初民,则是一种巫术中介。通过它,使原始人类体验到朦胧、混沌的生命存在的一种神秘,从而达到实用的功利目的。众所周知,原始人类在远古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知识极贫乏,对大千世界无所知晓,对宇宙奥秘深感莫测。猛兽的袭击,疾病的传染以及自然灾害等,无时不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因此,面对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和宇宙万物,他们便产生出一种恐惧感,觉得在那些威慑人们的种种现象背后还有着特殊的物体存在。这便在他们头脑中显现出一种“神的幻影”。与此同时,原始人类又对天地万物寄寓着希望,幻想着有一种超人的神奇力量助人一臂之力,使人安宁度日,带给人间以幸福。于是,人们的心中又升起一尊尊崇拜偶像,这便是“自然崇拜”。这些形成了原始宗教的思想基础,集中地体现在“自然神”的“万物有灵”的思维观念上。后来,原始人的劳动生活环境逐渐趋于固定,人们开始在自己生存的那一特定环境里选择某一自然物,作为崇拜的对象,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原始人在人与崇拜物之间特殊的关联中,寻觅体验着一种神秘而迷妄的信念。或祈求保佑,消灾除害;或占卜吉凶,预祝丰收。虚幻的巫术活动开始了。原始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人们产生了“灵魂不灭”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和躯体是可以分离的,并能单独存在。灵魂可以化作无形的“神灵”,以一种神奇的威力对在世的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由此,生者对死者的灵魂产生惊恐而加以崇拜,祭祀鬼神的活动便由此开始。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充满了“神秘”的因素。“神”的观念形成,支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想。这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那样:“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以至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神话的创造,正是原始人以这种意识形态去认识和理解自然界,表达他们渴望“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的产物。以上我们对神话思维的神秘性加以论述旨在说明,丝路神话依然是在西域各民族原始初民神话思维的支配下,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神秘意识,弥漫着一抹斑斓的神秘色彩。丝路神话的这种神秘性,一方面表明西域初民的无知,同时又说明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是与社会、自我存在的功利作用相关联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自身无能的情况下,便寄希望于“神”的身上。这在丝路神话中的创世神话、族源神话和自然神话中尤为突出。
意大利历史哲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柯,他把人类的心理功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最初只有感受而不能知觉,接着用一种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①在产生神话的原始社会中,原始人是凭着感官作为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的,西域初民亦不例外。在那个朦胧混沌的洪荒时代,他们还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还限于感性方面。他们对于宇宙奥秘的探索,在不知而求知中是通过感官,根据直接的直觉,去探索,去认识,去解释和行动的,从而在记忆中获得了对客观事物的某些形象。西域原始初民的神话创作,便是描述他们所获得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将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形象的“表象”加以再现。这种神话思维的感官性,在西域初民创造的丝路神话中具体表现为模仿性和拟人性。如在达斡尔族神话中,“洞穴神话”颇引人注目。在他们先民的生活经历中,曾经有过栖息洞穴、树丛的生活。在他们的思维意识深处,认为奇特的山峰、山洞和古树,是神灵栖息之处。通过感官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加之出自本能的再现性模仿,在达斡尔人的思维中,“洞穴”等就成为联系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的媒介,于是产生了《嘎西讷洞神话》和《车齐热讷洞神话》。又如哈萨克族神话《月亮藏身》。太阳和月亮这对孪生美女,因相互嫉妒,彼此交恶。最后太阳抓破了月亮的脸,月亮出现了黑斑,不得已经常躲着太阳。这则颇具情趣的神话反映出哈萨克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具有的一种类似儿童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思维世界里,主体与客体还混为一体,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在原始的思想中,日与月大都是活的东西,而且有人性”。②在这种“以己度物”、“以物拟人”的思维支配下,他们不自觉地将万物拟人化,描绘出人与日月情深意厚,亲如一家的情景。从中也可看出,哈萨克先民思维河床中流淌着丰富不竭的原始想象的河水。
丝路神话是西域原始初民神话思维作用的结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一切似乎只是一种梦幻般的存在。但是,丝路神话作为西域早期文化象征性的标记,其中蕴涵着各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风俗、艺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它是丝路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丝路神话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种文化实体。它具有独特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如果我们将丝路神话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的结构功能大体可分为表层和深层两部分。表层部分又由两个层面构成,即由神话的语音、文字所组成的语句层面和由神话的语句集合构成的语义层面构成;深层部分主要指神话的深层结构所蕴涵的文化隐义层面。这一层面构成了对神话的真正解释。
从表层结构功能看,丝路神话至少具有以下三种价值功能:其一,解释性功能。丝路神话是西域原始初民的“哲学”和“科学”。他们的认识感知方式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是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①。丝路各民族先民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世界宇宙的形成,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解释他们自身的来源,解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这种解释性功能在我们前面所表述的丝路创世神话、自然神话、族源神话以及英雄神话中显示得再充分不过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丝路神话的解释性功能“是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论述神话的产生时指出:“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使人类“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②。丝路神话是西域原始初民的精神产物,他们凭借特殊形式的想象——幻想,把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彼时的现实生活和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交错组合,巧妙编织,形象地展现出一个“幻想世界”。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不断创造出一个个衍化发展着的神话形象。通过种种神话形象,生动具体“形象化”地体现出他们对主观化了的外部世界的种种神奇的解释。
在西域的丝路神话中,出现有千姿百态的神话形象。如果根据它们的外形特征和纵向的发展,我们大体可将此分为三种类型和三个阶段。一是象形型神话形象,这是最原始的形象,也是最低层次的形象;二是复合型神话形象,这是在象形型神话形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神话形象发展中级阶段的产物;三是人型或符号型神话形象,这是神话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如果用简明的方式来表示,即:
在我国丝路神话中,象形型神话形象最为丰富,复合型神话形象次之,人型形象又次之,而符号型则更少。这里一方面表明丝路民族神话与国内中原神话及西方外国神话相比,具有更浓厚的原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丝路神话中的解释性功能呈现出由低级趋向高级,由实用功利性逐渐发展为审美、非物态化状态。
在丝路神话中,存在有大量的象形型神话形象。这类形象大多没有经过“作者”和流传者更多的综合和加工,其形象本身就是客观世界的某一物体,或者突出和夸张这个实体的某种特征。丝路原始初民正是借助这类形象解释和寄寓着自己最原始的观念。例如太阳,在丝路创世神话和自然神话中,它既不是“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太阳帝,也不是希腊神话中那个弹奏着七弦琴的裸体少年阿波罗,而是发着光和热的圆球形的太阳本身。类似“太阳”这种象形型的神话形象在丝路神话中还有很多,如用犄角顶起地球的公牛、生下五个儿子的树神、引导军队前进的苍狼、开口说人话的神鹰、奔驰如飞的神驹、能幻化成美女的白天鹅等等。这类神话形象大都具有直观性和物态化的特征,在西域初民原始思维的制约下,用幻想代替现实,以解释和说明自然现象、种族来源等。
随着西域原始初民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开始学会运用直观的综合方法去创造神话形象。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能够运用现实生活中所感知的某种具体事物作为神话里的形象,而且能进一步运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种种表象,在幻想中复合构造某个新的神话形象,这样就产生出复合型的神话形象。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复合型神话形象在我国丝路神话中也较丰富。它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几种动物的复合体,一类是半人半兽形,以后者居多。如维吾尔神话中亦人亦兽的“乌古斯”、“人熊”库尔班;哈萨克神话中的人头鸟身的飞禽之神“萨木勒克”等。在以半人半兽为主的复合型神话形象中,其特征还未摆脱物态化的象形型神话形象的影响。它的解释性功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由图腾崇拜转向祖先崇拜的社会历史内容。远古时期,在我国辽阔的西域土地上氏族部落林立。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神话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氏族部落的战争和迁徙流动中,各个氏族部落不断地兼并融合形成新的氏族部落。而代表这些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神话形象也随之而进行着横向的综合,产生了代表新的更高层次的部落群体的图腾标志或神话形象。例如在维吾尔族神话《乌古斯传》中,“乌古斯”这个神话形象是由“公牛”、“狼”,“黑貂”、“熊”的形象综合构成。它形象地反映出维吾尔族是由牛图腾、狼图腾、貂图腾以及熊图腾等众多氏族联合为一个部落的过程。在乌古斯这个由众多动物图腾集于一身的神话形象中,已经突出地显露出“人”的形象来,即形成半人半兽形的神话形象。这里,一方面表明了杰出人物的作用,显示了乌古斯代表着维吾尔人的祖先,具有了祖先崇拜的历史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在神话形象中掺入具体的动物形象,以表明区别不同氏族的作用和使命还未完全消失(如果单用人形就不能识别),显示出维吾尔先民在人类初期的动物偶像崇拜意识。
当神话形象由复合型发展到人型(或者是符号型)时,神话已经开始迈进文明时代的门槛,从而进入了高级阶段。在丝路神话中,神话形象的物态化程度减低到最低限度,形象的表象已经摆脱了怪异多样的形态,渐进为匀称协调的“人”的面目。例如,在塔吉克神话《公主堡》中,美丽的汉族公主和骑着神驹的英俊男子太阳神均为人的形象。在维吾尔神话中有降伏神龙的龟兹王的形象,塔塔尔族神话中有银须皓发仙人赫秩儿的形象。这些神话形象均具有“人”的面目、语言和思想感情,已经完全看不到早期神话中丑陋怪异的动物的踪影了。丝路的人型神话表明,西域原始先民到此时视野已经扩大,对不同种族,不同民情风俗的部落和自然社会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原始思维已经开始解体。神话的解释性功能开始失去实用功利性质,神话“作者”的审美主体逐渐形成,开始作为“艺术品”的丝路神话,“神”性消退,而“人”性正在萌发。
其二,礼仪性功能。丝路神话在远古先民那里并不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而是具有实用性的礼仪规范和价值规范的效力。例如在丝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存有宗教祭祀崇拜活动,而丝路神话正是为这种活动提供了根据和保证。在大量的丝路宗教神话中(包括原始宗教神话),先民们把某种宗教的起源推向荒古,奉为神祖恩赐的法宝,使全体参加祭祀者坚信不疑,并视为求生和发展的根本方法。
原始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①,其基本内涵是用虚妄的认识和行动来满足求食和增殖的需要。神话,正是在原始意识支配下,透过宗教的礼仪来实现原始初民求食和增殖的感情愿望的一种精神纽带。在丝路神话中,这种宗教礼仪主要体现在对诸多神祗的崇拜上。
例如对自然神的崇拜。自然是宗教最原始的对象。在丝路自然神话中,那种原始初民与自然之间既恐惧又依赖的特殊关系,促使西域原始初民根据自身的主观需要来幻化创造出众多的自然神祗,出现了太阳神、月亮神、星辰神、山神、水神、风神、雪神、火神、树神等繁多的崇拜对象。这种对自然神的幻化和崇拜,来自功利的需要,即把自身恐惧和依赖的感情寄托在对人类生活关系重大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身上。对“火”的崇拜,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火,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可以把生食变成熟食,可以防止野兽的袭击,而火的明灭,火焰的曳动,又最容易激起人们的神秘感。依赖感和神秘感相结合,乃把火现为具有特殊力量的神,并因此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崇拜仪式和礼俗。在哈萨克神话、柯尔克孜神话、塔吉克神话中,多处可见“拜火”的遗迹。其目的是用火来保护人类的安全。如,转场时烧两堆火,让畜群从火堆中间穿过,火的熄灭会带来人畜的大量死亡等。这正如希腊语中,“火的熄灭”与“氏族的灭亡”属同一词语一样。
又如对图腾物和始祖神的崇拜。在丝路民族神话中,苍狼崇拜、天鹅崇拜、树崇拜、鹿崇拜、鹰崇拜、冰山崇拜等皆属于此类。丝路原始初民通过对这些动植物图腾物的崇拜,来显示本氏族与某一动植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以解释氏族的来源。如维吾尔族神话,在后世汉文史书的有关记载中,多处有“拜狼纛”、“树狼头纛”、“施金狼头”的记述。这种以动植物为图腾物的始祖崇拜,发展到后来即成为某个氏族民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受到该氏族部落的信仰和膜拜,直至今天,这些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仍成为某些民族坚韧的精神象征。
除此之外,在丝路神话中还有对生殖的崇拜和对英雄神祗及鬼魂的崇拜,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宗教礼仪构成了丝路神话的重要内容和功能。没有对神的崇拜,就没有神话。丝路神话在对神的宗教仪式中产生、流传、发展。没有神的祭坛,便没有丝路的文坛。
丝路神话除了具有神的礼仪性功能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某种法规作用。在西域,远古时期并无法律,也没有专设的法律执行机构。而神话往往在人们发生诉讼时,由神祗来法定曲直,起到一种法规作用。另外,那时的原始初民也不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价值观念,以神的名义起誓,就是行为的最高约束力量。这样,丝路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对建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规范行为准则,保护氏族部落神主的尊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力。最后,丝路神话还具有加强西域各氏族部落内部凝聚力,组成有力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突出作用。
其三,操作性功能。从本质上讲,丝路神话在西域原始初民手中显示出一种巫术的实践力量。在洪水、干早、地震、瘟疫等灾害面前,他们根据神话的启示,祈求神灵保佑,以消灾除难。例如,哈萨克神话中记述的求雨仪式“塔萨特克”。干早季节在河边,人们聚集在一起,向腾格里宰牲祭祀,祈求雨神降雨。后来哈萨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掺入了悬挂《古兰经》,大毛拉念诵求雨的祷文,众人向腾格里和真主叩头祷告等内容。求神驱病的“巴克思跳神”。在哈萨克神话中,萨满教巫师巴克思应邀到病人或显贵人家跳神。巴克思一边弹奏着召唤鬼神的乐曲,一边歌唱祷告腾格里的歌曲;不久,巴克思神情恐怖恍惚,浑身颤抖,围绕火堆边呼唤鬼神之名,边作出和魔鬼搏斗的动作,甚至跳上毡房天窗,或骑马绕毡房奔跑,大喊大叫,最后昏迷倒地;巴克思醒来后向人们诉说自己与神灵见面交谈的经过,以预言未来和消除附依在人身上的鬼怪魂魄。在维吾尔族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情景,如杀羊祭祀雨神亚合提汗、驱鬼祛病的“奥特拉西”等。在塔吉克神话中有祈求神牛,以防地震不测等。在丝路英雄神话中,这种占卜求卦、祭祀神灵的情节更是比比皆是。氏族部落的英雄们,每逢战时高呼神灵的名字,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每逢重大事件之前,他们要观测天气,祭祀神灵,选择吉日,以趋避凶神。综上所述,丝路神话以神灵的神秘力量为中介,调整着原始初民与客观世界的种种不和谐关系,体现着原始艺术所固有的以实用功利为目的的操作性功能。
以上我们对丝路神话的表层功能进行了简明的叙述。从丝路神话在整个丝路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丝路民间文学其他形式的影响角度来看,丝路神话的深层结构功能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大约更为重要。在丝路原始先民的文化中,神话并不是一种单纯想象的虚构物,也不是一些荒谬有趣的故事,而是以原始初民的真实感和神圣感为基础的渗透着独特神话思维的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文化。丝路神话,作为丝路各民族精神植株上开放的第一朵奇葩,它在原始初民心目中的地位虽不及在今天文学艺术园地里那样芳香袭人,但是,在人类艺术漫漫长夜中,它却是露出的第一线曙光。丝路神话以其鲜活瑰丽的原始意象,积淀在后世丝路文化和丝路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深刻地体现出丝路各民族的早期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在长期的承传中,它转化为一系列神话原型和文学母题,形成了丝路各民族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和左右着丝路民族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如果我们展开丝路神话长卷,就会醒目地看到一系列光彩夺目的神话篇章:神奇的迦萨甘创造了天地万物;美丽的天鹅女与年轻的勇士结为伉俪,繁衍了哈萨克部落;英武的乌古斯可汗在苍狼的引导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白雪皑皑的慕士塔格冰峰上,神鹰飞翔,鲁斯塔木之弓化作美丽的彩虹,横跨在天上;顶地球的公牛,稍不留神便山摇地动;太阳与月亮两姐妹在天上相互追逐,戏谑玩耍..透过这种种神话的万花筒,我们不仅观察到丝路各民族的童年,更为重要的是向我们今人提供了一把研究他们现状和未来的金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对丝路神话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纯文学性的研究,乃是对丝路各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的研究——对一种民族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探索。
附注
①摘自《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
①摘自《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
①摘自《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
②摘自《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11章。
②林惠祥:《人类学论著》。
①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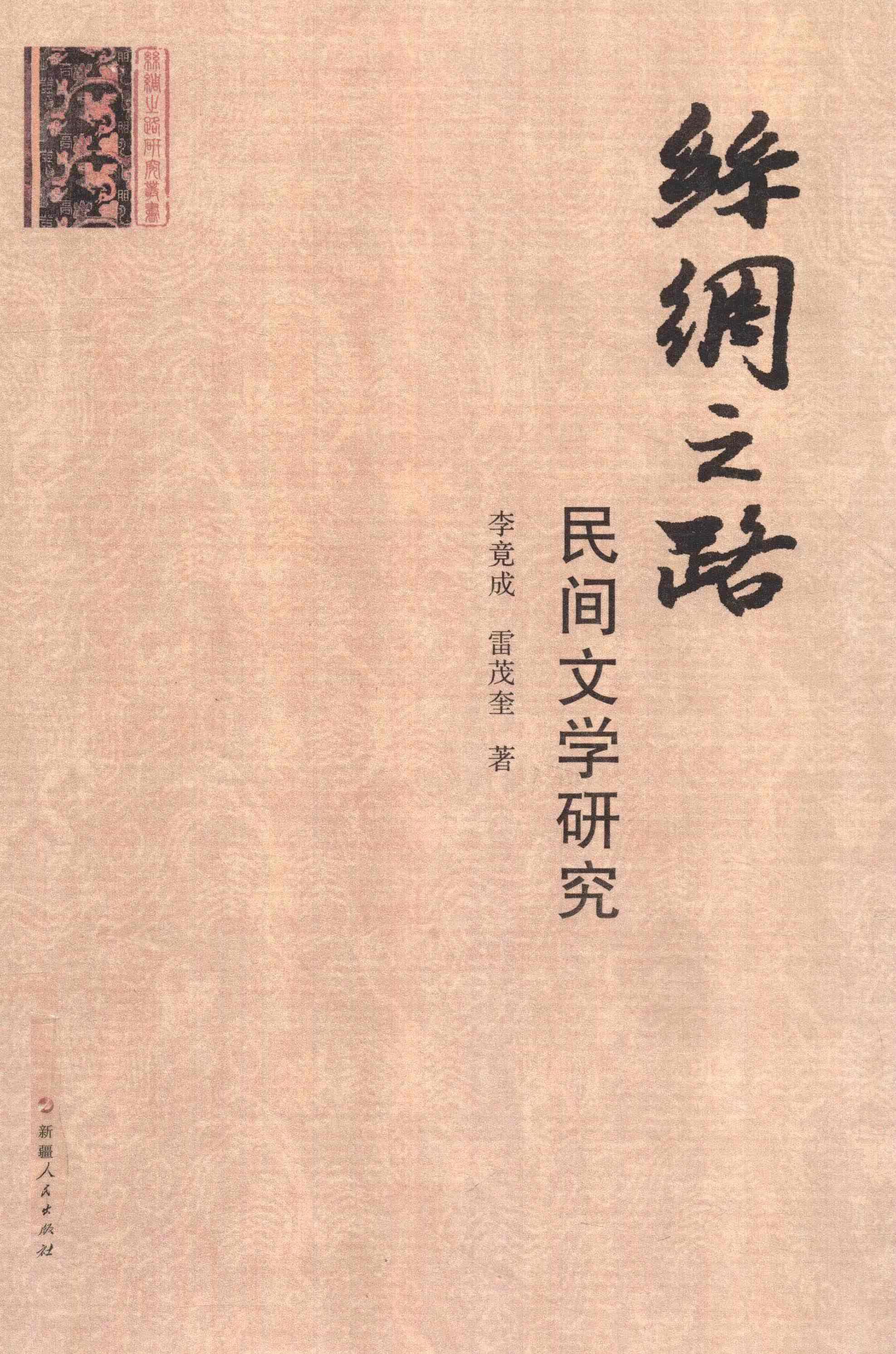
《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民族神话、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丝绸之路民族英雄史诗、丝绸之路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丝绸之路民族民歌、丝绸之路民族民间谚语和谜语等。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