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域文化的分期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274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西域文化的分期 |
| 分类号: | I207.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05-01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纵观西域文化史,史前,为西域文化的生成期;汉唐,为西域文化的发展鼎盛期;宋元明清,为西域文化的曲折发展期。 |
| 关键词: | 民间文学 分期 西域文化 |
内容
纵观西域文化史,史前,为西域文化的生成期;汉唐,为西域文化的发展鼎盛期;宋元明清,为西域文化的曲折发展期。
西域文化的生成期
新石器社会晚期欧亚大陆数百上千年的种族大迁徙,孕育了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塞人文化、乌孙文化、姑师文化是西域史前时期主要的文化形态;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萨满教是西域先民主要的原始宗教文化。
迄今为止,考古学和人类学成果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欧亚大陆上发生了一场种族大迁徙。当时世界上两大游牧文化——雅利安文化和阿勒泰文化,分别从东欧和中亚地区自西向东运动,试图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寻求生命永恒。这场自西向东的种族大迁徙对欧亚大陆诸多文明区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极大的促进。学术界认为,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就孕育在上述人类种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中。当然在这其中,东方的黄河文明对西域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资料考证,西域史前时期的种族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欧洲人种,也有蒙古人种,还有两者的混合性。这些种族发展到后期,主要形成了塞人文化、乌孙文化和姑师文化。在西域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等遗址中,学者们发现这里有早期塞人的遗存物,具有塞人文化的特征;在伊犁地区的夏台、波马、萨尔霍布等墓葬中,有乌孙文化的明显痕迹;在吐鲁番附近的苏巴什、艾丁湖、乌拉泊等墓葬中,又有姑师文化的踪迹。这些西域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种种遗迹说明,西域史前就已有不同种族生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同时,不同种族与周围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又形成了混合型文化的特征。
据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资料,至少在6000年以前,西域就已经存在着原始宗教文化。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以后向人为宗教过渡的萨满教。
远古时期的西域,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惧怕和崇拜,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尤其在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中,广泛存在着对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以及动植物的崇拜。今天我们在大量的民族语言、民俗和历史典籍、考古遗址甚至岩画中,还能看到诸如“腾格里”、祭祀中的“咒语”、“天山”、用兽名纪年等现象。祖先崇拜,在西域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历代相传,在史书中也不乏匈奴人、鲜卑人和突厥可汗祭祀祖先的记载。图腾崇拜,在西域原始初民中普遍地存在着。在《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我们看到在远古昆仑山一带有一个以虎、豹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在今维吾尔史诗《乌古可汗》中,有“苍狼引路”、“公牛腿,狼腰,黑貂肩,熊胸”的乌古可汗的形象,以猛兽为图腾崇拜是远古时期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到了史前晚期,日渐强大的游牧民族虽中心在蒙古高原,但其西翼大部占据天山、阿尔泰山一带,他们与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各民族有密切的联系,这时候萨满教成为他们主要的精神支柱。随着历史的发展,萨满教相继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部落中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
总之,多源头的西域多种族的形成,不同类型的生产生活文化雏形的形成,各个种族原始宗教的生成和演变,这些是西域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
汉唐时期(约公元1世纪~近10世纪)——西域文化的鼎盛期
汉唐千年历史造就了西域文化第一次最具光彩的鼎盛期。“丝绸之路”的凿通、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兴盛,使得西域文化呈现多元化的态势;突厥人从游牧到定居、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西域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自汉至唐近一千年的历史,造就了西域文化叩开文明社会大门后的第一次最具光彩的鼎盛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出使大月氏;汉代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连绵战事,郑吉成为西域第一任都护使;“丝绸之路”的贯通,促使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大交流..这一切促进了当时西域民族文化的空前发展。如,后人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木牍、文书、贝叶经文以及古币上的发现,当时已经使用着多种语言文字,诸如用婆罗迷字母斜体书写的“吐火罗语”、用婆罗迷字母直体书写的“和田塞语”、用阿拉美字母写的“佉卢文”等;在西域的南部和北部出现了定居农耕和游牧并存的经济文化形态。“丝绸之路”把沙漠中的各个绿洲连接贯通,并向东西方延伸,使其经济贸易得以较大的发展;随着汉代军事屯田,中原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传入西域,客观上促使塔里木绿洲诸国的农业发展。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由印度沿“丝绸之路”自南向北传入西域各地。虽然其间与萨满教、祆教等多有抵牾,但到公元4世纪前后,西域佛教的发展已经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域的一些国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各城郭国相互兼并,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在由汉至魏晋到隋唐熠熠闪光的佛教文化时期,西域相继产生了龟兹、于阗、高昌等佛教文化中心。广泛的社会基础,完善的佛教祖师和仪式,加之大法师鸠摩罗什波及中原的广泛影响,佛教文化对此时的西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就艺术而言,于阗热瓦克佛寺佛像造型上的“陀螺”艺术风格透露出源于印度佛教艺术的踪迹;龟兹克孜尔石窟和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佛教壁画,则更多显示出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渐变的多姿多彩;唐朝时期于阗尉迟乙僧父子运用凹凸技法,表现佛教内容和西域人物、花鸟,震惊长安;龟兹乐在唐十部乐中的崇高地位以及西域杰出音乐家苏祗婆音乐理论的创立和传播,使得西域古代乐舞已超越了宗教文化的范围,在中外艺术交流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隋唐时期是西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上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上西域此时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外,西域古代民族的突厥化,也是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此时,西域北部操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并转入定居,逐渐与当地古代先民融合,突厥语逐渐取代了古语,成为当地流行的语言。随着后来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发展,西域各地的文化也逐渐趋向于伊斯兰文化,奠定了近代新疆文化的面貌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域的突厥化,是新疆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隋唐时期正处于这一转折点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在西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回鹘西迁,西域文化进入新时期;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的兴衰更迭,西域文化高潮迭起,曲折发展;新疆建省,西域——新疆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新的历程。
宋元明清时期(约公元10世纪~19世纪中叶)
西域这一时期近千年的历史文化,由于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宋辽金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这一时期是整个西域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从此西域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公元9世纪末,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以西、帕米尔高原以北地区建立了西域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王朝——喀喇汗王朝。据史籍记载,公元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波格拉罕撒图科正式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斯兰汗木萨把伊斯兰教推行到整个汗国,这样自公元9世纪末传入西域的伊斯兰教,成为他们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人以及操突厥语的某些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之,封建制度在汗国内得到普遍确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喀喇汗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广大走向定居的游牧民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这一文化当时最具代表的是马合木提·喀什噶里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
与喀喇汗王朝同时,西迁的回鹘人还建立了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在经济、宗教、文化上采取宽容开放的政策。在现出土的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用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婆罗迷文、藏文、汉文抄录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等的经卷。其中,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被认为是西域戏剧的雏形,在新疆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流行在回鹘民间的散文体史诗《乌古斯可汗》,也在高昌回鹘王国后期经文人加工定型,使其在新疆民间文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重要价值。
12世纪初,女真人耶律大石率部西征,先后降服高昌回鹘王国、东西两部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国,建立起强大的西辽帝国,建都巴拉沙衮。东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喇契丹。耶律大石西征,给西域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对正在封建化的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阿赫玛德·玉格乃克写的神学长诗《真理的入门》在驾驭语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维吾尔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蒙元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12~14世纪的亚洲历史,史称蒙古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了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在这一时期的西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出兵西域,相继灭了西夏、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当时,聚集在天山东段的——畏吾儿人也归顺了蒙古汗。在蒙元时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各种宗教,使得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及道教、天主教在西域流行和发展。同时各个民族多种语言文字也并存着,如操蒙古语的民族使用蒙古文,部分契丹人使用契丹文;操突厥语诸部族依所住地域和信仰宗教的不同,分别使用畏吾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和察合台文;信奉伊斯兰教的操波斯语民族则使用回回文(波斯文),有些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则使用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
总之,这一阶段西域文化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态,同时伊斯兰文明也呈现着从西向东扩张的趋势。
明、清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13世纪中期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察合台汗国”,14世纪中叶汗国分裂,战乱不断。16世纪初“叶尔羌汗国”建立,蒙古部族向农业定居方式过渡,西域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经济开始恢复并向前发展,西域文化也随之复苏发展。这一时期西域文化主要的特征是,由宋辽金时期的突厥文化转入较全面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思想意识、文学艺术。当然,这种影响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原有文化的基质,在新疆近代各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其文化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人文景观。自清初至新疆建省前,清王朝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叛乱、统一新疆、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基本无暇顾及文化。
以上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尔羌汗国的文化史籍。叶尔羌汗国是继喀喇汗王朝之后又一座文化高峰。其文化成就,一是以马黑麻·海答尔·朵豁剌悌的《拉失德史》和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为代表的史学成就;二是以阿曼尼沙汗收集、整理、编创的《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音乐文化成就。这些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对现代维吾尔族和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近代新疆建省后和当代时期(1884~)
1884年(光绪十年),清王朝驱除阿古柏反动势力后,又与俄国交涉收复伊犁,在新疆实行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度,从此“新疆”赫然写在祖国的版图上。19世纪末以后,清王朝在新疆推行一系列文化制度,如在政府各部门推行双语政策,开办新学堂,官修新疆方志等。建省前后,新疆文化主要呈现以下状态:一是伊斯兰教在天山南路进一步发展,当地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藏传佛教的传入,尤其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对厄鲁特蒙古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随着清王朝对新疆的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较前相比汉民族文化大规模进入新疆,在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汉民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
继杨增新、金树仁之后,1933年盛世才上台统治新疆,新疆现代社会文化一度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盛世才以“六大政策”为旗帜,亲俄联共,实施一系列文化建设措施,顺应历史,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如,发展教育,兴办各类学校并吸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创办改版《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各民族的进步报刊;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领导参与成立“反帝会”及民族文化促进会,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起了主导作用。1942年后,盛世才公开投向蒋介石国民党怀抱,反苏反共的文化宣传甚嚣尘上,致使新疆上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蒙上了国民党统治的浓重政治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新疆文化经历了建国初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机构和文化政策的时期。尽管60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逆流,但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文化又迎来了新的文化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期,这给新疆文化的建构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新的繁荣。如,在各个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方面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史诗《玛纳斯》、《江格尔》的出版,给新疆文化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十二木卡姆》的挖掘整理出版和研究,高水平的少数民族音乐歌舞艺术的演出传播,使新疆“歌舞之乡”的美誉传遍国内外;各民族文学、艺术、影视不断发展,产生了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民族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普遍提高;各民族语言文字有了新的发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科技卫生事业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疆的宗教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引导各民族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趋势,呈现着多种宗教并存的人文特色。总之,社会主义新疆的人文呈现着过去任何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新疆各民族文化正在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新疆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新疆当代各民族的文化,正在为实现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而蓬勃向前发展。
从历史的“西域”到当代的“新疆”,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异质文化的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在亚洲中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数千年的进行着,形成了世界多元文化的范本和奇观。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赋予了西域一新疆文化在经历了多种经典文化的筛选和积淀后,越发成熟和自觉。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多元一体的新疆文化必将弘扬源远流长的西域文化传统,创造各民族新的文化奇迹,建设无愧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盛世。
综上所述,西域文化因其汇聚了众多的民族文化、独特多样的地理文化和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与辐射使这儿的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整合,使西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复杂性;开放——交流性;隶属中华大文化的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多元一复杂性特征
西域自古以来聚居众多民族,他们以其独特的民族历史传统和生产方式以及宗教习俗,为自己民族扬起了一面面色彩明丽、富有民族个性的精神文化旗帜。这种个性殊异的民族性,是造就西域多元文化的重要的内部原因,以民间说唱、歌舞为例子。在新疆,你若对某个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生动的理解,莫过于去参加他们的说唱或歌舞表演。在那里,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品格可以得到最形象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如: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汉族的“舞龙”、“跑早船”,回族的“漫花儿”,锡伯族的“舞春”,蒙古族的“那达慕演唱,”柯尔克孜族的“库木孜弹唱”,塔吉克族的“鹰舞”等等。在这些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中,他们在自己民族乐器伴奏中运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形式和舞蹈形式演唱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鲜明的民族文化氛围在熏陶感染着你,同时你又为多样而又精湛的民族艺术感到惊讶和由衷的折服。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使你领略到新疆多元文化的面貌。
特殊的地理文化是形成西域文化多元复杂性的外部条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西域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西域民族独特的生态环境,西域特殊的文化形态首先是西域各民族长期以来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它区别于内地的西域的独特的地理形态和生态空间,决定了西域各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西域各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促成了西域民族中大相径庭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品格。
西域文化源于高山、大漠、绿洲、草原。俯瞰西域,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天山南北两侧,有两条广阔狭长的荒漠草原绿洲带。北疆哈萨克等游牧民族,生存于大山峡谷中,游动于水域草原之间。“草原文化圈”给他们更多的是游动、探索、创造的动力,赋予他们的文化性格是刻苦坚韧、豪迈顽强、慓悍勇敢、充满自由乐观的活力。南疆维吾尔族,经历历代农耕生存方式为主的“绿洲文化”。这种“绿洲文化”使现代人在先辈的坚韧豪爽中增添了活泼幽默,在率真乐观中融入了冷静与机智。
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迫使和某种社会政治历史的缘故,西域不少民族历经民族大迁徙和大征战。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西域不少民族文化在面临民族劫难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运而生或发生变异,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文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西域历史上,游牧与征战始终伴随着柯尔克孜族的形成和发展。史诗《玛纳斯》中所蕴含的深沉悲壮的民族情感所迸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火花,无一不生自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土壤中。八代部落首领英雄家谱史传性的故事,经过“玛纳斯”世世代代的传唱,经过柯尔克孜族英雄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泡、生成、演变、整合,《玛纳斯》呈现出我们今人所看的动态化的活的复杂形态。《玛纳斯》不愧为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典范,不愧为西域古代英雄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时期,西域民族文化呈现出单纯多神崇拜特色。随着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衍变发展,原始多神宗教文化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现代宗教文化。这样,在西域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渗透着浓重宗教气息的西域民族文化势必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多元复杂性。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隶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人的先民,曾经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以后甚至到今天仍保留着该教的残余影响。公元840年回鹘漠北西迁后,同时亦信奉祆教(俗称“拜火教”)。大约公元5世纪前后,道教已在高昌回鹘人中传播,经隋唐直至宋元时期。公元6~7世纪,摩尼教输入当时居住漠北的回鹘部落中,并于公元762年之后成为回鹘的国教。回鹘西迁后当时的龟兹、于阗、高昌一度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公元9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经过长期的传播在15世纪后期取代了上述的各种信仰而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使维吾尔人实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以上这种由多神崇拜到一种信仰的历史事实,使得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相应出现了多元复杂状态。总之,西域文化丰厚的社会、历史、宗教等内涵,程度不同地显示着以一定文化模式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品格。而这种文化模式的更迭与并存,对西域文化的多元、复杂的生存状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域,以生产方式而论,有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等;以自然地域而论,有草原文化、绿洲文化、高原文化、盆地文化等;以民族生成和迁徙而论,有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以语言文字而论,有阿尔泰语系文化、汉藏语系文化、印欧语系文化等;以宗教信仰而论,有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这些多元文化分期地在西域这块神奇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发展,相互冲撞、整合,为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注释。
开放——交流性特征
审视西域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开放性的文化品格。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早期种族迁徙史以及主要地域文明形成的角度去发掘新疆文化形成的动因,就会看到“开放”、“交流”是形成发展西域独特文化形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在新石器社会晚期,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数百上千年的民族大迁徙。其中,东迁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基于地理和民族冲突等原因,分为三支:最北的一支经过贝加尔湖到达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形成了部分坚昆人和鲜卑人的先祖;中间的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一直向东到达敦煌至祁连山之间,成为大月氏的祖先;南路一支因受阻于兴都库什山而向南转移,沿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次大陆,与当地土著人融合,建立了印度文明。另外,属于阿尔泰语系种的游牧文化,以乌拉尔山、阿尔泰山、阴山为东向的起点,各部落不断东迁,构成当今东北亚广大地区民族文化分布格局。东进的游牧文化在陕西一带与中原农耕文化发生冲突而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横贯中国北部乃至朝鲜、日本,形成了阿尔泰绿色草原文化带;南支与当地及百越文化相融,形成了照叶林带文化。后来,历代中国中原汉文化迫于西、北、南文化的包围,东趋大海无望,只得“逐鹿中原”以安天下。这样就架构成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哲学支点。若想统治中国,必先巩固西北,御敌于长城以北,否则便亡国灭种。据此,才有了数代中原王朝的远征匈奴、突厥、吐蕃之战以及“和亲”等诸事。自汉唐以来直至宋元,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把上述的政治、军事方略延伸到经济、文化的领域。“丝绸之路”便生长、繁荣在这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怀抱中。新疆历代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铺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才使其融汇东西南北之长,以特殊诱人的光彩闪烁于世界文化之长河,演奏着令人心醉的乐章。
以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经典代表《十二木卡姆》为例。从音乐民族学角度对“木卡姆”进行一番考察,人们就会发现,西域“木卡姆”的曲调和结构颇似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各国的“努巴”,土耳其的“马卡姆”,伊朗的“达斯特加赫”,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等的“马卡姆”,巴基斯坦的“拉格”,克什米尔“卡拉姆”等。从这种“木卡姆音乐文化”现象,大致能得出以下结论:“木卡姆”音乐流传区域恰恰是前面所述的民族迁徙所经之地,属丝绸之路中西段;流传“木卡姆”的民族基本上属于阿拉伯人、阿尔泰语系民族以及雅利安人的后裔,这些民族大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木卡姆”音乐成熟在伊斯兰音乐的滋养中,其源头是阿尔泰人和雅利安人等游牧民族的音乐文化,成熟在西域农耕文化的氛围中。另外,从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来看,《十二木卡姆》受西域龟兹乐的影响很深。西域龟兹乐西渐,影响着诸如《十二木卡姆》这样的民族音乐精品;东渐,则影响着唐宋之曲,甚至金元戏曲音乐。可以说《十二木卡姆》的音乐形式与中原汉文化中的戏曲音乐形式属同一根系。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西域音乐文化,以其开放的性格,在众多民族匆匆走过的历史长河中,关照到自己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塞种人、匈奴人、突厥人、雅利安人、阿拉伯人等是这一音乐文化忠实的民族载体;阿尔泰语系文化、雅利安文化、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是这一音乐文化热忱的文化载体;“丝绸之路”是这一音乐文化忠于职守的文化地理载体;上古民族的东迁,中古北方民族的西迁是这一音乐文化得以传播的广阔舞台;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东渐是促使这一音乐文化走向成熟的动力机制和历史机遇。
西域文化的这种“开放”品格,还与西域民族特有的经济生活、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有关。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实用功利性的价值取向,粗犷、豪放、直率的民族性格,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凝聚成西域民族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性的心理素质。对待外来文化,显得积极主动、宽容大度,择其优而为我所用。尤其是古代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不断撞击,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一直在促进西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开放的民族性格,使得西域各个民族随时选择适于自己发展的文化因子,使其文化不断得以重构,自古以来西域辉煌的文化基业,正赖于此发展。
在对开放一交流性论述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与此关联的另一个文化特征,这就是断续性。西域文化的断续性自有其成因。一般而论,由于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迁徙频繁,难以及时总结自然斗争、生产斗争经验,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政治统治的不稳定性也难免殃及文化。因此,从纵向看西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程度差异较大,呈现出跳跃性、断续性,难以形成深厚的稳定的文化传统。深入透视,西域文化的这种断续性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缘由。以丝路文化为例。正面看,它促成西域文化的繁荣。负面看,它又带来了西域文化的某个缺憾。简明地说,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冲击过于频繁,致使西域文化和文化史存在着明显的断层,而缺乏应有的积淀。丝路的长期繁荣,使得西域文化的整合造成了困难。许多文化素材被一浪接一浪的文化交流大潮淹没,结果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难以构成文化传统的养料。如前所述,在维吾尔文化史上各种宗教走马灯般轮番登台,频繁的信仰改宗,给维吾尔文化的整合与文化体系的确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其文化史出现了不少断裂。
近现代以来,西域文化基本属于远离高度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的文化。这种“边缘文化”的属性也使西域文化呈现出断续性、落后性的特征。我们不妨再看看历史。自从蒙古人西征和马可·波罗东游之后,贯穿西域的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发生文化交流的大事。随着欧洲各国纷纷改道海上寻求出路,热闹了十几个世纪的丝绸古道终于沉寂了下来,只留下骆驼商队的残骸和被风沙或民族大迁徙浪潮摧毁的故国废墟,供后人凭吊。从此,封闭成了西域文化变奏曲中不和谐的主调。西域文化的隔离机制日益强化,各民族文化得以积累和保存,民族特色愈加鲜明,致使个别地方至今仍存在相当封闭的文化风俗(如有些早已农耕定居的民族在某些地区仍有浓厚的游牧习性)。纵观西域文化发展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开放的文化景观。但丝路的长期繁荣又给古代的新疆文化整合和文化积淀带来了困难。随着古丝路的衰落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西域日益走向封闭。这种西域文化史上的“二律背反”,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困惑和思索。如何跨越自然屏障,弘扬丝路文化传统,重振丝路雄风,开发和建设新疆,使之在未来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重放异彩,这是每个有志之士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隶属中华大文化的一体化特征如前所述,多元发生、多元并存是西域——新疆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机制;开放、交流是其文化传统的主导品格。但总的来说,西域——新疆文化又是整个大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多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
这种多元一体化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域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既有个性,互相区别,又存在着密切联系。从本质上说。西域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彼此孤立的。而且历时愈久,各种文化与西域文化整体的关系也愈加不可分。甚至某种文化实体,如塞人文化、乌孙文化、突厥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消失,也只是形式上的消失,实质上它的各种因素已融入西域——新疆文化的整体之中。这说明西域——新疆文化的多元性是统一的多元性。二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西域——新疆文化又是整个中华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时愈久,联系愈加密切,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倾向愈加明显。
自汉唐以来,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各种交流始终不断。政治上的联姻,军事上的结盟,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交流等等这一切,构成了西域民族文化的主要篇章。回顾历史:汉代张骞奉旨出使西域,架起中外交流的“丝绸之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由长安远嫁西域乌孙,谱写了友谊篇章;郑吉奉诏任西域第一都护,从此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东晋法显和唐玄奘经西域到印度求取佛法,撰写《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到中原翻译传播大乘经典,弘扬佛法;尉迟乙僧父子人物画技法传入中原,引起轰动;苏祗婆西域乐舞在长安献艺,丰富了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宝库;清禁烟英雄林则徐遣戍新疆,为各族儿女屯垦戍边做好事;左宗棠率军进疆平叛退敌,使新疆回到祖国的怀抱..以上这些西域与中原交流的佳话,旨在说明,自古以来西域文化就与中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种连绵不绝的双向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趋同的文化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民族平等的祖国大家庭里,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和方向,新疆文化在中华大文化格局中更有向心力、亲和力和凝聚力。中华文化的共性与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富有个性的文化并不相悖,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也因其众多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蕴涵而显示出博大深厚的风采。
西域文化的生成期
新石器社会晚期欧亚大陆数百上千年的种族大迁徙,孕育了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塞人文化、乌孙文化、姑师文化是西域史前时期主要的文化形态;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萨满教是西域先民主要的原始宗教文化。
迄今为止,考古学和人类学成果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欧亚大陆上发生了一场种族大迁徙。当时世界上两大游牧文化——雅利安文化和阿勒泰文化,分别从东欧和中亚地区自西向东运动,试图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寻求生命永恒。这场自西向东的种族大迁徙对欧亚大陆诸多文明区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极大的促进。学术界认为,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就孕育在上述人类种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中。当然在这其中,东方的黄河文明对西域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资料考证,西域史前时期的种族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欧洲人种,也有蒙古人种,还有两者的混合性。这些种族发展到后期,主要形成了塞人文化、乌孙文化和姑师文化。在西域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等遗址中,学者们发现这里有早期塞人的遗存物,具有塞人文化的特征;在伊犁地区的夏台、波马、萨尔霍布等墓葬中,有乌孙文化的明显痕迹;在吐鲁番附近的苏巴什、艾丁湖、乌拉泊等墓葬中,又有姑师文化的踪迹。这些西域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种种遗迹说明,西域史前就已有不同种族生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同时,不同种族与周围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又形成了混合型文化的特征。
据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资料,至少在6000年以前,西域就已经存在着原始宗教文化。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以后向人为宗教过渡的萨满教。
远古时期的西域,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惧怕和崇拜,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尤其在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中,广泛存在着对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以及动植物的崇拜。今天我们在大量的民族语言、民俗和历史典籍、考古遗址甚至岩画中,还能看到诸如“腾格里”、祭祀中的“咒语”、“天山”、用兽名纪年等现象。祖先崇拜,在西域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历代相传,在史书中也不乏匈奴人、鲜卑人和突厥可汗祭祀祖先的记载。图腾崇拜,在西域原始初民中普遍地存在着。在《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我们看到在远古昆仑山一带有一个以虎、豹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在今维吾尔史诗《乌古可汗》中,有“苍狼引路”、“公牛腿,狼腰,黑貂肩,熊胸”的乌古可汗的形象,以猛兽为图腾崇拜是远古时期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到了史前晚期,日渐强大的游牧民族虽中心在蒙古高原,但其西翼大部占据天山、阿尔泰山一带,他们与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各民族有密切的联系,这时候萨满教成为他们主要的精神支柱。随着历史的发展,萨满教相继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部落中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
总之,多源头的西域多种族的形成,不同类型的生产生活文化雏形的形成,各个种族原始宗教的生成和演变,这些是西域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
汉唐时期(约公元1世纪~近10世纪)——西域文化的鼎盛期
汉唐千年历史造就了西域文化第一次最具光彩的鼎盛期。“丝绸之路”的凿通、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兴盛,使得西域文化呈现多元化的态势;突厥人从游牧到定居、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西域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自汉至唐近一千年的历史,造就了西域文化叩开文明社会大门后的第一次最具光彩的鼎盛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出使大月氏;汉代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连绵战事,郑吉成为西域第一任都护使;“丝绸之路”的贯通,促使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大交流..这一切促进了当时西域民族文化的空前发展。如,后人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木牍、文书、贝叶经文以及古币上的发现,当时已经使用着多种语言文字,诸如用婆罗迷字母斜体书写的“吐火罗语”、用婆罗迷字母直体书写的“和田塞语”、用阿拉美字母写的“佉卢文”等;在西域的南部和北部出现了定居农耕和游牧并存的经济文化形态。“丝绸之路”把沙漠中的各个绿洲连接贯通,并向东西方延伸,使其经济贸易得以较大的发展;随着汉代军事屯田,中原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传入西域,客观上促使塔里木绿洲诸国的农业发展。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由印度沿“丝绸之路”自南向北传入西域各地。虽然其间与萨满教、祆教等多有抵牾,但到公元4世纪前后,西域佛教的发展已经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域的一些国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各城郭国相互兼并,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在由汉至魏晋到隋唐熠熠闪光的佛教文化时期,西域相继产生了龟兹、于阗、高昌等佛教文化中心。广泛的社会基础,完善的佛教祖师和仪式,加之大法师鸠摩罗什波及中原的广泛影响,佛教文化对此时的西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就艺术而言,于阗热瓦克佛寺佛像造型上的“陀螺”艺术风格透露出源于印度佛教艺术的踪迹;龟兹克孜尔石窟和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佛教壁画,则更多显示出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渐变的多姿多彩;唐朝时期于阗尉迟乙僧父子运用凹凸技法,表现佛教内容和西域人物、花鸟,震惊长安;龟兹乐在唐十部乐中的崇高地位以及西域杰出音乐家苏祗婆音乐理论的创立和传播,使得西域古代乐舞已超越了宗教文化的范围,在中外艺术交流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隋唐时期是西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上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上西域此时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外,西域古代民族的突厥化,也是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此时,西域北部操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并转入定居,逐渐与当地古代先民融合,突厥语逐渐取代了古语,成为当地流行的语言。随着后来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发展,西域各地的文化也逐渐趋向于伊斯兰文化,奠定了近代新疆文化的面貌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域的突厥化,是新疆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隋唐时期正处于这一转折点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在西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回鹘西迁,西域文化进入新时期;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的兴衰更迭,西域文化高潮迭起,曲折发展;新疆建省,西域——新疆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新的历程。
宋元明清时期(约公元10世纪~19世纪中叶)
西域这一时期近千年的历史文化,由于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宋辽金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这一时期是整个西域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从此西域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公元9世纪末,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以西、帕米尔高原以北地区建立了西域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王朝——喀喇汗王朝。据史籍记载,公元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波格拉罕撒图科正式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斯兰汗木萨把伊斯兰教推行到整个汗国,这样自公元9世纪末传入西域的伊斯兰教,成为他们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人以及操突厥语的某些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之,封建制度在汗国内得到普遍确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喀喇汗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广大走向定居的游牧民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这一文化当时最具代表的是马合木提·喀什噶里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
与喀喇汗王朝同时,西迁的回鹘人还建立了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在经济、宗教、文化上采取宽容开放的政策。在现出土的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用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婆罗迷文、藏文、汉文抄录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等的经卷。其中,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被认为是西域戏剧的雏形,在新疆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流行在回鹘民间的散文体史诗《乌古斯可汗》,也在高昌回鹘王国后期经文人加工定型,使其在新疆民间文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重要价值。
12世纪初,女真人耶律大石率部西征,先后降服高昌回鹘王国、东西两部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国,建立起强大的西辽帝国,建都巴拉沙衮。东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喇契丹。耶律大石西征,给西域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对正在封建化的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阿赫玛德·玉格乃克写的神学长诗《真理的入门》在驾驭语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维吾尔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蒙元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12~14世纪的亚洲历史,史称蒙古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了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在这一时期的西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出兵西域,相继灭了西夏、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当时,聚集在天山东段的——畏吾儿人也归顺了蒙古汗。在蒙元时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各种宗教,使得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及道教、天主教在西域流行和发展。同时各个民族多种语言文字也并存着,如操蒙古语的民族使用蒙古文,部分契丹人使用契丹文;操突厥语诸部族依所住地域和信仰宗教的不同,分别使用畏吾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和察合台文;信奉伊斯兰教的操波斯语民族则使用回回文(波斯文),有些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则使用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
总之,这一阶段西域文化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态,同时伊斯兰文明也呈现着从西向东扩张的趋势。
明、清历史阶段的西域文化
13世纪中期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察合台汗国”,14世纪中叶汗国分裂,战乱不断。16世纪初“叶尔羌汗国”建立,蒙古部族向农业定居方式过渡,西域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经济开始恢复并向前发展,西域文化也随之复苏发展。这一时期西域文化主要的特征是,由宋辽金时期的突厥文化转入较全面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思想意识、文学艺术。当然,这种影响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原有文化的基质,在新疆近代各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其文化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人文景观。自清初至新疆建省前,清王朝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叛乱、统一新疆、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基本无暇顾及文化。
以上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尔羌汗国的文化史籍。叶尔羌汗国是继喀喇汗王朝之后又一座文化高峰。其文化成就,一是以马黑麻·海答尔·朵豁剌悌的《拉失德史》和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为代表的史学成就;二是以阿曼尼沙汗收集、整理、编创的《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音乐文化成就。这些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对现代维吾尔族和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近代新疆建省后和当代时期(1884~)
1884年(光绪十年),清王朝驱除阿古柏反动势力后,又与俄国交涉收复伊犁,在新疆实行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度,从此“新疆”赫然写在祖国的版图上。19世纪末以后,清王朝在新疆推行一系列文化制度,如在政府各部门推行双语政策,开办新学堂,官修新疆方志等。建省前后,新疆文化主要呈现以下状态:一是伊斯兰教在天山南路进一步发展,当地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藏传佛教的传入,尤其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对厄鲁特蒙古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随着清王朝对新疆的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较前相比汉民族文化大规模进入新疆,在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汉民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
继杨增新、金树仁之后,1933年盛世才上台统治新疆,新疆现代社会文化一度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盛世才以“六大政策”为旗帜,亲俄联共,实施一系列文化建设措施,顺应历史,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如,发展教育,兴办各类学校并吸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创办改版《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各民族的进步报刊;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领导参与成立“反帝会”及民族文化促进会,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起了主导作用。1942年后,盛世才公开投向蒋介石国民党怀抱,反苏反共的文化宣传甚嚣尘上,致使新疆上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蒙上了国民党统治的浓重政治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新疆文化经历了建国初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机构和文化政策的时期。尽管60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逆流,但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文化又迎来了新的文化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期,这给新疆文化的建构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新的繁荣。如,在各个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方面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史诗《玛纳斯》、《江格尔》的出版,给新疆文化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十二木卡姆》的挖掘整理出版和研究,高水平的少数民族音乐歌舞艺术的演出传播,使新疆“歌舞之乡”的美誉传遍国内外;各民族文学、艺术、影视不断发展,产生了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民族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普遍提高;各民族语言文字有了新的发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科技卫生事业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疆的宗教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引导各民族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趋势,呈现着多种宗教并存的人文特色。总之,社会主义新疆的人文呈现着过去任何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新疆各民族文化正在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新疆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新疆当代各民族的文化,正在为实现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而蓬勃向前发展。
从历史的“西域”到当代的“新疆”,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异质文化的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在亚洲中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数千年的进行着,形成了世界多元文化的范本和奇观。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赋予了西域一新疆文化在经历了多种经典文化的筛选和积淀后,越发成熟和自觉。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多元一体的新疆文化必将弘扬源远流长的西域文化传统,创造各民族新的文化奇迹,建设无愧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盛世。
综上所述,西域文化因其汇聚了众多的民族文化、独特多样的地理文化和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与辐射使这儿的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整合,使西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复杂性;开放——交流性;隶属中华大文化的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多元一复杂性特征
西域自古以来聚居众多民族,他们以其独特的民族历史传统和生产方式以及宗教习俗,为自己民族扬起了一面面色彩明丽、富有民族个性的精神文化旗帜。这种个性殊异的民族性,是造就西域多元文化的重要的内部原因,以民间说唱、歌舞为例子。在新疆,你若对某个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生动的理解,莫过于去参加他们的说唱或歌舞表演。在那里,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品格可以得到最形象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如: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汉族的“舞龙”、“跑早船”,回族的“漫花儿”,锡伯族的“舞春”,蒙古族的“那达慕演唱,”柯尔克孜族的“库木孜弹唱”,塔吉克族的“鹰舞”等等。在这些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中,他们在自己民族乐器伴奏中运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形式和舞蹈形式演唱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鲜明的民族文化氛围在熏陶感染着你,同时你又为多样而又精湛的民族艺术感到惊讶和由衷的折服。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使你领略到新疆多元文化的面貌。
特殊的地理文化是形成西域文化多元复杂性的外部条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西域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西域民族独特的生态环境,西域特殊的文化形态首先是西域各民族长期以来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它区别于内地的西域的独特的地理形态和生态空间,决定了西域各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西域各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促成了西域民族中大相径庭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品格。
西域文化源于高山、大漠、绿洲、草原。俯瞰西域,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天山南北两侧,有两条广阔狭长的荒漠草原绿洲带。北疆哈萨克等游牧民族,生存于大山峡谷中,游动于水域草原之间。“草原文化圈”给他们更多的是游动、探索、创造的动力,赋予他们的文化性格是刻苦坚韧、豪迈顽强、慓悍勇敢、充满自由乐观的活力。南疆维吾尔族,经历历代农耕生存方式为主的“绿洲文化”。这种“绿洲文化”使现代人在先辈的坚韧豪爽中增添了活泼幽默,在率真乐观中融入了冷静与机智。
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迫使和某种社会政治历史的缘故,西域不少民族历经民族大迁徙和大征战。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西域不少民族文化在面临民族劫难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运而生或发生变异,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文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西域历史上,游牧与征战始终伴随着柯尔克孜族的形成和发展。史诗《玛纳斯》中所蕴含的深沉悲壮的民族情感所迸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火花,无一不生自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土壤中。八代部落首领英雄家谱史传性的故事,经过“玛纳斯”世世代代的传唱,经过柯尔克孜族英雄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泡、生成、演变、整合,《玛纳斯》呈现出我们今人所看的动态化的活的复杂形态。《玛纳斯》不愧为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典范,不愧为西域古代英雄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时期,西域民族文化呈现出单纯多神崇拜特色。随着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衍变发展,原始多神宗教文化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现代宗教文化。这样,在西域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渗透着浓重宗教气息的西域民族文化势必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多元复杂性。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隶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人的先民,曾经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以后甚至到今天仍保留着该教的残余影响。公元840年回鹘漠北西迁后,同时亦信奉祆教(俗称“拜火教”)。大约公元5世纪前后,道教已在高昌回鹘人中传播,经隋唐直至宋元时期。公元6~7世纪,摩尼教输入当时居住漠北的回鹘部落中,并于公元762年之后成为回鹘的国教。回鹘西迁后当时的龟兹、于阗、高昌一度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公元9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经过长期的传播在15世纪后期取代了上述的各种信仰而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使维吾尔人实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以上这种由多神崇拜到一种信仰的历史事实,使得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相应出现了多元复杂状态。总之,西域文化丰厚的社会、历史、宗教等内涵,程度不同地显示着以一定文化模式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品格。而这种文化模式的更迭与并存,对西域文化的多元、复杂的生存状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域,以生产方式而论,有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等;以自然地域而论,有草原文化、绿洲文化、高原文化、盆地文化等;以民族生成和迁徙而论,有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以语言文字而论,有阿尔泰语系文化、汉藏语系文化、印欧语系文化等;以宗教信仰而论,有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这些多元文化分期地在西域这块神奇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发展,相互冲撞、整合,为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注释。
开放——交流性特征
审视西域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开放性的文化品格。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早期种族迁徙史以及主要地域文明形成的角度去发掘新疆文化形成的动因,就会看到“开放”、“交流”是形成发展西域独特文化形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在新石器社会晚期,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数百上千年的民族大迁徙。其中,东迁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基于地理和民族冲突等原因,分为三支:最北的一支经过贝加尔湖到达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形成了部分坚昆人和鲜卑人的先祖;中间的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一直向东到达敦煌至祁连山之间,成为大月氏的祖先;南路一支因受阻于兴都库什山而向南转移,沿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次大陆,与当地土著人融合,建立了印度文明。另外,属于阿尔泰语系种的游牧文化,以乌拉尔山、阿尔泰山、阴山为东向的起点,各部落不断东迁,构成当今东北亚广大地区民族文化分布格局。东进的游牧文化在陕西一带与中原农耕文化发生冲突而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横贯中国北部乃至朝鲜、日本,形成了阿尔泰绿色草原文化带;南支与当地及百越文化相融,形成了照叶林带文化。后来,历代中国中原汉文化迫于西、北、南文化的包围,东趋大海无望,只得“逐鹿中原”以安天下。这样就架构成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哲学支点。若想统治中国,必先巩固西北,御敌于长城以北,否则便亡国灭种。据此,才有了数代中原王朝的远征匈奴、突厥、吐蕃之战以及“和亲”等诸事。自汉唐以来直至宋元,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把上述的政治、军事方略延伸到经济、文化的领域。“丝绸之路”便生长、繁荣在这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怀抱中。新疆历代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铺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才使其融汇东西南北之长,以特殊诱人的光彩闪烁于世界文化之长河,演奏着令人心醉的乐章。
以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经典代表《十二木卡姆》为例。从音乐民族学角度对“木卡姆”进行一番考察,人们就会发现,西域“木卡姆”的曲调和结构颇似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各国的“努巴”,土耳其的“马卡姆”,伊朗的“达斯特加赫”,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等的“马卡姆”,巴基斯坦的“拉格”,克什米尔“卡拉姆”等。从这种“木卡姆音乐文化”现象,大致能得出以下结论:“木卡姆”音乐流传区域恰恰是前面所述的民族迁徙所经之地,属丝绸之路中西段;流传“木卡姆”的民族基本上属于阿拉伯人、阿尔泰语系民族以及雅利安人的后裔,这些民族大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木卡姆”音乐成熟在伊斯兰音乐的滋养中,其源头是阿尔泰人和雅利安人等游牧民族的音乐文化,成熟在西域农耕文化的氛围中。另外,从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来看,《十二木卡姆》受西域龟兹乐的影响很深。西域龟兹乐西渐,影响着诸如《十二木卡姆》这样的民族音乐精品;东渐,则影响着唐宋之曲,甚至金元戏曲音乐。可以说《十二木卡姆》的音乐形式与中原汉文化中的戏曲音乐形式属同一根系。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西域音乐文化,以其开放的性格,在众多民族匆匆走过的历史长河中,关照到自己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塞种人、匈奴人、突厥人、雅利安人、阿拉伯人等是这一音乐文化忠实的民族载体;阿尔泰语系文化、雅利安文化、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是这一音乐文化热忱的文化载体;“丝绸之路”是这一音乐文化忠于职守的文化地理载体;上古民族的东迁,中古北方民族的西迁是这一音乐文化得以传播的广阔舞台;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东渐是促使这一音乐文化走向成熟的动力机制和历史机遇。
西域文化的这种“开放”品格,还与西域民族特有的经济生活、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有关。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实用功利性的价值取向,粗犷、豪放、直率的民族性格,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凝聚成西域民族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性的心理素质。对待外来文化,显得积极主动、宽容大度,择其优而为我所用。尤其是古代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不断撞击,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一直在促进西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开放的民族性格,使得西域各个民族随时选择适于自己发展的文化因子,使其文化不断得以重构,自古以来西域辉煌的文化基业,正赖于此发展。
在对开放一交流性论述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与此关联的另一个文化特征,这就是断续性。西域文化的断续性自有其成因。一般而论,由于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迁徙频繁,难以及时总结自然斗争、生产斗争经验,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政治统治的不稳定性也难免殃及文化。因此,从纵向看西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程度差异较大,呈现出跳跃性、断续性,难以形成深厚的稳定的文化传统。深入透视,西域文化的这种断续性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缘由。以丝路文化为例。正面看,它促成西域文化的繁荣。负面看,它又带来了西域文化的某个缺憾。简明地说,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冲击过于频繁,致使西域文化和文化史存在着明显的断层,而缺乏应有的积淀。丝路的长期繁荣,使得西域文化的整合造成了困难。许多文化素材被一浪接一浪的文化交流大潮淹没,结果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难以构成文化传统的养料。如前所述,在维吾尔文化史上各种宗教走马灯般轮番登台,频繁的信仰改宗,给维吾尔文化的整合与文化体系的确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其文化史出现了不少断裂。
近现代以来,西域文化基本属于远离高度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的文化。这种“边缘文化”的属性也使西域文化呈现出断续性、落后性的特征。我们不妨再看看历史。自从蒙古人西征和马可·波罗东游之后,贯穿西域的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发生文化交流的大事。随着欧洲各国纷纷改道海上寻求出路,热闹了十几个世纪的丝绸古道终于沉寂了下来,只留下骆驼商队的残骸和被风沙或民族大迁徙浪潮摧毁的故国废墟,供后人凭吊。从此,封闭成了西域文化变奏曲中不和谐的主调。西域文化的隔离机制日益强化,各民族文化得以积累和保存,民族特色愈加鲜明,致使个别地方至今仍存在相当封闭的文化风俗(如有些早已农耕定居的民族在某些地区仍有浓厚的游牧习性)。纵观西域文化发展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开放的文化景观。但丝路的长期繁荣又给古代的新疆文化整合和文化积淀带来了困难。随着古丝路的衰落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西域日益走向封闭。这种西域文化史上的“二律背反”,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困惑和思索。如何跨越自然屏障,弘扬丝路文化传统,重振丝路雄风,开发和建设新疆,使之在未来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重放异彩,这是每个有志之士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隶属中华大文化的一体化特征如前所述,多元发生、多元并存是西域——新疆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机制;开放、交流是其文化传统的主导品格。但总的来说,西域——新疆文化又是整个大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多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
这种多元一体化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域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既有个性,互相区别,又存在着密切联系。从本质上说。西域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彼此孤立的。而且历时愈久,各种文化与西域文化整体的关系也愈加不可分。甚至某种文化实体,如塞人文化、乌孙文化、突厥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消失,也只是形式上的消失,实质上它的各种因素已融入西域——新疆文化的整体之中。这说明西域——新疆文化的多元性是统一的多元性。二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西域——新疆文化又是整个中华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时愈久,联系愈加密切,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倾向愈加明显。
自汉唐以来,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各种交流始终不断。政治上的联姻,军事上的结盟,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交流等等这一切,构成了西域民族文化的主要篇章。回顾历史:汉代张骞奉旨出使西域,架起中外交流的“丝绸之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由长安远嫁西域乌孙,谱写了友谊篇章;郑吉奉诏任西域第一都护,从此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东晋法显和唐玄奘经西域到印度求取佛法,撰写《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到中原翻译传播大乘经典,弘扬佛法;尉迟乙僧父子人物画技法传入中原,引起轰动;苏祗婆西域乐舞在长安献艺,丰富了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宝库;清禁烟英雄林则徐遣戍新疆,为各族儿女屯垦戍边做好事;左宗棠率军进疆平叛退敌,使新疆回到祖国的怀抱..以上这些西域与中原交流的佳话,旨在说明,自古以来西域文化就与中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种连绵不绝的双向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趋同的文化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民族平等的祖国大家庭里,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和方向,新疆文化在中华大文化格局中更有向心力、亲和力和凝聚力。中华文化的共性与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富有个性的文化并不相悖,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也因其众多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蕴涵而显示出博大深厚的风采。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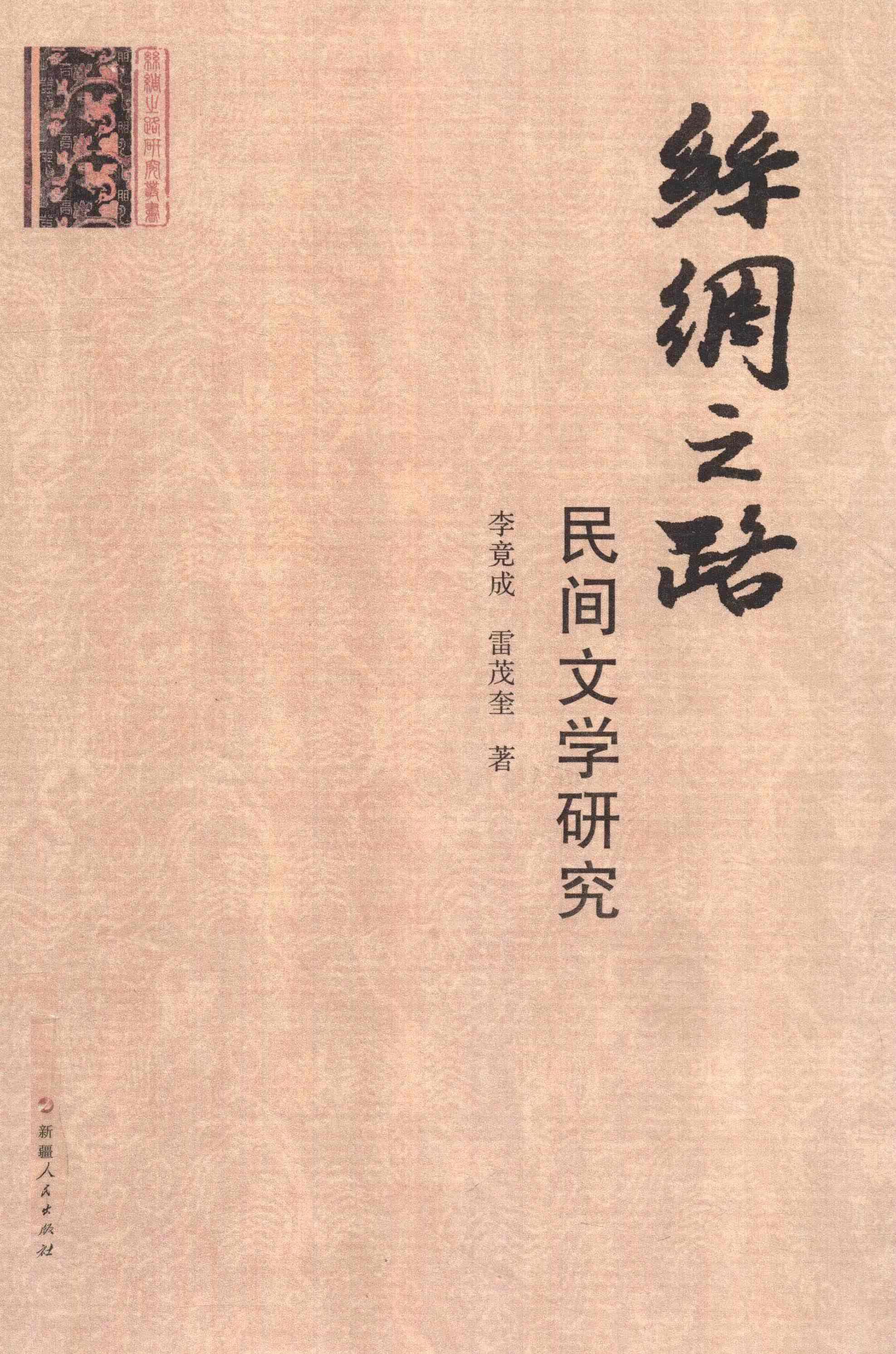
《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民族神话、丝绸之路民族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丝绸之路民族英雄史诗、丝绸之路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丝绸之路民族民歌、丝绸之路民族民间谚语和谜语等。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