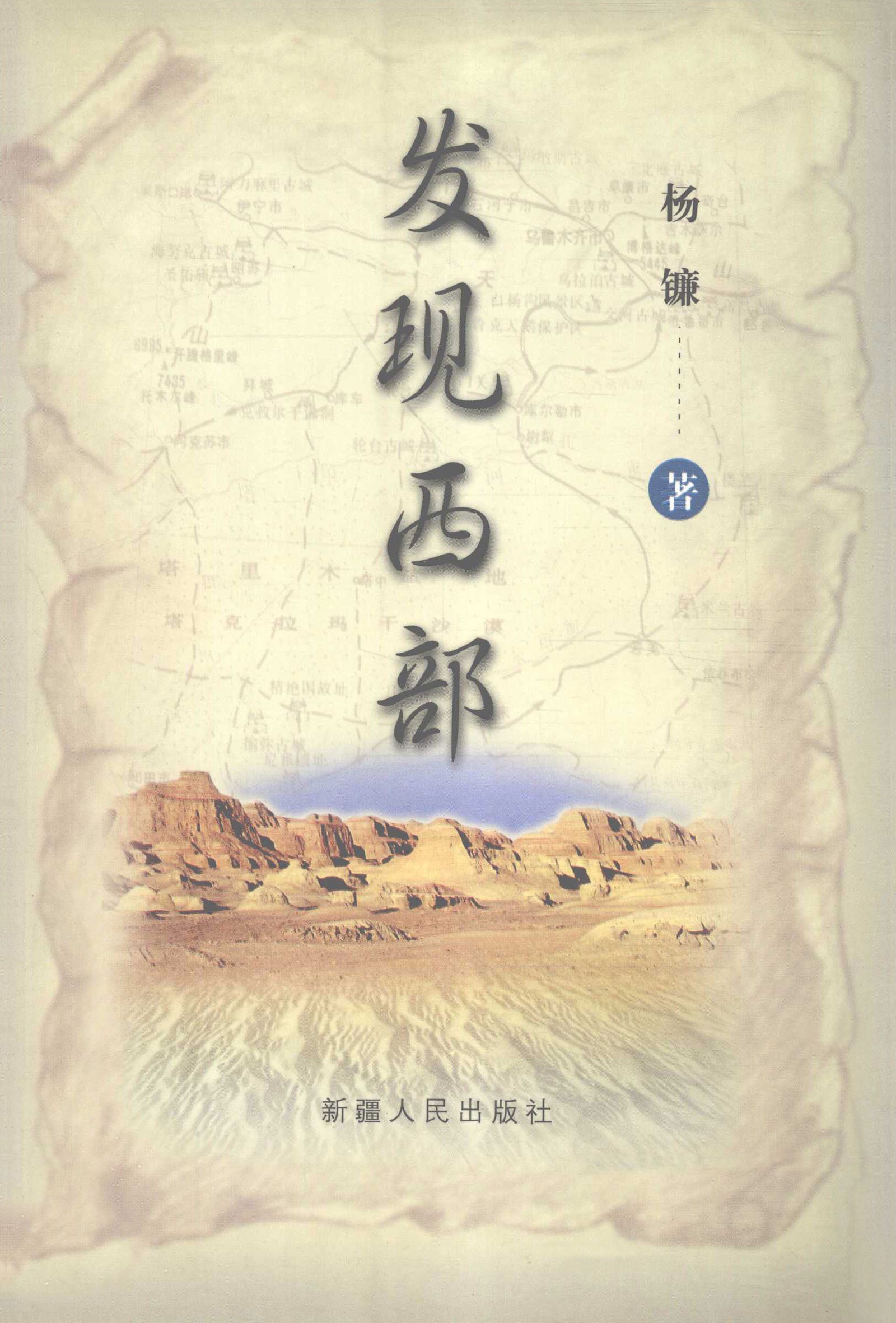四
| 内容出处: | 《发现西部》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69813 |
| 颗粒名称: | 四 |
| 分类号: | F426;F127;I267 |
| 页数: | 8 |
| 页码: | 16-23 |
| 摘要: |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斯文·赫定所写的游记和他的探险活动本身具有大致相当的知名度。比如他专门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在二三十年代是最有影响的科学普及读物,很快就译成一二十种文字,中国曾有李述礼、孙仲宽两个译本,而李述礼译本自1934年初版,到80年代,在大陆及台湾重印了数十次,仅上海书店1984年8月,一次就印了1.5万册。《马仲英逃亡记》于1987年译成中文出版,很快又译成维吾尔文出版,汉、维两种文本共印2.5万余册,在当前的同类著作中,其印数是相当大的。 |
| 关键词: | 第三卷 马仲英 罗布泊 盛世才 乌鲁木齐 |
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斯文·赫定所写的游记和他的探险活动本身具有大致相当的知名度。比如他专门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在二三十年代是最有影响的科学普及读物,很快就译成一二十种文字,中国曾有李述礼、孙仲宽两个译本,而李述礼译本自1934年初版,到80年代,在大陆及台湾重印了数十次,仅上海书店1984年8月,一次就印了1.5万册。《马仲英逃亡记》于1987年译成中文出版,很快又译成维吾尔文出版,汉、维两种文本共印2.5万余册,在当前的同类著作中,其印数是相当大的。他的书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比如有一篇评论青年作家马原的文章就指出:马原受到斯文·赫定的明显影响,而《亚洲腹地旅行记》是马原最爱读的书籍之一。
斯文·赫定的旅行记受到欢迎,当然首先取决于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笔下涉及的内容往往是独家的,你在别处是无法获悉的。另外,他也是颇具文学才能的人,其游记一向以文字形象、生动,充满人情味而著称。他写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在坎坷旅途中不论条件多么恶劣,他总是坚持当天记下观感,甚至在骑骆驼的行程当中,他也能一边作地图测绘,一边写笔记。所以,他的游记往往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并使读者能领略到他的呼吸和脉搏,仿佛正与他共同跋涉在漫漫长途中,其感染力与穿透力是一致公认的。而这些特点,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由于其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其眼界与同时代人绝不重复,使《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成为描写1927~1935年中国(主要是西部地区)无可替代的作品,书中许多形象具体的画面都是可贵的历史资料。
在这八年当中,斯文·赫定活动的地域跨度相当大,结识的人物品级相当杂。他笔下的人物上至当时中国的执政者如蒋介石、汪精卫,下至西部的流浪汉、乞丐。他曾为蒙古王公、班禅活佛、外蒙古难民团领袖、一般的喇嘛、额济纳及和静的土尔扈特王爷、被革出教门放逐到居延的藏族释子、西部的土匪、罗布人的后裔、已成为“归化族”的白俄、仆役等许多人物留下了一幅幅准确、客观、栩栩如生的“画像”。在第三卷中,他写到与当时新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交往,比如盛世才、马仲英、神秘的“李教授”、土耳其人凯末尔、“哈密虎”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土尔扈特最后一位领主满楚克札布、马虎山、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两个来历不明的波兰人等等,无一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着墨不多,但马仲英的狂妄与天真、盛世才的阴鸷与权术、尧乐博斯的圆滑世故,都达到呼之欲出的地步。斯文·赫定在吐鲁番曾多次见到了自称是“李教授”的神秘人物,他一眼就看穿了李的伪装,并写道:李教授和他的四个学生“说他们想在新疆呆五年,研究地方语言文学。新疆的语言文学”!描写既有分寸又有洞察力,其实从一见面他就认定此人是负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人。在吐鲁番结识的另一个奇人是马仲英身边的“范增”——凯末尔·卡雅阿凡提。这位“亚父”是土耳其人,在有些书中,他是相当神秘莫测的人,但斯文·赫定却在“生日宴会”一节(卷三第五章),捕捉到了凯末尔的乡愁,使他还原为一个一事无成、流落他乡的说客,其身上的外衣被无形中剥脱干净。在“焉耆的土尔扈特亲王”一节(卷三第八章)中,写到与满汗王的短暂会晤,由于满汗王的叔叔多布顿活佛与考察团早有交往,与期文·赫定也有私交,所以赫定对满汗王很感兴趣。但他很快就觉察到:一、满汗王对其已故叔父有特殊的反感;二、满汗王“权力太有限了”,不是名副其实的封建领主。熟悉新疆现代史的人,当然都知道这是十分准确的概括。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文·赫定被拘于乌鲁木齐时,在一次运动会上见到了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在“运动会”一节(卷三第九章)中所写到的和加尼牙孜,只用几笔简练的勾勒,就凸现出其神态、为人,其处境及内心的矛盾,真把这个当年反政府的英雄,当时名义的“座上客”、实际的“阶下囚”的故作镇静与自持所掩盖的虚弱和高度紧张,原原本本地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斯文·赫定笔下,这位当年一呼百应,被很多人寄以厚望的人已经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他的彻底销声匿迹是指日可待了。
除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写也是相当成功,颇具吸引力的。
斯文·赫定两次来新疆:1928年与1934年,都是新疆现代史的重大转折时刻。当1928年考察团在乌鲁木齐时,发生了督军杨增新被刺事件。随着金树仁的上台,新疆现代史的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了,而陷入了连年的内战。当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达到关键时刻,即胜负将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对其在乌鲁木齐所经历的一切,都作了客观、忠实的记述。
通过斯文·赫定的描写,再现了“高度自治”前的内蒙古各界人物及山川风物,刻画了大乱将起、危机四伏的乌鲁木齐政界,揭示了觥筹交错掩盖下的明争暗斗,突出了马仲英建立“图兰”伊斯兰国梦想的破灭,感传了“四·一二”政变后乌鲁木齐的恐怖与紧张,描写了河西走廊为马步芳家族占据后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不但都是可以取资的重要的历史记录,而且能够给人以形象化的、立体的感受。比如在“乌鲁木齐的欢乐与悲哀”一节(卷三第九章),以风俗画的笔法描写了乌鲁木齐的“三朝元老”李溶在丧偶十余天后,立即续娶比他小30岁的寡妇为新娘,在喜剧的氛围中,又使人感受到乌鲁木齐市民那种对未来毫无把握的绝望心理。而关于乌鲁木齐1934年遇到地震的内容,则从另一个侧面渲染、烘托出盛世才统治下的首府的那种末日来临的莫名隐忧。
总之,斯文·赫定以洞悉肺腑的目光审视着见到的每一个人;以探究本源的思考推敲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而这一切都是以准确的、讲究分寸感的笔触传达给读者的。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空间跨度都相当大的作品,它之所以能给人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首先是由一个执著的主人公——斯文·赫定本人——的遭逢际遇贯穿始终,其次是有认识中国西部、开发中国西部的宏大构想总领全书。
认识中国西北,正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基本任务,而多达55卷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则是其成果的具体反映。作为这55卷之书的总序或导言,《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则始终紧紧围绕着认识西北这一点来分派笔墨,展开篇幅。而且,全书并不仅限于这些,还恰到好处地把眼光引向开发中国西北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本书第三卷对此所作的阐述、发挥尤为精辟。
斯文·赫定于1934年闯入战火方炽的新疆,就是为了勘测修建连接内地与新疆的交通干线。在第三卷中,作者特意详尽地介绍了从内蒙古进疆,及越过安西,穿越河西走廊等路段沿途的山川物态、道路好坏。比方对甘肃公路的描述,就给人留下了路途坎坷崎岖、交通梗阻不便的印象,而修建公路之议就更显见其迫切与必要。这样,当我们读到作者反对西北要隘纷设税卡,层层盘剥商旅的段落时,就对其立论主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在第三卷中,作者时隔30年重返罗布泊的章节是全书最有魅力的部分。
作者刻画了孔雀河上的处女航,罗布泊新水域的迷人的风光,楼兰古老文明与河流湖泊的依存关系,从东向西走向罗布泊的艰苦困顿以及故地重游的新鲜感、怀旧情愫,及只可意会的怅惘难言的迟暮之感。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作者分明有意指出岁月在流逝,而生活却从未停滞。以上这许多笔墨,都是作者的一个奇思妙想的反衬: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罗布荒原与白龙堆沙漠复苏,看到死去的古老楼兰文明在当代重现光彩。在“结束了囚禁生活”这一节(卷三第六章)中,作者因意外地获得了去罗布泊的机会,便着意表明:
去罗布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出现了光辉的前景,在原计划中,我就曾向南京政府提过塔里木河下游及孔雀河的利用问题。引水入罗布沙漠,使2000年前的古楼兰城附近的村庄复活,把那里的冲积平原变成良田和花园。这情景在34年前——1900年3月28日我发现楼兰废墟时——就曾梦想过。
在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涉及到的另一个强烈吸引着我的问题是:让汽车公路经过楼兰,使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复苏,建立起中国内地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交通运输和联系纽带。
尽管这一梦想今天仍未成为现实,但我认为,它的确是彻底改变塔里木地区(主要是其东端)的生态环境的最有魄力、最具历史感的计划之一。
今天,内地与西北(主要指新疆)的交通已有极大的改观。与3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今天到乌鲁木齐或喀什噶尔,有汽车、火车及飞机可供选择,而那条将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也已修至中国极西的阿拉山口。今天,当我们在坐汽车、坐火车或乘飞机前往新疆的旅途中捧读《亚洲腹地探险八年》,除了会产生强烈的沧桑之感,也会一再为那个70岁老翁的预见性、执著精神、无畏气概所感染,使我们在理解与沟通中跨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这部长达数十万字的三卷著作中,斯文·赫定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对中国西部的土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也得到了相当集中的表述。
在1900年发现楼兰遗址的探险行程中,斯文·赫定雇有一个当地的维吾尔族——“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又译为于得克)。在一次宿营时,发现他们携带的惟一一把铁锹遗失在昨天的驻地,斯文·赫定派奥尔得克返回寻找。风尘仆仆的奥尔得克带回的,除宝贵的铁锹,还有几块木雕。就是由于这样的意外机缘,震惊国际考古界的楼兰古城在一年后被发现了。时隔34年,当斯文·赫定再次来到罗布泊时,他与奥尔得克重逢了。“孔雀河上的第一天”这一节(卷三第七章)中,斯文·赫定以真挚又略带感伤的笔触,描写了那个坚信斯文·赫定许诺“一定还会回来”而等候了三十多年的老人的形象:
船斜穿过河面,在骑士下马的地方靠岸。那老人从岸上滑到船上,他来到面前,眼含热泪拉着我的双手,艰苦的岁月在他的手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这真的是奥尔得克!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老朋友,时光的磨难留在了他的脸上。他很瘦,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胡子挂在尖尖的下巴上,看上去很衰弱。老人带着一顶羊皮镶边的破帽子,披着件已发白的破旧的维吾尔式短大衣,腰上扎条布带子,脚上那双破靴子告诉人们,它曾穿行过了多少沙漠、草原和树丛。
在两位古稀老人深情的对视中,尽管几十年时光弹指而逝,他们又有很不相同的境况,但积淀在心头的思念却并无二致。
这一节及下一节“蜿蜒的河”都是相当感人的篇章。“蜿蜒的河”中以轻淡的笔墨勾画了阿克苏甫村的风光,而作者表达出的那种寂寞、肃穆、自尊又略显孤芳自赏的美感,在今天仍能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这些篇什所具有的对西部土地与人民的情感,丝毫也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减淡。
在艰难长途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全体中外团员共同庆祝了中国当时的国庆——双十节。在《长征记》、《徐旭生西游日记》及本书中,对此都作了记述。与中法科学考察团的作为相比,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一般来说,斯文·赫定的探险或考察是以发现为目的,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他与其他外国探险家的不同之处。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做交易。当他要率领汽车考察队出发时,“经常光临我们院子的古董商使已经相当紧张的空气更加炽热,他们不停地喊叫。我不会与他们做买卖,既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些人达成任何交易”(卷二第十二章)。在路经吐鲁番时,见到为德国人勒柯克等的劫掠后的千佛洞,他对此表示了明确无误的义愤(参见《长征记》第270页)。从他路经敦煌时,对那些洞窟缺乏应有的兴趣看来,也可以反证出,他主要是以地理上的发现自负,与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等人虽同属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西域探险家,但的确并不能一概而论之。有人曾指责斯文·赫定于1900年前后于库车的千佛洞劫走了60峰骆驼的文物,那是毫无根据的。斯文·赫定一生从未到过库车及其附近,1900年没有,1927~1935年间也没有。1934年他想路经库车去喀什,但被马仲英部拘禁于库车以东几百公里的库尔勒,此后也未能再向西前进一步。
如同斯文·赫定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文笔相当生动,读过自额济纳到哈密的行程、库尔勒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老罗布泊复苏后的欣欣向荣的风光等段落,都会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斯文·赫定的旅行记受到欢迎,当然首先取决于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笔下涉及的内容往往是独家的,你在别处是无法获悉的。另外,他也是颇具文学才能的人,其游记一向以文字形象、生动,充满人情味而著称。他写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在坎坷旅途中不论条件多么恶劣,他总是坚持当天记下观感,甚至在骑骆驼的行程当中,他也能一边作地图测绘,一边写笔记。所以,他的游记往往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并使读者能领略到他的呼吸和脉搏,仿佛正与他共同跋涉在漫漫长途中,其感染力与穿透力是一致公认的。而这些特点,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由于其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其眼界与同时代人绝不重复,使《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成为描写1927~1935年中国(主要是西部地区)无可替代的作品,书中许多形象具体的画面都是可贵的历史资料。
在这八年当中,斯文·赫定活动的地域跨度相当大,结识的人物品级相当杂。他笔下的人物上至当时中国的执政者如蒋介石、汪精卫,下至西部的流浪汉、乞丐。他曾为蒙古王公、班禅活佛、外蒙古难民团领袖、一般的喇嘛、额济纳及和静的土尔扈特王爷、被革出教门放逐到居延的藏族释子、西部的土匪、罗布人的后裔、已成为“归化族”的白俄、仆役等许多人物留下了一幅幅准确、客观、栩栩如生的“画像”。在第三卷中,他写到与当时新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交往,比如盛世才、马仲英、神秘的“李教授”、土耳其人凯末尔、“哈密虎”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土尔扈特最后一位领主满楚克札布、马虎山、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两个来历不明的波兰人等等,无一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着墨不多,但马仲英的狂妄与天真、盛世才的阴鸷与权术、尧乐博斯的圆滑世故,都达到呼之欲出的地步。斯文·赫定在吐鲁番曾多次见到了自称是“李教授”的神秘人物,他一眼就看穿了李的伪装,并写道:李教授和他的四个学生“说他们想在新疆呆五年,研究地方语言文学。新疆的语言文学”!描写既有分寸又有洞察力,其实从一见面他就认定此人是负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人。在吐鲁番结识的另一个奇人是马仲英身边的“范增”——凯末尔·卡雅阿凡提。这位“亚父”是土耳其人,在有些书中,他是相当神秘莫测的人,但斯文·赫定却在“生日宴会”一节(卷三第五章),捕捉到了凯末尔的乡愁,使他还原为一个一事无成、流落他乡的说客,其身上的外衣被无形中剥脱干净。在“焉耆的土尔扈特亲王”一节(卷三第八章)中,写到与满汗王的短暂会晤,由于满汗王的叔叔多布顿活佛与考察团早有交往,与期文·赫定也有私交,所以赫定对满汗王很感兴趣。但他很快就觉察到:一、满汗王对其已故叔父有特殊的反感;二、满汗王“权力太有限了”,不是名副其实的封建领主。熟悉新疆现代史的人,当然都知道这是十分准确的概括。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文·赫定被拘于乌鲁木齐时,在一次运动会上见到了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在“运动会”一节(卷三第九章)中所写到的和加尼牙孜,只用几笔简练的勾勒,就凸现出其神态、为人,其处境及内心的矛盾,真把这个当年反政府的英雄,当时名义的“座上客”、实际的“阶下囚”的故作镇静与自持所掩盖的虚弱和高度紧张,原原本本地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斯文·赫定笔下,这位当年一呼百应,被很多人寄以厚望的人已经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他的彻底销声匿迹是指日可待了。
除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写也是相当成功,颇具吸引力的。
斯文·赫定两次来新疆:1928年与1934年,都是新疆现代史的重大转折时刻。当1928年考察团在乌鲁木齐时,发生了督军杨增新被刺事件。随着金树仁的上台,新疆现代史的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了,而陷入了连年的内战。当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达到关键时刻,即胜负将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对其在乌鲁木齐所经历的一切,都作了客观、忠实的记述。
通过斯文·赫定的描写,再现了“高度自治”前的内蒙古各界人物及山川风物,刻画了大乱将起、危机四伏的乌鲁木齐政界,揭示了觥筹交错掩盖下的明争暗斗,突出了马仲英建立“图兰”伊斯兰国梦想的破灭,感传了“四·一二”政变后乌鲁木齐的恐怖与紧张,描写了河西走廊为马步芳家族占据后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不但都是可以取资的重要的历史记录,而且能够给人以形象化的、立体的感受。比如在“乌鲁木齐的欢乐与悲哀”一节(卷三第九章),以风俗画的笔法描写了乌鲁木齐的“三朝元老”李溶在丧偶十余天后,立即续娶比他小30岁的寡妇为新娘,在喜剧的氛围中,又使人感受到乌鲁木齐市民那种对未来毫无把握的绝望心理。而关于乌鲁木齐1934年遇到地震的内容,则从另一个侧面渲染、烘托出盛世才统治下的首府的那种末日来临的莫名隐忧。
总之,斯文·赫定以洞悉肺腑的目光审视着见到的每一个人;以探究本源的思考推敲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而这一切都是以准确的、讲究分寸感的笔触传达给读者的。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空间跨度都相当大的作品,它之所以能给人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首先是由一个执著的主人公——斯文·赫定本人——的遭逢际遇贯穿始终,其次是有认识中国西部、开发中国西部的宏大构想总领全书。
认识中国西北,正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基本任务,而多达55卷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则是其成果的具体反映。作为这55卷之书的总序或导言,《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则始终紧紧围绕着认识西北这一点来分派笔墨,展开篇幅。而且,全书并不仅限于这些,还恰到好处地把眼光引向开发中国西北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本书第三卷对此所作的阐述、发挥尤为精辟。
斯文·赫定于1934年闯入战火方炽的新疆,就是为了勘测修建连接内地与新疆的交通干线。在第三卷中,作者特意详尽地介绍了从内蒙古进疆,及越过安西,穿越河西走廊等路段沿途的山川物态、道路好坏。比方对甘肃公路的描述,就给人留下了路途坎坷崎岖、交通梗阻不便的印象,而修建公路之议就更显见其迫切与必要。这样,当我们读到作者反对西北要隘纷设税卡,层层盘剥商旅的段落时,就对其立论主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在第三卷中,作者时隔30年重返罗布泊的章节是全书最有魅力的部分。
作者刻画了孔雀河上的处女航,罗布泊新水域的迷人的风光,楼兰古老文明与河流湖泊的依存关系,从东向西走向罗布泊的艰苦困顿以及故地重游的新鲜感、怀旧情愫,及只可意会的怅惘难言的迟暮之感。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作者分明有意指出岁月在流逝,而生活却从未停滞。以上这许多笔墨,都是作者的一个奇思妙想的反衬: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罗布荒原与白龙堆沙漠复苏,看到死去的古老楼兰文明在当代重现光彩。在“结束了囚禁生活”这一节(卷三第六章)中,作者因意外地获得了去罗布泊的机会,便着意表明:
去罗布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出现了光辉的前景,在原计划中,我就曾向南京政府提过塔里木河下游及孔雀河的利用问题。引水入罗布沙漠,使2000年前的古楼兰城附近的村庄复活,把那里的冲积平原变成良田和花园。这情景在34年前——1900年3月28日我发现楼兰废墟时——就曾梦想过。
在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涉及到的另一个强烈吸引着我的问题是:让汽车公路经过楼兰,使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复苏,建立起中国内地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交通运输和联系纽带。
尽管这一梦想今天仍未成为现实,但我认为,它的确是彻底改变塔里木地区(主要是其东端)的生态环境的最有魄力、最具历史感的计划之一。
今天,内地与西北(主要指新疆)的交通已有极大的改观。与3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今天到乌鲁木齐或喀什噶尔,有汽车、火车及飞机可供选择,而那条将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也已修至中国极西的阿拉山口。今天,当我们在坐汽车、坐火车或乘飞机前往新疆的旅途中捧读《亚洲腹地探险八年》,除了会产生强烈的沧桑之感,也会一再为那个70岁老翁的预见性、执著精神、无畏气概所感染,使我们在理解与沟通中跨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这部长达数十万字的三卷著作中,斯文·赫定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对中国西部的土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也得到了相当集中的表述。
在1900年发现楼兰遗址的探险行程中,斯文·赫定雇有一个当地的维吾尔族——“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又译为于得克)。在一次宿营时,发现他们携带的惟一一把铁锹遗失在昨天的驻地,斯文·赫定派奥尔得克返回寻找。风尘仆仆的奥尔得克带回的,除宝贵的铁锹,还有几块木雕。就是由于这样的意外机缘,震惊国际考古界的楼兰古城在一年后被发现了。时隔34年,当斯文·赫定再次来到罗布泊时,他与奥尔得克重逢了。“孔雀河上的第一天”这一节(卷三第七章)中,斯文·赫定以真挚又略带感伤的笔触,描写了那个坚信斯文·赫定许诺“一定还会回来”而等候了三十多年的老人的形象:
船斜穿过河面,在骑士下马的地方靠岸。那老人从岸上滑到船上,他来到面前,眼含热泪拉着我的双手,艰苦的岁月在他的手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这真的是奥尔得克!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老朋友,时光的磨难留在了他的脸上。他很瘦,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胡子挂在尖尖的下巴上,看上去很衰弱。老人带着一顶羊皮镶边的破帽子,披着件已发白的破旧的维吾尔式短大衣,腰上扎条布带子,脚上那双破靴子告诉人们,它曾穿行过了多少沙漠、草原和树丛。
在两位古稀老人深情的对视中,尽管几十年时光弹指而逝,他们又有很不相同的境况,但积淀在心头的思念却并无二致。
这一节及下一节“蜿蜒的河”都是相当感人的篇章。“蜿蜒的河”中以轻淡的笔墨勾画了阿克苏甫村的风光,而作者表达出的那种寂寞、肃穆、自尊又略显孤芳自赏的美感,在今天仍能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这些篇什所具有的对西部土地与人民的情感,丝毫也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减淡。
在艰难长途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全体中外团员共同庆祝了中国当时的国庆——双十节。在《长征记》、《徐旭生西游日记》及本书中,对此都作了记述。与中法科学考察团的作为相比,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一般来说,斯文·赫定的探险或考察是以发现为目的,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他与其他外国探险家的不同之处。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做交易。当他要率领汽车考察队出发时,“经常光临我们院子的古董商使已经相当紧张的空气更加炽热,他们不停地喊叫。我不会与他们做买卖,既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些人达成任何交易”(卷二第十二章)。在路经吐鲁番时,见到为德国人勒柯克等的劫掠后的千佛洞,他对此表示了明确无误的义愤(参见《长征记》第270页)。从他路经敦煌时,对那些洞窟缺乏应有的兴趣看来,也可以反证出,他主要是以地理上的发现自负,与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等人虽同属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西域探险家,但的确并不能一概而论之。有人曾指责斯文·赫定于1900年前后于库车的千佛洞劫走了60峰骆驼的文物,那是毫无根据的。斯文·赫定一生从未到过库车及其附近,1900年没有,1927~1935年间也没有。1934年他想路经库车去喀什,但被马仲英部拘禁于库车以东几百公里的库尔勒,此后也未能再向西前进一步。
如同斯文·赫定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文笔相当生动,读过自额济纳到哈密的行程、库尔勒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老罗布泊复苏后的欣欣向荣的风光等段落,都会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