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赵 明
一九四四年九月,统治新疆十二年的盛世才,偕带家眷,满载着从新疆各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脂膏,在秋风凄雨和人民的咒骂声中,灰溜溜地滚出新疆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接着,国民党为了实现其反动统治,大批党军政人员越过浩瀚戈壁,象洪水猛兽似的向天山南北拥来。
在这新旧交替,社会上一片混乱,人心动荡不定的关键时刻,革命风暴应运而起,在乌鲁木齐“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了;在伊犁各族人民起义了,并迅速地建立起伊、塔、阿三区革命民主政权。斗争矛头一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新盟”)是由过去多年接受党的培养教育的八名革命青年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创建的。他们是:张志远(现名张伯中)、赵普琳(现名赵明)、王笃从(现名王韬)、张玉珍(现名张玮)、姚品兰(现名姚向黎)、韩世翼、王适纯、李玉祥,年龄小的才十九岁,大的也只是二十五、六岁。他们举手宣誓,决心要把关押在新疆狱中的共产党人手中的革命红旗接过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干革命。经过讨论,确定了当前要干的四项主要任务:
一、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宣传、组织活动,大力发展“新盟”成员,动员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二、积极寻找党的领导,争取将“新盟”交由党来领导;
三、积极与伊、塔、阿三区革命政府建立联系,互相配合,协同动作,共同从事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四、尽力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援狱中的中共党员。
根据第四项任务,“新盟”派张玉珍、姚品兰等女同志出面,趁狱中中共党员去北门第一医院看病的机会,通过医院药剂员贡秀琴与他们建立了经常可靠的联系。为了寻找党的领导,“新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派张志远去重庆,找到了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受到曾在新疆担任过党代表的邓发和宋黎同志的接待。他汇报了“新盟”创建经过、组织与活动情况,并要求党派人到新疆来进行领导。
邓发和宋黎同志向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同志汇报后,董老指示:当前我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焦点不在新疆,不在大西北,而在东北。东北拿下来了,关内解放就有了依靠和希望;内地解放了,新疆和整个大西北也就随之解放了。现在东北非常需要地方干部,你们“新盟”中东北人多,应尽量向东北转移,不能转移的,留在新疆,暂时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号,应广泛开展民主运动。
张志远同志将董老的指示,用密语写信转告给我们,然后通过父辈的老关系,随着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东北去了。
当时“新盟”由我负总责。我接到张志远同志信后,把董老的指示向大家作了传达,征询大家的意见,愿去东北的去东北,愿去延安的去延安,愿留在新疆的留在新疆。结果表示愿去东北的占大半,愿直接去延安的有三人,其余同志愿留在新疆继续干。
我把牺牲在监狱中的哥哥赵普源留下来的家当变卖了,又向在新疆银行工作的好友孙哲同志要了一笔钱,用作补贴大家的路费,开始进行向东北转移的准备工作。
“新盟”成员姚廷枢(现名姚艮)在张志远同志去重庆不久,也随后到了重庆,住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同志家。一天阎宝航带姚艮去中共代表团,邓发同志提出,为营救新疆狱中的中共党员,需要一份名单,在中央组织部档案里查不到,能不能通过“新盟”,搞出一份在押中共人员的名单来?姚艮同志以密语写信告诉了我。我通过张玉珍等女同志将中共代表团要名单的事转达给了狱中的中共党员。
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我乘卡车离开乌鲁木齐去兰州,因路上耽搁,五月初才到达。这时张玉珍同志乘飞机已先我到了兰州,在南门外纱厂巷一号,与早在一九四五年春天结婚后就去到兰州的韩世翼和姚向黎夫妇住一个院。我一找到她,她就把一份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员名单交给了我,还附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后来得知这份名单和信是两位老红军谢良(解放后任一炮副政委)和罗云章写的。
当时内战烽火已在各地燃烧,稍一迟误,关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就休想出来。这些人许多是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不少是我的老师,也有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亲密同志。救亲人急如星火,可是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又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动员时期,没有特殊关系,车、船、飞机票都很难买。而由大西北去大西南又关口重重,路途遥远,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名单和信送到重庆交中共代表团呢?我想不出办法,直在地上打转转。
我在兰州唯一的一个熟人是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叫靳士耀的,当时在兰州西北医院当主治大夫,我求他想办法给我买了张飞机票。我把新疆狱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缝在西服垫肩里,乘上飞机,飞过云雾漫的秦岭,到达雾都重庆。
真巧,这天雾都重庆没有雾,天气非常晴朗,重重山峦、长江、嘉陵江都历历在目。飞机一降落,我提着小皮箱,随着乘客走下舷梯,登上水泥台阶,走上街头,累得满头大汗。街上商店林立、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市声嘈杂,呈现出“陪都”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
“到哪里去找中共代表团呢?”当时,我有两个打算:一是要找在新疆学院为我们授课的茅盾老师,我知道他在重庆,而且与党有联系,但不知道他的详细住址,需要打听;一是要找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教我们英文课的贾丽南老师,他在北碚《时与潮》杂志社,常把中国进步小说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他离开学校时,把满满一柳条包书留给数学老师吴宗涵,吴老师又转给了我。其中有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件、高尔基选集、中国进步青年作家的作品及一些社会科学书,这些书对我革命思想的成长起了一定作用。
我买了一张重庆市交通图,按图由七星岗乘公共汽车去北碚,打算先找到贾丽南老师,好有个住处。他认识斯诺,也许能帮助我找到中共代表团,并了解茅盾老师的住处。可是到《时与潮》杂志社一打问,贾丽南老师已离开那里了。我又坐公共汽车回到市内,找新华书店,想通过他们问清茅盾老师的确切住址。可是这时新华书店在较场口事件时已被国民党特务砸得稀巴烂,被迫关门了。
天快黑了,怎么办?先找个住处再说吧。我又回到中华路,碰到一家旅馆就走了进去,招待员给我开了一个房间,我正要进房,新疆学院的一位老同学韩灵锐由对面房间出来,他也许听见了我的话音。他是个非常稳重、态度和蔼、待人诚恳、不苟言笑的老学友。我在政经二系,他在教育二系,不同班,但都在学生会工作,比较熟,他也是东北人,他爱人和我嫂嫂是一九三五年冬由北京同车去新疆的,因之与我兄嫂也很熟。我哥哥牺牲在监狱中后,嫂嫂去了兰州,小侄也是由他们夫妇带到兰州去的。
我俩一同走进房间,我告诉他,“我是由兰州坐飞机来的,有点急事,想找茅盾老师。”他说,“他已不在这里,回上海啦!”这下子我可傻眼了。两个熟识的人都不在重庆了。重庆特务如麻,我不敢公开打听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怎么办呢?在谈话中,韩灵锐告诉我,在重庆还有两个熟人,一个是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宋伯翔,一个是新疆学院的同学李玉祥。宋伯翔我久闻其名,是所谓“十大博士”之一,但从未见过面,现在重庆国民党的一个机关里任职。李玉祥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者之一,和我们一起活动了几个月之后,不辞而别,到关内另找出路,先到兰州,后又到重庆,现在是朱炳办的“新绥汽车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我考虑,通过这两个人打问中共代表团不对路,想来想去,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找诗人臧克家去!
臧克家我并不认识,只是在北平读初中时,读过他的诗集《烙印》和《罪恶的黑手》。为什么想起找他来了呢?原来臧克家的爱人郑曼,是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许青航和孙海澜的同学。他俩由新疆去东北途经兰州时,给我留下一封给郑曼和臧克家同志的介绍信,让我在重庆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他们。现在没有别的门路可走,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当时我想,他们也许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地址,说不定和中共代表团还有联系呢!
第二天,我就按介绍信上写的地址,到歌乐山大天池六号去找臧克家夫妇。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他们看了介绍信,知道我是哪一路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们的住房很狭小,陈设简单,生活很朴素。
郑曼同志小产之后不久,头上扎着一条白带子,面容有点憔悴。臧克家同志个子瘦高,双目炯炯有神。他性格爽直,不失山东人的特性。
我讲了我与许青航和孙海澜的亲密关系,新疆局势的变化,然后我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要找中共代表团,但不知道地址。”
臧克家同志说:“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我也不清楚。可是我知道《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你可以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中共代表团的地址。”
我把他告诉我的《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的地址标在重庆市交通图上。他热情地要留我住下,可是我身负重任,只好推辞说:“等把事情办完了,再来打扰你们。”我把带给茅盾老师的吐鲁番葡萄干和哈密瓜干留给他们,起身就走。葡萄干和瓜干,那时在重庆算是新鲜东西,解放后我再去拜望他们时,他们一下认不出我来,我一提当年送葡萄干和瓜干的事,他们马上想起来了,欢欣地谈叙了旧事。
告别了臧克家和郑曼同志,我回到旅馆,邀上韩灵锐同志一起去找《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他为人比较深沉,了解我的思想情况。他什么也没有问,就按我说的地址,把我带到《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所在的一条暗巷口。他转身走了,我独自走了进去。
一个瘦削的中年人,留着松蓬蓬的分发、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是由新疆来的,我是新疆学院毕业的,我的院长、教务长、军事教官、系主任、讲师都是中共党员,我和他们一起坐过监狱,受他们的委托,有要事会见中共代表团。
他打量了我一下,我急忙拿出新疆学院毕业证书,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下,交还给我,明确地告诉了中共代表团的地址——上清寺路曾家岩十号。我高兴地和他握了握手,告辞出来。在热闹的地方转了几个圈,看看后面没有“尾巴”,我径直去到曾家岩十号。
说明了来意,门房把我领到一间会客室,叫我等着。不一会,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中年人由里屋走出来,他打量了我一下,我急忙作了自我介绍,并掏出新疆学院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了。他亲切地让我在小沙发上坐下。我问了他的姓名,他说叫魏传统。
“魏传统!”我惊喜异常。我读过他写的小册子,专题阐述革命转变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张志远和姚枢廷来找过代表团,由邓发和宋黎接待的,代表团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我这次是专程来送名单的,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脱下西服上身,当着他的面拆开垫肩取出名单和信,交给了他。他接过去聚精会神地仔细读着。
名单和信都是用浅黄色毛边纸,直行写的,张玉珍同志由新疆带出时,是藏在高跟皮鞋后根里的,有的字迹已经磨损,不易看清。我在一边帮他辨认。名单一共写了一百六十二人,大人小孩一个不漏,其中包括已经牺牲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和在狱中叛变了的孟一鸣(徐梦秋)、潘柏南(潘同)、刘西屏、黄义明、任远光、段进启等。但都是以“听说”这种不确定的口气写的,我以肯定的口气对魏传统同志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确实是牺牲了,是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被敌人杀害的;孟一鸣、潘柏南、刘西屏、黄义明、任远光、段进启等人确实是叛变了,已经离开了监狱。”
魏传统同志读完名单和信,我告诉他:“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被关在新疆狱中的中共党人有经常可靠的联系,党如果有什么指示要带给他们,我可以再专程返回新疆去。”
魏传统同志说:“我们考虑,考虑!”
我把我住的旅馆名称、房间号数留给了他。我告诉他:“我们‘新盟’许多同志根据董老指示,正在陆续向东北转移,也有的同志要直接去延安。”我问他:“去延安怎样走比较安全?”他说:“可由甘肃庆阳或环县进解放区,那里我们的力量强,空隙大。”后来“新盟”成员杜芳、王怀品、刘一匡三同志由新疆奔赴延安,就是按魏传统同志指的路径去陕甘宁边区的。
魏传统同志拿过来当日的《新华日报》指给我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在打长春,关内停战,东北要大打起来。东北很需要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你们转移到东北,非常必要。”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当前形势。
我告辞出来,双肩上象卸了一副重担,身轻似燕,健步如飞,在热闹的商业区转了一会,没有发现后面有“尾巴”,我怡然自得地回到了旅馆。
专程来重庆给中共代表团送名单和信的使命完成了,当前要做的是赶快回到兰州,迎候由新疆陆续出来的同志,一起去东北;迟了.内战一大打起来,交通被切断,就难走了。
我和韩灵锐同志商量一起回兰州的问题。
来时,由靳士耀同学给想法买的飞机票;回程,如果与达宫贵人预买飞机票,根本不敢去想,就是去川北的长途汽车票,没有熟人,也休想买到票。我和韩灵锐同志天天上街跑车行货,寻找去宝鸡的“黄鱼车”。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多礼拜时间,才找到一辆去宝鸡运送汽油的美国JMC牌军用小轮卡车。我来不及去歌乐山向臧克家和郑曼同志告别,搭上这辆“黄鱼车”就同韩灵锐同志一同起身走了。
来重庆时,乘飞机穿云过雾,天府锦绣什么也没看到;回程坐汽车,爬山越岭,横渡江河,却饱赏了“蜀江水碧,蜀山青”的绮丽风光,也经历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险途程。
车到了宝鸡,想由天水抄近路,北上兰州。但因铁路塌方,火车不通,只好折而向东去西安,然后再找“黄鱼车”西去兰州。
当时火车没有准确的发车时间,只得守候在站台上寸步不离,以免错过时机。
一列火车进站了,人们象潮水一样拥上前去,争先恐后,拥在各个车厢门口,谁也休想挤进去。人急智生,我看到一个车厢的窗子开着,我拉着韩灵锐同志跑上前去,叫他把我抱起来,我顺着窗口爬了进去,占了一排座位,韩灵锐又把东西一件件递了进来。
车厢内旅客挤得水泄不通,我突然发现一个叫徐志诚的高个青年,痴呆呆地站在我近前。他是国民党反动派“劫收”新疆时入新的,在空军工作,能画几笔画,能写几首只有他们小圈子里的人才能欣赏的小诗。他曾看上了我们“新盟”一个女同志,死死缠住不放。我在这个女同志家里见过他一面。这时他痴呆呆地站在那里,样子十分狼狈。我给他让出个座位,他坐下来了,不一会又莫明其妙地让给了别人,又是痴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徐志诚是个什么人,我们了若指掌,此时此地又在火车上出洋相,不得不引起我的警惕。
到了西安,我和韩灵锐在东大街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又象在重庆一样,天天跑车行货栈找“黄鱼车”。又花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一部去兰州的“黄鱼车”。这是一辆破旧的三吨道奇,与小轮JMC大卡车比较,寒酸得简直象一个叫花子。但货物却装了十来吨,走起来摇摇晃晃的,人坐在上面,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摔下来。
车是旧车,又超载了两三倍重量的货物,跑不了多远就停下来修理一次。当时有个顺口溜,用十个数字描绘这种情况:“一去二三里,加水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一路上卡车又是加油,又是加水,又是修理,爬行了五六天,才到兰州。
我把由重庆生活书店买到的中共七大文件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给韩世翼、张玉珍和几位已到达兰州的同志传阅,我则住进了西北医院,一方面检查了一下身体,治了治一点小毛病,一方面迎候由新疆出来的同志。
六月十九日,我和爱人进城,走到南门外十字路口,看到由城里开出来一列带篷大卡车,走到十字路口停下来了。车篷上满是尘土,一望即知是经过长途跋涉的,心想也许是由新疆出来的。我们停住脚步,站在路边观望着。不一会,从离我们不远的一部卡车上跳下几个人来,拍打身上的尘土,我仔细一看,发现了于村同志,高兴极了。
于村同志是一九三八年由延安派到新疆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是搞戏剧的。我在新疆学院时,请他教过抗战歌曲,帮助排演过抗战话剧。一九四一年在反帝总会,我们在一起工作将近一年,还同台演出过话剧,我从来没对他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后来我被调到师范学校工作,于村同志曾骑马跑到十几里外的老满城专程去看我。这次,我冒着生命危险,飞越秦岭到雾都重庆给中共代表团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除了一般地受革命责任感的驱使外,也是出于对这些曾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师、同志、朋友的深厚情感。
我指着卡车惊喜地对爱人说:“那不是于村同志?!他们出来了!”心里想,“这次去重庆,总算没有白跑!”
据说,当晚他们被安顿在五泉山下的一个招待所里住,我邀集已到达兰州的“新盟”成员张玉珍、姚品兰、韩世翼、王琢成、桂声等同志,于晚饭后一同上五泉山。一边走,一边放声高唱新疆歌曲。我们想,他们一定会听出是我们在为他们而唱。可是第二天一看兰州小报,原来他们住的是东郊外七星墩,不是五泉山。而我们当时满怀革命激情,起劲地唱时,还以为他们真能听到咧!
整整二十年后,“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死党谢富治和他们在公安部的代理人李震、施义之,唆使他们豢养的“东方红战斗队”以诬陷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送进了监狱,一关六年,每天四个窝窝头,一碗清汤水,几乎饿死病死在狱中。罪名之一,就是硬说我把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人名单送给了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逼我非承认不可。与此同时,康生一伙也给由新疆狱中返回延安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迫害。
在新疆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并非一般的地下党,是应盛世才的请求,由延安公开派去的,或是去苏联治病,顺道留下来的,一部分是西路军留下来学航空技术的。谁是共产党人盛世才都知道,并被奉为上宾,委以要职。陈潭秋是党代表,毛泽民是财政厅长(后任民政厅长)、孟一鸣是教育厅长、潘柏南是和田警备司令、刘西屏是哈密行政长、黄义明是管军队财务的边防督办公署经理处长、黄火青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后调阿克苏任行政长)、汪哮春是《新疆日报》社社长、李宗林是编辑长、林基路是新疆学院教务长、李志梁是省立一中校长……,只是到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利用国内外局势逆转的时机,公开投靠蒋介石时,才把这些“昨日座上宾”变成了“今日阶下囚,”并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杀害。至于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他早早就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还派了个所谓“中央审判团”到新疆复审。“造反派”逼我承认把新疆在押中共人员名单送给了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只是说明他们无知。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追问我送名单的事,原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康生、江青这一帮大坏蛋,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就授意各“造反派”组织,揪所谓“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企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特别是空军许多负责干部都是新疆航空队的),妄想从我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一九七三年六月末,即在林彪事件之后,“造反派”对我的诬陷被揭穿了,不得不为我平反,放出监牢。
一天,我到三〇一医院去看一炮副政委谢良同志,他也是刚放出来不久,高血压、颈部骨质增生,心脏也不好。他一见我就以江西老表的浓重口音激动地说:“赵明同志呀,为了名单的事,我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毒打呀!”他指给我看头上和身上的伤痕,他们问我“名单是怎样送到重庆去的?交给了谁?”我答不出,就狠狠打我。那次在袁子钦家见面时好好谈谈就好了!
袁子钦,解放初期是总政干部部长,后升任总政副主任,他的爱人鲁毅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闲谈中,她提到谢良常到她家去,并打问过我。我说:“我知道他,没见过面,倒是很想见见。”她说:“那好办,哪天他到我家来,我打电话告诉你。”
果然,一天鲁毅同志打电话给我,“谢良同志今天中午到我家里来,你也来吧,一起在我家吃午饭!”我到时,谢良同志已经先到。他一见我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到重庆送名单的就是你!”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望着他的眼晴说:“开出名单,给主席写信的就是你!”
我怕人家说我“夸功”,从来不提到重庆送名单的事,就是在自传中,也只简单提了一句。这时谢良同志没有往下问,我也就没有往下说。两人亲热地在院中肩并肩地照了一个半身像片,然后就入席吃中午饭,再没提及送名单的事,因之,他不知道送名单的全部过程。“文革”中“造反派”一追问,他说不清,道不明,白白挨了许多顿揍。这次我到三○一医院去看他,他才要我讲了送名单的整个过程。当我谈到把名单亲自交给了魏传统同志时,他说:“魏传统?!他就在这里养病,在我隔壁住。”问我:“你想不想看看他?”我说:“我想去,知道知道他收到名单以后怎么办了。”他说:“走,我领你去!”
谢良同志拄着拐杖领我到了隔壁病房,见了魏传统同志。他已不是我二十七年前见的那个样子了,那时清瘦,现在胖了,面色红润了。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点不显得老。谢良同志做了介绍,当说起送名单的事时,魏统传同志说:“文革中有人来调查过,我写了证明材料。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穿着一身浅灰色西服,当着我的面,由西服垫肩里拆出来名单,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看后,做为特急件,第二天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南京,交给了周总理。那时中共代表团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曾家岩十号留给了中共四川省委,我当时是四川省委秘书长。”
后来由读到过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得知:周总理拿到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后不久,正值张治中先生要到新疆接任省府主席职务。周总理对张治中先生说:“新疆监狱中还押着我们一批人,请你到新疆后,务必帮忙给送回延安去。”并把名单交给了他。张治中先生未负周总理的委托,到新疆后,亲自到狱中看望了这批同志,然后派了十辆大卡车,由刘亚哲护送,把这批同志安全地护送回了延安。
我送给中共代表团的名单上一共开列了一百六十二个名字,除去叛徒及其家属外,由乌鲁木齐出发时是一百三十一人,路途上有两个孩子病故,到达延安的是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马明方、方志纯、李宗林、刘护平、李渥如、高登榜、吉合、谢良、张子意、吕黎平、方槐、袁彬、黎明、金生、郭慎先、李志梁、张东月、李何、于村、白大方、陈浩然、王韵雪、朱旦华、陈茵素、沈谷南等党政军和文教方面的负责干部及烈士家属。我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应邀去新疆参加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见到郑英(在新疆时叫李霞,廖志高同志爱人)同志,她告诉我:中共代表团由南京撤回延安时,她正在中组部工作,我们送的那份名单,由她经手归档的。
这批人到延安时,朱总司令曾到十里之外去迎接,毛主席亲自接见,延安各界开了欢迎大会,表示亲切慰问,然后分头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文革”中不少同志又重遭迫害,李宗林、沈谷南、白大方、曹建培、胡鉴等人被迫害致死,马明方、杨之华被囚死牢中,刘护平出狱后没有离开过医院,张子意出狱后常年生病,死于医院中……
宋诗人黄庭坚有两句名句:“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当年在新疆工作过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经受了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道路,无论是幸存者,也无论是牺牲者,他们确实是点污不沾,纯贞自洁的花朵——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一九四四年九月,统治新疆十二年的盛世才,偕带家眷,满载着从新疆各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脂膏,在秋风凄雨和人民的咒骂声中,灰溜溜地滚出新疆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接着,国民党为了实现其反动统治,大批党军政人员越过浩瀚戈壁,象洪水猛兽似的向天山南北拥来。
在这新旧交替,社会上一片混乱,人心动荡不定的关键时刻,革命风暴应运而起,在乌鲁木齐“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了;在伊犁各族人民起义了,并迅速地建立起伊、塔、阿三区革命民主政权。斗争矛头一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新盟”)是由过去多年接受党的培养教育的八名革命青年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创建的。他们是:张志远(现名张伯中)、赵普琳(现名赵明)、王笃从(现名王韬)、张玉珍(现名张玮)、姚品兰(现名姚向黎)、韩世翼、王适纯、李玉祥,年龄小的才十九岁,大的也只是二十五、六岁。他们举手宣誓,决心要把关押在新疆狱中的共产党人手中的革命红旗接过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干革命。经过讨论,确定了当前要干的四项主要任务:
一、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宣传、组织活动,大力发展“新盟”成员,动员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二、积极寻找党的领导,争取将“新盟”交由党来领导;
三、积极与伊、塔、阿三区革命政府建立联系,互相配合,协同动作,共同从事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四、尽力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援狱中的中共党员。
根据第四项任务,“新盟”派张玉珍、姚品兰等女同志出面,趁狱中中共党员去北门第一医院看病的机会,通过医院药剂员贡秀琴与他们建立了经常可靠的联系。为了寻找党的领导,“新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派张志远去重庆,找到了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受到曾在新疆担任过党代表的邓发和宋黎同志的接待。他汇报了“新盟”创建经过、组织与活动情况,并要求党派人到新疆来进行领导。
邓发和宋黎同志向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同志汇报后,董老指示:当前我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焦点不在新疆,不在大西北,而在东北。东北拿下来了,关内解放就有了依靠和希望;内地解放了,新疆和整个大西北也就随之解放了。现在东北非常需要地方干部,你们“新盟”中东北人多,应尽量向东北转移,不能转移的,留在新疆,暂时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号,应广泛开展民主运动。
张志远同志将董老的指示,用密语写信转告给我们,然后通过父辈的老关系,随着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东北去了。
当时“新盟”由我负总责。我接到张志远同志信后,把董老的指示向大家作了传达,征询大家的意见,愿去东北的去东北,愿去延安的去延安,愿留在新疆的留在新疆。结果表示愿去东北的占大半,愿直接去延安的有三人,其余同志愿留在新疆继续干。
我把牺牲在监狱中的哥哥赵普源留下来的家当变卖了,又向在新疆银行工作的好友孙哲同志要了一笔钱,用作补贴大家的路费,开始进行向东北转移的准备工作。
“新盟”成员姚廷枢(现名姚艮)在张志远同志去重庆不久,也随后到了重庆,住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同志家。一天阎宝航带姚艮去中共代表团,邓发同志提出,为营救新疆狱中的中共党员,需要一份名单,在中央组织部档案里查不到,能不能通过“新盟”,搞出一份在押中共人员的名单来?姚艮同志以密语写信告诉了我。我通过张玉珍等女同志将中共代表团要名单的事转达给了狱中的中共党员。
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我乘卡车离开乌鲁木齐去兰州,因路上耽搁,五月初才到达。这时张玉珍同志乘飞机已先我到了兰州,在南门外纱厂巷一号,与早在一九四五年春天结婚后就去到兰州的韩世翼和姚向黎夫妇住一个院。我一找到她,她就把一份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员名单交给了我,还附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后来得知这份名单和信是两位老红军谢良(解放后任一炮副政委)和罗云章写的。
当时内战烽火已在各地燃烧,稍一迟误,关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就休想出来。这些人许多是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不少是我的老师,也有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亲密同志。救亲人急如星火,可是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又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动员时期,没有特殊关系,车、船、飞机票都很难买。而由大西北去大西南又关口重重,路途遥远,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名单和信送到重庆交中共代表团呢?我想不出办法,直在地上打转转。
我在兰州唯一的一个熟人是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叫靳士耀的,当时在兰州西北医院当主治大夫,我求他想办法给我买了张飞机票。我把新疆狱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缝在西服垫肩里,乘上飞机,飞过云雾漫的秦岭,到达雾都重庆。
真巧,这天雾都重庆没有雾,天气非常晴朗,重重山峦、长江、嘉陵江都历历在目。飞机一降落,我提着小皮箱,随着乘客走下舷梯,登上水泥台阶,走上街头,累得满头大汗。街上商店林立、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市声嘈杂,呈现出“陪都”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
“到哪里去找中共代表团呢?”当时,我有两个打算:一是要找在新疆学院为我们授课的茅盾老师,我知道他在重庆,而且与党有联系,但不知道他的详细住址,需要打听;一是要找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教我们英文课的贾丽南老师,他在北碚《时与潮》杂志社,常把中国进步小说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他离开学校时,把满满一柳条包书留给数学老师吴宗涵,吴老师又转给了我。其中有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件、高尔基选集、中国进步青年作家的作品及一些社会科学书,这些书对我革命思想的成长起了一定作用。
我买了一张重庆市交通图,按图由七星岗乘公共汽车去北碚,打算先找到贾丽南老师,好有个住处。他认识斯诺,也许能帮助我找到中共代表团,并了解茅盾老师的住处。可是到《时与潮》杂志社一打问,贾丽南老师已离开那里了。我又坐公共汽车回到市内,找新华书店,想通过他们问清茅盾老师的确切住址。可是这时新华书店在较场口事件时已被国民党特务砸得稀巴烂,被迫关门了。
天快黑了,怎么办?先找个住处再说吧。我又回到中华路,碰到一家旅馆就走了进去,招待员给我开了一个房间,我正要进房,新疆学院的一位老同学韩灵锐由对面房间出来,他也许听见了我的话音。他是个非常稳重、态度和蔼、待人诚恳、不苟言笑的老学友。我在政经二系,他在教育二系,不同班,但都在学生会工作,比较熟,他也是东北人,他爱人和我嫂嫂是一九三五年冬由北京同车去新疆的,因之与我兄嫂也很熟。我哥哥牺牲在监狱中后,嫂嫂去了兰州,小侄也是由他们夫妇带到兰州去的。
我俩一同走进房间,我告诉他,“我是由兰州坐飞机来的,有点急事,想找茅盾老师。”他说,“他已不在这里,回上海啦!”这下子我可傻眼了。两个熟识的人都不在重庆了。重庆特务如麻,我不敢公开打听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怎么办呢?在谈话中,韩灵锐告诉我,在重庆还有两个熟人,一个是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宋伯翔,一个是新疆学院的同学李玉祥。宋伯翔我久闻其名,是所谓“十大博士”之一,但从未见过面,现在重庆国民党的一个机关里任职。李玉祥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者之一,和我们一起活动了几个月之后,不辞而别,到关内另找出路,先到兰州,后又到重庆,现在是朱炳办的“新绥汽车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我考虑,通过这两个人打问中共代表团不对路,想来想去,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找诗人臧克家去!
臧克家我并不认识,只是在北平读初中时,读过他的诗集《烙印》和《罪恶的黑手》。为什么想起找他来了呢?原来臧克家的爱人郑曼,是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许青航和孙海澜的同学。他俩由新疆去东北途经兰州时,给我留下一封给郑曼和臧克家同志的介绍信,让我在重庆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他们。现在没有别的门路可走,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当时我想,他们也许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地址,说不定和中共代表团还有联系呢!
第二天,我就按介绍信上写的地址,到歌乐山大天池六号去找臧克家夫妇。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他们看了介绍信,知道我是哪一路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们的住房很狭小,陈设简单,生活很朴素。
郑曼同志小产之后不久,头上扎着一条白带子,面容有点憔悴。臧克家同志个子瘦高,双目炯炯有神。他性格爽直,不失山东人的特性。
我讲了我与许青航和孙海澜的亲密关系,新疆局势的变化,然后我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要找中共代表团,但不知道地址。”
臧克家同志说:“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我也不清楚。可是我知道《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你可以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中共代表团的地址。”
我把他告诉我的《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的地址标在重庆市交通图上。他热情地要留我住下,可是我身负重任,只好推辞说:“等把事情办完了,再来打扰你们。”我把带给茅盾老师的吐鲁番葡萄干和哈密瓜干留给他们,起身就走。葡萄干和瓜干,那时在重庆算是新鲜东西,解放后我再去拜望他们时,他们一下认不出我来,我一提当年送葡萄干和瓜干的事,他们马上想起来了,欢欣地谈叙了旧事。
告别了臧克家和郑曼同志,我回到旅馆,邀上韩灵锐同志一起去找《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他为人比较深沉,了解我的思想情况。他什么也没有问,就按我说的地址,把我带到《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所在的一条暗巷口。他转身走了,我独自走了进去。
一个瘦削的中年人,留着松蓬蓬的分发、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是由新疆来的,我是新疆学院毕业的,我的院长、教务长、军事教官、系主任、讲师都是中共党员,我和他们一起坐过监狱,受他们的委托,有要事会见中共代表团。
他打量了我一下,我急忙拿出新疆学院毕业证书,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下,交还给我,明确地告诉了中共代表团的地址——上清寺路曾家岩十号。我高兴地和他握了握手,告辞出来。在热闹的地方转了几个圈,看看后面没有“尾巴”,我径直去到曾家岩十号。
说明了来意,门房把我领到一间会客室,叫我等着。不一会,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中年人由里屋走出来,他打量了我一下,我急忙作了自我介绍,并掏出新疆学院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了。他亲切地让我在小沙发上坐下。我问了他的姓名,他说叫魏传统。
“魏传统!”我惊喜异常。我读过他写的小册子,专题阐述革命转变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张志远和姚枢廷来找过代表团,由邓发和宋黎接待的,代表团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我这次是专程来送名单的,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脱下西服上身,当着他的面拆开垫肩取出名单和信,交给了他。他接过去聚精会神地仔细读着。
名单和信都是用浅黄色毛边纸,直行写的,张玉珍同志由新疆带出时,是藏在高跟皮鞋后根里的,有的字迹已经磨损,不易看清。我在一边帮他辨认。名单一共写了一百六十二人,大人小孩一个不漏,其中包括已经牺牲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和在狱中叛变了的孟一鸣(徐梦秋)、潘柏南(潘同)、刘西屏、黄义明、任远光、段进启等。但都是以“听说”这种不确定的口气写的,我以肯定的口气对魏传统同志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确实是牺牲了,是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被敌人杀害的;孟一鸣、潘柏南、刘西屏、黄义明、任远光、段进启等人确实是叛变了,已经离开了监狱。”
魏传统同志读完名单和信,我告诉他:“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被关在新疆狱中的中共党人有经常可靠的联系,党如果有什么指示要带给他们,我可以再专程返回新疆去。”
魏传统同志说:“我们考虑,考虑!”
我把我住的旅馆名称、房间号数留给了他。我告诉他:“我们‘新盟’许多同志根据董老指示,正在陆续向东北转移,也有的同志要直接去延安。”我问他:“去延安怎样走比较安全?”他说:“可由甘肃庆阳或环县进解放区,那里我们的力量强,空隙大。”后来“新盟”成员杜芳、王怀品、刘一匡三同志由新疆奔赴延安,就是按魏传统同志指的路径去陕甘宁边区的。
魏传统同志拿过来当日的《新华日报》指给我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在打长春,关内停战,东北要大打起来。东北很需要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你们转移到东北,非常必要。”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当前形势。
我告辞出来,双肩上象卸了一副重担,身轻似燕,健步如飞,在热闹的商业区转了一会,没有发现后面有“尾巴”,我怡然自得地回到了旅馆。
专程来重庆给中共代表团送名单和信的使命完成了,当前要做的是赶快回到兰州,迎候由新疆陆续出来的同志,一起去东北;迟了.内战一大打起来,交通被切断,就难走了。
我和韩灵锐同志商量一起回兰州的问题。
来时,由靳士耀同学给想法买的飞机票;回程,如果与达宫贵人预买飞机票,根本不敢去想,就是去川北的长途汽车票,没有熟人,也休想买到票。我和韩灵锐同志天天上街跑车行货,寻找去宝鸡的“黄鱼车”。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多礼拜时间,才找到一辆去宝鸡运送汽油的美国JMC牌军用小轮卡车。我来不及去歌乐山向臧克家和郑曼同志告别,搭上这辆“黄鱼车”就同韩灵锐同志一同起身走了。
来重庆时,乘飞机穿云过雾,天府锦绣什么也没看到;回程坐汽车,爬山越岭,横渡江河,却饱赏了“蜀江水碧,蜀山青”的绮丽风光,也经历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险途程。
车到了宝鸡,想由天水抄近路,北上兰州。但因铁路塌方,火车不通,只好折而向东去西安,然后再找“黄鱼车”西去兰州。
当时火车没有准确的发车时间,只得守候在站台上寸步不离,以免错过时机。
一列火车进站了,人们象潮水一样拥上前去,争先恐后,拥在各个车厢门口,谁也休想挤进去。人急智生,我看到一个车厢的窗子开着,我拉着韩灵锐同志跑上前去,叫他把我抱起来,我顺着窗口爬了进去,占了一排座位,韩灵锐又把东西一件件递了进来。
车厢内旅客挤得水泄不通,我突然发现一个叫徐志诚的高个青年,痴呆呆地站在我近前。他是国民党反动派“劫收”新疆时入新的,在空军工作,能画几笔画,能写几首只有他们小圈子里的人才能欣赏的小诗。他曾看上了我们“新盟”一个女同志,死死缠住不放。我在这个女同志家里见过他一面。这时他痴呆呆地站在那里,样子十分狼狈。我给他让出个座位,他坐下来了,不一会又莫明其妙地让给了别人,又是痴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徐志诚是个什么人,我们了若指掌,此时此地又在火车上出洋相,不得不引起我的警惕。
到了西安,我和韩灵锐在东大街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又象在重庆一样,天天跑车行货栈找“黄鱼车”。又花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一部去兰州的“黄鱼车”。这是一辆破旧的三吨道奇,与小轮JMC大卡车比较,寒酸得简直象一个叫花子。但货物却装了十来吨,走起来摇摇晃晃的,人坐在上面,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摔下来。
车是旧车,又超载了两三倍重量的货物,跑不了多远就停下来修理一次。当时有个顺口溜,用十个数字描绘这种情况:“一去二三里,加水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一路上卡车又是加油,又是加水,又是修理,爬行了五六天,才到兰州。
我把由重庆生活书店买到的中共七大文件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给韩世翼、张玉珍和几位已到达兰州的同志传阅,我则住进了西北医院,一方面检查了一下身体,治了治一点小毛病,一方面迎候由新疆出来的同志。
六月十九日,我和爱人进城,走到南门外十字路口,看到由城里开出来一列带篷大卡车,走到十字路口停下来了。车篷上满是尘土,一望即知是经过长途跋涉的,心想也许是由新疆出来的。我们停住脚步,站在路边观望着。不一会,从离我们不远的一部卡车上跳下几个人来,拍打身上的尘土,我仔细一看,发现了于村同志,高兴极了。
于村同志是一九三八年由延安派到新疆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是搞戏剧的。我在新疆学院时,请他教过抗战歌曲,帮助排演过抗战话剧。一九四一年在反帝总会,我们在一起工作将近一年,还同台演出过话剧,我从来没对他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后来我被调到师范学校工作,于村同志曾骑马跑到十几里外的老满城专程去看我。这次,我冒着生命危险,飞越秦岭到雾都重庆给中共代表团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除了一般地受革命责任感的驱使外,也是出于对这些曾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师、同志、朋友的深厚情感。
我指着卡车惊喜地对爱人说:“那不是于村同志?!他们出来了!”心里想,“这次去重庆,总算没有白跑!”
据说,当晚他们被安顿在五泉山下的一个招待所里住,我邀集已到达兰州的“新盟”成员张玉珍、姚品兰、韩世翼、王琢成、桂声等同志,于晚饭后一同上五泉山。一边走,一边放声高唱新疆歌曲。我们想,他们一定会听出是我们在为他们而唱。可是第二天一看兰州小报,原来他们住的是东郊外七星墩,不是五泉山。而我们当时满怀革命激情,起劲地唱时,还以为他们真能听到咧!
整整二十年后,“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死党谢富治和他们在公安部的代理人李震、施义之,唆使他们豢养的“东方红战斗队”以诬陷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送进了监狱,一关六年,每天四个窝窝头,一碗清汤水,几乎饿死病死在狱中。罪名之一,就是硬说我把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人名单送给了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逼我非承认不可。与此同时,康生一伙也给由新疆狱中返回延安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迫害。
在新疆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并非一般的地下党,是应盛世才的请求,由延安公开派去的,或是去苏联治病,顺道留下来的,一部分是西路军留下来学航空技术的。谁是共产党人盛世才都知道,并被奉为上宾,委以要职。陈潭秋是党代表,毛泽民是财政厅长(后任民政厅长)、孟一鸣是教育厅长、潘柏南是和田警备司令、刘西屏是哈密行政长、黄义明是管军队财务的边防督办公署经理处长、黄火青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后调阿克苏任行政长)、汪哮春是《新疆日报》社社长、李宗林是编辑长、林基路是新疆学院教务长、李志梁是省立一中校长……,只是到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利用国内外局势逆转的时机,公开投靠蒋介石时,才把这些“昨日座上宾”变成了“今日阶下囚,”并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杀害。至于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他早早就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还派了个所谓“中央审判团”到新疆复审。“造反派”逼我承认把新疆在押中共人员名单送给了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只是说明他们无知。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追问我送名单的事,原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康生、江青这一帮大坏蛋,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就授意各“造反派”组织,揪所谓“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企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特别是空军许多负责干部都是新疆航空队的),妄想从我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一九七三年六月末,即在林彪事件之后,“造反派”对我的诬陷被揭穿了,不得不为我平反,放出监牢。
一天,我到三〇一医院去看一炮副政委谢良同志,他也是刚放出来不久,高血压、颈部骨质增生,心脏也不好。他一见我就以江西老表的浓重口音激动地说:“赵明同志呀,为了名单的事,我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毒打呀!”他指给我看头上和身上的伤痕,他们问我“名单是怎样送到重庆去的?交给了谁?”我答不出,就狠狠打我。那次在袁子钦家见面时好好谈谈就好了!
袁子钦,解放初期是总政干部部长,后升任总政副主任,他的爱人鲁毅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闲谈中,她提到谢良常到她家去,并打问过我。我说:“我知道他,没见过面,倒是很想见见。”她说:“那好办,哪天他到我家来,我打电话告诉你。”
果然,一天鲁毅同志打电话给我,“谢良同志今天中午到我家里来,你也来吧,一起在我家吃午饭!”我到时,谢良同志已经先到。他一见我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到重庆送名单的就是你!”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望着他的眼晴说:“开出名单,给主席写信的就是你!”
我怕人家说我“夸功”,从来不提到重庆送名单的事,就是在自传中,也只简单提了一句。这时谢良同志没有往下问,我也就没有往下说。两人亲热地在院中肩并肩地照了一个半身像片,然后就入席吃中午饭,再没提及送名单的事,因之,他不知道送名单的全部过程。“文革”中“造反派”一追问,他说不清,道不明,白白挨了许多顿揍。这次我到三○一医院去看他,他才要我讲了送名单的整个过程。当我谈到把名单亲自交给了魏传统同志时,他说:“魏传统?!他就在这里养病,在我隔壁住。”问我:“你想不想看看他?”我说:“我想去,知道知道他收到名单以后怎么办了。”他说:“走,我领你去!”
谢良同志拄着拐杖领我到了隔壁病房,见了魏传统同志。他已不是我二十七年前见的那个样子了,那时清瘦,现在胖了,面色红润了。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点不显得老。谢良同志做了介绍,当说起送名单的事时,魏统传同志说:“文革中有人来调查过,我写了证明材料。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穿着一身浅灰色西服,当着我的面,由西服垫肩里拆出来名单,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看后,做为特急件,第二天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南京,交给了周总理。那时中共代表团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曾家岩十号留给了中共四川省委,我当时是四川省委秘书长。”
后来由读到过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得知:周总理拿到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后不久,正值张治中先生要到新疆接任省府主席职务。周总理对张治中先生说:“新疆监狱中还押着我们一批人,请你到新疆后,务必帮忙给送回延安去。”并把名单交给了他。张治中先生未负周总理的委托,到新疆后,亲自到狱中看望了这批同志,然后派了十辆大卡车,由刘亚哲护送,把这批同志安全地护送回了延安。
我送给中共代表团的名单上一共开列了一百六十二个名字,除去叛徒及其家属外,由乌鲁木齐出发时是一百三十一人,路途上有两个孩子病故,到达延安的是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马明方、方志纯、李宗林、刘护平、李渥如、高登榜、吉合、谢良、张子意、吕黎平、方槐、袁彬、黎明、金生、郭慎先、李志梁、张东月、李何、于村、白大方、陈浩然、王韵雪、朱旦华、陈茵素、沈谷南等党政军和文教方面的负责干部及烈士家属。我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应邀去新疆参加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见到郑英(在新疆时叫李霞,廖志高同志爱人)同志,她告诉我:中共代表团由南京撤回延安时,她正在中组部工作,我们送的那份名单,由她经手归档的。
这批人到延安时,朱总司令曾到十里之外去迎接,毛主席亲自接见,延安各界开了欢迎大会,表示亲切慰问,然后分头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文革”中不少同志又重遭迫害,李宗林、沈谷南、白大方、曹建培、胡鉴等人被迫害致死,马明方、杨之华被囚死牢中,刘护平出狱后没有离开过医院,张子意出狱后常年生病,死于医院中……
宋诗人黄庭坚有两句名句:“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当年在新疆工作过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经受了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道路,无论是幸存者,也无论是牺牲者,他们确实是点污不沾,纯贞自洁的花朵——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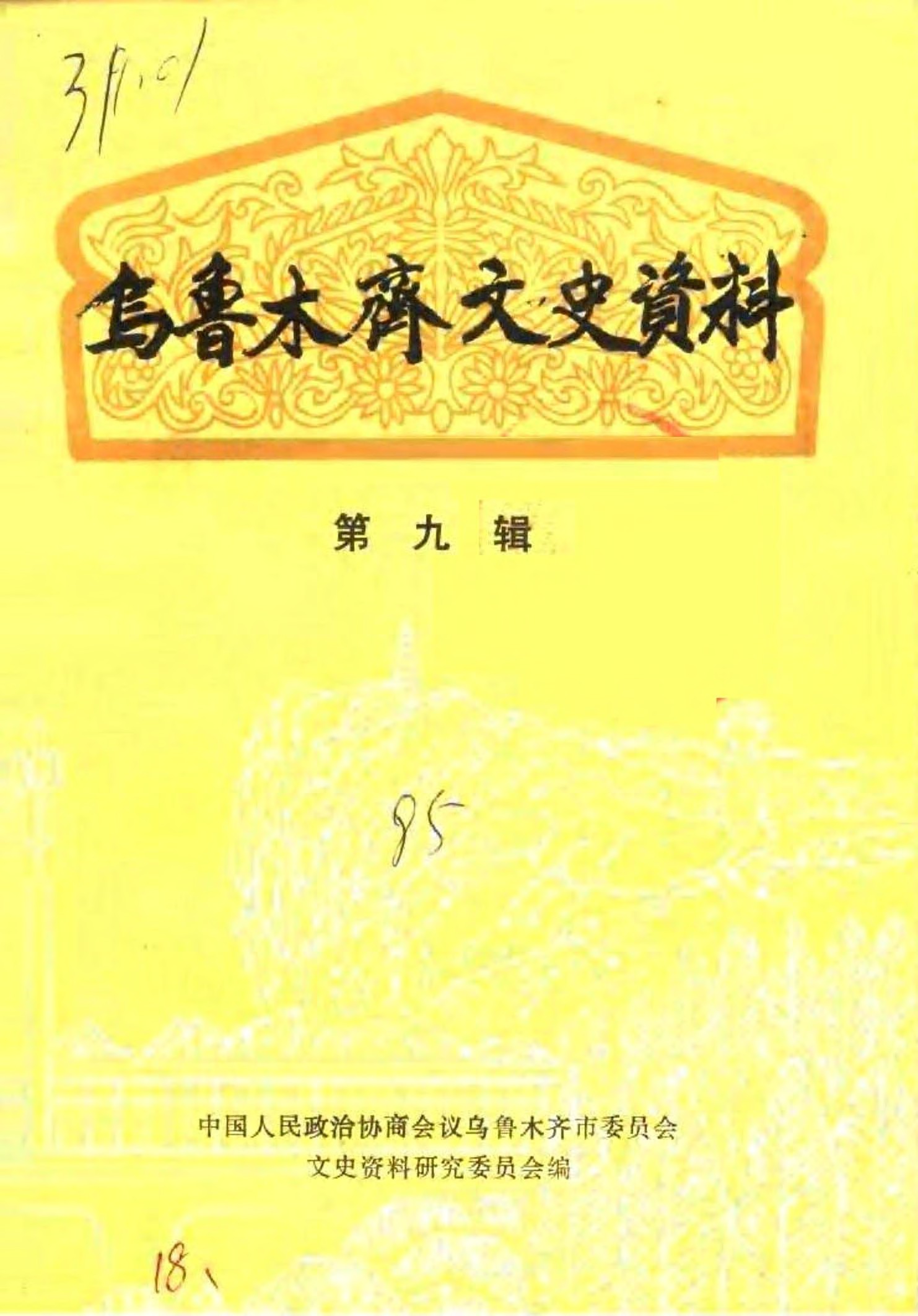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 第九辑》
出版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出版地:1985
本书是一部资料集。收录了乌鲁木齐各个领域代表人物回忆的文章等,以便了解乌鲁木齐的历史发展。章节包含:文史资料选辑、人物传记、地方风土。本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