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狼患见闻
| 内容出处: | 《金塔文史资料第一—八辑合订本(三)》 图书 |
| 唯一号: | 292720020230001319 |
| 颗粒名称: | 旧社会的狼患见闻 |
| 分类号: | I251 |
| 页数: | 3 |
| 页码: | 302-30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旧社会时期金塔县遭受了狼害的困扰。狼在偏僻的乡村出没,袭击伤害人畜,成为社会公害。回忆中描述了一些真实的狼害事件。在解放前后,旧县府没有采取措施消除狼害,导致狼患四起,给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 |
| 关键词: | 金塔县 狼害 社会公害 |
内容
狼,这种残忍凶恶的野兽,旧社会一度时期,在偏僻的乡村到处流窜,隐伏在沙丘、柴墩或沟渠等暗处,突然袭击伤害人畜,已成为社会公害。兹据各方亲历者回忆当时恶狼为害的一些真实惨状,综合叙述如下:
张文质回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因公务与警察蔡兴福去东区乡(现三合、东坝、大庄子)一带,路经大柳林,听说梁学仁的6岁女孩被狼叼去;转到头墩,又有该村张家的男孩被狼食;又转到牛头湾,住在亲戚张其成家,正是那天,其兄张其瑞正在棉田中锄草,8岁男孩在埂边玩耍,猛听叫唤,抬头已见狼把孩子衔上,张急忙把锄头扔下就追,趁狼放下孩子换气的之机,张将孩子夺回抱在怀中,狼见食物被夺,反扑过来,可惜张手中无物,一手抱孩子,一手脱下鞋子打狼,狼又把孩子从张肩上叼去,张也喘气倒地,后面人闻声追来,孩子已被咬死。一次下夹墩湾(现属芨芨乡)有魏姓婆媳俩在田中薅草,忽听身边的小孩叫唤,媳妇大嚎,婆子忙把手中的铁铲向狼掷去,击中狼鼻,狼痛张口,孩子挣脱得救,狼也跑了。据说那年全县有17个男女孩子死于狼口。至于狼吃羊只甚至吃小牛、骆驼,更是常事,真是豺狼当道,令人感叹不已。
又据王成相回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狼为患更甚。有时狼单独行动,有时成群结队,人畜伤亡甚大,尤其磨三分、旧寺墩、生地湾一带(现古城、西坝等地),饿狼出没骚扰,人畜极不安全。那年春季王跟父亲到后墩三塘河沿放羊,猛然发现有14只狼扑向羊群,父亲边吼叫,边唤来周围放牧人帮助防护,当时有十多个壮年小伙子,各执棍棒向狼群进攻,才把狼群撵跑。那时候无人敢单身放牧,甚至不敢单身干活。威虏七号(现古城光明村)农民张宗年家境贫寒,买不起灯油,从田间回来摸黑坐在厨房门槛上吃晚饭,冷不防一狼扑院内叼走小孩,父母急追,狼已把小孩脸面撕破,虽未毙命,但右眼致瞎,长成疤脸。还有王俊章7岁的男孩在房顶玩耍,从屋后下房时亦被墙后窥探已久的饿狼咬死。现在常见有个别老年人面容毁坏,缺耳少腮,口鼻歪斜,人称“狼疤吃”,都是当年狼口余生者。
由于旧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狼害,任其豺狼繁殖蔓延,造成狼患四起,贻害无穷。
当时医药条件差,被狼咬伤者抢救困难,当地唯一的一个医生叫华来福,住中东乡团结村王安吉家,配备治疗狼伤药物,常有被狼咬伤者,远道用驴驮、车拽来华处求治。据华先生说,经他手治好的狼伤者大小有30余人,还有重伤致死,或未及医疗,或就地咬死,街上逃跑吞食大人小孩两年内约计有数十人之多。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生活,提倡急切消灭狼害,把打狼列为保障人民生计的重任来抓,并把这项任务交建设科主办,动员各乡完成,由副县长成发昌督导,并采取以下措施:
(1)动员各乡勇敢、机智、有经验的土枪手、民兵,用猎枪打,挟脑挟,挖狼穴,捉狼崽,千方百计肃清狼源。
(2)在狼出没最多的生地湾(现生地湾农场)组织八个土枪手、民兵等参加的打狼队,并发给步枪,由社主任王约章率领远出寻狼窝、掏狼娃,打潜伏之狼。
(3)通函邻县市及额济纳旗联合消灭逃入之狼。
(4)县政府为调动广大群众打狼的积极性,规定打死大小狼只,以交验狼皮、狼娃为据,每只奖人民币12元,铁挟脑一副,以资鼓励。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很快在全县掀起了打狼高潮。如中东三湾沟村赵生梓只身带刀,深入狼穴,抓出大狼1只,狼娃3只;原生地湾农业社副主任葛天培一天挖了12只狼娃,用筐驮交政府;古城一姓阎的民兵挖狼洞掏狼娃7只,挟捉大狼5只,一年中共捉大小狼12只。仅1953年统计,全县共消灭大小狼127只。经过逐年消灭,狼患逐年减少,现在境内狼已基本绝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张文质回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因公务与警察蔡兴福去东区乡(现三合、东坝、大庄子)一带,路经大柳林,听说梁学仁的6岁女孩被狼叼去;转到头墩,又有该村张家的男孩被狼食;又转到牛头湾,住在亲戚张其成家,正是那天,其兄张其瑞正在棉田中锄草,8岁男孩在埂边玩耍,猛听叫唤,抬头已见狼把孩子衔上,张急忙把锄头扔下就追,趁狼放下孩子换气的之机,张将孩子夺回抱在怀中,狼见食物被夺,反扑过来,可惜张手中无物,一手抱孩子,一手脱下鞋子打狼,狼又把孩子从张肩上叼去,张也喘气倒地,后面人闻声追来,孩子已被咬死。一次下夹墩湾(现属芨芨乡)有魏姓婆媳俩在田中薅草,忽听身边的小孩叫唤,媳妇大嚎,婆子忙把手中的铁铲向狼掷去,击中狼鼻,狼痛张口,孩子挣脱得救,狼也跑了。据说那年全县有17个男女孩子死于狼口。至于狼吃羊只甚至吃小牛、骆驼,更是常事,真是豺狼当道,令人感叹不已。
又据王成相回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狼为患更甚。有时狼单独行动,有时成群结队,人畜伤亡甚大,尤其磨三分、旧寺墩、生地湾一带(现古城、西坝等地),饿狼出没骚扰,人畜极不安全。那年春季王跟父亲到后墩三塘河沿放羊,猛然发现有14只狼扑向羊群,父亲边吼叫,边唤来周围放牧人帮助防护,当时有十多个壮年小伙子,各执棍棒向狼群进攻,才把狼群撵跑。那时候无人敢单身放牧,甚至不敢单身干活。威虏七号(现古城光明村)农民张宗年家境贫寒,买不起灯油,从田间回来摸黑坐在厨房门槛上吃晚饭,冷不防一狼扑院内叼走小孩,父母急追,狼已把小孩脸面撕破,虽未毙命,但右眼致瞎,长成疤脸。还有王俊章7岁的男孩在房顶玩耍,从屋后下房时亦被墙后窥探已久的饿狼咬死。现在常见有个别老年人面容毁坏,缺耳少腮,口鼻歪斜,人称“狼疤吃”,都是当年狼口余生者。
由于旧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狼害,任其豺狼繁殖蔓延,造成狼患四起,贻害无穷。
当时医药条件差,被狼咬伤者抢救困难,当地唯一的一个医生叫华来福,住中东乡团结村王安吉家,配备治疗狼伤药物,常有被狼咬伤者,远道用驴驮、车拽来华处求治。据华先生说,经他手治好的狼伤者大小有30余人,还有重伤致死,或未及医疗,或就地咬死,街上逃跑吞食大人小孩两年内约计有数十人之多。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生活,提倡急切消灭狼害,把打狼列为保障人民生计的重任来抓,并把这项任务交建设科主办,动员各乡完成,由副县长成发昌督导,并采取以下措施:
(1)动员各乡勇敢、机智、有经验的土枪手、民兵,用猎枪打,挟脑挟,挖狼穴,捉狼崽,千方百计肃清狼源。
(2)在狼出没最多的生地湾(现生地湾农场)组织八个土枪手、民兵等参加的打狼队,并发给步枪,由社主任王约章率领远出寻狼窝、掏狼娃,打潜伏之狼。
(3)通函邻县市及额济纳旗联合消灭逃入之狼。
(4)县政府为调动广大群众打狼的积极性,规定打死大小狼只,以交验狼皮、狼娃为据,每只奖人民币12元,铁挟脑一副,以资鼓励。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很快在全县掀起了打狼高潮。如中东三湾沟村赵生梓只身带刀,深入狼穴,抓出大狼1只,狼娃3只;原生地湾农业社副主任葛天培一天挖了12只狼娃,用筐驮交政府;古城一姓阎的民兵挖狼洞掏狼娃7只,挟捉大狼5只,一年中共捉大小狼12只。仅1953年统计,全县共消灭大小狼127只。经过逐年消灭,狼患逐年减少,现在境内狼已基本绝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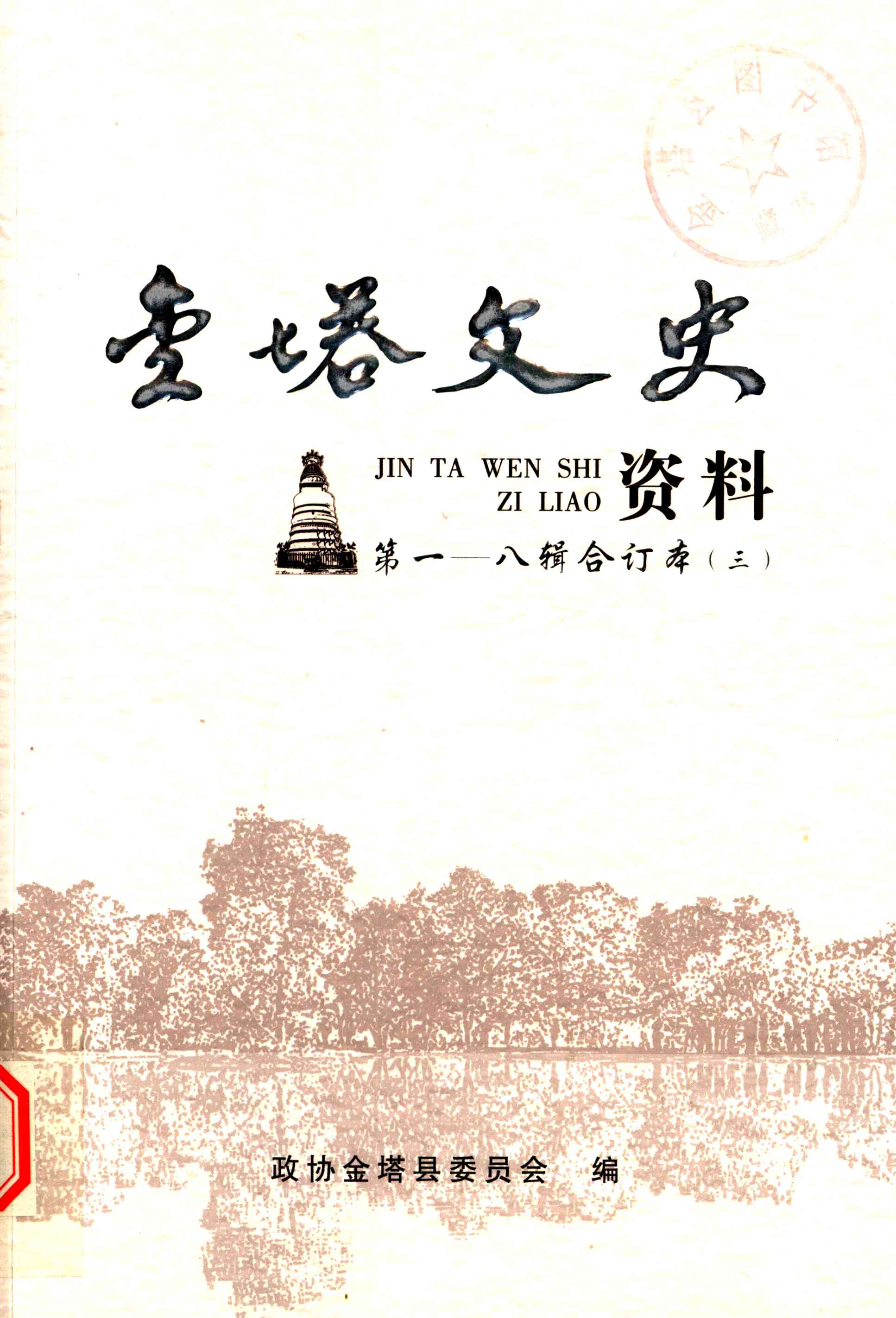
相关地名
金塔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