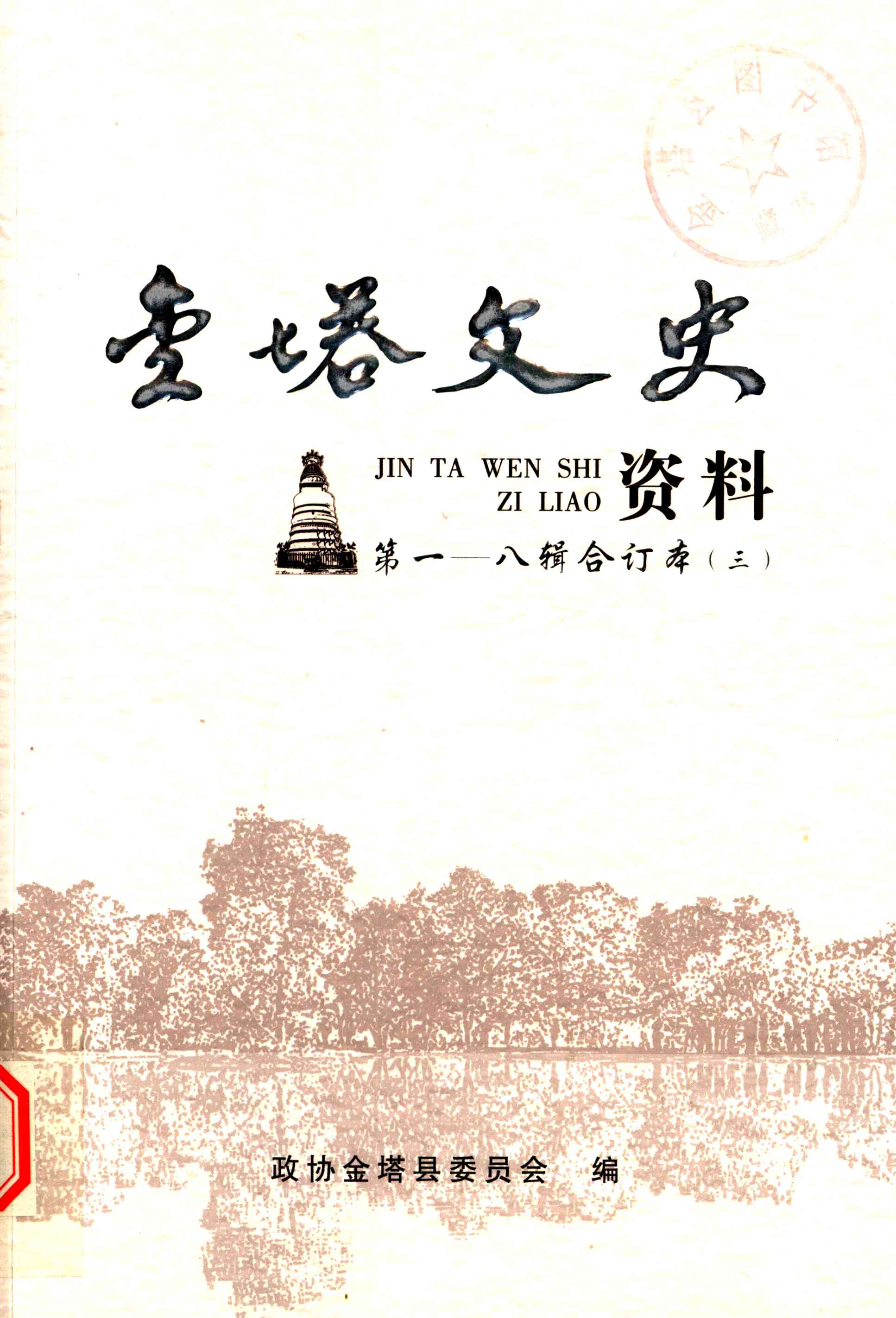上海支教青年在金塔
| 内容出处: | 《金塔文史资料第一—八辑合订本(三)》 图书 |
| 唯一号: | 292720020230001300 |
| 颗粒名称: | 上海支教青年在金塔 |
| 分类号: | K206.6 |
| 页数: | 4 |
| 页码: | 241-24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1956年,甘肃省教育厅派人去上海招聘青年教师,他们毅然报名参加支边工作。一列火车从上海出发,载着近千名支边青年来到甘肃。他们经历了长途旅行,最终分配到各个县进行支教。他们在金塔县坚守岗位,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见证了金塔的发展变化。他们的付出和努力使他们无愧于金塔教育。 |
| 关键词: | 金塔县 上海 支教 |
内容
1956年,甘肃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提高师资水平、发展本省基础教育”的部署,派专人去上海进行招聘青年教师的工作。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青年学生中动员支边人员,当时尚属首次。去沪招教的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各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深入中学、街道、里弄进行宣传,召开毕业生和家长座谈会,做思想教育工作,在“把一腔热血奉献给西北边疆教育事业”口号的感召下,很多青年毅然在报名册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同年3月12日上午,一列专送支边青年去甘肃的火车在上海站待发。虽没有送行仪式,但场面确实是空前的。上千名没出过远门、20岁左右的支边青年与数倍于送行的家长、亲属频频告别,连连嘱咐,汇成了让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情景。火车刚出上海站,这些以前互不相识的青年开始交谈,互相询问:何校念书?家住哪里?当谈到双方都了解的人或事时,发出激动的共鸣。有的此时才明白同住一条街道,甚至一条里弄内,大城市的繁杂使这之前他们只能是相互陌路,支边的号召把他们变成为同行,喊声、笑声此起彼伏。
由于长途坐车,大家的腿、脚都肿胀的厉害。第五天车抵兰州,全体青年在兰州住宿一夜,人们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当时兰州还很落后,看不出是个省会的样子,街道狭小,平房、土房是主体,自来水尚不普遍,多是拉运黄河水的驴车、马车。兰州一宿后,绝大部分人继续西行,这给大家认为兰州是终点的想法,写了个大大的“不”字。兰州过后大片戈壁滩愈来愈多,西北荒凉的面貌展现在这些青年面前。车到武威又留下了一批人,车厢空位更多,继续西行的青年们情绪也显得不安。当时兰新线刚铺到张掖,在张掖留下一部分人以后,被分配到洒泉的支边青年只得乘汽车前行。在城市里常坐电车的青年第一次坐敞篷大卡车长途旅行。既感新鲜又不舒服。上路后不久就刮起大风,西北春天的狂风,向这批南方青年显示了它的威力。回到酒泉已是晚上,个个都成了“土人”。当时分到酒泉的支教估计有300名。休整了一天就投入了紧张的任教培训。酒泉师范2个班,酒泉中学4个班,全部是正规的中等师范教材。要把两年的师范主要课程压缩在半年内学完,可以想象学习的紧张程度。由于上海青年从小所受的基础教育扎实,接受能力及领悟能力较强,尽管学习进度快,但学习成绩都不错。当时酒泉虽然城区建设简陋,但学习环境比较好,专区领导对上海青年的生活,尽了最大努力予以照顾。主食基本是大米,副食也较丰富。学习紧张,大家都得全身心的投入,所以除偶而有个别女生由于想家,有“嚎啕”的事外,整体的情绪是安定的。紧张的半年过去了,学习后期才知道,酒泉县并非最终的工作地点,分配去其他各县又是一次考验。当时留在酒泉县的约占学习人数的一半,其余都分在敦煌、安西、玉门、金塔4县。金塔是各县分配人数较少的县,整整30名。县上派柴政源同志把沪籍支教青年接回金塔。那时城内荒凉冷落,下车后大家还在问:“县城在哪里?”
到金塔离开校还有一段时间,又在城关镇的一所民办小学里集中学习了10多天后,同当时全县6所完小的校长、教导主任一起进行开学前的辅导,并对支边教师进行了工作分配,县长张和祥还作了专门的讲话,介绍了金塔的情况,勉励沪籍教师扎根金塔。教育科长李春智主持了分配会议,少数几个人分配在县宣传部、教育科、文化科、文化馆等单位,南关小学分了8人,县城幼儿园分了1人,其余都分在农村的二完小(现东坝大坝)、三完小(现中东镇)、四完小(现古城乡)、鼎新进化完小、三金乡金石完小(现金塔乡东沟)等5所小学。到学校后生活反差之大,是以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当时金塔城乡都没电,还得适应夜晚在煤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面食为主的一日两餐集体伙食成了家常饭。1956年沪籍教师在甘肃度过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在旧庙房、纸糊窗及简陋的取暖条件下,很多人手、脸冻肿,脚上长了冻疮。语言隔阂,习俗差异,又都是对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沪籍年轻教师生活上的磨炼,但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宽松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大搞勤工俭学,教师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时间数倍于前,甚至不分白天黑夜,有的学校教师白天上课,晚上还有深翻地的任务。1959年、1960年又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挨了饿,身体出现浮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近半数沪籍教师回了上海。1958年11月酒金两县合并后,章关寅等8人调到洒泉城关镇各小学任教,1964年何永华、谢育征调到金塔,他们夫妇俩最初是被分配在高台县。到1965年,金塔还有11名沪籍教师,大多在农村学校工作。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1973年沈福寿调酒泉。1985年梁星海调回上海。为照顾单身,吴惠龙1984年调安徽。1986年后至今留在金塔的还有赵惠娟、冯美云、米国伟、周惠英、何永华、谢育征、李棨、黄凤珍等8人。这些扎根金塔的沪籍教师现在都已年过半百,有的不只是两鬓染霜,而已是满头银丝了,他们的子女大都已投身于本地建设之中。
金塔解放至今47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却生活了41年。41年对一个人来说并不短暂,而且是一生中最富色彩的阶段,他们目睹了巨大变化,从无电无自来水、满目荒夷、似城非城的旧县城、群众勉强温饱的生活,到今天马路宽阔笔直、高楼林立面貌焕然一新的县城、步向小康的广大农村,40多年的沧桑,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外来见证人,因而对金塔的一草一木怀有难忘的情怀,而且这变化中也有各自的心血辛苦,这种感情就格外珍贵。他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和10多万金塔人民的期望,他们中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班主任,有的获得了省地园丁奖,有的被树为优秀党员,有的成了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尽管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弱点和不足,但值得自豪的一点:把服从组织分配为天职,即使在教师改行成风的前些年月里,他们没有一人主动提出不当教师,有几个人离开教育进入其他行列,但都是组织需要而调动。这种对教育事业执着的爱,正是在教育界长期工作所形成的。金塔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对他们极大的慰籍。旧庙孤灯的教学条件早已成为历史,城乡崭新的校舍、教学楼、电化教学手段,学生统一的着装,都在告诉他们,党的尊师重教的战略部署由蓝图逐步变成了现实,教育对象的成长给了他们最好的精神回报,他们当年的学生现在正活跃在本县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城乡各条战线上,大批本县籍教师走上讲台,其中有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撑起了金塔教育的支柱。后继有人,事业兴旺的景象使他们完全忘记了往日的凄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天,五十年代中期从上海到金塔支教,现在教育界的或不在教育界的,退休的或在职的,在金塔或已调离到外县的,仍深深眷恋着金塔这方热土,在某一天他们撒手“西去”时,会对子女说:“我无愧于金塔,无愧于金塔教育,无愧于此生!”
(本文作者系原金塔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由于长途坐车,大家的腿、脚都肿胀的厉害。第五天车抵兰州,全体青年在兰州住宿一夜,人们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当时兰州还很落后,看不出是个省会的样子,街道狭小,平房、土房是主体,自来水尚不普遍,多是拉运黄河水的驴车、马车。兰州一宿后,绝大部分人继续西行,这给大家认为兰州是终点的想法,写了个大大的“不”字。兰州过后大片戈壁滩愈来愈多,西北荒凉的面貌展现在这些青年面前。车到武威又留下了一批人,车厢空位更多,继续西行的青年们情绪也显得不安。当时兰新线刚铺到张掖,在张掖留下一部分人以后,被分配到洒泉的支边青年只得乘汽车前行。在城市里常坐电车的青年第一次坐敞篷大卡车长途旅行。既感新鲜又不舒服。上路后不久就刮起大风,西北春天的狂风,向这批南方青年显示了它的威力。回到酒泉已是晚上,个个都成了“土人”。当时分到酒泉的支教估计有300名。休整了一天就投入了紧张的任教培训。酒泉师范2个班,酒泉中学4个班,全部是正规的中等师范教材。要把两年的师范主要课程压缩在半年内学完,可以想象学习的紧张程度。由于上海青年从小所受的基础教育扎实,接受能力及领悟能力较强,尽管学习进度快,但学习成绩都不错。当时酒泉虽然城区建设简陋,但学习环境比较好,专区领导对上海青年的生活,尽了最大努力予以照顾。主食基本是大米,副食也较丰富。学习紧张,大家都得全身心的投入,所以除偶而有个别女生由于想家,有“嚎啕”的事外,整体的情绪是安定的。紧张的半年过去了,学习后期才知道,酒泉县并非最终的工作地点,分配去其他各县又是一次考验。当时留在酒泉县的约占学习人数的一半,其余都分在敦煌、安西、玉门、金塔4县。金塔是各县分配人数较少的县,整整30名。县上派柴政源同志把沪籍支教青年接回金塔。那时城内荒凉冷落,下车后大家还在问:“县城在哪里?”
到金塔离开校还有一段时间,又在城关镇的一所民办小学里集中学习了10多天后,同当时全县6所完小的校长、教导主任一起进行开学前的辅导,并对支边教师进行了工作分配,县长张和祥还作了专门的讲话,介绍了金塔的情况,勉励沪籍教师扎根金塔。教育科长李春智主持了分配会议,少数几个人分配在县宣传部、教育科、文化科、文化馆等单位,南关小学分了8人,县城幼儿园分了1人,其余都分在农村的二完小(现东坝大坝)、三完小(现中东镇)、四完小(现古城乡)、鼎新进化完小、三金乡金石完小(现金塔乡东沟)等5所小学。到学校后生活反差之大,是以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当时金塔城乡都没电,还得适应夜晚在煤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面食为主的一日两餐集体伙食成了家常饭。1956年沪籍教师在甘肃度过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在旧庙房、纸糊窗及简陋的取暖条件下,很多人手、脸冻肿,脚上长了冻疮。语言隔阂,习俗差异,又都是对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沪籍年轻教师生活上的磨炼,但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宽松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大搞勤工俭学,教师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时间数倍于前,甚至不分白天黑夜,有的学校教师白天上课,晚上还有深翻地的任务。1959年、1960年又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挨了饿,身体出现浮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近半数沪籍教师回了上海。1958年11月酒金两县合并后,章关寅等8人调到洒泉城关镇各小学任教,1964年何永华、谢育征调到金塔,他们夫妇俩最初是被分配在高台县。到1965年,金塔还有11名沪籍教师,大多在农村学校工作。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1973年沈福寿调酒泉。1985年梁星海调回上海。为照顾单身,吴惠龙1984年调安徽。1986年后至今留在金塔的还有赵惠娟、冯美云、米国伟、周惠英、何永华、谢育征、李棨、黄凤珍等8人。这些扎根金塔的沪籍教师现在都已年过半百,有的不只是两鬓染霜,而已是满头银丝了,他们的子女大都已投身于本地建设之中。
金塔解放至今47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却生活了41年。41年对一个人来说并不短暂,而且是一生中最富色彩的阶段,他们目睹了巨大变化,从无电无自来水、满目荒夷、似城非城的旧县城、群众勉强温饱的生活,到今天马路宽阔笔直、高楼林立面貌焕然一新的县城、步向小康的广大农村,40多年的沧桑,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外来见证人,因而对金塔的一草一木怀有难忘的情怀,而且这变化中也有各自的心血辛苦,这种感情就格外珍贵。他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和10多万金塔人民的期望,他们中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班主任,有的获得了省地园丁奖,有的被树为优秀党员,有的成了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尽管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弱点和不足,但值得自豪的一点:把服从组织分配为天职,即使在教师改行成风的前些年月里,他们没有一人主动提出不当教师,有几个人离开教育进入其他行列,但都是组织需要而调动。这种对教育事业执着的爱,正是在教育界长期工作所形成的。金塔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对他们极大的慰籍。旧庙孤灯的教学条件早已成为历史,城乡崭新的校舍、教学楼、电化教学手段,学生统一的着装,都在告诉他们,党的尊师重教的战略部署由蓝图逐步变成了现实,教育对象的成长给了他们最好的精神回报,他们当年的学生现在正活跃在本县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城乡各条战线上,大批本县籍教师走上讲台,其中有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撑起了金塔教育的支柱。后继有人,事业兴旺的景象使他们完全忘记了往日的凄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天,五十年代中期从上海到金塔支教,现在教育界的或不在教育界的,退休的或在职的,在金塔或已调离到外县的,仍深深眷恋着金塔这方热土,在某一天他们撒手“西去”时,会对子女说:“我无愧于金塔,无愧于金塔教育,无愧于此生!”
(本文作者系原金塔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