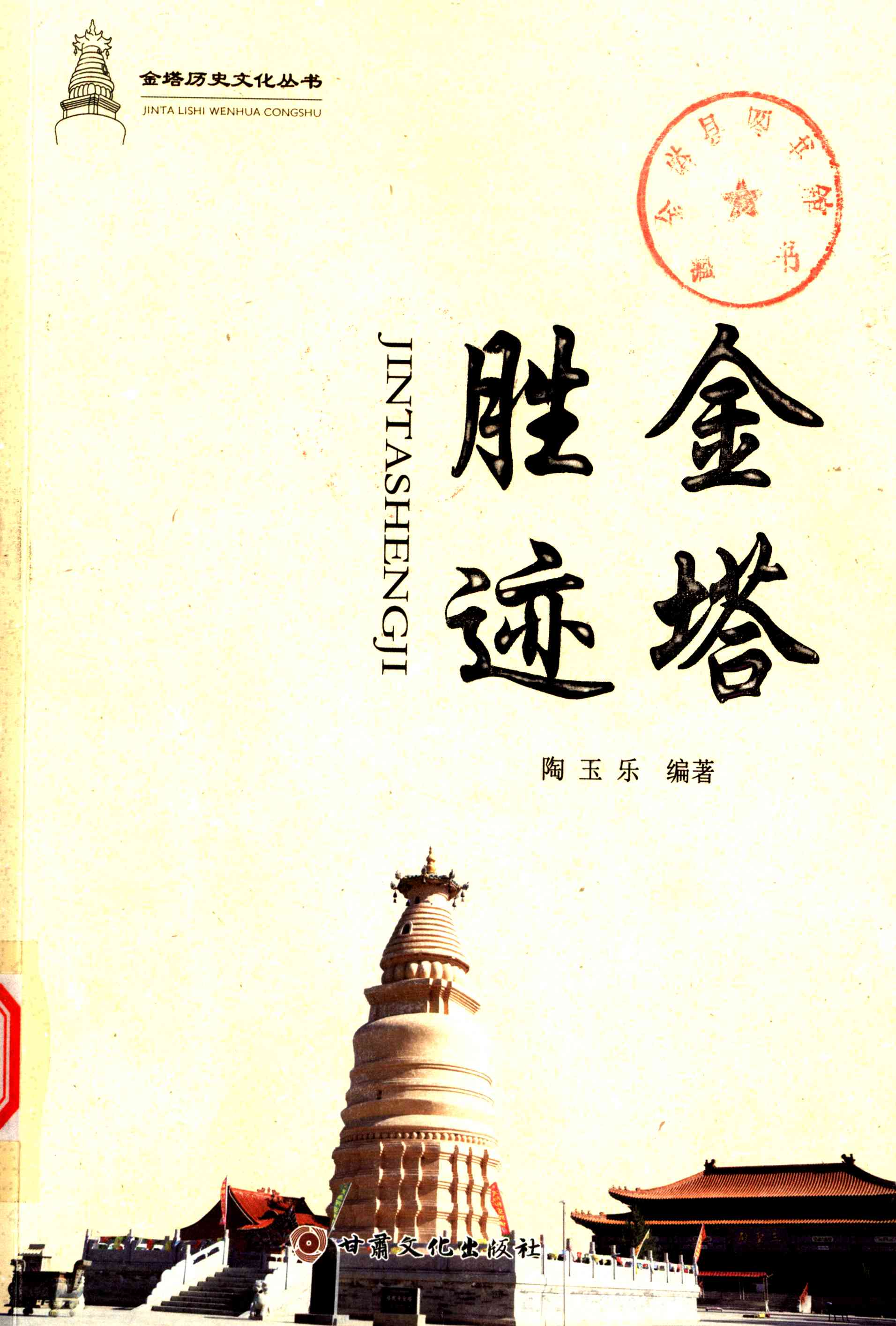内容
2011年4月,金塔县博物馆对金塔县板滩墓群内一座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该墓葬位于墓群西北角的戈壁滩上,墓冢为砂砾石堆积,呈圆球状,直径约3.6米,高约1.2米。有砂砾石堆积的明显墓道,呈东北-西南走向。墓道为斜坡形,宽2米,长约13米。墓门为圆形,块石封门。墓室结构为土洞单室墓,平面呈椭圆形,剖面呈半圆形,墓顶呈弧形。墓室东西长2.8米,南北宽1.8米,高约1.5米。为双人合葬墓。墓室被盗掘,棺木及人骨扰乱严重。棺木呈东西向摆放,北侧的棺木已损毁,仅见残片,南侧棺木较完整,木质为沙枣木。
本次清理共出土遗物21件,其中陶器3件,弦纹灰陶罐、灰陶灶、灰陶甑各1件;棺画1副,棺盖内侧并排画着5幅动物画像,有马、羊等动物形象;木牌楼1个,上下共有三层,6幅画面,内容为人物和松鹤;木版画11块,画面内容以人物和松鹤为主,一块木板用白、黑、黄三色画一白虎形象,昂首张口;带绳木塞1个;五铢钱2枚;粮食标本1份,在旋纹灰陶罐中保存有糜子颗粒,已严重钙化。衣物疏1件,该衣物疏为一长方形木牍,已残缺不全,字迹模糊不清,所书文字从木牍右上角起头竖写,残存七行。依稀可辨有墨笔书写的“故布衫一领”“故纑群(裙)一领”“故口器一口”“故丝口口一量”“故口履一量”“二双”“故口衣一具”“杂衣物五十六种口”等字。据此推断,这可能是墓主人随葬物品的清单,即“衣物疏”。此衣物疏在金塔汉晋墓葬中首次发现,实属罕见。
衣物疏的发展演变过程
衣物疏是古人放置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清单。墓中随葬物品清单的习俗,在华夏文明中由来已久。衣物疏,是从遣册发展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遣策的一种。遣策是战国时期先秦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遣册一名昉自《仪礼·既夕》,该篇有“书赗冒于方”“书遣于策”二句,“方”指木板,“策”指竹简。陈直先生释曰:“写于方者,为丧礼之登记簿,写于策者,为随葬品之清单。”据《仪礼·既夕礼》载:“凡将礼,必请而后拜送。兄弟,、奠可也。所知,则赗冒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东汉郑玄注云:“方,板也。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又云:“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唐贾公颜疏:“以宾客所致,有赙、有赗、有赠、有奠,直云‘书赗’者,举首而言,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数不同。”又云:“云‘策,简’者,编连为策,不编为简。故《春秋左氏传》云南史氏执简以往,上书赗云方,此言书遣于策,不同者。《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以宾客赠物名字少,故书于方,则尽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赠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书之于策。”根据上述记载,记录与死者随葬的物品有“赗冒方”与“遣策”两种,前者是对助丧赠人员及其所赠物品的记录,书于方牍;后者是对遣送死人所用随葬物品的记录,书于简策,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从此墓葬中出土的衣物疏看,其内容为死者随葬物品,按《仪礼·即夕礼》之规定应该书于简册,但事实却是书写在“方”即木板上。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这种情况较多,故有学者认为:“书写赗赠材料与古书记载的不同,可能出于地域或时代差异的缘故”。“赗方”与“遣策”所记内容较为广泛,衣物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公羊传·隐公元年》载:“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何休注云:“赗,犹覆也;赙,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襚犹遗也,遗是助死之礼。知生者赗赙,知死者赠襚。”可见,在随葬物品中,有衣衾、车马、玩好、财货等,衣物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遣策应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就是较为单纯的随葬物品清单。所谓广义,就是记录与丧葬礼仪有关的各种物品,包括赗赙赠奠及随葬物品等。
遣策的类型主要有四种:一是记录随葬物品。这类遣策在已考古发现的遣册中占多数,记录的随葬物品有漆器、陶器、衣物、食物、乐器等。二是记录随葬物品和葬仪用物。这种既记随葬物品也记葬仪用物的遣策并不多见,其记录的内容较为丰富。所记物品大多是各种衣物、佩饰和日用品,其中有衣物和兵器注明物主,应为他人所赠。但有的这类遣册所记内容均不见实物,可能与葬仪有关。三是记录随葬衣物。一般用一块或二块木牍记录随葬衣物,与出土实物对照基本相符,有人因此称之为“衣物疏”或“衣物券”。这类“衣物疏”一般出现在汉晋时期的中小型墓葬中。四是记录葬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等。这类遣策只记录车马兵甲之类而不记随葬物品,所记录的内容在墓中找不到具体实物,可能专用于葬仪,主要见于战国楚墓出土遣策。
到了汉朝初年,古墓中又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遣策”的简牍,学者或称之为“告墓牍”,或名之曰“告地下官吏文”,有的学者也叫“告地策”。“告墓牍”与遣策虽然存在着渊源关系,但遣策仅是随葬物品的清单而已,而“告墓牍”虽然也有随葬品清单的作用,但已不像遣策那样详细地罗列随葬物品,具有了鲜明的宗教含义。这反映了在西汉前期,从战国以来单纯记录随葬品目录清单的遣策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希望通过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的官吏之间的行政手续移交,可以使死者在冥界过着与生前同样生活的观念。“告墓牍”实际上被当作一种冥界凭证,用以保障亡灵在冥界正当通行、居留和占有财物的权利。这一时期,在记录随葬物品内容颇为广泛的“赗方”与“遣策”的基础上,专门的“衣物疏”“物疏”“小物疏”等出现。在汉代的“衣物疏”中,并没有战国时期那种“赗方”与“遣策”的严格区分,而是融合了二者,而且所记也主要是衣、被一类。根据考古结果,汉初“物疏”记录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在汉武帝以前各墓出土的物疏简牍(即登记随葬物品的简牍)均出于棺外,如头箱、边箱内,而武帝以后各墓物疏牍均出于棺内。究其内容,出于棺外的物疏简牍记录内容比较全面,包括椁箱及棺内的随葬品;而出于棺内的物疏牍所记内容仅限于棺内,棺外椁内的随葬品则不予记录。这种差别可能是当时葬俗变化的一种反映。武帝以前实行单人葬,墓中棺内外的随葬品均为墓主一人所有;而武帝以后,出物疏牍的墓多为合葬墓,棺内随葬品为个人所有,而棺外随葬品可能为合葬者共同享有。所以把物疏牍放入棺内只记录棺内明确属于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基于对合葬的考虑,即棺外椁内的随葬品非一人独有,应为墓内合葬者共享之物。这件衣物疏因棺木腐朽损毁严重,无法判断其是在棺内还是棺外,但从书写内容看应为一人随葬衣物。随着人间社会土地买卖的盛行,约从东汉开始,又流行一种在墓中放置“墓莂”(俗称“买地券”)的习俗。就是模拟人间土地买卖的契券格式,虚构向神灵购买坟墓地权的契券,这种契约多数是刻在长方形的铅板上,也有的刻在玉板或书写在铁板、陶柱、青砖和石等物之上。待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在幕中放置一种陶质的“镇墓瓶”,瓶内有时还盛放朱砂、雄黄、水晶等物,瓶上有朱书文字和附录,当代学者称这种文书为“镇墓文”或“镇墓解除文”。镇墓文的主要内容为解殃文辞,其作用是以文告的形式,告诫地下鬼怪不能对死者进行侵扰,以便使生人家宅安宁。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地使者”的名义为主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生死有别,勿事纠缠。反映了早期道教的思想。汉代宗教神秘感趋于强烈,巫风兴盛,不但新出现多种源于方术迷信的丧葬文书,而且遣册也向巫风靠近。遣册原有的纪实功能似有退缩的趋势,其表现一为出现虚随葬物品的现象;二为所记物品渐专注于随身衣物,亦即由“器疏”向“衣物疏”转化。
魏晋时期,“告墓牍”与“镇墓文”渐行消失,“衣物疏”继续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定式,疏中虚随葬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疏中所记物品数量过大。例如“故黄金千两”,显然属于虚。有的后文缀以“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之句,“时见”即在场见证者。此墓葬中发现的白虎形象,可能就起到了见证的作用,可能还有青龙形象,可惜已被损毁。“青龙”“白虎”通常与“朱雀”“玄武”连用,是汉代人特喜称引的四方星宿之神。这种迷信性质的衣物疏有的主要是请神灵为死者的财物作证,有的主要是请神灵允许亡灵在冥界通行,有的两种祈愿并陈;有的直接以世俗语言正告他人(鬼魂)不得冒名认物,有的袭用“如律令”‘“急急如律令”之类巫术用语以借助于神。
南北朝时期,“衣物疏”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无论在内容还是性质上,与前期衣物疏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文书中多次出现的“敬移五道大神”和“故移”“事事依移”“从移令”等用语,表明其可能使用了当时同级官府部门之间公文来往的“移文”格式。皆为知会地下神灵一类的文告。唐代时,据《礼记·曲礼下》“书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门”条唐人孔颖达疏曰(20):“书方”者,此谓臣有死于公宫,应须凶具,此下诸物,并宜告而后入者也。书谓条录送死者对象数目多少,如今死人移书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书之,故云“书方”也。可见,唐代时把有关死者随葬品的清单称为“死人移书”。
综上所述,有关古代死人随葬品清单的发展演变,其实经历了“赗方”与“遣策”“告墓牍”与“衣物疏”(或“物疏”“小物疏”)、“死人移书”或“移文”几个阶段,不同的时代,与死者一同埋入地下的随葬品清单也有不同的名称。
考古价值
该衣物疏虽残缺不全,字迹多处漫漶不清,但从残存的字迹中依然可考述出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变化、服饰文化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此衣物疏在金塔首次发现,实属罕见,一方面填补了空白,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该地区这一时期的民俗和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佐证。衣物疏是古人放置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清单,它是从战国时期先秦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清单的遣册发展而来的。它起源于西汉,魏晋时已很盛行。它没有战国时期那种“赗方”与“遣策”的严格区分,而是融合了二者,而且所记也主要是衣、被一类。这件“衣物疏”从残存文字中看,也主要是衣、被一类。“衣物疏”中的“杂衣物五十六种口”,缺的字可能是“疏”,就是说这件衣物疏共记录了墓主人五十六件随葬衣物。这说明在魏晋时期,金塔与中原地区一样,也出现了随葬“衣物疏”的习俗。
可以考证魏晋衣物疏的书写格式和用词规范。据考古结果,魏晋衣物疏多以“质地+名称+数量词”的形式记录随葬衣物,这件衣物疏,基本上也是这种记录方式。如“布衫”“纑群(裙)”“口履”“口衣”就是衣物质地和名称。而“一领”“一量”“二双”“一具”则为数量词。在魏晋衣物疏中,“领”,主要用来称量衣被,以称量上衣的居多。如甘肃高台前凉墓《都中赵双衣物疏》牍记“故疏单衣一领”“故练幅衫一领”“故练大襦一领”“故练小襦一领”“故练被一领”,“具”主要用来修饰完整、成套的器物。如甘肃高台前凉墓《赵阿兹衣物疏》牍记“故紫春囊一具”“故紫搔囊一具”“故刀尺一具”等。“量”作为量词,从出土的魏晋衣物疏中看,全部用来修饰鞋(靴)袜。江西南昌西晋吴应墓《衣物疏》牍记“故白布袜一量”“故丝履一量”;湖南长沙东晋墓《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石板记“故练袜一量”“故斑头履一量”;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晋墓《姬瑜衣物疏》牍记“故练袜一量”“故青纟履一量”;甘肃高台东晋胡运千墓《衣物疏》牍记“故履一量”等。“双”与“量”的用法基本相同,也多用来称量鞋(靴)袜。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服饰文化。从这件随葬衣物疏清单内容看,当时活着的人们希望死者在冥世继续生活,所以为他们陪葬了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一切物品,上至冠帽,下至鞋袜,春夏秋冬,里里外外应有尽有,如衣、裙、裤、面衣、鞋、袜、枕、被、褥、糸(丝)带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饰品,再现了当时这一地区居民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匈奴后,西汉王朝在金塔境内始置会水县,这也是金塔最早的建置。为了经营河西,阻止匈奴南下,汉王朝在酒泉郡北部,黑河通道险要位置处的会水、居延一带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设置长城塞防等防御体系,并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屯田。由于汉王朝的苦心经营,给会水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发展环境。加之会水绿洲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会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至西汉中期已是农牧兴盛、社会繁荣。东汉初年,光武帝为了尽快恢复遭到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推行讲文休武,与民休息以“柔道”治天下的政策,会水一带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东汉中期已达到鼎盛时期。曹魏政权控制河西之后,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经营河西地区,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西晋政权建立后,为巩固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社会经济曾呈现出短暂的繁荣局面。尤其是晋惠帝元康五年(前295年)改福禄县(今酒泉肃州)为会水县,充分说明了会水的影响力。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前526年)会水县弃,至此,历时500余年的会水县画上了句号。可以说,魏晋时期的会水县是金塔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裕,墓中随葬众多衣物也就不难理解。这件衣物疏中“布衫”“纑群(裙)”“布裙”“口履”“口衣”和“糸(丝)带”等衣物和饰品应有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妇女服装则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足上多穿履、靴等。因此,从这件衣物疏所列出的随葬衣物看,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
为研究金塔魏晋历史提供了依据。这件衣物疏,由于墓室早期被盗,衣物疏残缺不全,墓葬中未发现有纪年的文字记载,衣物疏中也未出现明确的纪年和人名,但从衣物疏的书写内容看,应为魏晋时期。首先,这件衣物疏中记载的都是实物,没有出现虚指,这明显是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定式。有的后文缀以“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之句,“时见”即在场见证者,此衣物疏因残缺严重,有无以上之句无从考证,但墓葬中发现的绘制于木板上的白虎形象,可能就起到了见证的作用,也许还有青龙形象,可能已被损毁。“青龙”“白虎”通常与“朱雀”“玄武”连用,是汉代人特喜称引的四方星宿之神。这种迷信性质的衣物疏有的主要是请神灵为死者的财物作证,有的主要是请神灵允许亡灵在冥界通行,有的两种祈愿并陈;有的直接以世俗语言正告他人(鬼魂)不得冒名认物,有的袭用“如律令”“急急如律令”之类巫术用语以借助于神。其次,从这件衣物疏中量词的使用情况看,“量”出现了许多次。李明晓认为“量”用法基本同“两”,称量鞋(靴)袜,不过只见于晋代简牍。从这一点看,此衣物疏的时代应该在晋代。
为研究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汉字演变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自觉的一个时期,书法艺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促使书法正式走向审美艺术之路,即开始了真正自觉地体现主体的生命意识。个性风度,气质品格,加之魏晋风度这种风气的盛行,更加给当时书法的发展根植了新鲜且肥沃的土壤,可谓真正达到了“随意”的状态。书法美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真正从记事转为任心,从象形变为表意,从书写变为书法,从实用变为审美的道路,魏晋书法在魏晋风度的笼罩下,逐渐走向了风格的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趋于成熟,孕育了王羲之、王献之、钟繇、索靖、王珣、陆机、张芝等举世闻名的大批书法家。并且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也随之确立。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这件衣物疏所用字体为行楷。由于魏晋人自由、解放的精神,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脱、纵情任情、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言行风范淋漓地表现出晋人的生活态度、文化心理和韵致风度,书法艺术也就成为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载体。这一时期,一种真正抒情的“纯”书法成熟了,这种书法的“纯”也就是一种美学思想,是“尚韵”的一种表现。“韵”体现在书风上,是一种飘逸妍美、简远清雅的书风。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中国书法开始了楷、行、草并行时代。从这件衣物疏的字体看,它间于行书和楷书之间,用笔随意洒脱,显示出秀整轻逸。它突破了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结构严谨、字形定型和提笔、顿笔、转笔等运用要求严格的特点,它将楷书的体势、点画变得圆转连带、变化多样,结字自由,用笔灵活、方便,很少有逆锋、顿笔、停笔等严格的运笔,行笔巧妙。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行楷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券中竖行之间间距基本匀称,而横行则依字布局,随机谋篇。如“一领”两字和“一具”两字,仅占一个字的位置,避免了“一”字因笔画过简所带来的空旷;而对于笔画过于繁复之字,如“裙”“双”等字则将整体布局适当紧凑匀称。这方衣物疏是普通老百姓随葬用品,这一宽松的民间环境,造就了其在总体布局上的无拘无束和朴拙真率,展示出奔放流畅、伸缩自如、亦方亦圆、跌宕起伏的风格,孕育出一种极富审美艺术的天趣新姿。魏晋时期是中国汉字书法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件衣物疏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的活标本。
本次清理共出土遗物21件,其中陶器3件,弦纹灰陶罐、灰陶灶、灰陶甑各1件;棺画1副,棺盖内侧并排画着5幅动物画像,有马、羊等动物形象;木牌楼1个,上下共有三层,6幅画面,内容为人物和松鹤;木版画11块,画面内容以人物和松鹤为主,一块木板用白、黑、黄三色画一白虎形象,昂首张口;带绳木塞1个;五铢钱2枚;粮食标本1份,在旋纹灰陶罐中保存有糜子颗粒,已严重钙化。衣物疏1件,该衣物疏为一长方形木牍,已残缺不全,字迹模糊不清,所书文字从木牍右上角起头竖写,残存七行。依稀可辨有墨笔书写的“故布衫一领”“故纑群(裙)一领”“故口器一口”“故丝口口一量”“故口履一量”“二双”“故口衣一具”“杂衣物五十六种口”等字。据此推断,这可能是墓主人随葬物品的清单,即“衣物疏”。此衣物疏在金塔汉晋墓葬中首次发现,实属罕见。
衣物疏的发展演变过程
衣物疏是古人放置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清单。墓中随葬物品清单的习俗,在华夏文明中由来已久。衣物疏,是从遣册发展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遣策的一种。遣策是战国时期先秦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遣册一名昉自《仪礼·既夕》,该篇有“书赗冒于方”“书遣于策”二句,“方”指木板,“策”指竹简。陈直先生释曰:“写于方者,为丧礼之登记簿,写于策者,为随葬品之清单。”据《仪礼·既夕礼》载:“凡将礼,必请而后拜送。兄弟,、奠可也。所知,则赗冒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东汉郑玄注云:“方,板也。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又云:“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唐贾公颜疏:“以宾客所致,有赙、有赗、有赠、有奠,直云‘书赗’者,举首而言,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数不同。”又云:“云‘策,简’者,编连为策,不编为简。故《春秋左氏传》云南史氏执简以往,上书赗云方,此言书遣于策,不同者。《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以宾客赠物名字少,故书于方,则尽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赠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书之于策。”根据上述记载,记录与死者随葬的物品有“赗冒方”与“遣策”两种,前者是对助丧赠人员及其所赠物品的记录,书于方牍;后者是对遣送死人所用随葬物品的记录,书于简策,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从此墓葬中出土的衣物疏看,其内容为死者随葬物品,按《仪礼·即夕礼》之规定应该书于简册,但事实却是书写在“方”即木板上。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这种情况较多,故有学者认为:“书写赗赠材料与古书记载的不同,可能出于地域或时代差异的缘故”。“赗方”与“遣策”所记内容较为广泛,衣物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公羊传·隐公元年》载:“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何休注云:“赗,犹覆也;赙,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襚犹遗也,遗是助死之礼。知生者赗赙,知死者赠襚。”可见,在随葬物品中,有衣衾、车马、玩好、财货等,衣物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遣策应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就是较为单纯的随葬物品清单。所谓广义,就是记录与丧葬礼仪有关的各种物品,包括赗赙赠奠及随葬物品等。
遣策的类型主要有四种:一是记录随葬物品。这类遣策在已考古发现的遣册中占多数,记录的随葬物品有漆器、陶器、衣物、食物、乐器等。二是记录随葬物品和葬仪用物。这种既记随葬物品也记葬仪用物的遣策并不多见,其记录的内容较为丰富。所记物品大多是各种衣物、佩饰和日用品,其中有衣物和兵器注明物主,应为他人所赠。但有的这类遣册所记内容均不见实物,可能与葬仪有关。三是记录随葬衣物。一般用一块或二块木牍记录随葬衣物,与出土实物对照基本相符,有人因此称之为“衣物疏”或“衣物券”。这类“衣物疏”一般出现在汉晋时期的中小型墓葬中。四是记录葬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等。这类遣策只记录车马兵甲之类而不记随葬物品,所记录的内容在墓中找不到具体实物,可能专用于葬仪,主要见于战国楚墓出土遣策。
到了汉朝初年,古墓中又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遣策”的简牍,学者或称之为“告墓牍”,或名之曰“告地下官吏文”,有的学者也叫“告地策”。“告墓牍”与遣策虽然存在着渊源关系,但遣策仅是随葬物品的清单而已,而“告墓牍”虽然也有随葬品清单的作用,但已不像遣策那样详细地罗列随葬物品,具有了鲜明的宗教含义。这反映了在西汉前期,从战国以来单纯记录随葬品目录清单的遣策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希望通过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的官吏之间的行政手续移交,可以使死者在冥界过着与生前同样生活的观念。“告墓牍”实际上被当作一种冥界凭证,用以保障亡灵在冥界正当通行、居留和占有财物的权利。这一时期,在记录随葬物品内容颇为广泛的“赗方”与“遣策”的基础上,专门的“衣物疏”“物疏”“小物疏”等出现。在汉代的“衣物疏”中,并没有战国时期那种“赗方”与“遣策”的严格区分,而是融合了二者,而且所记也主要是衣、被一类。根据考古结果,汉初“物疏”记录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在汉武帝以前各墓出土的物疏简牍(即登记随葬物品的简牍)均出于棺外,如头箱、边箱内,而武帝以后各墓物疏牍均出于棺内。究其内容,出于棺外的物疏简牍记录内容比较全面,包括椁箱及棺内的随葬品;而出于棺内的物疏牍所记内容仅限于棺内,棺外椁内的随葬品则不予记录。这种差别可能是当时葬俗变化的一种反映。武帝以前实行单人葬,墓中棺内外的随葬品均为墓主一人所有;而武帝以后,出物疏牍的墓多为合葬墓,棺内随葬品为个人所有,而棺外随葬品可能为合葬者共同享有。所以把物疏牍放入棺内只记录棺内明确属于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基于对合葬的考虑,即棺外椁内的随葬品非一人独有,应为墓内合葬者共享之物。这件衣物疏因棺木腐朽损毁严重,无法判断其是在棺内还是棺外,但从书写内容看应为一人随葬衣物。随着人间社会土地买卖的盛行,约从东汉开始,又流行一种在墓中放置“墓莂”(俗称“买地券”)的习俗。就是模拟人间土地买卖的契券格式,虚构向神灵购买坟墓地权的契券,这种契约多数是刻在长方形的铅板上,也有的刻在玉板或书写在铁板、陶柱、青砖和石等物之上。待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在幕中放置一种陶质的“镇墓瓶”,瓶内有时还盛放朱砂、雄黄、水晶等物,瓶上有朱书文字和附录,当代学者称这种文书为“镇墓文”或“镇墓解除文”。镇墓文的主要内容为解殃文辞,其作用是以文告的形式,告诫地下鬼怪不能对死者进行侵扰,以便使生人家宅安宁。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地使者”的名义为主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生死有别,勿事纠缠。反映了早期道教的思想。汉代宗教神秘感趋于强烈,巫风兴盛,不但新出现多种源于方术迷信的丧葬文书,而且遣册也向巫风靠近。遣册原有的纪实功能似有退缩的趋势,其表现一为出现虚随葬物品的现象;二为所记物品渐专注于随身衣物,亦即由“器疏”向“衣物疏”转化。
魏晋时期,“告墓牍”与“镇墓文”渐行消失,“衣物疏”继续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定式,疏中虚随葬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疏中所记物品数量过大。例如“故黄金千两”,显然属于虚。有的后文缀以“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之句,“时见”即在场见证者。此墓葬中发现的白虎形象,可能就起到了见证的作用,可能还有青龙形象,可惜已被损毁。“青龙”“白虎”通常与“朱雀”“玄武”连用,是汉代人特喜称引的四方星宿之神。这种迷信性质的衣物疏有的主要是请神灵为死者的财物作证,有的主要是请神灵允许亡灵在冥界通行,有的两种祈愿并陈;有的直接以世俗语言正告他人(鬼魂)不得冒名认物,有的袭用“如律令”‘“急急如律令”之类巫术用语以借助于神。
南北朝时期,“衣物疏”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无论在内容还是性质上,与前期衣物疏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文书中多次出现的“敬移五道大神”和“故移”“事事依移”“从移令”等用语,表明其可能使用了当时同级官府部门之间公文来往的“移文”格式。皆为知会地下神灵一类的文告。唐代时,据《礼记·曲礼下》“书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门”条唐人孔颖达疏曰(20):“书方”者,此谓臣有死于公宫,应须凶具,此下诸物,并宜告而后入者也。书谓条录送死者对象数目多少,如今死人移书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书之,故云“书方”也。可见,唐代时把有关死者随葬品的清单称为“死人移书”。
综上所述,有关古代死人随葬品清单的发展演变,其实经历了“赗方”与“遣策”“告墓牍”与“衣物疏”(或“物疏”“小物疏”)、“死人移书”或“移文”几个阶段,不同的时代,与死者一同埋入地下的随葬品清单也有不同的名称。
考古价值
该衣物疏虽残缺不全,字迹多处漫漶不清,但从残存的字迹中依然可考述出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变化、服饰文化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此衣物疏在金塔首次发现,实属罕见,一方面填补了空白,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该地区这一时期的民俗和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佐证。衣物疏是古人放置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清单,它是从战国时期先秦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清单的遣册发展而来的。它起源于西汉,魏晋时已很盛行。它没有战国时期那种“赗方”与“遣策”的严格区分,而是融合了二者,而且所记也主要是衣、被一类。这件“衣物疏”从残存文字中看,也主要是衣、被一类。“衣物疏”中的“杂衣物五十六种口”,缺的字可能是“疏”,就是说这件衣物疏共记录了墓主人五十六件随葬衣物。这说明在魏晋时期,金塔与中原地区一样,也出现了随葬“衣物疏”的习俗。
可以考证魏晋衣物疏的书写格式和用词规范。据考古结果,魏晋衣物疏多以“质地+名称+数量词”的形式记录随葬衣物,这件衣物疏,基本上也是这种记录方式。如“布衫”“纑群(裙)”“口履”“口衣”就是衣物质地和名称。而“一领”“一量”“二双”“一具”则为数量词。在魏晋衣物疏中,“领”,主要用来称量衣被,以称量上衣的居多。如甘肃高台前凉墓《都中赵双衣物疏》牍记“故疏单衣一领”“故练幅衫一领”“故练大襦一领”“故练小襦一领”“故练被一领”,“具”主要用来修饰完整、成套的器物。如甘肃高台前凉墓《赵阿兹衣物疏》牍记“故紫春囊一具”“故紫搔囊一具”“故刀尺一具”等。“量”作为量词,从出土的魏晋衣物疏中看,全部用来修饰鞋(靴)袜。江西南昌西晋吴应墓《衣物疏》牍记“故白布袜一量”“故丝履一量”;湖南长沙东晋墓《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石板记“故练袜一量”“故斑头履一量”;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晋墓《姬瑜衣物疏》牍记“故练袜一量”“故青纟履一量”;甘肃高台东晋胡运千墓《衣物疏》牍记“故履一量”等。“双”与“量”的用法基本相同,也多用来称量鞋(靴)袜。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服饰文化。从这件随葬衣物疏清单内容看,当时活着的人们希望死者在冥世继续生活,所以为他们陪葬了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一切物品,上至冠帽,下至鞋袜,春夏秋冬,里里外外应有尽有,如衣、裙、裤、面衣、鞋、袜、枕、被、褥、糸(丝)带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饰品,再现了当时这一地区居民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匈奴后,西汉王朝在金塔境内始置会水县,这也是金塔最早的建置。为了经营河西,阻止匈奴南下,汉王朝在酒泉郡北部,黑河通道险要位置处的会水、居延一带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设置长城塞防等防御体系,并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屯田。由于汉王朝的苦心经营,给会水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发展环境。加之会水绿洲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会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至西汉中期已是农牧兴盛、社会繁荣。东汉初年,光武帝为了尽快恢复遭到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推行讲文休武,与民休息以“柔道”治天下的政策,会水一带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东汉中期已达到鼎盛时期。曹魏政权控制河西之后,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经营河西地区,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西晋政权建立后,为巩固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社会经济曾呈现出短暂的繁荣局面。尤其是晋惠帝元康五年(前295年)改福禄县(今酒泉肃州)为会水县,充分说明了会水的影响力。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前526年)会水县弃,至此,历时500余年的会水县画上了句号。可以说,魏晋时期的会水县是金塔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裕,墓中随葬众多衣物也就不难理解。这件衣物疏中“布衫”“纑群(裙)”“布裙”“口履”“口衣”和“糸(丝)带”等衣物和饰品应有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妇女服装则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足上多穿履、靴等。因此,从这件衣物疏所列出的随葬衣物看,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
为研究金塔魏晋历史提供了依据。这件衣物疏,由于墓室早期被盗,衣物疏残缺不全,墓葬中未发现有纪年的文字记载,衣物疏中也未出现明确的纪年和人名,但从衣物疏的书写内容看,应为魏晋时期。首先,这件衣物疏中记载的都是实物,没有出现虚指,这明显是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定式。有的后文缀以“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之句,“时见”即在场见证者,此衣物疏因残缺严重,有无以上之句无从考证,但墓葬中发现的绘制于木板上的白虎形象,可能就起到了见证的作用,也许还有青龙形象,可能已被损毁。“青龙”“白虎”通常与“朱雀”“玄武”连用,是汉代人特喜称引的四方星宿之神。这种迷信性质的衣物疏有的主要是请神灵为死者的财物作证,有的主要是请神灵允许亡灵在冥界通行,有的两种祈愿并陈;有的直接以世俗语言正告他人(鬼魂)不得冒名认物,有的袭用“如律令”“急急如律令”之类巫术用语以借助于神。其次,从这件衣物疏中量词的使用情况看,“量”出现了许多次。李明晓认为“量”用法基本同“两”,称量鞋(靴)袜,不过只见于晋代简牍。从这一点看,此衣物疏的时代应该在晋代。
为研究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汉字演变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自觉的一个时期,书法艺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促使书法正式走向审美艺术之路,即开始了真正自觉地体现主体的生命意识。个性风度,气质品格,加之魏晋风度这种风气的盛行,更加给当时书法的发展根植了新鲜且肥沃的土壤,可谓真正达到了“随意”的状态。书法美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真正从记事转为任心,从象形变为表意,从书写变为书法,从实用变为审美的道路,魏晋书法在魏晋风度的笼罩下,逐渐走向了风格的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趋于成熟,孕育了王羲之、王献之、钟繇、索靖、王珣、陆机、张芝等举世闻名的大批书法家。并且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也随之确立。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这件衣物疏所用字体为行楷。由于魏晋人自由、解放的精神,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脱、纵情任情、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言行风范淋漓地表现出晋人的生活态度、文化心理和韵致风度,书法艺术也就成为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载体。这一时期,一种真正抒情的“纯”书法成熟了,这种书法的“纯”也就是一种美学思想,是“尚韵”的一种表现。“韵”体现在书风上,是一种飘逸妍美、简远清雅的书风。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中国书法开始了楷、行、草并行时代。从这件衣物疏的字体看,它间于行书和楷书之间,用笔随意洒脱,显示出秀整轻逸。它突破了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结构严谨、字形定型和提笔、顿笔、转笔等运用要求严格的特点,它将楷书的体势、点画变得圆转连带、变化多样,结字自由,用笔灵活、方便,很少有逆锋、顿笔、停笔等严格的运笔,行笔巧妙。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行楷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券中竖行之间间距基本匀称,而横行则依字布局,随机谋篇。如“一领”两字和“一具”两字,仅占一个字的位置,避免了“一”字因笔画过简所带来的空旷;而对于笔画过于繁复之字,如“裙”“双”等字则将整体布局适当紧凑匀称。这方衣物疏是普通老百姓随葬用品,这一宽松的民间环境,造就了其在总体布局上的无拘无束和朴拙真率,展示出奔放流畅、伸缩自如、亦方亦圆、跌宕起伏的风格,孕育出一种极富审美艺术的天趣新姿。魏晋时期是中国汉字书法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件衣物疏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的活标本。
相关地名
金塔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