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佑作品
| 内容出处: | 《山丹县六十年文学作品集》 图书 |
| 唯一号: | 292420020220001845 |
| 颗粒名称: | 陈天佑作品 |
| 分类号: | I24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74-283 |
| 摘要: | 本文记述山丹县陈天佑作品,其中介绍了小说《年事》。 |
| 关键词: | 山丹县 陈天佑 小说 |
内容
作者简介:陈天佑,生于1971年10月,山丹县李桥乡人。1989年毕业于张掖师范学校,1996年毕业于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张掖市作家协会理事。先后当过教师、记者、公务员,现在中共张掖市委某机关工作。2003年至今,先后在《北方文学》、《飞天》、《青年作家》、《鹿鸣》、《绿洲》等省内外十几家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三十余万字。获“首届金张掖文艺奖”;甘肃省第二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十六届优秀杂文奖。并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年事(小说)
王采和女人刘毛是早晨六点多下了车的。
坐了一夜的长途汽车,这会儿走在路上,刘毛有些晕车的反应,头昏昏沉沉的,两鬓那儿鼓胀鼓胀的,就觉得那路还有路上的干桠巴杨树都在动。其实,刚一下车,借着车站的灯光,王采就看见了刘毛的脸色发白,明显是晕了车的样子。
背的东西又比较多,大大小小,一共五个包。
两口子在外面打工挣钱,要过年了,总得买点儿东西吧。说是少买点,可是到了批发市场,刘毛还是忍不住要买,茶几上放的塑料,扯了一块米黄色的,又买了一把削洋芋皮的削皮刀,什么沙发垫、床单、竹编的果篮、玻璃醋壶、沉香炉、糖果盒、调料盒、牙签罐、针头线脑,杂七杂八装了一包。王采买了一把镂花的匕首,给父亲买了一个琥珀烟嘴,一咬牙,又给儿子买了一辆电动坦克车。
王采用绳子把两个包的提手连起来,然后搭在肩膀上,腾出手来,又提了一个;刘毛提两个小的,两个人摇摇晃晃就上了路。一路上,刘毛几次蹲在路边上干呕,想吐,又吐不出来。王采从包里掏出茶罐子来,就是一个罐头瓶子,茶已经冰得刺骨。王采双手焐着,仿佛能焐热一点似的。王采说,喝口吧,喝口茶就好了。刘毛接过去喝了一口,没有咽下去,在嘴里咕噜了几下,吐掉了。再走的时候,王采又多了一个包,只给刘毛只留下一个最轻的。
腊月里的天,正是最冷的时候。这个时辰仿佛又更冷了一层,怪喳喳的冷,仿佛周围的风都长着冰茬子,人的身上哪儿开个缝,哪儿就会有冰茬子直刺进肉里来。一阵接一阵的风刮过来,把路边的枯枝败叶刮得满地乱跑,发出的声音很清脆,是那种冻干了的哗啦哗啦的声音。路边的树都冻得咯吧咯吧地响,是寒气渗到树关节里的声音。天上的星星很亮,也仿佛是冻亮了一层似的,一个一个亮呱呱地哆嗦着。路上有一层积雪,风吹着吱咛吱咛的声音,远去了。
“歇一会儿再走吧。”刘毛气喘吁吁地说。王采放下肩上的包。刘毛的手已经脱下了手套,这双手很熟练地罩在了王采的耳朵上,停了一会,又滑到了王采的脸上,他的脸宽,她要移动好几次手,才把他的脸焐了一遍。“身上热着哩。”王采跺着脚说。他说着又把刘毛的围巾往紧里扎了一下,把她头上套的帽子往下拉了拉,两个人又开始走,吱咛吱咛,吱咛吱咛……
快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已有一竿子高了。
王采和刘毛不约而同地站住了,村子就在他们的面前,几十户人家像几十个乱落的棋子丢在山坳里。村口的那老杨树上,几只乌鸦在树顶上盘旋了一阵,落了下来。老树的后面是一排人家,家家户户的烟囱里炊烟袅袅,在这寒冷的日子里,散发着一丝温暖的气息。一只甩着大尾巴的黄狗从一家院里跑出来了,那好像是翠翠家的狗。没错,是翠翠家的狗。那只狗跑到墙角边,抬起一条腿来洒了一泡快乐的尿,然后飞快地跑进了前面的树林,这儿嗅嗅,那儿望望,然后又从门洞子里钻进去了。
刘毛取下口罩,向手上呵了一口气,“终于到了。”她说。她有些激动,眼睛里不知咋的就潮湿了。
“不知道红红起来了没有?”刘毛望着丈夫,笑着说,说起了孩子,她的脸上的表情就复杂起来,一脸幸福的怜悯。马上见到孩子了,她当然高兴,但一想到离开孩子这么久,觉得欠了孩子的,那脸上就是兴奋与怜悯相杂起来的样子,脸色如一盆温婉的热水。
“一年没见,一定长高了,见了我们不定有多高兴呢!”王采定眼看着刘毛说。两人话多起来了,说说笑笑,不由得就加快了脚步。
一进村子,一切都熟悉起来。
村口的老树,德庄叔家门前的那条旧石碾子;顺着马路往前走,刘大家的门前的雕花的石凳子;刘二家南墙跟的老犁,伸着长长的臂,仿佛是杂技演员伸出来的长腿;刘三家的墙头上码着的一捆一捆的燕麦,路边上的房子后面都是收拾的四四方方的粪堆,等着发好了来年耕作时上地呢。村子里烟囱里飘荡的轻烟散发着植物秸秆燃烧出来的味儿,这味道,王采和刘毛都是熟悉的,带着泥土的气息,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闻着这香气,刘毛的胸中立时就升腾起一种像麦粒那样饱满的气息来。这会儿,太阳又升高了点,天气温暖多了。德庄叔家南墙那儿是老汉们蹲着晒太阳聊天的地方,墙皮被磨得光溜溜的,仿佛像打磨过似的,太阳照在那里,格外地耀眼,白晃晃地闪着光。王采看着,脑子里不知咋的就冒出他家喂牲口的那个土槽来,也磨得光溜溜的,也暖和的让人慵懒。想到这,王采的目光不觉也就亲切起来,他觉得那垛墙正向着他笑。
到了家门口,刘毛没有急着敲门,她猫着身子从门缝里往里瞅,看得不太清楚,她把门往里推了推,又移动身子瞅了一阵。院子中间的花池里堆着厚厚一堆雪,院子里洒上了水,一冻就起了土皮,太阳照亮了半个院子,整个院落里,都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弥漫着淡淡的水气。两只鸡在墙角觅食,一切都是安详的样子。
“好像没什么动静,敢情还睡着哩!”她小声嘀咕。她哐哐地敲了几下门,屋子的门开了,刘毛从门缝里瞅清楚了,是婆婆出来了,接着,公公披着衣服也出来了,两个人看起来还算精神,刘毛往后面瞅,却没有发现红红出来。
门开了后,婆婆惊喜得大呼小叫,说,“怎么不提前说一声,让他爷爷使了车去接你们去。”公公已经笑呵呵地快步到了跟前,帮着提了包。进了屋,刘毛的眼睛就直直地向炕上瞅去,却没有发现红红。刘毛问:“红红呢,这么早就玩去了?”婆婆笑着说:“他外爷昨儿个接走了,说是他外婆想外孙了,接去小住几天,还说赶你们回来就送过来呢。”刘毛心里挺高兴,王采却有一点失望。“长高了吧?”刘毛问,说着就走近墙上挂着的相架,那儿有几张红红小时候的照片,小家伙望着他们笑,刘毛用手把照片上孩子的脸摸了摸。这当儿,王采已打开了包,一样一样地往出来拿东西。给娘买的一件夹袄,给老子买的一双棉皮鞋,烟嘴,给红红买的最多,两套衣服外,还有一个兔儿头转笔刀,还有电动坦克。要是孩子在的话,早就兴奋地奔过来了。孩子不在,两个人心里其实都在想要是孩子在多好。四个人动手又把孩子的东西原装进了包里,把包放在墙旮旯里。四个人在脑子里都想象了一下孩子回来后奔向那个包的兴奋劲,不免都生出些遗憾来。
回到北屋,这是他们三口子住的屋。屋子可能有好几天没有打扫了,屋子里不住人,就容易脏,桌子上的灰尘都落了厚厚一层。刘毛拉开窗帘,太阳光射进来,一条光柱里灰尘肆无忌惮地飞舞着。炕上整整齐齐放着一摞红红的衣服,刘毛走过去一件一件拿起来放在鼻子下,仔细地闻,然后又一件一件叠好。王采笑着问:“闻啥?”刘毛红了脸,说:“就想闻一下。”两个人又开始打扫卫生,刘毛风卷残云般把炕上的东西卷去,又取出一个花头巾来,包在了王采的头上,让他拿笤帚扫墙壁上的灰尘,她擦桌子,扫地。
中午的时候,屋子打扫干净了。刘毛出去在外面巡了几趟,每次都深沉地向对面的山嘴上望一阵。这时,王采娘进来问王采,“吃啥呢?我给你们做去。”王采抓了抓头发说:“太想吃一顿和停子了。”他娘笑道:“那我这就去做。”刘毛出来说:“妈,我来帮你。”两个人就到了南屋,王采说完之后,也来到了南屋,抽出两支烟来,爷俩一人一支,开始惬意地吸起来。王采娘开始和面,这面要反反复复揉,揉过一阵后,再放在瓷盆子里捂一阵,然后再揉,等揉精了之后,做成剂子。王采妈揉面的当儿,刘毛已经剥了蒜、葱,切好了红辣椒、腌好的酸白菜。王采的父亲从北屋梁下的肉架子上卸下一条肉来,王采扔掉烟头,开始切冻肉,刘毛说:“不要切成钉子了,要切大点儿才好。”王采就都切成大拇指头那样大的肉块子,切了满满两大碗。这面,王采娘已把锅放在了火炉上,倒了两勺清油,待油过之后,将肉块放进锅里,施上花椒、草果、辣椒、大蒜等料开始炒,待八成熟之后,又滴上酱油和醋,加入葱花,然后加水烧开。水开后,娘俩开始下面,下的都是指头肚大的面片。这时,香气就飘散在屋里,王采看了一眼油汪汪的汤水,早咽起了唾沫,喉节一动一动的。“在外面,最想吃的就是这一顿了,可在外面,怎么也做不出这儿的味道来。看来还真是人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采的感慨还没发表完,刘毛和公婆的最后一片面已掉进了锅里。王采娘又端来一碟子腌制的胡萝卜、辣椒、酸白菜。这顿饭,王采狼吞虎咽不歇气儿三碗下肚,他舔舔嘴唇,咂着嘴巴,望着锅里的饭已不多,刘毛她们每人一碗都没吃完。王采便抽出一根烟来,狠狠地吸了一口,悠长地吐出来。饭后抽一口,这是他的习惯。
下午,王采和刘毛分头忙,刘毛收拾屋子,王采开始起牲口圈里的粪。刘毛把炕上铺的东西全部换下来洗了,又换上了新的。墙上贴上了新买的几幅年画,正墙贴的是一幅虎啸山岗图,是王采买的。炕上两边墙上,一边贴的是猫戏图,玛瑙似的猫眼最惹人喜爱,一边贴的是童嬉图,几个憨态可掬的胖娃扑蝶的扑蝶,捉虫子的捉虫子,一样逗人喜欢。画贴在两边墙上,刚好上了新绷的布墙围,布墙围是浅绿底儿米黄色碎花的,这是刘毛喜欢的颜色。王采这边把牲口圈打扫干净后,又将院落整顿了一番,先是将院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上,他特意在后院的土墙上钉了几个木头楔子,把绳索、扎鞭、废旧的车轮胎全部挂起来。这是他从外面学来的。他在打工时曾去过一家,那家院落的干净整索让他吃惊。然后,他又将柴草之类的东西整顿了一番,后院里有他父亲晒下的一大摊牛粪块,散乱地摊了一地,王采收拾出一处墙旮旯来,用大块码出一个四方的垛子来,然后将碎的全部放在里面,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采进屋发现屋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炕上花花绿绿的,墙上的年画更让这屋子增色不少,火炉上煨着一小堆柏枝,屋里香气四溢,茶壶里的茶刚刚烧开,冒着热气。刘毛已开始做饭,王采看着,心里不觉也随之亮堂起来。王采又抽出一根烟来,坐在炉旁边抽烟边望着女人做饭,女人的身子随着揉面的动作一动一动的,胸脯上那两个东西像两只调皮的兔子,一探一探地,仿佛试探着要从毛衫底下跑出来似的。王采发现,刘毛的身材其实不错,该肥的地方肥,该细的地方细,她的臀部以下尤其好看,虽然做粗活,但保持得相当好,臀是所说的翘臀,宽度刚合适,大腿浑圆而匀称,小腿那儿修长修长的,整个看起来,紧绷绷的。王采的烟与柏枝的烟升腾起来,交织在一起,翻腾着,滚动着。
女人回头看见王采呆呆地异样地看着她,问:“你咋这么看我哩?”
王采吐一口烟,做个鬼脸,说:“天咋黑的这么慢呢?”
刘毛听了,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跟。
早晨,王采醒来后,发现刘毛已经下了炕。水已经烧开了,屋里还有些烟气,弥漫着燃烧了麦秸柴草的香气。王采一抬眼,便与墙上猫的眼睛撞上了。接着,他又看见了那几个孩童高高撅着的屁股。那几张画还散发着纸的香气,一股爱怜之意便如轻烟一般从他的心底油然升起来。南边屋里已经响起了鼓风机的声音,接着,一阵一阵油香飘过来,再接着,就响起了哗啦啦的油炸的声音,那声音欢快地清脆地像燃放着一挂小鞭炮,整个屋子里仿佛正在弹奏一曲美妙的生活曲,奏得满屋子都灿烂起来。王采循着香气走进来,那香浓浓的,略带着些涩味。王采进了屋,看见刘毛和娘在一起做着油果子,父亲身上挂着一块油布,在油锅边负责炸,父亲做得一丝不苟,放进去,炸一阵,再翻过来,看两边都炸得油黄油黄起了油泡泡时,空干了油,捞出来。父亲的脸和炸好的油果子一样,也黄亮黄亮的。油果子炸了满满一脸盆,又开始炸糖花子。黑糖放进热油里,再拌上一点儿面,拌匀了,倒出来,用擀杖擀成薄薄一张饼的样子,再将和好的面擀开,把刚才的糖饼放上去,对折,切成手掌大小的方块,再在方块的一边上用刀轻轻切上几道花纹,留一指宽的梁,把梁下面用刀均匀切开,分成细条儿,然后向两边卷上去,卷成一个个卷儿,放入锅里炸,这东西吃起来又酥又甜。王采最爱吃糖花子了,闻着那甜丝丝的香气,王采的手不觉就向盆子里伸过去,刘毛眼疾手快,“啪”一巴掌打在他的手背上,笑着说:“去,洗脸去。”王采搓搓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闻着都挺香。”王采洗了脸,望了望那半盆黄棱棱的糖花子,走出屋来,先拉水去了。
王采闻着屋里缭绕的柏枝香气,他烧了一大锅水,找出了自己的脏衣服,又把孩子的几件衣裤和刘毛的两件上衣放进了水盆,准备洗。这时,电话铃响了。王采接了起来,没想到是翠翠打来的。翠翠有些不好意思,在电话里支吾着不知怎么说好了。王采能想到翠翠在那边打电话时的别扭相。翠翠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要是过年看料场的话,工资给得高,所以,自己不准备回家过年了。然后,翠翠说:自己不回去,就是放心不下老爸,过年一个人,怎么过呀。王采听明白了,王采想了想,说:“你就安心待着吧,干爹我请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年,你就放心好了。”王采听见那边松了一口气。再接下来,翠翠的语气明显轻松了,最后,好像还有点缠绵,在说“谢谢”的时候,她竟哽咽起来。
王采能想到,她的眼睛肯定是红红的。
翠翠的父亲是王采的干爹。王采六岁的时候,毛病儿多,王采的父母请翠翠的父亲给他戴了锁。翠翠的母亲死得早,父亲只有她一个女儿。因为只有这一个女儿,父亲对翠翠就有了很多的心愿。当年,翠翠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到翠翠家提亲的人一串接一串,王采也在其中,王采的父母希望他们两亲家之间能做成这门亲事,亲上加亲。早先的时候,翠翠的父亲好像也有那么点意思,在不同的场合,言语中也流露过,甚至拉着王采的手叫过女婿。好像有一阵子,对待王采的态度也更加亲热了。可是,后来翠翠的父亲还是改变了主意,待翠翠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决意要招个上门女婿。王采的父母请了很多人做翠翠父亲的工作,也没有做通。翠翠的父亲想让翠翠将来生的孩子跟他的姓,王采父亲也只有他一个儿子,显然不可能作上门女婿。
那年年末,翠翠的父亲给她招了邻村一个叫张宝的人作女婿。翠翠结婚一年后,生了个女儿。可就是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张宝却带了他家两万块钱的存折不见了。他说是去买四轮车的,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听村上一起去的人说,张宝跟人去城里耍赌博,一晚上就把两万块输光了。也有人说,张宝在城里嫖女人,被人家男人抓了现场,两万块钱让人搜走了。他中了人家设的圈套,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张宝走了后,翠翠埋怨过父亲。翠翠的父亲觉得是自己害了翠翠,整天价愁眉苦脸的。他本来就好喝酒,现在逢人就要拉进屋里去喝,喝醉了就向人诉苦。真是祸不单行,有一天,他又喝醉了酒,没有照看好翠翠的孩子,结果三岁的孩子扒翻了炉子上的开水锅,半锅刚烧开的水从孩子的头上浇了上去,孩子被送到医院,但由于烫得太重,又耽误了时间,孩子在医院里躺了几天最终没能挺过来。
这样,翠翠也不想往家里待了,也随同村的人一起到外面打工,几年时间,当小工、挖管沟、种地,什么都干。这几年里,翠翠父亲须发皆白,他更加离不开酒了,翠翠给他寄来的钱,他差不多都买酒喝了。村上的人都看见过他喝醉酒的样子,他一喝醉,就直挺挺地躺在南墙跟里,嘴里拉着涎水。他的脸,因为经常喝酒,变得蜡黄蜡黄,眼睛里经常充满血丝,手呢,也越来越抖得厉害。
晚上的屋子里又熏上了柏枝子,满屋子的香气。刘毛泡了一壶桂圆冰糖茶,给王采倒了一杯,自己端一杯,刘毛边喝边在炕边上给孩子熨过年的新衣服,是一套蓝色的夹克服。孩子明天早晨就要来了,他外爷要送他回家来。刘毛嘴里哼着曲儿,身子一晃一晃的。熨好了,摊展,抹平,叠好,放在柜子里自己的衣服上面。
想起翠翠,王采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时候追翠翠的时候,他的心像块巴望一场急雨滋润的干旱地。眼看着翠翠要离自己而去,在翠翠面前,他的眼睛竟也红红的,他差点就掉眼泪。翠翠要招张宝的时候,他真的还偷偷哭了一场。
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挣上钱,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圆圆满满,不要落在了人家的后面。
他娶了刘毛,刘毛是邻村的姑娘,长得平常,没有翠翠好看,是放进人堆里就不易找出来的那种。刘毛只想把小日子过滋润,做家务做饭都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做和停子,那是跟她妈学来的。他们结婚后就去外地打工,格尔木、敦煌、阿克塞、喀什都去过。几年下来,有了不少的积蓄。但这会儿,想起翠翠那凄苦的样子,王采的心就软了。
王采就是那种心软的男人,对女人的,王采更是下不了狠心来。
和刘毛疯狂过温存过之后,王采觉得可以对刘毛提这事儿了,他便试探着说:“翠翠打电话了,你知道是干啥么?”
刘毛一愣,想了想,揶揄道:“当然是想你了呀。”说完,笑吟吟地看着王采的反应。
王采笑了一下,说:“哪儿是想我了,是想干爹了。”
刘毛说:“是想你了吧,别不好意思——想干爹,干嘛偏给你打电话?”
王采说:“这不要过年了,她不回来了,让我帮着照顾一下干爹。”
刘毛变了脸色,但依然笑着说:“翠翠让你照顾他爹,有什么意思哩吧?是不是让你认她的爹作爹呢?”
刘毛边说着边看王采的反应,王采长着一双柳叶似的细长细长的眼睛,见人就是个笑,一笑,那双眼睛就更加细长了。
王采果然拉长那双眼睛笑了一下,一伸手,他从枕头下摸出纸烟盒来,抽一根,点上,烟在他的脸上面升腾着。好半天了,刘毛说:“你是不是后悔了?”王采吐一口烟,说:“我后悔啥呢,你尽瞎想。”半晌,刘毛幽幽地说:“她当初可没嫁给你哩。”王采说:“嫁给了,还有你么?”刘毛不说话了,又过了半天,刘毛说:“那咋办呢?你明儿给她家送点糖花、油果子吧。今儿三十了,妈炸得多,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王采说:“不是要吃的,关键是,他一个人挺孤单的。”王采感觉刘毛的身子一下警觉起来,她的一只脚伸出了被子,像一只竖起来的大耳朵。“能不能把干爹一成接过来过年,再多少给点花的钱。”王采小心地说。过了半天,刘毛说:“接来我侍候也可以,还给钱干啥?”王采说,“他家烧的都快没有了,这样冷的天,总得让拉点烧的吧。”忽一下,那只“大耳朵”钻进了被窝。刘毛翻过身去,把王采身上的被子也扯走了。
王采扯过一点被子角盖在身上,他想,也难怪,让她侍候干爹,已经不易了。再给钱,对女人来说,就更难了。虽然,他们是有些积蓄,但那容易吗?那是爬冰卧雪流血流汗靠卖力气一点一点挣来的,打工的钱不容易,刘毛格外地珍惜。刘毛在格尔木商场看上了一双皮靴,二百多块,看了又看,试了又试,最后,一咬牙还是放下了没买,冬天一直穿着前年买的那双,脚冻肿了好几次,一到晚上就肿痛难忍。两人曾几次许着要改善一下伙食,看着四川人开的火锅店里人来人往,两个人走进去看了一下,刘毛说闻着都香。两口子商量好了赶回家吃一顿,美美吃一顿。“菜要的多多的。”刘毛咂着嘴说。王采说:“这里的羊肉才好吃哩。”但最后一听一顿要吃掉一百多,还是没有去。在火锅店外面转旋了半天,刘毛在市场上买了两个肉夹饼,自己吃了半个,剩余的王采都吃了,连声说香。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没有坐过摩的,多远的路,都是跑着回来,其实打一次也就三块钱。但是刘毛不打,刘毛说钱就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她有一件毛衣,洗了拆,拆了洗,舍不得再买一件新的。她买东西,哪怕几分钱都要拉开架式,和人家来一番讨价还价。白菜从两毛一把涨成了三毛一把,她都要抱怨半天。钱挣得不容易啊,哪能白白地拿来送别人呢?自己挣得钱儿就成了自己身上的肉,哪儿能随便割舍的下呢?
大年三十,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屋里明显地冷了,刘毛照例早早起来,生了火。王采缩在暖和的被窝里抽了一根烟。屋里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王采抽着烟,说:“我今天就去请干爹过来,你取三百块钱,我让人给拉一车煤块。”刘毛侍弄着火炉,“啪”的一声,炉盖掉在了炉面上,发出的哗啦声响了好一阵。刘毛拿起火条往炉里狠狠地捅了几下,又听见嗵嗵嗵地砸煤块,接着就往炉膛里放煤块,一块又一块,一块又一块,仿佛要把炉膛塞得满满的才会罢休。
王采开始穿衣服,看着刘毛有些不对劲,只低着头一声不吭。王采又仔细一看,才发现刘毛在哭。王采知道,刘毛一哭,说明她同意了,多年夫妻成知己,刘毛的脾性,王采是知道的,长着一副豆腐心,她要不同意的事,就会笑脸儿和你商量,做你的工作,她一哭,这事就松口了。这是她一贯的表现。王采心里一热,就帮着扫起地来,王采很少干家务活,连扫地的事儿都很少干,显得很笨拙。刘毛过来,从墙柜子里摸出一个包袱来,数了一沓钱,数了两遍,塞给王采,说:“还不给人家送去。”王采拿了,说:“翠翠回来,我让她谢你。”刘毛说:“你应该让她好好谢谢你,你让她怎么谢你,她都会同意的,你就像她女婿似的。”
王采让母亲准备了些蒸炸之物,花卷、糖花、油饼各样拿了一些,合在一起也不少了,满满一篮子。
王采把东西给翠翠家送去。到了翠翠家,翠翠的父亲木然地坐在炉子旁边,屋子里还散发着酒气。屋子倒是宽阔,但里面的陈设却没有多少。房子大,一大,就有些冷清。看见王采进来,翠翠的父亲有些吃惊,“干爹,给你送点吃的东西,都是我妈做的。”王采笑着说,边说边把炉子盖取开,炉子里的火快要灭了,王采往炉子里加了几块牛粪,又顺手将茶壶放上。翠翠的父亲抖着手,一迭声地说:“送这么多干啥,我哪能吃了这么多。”。王采说,说:“我已经让人拉煤去了。”翠翠的父亲有些木然,他显然不知道怎么说好。过了一阵,才喃喃道:“家里还有牛粪,能烧到明年春上。”他的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王采又说:“爹特地让我来请你过去和我们一起过年。”翠翠的父亲听了,慌忙说:“自己这样子,哪儿也不去了。一个人,也习惯了。你回去给你爹说谢。”王采哪儿肯依,说:“干爹,这些年,您也不容易,您不去,村里人会笑话我。”翠翠父亲的眼睛红了,接着,眼泪就下来了,他用手掌一下一下地抹着泪水。炉子上的水开了,茶壶嘴里突突突,突突突突地冒着热气。
和翠翠父亲从他家出来,天突然晴了,太阳很亮,地上也很亮。王采刚进门,就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儿子回来了。岳父正坐在炉子旁喝茶,孩子拿着给他买上的坦克在地上玩,嘴里模仿坦克发着突突的声音。三个老人亲热地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聊天。
年三十,打扫完了院落,拉完了雪,刘毛打好了浆子,王采开始贴对联、门神、门帘,孩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帮忙。到了下午,满院子的红对联,花花绿绿的门帘门神,农家院落里喜庆的气息越来越浓。晚上,按风俗要吃臊子面,刘毛和娘做了一桌子菜。腌白菜、胡萝卜丝是少不了的,羊肉是黄焖的,切好了放的蒜片,一盘肘子肉,油汪汪的,鱼是酸辣鱼,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牛头肉,热气腾腾,黄亮黄亮的。大家有说有笑,王采吸溜着打开一瓶从青海带来的青稞酒,往地上奠了一下,王采看见,干爹的喉节动了一下,他给干爹敬了,又给父母敬了。然后,盘腿坐在炕上,说:“干爹,今儿我和您好好喝两杯。”干爹却咂了两下嘴,一口气喝了酒盘里剩下的几杯,又咂一下嘴,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你爹不多喝酒,今儿干爹也不多喝了。把这东西收拾了,你陪我和你爹掀一阵牛九怎么样?”王采和他父亲都说好,王采说:“不带点彩不红火,要带点小彩才好。”又从衣裳口袋里掏出些零钱来分给了两个老人,说好了一个子儿两毛,三个人就掀起了牛九。这时,外面响起了鞭炮声,偶尔还可以看见有人家放满天星。八点钟,中央台的联欢晚会也开了,一家人放完了炮,王采领着儿子给长辈磕了头回来,孩子早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炮,到外面放去了。啪一嗵--村子里的炮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地响起来。
第二天,正月初一,王采早早起来接“爷”,孩子看了半宿的电视,起得晚,一睁眼,就闻到两种香味,一种是柏枝味,他娘往炉子里放了柏枝,另一种是饭香,奶奶、妈妈、两个爷爷正在一起说说笑笑包饺子。孩子一骨碌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头顶下整整齐齐叠着他要穿的新衣服。
穿上了新衣服,拿了坦克车,孩子从屋里飞出来。一出门,就看见院子中央,大堆的鞭炮碎片,红红的一地,像一朵朵梅花盛开在那里。
(原载《飞天》,并被《小说选刊》转载)
年事(小说)
王采和女人刘毛是早晨六点多下了车的。
坐了一夜的长途汽车,这会儿走在路上,刘毛有些晕车的反应,头昏昏沉沉的,两鬓那儿鼓胀鼓胀的,就觉得那路还有路上的干桠巴杨树都在动。其实,刚一下车,借着车站的灯光,王采就看见了刘毛的脸色发白,明显是晕了车的样子。
背的东西又比较多,大大小小,一共五个包。
两口子在外面打工挣钱,要过年了,总得买点儿东西吧。说是少买点,可是到了批发市场,刘毛还是忍不住要买,茶几上放的塑料,扯了一块米黄色的,又买了一把削洋芋皮的削皮刀,什么沙发垫、床单、竹编的果篮、玻璃醋壶、沉香炉、糖果盒、调料盒、牙签罐、针头线脑,杂七杂八装了一包。王采买了一把镂花的匕首,给父亲买了一个琥珀烟嘴,一咬牙,又给儿子买了一辆电动坦克车。
王采用绳子把两个包的提手连起来,然后搭在肩膀上,腾出手来,又提了一个;刘毛提两个小的,两个人摇摇晃晃就上了路。一路上,刘毛几次蹲在路边上干呕,想吐,又吐不出来。王采从包里掏出茶罐子来,就是一个罐头瓶子,茶已经冰得刺骨。王采双手焐着,仿佛能焐热一点似的。王采说,喝口吧,喝口茶就好了。刘毛接过去喝了一口,没有咽下去,在嘴里咕噜了几下,吐掉了。再走的时候,王采又多了一个包,只给刘毛只留下一个最轻的。
腊月里的天,正是最冷的时候。这个时辰仿佛又更冷了一层,怪喳喳的冷,仿佛周围的风都长着冰茬子,人的身上哪儿开个缝,哪儿就会有冰茬子直刺进肉里来。一阵接一阵的风刮过来,把路边的枯枝败叶刮得满地乱跑,发出的声音很清脆,是那种冻干了的哗啦哗啦的声音。路边的树都冻得咯吧咯吧地响,是寒气渗到树关节里的声音。天上的星星很亮,也仿佛是冻亮了一层似的,一个一个亮呱呱地哆嗦着。路上有一层积雪,风吹着吱咛吱咛的声音,远去了。
“歇一会儿再走吧。”刘毛气喘吁吁地说。王采放下肩上的包。刘毛的手已经脱下了手套,这双手很熟练地罩在了王采的耳朵上,停了一会,又滑到了王采的脸上,他的脸宽,她要移动好几次手,才把他的脸焐了一遍。“身上热着哩。”王采跺着脚说。他说着又把刘毛的围巾往紧里扎了一下,把她头上套的帽子往下拉了拉,两个人又开始走,吱咛吱咛,吱咛吱咛……
快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已有一竿子高了。
王采和刘毛不约而同地站住了,村子就在他们的面前,几十户人家像几十个乱落的棋子丢在山坳里。村口的那老杨树上,几只乌鸦在树顶上盘旋了一阵,落了下来。老树的后面是一排人家,家家户户的烟囱里炊烟袅袅,在这寒冷的日子里,散发着一丝温暖的气息。一只甩着大尾巴的黄狗从一家院里跑出来了,那好像是翠翠家的狗。没错,是翠翠家的狗。那只狗跑到墙角边,抬起一条腿来洒了一泡快乐的尿,然后飞快地跑进了前面的树林,这儿嗅嗅,那儿望望,然后又从门洞子里钻进去了。
刘毛取下口罩,向手上呵了一口气,“终于到了。”她说。她有些激动,眼睛里不知咋的就潮湿了。
“不知道红红起来了没有?”刘毛望着丈夫,笑着说,说起了孩子,她的脸上的表情就复杂起来,一脸幸福的怜悯。马上见到孩子了,她当然高兴,但一想到离开孩子这么久,觉得欠了孩子的,那脸上就是兴奋与怜悯相杂起来的样子,脸色如一盆温婉的热水。
“一年没见,一定长高了,见了我们不定有多高兴呢!”王采定眼看着刘毛说。两人话多起来了,说说笑笑,不由得就加快了脚步。
一进村子,一切都熟悉起来。
村口的老树,德庄叔家门前的那条旧石碾子;顺着马路往前走,刘大家的门前的雕花的石凳子;刘二家南墙跟的老犁,伸着长长的臂,仿佛是杂技演员伸出来的长腿;刘三家的墙头上码着的一捆一捆的燕麦,路边上的房子后面都是收拾的四四方方的粪堆,等着发好了来年耕作时上地呢。村子里烟囱里飘荡的轻烟散发着植物秸秆燃烧出来的味儿,这味道,王采和刘毛都是熟悉的,带着泥土的气息,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闻着这香气,刘毛的胸中立时就升腾起一种像麦粒那样饱满的气息来。这会儿,太阳又升高了点,天气温暖多了。德庄叔家南墙那儿是老汉们蹲着晒太阳聊天的地方,墙皮被磨得光溜溜的,仿佛像打磨过似的,太阳照在那里,格外地耀眼,白晃晃地闪着光。王采看着,脑子里不知咋的就冒出他家喂牲口的那个土槽来,也磨得光溜溜的,也暖和的让人慵懒。想到这,王采的目光不觉也就亲切起来,他觉得那垛墙正向着他笑。
到了家门口,刘毛没有急着敲门,她猫着身子从门缝里往里瞅,看得不太清楚,她把门往里推了推,又移动身子瞅了一阵。院子中间的花池里堆着厚厚一堆雪,院子里洒上了水,一冻就起了土皮,太阳照亮了半个院子,整个院落里,都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弥漫着淡淡的水气。两只鸡在墙角觅食,一切都是安详的样子。
“好像没什么动静,敢情还睡着哩!”她小声嘀咕。她哐哐地敲了几下门,屋子的门开了,刘毛从门缝里瞅清楚了,是婆婆出来了,接着,公公披着衣服也出来了,两个人看起来还算精神,刘毛往后面瞅,却没有发现红红出来。
门开了后,婆婆惊喜得大呼小叫,说,“怎么不提前说一声,让他爷爷使了车去接你们去。”公公已经笑呵呵地快步到了跟前,帮着提了包。进了屋,刘毛的眼睛就直直地向炕上瞅去,却没有发现红红。刘毛问:“红红呢,这么早就玩去了?”婆婆笑着说:“他外爷昨儿个接走了,说是他外婆想外孙了,接去小住几天,还说赶你们回来就送过来呢。”刘毛心里挺高兴,王采却有一点失望。“长高了吧?”刘毛问,说着就走近墙上挂着的相架,那儿有几张红红小时候的照片,小家伙望着他们笑,刘毛用手把照片上孩子的脸摸了摸。这当儿,王采已打开了包,一样一样地往出来拿东西。给娘买的一件夹袄,给老子买的一双棉皮鞋,烟嘴,给红红买的最多,两套衣服外,还有一个兔儿头转笔刀,还有电动坦克。要是孩子在的话,早就兴奋地奔过来了。孩子不在,两个人心里其实都在想要是孩子在多好。四个人动手又把孩子的东西原装进了包里,把包放在墙旮旯里。四个人在脑子里都想象了一下孩子回来后奔向那个包的兴奋劲,不免都生出些遗憾来。
回到北屋,这是他们三口子住的屋。屋子可能有好几天没有打扫了,屋子里不住人,就容易脏,桌子上的灰尘都落了厚厚一层。刘毛拉开窗帘,太阳光射进来,一条光柱里灰尘肆无忌惮地飞舞着。炕上整整齐齐放着一摞红红的衣服,刘毛走过去一件一件拿起来放在鼻子下,仔细地闻,然后又一件一件叠好。王采笑着问:“闻啥?”刘毛红了脸,说:“就想闻一下。”两个人又开始打扫卫生,刘毛风卷残云般把炕上的东西卷去,又取出一个花头巾来,包在了王采的头上,让他拿笤帚扫墙壁上的灰尘,她擦桌子,扫地。
中午的时候,屋子打扫干净了。刘毛出去在外面巡了几趟,每次都深沉地向对面的山嘴上望一阵。这时,王采娘进来问王采,“吃啥呢?我给你们做去。”王采抓了抓头发说:“太想吃一顿和停子了。”他娘笑道:“那我这就去做。”刘毛出来说:“妈,我来帮你。”两个人就到了南屋,王采说完之后,也来到了南屋,抽出两支烟来,爷俩一人一支,开始惬意地吸起来。王采娘开始和面,这面要反反复复揉,揉过一阵后,再放在瓷盆子里捂一阵,然后再揉,等揉精了之后,做成剂子。王采妈揉面的当儿,刘毛已经剥了蒜、葱,切好了红辣椒、腌好的酸白菜。王采的父亲从北屋梁下的肉架子上卸下一条肉来,王采扔掉烟头,开始切冻肉,刘毛说:“不要切成钉子了,要切大点儿才好。”王采就都切成大拇指头那样大的肉块子,切了满满两大碗。这面,王采娘已把锅放在了火炉上,倒了两勺清油,待油过之后,将肉块放进锅里,施上花椒、草果、辣椒、大蒜等料开始炒,待八成熟之后,又滴上酱油和醋,加入葱花,然后加水烧开。水开后,娘俩开始下面,下的都是指头肚大的面片。这时,香气就飘散在屋里,王采看了一眼油汪汪的汤水,早咽起了唾沫,喉节一动一动的。“在外面,最想吃的就是这一顿了,可在外面,怎么也做不出这儿的味道来。看来还真是人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采的感慨还没发表完,刘毛和公婆的最后一片面已掉进了锅里。王采娘又端来一碟子腌制的胡萝卜、辣椒、酸白菜。这顿饭,王采狼吞虎咽不歇气儿三碗下肚,他舔舔嘴唇,咂着嘴巴,望着锅里的饭已不多,刘毛她们每人一碗都没吃完。王采便抽出一根烟来,狠狠地吸了一口,悠长地吐出来。饭后抽一口,这是他的习惯。
下午,王采和刘毛分头忙,刘毛收拾屋子,王采开始起牲口圈里的粪。刘毛把炕上铺的东西全部换下来洗了,又换上了新的。墙上贴上了新买的几幅年画,正墙贴的是一幅虎啸山岗图,是王采买的。炕上两边墙上,一边贴的是猫戏图,玛瑙似的猫眼最惹人喜爱,一边贴的是童嬉图,几个憨态可掬的胖娃扑蝶的扑蝶,捉虫子的捉虫子,一样逗人喜欢。画贴在两边墙上,刚好上了新绷的布墙围,布墙围是浅绿底儿米黄色碎花的,这是刘毛喜欢的颜色。王采这边把牲口圈打扫干净后,又将院落整顿了一番,先是将院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上,他特意在后院的土墙上钉了几个木头楔子,把绳索、扎鞭、废旧的车轮胎全部挂起来。这是他从外面学来的。他在打工时曾去过一家,那家院落的干净整索让他吃惊。然后,他又将柴草之类的东西整顿了一番,后院里有他父亲晒下的一大摊牛粪块,散乱地摊了一地,王采收拾出一处墙旮旯来,用大块码出一个四方的垛子来,然后将碎的全部放在里面,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采进屋发现屋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炕上花花绿绿的,墙上的年画更让这屋子增色不少,火炉上煨着一小堆柏枝,屋里香气四溢,茶壶里的茶刚刚烧开,冒着热气。刘毛已开始做饭,王采看着,心里不觉也随之亮堂起来。王采又抽出一根烟来,坐在炉旁边抽烟边望着女人做饭,女人的身子随着揉面的动作一动一动的,胸脯上那两个东西像两只调皮的兔子,一探一探地,仿佛试探着要从毛衫底下跑出来似的。王采发现,刘毛的身材其实不错,该肥的地方肥,该细的地方细,她的臀部以下尤其好看,虽然做粗活,但保持得相当好,臀是所说的翘臀,宽度刚合适,大腿浑圆而匀称,小腿那儿修长修长的,整个看起来,紧绷绷的。王采的烟与柏枝的烟升腾起来,交织在一起,翻腾着,滚动着。
女人回头看见王采呆呆地异样地看着她,问:“你咋这么看我哩?”
王采吐一口烟,做个鬼脸,说:“天咋黑的这么慢呢?”
刘毛听了,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跟。
早晨,王采醒来后,发现刘毛已经下了炕。水已经烧开了,屋里还有些烟气,弥漫着燃烧了麦秸柴草的香气。王采一抬眼,便与墙上猫的眼睛撞上了。接着,他又看见了那几个孩童高高撅着的屁股。那几张画还散发着纸的香气,一股爱怜之意便如轻烟一般从他的心底油然升起来。南边屋里已经响起了鼓风机的声音,接着,一阵一阵油香飘过来,再接着,就响起了哗啦啦的油炸的声音,那声音欢快地清脆地像燃放着一挂小鞭炮,整个屋子里仿佛正在弹奏一曲美妙的生活曲,奏得满屋子都灿烂起来。王采循着香气走进来,那香浓浓的,略带着些涩味。王采进了屋,看见刘毛和娘在一起做着油果子,父亲身上挂着一块油布,在油锅边负责炸,父亲做得一丝不苟,放进去,炸一阵,再翻过来,看两边都炸得油黄油黄起了油泡泡时,空干了油,捞出来。父亲的脸和炸好的油果子一样,也黄亮黄亮的。油果子炸了满满一脸盆,又开始炸糖花子。黑糖放进热油里,再拌上一点儿面,拌匀了,倒出来,用擀杖擀成薄薄一张饼的样子,再将和好的面擀开,把刚才的糖饼放上去,对折,切成手掌大小的方块,再在方块的一边上用刀轻轻切上几道花纹,留一指宽的梁,把梁下面用刀均匀切开,分成细条儿,然后向两边卷上去,卷成一个个卷儿,放入锅里炸,这东西吃起来又酥又甜。王采最爱吃糖花子了,闻着那甜丝丝的香气,王采的手不觉就向盆子里伸过去,刘毛眼疾手快,“啪”一巴掌打在他的手背上,笑着说:“去,洗脸去。”王采搓搓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闻着都挺香。”王采洗了脸,望了望那半盆黄棱棱的糖花子,走出屋来,先拉水去了。
王采闻着屋里缭绕的柏枝香气,他烧了一大锅水,找出了自己的脏衣服,又把孩子的几件衣裤和刘毛的两件上衣放进了水盆,准备洗。这时,电话铃响了。王采接了起来,没想到是翠翠打来的。翠翠有些不好意思,在电话里支吾着不知怎么说好了。王采能想到翠翠在那边打电话时的别扭相。翠翠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要是过年看料场的话,工资给得高,所以,自己不准备回家过年了。然后,翠翠说:自己不回去,就是放心不下老爸,过年一个人,怎么过呀。王采听明白了,王采想了想,说:“你就安心待着吧,干爹我请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年,你就放心好了。”王采听见那边松了一口气。再接下来,翠翠的语气明显轻松了,最后,好像还有点缠绵,在说“谢谢”的时候,她竟哽咽起来。
王采能想到,她的眼睛肯定是红红的。
翠翠的父亲是王采的干爹。王采六岁的时候,毛病儿多,王采的父母请翠翠的父亲给他戴了锁。翠翠的母亲死得早,父亲只有她一个女儿。因为只有这一个女儿,父亲对翠翠就有了很多的心愿。当年,翠翠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到翠翠家提亲的人一串接一串,王采也在其中,王采的父母希望他们两亲家之间能做成这门亲事,亲上加亲。早先的时候,翠翠的父亲好像也有那么点意思,在不同的场合,言语中也流露过,甚至拉着王采的手叫过女婿。好像有一阵子,对待王采的态度也更加亲热了。可是,后来翠翠的父亲还是改变了主意,待翠翠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决意要招个上门女婿。王采的父母请了很多人做翠翠父亲的工作,也没有做通。翠翠的父亲想让翠翠将来生的孩子跟他的姓,王采父亲也只有他一个儿子,显然不可能作上门女婿。
那年年末,翠翠的父亲给她招了邻村一个叫张宝的人作女婿。翠翠结婚一年后,生了个女儿。可就是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张宝却带了他家两万块钱的存折不见了。他说是去买四轮车的,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听村上一起去的人说,张宝跟人去城里耍赌博,一晚上就把两万块输光了。也有人说,张宝在城里嫖女人,被人家男人抓了现场,两万块钱让人搜走了。他中了人家设的圈套,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张宝走了后,翠翠埋怨过父亲。翠翠的父亲觉得是自己害了翠翠,整天价愁眉苦脸的。他本来就好喝酒,现在逢人就要拉进屋里去喝,喝醉了就向人诉苦。真是祸不单行,有一天,他又喝醉了酒,没有照看好翠翠的孩子,结果三岁的孩子扒翻了炉子上的开水锅,半锅刚烧开的水从孩子的头上浇了上去,孩子被送到医院,但由于烫得太重,又耽误了时间,孩子在医院里躺了几天最终没能挺过来。
这样,翠翠也不想往家里待了,也随同村的人一起到外面打工,几年时间,当小工、挖管沟、种地,什么都干。这几年里,翠翠父亲须发皆白,他更加离不开酒了,翠翠给他寄来的钱,他差不多都买酒喝了。村上的人都看见过他喝醉酒的样子,他一喝醉,就直挺挺地躺在南墙跟里,嘴里拉着涎水。他的脸,因为经常喝酒,变得蜡黄蜡黄,眼睛里经常充满血丝,手呢,也越来越抖得厉害。
晚上的屋子里又熏上了柏枝子,满屋子的香气。刘毛泡了一壶桂圆冰糖茶,给王采倒了一杯,自己端一杯,刘毛边喝边在炕边上给孩子熨过年的新衣服,是一套蓝色的夹克服。孩子明天早晨就要来了,他外爷要送他回家来。刘毛嘴里哼着曲儿,身子一晃一晃的。熨好了,摊展,抹平,叠好,放在柜子里自己的衣服上面。
想起翠翠,王采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时候追翠翠的时候,他的心像块巴望一场急雨滋润的干旱地。眼看着翠翠要离自己而去,在翠翠面前,他的眼睛竟也红红的,他差点就掉眼泪。翠翠要招张宝的时候,他真的还偷偷哭了一场。
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挣上钱,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圆圆满满,不要落在了人家的后面。
他娶了刘毛,刘毛是邻村的姑娘,长得平常,没有翠翠好看,是放进人堆里就不易找出来的那种。刘毛只想把小日子过滋润,做家务做饭都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做和停子,那是跟她妈学来的。他们结婚后就去外地打工,格尔木、敦煌、阿克塞、喀什都去过。几年下来,有了不少的积蓄。但这会儿,想起翠翠那凄苦的样子,王采的心就软了。
王采就是那种心软的男人,对女人的,王采更是下不了狠心来。
和刘毛疯狂过温存过之后,王采觉得可以对刘毛提这事儿了,他便试探着说:“翠翠打电话了,你知道是干啥么?”
刘毛一愣,想了想,揶揄道:“当然是想你了呀。”说完,笑吟吟地看着王采的反应。
王采笑了一下,说:“哪儿是想我了,是想干爹了。”
刘毛说:“是想你了吧,别不好意思——想干爹,干嘛偏给你打电话?”
王采说:“这不要过年了,她不回来了,让我帮着照顾一下干爹。”
刘毛变了脸色,但依然笑着说:“翠翠让你照顾他爹,有什么意思哩吧?是不是让你认她的爹作爹呢?”
刘毛边说着边看王采的反应,王采长着一双柳叶似的细长细长的眼睛,见人就是个笑,一笑,那双眼睛就更加细长了。
王采果然拉长那双眼睛笑了一下,一伸手,他从枕头下摸出纸烟盒来,抽一根,点上,烟在他的脸上面升腾着。好半天了,刘毛说:“你是不是后悔了?”王采吐一口烟,说:“我后悔啥呢,你尽瞎想。”半晌,刘毛幽幽地说:“她当初可没嫁给你哩。”王采说:“嫁给了,还有你么?”刘毛不说话了,又过了半天,刘毛说:“那咋办呢?你明儿给她家送点糖花、油果子吧。今儿三十了,妈炸得多,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王采说:“不是要吃的,关键是,他一个人挺孤单的。”王采感觉刘毛的身子一下警觉起来,她的一只脚伸出了被子,像一只竖起来的大耳朵。“能不能把干爹一成接过来过年,再多少给点花的钱。”王采小心地说。过了半天,刘毛说:“接来我侍候也可以,还给钱干啥?”王采说,“他家烧的都快没有了,这样冷的天,总得让拉点烧的吧。”忽一下,那只“大耳朵”钻进了被窝。刘毛翻过身去,把王采身上的被子也扯走了。
王采扯过一点被子角盖在身上,他想,也难怪,让她侍候干爹,已经不易了。再给钱,对女人来说,就更难了。虽然,他们是有些积蓄,但那容易吗?那是爬冰卧雪流血流汗靠卖力气一点一点挣来的,打工的钱不容易,刘毛格外地珍惜。刘毛在格尔木商场看上了一双皮靴,二百多块,看了又看,试了又试,最后,一咬牙还是放下了没买,冬天一直穿着前年买的那双,脚冻肿了好几次,一到晚上就肿痛难忍。两人曾几次许着要改善一下伙食,看着四川人开的火锅店里人来人往,两个人走进去看了一下,刘毛说闻着都香。两口子商量好了赶回家吃一顿,美美吃一顿。“菜要的多多的。”刘毛咂着嘴说。王采说:“这里的羊肉才好吃哩。”但最后一听一顿要吃掉一百多,还是没有去。在火锅店外面转旋了半天,刘毛在市场上买了两个肉夹饼,自己吃了半个,剩余的王采都吃了,连声说香。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没有坐过摩的,多远的路,都是跑着回来,其实打一次也就三块钱。但是刘毛不打,刘毛说钱就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她有一件毛衣,洗了拆,拆了洗,舍不得再买一件新的。她买东西,哪怕几分钱都要拉开架式,和人家来一番讨价还价。白菜从两毛一把涨成了三毛一把,她都要抱怨半天。钱挣得不容易啊,哪能白白地拿来送别人呢?自己挣得钱儿就成了自己身上的肉,哪儿能随便割舍的下呢?
大年三十,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屋里明显地冷了,刘毛照例早早起来,生了火。王采缩在暖和的被窝里抽了一根烟。屋里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王采抽着烟,说:“我今天就去请干爹过来,你取三百块钱,我让人给拉一车煤块。”刘毛侍弄着火炉,“啪”的一声,炉盖掉在了炉面上,发出的哗啦声响了好一阵。刘毛拿起火条往炉里狠狠地捅了几下,又听见嗵嗵嗵地砸煤块,接着就往炉膛里放煤块,一块又一块,一块又一块,仿佛要把炉膛塞得满满的才会罢休。
王采开始穿衣服,看着刘毛有些不对劲,只低着头一声不吭。王采又仔细一看,才发现刘毛在哭。王采知道,刘毛一哭,说明她同意了,多年夫妻成知己,刘毛的脾性,王采是知道的,长着一副豆腐心,她要不同意的事,就会笑脸儿和你商量,做你的工作,她一哭,这事就松口了。这是她一贯的表现。王采心里一热,就帮着扫起地来,王采很少干家务活,连扫地的事儿都很少干,显得很笨拙。刘毛过来,从墙柜子里摸出一个包袱来,数了一沓钱,数了两遍,塞给王采,说:“还不给人家送去。”王采拿了,说:“翠翠回来,我让她谢你。”刘毛说:“你应该让她好好谢谢你,你让她怎么谢你,她都会同意的,你就像她女婿似的。”
王采让母亲准备了些蒸炸之物,花卷、糖花、油饼各样拿了一些,合在一起也不少了,满满一篮子。
王采把东西给翠翠家送去。到了翠翠家,翠翠的父亲木然地坐在炉子旁边,屋子里还散发着酒气。屋子倒是宽阔,但里面的陈设却没有多少。房子大,一大,就有些冷清。看见王采进来,翠翠的父亲有些吃惊,“干爹,给你送点吃的东西,都是我妈做的。”王采笑着说,边说边把炉子盖取开,炉子里的火快要灭了,王采往炉子里加了几块牛粪,又顺手将茶壶放上。翠翠的父亲抖着手,一迭声地说:“送这么多干啥,我哪能吃了这么多。”。王采说,说:“我已经让人拉煤去了。”翠翠的父亲有些木然,他显然不知道怎么说好。过了一阵,才喃喃道:“家里还有牛粪,能烧到明年春上。”他的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王采又说:“爹特地让我来请你过去和我们一起过年。”翠翠的父亲听了,慌忙说:“自己这样子,哪儿也不去了。一个人,也习惯了。你回去给你爹说谢。”王采哪儿肯依,说:“干爹,这些年,您也不容易,您不去,村里人会笑话我。”翠翠父亲的眼睛红了,接着,眼泪就下来了,他用手掌一下一下地抹着泪水。炉子上的水开了,茶壶嘴里突突突,突突突突地冒着热气。
和翠翠父亲从他家出来,天突然晴了,太阳很亮,地上也很亮。王采刚进门,就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儿子回来了。岳父正坐在炉子旁喝茶,孩子拿着给他买上的坦克在地上玩,嘴里模仿坦克发着突突的声音。三个老人亲热地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聊天。
年三十,打扫完了院落,拉完了雪,刘毛打好了浆子,王采开始贴对联、门神、门帘,孩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帮忙。到了下午,满院子的红对联,花花绿绿的门帘门神,农家院落里喜庆的气息越来越浓。晚上,按风俗要吃臊子面,刘毛和娘做了一桌子菜。腌白菜、胡萝卜丝是少不了的,羊肉是黄焖的,切好了放的蒜片,一盘肘子肉,油汪汪的,鱼是酸辣鱼,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牛头肉,热气腾腾,黄亮黄亮的。大家有说有笑,王采吸溜着打开一瓶从青海带来的青稞酒,往地上奠了一下,王采看见,干爹的喉节动了一下,他给干爹敬了,又给父母敬了。然后,盘腿坐在炕上,说:“干爹,今儿我和您好好喝两杯。”干爹却咂了两下嘴,一口气喝了酒盘里剩下的几杯,又咂一下嘴,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你爹不多喝酒,今儿干爹也不多喝了。把这东西收拾了,你陪我和你爹掀一阵牛九怎么样?”王采和他父亲都说好,王采说:“不带点彩不红火,要带点小彩才好。”又从衣裳口袋里掏出些零钱来分给了两个老人,说好了一个子儿两毛,三个人就掀起了牛九。这时,外面响起了鞭炮声,偶尔还可以看见有人家放满天星。八点钟,中央台的联欢晚会也开了,一家人放完了炮,王采领着儿子给长辈磕了头回来,孩子早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炮,到外面放去了。啪一嗵--村子里的炮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地响起来。
第二天,正月初一,王采早早起来接“爷”,孩子看了半宿的电视,起得晚,一睁眼,就闻到两种香味,一种是柏枝味,他娘往炉子里放了柏枝,另一种是饭香,奶奶、妈妈、两个爷爷正在一起说说笑笑包饺子。孩子一骨碌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头顶下整整齐齐叠着他要穿的新衣服。
穿上了新衣服,拿了坦克车,孩子从屋里飞出来。一出门,就看见院子中央,大堆的鞭炮碎片,红红的一地,像一朵朵梅花盛开在那里。
(原载《飞天》,并被《小说选刊》转载)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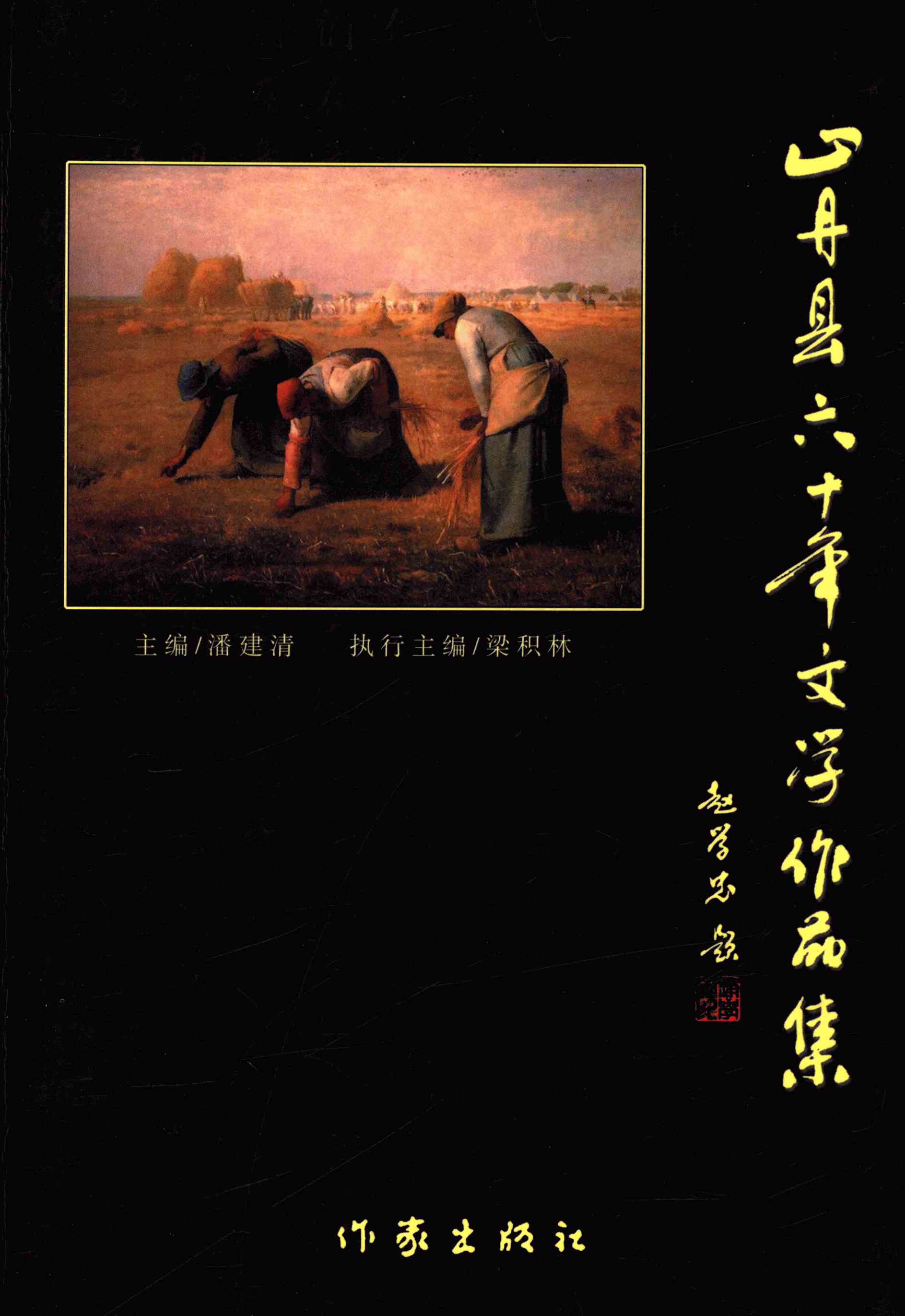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陈天佑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
相关作品
年事
相关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