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活作品
| 内容出处: | 《山丹县六十年文学作品集》 图书 |
| 唯一号: | 292420020220001821 |
| 颗粒名称: | 何茂活作品 |
| 分类号: | I267 |
| 页数: | 7 |
| 页码: | 144-150 |
| 摘要: | 本文记述山丹县何茂活所作散文作品,其中介绍了《荣枯曲曲直芨芨草》、《身后那两道辙》、《老家的两棵松树》、《拜谒古烽墩》。 |
| 关键词: | 山丹县 何茂活 散文 |
内容
作者简介:何茂活,男,1963年9月12日出生于山丹大马营前山村,1983年7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山丹军马场工作18年,2001年2月调至河西学院中文系工作,现任该系人文教育教研室主任、教授,讲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逻辑学等课程。为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甘肃省作协会员,张掖市作协理事。在《孔子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国地方志》、《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2007年12月出版专著《山丹方言志》(甘肃人民出版社)。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文百余篇(首)。
荣枯曲曲直芨芨草(散文)
芨芨草,是一种极普通的草,《辞海》中的解释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秆多数,丛生。叶片坚韧,纵向卷折……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及内蒙古等地。通常生长在微碱性土壤中。秆、叶可作造纸和人造丝的原料……”
然而,就是这极普通的草,却与河西人的生活有很大关系。在我的家乡山丹,芨芨草几乎可以说无处不有,无时不在。
记得小时候,每当夏季,在一些荒凉的芨芨滩里,芨芨草青青如盖,随风俯仰。牧童们往往信手拔上一些,辫成鞭杆状,用以驱打牲畜。爱美的小姑娘则用芨芨、树枝和蓝荧荧的马莲花编成花环般的头饰,用来遮日晒,防蚊蝇。当芨芨渐成青黄色时,亦即“饱”了七八成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拔它了。那一根根挺拔青翠、摇曳生姿的芨芨草,竟被人用一根叫“拔棍”的东西连根拔下,一个个青壮的生命从此便告别了细雨的沐浴和清风的吹拂。“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傍晚的时候,人们总能看见,在牛背上或牧人的肩上,总有几捆青湛湛的芨芨,一颠一晃地撩拨着暮霭,飘进农家的院落。
深秋及初冬季节,芨芨草渐成浅黄色。这时要拔它,就只能一根一根地“抽”了。这样抽来的芨芨,极富弹性和韧性,一般只舍得用来搓绳。搓绳的工序是先用榔头把芨芨捶扁拍松,目的是使其柔顺,易于绞合。然后在上面喷点温水,就可动手搓单坯了。所谓单坯,其实也是双股。将搓好的单坯拧上劲后,便可根据需要合成不同用途和不同规格的“草绳”。过去农家用的草绳,大约有拴拉牲畜用的縻绳和缰绳,煞车用的大绳,车或犁上的靷绳,还有井绳、筐系绳、耙耱绳等等,长短粗细各不相同,搓和拧的工艺也有不同的讲究。这种用长饱了的芨芨拧成的绳,不仅耐拉耐磨,而且还耐水浸耐日晒,一根绳可用多年,老年人说它像筋丝子似的。
严冬季节,朔风萧瑟,瑞雪飘飞,白色的芨芨在寒风中峭然挺立,发出丝丝的哨音。如遇霜雪,便成了晶莹剔透的纤纤玉柱。多年来未被拔掉的芨芨则变成了瓦蓝色,人们称之为枯芨芨。这种枯芨芨因其易得而易燃的特点,同样受到农家人的青睐,家家的炕席下都压着一两把这样的芨芨。抽旱烟的老人,有一根枯芨芨,一盏煤油灯,便觉神清气顺,倦意顿消;炉灶引火时,主妇们也不免将席下的“宝物”暂借一用;就连小学生上学也常常是提一串干牛粪,夹一把枯芨芨。
当拔来的芨芨仍不敷使用时,我们的祖先还曾将房前屋后、山山洼洼里的芨芨连根刨出,晒干后作引火做饭的燃料。有的即获幸免也逃不脱烈火焚烧的“厄运”,那是牧人们为了取暖而点燃的。在苍茫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刚直的芨芨竟以它的生命之火向牧人们奉献出一片赤诚。大火过后,满目灰烬,遍地焦土,其势壮烈,其景惨然。好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翌年的春天,复活的生命更加郁郁葱葱了。
河西人之于芨芨草,可谓司空见惯矣。芨芨草的诸多功用,乡民们认为土俗之至,“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一事一物,既存在就有其生命,既有生命就有其价值,更何况千百年来为河西人编织了生活,编织了希望,编织了历史的芨芨草呢?
芨芨草的功用,实在是太多了。比如编织炕席(当地称打席子),过去家家炕上都少不了一块芨芨编的席子。它较苇席有耐磨耐烫耐折的特点。在隔潮、防火方面也明显优于苇席。过去盖房,也有用席子代替竹帘或苇箔的,不过这种席织得很松很粗糙。再如粮囤,有方有圆,大者盛粮两三石。这种囤子盛粮干燥防霉,易于贮运。所不足者,易遭鼠盗耳。因此如今让位于粮仓了。比囤子小的有各种筐具,如背筐、驮筐、拉筐、挑筐等。较有特色的有盛馍馍的笸子样大筐,它一般有底有盖,可盛一“大锅”甚至更多的馒头。还有一种名为“气死狗”的背篓极为有趣,篓子主体约如放大的墨水瓶,腹大口小,比拳头略大的口上有盖相覆,并以皮襻相连绾。据说狗若伸进头去,衔了馒头后将进退两难,无法自拔。近日读报,似乎说非洲某国土人一捕兽机关即用此理。
芨芨的妙用,小到家居的多个方面,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无用不精。如栽扫帚、编笊篱(山丹人称之为掐笊篱)、扎洗锅用的刷帚、扎草圈(大锅的锅与盖之间的垫圈,作用约如笼屉圈和高压锅的锅圈)等等。如果说拿芨芨扎那种在馍馍上点花儿的“花剁子”,还透露着乡土生活的土俗和落后的话,用芨芨制作的学童们识数用的算筹,则正浓缩了生生不息的乡民们对于文化知识、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那小小的芨芨棍儿,谁说不是他们手中纤细而又沉重的接力棒呢?
河西人,从呱呱坠地之时,就与芨芨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儿出生后门口挂的那把弓箭就是用芨芨做的(当然生了女孩挂的就是红布条了)。当那些跟芨芨打了一辈子交道,碌碌一生、辛苦备尝的农人,终于瞑目百年的时候,芨芨仍未忘了为他们送上最后一程——家人祭奠和亲友乡邻吊唁时所献的大供(当地俗称壳篓子),就是用碗口大的芨芨筐衬底,蒸出的外圆中空的大蒸馍。至于空心的馍馍是否蕴涵着“死去元知万事空”的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到出殡下葬的时候,还要用面捏一只公鸡,用芨芨做一张弓箭,作为陪葬之物。陪葬公鸡的寓意大概是为了替死者啼鸣报晓,驱除昏昧寂寞,并且期望它高唱祖茔之太平,启佑后世之昌隆;这张弓箭则正与初来人世时门前所悬者遥相呼应,大概表露着逝者一生来矢志功名的雄图大志和离世前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吧!
日月递嬗,草木荣枯,时移世易,人事两殊。芨芨草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地消匿引退了。比如炕席,虽然在农家的新房里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它昔日的风光却早被层层叠叠的毡毯被褥给占尽了。各种筐囤已很少见到,至于笊篱之类则更是完全绝迹了。那些筋丝子似的草绳,毕竟不如麻绳、尼龙绳等结实耐用,尤其不如它们一买即可,便捷省事。那种以芨芨草烧火做饭的往事,也许永远变成了历史,因为如今的液化气灶已陆续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灶房。
芨芨草与我们的民俗渐渐地远离,这是芨芨的幸事,更是河西乡民的幸事。可是,强劲有力的芨芨草,曲张有节的芨芨草,“秆叶可以造纸”的芨芨草,你难道能甘于寂寞,难道能就这样无言地与我们的生活断然揖别吗?
(原载《丝绸之路》)
身后那两道辙(散文)
人生之路,如果一岁看作一里,那么我已走过了不很平坦也不多坎坷的三十里路程。回首凝望,两道似隐似现的辙印逶迤身后,那是我的双脚——或者说我就是一辆双轮车——碾成的。这辆车,不停地前行,不停地检修,苦苦甘甘,风风雨雨。回望之间,两道车辙幻作两条蛟龙,斗智争雄,各不相让。我恍然彻悟:三十里的路程为何走得这般吃力。
两道辙是两条蛟龙,一条是勤奋,一条是惫懒。曾几何时,油灯下,晨曦中,寒窗苦读,勤苦备至。后来有了一张印有烫金大字的文凭,于是便有了职业有了饭碗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职称,于是也便有了资本有了骄傲有了牢骚有了不甘就此罢休的新的憧憬。在新的探索和追寻中又时而自奋时而懈怠,时而空虚时而自满,时而自责时而自慰。常常,一个在起床前拟订的宏伟计划,睡觉时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依然如故的枕席,同时又以一个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渐渐地,勤奋与惫懒成了一对貌合神离、沉默寡言的孪生兄弟,相安无事地并行不悖。偶有龃龉,便令我痛苦数日。
两道辙是两条蛟龙,一条依恋乡野,一条向往都市。我的车拉过乡野,乡里人看它嫌洋;我的车拉到城市,城里人见它嫌土。那辘辘的车声,曾融入牧笛的清越悠扬,也曾混进卡拉OK的狂放劲健。我的车轮,一只是文明,一只是愚昧;一只是高傲,一只是谦卑;一只是坦诚,一只是虚伪;一只是桀骜,一只是驯顺;一只是宽宏,一只是褊狭;一只是物欲的诱惑,一只是信念的羁縻;一只悠闲如圆月,文静而悒郁;一只豪迈如骄阳,热情而昂奋。两只车轮难走各式各样的路,在只有独木桥的地方,只得挥汗来一番“单轮飞越”的杂耍,耍得熟了,倒觉别有趣味。在下里巴人的土炕头,我能自顾自地欣赏窗外的“阳春白雪”,在清韵徐歇之际,我也能旁若无人地来两句“呕哑啁哳”。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细品这人生的况味,总觉得自己车上这些酸甜苦辣既使精心调配也难调众口。
两条辙是两条蛟龙,一条是深沉,一条是浮浅。深沉如犁,躬身荒野,不求闻达,澹泊自安,只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敢期“春种满园皆碧玉,秋收遍野尽黄金”。浮浅如风,随意折转,左右奔突,临难闪避,见隙而行。回首身后那两道辙印,多少次跟随并不高明的车手,走了许多弯路;多少次路遇险峻但并不必要求助的时候,我曾呼唤过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多少次在理当我行我素的时候,因众人的窃窃私语和目光攒射而心慌意乱,掉转车头。所幸那辙印弯了又直,直了又弯,心有一片磁针石,千折百回未肯休。那长长的辙印中,有几段是那样沉稳有力,深深地镌刻在无人走过的地方。
身后那两道辙,曲曲弯弯,深深浅浅,想不通人生为何这样繁难,不明白别人的双轮车上究竟装了些什么奇珍异宝。询问如我一般平常的路人,原来他们也大体如我,那用来装载行囊的车子,一路上售出勤奋,回收惫懒;售出文明,回收愚昧;售出坦诚,回收虚伪;售出深沉,回收浮浅。若有人执意要看车上的废品,我们会极不情愿地让他看看,至于有人要把这些废品转手高价倒卖,那便是见利忘义的昧心之举了。
身后那两道辙,深深浅浅,曲曲弯弯。一辆车,走过春夏秋冬三十载;两只轮,在互不相让的较量中书写一路人生的感慨。我愿换上两只簇新如一的车轮,碾两道簇新如一的辙印,一样的轻快潇洒,一样的踏实稳健,前方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平,越走越宽。
(原载《经济参考报》)
老家的两棵松树(散文)
老家是一个用黄土夯筑的大庄子,庄子后面有两棵青翠的祁连松。
老家其实不远,30里地,可是我竟有20多年没有去过了。这次因堂伯母的去世,我终于有机会回了一趟“遥远”的老家。
多年前的记忆,本来就是一张曝光不足的黑白照片,如今在头脑的影集里更显得黯淡无光了。在关于老家的有限记忆里,除了那挂为堂哥娶亲的马车,再就只剩那座高深莫测的大庄子和庄子后面的两棵松树了。
庄子是曾祖父手上创下的家业,到现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从曾祖父到现在的主人——堂弟茂林,院里的房屋不知修过几次了,可是这个土筑的庄子仍保持着旧有的庄重和威严。四壁上清晰的板筑纹路依旧十分清晰,尤其是北墙的外侧,按理说是受风雨侵蚀最为严重的部分,可是偏偏这面墙壁几乎像新筑的一般,大概是由于下雨时墙头上泥水的流注,使平整的墙壁上仿佛涂上了一层富含胶质的岩浆,把我想看到的苍凉密密实实地掩藏在了里边。只有那蜿蜒而下的裂缝,让人想到先祖皲裂的手掌和满面的沟回。
我在这里极力地搜寻先祖的遗迹,可是鲜有收获,心里不免生出丝丝的怅惘。在堂屋的穿廊里抬头仰望,在布满尘灰的桁檩间,竟发现一双我从未见过的颇有古意的厚底棉鞋,这种鞋布面毡底,做工极为考究,鞋底约有四五公分,鞋面上也多有装饰,因此老辈人称为“大加工的鸡窝窝”。可巧的是,在堂屋的正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上,长袍美髯的堂祖父穿的似乎正是这双鞋。据茂林讲,这双鞋堂伯父生前也曾穿过。房子翻修了以后,老人就把它随手放在了那上边。可是我想,将这样一双“敝屣”放在这样一个“有碍观瞻”的地方,究竟是信手无意,还是别有所期呢?看着披麻戴孝的年仅四五岁的小堂侄——将来这座宅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听着呜呜咽咽的唢呐声,跪在列祖列宗的灵前,我禁不住泪下如注了。
在老家两天,充塞心头的除了对世事匆匆的深深感喟,就是对贫瘠荒凉的痛切忧思。老家所在的地方名叫双湖,数十年前曾祖父在几十里外垦田置地,所选的地方竟然也叫双湖。老家双湖究竟有没有湖,不得而知。但那里种树比较容易成活,尤其是杨树。那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杨树,而惟独我们何家老宅的后面有两棵挺拔傲岸的祁连松。小时候到老家去,听说这两棵树年长于我们的祖父,心中便无限敬仰。这次拜望它们,感到它们的生长虽然非常缓慢,但是在干坼的黄土地上显得格外富有生机。在宅子的四周,几十年来栽了不少的杨树,有一些已伐去作了建房的材料,惟独这两棵松树,至今仍旧盎然地葱郁着,成了冬春季节宅院内外惟有的绿色。在我的眼里,这两棵青松不啻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更是一种来自历史和未来的殷殷期待。它们的怡然健在,使我对堂伯父一家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现在我们所在的双湖,倒确实有湖,但所谓湖,只不过是人们对沼泽地的一种俗称。“湖”里的水原本是很充沛的。记得小时候,每当春夏时节,一到夜幕降临,水里的青蛙便开始高声吟唱了。住在清幽幽的小山村里,倒颇有点“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味道。可是这些年来,耕地不断扩展,“湖”滩日渐萎缩,“湖”里的水已经很少,过去冬季冰雪皑皑、夏季水草如茵的地方,现在一片焦黄。前几天一个傍晚,陪耕地归来的父亲走过被近年新开的荒地紧紧围困的小“湖”,听见几声可怜的蛙鸣,我的心不禁凄然。
我突然想起老家里先祖留给我们的那两棵顽强的松树,是它们在我的心头投下了一片浓郁的绿荫。我还想起为堂伯母送葬的那天早上,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村里人敲响的干涩、凄厉的锣声,是它使我深深地感到了时光的悠远和人生的短暂。今天,面对脚下的这片黄土,遥想着百十年后的子子孙孙,我不禁诘问自己:作为先民的后裔,作为后人的祖先,我们应当和能够留给后人的又该是什么呢?
拜谒古烽墩(散文)
自小生活在甘凉古道边,对烽火墩台可谓司空见惯了。在过去四十年漫长而匆促的岁月里,也曾想走近它,瞻仰它,甚至想登上它的巅头。但是这么多年,这样的念头往往是稍纵即逝,因此久未如愿。直至今年盛夏,我才乘便在草原的深处瞻仰了一处烽墩。其实与其说是烽墩,不如说是古烽墩遗址。
这是大马营草原腹地的四墩烽火台。这处建于明代的烽墩原是两座,一南一北,相距约十米,因数百年风雨侵蚀,所见者唯两座土丘而已。土丘之上,荒草萋萋,随风飘摇。土丘旁,辙印纵横,足迹斑斑,想必来者中不乏凭吊之人。土丘的基部可见几个残破的洞窟,大概是早年的牧人为栖身避雨而挖的。在一个破洞里,有一段胳膊粗的朽木半露着断茬,伸手一掰,断木竟枯朽得近乎成灰了。从残留的丝瓜络似的黄褐色纤维上可以推想,它是当年夯土墩时所用的松椽。站在土丘旁,环顾四周,禾麦青青,一望无垠,菜花飘香,蜂蝶嘤嘤。古老的烽火台就这样老态龙钟地蹲踞在这无边的花海碧浪里。一时间,这两座土丘,在我的眼里完全幻作了两座坟墓,它的主人似乎纯粹是一介草民,它的身心本来就与主人的故事一样千疮百孔。或许再过几十年,这两尊荒冢将永远被湮没在朔风衰草之中。
但是,在它的家族中,也有不屈的强者至今仍傲然挺立着,讲述它们昔日的辉煌。
农历七月十五,我偕家人去到多年未曾去过的先人坟头焚香压纸,默然祷祝。返回的路上,我独步登上了那座高高的墩洼山。山在群峰间并不见奇,但因这饱经沧桑的烽墩,便格外令人敬仰。这个烽墩同样建于明代,虽经风雨剥蚀,不见了当年的棱角,但其基本规模并未破坏。墩高约七八米,东、南两壁较为挺直,只是上面布满了鸟雀的洞窠,基部像城墙根一样颓朽进许多。墩身上有几处地方缝隙大开,颇有摇摇欲坠之感。墩的西、北两侧,因雨水冲刷和登临者的攀援,大致变成了坡形,自底到顶,有渐高渐疏的荒草。轻攀着草茎,手脚并用,我竟登上了这久已向往的墩台。
登台远望,山峦起伏,宛如细浪泥丸,祁连焉支,尽收眼底。十里之外,南北东西各有烽墩相望,势成犄角,矗立赫然。伫望之间,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狼烟滚滚、兵戈阵阵的历史场景。这苍老的烽墩啊,在你颓败的躯体和干涩的眉目间,不知遭遇了多少风刀霜剑,融汇了多少荣辱悲欢。你像一位退役的老将,遍体的疮痍掩不住你昔日的威武。而今在你身边的沟沟洼洼和山山峁峁间,农人们正在收拾成熟的庄稼,漫山遍野一片宁谧和安详。惟有那满载着农民血汗和希望的胶轮马车,在陡窄的坡道上吟唱着古老的歌谣。
我曾登过泰山,但除却孔老夫子给我的“成见”以外,我并没有体会到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怀和意境。倒是在这个小小的烽墩山上,我却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和怅惘。当我在山顶上留连顾盼的时候,“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圆圆的月亮已从东山升起,山坳里家家的房顶上,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噢,圆缺有常、亘古不变的明月,你不知疲倦地照耀着,照耀着沉默无言的苍凉历史,也照耀着我生生不息的父老兄弟,照耀着山里人家岁岁相同而又日日各异的繁忙与清苦。在这云淡风清的夜晚,愿你与夜夜谋面的烽墩拉起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
(以上作品原载《张掖广播电视报》)
荣枯曲曲直芨芨草(散文)
芨芨草,是一种极普通的草,《辞海》中的解释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秆多数,丛生。叶片坚韧,纵向卷折……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及内蒙古等地。通常生长在微碱性土壤中。秆、叶可作造纸和人造丝的原料……”
然而,就是这极普通的草,却与河西人的生活有很大关系。在我的家乡山丹,芨芨草几乎可以说无处不有,无时不在。
记得小时候,每当夏季,在一些荒凉的芨芨滩里,芨芨草青青如盖,随风俯仰。牧童们往往信手拔上一些,辫成鞭杆状,用以驱打牲畜。爱美的小姑娘则用芨芨、树枝和蓝荧荧的马莲花编成花环般的头饰,用来遮日晒,防蚊蝇。当芨芨渐成青黄色时,亦即“饱”了七八成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拔它了。那一根根挺拔青翠、摇曳生姿的芨芨草,竟被人用一根叫“拔棍”的东西连根拔下,一个个青壮的生命从此便告别了细雨的沐浴和清风的吹拂。“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傍晚的时候,人们总能看见,在牛背上或牧人的肩上,总有几捆青湛湛的芨芨,一颠一晃地撩拨着暮霭,飘进农家的院落。
深秋及初冬季节,芨芨草渐成浅黄色。这时要拔它,就只能一根一根地“抽”了。这样抽来的芨芨,极富弹性和韧性,一般只舍得用来搓绳。搓绳的工序是先用榔头把芨芨捶扁拍松,目的是使其柔顺,易于绞合。然后在上面喷点温水,就可动手搓单坯了。所谓单坯,其实也是双股。将搓好的单坯拧上劲后,便可根据需要合成不同用途和不同规格的“草绳”。过去农家用的草绳,大约有拴拉牲畜用的縻绳和缰绳,煞车用的大绳,车或犁上的靷绳,还有井绳、筐系绳、耙耱绳等等,长短粗细各不相同,搓和拧的工艺也有不同的讲究。这种用长饱了的芨芨拧成的绳,不仅耐拉耐磨,而且还耐水浸耐日晒,一根绳可用多年,老年人说它像筋丝子似的。
严冬季节,朔风萧瑟,瑞雪飘飞,白色的芨芨在寒风中峭然挺立,发出丝丝的哨音。如遇霜雪,便成了晶莹剔透的纤纤玉柱。多年来未被拔掉的芨芨则变成了瓦蓝色,人们称之为枯芨芨。这种枯芨芨因其易得而易燃的特点,同样受到农家人的青睐,家家的炕席下都压着一两把这样的芨芨。抽旱烟的老人,有一根枯芨芨,一盏煤油灯,便觉神清气顺,倦意顿消;炉灶引火时,主妇们也不免将席下的“宝物”暂借一用;就连小学生上学也常常是提一串干牛粪,夹一把枯芨芨。
当拔来的芨芨仍不敷使用时,我们的祖先还曾将房前屋后、山山洼洼里的芨芨连根刨出,晒干后作引火做饭的燃料。有的即获幸免也逃不脱烈火焚烧的“厄运”,那是牧人们为了取暖而点燃的。在苍茫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刚直的芨芨竟以它的生命之火向牧人们奉献出一片赤诚。大火过后,满目灰烬,遍地焦土,其势壮烈,其景惨然。好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翌年的春天,复活的生命更加郁郁葱葱了。
河西人之于芨芨草,可谓司空见惯矣。芨芨草的诸多功用,乡民们认为土俗之至,“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一事一物,既存在就有其生命,既有生命就有其价值,更何况千百年来为河西人编织了生活,编织了希望,编织了历史的芨芨草呢?
芨芨草的功用,实在是太多了。比如编织炕席(当地称打席子),过去家家炕上都少不了一块芨芨编的席子。它较苇席有耐磨耐烫耐折的特点。在隔潮、防火方面也明显优于苇席。过去盖房,也有用席子代替竹帘或苇箔的,不过这种席织得很松很粗糙。再如粮囤,有方有圆,大者盛粮两三石。这种囤子盛粮干燥防霉,易于贮运。所不足者,易遭鼠盗耳。因此如今让位于粮仓了。比囤子小的有各种筐具,如背筐、驮筐、拉筐、挑筐等。较有特色的有盛馍馍的笸子样大筐,它一般有底有盖,可盛一“大锅”甚至更多的馒头。还有一种名为“气死狗”的背篓极为有趣,篓子主体约如放大的墨水瓶,腹大口小,比拳头略大的口上有盖相覆,并以皮襻相连绾。据说狗若伸进头去,衔了馒头后将进退两难,无法自拔。近日读报,似乎说非洲某国土人一捕兽机关即用此理。
芨芨的妙用,小到家居的多个方面,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无用不精。如栽扫帚、编笊篱(山丹人称之为掐笊篱)、扎洗锅用的刷帚、扎草圈(大锅的锅与盖之间的垫圈,作用约如笼屉圈和高压锅的锅圈)等等。如果说拿芨芨扎那种在馍馍上点花儿的“花剁子”,还透露着乡土生活的土俗和落后的话,用芨芨制作的学童们识数用的算筹,则正浓缩了生生不息的乡民们对于文化知识、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那小小的芨芨棍儿,谁说不是他们手中纤细而又沉重的接力棒呢?
河西人,从呱呱坠地之时,就与芨芨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儿出生后门口挂的那把弓箭就是用芨芨做的(当然生了女孩挂的就是红布条了)。当那些跟芨芨打了一辈子交道,碌碌一生、辛苦备尝的农人,终于瞑目百年的时候,芨芨仍未忘了为他们送上最后一程——家人祭奠和亲友乡邻吊唁时所献的大供(当地俗称壳篓子),就是用碗口大的芨芨筐衬底,蒸出的外圆中空的大蒸馍。至于空心的馍馍是否蕴涵着“死去元知万事空”的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到出殡下葬的时候,还要用面捏一只公鸡,用芨芨做一张弓箭,作为陪葬之物。陪葬公鸡的寓意大概是为了替死者啼鸣报晓,驱除昏昧寂寞,并且期望它高唱祖茔之太平,启佑后世之昌隆;这张弓箭则正与初来人世时门前所悬者遥相呼应,大概表露着逝者一生来矢志功名的雄图大志和离世前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吧!
日月递嬗,草木荣枯,时移世易,人事两殊。芨芨草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地消匿引退了。比如炕席,虽然在农家的新房里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它昔日的风光却早被层层叠叠的毡毯被褥给占尽了。各种筐囤已很少见到,至于笊篱之类则更是完全绝迹了。那些筋丝子似的草绳,毕竟不如麻绳、尼龙绳等结实耐用,尤其不如它们一买即可,便捷省事。那种以芨芨草烧火做饭的往事,也许永远变成了历史,因为如今的液化气灶已陆续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灶房。
芨芨草与我们的民俗渐渐地远离,这是芨芨的幸事,更是河西乡民的幸事。可是,强劲有力的芨芨草,曲张有节的芨芨草,“秆叶可以造纸”的芨芨草,你难道能甘于寂寞,难道能就这样无言地与我们的生活断然揖别吗?
(原载《丝绸之路》)
身后那两道辙(散文)
人生之路,如果一岁看作一里,那么我已走过了不很平坦也不多坎坷的三十里路程。回首凝望,两道似隐似现的辙印逶迤身后,那是我的双脚——或者说我就是一辆双轮车——碾成的。这辆车,不停地前行,不停地检修,苦苦甘甘,风风雨雨。回望之间,两道车辙幻作两条蛟龙,斗智争雄,各不相让。我恍然彻悟:三十里的路程为何走得这般吃力。
两道辙是两条蛟龙,一条是勤奋,一条是惫懒。曾几何时,油灯下,晨曦中,寒窗苦读,勤苦备至。后来有了一张印有烫金大字的文凭,于是便有了职业有了饭碗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职称,于是也便有了资本有了骄傲有了牢骚有了不甘就此罢休的新的憧憬。在新的探索和追寻中又时而自奋时而懈怠,时而空虚时而自满,时而自责时而自慰。常常,一个在起床前拟订的宏伟计划,睡觉时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依然如故的枕席,同时又以一个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渐渐地,勤奋与惫懒成了一对貌合神离、沉默寡言的孪生兄弟,相安无事地并行不悖。偶有龃龉,便令我痛苦数日。
两道辙是两条蛟龙,一条依恋乡野,一条向往都市。我的车拉过乡野,乡里人看它嫌洋;我的车拉到城市,城里人见它嫌土。那辘辘的车声,曾融入牧笛的清越悠扬,也曾混进卡拉OK的狂放劲健。我的车轮,一只是文明,一只是愚昧;一只是高傲,一只是谦卑;一只是坦诚,一只是虚伪;一只是桀骜,一只是驯顺;一只是宽宏,一只是褊狭;一只是物欲的诱惑,一只是信念的羁縻;一只悠闲如圆月,文静而悒郁;一只豪迈如骄阳,热情而昂奋。两只车轮难走各式各样的路,在只有独木桥的地方,只得挥汗来一番“单轮飞越”的杂耍,耍得熟了,倒觉别有趣味。在下里巴人的土炕头,我能自顾自地欣赏窗外的“阳春白雪”,在清韵徐歇之际,我也能旁若无人地来两句“呕哑啁哳”。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细品这人生的况味,总觉得自己车上这些酸甜苦辣既使精心调配也难调众口。
两条辙是两条蛟龙,一条是深沉,一条是浮浅。深沉如犁,躬身荒野,不求闻达,澹泊自安,只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敢期“春种满园皆碧玉,秋收遍野尽黄金”。浮浅如风,随意折转,左右奔突,临难闪避,见隙而行。回首身后那两道辙印,多少次跟随并不高明的车手,走了许多弯路;多少次路遇险峻但并不必要求助的时候,我曾呼唤过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多少次在理当我行我素的时候,因众人的窃窃私语和目光攒射而心慌意乱,掉转车头。所幸那辙印弯了又直,直了又弯,心有一片磁针石,千折百回未肯休。那长长的辙印中,有几段是那样沉稳有力,深深地镌刻在无人走过的地方。
身后那两道辙,曲曲弯弯,深深浅浅,想不通人生为何这样繁难,不明白别人的双轮车上究竟装了些什么奇珍异宝。询问如我一般平常的路人,原来他们也大体如我,那用来装载行囊的车子,一路上售出勤奋,回收惫懒;售出文明,回收愚昧;售出坦诚,回收虚伪;售出深沉,回收浮浅。若有人执意要看车上的废品,我们会极不情愿地让他看看,至于有人要把这些废品转手高价倒卖,那便是见利忘义的昧心之举了。
身后那两道辙,深深浅浅,曲曲弯弯。一辆车,走过春夏秋冬三十载;两只轮,在互不相让的较量中书写一路人生的感慨。我愿换上两只簇新如一的车轮,碾两道簇新如一的辙印,一样的轻快潇洒,一样的踏实稳健,前方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平,越走越宽。
(原载《经济参考报》)
老家的两棵松树(散文)
老家是一个用黄土夯筑的大庄子,庄子后面有两棵青翠的祁连松。
老家其实不远,30里地,可是我竟有20多年没有去过了。这次因堂伯母的去世,我终于有机会回了一趟“遥远”的老家。
多年前的记忆,本来就是一张曝光不足的黑白照片,如今在头脑的影集里更显得黯淡无光了。在关于老家的有限记忆里,除了那挂为堂哥娶亲的马车,再就只剩那座高深莫测的大庄子和庄子后面的两棵松树了。
庄子是曾祖父手上创下的家业,到现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从曾祖父到现在的主人——堂弟茂林,院里的房屋不知修过几次了,可是这个土筑的庄子仍保持着旧有的庄重和威严。四壁上清晰的板筑纹路依旧十分清晰,尤其是北墙的外侧,按理说是受风雨侵蚀最为严重的部分,可是偏偏这面墙壁几乎像新筑的一般,大概是由于下雨时墙头上泥水的流注,使平整的墙壁上仿佛涂上了一层富含胶质的岩浆,把我想看到的苍凉密密实实地掩藏在了里边。只有那蜿蜒而下的裂缝,让人想到先祖皲裂的手掌和满面的沟回。
我在这里极力地搜寻先祖的遗迹,可是鲜有收获,心里不免生出丝丝的怅惘。在堂屋的穿廊里抬头仰望,在布满尘灰的桁檩间,竟发现一双我从未见过的颇有古意的厚底棉鞋,这种鞋布面毡底,做工极为考究,鞋底约有四五公分,鞋面上也多有装饰,因此老辈人称为“大加工的鸡窝窝”。可巧的是,在堂屋的正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上,长袍美髯的堂祖父穿的似乎正是这双鞋。据茂林讲,这双鞋堂伯父生前也曾穿过。房子翻修了以后,老人就把它随手放在了那上边。可是我想,将这样一双“敝屣”放在这样一个“有碍观瞻”的地方,究竟是信手无意,还是别有所期呢?看着披麻戴孝的年仅四五岁的小堂侄——将来这座宅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听着呜呜咽咽的唢呐声,跪在列祖列宗的灵前,我禁不住泪下如注了。
在老家两天,充塞心头的除了对世事匆匆的深深感喟,就是对贫瘠荒凉的痛切忧思。老家所在的地方名叫双湖,数十年前曾祖父在几十里外垦田置地,所选的地方竟然也叫双湖。老家双湖究竟有没有湖,不得而知。但那里种树比较容易成活,尤其是杨树。那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杨树,而惟独我们何家老宅的后面有两棵挺拔傲岸的祁连松。小时候到老家去,听说这两棵树年长于我们的祖父,心中便无限敬仰。这次拜望它们,感到它们的生长虽然非常缓慢,但是在干坼的黄土地上显得格外富有生机。在宅子的四周,几十年来栽了不少的杨树,有一些已伐去作了建房的材料,惟独这两棵松树,至今仍旧盎然地葱郁着,成了冬春季节宅院内外惟有的绿色。在我的眼里,这两棵青松不啻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更是一种来自历史和未来的殷殷期待。它们的怡然健在,使我对堂伯父一家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现在我们所在的双湖,倒确实有湖,但所谓湖,只不过是人们对沼泽地的一种俗称。“湖”里的水原本是很充沛的。记得小时候,每当春夏时节,一到夜幕降临,水里的青蛙便开始高声吟唱了。住在清幽幽的小山村里,倒颇有点“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味道。可是这些年来,耕地不断扩展,“湖”滩日渐萎缩,“湖”里的水已经很少,过去冬季冰雪皑皑、夏季水草如茵的地方,现在一片焦黄。前几天一个傍晚,陪耕地归来的父亲走过被近年新开的荒地紧紧围困的小“湖”,听见几声可怜的蛙鸣,我的心不禁凄然。
我突然想起老家里先祖留给我们的那两棵顽强的松树,是它们在我的心头投下了一片浓郁的绿荫。我还想起为堂伯母送葬的那天早上,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村里人敲响的干涩、凄厉的锣声,是它使我深深地感到了时光的悠远和人生的短暂。今天,面对脚下的这片黄土,遥想着百十年后的子子孙孙,我不禁诘问自己:作为先民的后裔,作为后人的祖先,我们应当和能够留给后人的又该是什么呢?
拜谒古烽墩(散文)
自小生活在甘凉古道边,对烽火墩台可谓司空见惯了。在过去四十年漫长而匆促的岁月里,也曾想走近它,瞻仰它,甚至想登上它的巅头。但是这么多年,这样的念头往往是稍纵即逝,因此久未如愿。直至今年盛夏,我才乘便在草原的深处瞻仰了一处烽墩。其实与其说是烽墩,不如说是古烽墩遗址。
这是大马营草原腹地的四墩烽火台。这处建于明代的烽墩原是两座,一南一北,相距约十米,因数百年风雨侵蚀,所见者唯两座土丘而已。土丘之上,荒草萋萋,随风飘摇。土丘旁,辙印纵横,足迹斑斑,想必来者中不乏凭吊之人。土丘的基部可见几个残破的洞窟,大概是早年的牧人为栖身避雨而挖的。在一个破洞里,有一段胳膊粗的朽木半露着断茬,伸手一掰,断木竟枯朽得近乎成灰了。从残留的丝瓜络似的黄褐色纤维上可以推想,它是当年夯土墩时所用的松椽。站在土丘旁,环顾四周,禾麦青青,一望无垠,菜花飘香,蜂蝶嘤嘤。古老的烽火台就这样老态龙钟地蹲踞在这无边的花海碧浪里。一时间,这两座土丘,在我的眼里完全幻作了两座坟墓,它的主人似乎纯粹是一介草民,它的身心本来就与主人的故事一样千疮百孔。或许再过几十年,这两尊荒冢将永远被湮没在朔风衰草之中。
但是,在它的家族中,也有不屈的强者至今仍傲然挺立着,讲述它们昔日的辉煌。
农历七月十五,我偕家人去到多年未曾去过的先人坟头焚香压纸,默然祷祝。返回的路上,我独步登上了那座高高的墩洼山。山在群峰间并不见奇,但因这饱经沧桑的烽墩,便格外令人敬仰。这个烽墩同样建于明代,虽经风雨剥蚀,不见了当年的棱角,但其基本规模并未破坏。墩高约七八米,东、南两壁较为挺直,只是上面布满了鸟雀的洞窠,基部像城墙根一样颓朽进许多。墩身上有几处地方缝隙大开,颇有摇摇欲坠之感。墩的西、北两侧,因雨水冲刷和登临者的攀援,大致变成了坡形,自底到顶,有渐高渐疏的荒草。轻攀着草茎,手脚并用,我竟登上了这久已向往的墩台。
登台远望,山峦起伏,宛如细浪泥丸,祁连焉支,尽收眼底。十里之外,南北东西各有烽墩相望,势成犄角,矗立赫然。伫望之间,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狼烟滚滚、兵戈阵阵的历史场景。这苍老的烽墩啊,在你颓败的躯体和干涩的眉目间,不知遭遇了多少风刀霜剑,融汇了多少荣辱悲欢。你像一位退役的老将,遍体的疮痍掩不住你昔日的威武。而今在你身边的沟沟洼洼和山山峁峁间,农人们正在收拾成熟的庄稼,漫山遍野一片宁谧和安详。惟有那满载着农民血汗和希望的胶轮马车,在陡窄的坡道上吟唱着古老的歌谣。
我曾登过泰山,但除却孔老夫子给我的“成见”以外,我并没有体会到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怀和意境。倒是在这个小小的烽墩山上,我却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和怅惘。当我在山顶上留连顾盼的时候,“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圆圆的月亮已从东山升起,山坳里家家的房顶上,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噢,圆缺有常、亘古不变的明月,你不知疲倦地照耀着,照耀着沉默无言的苍凉历史,也照耀着我生生不息的父老兄弟,照耀着山里人家岁岁相同而又日日各异的繁忙与清苦。在这云淡风清的夜晚,愿你与夜夜谋面的烽墩拉起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
(以上作品原载《张掖广播电视报》)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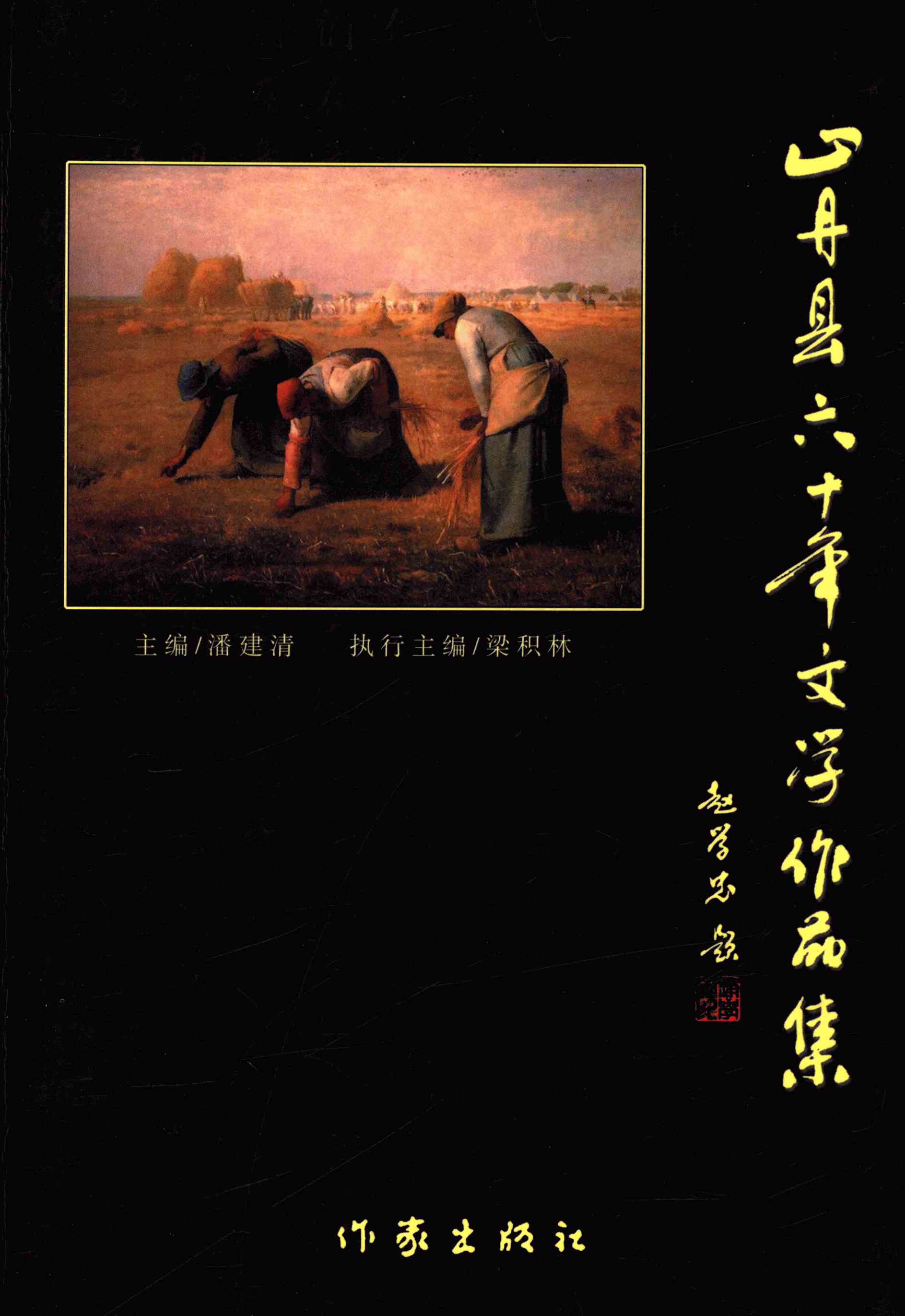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何茂活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