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平作品
| 内容出处: | 《山丹县六十年文学作品集》 图书 |
| 唯一号: | 292420020220001819 |
| 颗粒名称: | 杨桂平作品 |
| 分类号: | I267 |
| 页数: | 9 |
| 页码: | 128-136 |
| 摘要: | 本文记述山丹县杨桂平所作的散文,其中介绍了《北方,我童年的摇篮》、《乡村葬礼》、《民工重喜》。 |
| 关键词: | 山丹县 杨桂平 散文 |
内容
作者简介:杨桂平,女,生于美丽的大马营草原。自修法律本科毕业。先后从事过乡镇、乡企工作,后曾经商数年,现在林业系统工作。爱好文学,1985年散文《焉支行》获上海《少年文艺》全国征文一等奖并入选山丹县志。先后在天津《中华少年》及省内多家报刊发表散文《北方,我的摇篮》《我的村庄》《爱的味道》《乡村葬礼》;小说《桃花依旧》《民工重喜》等50多篇。最近完成短篇小说《这个冬天没下雪》
北方,我童年的摇篮
(散文)
离开故乡六、七年了,我从一个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山村傻妮子长成了十七岁的姑娘了。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吃惊,可那北方孩子所特有的童趣却依然如故。我的思绪飞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北方孩子的世界象摹上的鲜花一样丰富多彩。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有他们无比的快乐。
一
北方的春天,不是迈着轻盈的步伐静悄悄地来的,而是驾驶着狂风呼啸而来,象千军万马在奔驰、呐喊、厮杀!这时,虽然没有春的迹象,但她确实来了。
狂暴的风怎能锁住我们那一颗好奇的童心。叫上一行伙伴,溜出门,撒腿就向广袤的草地跑去,扑进那枯黄的草地,眼紧紧盯着地皮,狂风似乎不存在了,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突然,哪一个叫了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好几颗脑袋碰在一起,碰的生疼也不叫喊,只急急地扒开枯草,最里边露出一行行嫩嫩的黄生生的青草芽。
抽青草芽儿,是我们的一大乐趣。用嫩生生的小指头捏住草芽儿上上抽,露出根部那白嫩白嫩的一截。我们高兴得大喊大叫。带回去给妈妈瞧,可妈妈说:“失去了孩子,大地妈妈会哭的。你们贪玩时,妈妈不也急着去找吗?”是这样的。后来我们不再抽了,只许看,看足了几双小手便又慎重地、轻轻地抹平枯黄的草,盖住这刚诞生的生命。幼稚的童心从此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天天盼它长高、长大,开出花儿、结出籽儿……
二
如果早春是一支旋律粗犷高昂的交响乐。那么,当春浓过后,她又奏起一支柔和的抒情曲。夏天便踏着这和谐的旋律向我们走来。这个时候,天地就属于孩子们了。千里草原是无垠的大海,又似一张绿绒绒的大地毯,一直铺到和蓝天相衔的地方。繁忙的妈妈是顾不上我们的,只是把我们交给这绿的摇篮。鸟声、蛐蛐声是我们悦耳的摇篮曲。
我们一个个都是大自然的女儿。在草甸这偌大的幼儿园里,牛羊是我们最要好的伙伴;鲜花、昆虫是我们最称心的玩乐具。在这个幼儿园里,我懂得了思考、幻想。可我也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有彩虹呢?白云飞到哪儿去啦?薄暮时,便带着最乐意做的这些作业回家了。草甸上,热烈的夏风还给了我们北方人特有的皮肤,虽然没有江南孩子隽秀的美,却有她们所没有的粗犷的美;就象白杨虽然没有杨柳的婀娜,却有自身的挺拔。
广阔的草原上,似乎太阳也迟迟不肯落下。收工的人们披着晚霞归来,炊烟开始升起,那“嗞啦”的炒菜声惊得夕阳不小心滑下山丘,星星开始眨眼了。这时,我和伙伴们还没在家打照面呢。我们呵,正聚在村边那平整的草甸上,完成我们的“作业”呢!
村里的刘姐姐是个故事兜,一块彩云也让她讲出好几个故事呢。虽然妈妈在静夜讲了好多遍,可我还想往那儿凑,妈妈对我们毫无办法。白天的那些“作业”在刘姐姐的绘声绘色中解决了。
雨过天晴,彩虹当空,虹是什么?村里大伯讲,那是龙在吸水;妈妈说,那是仙女织就的锦缎;可刘姐姐说得更神。那是登天的彩桥,有福气的人就能登上它到天堂里过好日子。过好日子,我没想过,可那时我幼稚的心里却在想画书里的孙悟空、嫦娥仙子一定在登天彩桥通向的地方。登上彩桥的愿望压倒了以往曾最神往的能够骑马转一圈(伙伴们都敢)的愿望。睡梦中,彩桥无限延伸,伸得很远、很远……
三
秋天,真是个技艺高超的画师,它挥动着满蘸金粉的笔,在这绿的底色上大涂大抹,把个故乡抹的金光灿灿,一块一块的豆地似姐姐们金黄色的围巾,东抛一块、西抛一块。
豆儿黄了,拾豆去。拾豆子,也是故乡孩子的一大乐趣。拽在妈妈的后面,提个篮子,便上地了。拾呀拾,伙伴排成一溜,比赛谁快!男孩老在前面,可豆儿最少;女孩儿却没有了草甸上的野气,半天才向前一步,可滴溜圆的豆豆滚篮子。妈妈夸着,满篮的豆儿也在咧个嘴巴笑着!
整个秋,我和妈妈一样,忙得象豆儿也咧个嘴巴笑着!
整个秋,我们和妈妈一样,忙得象豆儿滴溜溜转。好忙的秋啊……
四
冬,是故乡孩子最快乐的季节。
雪,铺天盖地的大雪,把个枯黄的草甸子捂得严严实实。风恣肆地在旷野上呼啸,雪片子漫天飞舞,扑打在脸面上就象抓似的痛。
北方的雪,一下就几尺厚,庄稼人缩在屋里,整个秋季的辛劳便融化在这白雪里,为来年的希望积蓄着力量。孩子们却拿出晚秋就准备下的冰车,早溜到那晶莹莹的天地里去了。
记得我还曾偷出妈妈的烧火棍,架子车上的档板,换回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冰车。当然,少不了挨妈妈几巴掌,可我有了自己的冰车,别提多高兴了。故乡的孩子,没有冰车要被伙伴们瞧不起的。所以,我的伙伴们几乎人人都有。
那条结实绵长的玉带,永远是孩子们的乐园。只要我的哪一个伙伴喊一声:“溜冰去喽!”我们便一个个猫似地从家里溜了出来。
北方的冬真是寒冷,北风呼呼地叫着、吹着,吹得我们的脸和手通红通红,在晶亮的冰面上一映,似一朵朵傲雪盛开的腊梅。我们也似梅花般喜爱这白皑皑的世界。那欢乐的笑声,随着满天雪花飞舞,幼稚的童趣洋溢在沾满水碴儿的鼻尖上。在这晶莹的世界里,我们个个成了雪娃娃,在隆冬的怀抱里玩呵玩,玩得忘了寒冷,忘了屋里干着急的妈妈。这冰晶晶的一纪哟,把我的童年裹在一片净洁里……
故乡啊,你的早春给了我桀骜不驯的性格;盛夏给我插上了幼想的翅膀;金秋给了我丰收的快乐;隆冬送我一双晶莹的眼睛和水晶一般的童心。纯洁,北方孩子的本色。
故乡啊,你给了我一个欢乐的童年。少年的我,又在时时想着怎样才能给你一个丰丰盛盛的回报啊……
乡村葬礼(散文)
十月初寒,日子里莫名地多了许多忧伤。先是失去了一位朋友,接着又失去了几位亲友。于是我忙着参加他们的葬礼,忙碌中忧伤反而淡了许多。
在乡下,除了婚礼,葬礼是最隆重、最繁忙的礼节。年轻人意外离去,带来的巨大悲痛几乎冲垮亲人们的意志。他们的葬礼匆忙、简单,但那深深的悲伤和痛苦却持续地、长久笼罩在亲人的周围,从那哀痛的氛围解脱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老年人离世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将近古稀之年的老年人去世,他们的子孙将伤心与哀痛用另一种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这就是最典型、最隆重的葬礼。
我年轻的朋友刚过而立之年,因为意外而离去,在她的葬礼上,亲人、还有朋友们都痛苦不已。年轻的生命,昨天还笑语盈盈,今日却桃花凋零。看着她那可爱不懂事的孩子,还有悲痛欲绝的父母。我宁愿相信她还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灵魂出了一趟远门。钻心的疼痛遍布空气中,我不想看到她离去的面容,我愿我心中珍藏她生动活泼的笑容一辈子。朋友们都承受不起她的离开,何况她的亲人。葬礼几乎在压抑的悲痛中进行着,除了她的父母撕心裂肺的痛哭,哭得不省人事,孩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幼稚的脸庞泪滴未干就靠在一位朋友怀里睡着了。我们没有人说话,互相用一种绝望的眼神交换着悲痛与伤心。
这样的葬礼参加一次就够了,再也不要遇到,永不去再想。因为乡下有许多讲究,朋友因意外在外面出的事,她的身体在死后不能进自家的门,在寒风中飒飒抖动的帐篷里,她的灵魂是否在九天之外徘徊,不忍离去,深深依恋着她的父母,丈夫和孩子,是否为她冰冷、孤独的身躯在哭泣……
参加老人的葬礼却是大不相同,那份悲哀与伤痛都是在有条不紊的秩序与礼节中渲染出来的。没有大痛大悲,那种忧伤无奈地,按部就班地按照礼节一道一道地表达出来。那哭腔都是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的。这样的葬礼算得上正规的彩排了,有编导、有演员、有道具,还有许多观众。在乡下这样的葬礼很隆重,也表现出子孙的“孝心”,但更像是给离去的亲人开一场盛大的“欢送会”。
在乡下葬礼中最讲究的就是“房子”之材。人活着的时候安生立命,造屋建瓴,死了也要让灵魂有所依托,“房子”是很讲究的,一般都是上好的松木。古时的富贵人家必是棺椁齐备,稍次者也要是“金匣套材”,一般人家是“子底子盖”。当然也有贫穷的人家用草席安葬,那种不仅仅是痛失亲人的哀伤,还有不尽言谈的苦楚在当中。到了如今,说不上有多奢侈,但棺木在知天命之年以前必定要给老人准备停当,好让老人安心,也要表出子孙的孝心,几乎都是“金匣套材”。
我的已去逝的亲友就在生前谈论死后安葬的棺木,他们神情坦然,似乎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大事,凝重的表情还是有的。想想人死如灯灭,谁又能带走什么或不带走什么。他们历经了世事的几多沉浮沧桑,对生死不是看透之极,也是处之泰然了一点。“三国志”上说:“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生生死死,循环往复,生是有限的,死却是永恒的。这是一种自然之道。老人们看开了,便也坦然。但活着的人更要紧的是要活出质量来。
在参加亲友的葬礼中,我见到了画好的“房子”,龙飞凤舞,绚丽多彩,据说人死后都要足登“莲花”上“天堂”。“房子”一头画好的莲花栩栩如生,风吹荷动,灵魂似乎安然升入天国,对生者也是莫大的安慰。对画“房子”来说,也是有讲究的,怎样画要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品德、德智,也算是对去世者的一种人生总结吧。但人死如灯灭,纵有天大的功过,也是留与后人追怀悼念而已。这样的讲究,以我看来,只是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与鞭策。
葬礼中最感动人的我认为是安葬前夕的“洒灯”这个祭祀活动了。我不懂这个礼节流传下来的真正意义。只是凭着感觉理解它的含义。祭祀活动的主持,一般是请来的信奉道教和佛教的人担当,他们在前面吟唱着,哀乐齐奏,后面跟着穿着白衣头挂白练的亲人与朋友有节奏地三叩九拜,每个人手中都执着用纸糊制的形形色色的祭祀车马、仙鹤、花圈等祭品。庞大的队伍要围绕村子缓慢地转一圈。哀乐声也很缓慢而悠长,夹着亲人悲怆的哭声,飘荡在空旷的乡村四野上空,散漫得很远很远,火化的纸钱明明灭灭……那种悲伤不由得从胸腔里澎湃而发,似乎逝者的灵魂也在上空飘荡,它俯瞰着悲伤的亲人,熟悉的村庄,带着对故土的怀念,对亲人深深地依恋,最后看上一眼,走上一趟,步履缓慢而沉重。生死不由自己选择的无奈,对尘世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从那哀怨而忧伤的唢呐调儿里徐徐流淌出来……
在我参加的葬礼中最热闹、最有味的时候是“开悼”。“开悼”就是官方所说的追悼会。但民间的这种形式或内容更繁杂,表现的更生活一些。除了花圈挽幛必不可少,还要“摆祭”,一般是亡者的直系亲友把自家精心赶制出来的粮食供品和牲畜供品摆放灵前进行的一次宗品大展览。供品五花八门,有面制的动物,面制的水果,面制的人儿,生活中有的这儿都有,井然有序,像是一种生活的场景。这时候,随着司仪的抑扬顿挫的吆喝和吹鼓手们激情奔放的哀乐鼓奏,人们要打恭做揖,亲近的女眷们不管真假,都不得不在灵堂前下跪嚎哭。“开悼”结束了,她们哭声成了另一道风景。哭声不一样,心情也各异。大部分女眷在人们的半拉半劝下起身去厨房忙活了。只有哭得悽悽惶惶,呜咽不成调的是亡者至亲的人。她们的哭声悲痛欲绝,大有同亡者同去的架势,惹得一旁看热闹的老年妇女们一阵阵心酸,忍不住掩面而泣。最有特色的是那种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的哭。我在本家奶奶葬礼中,不会像她们那样哭,只有心酸,默默流泪,旁边的老姑母哭得抑扬顿挫,似哭似唱的历数着老人生前的为人热心,贤惠善良。我听得入迷,这时大嫂俯耳问姑母她看管的用品在哪,姑母一边依旧好像没听见一样哭着,一边用手子里指着西厢房那边,用她那特别的哭腔说:“在…西厢房…的…大立…柜子里…呀……”。我忍不住笑了,大嫂却严肃的瞪我一眼,拉起我就走了。姑母的哭声依旧有腔有调。
在我参加的几次葬礼中我感觉最伤感和悲痛的时候,也是葬礼的高峰时刻,就是七天以后的“出殡”。那是葬礼的悲痛达到了极致。墓穴早已在前一天挖好,出殡前夕入殓,翌晨抬棺出殡,到墓地安葬。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又开始了。人死不能复生,子孙只有在清明,年节上祭奠失去的亲人,表达哀思,这也是人心情偶尔释放的一种方式。真真的伤痛还是埋在心底,轻易不会示人。
本家奶奶送葬的早晨是一个清秋寒露的日子,鱼肚白的天空还有几个星星在闪着眼,弯月如钩,清冷的空气如凝结在一起,远处的山坳黑嘘嘘的蹲在那里,它也许经历了无数次相同的场面,已变得既不悲伤也不痛苦。送葬的队伍静悄悄的行走,生怕惊醒了安睡的灵魂,要在不知不觉,毫无痛苦的情形中让离世的人安然入土。只有第三锨土覆盖在死者身上,唢呐声骤然响起,就有悲痛的人发出抑制不住的痛哭声……
人生已安然走远,离去的只是人的躯体,那种为人的精神要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在后代乃至在宇宙中永存的。活着的人,当然要活出精神来。
民工重喜(小说)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你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工身上,却让我们感到悲哀至极。
青海、柴达木盆地、茫崖镇。
沙尘瀑、骤雨、冰雹、大雪。
这些真实而冷酷的名词。民工重喜做梦也没想到它们会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且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人们永远记不住民工重喜的名字,却会对这些名词刻骨铭心。
下午六点还不到,放线工重喜看到西边飘过来的那片黑云时,惊恐万分,等不得收工的号令撒腿就往回跑,半道上碰到前来收工的队长。这次队长没有喝叱他,只是说:“天要下雨啦,你穿得单薄了一点吧。背心、背心呢?!”一下子,重喜头里嗡的一下,那个装工具的背心夹层里还装着自己的存折呢?怎么能忘了这么重要的东西。重喜毅然往回走,边走边和天边的黑云赛跑,慌乱中让什么东西拌了一下,差点摔倒。一看原来背心就在脚底下,光顾着看云了,差点错过放背心的地方。这不就是天热那会儿喝水吃干粮的地方嘛,重喜自嘲地笑了。甚至有点欣喜苦狂,一把抓起背心学着电视剧中的样子亲吻了一下,突然听到有人喊:沙尘暴来了,快下山呀!喊声在山洼里来回游荡,却看不见人影,重喜猛地想起得赶紧回呀!
沙尘暴说到就到,像一个饥饿的野兽,铺头盖脸地扑向重喜,眼睛睁不开了,满嘴都是泥沙。只得紧了紧身上的背心,重喜迎着风沙跌跌磕磕的往回走。谁知沙尘暴还没过去,一阵密如利剑的倾盆大雨伴着炸耳的雷声来得更加凶猛,瞬间重喜就成了落汤鸡。转眼间,山洼里洪流纵横,似万马奔腾汇入沟底,形成一条发怒的暴龙冲山而出。重喜看得目瞪口呆,紧紧抓着岩石草皮,以防自己让这条暴龙吞没。他护着脸,顺着山道小心拔出陷进泥泞的脚,一步一步向前慢慢走,再也不敢贪快,心想我可不能掉下去,掉下去我的存折就没了。重喜不由得摸了摸怀中的存折,硬邦邦的还在,重喜心里踏实多了。重喜想起媳妇说揣着折子就好像揣着媳妇一样。出来打工时,重喜想把存折放下,可媳妇说你就拿着吧,同村的山娃打工几年了,一分工钱没要着,还要饭回来了,你就以防万一吧!重喜就揣上了,可心里想,有再急的事,我也不会动存折上的一分钱。可媳妇说,你就当把我揣怀里了,重喜就没话说了。重喜有点想媳妇了,于是加快了步子。
这个不长眼的老天爷!重喜心里狠狠骂道,势利得让人心寒,难道人穷了,连老天爷也不帮衬,说变就变脸,雨中又夹着豆子大的冰雹砸了下来,重喜摸摸发麻的脸颊,脸上恣意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重喜有点后悔了,不该不听媳妇的话,听信包工头的花言巧语,说这野外放线工就是来回多跑几步路的事,况且人家又是最大的物探公司,给的工钱又很诱人。自己一合算,干几个月回去,就可以凑够媳妇舅舅要得那两万元了,就可以堂堂正正,热热闹闹把媳妇娶回家了。可这老天爷一变脸,摊上如此倒霉的天气,怕要把自个的命搭上了。这样一想重喜心里一激凌,不能死!媳妇还盼着自己回去呢!回去娶她呢!重喜心里升起一股热切的希望来,精神好像也足了些,咬着牙终于走出了山。到了平地,倒处是泥,一走脚下就打滑,不过重喜还是松了一口气,却感到身体没有气力了,牙齿在打颤,浑身冰凉。重喜这会儿万分想念媳妇烧的热炕,还有媳妇那热热的身子……
五年前,重喜把媳妇从青海领到老家古浪,可自家穷得叮当响,眼睁睁地看着媳妇舅舅心满意足的点着同村富贵家的钞票,媳妇成了富贵的婆姨!重喜灰心丧气的,也像村里的懒汉一样在墙跟晒了三天太阳,暖洋洋的阳光照着重喜,重喜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有太阳照着,有没有媳妇不是很重要了。“啪”的一声,重喜脸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是老爹吧,老爹说:“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五尺汉子,出去挣去!挣个媳妇回来”!那一巴掌就把重喜撵出了家。可这会儿却听到有人在吼叫,是队长的声音:“快起来,不能睡!混蛋!不能睡!爬也要爬回去。”可重喜好像没有当年走出村子的勇气了。重喜睁了睁眼,冰雹不知啥时停了,弥天大雪像疯了的一群白蝴蝶,铺天盖地而来,像要把人埋在这儿。身上单薄的背心像铁盔甲一样发出咔嚓嚓清脆的声音,在这空寂的野外却有地动山摇的感觉。背心还在身上!重喜竟然觉得一点不冷,虽然天气骤然降温了。睡这儿比媳妇烧的热炕还暖和,重喜不想醒来,睡够了,明天还要上工挣钱呢?马上就凑够两万了。有人在推他,重喜眼前模糊一片,几个人影像在演皮影戏,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重喜像要飞起来了,这种感觉真好!重喜感到很满足,马上就够两万元了,凑够两万元,就可以娶媳妇回家了。那个贫穷的家,可重喜还是想回去,回去对富贵说:本来就是我的媳妇!我娶回来了!当年重喜看到媳妇成了别人的,心痛的突突跳,挨了老爹的一巴掌后,一狠心从家里跑了出来,买个绱鞋的机子东奔西走,倒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心里头终究不踏实。三年后,衣着光鲜的他回到老家那个穷沟沟时,媳妇连抱带拽地领着三个女娃子把他堵在了村口,媳妇在重喜面前泪一把,鼻一把地怨他,说重喜把她带到了火坑里,成了生娃的机器。三年没生出个带把的,三个丫头片子让她受够了气。偷着跑了几次,让男人抓回来,揍得半死,如今一听到男人的声音就打颤。先前水灵灵的大姑娘变成了蓬头垢面的邋遢婆姨!重喜看得心里翻江倒海,不是个滋味!年三十晚上不顾一切领着媳妇又偷跑了出来。从此,东躲西藏,背着绱鞋机子尽往山洼洼,穷沟沟里走。媳妇怨他不能给她一个安稳日子过,没办法,家里回不了,只好回到媳妇娘家,可媳妇娘家只有一个把媳妇拉扯大的舅舅。好在舅舅现在生活好了,也没说啥,还让媳妇帮忙料理自己的杂货店,挣几个生活费。舅舅又对重喜说,你拿来2万元钱,舅舅周旋着把离婚证办来了,你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家了,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平时绱鞋日子还能过去,攒下的钱离2万元还差8000元呢!可凭空里拿出8000多块钱,重喜愁得心焦。那天,找人的工头一说,重喜二话没说就要跟着去。媳妇不让走,从没和媳妇红过脸的重喜甚至还喝了点酒和媳妇闹了别扭。干了一个月,钱倒是差不多了。重喜想,挨过了这倒霉的天气,再干几天就回,真有点想媳妇了,这太阳可真暖和啊,像村头晒过的太阳一样叫人无忧无虑,民工重喜心满意足地睡着了,睡得踏踏实实,嘴角溢着幸福的微笑,手里捏着一个农村信用社鲜红的折子。
皑皑白雪下的格尔木肃然寂静,二十二医院太平间15个牌子上写着遇难的15人的姓名。重喜的哥哥木然地看着弟弟的遗物,他不相信弟弟已不在了,也许他把行李、包裹遗忘在这儿了。这个从小就不着家的弟弟啊!
格尔木殡仪馆,烧纸痛哭,火焰冲天。15个亡魂乘风而去,留下一堆尘埃!
5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播出专题片《冰魂》,主持人阿丘哽咽难言。背景中事发地点大乌斯工区崎岖地貌,让冰雪覆盖着,寂静地像是月球表面,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阳光依旧照下来,安详而热烈。
后记:青海遇难的民工15人,我们山丹去了2人,其中1人是从古浪打工到山丹,转辗又到青海花土沟打工的民工。事出后,死者的哥哥领到了全部的抚恤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的他看到弟弟的尸骨时没有流下几滴眼泪,可看到那么多钱时却放声大哭!是悲哀,还是狂喜?让人不明就理,那个并没有和重喜成家的媳妇也哭哭啼啼的来了,看到亡人的骨灰,她说你个害人的呀,我又要到哪里去找安身的地方!擦干眼泪,她小心地试着问重喜的哥哥,说起了存折的事,说是她和死者共同的积蓄。可是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存折。她抱着骨灰哭得要死要活!好在调解人看在亡人的份上,也给了她一定的补偿。她才止了泪,便回了娘家。不知她是否有个舅舅。
贫穷真是个可恶的字眼,它使人们格外重视钱的存在。可随之而来的冷漠和无情让道德和良心显得更加苍白无力,终究拭不去人们心灵上让金钱蒙上的那一层灰尘,只能靠法律来解决。贫穷这把锁是生锈了,开锁的钥匙在哪儿呢?
(以上作品原载《张掖日报》、《焉支山》)
北方,我童年的摇篮
(散文)
离开故乡六、七年了,我从一个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山村傻妮子长成了十七岁的姑娘了。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吃惊,可那北方孩子所特有的童趣却依然如故。我的思绪飞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北方孩子的世界象摹上的鲜花一样丰富多彩。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有他们无比的快乐。
一
北方的春天,不是迈着轻盈的步伐静悄悄地来的,而是驾驶着狂风呼啸而来,象千军万马在奔驰、呐喊、厮杀!这时,虽然没有春的迹象,但她确实来了。
狂暴的风怎能锁住我们那一颗好奇的童心。叫上一行伙伴,溜出门,撒腿就向广袤的草地跑去,扑进那枯黄的草地,眼紧紧盯着地皮,狂风似乎不存在了,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突然,哪一个叫了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好几颗脑袋碰在一起,碰的生疼也不叫喊,只急急地扒开枯草,最里边露出一行行嫩嫩的黄生生的青草芽。
抽青草芽儿,是我们的一大乐趣。用嫩生生的小指头捏住草芽儿上上抽,露出根部那白嫩白嫩的一截。我们高兴得大喊大叫。带回去给妈妈瞧,可妈妈说:“失去了孩子,大地妈妈会哭的。你们贪玩时,妈妈不也急着去找吗?”是这样的。后来我们不再抽了,只许看,看足了几双小手便又慎重地、轻轻地抹平枯黄的草,盖住这刚诞生的生命。幼稚的童心从此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天天盼它长高、长大,开出花儿、结出籽儿……
二
如果早春是一支旋律粗犷高昂的交响乐。那么,当春浓过后,她又奏起一支柔和的抒情曲。夏天便踏着这和谐的旋律向我们走来。这个时候,天地就属于孩子们了。千里草原是无垠的大海,又似一张绿绒绒的大地毯,一直铺到和蓝天相衔的地方。繁忙的妈妈是顾不上我们的,只是把我们交给这绿的摇篮。鸟声、蛐蛐声是我们悦耳的摇篮曲。
我们一个个都是大自然的女儿。在草甸这偌大的幼儿园里,牛羊是我们最要好的伙伴;鲜花、昆虫是我们最称心的玩乐具。在这个幼儿园里,我懂得了思考、幻想。可我也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有彩虹呢?白云飞到哪儿去啦?薄暮时,便带着最乐意做的这些作业回家了。草甸上,热烈的夏风还给了我们北方人特有的皮肤,虽然没有江南孩子隽秀的美,却有她们所没有的粗犷的美;就象白杨虽然没有杨柳的婀娜,却有自身的挺拔。
广阔的草原上,似乎太阳也迟迟不肯落下。收工的人们披着晚霞归来,炊烟开始升起,那“嗞啦”的炒菜声惊得夕阳不小心滑下山丘,星星开始眨眼了。这时,我和伙伴们还没在家打照面呢。我们呵,正聚在村边那平整的草甸上,完成我们的“作业”呢!
村里的刘姐姐是个故事兜,一块彩云也让她讲出好几个故事呢。虽然妈妈在静夜讲了好多遍,可我还想往那儿凑,妈妈对我们毫无办法。白天的那些“作业”在刘姐姐的绘声绘色中解决了。
雨过天晴,彩虹当空,虹是什么?村里大伯讲,那是龙在吸水;妈妈说,那是仙女织就的锦缎;可刘姐姐说得更神。那是登天的彩桥,有福气的人就能登上它到天堂里过好日子。过好日子,我没想过,可那时我幼稚的心里却在想画书里的孙悟空、嫦娥仙子一定在登天彩桥通向的地方。登上彩桥的愿望压倒了以往曾最神往的能够骑马转一圈(伙伴们都敢)的愿望。睡梦中,彩桥无限延伸,伸得很远、很远……
三
秋天,真是个技艺高超的画师,它挥动着满蘸金粉的笔,在这绿的底色上大涂大抹,把个故乡抹的金光灿灿,一块一块的豆地似姐姐们金黄色的围巾,东抛一块、西抛一块。
豆儿黄了,拾豆去。拾豆子,也是故乡孩子的一大乐趣。拽在妈妈的后面,提个篮子,便上地了。拾呀拾,伙伴排成一溜,比赛谁快!男孩老在前面,可豆儿最少;女孩儿却没有了草甸上的野气,半天才向前一步,可滴溜圆的豆豆滚篮子。妈妈夸着,满篮的豆儿也在咧个嘴巴笑着!
整个秋,我和妈妈一样,忙得象豆儿也咧个嘴巴笑着!
整个秋,我们和妈妈一样,忙得象豆儿滴溜溜转。好忙的秋啊……
四
冬,是故乡孩子最快乐的季节。
雪,铺天盖地的大雪,把个枯黄的草甸子捂得严严实实。风恣肆地在旷野上呼啸,雪片子漫天飞舞,扑打在脸面上就象抓似的痛。
北方的雪,一下就几尺厚,庄稼人缩在屋里,整个秋季的辛劳便融化在这白雪里,为来年的希望积蓄着力量。孩子们却拿出晚秋就准备下的冰车,早溜到那晶莹莹的天地里去了。
记得我还曾偷出妈妈的烧火棍,架子车上的档板,换回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冰车。当然,少不了挨妈妈几巴掌,可我有了自己的冰车,别提多高兴了。故乡的孩子,没有冰车要被伙伴们瞧不起的。所以,我的伙伴们几乎人人都有。
那条结实绵长的玉带,永远是孩子们的乐园。只要我的哪一个伙伴喊一声:“溜冰去喽!”我们便一个个猫似地从家里溜了出来。
北方的冬真是寒冷,北风呼呼地叫着、吹着,吹得我们的脸和手通红通红,在晶亮的冰面上一映,似一朵朵傲雪盛开的腊梅。我们也似梅花般喜爱这白皑皑的世界。那欢乐的笑声,随着满天雪花飞舞,幼稚的童趣洋溢在沾满水碴儿的鼻尖上。在这晶莹的世界里,我们个个成了雪娃娃,在隆冬的怀抱里玩呵玩,玩得忘了寒冷,忘了屋里干着急的妈妈。这冰晶晶的一纪哟,把我的童年裹在一片净洁里……
故乡啊,你的早春给了我桀骜不驯的性格;盛夏给我插上了幼想的翅膀;金秋给了我丰收的快乐;隆冬送我一双晶莹的眼睛和水晶一般的童心。纯洁,北方孩子的本色。
故乡啊,你给了我一个欢乐的童年。少年的我,又在时时想着怎样才能给你一个丰丰盛盛的回报啊……
乡村葬礼(散文)
十月初寒,日子里莫名地多了许多忧伤。先是失去了一位朋友,接着又失去了几位亲友。于是我忙着参加他们的葬礼,忙碌中忧伤反而淡了许多。
在乡下,除了婚礼,葬礼是最隆重、最繁忙的礼节。年轻人意外离去,带来的巨大悲痛几乎冲垮亲人们的意志。他们的葬礼匆忙、简单,但那深深的悲伤和痛苦却持续地、长久笼罩在亲人的周围,从那哀痛的氛围解脱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老年人离世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将近古稀之年的老年人去世,他们的子孙将伤心与哀痛用另一种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这就是最典型、最隆重的葬礼。
我年轻的朋友刚过而立之年,因为意外而离去,在她的葬礼上,亲人、还有朋友们都痛苦不已。年轻的生命,昨天还笑语盈盈,今日却桃花凋零。看着她那可爱不懂事的孩子,还有悲痛欲绝的父母。我宁愿相信她还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灵魂出了一趟远门。钻心的疼痛遍布空气中,我不想看到她离去的面容,我愿我心中珍藏她生动活泼的笑容一辈子。朋友们都承受不起她的离开,何况她的亲人。葬礼几乎在压抑的悲痛中进行着,除了她的父母撕心裂肺的痛哭,哭得不省人事,孩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幼稚的脸庞泪滴未干就靠在一位朋友怀里睡着了。我们没有人说话,互相用一种绝望的眼神交换着悲痛与伤心。
这样的葬礼参加一次就够了,再也不要遇到,永不去再想。因为乡下有许多讲究,朋友因意外在外面出的事,她的身体在死后不能进自家的门,在寒风中飒飒抖动的帐篷里,她的灵魂是否在九天之外徘徊,不忍离去,深深依恋着她的父母,丈夫和孩子,是否为她冰冷、孤独的身躯在哭泣……
参加老人的葬礼却是大不相同,那份悲哀与伤痛都是在有条不紊的秩序与礼节中渲染出来的。没有大痛大悲,那种忧伤无奈地,按部就班地按照礼节一道一道地表达出来。那哭腔都是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的。这样的葬礼算得上正规的彩排了,有编导、有演员、有道具,还有许多观众。在乡下这样的葬礼很隆重,也表现出子孙的“孝心”,但更像是给离去的亲人开一场盛大的“欢送会”。
在乡下葬礼中最讲究的就是“房子”之材。人活着的时候安生立命,造屋建瓴,死了也要让灵魂有所依托,“房子”是很讲究的,一般都是上好的松木。古时的富贵人家必是棺椁齐备,稍次者也要是“金匣套材”,一般人家是“子底子盖”。当然也有贫穷的人家用草席安葬,那种不仅仅是痛失亲人的哀伤,还有不尽言谈的苦楚在当中。到了如今,说不上有多奢侈,但棺木在知天命之年以前必定要给老人准备停当,好让老人安心,也要表出子孙的孝心,几乎都是“金匣套材”。
我的已去逝的亲友就在生前谈论死后安葬的棺木,他们神情坦然,似乎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大事,凝重的表情还是有的。想想人死如灯灭,谁又能带走什么或不带走什么。他们历经了世事的几多沉浮沧桑,对生死不是看透之极,也是处之泰然了一点。“三国志”上说:“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生生死死,循环往复,生是有限的,死却是永恒的。这是一种自然之道。老人们看开了,便也坦然。但活着的人更要紧的是要活出质量来。
在参加亲友的葬礼中,我见到了画好的“房子”,龙飞凤舞,绚丽多彩,据说人死后都要足登“莲花”上“天堂”。“房子”一头画好的莲花栩栩如生,风吹荷动,灵魂似乎安然升入天国,对生者也是莫大的安慰。对画“房子”来说,也是有讲究的,怎样画要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品德、德智,也算是对去世者的一种人生总结吧。但人死如灯灭,纵有天大的功过,也是留与后人追怀悼念而已。这样的讲究,以我看来,只是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与鞭策。
葬礼中最感动人的我认为是安葬前夕的“洒灯”这个祭祀活动了。我不懂这个礼节流传下来的真正意义。只是凭着感觉理解它的含义。祭祀活动的主持,一般是请来的信奉道教和佛教的人担当,他们在前面吟唱着,哀乐齐奏,后面跟着穿着白衣头挂白练的亲人与朋友有节奏地三叩九拜,每个人手中都执着用纸糊制的形形色色的祭祀车马、仙鹤、花圈等祭品。庞大的队伍要围绕村子缓慢地转一圈。哀乐声也很缓慢而悠长,夹着亲人悲怆的哭声,飘荡在空旷的乡村四野上空,散漫得很远很远,火化的纸钱明明灭灭……那种悲伤不由得从胸腔里澎湃而发,似乎逝者的灵魂也在上空飘荡,它俯瞰着悲伤的亲人,熟悉的村庄,带着对故土的怀念,对亲人深深地依恋,最后看上一眼,走上一趟,步履缓慢而沉重。生死不由自己选择的无奈,对尘世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从那哀怨而忧伤的唢呐调儿里徐徐流淌出来……
在我参加的葬礼中最热闹、最有味的时候是“开悼”。“开悼”就是官方所说的追悼会。但民间的这种形式或内容更繁杂,表现的更生活一些。除了花圈挽幛必不可少,还要“摆祭”,一般是亡者的直系亲友把自家精心赶制出来的粮食供品和牲畜供品摆放灵前进行的一次宗品大展览。供品五花八门,有面制的动物,面制的水果,面制的人儿,生活中有的这儿都有,井然有序,像是一种生活的场景。这时候,随着司仪的抑扬顿挫的吆喝和吹鼓手们激情奔放的哀乐鼓奏,人们要打恭做揖,亲近的女眷们不管真假,都不得不在灵堂前下跪嚎哭。“开悼”结束了,她们哭声成了另一道风景。哭声不一样,心情也各异。大部分女眷在人们的半拉半劝下起身去厨房忙活了。只有哭得悽悽惶惶,呜咽不成调的是亡者至亲的人。她们的哭声悲痛欲绝,大有同亡者同去的架势,惹得一旁看热闹的老年妇女们一阵阵心酸,忍不住掩面而泣。最有特色的是那种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的哭。我在本家奶奶葬礼中,不会像她们那样哭,只有心酸,默默流泪,旁边的老姑母哭得抑扬顿挫,似哭似唱的历数着老人生前的为人热心,贤惠善良。我听得入迷,这时大嫂俯耳问姑母她看管的用品在哪,姑母一边依旧好像没听见一样哭着,一边用手子里指着西厢房那边,用她那特别的哭腔说:“在…西厢房…的…大立…柜子里…呀……”。我忍不住笑了,大嫂却严肃的瞪我一眼,拉起我就走了。姑母的哭声依旧有腔有调。
在我参加的几次葬礼中我感觉最伤感和悲痛的时候,也是葬礼的高峰时刻,就是七天以后的“出殡”。那是葬礼的悲痛达到了极致。墓穴早已在前一天挖好,出殡前夕入殓,翌晨抬棺出殡,到墓地安葬。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又开始了。人死不能复生,子孙只有在清明,年节上祭奠失去的亲人,表达哀思,这也是人心情偶尔释放的一种方式。真真的伤痛还是埋在心底,轻易不会示人。
本家奶奶送葬的早晨是一个清秋寒露的日子,鱼肚白的天空还有几个星星在闪着眼,弯月如钩,清冷的空气如凝结在一起,远处的山坳黑嘘嘘的蹲在那里,它也许经历了无数次相同的场面,已变得既不悲伤也不痛苦。送葬的队伍静悄悄的行走,生怕惊醒了安睡的灵魂,要在不知不觉,毫无痛苦的情形中让离世的人安然入土。只有第三锨土覆盖在死者身上,唢呐声骤然响起,就有悲痛的人发出抑制不住的痛哭声……
人生已安然走远,离去的只是人的躯体,那种为人的精神要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在后代乃至在宇宙中永存的。活着的人,当然要活出精神来。
民工重喜(小说)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你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工身上,却让我们感到悲哀至极。
青海、柴达木盆地、茫崖镇。
沙尘瀑、骤雨、冰雹、大雪。
这些真实而冷酷的名词。民工重喜做梦也没想到它们会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且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人们永远记不住民工重喜的名字,却会对这些名词刻骨铭心。
下午六点还不到,放线工重喜看到西边飘过来的那片黑云时,惊恐万分,等不得收工的号令撒腿就往回跑,半道上碰到前来收工的队长。这次队长没有喝叱他,只是说:“天要下雨啦,你穿得单薄了一点吧。背心、背心呢?!”一下子,重喜头里嗡的一下,那个装工具的背心夹层里还装着自己的存折呢?怎么能忘了这么重要的东西。重喜毅然往回走,边走边和天边的黑云赛跑,慌乱中让什么东西拌了一下,差点摔倒。一看原来背心就在脚底下,光顾着看云了,差点错过放背心的地方。这不就是天热那会儿喝水吃干粮的地方嘛,重喜自嘲地笑了。甚至有点欣喜苦狂,一把抓起背心学着电视剧中的样子亲吻了一下,突然听到有人喊:沙尘暴来了,快下山呀!喊声在山洼里来回游荡,却看不见人影,重喜猛地想起得赶紧回呀!
沙尘暴说到就到,像一个饥饿的野兽,铺头盖脸地扑向重喜,眼睛睁不开了,满嘴都是泥沙。只得紧了紧身上的背心,重喜迎着风沙跌跌磕磕的往回走。谁知沙尘暴还没过去,一阵密如利剑的倾盆大雨伴着炸耳的雷声来得更加凶猛,瞬间重喜就成了落汤鸡。转眼间,山洼里洪流纵横,似万马奔腾汇入沟底,形成一条发怒的暴龙冲山而出。重喜看得目瞪口呆,紧紧抓着岩石草皮,以防自己让这条暴龙吞没。他护着脸,顺着山道小心拔出陷进泥泞的脚,一步一步向前慢慢走,再也不敢贪快,心想我可不能掉下去,掉下去我的存折就没了。重喜不由得摸了摸怀中的存折,硬邦邦的还在,重喜心里踏实多了。重喜想起媳妇说揣着折子就好像揣着媳妇一样。出来打工时,重喜想把存折放下,可媳妇说你就拿着吧,同村的山娃打工几年了,一分工钱没要着,还要饭回来了,你就以防万一吧!重喜就揣上了,可心里想,有再急的事,我也不会动存折上的一分钱。可媳妇说,你就当把我揣怀里了,重喜就没话说了。重喜有点想媳妇了,于是加快了步子。
这个不长眼的老天爷!重喜心里狠狠骂道,势利得让人心寒,难道人穷了,连老天爷也不帮衬,说变就变脸,雨中又夹着豆子大的冰雹砸了下来,重喜摸摸发麻的脸颊,脸上恣意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重喜有点后悔了,不该不听媳妇的话,听信包工头的花言巧语,说这野外放线工就是来回多跑几步路的事,况且人家又是最大的物探公司,给的工钱又很诱人。自己一合算,干几个月回去,就可以凑够媳妇舅舅要得那两万元了,就可以堂堂正正,热热闹闹把媳妇娶回家了。可这老天爷一变脸,摊上如此倒霉的天气,怕要把自个的命搭上了。这样一想重喜心里一激凌,不能死!媳妇还盼着自己回去呢!回去娶她呢!重喜心里升起一股热切的希望来,精神好像也足了些,咬着牙终于走出了山。到了平地,倒处是泥,一走脚下就打滑,不过重喜还是松了一口气,却感到身体没有气力了,牙齿在打颤,浑身冰凉。重喜这会儿万分想念媳妇烧的热炕,还有媳妇那热热的身子……
五年前,重喜把媳妇从青海领到老家古浪,可自家穷得叮当响,眼睁睁地看着媳妇舅舅心满意足的点着同村富贵家的钞票,媳妇成了富贵的婆姨!重喜灰心丧气的,也像村里的懒汉一样在墙跟晒了三天太阳,暖洋洋的阳光照着重喜,重喜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有太阳照着,有没有媳妇不是很重要了。“啪”的一声,重喜脸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是老爹吧,老爹说:“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五尺汉子,出去挣去!挣个媳妇回来”!那一巴掌就把重喜撵出了家。可这会儿却听到有人在吼叫,是队长的声音:“快起来,不能睡!混蛋!不能睡!爬也要爬回去。”可重喜好像没有当年走出村子的勇气了。重喜睁了睁眼,冰雹不知啥时停了,弥天大雪像疯了的一群白蝴蝶,铺天盖地而来,像要把人埋在这儿。身上单薄的背心像铁盔甲一样发出咔嚓嚓清脆的声音,在这空寂的野外却有地动山摇的感觉。背心还在身上!重喜竟然觉得一点不冷,虽然天气骤然降温了。睡这儿比媳妇烧的热炕还暖和,重喜不想醒来,睡够了,明天还要上工挣钱呢?马上就凑够两万了。有人在推他,重喜眼前模糊一片,几个人影像在演皮影戏,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重喜像要飞起来了,这种感觉真好!重喜感到很满足,马上就够两万元了,凑够两万元,就可以娶媳妇回家了。那个贫穷的家,可重喜还是想回去,回去对富贵说:本来就是我的媳妇!我娶回来了!当年重喜看到媳妇成了别人的,心痛的突突跳,挨了老爹的一巴掌后,一狠心从家里跑了出来,买个绱鞋的机子东奔西走,倒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心里头终究不踏实。三年后,衣着光鲜的他回到老家那个穷沟沟时,媳妇连抱带拽地领着三个女娃子把他堵在了村口,媳妇在重喜面前泪一把,鼻一把地怨他,说重喜把她带到了火坑里,成了生娃的机器。三年没生出个带把的,三个丫头片子让她受够了气。偷着跑了几次,让男人抓回来,揍得半死,如今一听到男人的声音就打颤。先前水灵灵的大姑娘变成了蓬头垢面的邋遢婆姨!重喜看得心里翻江倒海,不是个滋味!年三十晚上不顾一切领着媳妇又偷跑了出来。从此,东躲西藏,背着绱鞋机子尽往山洼洼,穷沟沟里走。媳妇怨他不能给她一个安稳日子过,没办法,家里回不了,只好回到媳妇娘家,可媳妇娘家只有一个把媳妇拉扯大的舅舅。好在舅舅现在生活好了,也没说啥,还让媳妇帮忙料理自己的杂货店,挣几个生活费。舅舅又对重喜说,你拿来2万元钱,舅舅周旋着把离婚证办来了,你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家了,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平时绱鞋日子还能过去,攒下的钱离2万元还差8000元呢!可凭空里拿出8000多块钱,重喜愁得心焦。那天,找人的工头一说,重喜二话没说就要跟着去。媳妇不让走,从没和媳妇红过脸的重喜甚至还喝了点酒和媳妇闹了别扭。干了一个月,钱倒是差不多了。重喜想,挨过了这倒霉的天气,再干几天就回,真有点想媳妇了,这太阳可真暖和啊,像村头晒过的太阳一样叫人无忧无虑,民工重喜心满意足地睡着了,睡得踏踏实实,嘴角溢着幸福的微笑,手里捏着一个农村信用社鲜红的折子。
皑皑白雪下的格尔木肃然寂静,二十二医院太平间15个牌子上写着遇难的15人的姓名。重喜的哥哥木然地看着弟弟的遗物,他不相信弟弟已不在了,也许他把行李、包裹遗忘在这儿了。这个从小就不着家的弟弟啊!
格尔木殡仪馆,烧纸痛哭,火焰冲天。15个亡魂乘风而去,留下一堆尘埃!
5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播出专题片《冰魂》,主持人阿丘哽咽难言。背景中事发地点大乌斯工区崎岖地貌,让冰雪覆盖着,寂静地像是月球表面,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阳光依旧照下来,安详而热烈。
后记:青海遇难的民工15人,我们山丹去了2人,其中1人是从古浪打工到山丹,转辗又到青海花土沟打工的民工。事出后,死者的哥哥领到了全部的抚恤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的他看到弟弟的尸骨时没有流下几滴眼泪,可看到那么多钱时却放声大哭!是悲哀,还是狂喜?让人不明就理,那个并没有和重喜成家的媳妇也哭哭啼啼的来了,看到亡人的骨灰,她说你个害人的呀,我又要到哪里去找安身的地方!擦干眼泪,她小心地试着问重喜的哥哥,说起了存折的事,说是她和死者共同的积蓄。可是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存折。她抱着骨灰哭得要死要活!好在调解人看在亡人的份上,也给了她一定的补偿。她才止了泪,便回了娘家。不知她是否有个舅舅。
贫穷真是个可恶的字眼,它使人们格外重视钱的存在。可随之而来的冷漠和无情让道德和良心显得更加苍白无力,终究拭不去人们心灵上让金钱蒙上的那一层灰尘,只能靠法律来解决。贫穷这把锁是生锈了,开锁的钥匙在哪儿呢?
(以上作品原载《张掖日报》、《焉支山》)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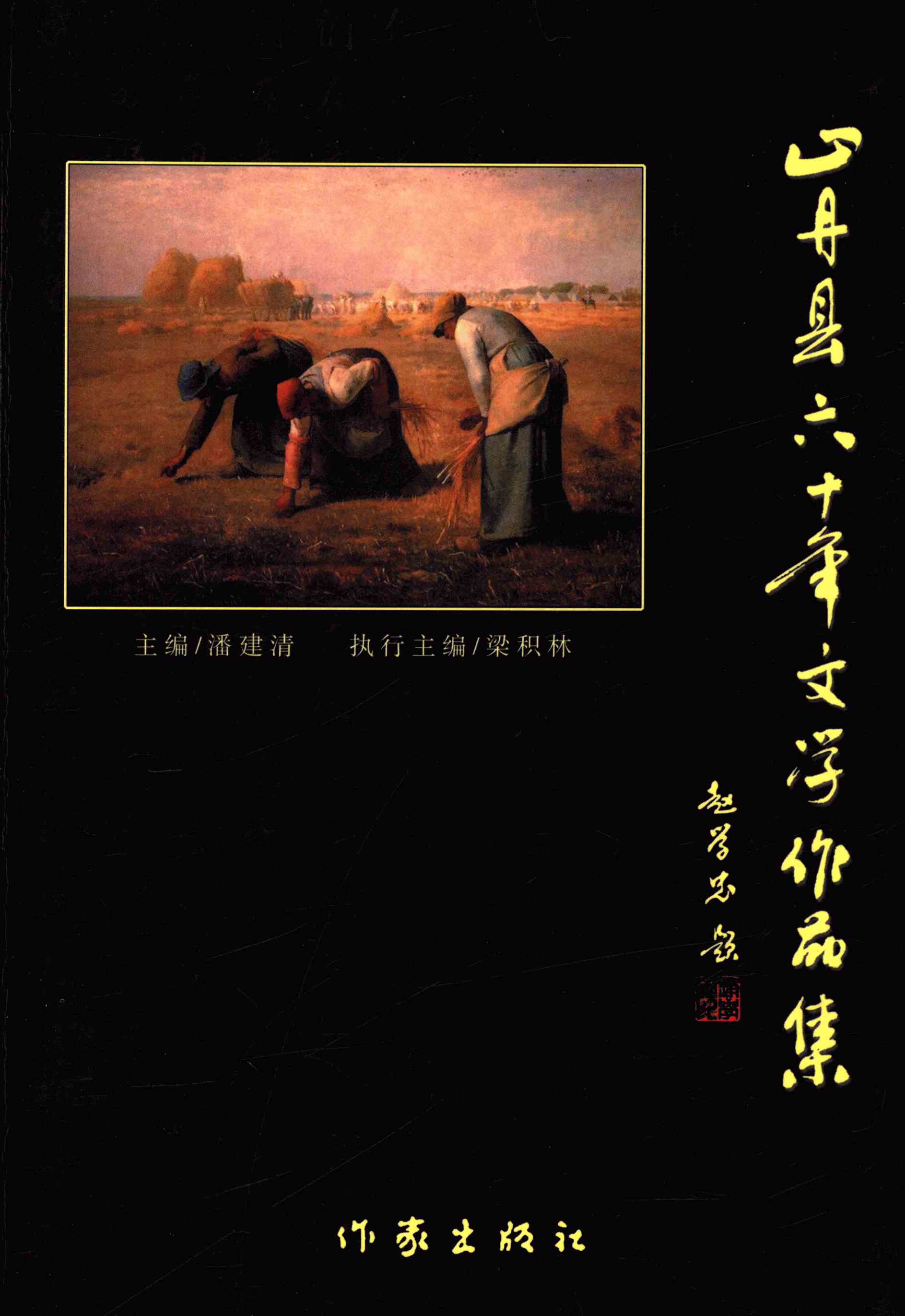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杨桂平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