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淞作品
| 内容出处: | 《山丹县六十年文学作品集》 图书 |
| 唯一号: | 292420020220001811 |
| 颗粒名称: | 张淞作品 |
| 分类号: | I247 |
| 页数: | 9 |
| 页码: | 78-86 |
| 摘要: | 本文记述山丹县张淞所作的小说《流泪无悔》内容介绍。 |
| 关键词: | 山丹县 张淞 小说 |
内容
作者简介:张淞,原名张松,1962年9月3日生,甘肃省山丹县人。发表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诗歌、散文、评论及杂文百余篇(首),著有文学作品集《焉支深处》、传记《张氏家谱》。偶尔获奖。现为《中国作家》签约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易经学会会员。
流泪无悔(小说)
一
聊天是我的嗜好,我特喜欢聊天。
阿克赛石棉矿地处祁连山脉的阿尔金山,海拔4300多米,山高阴雨多,当然聊天的机会更多。每逢下雨天我和兄弟们挤在白房子里东拉西扯鸡毛蒜皮地聊。聊啥呢?聊很早以前,有小孩在路旁玩,看见一个大胡子老头走过来,一孩子叫道,大胡子迎风走,光见胡子不见口。老头一听黑下脸来把胡子一捋吼道,瞎狗,这不是口是你妈的B!那小孩子吓坏了,跑回家把这事诉说了母亲。孩子的母亲听了大笑,直叫肚子疼,孩子问母亲笑啥,母亲说,老头在骂自己呢!正聊高兴时,有人敲门。
“我找张书记。”李若男推门进屋来,扑闪着那好看的杏眼。
“你找张书记?——我说若男啊!你可找对了。你是看手相?还是算命?”坐在床上的李得德虚喋喋不休地搭上了话。
“随便。听人说张书记算卦算得准,我想试试。”
你是什么东西,是试金石?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这么“随便”?“试试”?可笑!我心里质问着,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怎么?不情愿?就凭张书记这态度,看来也是图有虚名了!”
她这么说着,挑战似的看着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哼!算卦?你算什么东西!可是,话说回来,我如果不算这卦,在兄弟们面前有失脸面。再说兄弟们都一个个用真诚的目光期待着。
“老张,给李妹子算一卦!”李德虚用命令似的口吻说,其实他的岁数比我大。
我傲慢地坐定,斜了李若男一眼,问,“李小姐,你算啥?”话刚出口,自己就觉的有点阴阳怪气。对,阴阳先生就该阴阳怪气,这样才具备阴阳家的气质嘛!不是吗?八卦的鼻祖——伏羲氏怎么穿着一件怪里怪气的阴阳袍呢!
“你是张半仙,不知道我来算啥?”杏眼圆睁,看来李若男真要较劲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为什么叫李若男,看来她的父亲很懂文化,很能研究人,是位人学家,就其好胜好强的性格才给她取了这个名字。他却不知道会给她带来一生的犟劲,这犟劲将对她的婚姻、家庭乃至事业带来不幸,她的一生也将在不幸中度过。
我说,“你写个字吧!”
“写啥字?”
“随便!”
李若男笑了笑,眼珠儿咕辘辘一转,掏出钢笔在一页纸上正正楷楷地写出一个字递在了我的面前,那遒劲有力的“生”字跳入眼帘了。噢!一个独体字。我不由自主地瞟了李若男一眼,她那盛气凌人的样子叫人心虚。
我在“生”字左边加上了“忄”旁,于是“生”变成了“性”。猛然茅塞顿开,激动得差点儿手足舞蹈起来,连说话的声音都打颤了。李若男,你听好了!君子问凶不问吉,我可直说了。李若男偏着头点了点,那自鸣自得的得意劲儿简直旁若无人。
“你是问夫妻关系。我直言告诉你,你夫妻关系不好!”
“为啥?”
“你不是写了一个‘生’字吗?你看,‘性’字少了个‘忄’旁,没心了。你知道吗?性是什么?性是爱之神也!没‘心’的爱怎么会好呢?我断定你夫妻关系不好!”
此时的李若男哟,那咄咄逼人的架势不见了,像一个泄气的皮球,杏眼内遮了一层灰灰的光,低下头脚尖儿来回在地面上划着,一会儿地面上划出了一个深深的“一”字。
李得虚凑上去哑着嗓子说,“李妹子放心,如果你离婚了,我就和你好!”
李若男抬起头,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开门走了。从门外吹进一丝凉风。
二
李得虚何许人也?亲爱的读者,此人在本文中虽不是我写的主人翁,但此人不得不提,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了对比好坏的作用。他的骨子里流着母体遗传下来的气血,他的思想、他的意识、他的生活态度,他的工作作风每时每刻都继承了他母亲的懒惰和好事之本能。因此对他不必讳忌。他的出现全当本文的亲属传话行走。因此就得说说他的生世。
他的母亲叫齐桃花。解放前夕,十三岁便出脱得如花似玉了。齐桃花成天喜欢打扮,卖弄风骚,自卖于山丹县城东马家花园做了暗娼。可恨好景不长,一年后,山丹城解放了,齐桃花鼻一把泪一把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政府念她年幼,保释于家中。三年后,齐桃花赶上了大跃进的好时光,随大跃进的革命队伍上了山丹县城东的独峰山顶大炼钢铁了。在革命队伍中,她凭自己的残月风姿略施小计,混进了集体食堂,堂而皇之的成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阵营里的炊事员。孑身一人,偷情骂俏,好不快乐。直到六零年齐桃花才下嫁于李家礳台的大户李家为媳妇。时隔半年,齐桃花生了一男孩。当时,民风正派,李家礳台出了一首歌谣:“怪哉、怪哉!李家礳台出了个怪胎。”李得虚的父亲听不惯这歌谣,看不惯父老乡亲的轻视,又恰逢庚子年,他为了记住这顶绿帽子的耻辱,给男孩取名叫“子虚”娃,待子虚娃懂事上学读书时,他心里还记恨着这奇耻大辱,根据李氏家族排行给取了大名叫李得虚。因为他正好占“得”字辈,同时他父亲也了却了这个不是儿子的儿子的心愿。
李得虚自懂事以来,完全继承了母亲齐桃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好吃懒做耍无赖。上学时不好好学习,调叫男同学问女老师“不调戏妇女”是啥意思?气得女老师有口难言。成人后,参加农业社劳动,要求生产队长调他去妇女组干活,说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否则疯狗一条,扬言队长跟某某女人睡过觉。你想在当时的社会里这般话队长能担得起?至于有无此事,这句话当时可是一个重型的定时炸弹,要上纲上线的。不是吗,有一次他强迫嫖本队一女人被巡夜的基干民兵当场抓获。在批斗会上他是这样交待的:“我不是人,我该死!队长倒好,你日我的得谋嫂,你就日到心上了,肉上了;我日人家的婆娘就日到纲上了,线上了。”看看,这样的人真是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就其这样的无赖改革开放的春风都没有吹动他。庄稼误了,土地荒了,一荒竟荒了十几年。父亲气死了,齐桃花活着,她指望着这宝贝公子哥成家立业呢。可是李得虚每天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从东庄窜到西庄,今日搓麻将明天喝烧酒,哪还管什么母亲的养老送终,自己成家立业、娶妻养子呢!陈老板是他的亲戚,看不惯他的行为,强制他上了石棉矿。趁好,他的恶习在石棉矿找到了用武之地,不几年便混上了石棉矿的领导头头。
三
阿尔金山红柳沟石棉矿系河西走廊西端酒泉地区阿克塞自治县管辖区内,山的走向为东西行。山崖陡峭,气势雄伟,怪石林立,寸毛不生,山顶终年积雪皑皑。向北望去,便是茫茫黄沙戈壁,号称“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所地。红柳沟石棉矿自春至冬终日特大灰色尘暴遮天蔽日,再加上高海拔缺氧,环境十分恶劣,给石棉矿民工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民工们都发出同样的感慨,“钱是命,命是屌。可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照样又上了石棉矿。
二千零四年的春天,我照样上了石棉矿。
经过一冬一春的清覆盖准备工作,原料挖出来了,白皑皑的山坡上矗立起了吸棉机。今天是开机的日子,是民工们庆喜的日子。石棉很快通过吸棉机筛出来装进了包装袋。包装的石棉码成了方方正正楼房般的垛子,等待着装车拉往石棉交易市场。
我的生产矿长竟是李得虚。我从来没见他头上戴过安全帽,只是一条脏兮兮的头巾斜三横四地系在头上,混进女人群里分不清是男是女。他个头又高又瘦,于是,获了“长人”之雅号。当然,也就有人冲他开玩笑,“老李,你站着这么高,爬下有多长?”他只冲那人翻两下白眼,做出一个很生气的样子以示警告。
一天,我的顶头上司李得虚对我说要调换我的喂料工作。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讳忌的说为了李若男,让我去背石棉袋。他还说,我是男人,应该比女同志多干点活,多照顾女同志,我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是他领导我。
第二天上班,“长人”真的当着全矿人的面宣布了他的决定。
李若男站在筛子嘴前一针一针封着石棉袋口,一面骂“长人”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一面看着我吭哧吭哧背石棉袋。背石棉袋子确实是个苦力活,尤其对我这个村干部而言,确实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妈的,李得虚什么狗官!可不是吗?在这权欲横行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竟也懂得这个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理儿。当然,李得虚这个狗官,这个势力小人,趁着手里有权便使唤使唤我这个使唤过人的劳动力。
李若男干活很麻利,一边封口一边抽空帮我背石绵袋子,我暗暗地看着她那匀称端庄的身材,扛着百十斤石棉袋子,迈着健壮的步子来回穿梭在筛子与垛子之间。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丝酸酸的滋味。李若男背完石棉袋,摘下防尘口罩喘气儿,满脸汗津津的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气味。她时不时用眼睛瞟着我,瞟我的那一眼似乎给我猛的一击。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她几眼,她好漂亮,脸盘圆圆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两腿直直的,那胸脯的地方,高高地矗成两座小山,迷人挑逗,每一处都体现了一个少妇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猛然间似乎我和她的距离拉短了许多。于是,她的身材便成了我赏识女人特殊的规格。因此,我用这种眼光把石棉矿所有的女人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了。
李若男干活很麻利,除自己的工作外时常帮助别人干活。在她的眼里世界上好像没有不喜欢她的人,似乎她也喜欢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每个人见了她都很尊重她。她也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个活泼开朗的女性。
一天,座机突然停电,筛子像喘气的老牛停止了呼吸。李若男手提两个麻袋来到棉垛子旁坐下来,她朝我招招手又指了指身边的麻袋示意我坐下来休息。我就坐在了她的身旁。她对我说;“你算得卦真灵。”我问“真灵吗?”她说:“真灵。”
下面是她的自述。
张书记,我可算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我的父亲是全县八九十年代多次表彰过的能人,农民企业家。父亲经营着一辆汽车和一家煤矿,因九五年不慎,煤矿塌方一次性死伤七人,经济赔偿和血的教训使父亲的精神崩溃了,幸福的家庭也随之塌方了,母亲因此事染上了疾病。父亲为了不让我受罪,把我嫁给了高寨堡村书记的儿子,身为人妻了。
我的老公公自文革当书记至今三十多年了,人十分狡猾,但对生活很严慎。他家的庄前屋后栽满了白杨树,每年春天,老公公将树枝儿砍下来,细心地扎成碗口粗的小把晒在后院里,码在屋沿上备一年来烧水做饭的柴禾用。每顿饭只限我烧三把,多烧一把都不行,如果多烧一把就会骂我扫尾巴。更可恨的是我的老婆婆,她习惯于夫高妻高,在村子里耀武扬威,仗男人是书记的面子,从来不把我当儿媳妇看待。更可恨的是每当我例假来时,张书记,她不让我买卫生纸用,她为我热情地用破麻袋片、尼龙袋子缝块垫子用。我说,这东西不能用,会得病的。她哟哟着嚷,女人天生的贱货!她说她用了一辈子怎么没有得上过啥病,男女不是养了好几个。你问我的丈夫,他天生的软骨头,凡事对与错都站在他母亲的一面,没有主见,从来不知道疼我爱我。说句你见笑的话,就连过“夫妻生活”他都是自顾自,从来都不管我的精神和心情,完事倒头睡。你说,张书记,这样的家庭叫我怎么个过法?我在这个家又怎么能活出个人来?无奈,我只好回了娘家。我出门三年了,他们大小人没有上过我娘家的门,从来没管过我的死活,还把我儿子藏起来不让我见面。你说,他们是人吗?他们有人性吗?你问我为啥不离婚,我不离,我舍不得我的儿子。我挣三年钱,在县城里开个小卖部,供儿子上学。张书记,你说我的想法对不对?
以后的日月里,我和李若男无话不说、无题不谈。我们一起谈生活、谈工作、谈家庭、谈孩子,谈矿山上发生的鸡毛蒜皮之事。
有一次,突然她的情绪一落千丈,杏眼失去了平日的光彩。眼光灰灰的,伤感而凄凉地说,太累了,她历尽了世态的炎凉,饱尝了人情的冷淡,经历了人间的生死别离,对人生,对生活已失去了信心,如果不是父母、不是那小冤家早一死了之了。
李若男啊李若男,我一气之下对她训斥到:原来你也这么虚伪,平时你的倔劲哪里去了?我还说你是生活的强者,原来你也这么软弱,是个懦夫,是个混蛋王八蛋!你说,你经历了生死别离,你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死别离?你失去过父亲吗?没有!你失去过儿女吗?也没有。受了一点点委屈,就觉得了不起!不说了,你去死啊!你和祥林嫂的毛毛有什么区别,狼来啦,狼来啦!总有一天你会被狼吃了!滚!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事后好几天,她一直躲着我不和我说话,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似乎瘦了许多。有时我自问,我凭什么要生气,又凭什么训人家呢!
感谢生活。
几天后,她暗暗塞给我一页叠成四方四正的纸条。当时我的心“突突突”跳个不停,我真不知道我的心为什么要跳。我急切地避开人群展开那页纸,纸上写道:
我想告诉你
我很珍惜我俩的缘份
时间流失物换星移
你是我的知己
这仅仅是一首小诗吗?不。她是现代含蓄的内心表白,她的表白比世界上自古至今人类所写的情书都含蓄,同时又比任何情书都热烈而激情,让我措手不及又束手无策。
一月一次轮班作业的时间到了,我俩调上夜班。
时令已春夏交替,但矿山上的温差很大,晚上很冷,我们都穿着棉衣去上班。
夜,很黑很深,满天的星斗被飞扬的石棉粉尘遮挡的迷迷茫茫,摇摇曳曳。吸棉机运转着,灯光孤单单的一个望着一个,似乎它们之间的情感也被粉尘割断了,颤抖着无法接吻。
李若男问我困吗,我说有点。她说困了就唱歌。我问她会唱歌吗,她说她给我唱一首歌。于是她唱起了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
第二天,李若男约我去冰山拔雪莲。
冰山——它不是祁连雪山的主峰,但山势陡峭,一条弯弯扭扭的羊肠小路从山的脚下随风飘至山顶。我和李若男吃力地向山顶爬。汗水浸透了她的脸,透出一抹熟红了的苹果色。引人深思、诱人遐想。山顶上空气稀薄,压力大,我觉得胸闷,气喘伴随着时不时的恶心呕吐。李若男望着我的狼狈样直笑,打趣地说:“张书记,你老了,我扶你下山吧。”“回吗?”我问。“回啥呀,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强的意志终会一事无成!张书记,走,顺着这条山沟下去上那道梁准会能拔上雪莲。”我俩顺山沟朝下走,还没见谷底却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冰潭。冰潭平如毛毡,亮晶晶像面大镜子。冰潭上各种冰花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惬意。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壮丽景观,激动地喊:“若男,看,多美的冰上世界!”
李若男像山雀一般跳在冰潭旁高声叫:“哇——妙!简直妙极了。张书记快看,里面有房子。”
“这冰潭像房子,”
“不,像一张象牙床!”
“像床?”
“是啊,像床。看,床上还有俩个人呢!”
“你疯了!扯哪里了。”
“张书记,你看嘛!”她拉起我的手要我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冰潭上照出了我俩的人影,人影儿靠的那么近。我有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抬眼瞪她,李若男的脸一下子变得潮红了,羞搭搭地捂上了嘴背过身去。
四
以后的日月里,我和她一起劳动的时间逐渐少了。终于有一天,“长人”对我说,老板念你是村里的干部,为了照顾你,调你去棉台做守夜、发放石棉的事,吃住都在山上。当日,民工用石棉袋子给我码了个小窝棚,搬来行李灶具。我便住了进去。
那一夜,我破例失眠了,躺在床上看着刺眼的灯光发呆,惶惶惚惚中想起了她。这样,我跟她一起劳动了几个月的情景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自问为什么会想她呢?为什么一天不见她就寂寞难耐呢?这分明是我对她产生了那种特殊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到底叫“啥情”呢?我所看过的电影电视中,我所读过的小说中,这种情看到过、也读到过,可这种情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这种情错在哪里?结论都落在女人身上,都说她们坏,在勾引男人。这样的女人究竟算是可爱呢,还是可坏呢!我一一在脑海里检点着,同时与自己的妻子作了比较。
是啊!这些日子风言风语传说,我和李若男好上了。那个“好”字让我心惊肉跳。特别是看到有些人挤眉弄眼的样子真叫人难挨。
就这样糊糊涂涂想了一夜。
李得虚这些日子咋了?怎么跟我过不去,就连陈老板对我也有了看法,是不是对我和李若男的来往有了意见?
人啊!
五
雨季来临了。
六月的天,说翻脸就翻脸。刚才还骄阳红日,一会儿竟乌云翻滚、雷声夹着暴雨倾盆而来。渐渐地变成了冰糊状,最后飘飘扬扬下起了鸟头般的雪片。这场雪下了七天七夜。
麻袋房里断电了,关上门屋里一片漆黑,孤单之中自己心里也一片乌黑。门外的山风卷着雪花时儿从门缝里吹进来打个转落在屋里,猛个儿使人打冷颤,透心的凉。点一根蜡烛,火苗轻轻地晃动,晃的我心里着实地难受。身下是冷冰冰的床,我隔着一条单薄的床铺摸到了七高八低不平的床板,心里越发寒酸。十几年来我一直跟妻子范文化贴在那棉软的席梦思床上,日久天长享受着人间的恩爱。然而今夜,木床高低不平冰冷潮湿的冷峻却从身子下慢慢升起,我的肉体突然召唤另一个肉体的温暖了。这个肉体不是妻子的,而且真真切切的需要她。觉得有她陪伴我一次既使流放到天涯海角也心甘、值得。特别是今天。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门外的风很大,卷起了满山遍洼的雪,像狂奔的一群野马扬起的尘灰,一会儿落在山尖,一会儿落在了山洼。天地间白茫茫雾腾腾的,整个山谷中不见一个人影。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木门突然被轻轻推开了,一股山风夹着雪片将蜡烛的火苗摇曳不停,风雪中她走了进来。粉红的头巾裹着乌黑的亮发,一页雪白的口罩遮住那圆圆的脸,像一朵春天里盛开的粉团花,那双好看的杏眼扑闪闪看着我,深沉、多情、温顺而善良。猛然间,我从那双漂亮的眼睛里读到了好多珍贵的东西!我的眼睛潮湿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她小鸟般依在我的身旁,将那冻得冰冷的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你病了?在发烧。”我摇摇头,两行泪水流了出来。她轻轻地替我擦着泪水,伤感地说:“别这样,我也想你!来,给你过生日。”
她从随身带的背包里取出两只红蜡烛,一瓶白酒和两个苹果放在我用木板自钉的桌子上。她一一按顺序排放好,点燃蜡烛转过身来,眼睛内射出奇异的光彩,握着我的手,轻轻祝愿: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
门外一阵吵闹,木门被撞开了。李得虚领着五、六个小伙子闯进屋内,骂道:
“好啊!骚货!我对你咋了?我告诉你,我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过我的手心的!李若男,你好好陪老子去喝酒!不去?哼!别怪我不给面子。”他转脸对我说:
“老张,你说呢?”
“李矿,我看……”
“看,看你妈的头!弟兄们,给我开导开导这对狗男女!”
他们不由分辩,一拥而上将我和李若男打到在地上。折断了生日红蜡烛,推翻了桌子,骂骂咧咧拖着李若男走了。
六
自那日,李若男离开了石棉矿。
我被老板叫到矿长室去“谈心”。
一个月后,我收到李若男托嘱给拉运石棉的司机捎来的一封信。张书记:
请原谅我没有跟你告别,我想,这样对你会好些。你是个好人!
你不要问我离开石棉矿的原因,也不要问我去了哪里,在我和你共同劳动了的日子里,你给我带来了欢乐,是我真正懂得了怎样面对人生。我多么希望你在权欲横行、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不要同李得虚一伙同流合污。希望你像从前那样,洁身自好。希望你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做人,去净化社会,陶冶情操!虽然这样活人有点累,却活的堂堂正正!你说是吗?!
请多保重!
李若男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原载文学作品集《焉支深处》)
流泪无悔(小说)
一
聊天是我的嗜好,我特喜欢聊天。
阿克赛石棉矿地处祁连山脉的阿尔金山,海拔4300多米,山高阴雨多,当然聊天的机会更多。每逢下雨天我和兄弟们挤在白房子里东拉西扯鸡毛蒜皮地聊。聊啥呢?聊很早以前,有小孩在路旁玩,看见一个大胡子老头走过来,一孩子叫道,大胡子迎风走,光见胡子不见口。老头一听黑下脸来把胡子一捋吼道,瞎狗,这不是口是你妈的B!那小孩子吓坏了,跑回家把这事诉说了母亲。孩子的母亲听了大笑,直叫肚子疼,孩子问母亲笑啥,母亲说,老头在骂自己呢!正聊高兴时,有人敲门。
“我找张书记。”李若男推门进屋来,扑闪着那好看的杏眼。
“你找张书记?——我说若男啊!你可找对了。你是看手相?还是算命?”坐在床上的李得德虚喋喋不休地搭上了话。
“随便。听人说张书记算卦算得准,我想试试。”
你是什么东西,是试金石?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这么“随便”?“试试”?可笑!我心里质问着,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怎么?不情愿?就凭张书记这态度,看来也是图有虚名了!”
她这么说着,挑战似的看着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哼!算卦?你算什么东西!可是,话说回来,我如果不算这卦,在兄弟们面前有失脸面。再说兄弟们都一个个用真诚的目光期待着。
“老张,给李妹子算一卦!”李德虚用命令似的口吻说,其实他的岁数比我大。
我傲慢地坐定,斜了李若男一眼,问,“李小姐,你算啥?”话刚出口,自己就觉的有点阴阳怪气。对,阴阳先生就该阴阳怪气,这样才具备阴阳家的气质嘛!不是吗?八卦的鼻祖——伏羲氏怎么穿着一件怪里怪气的阴阳袍呢!
“你是张半仙,不知道我来算啥?”杏眼圆睁,看来李若男真要较劲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为什么叫李若男,看来她的父亲很懂文化,很能研究人,是位人学家,就其好胜好强的性格才给她取了这个名字。他却不知道会给她带来一生的犟劲,这犟劲将对她的婚姻、家庭乃至事业带来不幸,她的一生也将在不幸中度过。
我说,“你写个字吧!”
“写啥字?”
“随便!”
李若男笑了笑,眼珠儿咕辘辘一转,掏出钢笔在一页纸上正正楷楷地写出一个字递在了我的面前,那遒劲有力的“生”字跳入眼帘了。噢!一个独体字。我不由自主地瞟了李若男一眼,她那盛气凌人的样子叫人心虚。
我在“生”字左边加上了“忄”旁,于是“生”变成了“性”。猛然茅塞顿开,激动得差点儿手足舞蹈起来,连说话的声音都打颤了。李若男,你听好了!君子问凶不问吉,我可直说了。李若男偏着头点了点,那自鸣自得的得意劲儿简直旁若无人。
“你是问夫妻关系。我直言告诉你,你夫妻关系不好!”
“为啥?”
“你不是写了一个‘生’字吗?你看,‘性’字少了个‘忄’旁,没心了。你知道吗?性是什么?性是爱之神也!没‘心’的爱怎么会好呢?我断定你夫妻关系不好!”
此时的李若男哟,那咄咄逼人的架势不见了,像一个泄气的皮球,杏眼内遮了一层灰灰的光,低下头脚尖儿来回在地面上划着,一会儿地面上划出了一个深深的“一”字。
李得虚凑上去哑着嗓子说,“李妹子放心,如果你离婚了,我就和你好!”
李若男抬起头,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开门走了。从门外吹进一丝凉风。
二
李得虚何许人也?亲爱的读者,此人在本文中虽不是我写的主人翁,但此人不得不提,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了对比好坏的作用。他的骨子里流着母体遗传下来的气血,他的思想、他的意识、他的生活态度,他的工作作风每时每刻都继承了他母亲的懒惰和好事之本能。因此对他不必讳忌。他的出现全当本文的亲属传话行走。因此就得说说他的生世。
他的母亲叫齐桃花。解放前夕,十三岁便出脱得如花似玉了。齐桃花成天喜欢打扮,卖弄风骚,自卖于山丹县城东马家花园做了暗娼。可恨好景不长,一年后,山丹城解放了,齐桃花鼻一把泪一把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政府念她年幼,保释于家中。三年后,齐桃花赶上了大跃进的好时光,随大跃进的革命队伍上了山丹县城东的独峰山顶大炼钢铁了。在革命队伍中,她凭自己的残月风姿略施小计,混进了集体食堂,堂而皇之的成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阵营里的炊事员。孑身一人,偷情骂俏,好不快乐。直到六零年齐桃花才下嫁于李家礳台的大户李家为媳妇。时隔半年,齐桃花生了一男孩。当时,民风正派,李家礳台出了一首歌谣:“怪哉、怪哉!李家礳台出了个怪胎。”李得虚的父亲听不惯这歌谣,看不惯父老乡亲的轻视,又恰逢庚子年,他为了记住这顶绿帽子的耻辱,给男孩取名叫“子虚”娃,待子虚娃懂事上学读书时,他心里还记恨着这奇耻大辱,根据李氏家族排行给取了大名叫李得虚。因为他正好占“得”字辈,同时他父亲也了却了这个不是儿子的儿子的心愿。
李得虚自懂事以来,完全继承了母亲齐桃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好吃懒做耍无赖。上学时不好好学习,调叫男同学问女老师“不调戏妇女”是啥意思?气得女老师有口难言。成人后,参加农业社劳动,要求生产队长调他去妇女组干活,说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否则疯狗一条,扬言队长跟某某女人睡过觉。你想在当时的社会里这般话队长能担得起?至于有无此事,这句话当时可是一个重型的定时炸弹,要上纲上线的。不是吗,有一次他强迫嫖本队一女人被巡夜的基干民兵当场抓获。在批斗会上他是这样交待的:“我不是人,我该死!队长倒好,你日我的得谋嫂,你就日到心上了,肉上了;我日人家的婆娘就日到纲上了,线上了。”看看,这样的人真是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就其这样的无赖改革开放的春风都没有吹动他。庄稼误了,土地荒了,一荒竟荒了十几年。父亲气死了,齐桃花活着,她指望着这宝贝公子哥成家立业呢。可是李得虚每天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从东庄窜到西庄,今日搓麻将明天喝烧酒,哪还管什么母亲的养老送终,自己成家立业、娶妻养子呢!陈老板是他的亲戚,看不惯他的行为,强制他上了石棉矿。趁好,他的恶习在石棉矿找到了用武之地,不几年便混上了石棉矿的领导头头。
三
阿尔金山红柳沟石棉矿系河西走廊西端酒泉地区阿克塞自治县管辖区内,山的走向为东西行。山崖陡峭,气势雄伟,怪石林立,寸毛不生,山顶终年积雪皑皑。向北望去,便是茫茫黄沙戈壁,号称“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所地。红柳沟石棉矿自春至冬终日特大灰色尘暴遮天蔽日,再加上高海拔缺氧,环境十分恶劣,给石棉矿民工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民工们都发出同样的感慨,“钱是命,命是屌。可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照样又上了石棉矿。
二千零四年的春天,我照样上了石棉矿。
经过一冬一春的清覆盖准备工作,原料挖出来了,白皑皑的山坡上矗立起了吸棉机。今天是开机的日子,是民工们庆喜的日子。石棉很快通过吸棉机筛出来装进了包装袋。包装的石棉码成了方方正正楼房般的垛子,等待着装车拉往石棉交易市场。
我的生产矿长竟是李得虚。我从来没见他头上戴过安全帽,只是一条脏兮兮的头巾斜三横四地系在头上,混进女人群里分不清是男是女。他个头又高又瘦,于是,获了“长人”之雅号。当然,也就有人冲他开玩笑,“老李,你站着这么高,爬下有多长?”他只冲那人翻两下白眼,做出一个很生气的样子以示警告。
一天,我的顶头上司李得虚对我说要调换我的喂料工作。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讳忌的说为了李若男,让我去背石棉袋。他还说,我是男人,应该比女同志多干点活,多照顾女同志,我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是他领导我。
第二天上班,“长人”真的当着全矿人的面宣布了他的决定。
李若男站在筛子嘴前一针一针封着石棉袋口,一面骂“长人”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一面看着我吭哧吭哧背石棉袋。背石棉袋子确实是个苦力活,尤其对我这个村干部而言,确实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妈的,李得虚什么狗官!可不是吗?在这权欲横行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竟也懂得这个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理儿。当然,李得虚这个狗官,这个势力小人,趁着手里有权便使唤使唤我这个使唤过人的劳动力。
李若男干活很麻利,一边封口一边抽空帮我背石绵袋子,我暗暗地看着她那匀称端庄的身材,扛着百十斤石棉袋子,迈着健壮的步子来回穿梭在筛子与垛子之间。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丝酸酸的滋味。李若男背完石棉袋,摘下防尘口罩喘气儿,满脸汗津津的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气味。她时不时用眼睛瞟着我,瞟我的那一眼似乎给我猛的一击。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她几眼,她好漂亮,脸盘圆圆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两腿直直的,那胸脯的地方,高高地矗成两座小山,迷人挑逗,每一处都体现了一个少妇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猛然间似乎我和她的距离拉短了许多。于是,她的身材便成了我赏识女人特殊的规格。因此,我用这种眼光把石棉矿所有的女人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了。
李若男干活很麻利,除自己的工作外时常帮助别人干活。在她的眼里世界上好像没有不喜欢她的人,似乎她也喜欢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每个人见了她都很尊重她。她也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个活泼开朗的女性。
一天,座机突然停电,筛子像喘气的老牛停止了呼吸。李若男手提两个麻袋来到棉垛子旁坐下来,她朝我招招手又指了指身边的麻袋示意我坐下来休息。我就坐在了她的身旁。她对我说;“你算得卦真灵。”我问“真灵吗?”她说:“真灵。”
下面是她的自述。
张书记,我可算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我的父亲是全县八九十年代多次表彰过的能人,农民企业家。父亲经营着一辆汽车和一家煤矿,因九五年不慎,煤矿塌方一次性死伤七人,经济赔偿和血的教训使父亲的精神崩溃了,幸福的家庭也随之塌方了,母亲因此事染上了疾病。父亲为了不让我受罪,把我嫁给了高寨堡村书记的儿子,身为人妻了。
我的老公公自文革当书记至今三十多年了,人十分狡猾,但对生活很严慎。他家的庄前屋后栽满了白杨树,每年春天,老公公将树枝儿砍下来,细心地扎成碗口粗的小把晒在后院里,码在屋沿上备一年来烧水做饭的柴禾用。每顿饭只限我烧三把,多烧一把都不行,如果多烧一把就会骂我扫尾巴。更可恨的是我的老婆婆,她习惯于夫高妻高,在村子里耀武扬威,仗男人是书记的面子,从来不把我当儿媳妇看待。更可恨的是每当我例假来时,张书记,她不让我买卫生纸用,她为我热情地用破麻袋片、尼龙袋子缝块垫子用。我说,这东西不能用,会得病的。她哟哟着嚷,女人天生的贱货!她说她用了一辈子怎么没有得上过啥病,男女不是养了好几个。你问我的丈夫,他天生的软骨头,凡事对与错都站在他母亲的一面,没有主见,从来不知道疼我爱我。说句你见笑的话,就连过“夫妻生活”他都是自顾自,从来都不管我的精神和心情,完事倒头睡。你说,张书记,这样的家庭叫我怎么个过法?我在这个家又怎么能活出个人来?无奈,我只好回了娘家。我出门三年了,他们大小人没有上过我娘家的门,从来没管过我的死活,还把我儿子藏起来不让我见面。你说,他们是人吗?他们有人性吗?你问我为啥不离婚,我不离,我舍不得我的儿子。我挣三年钱,在县城里开个小卖部,供儿子上学。张书记,你说我的想法对不对?
以后的日月里,我和李若男无话不说、无题不谈。我们一起谈生活、谈工作、谈家庭、谈孩子,谈矿山上发生的鸡毛蒜皮之事。
有一次,突然她的情绪一落千丈,杏眼失去了平日的光彩。眼光灰灰的,伤感而凄凉地说,太累了,她历尽了世态的炎凉,饱尝了人情的冷淡,经历了人间的生死别离,对人生,对生活已失去了信心,如果不是父母、不是那小冤家早一死了之了。
李若男啊李若男,我一气之下对她训斥到:原来你也这么虚伪,平时你的倔劲哪里去了?我还说你是生活的强者,原来你也这么软弱,是个懦夫,是个混蛋王八蛋!你说,你经历了生死别离,你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死别离?你失去过父亲吗?没有!你失去过儿女吗?也没有。受了一点点委屈,就觉得了不起!不说了,你去死啊!你和祥林嫂的毛毛有什么区别,狼来啦,狼来啦!总有一天你会被狼吃了!滚!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事后好几天,她一直躲着我不和我说话,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似乎瘦了许多。有时我自问,我凭什么要生气,又凭什么训人家呢!
感谢生活。
几天后,她暗暗塞给我一页叠成四方四正的纸条。当时我的心“突突突”跳个不停,我真不知道我的心为什么要跳。我急切地避开人群展开那页纸,纸上写道:
我想告诉你
我很珍惜我俩的缘份
时间流失物换星移
你是我的知己
这仅仅是一首小诗吗?不。她是现代含蓄的内心表白,她的表白比世界上自古至今人类所写的情书都含蓄,同时又比任何情书都热烈而激情,让我措手不及又束手无策。
一月一次轮班作业的时间到了,我俩调上夜班。
时令已春夏交替,但矿山上的温差很大,晚上很冷,我们都穿着棉衣去上班。
夜,很黑很深,满天的星斗被飞扬的石棉粉尘遮挡的迷迷茫茫,摇摇曳曳。吸棉机运转着,灯光孤单单的一个望着一个,似乎它们之间的情感也被粉尘割断了,颤抖着无法接吻。
李若男问我困吗,我说有点。她说困了就唱歌。我问她会唱歌吗,她说她给我唱一首歌。于是她唱起了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
第二天,李若男约我去冰山拔雪莲。
冰山——它不是祁连雪山的主峰,但山势陡峭,一条弯弯扭扭的羊肠小路从山的脚下随风飘至山顶。我和李若男吃力地向山顶爬。汗水浸透了她的脸,透出一抹熟红了的苹果色。引人深思、诱人遐想。山顶上空气稀薄,压力大,我觉得胸闷,气喘伴随着时不时的恶心呕吐。李若男望着我的狼狈样直笑,打趣地说:“张书记,你老了,我扶你下山吧。”“回吗?”我问。“回啥呀,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强的意志终会一事无成!张书记,走,顺着这条山沟下去上那道梁准会能拔上雪莲。”我俩顺山沟朝下走,还没见谷底却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冰潭。冰潭平如毛毡,亮晶晶像面大镜子。冰潭上各种冰花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惬意。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壮丽景观,激动地喊:“若男,看,多美的冰上世界!”
李若男像山雀一般跳在冰潭旁高声叫:“哇——妙!简直妙极了。张书记快看,里面有房子。”
“这冰潭像房子,”
“不,像一张象牙床!”
“像床?”
“是啊,像床。看,床上还有俩个人呢!”
“你疯了!扯哪里了。”
“张书记,你看嘛!”她拉起我的手要我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冰潭上照出了我俩的人影,人影儿靠的那么近。我有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抬眼瞪她,李若男的脸一下子变得潮红了,羞搭搭地捂上了嘴背过身去。
四
以后的日月里,我和她一起劳动的时间逐渐少了。终于有一天,“长人”对我说,老板念你是村里的干部,为了照顾你,调你去棉台做守夜、发放石棉的事,吃住都在山上。当日,民工用石棉袋子给我码了个小窝棚,搬来行李灶具。我便住了进去。
那一夜,我破例失眠了,躺在床上看着刺眼的灯光发呆,惶惶惚惚中想起了她。这样,我跟她一起劳动了几个月的情景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自问为什么会想她呢?为什么一天不见她就寂寞难耐呢?这分明是我对她产生了那种特殊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到底叫“啥情”呢?我所看过的电影电视中,我所读过的小说中,这种情看到过、也读到过,可这种情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这种情错在哪里?结论都落在女人身上,都说她们坏,在勾引男人。这样的女人究竟算是可爱呢,还是可坏呢!我一一在脑海里检点着,同时与自己的妻子作了比较。
是啊!这些日子风言风语传说,我和李若男好上了。那个“好”字让我心惊肉跳。特别是看到有些人挤眉弄眼的样子真叫人难挨。
就这样糊糊涂涂想了一夜。
李得虚这些日子咋了?怎么跟我过不去,就连陈老板对我也有了看法,是不是对我和李若男的来往有了意见?
人啊!
五
雨季来临了。
六月的天,说翻脸就翻脸。刚才还骄阳红日,一会儿竟乌云翻滚、雷声夹着暴雨倾盆而来。渐渐地变成了冰糊状,最后飘飘扬扬下起了鸟头般的雪片。这场雪下了七天七夜。
麻袋房里断电了,关上门屋里一片漆黑,孤单之中自己心里也一片乌黑。门外的山风卷着雪花时儿从门缝里吹进来打个转落在屋里,猛个儿使人打冷颤,透心的凉。点一根蜡烛,火苗轻轻地晃动,晃的我心里着实地难受。身下是冷冰冰的床,我隔着一条单薄的床铺摸到了七高八低不平的床板,心里越发寒酸。十几年来我一直跟妻子范文化贴在那棉软的席梦思床上,日久天长享受着人间的恩爱。然而今夜,木床高低不平冰冷潮湿的冷峻却从身子下慢慢升起,我的肉体突然召唤另一个肉体的温暖了。这个肉体不是妻子的,而且真真切切的需要她。觉得有她陪伴我一次既使流放到天涯海角也心甘、值得。特别是今天。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门外的风很大,卷起了满山遍洼的雪,像狂奔的一群野马扬起的尘灰,一会儿落在山尖,一会儿落在了山洼。天地间白茫茫雾腾腾的,整个山谷中不见一个人影。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木门突然被轻轻推开了,一股山风夹着雪片将蜡烛的火苗摇曳不停,风雪中她走了进来。粉红的头巾裹着乌黑的亮发,一页雪白的口罩遮住那圆圆的脸,像一朵春天里盛开的粉团花,那双好看的杏眼扑闪闪看着我,深沉、多情、温顺而善良。猛然间,我从那双漂亮的眼睛里读到了好多珍贵的东西!我的眼睛潮湿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她小鸟般依在我的身旁,将那冻得冰冷的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你病了?在发烧。”我摇摇头,两行泪水流了出来。她轻轻地替我擦着泪水,伤感地说:“别这样,我也想你!来,给你过生日。”
她从随身带的背包里取出两只红蜡烛,一瓶白酒和两个苹果放在我用木板自钉的桌子上。她一一按顺序排放好,点燃蜡烛转过身来,眼睛内射出奇异的光彩,握着我的手,轻轻祝愿: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
门外一阵吵闹,木门被撞开了。李得虚领着五、六个小伙子闯进屋内,骂道:
“好啊!骚货!我对你咋了?我告诉你,我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过我的手心的!李若男,你好好陪老子去喝酒!不去?哼!别怪我不给面子。”他转脸对我说:
“老张,你说呢?”
“李矿,我看……”
“看,看你妈的头!弟兄们,给我开导开导这对狗男女!”
他们不由分辩,一拥而上将我和李若男打到在地上。折断了生日红蜡烛,推翻了桌子,骂骂咧咧拖着李若男走了。
六
自那日,李若男离开了石棉矿。
我被老板叫到矿长室去“谈心”。
一个月后,我收到李若男托嘱给拉运石棉的司机捎来的一封信。张书记:
请原谅我没有跟你告别,我想,这样对你会好些。你是个好人!
你不要问我离开石棉矿的原因,也不要问我去了哪里,在我和你共同劳动了的日子里,你给我带来了欢乐,是我真正懂得了怎样面对人生。我多么希望你在权欲横行、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不要同李得虚一伙同流合污。希望你像从前那样,洁身自好。希望你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做人,去净化社会,陶冶情操!虽然这样活人有点累,却活的堂堂正正!你说是吗?!
请多保重!
李若男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原载文学作品集《焉支深处》)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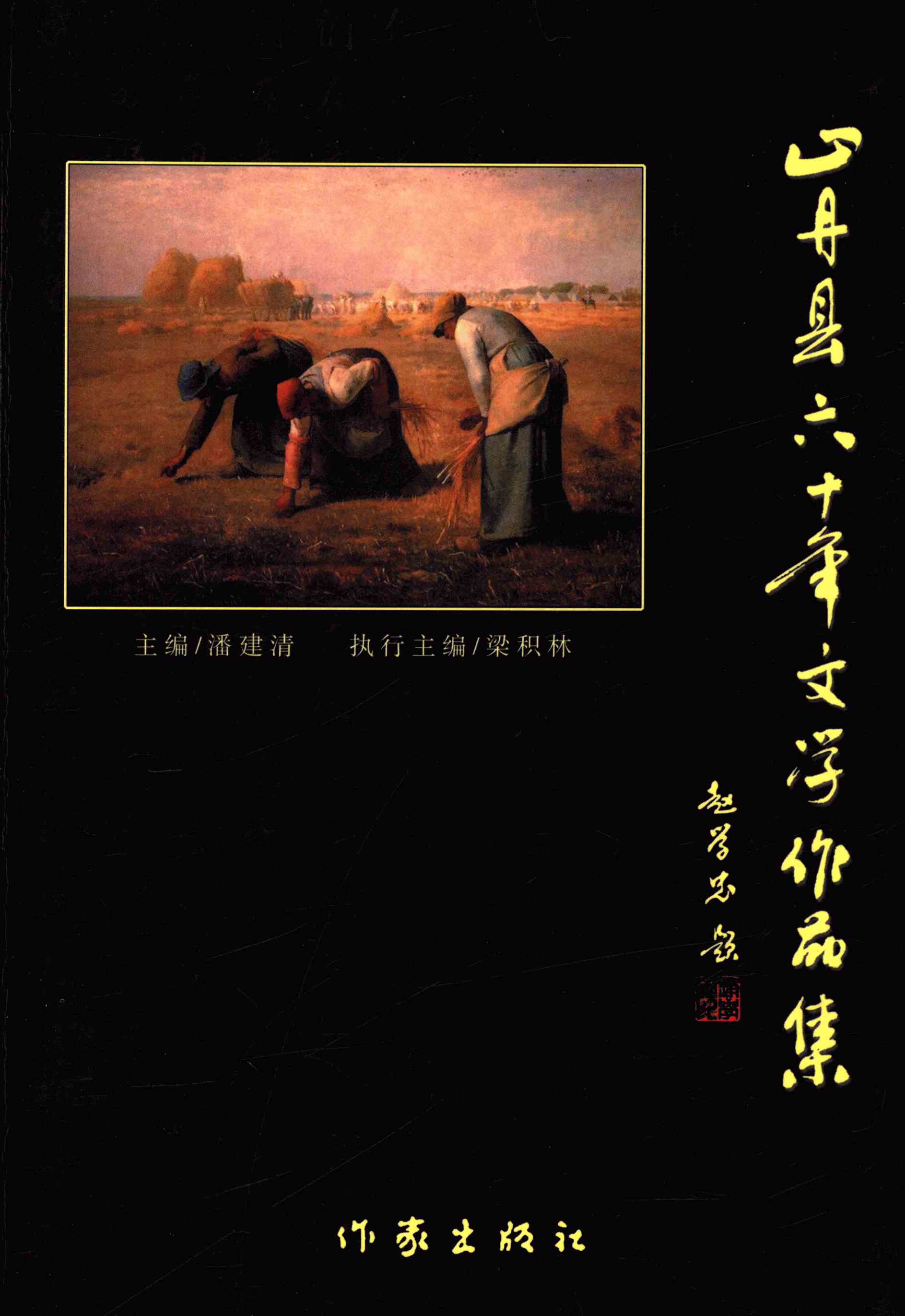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张淞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