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琛世作品
| 内容出处: | 《山丹县六十年文学作品集》 图书 |
| 唯一号: | 292420020220001806 |
| 颗粒名称: | 梁琛世作品 |
| 分类号: | I247.7 |
| 页数: | 9 |
| 页码: | 7-15 |
| 摘要: | 本文记述山丹县梁琛世作品《文俊杰卖粮(小说)》。 |
| 关键词: | 山丹县 小说 梁琛世 |
内容
作者简介:梁琛世(1946—1990),山丹县陈户乡西门村人,自考毕业于西北师大。六二年因公致残,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先后在《飞天》、《陇苗》、《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多篇;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俊杰卖粮(小说)
一九八〇年三月秋天,河西走廊麦泛金浪,千里飘香,家家户户囤破仓流,只愁粮多没处搁,争着抢着卖余粮。
路上,人欢马叫,卖粮的社员迎着朝阳象流水似的朝粮管所涌来。肩挑的,手提的,人拉的,马驮的,有使驴车儿的,也有自行车捎的。嗬嗬!比过会还红火哩。
日头踩上树梢儿了,卖粮的人闹嚷嚷的,一拉溜儿排了半里长,粮管所的两扇铁花栏门却紧紧地锁着。社员们粘满尘土的脸上呈现出既焦燥又无可奈何的神色,谁知道啥时光才开门哪!有那火炮性子的,意唧哩哐啷地踢打着花栏门出气:
“见天都是十点过了才开门,哼!还只开当中这扇小铁门。快响午了,还不见个鬼面!”
“没活头,农民呀,几时都没活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粮是不少,可光跟上卖粮就淘神气得人肋巴骨痛!我那一架子车胡麻,卖了十一天没卖掉!”
一阵手扶拖拉机的吼声碾碎了年轻人的牢骚。机手驱拖拉机左拐右绕,离大道,避人流,把车停刹在墙跟前。有人一见拖拉机就喊:“呀咳!快瞭哪,是文老师来卖粮了!天尊爷,还开着‘铁蚂蚱’哩。遮在他后襟下,我们今个能使车子进粮管所啦!”
人们扭头望去,见文老师离开司机座,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象是有啥揪心的难事。见他过来,人们脸上露出笑眯眯的慰藉,自动闪开一条路,指点着花栏门央告他:“你叫‘仓官’快开门吧,文老师!”
“我……”文老师话到舌尖儿上又咽了回去,站在人伙儿里,有苦难言地说,“我和你们还不是一个样,有甚神通能叫开这大门呢……”
“吁!”一个声嗓甜脆的女人辩驳道,“说天上,道地下,你们是老同学呀!”
“我……我……”文老师结结巴巴地说,“反正……反正……唉!我们这些庄稼人……”
“同是庄稼人,却也有个等级。”小伙子口齿尖利,“再有哪个种田的每月能拿公家十五块工资?……”他是指文老师当社请教师的事。
“反正我是个不值一文的草木之人。”文老师实打实地说。
那小伙子不由分说,拉住文老师胳膊喊道:“往后挪,请文教师叫门!”
人们簇拥着文老师到铁花栏门前。瞅着门扇上悬吊的黑漆锁,文老师揉揉眼睛,退回拖拉机旁。他打车箱里翻出疙瘩垒垂的尿素袋子,抡肩上搭着,复又回到大门口,攀着钢筋从门扇高头翻进去,趿着那双没后跟的条绒锥弯子鞋“呱嗒呱嗒”直奔办公室走去。
登上滑鱼鱼的水磨石台阶儿,听办公室里头“叭!叭!”像炮炸,一个嘎哑的破锣嗓门兴奋地嚷:“奶奶个熊呕,这一回啊,哦哈!你这狼不嚼的死娃子快乖乖投降呗……”文老师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面前的绿油漆门,见小头小脑的褚保管和会计小王围在锃亮的办公桌上下象棋。小王的“老爷”被对方仨卒困死了,急得他小白脸儿茄紫。褚保管却乐得怪声野气地欢叫,摇晃着那杆特长的脖子,敲得棋子儿“叭!叭!”炸炮儿响。
另一边,粮管所主任和几个工作人员在嘻嘻哈哈地玩“牛九”,面前堆着成条的香烟。他们只顾玩牌,对文老师的进来视而不见。
见没人答理自己,文老师不自在得很。站在门槛上,进不好进,出不好出,最终还硬着头皮进了屋。他缩手缩脚地来到主任身旁,递着笑脸儿,买好地说:“主任玩‘牛九’啊!”忙不迭地从尿素袋子里掏出红艳艳的楸子呈献上去。趁他们叼吃楸子的机会,恳求道:“麻烦主任使个人把大门上的锁开了吧!今个卖粮……”
“去找老褚吧,我们几个还有事!”主任说话间已装满两兜儿楸子,叫牌友们:“走呵,把东西都收拾上,到厨房来!”他身先士卒的朝外走,只给文老师抛丢下一串笑声:“……哈哈,我才赢了一条条……”几个衣冠楚楚的人哪!就这么公然把纸烟条子挟胳肢窝里,兴致盎然地尾随主任出了门。
文老师提着减轻了分量的尿素袋子,盯着紧关的那扇绿油漆门,眼里金星乱迸。羞愧、憋气、迷茫,愤懑齐袭上心头。……
两个棋友,先是喊,接着是吵,吵着,吵着骂了起来,骂着骂着动起手来。声嘶力竭的争吵声唤醒了正在发呆的文老师。他既不敢劝,又不敢拉,又烦心,又厌恶。只得手提尿素袋子上前答讪:“没走好了重走嘛,嚷啥!喂,褚主任、王主任、来,吃两个楸子,消消气。”
于是乎,两位骋驰沙场的“战将”重操旧业,再动干戈,边吃边嘟噜。
文老师见褚保管棋术拙劣,时时有败北的危险,只得捺住心火为他充当“军师”。指拨着走了两步,棋局转胜,褚保管又“叭!叭!”敲响了棋子儿,颤儿悠地抖晃着硕笨的躯体,舔嘴咂舌地吃着楸子,问文老师:“今天晴晴的,啥风把你刮来了?”
“我,唉……娃子病得不行了,来卖几个粮……”文老师鼻疙瘩尖儿上渗出了汗星子,陪着十二分小心,试试探探地说,“今个来卖粮的人太多,是不是先把大门上的锁开……”
“嘿嘿!卖粮的人哪天不多?也不知道这一九八〇年三月着了啥魔,一秋天忙得人连个松宽屁都没放过。奶奶个熊!”突然,褚保管的脸黄了,嗓音也走了调儿,“我的妈呀!踩,踩……踩我的‘车’啦!……”
文老师焦燥不安,心里急得火焚焚的;手扶拖拉机是隔壁邻舍裴天颜打公社机站承包来的,人家明天要进城拉油;儿子捍东娃病得连炕下不成,得赶快卖了粮送他去住院;医生说,若是再耽误,就得进专区医院去开刀;门外头,前来卖粮的众多庄稼人眼巴巴地盼他早些去开门。可是……唉!只为今个能顺顺当当卖了粮,还得替“褚长脖子”保“车”救驾……他使出平生本事为老同学效力。在“军师”的指挥中,褚保管连羸三局。
趁他过了棋瘾,在兴头儿上,文老师拍打着褚保管的肩胛骨笑盈盈地说:“褚‘主任’!把大门……”
“大门不能随便儿开呐,就是天王爷来也不能开呐!”褚保管品尝着文老师酬献他的“兰州”烟,以大老板的口气说,“这里是国家机关单位,不是屁窝子大的农家小院,也不是车马店!放他们进来,牲口拉粪尿尿像啥话?谁想卖粮,进小门往晒场上背;嫌费力,拉倒!少收粮,我少麻烦;反正我月月就那六十来块钱,粮收的再多,也没人给我加一块工资。奶奶个熊,我老褚就是这么个吃铁把耧铧子的人;不服了告去,告到哪里,也是干蛋!”
听他话里带话,文老师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毫无知觉地搓着皱裂的双手,哼哼唧唧地说:“我,你……你也知道我是个直杠杠人,办事没个分寸,是咋想的,就咋做,一时之间,就……唉!七六年到现在都五年了,那些陈年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啥。你褚‘主任’宰相肚里能行船,没点容人之量还行!……嘻嘻,我今个开的是手扶拖拉机……”
“你开‘三叉戟’来也是白搭!”小王输了棋,心上记恨着文“军师”,绷着他那并不吓人的小白脸儿,扮出很有权威的派头宣称:“任何车辆不准进来,这是制度……”
“咦呦!”一个娇声嫩气的女人,人没露面声先进了门。她手握扶手,从门缝儿里塞进半张挤扁的桃腮,喊褚保管:“姐夫哎!走唦,哄的人把粮拉来了,你可不见面!”
“噢,是月娥呵!就走!就走!”褚保管朝那女人递去一脸和霭可亲的笑,捋着突凸的喉管解释道,“只顾下棋,把你卖粮的事给忘了。”说着,早已撩开他的直筒裤子擦油皮鞋出了门。
“嘻嘻!饭后一口烟,香似小姨子的嘴……”小王油腔滑调,连说带笑。
文老师见他为小姨子去开大门,紧忙扯起空尿素袋子,抢天摸地地撵出门。
褚保管从裤腰带上抽出串索落叮噹的钥匙,开了铁花栏门他双手挟腰,堵塞在门口,虎视眈耽地瞪着卖粮的庄稼人,明明给小姨子循私情,却偏把人情卖给文老师:“都往后退,给文老师让个路,叫他的手扶先进。喂!事先声明:谁若是鸡屁眼里插筷子——胡捣蛋!今天再别想卖粮。”
趁这工夫,褚保管朝他小姨子挤眉弄眼地说:“快进呵,愣着叫我背你不成?”那女人朝他莞尔一笑,掂起架子车辕条,迈着轻盈的步点儿进粮管所里头去了。
褚保管催文老师把车开里头去,文老师迟怠着想叫大伙儿先进,褚保管不高兴了,黑着脸问:“你进呀不?”说着,作出关门落锁的势头儿。
文老师左右为难。不进吧,自家急的等钱花;进去吧,大伙儿还当是姓文的自顾不暇耍奸滑。想起骨瘦嶙嶙的捍东娃,就甚事儿也顾不得了。唉,火烧眉毛眼前急,卖粮要紧!
待文老师的机子进了粮管所,褚保管哐啷啷关锁实大门,只开那扇尺把大的小铁门容人出入。庄稼人只有唉声叹气的权,掮着沉重的麻袋,汗流浃背地挤进狗洞似的小铁门,往很远很远的晒场上蠕动。
文老师把上千斤粮卸完时,动作麻利的褚保管也已将他小姨子的粮入了库。恭候着他为她开了单据,他才请褚保管检验自己卖的麦子。褚保管说:“捧一把来看看!”文老师捧着麦子还没转回身,褚保管就颠着长脖子下了令:“晒!”
“来前又晒了三天。”文老师亮掌请褚保管查看,见他懒的理睬,就把一粒圆鼓噜的麦子喂嘴里“咯嘣”咬响了,喃喃自语地说,“干干的……”
“干也得晒!”褚保管起身要走,嘲讥道,“刀响就吃面,哪有那么好的事!
说罢,头一甩,踏着吱吱作响的擦油皮鞋回办公室了。
文老师手里摄着金亮的麦子,象木桩似的竖着,仿佛是谁使了“定身法”把他定住了。
晒场上,各类谷物晒得一摊一摊的;金灿灿的麦子,紫红紫红的油籽,驼色的胡麻,珍珠般的豌豆……平展展的晒场就象块缀满五花麻绿布丁的地毯。
鸟儿归窝了,西山嘴上只剩下一抹红云。
夜幕徐徐张开了,褚保管拿花手绢儿抹着油渍渍嘴壳子,“呃!呃”地打着饱隔儿出了门。文老师笑脸儿迎上前:“你吃过饭啦,褚‘主任’!嘿嘿!天黑了,粮不收了你得让我把机子开回去呀。几个碎娃蛋丢家里……请你把大门开……”
“早就给你说过钥匙丢了,钥匙丢了!天这么黑了你还不回去,粮管所的东西丢了谁负责?”接过文老师呈献的纸烟,褚保管鼻孔里喷出两股烟气,一股冷气,“哎!没办法。找个地方住去吧,到明天再说!”
“我那点粮……”
“咦吔,不是早就对你说么!叫你再晒两天,再晒两天!”
文老师忙把仅有的少半盒“兰州”烟递过,褚保管的哑嗓门变了调儿:“真是小气鬼!这么几根能干啥?给盒囫囵的行不行?怕我姓褚的还不起你一盒烂损烟?”烟装进兜里又接着说,“老文啊,卖粮走后门的事可万万干不得!我是国家干部,拿着人民的,吃着人民的,就得对党操心,对人民负责。决不能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就放弃党的政策而乱搞一气。曾记得七六年夏天就因为供应粮的事,你向专区写信告过我的状,你告得好!实话好!咱有错就改。所以,抽烟归抽烟,卖粮归卖粮。啊!”就这样粮没卖成,手扶拖拉机也开不出大门。
银盘似的一轮明月悬挂当空,一圈昏浊的月晕绕缠在他身上,令人厌憎。文老师双手儿抱着膝盖圪蹴在粮管所外头的墙旮旯里,面对月晕,长叹短吁。
坐着,想着,就想起了捍东娃的妈。
那是一九七六年。公社、大队要求家家出工,人人下地,户户上锁,否则以“反对农业学大寨”论处。偏偏这时捍东娃害了病。俗话说,儿是娘的连心肉。儿子一病,当娘的出不了工,当权的说她开小差,磨洋工,是那个“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干女子。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她被“棒棒队”牵着,胸前挂了串臭鞋烂袜子,在人山人海的工地上游斗示众。天爷爷!她哪里见过这阵势啊!往常时节,在几十号人的小会场上,看人家挨斗,她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哩,让她在众目睽睽中……啊!文老师放学回家,见她披头散发的不成个人样儿了。据医生说,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又有医生说是创作性“神经病”。唉!屋里冷灰死灶的,锅锅子闲得只有吊在梁上当锣敲了,供应粮还在粮管所里,买点子粮就如镜里摘花,难呀!堂堂男子汉,没本事弄钱给她医治病,又让她的病身子饿着……买粮!上刀山也得买回那些口粮!哟,七进粮管所,险乎跑断筋。粮,一粒也没买成。那褚长脖子简单是个烫手的山药,扎手的刺猬。早去了,他正在下棋不上班;晚去了,他不是提前下了班胡逛荡,就是推说没单据。唉!眼见得她黄皮寡瘦,娃子们饿得吱哇乱叫,倒把人家隔壁的裴大妈负累的,把她仅有一点点口粮也贴补光了。急得他抓屁股搓腮。有人给他提个醒儿:“你呀,傻里巴唧的!‘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话忘了?人都说:‘想吃供应粮,给仓官送只羊。’你不给仓官嘴上画个‘十字’,能买来粮?三耽搁两耽搁,到月底给你作废了,你一家人吃露水喝风?”嘿,这回才算摸清了门道。拿啥送礼呢?家景穷得捉襟见肘,连买盒火柴的一枚硬币也搜刮不出来。生来不会拐弯抹角儿的文俊杰,以为是老同学,就直戳戳地跟褚长脖子说:“求你把我那丁点儿免费供应粮秤给吧!人嘛,谁没个心……你需要点啥?只要我有的,都给你;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家里没有的,只要你需要,我也想方设法一定帮办!”“真的”?褚长脖子却是个爽快人,张口就提出个码数,“那好呵!你拿百十个鸡蛋来,外捎四只老母鸡。心想不要你的吧,你已经提出来了。人情面子值千金哩,难得你在我面前头一回张口,我咋好意思给你糊上呢?糊上了,你还当姓褚的当了个芝麻大的粮官,连老同学的情面也不领了。要吧,你女人有病,家里生活也困难。我本人倒无所谓,吃个鸡蛋也不上天!主要我们主任的夫人在坐月子,你来秤粮,多儿少的总得向人家表个态呀。当然喽,给你秤粮的时候,把秤杆子适当翘高些……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让你吃亏为原则!行呀不?”不行又该咋呢?求亲告邻……鸡和蛋总算凑合够了;粮,买来了。这事儿搁别人,忍一忍就过了。可文俊杰越想越不是滋味。脑壳子一热,就向专区革命会写了信,褚长脖子坑害人的事,实打实地给说了。又非常诚恳地检查了自己不该放弃原则,同流合污,助长干部犯错误。嘿!一纸八分钱的信竟把灾祸招进家门。上级把信转给粮管所,粮管所把信转给公社,文俊杰落了个“诬告国家干部诋毁红色政权”的罪名。《自我检讨》写了上万言不说,社请老师也当不成了,还罚下十万土块,限十天在公社端完。……
不知月亮是啥时落的。远处,狗在汪汪叫;近处,鸡在喔喔嘀。一阵阵料峭的山风袭来,冷得文老师直嗑牙巴骨,背皮子也发起麻来。他从捍东娃的妈,又想到捍东娃。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捍东娃病了,医生说是急性肾炎,得住院。住院就要钱,好在粮食不少,卖粮。可是又碰到褚长脖子。有什么办法?磨呗。
后晌,文老师不厌其烦地跟着褚保管的屁股转:“褚‘主任’呵!我出门三天了,是借的公社的手扶拖拉机。也不知捍东娃……”
“嗨,你这号人就是难缠!在我跟前讲那么多客观顶啥用?”褚保管朝瓜果摊子那边走着说:“说的叫你晒,叫你晒你死皮赖脸……”
“又晒了三天哪!”文老师撕住褚保管的黑呢子制服不放,“人家裴天颜也是官身子由不得自己,机子……求求你把大门开了,让我把机子先送回去!……”
“给你说的钥匙丢了,钥匙丢了!见天吱吱哇哇的叫,象是小老婆睡在了脚后头!”褚保管抡甩脱身子,指着文老师鼻尖儿乍呼:“我们粮管所又不是你的灶房,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真是人善被人欺呀!褚长脖子见文老师服服帖帖,就突然问道:“那年你告我的状,是长了花儿,还是戴了朵儿?咋没跳进眼窝来把我胀死唦?”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若知道……我也不枉费纸墨地写那份惹祸招灾的信了!”
“嘿嘿!后悔了?”褚保管拍膝打掌,笑得开心。象猫捕住了老鼠,先不忙吃,逗着玩似的。
“怪我不是人,咸(闲)老婆了淡操心,枉生了一双瞎窟窿眼睛!”文老师诅咒着自己,低三下四地朝褚保管求饶说好话,“求你发个善心,看在那病娃子的……”说着说着,竟流下了辛酸混浊的泪。
“嚎啥!”褚保管总算开了大恩(也许是文老师那几滴不值钱的泪值了钱),“你那粮本来是‘孱次品’见你可怜巴巴的,我就昧着良心收了吧。别哭天嚎地的出洋象了,扬扬过筛子去吧”!
文老师趿着没后跟的鞋,蹦儿跳地跑。鞋奔丢了,索性赤脚板去背粮。瞧那乐劲儿,真比过年娶媳妇还高兴。
褚保管翘着二郎腿坐椅子上,叼根纸烟棒子,吞云吐雾,欣赏着掮麻袋过“五关”的庄稼人那各种各样儿的憨态……
文老师头顶毒热的太阳,脚踩火烫的晒场,驮着沉重的麻袋穿梭般跑。头上汗珠撒豆儿般淌,却不知道累。粮,少一半入了库,多一半正在过磅秤。虽然在星光下宿了三天,闯过最后这道工序,粮,算卖定了!哈,卖了粮就领捍东娃去医院……
“姐夫哎!把东西都给你送来了。”那个娇声嫩气的女人一阵风似地来到褚保管跟前,连推带搡,“你快去大门呀,东西丢了我不管!姐姐叫我在广州买的黄花菜、木耳、虾米、鱿鱼、紫菜都给你拿来了。还有过八月十五的牛肉、鸡、面筋、蘑菇……”
“哎呀!都三点一刻了!”褚保管撩起袖口瞄一眼手表,大惊小怪地叫唤起来。转回身,见文老师猫腰躬背,把肩上的粮麻袋卸在磅秤上。他跨前一步抓住他衣裳领子往外推:“走走走!我要回家过八月十五唠!”文老师左扭右扭不情愿,褚保管使足劲儿狠揪,“咯吱”一响,文老师在衣裳扯豁条长口子,钮扣儿滴溜溜四溅飞旋,褚保管抬掌动蹄,冲文老师屁股墩砸一膝盖,见他碰碰磕磕栽出门,就手脚麻利地关紧仓库门,“喀嚓”一响锁上了。
“哎!这……”文老师摸摸勒红的脖子,揉揉跌痛的额头,指点着晒场上并排站立的粮袋,朝已经出了大门的褚保管喊:“我这几麻袋粮……”突然,见身板粗壮的斐天颜进了花栏门,喘着粗气奔晒场跑来:“文……文,文……”
文老师知道他会发脾气的,憋得脸红脖子粗,盯着糊满垢的赤脚板抠指头,只觉裴天颜喷出的热气直往脸上扑。惭愧地说:“公社的手扶机子,我,我……”
“不,不……”裴天颜结结巴巴地,干急说不出口,“捍,捍……娃子,他,他他……”
“啊?!”文老师肝胆俱裂,心象刀戳的痛,眼前金星进旋,张开手臂扑向苍天,揪心撕肺的惨叫一声:“老天爷呀……”
捍东娃死了!粮也终于卖了。
然而,文俊杰并没有垮掉。卖粮的事积淤在心头,郁郁不乐。他翻来覆去地想,褚长脖子的所作所为不像共产党员,我文俊杰不能因为它就对共产党心冷!不行,还是得向上级党委反映,如若让褚长脖子那样的坏蛆横行乡里,咱庄稼人还有活的路吗?你看,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粮食越来越多;往后啊卖粮的时辰多哩!……豁上社请老师当不成也要向党反映!咋?今年是一九八0年,“四害”横行的那个岁月再也不复返了。社会上的弊病,阴暗的人,阴暗的事,党报上披露的一个劲。对唠!干脆给报社写信反映,万一有个闪失,蹲监狱也行!总不能开除我的国籍吧!……
信,寄走了。他盼着,盼着……即将发生的是希望,还是失望?是福音,还是灾难?那只有天知道!他反正豁出去了!
天大的喜讯,“文俊杰”三个字在报上露面了。他的信和成千上万读者见面了!还有段《编者按》哩。报社呼吁有关部门对粮管所营私舞弊、压价勒索的公职人员严肃处理!一见报呵,可把庄稼人喜坏了,大小人儿翘着拇指夸奖:“哟,文老师把我们庄户人的心里话掏给党了。往后呵,卖粮再也不犯愁了!”
嗬,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小吉普开到文老师家门口了。来的是专区和县委的书记,他们握着文老师的手乐呵呵的寒暄,拉家常,话“四化”,那股子亲热劲儿就别提了。临别,他们告诉文老师,专区行署人事处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将粮管所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对那些犯错误的干部职工即将做出组织处理。还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
真的,褚长脖子回家了。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晴天。蓝晶晶的天,亮净得象洗过似的。喜鹊喳喳叫,行人在说笑,通往粮管所的路上,人喊马叫,车轮滚滚。一辆手扶拖拉机在路上奔驰,机手是裴天颜,车箱里是冒尖儿的粮袋……
(原载《陇苗》)
文俊杰卖粮(小说)
一九八〇年三月秋天,河西走廊麦泛金浪,千里飘香,家家户户囤破仓流,只愁粮多没处搁,争着抢着卖余粮。
路上,人欢马叫,卖粮的社员迎着朝阳象流水似的朝粮管所涌来。肩挑的,手提的,人拉的,马驮的,有使驴车儿的,也有自行车捎的。嗬嗬!比过会还红火哩。
日头踩上树梢儿了,卖粮的人闹嚷嚷的,一拉溜儿排了半里长,粮管所的两扇铁花栏门却紧紧地锁着。社员们粘满尘土的脸上呈现出既焦燥又无可奈何的神色,谁知道啥时光才开门哪!有那火炮性子的,意唧哩哐啷地踢打着花栏门出气:
“见天都是十点过了才开门,哼!还只开当中这扇小铁门。快响午了,还不见个鬼面!”
“没活头,农民呀,几时都没活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粮是不少,可光跟上卖粮就淘神气得人肋巴骨痛!我那一架子车胡麻,卖了十一天没卖掉!”
一阵手扶拖拉机的吼声碾碎了年轻人的牢骚。机手驱拖拉机左拐右绕,离大道,避人流,把车停刹在墙跟前。有人一见拖拉机就喊:“呀咳!快瞭哪,是文老师来卖粮了!天尊爷,还开着‘铁蚂蚱’哩。遮在他后襟下,我们今个能使车子进粮管所啦!”
人们扭头望去,见文老师离开司机座,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象是有啥揪心的难事。见他过来,人们脸上露出笑眯眯的慰藉,自动闪开一条路,指点着花栏门央告他:“你叫‘仓官’快开门吧,文老师!”
“我……”文老师话到舌尖儿上又咽了回去,站在人伙儿里,有苦难言地说,“我和你们还不是一个样,有甚神通能叫开这大门呢……”
“吁!”一个声嗓甜脆的女人辩驳道,“说天上,道地下,你们是老同学呀!”
“我……我……”文老师结结巴巴地说,“反正……反正……唉!我们这些庄稼人……”
“同是庄稼人,却也有个等级。”小伙子口齿尖利,“再有哪个种田的每月能拿公家十五块工资?……”他是指文老师当社请教师的事。
“反正我是个不值一文的草木之人。”文老师实打实地说。
那小伙子不由分说,拉住文老师胳膊喊道:“往后挪,请文教师叫门!”
人们簇拥着文老师到铁花栏门前。瞅着门扇上悬吊的黑漆锁,文老师揉揉眼睛,退回拖拉机旁。他打车箱里翻出疙瘩垒垂的尿素袋子,抡肩上搭着,复又回到大门口,攀着钢筋从门扇高头翻进去,趿着那双没后跟的条绒锥弯子鞋“呱嗒呱嗒”直奔办公室走去。
登上滑鱼鱼的水磨石台阶儿,听办公室里头“叭!叭!”像炮炸,一个嘎哑的破锣嗓门兴奋地嚷:“奶奶个熊呕,这一回啊,哦哈!你这狼不嚼的死娃子快乖乖投降呗……”文老师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面前的绿油漆门,见小头小脑的褚保管和会计小王围在锃亮的办公桌上下象棋。小王的“老爷”被对方仨卒困死了,急得他小白脸儿茄紫。褚保管却乐得怪声野气地欢叫,摇晃着那杆特长的脖子,敲得棋子儿“叭!叭!”炸炮儿响。
另一边,粮管所主任和几个工作人员在嘻嘻哈哈地玩“牛九”,面前堆着成条的香烟。他们只顾玩牌,对文老师的进来视而不见。
见没人答理自己,文老师不自在得很。站在门槛上,进不好进,出不好出,最终还硬着头皮进了屋。他缩手缩脚地来到主任身旁,递着笑脸儿,买好地说:“主任玩‘牛九’啊!”忙不迭地从尿素袋子里掏出红艳艳的楸子呈献上去。趁他们叼吃楸子的机会,恳求道:“麻烦主任使个人把大门上的锁开了吧!今个卖粮……”
“去找老褚吧,我们几个还有事!”主任说话间已装满两兜儿楸子,叫牌友们:“走呵,把东西都收拾上,到厨房来!”他身先士卒的朝外走,只给文老师抛丢下一串笑声:“……哈哈,我才赢了一条条……”几个衣冠楚楚的人哪!就这么公然把纸烟条子挟胳肢窝里,兴致盎然地尾随主任出了门。
文老师提着减轻了分量的尿素袋子,盯着紧关的那扇绿油漆门,眼里金星乱迸。羞愧、憋气、迷茫,愤懑齐袭上心头。……
两个棋友,先是喊,接着是吵,吵着,吵着骂了起来,骂着骂着动起手来。声嘶力竭的争吵声唤醒了正在发呆的文老师。他既不敢劝,又不敢拉,又烦心,又厌恶。只得手提尿素袋子上前答讪:“没走好了重走嘛,嚷啥!喂,褚主任、王主任、来,吃两个楸子,消消气。”
于是乎,两位骋驰沙场的“战将”重操旧业,再动干戈,边吃边嘟噜。
文老师见褚保管棋术拙劣,时时有败北的危险,只得捺住心火为他充当“军师”。指拨着走了两步,棋局转胜,褚保管又“叭!叭!”敲响了棋子儿,颤儿悠地抖晃着硕笨的躯体,舔嘴咂舌地吃着楸子,问文老师:“今天晴晴的,啥风把你刮来了?”
“我,唉……娃子病得不行了,来卖几个粮……”文老师鼻疙瘩尖儿上渗出了汗星子,陪着十二分小心,试试探探地说,“今个来卖粮的人太多,是不是先把大门上的锁开……”
“嘿嘿!卖粮的人哪天不多?也不知道这一九八〇年三月着了啥魔,一秋天忙得人连个松宽屁都没放过。奶奶个熊!”突然,褚保管的脸黄了,嗓音也走了调儿,“我的妈呀!踩,踩……踩我的‘车’啦!……”
文老师焦燥不安,心里急得火焚焚的;手扶拖拉机是隔壁邻舍裴天颜打公社机站承包来的,人家明天要进城拉油;儿子捍东娃病得连炕下不成,得赶快卖了粮送他去住院;医生说,若是再耽误,就得进专区医院去开刀;门外头,前来卖粮的众多庄稼人眼巴巴地盼他早些去开门。可是……唉!只为今个能顺顺当当卖了粮,还得替“褚长脖子”保“车”救驾……他使出平生本事为老同学效力。在“军师”的指挥中,褚保管连羸三局。
趁他过了棋瘾,在兴头儿上,文老师拍打着褚保管的肩胛骨笑盈盈地说:“褚‘主任’!把大门……”
“大门不能随便儿开呐,就是天王爷来也不能开呐!”褚保管品尝着文老师酬献他的“兰州”烟,以大老板的口气说,“这里是国家机关单位,不是屁窝子大的农家小院,也不是车马店!放他们进来,牲口拉粪尿尿像啥话?谁想卖粮,进小门往晒场上背;嫌费力,拉倒!少收粮,我少麻烦;反正我月月就那六十来块钱,粮收的再多,也没人给我加一块工资。奶奶个熊,我老褚就是这么个吃铁把耧铧子的人;不服了告去,告到哪里,也是干蛋!”
听他话里带话,文老师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毫无知觉地搓着皱裂的双手,哼哼唧唧地说:“我,你……你也知道我是个直杠杠人,办事没个分寸,是咋想的,就咋做,一时之间,就……唉!七六年到现在都五年了,那些陈年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啥。你褚‘主任’宰相肚里能行船,没点容人之量还行!……嘻嘻,我今个开的是手扶拖拉机……”
“你开‘三叉戟’来也是白搭!”小王输了棋,心上记恨着文“军师”,绷着他那并不吓人的小白脸儿,扮出很有权威的派头宣称:“任何车辆不准进来,这是制度……”
“咦呦!”一个娇声嫩气的女人,人没露面声先进了门。她手握扶手,从门缝儿里塞进半张挤扁的桃腮,喊褚保管:“姐夫哎!走唦,哄的人把粮拉来了,你可不见面!”
“噢,是月娥呵!就走!就走!”褚保管朝那女人递去一脸和霭可亲的笑,捋着突凸的喉管解释道,“只顾下棋,把你卖粮的事给忘了。”说着,早已撩开他的直筒裤子擦油皮鞋出了门。
“嘻嘻!饭后一口烟,香似小姨子的嘴……”小王油腔滑调,连说带笑。
文老师见他为小姨子去开大门,紧忙扯起空尿素袋子,抢天摸地地撵出门。
褚保管从裤腰带上抽出串索落叮噹的钥匙,开了铁花栏门他双手挟腰,堵塞在门口,虎视眈耽地瞪着卖粮的庄稼人,明明给小姨子循私情,却偏把人情卖给文老师:“都往后退,给文老师让个路,叫他的手扶先进。喂!事先声明:谁若是鸡屁眼里插筷子——胡捣蛋!今天再别想卖粮。”
趁这工夫,褚保管朝他小姨子挤眉弄眼地说:“快进呵,愣着叫我背你不成?”那女人朝他莞尔一笑,掂起架子车辕条,迈着轻盈的步点儿进粮管所里头去了。
褚保管催文老师把车开里头去,文老师迟怠着想叫大伙儿先进,褚保管不高兴了,黑着脸问:“你进呀不?”说着,作出关门落锁的势头儿。
文老师左右为难。不进吧,自家急的等钱花;进去吧,大伙儿还当是姓文的自顾不暇耍奸滑。想起骨瘦嶙嶙的捍东娃,就甚事儿也顾不得了。唉,火烧眉毛眼前急,卖粮要紧!
待文老师的机子进了粮管所,褚保管哐啷啷关锁实大门,只开那扇尺把大的小铁门容人出入。庄稼人只有唉声叹气的权,掮着沉重的麻袋,汗流浃背地挤进狗洞似的小铁门,往很远很远的晒场上蠕动。
文老师把上千斤粮卸完时,动作麻利的褚保管也已将他小姨子的粮入了库。恭候着他为她开了单据,他才请褚保管检验自己卖的麦子。褚保管说:“捧一把来看看!”文老师捧着麦子还没转回身,褚保管就颠着长脖子下了令:“晒!”
“来前又晒了三天。”文老师亮掌请褚保管查看,见他懒的理睬,就把一粒圆鼓噜的麦子喂嘴里“咯嘣”咬响了,喃喃自语地说,“干干的……”
“干也得晒!”褚保管起身要走,嘲讥道,“刀响就吃面,哪有那么好的事!
说罢,头一甩,踏着吱吱作响的擦油皮鞋回办公室了。
文老师手里摄着金亮的麦子,象木桩似的竖着,仿佛是谁使了“定身法”把他定住了。
晒场上,各类谷物晒得一摊一摊的;金灿灿的麦子,紫红紫红的油籽,驼色的胡麻,珍珠般的豌豆……平展展的晒场就象块缀满五花麻绿布丁的地毯。
鸟儿归窝了,西山嘴上只剩下一抹红云。
夜幕徐徐张开了,褚保管拿花手绢儿抹着油渍渍嘴壳子,“呃!呃”地打着饱隔儿出了门。文老师笑脸儿迎上前:“你吃过饭啦,褚‘主任’!嘿嘿!天黑了,粮不收了你得让我把机子开回去呀。几个碎娃蛋丢家里……请你把大门开……”
“早就给你说过钥匙丢了,钥匙丢了!天这么黑了你还不回去,粮管所的东西丢了谁负责?”接过文老师呈献的纸烟,褚保管鼻孔里喷出两股烟气,一股冷气,“哎!没办法。找个地方住去吧,到明天再说!”
“我那点粮……”
“咦吔,不是早就对你说么!叫你再晒两天,再晒两天!”
文老师忙把仅有的少半盒“兰州”烟递过,褚保管的哑嗓门变了调儿:“真是小气鬼!这么几根能干啥?给盒囫囵的行不行?怕我姓褚的还不起你一盒烂损烟?”烟装进兜里又接着说,“老文啊,卖粮走后门的事可万万干不得!我是国家干部,拿着人民的,吃着人民的,就得对党操心,对人民负责。决不能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就放弃党的政策而乱搞一气。曾记得七六年夏天就因为供应粮的事,你向专区写信告过我的状,你告得好!实话好!咱有错就改。所以,抽烟归抽烟,卖粮归卖粮。啊!”就这样粮没卖成,手扶拖拉机也开不出大门。
银盘似的一轮明月悬挂当空,一圈昏浊的月晕绕缠在他身上,令人厌憎。文老师双手儿抱着膝盖圪蹴在粮管所外头的墙旮旯里,面对月晕,长叹短吁。
坐着,想着,就想起了捍东娃的妈。
那是一九七六年。公社、大队要求家家出工,人人下地,户户上锁,否则以“反对农业学大寨”论处。偏偏这时捍东娃害了病。俗话说,儿是娘的连心肉。儿子一病,当娘的出不了工,当权的说她开小差,磨洋工,是那个“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干女子。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她被“棒棒队”牵着,胸前挂了串臭鞋烂袜子,在人山人海的工地上游斗示众。天爷爷!她哪里见过这阵势啊!往常时节,在几十号人的小会场上,看人家挨斗,她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哩,让她在众目睽睽中……啊!文老师放学回家,见她披头散发的不成个人样儿了。据医生说,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又有医生说是创作性“神经病”。唉!屋里冷灰死灶的,锅锅子闲得只有吊在梁上当锣敲了,供应粮还在粮管所里,买点子粮就如镜里摘花,难呀!堂堂男子汉,没本事弄钱给她医治病,又让她的病身子饿着……买粮!上刀山也得买回那些口粮!哟,七进粮管所,险乎跑断筋。粮,一粒也没买成。那褚长脖子简单是个烫手的山药,扎手的刺猬。早去了,他正在下棋不上班;晚去了,他不是提前下了班胡逛荡,就是推说没单据。唉!眼见得她黄皮寡瘦,娃子们饿得吱哇乱叫,倒把人家隔壁的裴大妈负累的,把她仅有一点点口粮也贴补光了。急得他抓屁股搓腮。有人给他提个醒儿:“你呀,傻里巴唧的!‘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话忘了?人都说:‘想吃供应粮,给仓官送只羊。’你不给仓官嘴上画个‘十字’,能买来粮?三耽搁两耽搁,到月底给你作废了,你一家人吃露水喝风?”嘿,这回才算摸清了门道。拿啥送礼呢?家景穷得捉襟见肘,连买盒火柴的一枚硬币也搜刮不出来。生来不会拐弯抹角儿的文俊杰,以为是老同学,就直戳戳地跟褚长脖子说:“求你把我那丁点儿免费供应粮秤给吧!人嘛,谁没个心……你需要点啥?只要我有的,都给你;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家里没有的,只要你需要,我也想方设法一定帮办!”“真的”?褚长脖子却是个爽快人,张口就提出个码数,“那好呵!你拿百十个鸡蛋来,外捎四只老母鸡。心想不要你的吧,你已经提出来了。人情面子值千金哩,难得你在我面前头一回张口,我咋好意思给你糊上呢?糊上了,你还当姓褚的当了个芝麻大的粮官,连老同学的情面也不领了。要吧,你女人有病,家里生活也困难。我本人倒无所谓,吃个鸡蛋也不上天!主要我们主任的夫人在坐月子,你来秤粮,多儿少的总得向人家表个态呀。当然喽,给你秤粮的时候,把秤杆子适当翘高些……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让你吃亏为原则!行呀不?”不行又该咋呢?求亲告邻……鸡和蛋总算凑合够了;粮,买来了。这事儿搁别人,忍一忍就过了。可文俊杰越想越不是滋味。脑壳子一热,就向专区革命会写了信,褚长脖子坑害人的事,实打实地给说了。又非常诚恳地检查了自己不该放弃原则,同流合污,助长干部犯错误。嘿!一纸八分钱的信竟把灾祸招进家门。上级把信转给粮管所,粮管所把信转给公社,文俊杰落了个“诬告国家干部诋毁红色政权”的罪名。《自我检讨》写了上万言不说,社请老师也当不成了,还罚下十万土块,限十天在公社端完。……
不知月亮是啥时落的。远处,狗在汪汪叫;近处,鸡在喔喔嘀。一阵阵料峭的山风袭来,冷得文老师直嗑牙巴骨,背皮子也发起麻来。他从捍东娃的妈,又想到捍东娃。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捍东娃病了,医生说是急性肾炎,得住院。住院就要钱,好在粮食不少,卖粮。可是又碰到褚长脖子。有什么办法?磨呗。
后晌,文老师不厌其烦地跟着褚保管的屁股转:“褚‘主任’呵!我出门三天了,是借的公社的手扶拖拉机。也不知捍东娃……”
“嗨,你这号人就是难缠!在我跟前讲那么多客观顶啥用?”褚保管朝瓜果摊子那边走着说:“说的叫你晒,叫你晒你死皮赖脸……”
“又晒了三天哪!”文老师撕住褚保管的黑呢子制服不放,“人家裴天颜也是官身子由不得自己,机子……求求你把大门开了,让我把机子先送回去!……”
“给你说的钥匙丢了,钥匙丢了!见天吱吱哇哇的叫,象是小老婆睡在了脚后头!”褚保管抡甩脱身子,指着文老师鼻尖儿乍呼:“我们粮管所又不是你的灶房,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真是人善被人欺呀!褚长脖子见文老师服服帖帖,就突然问道:“那年你告我的状,是长了花儿,还是戴了朵儿?咋没跳进眼窝来把我胀死唦?”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若知道……我也不枉费纸墨地写那份惹祸招灾的信了!”
“嘿嘿!后悔了?”褚保管拍膝打掌,笑得开心。象猫捕住了老鼠,先不忙吃,逗着玩似的。
“怪我不是人,咸(闲)老婆了淡操心,枉生了一双瞎窟窿眼睛!”文老师诅咒着自己,低三下四地朝褚保管求饶说好话,“求你发个善心,看在那病娃子的……”说着说着,竟流下了辛酸混浊的泪。
“嚎啥!”褚保管总算开了大恩(也许是文老师那几滴不值钱的泪值了钱),“你那粮本来是‘孱次品’见你可怜巴巴的,我就昧着良心收了吧。别哭天嚎地的出洋象了,扬扬过筛子去吧”!
文老师趿着没后跟的鞋,蹦儿跳地跑。鞋奔丢了,索性赤脚板去背粮。瞧那乐劲儿,真比过年娶媳妇还高兴。
褚保管翘着二郎腿坐椅子上,叼根纸烟棒子,吞云吐雾,欣赏着掮麻袋过“五关”的庄稼人那各种各样儿的憨态……
文老师头顶毒热的太阳,脚踩火烫的晒场,驮着沉重的麻袋穿梭般跑。头上汗珠撒豆儿般淌,却不知道累。粮,少一半入了库,多一半正在过磅秤。虽然在星光下宿了三天,闯过最后这道工序,粮,算卖定了!哈,卖了粮就领捍东娃去医院……
“姐夫哎!把东西都给你送来了。”那个娇声嫩气的女人一阵风似地来到褚保管跟前,连推带搡,“你快去大门呀,东西丢了我不管!姐姐叫我在广州买的黄花菜、木耳、虾米、鱿鱼、紫菜都给你拿来了。还有过八月十五的牛肉、鸡、面筋、蘑菇……”
“哎呀!都三点一刻了!”褚保管撩起袖口瞄一眼手表,大惊小怪地叫唤起来。转回身,见文老师猫腰躬背,把肩上的粮麻袋卸在磅秤上。他跨前一步抓住他衣裳领子往外推:“走走走!我要回家过八月十五唠!”文老师左扭右扭不情愿,褚保管使足劲儿狠揪,“咯吱”一响,文老师在衣裳扯豁条长口子,钮扣儿滴溜溜四溅飞旋,褚保管抬掌动蹄,冲文老师屁股墩砸一膝盖,见他碰碰磕磕栽出门,就手脚麻利地关紧仓库门,“喀嚓”一响锁上了。
“哎!这……”文老师摸摸勒红的脖子,揉揉跌痛的额头,指点着晒场上并排站立的粮袋,朝已经出了大门的褚保管喊:“我这几麻袋粮……”突然,见身板粗壮的斐天颜进了花栏门,喘着粗气奔晒场跑来:“文……文,文……”
文老师知道他会发脾气的,憋得脸红脖子粗,盯着糊满垢的赤脚板抠指头,只觉裴天颜喷出的热气直往脸上扑。惭愧地说:“公社的手扶机子,我,我……”
“不,不……”裴天颜结结巴巴地,干急说不出口,“捍,捍……娃子,他,他他……”
“啊?!”文老师肝胆俱裂,心象刀戳的痛,眼前金星进旋,张开手臂扑向苍天,揪心撕肺的惨叫一声:“老天爷呀……”
捍东娃死了!粮也终于卖了。
然而,文俊杰并没有垮掉。卖粮的事积淤在心头,郁郁不乐。他翻来覆去地想,褚长脖子的所作所为不像共产党员,我文俊杰不能因为它就对共产党心冷!不行,还是得向上级党委反映,如若让褚长脖子那样的坏蛆横行乡里,咱庄稼人还有活的路吗?你看,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粮食越来越多;往后啊卖粮的时辰多哩!……豁上社请老师当不成也要向党反映!咋?今年是一九八0年,“四害”横行的那个岁月再也不复返了。社会上的弊病,阴暗的人,阴暗的事,党报上披露的一个劲。对唠!干脆给报社写信反映,万一有个闪失,蹲监狱也行!总不能开除我的国籍吧!……
信,寄走了。他盼着,盼着……即将发生的是希望,还是失望?是福音,还是灾难?那只有天知道!他反正豁出去了!
天大的喜讯,“文俊杰”三个字在报上露面了。他的信和成千上万读者见面了!还有段《编者按》哩。报社呼吁有关部门对粮管所营私舞弊、压价勒索的公职人员严肃处理!一见报呵,可把庄稼人喜坏了,大小人儿翘着拇指夸奖:“哟,文老师把我们庄户人的心里话掏给党了。往后呵,卖粮再也不犯愁了!”
嗬,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小吉普开到文老师家门口了。来的是专区和县委的书记,他们握着文老师的手乐呵呵的寒暄,拉家常,话“四化”,那股子亲热劲儿就别提了。临别,他们告诉文老师,专区行署人事处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将粮管所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对那些犯错误的干部职工即将做出组织处理。还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
真的,褚长脖子回家了。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晴天。蓝晶晶的天,亮净得象洗过似的。喜鹊喳喳叫,行人在说笑,通往粮管所的路上,人喊马叫,车轮滚滚。一辆手扶拖拉机在路上奔驰,机手是裴天颜,车箱里是冒尖儿的粮袋……
(原载《陇苗》)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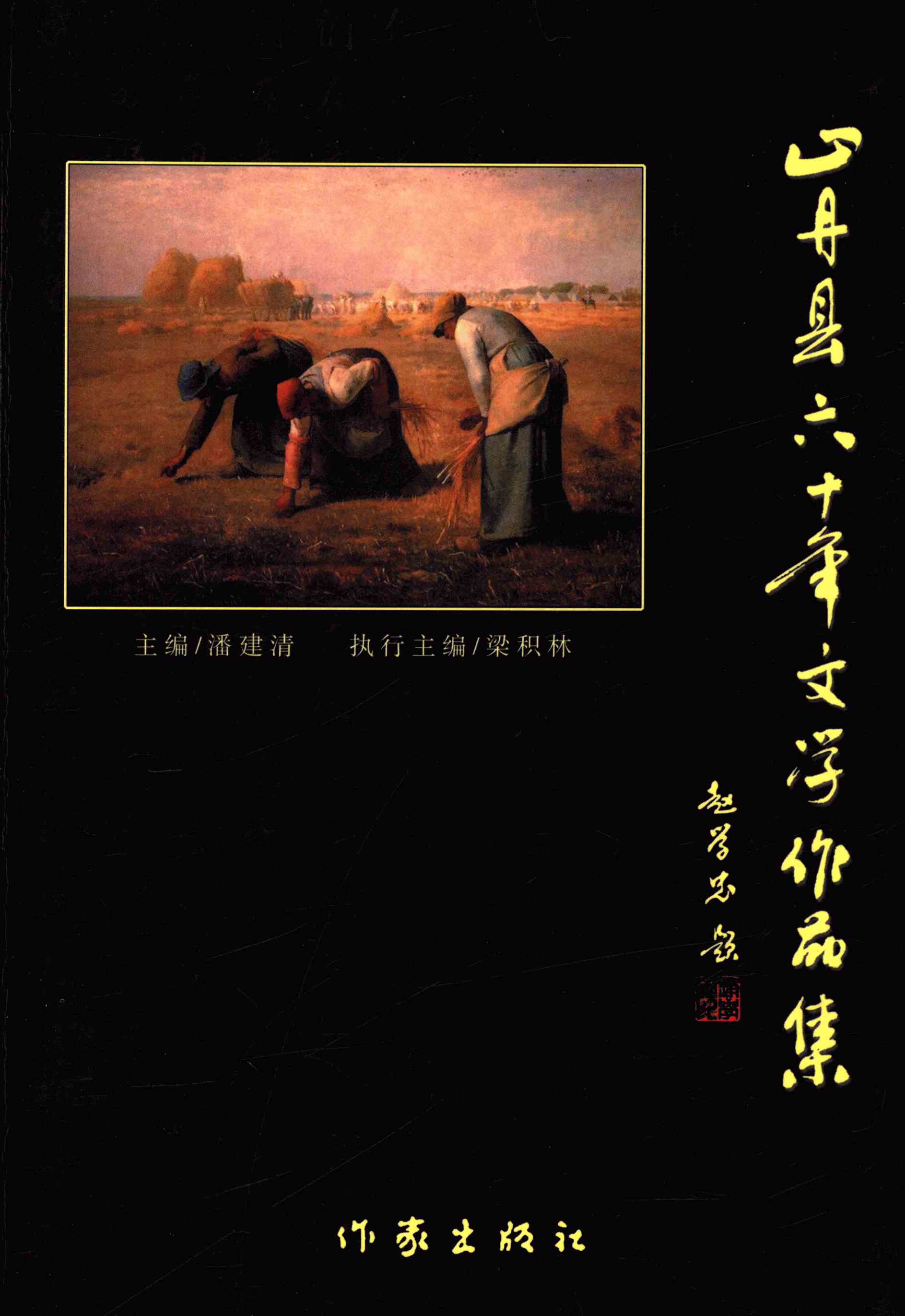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梁琛世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