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滋云作品
| 内容出处: | 《山丹县六十年文学作品集》 图书 |
| 唯一号: | 292420020220001805 |
| 颗粒名称: | 萧滋云作品 |
| 分类号: | I247.7 |
| 页数: | 6 |
| 页码: | 1-6 |
| 摘要: | 本文记述山丹县萧滋云所作的我和沙妮(小说)。 |
| 关键词: | 山丹县 小说 萧滋云 |
内容
作者简介:萧滋云,1942年农历中元节生于甘肃省山丹县焉支山下。当过煤窑工人、民请教师,1979年转干调入县文化系统。自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论文数百篇,其中散文《《恩师深情书信传》》等四篇在省内外获奖。有长篇纪实文学《芦堡之路》(与人合作)、长篇散文《情系焉支山》、论文集《日记写作浅谈》、中篇小说集《五彩梦》(与女儿萧金秀合作)等作品出版。自从1957年开始写日记至今没有中断过,写成1400余万字,即将付梓。现任民刊《《日记》杂志主编。
我和沙妮(小说)
经酒泉,过玉门,西去阳关,越走越荒凉:望不断的马鬃山,仿佛山随车速,变戏法似地无限向前延伸;走不完的沙石滩,大沙丘成波浪式,还一动不动,好像下面鼓着风,随时都有被推移涨起的可能性。
我用胳肘碰了碰紧挨我坐着的沙妮:“看,沙刺。”
沙妮往一边挤了挤我,尽力将上身倾斜于窗前,忽闪了一下重眼皮,深深吸了一口气赞叹:“多美啊!”
真的,小沙丘上长满了沙刺,高高低低,相衬互映。高的沙刺顶端,有的成粉色,像梅花,有的呈浅黄,像芦花,在茫茫戈壁中顽强生长,梳洗打扮,别具一番风格。也许是沙丘生水,沙刺又能固定小沙丘的缘故,他俩才相依为命地生存下来了。
我承受不住沙妮的压力,礼貌地提醒:“对不起。”
沙妮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移移屁股坐稳,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边塞风光出神。
我开玩笑:“你为什么叫沙妮呢?应该叫沙刺。”说完,不知我和什么联想上了,忍不住地“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沙妮却不笑,甜甜地对我说:“我原来的名字真叫沙刺,取沙里生,沙里长,立志于治沙研究事业的含义。可是所里的人嫌太俗气,还开我的玩笑,‘沙刺,沙刺,谁敢和你接近?还是叫沙妮吧,两方面的意思都有了,也好听,像个姑娘的名字。’我一想,说得在理,点头同意,从此我就叫沙妮了。……你听的呀没有?”
我经受不住一路的颠簸,感到有点昏昏欲睡,尤其是上眼皮,沉重得怎么使劲也抬不起来。
沙妮见我疲倦成这样,再没责怪,用下巴指指她的肩膀,柔情地说:“睡一会儿吧!”
一觉醒来,睡眼惺忪,立时辨别不清到哪里了,茫茫大漠,变幻万千:风刮个不停,蒙天迷地,如泣如诉,戈壁不知何故,全变成了白雪上又落了层黄土那么一种颜色。远处起风推尘于半天空,好像下珍珍雪,上下飞卷着。再远处的马鬃、祁连隐去高入云霄的真面目。天似穹庐,把我们笼罩在越来越小的空间,使人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
大轿车也嫌窒息,加速跑了一段路程,风小了,戈壁显出表绿色,一马平川,望不到头。没树,没草,只有小小的沙丘、沙堆上偶尔覆盖着一丛沙刺,显出耀眼的葱绿。
我真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远山如烟似云,慢慢飘荡。一处顶峰的烽火台,作怪地不随山拼命前行,却轻盈淡定地朝后退去。
我正看得出神,觉得下巴被什么摸了摸,低头看,是一个鲜亮熟透的西红柿,沙妮瞪巴眼儿望着我笑,扬扬下巴:“吃吧!”
一路刮的都是热风,再加车身颠动,真口干舌燥了,可我不能独吞,转身后望,车厢里的旅客人手一个,知道沙妮把鼓鼓的提包腾空了,心中顿时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将西红柿送到嘴边,美美地咬下一口,透心儿甜。
我对西红柿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我和沙妮得以结合的媒介,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
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去敦煌参观,沙妮从莫高窟回来,在酒泉,吃饭时凑在一个桌子上。我倒了满满一小碗汤,没把住手指,一打晃,几点汤水溅到沙妮的粉红绦凉衬衣上,觉得非常失礼,赶忙给她陪不是。沙妮二话没说,丢下饭碗,十分不乐意地回宿舍去了。
我也没有喝汤,到街上买了包肥皂粉,称了一斤西红柿,到隔壁沙妮住的房间陪情道歉。沙妮从被褥上爬起来,看她红肿的双眼,一定是刚刚哭过。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我脑子反映慢,按事先编好的话说:“这是包肥皂粉,麻烦你把衬衣洗洗。刚才怪我不小心。这几个西红柿,你吃,你没喝汤,这会儿一定渴了。”
我吭吭哧哧地刚说完,没想到沙妮“咯咯咯”笑得浑身抖动。我像一个小丑站在那里,叫沙妮笑得透透出了一身汗。可能沙妮看出了我的窘态,收敛住笑,起身拣了一个顶大的西红柿,用开水冲冲,剥去粗皮,递给我:“既然是你送给我的,就算我的了,吃吧!”
我没料到一个路途相逢的陌生姑娘会这般落落大方,说什么也不肯接。沙妮看不惯我的做作,皱皱眉头,从包里找出把小刀来,将西红柿一切两半,递给我一半:“我陪你吃。快接住,看汁水滴了人家一手。”我的脸虽说一直涨红到耳朵根去,可是不得不接过西红柿……
从这以后,我和沙妮互留地址,书信往来,才知她在一个治沙研究所工作。她爱这一行,改名沙妮,发誓为治沙事业奋斗终生。因为熟悉了,我也告诉她自己喜欢写诗,尤其爱写新边塞诗,沙刺,红柳,骆驼,戈壁,敦煌,阳关,是我歌颂的主要对象。
再以后,就是恋爱。
今天,是乘参观之便旅行结婚。别的新婚夫妇旅行,向往江南水乡,往北京、上海等繁华、喧闹的大城市跑,我俩呢,偏偏选准到这飞沙走石的阳关来。没办法,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正如同志们给我俩送的雅号一样:“一对沙(傻)子。”
沙妮却没有半点倦意,双目贪婪地望着窗外,好像下决心要把阳关边塞风光记在脑子里似的。
“快,快看!”
沙滩上出现了村落房顶,错落有致,我欣喜盼望快点到农村庄院,马上又能看到一棵绿树了。你想想,走了大半天,远山没草,近地无树,空中无鸟,突然有一棵绿树出现在眼前,盼望远客归来似地向你频频点头致意,该有多么高兴?!
车到跟前,却使我大失所望,哪里是村庄屋顶,原来是上古哪朝哪代山洪冲积而成的土台,土堆,土丘,成偌大的猪像,牛像,象像,在那里笨重地一挪一动,车越走得快,你越看得清晰真切。
“美不?”沙妮用双手撑着下巴,眯缝起双眼用心思,“走过的路途,虽然也出现过水库,绿洲,村落,拱桥,大漠道,古城堡,但我觉得都没这假象壮观,真切。我的新边塞诗人,这些能入诗吗?”
我发自内心的感叹:“沙妮,你什么都懂得,也提起笔来写丝路新诗吧!”
沙妮不以为是我讽刺她,报以我一个会心的微笑:“茫茫大漠有五彩七色,就看会不会将她涂描。”
听熟悉地理的人说,轿车一进入北戈壁,比南戈壁还热。一会儿,这话就见效了,人们都像闷在蒸笼里,一身接一身地出汗。我放下窗玻璃,原指望叫透透凉风,哪知反倒热火扑面,燎烧得让你难以忍受,只得原抬起窗玻璃,车厢里虽说闷热晕人,总比烈火炽烤好受得多。沙妮的脸面烧得像熟透了的西红柿,汗水淋淋,也来不及往干擦,冲着大家微笑了一下,扭秧歌般走到售票员的座前,一边解开麻袋口,一边非常严肃地声明:“两人一个西瓜,自前而后,自左而右发,别争别抢别谢我,算是我俩请大家的客。”
这真叫雪中送炭,暑天送瓜,再及时不过了,旅客们同时欢呼起来:“沙妮,你请我们吃喜瓜呀?”
沙妮说:“舌头是个软的,随你怎么说都行。”
溜圆熟透了的甘州瓜传到了每个人的手里,啧啧不已。有人渴极了,来不及往出掏小刀,干脆抡起拳头,“嗵-”一下把瓜砸烂,一人掰一半粗嚼快咽。
沙妮心细,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她竟料理得这么周到。这样的待客方式,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有着如此粗犷浓厚的阳关风味。我想十碗八盘的美酒佳淆,客人们打嗝剔牙之后,也许早忘在脑后了,可是对在阳关途中的一个西红柿,半牙甘州瓜的款待,大概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沙妮呀沙妮,你这个傻姑娘,就是与众不同。
胖胖的领队用印花手绢擦了擦嘴,高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先进敦煌县城住招待所休息呢,还是先参观月牙泉后进城呢?
后一条是沙妮向胖领队提出的。同志们心里都清楚,又加刚刚吃过沙妮的西瓜,恰逢我俩的喜庆日子,自然异口同声先去月牙泉。这使得沙妮很高兴,抓住我的双手摇了又摇,要说的千方百计都摇在这里面了。
大轿车载着我们一行二十五人在蒙蒙天色中向月牙泉急驶。
听胖领队兼向导说,快到了,车速却不吉祥地慢下来,最后前后点晃了点晃,干脆停下了。我们只好下车徒步而行。
原来是前面的轿车挡路,四个轮子深陷在细沙中难以行驶。右边一台推土机正往掉推昨晚刮积在公路上的细沙。风不大,在沙丘上却特别地显示威力,尤其是细沙在推板前移动时,一小股一小股地被吹起来,迷人眼目。沙丘上却留下了水浪似的细致的波纹,仿佛一股劲地抖动。
我看见一丛沙刺在风中嗦嗦摇曳,走近弯下腰身听,声响如同翻江倒海一般,刚想折下一枝来研究研究,伸到半路的手却被五个纤细的的指头抓住了,撩起眼皮看,是沙妮。
“别糟蹋它。”
沙妮是治沙研究所的,自然对沙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只好冲她尴尬地笑了笑。
沙妮真会谅解人,刚才一派严肃的面孔立刻换成了笑模样儿,拉我蹲下,用双手小心地托过一枝沙刺来叫我看。
怪,沙刺根本没什么叶子,只是多次分枝,成短节针状形,挥发量小,这大概就是它能够在沙漠荒滩顽强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我们几个朝前探了探路,人多力量大,推也能把轿车推过去,可是返回时,却无论如何也爬不上这段堆积细沙的大漫坡。众人所见略同,于是,一个个垂头丧气地上了车。
胖领队很能理解我和沙妮的心情,问道:“明天再来吧?”
我望望沙妮,征求她的意见。
沙妮真尖,在这种场所下从不露出对我的半点亲近,朝车上的同志们挥了挥手:“下午七点来接我们一下。再见!”
轿车吼吼发动,缓缓绕半圆打个倒转,扬沙起尘开走了。
我不知道沙妮把我留下干什么,只好愣愣地站着。
沙妮拉了我一把:“尽傻立着干什么,走啊!”
“上哪儿?”
“月牙泉。放心,我作向导,抄捷径走。”
在这种时候,你想我能不服从她吗?
敦煌的沙就是多,公路旁,小道上,树丛中,比比皆是。我俩开动11号(两条腿),大胆地手拉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艰难行进。
月牙泉,是我早已向往的圣地,真正去瞻仰她的美容,还是第一次,所以沿途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到非常新鲜。放眼望去,尽是沙漠,横在眼前的几座大山,也被细沙遮盖了真面目。
开始爬山时,沙妮故意丢下我,只顾走自己的路。我一看山势陡峻,生怕掉队遭沙妮嘲笑,加快脚步往前赶,却怎么也赶不快,走一步,退两步,格外费力。爬了一段,我才知道爬的是沙山。天呐,这么陡峻、绵长的山峰迭丘,竟然是沙的世界!我尽量装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一脚踏下去,软绵绵的,再往起抬脚时便是一个坑,觉出脚下的沙在朝后流动。一会儿,便汗流浃背。
沙妮存心使坏,领我顺一条坡度很陡的山梁走,不大工夫,我和沙妮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回头望,不知怎么幻影处同车的人都跟来了,自动排成队,一个比一个小,佝偻着身躯向前。我尽量使自己的脚下稳重,不至于因打晃滚到山脚下去。
沙妮大概觉得不等等我显得太无情无意,,转身站定,见我扭秧歌,拍手笑个不停:“看你那么怕的,还算个男子汉大丈夫哩!其实沙久经风吹日晒,复盖积压,坚实着呢。只要你抬脚时五个脚趾用力不猛,也不多费劲,更不会因跌跤发生意外事故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沙妮特意滚了几滚叫我看。
我趁机站下喘了几口气,靠沙妮的牵扯,终于爬到山顶了。一屁股软软坐下去,不想再起来。
看见了。说也怪,四面都是沙山,中间盆地般低下去的就是月牙泉---真像农历初四、五的一弯新月,水绿得可爱,泛起粼粼银波,上游芦苇丛生,西边果木遮地,万绿丛中露出一角粉白墙壁,别是一番天地。
沙妮酷爱沙,面对沙山,眯缝起双眼看不够,好一阵,自言自语:“我们的治沙研究哪天要治到月牙泉边来,多好呀!”
我立刻动了文思,诗兴大作:“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定能。月牙泉,我会常来看望你,打扮你,诉说我的梦,又痛苦,又甜蜜。”
“真的吗?”沙妮斜起脸盘问我,上眼皮特别地朝后描,并不等我回答,结实捧起一抔沙,任凭从指缝往下流,“我爱沙,更恨沙,说来也矛盾得很,飞沙走石,对人类的健康有影响,最可恨的是沙丘移动,吞没庄园良田。什么时候把沙丘完全固定住,并叫它生水长树,就好了。”
我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心中一定有数。”
沙妮娇嗔地白了我一眼:“当然!”动手脱掉鞋袜。
我惊叫了一声:“你要打赤脚?”一位新娘子这般泼辣,万一叫人看见,事后会被传为笑柄的。
沙妮根本不听:“你大惊小怪个什么呀?”还围过来连哄带缠把我的鞋袜也脱了,用手理理飘到眼前的秀发,感慨万端地说:“投胎于人,谈何容易。我的人生观很简单:工作时,专心致志,玩耍时,痛快淋漓,这才叫珍惜生命,不对吗?”用双手拉住我的胳膊,喊声“一二”把我拉起来,并和我手挽手,管我同意不同意,扯拉着就往下跑。
这时,我才觉出这样很舒适,又省力,只是细沙有点烫脚,没有我预料中的天旋地转,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就像腾云驾雾般似地一气跑到月牙泉边,才感到浑身发热,口干舌燥,往高卷了卷裤子,脱去衬衣,满脸通脖子地大洗起来,分外凉爽提神。
沙妮怕沾湿气,穿好鞋袜,蹲在月牙泉边,望着自己映在水中折折抖抖的倒影出神。忽然想起什么来了,将双手浸在水中,害羞地笑了一下,生怕被我看见,忙把脸面低下去,好一阵,才用手揉着右眼皮“哎呀”“哎呀”地呻唤。
我问:“怎么啦?”
沙妮站起来,慢慢向我走近,撒娇地说:“也许揉进去了粒沙子,你快来给我翻翻。”
我抛了抛手上的水,掏出手绢擦干,紧挨沙妮,左手托住她的下巴,用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非常小心地凑上去,准备翻眼睑。
沙妮的左眼忽然睁大了,乌黑闪亮。深情脉脉地望着我,趁势偎在怀里。
我先一怔,等到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双手使劲搂住沙妮的腰身,用赤热的双唇吻着她青青的眉峰……
(原载《阳关》)
我和沙妮(小说)
经酒泉,过玉门,西去阳关,越走越荒凉:望不断的马鬃山,仿佛山随车速,变戏法似地无限向前延伸;走不完的沙石滩,大沙丘成波浪式,还一动不动,好像下面鼓着风,随时都有被推移涨起的可能性。
我用胳肘碰了碰紧挨我坐着的沙妮:“看,沙刺。”
沙妮往一边挤了挤我,尽力将上身倾斜于窗前,忽闪了一下重眼皮,深深吸了一口气赞叹:“多美啊!”
真的,小沙丘上长满了沙刺,高高低低,相衬互映。高的沙刺顶端,有的成粉色,像梅花,有的呈浅黄,像芦花,在茫茫戈壁中顽强生长,梳洗打扮,别具一番风格。也许是沙丘生水,沙刺又能固定小沙丘的缘故,他俩才相依为命地生存下来了。
我承受不住沙妮的压力,礼貌地提醒:“对不起。”
沙妮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移移屁股坐稳,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边塞风光出神。
我开玩笑:“你为什么叫沙妮呢?应该叫沙刺。”说完,不知我和什么联想上了,忍不住地“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沙妮却不笑,甜甜地对我说:“我原来的名字真叫沙刺,取沙里生,沙里长,立志于治沙研究事业的含义。可是所里的人嫌太俗气,还开我的玩笑,‘沙刺,沙刺,谁敢和你接近?还是叫沙妮吧,两方面的意思都有了,也好听,像个姑娘的名字。’我一想,说得在理,点头同意,从此我就叫沙妮了。……你听的呀没有?”
我经受不住一路的颠簸,感到有点昏昏欲睡,尤其是上眼皮,沉重得怎么使劲也抬不起来。
沙妮见我疲倦成这样,再没责怪,用下巴指指她的肩膀,柔情地说:“睡一会儿吧!”
一觉醒来,睡眼惺忪,立时辨别不清到哪里了,茫茫大漠,变幻万千:风刮个不停,蒙天迷地,如泣如诉,戈壁不知何故,全变成了白雪上又落了层黄土那么一种颜色。远处起风推尘于半天空,好像下珍珍雪,上下飞卷着。再远处的马鬃、祁连隐去高入云霄的真面目。天似穹庐,把我们笼罩在越来越小的空间,使人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
大轿车也嫌窒息,加速跑了一段路程,风小了,戈壁显出表绿色,一马平川,望不到头。没树,没草,只有小小的沙丘、沙堆上偶尔覆盖着一丛沙刺,显出耀眼的葱绿。
我真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远山如烟似云,慢慢飘荡。一处顶峰的烽火台,作怪地不随山拼命前行,却轻盈淡定地朝后退去。
我正看得出神,觉得下巴被什么摸了摸,低头看,是一个鲜亮熟透的西红柿,沙妮瞪巴眼儿望着我笑,扬扬下巴:“吃吧!”
一路刮的都是热风,再加车身颠动,真口干舌燥了,可我不能独吞,转身后望,车厢里的旅客人手一个,知道沙妮把鼓鼓的提包腾空了,心中顿时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将西红柿送到嘴边,美美地咬下一口,透心儿甜。
我对西红柿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我和沙妮得以结合的媒介,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
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去敦煌参观,沙妮从莫高窟回来,在酒泉,吃饭时凑在一个桌子上。我倒了满满一小碗汤,没把住手指,一打晃,几点汤水溅到沙妮的粉红绦凉衬衣上,觉得非常失礼,赶忙给她陪不是。沙妮二话没说,丢下饭碗,十分不乐意地回宿舍去了。
我也没有喝汤,到街上买了包肥皂粉,称了一斤西红柿,到隔壁沙妮住的房间陪情道歉。沙妮从被褥上爬起来,看她红肿的双眼,一定是刚刚哭过。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我脑子反映慢,按事先编好的话说:“这是包肥皂粉,麻烦你把衬衣洗洗。刚才怪我不小心。这几个西红柿,你吃,你没喝汤,这会儿一定渴了。”
我吭吭哧哧地刚说完,没想到沙妮“咯咯咯”笑得浑身抖动。我像一个小丑站在那里,叫沙妮笑得透透出了一身汗。可能沙妮看出了我的窘态,收敛住笑,起身拣了一个顶大的西红柿,用开水冲冲,剥去粗皮,递给我:“既然是你送给我的,就算我的了,吃吧!”
我没料到一个路途相逢的陌生姑娘会这般落落大方,说什么也不肯接。沙妮看不惯我的做作,皱皱眉头,从包里找出把小刀来,将西红柿一切两半,递给我一半:“我陪你吃。快接住,看汁水滴了人家一手。”我的脸虽说一直涨红到耳朵根去,可是不得不接过西红柿……
从这以后,我和沙妮互留地址,书信往来,才知她在一个治沙研究所工作。她爱这一行,改名沙妮,发誓为治沙事业奋斗终生。因为熟悉了,我也告诉她自己喜欢写诗,尤其爱写新边塞诗,沙刺,红柳,骆驼,戈壁,敦煌,阳关,是我歌颂的主要对象。
再以后,就是恋爱。
今天,是乘参观之便旅行结婚。别的新婚夫妇旅行,向往江南水乡,往北京、上海等繁华、喧闹的大城市跑,我俩呢,偏偏选准到这飞沙走石的阳关来。没办法,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正如同志们给我俩送的雅号一样:“一对沙(傻)子。”
沙妮却没有半点倦意,双目贪婪地望着窗外,好像下决心要把阳关边塞风光记在脑子里似的。
“快,快看!”
沙滩上出现了村落房顶,错落有致,我欣喜盼望快点到农村庄院,马上又能看到一棵绿树了。你想想,走了大半天,远山没草,近地无树,空中无鸟,突然有一棵绿树出现在眼前,盼望远客归来似地向你频频点头致意,该有多么高兴?!
车到跟前,却使我大失所望,哪里是村庄屋顶,原来是上古哪朝哪代山洪冲积而成的土台,土堆,土丘,成偌大的猪像,牛像,象像,在那里笨重地一挪一动,车越走得快,你越看得清晰真切。
“美不?”沙妮用双手撑着下巴,眯缝起双眼用心思,“走过的路途,虽然也出现过水库,绿洲,村落,拱桥,大漠道,古城堡,但我觉得都没这假象壮观,真切。我的新边塞诗人,这些能入诗吗?”
我发自内心的感叹:“沙妮,你什么都懂得,也提起笔来写丝路新诗吧!”
沙妮不以为是我讽刺她,报以我一个会心的微笑:“茫茫大漠有五彩七色,就看会不会将她涂描。”
听熟悉地理的人说,轿车一进入北戈壁,比南戈壁还热。一会儿,这话就见效了,人们都像闷在蒸笼里,一身接一身地出汗。我放下窗玻璃,原指望叫透透凉风,哪知反倒热火扑面,燎烧得让你难以忍受,只得原抬起窗玻璃,车厢里虽说闷热晕人,总比烈火炽烤好受得多。沙妮的脸面烧得像熟透了的西红柿,汗水淋淋,也来不及往干擦,冲着大家微笑了一下,扭秧歌般走到售票员的座前,一边解开麻袋口,一边非常严肃地声明:“两人一个西瓜,自前而后,自左而右发,别争别抢别谢我,算是我俩请大家的客。”
这真叫雪中送炭,暑天送瓜,再及时不过了,旅客们同时欢呼起来:“沙妮,你请我们吃喜瓜呀?”
沙妮说:“舌头是个软的,随你怎么说都行。”
溜圆熟透了的甘州瓜传到了每个人的手里,啧啧不已。有人渴极了,来不及往出掏小刀,干脆抡起拳头,“嗵-”一下把瓜砸烂,一人掰一半粗嚼快咽。
沙妮心细,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她竟料理得这么周到。这样的待客方式,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有着如此粗犷浓厚的阳关风味。我想十碗八盘的美酒佳淆,客人们打嗝剔牙之后,也许早忘在脑后了,可是对在阳关途中的一个西红柿,半牙甘州瓜的款待,大概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沙妮呀沙妮,你这个傻姑娘,就是与众不同。
胖胖的领队用印花手绢擦了擦嘴,高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先进敦煌县城住招待所休息呢,还是先参观月牙泉后进城呢?
后一条是沙妮向胖领队提出的。同志们心里都清楚,又加刚刚吃过沙妮的西瓜,恰逢我俩的喜庆日子,自然异口同声先去月牙泉。这使得沙妮很高兴,抓住我的双手摇了又摇,要说的千方百计都摇在这里面了。
大轿车载着我们一行二十五人在蒙蒙天色中向月牙泉急驶。
听胖领队兼向导说,快到了,车速却不吉祥地慢下来,最后前后点晃了点晃,干脆停下了。我们只好下车徒步而行。
原来是前面的轿车挡路,四个轮子深陷在细沙中难以行驶。右边一台推土机正往掉推昨晚刮积在公路上的细沙。风不大,在沙丘上却特别地显示威力,尤其是细沙在推板前移动时,一小股一小股地被吹起来,迷人眼目。沙丘上却留下了水浪似的细致的波纹,仿佛一股劲地抖动。
我看见一丛沙刺在风中嗦嗦摇曳,走近弯下腰身听,声响如同翻江倒海一般,刚想折下一枝来研究研究,伸到半路的手却被五个纤细的的指头抓住了,撩起眼皮看,是沙妮。
“别糟蹋它。”
沙妮是治沙研究所的,自然对沙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只好冲她尴尬地笑了笑。
沙妮真会谅解人,刚才一派严肃的面孔立刻换成了笑模样儿,拉我蹲下,用双手小心地托过一枝沙刺来叫我看。
怪,沙刺根本没什么叶子,只是多次分枝,成短节针状形,挥发量小,这大概就是它能够在沙漠荒滩顽强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我们几个朝前探了探路,人多力量大,推也能把轿车推过去,可是返回时,却无论如何也爬不上这段堆积细沙的大漫坡。众人所见略同,于是,一个个垂头丧气地上了车。
胖领队很能理解我和沙妮的心情,问道:“明天再来吧?”
我望望沙妮,征求她的意见。
沙妮真尖,在这种场所下从不露出对我的半点亲近,朝车上的同志们挥了挥手:“下午七点来接我们一下。再见!”
轿车吼吼发动,缓缓绕半圆打个倒转,扬沙起尘开走了。
我不知道沙妮把我留下干什么,只好愣愣地站着。
沙妮拉了我一把:“尽傻立着干什么,走啊!”
“上哪儿?”
“月牙泉。放心,我作向导,抄捷径走。”
在这种时候,你想我能不服从她吗?
敦煌的沙就是多,公路旁,小道上,树丛中,比比皆是。我俩开动11号(两条腿),大胆地手拉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艰难行进。
月牙泉,是我早已向往的圣地,真正去瞻仰她的美容,还是第一次,所以沿途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到非常新鲜。放眼望去,尽是沙漠,横在眼前的几座大山,也被细沙遮盖了真面目。
开始爬山时,沙妮故意丢下我,只顾走自己的路。我一看山势陡峻,生怕掉队遭沙妮嘲笑,加快脚步往前赶,却怎么也赶不快,走一步,退两步,格外费力。爬了一段,我才知道爬的是沙山。天呐,这么陡峻、绵长的山峰迭丘,竟然是沙的世界!我尽量装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一脚踏下去,软绵绵的,再往起抬脚时便是一个坑,觉出脚下的沙在朝后流动。一会儿,便汗流浃背。
沙妮存心使坏,领我顺一条坡度很陡的山梁走,不大工夫,我和沙妮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回头望,不知怎么幻影处同车的人都跟来了,自动排成队,一个比一个小,佝偻着身躯向前。我尽量使自己的脚下稳重,不至于因打晃滚到山脚下去。
沙妮大概觉得不等等我显得太无情无意,,转身站定,见我扭秧歌,拍手笑个不停:“看你那么怕的,还算个男子汉大丈夫哩!其实沙久经风吹日晒,复盖积压,坚实着呢。只要你抬脚时五个脚趾用力不猛,也不多费劲,更不会因跌跤发生意外事故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沙妮特意滚了几滚叫我看。
我趁机站下喘了几口气,靠沙妮的牵扯,终于爬到山顶了。一屁股软软坐下去,不想再起来。
看见了。说也怪,四面都是沙山,中间盆地般低下去的就是月牙泉---真像农历初四、五的一弯新月,水绿得可爱,泛起粼粼银波,上游芦苇丛生,西边果木遮地,万绿丛中露出一角粉白墙壁,别是一番天地。
沙妮酷爱沙,面对沙山,眯缝起双眼看不够,好一阵,自言自语:“我们的治沙研究哪天要治到月牙泉边来,多好呀!”
我立刻动了文思,诗兴大作:“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定能。月牙泉,我会常来看望你,打扮你,诉说我的梦,又痛苦,又甜蜜。”
“真的吗?”沙妮斜起脸盘问我,上眼皮特别地朝后描,并不等我回答,结实捧起一抔沙,任凭从指缝往下流,“我爱沙,更恨沙,说来也矛盾得很,飞沙走石,对人类的健康有影响,最可恨的是沙丘移动,吞没庄园良田。什么时候把沙丘完全固定住,并叫它生水长树,就好了。”
我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心中一定有数。”
沙妮娇嗔地白了我一眼:“当然!”动手脱掉鞋袜。
我惊叫了一声:“你要打赤脚?”一位新娘子这般泼辣,万一叫人看见,事后会被传为笑柄的。
沙妮根本不听:“你大惊小怪个什么呀?”还围过来连哄带缠把我的鞋袜也脱了,用手理理飘到眼前的秀发,感慨万端地说:“投胎于人,谈何容易。我的人生观很简单:工作时,专心致志,玩耍时,痛快淋漓,这才叫珍惜生命,不对吗?”用双手拉住我的胳膊,喊声“一二”把我拉起来,并和我手挽手,管我同意不同意,扯拉着就往下跑。
这时,我才觉出这样很舒适,又省力,只是细沙有点烫脚,没有我预料中的天旋地转,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就像腾云驾雾般似地一气跑到月牙泉边,才感到浑身发热,口干舌燥,往高卷了卷裤子,脱去衬衣,满脸通脖子地大洗起来,分外凉爽提神。
沙妮怕沾湿气,穿好鞋袜,蹲在月牙泉边,望着自己映在水中折折抖抖的倒影出神。忽然想起什么来了,将双手浸在水中,害羞地笑了一下,生怕被我看见,忙把脸面低下去,好一阵,才用手揉着右眼皮“哎呀”“哎呀”地呻唤。
我问:“怎么啦?”
沙妮站起来,慢慢向我走近,撒娇地说:“也许揉进去了粒沙子,你快来给我翻翻。”
我抛了抛手上的水,掏出手绢擦干,紧挨沙妮,左手托住她的下巴,用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非常小心地凑上去,准备翻眼睑。
沙妮的左眼忽然睁大了,乌黑闪亮。深情脉脉地望着我,趁势偎在怀里。
我先一怔,等到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双手使劲搂住沙妮的腰身,用赤热的双唇吻着她青青的眉峰……
(原载《阳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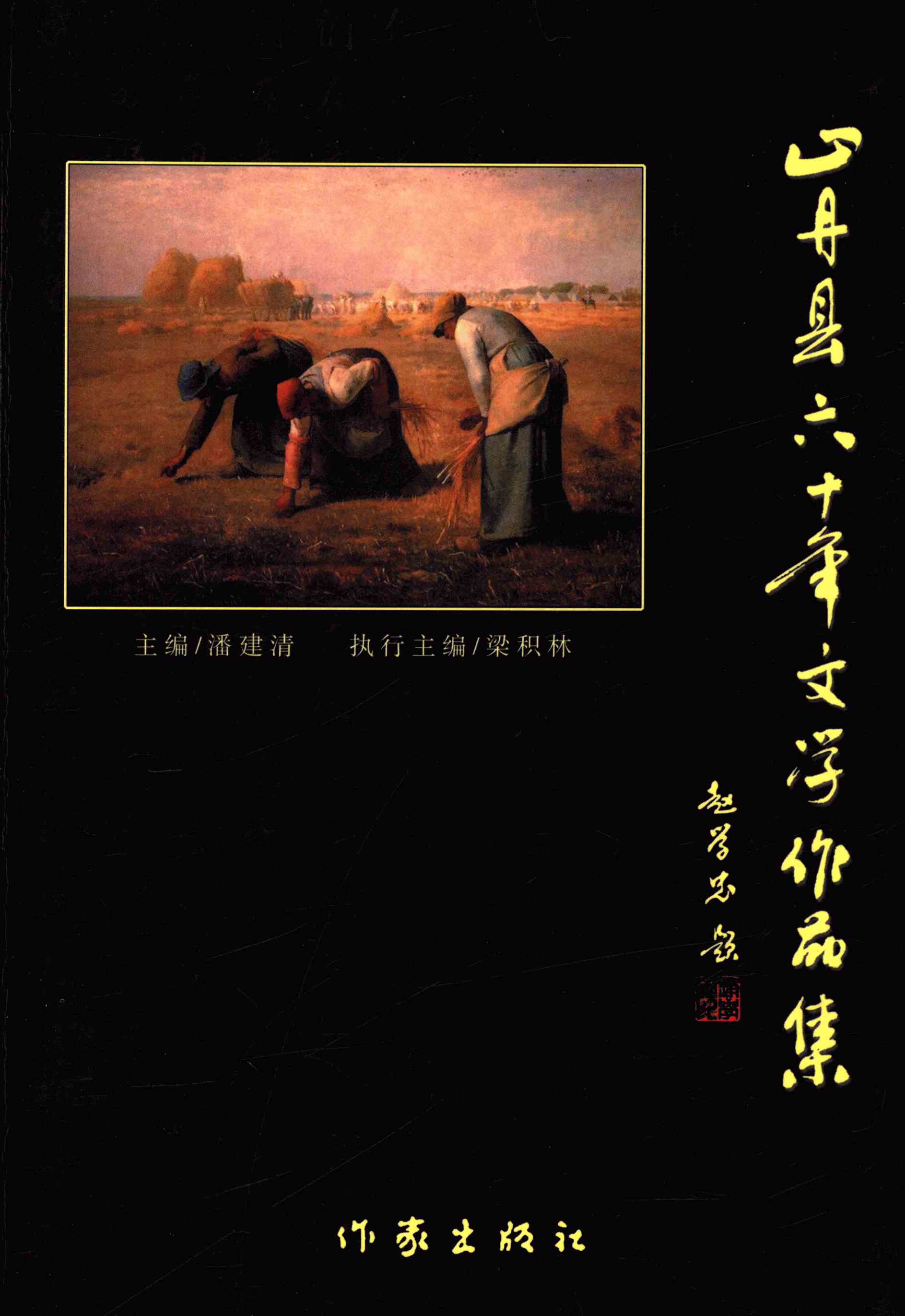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萧滋云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