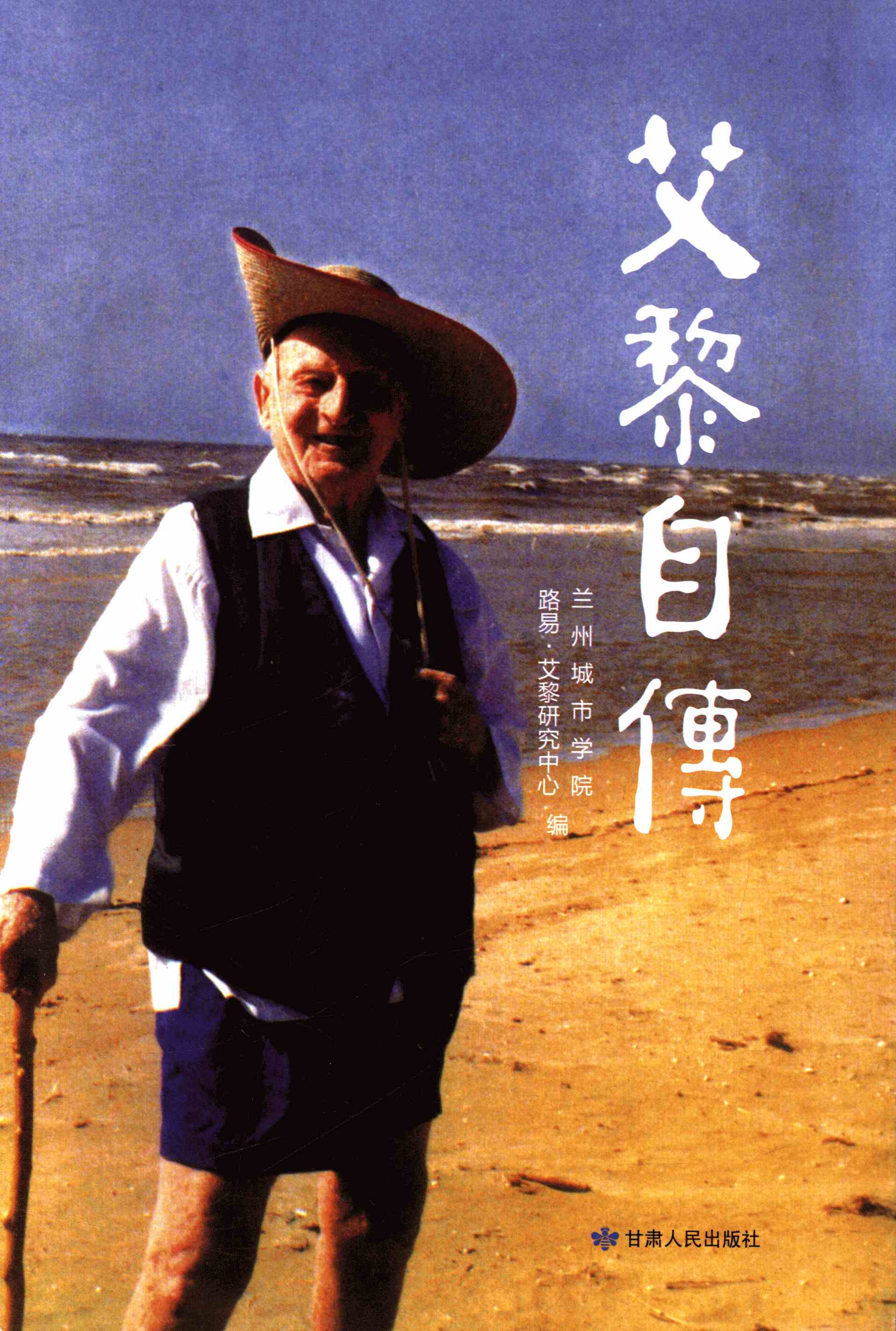内容
我搬进学校接替乔治遗留下的工作时,在学校旁边先前摔跤比武的擂台盖了一座小屋。那地方在很早的时候还作过别的用途,但不管怎样,在较低的坡上平出了一块地来,以后几年,按我自己的设计盖起的房子就坐落在那里。中间是院子,院子两端的泥墙上各开一个门,到晚上才关。院子的一边,从这头到那头,是分成3间的起居室兼卧室,我住左边一间,孩子们住右边一间,对面是一间长房子,作为厨房、厨子的住房和库房。乔治·何克4个养子中的两个——老三和老四,还有另外两个很有前途的孩子曹百成和张维善,都因年龄太小不能去住学校宿舍,跟我住在一起。聂家兄弟是“工合”工作者——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聂长林的儿子。聂搬到一个合作中心去后,这个中心随即被国民党士兵捣毁了,他被吊起来打了一顿。合作社的其他社员,把他放了下来,送到山西太行山,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工合”分支机构。他有病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留在宝鸡,情况很惨。妻子不幸因患癌症病死。由于无人敢收留一个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孩子,乔治就把他们全部收养下来,并从双石铺带到山丹。乔治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的父亲也终于在东北找到了,他已是那里的一位领导干部,一家人得到了团圆。
在山丹,乔治死后,我起先有一种孤独感。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活泼,又使我高兴起来,每顿饭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定出了许多小规矩,如:不许在家里哭,谁要哭就到擂台去哭。别人做事时不许在室内到处玩,谁想玩就到外面去玩等等。因此,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每周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六晚上去洗澡。学校里盖了几间小浴室,我们一起到其中的一间浴室去,在热水里泡呀,搓呀,擦呀。穿衣服之前大家都围在那只从双石铺拉来的大铁炉子旁边,先美餐一顿。炉子上通常炖着一大锅杏干、新疆葡萄干、冻梨和姜块,大家用长把铜勺舀着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尤其要是加上了一些蜂蜜的话。这时又讲故事,又说笑话,真是不亦乐乎。老四那时才四五岁,他喜欢听我讲《杰克和豆秸》这个故事,但我把内容适当地中国化了。每当我讲到“菲—法—福—富姆”①时,他便心惊胆战。事情不如意,我开始发脾气时,曹百成就会面带最开朗的笑容问:“你为什么这样生气?”并且对着我笑,直到我觉得情况似乎好些为止。除此之外,我当父母的责任不外乎就是注意让他们洗澡,吃得饱,至少做一些家庭作业,以及冬天不受冻而已。老四有一次的确得了肺炎之类的病,但后来病就好了。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些孩子为我做的比我能为他们做的还多,因为他们的确使我摆脱了孤独,不去想当时的一切问题和事情。自然,人们一闪念会回想起往昔曾影响过自己的一些小事。记得有一回,我在大热天用铁锹在农场挖了一天渠,累得要死。我留下来做最后的清理工作,而孩子们像大雁一样排着笔直的队形,轻捷地穿过荒草原,跑回去吃晚饭了。这时,突然间刮起了阴森森的大风。我顶着风艰苦地沿路慢慢往回走。一时之间,中年人的疲乏感把我征服了。然而,风沙之中,从沟壑里传来了令人欣喜的呼唤。曹百成牵着学校里的一只骆驼——那只大白骆驼正朝我走来。回家的5公里路走得又气派又舒服,穿过城门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门要那么高,因为骑在骆驼背上刚好不碰顶。
我所住的擂台,也是有些生产组的学生到操场去的必经之路。每天早晨在那里升旗,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擂台后门进来,穿过我过厅里铺砖的小道,由前门出去,是条捷径。有我睡炕的那间房,通向中间的一间,那里两扇很阔的门,除非在最冷的天气,经常朝院子敞开着。我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兼多用途起居室的入门处,铺了一块毡垫。有一天早晨,我还光着身子在睡觉(这是我从西北农民那里学来的最舒服的睡觉方式),突然,梦被搅乱,因为被子已被迅速拖上来,蒙住了我的头,在我全身组织最软的部位响亮地打了两下,我还未能从被子中解脱之前,肇事者已无影无踪了,只听见远处传来他们欢快的、憋不住的笑声。他们早已从擂台正面的台阶跑下去,消失在大门外操场的方向。不过,我仿佛可以听出是谁的笑声,而且知道准是预备班里那些正值狂躁的年龄的孩子中的一个干的。于是,我把被子推回原处,准备再补上一小觉。可是,睡意全无了。我是否该生气或发火并找出肇事者呢?我的那条狗斯金皮似乎很欣赏这件事,它伸出前爪扒着炕沿,站在那里,像是期待着再发生别的有趣的事。
我在山丹的日子里还有一番感到陶醉的经历,那就是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巡视校内的各生产组。通常第一节课后我就出发,可每到一个作业现场就舍不得离开了。我看到人们在手脑并用地劳动。当他们的手指在制坯轮上捏塑着陶罐时,那边熄灭了火的窑在出窑;玻璃器皿正吹出来,一摞摞瓶子被装进退火炉里。在造纸组,只见在小型蒸汽机的响声中,张世昌和他的伙伴们忙个不停。在纺织组,我们骄傲地看到毛纺成套设备终于安装停当并开机工作了,100多只纱锭转动着,织布机织出了毯子、哔叽或斜纹布;一只水泵正把外面的河水抽到染缸里来。我到缝纫组,看见山丹当地的孩子王延义正在裁剪和缝纫的学生中间忙着。我得先去针织组检查新设计的毛衣和袜子式样,才能到皮革组去看刮皮、抛光、上色以及皮袄的制作。随后,跨过小河到面粉组,再转到它房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甜菜制糖的地方。这时,要再向外走去看农场或煤矿,一般就太晚了,需要专门安排一个下午才行。我就在回城的路上经过电机组和运输组,看磨曲轴和装配新活塞。最后才到机械组、印刷组和医院。此时,机械组的锅炉上的汽笛就该鸣响了,该去吃晚饭和准备晚上开会或学习了。
这也许听起来很有些田园风味,其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笑脸,比在我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多,一天中为时也更长。这里的孩子中,青春期的烦恼似乎比我年轻时在学校的烦恼要少。这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每天都要为学校做出上百个决定,要收进或送出许多信件或报告,同中国国内外的支持者保持联系。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天。也许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有点时间回顾往昔的欢乐和痛苦:孩提时代,带着一本书,爬在高高的鸦茅丛中,消磨夏天的星期日。在韦斯特科特老家的炉火旁与朋友们悄悄地谈天。在战时的上海,有一名军官是怎样打那身为骄横象征的日本人的耳光……然后又回到欢乐中来。傍晚,坐在陶瓷组的水车旁,静静的水纹映出冬日的树影。老磨坊和远处的积雪,同杜安芳商量釉料等实际问题,身背后其他的人正拿着筷子、端着碗在吃晚饭。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下午的风沙吹得我眼睛发涩,我闭上了眼睛。
在山丹,乔治死后,我起先有一种孤独感。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活泼,又使我高兴起来,每顿饭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定出了许多小规矩,如:不许在家里哭,谁要哭就到擂台去哭。别人做事时不许在室内到处玩,谁想玩就到外面去玩等等。因此,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每周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六晚上去洗澡。学校里盖了几间小浴室,我们一起到其中的一间浴室去,在热水里泡呀,搓呀,擦呀。穿衣服之前大家都围在那只从双石铺拉来的大铁炉子旁边,先美餐一顿。炉子上通常炖着一大锅杏干、新疆葡萄干、冻梨和姜块,大家用长把铜勺舀着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尤其要是加上了一些蜂蜜的话。这时又讲故事,又说笑话,真是不亦乐乎。老四那时才四五岁,他喜欢听我讲《杰克和豆秸》这个故事,但我把内容适当地中国化了。每当我讲到“菲—法—福—富姆”①时,他便心惊胆战。事情不如意,我开始发脾气时,曹百成就会面带最开朗的笑容问:“你为什么这样生气?”并且对着我笑,直到我觉得情况似乎好些为止。除此之外,我当父母的责任不外乎就是注意让他们洗澡,吃得饱,至少做一些家庭作业,以及冬天不受冻而已。老四有一次的确得了肺炎之类的病,但后来病就好了。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些孩子为我做的比我能为他们做的还多,因为他们的确使我摆脱了孤独,不去想当时的一切问题和事情。自然,人们一闪念会回想起往昔曾影响过自己的一些小事。记得有一回,我在大热天用铁锹在农场挖了一天渠,累得要死。我留下来做最后的清理工作,而孩子们像大雁一样排着笔直的队形,轻捷地穿过荒草原,跑回去吃晚饭了。这时,突然间刮起了阴森森的大风。我顶着风艰苦地沿路慢慢往回走。一时之间,中年人的疲乏感把我征服了。然而,风沙之中,从沟壑里传来了令人欣喜的呼唤。曹百成牵着学校里的一只骆驼——那只大白骆驼正朝我走来。回家的5公里路走得又气派又舒服,穿过城门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门要那么高,因为骑在骆驼背上刚好不碰顶。
我所住的擂台,也是有些生产组的学生到操场去的必经之路。每天早晨在那里升旗,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擂台后门进来,穿过我过厅里铺砖的小道,由前门出去,是条捷径。有我睡炕的那间房,通向中间的一间,那里两扇很阔的门,除非在最冷的天气,经常朝院子敞开着。我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兼多用途起居室的入门处,铺了一块毡垫。有一天早晨,我还光着身子在睡觉(这是我从西北农民那里学来的最舒服的睡觉方式),突然,梦被搅乱,因为被子已被迅速拖上来,蒙住了我的头,在我全身组织最软的部位响亮地打了两下,我还未能从被子中解脱之前,肇事者已无影无踪了,只听见远处传来他们欢快的、憋不住的笑声。他们早已从擂台正面的台阶跑下去,消失在大门外操场的方向。不过,我仿佛可以听出是谁的笑声,而且知道准是预备班里那些正值狂躁的年龄的孩子中的一个干的。于是,我把被子推回原处,准备再补上一小觉。可是,睡意全无了。我是否该生气或发火并找出肇事者呢?我的那条狗斯金皮似乎很欣赏这件事,它伸出前爪扒着炕沿,站在那里,像是期待着再发生别的有趣的事。
我在山丹的日子里还有一番感到陶醉的经历,那就是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巡视校内的各生产组。通常第一节课后我就出发,可每到一个作业现场就舍不得离开了。我看到人们在手脑并用地劳动。当他们的手指在制坯轮上捏塑着陶罐时,那边熄灭了火的窑在出窑;玻璃器皿正吹出来,一摞摞瓶子被装进退火炉里。在造纸组,只见在小型蒸汽机的响声中,张世昌和他的伙伴们忙个不停。在纺织组,我们骄傲地看到毛纺成套设备终于安装停当并开机工作了,100多只纱锭转动着,织布机织出了毯子、哔叽或斜纹布;一只水泵正把外面的河水抽到染缸里来。我到缝纫组,看见山丹当地的孩子王延义正在裁剪和缝纫的学生中间忙着。我得先去针织组检查新设计的毛衣和袜子式样,才能到皮革组去看刮皮、抛光、上色以及皮袄的制作。随后,跨过小河到面粉组,再转到它房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甜菜制糖的地方。这时,要再向外走去看农场或煤矿,一般就太晚了,需要专门安排一个下午才行。我就在回城的路上经过电机组和运输组,看磨曲轴和装配新活塞。最后才到机械组、印刷组和医院。此时,机械组的锅炉上的汽笛就该鸣响了,该去吃晚饭和准备晚上开会或学习了。
这也许听起来很有些田园风味,其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笑脸,比在我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多,一天中为时也更长。这里的孩子中,青春期的烦恼似乎比我年轻时在学校的烦恼要少。这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每天都要为学校做出上百个决定,要收进或送出许多信件或报告,同中国国内外的支持者保持联系。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天。也许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有点时间回顾往昔的欢乐和痛苦:孩提时代,带着一本书,爬在高高的鸦茅丛中,消磨夏天的星期日。在韦斯特科特老家的炉火旁与朋友们悄悄地谈天。在战时的上海,有一名军官是怎样打那身为骄横象征的日本人的耳光……然后又回到欢乐中来。傍晚,坐在陶瓷组的水车旁,静静的水纹映出冬日的树影。老磨坊和远处的积雪,同杜安芳商量釉料等实际问题,身背后其他的人正拿着筷子、端着碗在吃晚饭。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下午的风沙吹得我眼睛发涩,我闭上了眼睛。
相关人物
艾黎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