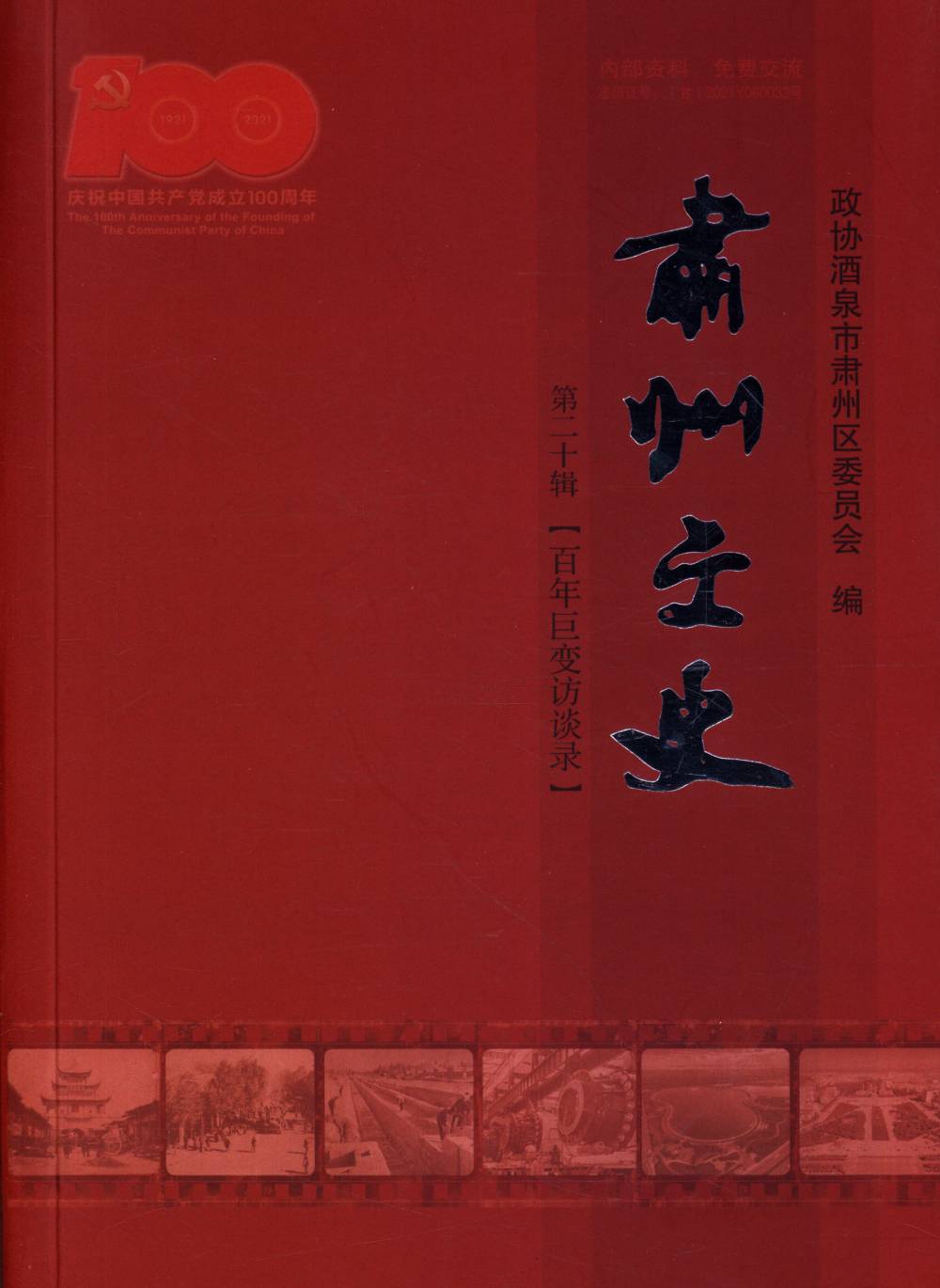乡巴佬进城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6587 |
| 颗粒名称: | 乡巴佬进城 |
| 分类号: | C913.3 |
| 页数: | 6 |
| 页码: | 479-484 |
| 摘要: | 被采访者介绍农民进城采用的交通工具和生活现状。 |
| 关键词: | 社会生活 肃州 进城 |
内容
乡巴佬进城采访对象:孔兆才,生于1941年,东洞镇棉花滩村农民。
采访人:张万生采访时间:2019年5月采访地点:大街2019年夏天,我和多年前的老朋友孔兆才在街上相遇,见他精神矍铄,衣冠整洁,走路直愣愣的。问他气色怎么这么好,像个退休人员一样。他笑呵呵地说:“我都进城三年了,住上了高楼,家里还有小汽车,日子过得和城里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你没想到吧!”接着,我们就聊起了他进城的话题。
采访人:老孔,你从前吃过不少苦,当地人都知道你身上有很多故事,别人还为你编了顺口溜:“孔家老大爱进城,下个馆子尝荤腥。破衣烂衫蓬头面,被人撵出馄饨店。”你不妨再说一说这些往事。
孔兆才:既然你想听,我就把过去进城的那些事说一说。我是个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人,年轻时因为长得还算标致,总想在同龄人中间出个风头,但由于家境贫寒,遇到了不少丢人事。
1958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队长调我和生产队的谢德林等六个人赶着大车古辘车(旧时的木车古辘大车)去城里送木料。刚解放那阵子,我家里还很贫穷,没有什么衣服可换,就穿着破衣烂衫和露出脚趾头的锥绾子鞋进城了。卸完木料,大家都在东大街的青年巷子歇着。我肚子饿了,想到大街对面的馆子吃一碗馄饨,摸来摸去,身上摸出了一块三毛钱,就毛手毛脚走进了馆子。没想到掌柜的凶神恶煞地骂道:“哪里来的’叫花子’,到别处去要,不要影响我的生意!”连推带操,把我赶出馆子。饭没有吃成,倒叫人家当成了 “叫花子”,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进城。我想着这些城里人怎么这么可恶,不就是穿得烂了些,怎么就把人往外撵呢?以后每当我想起被撵出馆子的往事,就下定决心再到那个饭馆去吃馄饨,看你怎么把我往出撵。
18岁那年,我和谢成德又一次赶着大姑辘车往酒泉城里的郭府巷送石料墩子。这一次我穿了一身洗过的旧衣服,虽说上衣和裤子都带有几块补丁,但补丁和衣服的颜色大体上一样。只是两条裤腿前面的补丁一块上一些,一块下一些,看起来不怎么协调。我还特意把脚上的榔头鞋换成了弟弟的栽毛鞋。由于鞋小,刚一穿上,一只鞋头子就绷开了一道口子,大拇脚趾头露了出来,我也没有在意,穿着这双鞋就上路了。进城卸完石料,我和谢成德到上次的馄饨馆子每人要了一大碗馄饨。掌柜见我掏出了三张五块的票子,满脸堆笑把饭钱接了过去。吃完馄饨出门时,才发现另一只鞋的头子也绷开了。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望着我的鞋,又望着我裤子上不协调的补丁说:“小伙子,以后进城把自己收拾利索一点,再不要穿着露出脚趾头的鞋进城了。”我望着自己的鞋满脸通红。这是我第二次进城。
记得19岁那年的春天,队长调人送两车芨芨到博物馆,我跳起来说:“队长,我去,那里的路我熟。”队长说:“看你那一身邋遢相,还穿着踏后跟鞋,再不要给我们乡下人丢人了。”我急忙说:“我有新衣服新鞋,只是平时舍不得穿,你就让我去吧!”队长终于让我去了。车在南门上停了下来,我赶忙把新衣服、新鞋拿出来换上,然后把装旧衣服、旧鞋的包挂在车排底下。这一次进城还真是个意外,芨芨卸完了,工地上的头头不但不小看人,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大盘炒面。这是我第三次进城。
采访人:后来的情况怎样?孔兆才:后来,我陆陆续续进过好多次城,再也没有遇到像前两次那样的难堪场面,毕竟是我长大了。21岁那年的春天,我和同大队三队的姑娘王金香相识,并在秋天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十二年里,我们有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家庭负担越来越重,除了不饿肚子以外,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34岁那年(1975年),队长派我到酒泉城里去修影剧院,我背着简单的铺盖,穿着补丁裤子,脚蹬黄球鞋,又进了城,开始在工地上干活。起初,大家都是从各公社调来的民工,挖坑搬石头都很卖力,分不出什么高下。干到快十天的时候,我的裤子扯了个口子,鞋也成了鸭鸭嘴,那个领工员看我不顺眼,总让我干最重的活。连续和了三天水泥,我实在累得没劲了,就坐在旁边的水泥垛上歇了歇,那个领工员看见了,骂骂咧咧地走过来把我从水泥垛上拉下来,还踢了我一脚。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和他对骂起来。这个领工员见我敢还口,骂道:“看你那窝囊样子,像叫花子一样,还想偷懒,”说着又踢了我一脚。我气不从一处来,跳起来採住他的领巴子,照着脸上捣了一拳头,他的鼻血就流出来了。我知道闯祸了,第二天,工地上负责人宣布,让我赶快离开工地,并通知生产队另派人来顶替我。这是我一生中在城里遭遇到的最伤自尊心的事情,也让我再次尝到了人穷受人欺的滋味。
在以后的岁月里,按照大集体的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工分、分口粮,勉强维持着生活。但娃娃多,日子过得艰难。1979年大儿子考进了酒泉中学,我要送儿子到学校去报名,总得穿件像样的裤子,想来想去,只能穿着给老婆新做的裤子出门了。老婆说:“你这不是丢人吗?女人的裤子男人怎么穿呢? ”我说:“不丢人,你那偏口裤子我穿上别人是不会注意的,”就这样,我假装体面地把儿子送到了学校,还和儿子在街上吃了大米饭和肉炒菜。这是我又一次进城,也是我心情最舒畅的一次进城。
改革开放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年就大见成效,我所承担的作业组超额完成了任务,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还每户多分了十斤清油和三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也收入不错,卖了三头猪,收入二百多元,算是有钱了,我和老婆坐着每人掏六毛钱的班车进城了。两口子心情特别好,老婆没进过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来到以前让我伤心过的馄饨馆子里要了一盘子红烧肉,美美地吃了一顿。我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算是风风光光地进了一趟城。
从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也和整个社会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大儿子考进了地质大学,小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里,我和妻子被乡政府请到政府大院里,戴上大红花,和其他的家长们共同送应征青年到酒泉影剧院参加欢送大会。我们胸戴大红花走过大街时,行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来到馄饨饭馆里,老板又让座,又倒茶水,热情得让人有些不自在。这一次进城,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坐在影剧院里听领导讲话时,我喜极而泣,眼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还在小声抽泣。老婆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呢?还哭得这么伤心?”我说: “今天我们坐的地方就是当年我被领工员小看过的地方,因为穷我才被人家看不起,想起这些,我咋能不伤心呢!”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城乡人民的经济收入翻了几番。从2013年开始,买小汽车成了乡下人追求的目标,人们相互攀比,赶集、走亲戚,甚至到地上干活都开着小汽车,现在的农民真叫个气派。买房子进城,也成为一种新时尚,许多人家即使背债欠账也要买,因为儿子要结婚了,城里没有楼房,婚是绝对结不了的。近几年政府补贴危房改造,挨家挨户搞厕所革命,支持农户安热水器等现代设施,环境卫生有了大变样。我虽然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当上城里人,可我总舍不得养活了我一辈子的土地。这几年土地流转很快,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城里有了楼房,老汉老婆子都到城里养老,在子女们的极力劝说下,我也当上了城里人。
采访人:谈谈你的感受。
孔兆才:回想起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那些心酸的事情,让人终生难忘。现在老了老了赶上了这么好的社会,拿着政府发的老年补贴,享受着合作医疗和大病医疗补助,现在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没有共产党的好领导,哪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采访人:张万生采访时间:2019年5月采访地点:大街2019年夏天,我和多年前的老朋友孔兆才在街上相遇,见他精神矍铄,衣冠整洁,走路直愣愣的。问他气色怎么这么好,像个退休人员一样。他笑呵呵地说:“我都进城三年了,住上了高楼,家里还有小汽车,日子过得和城里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你没想到吧!”接着,我们就聊起了他进城的话题。
采访人:老孔,你从前吃过不少苦,当地人都知道你身上有很多故事,别人还为你编了顺口溜:“孔家老大爱进城,下个馆子尝荤腥。破衣烂衫蓬头面,被人撵出馄饨店。”你不妨再说一说这些往事。
孔兆才:既然你想听,我就把过去进城的那些事说一说。我是个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人,年轻时因为长得还算标致,总想在同龄人中间出个风头,但由于家境贫寒,遇到了不少丢人事。
1958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队长调我和生产队的谢德林等六个人赶着大车古辘车(旧时的木车古辘大车)去城里送木料。刚解放那阵子,我家里还很贫穷,没有什么衣服可换,就穿着破衣烂衫和露出脚趾头的锥绾子鞋进城了。卸完木料,大家都在东大街的青年巷子歇着。我肚子饿了,想到大街对面的馆子吃一碗馄饨,摸来摸去,身上摸出了一块三毛钱,就毛手毛脚走进了馆子。没想到掌柜的凶神恶煞地骂道:“哪里来的’叫花子’,到别处去要,不要影响我的生意!”连推带操,把我赶出馆子。饭没有吃成,倒叫人家当成了 “叫花子”,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进城。我想着这些城里人怎么这么可恶,不就是穿得烂了些,怎么就把人往外撵呢?以后每当我想起被撵出馆子的往事,就下定决心再到那个饭馆去吃馄饨,看你怎么把我往出撵。
18岁那年,我和谢成德又一次赶着大姑辘车往酒泉城里的郭府巷送石料墩子。这一次我穿了一身洗过的旧衣服,虽说上衣和裤子都带有几块补丁,但补丁和衣服的颜色大体上一样。只是两条裤腿前面的补丁一块上一些,一块下一些,看起来不怎么协调。我还特意把脚上的榔头鞋换成了弟弟的栽毛鞋。由于鞋小,刚一穿上,一只鞋头子就绷开了一道口子,大拇脚趾头露了出来,我也没有在意,穿着这双鞋就上路了。进城卸完石料,我和谢成德到上次的馄饨馆子每人要了一大碗馄饨。掌柜见我掏出了三张五块的票子,满脸堆笑把饭钱接了过去。吃完馄饨出门时,才发现另一只鞋的头子也绷开了。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望着我的鞋,又望着我裤子上不协调的补丁说:“小伙子,以后进城把自己收拾利索一点,再不要穿着露出脚趾头的鞋进城了。”我望着自己的鞋满脸通红。这是我第二次进城。
记得19岁那年的春天,队长调人送两车芨芨到博物馆,我跳起来说:“队长,我去,那里的路我熟。”队长说:“看你那一身邋遢相,还穿着踏后跟鞋,再不要给我们乡下人丢人了。”我急忙说:“我有新衣服新鞋,只是平时舍不得穿,你就让我去吧!”队长终于让我去了。车在南门上停了下来,我赶忙把新衣服、新鞋拿出来换上,然后把装旧衣服、旧鞋的包挂在车排底下。这一次进城还真是个意外,芨芨卸完了,工地上的头头不但不小看人,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大盘炒面。这是我第三次进城。
采访人:后来的情况怎样?孔兆才:后来,我陆陆续续进过好多次城,再也没有遇到像前两次那样的难堪场面,毕竟是我长大了。21岁那年的春天,我和同大队三队的姑娘王金香相识,并在秋天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十二年里,我们有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家庭负担越来越重,除了不饿肚子以外,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34岁那年(1975年),队长派我到酒泉城里去修影剧院,我背着简单的铺盖,穿着补丁裤子,脚蹬黄球鞋,又进了城,开始在工地上干活。起初,大家都是从各公社调来的民工,挖坑搬石头都很卖力,分不出什么高下。干到快十天的时候,我的裤子扯了个口子,鞋也成了鸭鸭嘴,那个领工员看我不顺眼,总让我干最重的活。连续和了三天水泥,我实在累得没劲了,就坐在旁边的水泥垛上歇了歇,那个领工员看见了,骂骂咧咧地走过来把我从水泥垛上拉下来,还踢了我一脚。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和他对骂起来。这个领工员见我敢还口,骂道:“看你那窝囊样子,像叫花子一样,还想偷懒,”说着又踢了我一脚。我气不从一处来,跳起来採住他的领巴子,照着脸上捣了一拳头,他的鼻血就流出来了。我知道闯祸了,第二天,工地上负责人宣布,让我赶快离开工地,并通知生产队另派人来顶替我。这是我一生中在城里遭遇到的最伤自尊心的事情,也让我再次尝到了人穷受人欺的滋味。
在以后的岁月里,按照大集体的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工分、分口粮,勉强维持着生活。但娃娃多,日子过得艰难。1979年大儿子考进了酒泉中学,我要送儿子到学校去报名,总得穿件像样的裤子,想来想去,只能穿着给老婆新做的裤子出门了。老婆说:“你这不是丢人吗?女人的裤子男人怎么穿呢? ”我说:“不丢人,你那偏口裤子我穿上别人是不会注意的,”就这样,我假装体面地把儿子送到了学校,还和儿子在街上吃了大米饭和肉炒菜。这是我又一次进城,也是我心情最舒畅的一次进城。
改革开放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年就大见成效,我所承担的作业组超额完成了任务,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还每户多分了十斤清油和三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也收入不错,卖了三头猪,收入二百多元,算是有钱了,我和老婆坐着每人掏六毛钱的班车进城了。两口子心情特别好,老婆没进过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来到以前让我伤心过的馄饨馆子里要了一盘子红烧肉,美美地吃了一顿。我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算是风风光光地进了一趟城。
从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也和整个社会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大儿子考进了地质大学,小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里,我和妻子被乡政府请到政府大院里,戴上大红花,和其他的家长们共同送应征青年到酒泉影剧院参加欢送大会。我们胸戴大红花走过大街时,行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来到馄饨饭馆里,老板又让座,又倒茶水,热情得让人有些不自在。这一次进城,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坐在影剧院里听领导讲话时,我喜极而泣,眼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还在小声抽泣。老婆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呢?还哭得这么伤心?”我说: “今天我们坐的地方就是当年我被领工员小看过的地方,因为穷我才被人家看不起,想起这些,我咋能不伤心呢!”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城乡人民的经济收入翻了几番。从2013年开始,买小汽车成了乡下人追求的目标,人们相互攀比,赶集、走亲戚,甚至到地上干活都开着小汽车,现在的农民真叫个气派。买房子进城,也成为一种新时尚,许多人家即使背债欠账也要买,因为儿子要结婚了,城里没有楼房,婚是绝对结不了的。近几年政府补贴危房改造,挨家挨户搞厕所革命,支持农户安热水器等现代设施,环境卫生有了大变样。我虽然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当上城里人,可我总舍不得养活了我一辈子的土地。这几年土地流转很快,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城里有了楼房,老汉老婆子都到城里养老,在子女们的极力劝说下,我也当上了城里人。
采访人:谈谈你的感受。
孔兆才:回想起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那些心酸的事情,让人终生难忘。现在老了老了赶上了这么好的社会,拿着政府发的老年补贴,享受着合作医疗和大病医疗补助,现在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没有共产党的好领导,哪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