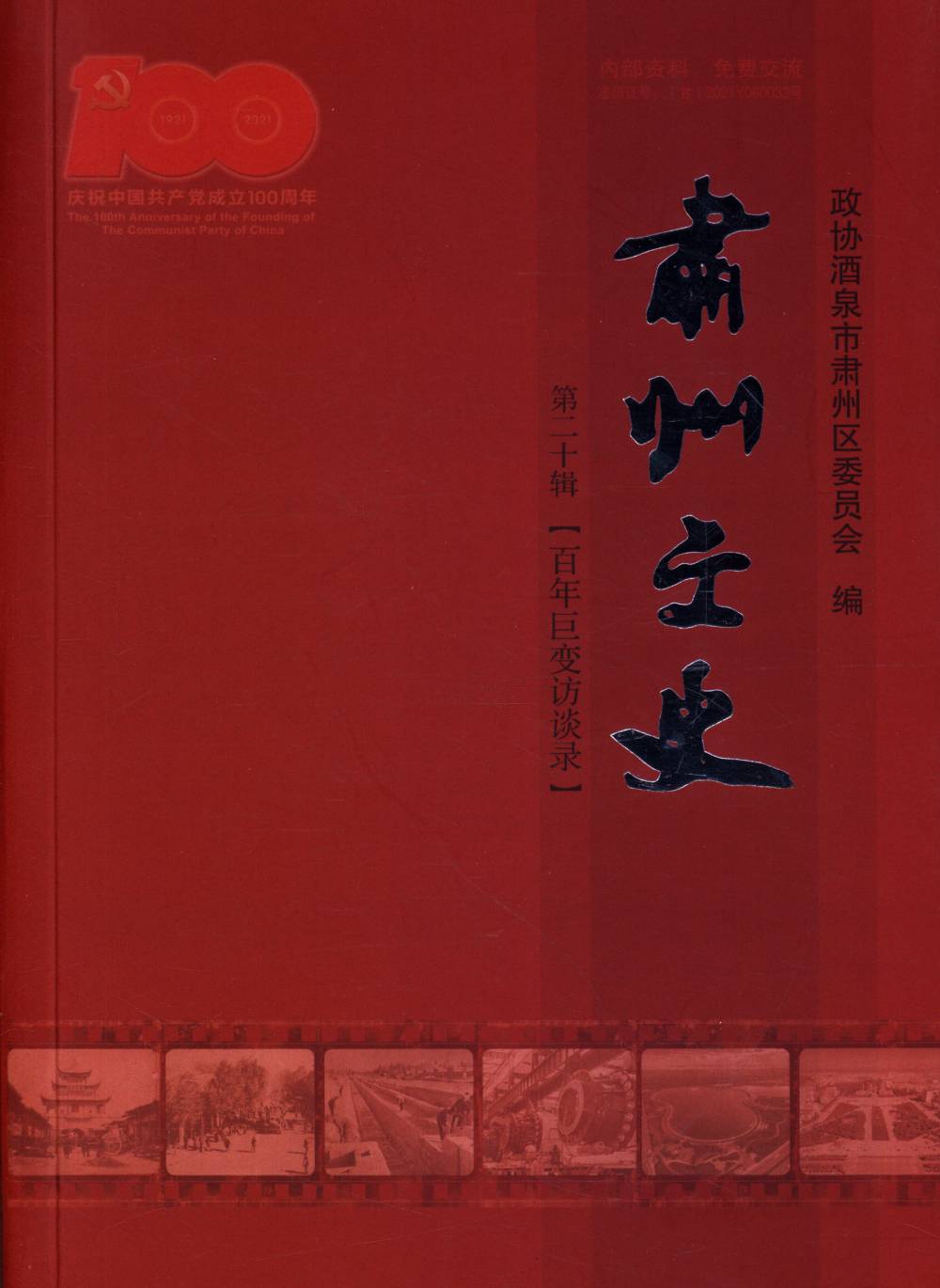吃水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6554 |
| 颗粒名称: | 吃水 |
| 分类号: | C913.3 |
| 页数: | 3 |
| 页码: | 421-423 |
| 摘要: | 采访对象:罗世银,四十年代出生在黄泥堡裕固族乡新湖村,社教后当生产队会计,1983年当乡干部直至退休。采访主题:吃水。采访日期:2020年12月5日 |
| 关键词: | 社会生活 肃州 饮水 |
内容
吃水采访对象:罗世银,四十年代出生在黄泥堡裕固族乡新湖村,社教后当生产队会计,1983年当乡干部直至退休。
采访人:周聪德采访日期:2020年12月5日采访地点:肃州区文化馆三楼采访人:麻烦您讲一下从小时候到现在人饮水的发展历程。
罗世银:我小时候吃水艰难得很,庄子南里有个淌水浇地的官沟,水一淌下来,人就吃沟里的水,水淌过就吃沟里汪下的死水渗水,渗水羊啊牛啊也吃,水里面牛羊杷上粪了人也得撇得吃,不吃没办法,渗水吃完沟里没水了,就得去远处驮水吃。新湖南面有个索家井,用柳斗打地吃,再一个就是黄泥堡二队西头子有个杜家井,就吃这两口井里的水。
采访人:水是怎么运输的?罗世银:驴驮的呢。每家都有一对驮水的大木桶,桶上有两个耳子,穿上担子,驴的脊背上备着鞍子,两个木桶用担子穿起来搭在鞍子上,一边一个桶,驮一次能吃一两天,费些每天驮一次,省着些用隔一天驮一次。木桶上有盖子封顶,边边上有个斜拐拐,开着个三角子尖尖,就像茶壶的嘴嘴,水打上从嘴子里倒进去,一边倒一柳斗,循环几次,直到两个木桶盛满,把口子用木头塞子塞住。
驮水时间长了,驴也习惯了,塞子塞上不用下令就自己走开了。
采访人:井上驮水有多远?罗世黄泥堡二队杜家井大约有两公里半路,索家井在红泉东面南头子,大约也有两三公里。驮一回水快些也得一两个小时,慢些就得一假,井上打水的人多了就得等。官沟里驮渗水没远近,一次下午去驮水,沿着官沟找水,快到黄泥堡四队了才见到一汪水,水桶没舀满就没了,回来就擦麻子了,路都看不清了。
驮水采访人:您继续讲吃水的发展历程。
罗世艮:大约六十年代,杜家井、索家井枯竭,我们没处驮水了,就到新湖二队妥家门上驮水,妥家门上有口苦水井,不吃也没办法。后来,大约到了七十年代,新湖学校门口打了口机井,井水还可以,不苦,是个探井,打开打算要封掉,结果没封,打井的人就走了。探井不停地冒水,水冒得半人高,冒了好几年,我们就从这个井上驮水。冒了几年水越来越小了,最后不冒了,这时各生产队开始打机井了,一个生产队打了一眼,吃水就近便多了,水质也好。从此,不用驴驮子搭上驮水了,水桶挑上挑水就行了,水桶也是铁皮的,比木头桶子轻多了,现吃现挑。我们那里地下水旺得很,井打开就冒水,我们队里打了一眼机井,跟探井一样就冒水的呢,半人高的白鼓撅。确实好水,水井六十米深。再后来,紧接着就是用小钻钻打手压井,一家子打一眼,打三十米深,下个比指头粗些的管子,水自己往出冒,不用了口子扎住就不冒了,也是好水。也有井头安上压的,压起也不费事。到了新世纪初期,村里通上了自来水,我们家刚通自来水就进城了,城里早就是自来水。
吃水的过程就是这样,从外村驮水,到本村驮水,再到本队挑水,又到自己家里提水,直至水到锅头夹道,水质也由苦涩变得纯净。
采访人:周聪德采访日期:2020年12月5日采访地点:肃州区文化馆三楼采访人:麻烦您讲一下从小时候到现在人饮水的发展历程。
罗世银:我小时候吃水艰难得很,庄子南里有个淌水浇地的官沟,水一淌下来,人就吃沟里的水,水淌过就吃沟里汪下的死水渗水,渗水羊啊牛啊也吃,水里面牛羊杷上粪了人也得撇得吃,不吃没办法,渗水吃完沟里没水了,就得去远处驮水吃。新湖南面有个索家井,用柳斗打地吃,再一个就是黄泥堡二队西头子有个杜家井,就吃这两口井里的水。
采访人:水是怎么运输的?罗世银:驴驮的呢。每家都有一对驮水的大木桶,桶上有两个耳子,穿上担子,驴的脊背上备着鞍子,两个木桶用担子穿起来搭在鞍子上,一边一个桶,驮一次能吃一两天,费些每天驮一次,省着些用隔一天驮一次。木桶上有盖子封顶,边边上有个斜拐拐,开着个三角子尖尖,就像茶壶的嘴嘴,水打上从嘴子里倒进去,一边倒一柳斗,循环几次,直到两个木桶盛满,把口子用木头塞子塞住。
驮水时间长了,驴也习惯了,塞子塞上不用下令就自己走开了。
采访人:井上驮水有多远?罗世黄泥堡二队杜家井大约有两公里半路,索家井在红泉东面南头子,大约也有两三公里。驮一回水快些也得一两个小时,慢些就得一假,井上打水的人多了就得等。官沟里驮渗水没远近,一次下午去驮水,沿着官沟找水,快到黄泥堡四队了才见到一汪水,水桶没舀满就没了,回来就擦麻子了,路都看不清了。
驮水采访人:您继续讲吃水的发展历程。
罗世艮:大约六十年代,杜家井、索家井枯竭,我们没处驮水了,就到新湖二队妥家门上驮水,妥家门上有口苦水井,不吃也没办法。后来,大约到了七十年代,新湖学校门口打了口机井,井水还可以,不苦,是个探井,打开打算要封掉,结果没封,打井的人就走了。探井不停地冒水,水冒得半人高,冒了好几年,我们就从这个井上驮水。冒了几年水越来越小了,最后不冒了,这时各生产队开始打机井了,一个生产队打了一眼,吃水就近便多了,水质也好。从此,不用驴驮子搭上驮水了,水桶挑上挑水就行了,水桶也是铁皮的,比木头桶子轻多了,现吃现挑。我们那里地下水旺得很,井打开就冒水,我们队里打了一眼机井,跟探井一样就冒水的呢,半人高的白鼓撅。确实好水,水井六十米深。再后来,紧接着就是用小钻钻打手压井,一家子打一眼,打三十米深,下个比指头粗些的管子,水自己往出冒,不用了口子扎住就不冒了,也是好水。也有井头安上压的,压起也不费事。到了新世纪初期,村里通上了自来水,我们家刚通自来水就进城了,城里早就是自来水。
吃水的过程就是这样,从外村驮水,到本村驮水,再到本队挑水,又到自己家里提水,直至水到锅头夹道,水质也由苦涩变得纯净。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