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经历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6530 |
| 颗粒名称: | 难忘的经历 |
| 分类号: | K294.23 |
| 页数: | 5 |
| 页码: | 330-334 |
| 摘要: | 薛维新和马维义回忆少年时代上学的艰苦以及长大以后在农村任教时遇到的艰辛。 |
| 关键词: | 肃州 酒泉 文史资料 |
内容
难忘的经历
采访对象:薛维新,生于1939年9月,丰乐镇人。从1958年起一直在丰乐任教,曾任丰乐中学和二坝小学校长。1998年退休。
马维义,生于1951年,原屯升乡上寨村人。七十年代民办教师,1987年转为公办教师,曾任乡教委会计、中心小学校长。2011年退休。
采访人:张正彬采访时间:2017年10月13日、2017年10月17日采访地点:东关什字、阳光小区采访人:请您谈谈少年时代上学路上的艰辛和农村学校的见闻。
薛维新:我家在祁连山下的丰乐公社,自然环境不好,从小就听大人说“出了酒泉城,唯有丰乐穷”。1954年我到城里上酒中时,家里没钱,车啊啥的都没有,我老子用两头驴驮了两袋麦子,让我骑了另一头驴,他跟在后面赶驴,带我到城里报名上学。当时的甘新公路是砂石路,不瓷实,上面有一层黄沙,汽车轧过去,一路尘土飞得老高,半天都看不见汽车的影子。我们赶头走到上坝营尔天就黑了,就在车马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接着赶路,到总寨西店天又黑了,又住了一夜,直到第三天才进了城。第四天,老子把麦子卖掉,凑够了学费和伙食费,把我安顿下来。第五天就赶上三头毛驴回家,赶到丰乐又得走两天,到了第六天天黑才能回到家。那时候虽然解放了,但沿山一带还有匪患,所幸没有遇上土匪。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别的学生都被家里人接走了,我家劳力缺,没人来接,就得等个七八一十天。那时候钟楼寺的和尚住在酒中前面,我就到和尚那里混斋饭吃。实在不行了,就到大街上下馆子,花三毛钱买一碗甜面条外加一个馒头充饥。
马维义:我是1958年上学的,在村上读初小,在公社读高小。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年级班里有八岁的,也有十八的,那些年龄大的学生是因为扫除青壮年文盲被扫进学校的。那时候,好多人家的娃娃光着脚上学,多数学生穿的是褐子和老土布做的衣服,身上还打着补丁。全村三十多个学生只有一个老师,上四年级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开不了课,只好去重读三年级。我从五年级开始到公社上高小,当时全公社十个大队,上五年级的只有九个学生,别的学生不是考不上就是上不起。采访人:您上初中时给学校倒土坯是怎么回事?薛维新:1956年,我十三岁的时候到酒泉市一中上初中,后来按成绩取到了酒泉中学。当时的一中正在搞修建,报名时学校要求先完成一中的劳动任务——每个学生倒400个土坯,倒够再来报名,这些土坯是学校修教室用的。那时候,一中的操场里挖着深坑,倒土坯的学生都在那里劳动。我家里的条件不行,吃得差,个子小,干不动力气活,我就脱掉上衣,把裤子挽得高高的,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才倒够土坯。
1976年银达公社银达大队学校采访人:谈谈您在农村任教时开展全民办学的情况。
薛维新:1969年,上面号召全民办学,丰乐公社办起了初中班,成了一所小学到初中连读的学校,教育局让我当校长。当时没有教室,就发动全公社的人到学校倒土坯,老师学生、男女老少都不例外,一个人500块土坯,一二年级的学生由家长完成,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自己完成。我虽然是个校长,自己的土坯也还是自己倒。就这样土坯还是不够,椽子檩子都缺,学生没处住。当时我还带领学生到祁连山上采伐过松树,想了好多办法,又修了十二间学生宿舍。修学校时教育局拨了些钱和材料,群众捐了些,二十几个教师、四百多学生苦了三四年,才把中学建起来,一直用到1982年又拆掉修成了砖木结构。
采访人:谈谈农村教育教学条件的改善情况。
马维义:1958年我在上寨堡子上初小时,学校是一座破庙,墙上的壁画被铲得分辨不清,用的课桌是庙里用过的破条桌。冬天烤火没有煤,实在冻得不行了,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拆庙。到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挨饿学校关门,老师也跑了。我当民办教师以后,到了七十年代,学校都建起了土坯房,里外刷上白灰,看起来整齐多了。八十年代初,学校又修了一次,教室都修成砖基础砖柱子,校门变成了铁大门。以前,老师们睡的是实心炕,因为睡得时间久了,中间的夯土被磨下去,样子很像喂牲口用的土坯槽,老师们把麦草铺在 “槽”里,铺瓷实些,头脚和身体才能趁平。八十年代初,这些“槽”都换成了木头床,床是我们一棵白杨树24元钱买回来打成木板,请木匠做的。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学校办学标准是“六配套”,各学校又查出了一大批危房,乡政府计划先修中心小学,再修别的小学。当时建材很缺,从教育局到乡政府都在积极想办法。上面给的修建资金不够用,乡政府和村上还发动群众进行了捐款。这一轮修建,使各学校变成了农村最高档、最漂亮的建筑,新建的教室一砖到顶,宽敞明亮。2000年以后,修建资金政府全包,学校建得一座比一座好,里面的配套设施多数是我没有用过的,有些甚至没有见过,这样的办学条件,我过去是想都不敢想啊!薛维新: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要求“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多,学校的面貌变化很大,现在农村的学校都变成了楼房。
采访对象:薛维新,生于1939年9月,丰乐镇人。从1958年起一直在丰乐任教,曾任丰乐中学和二坝小学校长。1998年退休。
马维义,生于1951年,原屯升乡上寨村人。七十年代民办教师,1987年转为公办教师,曾任乡教委会计、中心小学校长。2011年退休。
采访人:张正彬采访时间:2017年10月13日、2017年10月17日采访地点:东关什字、阳光小区采访人:请您谈谈少年时代上学路上的艰辛和农村学校的见闻。
薛维新:我家在祁连山下的丰乐公社,自然环境不好,从小就听大人说“出了酒泉城,唯有丰乐穷”。1954年我到城里上酒中时,家里没钱,车啊啥的都没有,我老子用两头驴驮了两袋麦子,让我骑了另一头驴,他跟在后面赶驴,带我到城里报名上学。当时的甘新公路是砂石路,不瓷实,上面有一层黄沙,汽车轧过去,一路尘土飞得老高,半天都看不见汽车的影子。我们赶头走到上坝营尔天就黑了,就在车马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接着赶路,到总寨西店天又黑了,又住了一夜,直到第三天才进了城。第四天,老子把麦子卖掉,凑够了学费和伙食费,把我安顿下来。第五天就赶上三头毛驴回家,赶到丰乐又得走两天,到了第六天天黑才能回到家。那时候虽然解放了,但沿山一带还有匪患,所幸没有遇上土匪。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别的学生都被家里人接走了,我家劳力缺,没人来接,就得等个七八一十天。那时候钟楼寺的和尚住在酒中前面,我就到和尚那里混斋饭吃。实在不行了,就到大街上下馆子,花三毛钱买一碗甜面条外加一个馒头充饥。
马维义:我是1958年上学的,在村上读初小,在公社读高小。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年级班里有八岁的,也有十八的,那些年龄大的学生是因为扫除青壮年文盲被扫进学校的。那时候,好多人家的娃娃光着脚上学,多数学生穿的是褐子和老土布做的衣服,身上还打着补丁。全村三十多个学生只有一个老师,上四年级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开不了课,只好去重读三年级。我从五年级开始到公社上高小,当时全公社十个大队,上五年级的只有九个学生,别的学生不是考不上就是上不起。采访人:您上初中时给学校倒土坯是怎么回事?薛维新:1956年,我十三岁的时候到酒泉市一中上初中,后来按成绩取到了酒泉中学。当时的一中正在搞修建,报名时学校要求先完成一中的劳动任务——每个学生倒400个土坯,倒够再来报名,这些土坯是学校修教室用的。那时候,一中的操场里挖着深坑,倒土坯的学生都在那里劳动。我家里的条件不行,吃得差,个子小,干不动力气活,我就脱掉上衣,把裤子挽得高高的,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才倒够土坯。
1976年银达公社银达大队学校采访人:谈谈您在农村任教时开展全民办学的情况。
薛维新:1969年,上面号召全民办学,丰乐公社办起了初中班,成了一所小学到初中连读的学校,教育局让我当校长。当时没有教室,就发动全公社的人到学校倒土坯,老师学生、男女老少都不例外,一个人500块土坯,一二年级的学生由家长完成,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自己完成。我虽然是个校长,自己的土坯也还是自己倒。就这样土坯还是不够,椽子檩子都缺,学生没处住。当时我还带领学生到祁连山上采伐过松树,想了好多办法,又修了十二间学生宿舍。修学校时教育局拨了些钱和材料,群众捐了些,二十几个教师、四百多学生苦了三四年,才把中学建起来,一直用到1982年又拆掉修成了砖木结构。
采访人:谈谈农村教育教学条件的改善情况。
马维义:1958年我在上寨堡子上初小时,学校是一座破庙,墙上的壁画被铲得分辨不清,用的课桌是庙里用过的破条桌。冬天烤火没有煤,实在冻得不行了,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拆庙。到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挨饿学校关门,老师也跑了。我当民办教师以后,到了七十年代,学校都建起了土坯房,里外刷上白灰,看起来整齐多了。八十年代初,学校又修了一次,教室都修成砖基础砖柱子,校门变成了铁大门。以前,老师们睡的是实心炕,因为睡得时间久了,中间的夯土被磨下去,样子很像喂牲口用的土坯槽,老师们把麦草铺在 “槽”里,铺瓷实些,头脚和身体才能趁平。八十年代初,这些“槽”都换成了木头床,床是我们一棵白杨树24元钱买回来打成木板,请木匠做的。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学校办学标准是“六配套”,各学校又查出了一大批危房,乡政府计划先修中心小学,再修别的小学。当时建材很缺,从教育局到乡政府都在积极想办法。上面给的修建资金不够用,乡政府和村上还发动群众进行了捐款。这一轮修建,使各学校变成了农村最高档、最漂亮的建筑,新建的教室一砖到顶,宽敞明亮。2000年以后,修建资金政府全包,学校建得一座比一座好,里面的配套设施多数是我没有用过的,有些甚至没有见过,这样的办学条件,我过去是想都不敢想啊!薛维新: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要求“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多,学校的面貌变化很大,现在农村的学校都变成了楼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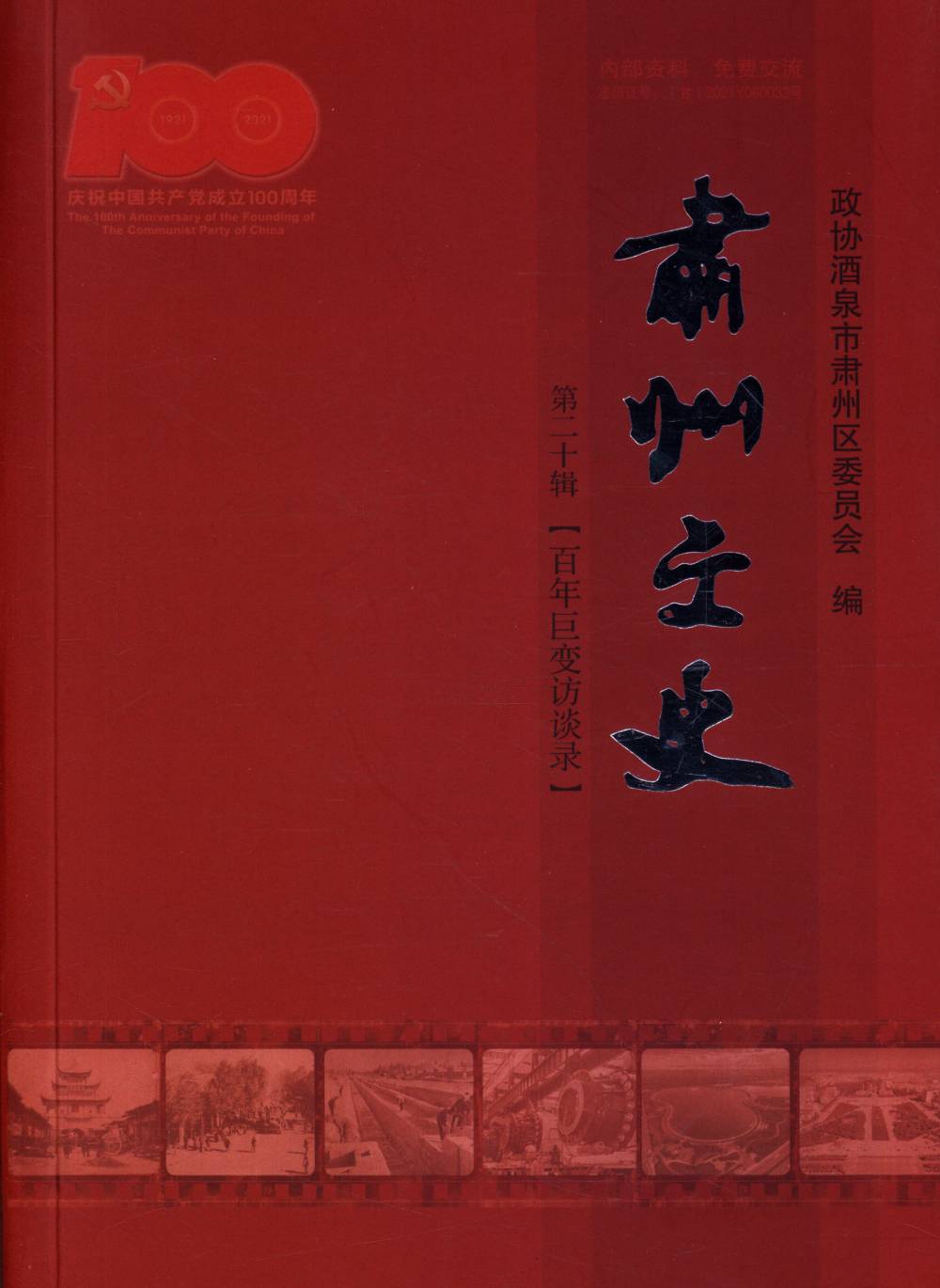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张正彬
责任者